回忆我的导师王栻先生
| 内容出处: | 《平阳文史资料第三十三期》 图书 |
| 唯一号: | 113520020230000820 |
| 颗粒名称: | 回忆我的导师王栻先生 |
| 分类号: | K825 |
| 页数: | 15 |
| 页码: | 85-99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王栻先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我成为他的研究生是因为他在1976年招收了三届硕士研究生,我是他的第三届招收的研究生。我选择报考王栻先生是因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专家,尤其在中国研究严复方面有重要贡献。王先生对我的学术发展给予了重要的指导和支持,开设了专门的课程,并为我的毕业论文提供了指导。 |
| 关键词: | 王栻 研究生 人物 |
内容
我是怎样成为王栻先生的研究生的
王栻先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研究严复的第一人。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以后,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了三届硕士研究生,共五人。我是他的第三届招收的研究生,是1980年春考的,1980年9月1日进校。那届王栻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研究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全系也只招收了三个人,另两个是中国古代史的。原因可能是自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后,在1978年和1979年连续两年招得太多,到1980年国家紧缩招生人数;而1980年是“老三届”考研的最后一届,到1981年,文革后招收的大学第一届本科生就可以毕业报考研究生了。
我为啥会报考王栻先生的研究生呢?
我是江苏省盐城人,在大学本科读的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本与历史系关系不大。但我自小就喜欢学历史,却在1963年9月考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刚学了了两年的纲纲条条,就懵懵懂懂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中。自经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及其破灭,看到了无数的欺骗、阴谋、迫害、撕裂、杀戮和血腥以后,我就想研究这段复杂历史的来龙去脉及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影响和人事纠葛。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1月召开,邓小平同志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法西斯本质和个人崇拜的危害,呼吁中国必须补上思想启蒙这堂课后,我对中国近代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近代启蒙思想史的学习就更加迫切,而对学习枯燥的哲学条条本本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终于我离开了哲学系,报考历史系的近代思想史专业。但天有不测风云,在1978年和1979年我的父母因生活的艰难,连续因病去世,使我无暇报考研究生,直到1980年,我才搭上了“老三届”考研的末班车。
当我决定报考大学历史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时,环顾海内,只有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栻先生等少数教授能够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像南京大学历史系当今名气很大的一些教授,那时还只是普通的讲师,讲师连招收研究生的资格还不具备呢,更何况他们也不是搞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我决定报考王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后,就想了解王先生。我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友和有关资料中了解到,王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原名王载栻,字抱冲,浙江平阳(今归温州市管辖)人,是平阳先贤王理孚之子。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7月24日。1935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考上该校研究院,专攻清史。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家乡温州,参加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平阳临时中学任教,开设国耻课,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后来他一度到省立温州师范学校任教。1939年他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受聘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时校址迁至成都华西坝)任历史系教授。抗战胜利后,他随校迁往南京。直到1952年,共和国教育部全面学习苏联,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王先生转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多年写作与发表了许多论著,例如,《明朝的太监与女人》(署名王抱冲,刊《宇宙风》第二十九期,1936年11月16日出版)、《中国历史科学化》(刊《大学》1942年第一卷第七期)、《汉代的官俸》(刊《思想与时代》1943年8月号)、《籍俸与陋规》(刊《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4年出版)、《谈清代的考试制度》(刊《中国青年》第一卷二期,1947年4月出版)等。近年来,他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维新运动史和严复的研究,发表了《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的思想与活动》(刊《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张之洞与维新运动》(刊《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1962年,他应中华书局之约,着手校订近代思想家严复的全部著作(即《严复集》)。
我知道了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因为王先生从事的研究正是我当时热衷学习和希望钻研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学问,而王先生又是一位一位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老教授,能得到他的亲手指导,钻研我喜爱的学问,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我毫不犹豫、毫不选择地报考了王先生的研究生,并在1980年6月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后来的历史证明,我选对了,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王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
1980年9月1日,我再次踏进了南京大学的校门,成为王栻先生的研究生。
进校的第一天,我便去拜望王先生。那时他全家住在南京大学南园一座古老的大屋顶建筑里。全家几个人挤在一起住,狭小的客厅和几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书籍和报刊杂志,显得拥挤不堪,但却充满了书香气,这是被十年“文革”扫荡而久违的书香气又重返大学校园了,使我十分兴奋。王先生在客厅里迎侯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69岁。我看到他是中等偏高的身材,不胖,头顶部已“秃顶”,头发已经很稀少,多已白了,额头上闪着智慧的亮光,皮肤白皙,相貌堂堂,鼻梁挺直,双目含笑,衣着整洁、风度儒雅。他的夫人,就是我的王师母,在旁扶住他,个头比他矮些,但显然身体比他要好些,像个知识女性。他们客气地招呼我坐下,与我亲切地交谈起来。
我首先向王先生汇报了我的情况,王先生说,他都了解了。他称赞我的考研成绩很好,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这两门专业课考得好。他说:“看得出你的知识面广,基础扎实,记忆力也好。我与几位教师在出这两门专业课试卷时,除了出几道问答题,考你们考生的分析能力,另外特地多出名词解释题,共有60道,就是想考考你们的知识面。想不到在这么多考生中,只有你如数家珍,全部答出来了。特别是‘沈葆桢’这个词条给我印象深,你不仅答出他的生平和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还写出他晚年到南京任两江总督四年,为江苏治水和海防等四处奔走,最后死在南京,尤其是你还写明沈是林则徐的女婿,是与林则徐一脉相承的。这些知识在目前的教科书里都是没有的。这说明你读书较多,有一定的分析能力,超过了其他考生。所以今年我只招收了你一个研究生。望你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我听了既高兴、感动,又十分惊讶,想不到如此高龄的王先生在忙于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同时,对招收一个研究生竟如此认真、细致,并寄予热烈的期望。我能不倍加努力奋进吗?
王栻先生给我简单介绍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的要求、课程和学习注意事项。王先生拿出他不久前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的《严复传》和由南京大学内部出版的《维新运动史》上、下册送给我,作为学习资料。他告诉我,前一年哲学家李泽厚特地到南京大学来拜望他,向他了解严复生平和论著的一些问题,因为王先生是海内外研究严复的第一人和最优秀的专家。王先生热情地尽其所知告诉了李泽厚先生。不久,李先生就在北京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严复》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影响很大,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观点,我在当时反复看了多遍,对我报考研究生的复习发挥了很大的的作用。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篇论文里也有我们王先生的贡献啊。我怀着感激与敬佩的心情离开了王先生的家。此后我就经常往王先生家跑了,那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开学不久,我终于等到了王先生给我开课。王先生自国家恢复高考后,在1978年秋招收了一个研究生,在1979年秋招收了三个研究生,这四个研究生是我的“学兄”;在1980年只招收了一个研究生,那就是我。因此,这年王栻先生开课时,只有我一个学生去听。王先生行动不便,每次我都是到他家中的客厅里去上课。当我到王栻先生家中时,王师母给我倒一杯茶后,就与家中其他人离开客厅,回避到房间里,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王栻先生两个人。后来我得知,王先生给前两届研究生开课时也是这样。王栻先生全家为培养研究生作出了很多牺牲。这年,虽只是对我一个学生开课,王先生教学却总是十分认真、严肃。他慢慢地讲解课本,讲解严复的原著,介绍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谈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举例详尽,分析细致。他在讲解维新运动志士和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时,对温州籍的黄体芳、黄绍箕两人(著名演员黄宗江、黄宗英的先人)讲解尤为详尽,带着深深的敬意,显示了他对家乡温州的广泛了解和深厚感情。王先生给我开课约一年,两个学期,使我的知识不断增长,使我的分析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对戊戌变法前后的近代启蒙思想史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影响等,引起我浓厚的兴趣,走上研究的道路。我选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严复的政治思想及其演变》,得到了王先生的首肯和支持。这篇论文的写作不仅使我得到了一次学术写作的锻炼,而且打下了我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可以说,王先生是我一生学术道路的引路人。
王先生不仅学养深厚,而且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他曾动情地对我说:“我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不久,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自1937年7月抗战之日起,至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前后四十年,正当我壮年及成熟时期,却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与做学问,浪费了光阴,成果不多。直到目前,看到祖国前途光明,我们大学教师也可以认真做点学问了,但我已经垂垂老矣,感到精力衰颓。回想我自清华毕业以后的四十年中,最多只能挤点时间,读点书,写几篇文章,还要担惊受怕。我现在的学识积累,最多不过像三四十岁人的水平……。”自责之切,殷殷可见。我听了百感交集。是啊,像王先生这样天资聪慧,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学者,在当时的中国本就不多,凤毛麟角,他们本可以大有作为,为学术和教育做出更多的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的。但历史却捉弄和折磨了他们,使他们才无所施,仰天长叹,空白了少年头。然而这能怪他们吗?不!这是那个时代的过错,而并非个人的责任。日本的侵略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十多年的灾难;更不可思议的是,在1949年后的二十多年的所谓“和平年代”里,也是运动不断,折腾不断,中国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到了1966年“文革”十年浩劫,全国的各类学校竟被全部砸烂,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遭到前所未有的凌辱和摧残,冤死者不知凡几,能苟活者已属不易,只求偷生于乱世,哪有心思与条件去钻研学问?全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一片荒凉。王先生真诚的倾诉,正反映了那个时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奈以及未能尽展才华的深深遗憾。
然而,令人敬佩的是,王先生在那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仍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冒着风险,克服困难,抓紧点滴时间和一切难得的机会,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钻研学问,写作论著,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他在抗战前后的动荡年间,先后发表了《中国历史科学化》《汉代的官俸》《籍俸与陋规》《谈清代的考试制度》等多篇论文;在1940年,他与沈鉴合作编著的《国耻史讲话》,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在1948年12月,他独立完成的《慈禧太后传》,由正风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在史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维新运动史和严复、张之洞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在1960年写成数十万字的《维新运动》上下册,作为大学教材,于1964年由南京大学内部出版,内容丰富,资料齐全,文字流畅,发前人所未发,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此专题的学术著作,深得史学界和学生们的赞誉。1981年,王先生在夫人陈秀梅和五子王平的协助下,对此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第四章,准备送出版社正式出版。
王先生晚年投入最多的,是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研究。他写成的《严复传》,于1957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完整论述严复的专著。严复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早年被清政府派遣英国学习海军,深入钻研了西学,对西方近代的历史和思想发展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回国后,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校长”。1895年以后,他在甲午战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刺激下,先后写下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雄文,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西方名著,以一种全新的思想,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风行海内,洛阳纸贵,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心高气傲的康有为也对他十分敬佩;胡适誉他为“近世介绍西学的第一人”,毛泽东更把他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个代表人物之一。但严复的译著,文字艰深,学术界多年没人对他的生平和思想作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论述。王先生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严复传》是第一本完整论述严复生平与思想的专著,不仅论析和肯定了这位思想家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实际活动,而且分析了他的译著的先进思想与理论贡献。王栻先生在《严复与严译名著》一文中写道:“我们可以大胆地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这位43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对于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甲午战争前曾经到过外国的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之流,甲午战争后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正因为他对严复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的《严复传》才写得全面而深刻,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文革”结束后,1976年,王栻先生将《严复传》修改,增补了《严复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一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欢迎与赞誉。
正由于王先生是研究严复的第一人,成果斐然,1962年,中华书局特地约请王先生编辑校订严复的全部著作,准备出版《严复集》。王栻教授立即带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部分中青年教师,日以继夜地投入了工作。但因王栻先生的健康和资料匮乏等诸多因所困扰,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袭来,使这项工作一拖再拖;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开始了这项工作。令我感到荣幸的是,我和王栻先生的其他研究生一道,从入学开始,就在王栻先生的安排和领导下,参加了这项工作。我在抄录和整理严复的论著时,看到了王栻先生多年来亲笔写下的研究和整理严复译著的许多手稿和批语,写得那么工整、认真和细致,不仅使我学到了严复思想学术的精髓,而且得到了一次学术研究的锻炼。
王先生虽年高体弱,行动不便,但他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还关心着国家时政大事,关心着他所在的历史系的发展。南京大学历史系是个老系,解放初院系调整时由几家高校的历史系合并而成,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又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矛盾重重。1981年冬天,系里教职员工在对系里发展战略和道路上发生了分歧和激烈的争辩。按理说,已七十高龄的王先生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不理不睬。但他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面对他衷心热爱的历史学发展,心情难以平静下来。他经认真的调查和思考,精心写下了他的意见。系里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那天,正是一个北风呼号的严寒日子,王先生特地穿上一身新棉衣,让我们搀扶着,从南京大学的南园住宅区,步行走到北园教学区的西南大楼,登上三楼,走进历史系的会议室。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意见,陈述了他的论证。与会全体人员未必都同意他的全部见解,但大家都被他的满腔爱国、爱系热情和精神所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七十高龄的王栻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公众集会活动与发表讲话。多年以后,我仍记得那感人的场面。
王先生对朋友的热情和真挚也曾深深感动了我。那是在1981年12月17日,一个寒冷的冬日,王栻先生参加我上一届几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答辩,主持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汤志钧教授。汤先生也是王先生的多年学友。我担任论文答辩会的记录,亲眼看到王栻先生对汤先生的尊敬和热情。答辩会结束后,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王先生回家,当走到南京大学南园八舍前的道路上,突然听到王栻先生惊呼一声,挣脱我的搀扶,快步走上前去,与一位迎面而来的老先生热烈地握手,连声问候,脸上荡漾着由衷的欢笑。我被王先生的这一举动和难得见到的热情洋溢感染了,呆呆地站在一旁,很久才把这两位老学者送回家。事后王栻先生告诉我,那位老教授是他的温州老乡、考古学家夏鼐。他们两人已经相识相交几十年,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在生活上互相帮助。这次夏鼐先生到南京参加学术会议,特地到南京大学拜访王先生和中文系的管雄教授两位旧友。我感到,在无数“运动”和“文革”浩劫深刻广泛地破坏了中国的人与人的关系后,老一辈学者之间的这种历经风雨始终不渝的互相信任和深厚友情,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楷模。
王栻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指导我,在生活上也关心我。特别是在1981年暑假,我离开南京,回到我在“文革”中工作过的地方,家庭生活一度发生了一些波折和困难。暑假结束我回到南京大学后,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向王栻先生汇报和求教。王栻先生微笑着迎接我。他说他在暑假中就及时知道了我的情况。他挥了挥手,根本没当一回事,对我说,现在不是“文革”那时代了,国家在向好,人民在向好,学校在向好,因此每个人也都会向好,个人生活上碰到一些波折和困难,在人生道路上是难免的,很快就会过去。只要努力,前途广阔。他要求我不要多想个人生活上的得失,而要更多地投身到史学研究中去,那里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呢!我听了心里热呼呼的,原来,王先生在时时关心着我啊。我感到他真是一笑解我千愁!他是我的学术导师,同时还是我生活上的父辈。在我生活道路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王先生给了我指点、勇气和信心,而他的家人则给了我生活上多方面热情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顺利渡过难关,奋发而前行,我后来能有许多进步,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取得一些成绩,是与王先生以及其它许多老师对我的关心、指点和鼓舞,分不开的。
王先生去世前后
正当王先生以全部身心投入新时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他的多种学术成果即将源源不断地问世时,疾病无情地打断了他的工作。
那是在1982年2月11日,学校开学后不久,我正在南京大学图书馆里查阅史料,忽然系里派人来找到我,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先生突然病倒了,而且病状严重,要我快去其家。
当我赶到王栻先生的家中时,只见他已经昏迷不醒。大家赶忙把他送到南京医疗条件最好的江苏省人民医院。我经了解才得知,王先生多年患有高血压等病,他一直是带病工作。这天他遇见一位友人来访,高兴之余,就与那友人下起了象棋。也许是用脑过度,也许是高兴激动,他在下棋时突发脑溢血晕倒,病像凶险。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生立即对王先生进行抢救,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王先生的病情稳定下来,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的神智却未能恢复,一直在昏迷中。
我与王先生的家人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领导和教师,站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病房的走廊里,心情十分悲痛难过。医生告诉我们,王先生的病情一时难以好转,希望王先生的家人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生,配合医生,做好长期的护理。经王先生的家人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领导协商,决定,在王先生治疗期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雇请一位护工,在白天对王先生进行护理,而在每天晚上,则由王先生的几个儿子和我以及另一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俞政轮流担任护理。我立即答应并开始了工作,因为我想,这是我这个做学生的,对敬爱的王先生在这时所应做、所能做的的事了。为了能挽救王先生的生命,哪怕能延长他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的生命,我啥都愿意做,啥都愿意付出。
从那天开始,我和王先生的几个儿子以及俞政轮流担任王先生的夜间护理,从晚上七时直到第二天清晨七时。尽管当时我正写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时间紧迫,但轮到我值夜班时,我都提前从南京大学赶到医院。我为王先生擦拭身体,清理大小便等,并尽可能流通病房的空气。夜深人静时,我看着昏迷中的王先生的苍白面孔,流着泪祈祷,愿王先生尽快恢复健康!
但王先生的疾病在不断恶化。一天深夜,正是我值班,忽然发现王先生的呼吸急促,脸色变得灰白,这是病危的迹象。我立即喊来医生抢救。医生对我说,必须打开王先生的头盖骨,洗净溢出的血迹,而这很危险,必须要王先生的家人与单位领导签字,越快越好。我立即骑着自行车冲出医院,在深夜的南京马路上疾驰,喊醒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茅家琦和系总支书记孟克,把他们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签字和商讨,直忙到天亮。手术成功了,王先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仍然没有能苏醒过来,而且更加昏沉了。
医生终无回天之力,王先生在昏迷一年多时间后,终于在1983年2月13日去世。南京大学为王先生举办了隆重而肃穆的追悼会。在北京的夏鼐先生接到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讣告后,托人献了花圈,并寄来挽联:
三千里外凶闻,岁首成佛成仙,著史宏才君未尽;
五十年来风雨,交情胜金胜石,伤心老泪我无多。
对王栻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整理和出版他的论著,继承他未竟的学术事业。
首先是《严复集》。这是王先生早在1962年就应中华书局之约而接受的任务。多年来,他带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部分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整理点校,倾注了全部心力。王先生去世后,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部分中青年教师和王先生的研究生抓紧时间编校,终于在1986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五册,收集了严复的全部诗文、书信、日记、翻译按语,附录严复年谱等。署名王栻主编。该书是目前所有严复作品集中收录最全、质量最好的集子,成为研究维新运动尤其是研究严复的必备书。
其次是《维新运动》。王先生在“文革”后已经对此书内部出版的初稿本进行了较大的修改。王先生去世后,由他的研究生进行整理,于1986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8万字,以大量的史料作基础,对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起、在戊戌变法达到高峰的中国近代维新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和深刻的分析论证,注重学术创新,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王先生还有几部未刊行的手稿,现为温州学人方韶毅收藏,包括《严几道年谱》《甲午战后之联俄政策》《清代汉大臣身家考》《清代汉臣身家表》等。我希望有关部门能资助出版印行这些论著,以告慰王栻先生于九泉之下,并惠及学术界。
王先生,你安息吧!你的同志,你的友人,你的同乡,你的学生,都将永远把你记在心中。
附王栻佚文一篇
父亲的六十生辰
民国廿四年阳历正月初六日,是父亲六十岁的生辰,父亲不愿铺张,但家中人们总觉得父亲辛苦了六十年,幸有今日,不能没有庆祝的表示,于是决定初六日不接外宾,是限自己家中人们开一个庆祝会。
初五日夜间,已经热闹,大厅堂中的各种布置已经引起全家人的忙碌与笑声。最快乐的是孩子们,他们看见大厅堂中男人们东奔西跑,女人们聚群谈笑,便无形之间特别高兴起来,踢踺子,捉迷藏,打架,样样都来,最出风头的是阿淦与阿奂。直到十二时,已经夜半,布置才了。大哥、二哥都决定夜间不睡,因为家中人三时须起来,但是我们都恐明天精神不支,都愿先去睡了,请两位哥哥同仆人们到时候喊醒我们。
那天晚上最忙碌的是二哥,好像他的兴致特别好。他为拜寿不知怎样拜法,问了雪玉先生,问了其他客人们,最后他还问了林椿。因为各人所说不同,莫知所从,他又去翻《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没头没脑地查了半天,不得解决,终又从雪玉先生之说,行一跪四拜之礼。既然定了,他又请大哥大嫂及我们各对夫妇练习一番,别教明天闹笑话。大家羞在别人面前学,都愿关起门来在睡觉之前练习一回。那天晚上,二嫂暂宿母亲的外间,二哥不能在一起学拜,后来他笑说:“反正明天阿哥阿嫂领头,他俩怎样,我俩就怎样好了。”
电灯还亮的时候,我们都起来了,大约正是早晨三时,大家心里都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停一忽儿,就开始拜寿。先由父亲拜天拜地,拜神拜祖,以后请父亲母亲就位。母亲最客气,连儿子媳妇们拜贺之时,也不敢坐着。五、六两弟不在家,我们兄弟四对夫妇拜了之后,接着是三位姊妹及下辈子侄,再接着有小叔小婶、明、二姊、凤及雪玉先生及林椿等人,礼毕约在六时。
我因为恐怕下午接客忙,(虽然我们不招待宾客,但宾客上门,我们不得不接待),精神不支,就先去睡了,整整睡了五六个钟头,起来已是中午了。这天宾客虽然不多,可是尽是无聊的人,我们本来预备过着一种家庭之乐的,但结果都变成无聊的应酬了,心中总觉美中不足,我们四兄弟又商量聚餐办法。二哥提议将中午多余下来的三桌菜料再作晚上家人聚餐之用,用西餐法,各人一份菜,全家人聚在一起,半筵时,还请父亲训话。我们以为这办法不但新鲜有趣,而且极饶意义,我们全家大大小小的人聚在一起吃饭,这还是创举呢!于是大家又忙着吩咐厨房,安排桌椅,又教阿奂作谜语,教阿荆讲故事,教阿奂击鼓乱唱,教阿冏倒地乱滚,以博大家一笑,作散场之用。我们八时就座,地点在大厅堂,座位次序如下(系一品字形座位图,略)。小叔中途插入,仑因睡未到。
大家到时,都带笑容,但是大家因父亲在座,不能大笑。阿奂因为阿友在座,不能乱叫,所以空气是静穆的。后来阿荆因为汤面未曾吃完,给厨子拿去了,放声大哭。大家放留声机的“洋人大笑”来哄她,可是没有效果。姊姊打趣说:“笑声不及哭声响亮呢!”全场才开始了微笑。
酒半筵,请父亲训话,全场肃然。父亲四顾左右,乃作训辞曰:“今晚全家在一起联桌聚餐,此为吾家初有事,融融洩洩,殊为家庭之乐事。以诸儿之劝,乃与汝曹全家人作此谈话,然亦固予之所愿也。
今日为予六十生辰,花甲重逢,本是一极平常事。古人七十为下寿,何况六十耶?清初吕晚村先生六十时,儿孙辈欲为贺寿,先生严拒之,正此意也。然予今从俗例,于此六十之年,愿受汝辈之一祝者,亦自有说也。
我王氏自迁鳌江以来,累世积德,然寿皆未及六十者。予幸食前代之德,今日居然苍髯白发、皤然老翁矣,此足喜者一也。累代以四子为多,吾曾吾祖皆仅一子侍老,今吾幸有六子,诸儿虽不见出人头地,犹未有隳败之象,此可喜者二也。前代惟吾高、曾二祖较富,吾祖吾父已渐穷困,屡有衣食之虞。今吾家虽不富饶,已是小康之家,较之前代颇见起色,此三可喜者也。然汝曹当此诸可喜之事,皆食先人积德之报。先人百年操业之苦,乃造今日之福也。
“今日在座之人,处境皆在中人之上者,然祖上之穷困,有非汝曹所可知者,座中惟吾与汝母及汝叔三人知之而已。吾家穷困时,什物房舍仅值八十千钱,迫而移居西桥。犹忆三十年前,余赴杭求学,筹款不及三十千钱,以十千钱奉老父,以三千钱予汝母,盖彤儿犹在腹中也。途中往返,必坐统舱,羊溺横流,臭味扑鼻,雨雪纷纷,衣被尽湿。试问今日汝曹享用,较余当日为何如耶?
家庭不以勤俭自励,不自艰难处着想,未有不败者。予非劝汝曹一味节俭,特用钱之际,宜思来处不易耳。予亦不望尔曹他日作富家子女,能如今日之衣食无虞,于愿足矣。特望尔曹各作端正之人,自强不息,不见毁于乡里,至于事业大小成毁,所弗论也。汝曹勉之!”
训词毕,半晌肃然,于是姊姊轻轻地说:“爸爸说在座的人处境都在中人之上,这话很对,只是我不在内,我的命运比在座的人都苦些。”
一忽儿,父亲先离座,阿阁便哈哈大笑,原来她早早看见对面大哥吃得汗珠儿挂满了额头,早已忍不住要笑了。于是大家跟着笑了一阵,大家心里松畅了许多,开始放任的谈话。谈笑的中心是往事的追忆。姊姊嘲笑母亲道:“现在我的家境正同母亲从前的一样,我还记得从前父亲在杭州任事时,母亲天天捧着五百块钱,每天日间放在柜里,夜里放在枕头边。还每天一五一十的数着,数得津津有味呢!”大哥接着说:“我只七岁时的家境更苦呢!那时没有蔬菜,每顿饭都硬咽下去,免不了还时常含着眼泪吃饭呢!”
陈仑、阿荆、阿冏、阿奂本来预备干些玩意儿,作散场之用的,但是因为前一晚睡得太不够了,都先去睡去。我们到了十时半,就在随便谈话笑声中散会了。
王栻先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研究严复的第一人。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以后,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了三届硕士研究生,共五人。我是他的第三届招收的研究生,是1980年春考的,1980年9月1日进校。那届王栻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研究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全系也只招收了三个人,另两个是中国古代史的。原因可能是自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后,在1978年和1979年连续两年招得太多,到1980年国家紧缩招生人数;而1980年是“老三届”考研的最后一届,到1981年,文革后招收的大学第一届本科生就可以毕业报考研究生了。
我为啥会报考王栻先生的研究生呢?
我是江苏省盐城人,在大学本科读的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本与历史系关系不大。但我自小就喜欢学历史,却在1963年9月考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刚学了了两年的纲纲条条,就懵懵懂懂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中。自经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及其破灭,看到了无数的欺骗、阴谋、迫害、撕裂、杀戮和血腥以后,我就想研究这段复杂历史的来龙去脉及其深刻的背景、原因、影响和人事纠葛。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1月召开,邓小平同志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法西斯本质和个人崇拜的危害,呼吁中国必须补上思想启蒙这堂课后,我对中国近代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近代启蒙思想史的学习就更加迫切,而对学习枯燥的哲学条条本本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终于我离开了哲学系,报考历史系的近代思想史专业。但天有不测风云,在1978年和1979年我的父母因生活的艰难,连续因病去世,使我无暇报考研究生,直到1980年,我才搭上了“老三届”考研的末班车。
当我决定报考大学历史系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时,环顾海内,只有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栻先生等少数教授能够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像南京大学历史系当今名气很大的一些教授,那时还只是普通的讲师,讲师连招收研究生的资格还不具备呢,更何况他们也不是搞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我决定报考王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后,就想了解王先生。我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友和有关资料中了解到,王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原名王载栻,字抱冲,浙江平阳(今归温州市管辖)人,是平阳先贤王理孚之子。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7月24日。1935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考上该校研究院,专攻清史。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家乡温州,参加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平阳临时中学任教,开设国耻课,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后来他一度到省立温州师范学校任教。1939年他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受聘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时校址迁至成都华西坝)任历史系教授。抗战胜利后,他随校迁往南京。直到1952年,共和国教育部全面学习苏联,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王先生转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多年写作与发表了许多论著,例如,《明朝的太监与女人》(署名王抱冲,刊《宇宙风》第二十九期,1936年11月16日出版)、《中国历史科学化》(刊《大学》1942年第一卷第七期)、《汉代的官俸》(刊《思想与时代》1943年8月号)、《籍俸与陋规》(刊《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4年出版)、《谈清代的考试制度》(刊《中国青年》第一卷二期,1947年4月出版)等。近年来,他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维新运动史和严复的研究,发表了《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的思想与活动》(刊《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张之洞与维新运动》(刊《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1962年,他应中华书局之约,着手校订近代思想家严复的全部著作(即《严复集》)。
我知道了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因为王先生从事的研究正是我当时热衷学习和希望钻研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学问,而王先生又是一位一位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老教授,能得到他的亲手指导,钻研我喜爱的学问,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我毫不犹豫、毫不选择地报考了王先生的研究生,并在1980年6月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后来的历史证明,我选对了,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王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
1980年9月1日,我再次踏进了南京大学的校门,成为王栻先生的研究生。
进校的第一天,我便去拜望王先生。那时他全家住在南京大学南园一座古老的大屋顶建筑里。全家几个人挤在一起住,狭小的客厅和几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书籍和报刊杂志,显得拥挤不堪,但却充满了书香气,这是被十年“文革”扫荡而久违的书香气又重返大学校园了,使我十分兴奋。王先生在客厅里迎侯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69岁。我看到他是中等偏高的身材,不胖,头顶部已“秃顶”,头发已经很稀少,多已白了,额头上闪着智慧的亮光,皮肤白皙,相貌堂堂,鼻梁挺直,双目含笑,衣着整洁、风度儒雅。他的夫人,就是我的王师母,在旁扶住他,个头比他矮些,但显然身体比他要好些,像个知识女性。他们客气地招呼我坐下,与我亲切地交谈起来。
我首先向王先生汇报了我的情况,王先生说,他都了解了。他称赞我的考研成绩很好,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这两门专业课考得好。他说:“看得出你的知识面广,基础扎实,记忆力也好。我与几位教师在出这两门专业课试卷时,除了出几道问答题,考你们考生的分析能力,另外特地多出名词解释题,共有60道,就是想考考你们的知识面。想不到在这么多考生中,只有你如数家珍,全部答出来了。特别是‘沈葆桢’这个词条给我印象深,你不仅答出他的生平和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还写出他晚年到南京任两江总督四年,为江苏治水和海防等四处奔走,最后死在南京,尤其是你还写明沈是林则徐的女婿,是与林则徐一脉相承的。这些知识在目前的教科书里都是没有的。这说明你读书较多,有一定的分析能力,超过了其他考生。所以今年我只招收了你一个研究生。望你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我听了既高兴、感动,又十分惊讶,想不到如此高龄的王先生在忙于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同时,对招收一个研究生竟如此认真、细致,并寄予热烈的期望。我能不倍加努力奋进吗?
王栻先生给我简单介绍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的要求、课程和学习注意事项。王先生拿出他不久前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的《严复传》和由南京大学内部出版的《维新运动史》上、下册送给我,作为学习资料。他告诉我,前一年哲学家李泽厚特地到南京大学来拜望他,向他了解严复生平和论著的一些问题,因为王先生是海内外研究严复的第一人和最优秀的专家。王先生热情地尽其所知告诉了李泽厚先生。不久,李先生就在北京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严复》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影响很大,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观点,我在当时反复看了多遍,对我报考研究生的复习发挥了很大的的作用。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篇论文里也有我们王先生的贡献啊。我怀着感激与敬佩的心情离开了王先生的家。此后我就经常往王先生家跑了,那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开学不久,我终于等到了王先生给我开课。王先生自国家恢复高考后,在1978年秋招收了一个研究生,在1979年秋招收了三个研究生,这四个研究生是我的“学兄”;在1980年只招收了一个研究生,那就是我。因此,这年王栻先生开课时,只有我一个学生去听。王先生行动不便,每次我都是到他家中的客厅里去上课。当我到王栻先生家中时,王师母给我倒一杯茶后,就与家中其他人离开客厅,回避到房间里,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王栻先生两个人。后来我得知,王先生给前两届研究生开课时也是这样。王栻先生全家为培养研究生作出了很多牺牲。这年,虽只是对我一个学生开课,王先生教学却总是十分认真、严肃。他慢慢地讲解课本,讲解严复的原著,介绍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谈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举例详尽,分析细致。他在讲解维新运动志士和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时,对温州籍的黄体芳、黄绍箕两人(著名演员黄宗江、黄宗英的先人)讲解尤为详尽,带着深深的敬意,显示了他对家乡温州的广泛了解和深厚感情。王先生给我开课约一年,两个学期,使我的知识不断增长,使我的分析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对戊戌变法前后的近代启蒙思想史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影响等,引起我浓厚的兴趣,走上研究的道路。我选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严复的政治思想及其演变》,得到了王先生的首肯和支持。这篇论文的写作不仅使我得到了一次学术写作的锻炼,而且打下了我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可以说,王先生是我一生学术道路的引路人。
王先生不仅学养深厚,而且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他曾动情地对我说:“我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不久,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自1937年7月抗战之日起,至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前后四十年,正当我壮年及成熟时期,却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与做学问,浪费了光阴,成果不多。直到目前,看到祖国前途光明,我们大学教师也可以认真做点学问了,但我已经垂垂老矣,感到精力衰颓。回想我自清华毕业以后的四十年中,最多只能挤点时间,读点书,写几篇文章,还要担惊受怕。我现在的学识积累,最多不过像三四十岁人的水平……。”自责之切,殷殷可见。我听了百感交集。是啊,像王先生这样天资聪慧,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学者,在当时的中国本就不多,凤毛麟角,他们本可以大有作为,为学术和教育做出更多的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的。但历史却捉弄和折磨了他们,使他们才无所施,仰天长叹,空白了少年头。然而这能怪他们吗?不!这是那个时代的过错,而并非个人的责任。日本的侵略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十多年的灾难;更不可思议的是,在1949年后的二十多年的所谓“和平年代”里,也是运动不断,折腾不断,中国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到了1966年“文革”十年浩劫,全国的各类学校竟被全部砸烂,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遭到前所未有的凌辱和摧残,冤死者不知凡几,能苟活者已属不易,只求偷生于乱世,哪有心思与条件去钻研学问?全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一片荒凉。王先生真诚的倾诉,正反映了那个时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奈以及未能尽展才华的深深遗憾。
然而,令人敬佩的是,王先生在那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仍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冒着风险,克服困难,抓紧点滴时间和一切难得的机会,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钻研学问,写作论著,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他在抗战前后的动荡年间,先后发表了《中国历史科学化》《汉代的官俸》《籍俸与陋规》《谈清代的考试制度》等多篇论文;在1940年,他与沈鉴合作编著的《国耻史讲话》,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在1948年12月,他独立完成的《慈禧太后传》,由正风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在史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维新运动史和严复、张之洞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在1960年写成数十万字的《维新运动》上下册,作为大学教材,于1964年由南京大学内部出版,内容丰富,资料齐全,文字流畅,发前人所未发,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此专题的学术著作,深得史学界和学生们的赞誉。1981年,王先生在夫人陈秀梅和五子王平的协助下,对此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第四章,准备送出版社正式出版。
王先生晚年投入最多的,是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研究。他写成的《严复传》,于1957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完整论述严复的专著。严复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早年被清政府派遣英国学习海军,深入钻研了西学,对西方近代的历史和思想发展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回国后,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校长”。1895年以后,他在甲午战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刺激下,先后写下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雄文,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西方名著,以一种全新的思想,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风行海内,洛阳纸贵,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心高气傲的康有为也对他十分敬佩;胡适誉他为“近世介绍西学的第一人”,毛泽东更把他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个代表人物之一。但严复的译著,文字艰深,学术界多年没人对他的生平和思想作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论述。王先生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严复传》是第一本完整论述严复生平与思想的专著,不仅论析和肯定了这位思想家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实际活动,而且分析了他的译著的先进思想与理论贡献。王栻先生在《严复与严译名著》一文中写道:“我们可以大胆地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这位43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对于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甲午战争前曾经到过外国的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之流,甲午战争后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正因为他对严复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的《严复传》才写得全面而深刻,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文革”结束后,1976年,王栻先生将《严复传》修改,增补了《严复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一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欢迎与赞誉。
正由于王先生是研究严复的第一人,成果斐然,1962年,中华书局特地约请王先生编辑校订严复的全部著作,准备出版《严复集》。王栻教授立即带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部分中青年教师,日以继夜地投入了工作。但因王栻先生的健康和资料匮乏等诸多因所困扰,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袭来,使这项工作一拖再拖;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开始了这项工作。令我感到荣幸的是,我和王栻先生的其他研究生一道,从入学开始,就在王栻先生的安排和领导下,参加了这项工作。我在抄录和整理严复的论著时,看到了王栻先生多年来亲笔写下的研究和整理严复译著的许多手稿和批语,写得那么工整、认真和细致,不仅使我学到了严复思想学术的精髓,而且得到了一次学术研究的锻炼。
王先生虽年高体弱,行动不便,但他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还关心着国家时政大事,关心着他所在的历史系的发展。南京大学历史系是个老系,解放初院系调整时由几家高校的历史系合并而成,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又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矛盾重重。1981年冬天,系里教职员工在对系里发展战略和道路上发生了分歧和激烈的争辩。按理说,已七十高龄的王先生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不理不睬。但他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面对他衷心热爱的历史学发展,心情难以平静下来。他经认真的调查和思考,精心写下了他的意见。系里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那天,正是一个北风呼号的严寒日子,王先生特地穿上一身新棉衣,让我们搀扶着,从南京大学的南园住宅区,步行走到北园教学区的西南大楼,登上三楼,走进历史系的会议室。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意见,陈述了他的论证。与会全体人员未必都同意他的全部见解,但大家都被他的满腔爱国、爱系热情和精神所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七十高龄的王栻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公众集会活动与发表讲话。多年以后,我仍记得那感人的场面。
王先生对朋友的热情和真挚也曾深深感动了我。那是在1981年12月17日,一个寒冷的冬日,王栻先生参加我上一届几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答辩,主持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汤志钧教授。汤先生也是王先生的多年学友。我担任论文答辩会的记录,亲眼看到王栻先生对汤先生的尊敬和热情。答辩会结束后,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王先生回家,当走到南京大学南园八舍前的道路上,突然听到王栻先生惊呼一声,挣脱我的搀扶,快步走上前去,与一位迎面而来的老先生热烈地握手,连声问候,脸上荡漾着由衷的欢笑。我被王先生的这一举动和难得见到的热情洋溢感染了,呆呆地站在一旁,很久才把这两位老学者送回家。事后王栻先生告诉我,那位老教授是他的温州老乡、考古学家夏鼐。他们两人已经相识相交几十年,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在生活上互相帮助。这次夏鼐先生到南京参加学术会议,特地到南京大学拜访王先生和中文系的管雄教授两位旧友。我感到,在无数“运动”和“文革”浩劫深刻广泛地破坏了中国的人与人的关系后,老一辈学者之间的这种历经风雨始终不渝的互相信任和深厚友情,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楷模。
王栻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指导我,在生活上也关心我。特别是在1981年暑假,我离开南京,回到我在“文革”中工作过的地方,家庭生活一度发生了一些波折和困难。暑假结束我回到南京大学后,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向王栻先生汇报和求教。王栻先生微笑着迎接我。他说他在暑假中就及时知道了我的情况。他挥了挥手,根本没当一回事,对我说,现在不是“文革”那时代了,国家在向好,人民在向好,学校在向好,因此每个人也都会向好,个人生活上碰到一些波折和困难,在人生道路上是难免的,很快就会过去。只要努力,前途广阔。他要求我不要多想个人生活上的得失,而要更多地投身到史学研究中去,那里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呢!我听了心里热呼呼的,原来,王先生在时时关心着我啊。我感到他真是一笑解我千愁!他是我的学术导师,同时还是我生活上的父辈。在我生活道路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王先生给了我指点、勇气和信心,而他的家人则给了我生活上多方面热情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顺利渡过难关,奋发而前行,我后来能有许多进步,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取得一些成绩,是与王先生以及其它许多老师对我的关心、指点和鼓舞,分不开的。
王先生去世前后
正当王先生以全部身心投入新时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他的多种学术成果即将源源不断地问世时,疾病无情地打断了他的工作。
那是在1982年2月11日,学校开学后不久,我正在南京大学图书馆里查阅史料,忽然系里派人来找到我,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先生突然病倒了,而且病状严重,要我快去其家。
当我赶到王栻先生的家中时,只见他已经昏迷不醒。大家赶忙把他送到南京医疗条件最好的江苏省人民医院。我经了解才得知,王先生多年患有高血压等病,他一直是带病工作。这天他遇见一位友人来访,高兴之余,就与那友人下起了象棋。也许是用脑过度,也许是高兴激动,他在下棋时突发脑溢血晕倒,病像凶险。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生立即对王先生进行抢救,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王先生的病情稳定下来,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的神智却未能恢复,一直在昏迷中。
我与王先生的家人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领导和教师,站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病房的走廊里,心情十分悲痛难过。医生告诉我们,王先生的病情一时难以好转,希望王先生的家人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生,配合医生,做好长期的护理。经王先生的家人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领导协商,决定,在王先生治疗期间,由南京大学历史系雇请一位护工,在白天对王先生进行护理,而在每天晚上,则由王先生的几个儿子和我以及另一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俞政轮流担任护理。我立即答应并开始了工作,因为我想,这是我这个做学生的,对敬爱的王先生在这时所应做、所能做的的事了。为了能挽救王先生的生命,哪怕能延长他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的生命,我啥都愿意做,啥都愿意付出。
从那天开始,我和王先生的几个儿子以及俞政轮流担任王先生的夜间护理,从晚上七时直到第二天清晨七时。尽管当时我正写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时间紧迫,但轮到我值夜班时,我都提前从南京大学赶到医院。我为王先生擦拭身体,清理大小便等,并尽可能流通病房的空气。夜深人静时,我看着昏迷中的王先生的苍白面孔,流着泪祈祷,愿王先生尽快恢复健康!
但王先生的疾病在不断恶化。一天深夜,正是我值班,忽然发现王先生的呼吸急促,脸色变得灰白,这是病危的迹象。我立即喊来医生抢救。医生对我说,必须打开王先生的头盖骨,洗净溢出的血迹,而这很危险,必须要王先生的家人与单位领导签字,越快越好。我立即骑着自行车冲出医院,在深夜的南京马路上疾驰,喊醒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茅家琦和系总支书记孟克,把他们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签字和商讨,直忙到天亮。手术成功了,王先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仍然没有能苏醒过来,而且更加昏沉了。
医生终无回天之力,王先生在昏迷一年多时间后,终于在1983年2月13日去世。南京大学为王先生举办了隆重而肃穆的追悼会。在北京的夏鼐先生接到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讣告后,托人献了花圈,并寄来挽联:
三千里外凶闻,岁首成佛成仙,著史宏才君未尽;
五十年来风雨,交情胜金胜石,伤心老泪我无多。
对王栻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整理和出版他的论著,继承他未竟的学术事业。
首先是《严复集》。这是王先生早在1962年就应中华书局之约而接受的任务。多年来,他带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部分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整理点校,倾注了全部心力。王先生去世后,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部分中青年教师和王先生的研究生抓紧时间编校,终于在1986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五册,收集了严复的全部诗文、书信、日记、翻译按语,附录严复年谱等。署名王栻主编。该书是目前所有严复作品集中收录最全、质量最好的集子,成为研究维新运动尤其是研究严复的必备书。
其次是《维新运动》。王先生在“文革”后已经对此书内部出版的初稿本进行了较大的修改。王先生去世后,由他的研究生进行整理,于1986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8万字,以大量的史料作基础,对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起、在戊戌变法达到高峰的中国近代维新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和深刻的分析论证,注重学术创新,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王先生还有几部未刊行的手稿,现为温州学人方韶毅收藏,包括《严几道年谱》《甲午战后之联俄政策》《清代汉大臣身家考》《清代汉臣身家表》等。我希望有关部门能资助出版印行这些论著,以告慰王栻先生于九泉之下,并惠及学术界。
王先生,你安息吧!你的同志,你的友人,你的同乡,你的学生,都将永远把你记在心中。
附王栻佚文一篇
父亲的六十生辰
民国廿四年阳历正月初六日,是父亲六十岁的生辰,父亲不愿铺张,但家中人们总觉得父亲辛苦了六十年,幸有今日,不能没有庆祝的表示,于是决定初六日不接外宾,是限自己家中人们开一个庆祝会。
初五日夜间,已经热闹,大厅堂中的各种布置已经引起全家人的忙碌与笑声。最快乐的是孩子们,他们看见大厅堂中男人们东奔西跑,女人们聚群谈笑,便无形之间特别高兴起来,踢踺子,捉迷藏,打架,样样都来,最出风头的是阿淦与阿奂。直到十二时,已经夜半,布置才了。大哥、二哥都决定夜间不睡,因为家中人三时须起来,但是我们都恐明天精神不支,都愿先去睡了,请两位哥哥同仆人们到时候喊醒我们。
那天晚上最忙碌的是二哥,好像他的兴致特别好。他为拜寿不知怎样拜法,问了雪玉先生,问了其他客人们,最后他还问了林椿。因为各人所说不同,莫知所从,他又去翻《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没头没脑地查了半天,不得解决,终又从雪玉先生之说,行一跪四拜之礼。既然定了,他又请大哥大嫂及我们各对夫妇练习一番,别教明天闹笑话。大家羞在别人面前学,都愿关起门来在睡觉之前练习一回。那天晚上,二嫂暂宿母亲的外间,二哥不能在一起学拜,后来他笑说:“反正明天阿哥阿嫂领头,他俩怎样,我俩就怎样好了。”
电灯还亮的时候,我们都起来了,大约正是早晨三时,大家心里都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停一忽儿,就开始拜寿。先由父亲拜天拜地,拜神拜祖,以后请父亲母亲就位。母亲最客气,连儿子媳妇们拜贺之时,也不敢坐着。五、六两弟不在家,我们兄弟四对夫妇拜了之后,接着是三位姊妹及下辈子侄,再接着有小叔小婶、明、二姊、凤及雪玉先生及林椿等人,礼毕约在六时。
我因为恐怕下午接客忙,(虽然我们不招待宾客,但宾客上门,我们不得不接待),精神不支,就先去睡了,整整睡了五六个钟头,起来已是中午了。这天宾客虽然不多,可是尽是无聊的人,我们本来预备过着一种家庭之乐的,但结果都变成无聊的应酬了,心中总觉美中不足,我们四兄弟又商量聚餐办法。二哥提议将中午多余下来的三桌菜料再作晚上家人聚餐之用,用西餐法,各人一份菜,全家人聚在一起,半筵时,还请父亲训话。我们以为这办法不但新鲜有趣,而且极饶意义,我们全家大大小小的人聚在一起吃饭,这还是创举呢!于是大家又忙着吩咐厨房,安排桌椅,又教阿奂作谜语,教阿荆讲故事,教阿奂击鼓乱唱,教阿冏倒地乱滚,以博大家一笑,作散场之用。我们八时就座,地点在大厅堂,座位次序如下(系一品字形座位图,略)。小叔中途插入,仑因睡未到。
大家到时,都带笑容,但是大家因父亲在座,不能大笑。阿奂因为阿友在座,不能乱叫,所以空气是静穆的。后来阿荆因为汤面未曾吃完,给厨子拿去了,放声大哭。大家放留声机的“洋人大笑”来哄她,可是没有效果。姊姊打趣说:“笑声不及哭声响亮呢!”全场才开始了微笑。
酒半筵,请父亲训话,全场肃然。父亲四顾左右,乃作训辞曰:“今晚全家在一起联桌聚餐,此为吾家初有事,融融洩洩,殊为家庭之乐事。以诸儿之劝,乃与汝曹全家人作此谈话,然亦固予之所愿也。
今日为予六十生辰,花甲重逢,本是一极平常事。古人七十为下寿,何况六十耶?清初吕晚村先生六十时,儿孙辈欲为贺寿,先生严拒之,正此意也。然予今从俗例,于此六十之年,愿受汝辈之一祝者,亦自有说也。
我王氏自迁鳌江以来,累世积德,然寿皆未及六十者。予幸食前代之德,今日居然苍髯白发、皤然老翁矣,此足喜者一也。累代以四子为多,吾曾吾祖皆仅一子侍老,今吾幸有六子,诸儿虽不见出人头地,犹未有隳败之象,此可喜者二也。前代惟吾高、曾二祖较富,吾祖吾父已渐穷困,屡有衣食之虞。今吾家虽不富饶,已是小康之家,较之前代颇见起色,此三可喜者也。然汝曹当此诸可喜之事,皆食先人积德之报。先人百年操业之苦,乃造今日之福也。
“今日在座之人,处境皆在中人之上者,然祖上之穷困,有非汝曹所可知者,座中惟吾与汝母及汝叔三人知之而已。吾家穷困时,什物房舍仅值八十千钱,迫而移居西桥。犹忆三十年前,余赴杭求学,筹款不及三十千钱,以十千钱奉老父,以三千钱予汝母,盖彤儿犹在腹中也。途中往返,必坐统舱,羊溺横流,臭味扑鼻,雨雪纷纷,衣被尽湿。试问今日汝曹享用,较余当日为何如耶?
家庭不以勤俭自励,不自艰难处着想,未有不败者。予非劝汝曹一味节俭,特用钱之际,宜思来处不易耳。予亦不望尔曹他日作富家子女,能如今日之衣食无虞,于愿足矣。特望尔曹各作端正之人,自强不息,不见毁于乡里,至于事业大小成毁,所弗论也。汝曹勉之!”
训词毕,半晌肃然,于是姊姊轻轻地说:“爸爸说在座的人处境都在中人之上,这话很对,只是我不在内,我的命运比在座的人都苦些。”
一忽儿,父亲先离座,阿阁便哈哈大笑,原来她早早看见对面大哥吃得汗珠儿挂满了额头,早已忍不住要笑了。于是大家跟着笑了一阵,大家心里松畅了许多,开始放任的谈话。谈笑的中心是往事的追忆。姊姊嘲笑母亲道:“现在我的家境正同母亲从前的一样,我还记得从前父亲在杭州任事时,母亲天天捧着五百块钱,每天日间放在柜里,夜里放在枕头边。还每天一五一十的数着,数得津津有味呢!”大哥接着说:“我只七岁时的家境更苦呢!那时没有蔬菜,每顿饭都硬咽下去,免不了还时常含着眼泪吃饭呢!”
陈仑、阿荆、阿冏、阿奂本来预备干些玩意儿,作散场之用的,但是因为前一晚睡得太不够了,都先去睡去。我们到了十时半,就在随便谈话笑声中散会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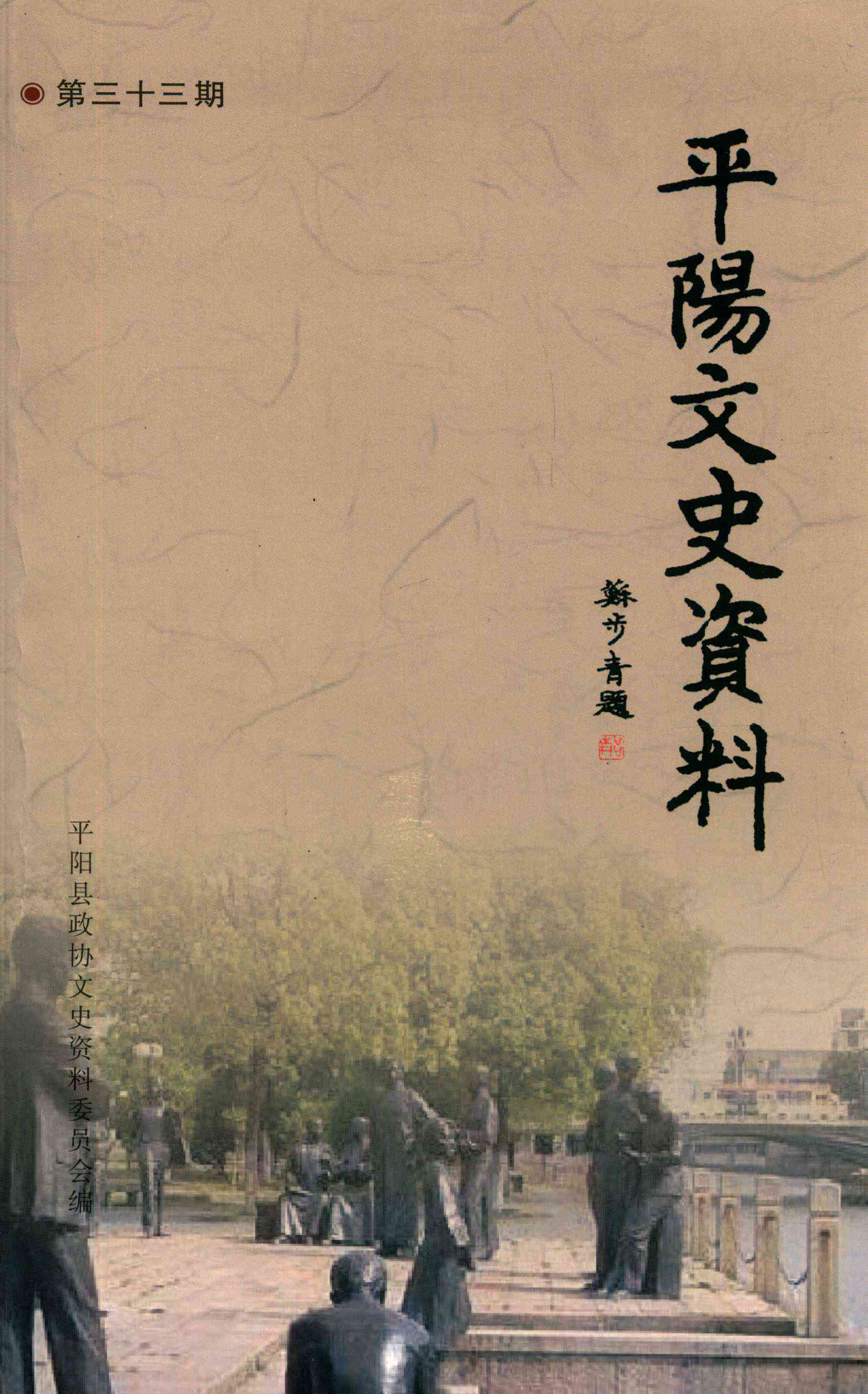
《平阳文史资料第三十三期》
本书收录了第十四届平阳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引雁荡山优质水源造福鳌江沿岸群众、共和前一年“海内奇才”宋恕病逝、忆美术史论家林树中的家乡文化情结、双璧争辉一文一武、空而不空续佛慧命、采访郑一平:谈捉捕张韶舞经过、记平阳刺绣老艺人姚秀英、一代贤臣两地情怀、芳径剪春萦梦远、吾家雁山下翠岩高千岑、侃侃陈公豪杰自负、鄱阳夹潦平生学读杨悌诗两组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