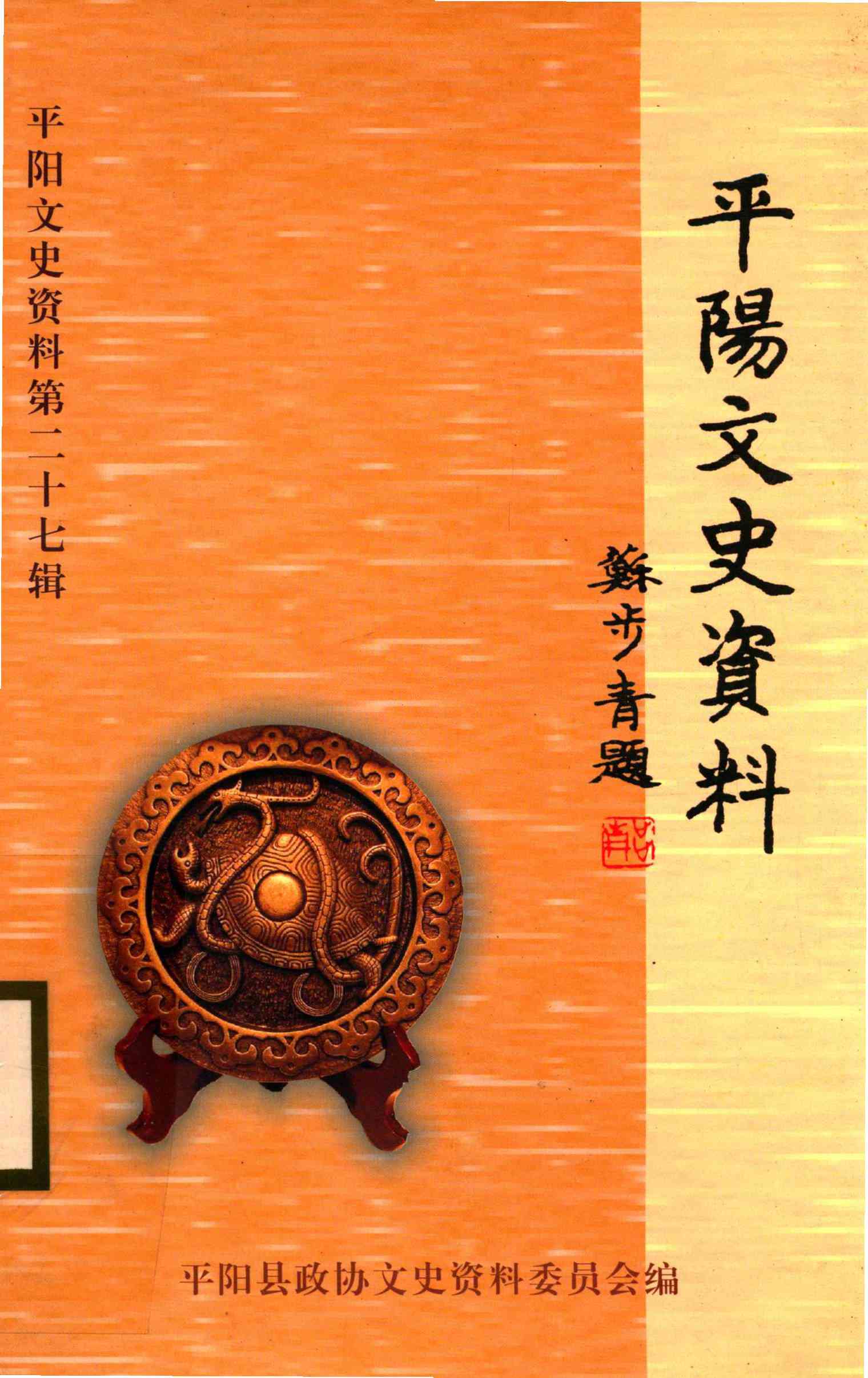蹉跎岁月
| 内容出处: | 《平阳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13520020230000667 |
| 颗粒名称: | 蹉跎岁月 |
| 其他题名: | 忆我的下乡插队生活 |
| 分类号: | K250.655 |
| 页数: | 6 |
| 页码: | 48-53 |
| 摘要: | 本文叙述了从准备下乡到抵达农村的过程,包括家庭的经济状况、兄弟姐妹的选择、市里的动员和威胁、欢送仪式和初到农村的适应过程。 |
| 关键词: | 知青文化 历史回忆 地方史志 |
内容
上世纪60年代,我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我们的青春热血、理想与追求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广阔天地、山山水水。
我家住温州市区县前头,家中有父母还有3个弟弟,6口人,蜗居在当时“解放”电影院边的斗室之中。全家人靠父亲一人每月30来元工资维持生活,寅吃卯粮已成习惯,家庭经济整年捉襟见肘。四姐弟中,唯有我的学历最高,读完初中三年。
1964年,在最高指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紧锣密鼓声中,我的二弟日刚到黑龙江支边,三弟日铨到灵昆岛插队。一个支边一个下乡,家里一下子少了两只饭碗,经济上倒是松口气,至于“将来”“前途”谁也不敢去考虑,谁也无法考虑。家中留下我与大弟日瑜。大弟跟人当学徒学做皮鞋。父母的意思,设法再留住我这个唯一的女孩子,日后好照顾。可是,事与愿违,雷厉风行的上山下乡运动声势浩大,市里给居民区的名额层层加码。市、街道、居民区三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轮番到我家做工作,把我家的门槛都踩烂了。他们每次走后,还甩下一句威胁性的而很有分量的话:“你若不响应,那你父亲的饭碗(工作)还得考虑考虑!”父母与我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期间听说有的地区,工作队对“钉子户”采取强力措施,比如纠集一班人整天坐在你家门口,敲锣打鼓,吵得你全家无法安宁;有的还在你家贴上白门对(白纸黑字的对联)。我们再三思忖,避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干脆争取主动,为了留住大弟,于是我带着户口本到街道“知青办”,办理下乡手续。
1964年12月份,街道为我们举行简单的欢送仪式,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永强区龙湾公社环一大队。市区至龙湾约20公里,公路路面坑坑洼洼,公交车处于瘫痪状态,我们挤上一辆半新不旧的拖拉机,一路颠簸来到大队部。接待我们的是大队老书记国荣,他宽厚仁慈,和蔼可亲,我们都称他国荣伯。他带我们到大队晒谷场边一幢三间平屋,这是市知青办拨款修建的简易房。共有四男四女八位知青。我们四个女孩子住一室,男孩子住一室,另一间作为我们共同使用的厨房兼农具室。按规定,还分给每人一块松木床板,一顶箬笠,一件蓑衣,一把锄头。八位知青都来自温州市区,彼此不认识。与我同室的女孩子中数我年龄最大,当时20岁,其余三位(丽华、青燕、微微)都只有17岁。无形中我成了他们的老大姐。我们到生产队里向大妈大嫂借了些旧凳桌,铺好棉被,总算安了家。
刚开始,农民们对我们的到来有点好奇,这些细皮嫩肉的城里姑娘与小伙子能经得住太阳暴晒,风吹雨淋吗?他们能在这里安心一辈子吗?村里有几个未成家的小伙子,农闲时经常到知青点里晃悠、聊天,特别是对女孩子大献殷勤、套近乎。大队干部对我们的到来做了精心安排。他们选择村里作风正派,生产经验丰富,善于助人为乐的农民,作为我们的师傅。八位知青配备八位师傅,任务是传帮带。大队干部还说你们有困难就找师傅。我的师傅名叫一昌,是位不到30岁的青年农民,憨厚诚实。平时说话有点腼腆。师母(其实我只少她几岁)也很厚道,很善良。农忙时,劳动强度强,时间长,中餐到晚餐之间都要吃“接力”,师母都会为我准备一份可口的点心。在当时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实在是难能可贵。我每次从家里(城里)回队,也带些肥皂、红糖之类紧缺物资相赠,因此关系比较融洽。有的知青就没有我这么幸运。午间休息,没有点心可吃,连脚丫泥巴也懒得洗,就在门板上躺一会儿,等待继续出工。
环一大队主要种植的是水稻,也有部分山园。我们与农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从播种、插秧、耘田、施肥、收割样样都干。一些知青从前连水田都未踩过,一下田未走几步就摔成“大泥鳅”。看见“蚂蝗”就叫“皇天”,偏偏这一带水田“蚂蝗”特别多。脚腿上叮满“蚂蝗”,又痒又痛,把它拔出后,两腿挂着血丝。但经过一段时间磨炼,也逐渐学会干农活。干完水田农活,还要上山种蕃茹。挑栏是最吃力的一项农活。即把猪牛栏里的猪牛粪挑到山上。头顶烈日,挑着又重又臭的猪牛粪,一步挨一步往山上攀登。队里为了照顾女知青,不让我们干这项重活。我们的任务是把猪牛粪用手掰开,分送到蕃茹园上。秋天,我们要上山砍柴,手拿柴刀,向那些杂草荆棘砍去,结果双手鲜血淋漓。为了表示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大家都不敢戴手套。冬天,上山掘蕃茹,刨、晒蕃茹丝这农活轻松不了多少,经常是双手冻得红肿、皴裂,有时长满冻疮。一天干下来,筋疲力尽,腰酸背痛,骨头像散了架,回到家里,澡也不想洗,饭也不想吃,真希望明天永远不会天亮。这样劳累一天,(队里照顾知青,给予优惠)评给我们每人每天5分工分,年终可分到四角五分至五角人民币。也就是说,即使天天出勤,每月只能拿到13元至15元。一年全勤,只有150元左右。其实不可能全勤,除了雨天、农闲,辛辛苦苦干一年,最多不会超过一百元。
当时白楼下有个水产加工厂。厂里生产任务繁忙,需雇临时工来加工水产品。为了增加知青收入,让附近大队知青去加工。当队里把这个任务分派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最开心的,因为可以穿上比较干净的衣服,不用风吹日晒,比较起来工作又轻松。可惜一年只轮到几天,真是狼多肉少,千载难逢。
开头几年,我们8人三餐合伙吃饭。每天由一人轮流值日,负责买菜烧菜煮饭。俗话说“共天下容易,共饭镬难”,后来时间一久,矛盾多了,吵嘴也多了。你说菜太贵,他说饭煮糊了……,只得散伙单干。但散伙后问题更多,更辛苦。干活回来,锅里冷冰冰,又要生火又要烧饭、烧菜,累得苦不堪言。
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们女知青最怕是干活时小便与回家洗澡,这是两大难题。干活的都是男人(当地妇女是不出垟的),想“方便”很不方便;再一个是洗澡,四个女孩子住在一起,当时没有卫生间,洗澡是个大问题。于是大家约法三章:每人各备一盆水,背靠背各自面壁,同时宽衣解带,洗毕穿好衣服后才允许回头。
光阴荏苒,时光流逝。在很多人眼里,我们这些人属于“三等公民”。当初的热情逐渐冷却了,前途也越来越渺茫了。大家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请假回家的时间多了,出工少了,一年中只在农忙时干几天活。大队对我们管束也宽松了,我们几乎成了队里可有可无的社员。大家都在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的出路。其中有的女知青嫁给当地殷实富裕的农民家庭;有的男知青与当地女青年结婚;有的通过关系的到厂家那怕手工作坊干临时工;幸运的被聘为当地民办教师。1970年,我年满26岁,整天为自己的前途唉声叹气。我既无高深文化,又无门道,但又亟待想跳出这“农门”,在当时谈何容易!老天爷还算有眼,这年,在一位亲戚的穿针引线下,把我知青关系转到平阳县万全区农村,当上一位民办教师。每月可拿到26元的工资(国家仅补助14元,有12元要到大队领取),比起“三等公民”不知好多少倍了,我已很知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青的春天来了。1979年我有幸参加平阳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考试,“白卷”年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什么“知识”可谈?许多人只认得自己的姓名、数十个常用汉字与阿拉伯字。记得当年作文题是《我们要学习张志新的大无畏精神》,据说全场白卷。这些修补地球的知青整天与泥巴打交道,哪有工夫关心“国家大事”?张志新是男是女也搞不清楚,哪里写得出什么“精神”?由于我当了几年民办教师,接触到一些文化,有幸考中。录用后重执教鞭,耕耘在三尺讲台,直止退休。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虽然我们韶华已逝,一切已事过境迁,但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重温尘封的记忆。它毕竟是共和国的一段历史,更是我人生的一段重要历程!
我家住温州市区县前头,家中有父母还有3个弟弟,6口人,蜗居在当时“解放”电影院边的斗室之中。全家人靠父亲一人每月30来元工资维持生活,寅吃卯粮已成习惯,家庭经济整年捉襟见肘。四姐弟中,唯有我的学历最高,读完初中三年。
1964年,在最高指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紧锣密鼓声中,我的二弟日刚到黑龙江支边,三弟日铨到灵昆岛插队。一个支边一个下乡,家里一下子少了两只饭碗,经济上倒是松口气,至于“将来”“前途”谁也不敢去考虑,谁也无法考虑。家中留下我与大弟日瑜。大弟跟人当学徒学做皮鞋。父母的意思,设法再留住我这个唯一的女孩子,日后好照顾。可是,事与愿违,雷厉风行的上山下乡运动声势浩大,市里给居民区的名额层层加码。市、街道、居民区三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轮番到我家做工作,把我家的门槛都踩烂了。他们每次走后,还甩下一句威胁性的而很有分量的话:“你若不响应,那你父亲的饭碗(工作)还得考虑考虑!”父母与我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期间听说有的地区,工作队对“钉子户”采取强力措施,比如纠集一班人整天坐在你家门口,敲锣打鼓,吵得你全家无法安宁;有的还在你家贴上白门对(白纸黑字的对联)。我们再三思忖,避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干脆争取主动,为了留住大弟,于是我带着户口本到街道“知青办”,办理下乡手续。
1964年12月份,街道为我们举行简单的欢送仪式,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永强区龙湾公社环一大队。市区至龙湾约20公里,公路路面坑坑洼洼,公交车处于瘫痪状态,我们挤上一辆半新不旧的拖拉机,一路颠簸来到大队部。接待我们的是大队老书记国荣,他宽厚仁慈,和蔼可亲,我们都称他国荣伯。他带我们到大队晒谷场边一幢三间平屋,这是市知青办拨款修建的简易房。共有四男四女八位知青。我们四个女孩子住一室,男孩子住一室,另一间作为我们共同使用的厨房兼农具室。按规定,还分给每人一块松木床板,一顶箬笠,一件蓑衣,一把锄头。八位知青都来自温州市区,彼此不认识。与我同室的女孩子中数我年龄最大,当时20岁,其余三位(丽华、青燕、微微)都只有17岁。无形中我成了他们的老大姐。我们到生产队里向大妈大嫂借了些旧凳桌,铺好棉被,总算安了家。
刚开始,农民们对我们的到来有点好奇,这些细皮嫩肉的城里姑娘与小伙子能经得住太阳暴晒,风吹雨淋吗?他们能在这里安心一辈子吗?村里有几个未成家的小伙子,农闲时经常到知青点里晃悠、聊天,特别是对女孩子大献殷勤、套近乎。大队干部对我们的到来做了精心安排。他们选择村里作风正派,生产经验丰富,善于助人为乐的农民,作为我们的师傅。八位知青配备八位师傅,任务是传帮带。大队干部还说你们有困难就找师傅。我的师傅名叫一昌,是位不到30岁的青年农民,憨厚诚实。平时说话有点腼腆。师母(其实我只少她几岁)也很厚道,很善良。农忙时,劳动强度强,时间长,中餐到晚餐之间都要吃“接力”,师母都会为我准备一份可口的点心。在当时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实在是难能可贵。我每次从家里(城里)回队,也带些肥皂、红糖之类紧缺物资相赠,因此关系比较融洽。有的知青就没有我这么幸运。午间休息,没有点心可吃,连脚丫泥巴也懒得洗,就在门板上躺一会儿,等待继续出工。
环一大队主要种植的是水稻,也有部分山园。我们与农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从播种、插秧、耘田、施肥、收割样样都干。一些知青从前连水田都未踩过,一下田未走几步就摔成“大泥鳅”。看见“蚂蝗”就叫“皇天”,偏偏这一带水田“蚂蝗”特别多。脚腿上叮满“蚂蝗”,又痒又痛,把它拔出后,两腿挂着血丝。但经过一段时间磨炼,也逐渐学会干农活。干完水田农活,还要上山种蕃茹。挑栏是最吃力的一项农活。即把猪牛栏里的猪牛粪挑到山上。头顶烈日,挑着又重又臭的猪牛粪,一步挨一步往山上攀登。队里为了照顾女知青,不让我们干这项重活。我们的任务是把猪牛粪用手掰开,分送到蕃茹园上。秋天,我们要上山砍柴,手拿柴刀,向那些杂草荆棘砍去,结果双手鲜血淋漓。为了表示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大家都不敢戴手套。冬天,上山掘蕃茹,刨、晒蕃茹丝这农活轻松不了多少,经常是双手冻得红肿、皴裂,有时长满冻疮。一天干下来,筋疲力尽,腰酸背痛,骨头像散了架,回到家里,澡也不想洗,饭也不想吃,真希望明天永远不会天亮。这样劳累一天,(队里照顾知青,给予优惠)评给我们每人每天5分工分,年终可分到四角五分至五角人民币。也就是说,即使天天出勤,每月只能拿到13元至15元。一年全勤,只有150元左右。其实不可能全勤,除了雨天、农闲,辛辛苦苦干一年,最多不会超过一百元。
当时白楼下有个水产加工厂。厂里生产任务繁忙,需雇临时工来加工水产品。为了增加知青收入,让附近大队知青去加工。当队里把这个任务分派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最开心的,因为可以穿上比较干净的衣服,不用风吹日晒,比较起来工作又轻松。可惜一年只轮到几天,真是狼多肉少,千载难逢。
开头几年,我们8人三餐合伙吃饭。每天由一人轮流值日,负责买菜烧菜煮饭。俗话说“共天下容易,共饭镬难”,后来时间一久,矛盾多了,吵嘴也多了。你说菜太贵,他说饭煮糊了……,只得散伙单干。但散伙后问题更多,更辛苦。干活回来,锅里冷冰冰,又要生火又要烧饭、烧菜,累得苦不堪言。
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们女知青最怕是干活时小便与回家洗澡,这是两大难题。干活的都是男人(当地妇女是不出垟的),想“方便”很不方便;再一个是洗澡,四个女孩子住在一起,当时没有卫生间,洗澡是个大问题。于是大家约法三章:每人各备一盆水,背靠背各自面壁,同时宽衣解带,洗毕穿好衣服后才允许回头。
光阴荏苒,时光流逝。在很多人眼里,我们这些人属于“三等公民”。当初的热情逐渐冷却了,前途也越来越渺茫了。大家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请假回家的时间多了,出工少了,一年中只在农忙时干几天活。大队对我们管束也宽松了,我们几乎成了队里可有可无的社员。大家都在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的出路。其中有的女知青嫁给当地殷实富裕的农民家庭;有的男知青与当地女青年结婚;有的通过关系的到厂家那怕手工作坊干临时工;幸运的被聘为当地民办教师。1970年,我年满26岁,整天为自己的前途唉声叹气。我既无高深文化,又无门道,但又亟待想跳出这“农门”,在当时谈何容易!老天爷还算有眼,这年,在一位亲戚的穿针引线下,把我知青关系转到平阳县万全区农村,当上一位民办教师。每月可拿到26元的工资(国家仅补助14元,有12元要到大队领取),比起“三等公民”不知好多少倍了,我已很知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青的春天来了。1979年我有幸参加平阳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考试,“白卷”年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什么“知识”可谈?许多人只认得自己的姓名、数十个常用汉字与阿拉伯字。记得当年作文题是《我们要学习张志新的大无畏精神》,据说全场白卷。这些修补地球的知青整天与泥巴打交道,哪有工夫关心“国家大事”?张志新是男是女也搞不清楚,哪里写得出什么“精神”?由于我当了几年民办教师,接触到一些文化,有幸考中。录用后重执教鞭,耕耘在三尺讲台,直止退休。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虽然我们韶华已逝,一切已事过境迁,但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重温尘封的记忆。它毕竟是共和国的一段历史,更是我人生的一段重要历程!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