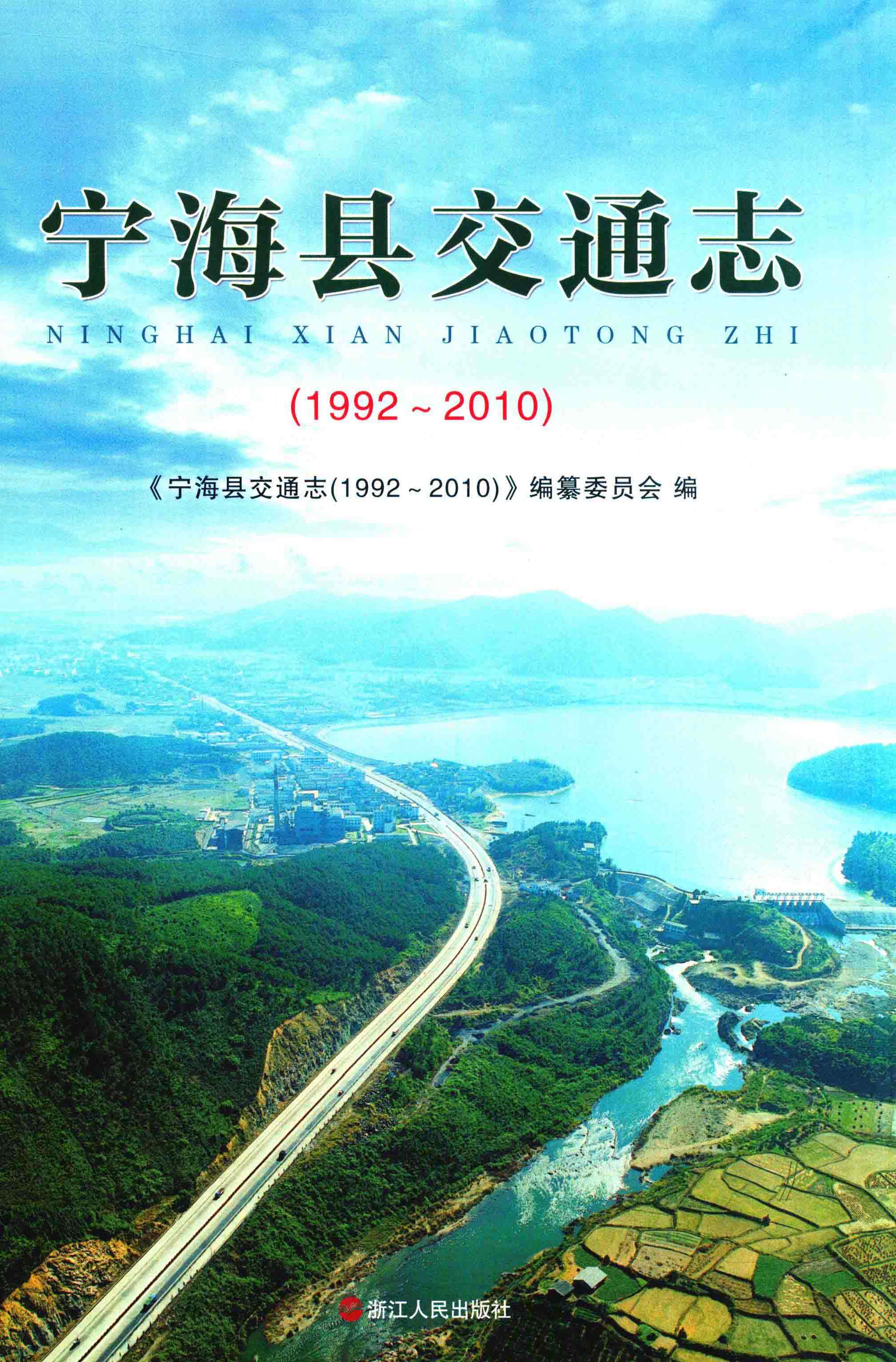内容
长街交通简况
长街地处三门湾畔,是三面环海的半岛。只有北面与本县胡陈乡及象山县丁岙、苏岙、马岙接壤,有陆路相通,其余出入均需乘船摆渡。古时长街半岛生产的农副产品大宗靠海上水运出口,小宗农副产品全凭肩挑步行至北部胡陈、力洋、茶院、桥头桥等地出售,交通极为不便。
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长街步行至县城,要经过沥头渡、毛屿渡、冷梵岭、白峤岭等渡口、山岭,跋山涉水,行程近百里,耗时近一天。由于交通极不方便,不少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
1958年省道盛宁线(宁象公路)建成通车。盛宁线途经胡陈,开始筹建胡陈至长街的公路,即从盛宁线K107+050处折南,越猫儿岭、山洋岭,经海岙塘、九江至长街。按山岭六级标准测设,弯道37处,平曲线最小半径15米,最大纵坡8%。由于当时机械化程度极低,施工难度相当大,国家补助资金1.7万元(宁象公路工程结余款),并提供钢钎雷管炸药,土地劳力由群众负担。当时社会群众的积极性极高,他们自带饭米、铺盖行李,吃住在工地上,按划分路段施工,全凭体力肩挑背扛,挥锤钢钎凿炮眼,劈山放岩,驳坎填沟,历时一年的艰苦奋战,一条全长12.6千米,路基宽7.5米,路面宽3.5米(含涵洞79道,桥梁1座长32.3延米)的砂石公路,于1959年12月竣工验收,1960年7月正式通车。自此,境内龙浦、青珠、山头、伍山、岳井等地民众可步行5~10千米到长街车站上车去县城。
以往,长街境内大都是烂泥路,有几条主干道为断续的小石板路,20世纪60年代初部分主干道被改建为手拉车路。1968年9月,按平原六级标准测设,国家补助1.7万元,土地劳力由沿途群众负担,实用劳力7.1万工,将长街至青珠农场段改建成长10千米的砂石公路,于1970年夏正式通车;1970年春,又动工修建长街至岳井公路。起于长街车站,经洋湖闸,跨车岙港,越山前岭至岳井,全长6.9千米。其间因资金材料不足而停工,1972年重新测设施工,1974年5月竣工,10月验收通车,总投资7.3万元,其中,国家补助4.5万元。
胡陈港筑坝截流后,1982年6月开始筹建明港至青珠农场公路,全长3.85千米。按“民办公助”的原则,国家补助5.5万元,有关部门出资:下洋涂工程指挥部3万元、青珠农场1.5万元、棉花厂包干6.4万元、青珠乡包干2.6万元、前横乡包干6.4万元,劳力由群众义务负担,至1985年12月竣工。该公路自力洋,经古渡、明港、农场、青珠、山头、大湖、长街、胡陈,经盛宁线回到力洋,沿力洋、明港、长街、胡陈各镇乡环绕一周,使农场到宁海的路程缩短13千米。
1998年10月,动工修建宁波市沿海南线一级公路宁海段,长街境内西起胡陈港大桥,东至伍山松岙码头,途经沥头、施家、娘娘宫、石桥头、渡头、松岙等10个自然村。2003年11月建成通车。把长街至宁海的路程缩短为31千米。
至此,长街外接县省道内连各自然村及工农业园区,路面拓宽上等级,道路货客运便捷高效,长街人进城只需半个小时,境内各村10~20分钟内可抵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交通建设,长街人摆脱了“出行难”的困境,改革开放的20年见证了长街跨入交通现代化的历程。
(陈培川 2013年12月)
天堑变通途
祖孙三代五人坐在小车里,从家出发,不到5分钟就到达松岙码头,刚好赶上汽轮渡启航。小车停在甲板的后部靠船舷的地方,车前已排满几十辆大小车辆。儿子坐在驾驶座上;孙儿坐在安全椅里,趴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大海和远处的群山,问这问那,坐在旁边的妈妈和奶奶做他的义务讲解员;我仰靠在副驾驶的座位上,闭目养神。一家人在温暖的车厢里任凭外面寒风呼啸,雨雪纷飞。渡轮正在横渡波涛汹涌的岳井洋,向对岸天宁码头驶去,我的心潮如同岳井洋上澎湃的浪涛翻腾不息。50多年前难忘的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我的祖居地在象山县石浦镇金鸡山,幼年随父母迁住在宁海县长街镇下湾塘村。祖母外婆以及主要亲戚都在金鸡山,我们要经常往来于两地,两地仅陆路就相距45里,要翻三座山岭,更伤脑筋的还要过两个渡,其中一个就是岳井渡。父亲和长兄是家里的劳力,需天天参加劳动,我们又小,有什么事大都是母亲来往两地。母亲生于清朝末年,裹过脚,走路极为不便,有时还要背着小孩,手提包袱,一天要步行这么远的路,可累坏了。那时的道路哪有现在这么好,大都是烂泥路(无一点沙石),稍好一点的是烂泥路铺上几块小石板,最好的是过山岭时走的石子路和自然山石路。烂泥路天晴时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下雨时一片泥泞,稍不注意就会滑倒,轻则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严重的会摔个仰面朝天。这样的路对老弱妇孺来说可苦坏了。
在上述的路上步行还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过渡了。我们要过的有两个渡,一个是中岙到大塘岛的中岙渡,此渡不宽,不到千米,以小舢板摇橹摆渡过往行人。即使有风浪也不太大,渡船也会很快横渡海港,到达对岸。可岳井渡就不同了,岳井渡从我县岳井的李家至象山大塘英山,宁海人称岳井渡,有时为了区别于岳井王家至隔洋塘的王家渡,也把岳井渡叫作李家渡;象山人叫它为英山渡。岳井洋号称十里洋面,实际上横渡直线距离四五里,但两岸衜头之间是斜对角的,至少相距六七里,再加上木帆渡船不是直线航行,实际行驶距离确有十来里。好在此渡的渡船比中岙渡的渡船大得多,载重量为十吨左右的大钓船。大钓船摆渡,无风时全靠船老大一人摇着一支橹驶船,速度很慢,客人中会摇橹的都会帮着摇边橹.这样速度会快些。如遇到顶头风,又是逆流,单一个船老大摇橹过渡至少要花两个小时。有风的话,可扯篷(帆)借助风力行驶,可省力得多了。岳井洋是南北流向,而摆渡是东西方向而行,不是顺风,但船老大会用掉戗的方式,借助风力,潮流,全靠船舵和帆及风力的合力,能使渡船不断变换行船方向,成“之”字形线路驶往对岸。如遇到刮大北风,又是涨潮,海浪特别大,渡船则如一片树叶在浪涛中颠簸前行。有时一浪打来,海水泼进船舱,乘客都成了“落汤鸡”。寒冬腊月,阴风怒号,滴水成冰,乘客之苦可想而知了。最危险的是渡船在掉戗转缭时,本来船侧向一边前行,船旁紧擦着海面,布篷的下角都浸在水里了,乘客心里已很紧张,当船老大一转舵,渡船改变行驶方向,随之,帆从一边甩向另一边,船即侧向另一边,乘客若不注意往往会从一侧倒向另一侧,这样一来帆船改变了重心,很容易造成转缭时翻船。经常往来的乘客此时都十分注意,转缭前船老大会高声告知:“要转缭了,大家坐稳,千万不能提起屁股。”但也有些从未乘过船的人,不知什么叫转缭,往往会出问题。大概我在十几岁时曾亲眼看见一个青年在转缭时从船的一侧滚到另一侧船帮,要不是一个大叔一手把他拉住,他肯定被抛到大海里去了。这个青年大概来自山区,恐怕不会游泳,掉到水里肯定要喝饱又咸又苦又涩又冷的海水了。
岳井渡两岸海涂上都建有衜头,衜头是用大块方石板从塘岸开始向下铺,一直铺到大潮汛最低潮时的水和泥涂的交接处,离岸越远,海涂越软,受风浪冲击越大,石板两边的木桩极易腐烂,年久失修,下截衜头的石板东倒西歪,有的陷入海涂中。再好的路段,石板上也积满一层厚厚的又稀又泥泞的淤泥,就是年轻力壮者也必须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前行,一不小心就会一屁股坐在满是泥浆的石板上,或双脚插入没膝的泥涂里。石板的四周又长满了蟌(学名藤壶)和牡蛎,往往会割破你的裤子,甚至腿脚,鲜血淋漓。记得一次过渡上英山衜头时,一对新婚夫妇回娘家,新女婿挑着一双套篮,不幸滑倒了,套篮里的礼品撒了一地,新女婿满身泥浆,右手掌还流着鲜血,新娘子哭了,夫妻俩不知所措……前面说过,我的母亲是裹过小脚的,遇到这种情况,她就用在路上事先捡来的木棍或竹竿当拐杖拄着,一步一步前行。有时好心的人也会搀扶她前行,帮她一把。最犯难的是遇到刮大北风,又是逆流,渡船被推向下游,无法在码头停靠,并且船与海涂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跳板够不着,这可苦坏了老弱妇孺。像我母亲这样的小脚女人就是站在泥涂里不动也会像木桩一样深深地陷进去,更不用说迈步行走了。摆渡的船老大都比较好,对老弱妇孺都会将他们一个一个背上岸。有个老大名叫妙香,大塘人,比我父亲大几岁,为人很好,背过我好几次,我们管他叫妙香伯。寒风凛冽,海涂边上都结了薄冰,他近六旬的人,将裤管卷到大腿根,在彻骨的海水里和没膝的淤泥里背着100来斤重的人深一脚浅一脚前行。这些船老大真了不起。还有一位船老大叫张生堂,虽然有时态度不大好,嘴里骂骂咧咧,可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边大声叫骂,边帮助他人。
那时候没有气象预报,出发时天气晴好,但到了近午或午后,什么时候下起大雨、刮起大风也不一定。岳井洋上空彤云密布,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惊涛拍岸,渡船不得不停渡了。过渡的人望洋兴叹,真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了。我母亲曾有好几次被阻,无法回家,且已是下午,又回不了老家。幸亏英山村的村民热情,只要有人借宿,都会收留无法过渡的素不相识的外乡人,从不收报酬。
车子发动了,把我遐思的野马勒住了缰绳。儿子将小车驶上了宽阔坚固的台宁码头,行不到千米就驶上了宁波沿海南线象山段的一级公路。十几分钟就到了老家。现在从家出发,如果上下船不耽误时间,不到40分钟就能到老家。母亲如在天有灵,知道当年的岳井洋天堑如今成了风浪无阻的通途,她的子孙后代再也不吃她当年吃过的苦,老人家定会含笑九泉。
(林常飞 2013年12月)
长街人上城记
编罢《宁海县交通志(1992~2010)》,深为我县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而惊叹,作为长街人,我对长街的交通变迁感受尤为深刻。
长街远离城关,虽有山岭河海阻隔,但直线距离不到30千米。走捷径上城,经沥头渡、毛屿渡,需一整天;若仅过沥头渡,需大半天。而长街东首隔洋塘人上城,还要增加岳井洋、山前渡,故连过三四个渡,费时需一天半。
后虽通了公路,也是绕道而行。先折北绕道胡陈、沥洋至城关;后折南绕道胡陈港大坝、沥洋至城关。车程近60千米,耗时近两个小时,还受颠簸劳顿之苦。长街人一直视上城路为畏途。
如今宁波市沿海南线宁海段宁松线开通,长街人上城走捷径,车程31千米,耗时仅半个小时,快捷、安全、轻松,畏途变通途。抚今忆昔,感慨良多,特以自己的几次经历作为历史的见证。
1958年秋,我有幸出席宁海县少年先锋队“除四害、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表彰会。由于长街至胡陈公路刚开始修建,长亭港至白峤港机动客货运输船已于1954年10月1日开航,所以我第一次上城走的是水路。那天午后,我步行10多里来到长亭港埠头。潮水涨得高高的,一张长跳板斜搁在浮动着的船舷上,胆子大的迈10多步就上了船,几位妇女走在抖动摇晃的跳板上不时发出尖叫,我也胆战心惊地跟着上了船。锚起,老大驾舵自北向南,迎着风破浪向前。行驶中,柴油机的噪声特别大,排出团团黑色烟雾,舱内显得很沉闷,加上船体振动、颤抖,一下子把大家搞得晕头转向。当驶出胡陈港口进入大洋折西时,突然海风大了起来,巨浪把船头拍打得砰砰响,顿时船体剧烈颠簸摇晃,不少人由此晕船、呕吐。待过了力洋港进入白峤港时,潮落,风浪缓和,航船才平稳下来。不久,航船停泊,待潮水涨到一定高度时,才驶抵水车港头埠。月光下,经水车村,穿过大溪滩小竹林区,沿溪边卵石路,进小南门,到达县政府招待所(孔庙)时,已是晚上10点。水陆路全程约70千米,历时近10个小时,当初认为乘汽帆船是一种享受,实际却感到身心疲惫。令人欣慰的是“大开眼界”了,第一次见到了电灯、长长的发光体(日光灯),有人告诉我这叫“电杖”,第一次见到汽车。
1960年1月7日公路通车,开创了长街人可乘汽车上城的历史。我第二次上城是在去宁海中学读书的1963年9月。当初,汽车以木炭为燃料,俗称白炭车。日发班车早晚各一班,成人票价1.22元,长街至宁海全程54.2千米,单程需两个小时左右。上城前几天,我托人好不容易买到一张车票。那天上午,自长街站出发,当汽车行驶到乌沙岭稍陡路段时,车胎就开始打滑,发动机咕噜咕噜,好一阵子汽车才爬上去,坐在前排的我感到煤焦臭气冲心、头晕,坐在我身旁的那位则呕出声来。经几个大转弯,山洋岭没有过半,车内好几个人与我一样,已呕吐了好几回。在殃及旁人的同时,我只得闭着眼睛瘫坐着。左右摇晃得厉害时,心里明白车子已绕过几个大转弯。当车子再度咕噜咕噜拉不动、倒退、停住,驾驶员叫大家下车将汽车推上岭时,才知道“老爷车”在爬猫儿岭陡峭段时,动力不足抛锚了。岭顶重新上车,启动开行,过胡陈、沥洋,爬过庙岭,到苔芳、路湾时才稍缓解定神。听人说,白峤岭比山洋岭更陡更盘旋。当过雪坡进入白峤村时我心情就开始紧张,果然,到白峤岭经几个转弯,车内“呕、呕”声四起,不少人又开始呕吐,接着不断盘旋不断呕吐,多次呕吐,呕出的就只是清水与青黄胆液。“老爷车”也咕噜咕噜吃力地爬行着,当爬到最陡峭时再次熄火、停车,大家再次从车上下来,待驾驶员摇动鼓风机给白炭炉不断鼓风,车子才重新启动开行,一波三折,总算抵达终点站小北门。下车时,头昏眼花天旋地转,辨不清东西南北。上城一次如同生了一场大病。
除了乘汽帆船、汽车上城外,第三种形式就是步行。说实在,有现成的公车不乘,选择步行回家,实属出于无奈。一则,乘车的痛苦已经充分领教,虽说费时仅两个小时,但晕车产生的后遗症,几天都恢复不过来。有人甚至看到车票,就开始头晕、恶心。二则,对穷学生来说3元钱人民助学金已够一个月的生活费,相比之下这1.22元车费不是小数目。住在岳井对岙洞的金敬和同学,为了省下长街至胡陈这段0.22元车旅费,在姐姐的帮助下,两人轮换肩担六七十斤行李(被褥、米、下饭菜),经大水库长堤,绕乌沙岭饭蒸山,翻越山洋岭、猫儿岭,历时近3个小时,肩头磨破,脚底起泡,下午1时总算赶到胡陈,乘上长街经胡陈至宁海城关的末班车。因当时上班族工资不足30元,父辈在生产队劳动高的仅五六角一天,而且要待年终分红,赚点钱的确不容易。所以,去宁海读高中的张晓邦、黄金法、鲍林岳、吴华松、金敬和、叶余青、黄道基等长街初中前七届毕业同学,普遍选择结伴步行。对于步行来说除了劳累以外,最担心的是过渡。俗话说“迟一步,差一渡”,一渡之差,摇橹摆渡来回需等候一两个小时。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次是1964年的一个星期六,上午课后,我与同学王其林、吴华松三人,临时商定回长街。由于事先没有回家的打算,中餐吃得不多,总认为没有行李,空着双手走走快一点,夏日天长,加上毛屿港已堵,只要沥头渡能过去就能到家。因此,匆促上路,抄小道,没多少时间就爬上了白峤岭,但都感到有点饿。正值杨梅上市,于是拿出6分钱在白峤村头买了2斤,解渴充饥,谁知吃了杨梅,一下子胃“烧”起来,越来越感到饥饿,当走过雪坡近亭头时,排出的小便都是红的,担心吃了“落地杨梅”中毒、闯祸了,拉出的是“血”。饥饿加害怕,为了赶渡继续前行。当走到石墙头路廊时已经相当疲惫,稍作休息,这时,突然响起两声闷雷,抬头见西南天边乌云崛起,分明是下雷雨的前兆,三人赶紧上路,指望能在下雨前走过毛屿塘岸。谁知走上塘岸没几分钟,天一下子暗了下来,紧接着电闪雷鸣,几声霹雳好像打在眼前。一阵狂风后,大雨倾盆,淋得我们睁不开眼睛,全身湿透,干燥的塘岸路顷刻淌水变得湿滑泥泞。我们立刻脱下千纽草鞋(家里人专为我们步行用碎布条代替稻草编织的草鞋),使出长街人走烂泥路的绝招,即勾起脚趾头在泥泞溜滑的泥路上高频率竞走。雨拼命地下着,也顾不得脚绊毛栗刺,摔倒爬起,连滚带爬,折腾了好久,才看见海岸边侧翻待修理的渔船,三人急忙钻到船底下躲雨,一身泥水又湿又冷。王其林调侃说,我们这副样子就是“落汤鸡”,连脚边这两只红钳蟹也在笑我们。吴华松接着说,这才叫“饥寒交迫”,你看那条弹涂鱼眨着眼望着我们这三个“憨头”。大约又过去了半个小时,雨才慢慢地停了下来,随之钻出了夕阳,为了赶渡,我们只得勉强上路。遇见卖桃的,又买了几分钱的桃,分吃了两个。到冷梵岭脚时,实在走不动了,吃下的桃子再次“烧”起来,更加难受。但心里明白过岭后前边就是沥头渡,过渡就可到家,于是互相鼓励,挣扎着前行。到渡口时,渡船早已过去,过不去了,尽管朝对岸拼足全力喊叫“老大过渡”,无人回应,只能望洋兴叹。当晚,投宿在洞门王其林娘舅家,娘舅看着我们这副狼狈相,心疼,马上给我们换衣、烤火取暖……第二天上午我们才蹒跚到家。
长街人上城难,往事桩桩,不胜一一枚举。俱往矣!
1960年7月,长街至胡陈公路通车,长街人可乘汽车上城。1978年,长街至青珠农场公路通车。1986年,力胡线(力洋经古渡、明港、农场、长街至胡陈)通车。1999年7月,车岙港大桥工程竣工。2003年,架起毛屿港、胡陈港大桥。6月,宁松线四车道一级公路开通,一下子把宁海与长街的公路里程缩短到31千米。从砂石路面到沥青、水泥混凝土路面,道路不断降坡、拓宽、截弯取直。原长街境内多数都是烂泥路,如今村村通公路,而且路面硬化上等级。路况与车况发生了质的变化,乘车的安全性与舒适度得到显著提高。现在,长街站至城区日均始发班车58辆246班次,路上有多个港湾式停靠站,上下车十分方便。除县乡道班车外,私家车已进入千家万户。如今,长街境内的人可在自己的村头、家门口乘车,心想事成,想要去哪就去哪,出行上城安全便捷,畏途变通途已成现实。
现代交通造福长街,长街人的“上城难”渐渐被淡忘,年轻一代更无从知晓。为了留住那段难忘的记忆,谨撰此文以记之。
(胡家康 201 3年1 2月)
长街地处三门湾畔,是三面环海的半岛。只有北面与本县胡陈乡及象山县丁岙、苏岙、马岙接壤,有陆路相通,其余出入均需乘船摆渡。古时长街半岛生产的农副产品大宗靠海上水运出口,小宗农副产品全凭肩挑步行至北部胡陈、力洋、茶院、桥头桥等地出售,交通极为不便。
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长街步行至县城,要经过沥头渡、毛屿渡、冷梵岭、白峤岭等渡口、山岭,跋山涉水,行程近百里,耗时近一天。由于交通极不方便,不少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
1958年省道盛宁线(宁象公路)建成通车。盛宁线途经胡陈,开始筹建胡陈至长街的公路,即从盛宁线K107+050处折南,越猫儿岭、山洋岭,经海岙塘、九江至长街。按山岭六级标准测设,弯道37处,平曲线最小半径15米,最大纵坡8%。由于当时机械化程度极低,施工难度相当大,国家补助资金1.7万元(宁象公路工程结余款),并提供钢钎雷管炸药,土地劳力由群众负担。当时社会群众的积极性极高,他们自带饭米、铺盖行李,吃住在工地上,按划分路段施工,全凭体力肩挑背扛,挥锤钢钎凿炮眼,劈山放岩,驳坎填沟,历时一年的艰苦奋战,一条全长12.6千米,路基宽7.5米,路面宽3.5米(含涵洞79道,桥梁1座长32.3延米)的砂石公路,于1959年12月竣工验收,1960年7月正式通车。自此,境内龙浦、青珠、山头、伍山、岳井等地民众可步行5~10千米到长街车站上车去县城。
以往,长街境内大都是烂泥路,有几条主干道为断续的小石板路,20世纪60年代初部分主干道被改建为手拉车路。1968年9月,按平原六级标准测设,国家补助1.7万元,土地劳力由沿途群众负担,实用劳力7.1万工,将长街至青珠农场段改建成长10千米的砂石公路,于1970年夏正式通车;1970年春,又动工修建长街至岳井公路。起于长街车站,经洋湖闸,跨车岙港,越山前岭至岳井,全长6.9千米。其间因资金材料不足而停工,1972年重新测设施工,1974年5月竣工,10月验收通车,总投资7.3万元,其中,国家补助4.5万元。
胡陈港筑坝截流后,1982年6月开始筹建明港至青珠农场公路,全长3.85千米。按“民办公助”的原则,国家补助5.5万元,有关部门出资:下洋涂工程指挥部3万元、青珠农场1.5万元、棉花厂包干6.4万元、青珠乡包干2.6万元、前横乡包干6.4万元,劳力由群众义务负担,至1985年12月竣工。该公路自力洋,经古渡、明港、农场、青珠、山头、大湖、长街、胡陈,经盛宁线回到力洋,沿力洋、明港、长街、胡陈各镇乡环绕一周,使农场到宁海的路程缩短13千米。
1998年10月,动工修建宁波市沿海南线一级公路宁海段,长街境内西起胡陈港大桥,东至伍山松岙码头,途经沥头、施家、娘娘宫、石桥头、渡头、松岙等10个自然村。2003年11月建成通车。把长街至宁海的路程缩短为31千米。
至此,长街外接县省道内连各自然村及工农业园区,路面拓宽上等级,道路货客运便捷高效,长街人进城只需半个小时,境内各村10~20分钟内可抵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交通建设,长街人摆脱了“出行难”的困境,改革开放的20年见证了长街跨入交通现代化的历程。
(陈培川 2013年12月)
天堑变通途
祖孙三代五人坐在小车里,从家出发,不到5分钟就到达松岙码头,刚好赶上汽轮渡启航。小车停在甲板的后部靠船舷的地方,车前已排满几十辆大小车辆。儿子坐在驾驶座上;孙儿坐在安全椅里,趴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大海和远处的群山,问这问那,坐在旁边的妈妈和奶奶做他的义务讲解员;我仰靠在副驾驶的座位上,闭目养神。一家人在温暖的车厢里任凭外面寒风呼啸,雨雪纷飞。渡轮正在横渡波涛汹涌的岳井洋,向对岸天宁码头驶去,我的心潮如同岳井洋上澎湃的浪涛翻腾不息。50多年前难忘的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我的祖居地在象山县石浦镇金鸡山,幼年随父母迁住在宁海县长街镇下湾塘村。祖母外婆以及主要亲戚都在金鸡山,我们要经常往来于两地,两地仅陆路就相距45里,要翻三座山岭,更伤脑筋的还要过两个渡,其中一个就是岳井渡。父亲和长兄是家里的劳力,需天天参加劳动,我们又小,有什么事大都是母亲来往两地。母亲生于清朝末年,裹过脚,走路极为不便,有时还要背着小孩,手提包袱,一天要步行这么远的路,可累坏了。那时的道路哪有现在这么好,大都是烂泥路(无一点沙石),稍好一点的是烂泥路铺上几块小石板,最好的是过山岭时走的石子路和自然山石路。烂泥路天晴时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下雨时一片泥泞,稍不注意就会滑倒,轻则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严重的会摔个仰面朝天。这样的路对老弱妇孺来说可苦坏了。
在上述的路上步行还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过渡了。我们要过的有两个渡,一个是中岙到大塘岛的中岙渡,此渡不宽,不到千米,以小舢板摇橹摆渡过往行人。即使有风浪也不太大,渡船也会很快横渡海港,到达对岸。可岳井渡就不同了,岳井渡从我县岳井的李家至象山大塘英山,宁海人称岳井渡,有时为了区别于岳井王家至隔洋塘的王家渡,也把岳井渡叫作李家渡;象山人叫它为英山渡。岳井洋号称十里洋面,实际上横渡直线距离四五里,但两岸衜头之间是斜对角的,至少相距六七里,再加上木帆渡船不是直线航行,实际行驶距离确有十来里。好在此渡的渡船比中岙渡的渡船大得多,载重量为十吨左右的大钓船。大钓船摆渡,无风时全靠船老大一人摇着一支橹驶船,速度很慢,客人中会摇橹的都会帮着摇边橹.这样速度会快些。如遇到顶头风,又是逆流,单一个船老大摇橹过渡至少要花两个小时。有风的话,可扯篷(帆)借助风力行驶,可省力得多了。岳井洋是南北流向,而摆渡是东西方向而行,不是顺风,但船老大会用掉戗的方式,借助风力,潮流,全靠船舵和帆及风力的合力,能使渡船不断变换行船方向,成“之”字形线路驶往对岸。如遇到刮大北风,又是涨潮,海浪特别大,渡船则如一片树叶在浪涛中颠簸前行。有时一浪打来,海水泼进船舱,乘客都成了“落汤鸡”。寒冬腊月,阴风怒号,滴水成冰,乘客之苦可想而知了。最危险的是渡船在掉戗转缭时,本来船侧向一边前行,船旁紧擦着海面,布篷的下角都浸在水里了,乘客心里已很紧张,当船老大一转舵,渡船改变行驶方向,随之,帆从一边甩向另一边,船即侧向另一边,乘客若不注意往往会从一侧倒向另一侧,这样一来帆船改变了重心,很容易造成转缭时翻船。经常往来的乘客此时都十分注意,转缭前船老大会高声告知:“要转缭了,大家坐稳,千万不能提起屁股。”但也有些从未乘过船的人,不知什么叫转缭,往往会出问题。大概我在十几岁时曾亲眼看见一个青年在转缭时从船的一侧滚到另一侧船帮,要不是一个大叔一手把他拉住,他肯定被抛到大海里去了。这个青年大概来自山区,恐怕不会游泳,掉到水里肯定要喝饱又咸又苦又涩又冷的海水了。
岳井渡两岸海涂上都建有衜头,衜头是用大块方石板从塘岸开始向下铺,一直铺到大潮汛最低潮时的水和泥涂的交接处,离岸越远,海涂越软,受风浪冲击越大,石板两边的木桩极易腐烂,年久失修,下截衜头的石板东倒西歪,有的陷入海涂中。再好的路段,石板上也积满一层厚厚的又稀又泥泞的淤泥,就是年轻力壮者也必须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前行,一不小心就会一屁股坐在满是泥浆的石板上,或双脚插入没膝的泥涂里。石板的四周又长满了蟌(学名藤壶)和牡蛎,往往会割破你的裤子,甚至腿脚,鲜血淋漓。记得一次过渡上英山衜头时,一对新婚夫妇回娘家,新女婿挑着一双套篮,不幸滑倒了,套篮里的礼品撒了一地,新女婿满身泥浆,右手掌还流着鲜血,新娘子哭了,夫妻俩不知所措……前面说过,我的母亲是裹过小脚的,遇到这种情况,她就用在路上事先捡来的木棍或竹竿当拐杖拄着,一步一步前行。有时好心的人也会搀扶她前行,帮她一把。最犯难的是遇到刮大北风,又是逆流,渡船被推向下游,无法在码头停靠,并且船与海涂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跳板够不着,这可苦坏了老弱妇孺。像我母亲这样的小脚女人就是站在泥涂里不动也会像木桩一样深深地陷进去,更不用说迈步行走了。摆渡的船老大都比较好,对老弱妇孺都会将他们一个一个背上岸。有个老大名叫妙香,大塘人,比我父亲大几岁,为人很好,背过我好几次,我们管他叫妙香伯。寒风凛冽,海涂边上都结了薄冰,他近六旬的人,将裤管卷到大腿根,在彻骨的海水里和没膝的淤泥里背着100来斤重的人深一脚浅一脚前行。这些船老大真了不起。还有一位船老大叫张生堂,虽然有时态度不大好,嘴里骂骂咧咧,可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边大声叫骂,边帮助他人。
那时候没有气象预报,出发时天气晴好,但到了近午或午后,什么时候下起大雨、刮起大风也不一定。岳井洋上空彤云密布,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惊涛拍岸,渡船不得不停渡了。过渡的人望洋兴叹,真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了。我母亲曾有好几次被阻,无法回家,且已是下午,又回不了老家。幸亏英山村的村民热情,只要有人借宿,都会收留无法过渡的素不相识的外乡人,从不收报酬。
车子发动了,把我遐思的野马勒住了缰绳。儿子将小车驶上了宽阔坚固的台宁码头,行不到千米就驶上了宁波沿海南线象山段的一级公路。十几分钟就到了老家。现在从家出发,如果上下船不耽误时间,不到40分钟就能到老家。母亲如在天有灵,知道当年的岳井洋天堑如今成了风浪无阻的通途,她的子孙后代再也不吃她当年吃过的苦,老人家定会含笑九泉。
(林常飞 2013年12月)
长街人上城记
编罢《宁海县交通志(1992~2010)》,深为我县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而惊叹,作为长街人,我对长街的交通变迁感受尤为深刻。
长街远离城关,虽有山岭河海阻隔,但直线距离不到30千米。走捷径上城,经沥头渡、毛屿渡,需一整天;若仅过沥头渡,需大半天。而长街东首隔洋塘人上城,还要增加岳井洋、山前渡,故连过三四个渡,费时需一天半。
后虽通了公路,也是绕道而行。先折北绕道胡陈、沥洋至城关;后折南绕道胡陈港大坝、沥洋至城关。车程近60千米,耗时近两个小时,还受颠簸劳顿之苦。长街人一直视上城路为畏途。
如今宁波市沿海南线宁海段宁松线开通,长街人上城走捷径,车程31千米,耗时仅半个小时,快捷、安全、轻松,畏途变通途。抚今忆昔,感慨良多,特以自己的几次经历作为历史的见证。
1958年秋,我有幸出席宁海县少年先锋队“除四害、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表彰会。由于长街至胡陈公路刚开始修建,长亭港至白峤港机动客货运输船已于1954年10月1日开航,所以我第一次上城走的是水路。那天午后,我步行10多里来到长亭港埠头。潮水涨得高高的,一张长跳板斜搁在浮动着的船舷上,胆子大的迈10多步就上了船,几位妇女走在抖动摇晃的跳板上不时发出尖叫,我也胆战心惊地跟着上了船。锚起,老大驾舵自北向南,迎着风破浪向前。行驶中,柴油机的噪声特别大,排出团团黑色烟雾,舱内显得很沉闷,加上船体振动、颤抖,一下子把大家搞得晕头转向。当驶出胡陈港口进入大洋折西时,突然海风大了起来,巨浪把船头拍打得砰砰响,顿时船体剧烈颠簸摇晃,不少人由此晕船、呕吐。待过了力洋港进入白峤港时,潮落,风浪缓和,航船才平稳下来。不久,航船停泊,待潮水涨到一定高度时,才驶抵水车港头埠。月光下,经水车村,穿过大溪滩小竹林区,沿溪边卵石路,进小南门,到达县政府招待所(孔庙)时,已是晚上10点。水陆路全程约70千米,历时近10个小时,当初认为乘汽帆船是一种享受,实际却感到身心疲惫。令人欣慰的是“大开眼界”了,第一次见到了电灯、长长的发光体(日光灯),有人告诉我这叫“电杖”,第一次见到汽车。
1960年1月7日公路通车,开创了长街人可乘汽车上城的历史。我第二次上城是在去宁海中学读书的1963年9月。当初,汽车以木炭为燃料,俗称白炭车。日发班车早晚各一班,成人票价1.22元,长街至宁海全程54.2千米,单程需两个小时左右。上城前几天,我托人好不容易买到一张车票。那天上午,自长街站出发,当汽车行驶到乌沙岭稍陡路段时,车胎就开始打滑,发动机咕噜咕噜,好一阵子汽车才爬上去,坐在前排的我感到煤焦臭气冲心、头晕,坐在我身旁的那位则呕出声来。经几个大转弯,山洋岭没有过半,车内好几个人与我一样,已呕吐了好几回。在殃及旁人的同时,我只得闭着眼睛瘫坐着。左右摇晃得厉害时,心里明白车子已绕过几个大转弯。当车子再度咕噜咕噜拉不动、倒退、停住,驾驶员叫大家下车将汽车推上岭时,才知道“老爷车”在爬猫儿岭陡峭段时,动力不足抛锚了。岭顶重新上车,启动开行,过胡陈、沥洋,爬过庙岭,到苔芳、路湾时才稍缓解定神。听人说,白峤岭比山洋岭更陡更盘旋。当过雪坡进入白峤村时我心情就开始紧张,果然,到白峤岭经几个转弯,车内“呕、呕”声四起,不少人又开始呕吐,接着不断盘旋不断呕吐,多次呕吐,呕出的就只是清水与青黄胆液。“老爷车”也咕噜咕噜吃力地爬行着,当爬到最陡峭时再次熄火、停车,大家再次从车上下来,待驾驶员摇动鼓风机给白炭炉不断鼓风,车子才重新启动开行,一波三折,总算抵达终点站小北门。下车时,头昏眼花天旋地转,辨不清东西南北。上城一次如同生了一场大病。
除了乘汽帆船、汽车上城外,第三种形式就是步行。说实在,有现成的公车不乘,选择步行回家,实属出于无奈。一则,乘车的痛苦已经充分领教,虽说费时仅两个小时,但晕车产生的后遗症,几天都恢复不过来。有人甚至看到车票,就开始头晕、恶心。二则,对穷学生来说3元钱人民助学金已够一个月的生活费,相比之下这1.22元车费不是小数目。住在岳井对岙洞的金敬和同学,为了省下长街至胡陈这段0.22元车旅费,在姐姐的帮助下,两人轮换肩担六七十斤行李(被褥、米、下饭菜),经大水库长堤,绕乌沙岭饭蒸山,翻越山洋岭、猫儿岭,历时近3个小时,肩头磨破,脚底起泡,下午1时总算赶到胡陈,乘上长街经胡陈至宁海城关的末班车。因当时上班族工资不足30元,父辈在生产队劳动高的仅五六角一天,而且要待年终分红,赚点钱的确不容易。所以,去宁海读高中的张晓邦、黄金法、鲍林岳、吴华松、金敬和、叶余青、黄道基等长街初中前七届毕业同学,普遍选择结伴步行。对于步行来说除了劳累以外,最担心的是过渡。俗话说“迟一步,差一渡”,一渡之差,摇橹摆渡来回需等候一两个小时。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次是1964年的一个星期六,上午课后,我与同学王其林、吴华松三人,临时商定回长街。由于事先没有回家的打算,中餐吃得不多,总认为没有行李,空着双手走走快一点,夏日天长,加上毛屿港已堵,只要沥头渡能过去就能到家。因此,匆促上路,抄小道,没多少时间就爬上了白峤岭,但都感到有点饿。正值杨梅上市,于是拿出6分钱在白峤村头买了2斤,解渴充饥,谁知吃了杨梅,一下子胃“烧”起来,越来越感到饥饿,当走过雪坡近亭头时,排出的小便都是红的,担心吃了“落地杨梅”中毒、闯祸了,拉出的是“血”。饥饿加害怕,为了赶渡继续前行。当走到石墙头路廊时已经相当疲惫,稍作休息,这时,突然响起两声闷雷,抬头见西南天边乌云崛起,分明是下雷雨的前兆,三人赶紧上路,指望能在下雨前走过毛屿塘岸。谁知走上塘岸没几分钟,天一下子暗了下来,紧接着电闪雷鸣,几声霹雳好像打在眼前。一阵狂风后,大雨倾盆,淋得我们睁不开眼睛,全身湿透,干燥的塘岸路顷刻淌水变得湿滑泥泞。我们立刻脱下千纽草鞋(家里人专为我们步行用碎布条代替稻草编织的草鞋),使出长街人走烂泥路的绝招,即勾起脚趾头在泥泞溜滑的泥路上高频率竞走。雨拼命地下着,也顾不得脚绊毛栗刺,摔倒爬起,连滚带爬,折腾了好久,才看见海岸边侧翻待修理的渔船,三人急忙钻到船底下躲雨,一身泥水又湿又冷。王其林调侃说,我们这副样子就是“落汤鸡”,连脚边这两只红钳蟹也在笑我们。吴华松接着说,这才叫“饥寒交迫”,你看那条弹涂鱼眨着眼望着我们这三个“憨头”。大约又过去了半个小时,雨才慢慢地停了下来,随之钻出了夕阳,为了赶渡,我们只得勉强上路。遇见卖桃的,又买了几分钱的桃,分吃了两个。到冷梵岭脚时,实在走不动了,吃下的桃子再次“烧”起来,更加难受。但心里明白过岭后前边就是沥头渡,过渡就可到家,于是互相鼓励,挣扎着前行。到渡口时,渡船早已过去,过不去了,尽管朝对岸拼足全力喊叫“老大过渡”,无人回应,只能望洋兴叹。当晚,投宿在洞门王其林娘舅家,娘舅看着我们这副狼狈相,心疼,马上给我们换衣、烤火取暖……第二天上午我们才蹒跚到家。
长街人上城难,往事桩桩,不胜一一枚举。俱往矣!
1960年7月,长街至胡陈公路通车,长街人可乘汽车上城。1978年,长街至青珠农场公路通车。1986年,力胡线(力洋经古渡、明港、农场、长街至胡陈)通车。1999年7月,车岙港大桥工程竣工。2003年,架起毛屿港、胡陈港大桥。6月,宁松线四车道一级公路开通,一下子把宁海与长街的公路里程缩短到31千米。从砂石路面到沥青、水泥混凝土路面,道路不断降坡、拓宽、截弯取直。原长街境内多数都是烂泥路,如今村村通公路,而且路面硬化上等级。路况与车况发生了质的变化,乘车的安全性与舒适度得到显著提高。现在,长街站至城区日均始发班车58辆246班次,路上有多个港湾式停靠站,上下车十分方便。除县乡道班车外,私家车已进入千家万户。如今,长街境内的人可在自己的村头、家门口乘车,心想事成,想要去哪就去哪,出行上城安全便捷,畏途变通途已成现实。
现代交通造福长街,长街人的“上城难”渐渐被淡忘,年轻一代更无从知晓。为了留住那段难忘的记忆,谨撰此文以记之。
(胡家康 201 3年1 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