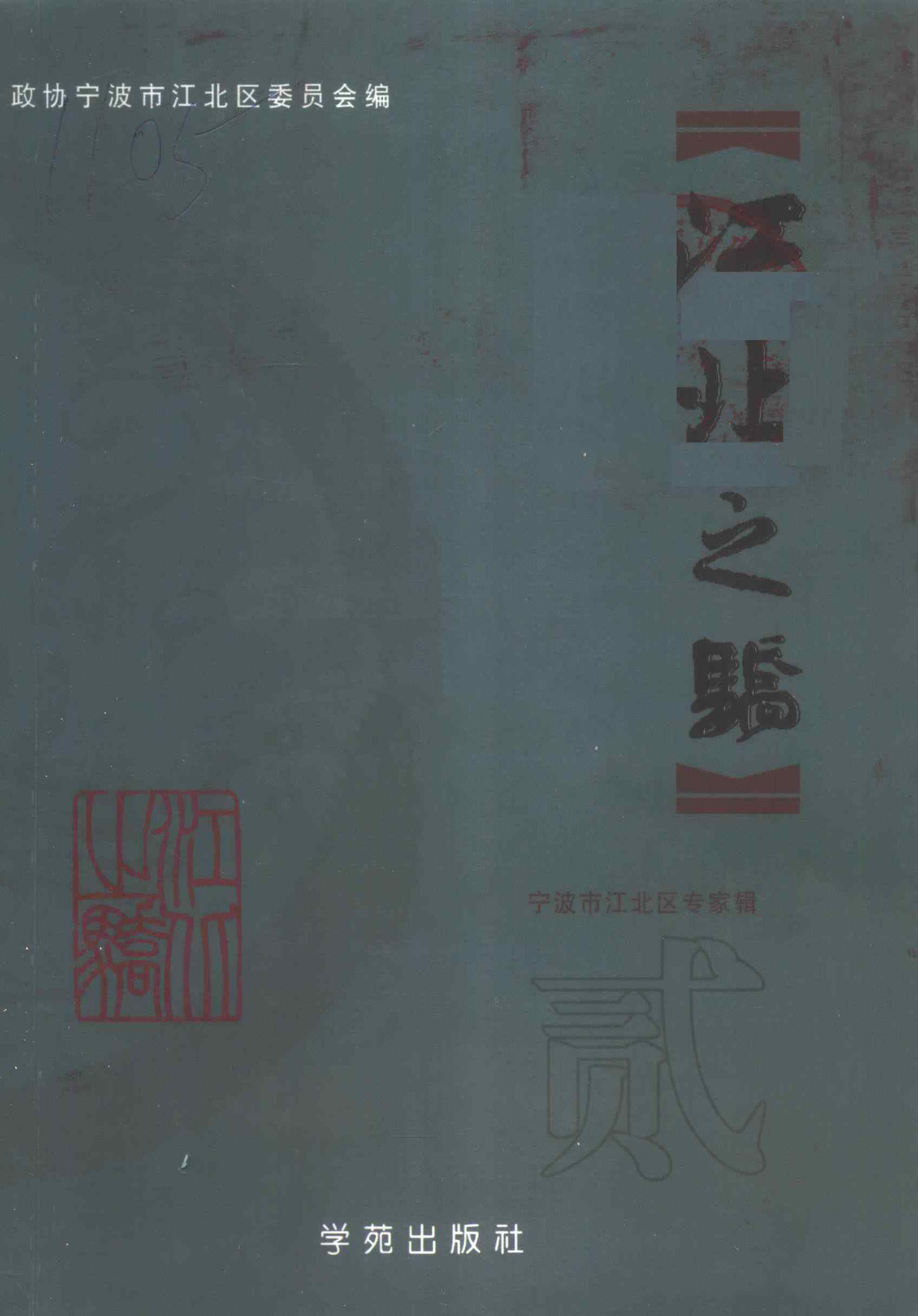内容
毛荣贵
命运,是令人肃然的字眼,庄重(serious,solemn)而又瑰丽(magnificent)!
命运,又是一个活泼的字眼,善变(changable)而又扑朔!
人生为船,光阴则如流水。回首人生已经走过的道路,波峰浪谷之间,分明存在着一条清晰可见的“航道”;而放眼明日之途,却是茫漠一片。
回眸近60年的人生,我常想,所谓机遇(acci-dent;goodluck),其实可作如此具体诠注(notesandcommentary):人皆世界之过客(passingtraveler),因偶然性的作用,你与某君,或曰世界之另一过客,不期而遇,而此君的出现,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你的命运。
与此君相遇,真如萍水相逢,可遇而不可求。
屈指算来,以下三位,改变了我的命运,是我的“命运之神”!
(一)
叶怀德先生。
1956年是中国“红火”的一年。此前,通过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已经把“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扫清,于是一个“欢天喜地”的“公私合营”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这个运动也叫“私营资本主义商业和平改造运动”。
随着“公私合营”的深入发展,不少单位进行了重组,其人员也进行了重新调配。1956年10月,我的父亲毛敖其和叶怀德先生,两位相逢于位于徐家汇的上海市第六百货公司(简称“中百六店”),两人又同时分配到化妆品柜台。
如此这般(suchandsuch),父亲和叶先生就成了同事,朝夕相处。
1956年12月的一次月中盘点,化妆品柜台的销货款短缺了180元整。新组合的柜台集体面临麻烦,6位售货员来自不同单位,背景各不相同。销货款之短缺,令众人不快,人人自危(everyonefeelsin-secure)。怀疑目光基本投向我的父亲。原因有二:一是,在同柜台的6名售货员中,我父亲家境最贫寒,二是,事发以来我父亲最少“辩白”,显得“辞穷”。
商店领导准备和我父亲最后“摊牌”,让他主动“交代”问题,争取走“自首”的道路。此时,店内有人写了检举信,检举人称:在她去银行办事时,恰见化妆品柜台的W在存款,而且手里拿着大把现金。
于是,公司派人到附近银行进行调查。调查证实W的存款数,不多不少,正巧是180元整,而W的存款之日离开发工资还有一周时间,W的月薪仅45元。经过公司领导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八字政策,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作为一条法宝,用于对各类犯罪嫌疑人的攻心政策,成效虽然显著,却严重缺乏法治内涵)的政策攻心,W终于交代:柜台所短缺的180元销货款是他所拿。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W曾经是“辩白”最积极者,更加恶劣的是,W曾经向众人暗示:毛敖其值得注意。水落石出,父亲依然固我,默默工作。破案前,不因被人怀疑而悲、而表白;破案后,也不因他人“落难”(beindistress/meetwithmisfortune)而喜、而轻讽(touch/mock)。这一切被周围的人看在眼里,尤其是叶怀德先生。
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宁波慈城镇(顾家池头)的一个雇农家庭,是一个遗腹子(posthumous),我的祖母守寡一生,靠给别人干活,或摆小摊把我父亲养大。只念到小学五年级,父亲就因贫困而辍学,跟随别人到上海学生意。所谓“学生意”(即学徒),就是给一家店家打杂,要“承包”店里店外全部的重活苦活。
几十年的辛苦劳作,甚至使父亲养成了低头行路的习惯,而且,父亲吃饭的速度惊人的快,举家进餐,我们还没有吃到一半,父亲已经搁筷。
母亲给我们解释,父亲在“学生意”期间,要给老板家全桌的人添饭,而全桌的人(不包括我父亲)吃完后,父亲就必须“收桌”,不得继续吃下去。久而久之,父亲在如此苛刻的环境中,便自然养成了“吃快饭”的习惯。初中时,在一篇难得的“自由命题”的作文里,我写了一篇题为“父亲的一个令人心酸的习惯”的作文。Y老师在一周后的作文讲评课上,请我起立,给全班朗诵这篇作文,念着,念着,我大滴大滴的眼泪便掉了下来。记得当时班级里有个别同学见我泣不成声,居然偷着乐,且笑出声音来,Y老师鼓励我念下去,直至念完全文。念完之后,Y老师终于光火(provokedtoanger),对那位发出笑声的同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至今记得Y老师最重的一句话是“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
课后,我打开作文册,Y老师在评语里写道:毛荣贵,你在写这篇作文的时候肯定泪光闪烁,我看了你的作文,真的非常感动。文章要打动别人,先得打动自己。
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父亲,终年为钱而愁。然而,天下富人未必慷慨,天下穷人未必吝啬。母亲曾经不止一次,跟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家在镇江时,一年除夕,父亲终于向朋友借到了一点钱,可以勉强过年。但是,当他借了钱兴冲冲回家,在街角上遇到家中断炊的邻居M,父亲知情后,毫不犹豫地分一半借来的钱给邻居M。讲到这里,母亲总表现出一丝悔意,因为,当父亲回家把分钱给M的事情告诉母亲后,母亲曾怨怼过父亲,那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呀。但是,母亲总是要补上一句:你爸爸是对的。M家也有三个孩子等着过年呀!
这就是我的父亲!
相识没有多少日子,和父亲同柜台的叶先生就和我的父亲成了朋友。
1957年1月上旬某日。中百六店的化妆品柜台前顾客稀少。于是,叶先生和我的父亲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叶:“你的妻子和小孩在哪里?”
父亲:“在江苏镇江。”
叶:“你多少时间回家看望他们一次?”
父亲:“过年的时候,回去一次。”
叶:“你有几个小孩?”
父亲:“三个。”
叶:“儿子,还是女儿?”
父亲:“三个儿子。”
叶:“几岁了?”
父亲:“大的两个是双生,今年11周岁,小的8岁。”
叶:“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接到上海来住?”
父亲(略作迟疑,双眼避开了叶先生):“不瞒你说,拿不出这笔盘缠(travelingexpenses)。”
叶:“从镇江到上海,要多少盘缠?”
父亲(又作迟疑):“我算过,假如搭乘长江轮船,大概需要40元吧。”
叶(从上衣的胸袋取钱,递给我父亲):“我这里正好有40元钱。你马上寄到镇江去,让他们赶在春节之前到上海,在上海过个团圆年(ahappynewyearwithallthefamilymembersunderthesameroof)吧。”父亲(坚决地推辞):“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
叶:“为啥?”
父亲(望着叶先生的眼睛,一脸真诚):“我,我还不出这一大笔钱。”叶(一摆手):“别客气。你明天有钱了,就还我这40元,要是手头紧,就不必还我了,就算我叶怀德做了一件善事。”
叶先生再三坚持,父亲便不再作推辞。
1957年1月初,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中百六店一楼化妆品柜台内出现了这样一幕。使一个分居两地的家庭得以在上海团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毛家三兄弟,从此在上海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之旅。多少年之后,重访镇江,在和远亲旧邻交谈时,他们一致认为,若是我们当年不迁居上海,根据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我们读完小学就一定会辍学(dropout)在家,为了解决温饱,我们三兄弟将先后迅速“就业”,从最好的可能性去想,我们三兄弟也许会很快成为“工人阶级”之三员,大概是镇江的小厂。远亲旧邻们称叶先生是我们毛家的真正“救星”。
收到父亲的巨额汇款后,不识字的母亲开始坚持认为我们看错了数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小学五年级的我,已经有足够的“水平”,把父亲所写的“附言”,一五一十地念给母亲听,让母亲知道这笔汇款的原委(theinsndouts;thewholestory)。母亲带领我到镇江山巷邮局领取了汇款,并直接到派出所办理迁移户口手续。
在山巷派出所,一位头戴大盖帽的女警察和蔼地问我母亲:“为什么要迁户口到上海去呀?”
母亲用绍兴口音的镇江话回答:“小孩他爸爸在上海工作。”女警察灿烂一笑,说道,“好啊,全家到上海去团圆了。上海可是个大城市哟!”接着,还瞟了我一眼,说,“到了大上海,对小孩的发展也有好处。”
女警察的甜蜜笑容,多年来一直盘桓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特别是“发展”两个“大字”,留下殊深记忆。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对户籍管理采取了严格的“冻结”(freeze;congeal)方针,外地户口要入上海,简直有登青天之难。这样的家庭在上海何止千万:妻子带领小孩生活在上海,丈夫在外地工作,几十年都无法调回上海。无数对夫妻已经名存实亡,过着“牛郎织女,一年一会”的生活。
轮船响起浑厚而响亮的汽笛声,我和哥哥跑到最高一层甲板,望着夜色下渐渐远去的镇江港码头,久久舍不得离去。11周岁的我们,还做不出和镇江挥手告别的浪漫动作,还喊不出“别了,镇江!”这样浪漫的声音。江风凛冽,哥哥双臂伏在栏杆上,用很低沉的声音,呆呆地问我:“什么时候,我们再回来?”
我答:“不晓得。”
船,沿长江顺流而下。船的后方,灯火已经消失,船的前方,一片漆黑。
我们不知,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怎样一个东方大都市;
我们不知,7年之后,我们将双双考入中国的著名学府——复旦大学;
我们更不知,9年之后,我们亲爱的祖国爆发“文革”,国难开始。
⋯⋯
1957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五口,不是团聚于镇江小城,而是欢聚于上海。由父亲的另一位同事徐振荣先生的帮助,我们在上海西郊区(现属上海市徐汇区)的漕河泾镇租借了一间平房。
从十六浦船码头到漕河泾镇边缘的新家,已是深夜。次日早晨,一起床,我急奔门外,发现门口有竹林,不远处有清澈的小河流过。看惯了山,在山里“野”惯了的少年,再也见不到山了!不久之后,我们在附近找到了一处园林,那是上海滩青红帮头子黄金荣的私家花园——黄家花园(即现在的桂林公园)。
叶先生家住上海卢湾区淮海中路淮海坊75号(淮海路曾经是历史上的“法租界”,淮海路旧称“霞飞路”,淮海坊的旧称即“霞飞坊”)。现代中国有许多文人墨客曾经在淮海坊居住。自1937年起巴金就居住在淮海坊59号三楼,前后共生活了18年,其代表作《家春秋》——激流三部曲的《春》、《秋》两部均完成于此。1936年底,许广平携子周海婴来淮海坊居住,直至1948年离开去北方。鲁迅的著作就由许广平精心保存在63号的三楼。徐悲鸿、竺可桢、林风眠等名人也都曾是淮海坊的居民。
迁居上海之后,我们便自然成了叶先生家的常客,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周末时光。
从镇江到上海,惜别了大自然,却有机会感受大都市的繁华和文化。淮海坊附近就有当时上海的头轮电影院——国泰电影院。淮海电影院、嵩山电影院、上海电影院也步行可及(withinwalkingdis-tance)。我们先后观看了《章西女皇》、《一仆二主》、《巴格达窃贼》、《红菱艳》、《第十二夜》、《警察与小偷》、《社会中坚》等国外影片。此外,上海美术馆、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以及上海图书馆等,都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去处。
别了镇江金山、北固山、伯先公园所携带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的淮海路,我们又耳濡目染带有异国情味的都市文化,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一日,我和哥哥在茂名路上行走,忽见前面一人,身材魁梧,且非常面善,我先反应过来,那不是毛主席吗?他正背着手,沿茂名路由南往北行走,好像在皱眉凝思。我哥哥说,“是,是毛主席!”于是,我俩朝毛主席奔去。不料,从路旁忽然蹿出一中年男子,张开双臂,很客气地挡住我们的去路。他蹲下来,笑吟吟地跟我们说,首长正在散步休息,请我们稍息,行吗?我马上问:首长,是不是毛主席?那人只是含笑点头。接着,我们就向毛主席行注目礼,看着他往右拐入,缓步进入了锦江饭店的边门。
两日之后,上海各报头版报道了毛主席视察上海电机厂的消息。我记得,那是1961年5月1日。
1961年的“五·一”。
中国正笼罩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的阴影之中,市场供应极其紧张。人们走亲访友,假如要吃顿饭,都自带粮食。这在当时是寻常一景。我们也不例外,周末到叶先生家去,母亲总是为我们准备好小米袋,里面放着够我们吃几顿饭的米。那时,叶先生居然在三楼阳台养鸡成功,周末,到叶先生家就能吃到“阳台鸡”下的蛋。那年头,淮海坊三楼露天阳台养鸡的人家远不止叶先生一人。清晨,宁静的淮海坊里鸡声相闻。一觉醒来,先闻鸡鸣,让人疑在荒郊野外!就是大白天,母鸡下蛋后的叫声,也是此起彼伏(asonefalls,anotherrises)。现居淮海坊的人如何敢设想当年此景!
叶先生祖籍江苏无锡,自幼家境并不殷实,为了让他哥哥叶怀仁继续求学,他主动放弃了求学的机会,很早开始工作。叶怀仁与贺绿汀同班求学,解放前去了美国,成了当时旅美华人中的著名音乐家,擅长黑管演奏。而叶先生一直留在上海,终生未娶,孑然独居。1966年“文革”爆发,因他哥哥在美国,且按时从美国转道给他汇款,中百六店的造反派因此有了把柄,把叶先生定性为“里通外国分子”,剥夺了叶先生站柜台的资格,勒令叶先生改行扫地。叶先生是极要脸面之人,他宁死也不愿受此辱(disgrace)!先后两度服安眠药自杀,第一次未遂,第二次成功。
一直到叶先生惨别人世的那一刻,我们毛家还欠他40元。其实,又何止40元!我们迁居上海之后,几乎,每个周末我们到他家去,叶先生总要在我们回家之时,往我们的口袋里塞一些“车费”,母亲常用这些“车费”买米买菜,度过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叶先生自杀身亡的消息给我精神很深的刺激,从此,我不信此言!
1957年初叶先生的慨然相助,一改我们毛家命运,一改毛氏三兄弟的命运。至今,我还在想,从表面看,命运安排父亲和叶先生相逢于中百六店。若作深层次分析,假若父亲为人势利(snobbish),待人刁猾(cunning;crafty),即便与叶先生萍水相逢于中百六店,叶先生也未必会如此主动慷慨资助我的父亲啊!
我国有句成语:积恶余殃(accumulateevilandlateronesuffered)。其含义是:指多行不善,子孙必有恶报。我想,是否能对此成语作一反述:积德余惠(accumulatevirtueandlateronebenefited)。
一个人的命运,说到底,其实和上代或祖辈的德行有涉。
(二)
袁晚禾女士。
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党总支书记(1960年——1966年)。
1964年7月高考。当时,我所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而具体的系科又是这样排列的:
1.中文系;2.外文系;3.历史系
8月中旬,在母校南郊中学接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分明写着“外文系”,而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中文系”。大喜掩映着大憾,憧憬伴随着隐衷(feelingsortroublesonewishestokeeptooneself)。中文系毕竟是我的第一志愿啊!怎么会被外文系录取呢?难道我的语文考试成绩没有达到中文系的录取标准?难道语文基础知识考“砸锅”了?难道我的高考作文“离题”了?你看,人在痛苦时,其寻思会如此“离谱”。
1964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读报有感——干菜的故事”。我写得非常投入,似乎不是置身于决定前途的考场,而是坐在安静的教室里,完成平时老师布置的一篇命题作文,我由考卷提供的“干菜的故事”,翩然联想到我受尽人间苦难的祖辈,写作过程中,我强忍着,终于没有让眼泪滴在试卷上。一气呵成(atonego;withoutabreak)之后,尚有时间从容默诵一遍,作文字校正。至于别的科目,政治、历史、英语等,也都试途通达,毫无受阻的印象,各门考试的成绩应都在90以上。
进入复旦的最初两周,我甚至考虑过提出“转系”要求。
38年之后的今日,我的母校竟然容许学生转系,并认为这是一项教育改革。2002年12月,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很重要,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在哪里也很重要。兴趣是学生学习的重要驱动力。分数不能作为衡量学生潜能的标准,一张考卷是不能完全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的。要培养创造性人才,我们首先就要打破不利于调动学生内在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的体制,转系的措施只是对一考定终身的缺陷进行有限的弥补。对学校来说,此次转系还起到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活跃人才培养的空气。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假如当年允许我转系,我将毫不犹豫地转到中文系去。但是,回头想,还是不转系为好。兴趣固然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策动力,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的是:兴趣,是可以培养,也是会转移的呀!
不久,我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便开始与日俱增。
朱镕基在2001年回清华的一次谈话中坦承,在校时他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
读此,我产生强烈共鸣。我想套用朱镕基的这一席话:
⋯⋯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很需要外语人才的。
1964年国庆。复旦大学外文系举行了联欢晚会。
外文系的党总支书记袁晚禾,正巧坐在我的身边。当时的她还不到四十,是一位俄罗斯文学的副教授,虽然身居书记要职(keypost),平日待人却极为谦和,毫无架子。整日乐呵呵,笑吟吟的。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颇多学者风范。
入学以来,我第一次有机会和袁书记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一边欣赏师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我们一边进行了以下的交谈:袁:“你就是毛荣贵吧?”
我:“是。”
袁:“你有一个哥哥,叫毛荣富,你们俩是孪生兄弟,毛荣富在中文系,是吧?”
我:“是啊,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袁(浅笑):“谁让我是书记的呢!你们还没有踏进复旦大学的门,我就知道了。”
我(她的幽默,让我放松了许多):“哦⋯⋯”
袁(睁大眼,望着我):“毛荣贵,本来,你应该是中文系的学生哟!
我(惊愕):“真的?”
袁:“我还会编造故事来哄(coax)你吗?”
我(有几分急切,双眼盯着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袁(很耐心地):“8月份,我参加了招生工作。我们外文系的生源严重不足。(上个世纪60年代,高考几乎在“半秘密”状态中进行。有关机构不仅不向社会和考生公布高考成绩,而且不向社会公布录取分数的底线,考生也不知道大学专业招生的‘冷’与‘热’。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的外语类院系一直是学生报考热门,而当年,报考外语专业者寥寥,外语院系是绝对冷门。国门紧锁的中国,不仅不需要那么多的外语人才,而且能操外语者常怀莫名其妙的‘自危感’。)在招生结束的前一天,我有事到中文系的招生处,他们那里喜气洋洋,因为他们生源充足呀。我信手(atrandom)翻阅他们的材料。翻阅之间,突然注意到你和毛荣富的材料,从两人照片看,你们长相一模一样,复查看你们的出生年月,方知你们两个是孪生!这时候,我就开始动‘坏脑筋’了。”
我(大惑):“什么‘坏脑筋’呀?”
袁:(大笑):“把你‘挖’过来呀!我当场就向中文系招生小组提出。不料,他们坚决不同意。正要离去,忽见到学校的党委副书记C,我就向C提出此事。C书记浏览了你们两人的材料,正在考虑。我找到一个借口,说你们两人长相如此相象,同在中文系,不是惹麻烦吗?此话出口,众人皆笑。C书记就发话了:中文系就发扬一点‘合作精神’吧。我成功了!
我(想追根究底(gettotherootofthematter):“那怎么会选我,不选我哥哥到外文系呢?”
袁(哈哈笑起):“C书记有了态度,我就好办事了。在查看了你们的考分后,才决定把你拉到外文系来。因为,你哥哥的语文分数比你高几分,你的英语成绩比你哥哥的高几分。因此,就合情合理地把你调过来了!”
袁书记正说在兴头上,忽然来人,把她叫走了。
我颓然(dejected;disappointed)独坐。再也无心观赏台上的精彩演出,愤愤不平地想:原来如此!我是被“拉壮丁”一样硬拉到外文系来的!
我恨你,袁晚禾!
当晚,我直奔四号楼的中文系学生寝室,找到我哥哥,复述了我遭遇的“不幸”(adversity;setback),我们并排走在三号楼和七号楼之间由小石块铺成的路上,说到伤心处,竟然哽咽(chokewithsobs)失声⋯⋯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我学习英语的兴趣渐渐被点燃。回头再看袁晚禾书记,我真想大声说:我爱你,袁晚禾!
1965年12月---1966年7月,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师生在龙华公社参加四清运动,袁晚禾书记和我在同一大队(建华大队),我们有较多接触。四清结束回校不久,袁晚禾书记便遭受许多大字报的批判,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日,在大字报栏前,我读到一张攻击袁晚禾的大字报,其内容与四清有关,但是,大字报涉及的许多细节与我了解的事实不符。因此,我写下了“文革”中唯一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一点必须有所说明”,为袁晚禾洗雪(wipeout)。大字报贴出去的当晚,一位造反派的同窗J找到我,厉声质问:毛荣贵,运动刚刚发动起来,你不要站在对立面上。
我答:我写的全部是事实。
J双眉一扬,神气十足地对我说:毛荣贵,头脑不要简单,现在是什么时候?事实也要服从运动!
好一个“事实也要服从运动”!我沉默不语了。呜呼!这就是造反派的逻辑!
2002年2月23日(周六)在上海北京西路1277号国旅大厦三楼的红佳酒家,复旦外文系的校友(从1949年之前的老毕业生,到近年“新鲜出炉”者)聚会。几十年不见,当年的袁书记老了,但精神依然矍铄。我对她说,“袁老师,你是我的‘神’!
她睁大眼睛问:“什么神?
我笑答:“我的命运之神!1964年,在招生现场,要是你不把我从中文系‘拉’到了外文系,我的人生道路就要改写了!
双鬓霜染的袁晚禾依旧乐呵呵,依旧笑吟吟。
人,其实很近视。
人生之旅,必有曲折。假若人生真的能根据一个人眼前的喜怒哀乐来安排,痛快是痛快了,但是,未必就是好事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袁晚禾出现在中文系招生处,使我从中文系的新生名单消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外文系的学生,从表面看,似乎命运安排袁晚禾和我“相逢”于招生办公室。若作深层次分析,假若国家不是处在“闭关锁国”状态,人们对报考外文系趋之若鹜(gomadaboutsomethinglikeaduck),那么,即使袁晚禾和我“相逢”于招办,也绝不会有当年的故事了。
一个人的命运,说到底,其实和社会的背景有涉。
(三)
俞景路女士。
1978年4月。我在浙江玉环县坎门中学当老师(当语文老师,而非英语老师)已经是第6个年头,女儿也已经上幼儿园小班。
人生,走到这一步,就像驶入快车道,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光阴,将消失于转瞬。一颗曾经年青躁动的心,已经渐渐归于平静;
一颗曾经善作憧憬的心,已经慢慢趋于朴拙(simpleandsincere)。
心理上,作好了准备,精神上,也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海岛(玉环县)当一名中学教师,勤恳工作,挣一口饭吃,度过自己的未来岁月吧,闲时,推窗遥望苍茫的海面,偶尔,眼前会浮现1964年考入复旦大学时的旧景。少年得志哟!
一位同事C,曾经对我如此冷嘲:毛荣贵,我们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本来就应该分配到穷乡僻壤来工作,你和夫人毕业于堂堂复旦大学,想不到也⋯⋯
C的话没有说完,我就打断了他:“别说了!”
我知道C接下去还想说什么。我实在不想让C在我的心理伤痕上再洒一把盐。
我拍拍C的肩膀,拼凑两句古诗作答: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得到消息的当日,从不喝酒的我,竟然与夫人闭门干杯,直至酩酊(bedeaddrunken;bedrunkunderthetable)。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部署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1160万人。这是世界考试史上考生人数最多,最为壮观的一次考试。
我在玉环县城参加了高考阅卷工作。此时,1964年夏天参加高考的日子又复活于眼前,不过,失落的酸楚远远盖过了当年成功的喜悦。机会属于年轻人,而自己作为文革的殉葬品(gravegoods;funeraryob-ject),已成定局!
人生的许多机会,往往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来敲你的门。
1978年5月16日。平常一日。走出玉环县城的菜场,在县城食品商店的拐弯处的白墙,只见一张白晃晃的“安民告示”(anoticetoreassurethepublic)(“文革”流行语,出自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份“招生简章”!“招生简章”上方还有一行小字:杭州大学试招二年制进修班。
“招生简章”的总则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在党的11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以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技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经教育部通知和要求,杭州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五个系和气象、地理、英语三个专业举办一期二年制进修班,招收一九六三、六四、六五年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给予进修提高。
进修班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高等院校的实际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基础课师资,结业后,能够从事高等院校基础课的教学工作。
报名日期:1978年6月20日起至7月10日。
考试时间:1978年8月15日---16日。读完“招生简章”,我便离去,刚走出几步,我猛然醒悟:机遇来了。
手提竹篮(绝非现在大量使用的塑料袋),我一路疾走,刚进家门,就向夫人通报了这个消息。夫人马上提出,和我再去看一遍,并需记录其中重要内容。于是,我们带上笔和纸匆忙外出。
生活,骤然生变。除了上课和必要的家务之外,32岁的我投入复习迎考。五岁的女儿萍萍(小名)己经请同事搭乘便车带到上海,面交上海的弟弟毛荣发,由萍萍奶奶帮助带领。
教中学语文久矣!英语已经锈迹斑斑(rusty),复习伊始,甚至连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andSunday的拼写都发生困难。
两个月内,早起晚睡,赤膊上阵。
1978年8月14日下午从玉环海岛来到省城杭州,准备应试。时杭州流火,气温达38度。为了节省开销,借宿于杭州大学学生寝室。
不料,出师不利。
8月15日上午的“英语实践”考试,很不理想。pronunciation(发音)这样的单词拼写也拼错,甚至连takepartin(参加;参与)的造句也踌躇一时。
于是,次日(1978年8月16日,即考试的第二日)上午7:30,在天目山路的杭州大学大门出现了这样的一组历史镜头(shot):
杭州大学的校门里走出来三人:夫人、女儿和我。三人各头戴遮阳的草帽,夫人手里提着一只草绿色的军用水壶。这水壶是在乔司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时的“军用品”。当时,夏日出门,必带此水壶。当时的市场所谓“瓶装水”(bottledwater)尚无踪影,更不必说名目繁多的可乐、冰红茶、乌龙茶了。
与此同时,从杭州大学的校门外,步履匆匆,走进一人,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前来应试的俞景路,我复旦大学的同班女同学。
俞景路见我们三人“反其道而行之”,不去考场,反倒潇洒出校门,好生疑惑,问我:“马上就要考试了,你怎么往外跑,不考试啦?”
我对俞景路实话实说:“昨天的‘英语实践’考试,考砸了。大概没戏了。好不容易到省城来一次,今天决定游西湖去。”
俞闻此言,面露惊色,她是个直性子,马上提高了嗓门,对我说:“哎呀,我昨天也没有考好,经过十年动乱,原来在复旦学的早就忘了,再说,我们在复旦也没有学到多少呀。你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别人可能考得还不如你呢!”
我望了望我的夫人,以目光征求夫人意见。
“去吧,跟我一起去考场吧。”俞景路继续怂恿我。
此刻,俞说了一句让我和我的夫人铭记了一生的四个字:“机不可失(Opportunityknocksbutonce)!”
我又朝夫人望了望,她微微点头,用眼神告诉我:应该再去试一试。
告别妻女,我掉转头,和俞景路疾步同入考场。
这天上午考试内容是:汉语。除了汉语基础知识之外,还有汉语写作。作文题目四个字:新的一页。
考场寂静。
人人都在为人生的“新的一页”而奋斗。我也不例外。此情此景,又令我想起了1964年7月15日---17日在上海师范学院(即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参加高考的日子。
不过,比起当年高考,文笔更加老练、底气越发深沉、情感倍显浓烈,毕竟多活了12年,毕竟当了6年的高中语文教师,毕竟揭开人生“新的一页”是我心底的呼唤!
一挥而就,一气写了3000余字。
当日下午是英语口试。
为了迎接这次考试,我每日黎明即起,在海岛校园的幽静处,大声朗读,苦练口语。口试时,果然奏效。口试我的老师Y(后来成了我的英语精读老师),50开外,风度儒雅,口语流利。
Y老师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WheredoyoustaynowinHangzhouduringtheexaminationperiod?
(在考试期间,你在杭州住在哪里?)
我答:
IamafraidthatIcannotgiveyouaverydetailedreply,formyEnglishisnotthatgood.Iamnowjuststayinginthestudentsdormitoryonthiscampusbe-causeitistoomuchformetoputupinthehotelneartheWestLake,thoughIamsoeagertostaythere.
(因为我的英语不怎么好,所以我恐怕不能给你一个非常详尽回答。我就住在贵校校园的学生宿舍里,因为住在西湖边的旅馆里,对我来说太贵了,虽然我很想住在那里。)
脸色一直严肃的Y,听了我的这几句话,居然“哈哈”一笑。我所始料未及,一时紧张,以为什么地方讲错了。
见我紧张。Y老师极其和蔼地对我说:
Ok,Iamquitesatisfiedwithyourreply.Ihopethatyoullhavetheopportunityofstayingonthiscampusnotonlyforafewdaysbutforanothertwoyears!
(好,不错。我对你的回答相当满意。我希望你会得到这个机会,在这个校园里不是只住几天,而是住上两年!)
面对Y老师的幽默,一下子,我还反应不过来。他希望我在这个校园再住上两年,不就是等于说,希望我能考取,在这个美丽的校园再进修两年吗?
对Y老师的这个美意,立即表示了我的感谢。
大声说:Thankyousomuch!Itismygreatesthonortohaveyouasmyteacher!
(谢谢!有你这样的老师,是我最大的荣幸!)口试顺利结束。夏日的西子湖,正在向游人展示她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魅力。全家泛舟湖上,心情自是愉悦。特别是Y老师的“吉言”,让我心中希望重燃。
湖面粼粼的波光,我呆思:难道我将在杭州大学继续我在复旦大学因“文革”中断的学业?难道我们三口之家将告别海岛玉环,真的掀开人生的“新的一页”,来到杭城“从事高等院校基础课的教学工作”(招生简章语)?
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idealist),经过“文革”凄风苦雨(chillywindandcoldrainthatinspiresad-nessinaperson’smind)的“洗礼”,已经不敢再作1964年考入复旦时那样美好的前瞻。
我们暂住的学生寝室,可以遥望宝石山上保俶塔的婷婷倩影,我呆思:“赴考杭城”,若是一场戏,其“戏眼”(themostwonderfulpartofaplay)是在1978年8月16日晨7:30的杭州大学大门口。不过,这场戏,是成,是败,此刻尚不得而知,可能连“谨慎乐观”(cautiouslyoptimistic)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8月15日的首日应试毕竟……
“杭城应试”是成是败,已经不是我和夫人考虑最多的事情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女儿将来能一举完成学业,而不要像她的父母那样,不是因战乱,而是因国乱而中断了大学学业。
湖光山色,如此秀美!此时,我心酸楚。甚至,不知怎的,竟联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的结尾写的一段话:
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他们(笔者注:指“我”和闰土的后代水生与宏儿)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弃舟登岸。三潭印月是西湖风景之“绝佳处”,所谓“湖中有岛,岛中有湖”也。在如织的游人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国门开启不久,美国游客便蜂拥而至!一对美国夫妇,用“一次成相”的相机为我们全家摄影留念。当他们发现我会说英语时,老夫妻竟然兴奋不已。交谈之时,身边的人越聚越多。几分钟后,6岁的女儿拿着那张刚刚显影成功的彩色照片,睁大了眼睛,疑惑不解地问:“我们自己的相机为什么是黑白的,而且要搁很多天才能取出来?”美国人让我把女儿的问题译给他们听。我一生做过许多次译员,但是,首次译员是为我女儿做的。美国人听了我的翻译,越发兴奋,一把抱起我的女儿,高高举起,一边亲她的小脸,一边说:
Wedontknowitourselveswhythepicturecancomeoutinstantly,butwearesurewhenyouaregrownupyoucanunderstanditandyou11havethismagiccamera!Chinaisagreatcountry!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照片怎么一下子就出来了,但是,当你长大以后,你就会明白,而且你也会有这种神奇相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把美国游客的话翻译给我女儿听,没有想到的是,围观者竟然一起鼓掌!“杭城赴考”的高潮,想不到竟然出现在此风景绝佳处!
12年后,女儿在浙江临海参加高考,考取了上海海运学院英语系。英语系毕业后,她供职于上海浦东新区外办,任翻译。1994年她第一次出色完成了译员任务后,回到家中,悄悄地问我:“老爸,你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立志当一个译员的?”我说不知道。接着,她拿出一张照片,说,“从这一天开始。”我取过相片,才发现这就是1978年8月全家在杭州三潭映月的合影,是美国游客为我们全家拍摄的彩色“快照”(Palid;instantpicture)。呜呼!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就是如此这般,在“润物细无声”中默默进行着。
1978年9月5日——难忘的一日。
我在玉环县城,从邮递员手里收到了杭州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公函:我已被杭州大学录取,将在进修班学习两年。“文革”在复旦大学所造成的学业“欠账”,将偿还于异地!其间间隔12年(1966---1978年),时年32周岁。
……
9月10日,到杭州大学报到之日。
在招生办公室,我找到了负责招生的H,她热情地接待了我,有一见如故之感。H向我“交底”:“毛荣贵,本来我们并不准备录取你,因为你的‘英语实践课’的考试成绩仅得73分。而我们的录取底线是78分。”
“那怎么又录取我了呢?”我急问。
“主要是你的汉语成绩遥遥领先(getagoodhead;befarahead)于其他考生,你的成绩是93分,而第二名的成绩只有83分,你领先了10分。”H的记性真好,接着还补充道,“你的口试成绩也比较突出,100多名考生,口试成绩获得5分的,也只有六、七个人吧。你获得5分。”
我感激地注视着H,一时不知说啥是好。
坐在办公桌旁的一位老先生,站了起来,热情和我握手,微笑说,“毛荣贵,你好!经过集体讨论,招办还是决定录取你,主要考虑到你的‘综合素质’(至今,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复旦的毕业生功底好,有潜力,希望你抓紧两年的时间,努力学习!”
“他是我们招办的主任,F教授。”H介绍说。
32周岁的我,竟然像一个小学生,急切而又认真地向他们保证:“F主任,H老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抓紧这两年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学习!
俞景路也考取了进修班,在分别了8年之后,我们又成同窗。
我跟俞景路说,“你在杭州大学门口‘拉’了我一把,这可是性命交关的一‘拉’呀!”
俞景路跟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造化(smileoffor-tune)。”
我问:“此话怎讲?”
“那天,我本来不可能在杭州大学门口见到你们。”俞景路解释道,“我住在湖滨旅社,出门之后,发现手表忘记带了,考试没有手表怎么行呢?于是,我返身回旅社取表,这一折腾,大概耽搁了10分钟,否则,我早就进考场了。”
“哦⋯⋯”我应道。
“你应该感谢God,这也许是God的特意安排,让我忘记带手表了!然后在大门口ranintoyou!”个性活泼,擅长幽默的俞景路说。
俞景路1978年8月15日出现在杭州大学门口,使我重返考场,并获得了两年“回炉”的重要人生机遇,为日后成为一名教授奠基(layafoundation)。从表面看,这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但是,深入一步想,假若“四人帮”仍在横行,“文革”祸乱尚未结束,我和俞景路又怎么可能邂逅于杭州大学门口?
一个人的命运,说到底,其实和国运的盛衰(riseandfall;prosperityanddecline)有涉。
(本文原载《英语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
命运,是令人肃然的字眼,庄重(serious,solemn)而又瑰丽(magnificent)!
命运,又是一个活泼的字眼,善变(changable)而又扑朔!
人生为船,光阴则如流水。回首人生已经走过的道路,波峰浪谷之间,分明存在着一条清晰可见的“航道”;而放眼明日之途,却是茫漠一片。
回眸近60年的人生,我常想,所谓机遇(acci-dent;goodluck),其实可作如此具体诠注(notesandcommentary):人皆世界之过客(passingtraveler),因偶然性的作用,你与某君,或曰世界之另一过客,不期而遇,而此君的出现,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你的命运。
与此君相遇,真如萍水相逢,可遇而不可求。
屈指算来,以下三位,改变了我的命运,是我的“命运之神”!
(一)
叶怀德先生。
1956年是中国“红火”的一年。此前,通过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已经把“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扫清,于是一个“欢天喜地”的“公私合营”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这个运动也叫“私营资本主义商业和平改造运动”。
随着“公私合营”的深入发展,不少单位进行了重组,其人员也进行了重新调配。1956年10月,我的父亲毛敖其和叶怀德先生,两位相逢于位于徐家汇的上海市第六百货公司(简称“中百六店”),两人又同时分配到化妆品柜台。
如此这般(suchandsuch),父亲和叶先生就成了同事,朝夕相处。
1956年12月的一次月中盘点,化妆品柜台的销货款短缺了180元整。新组合的柜台集体面临麻烦,6位售货员来自不同单位,背景各不相同。销货款之短缺,令众人不快,人人自危(everyonefeelsin-secure)。怀疑目光基本投向我的父亲。原因有二:一是,在同柜台的6名售货员中,我父亲家境最贫寒,二是,事发以来我父亲最少“辩白”,显得“辞穷”。
商店领导准备和我父亲最后“摊牌”,让他主动“交代”问题,争取走“自首”的道路。此时,店内有人写了检举信,检举人称:在她去银行办事时,恰见化妆品柜台的W在存款,而且手里拿着大把现金。
于是,公司派人到附近银行进行调查。调查证实W的存款数,不多不少,正巧是180元整,而W的存款之日离开发工资还有一周时间,W的月薪仅45元。经过公司领导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八字政策,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作为一条法宝,用于对各类犯罪嫌疑人的攻心政策,成效虽然显著,却严重缺乏法治内涵)的政策攻心,W终于交代:柜台所短缺的180元销货款是他所拿。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W曾经是“辩白”最积极者,更加恶劣的是,W曾经向众人暗示:毛敖其值得注意。水落石出,父亲依然固我,默默工作。破案前,不因被人怀疑而悲、而表白;破案后,也不因他人“落难”(beindistress/meetwithmisfortune)而喜、而轻讽(touch/mock)。这一切被周围的人看在眼里,尤其是叶怀德先生。
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宁波慈城镇(顾家池头)的一个雇农家庭,是一个遗腹子(posthumous),我的祖母守寡一生,靠给别人干活,或摆小摊把我父亲养大。只念到小学五年级,父亲就因贫困而辍学,跟随别人到上海学生意。所谓“学生意”(即学徒),就是给一家店家打杂,要“承包”店里店外全部的重活苦活。
几十年的辛苦劳作,甚至使父亲养成了低头行路的习惯,而且,父亲吃饭的速度惊人的快,举家进餐,我们还没有吃到一半,父亲已经搁筷。
母亲给我们解释,父亲在“学生意”期间,要给老板家全桌的人添饭,而全桌的人(不包括我父亲)吃完后,父亲就必须“收桌”,不得继续吃下去。久而久之,父亲在如此苛刻的环境中,便自然养成了“吃快饭”的习惯。初中时,在一篇难得的“自由命题”的作文里,我写了一篇题为“父亲的一个令人心酸的习惯”的作文。Y老师在一周后的作文讲评课上,请我起立,给全班朗诵这篇作文,念着,念着,我大滴大滴的眼泪便掉了下来。记得当时班级里有个别同学见我泣不成声,居然偷着乐,且笑出声音来,Y老师鼓励我念下去,直至念完全文。念完之后,Y老师终于光火(provokedtoanger),对那位发出笑声的同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至今记得Y老师最重的一句话是“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
课后,我打开作文册,Y老师在评语里写道:毛荣贵,你在写这篇作文的时候肯定泪光闪烁,我看了你的作文,真的非常感动。文章要打动别人,先得打动自己。
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父亲,终年为钱而愁。然而,天下富人未必慷慨,天下穷人未必吝啬。母亲曾经不止一次,跟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家在镇江时,一年除夕,父亲终于向朋友借到了一点钱,可以勉强过年。但是,当他借了钱兴冲冲回家,在街角上遇到家中断炊的邻居M,父亲知情后,毫不犹豫地分一半借来的钱给邻居M。讲到这里,母亲总表现出一丝悔意,因为,当父亲回家把分钱给M的事情告诉母亲后,母亲曾怨怼过父亲,那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呀。但是,母亲总是要补上一句:你爸爸是对的。M家也有三个孩子等着过年呀!
这就是我的父亲!
相识没有多少日子,和父亲同柜台的叶先生就和我的父亲成了朋友。
1957年1月上旬某日。中百六店的化妆品柜台前顾客稀少。于是,叶先生和我的父亲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叶:“你的妻子和小孩在哪里?”
父亲:“在江苏镇江。”
叶:“你多少时间回家看望他们一次?”
父亲:“过年的时候,回去一次。”
叶:“你有几个小孩?”
父亲:“三个。”
叶:“儿子,还是女儿?”
父亲:“三个儿子。”
叶:“几岁了?”
父亲:“大的两个是双生,今年11周岁,小的8岁。”
叶:“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接到上海来住?”
父亲(略作迟疑,双眼避开了叶先生):“不瞒你说,拿不出这笔盘缠(travelingexpenses)。”
叶:“从镇江到上海,要多少盘缠?”
父亲(又作迟疑):“我算过,假如搭乘长江轮船,大概需要40元吧。”
叶(从上衣的胸袋取钱,递给我父亲):“我这里正好有40元钱。你马上寄到镇江去,让他们赶在春节之前到上海,在上海过个团圆年(ahappynewyearwithallthefamilymembersunderthesameroof)吧。”父亲(坚决地推辞):“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
叶:“为啥?”
父亲(望着叶先生的眼睛,一脸真诚):“我,我还不出这一大笔钱。”叶(一摆手):“别客气。你明天有钱了,就还我这40元,要是手头紧,就不必还我了,就算我叶怀德做了一件善事。”
叶先生再三坚持,父亲便不再作推辞。
1957年1月初,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中百六店一楼化妆品柜台内出现了这样一幕。使一个分居两地的家庭得以在上海团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毛家三兄弟,从此在上海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之旅。多少年之后,重访镇江,在和远亲旧邻交谈时,他们一致认为,若是我们当年不迁居上海,根据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我们读完小学就一定会辍学(dropout)在家,为了解决温饱,我们三兄弟将先后迅速“就业”,从最好的可能性去想,我们三兄弟也许会很快成为“工人阶级”之三员,大概是镇江的小厂。远亲旧邻们称叶先生是我们毛家的真正“救星”。
收到父亲的巨额汇款后,不识字的母亲开始坚持认为我们看错了数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小学五年级的我,已经有足够的“水平”,把父亲所写的“附言”,一五一十地念给母亲听,让母亲知道这笔汇款的原委(theinsndouts;thewholestory)。母亲带领我到镇江山巷邮局领取了汇款,并直接到派出所办理迁移户口手续。
在山巷派出所,一位头戴大盖帽的女警察和蔼地问我母亲:“为什么要迁户口到上海去呀?”
母亲用绍兴口音的镇江话回答:“小孩他爸爸在上海工作。”女警察灿烂一笑,说道,“好啊,全家到上海去团圆了。上海可是个大城市哟!”接着,还瞟了我一眼,说,“到了大上海,对小孩的发展也有好处。”
女警察的甜蜜笑容,多年来一直盘桓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特别是“发展”两个“大字”,留下殊深记忆。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对户籍管理采取了严格的“冻结”(freeze;congeal)方针,外地户口要入上海,简直有登青天之难。这样的家庭在上海何止千万:妻子带领小孩生活在上海,丈夫在外地工作,几十年都无法调回上海。无数对夫妻已经名存实亡,过着“牛郎织女,一年一会”的生活。
轮船响起浑厚而响亮的汽笛声,我和哥哥跑到最高一层甲板,望着夜色下渐渐远去的镇江港码头,久久舍不得离去。11周岁的我们,还做不出和镇江挥手告别的浪漫动作,还喊不出“别了,镇江!”这样浪漫的声音。江风凛冽,哥哥双臂伏在栏杆上,用很低沉的声音,呆呆地问我:“什么时候,我们再回来?”
我答:“不晓得。”
船,沿长江顺流而下。船的后方,灯火已经消失,船的前方,一片漆黑。
我们不知,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怎样一个东方大都市;
我们不知,7年之后,我们将双双考入中国的著名学府——复旦大学;
我们更不知,9年之后,我们亲爱的祖国爆发“文革”,国难开始。
⋯⋯
1957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五口,不是团聚于镇江小城,而是欢聚于上海。由父亲的另一位同事徐振荣先生的帮助,我们在上海西郊区(现属上海市徐汇区)的漕河泾镇租借了一间平房。
从十六浦船码头到漕河泾镇边缘的新家,已是深夜。次日早晨,一起床,我急奔门外,发现门口有竹林,不远处有清澈的小河流过。看惯了山,在山里“野”惯了的少年,再也见不到山了!不久之后,我们在附近找到了一处园林,那是上海滩青红帮头子黄金荣的私家花园——黄家花园(即现在的桂林公园)。
叶先生家住上海卢湾区淮海中路淮海坊75号(淮海路曾经是历史上的“法租界”,淮海路旧称“霞飞路”,淮海坊的旧称即“霞飞坊”)。现代中国有许多文人墨客曾经在淮海坊居住。自1937年起巴金就居住在淮海坊59号三楼,前后共生活了18年,其代表作《家春秋》——激流三部曲的《春》、《秋》两部均完成于此。1936年底,许广平携子周海婴来淮海坊居住,直至1948年离开去北方。鲁迅的著作就由许广平精心保存在63号的三楼。徐悲鸿、竺可桢、林风眠等名人也都曾是淮海坊的居民。
迁居上海之后,我们便自然成了叶先生家的常客,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周末时光。
从镇江到上海,惜别了大自然,却有机会感受大都市的繁华和文化。淮海坊附近就有当时上海的头轮电影院——国泰电影院。淮海电影院、嵩山电影院、上海电影院也步行可及(withinwalkingdis-tance)。我们先后观看了《章西女皇》、《一仆二主》、《巴格达窃贼》、《红菱艳》、《第十二夜》、《警察与小偷》、《社会中坚》等国外影片。此外,上海美术馆、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以及上海图书馆等,都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去处。
别了镇江金山、北固山、伯先公园所携带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的淮海路,我们又耳濡目染带有异国情味的都市文化,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一日,我和哥哥在茂名路上行走,忽见前面一人,身材魁梧,且非常面善,我先反应过来,那不是毛主席吗?他正背着手,沿茂名路由南往北行走,好像在皱眉凝思。我哥哥说,“是,是毛主席!”于是,我俩朝毛主席奔去。不料,从路旁忽然蹿出一中年男子,张开双臂,很客气地挡住我们的去路。他蹲下来,笑吟吟地跟我们说,首长正在散步休息,请我们稍息,行吗?我马上问:首长,是不是毛主席?那人只是含笑点头。接着,我们就向毛主席行注目礼,看着他往右拐入,缓步进入了锦江饭店的边门。
两日之后,上海各报头版报道了毛主席视察上海电机厂的消息。我记得,那是1961年5月1日。
1961年的“五·一”。
中国正笼罩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的阴影之中,市场供应极其紧张。人们走亲访友,假如要吃顿饭,都自带粮食。这在当时是寻常一景。我们也不例外,周末到叶先生家去,母亲总是为我们准备好小米袋,里面放着够我们吃几顿饭的米。那时,叶先生居然在三楼阳台养鸡成功,周末,到叶先生家就能吃到“阳台鸡”下的蛋。那年头,淮海坊三楼露天阳台养鸡的人家远不止叶先生一人。清晨,宁静的淮海坊里鸡声相闻。一觉醒来,先闻鸡鸣,让人疑在荒郊野外!就是大白天,母鸡下蛋后的叫声,也是此起彼伏(asonefalls,anotherrises)。现居淮海坊的人如何敢设想当年此景!
叶先生祖籍江苏无锡,自幼家境并不殷实,为了让他哥哥叶怀仁继续求学,他主动放弃了求学的机会,很早开始工作。叶怀仁与贺绿汀同班求学,解放前去了美国,成了当时旅美华人中的著名音乐家,擅长黑管演奏。而叶先生一直留在上海,终生未娶,孑然独居。1966年“文革”爆发,因他哥哥在美国,且按时从美国转道给他汇款,中百六店的造反派因此有了把柄,把叶先生定性为“里通外国分子”,剥夺了叶先生站柜台的资格,勒令叶先生改行扫地。叶先生是极要脸面之人,他宁死也不愿受此辱(disgrace)!先后两度服安眠药自杀,第一次未遂,第二次成功。
一直到叶先生惨别人世的那一刻,我们毛家还欠他40元。其实,又何止40元!我们迁居上海之后,几乎,每个周末我们到他家去,叶先生总要在我们回家之时,往我们的口袋里塞一些“车费”,母亲常用这些“车费”买米买菜,度过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叶先生自杀身亡的消息给我精神很深的刺激,从此,我不信此言!
1957年初叶先生的慨然相助,一改我们毛家命运,一改毛氏三兄弟的命运。至今,我还在想,从表面看,命运安排父亲和叶先生相逢于中百六店。若作深层次分析,假若父亲为人势利(snobbish),待人刁猾(cunning;crafty),即便与叶先生萍水相逢于中百六店,叶先生也未必会如此主动慷慨资助我的父亲啊!
我国有句成语:积恶余殃(accumulateevilandlateronesuffered)。其含义是:指多行不善,子孙必有恶报。我想,是否能对此成语作一反述:积德余惠(accumulatevirtueandlateronebenefited)。
一个人的命运,说到底,其实和上代或祖辈的德行有涉。
(二)
袁晚禾女士。
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党总支书记(1960年——1966年)。
1964年7月高考。当时,我所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而具体的系科又是这样排列的:
1.中文系;2.外文系;3.历史系
8月中旬,在母校南郊中学接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分明写着“外文系”,而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中文系”。大喜掩映着大憾,憧憬伴随着隐衷(feelingsortroublesonewishestokeeptooneself)。中文系毕竟是我的第一志愿啊!怎么会被外文系录取呢?难道我的语文考试成绩没有达到中文系的录取标准?难道语文基础知识考“砸锅”了?难道我的高考作文“离题”了?你看,人在痛苦时,其寻思会如此“离谱”。
1964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读报有感——干菜的故事”。我写得非常投入,似乎不是置身于决定前途的考场,而是坐在安静的教室里,完成平时老师布置的一篇命题作文,我由考卷提供的“干菜的故事”,翩然联想到我受尽人间苦难的祖辈,写作过程中,我强忍着,终于没有让眼泪滴在试卷上。一气呵成(atonego;withoutabreak)之后,尚有时间从容默诵一遍,作文字校正。至于别的科目,政治、历史、英语等,也都试途通达,毫无受阻的印象,各门考试的成绩应都在90以上。
进入复旦的最初两周,我甚至考虑过提出“转系”要求。
38年之后的今日,我的母校竟然容许学生转系,并认为这是一项教育改革。2002年12月,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很重要,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在哪里也很重要。兴趣是学生学习的重要驱动力。分数不能作为衡量学生潜能的标准,一张考卷是不能完全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的。要培养创造性人才,我们首先就要打破不利于调动学生内在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的体制,转系的措施只是对一考定终身的缺陷进行有限的弥补。对学校来说,此次转系还起到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活跃人才培养的空气。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假如当年允许我转系,我将毫不犹豫地转到中文系去。但是,回头想,还是不转系为好。兴趣固然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策动力,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的是:兴趣,是可以培养,也是会转移的呀!
不久,我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便开始与日俱增。
朱镕基在2001年回清华的一次谈话中坦承,在校时他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
读此,我产生强烈共鸣。我想套用朱镕基的这一席话:
⋯⋯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很需要外语人才的。
1964年国庆。复旦大学外文系举行了联欢晚会。
外文系的党总支书记袁晚禾,正巧坐在我的身边。当时的她还不到四十,是一位俄罗斯文学的副教授,虽然身居书记要职(keypost),平日待人却极为谦和,毫无架子。整日乐呵呵,笑吟吟的。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颇多学者风范。
入学以来,我第一次有机会和袁书记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一边欣赏师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我们一边进行了以下的交谈:袁:“你就是毛荣贵吧?”
我:“是。”
袁:“你有一个哥哥,叫毛荣富,你们俩是孪生兄弟,毛荣富在中文系,是吧?”
我:“是啊,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袁(浅笑):“谁让我是书记的呢!你们还没有踏进复旦大学的门,我就知道了。”
我(她的幽默,让我放松了许多):“哦⋯⋯”
袁(睁大眼,望着我):“毛荣贵,本来,你应该是中文系的学生哟!
我(惊愕):“真的?”
袁:“我还会编造故事来哄(coax)你吗?”
我(有几分急切,双眼盯着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袁(很耐心地):“8月份,我参加了招生工作。我们外文系的生源严重不足。(上个世纪60年代,高考几乎在“半秘密”状态中进行。有关机构不仅不向社会和考生公布高考成绩,而且不向社会公布录取分数的底线,考生也不知道大学专业招生的‘冷’与‘热’。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的外语类院系一直是学生报考热门,而当年,报考外语专业者寥寥,外语院系是绝对冷门。国门紧锁的中国,不仅不需要那么多的外语人才,而且能操外语者常怀莫名其妙的‘自危感’。)在招生结束的前一天,我有事到中文系的招生处,他们那里喜气洋洋,因为他们生源充足呀。我信手(atrandom)翻阅他们的材料。翻阅之间,突然注意到你和毛荣富的材料,从两人照片看,你们长相一模一样,复查看你们的出生年月,方知你们两个是孪生!这时候,我就开始动‘坏脑筋’了。”
我(大惑):“什么‘坏脑筋’呀?”
袁:(大笑):“把你‘挖’过来呀!我当场就向中文系招生小组提出。不料,他们坚决不同意。正要离去,忽见到学校的党委副书记C,我就向C提出此事。C书记浏览了你们两人的材料,正在考虑。我找到一个借口,说你们两人长相如此相象,同在中文系,不是惹麻烦吗?此话出口,众人皆笑。C书记就发话了:中文系就发扬一点‘合作精神’吧。我成功了!
我(想追根究底(gettotherootofthematter):“那怎么会选我,不选我哥哥到外文系呢?”
袁(哈哈笑起):“C书记有了态度,我就好办事了。在查看了你们的考分后,才决定把你拉到外文系来。因为,你哥哥的语文分数比你高几分,你的英语成绩比你哥哥的高几分。因此,就合情合理地把你调过来了!”
袁书记正说在兴头上,忽然来人,把她叫走了。
我颓然(dejected;disappointed)独坐。再也无心观赏台上的精彩演出,愤愤不平地想:原来如此!我是被“拉壮丁”一样硬拉到外文系来的!
我恨你,袁晚禾!
当晚,我直奔四号楼的中文系学生寝室,找到我哥哥,复述了我遭遇的“不幸”(adversity;setback),我们并排走在三号楼和七号楼之间由小石块铺成的路上,说到伤心处,竟然哽咽(chokewithsobs)失声⋯⋯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我学习英语的兴趣渐渐被点燃。回头再看袁晚禾书记,我真想大声说:我爱你,袁晚禾!
1965年12月---1966年7月,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师生在龙华公社参加四清运动,袁晚禾书记和我在同一大队(建华大队),我们有较多接触。四清结束回校不久,袁晚禾书记便遭受许多大字报的批判,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日,在大字报栏前,我读到一张攻击袁晚禾的大字报,其内容与四清有关,但是,大字报涉及的许多细节与我了解的事实不符。因此,我写下了“文革”中唯一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一点必须有所说明”,为袁晚禾洗雪(wipeout)。大字报贴出去的当晚,一位造反派的同窗J找到我,厉声质问:毛荣贵,运动刚刚发动起来,你不要站在对立面上。
我答:我写的全部是事实。
J双眉一扬,神气十足地对我说:毛荣贵,头脑不要简单,现在是什么时候?事实也要服从运动!
好一个“事实也要服从运动”!我沉默不语了。呜呼!这就是造反派的逻辑!
2002年2月23日(周六)在上海北京西路1277号国旅大厦三楼的红佳酒家,复旦外文系的校友(从1949年之前的老毕业生,到近年“新鲜出炉”者)聚会。几十年不见,当年的袁书记老了,但精神依然矍铄。我对她说,“袁老师,你是我的‘神’!
她睁大眼睛问:“什么神?
我笑答:“我的命运之神!1964年,在招生现场,要是你不把我从中文系‘拉’到了外文系,我的人生道路就要改写了!
双鬓霜染的袁晚禾依旧乐呵呵,依旧笑吟吟。
人,其实很近视。
人生之旅,必有曲折。假若人生真的能根据一个人眼前的喜怒哀乐来安排,痛快是痛快了,但是,未必就是好事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袁晚禾出现在中文系招生处,使我从中文系的新生名单消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外文系的学生,从表面看,似乎命运安排袁晚禾和我“相逢”于招生办公室。若作深层次分析,假若国家不是处在“闭关锁国”状态,人们对报考外文系趋之若鹜(gomadaboutsomethinglikeaduck),那么,即使袁晚禾和我“相逢”于招办,也绝不会有当年的故事了。
一个人的命运,说到底,其实和社会的背景有涉。
(三)
俞景路女士。
1978年4月。我在浙江玉环县坎门中学当老师(当语文老师,而非英语老师)已经是第6个年头,女儿也已经上幼儿园小班。
人生,走到这一步,就像驶入快车道,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光阴,将消失于转瞬。一颗曾经年青躁动的心,已经渐渐归于平静;
一颗曾经善作憧憬的心,已经慢慢趋于朴拙(simpleandsincere)。
心理上,作好了准备,精神上,也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海岛(玉环县)当一名中学教师,勤恳工作,挣一口饭吃,度过自己的未来岁月吧,闲时,推窗遥望苍茫的海面,偶尔,眼前会浮现1964年考入复旦大学时的旧景。少年得志哟!
一位同事C,曾经对我如此冷嘲:毛荣贵,我们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本来就应该分配到穷乡僻壤来工作,你和夫人毕业于堂堂复旦大学,想不到也⋯⋯
C的话没有说完,我就打断了他:“别说了!”
我知道C接下去还想说什么。我实在不想让C在我的心理伤痕上再洒一把盐。
我拍拍C的肩膀,拼凑两句古诗作答: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得到消息的当日,从不喝酒的我,竟然与夫人闭门干杯,直至酩酊(bedeaddrunken;bedrunkunderthetable)。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部署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1160万人。这是世界考试史上考生人数最多,最为壮观的一次考试。
我在玉环县城参加了高考阅卷工作。此时,1964年夏天参加高考的日子又复活于眼前,不过,失落的酸楚远远盖过了当年成功的喜悦。机会属于年轻人,而自己作为文革的殉葬品(gravegoods;funeraryob-ject),已成定局!
人生的许多机会,往往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来敲你的门。
1978年5月16日。平常一日。走出玉环县城的菜场,在县城食品商店的拐弯处的白墙,只见一张白晃晃的“安民告示”(anoticetoreassurethepublic)(“文革”流行语,出自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份“招生简章”!“招生简章”上方还有一行小字:杭州大学试招二年制进修班。
“招生简章”的总则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在党的11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以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技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经教育部通知和要求,杭州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五个系和气象、地理、英语三个专业举办一期二年制进修班,招收一九六三、六四、六五年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给予进修提高。
进修班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高等院校的实际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基础课师资,结业后,能够从事高等院校基础课的教学工作。
报名日期:1978年6月20日起至7月10日。
考试时间:1978年8月15日---16日。读完“招生简章”,我便离去,刚走出几步,我猛然醒悟:机遇来了。
手提竹篮(绝非现在大量使用的塑料袋),我一路疾走,刚进家门,就向夫人通报了这个消息。夫人马上提出,和我再去看一遍,并需记录其中重要内容。于是,我们带上笔和纸匆忙外出。
生活,骤然生变。除了上课和必要的家务之外,32岁的我投入复习迎考。五岁的女儿萍萍(小名)己经请同事搭乘便车带到上海,面交上海的弟弟毛荣发,由萍萍奶奶帮助带领。
教中学语文久矣!英语已经锈迹斑斑(rusty),复习伊始,甚至连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andSunday的拼写都发生困难。
两个月内,早起晚睡,赤膊上阵。
1978年8月14日下午从玉环海岛来到省城杭州,准备应试。时杭州流火,气温达38度。为了节省开销,借宿于杭州大学学生寝室。
不料,出师不利。
8月15日上午的“英语实践”考试,很不理想。pronunciation(发音)这样的单词拼写也拼错,甚至连takepartin(参加;参与)的造句也踌躇一时。
于是,次日(1978年8月16日,即考试的第二日)上午7:30,在天目山路的杭州大学大门出现了这样的一组历史镜头(shot):
杭州大学的校门里走出来三人:夫人、女儿和我。三人各头戴遮阳的草帽,夫人手里提着一只草绿色的军用水壶。这水壶是在乔司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时的“军用品”。当时,夏日出门,必带此水壶。当时的市场所谓“瓶装水”(bottledwater)尚无踪影,更不必说名目繁多的可乐、冰红茶、乌龙茶了。
与此同时,从杭州大学的校门外,步履匆匆,走进一人,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前来应试的俞景路,我复旦大学的同班女同学。
俞景路见我们三人“反其道而行之”,不去考场,反倒潇洒出校门,好生疑惑,问我:“马上就要考试了,你怎么往外跑,不考试啦?”
我对俞景路实话实说:“昨天的‘英语实践’考试,考砸了。大概没戏了。好不容易到省城来一次,今天决定游西湖去。”
俞闻此言,面露惊色,她是个直性子,马上提高了嗓门,对我说:“哎呀,我昨天也没有考好,经过十年动乱,原来在复旦学的早就忘了,再说,我们在复旦也没有学到多少呀。你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别人可能考得还不如你呢!”
我望了望我的夫人,以目光征求夫人意见。
“去吧,跟我一起去考场吧。”俞景路继续怂恿我。
此刻,俞说了一句让我和我的夫人铭记了一生的四个字:“机不可失(Opportunityknocksbutonce)!”
我又朝夫人望了望,她微微点头,用眼神告诉我:应该再去试一试。
告别妻女,我掉转头,和俞景路疾步同入考场。
这天上午考试内容是:汉语。除了汉语基础知识之外,还有汉语写作。作文题目四个字:新的一页。
考场寂静。
人人都在为人生的“新的一页”而奋斗。我也不例外。此情此景,又令我想起了1964年7月15日---17日在上海师范学院(即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参加高考的日子。
不过,比起当年高考,文笔更加老练、底气越发深沉、情感倍显浓烈,毕竟多活了12年,毕竟当了6年的高中语文教师,毕竟揭开人生“新的一页”是我心底的呼唤!
一挥而就,一气写了3000余字。
当日下午是英语口试。
为了迎接这次考试,我每日黎明即起,在海岛校园的幽静处,大声朗读,苦练口语。口试时,果然奏效。口试我的老师Y(后来成了我的英语精读老师),50开外,风度儒雅,口语流利。
Y老师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WheredoyoustaynowinHangzhouduringtheexaminationperiod?
(在考试期间,你在杭州住在哪里?)
我答:
IamafraidthatIcannotgiveyouaverydetailedreply,formyEnglishisnotthatgood.Iamnowjuststayinginthestudentsdormitoryonthiscampusbe-causeitistoomuchformetoputupinthehotelneartheWestLake,thoughIamsoeagertostaythere.
(因为我的英语不怎么好,所以我恐怕不能给你一个非常详尽回答。我就住在贵校校园的学生宿舍里,因为住在西湖边的旅馆里,对我来说太贵了,虽然我很想住在那里。)
脸色一直严肃的Y,听了我的这几句话,居然“哈哈”一笑。我所始料未及,一时紧张,以为什么地方讲错了。
见我紧张。Y老师极其和蔼地对我说:
Ok,Iamquitesatisfiedwithyourreply.Ihopethatyoullhavetheopportunityofstayingonthiscampusnotonlyforafewdaysbutforanothertwoyears!
(好,不错。我对你的回答相当满意。我希望你会得到这个机会,在这个校园里不是只住几天,而是住上两年!)
面对Y老师的幽默,一下子,我还反应不过来。他希望我在这个校园再住上两年,不就是等于说,希望我能考取,在这个美丽的校园再进修两年吗?
对Y老师的这个美意,立即表示了我的感谢。
大声说:Thankyousomuch!Itismygreatesthonortohaveyouasmyteacher!
(谢谢!有你这样的老师,是我最大的荣幸!)口试顺利结束。夏日的西子湖,正在向游人展示她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魅力。全家泛舟湖上,心情自是愉悦。特别是Y老师的“吉言”,让我心中希望重燃。
湖面粼粼的波光,我呆思:难道我将在杭州大学继续我在复旦大学因“文革”中断的学业?难道我们三口之家将告别海岛玉环,真的掀开人生的“新的一页”,来到杭城“从事高等院校基础课的教学工作”(招生简章语)?
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idealist),经过“文革”凄风苦雨(chillywindandcoldrainthatinspiresad-nessinaperson’smind)的“洗礼”,已经不敢再作1964年考入复旦时那样美好的前瞻。
我们暂住的学生寝室,可以遥望宝石山上保俶塔的婷婷倩影,我呆思:“赴考杭城”,若是一场戏,其“戏眼”(themostwonderfulpartofaplay)是在1978年8月16日晨7:30的杭州大学大门口。不过,这场戏,是成,是败,此刻尚不得而知,可能连“谨慎乐观”(cautiouslyoptimistic)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8月15日的首日应试毕竟……
“杭城应试”是成是败,已经不是我和夫人考虑最多的事情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女儿将来能一举完成学业,而不要像她的父母那样,不是因战乱,而是因国乱而中断了大学学业。
湖光山色,如此秀美!此时,我心酸楚。甚至,不知怎的,竟联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的结尾写的一段话:
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他们(笔者注:指“我”和闰土的后代水生与宏儿)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弃舟登岸。三潭印月是西湖风景之“绝佳处”,所谓“湖中有岛,岛中有湖”也。在如织的游人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国门开启不久,美国游客便蜂拥而至!一对美国夫妇,用“一次成相”的相机为我们全家摄影留念。当他们发现我会说英语时,老夫妻竟然兴奋不已。交谈之时,身边的人越聚越多。几分钟后,6岁的女儿拿着那张刚刚显影成功的彩色照片,睁大了眼睛,疑惑不解地问:“我们自己的相机为什么是黑白的,而且要搁很多天才能取出来?”美国人让我把女儿的问题译给他们听。我一生做过许多次译员,但是,首次译员是为我女儿做的。美国人听了我的翻译,越发兴奋,一把抱起我的女儿,高高举起,一边亲她的小脸,一边说:
Wedontknowitourselveswhythepicturecancomeoutinstantly,butwearesurewhenyouaregrownupyoucanunderstanditandyou11havethismagiccamera!Chinaisagreatcountry!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照片怎么一下子就出来了,但是,当你长大以后,你就会明白,而且你也会有这种神奇相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把美国游客的话翻译给我女儿听,没有想到的是,围观者竟然一起鼓掌!“杭城赴考”的高潮,想不到竟然出现在此风景绝佳处!
12年后,女儿在浙江临海参加高考,考取了上海海运学院英语系。英语系毕业后,她供职于上海浦东新区外办,任翻译。1994年她第一次出色完成了译员任务后,回到家中,悄悄地问我:“老爸,你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立志当一个译员的?”我说不知道。接着,她拿出一张照片,说,“从这一天开始。”我取过相片,才发现这就是1978年8月全家在杭州三潭映月的合影,是美国游客为我们全家拍摄的彩色“快照”(Palid;instantpicture)。呜呼!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就是如此这般,在“润物细无声”中默默进行着。
1978年9月5日——难忘的一日。
我在玉环县城,从邮递员手里收到了杭州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公函:我已被杭州大学录取,将在进修班学习两年。“文革”在复旦大学所造成的学业“欠账”,将偿还于异地!其间间隔12年(1966---1978年),时年32周岁。
……
9月10日,到杭州大学报到之日。
在招生办公室,我找到了负责招生的H,她热情地接待了我,有一见如故之感。H向我“交底”:“毛荣贵,本来我们并不准备录取你,因为你的‘英语实践课’的考试成绩仅得73分。而我们的录取底线是78分。”
“那怎么又录取我了呢?”我急问。
“主要是你的汉语成绩遥遥领先(getagoodhead;befarahead)于其他考生,你的成绩是93分,而第二名的成绩只有83分,你领先了10分。”H的记性真好,接着还补充道,“你的口试成绩也比较突出,100多名考生,口试成绩获得5分的,也只有六、七个人吧。你获得5分。”
我感激地注视着H,一时不知说啥是好。
坐在办公桌旁的一位老先生,站了起来,热情和我握手,微笑说,“毛荣贵,你好!经过集体讨论,招办还是决定录取你,主要考虑到你的‘综合素质’(至今,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复旦的毕业生功底好,有潜力,希望你抓紧两年的时间,努力学习!”
“他是我们招办的主任,F教授。”H介绍说。
32周岁的我,竟然像一个小学生,急切而又认真地向他们保证:“F主任,H老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抓紧这两年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学习!
俞景路也考取了进修班,在分别了8年之后,我们又成同窗。
我跟俞景路说,“你在杭州大学门口‘拉’了我一把,这可是性命交关的一‘拉’呀!”
俞景路跟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造化(smileoffor-tune)。”
我问:“此话怎讲?”
“那天,我本来不可能在杭州大学门口见到你们。”俞景路解释道,“我住在湖滨旅社,出门之后,发现手表忘记带了,考试没有手表怎么行呢?于是,我返身回旅社取表,这一折腾,大概耽搁了10分钟,否则,我早就进考场了。”
“哦⋯⋯”我应道。
“你应该感谢God,这也许是God的特意安排,让我忘记带手表了!然后在大门口ranintoyou!”个性活泼,擅长幽默的俞景路说。
俞景路1978年8月15日出现在杭州大学门口,使我重返考场,并获得了两年“回炉”的重要人生机遇,为日后成为一名教授奠基(layafoundation)。从表面看,这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但是,深入一步想,假若“四人帮”仍在横行,“文革”祸乱尚未结束,我和俞景路又怎么可能邂逅于杭州大学门口?
一个人的命运,说到底,其实和国运的盛衰(riseandfall;prosperityanddecline)有涉。
(本文原载《英语人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
相关地名
江北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