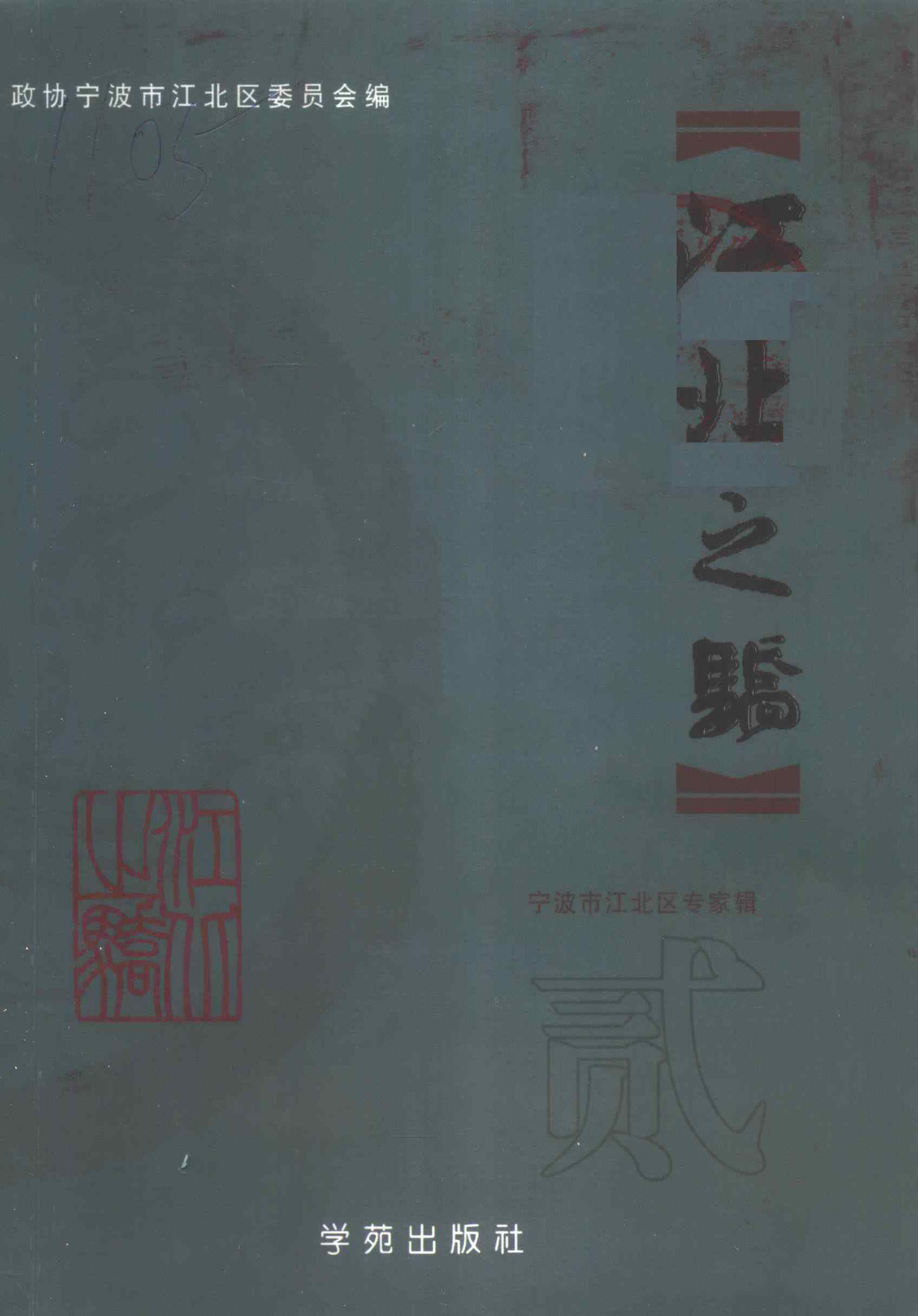内容
魏永征
而今,媒介法(又称新闻法、传媒法、大众传播法等)已经成为深受新闻界和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传媒大学王军副教授告诉我,下一学年她要给硕士生开新闻法选修课,牌子一挂出来,就有230名学生报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法律顾问、高级编辑徐迅报道:刚刚结束的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的舆论监督研讨会,热热闹闹来了200多人,而这样的会已经开到第四次了。去年,我受中国传媒大学之聘,在该校法律系招收博士生,经常有人从网上来信询问报考事项;今年该系又建立了硕士点,成为我国第一家集媒介法教学和研究为一体、媒介法专业学位授予机制齐全的专业学术机构。常常有人问我,你不学法律,是怎样进入媒介法领域的呢?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统一作答吧。
(一)
1986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任职助理研究员。夏天的某一天,所长宋军(资深新闻工作者、新闻史学者)把我找去,说:小潘(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找我,说启立同志(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到上海来说起,现在国家起草新闻法一下子恐怕出不来,是不是上海可以先搞一个地方法规,如果取得成果,就可以给全国立法提供经验。宣传部决定把启立交办的这件任务交给新闻所,新闻所先拿一个法规初稿出来,然后按照正常的立法程序提交市人大审议。宋军说,这件事就由我和你来做。
我很高兴地领受了这件任务。我们知道,1984年经彭真委员长批示同意,人大常委会决定将制定新闻法列入议事日程,由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负责起草工作,胡先生将起草班子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此在那里成立了新闻法研究室,室主任就是后来曾任新闻所所长的孙旭培(现任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他们作了很多工作,如编印期刊《新闻法通讯》,翻译各国新闻法,胡绩伟先生还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为全国新闻界所关注。我对自己能够参预这样的盛事,深感荣幸,同时也觉得是一项很好的学习机会。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要的问题是收集资料。孙旭培的班子在这方面风格很高,他们的成果随时在《新闻法研究》上发表,并且一直寄送给我们,他们搜集翻译的外国新闻法也出了书,这样我们就可以享用他们的现成成果。
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宋军先生是新闻史家,我们着重搜集的是中国近现代新闻法规的资料,包括一些审判个案,如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七君子案的全过程报道等。后来我们获知有一位姓刘的老先生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功夫,搜集清朝和民国初年、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主要新闻出版法规编辑了一部书,书稿已在出版社。可能是通过宋军的关系,我们得到了书稿的全部影印件(我记不清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影印件,推想宋军当时还兼任市委宣传部报刊处长,应该有较大方便调阅书稿,从著作权角度说,这当然不妥,但当时并无这类观念),厚厚一大包,经编者分门别类,检阅十分方便,这样我们又省了很多力气。刘先生编的这部书已在90年代出版。
其时,法律已经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介入了媒介,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新中国第一起新闻记者被控诽谤罪的《疯女之谜》案。这篇文章发表在《民主与法制》上,主题是为一位“疯女”辩“诬”,文中严辞斥责了“疯女”的丈夫,丈夫有异议,要求杂志更正未成,遂诉诸法律。当时只有《刑法》,《民法通则》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是以诽谤罪对两位作者提出起诉,由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受理,其实在案件后面还另有一些与本文无关的背景。我自《民主与法制》创办后就担任它的兼职编辑(我能够较快介入法律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民主与法制》的兼职,该刊有一个法律顾问处,负责人是我的老师施晨初先生,主要是处理信访中提出的各类法律问题),所以我得以同步了解案件的进展,当时我同《民主与法制》的同仁们都对这个案件情绪抵触,认为是对新闻记者的打击(本案一直到1988年审结,两位《民主与法制》记者被判犯诽谤罪,各单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详见王强华、魏永征主编:《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由此我想在法规中应当设法给新闻记者提供更多的保护。
我查到我的日记(1986年)中有一条记载:“9月30日:居家将新闻法规文稿写完,得二十三条。”这是这篇《上海市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初稿完成的日期。我已记不起宋军同我的具体工作进程。宋军是我的前辈,但他对新事物依旧保持着敏感,思想相当解放,并且有丰厚的新闻史学功底,所以他对这个文稿的主导作用是无可置疑的。现存文稿铅印本有二十六条,应该是我呈交宋军后,他亲自做了修改补充,然后送到市委宣传部印刷的。铅印本分发给全市新闻界头面人物,有没有报给胡启立,我就不知道了。计划是要开会征求意见的,但是后来没有开过,可能是1986年12月爆发学潮,1月胡耀邦下台,全国反自由化,没有时间过问此事。后来宋军曾给我看过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有关新闻法规的问题由于有些实体问题要由另外的法律来规定,而这些法律尚待制定,所以此稿缓议。算是有一个交代。
现在回头看这个稿子,当然是比较肤浅的。文稿中没有提“新闻自由”,而是提“言论出版自由”,这是宋军与我的共同意见,虽然我们都承认新闻自由,但是认为作为一个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循宪法,采用宪法的提法,“言论出版自由”包括了“新闻自由”。这还是可以成立的。文稿中还有一条:“新闻工作者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这出于我的手笔,并非宋军授意。我的老师夏鼎铭先生(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看了以后就很不以为然,说新闻媒介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监督政府,你这样写,新闻记者都是官员了,怎么监督政府?我还同夏老师争论,说是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法就有“国家的新闻工作者”的说法,我们的新闻记者事实上也都是国家干部,写上这一条,新闻记者可以得到更多的保障,比如采访受到阻碍,就可以告人家妨害公务,云云。这表明“官方媒体”的观念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里可谓根深蒂固。
(二)
1987年初,国务院成立新闻出版署,加强对全国新闻媒体的行政管理,按照国务院对新闻出版署职权的规定,起草新闻法的工作也转移到新闻出版署,以副署长王强华牵头组建新的起草班子,也吸收了原来起草班子中的若干人士。此事幕后,胡绩伟先生有回忆文章披露。
王强华先生(现任《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出身法学专业,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是发表真理标准文章的责任编辑,应该说,他来主持起草新闻法也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是由于屁股指挥脑袋的规律,他必须自觉站在官方立场说话,这样他同孙旭培之间就屡起冲突。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谁可以成为办报主体,孙旭培坚持主张应该是公民,王强华则坚持限于单位(法人),双方互不相让,相互指责都很激烈,最后孙离开了起草组。
王强华就任不久,就带了他的助手曹三明(现任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等到上海来调查研究,其时上海是全国“新闻官司”最集中的地方,新闻法起草者当然很关注。他们也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来,找我谈过,对《上海市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很感兴趣,我们就这样相识。
1987年秋,时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贾树枚(现任上海市记协主席)打电话给我,说王强华向他提出,在上海另外成立一个新闻法起草组,犹如北京起草组的“影子内阁”,也起草一个新闻法文稿,目的是给北京的起草组提供一个参考文本。经过有关领导研究,决定以当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龚心瀚(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为组长,贾树枚为副组长。贾说,你参加吧?我想这可能与上海已经起草过一个地方法规草稿有关。龚、贾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这件事他们一定会找我,我也断无推卸之理。
上海新闻法起草组成立后,完全仿照北京的体制,邀请上海各大新闻单位代表人士参加,解放日报是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总编辑助理贾安坤(后来担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秘书长),新民晚报是著名老杂文家冯英子,新华社上海分社是退休的前社长杨瑛,还有法律界人士,记得起的有黄浦区法院法官张双龙,缘新闻媒介大都在黄浦区,这家法院受理“新闻官司”较多,所以邀请他们的人参加。工作班子则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报刊处的干部们。
前期工作一是搜集和编辑资料,此事主要由报刊处的人做,我也介绍了几位我们新闻所的青年人来参加,编了各国新闻法分条目选辑、历史和现实的新闻纠纷案例汇编等一些专题资料。二是专题讨论,无非是新闻自由和新闻记者的权利、创办新闻单位的条件和行政管理、新闻侵权、新闻与司法等,本想每周或隔周举行一次,起草组全体参加,但是后来因为各人都有工作,有时多数人不能来,只好暂停,这样就时断时续。开起会来,众人畅所欲言,自由讨论,会后出简报。专题讨论有不少是有争论的,但并不激烈,比如创办报刊,就有只许法人办报还是可以允许民间办报两种意见,再如新闻官司,法律界的人士侧重于谈论新闻报道中的问题,要求尊重公民的各种人格权,我记得张双龙一次就谈了一个多小时,是有备而发,新闻界的人士则着重于谈论新闻记者的权利,反对动不动就是诽谤,这方面贾安坤说得最多,不过双方并没有针锋相对地争论,因为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其实是各有各的道理。
1988年上半年,开始起草。我们的起草工作有些特别,也是集体起草。我们先讨论了《新闻法》的总的提纲,大致分为总则、新闻机构、新闻工作者、新闻的采访和发表等部分,然后二三人自由组合,各分一部分去写。写出来后提交全组讨论,然后把这些文稿统写成一篇,统稿人就是我。统稿又经过集体讨论,最后由贾树枚和我定稿。1988年初夏,我们两人以及报刊处几个人住在一所宾馆里,逐条推敲修改,最后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上海起草小组·征求意见稿)》,于1988年7月印成上报北京。
其时《新闻法研究》发表了孙旭培主持的新闻法研究室“试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据说他们在1985年就写了一个初稿,现在发表的是在这个初稿基础上修改的第三稿。到秋天,我们也见到了王强华主持的官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征求意见稿)》的打印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不可磨灭的三个“新闻法文稿”。
这三个文稿都是独立完成的。孙旭培那里不用说;北京也关照我们上海起草组,事先也不要通气,看看大家各自有什么特点。等到各方摊牌一看,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所谓大同者,首先就是在确立新闻自由作为新闻法的一项核心原则是一致的。三个文稿都对新闻自由做出了规定,都规定行使新闻自由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都规定政府在平时不得实行新闻检查,都规定创设新闻机构实行审批制,都规定了新闻活动的法律底线(即禁载内容),都规定了新闻机构更正和答辩制度,等等。至于三者区别,按照王强华在1988年底向ChinaDaily谈话所说,新闻研究室的文稿规定各人有办私人报纸的自由,而另外两个文稿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争议三个文稿在见诸文字时已经有所淡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文稿在法律责任中有对侵犯新闻自由行为的制裁条款,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行为是对新闻自由的侵害”,包括:“对公民向新闻机构提供情况、发表意见进行阻挠或打击报复”,“对新闻工作者的正常工作进行阻挠、压制、恐吓,或者进行打击报复”,“非法阻止新闻出版物的发行和新闻的传播”等六项;第六十条规定“新闻自由受到侵害的新闻机构、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公民,可以向侵害人的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起申诉,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这个规定是我设计的。按照我当时具有的法律知识,认为法律既然规定了一项权利,权利人在受到侵犯时就应该有途径请求保护,也就是请求以法律的强制手段制止或制裁侵犯行为,否则怎么体现法律的保护呢?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任何权利必须有救济手段,没有救济就没有真正的权利。这个规定所设想的救济措施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行政救济还可行,司法救济其实是不可操作的,新闻自由属于政治权利(宪法权利),我国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侵犯请求司法保护的自诉机制。不过既然只是提供给官方起草组参考的“影子文稿”,如何操作就不去管它了。
1989年1月,时任新闻出版署秘书长梁衡(后来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率工作组来上海,就他们起草的新闻法文稿征求意见,一连开了三天座谈会,出席者包括上海新闻界、法律界的代表性人士,有现职的新闻媒介老总、著名记者,有教授学者,有法官律师,也有退休在家的前辈,人们听说要制定新闻法,都很关心,都踊跃前来发表意见,会议开得十分热闹,几乎欲罢不能。有关情况,在当时我主持的《新闻记者》杂志上有详细报道。
接下来的情况,已是众所周知,不须赘述。在15年后的今天来看,应该说当时的一些考虑确实过于超前,无论是在整个社会环境上,还是国家总体的法律制度上,文稿中所设想的一些原则,确实还没有实施的条件,所以文稿被搁置是必然的。
(三)
在新闻法讨论热潮的时候,我征得梁衡的同意,在《新闻记者》上开设了专栏,专门讨论有关新闻法的学术问题。后来形势发生变化,有些问题不能谈了,但是我实在有些舍不得取消这个话题。从1988年起,上海以至全国,“新闻官司”连绵不断,有“告记者热”之说。我决定把报道这类“新闻官司”作为杂志的经常性的重要内容。
我找到了两位长期作者,两员大将。一位是上海解放日报的陈斌,另一位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徐迅,他们各自都在本单位的政法部门工作,很投入,也很专业。徐迅本来就是中央政法大学的毕业生,陈斌没有上过大学(后来通过业余学习取得资格),但是通过多年的政法报道,他的法律知识根底相当厚实,报社碰到官司大都要他去处理。90年代初期的一些有影响的“新闻官司”,如刘晓庆名誉权案、游本昌名誉权案、李谷一名誉权案、杨沫名誉权隐私权案、陈凯歌名誉权案等,大都是他们给我写稿在杂志上披露的,成为我的杂志的亮点、卖点。这同他们的本职工作并不矛盾。他们所在的媒体都只能发表新闻,就他们所掌握的资料来说,其实只用去了冰山一角,很多好东西都留在笔记本上。我们杂志篇幅限制较小,可以写较长的深度报道,他们笔记本中的宝藏可以得到充分利用。我还建议他们着重要写争议,不要一纸判决就定是非,有些问题还是可以探讨的,这样杂志上就有多元的声音。随着“新闻官司”审判实践的发展,最高法院多次发布司法解释,我请徐迅利用她的地位,采访起草司法解释的大法官,请他们阐述有关精神,这样大大提高了我的杂志的权威度。
接着就有举办研讨会的考虑,提出这个动议的是继宋军担任新闻所所长的张家骏,比我高三届的复旦新闻系学长。他提出,“新闻官司”在实际生活中争议很大,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空白,邀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人士一起坐下来进行研讨,应该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趣的,名称可以叫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不过上海社会科学院靠国家全额拨款,是个穷单位,《新闻记者》也没有经费,靠广告收入贴补,自负盈亏,也是在低水平上运转,要开会就需要有财政支持。第一个给我们支持的是南通日报社。总编辑贾涛根与我在一些会议上相识,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实务人士,我向他说起开会的事,他非常感兴趣,表示欢迎到南通去开,报社提供食宿,还可以上狼山去游览一回。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向全国发放征集论文的通知,响应相当踊跃。我们收到中国新闻法制中心(这是在起草新闻法过程中成立的一个学术性组织,由新闻出版署主管,王强华是中心的负责人之一。我也曾是这个中心的研究员)秘书长曹三明的回信,表示对这个会很有兴趣,并且提议他们中心也可以充任主办单位。我把这个意思转告贾总编,两人都觉得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高会议的规格,并且希望王强华来参加这个会议。会议于1991年5月举行,开了三天。参加人士包括新闻或法律学者,新闻媒体老总,以及北京、上海和江苏新闻宣传的官员。王强华没有来,让曹三明带来了祝贺的口信。孙旭培带了他的学生张西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来出席,我拉他同曹三明3人一起合了一张影,作为三个新闻法文稿的主要执笔人的纪念,也算是弥合他们两家的某些芥蒂。上海方面,龚心瀚、贾树枚,以及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后来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学长都到场讲话,南通方面给他们很高的礼遇。这个会影响很大,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北京、我们和南通都很高兴。
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后来又开过两次。第二次1993年5月在宜兴举行,资助者是宜兴日报社,总编辑许周溥是比我高两届的复旦新闻系学长。第三次1996年5月在安徽马鞍山举行,资助者是马鞍山日报社,总编辑吴秀华也是新闻法研究的爱好者,写过几篇有关新闻纠纷的文章。这两次会议都有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参与主办,主题、规格和组成人员的成分,都同前一次相同。但是三次会都参加的没有几个,就是我、张西明、王国庆(现任新闻出版署报纸司副司长)这样几位。每次会议都邀请王强华,他都说来,但是临开会又都因事来不成。
有一件很值得记载的事情:在宜兴会议上,王国庆按照王强华的意思,请来了几位法官,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李大元、朝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承启等。那时朝阳区法院刚受理国贸中心诉作家吴祖光侵害名誉权案,《新闻记者》上发表一篇短评对此有所讥诮。会议前夕报社举行欢迎晚宴,我向杨承启敬酒,杨知道我是《新闻记者》负责人,拒绝同我碰杯。我了解原委后,当夜带了助手到他的住房向他解释,并提议在此案审结后本刊作全面报道,得到杨的谅解。后来朝阳法院依法判决吴祖光胜诉,我请张西明写评论,张写了一篇论证此案中体现的公允评论原则的论文,使此案成为经典性案例。我了解到杨承启顶着巨大压力,受理新疆工会小职员奚红起诉人民日报侵害名誉权案,花了8年时间使这位弱女子讨回了公道,更是对他怀有由衷的敬意。《新闻记者》是全国唯一报道这个案件结果的杂志。90年代后期,朝阳区法院在杨承启的主持下,在审理“新闻官司”方面有若干富有创意的判决,我都写了评论。我同杨成了互相倾慕的好朋友。在法官朋友的影响下,我对“新闻官司”的态度发生了“微调”,就是从起先一味“帮”媒介说话,转到看到媒介的弱点,应该着眼于寻求言论自由和名誉权的平衡。
曹三明后来离开了新闻出版署,继续担任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秘书长的宋克明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把三次会议的论文集中编辑为一本很厚的书,1998年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为也是可以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一笔的三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此后,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也无疾而终。
我通过参加起草新闻法,编辑杂志,举办研讨会,吸取了丰富的学术养料。1994年5月,我的第一本关于媒介法的著作《被告席上的记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4年12月20日于香港宝马山)
而今,媒介法(又称新闻法、传媒法、大众传播法等)已经成为深受新闻界和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传媒大学王军副教授告诉我,下一学年她要给硕士生开新闻法选修课,牌子一挂出来,就有230名学生报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法律顾问、高级编辑徐迅报道:刚刚结束的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的舆论监督研讨会,热热闹闹来了200多人,而这样的会已经开到第四次了。去年,我受中国传媒大学之聘,在该校法律系招收博士生,经常有人从网上来信询问报考事项;今年该系又建立了硕士点,成为我国第一家集媒介法教学和研究为一体、媒介法专业学位授予机制齐全的专业学术机构。常常有人问我,你不学法律,是怎样进入媒介法领域的呢?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统一作答吧。
(一)
1986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任职助理研究员。夏天的某一天,所长宋军(资深新闻工作者、新闻史学者)把我找去,说:小潘(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维明)找我,说启立同志(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到上海来说起,现在国家起草新闻法一下子恐怕出不来,是不是上海可以先搞一个地方法规,如果取得成果,就可以给全国立法提供经验。宣传部决定把启立交办的这件任务交给新闻所,新闻所先拿一个法规初稿出来,然后按照正常的立法程序提交市人大审议。宋军说,这件事就由我和你来做。
我很高兴地领受了这件任务。我们知道,1984年经彭真委员长批示同意,人大常委会决定将制定新闻法列入议事日程,由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负责起草工作,胡先生将起草班子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此在那里成立了新闻法研究室,室主任就是后来曾任新闻所所长的孙旭培(现任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他们作了很多工作,如编印期刊《新闻法通讯》,翻译各国新闻法,胡绩伟先生还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为全国新闻界所关注。我对自己能够参预这样的盛事,深感荣幸,同时也觉得是一项很好的学习机会。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要的问题是收集资料。孙旭培的班子在这方面风格很高,他们的成果随时在《新闻法研究》上发表,并且一直寄送给我们,他们搜集翻译的外国新闻法也出了书,这样我们就可以享用他们的现成成果。
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宋军先生是新闻史家,我们着重搜集的是中国近现代新闻法规的资料,包括一些审判个案,如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七君子案的全过程报道等。后来我们获知有一位姓刘的老先生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功夫,搜集清朝和民国初年、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主要新闻出版法规编辑了一部书,书稿已在出版社。可能是通过宋军的关系,我们得到了书稿的全部影印件(我记不清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影印件,推想宋军当时还兼任市委宣传部报刊处长,应该有较大方便调阅书稿,从著作权角度说,这当然不妥,但当时并无这类观念),厚厚一大包,经编者分门别类,检阅十分方便,这样我们又省了很多力气。刘先生编的这部书已在90年代出版。
其时,法律已经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介入了媒介,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新中国第一起新闻记者被控诽谤罪的《疯女之谜》案。这篇文章发表在《民主与法制》上,主题是为一位“疯女”辩“诬”,文中严辞斥责了“疯女”的丈夫,丈夫有异议,要求杂志更正未成,遂诉诸法律。当时只有《刑法》,《民法通则》还没有出台,所以他是以诽谤罪对两位作者提出起诉,由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受理,其实在案件后面还另有一些与本文无关的背景。我自《民主与法制》创办后就担任它的兼职编辑(我能够较快介入法律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民主与法制》的兼职,该刊有一个法律顾问处,负责人是我的老师施晨初先生,主要是处理信访中提出的各类法律问题),所以我得以同步了解案件的进展,当时我同《民主与法制》的同仁们都对这个案件情绪抵触,认为是对新闻记者的打击(本案一直到1988年审结,两位《民主与法制》记者被判犯诽谤罪,各单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详见王强华、魏永征主编:《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由此我想在法规中应当设法给新闻记者提供更多的保护。
我查到我的日记(1986年)中有一条记载:“9月30日:居家将新闻法规文稿写完,得二十三条。”这是这篇《上海市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初稿完成的日期。我已记不起宋军同我的具体工作进程。宋军是我的前辈,但他对新事物依旧保持着敏感,思想相当解放,并且有丰厚的新闻史学功底,所以他对这个文稿的主导作用是无可置疑的。现存文稿铅印本有二十六条,应该是我呈交宋军后,他亲自做了修改补充,然后送到市委宣传部印刷的。铅印本分发给全市新闻界头面人物,有没有报给胡启立,我就不知道了。计划是要开会征求意见的,但是后来没有开过,可能是1986年12月爆发学潮,1月胡耀邦下台,全国反自由化,没有时间过问此事。后来宋军曾给我看过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有关新闻法规的问题由于有些实体问题要由另外的法律来规定,而这些法律尚待制定,所以此稿缓议。算是有一个交代。
现在回头看这个稿子,当然是比较肤浅的。文稿中没有提“新闻自由”,而是提“言论出版自由”,这是宋军与我的共同意见,虽然我们都承认新闻自由,但是认为作为一个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循宪法,采用宪法的提法,“言论出版自由”包括了“新闻自由”。这还是可以成立的。文稿中还有一条:“新闻工作者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这出于我的手笔,并非宋军授意。我的老师夏鼎铭先生(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看了以后就很不以为然,说新闻媒介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监督政府,你这样写,新闻记者都是官员了,怎么监督政府?我还同夏老师争论,说是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法就有“国家的新闻工作者”的说法,我们的新闻记者事实上也都是国家干部,写上这一条,新闻记者可以得到更多的保障,比如采访受到阻碍,就可以告人家妨害公务,云云。这表明“官方媒体”的观念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里可谓根深蒂固。
(二)
1987年初,国务院成立新闻出版署,加强对全国新闻媒体的行政管理,按照国务院对新闻出版署职权的规定,起草新闻法的工作也转移到新闻出版署,以副署长王强华牵头组建新的起草班子,也吸收了原来起草班子中的若干人士。此事幕后,胡绩伟先生有回忆文章披露。
王强华先生(现任《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出身法学专业,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是发表真理标准文章的责任编辑,应该说,他来主持起草新闻法也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是由于屁股指挥脑袋的规律,他必须自觉站在官方立场说话,这样他同孙旭培之间就屡起冲突。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谁可以成为办报主体,孙旭培坚持主张应该是公民,王强华则坚持限于单位(法人),双方互不相让,相互指责都很激烈,最后孙离开了起草组。
王强华就任不久,就带了他的助手曹三明(现任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等到上海来调查研究,其时上海是全国“新闻官司”最集中的地方,新闻法起草者当然很关注。他们也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来,找我谈过,对《上海市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很感兴趣,我们就这样相识。
1987年秋,时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贾树枚(现任上海市记协主席)打电话给我,说王强华向他提出,在上海另外成立一个新闻法起草组,犹如北京起草组的“影子内阁”,也起草一个新闻法文稿,目的是给北京的起草组提供一个参考文本。经过有关领导研究,决定以当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龚心瀚(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为组长,贾树枚为副组长。贾说,你参加吧?我想这可能与上海已经起草过一个地方法规草稿有关。龚、贾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这件事他们一定会找我,我也断无推卸之理。
上海新闻法起草组成立后,完全仿照北京的体制,邀请上海各大新闻单位代表人士参加,解放日报是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总编辑助理贾安坤(后来担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秘书长),新民晚报是著名老杂文家冯英子,新华社上海分社是退休的前社长杨瑛,还有法律界人士,记得起的有黄浦区法院法官张双龙,缘新闻媒介大都在黄浦区,这家法院受理“新闻官司”较多,所以邀请他们的人参加。工作班子则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报刊处的干部们。
前期工作一是搜集和编辑资料,此事主要由报刊处的人做,我也介绍了几位我们新闻所的青年人来参加,编了各国新闻法分条目选辑、历史和现实的新闻纠纷案例汇编等一些专题资料。二是专题讨论,无非是新闻自由和新闻记者的权利、创办新闻单位的条件和行政管理、新闻侵权、新闻与司法等,本想每周或隔周举行一次,起草组全体参加,但是后来因为各人都有工作,有时多数人不能来,只好暂停,这样就时断时续。开起会来,众人畅所欲言,自由讨论,会后出简报。专题讨论有不少是有争论的,但并不激烈,比如创办报刊,就有只许法人办报还是可以允许民间办报两种意见,再如新闻官司,法律界的人士侧重于谈论新闻报道中的问题,要求尊重公民的各种人格权,我记得张双龙一次就谈了一个多小时,是有备而发,新闻界的人士则着重于谈论新闻记者的权利,反对动不动就是诽谤,这方面贾安坤说得最多,不过双方并没有针锋相对地争论,因为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其实是各有各的道理。
1988年上半年,开始起草。我们的起草工作有些特别,也是集体起草。我们先讨论了《新闻法》的总的提纲,大致分为总则、新闻机构、新闻工作者、新闻的采访和发表等部分,然后二三人自由组合,各分一部分去写。写出来后提交全组讨论,然后把这些文稿统写成一篇,统稿人就是我。统稿又经过集体讨论,最后由贾树枚和我定稿。1988年初夏,我们两人以及报刊处几个人住在一所宾馆里,逐条推敲修改,最后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上海起草小组·征求意见稿)》,于1988年7月印成上报北京。
其时《新闻法研究》发表了孙旭培主持的新闻法研究室“试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据说他们在1985年就写了一个初稿,现在发表的是在这个初稿基础上修改的第三稿。到秋天,我们也见到了王强华主持的官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征求意见稿)》的打印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不可磨灭的三个“新闻法文稿”。
这三个文稿都是独立完成的。孙旭培那里不用说;北京也关照我们上海起草组,事先也不要通气,看看大家各自有什么特点。等到各方摊牌一看,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所谓大同者,首先就是在确立新闻自由作为新闻法的一项核心原则是一致的。三个文稿都对新闻自由做出了规定,都规定行使新闻自由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都规定政府在平时不得实行新闻检查,都规定创设新闻机构实行审批制,都规定了新闻活动的法律底线(即禁载内容),都规定了新闻机构更正和答辩制度,等等。至于三者区别,按照王强华在1988年底向ChinaDaily谈话所说,新闻研究室的文稿规定各人有办私人报纸的自由,而另外两个文稿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争议三个文稿在见诸文字时已经有所淡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文稿在法律责任中有对侵犯新闻自由行为的制裁条款,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行为是对新闻自由的侵害”,包括:“对公民向新闻机构提供情况、发表意见进行阻挠或打击报复”,“对新闻工作者的正常工作进行阻挠、压制、恐吓,或者进行打击报复”,“非法阻止新闻出版物的发行和新闻的传播”等六项;第六十条规定“新闻自由受到侵害的新闻机构、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公民,可以向侵害人的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起申诉,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这个规定是我设计的。按照我当时具有的法律知识,认为法律既然规定了一项权利,权利人在受到侵犯时就应该有途径请求保护,也就是请求以法律的强制手段制止或制裁侵犯行为,否则怎么体现法律的保护呢?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任何权利必须有救济手段,没有救济就没有真正的权利。这个规定所设想的救济措施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行政救济还可行,司法救济其实是不可操作的,新闻自由属于政治权利(宪法权利),我国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侵犯请求司法保护的自诉机制。不过既然只是提供给官方起草组参考的“影子文稿”,如何操作就不去管它了。
1989年1月,时任新闻出版署秘书长梁衡(后来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率工作组来上海,就他们起草的新闻法文稿征求意见,一连开了三天座谈会,出席者包括上海新闻界、法律界的代表性人士,有现职的新闻媒介老总、著名记者,有教授学者,有法官律师,也有退休在家的前辈,人们听说要制定新闻法,都很关心,都踊跃前来发表意见,会议开得十分热闹,几乎欲罢不能。有关情况,在当时我主持的《新闻记者》杂志上有详细报道。
接下来的情况,已是众所周知,不须赘述。在15年后的今天来看,应该说当时的一些考虑确实过于超前,无论是在整个社会环境上,还是国家总体的法律制度上,文稿中所设想的一些原则,确实还没有实施的条件,所以文稿被搁置是必然的。
(三)
在新闻法讨论热潮的时候,我征得梁衡的同意,在《新闻记者》上开设了专栏,专门讨论有关新闻法的学术问题。后来形势发生变化,有些问题不能谈了,但是我实在有些舍不得取消这个话题。从1988年起,上海以至全国,“新闻官司”连绵不断,有“告记者热”之说。我决定把报道这类“新闻官司”作为杂志的经常性的重要内容。
我找到了两位长期作者,两员大将。一位是上海解放日报的陈斌,另一位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徐迅,他们各自都在本单位的政法部门工作,很投入,也很专业。徐迅本来就是中央政法大学的毕业生,陈斌没有上过大学(后来通过业余学习取得资格),但是通过多年的政法报道,他的法律知识根底相当厚实,报社碰到官司大都要他去处理。90年代初期的一些有影响的“新闻官司”,如刘晓庆名誉权案、游本昌名誉权案、李谷一名誉权案、杨沫名誉权隐私权案、陈凯歌名誉权案等,大都是他们给我写稿在杂志上披露的,成为我的杂志的亮点、卖点。这同他们的本职工作并不矛盾。他们所在的媒体都只能发表新闻,就他们所掌握的资料来说,其实只用去了冰山一角,很多好东西都留在笔记本上。我们杂志篇幅限制较小,可以写较长的深度报道,他们笔记本中的宝藏可以得到充分利用。我还建议他们着重要写争议,不要一纸判决就定是非,有些问题还是可以探讨的,这样杂志上就有多元的声音。随着“新闻官司”审判实践的发展,最高法院多次发布司法解释,我请徐迅利用她的地位,采访起草司法解释的大法官,请他们阐述有关精神,这样大大提高了我的杂志的权威度。
接着就有举办研讨会的考虑,提出这个动议的是继宋军担任新闻所所长的张家骏,比我高三届的复旦新闻系学长。他提出,“新闻官司”在实际生活中争议很大,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空白,邀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人士一起坐下来进行研讨,应该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趣的,名称可以叫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不过上海社会科学院靠国家全额拨款,是个穷单位,《新闻记者》也没有经费,靠广告收入贴补,自负盈亏,也是在低水平上运转,要开会就需要有财政支持。第一个给我们支持的是南通日报社。总编辑贾涛根与我在一些会议上相识,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实务人士,我向他说起开会的事,他非常感兴趣,表示欢迎到南通去开,报社提供食宿,还可以上狼山去游览一回。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向全国发放征集论文的通知,响应相当踊跃。我们收到中国新闻法制中心(这是在起草新闻法过程中成立的一个学术性组织,由新闻出版署主管,王强华是中心的负责人之一。我也曾是这个中心的研究员)秘书长曹三明的回信,表示对这个会很有兴趣,并且提议他们中心也可以充任主办单位。我把这个意思转告贾总编,两人都觉得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高会议的规格,并且希望王强华来参加这个会议。会议于1991年5月举行,开了三天。参加人士包括新闻或法律学者,新闻媒体老总,以及北京、上海和江苏新闻宣传的官员。王强华没有来,让曹三明带来了祝贺的口信。孙旭培带了他的学生张西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来出席,我拉他同曹三明3人一起合了一张影,作为三个新闻法文稿的主要执笔人的纪念,也算是弥合他们两家的某些芥蒂。上海方面,龚心瀚、贾树枚,以及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后来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学长都到场讲话,南通方面给他们很高的礼遇。这个会影响很大,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北京、我们和南通都很高兴。
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后来又开过两次。第二次1993年5月在宜兴举行,资助者是宜兴日报社,总编辑许周溥是比我高两届的复旦新闻系学长。第三次1996年5月在安徽马鞍山举行,资助者是马鞍山日报社,总编辑吴秀华也是新闻法研究的爱好者,写过几篇有关新闻纠纷的文章。这两次会议都有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参与主办,主题、规格和组成人员的成分,都同前一次相同。但是三次会都参加的没有几个,就是我、张西明、王国庆(现任新闻出版署报纸司副司长)这样几位。每次会议都邀请王强华,他都说来,但是临开会又都因事来不成。
有一件很值得记载的事情:在宜兴会议上,王国庆按照王强华的意思,请来了几位法官,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李大元、朝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承启等。那时朝阳区法院刚受理国贸中心诉作家吴祖光侵害名誉权案,《新闻记者》上发表一篇短评对此有所讥诮。会议前夕报社举行欢迎晚宴,我向杨承启敬酒,杨知道我是《新闻记者》负责人,拒绝同我碰杯。我了解原委后,当夜带了助手到他的住房向他解释,并提议在此案审结后本刊作全面报道,得到杨的谅解。后来朝阳法院依法判决吴祖光胜诉,我请张西明写评论,张写了一篇论证此案中体现的公允评论原则的论文,使此案成为经典性案例。我了解到杨承启顶着巨大压力,受理新疆工会小职员奚红起诉人民日报侵害名誉权案,花了8年时间使这位弱女子讨回了公道,更是对他怀有由衷的敬意。《新闻记者》是全国唯一报道这个案件结果的杂志。90年代后期,朝阳区法院在杨承启的主持下,在审理“新闻官司”方面有若干富有创意的判决,我都写了评论。我同杨成了互相倾慕的好朋友。在法官朋友的影响下,我对“新闻官司”的态度发生了“微调”,就是从起先一味“帮”媒介说话,转到看到媒介的弱点,应该着眼于寻求言论自由和名誉权的平衡。
曹三明后来离开了新闻出版署,继续担任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秘书长的宋克明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把三次会议的论文集中编辑为一本很厚的书,1998年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为也是可以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一笔的三次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此后,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也无疾而终。
我通过参加起草新闻法,编辑杂志,举办研讨会,吸取了丰富的学术养料。1994年5月,我的第一本关于媒介法的著作《被告席上的记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4年12月20日于香港宝马山)
相关地名
江北区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