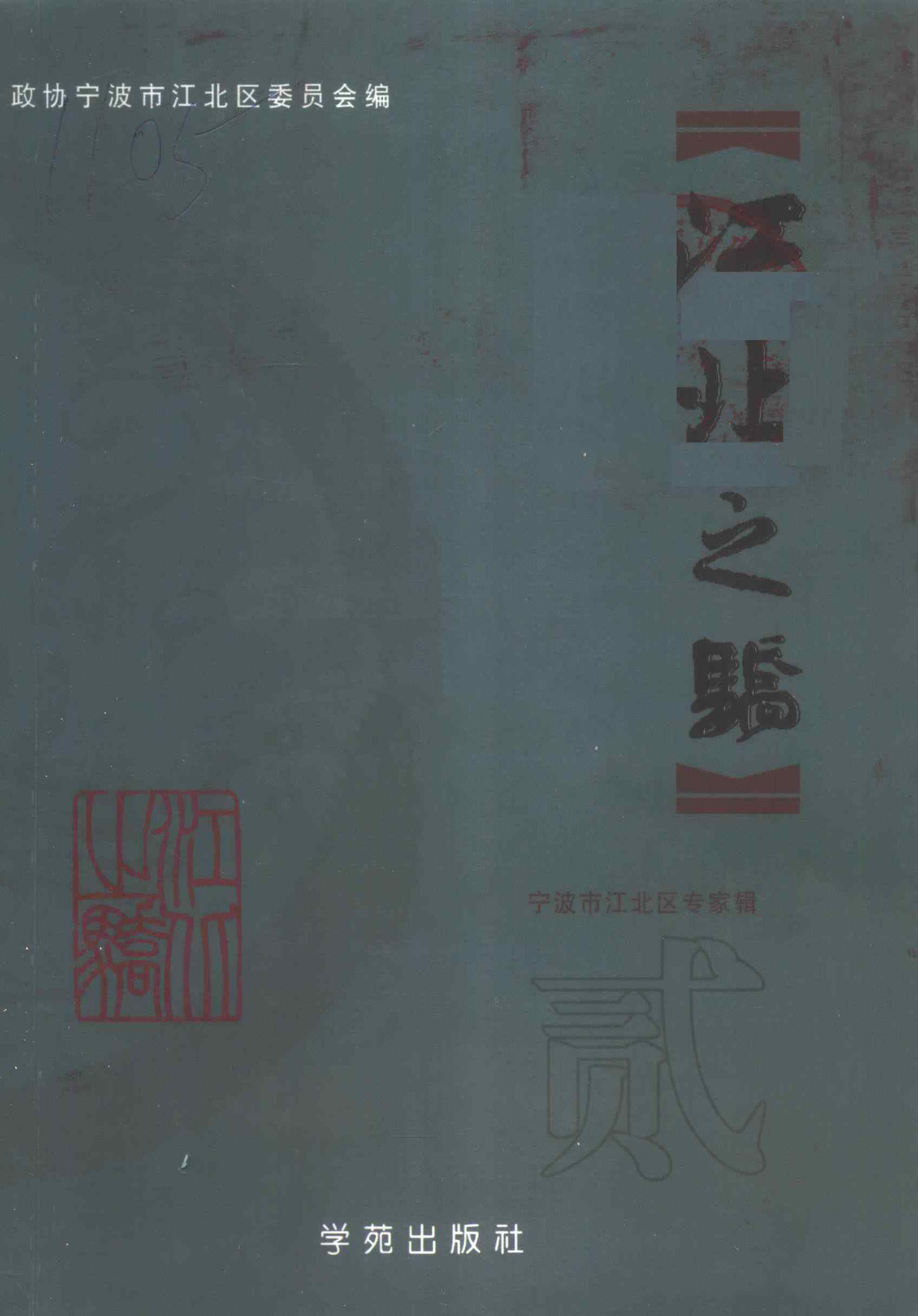内容
初到香港
1932年2月初,在淞沪战争日军炮火中,我和二哥乘加拿大邮轮“俄罗斯皇后”号离开上海去香港大学上学。船出吴淞口时,见到几艘日本军舰向吴淞炮轰,空中还有一架飞机盘旋观察。吴淞炮台大概已被击毁,未见还击。我抱着对日本侵略的满腔仇恨离开国门。此情此景,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忆犹新。
船行三日,在春节鞭炮声中到达九龙码头。已在香港大学上学的同乡秦省如约了也是上海去港的校友钱鸿陶和王宗炳,到码头接我们。他们带我们乘天星渡轮过海,到一家西式咖啡馆吃早点。随后乘出租车到当时上海学生集中住的宿舍马礼逊堂。那天雾很重。汽车不断左拐右弯,不断上爬,后来就只能从车的一侧见到街面,另一侧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我想汽车是在沿海马路上行驶。如此一直到马礼逊堂。他们带我们去见舍监博克塞先生(Mr.S.Boxer)(三十年代后期曾任大学的教务长)。他欢迎我们,问了我们有关上海战争的情况,然后说因为住房还没有全部调整好,只能让你们两人暂住在图书室内。住下后,他们先告诉我们大学宿舍的规矩和新生(greenhorns)的地位,告诫我们要尊重老生和不抵抗地承受老生的欺负。以后又带我们会见了假期中仍留在宿舍的外地学生,主要是从上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来的。我们不会讲广东话或福建话,只好有些结结巴巴地讲英语,有时引起新结识的同学们的笑弄,但看得出他们是好意的,所以我也不怕继续出丑。这天我过得很愉快。对于住房,虽然舍监对两人合住一房表示了歉意,我却以能住在从窗口能见到大海的房内感到很高兴。次晨醒来朝窗外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隔路有一幢不小的两层住宅,看不到海,使我很失望。宿舍的规矩,有住房空出时,住宿的学生都可申请,按住宿舍的年资长短分配。我到三年级时方分到二楼上的居室,从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海港和九龙,方满足了我的凤愿。马礼逊堂是大学宿舍中最高的,海拔近150米。常可见到浓雾的锋面从左或右漫移过来,直到把自己裹在雾内,那就又见不到隔路的房屋了。有一次,清晨我沿着有石级的山径去校部上课,雾浓得看不清路面,靠路熟和用足探索而行。我想起成语中有“伸手不见五指”之说,就特意伸出手臂,撑开和摆动手指,确实一点也见不到,方相信此语不虚。我曾专学中国古书两年,曾以古人之言、特别是“孔子曰”作为判断是非、虚实的依据。在学习几何、物理、化学之后开始改变这种观念,而港大的四年学习使我树立了新的观念:万事都须用逻辑分析、实践或实验来判断,不能完全不顾传统和权威意见,但也不能盲目迷信。
两位教师
我在港大机械系学习,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资格最老的、教原动机学的史密斯教授(C.A.MiddletonSmith)和教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布朗教授(W.Brown)。史密斯教授很少按教学大纲系统地讲解,似乎是随兴所至,海阔天空地谈论多方面的问题。对于原动机学,他介绍了几本参考书(其中一本是他自己早年的著作),让我们自学。他还要求我们自己到图书馆看工程方面的书籍和刊物,特别是英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刊物、《大英百科全书》和英国的TheEngineer和Engineering杂志。他在课上谈论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的有:不要只钻本专业的知识,而忽略建立一个宽广的知识基础,像用散沙堆金字塔,必须有一定宽广的基面方能将沙堆到一定的高度。机械工程师除应该有相邻的工程学科方面的知识外,还应有充分的、能将自己的想法和意图用文字正确和清晰地表达出来的能力。工程师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学和会计学知识,因为工程师不止于能完成某项工程或制成某种产品,而且要能比别人花费更少的费用。要重视理论和前人或自己的经验。想要超出已有的理论或过去的经验而迈出新的一步时,要特别谨慎。要准备出现没有预见到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又要有创新的勇气,总是墨守成规就不能进步。而人类常常是在反复和回流中不断地进步。他不是将这些论点作说教性的讲述,而是通过某些具体事例来讲述它们。我记得他谈到过的有:发明家瓦特在发明了有分开的凝气器的、因而大大地降低了煤耗率的蒸汽机之后,又发明了提前停止向汽缸供汽、以利用蒸汽膨胀做工的潜力,但是他却极力反对采用较高的蒸汽压力,反对他的助手默多克(W.Murdock)试制蒸汽汽车,这样,他限制了自己的发明的最大效益。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人在汽车(用蒸汽机驱动)的研制方面居于世界前茅,已有大客车在城市间来往,但在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限制行车速度要低于人行的速度,并必、须有人手持红旗在车前开路。这个被称为“红旗法案”的法规在以后30年间严重的影响了汽车工业在英国的发展。也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制造的大东方号汽船,排水量达27400顿,装蒸汽机共9500马力,有隔水舱和双层铁板船身,是当时超越时代的伟大工程成就,原定用于英国---印度间的客货运输,但由于与当时的海运条件不相适应,成为海运史上的最大失败。十九世纪末期,由于测量光速的结果与牛顿力学相矛盾而出现迷惑,爱因斯坦则因此创造了相对论;而镭的放射性恰恰是由于偶然性方引起注意和深入探讨。
史密斯教授在讲课中愿意听到学生提问题。我就常提问题,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我没有明白,希望得到补充说明。但有一次(在第一年级下学期)则变成我给他提出了补充事例。那时他谈到某方面知识的获得,也可能是另一方面、似乎没有关联的知识所起的作用。当时我因为入学考试英语水平不高,得不到免读英语。有一次,英语导师进行期中测试,说成绩好可以免读英语。考试方法是他读一篇论文,我们只听不记笔记。读两遍后,由我们用自己的文字重写听到的内容。他读的是一篇有关眼球结构和近视、远视等问题的论文。而这次考试的前几天,物理教授在讲光学时刚讲了凸镜成像和眼球结构。我平时上课本来就集中精神听讲和记笔记,因为我近视,对这堂课格外注意。像眼球这样内容,一般是不会在期终题中出现的,所以另外还有三、四个和我一起学英语的就没有注意。测试结果我得到免学,他们则需要继续学下去。物理学的课帮助我通过了英语测试。有同学提出,我这次测试成绩不能正确地反映我的英语水平,说我应请全班同学喝咖啡,否则要到英语导师处告发。我说我不怕,因为导师已经签发了免学书,他要收也收不回了。课室中包括教授在内,都笑了。我又提到英语导师在签证时问我是否常看报纸、刊物和小说,我说看。他又问我是看英文的还是中文的,我说都看。他随着建议我多看英文的,这样就将看报、看小说与学英语结合在一起了。史密斯教授顺着就说我们更应该多看工程方面刊物,这样就将学英语和学工程也结合在一起了。
这种谈论,我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都认为是一种闲谈,对于学好工程学科,尤其是对考试,似乎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在八十年代中,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卷》的编、审和定稿过程中,我常反复想到这类问题。在撰写这篇回忆中,经过更多的回想,我发现这些闲谈实际上对我从港大毕业后的工作和思想都产生过很大影响,是很有价值的“问题”。我现在感到的是,史密斯教授的这些“闲谈”如能组织得更系统、更严谨些,则其影响和作用就更大了。
布朗教授讲数学和应用数学课。我认为他是当时港大课讲得最好的教授。当时港大入学考试,对数学的要求比国内大学要低。进大学后,普通代数要从数列教起,解析几何和三角学则要从头教起。要在两年中教完工科学生所必须的数学知识,很不容易。但是布朗教授能以清晰易懂和富于风趣的语言,运用当时当地的事例,解释和说明数学和力学问题。当时在港大,上课只是讲解,基本上不做例题,也不布置学生做习题,上课不向学生提问,期中也没有考试。学生旷课不超过学期的三分之一,教师也无权干涉。但是数学课几乎总是满堂,旷课的学生很少。我记得学流体阻力时恰逢大雨,他就为我们计算不同直径的雨滴和冰雹从高空下降时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计算表明小冰雹最大可能的下降速度不大,伤不了人;但较大冰雹的下降速度可能大到可以打死牛。雨滴的比重虽大于冰雹,但是即使在高空中形成了较大的雨滴,下降到一定速度时,在空气阻力和气、水面间的摩擦作用下,会碎裂为小滴;另外,下降的雨滴是稍扁的球形,受到较球形为大的空气阻力。所以雨滴不可能很大,其最大速度也不大。在教相似理论时,电影院正放科幻电影“KingKong”(一个高近20米的大猩猩)。他用实际生物猩猩和人的体重、骨骼和肌肉的比例和强度,来计算KingKong的骨骼和肌肉的受力,证明它不可能在陆地上直立行走奔跃,也不能平伸手臂来举重物。当时港大学生很多有乘坐海船的经历,知道在风浪中大船摇摆都较慢,较平稳,而小船则摇摆较快,不平稳,使乘客感到不适。布朗教授在教船体摇摆和安稳性时,他先让大家议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家认为这是船体的量度因素所导致的特性。他随后才教船的摇摆和安全性等问题。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小船的宽度小、减小了船的摆动周期。但可由船舶设计师和通过改变装载(货物或压舱物)较大幅度地增大或缩短摇摆周期,就是减小或增大船的重心和稳心间的距离。大船安全性好,可以放低稳心,减小这个距离,牺牲一些安全性来换取较大的平稳性,即较长的摆动周期,而小船必须保持较大的重心和稳心距离,以获得足够的安全性。他说乘坐一条在风浪中摇摆很快的船很不舒适,但不必害怕。因为这船摇得快,是由于它有较大的复原位的力矩,摇过去后能很快回到原位。假如坐船感到摇摆变慢,觉得较原来更舒适,那可应该害怕了,因为重心在提高(如由于船舶进水),重心稳心间的距离缩短,复位力矩变小了。它很可能会摇得越来越慢,直到它摇过去后不再回来,而翻过去。分析计算的结论竟与直觉相反。
布朗教授在教学中常插入这类引人入胜的事例。他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清楚地理解复杂的理论分析,容易记住所教的计算公式,特别是记住公式中各个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我听课常坐在第一排,记下的笔记比较全。但我写字不好,总是将m、n、v、w等字母的上下圆角在急忙中都写成尖角。有一次在教最大值和最小值时,因为插入了其他话题,他忘了讲到哪里,就走到我的面前看我的笔记。他看到我在笔记中写的“最小值”(minimum),成为15个上下尖角,笑着走到黑板前描下这样写的字,并问大家认识不认识。大家都笑了。我笑着说,这是我的密码文字。布朗教授也笑着说:“这样我还得学一学,否则大考时我就无法判你的答卷了。”
下厂实习
港大工学院重视基础课,学得比较广泛和踏实。当时只分土木、机械、电气三个专业。一、二年级我们全部在一起学习,即使是每星期两个半天共八小时的机械工场实习,也是所有学生都去。三年级以后,我们仍与土木工程专业同学一起学钢结构学一年,与电气工程专业的同学一起学电工学两年。但是机械专业的主课原动机学主要靠学生自学,两年的机械设计则只教了在当时不再制造的12000马力超大型船用蒸汽机的设计。机械系没有机械制造工艺课程。在机械实习工场也没有系统的指导,我们只是在工人师傅指点下,自己操作干活。除必须按规定标准完成下料、划线和锯、锉、刮、研等钳工课题,以及车、刨、铣等切削课题外,可以较自由地领料干自己想干的工作。主管工场的是一位富有实际经验的英籍技师,但他没有工艺理论知识,也不讲课。他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安全问题。机械实验室也很简单,只做些原动机的试验和材料强度试验。
在工科学生团体的组织下,我们经常利用下午实验或实习时间到香港各机械工厂参观和学习,主要是去太古、黄埔和英国海军船厂,以及香港和九龙的发电厂、九龙的水泥厂、广九铁路机厂、各建筑工地等。各工厂都很重视这种参观,派有水平的工程师指导。这些活动成为我们学习热、冷加工工艺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对机械制造有兴趣,我还在一、二、三年级暑期自行联系到上海江南造船厂装配车间、香港太古船厂木模车间和九龙铁路机厂实习,学到了许多生产知识和操作手艺。到太古船坞实习是我写信给总经理格雷(Grey)联系的。他回信约我们去见他。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去,见到他后我们提出想到设计室实习。他说,你们实习时间不长(我们提两个月),学设计在大学中学习可能更有效,在工厂还应注意学实际生产知识。因为我谈过曾在江南厂的装配车间实习,他建议我们到他们的木模车间去,因为木模制造与铸件设计和生产都有关联,可以更好了解铸件设计和生产。他并说他自己的工厂生涯就是=在木模车间开始的。我们同意后,他亲自领我们到装配车间参观,又领我们到木模车间,要车间主任很好安排我们的实习。实习期满,我们到他办公室道谢。他高兴地说,假如毕业后来太古船厂求职,可以直接找他,他将给我们优先考虑。
听萧伯纳讲演
在港大期间,我见到过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他乘环航世界的邮船过香港。港大同学会请到他到港大大会堂(陆佑堂)与学生见面。我也去了,并挤在前面。他说他愿意与学生见面,但不愿做长篇讲话,只站着随便讲几句。他说,你们在大学学习,听了教授讲师许多课。他要告诫我们,首先要学会“忘记”,我们听到学到的东西,许多是不正确的,要引我们入歧途的。在学校必须学,不学毕不了业,但要会忘记,要将学到的东西忘记。大学领导和教授来参加这次会见的很少。布朗教授在场,他这时站在旁边,插嘴说:“你不用愁,他们忘记得比你想像的还要快呢!”我当时对萧伯纳的话难以理解,对这次会见感到茫然。直到八十年代,我方对他讲话的意义有所体会。
著名电影喜剧演员卓别林也曾到远东旅游,到过上海。港大学生会也想请他来港大与学生见面,并与他联系上了。但是他说,他根本不想到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因而未来港大。
1935年,史乐施(Dr.Sloss)到港大任校长(ViceChancellor),对校务进行某些改革。港大开始与中国教育部接触,并请高教司司长杭立武为港大校董(CourtMember)。计划对中文学院作较大的改变,不再单纯依靠中国旧文人,如只教古书的前清翰林。我听说想请胡适来港大当中文学院院长,并授予胡适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6年初胡适来港大参加1935年度的毕业典礼,接受这个学位。他也参加了港大Chancellor随后按每年常例举行的宴会。我是1935年毕业的,与胡适一起参加过这两次会。在宴会上,胡适作为港大名誉博士坐在主客席上并讲了话。我只记得他称赞港大的学习环境,并说我们港大本科毕业生是港大的亲生子女,而他很高兴被港大收为
养子,愿与我们一起为提高母校声望而努力。
港大Chancellor(香港总督兼任)的这个宴会在总督府大厅举行,参加者除当年的毕业生和学校的教授等外,还有港大校董会(court)的董事,也即香港当时的一些头面人物。宴会前先在客厅中接待,一切很隆重。入座时,我坐在一位总督军事副官(AidedeCamp)的旁边。副官很健谈,说他这军事副官的任务主要就是接待各种来宾。在侍者上菜由客人各自取菜时,总是劝我多取些。我认为宴会供菜必很多,想留些食量吃后面的菜。在上了汤和鱼后,上了下一个菜,我还是取得不多。这时他就说:“你多吃些!再不多吃就没有吃的了。”我取了双份,当晚才没有挨饿。因为在这个菜后就只有冰激凌、水果和咖啡了。宴会的菜比我们自己有时在市上西餐厅所吃还略欠丰盛。
兼职讲师
1940年初,因为原来讲授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课的讲师被征调到海军船坞服役。当时工学院系主任(Dean)雷德蒙教授(Prot.Redmond)找我去,问我是否愿意到港大作兼职讲师教这两门课。我说我是愿意的,但要立即上课,我没有时间备课。此外,需要征求我当时的工作单位黄埔船坞公司同意。雷德蒙教授说,没有时间准备你可以先按你自己的笔记讲。他知道我记的笔记完整。至于船坞公司,他已联系过,他们允许我每星期离开两个下午,学校可将部分课安排在晚上。我同意接受,但提出机械设计课不能再教那个已经不再制造和使用的12000马力蒸汽机。雷德蒙教授同意我的意见,并建议为及时开课,我可以先教一种较简单的机械产品的设计,接着再教更复杂的产品;第一种产品最好选一种常见的、有多种不同功能的机械零件的,第二种则最好是一种原动机。按照这次谈话,第一种我选择了手摇的、齿轮动、装有载荷自制的制动器的支柱式回转起重机。这种起重机我在船坞设计过,制成后使用效果较好。对于第二种产品。我有两种选择,一是船坞正在为战时应用的自由轮的主机,大约是3000马力的蒸汽机,二是船坞正在试制中的、气缸直径为350mm和500mm的低速船用柴油机。教蒸汽机当然简单,我当时也很熟悉,并对当时世界上为提高蒸汽机效率所开发的各种新式机型有所了解和研究,但是蒸汽机的盛期已过,已是暮年,不能作为大学的主教材。大型低速柴油机,船坞有整套引进的图纸和一些资料。我向船坞公司负责人请求允许我应用这些图纸和资料于教学,他说这些是从英国Harland&Wolte船厂引进的,而他们又是从荷兰的B&W公司引进的,公开这些资料需要事先得到他们的书面同意。当时战事紧张,即使本公司同意,他们两方面也不拒绝,也不能期望在一、二年中解决。所以后来我只能按照我原有的一本柴油机设计的参考书和在香港又买到的书中的资料来教中速柴油机的设计。但是能得到的资料不全、不系统,我又没有柴油机设计和制造的实际经验,准备时间也不充分,教学水平不高。现在想来也很感遗憾和歉愧。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我的教学生涯也就此终止。
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是大型修船和造船企业,工程师基本上都是英国人,但受过大学正规教育的很少。我在1936年进该公司时,包括公司经理(他是英国有名望的船舶建筑师)和我在内,可能只有五、六人,其余都是英国船厂或本公司当见习生或学徒出身。总经理对新型机械,尤其是新型蒸汽机和新型锅炉,很感兴趣,时常来设计室谈论。1938年初我辞职去参加中国海军的快艇大队,他还写信给香港大学,对香港大学的工科教学成绩表示赞赏,对我在船坞的工作表示满意,对我辞职去抗日虽然支持,却感到遗憾。此信后曾刊载于英国的工程杂志TheEngi-
neer1938年2月的“中国通讯”中。在1938年至1939年间,他又聘用港大毕业生四人,以及留英回来的华人工程师三人。1945年我在美国时,曾与他和史密斯教授通过信。
从香港到重庆
1942年4月我从日本占领的香港逃到当时为法国租借地的广州湾(现名湛江),然后步行六天到玉林,再乘长途汽车到柳州,换乘火车到桂林。
途经桂林时,我曾去英军服务团的桂林办事处,港大医学院的赖濂士教授(Porf.Ride)是代表团的团长,当时在桂林。当他知道我想到重庆去时,说他团里几天后有车到重庆去,可以带我一起去;到重庆后可去找王国栋教授(Porf.GordonKing),他带了一批医科未毕业的学生到国内,安排在贵阳、重庆几个医学院借读,他自己也在重庆的上海医学院教书。赖濂士教授知道我缺钱,送了我大约二、三百元钱。此后不久我即接受了中国植物油料公司的聘请,乘该公司汽车离开桂林,再也没有见到他。
(本文原载香港大学国内校友为庆祝母校八十周年校庆撰写的文集《一枝一叶总关情》,香港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
1932年2月初,在淞沪战争日军炮火中,我和二哥乘加拿大邮轮“俄罗斯皇后”号离开上海去香港大学上学。船出吴淞口时,见到几艘日本军舰向吴淞炮轰,空中还有一架飞机盘旋观察。吴淞炮台大概已被击毁,未见还击。我抱着对日本侵略的满腔仇恨离开国门。此情此景,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记忆犹新。
船行三日,在春节鞭炮声中到达九龙码头。已在香港大学上学的同乡秦省如约了也是上海去港的校友钱鸿陶和王宗炳,到码头接我们。他们带我们乘天星渡轮过海,到一家西式咖啡馆吃早点。随后乘出租车到当时上海学生集中住的宿舍马礼逊堂。那天雾很重。汽车不断左拐右弯,不断上爬,后来就只能从车的一侧见到街面,另一侧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我想汽车是在沿海马路上行驶。如此一直到马礼逊堂。他们带我们去见舍监博克塞先生(Mr.S.Boxer)(三十年代后期曾任大学的教务长)。他欢迎我们,问了我们有关上海战争的情况,然后说因为住房还没有全部调整好,只能让你们两人暂住在图书室内。住下后,他们先告诉我们大学宿舍的规矩和新生(greenhorns)的地位,告诫我们要尊重老生和不抵抗地承受老生的欺负。以后又带我们会见了假期中仍留在宿舍的外地学生,主要是从上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来的。我们不会讲广东话或福建话,只好有些结结巴巴地讲英语,有时引起新结识的同学们的笑弄,但看得出他们是好意的,所以我也不怕继续出丑。这天我过得很愉快。对于住房,虽然舍监对两人合住一房表示了歉意,我却以能住在从窗口能见到大海的房内感到很高兴。次晨醒来朝窗外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隔路有一幢不小的两层住宅,看不到海,使我很失望。宿舍的规矩,有住房空出时,住宿的学生都可申请,按住宿舍的年资长短分配。我到三年级时方分到二楼上的居室,从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海港和九龙,方满足了我的凤愿。马礼逊堂是大学宿舍中最高的,海拔近150米。常可见到浓雾的锋面从左或右漫移过来,直到把自己裹在雾内,那就又见不到隔路的房屋了。有一次,清晨我沿着有石级的山径去校部上课,雾浓得看不清路面,靠路熟和用足探索而行。我想起成语中有“伸手不见五指”之说,就特意伸出手臂,撑开和摆动手指,确实一点也见不到,方相信此语不虚。我曾专学中国古书两年,曾以古人之言、特别是“孔子曰”作为判断是非、虚实的依据。在学习几何、物理、化学之后开始改变这种观念,而港大的四年学习使我树立了新的观念:万事都须用逻辑分析、实践或实验来判断,不能完全不顾传统和权威意见,但也不能盲目迷信。
两位教师
我在港大机械系学习,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资格最老的、教原动机学的史密斯教授(C.A.MiddletonSmith)和教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布朗教授(W.Brown)。史密斯教授很少按教学大纲系统地讲解,似乎是随兴所至,海阔天空地谈论多方面的问题。对于原动机学,他介绍了几本参考书(其中一本是他自己早年的著作),让我们自学。他还要求我们自己到图书馆看工程方面的书籍和刊物,特别是英国机械工程学会的刊物、《大英百科全书》和英国的TheEngineer和Engineering杂志。他在课上谈论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的有:不要只钻本专业的知识,而忽略建立一个宽广的知识基础,像用散沙堆金字塔,必须有一定宽广的基面方能将沙堆到一定的高度。机械工程师除应该有相邻的工程学科方面的知识外,还应有充分的、能将自己的想法和意图用文字正确和清晰地表达出来的能力。工程师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学和会计学知识,因为工程师不止于能完成某项工程或制成某种产品,而且要能比别人花费更少的费用。要重视理论和前人或自己的经验。想要超出已有的理论或过去的经验而迈出新的一步时,要特别谨慎。要准备出现没有预见到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又要有创新的勇气,总是墨守成规就不能进步。而人类常常是在反复和回流中不断地进步。他不是将这些论点作说教性的讲述,而是通过某些具体事例来讲述它们。我记得他谈到过的有:发明家瓦特在发明了有分开的凝气器的、因而大大地降低了煤耗率的蒸汽机之后,又发明了提前停止向汽缸供汽、以利用蒸汽膨胀做工的潜力,但是他却极力反对采用较高的蒸汽压力,反对他的助手默多克(W.Murdock)试制蒸汽汽车,这样,他限制了自己的发明的最大效益。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人在汽车(用蒸汽机驱动)的研制方面居于世界前茅,已有大客车在城市间来往,但在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限制行车速度要低于人行的速度,并必、须有人手持红旗在车前开路。这个被称为“红旗法案”的法规在以后30年间严重的影响了汽车工业在英国的发展。也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制造的大东方号汽船,排水量达27400顿,装蒸汽机共9500马力,有隔水舱和双层铁板船身,是当时超越时代的伟大工程成就,原定用于英国---印度间的客货运输,但由于与当时的海运条件不相适应,成为海运史上的最大失败。十九世纪末期,由于测量光速的结果与牛顿力学相矛盾而出现迷惑,爱因斯坦则因此创造了相对论;而镭的放射性恰恰是由于偶然性方引起注意和深入探讨。
史密斯教授在讲课中愿意听到学生提问题。我就常提问题,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我没有明白,希望得到补充说明。但有一次(在第一年级下学期)则变成我给他提出了补充事例。那时他谈到某方面知识的获得,也可能是另一方面、似乎没有关联的知识所起的作用。当时我因为入学考试英语水平不高,得不到免读英语。有一次,英语导师进行期中测试,说成绩好可以免读英语。考试方法是他读一篇论文,我们只听不记笔记。读两遍后,由我们用自己的文字重写听到的内容。他读的是一篇有关眼球结构和近视、远视等问题的论文。而这次考试的前几天,物理教授在讲光学时刚讲了凸镜成像和眼球结构。我平时上课本来就集中精神听讲和记笔记,因为我近视,对这堂课格外注意。像眼球这样内容,一般是不会在期终题中出现的,所以另外还有三、四个和我一起学英语的就没有注意。测试结果我得到免学,他们则需要继续学下去。物理学的课帮助我通过了英语测试。有同学提出,我这次测试成绩不能正确地反映我的英语水平,说我应请全班同学喝咖啡,否则要到英语导师处告发。我说我不怕,因为导师已经签发了免学书,他要收也收不回了。课室中包括教授在内,都笑了。我又提到英语导师在签证时问我是否常看报纸、刊物和小说,我说看。他又问我是看英文的还是中文的,我说都看。他随着建议我多看英文的,这样就将看报、看小说与学英语结合在一起了。史密斯教授顺着就说我们更应该多看工程方面刊物,这样就将学英语和学工程也结合在一起了。
这种谈论,我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都认为是一种闲谈,对于学好工程学科,尤其是对考试,似乎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在八十年代中,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卷》的编、审和定稿过程中,我常反复想到这类问题。在撰写这篇回忆中,经过更多的回想,我发现这些闲谈实际上对我从港大毕业后的工作和思想都产生过很大影响,是很有价值的“问题”。我现在感到的是,史密斯教授的这些“闲谈”如能组织得更系统、更严谨些,则其影响和作用就更大了。
布朗教授讲数学和应用数学课。我认为他是当时港大课讲得最好的教授。当时港大入学考试,对数学的要求比国内大学要低。进大学后,普通代数要从数列教起,解析几何和三角学则要从头教起。要在两年中教完工科学生所必须的数学知识,很不容易。但是布朗教授能以清晰易懂和富于风趣的语言,运用当时当地的事例,解释和说明数学和力学问题。当时在港大,上课只是讲解,基本上不做例题,也不布置学生做习题,上课不向学生提问,期中也没有考试。学生旷课不超过学期的三分之一,教师也无权干涉。但是数学课几乎总是满堂,旷课的学生很少。我记得学流体阻力时恰逢大雨,他就为我们计算不同直径的雨滴和冰雹从高空下降时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计算表明小冰雹最大可能的下降速度不大,伤不了人;但较大冰雹的下降速度可能大到可以打死牛。雨滴的比重虽大于冰雹,但是即使在高空中形成了较大的雨滴,下降到一定速度时,在空气阻力和气、水面间的摩擦作用下,会碎裂为小滴;另外,下降的雨滴是稍扁的球形,受到较球形为大的空气阻力。所以雨滴不可能很大,其最大速度也不大。在教相似理论时,电影院正放科幻电影“KingKong”(一个高近20米的大猩猩)。他用实际生物猩猩和人的体重、骨骼和肌肉的比例和强度,来计算KingKong的骨骼和肌肉的受力,证明它不可能在陆地上直立行走奔跃,也不能平伸手臂来举重物。当时港大学生很多有乘坐海船的经历,知道在风浪中大船摇摆都较慢,较平稳,而小船则摇摆较快,不平稳,使乘客感到不适。布朗教授在教船体摇摆和安稳性时,他先让大家议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家认为这是船体的量度因素所导致的特性。他随后才教船的摇摆和安全性等问题。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小船的宽度小、减小了船的摆动周期。但可由船舶设计师和通过改变装载(货物或压舱物)较大幅度地增大或缩短摇摆周期,就是减小或增大船的重心和稳心间的距离。大船安全性好,可以放低稳心,减小这个距离,牺牲一些安全性来换取较大的平稳性,即较长的摆动周期,而小船必须保持较大的重心和稳心距离,以获得足够的安全性。他说乘坐一条在风浪中摇摆很快的船很不舒适,但不必害怕。因为这船摇得快,是由于它有较大的复原位的力矩,摇过去后能很快回到原位。假如坐船感到摇摆变慢,觉得较原来更舒适,那可应该害怕了,因为重心在提高(如由于船舶进水),重心稳心间的距离缩短,复位力矩变小了。它很可能会摇得越来越慢,直到它摇过去后不再回来,而翻过去。分析计算的结论竟与直觉相反。
布朗教授在教学中常插入这类引人入胜的事例。他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清楚地理解复杂的理论分析,容易记住所教的计算公式,特别是记住公式中各个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我听课常坐在第一排,记下的笔记比较全。但我写字不好,总是将m、n、v、w等字母的上下圆角在急忙中都写成尖角。有一次在教最大值和最小值时,因为插入了其他话题,他忘了讲到哪里,就走到我的面前看我的笔记。他看到我在笔记中写的“最小值”(minimum),成为15个上下尖角,笑着走到黑板前描下这样写的字,并问大家认识不认识。大家都笑了。我笑着说,这是我的密码文字。布朗教授也笑着说:“这样我还得学一学,否则大考时我就无法判你的答卷了。”
下厂实习
港大工学院重视基础课,学得比较广泛和踏实。当时只分土木、机械、电气三个专业。一、二年级我们全部在一起学习,即使是每星期两个半天共八小时的机械工场实习,也是所有学生都去。三年级以后,我们仍与土木工程专业同学一起学钢结构学一年,与电气工程专业的同学一起学电工学两年。但是机械专业的主课原动机学主要靠学生自学,两年的机械设计则只教了在当时不再制造的12000马力超大型船用蒸汽机的设计。机械系没有机械制造工艺课程。在机械实习工场也没有系统的指导,我们只是在工人师傅指点下,自己操作干活。除必须按规定标准完成下料、划线和锯、锉、刮、研等钳工课题,以及车、刨、铣等切削课题外,可以较自由地领料干自己想干的工作。主管工场的是一位富有实际经验的英籍技师,但他没有工艺理论知识,也不讲课。他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安全问题。机械实验室也很简单,只做些原动机的试验和材料强度试验。
在工科学生团体的组织下,我们经常利用下午实验或实习时间到香港各机械工厂参观和学习,主要是去太古、黄埔和英国海军船厂,以及香港和九龙的发电厂、九龙的水泥厂、广九铁路机厂、各建筑工地等。各工厂都很重视这种参观,派有水平的工程师指导。这些活动成为我们学习热、冷加工工艺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对机械制造有兴趣,我还在一、二、三年级暑期自行联系到上海江南造船厂装配车间、香港太古船厂木模车间和九龙铁路机厂实习,学到了许多生产知识和操作手艺。到太古船坞实习是我写信给总经理格雷(Grey)联系的。他回信约我们去见他。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去,见到他后我们提出想到设计室实习。他说,你们实习时间不长(我们提两个月),学设计在大学中学习可能更有效,在工厂还应注意学实际生产知识。因为我谈过曾在江南厂的装配车间实习,他建议我们到他们的木模车间去,因为木模制造与铸件设计和生产都有关联,可以更好了解铸件设计和生产。他并说他自己的工厂生涯就是=在木模车间开始的。我们同意后,他亲自领我们到装配车间参观,又领我们到木模车间,要车间主任很好安排我们的实习。实习期满,我们到他办公室道谢。他高兴地说,假如毕业后来太古船厂求职,可以直接找他,他将给我们优先考虑。
听萧伯纳讲演
在港大期间,我见到过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他乘环航世界的邮船过香港。港大同学会请到他到港大大会堂(陆佑堂)与学生见面。我也去了,并挤在前面。他说他愿意与学生见面,但不愿做长篇讲话,只站着随便讲几句。他说,你们在大学学习,听了教授讲师许多课。他要告诫我们,首先要学会“忘记”,我们听到学到的东西,许多是不正确的,要引我们入歧途的。在学校必须学,不学毕不了业,但要会忘记,要将学到的东西忘记。大学领导和教授来参加这次会见的很少。布朗教授在场,他这时站在旁边,插嘴说:“你不用愁,他们忘记得比你想像的还要快呢!”我当时对萧伯纳的话难以理解,对这次会见感到茫然。直到八十年代,我方对他讲话的意义有所体会。
著名电影喜剧演员卓别林也曾到远东旅游,到过上海。港大学生会也想请他来港大与学生见面,并与他联系上了。但是他说,他根本不想到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因而未来港大。
1935年,史乐施(Dr.Sloss)到港大任校长(ViceChancellor),对校务进行某些改革。港大开始与中国教育部接触,并请高教司司长杭立武为港大校董(CourtMember)。计划对中文学院作较大的改变,不再单纯依靠中国旧文人,如只教古书的前清翰林。我听说想请胡适来港大当中文学院院长,并授予胡适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6年初胡适来港大参加1935年度的毕业典礼,接受这个学位。他也参加了港大Chancellor随后按每年常例举行的宴会。我是1935年毕业的,与胡适一起参加过这两次会。在宴会上,胡适作为港大名誉博士坐在主客席上并讲了话。我只记得他称赞港大的学习环境,并说我们港大本科毕业生是港大的亲生子女,而他很高兴被港大收为
养子,愿与我们一起为提高母校声望而努力。
港大Chancellor(香港总督兼任)的这个宴会在总督府大厅举行,参加者除当年的毕业生和学校的教授等外,还有港大校董会(court)的董事,也即香港当时的一些头面人物。宴会前先在客厅中接待,一切很隆重。入座时,我坐在一位总督军事副官(AidedeCamp)的旁边。副官很健谈,说他这军事副官的任务主要就是接待各种来宾。在侍者上菜由客人各自取菜时,总是劝我多取些。我认为宴会供菜必很多,想留些食量吃后面的菜。在上了汤和鱼后,上了下一个菜,我还是取得不多。这时他就说:“你多吃些!再不多吃就没有吃的了。”我取了双份,当晚才没有挨饿。因为在这个菜后就只有冰激凌、水果和咖啡了。宴会的菜比我们自己有时在市上西餐厅所吃还略欠丰盛。
兼职讲师
1940年初,因为原来讲授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课的讲师被征调到海军船坞服役。当时工学院系主任(Dean)雷德蒙教授(Prot.Redmond)找我去,问我是否愿意到港大作兼职讲师教这两门课。我说我是愿意的,但要立即上课,我没有时间备课。此外,需要征求我当时的工作单位黄埔船坞公司同意。雷德蒙教授说,没有时间准备你可以先按你自己的笔记讲。他知道我记的笔记完整。至于船坞公司,他已联系过,他们允许我每星期离开两个下午,学校可将部分课安排在晚上。我同意接受,但提出机械设计课不能再教那个已经不再制造和使用的12000马力蒸汽机。雷德蒙教授同意我的意见,并建议为及时开课,我可以先教一种较简单的机械产品的设计,接着再教更复杂的产品;第一种产品最好选一种常见的、有多种不同功能的机械零件的,第二种则最好是一种原动机。按照这次谈话,第一种我选择了手摇的、齿轮动、装有载荷自制的制动器的支柱式回转起重机。这种起重机我在船坞设计过,制成后使用效果较好。对于第二种产品。我有两种选择,一是船坞正在为战时应用的自由轮的主机,大约是3000马力的蒸汽机,二是船坞正在试制中的、气缸直径为350mm和500mm的低速船用柴油机。教蒸汽机当然简单,我当时也很熟悉,并对当时世界上为提高蒸汽机效率所开发的各种新式机型有所了解和研究,但是蒸汽机的盛期已过,已是暮年,不能作为大学的主教材。大型低速柴油机,船坞有整套引进的图纸和一些资料。我向船坞公司负责人请求允许我应用这些图纸和资料于教学,他说这些是从英国Harland&Wolte船厂引进的,而他们又是从荷兰的B&W公司引进的,公开这些资料需要事先得到他们的书面同意。当时战事紧张,即使本公司同意,他们两方面也不拒绝,也不能期望在一、二年中解决。所以后来我只能按照我原有的一本柴油机设计的参考书和在香港又买到的书中的资料来教中速柴油机的设计。但是能得到的资料不全、不系统,我又没有柴油机设计和制造的实际经验,准备时间也不充分,教学水平不高。现在想来也很感遗憾和歉愧。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我的教学生涯也就此终止。
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是大型修船和造船企业,工程师基本上都是英国人,但受过大学正规教育的很少。我在1936年进该公司时,包括公司经理(他是英国有名望的船舶建筑师)和我在内,可能只有五、六人,其余都是英国船厂或本公司当见习生或学徒出身。总经理对新型机械,尤其是新型蒸汽机和新型锅炉,很感兴趣,时常来设计室谈论。1938年初我辞职去参加中国海军的快艇大队,他还写信给香港大学,对香港大学的工科教学成绩表示赞赏,对我在船坞的工作表示满意,对我辞职去抗日虽然支持,却感到遗憾。此信后曾刊载于英国的工程杂志TheEngi-
neer1938年2月的“中国通讯”中。在1938年至1939年间,他又聘用港大毕业生四人,以及留英回来的华人工程师三人。1945年我在美国时,曾与他和史密斯教授通过信。
从香港到重庆
1942年4月我从日本占领的香港逃到当时为法国租借地的广州湾(现名湛江),然后步行六天到玉林,再乘长途汽车到柳州,换乘火车到桂林。
途经桂林时,我曾去英军服务团的桂林办事处,港大医学院的赖濂士教授(Porf.Ride)是代表团的团长,当时在桂林。当他知道我想到重庆去时,说他团里几天后有车到重庆去,可以带我一起去;到重庆后可去找王国栋教授(Porf.GordonKing),他带了一批医科未毕业的学生到国内,安排在贵阳、重庆几个医学院借读,他自己也在重庆的上海医学院教书。赖濂士教授知道我缺钱,送了我大约二、三百元钱。此后不久我即接受了中国植物油料公司的聘请,乘该公司汽车离开桂林,再也没有见到他。
(本文原载香港大学国内校友为庆祝母校八十周年校庆撰写的文集《一枝一叶总关情》,香港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