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后
| 内容出处: | 《杨贤江全集 第一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12320020220006310 |
| 颗粒名称: | 病后 |
| 分类号: | G40-092.5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557-568 |
| 摘要: | 本文为杨贤江的病后,原载1922年3月30日《民国日报·觉悟》。 |
| 关键词: | 杨贤江 论著 病后 |
内容
一 开场白
素来不大会生病的我——只有十二岁时,记得曾生一场大病,几乎变成秃头老少年——现在居然病了,而且足足病了两个星期——从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九日。
到了现在,虽然还没有回复我底健康,但终算已离了病室底生活。回忆病时,曾感触到许多心事。我本是个多情善感的人,远从十年前,近从两年来,已经积累了不少的一般人所称为失意的苦痛。平时制裁力强时,还能把这些杂念压伏在下意识里,虽然有时也要奔突出来,但终于被遏住了。间或用文字发泄些郁闷,也就可以得少许的自慰。记得前年秋季赴粤以后,作过一篇一万多字的《赴粤杂感》,②把我个人的性格,人生观的转变,很详细地说了出来。不过此稿一直放在友人那里,始终没有发表。这次病倒,又不免往事重上心头,觉得说明白了似乎可以快意一点,所以就提起笔来写这篇文字。只是随想随写,加以病后精神欠缺,构思力薄弱,恐怕于文字及意义两方面都有杂乱的毛病,希望读者会原谅我。
二 病状
我底病,说起来,只是很小很小,几乎是不值得说的。表面的原因不过是伤风和咳嗽。医生屡向我“头痛”?“腰酸”?我都回说“不”,“不”。惟脉搏比平常快二三十次,体热比平常高半度多些。胃口当然是不大好,大便亦不通了几天。一位中医请我吃了二钱生大黄,还不见什么大效。他说我底体气实在太好了,所以毛病难以好得快。我听了他的话,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起初中药、西药并服,后来单服中药,最后单服西药。到现在还是在服疗咳嗽的西药。实在医我的病,药力本不是惟一的方法呵!
记得病后的第四夜,我真恐怖极了。入睡后,忽然神思糊涂,陷于恍忽迷离的状态,没节制的联想东奔西突,闹个不住。我想:我是变成疯狂了,快要搬到疯人院里去了,这将怎么好呢?于是我竟想不睡,怕睡熟了永不醒来。但后来不知怎的,一切全忘了。
这次初病时,我仍然想:平常忙忙碌碌不肯休息的,现在可要强迫你休息了。因为前几年虽然没有大病,有时却也要觉得不舒服;当那个时候,我就认为休息的一个机会,果然睡不了两三天,就恢复原状了。——这也许是我底呆想罢了。
又,从前觉得不适意时,我终能用心理作用自制,简直不认自己是有病。可是这次就大大的不然。虽则起初还把彼当作休息的机会,但不知怎样,暗地里就觉得这次的病是真的病了,又
认淹留病榻是当然的事了。于是一病竟病了这么久。GF信里也说:“心理作用与身体至有关系,望你不要存个‘病体如旧’的心。”可是我虽能理解这句话的不错,但终究没有勇气来自制,这真是平常的我所不能自信的呵!
三 孤独的悲哀
好苦呵!在这两星期中,孤零零地关在一间病室中,——这病室是一间统楼,本是我底卧室,也就是我底书斋、食堂、会客室——生生地把我活动的权利都剥夺了去。一个人到了病的时候,总希望有家人或至亲来慰问慰问,料理料理。但我从十二岁离开乡里以后,①就和亲旧隔绝了缘分,最初在杭州是这样,后来在南京、在广州都是这样,现在在上海,仍然是这样,所靠的只有几个朋友;但朋友各有职务,是不能常来作伴的。于是一有了病,就只好自己忍受,捱延,真到苦不堪言的时候,也只有流几滴泪,或呻吟几声罢了。
我虽活了二十多年,然小孩子底脾气仍然保藏着〔没〕有失去,所以遇着难过的时候,一想到家中的父母弟妹和在远处的知己好友,都不晓得我是在受痛苦,就不免淌下眼泪来了。事后回想,也觉得好笑,但在当时确不能自制。
最感不便的,便是虽在病中,还须自己倒茶,自己冲牛奶,自己烘面包。临时要什么东西,竟没有一个人来相帮。我于是感到无产阶级者乃是与病势不两立的了。——此段说来话长,且让下面另节再谈。
四 病中惟一的安慰者
上节说过孤独的悲哀,原是我这两星期的病榻生活所饱尝的,然幸而犹有一线生机,得不致于十分受不住寂寞之苦,而且心灵上还不绝地充满着希望之乐,这便是我病时所最感激,且将永远不会忘记的GF其人了。我病的第二天,伊就来看我。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谈话,但是伊底真挚的神情,已令我深深地受着无穷的感激。以后伊又每天寄我一封信,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精神才得不致枯竭,实在不能不说是由于伊底这些信所滋养的。我就在此要正式对伊表示我底谢意。
还有,在刚病倒的时候,在H地的YI,赠我白梅两朵。在刚离病榻生活的时候,在N地的TM,也赠我红梅两朵。TM信中说:“人每赠花以慰病者,我不能执花以趋兄前,惟寄兄红梅数朵以伴兄病耳。”伊们底这种盛情,都是我所感激不忘的,我也要在此对伊们表示我底谢意。
五 我也是现代青年烦闷者
我晓得,我这次的病,实由于感情生活上受着过多的失意所致。平时因为制裁力强,无法发泄;今乘肉体有病,使尔突围而出,几乎至于无可收拾。所以我自认这次是精神病。因为是精神病,故幻想特多,凡过去的种种失意事,都要一样一样涌上心头来。现在既动了笔,也就不免要说说明白,虽然没有什么功效,至少也可算透一口气。
现代的青年,差不多都觉得有些烦闷。烦闷几乎可以说是现代青年的专有症了。烦闷症的原因,我曾稍稍研究过,但还不能发表。GF说:“不快之感是人人有的,而尤其是我们青年;青年人的感情大概要丰富些,失意事也不免要多些。”我想这是的确的,现代的青年如果不感得有什么烦闷,什么失意,我敢说他们必然是变态的青年了。
我底病当然是现代青年底特有症里的一种。我不欲讳言,我是个多情的人,也就是个受着多情为累的人。以我底善感,我怎能不追思往事呢?朋友们虽然屡次劝我病中要安静,要休息,不要忧愁烦闷,不要追思往事,以引起不快之感,但我一经病倒,勇气全无,实在无法禁止我底游移不定、驰驱不已的病想。良友之言,只好暂时违背了。
六 我底苦痛一
现代很多的青年是受着家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害处。从家族主义受着的以婚姻不自由为最显。从资本主义受着的以求学不自由为最显。
不幸我都受着了,我已经是牺牲了不少的人生趣味,减去了不少的活动权利了。
我从毕业师范以后,为了家庭负担,为了进高等学校费用浩大不能胜任,就只好止住我底读书志愿而谋职业以糊口。差幸办事机关原是个高等学校,倒也并不缺少自修的机会。这样竟也能增长些断片的知识。不过我底读书的野心实在过于猛烈,像这样零碎和偶然的研究,万不足以满足我底欲望。好比一个强有力的人,只得些稀饭来喝喝,并且连这些也不能有确定的担保,怎能不心里焦灼呢?求学贵自修,古今来有学问者很多成于自修。这些道理,当然大家都能明白。不过据我这四五年来的经验,如果一面办事,一面求学,双方并进,一定很少成效。除非他的职业和他所欲求的学问性质是一样的,尚有进步可说。然这还须有个能自力研究的基础做前提才行。不然,纵使他用功异常,也只能得些普通的常识。若想从办事余暇里研究专门学问而能有心得,恐怕难成事实。这固由于人的精力有限,也因工读并行、心思不专之故。
我年来受着经济压迫,竟不得满足我底知识上的愿望,实在是我所认为苦痛的一种。
七 我底苦痛二
这一段要讲到我底婚姻的苦痛了。虽然这已是件过去的事,为我底朋友所已经晓得了的事,而且现在受着这苦痛的当事人已成了互相谅解的好友,似乎不必过于郑重地来说。但我底许多朋友也许有愿意得闻其详的,就是为个人计、为社会计,也许有声明的必要,所以就连带着在此地发表了。
当我只有十六岁而且还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可怜我已变做一个“有妇之夫”了。行过了“结婚式”,同居了七日,我仍回到学校里去念书。什么是“结婚”?什么是“结婚之乐”?我都莫明其妙。我和我底“妻”,在结婚前既不相闻问,在结婚后仍不识而目。现在回想这种“把戏”,真是可笑而又可悲!后来我到杭州读书,不但没有恋爱之想,连放假时也难得回家。那时对于这种“把戏”,已经有点发生疑问了。等毕业以后,到南高服务,①就开始了有意的不满意。我想:“漠不相关的两个人可以做终身的伴侣么?”“情感不投、兴趣不属的两个人可以永久同居么?”但我虽是这样想,到底不敢宣言离;而且还要用“人道”两字来慰藉自己。所以在这时期,也曾得过且过地混了几年;只是心底的悲哀,因受着过度的压抑,反而变成深厚。
到了民国八年,我底勉强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关不住了。因为我想:“伊虽不是有什么过失的女子,但和我没有深切的爱情,而又不能实行共同生活,何必定要结成‘夫妇关系’呢?”
不过虽然这样想,还不敢直接宣告和伊脱离关系,因为我又想:“伊到底也是个恶制度底下的产物,正和我一样;如果和伊完全断绝关系,在事实上伊将无以为生,而情谊上也觉难以为怀。”于是又把这个问题暂时“搁浅”。
但是不满意的终无法变成满意。我这个埋没的感情,到底又复活了起来。我以为这样隐忍能挨得几久呢?这种牺牲又岂可以永远呢?
如其“维持现状”,不特把“夫妻关系”成为虚名,亦且类于不明不白,徒使此心不安。而于个人生活的自由、精神的活泼皆有召〔招〕致错乱和阻迟的危险。几经思虑,几经踌躇,最后我为了尊重个人生活权利,为了破除社会结婚恶习,同时又受了不能公布的家庭黑幕的刺激,决意向伊提出离婚的要求了。这是民国九年八月间的事。
实在呢,我觉得所以必须离婚的原因,是不能一一列举的。因为这差不多是“直觉的”,正同两人想恋一想〔样〕,是说不出“究竟”或“所以然”。不过在我们中间,实在只有友谊而无恋爱。计自结婚到现在,名目上虽有十年多了,而实际同居的日数还不到一年。所以我对于伊,除了“陈陈相因”的敷衍以外,并没有发生过“心心相印”的爱情。在伊一方面呢,也只有对我的习俗上的相好和顺从,始终没有“非做好夫妻不可”的感觉。还有一层,伊到公婆家里以后,不大有过舒服的日子,身体是常常生病的。到了现在,简直病根深固,虽然请医服药,终无健康希望。这是伊从我国家族制度里所受的苦痛,我个人对伊还是要表示同情的。
我所提出的离婚要求,当然不是要伊和我完全断绝关系。我虽万不得已而竟出于离婚,但决不忍使伊受不能胜任的悲苦。我是这样对伊说:“我们虽是名义上做了多年的夫妻,但实际上我们已没有成为夫妻的必要。我们为求各个自由安全计,不如把这个虚名丢了,另外结成一种关系。我愿意担任你底教育费及生活费,即日离开这素所讨厌的家庭,而到女校里去读书,也得藉此体养你底身体。总之,我们的离婚,只是把夫妻关系变成友谊关系罢了。”起初,伊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要求,当然觉得非常难过。而“离婚”两字,尤其使伊不能忍受。自然,一个内地女子的见解,做人妻的被丈夫丢了,怎能不怕人家讥讽呢?后来经我几次解释,从实际方面证明我们虽然离太〔婚〕,但别方面还是有着关系。伊就也没有反对,答应我了。
原来伊自己也觉得不能做人的妻,即使不离婚,还是不能有夫妻关系的实效。而伊对于我的所谓苦痛也能理解得到,所以伊对于我底要求,除“离婚”两字怕失面子以外,并不觉得有怎样难受的地方。读书一层,因我曾经教过伊,本是伊所希望的。而家庭这个牢笼,又是伊愿意离开的。故我所说的条件,竟可以说是伊所欢迎的。就从那年秋季,伊跟了一位女先生,到邻县女子小学里去过学生生活了。
我底过去的婚姻史,就是这样完结。我愿意再在此地声明的,就是对于伊能谅解我底苦衷的一种好意和勇气,真是我所感激的。而离婚以后,因为各得心之所安,反使我们变成要好的朋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呵!
我底朋友,对于我底离婚事实,大概都早已晓得,不过经过详细,容或未知;而外间传述,又多谬误,所以我乘这个机会,特地写了出来,作为声明。(《妇女杂志》出“离婚问题号”,我本已答应做这篇文字。不料病魔来袭,竟使我错过机会,不及排入)
八习俗与烦闷
我两年来的失意,全是起于异性间的交际,而为恶习俗底横暴势力所激成的。自然,我是不甘受旧礼教的束缚,也不怕“多嘴”的人无理的说话的。只是对〔某些〕方面或者有所畏惧而不敢实行自己心之所安,或者实行了自己心之所安而竟〔招〕来外界的诽谤甚而至于中伤。这样,在我也不免要受着不快之感。而这种不快之感,在这短短的两年中真是实受得不少,于是便引起我仇视习俗和愤愤不平的心理。不幸结果乃是自己受亏!
无理的习俗,固然足以阻止人性的正当发展。而一般不彻底觉悟的男性所加于女性的引诱、恐吓,更足以使社交前途有无限的危险。我有一个朋友,因为被习惯的势力所束缚,乃至不敢聚谈,不敢同游。这是由于伊胆量太小,太无抵抗的勇气。然另有一个朋友,能不受恶势力的牵制,能实行交际的自由。这样算是很好了,但不料仍有一种不良的势力,横加侮蔑,而且这还是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所做的卑鄙手段。因此竟使伊见了社交公开而触目惊心。(去年十一月二日《妇女评论》上CF有一篇《社交公开的障碍》,也为此事而发)
诸位看,这是何等伤心的事!在我个人呢,我底行为只要出于正当的动机,我原不怕习俗底恐吓和人家底非难。但这是只能适用于自身,不可强迫我底友人来服从的呵!
由遵守习俗而引起烦闷,我在这次病中更饱尝其苦。我因为病了好久,不耐寂寞之苦,所以特写信请H地的朋友来看看我。我原晓得伊的胆子小,或者竟不敢来。但我既病得这么苦,又何妨一试?岂知果然不出我所料,等了几天,接到回信,伊说:“此地情形,你是晓得的。我并非胆小,但也不愿人家恣意讥评。”伊竟把这个算为不来的“最大理由”。那时我读完信,难过极了,就把信纸撕碎,原来我们底人情乃竟这样没有力量!我因可怜我那朋友底没有勇气,但我又当怎样可恶那万恶的习俗?我是要学做人的,我要和习俗反抗!我愿我底朋友都要有决心有毅力去和习俗反抗!
九 可怜哉无产阶级
我想:无产者与病,是势不两立的。而且无产者也没有生病的资格。只有资本家配生病,无产者怎好终日安坐着而不活动呵!
我病了十四日,而每日费用平均乃需五元。这样就一共用去了七十多元。当病得难过的时候,也想移到医院里去住。但后来一经探听,知道邻近的一个医院每日住院用费,三等是两角,二等是两元,头等是四元。我就不敢去了。
因为三等的房间和待遇,不见得比我现在的情形为好。头等当然是无望了,二等呢,实在也嫌太贵。原来住头、二等的用费,只包括房屋和普通医药及食费,如需要特别的医药及饮食物时,仍须另外出钱。我若移住医院,则每日所需,势必超出五元以上,这样,我的力量,实在不能胜任,所以只好作罢论了。
然而我还算有做医生的朋友可以请来诊视,有要好的朋友可以走来慰问,又有些朋友可以设法些钱,有些同居可以料理饮食。但是我想到那些工厂里作工的劳动者,拉车子的,做小贩的,他们全靠做一天活一天,万一身体失了健康,不得出去工作,将怎样过日呢?他们有请不动医生诊治的,有不得人料理的,也没有人去安慰,更没有人能借钱。他们底苦才真苦呵!比了他们,我还算是幸气〔运〕的呢。然而他们底苦怎样才得解救?我们对于不合理的、非人道的现代社会制度,就不能不有所感触了。
我曾听见一位医生说:“住在三等病院里的病人,我们原晓得应该怎样疗治的,然因为他们拿不出钱来买药,我们也只好坐视了。”这是何等悲痛的话!为什么人类世界竟有这等现象!
当我病了十四日之后,虽能勉强走动,但病体实在未愈,就到现在,伤风咳嗽依然存在,每天只能吃两碗饭,而精神界更属颓丧不堪,本来想暂离上海到别处去养病,否则也要多休息几天,可使健康恢复得快些;然这些在我们无产者在势是难做到的。因为每天的生活问题,是要每天解决的。所以在病的第十五天,我就出去做工了。我为了自己底面包,为了“家人”底面包,我是被迫着只好出去做工了。
从这次病,我对于资本主义的仇恨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归向,都要比未病前更急迫些,更亲切些。而我底意思,至少至少将来的医院和医生都要改为公有。因为现代的医院和医生,无异是资本阶级底专有品。
十 赘言
连续几夜,勉强执笔来写这篇文字;到此地,所必要说的话,仿佛可以完了。虽然心里仍然还有着零零碎碎的念头,但因为太杂乱了,又没有心力去整理,就算了罢,不再写了。
我把这篇“乱谈”,从头到尾地重读一遍,我自己发见我底弱点来了——或者读者,特别的是我底朋友,已经比我先发见了——就是我这个人太没有勇气,太偏于感情了。这些弱点,我都承认。偏于感情,不特病时为然,是我底生性这样。惟缺少勇气,似当别论。因为在未病以前,我确实不相信病,不相信药,并且不相信即使病了也不当像这次的颓丧、郁闷。但是说来奇怪,这次一经病倒,就觉万事皆休,中西医药乱吃了,过去的失意事都一件一件涌上心头来了。真如GF所说:“自己苦苦地想去,终觉越想越不高兴,越无生趣。”不瞒知我的朋友说,直到现在,我还是精神不畅,说话无味。要我说出理由来,我只有谨〔敬〕谢不敏。总之,过去的苦痛,现状的不满意,逼迫我太甚,使我失却抵抗能力,暂时屈服罢了。但我决不敢自暴自弃,我终要尽力忘却种种的失意,留此有用之身,干人类应做的事。知我的朋友!请你们监视我,勖勉我,督促我。
一九二二,三,十五夜起稿,廿一夜脱稿
1922年3月15~21日撰
原载1922年3月30日《民国日报·觉悟》
素来不大会生病的我——只有十二岁时,记得曾生一场大病,几乎变成秃头老少年——现在居然病了,而且足足病了两个星期——从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九日。
到了现在,虽然还没有回复我底健康,但终算已离了病室底生活。回忆病时,曾感触到许多心事。我本是个多情善感的人,远从十年前,近从两年来,已经积累了不少的一般人所称为失意的苦痛。平时制裁力强时,还能把这些杂念压伏在下意识里,虽然有时也要奔突出来,但终于被遏住了。间或用文字发泄些郁闷,也就可以得少许的自慰。记得前年秋季赴粤以后,作过一篇一万多字的《赴粤杂感》,②把我个人的性格,人生观的转变,很详细地说了出来。不过此稿一直放在友人那里,始终没有发表。这次病倒,又不免往事重上心头,觉得说明白了似乎可以快意一点,所以就提起笔来写这篇文字。只是随想随写,加以病后精神欠缺,构思力薄弱,恐怕于文字及意义两方面都有杂乱的毛病,希望读者会原谅我。
二 病状
我底病,说起来,只是很小很小,几乎是不值得说的。表面的原因不过是伤风和咳嗽。医生屡向我“头痛”?“腰酸”?我都回说“不”,“不”。惟脉搏比平常快二三十次,体热比平常高半度多些。胃口当然是不大好,大便亦不通了几天。一位中医请我吃了二钱生大黄,还不见什么大效。他说我底体气实在太好了,所以毛病难以好得快。我听了他的话,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起初中药、西药并服,后来单服中药,最后单服西药。到现在还是在服疗咳嗽的西药。实在医我的病,药力本不是惟一的方法呵!
记得病后的第四夜,我真恐怖极了。入睡后,忽然神思糊涂,陷于恍忽迷离的状态,没节制的联想东奔西突,闹个不住。我想:我是变成疯狂了,快要搬到疯人院里去了,这将怎么好呢?于是我竟想不睡,怕睡熟了永不醒来。但后来不知怎的,一切全忘了。
这次初病时,我仍然想:平常忙忙碌碌不肯休息的,现在可要强迫你休息了。因为前几年虽然没有大病,有时却也要觉得不舒服;当那个时候,我就认为休息的一个机会,果然睡不了两三天,就恢复原状了。——这也许是我底呆想罢了。
又,从前觉得不适意时,我终能用心理作用自制,简直不认自己是有病。可是这次就大大的不然。虽则起初还把彼当作休息的机会,但不知怎样,暗地里就觉得这次的病是真的病了,又
认淹留病榻是当然的事了。于是一病竟病了这么久。GF信里也说:“心理作用与身体至有关系,望你不要存个‘病体如旧’的心。”可是我虽能理解这句话的不错,但终究没有勇气来自制,这真是平常的我所不能自信的呵!
三 孤独的悲哀
好苦呵!在这两星期中,孤零零地关在一间病室中,——这病室是一间统楼,本是我底卧室,也就是我底书斋、食堂、会客室——生生地把我活动的权利都剥夺了去。一个人到了病的时候,总希望有家人或至亲来慰问慰问,料理料理。但我从十二岁离开乡里以后,①就和亲旧隔绝了缘分,最初在杭州是这样,后来在南京、在广州都是这样,现在在上海,仍然是这样,所靠的只有几个朋友;但朋友各有职务,是不能常来作伴的。于是一有了病,就只好自己忍受,捱延,真到苦不堪言的时候,也只有流几滴泪,或呻吟几声罢了。
我虽活了二十多年,然小孩子底脾气仍然保藏着〔没〕有失去,所以遇着难过的时候,一想到家中的父母弟妹和在远处的知己好友,都不晓得我是在受痛苦,就不免淌下眼泪来了。事后回想,也觉得好笑,但在当时确不能自制。
最感不便的,便是虽在病中,还须自己倒茶,自己冲牛奶,自己烘面包。临时要什么东西,竟没有一个人来相帮。我于是感到无产阶级者乃是与病势不两立的了。——此段说来话长,且让下面另节再谈。
四 病中惟一的安慰者
上节说过孤独的悲哀,原是我这两星期的病榻生活所饱尝的,然幸而犹有一线生机,得不致于十分受不住寂寞之苦,而且心灵上还不绝地充满着希望之乐,这便是我病时所最感激,且将永远不会忘记的GF其人了。我病的第二天,伊就来看我。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谈话,但是伊底真挚的神情,已令我深深地受着无穷的感激。以后伊又每天寄我一封信,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精神才得不致枯竭,实在不能不说是由于伊底这些信所滋养的。我就在此要正式对伊表示我底谢意。
还有,在刚病倒的时候,在H地的YI,赠我白梅两朵。在刚离病榻生活的时候,在N地的TM,也赠我红梅两朵。TM信中说:“人每赠花以慰病者,我不能执花以趋兄前,惟寄兄红梅数朵以伴兄病耳。”伊们底这种盛情,都是我所感激不忘的,我也要在此对伊们表示我底谢意。
五 我也是现代青年烦闷者
我晓得,我这次的病,实由于感情生活上受着过多的失意所致。平时因为制裁力强,无法发泄;今乘肉体有病,使尔突围而出,几乎至于无可收拾。所以我自认这次是精神病。因为是精神病,故幻想特多,凡过去的种种失意事,都要一样一样涌上心头来。现在既动了笔,也就不免要说说明白,虽然没有什么功效,至少也可算透一口气。
现代的青年,差不多都觉得有些烦闷。烦闷几乎可以说是现代青年的专有症了。烦闷症的原因,我曾稍稍研究过,但还不能发表。GF说:“不快之感是人人有的,而尤其是我们青年;青年人的感情大概要丰富些,失意事也不免要多些。”我想这是的确的,现代的青年如果不感得有什么烦闷,什么失意,我敢说他们必然是变态的青年了。
我底病当然是现代青年底特有症里的一种。我不欲讳言,我是个多情的人,也就是个受着多情为累的人。以我底善感,我怎能不追思往事呢?朋友们虽然屡次劝我病中要安静,要休息,不要忧愁烦闷,不要追思往事,以引起不快之感,但我一经病倒,勇气全无,实在无法禁止我底游移不定、驰驱不已的病想。良友之言,只好暂时违背了。
六 我底苦痛一
现代很多的青年是受着家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害处。从家族主义受着的以婚姻不自由为最显。从资本主义受着的以求学不自由为最显。
不幸我都受着了,我已经是牺牲了不少的人生趣味,减去了不少的活动权利了。
我从毕业师范以后,为了家庭负担,为了进高等学校费用浩大不能胜任,就只好止住我底读书志愿而谋职业以糊口。差幸办事机关原是个高等学校,倒也并不缺少自修的机会。这样竟也能增长些断片的知识。不过我底读书的野心实在过于猛烈,像这样零碎和偶然的研究,万不足以满足我底欲望。好比一个强有力的人,只得些稀饭来喝喝,并且连这些也不能有确定的担保,怎能不心里焦灼呢?求学贵自修,古今来有学问者很多成于自修。这些道理,当然大家都能明白。不过据我这四五年来的经验,如果一面办事,一面求学,双方并进,一定很少成效。除非他的职业和他所欲求的学问性质是一样的,尚有进步可说。然这还须有个能自力研究的基础做前提才行。不然,纵使他用功异常,也只能得些普通的常识。若想从办事余暇里研究专门学问而能有心得,恐怕难成事实。这固由于人的精力有限,也因工读并行、心思不专之故。
我年来受着经济压迫,竟不得满足我底知识上的愿望,实在是我所认为苦痛的一种。
七 我底苦痛二
这一段要讲到我底婚姻的苦痛了。虽然这已是件过去的事,为我底朋友所已经晓得了的事,而且现在受着这苦痛的当事人已成了互相谅解的好友,似乎不必过于郑重地来说。但我底许多朋友也许有愿意得闻其详的,就是为个人计、为社会计,也许有声明的必要,所以就连带着在此地发表了。
当我只有十六岁而且还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可怜我已变做一个“有妇之夫”了。行过了“结婚式”,同居了七日,我仍回到学校里去念书。什么是“结婚”?什么是“结婚之乐”?我都莫明其妙。我和我底“妻”,在结婚前既不相闻问,在结婚后仍不识而目。现在回想这种“把戏”,真是可笑而又可悲!后来我到杭州读书,不但没有恋爱之想,连放假时也难得回家。那时对于这种“把戏”,已经有点发生疑问了。等毕业以后,到南高服务,①就开始了有意的不满意。我想:“漠不相关的两个人可以做终身的伴侣么?”“情感不投、兴趣不属的两个人可以永久同居么?”但我虽是这样想,到底不敢宣言离;而且还要用“人道”两字来慰藉自己。所以在这时期,也曾得过且过地混了几年;只是心底的悲哀,因受着过度的压抑,反而变成深厚。
到了民国八年,我底勉强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关不住了。因为我想:“伊虽不是有什么过失的女子,但和我没有深切的爱情,而又不能实行共同生活,何必定要结成‘夫妇关系’呢?”
不过虽然这样想,还不敢直接宣告和伊脱离关系,因为我又想:“伊到底也是个恶制度底下的产物,正和我一样;如果和伊完全断绝关系,在事实上伊将无以为生,而情谊上也觉难以为怀。”于是又把这个问题暂时“搁浅”。
但是不满意的终无法变成满意。我这个埋没的感情,到底又复活了起来。我以为这样隐忍能挨得几久呢?这种牺牲又岂可以永远呢?
如其“维持现状”,不特把“夫妻关系”成为虚名,亦且类于不明不白,徒使此心不安。而于个人生活的自由、精神的活泼皆有召〔招〕致错乱和阻迟的危险。几经思虑,几经踌躇,最后我为了尊重个人生活权利,为了破除社会结婚恶习,同时又受了不能公布的家庭黑幕的刺激,决意向伊提出离婚的要求了。这是民国九年八月间的事。
实在呢,我觉得所以必须离婚的原因,是不能一一列举的。因为这差不多是“直觉的”,正同两人想恋一想〔样〕,是说不出“究竟”或“所以然”。不过在我们中间,实在只有友谊而无恋爱。计自结婚到现在,名目上虽有十年多了,而实际同居的日数还不到一年。所以我对于伊,除了“陈陈相因”的敷衍以外,并没有发生过“心心相印”的爱情。在伊一方面呢,也只有对我的习俗上的相好和顺从,始终没有“非做好夫妻不可”的感觉。还有一层,伊到公婆家里以后,不大有过舒服的日子,身体是常常生病的。到了现在,简直病根深固,虽然请医服药,终无健康希望。这是伊从我国家族制度里所受的苦痛,我个人对伊还是要表示同情的。
我所提出的离婚要求,当然不是要伊和我完全断绝关系。我虽万不得已而竟出于离婚,但决不忍使伊受不能胜任的悲苦。我是这样对伊说:“我们虽是名义上做了多年的夫妻,但实际上我们已没有成为夫妻的必要。我们为求各个自由安全计,不如把这个虚名丢了,另外结成一种关系。我愿意担任你底教育费及生活费,即日离开这素所讨厌的家庭,而到女校里去读书,也得藉此体养你底身体。总之,我们的离婚,只是把夫妻关系变成友谊关系罢了。”起初,伊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要求,当然觉得非常难过。而“离婚”两字,尤其使伊不能忍受。自然,一个内地女子的见解,做人妻的被丈夫丢了,怎能不怕人家讥讽呢?后来经我几次解释,从实际方面证明我们虽然离太〔婚〕,但别方面还是有着关系。伊就也没有反对,答应我了。
原来伊自己也觉得不能做人的妻,即使不离婚,还是不能有夫妻关系的实效。而伊对于我的所谓苦痛也能理解得到,所以伊对于我底要求,除“离婚”两字怕失面子以外,并不觉得有怎样难受的地方。读书一层,因我曾经教过伊,本是伊所希望的。而家庭这个牢笼,又是伊愿意离开的。故我所说的条件,竟可以说是伊所欢迎的。就从那年秋季,伊跟了一位女先生,到邻县女子小学里去过学生生活了。
我底过去的婚姻史,就是这样完结。我愿意再在此地声明的,就是对于伊能谅解我底苦衷的一种好意和勇气,真是我所感激的。而离婚以后,因为各得心之所安,反使我们变成要好的朋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呵!
我底朋友,对于我底离婚事实,大概都早已晓得,不过经过详细,容或未知;而外间传述,又多谬误,所以我乘这个机会,特地写了出来,作为声明。(《妇女杂志》出“离婚问题号”,我本已答应做这篇文字。不料病魔来袭,竟使我错过机会,不及排入)
八习俗与烦闷
我两年来的失意,全是起于异性间的交际,而为恶习俗底横暴势力所激成的。自然,我是不甘受旧礼教的束缚,也不怕“多嘴”的人无理的说话的。只是对〔某些〕方面或者有所畏惧而不敢实行自己心之所安,或者实行了自己心之所安而竟〔招〕来外界的诽谤甚而至于中伤。这样,在我也不免要受着不快之感。而这种不快之感,在这短短的两年中真是实受得不少,于是便引起我仇视习俗和愤愤不平的心理。不幸结果乃是自己受亏!
无理的习俗,固然足以阻止人性的正当发展。而一般不彻底觉悟的男性所加于女性的引诱、恐吓,更足以使社交前途有无限的危险。我有一个朋友,因为被习惯的势力所束缚,乃至不敢聚谈,不敢同游。这是由于伊胆量太小,太无抵抗的勇气。然另有一个朋友,能不受恶势力的牵制,能实行交际的自由。这样算是很好了,但不料仍有一种不良的势力,横加侮蔑,而且这还是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所做的卑鄙手段。因此竟使伊见了社交公开而触目惊心。(去年十一月二日《妇女评论》上CF有一篇《社交公开的障碍》,也为此事而发)
诸位看,这是何等伤心的事!在我个人呢,我底行为只要出于正当的动机,我原不怕习俗底恐吓和人家底非难。但这是只能适用于自身,不可强迫我底友人来服从的呵!
由遵守习俗而引起烦闷,我在这次病中更饱尝其苦。我因为病了好久,不耐寂寞之苦,所以特写信请H地的朋友来看看我。我原晓得伊的胆子小,或者竟不敢来。但我既病得这么苦,又何妨一试?岂知果然不出我所料,等了几天,接到回信,伊说:“此地情形,你是晓得的。我并非胆小,但也不愿人家恣意讥评。”伊竟把这个算为不来的“最大理由”。那时我读完信,难过极了,就把信纸撕碎,原来我们底人情乃竟这样没有力量!我因可怜我那朋友底没有勇气,但我又当怎样可恶那万恶的习俗?我是要学做人的,我要和习俗反抗!我愿我底朋友都要有决心有毅力去和习俗反抗!
九 可怜哉无产阶级
我想:无产者与病,是势不两立的。而且无产者也没有生病的资格。只有资本家配生病,无产者怎好终日安坐着而不活动呵!
我病了十四日,而每日费用平均乃需五元。这样就一共用去了七十多元。当病得难过的时候,也想移到医院里去住。但后来一经探听,知道邻近的一个医院每日住院用费,三等是两角,二等是两元,头等是四元。我就不敢去了。
因为三等的房间和待遇,不见得比我现在的情形为好。头等当然是无望了,二等呢,实在也嫌太贵。原来住头、二等的用费,只包括房屋和普通医药及食费,如需要特别的医药及饮食物时,仍须另外出钱。我若移住医院,则每日所需,势必超出五元以上,这样,我的力量,实在不能胜任,所以只好作罢论了。
然而我还算有做医生的朋友可以请来诊视,有要好的朋友可以走来慰问,又有些朋友可以设法些钱,有些同居可以料理饮食。但是我想到那些工厂里作工的劳动者,拉车子的,做小贩的,他们全靠做一天活一天,万一身体失了健康,不得出去工作,将怎样过日呢?他们有请不动医生诊治的,有不得人料理的,也没有人去安慰,更没有人能借钱。他们底苦才真苦呵!比了他们,我还算是幸气〔运〕的呢。然而他们底苦怎样才得解救?我们对于不合理的、非人道的现代社会制度,就不能不有所感触了。
我曾听见一位医生说:“住在三等病院里的病人,我们原晓得应该怎样疗治的,然因为他们拿不出钱来买药,我们也只好坐视了。”这是何等悲痛的话!为什么人类世界竟有这等现象!
当我病了十四日之后,虽能勉强走动,但病体实在未愈,就到现在,伤风咳嗽依然存在,每天只能吃两碗饭,而精神界更属颓丧不堪,本来想暂离上海到别处去养病,否则也要多休息几天,可使健康恢复得快些;然这些在我们无产者在势是难做到的。因为每天的生活问题,是要每天解决的。所以在病的第十五天,我就出去做工了。我为了自己底面包,为了“家人”底面包,我是被迫着只好出去做工了。
从这次病,我对于资本主义的仇恨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归向,都要比未病前更急迫些,更亲切些。而我底意思,至少至少将来的医院和医生都要改为公有。因为现代的医院和医生,无异是资本阶级底专有品。
十 赘言
连续几夜,勉强执笔来写这篇文字;到此地,所必要说的话,仿佛可以完了。虽然心里仍然还有着零零碎碎的念头,但因为太杂乱了,又没有心力去整理,就算了罢,不再写了。
我把这篇“乱谈”,从头到尾地重读一遍,我自己发见我底弱点来了——或者读者,特别的是我底朋友,已经比我先发见了——就是我这个人太没有勇气,太偏于感情了。这些弱点,我都承认。偏于感情,不特病时为然,是我底生性这样。惟缺少勇气,似当别论。因为在未病以前,我确实不相信病,不相信药,并且不相信即使病了也不当像这次的颓丧、郁闷。但是说来奇怪,这次一经病倒,就觉万事皆休,中西医药乱吃了,过去的失意事都一件一件涌上心头来了。真如GF所说:“自己苦苦地想去,终觉越想越不高兴,越无生趣。”不瞒知我的朋友说,直到现在,我还是精神不畅,说话无味。要我说出理由来,我只有谨〔敬〕谢不敏。总之,过去的苦痛,现状的不满意,逼迫我太甚,使我失却抵抗能力,暂时屈服罢了。但我决不敢自暴自弃,我终要尽力忘却种种的失意,留此有用之身,干人类应做的事。知我的朋友!请你们监视我,勖勉我,督促我。
一九二二,三,十五夜起稿,廿一夜脱稿
1922年3月15~21日撰
原载1922年3月30日《民国日报·觉悟》
附注
①本篇署名:YK。
②指1919年秋应聘赴广东肇庆任教未果之事。归后,于1920年12月撰写发表了《愁城生活录》(副题为“游粤杂记之一”,参见本卷第243~257页)。《赴粤杂感》一文今佚。
①指1906年离家赴郑巷溪山学堂住读,此为杨贤江接受学校教育之始。
①指1917年秋受聘任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处。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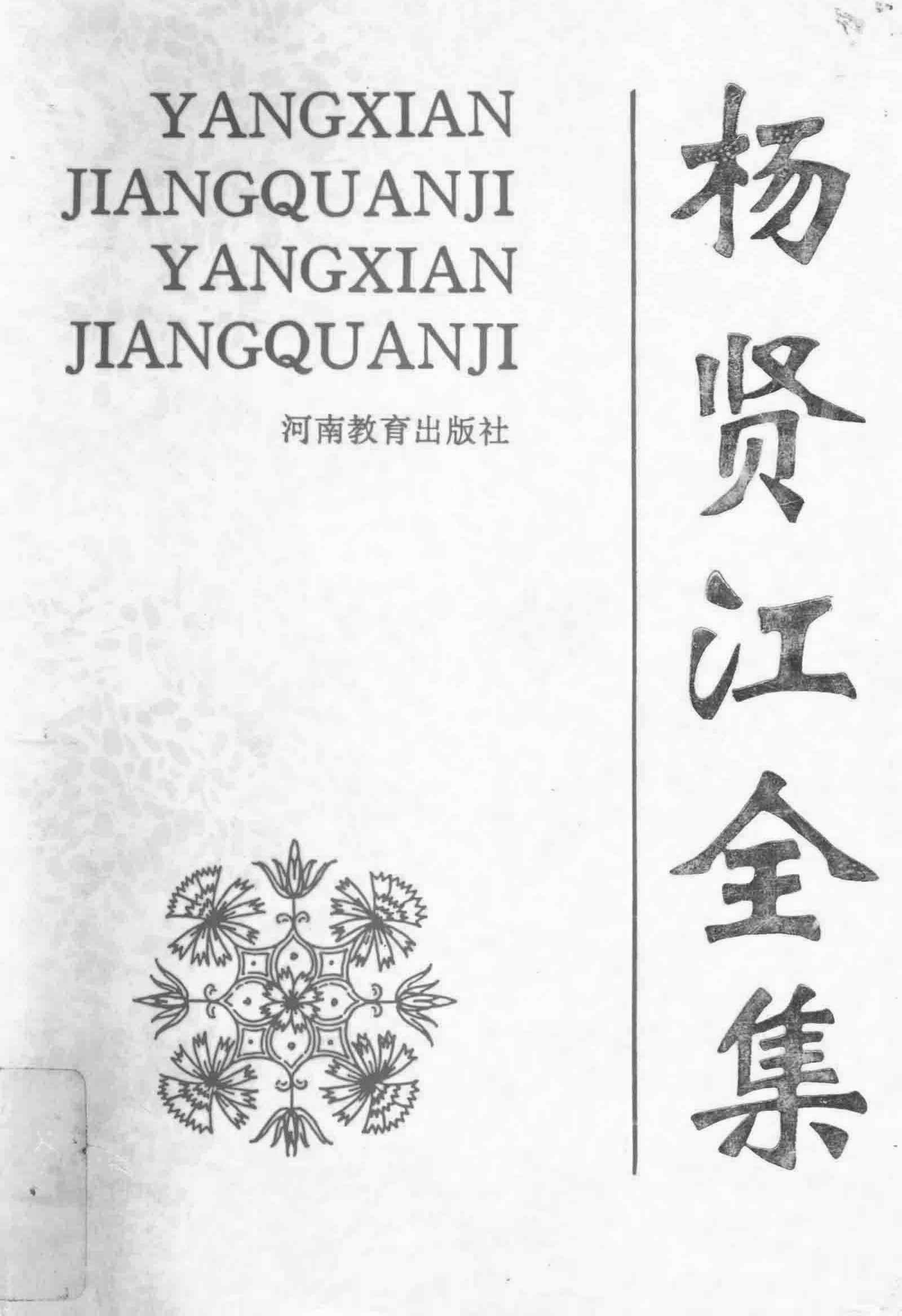
《杨贤江全集 第一卷》
出版者: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记述了杨贤江全集的编年原则的说明。全集采用“分类编年”体例,分为6卷。1~3卷为论著类;采用文论与专著混合编年方式。第一卷1913~1923年为体裁特殊的文论,包括日记、通信和答问,“论著”部分收入少量与正文内容密切相关的随文附录。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