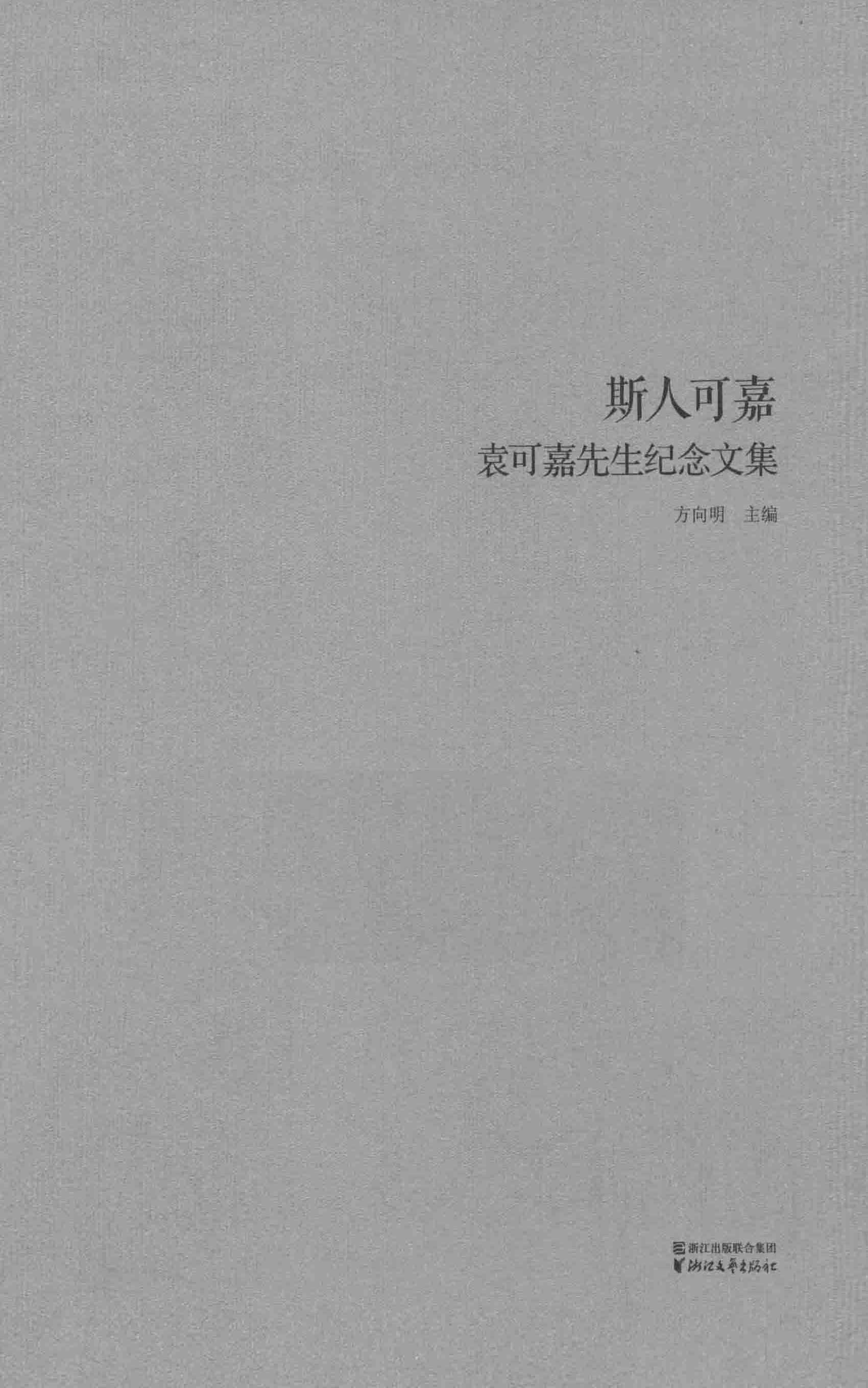内容
现代诗歌戏剧化或戏剧化倾向在西方诗学中显然有着更为悠久的传统,如波德莱尔、叶芝,尤其是在T.S.艾略特这里得到全面、综合的呈现。复调、情境、场景、细节、对话、戏剧性冲突在带有跨文体的色彩中进入诗歌写作。在中国,新诗的戏剧化是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倡导并在一部分诗人的诗歌实践中得到张扬,而这种短暂的新诗现代化的尝试与拓荒却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烟云和极端而偏狭的诗歌美学桎梏中被搁置、忽视甚至否定。而新诗戏剧化则在长时期的淡出文学史视野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中得到久违的再次出场。自这一时期起,作为“新诗戏剧化”的理论倡导者的袁可嘉先生显然在90年代以降的中国诗歌话语场中占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我们已经看到“新诗戏剧化”理论已经成了这一时期诗歌写作的圭臬甚至唯一的标杆。不可否认,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及其倡导无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在今天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纪已经走过十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具体到诗人、群体甚至整体性的时代氛围的诗歌写作中,“新诗戏剧化”作为主导性的现代诗歌的创作理念已经产生了相关的一些诗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显然并未引起诗坛和研究者的足够关注。
一
显然,新诗的戏剧化从诗歌写作的层面考量并非始自袁可嘉的倡导,作为新诗实践的一个方面,新诗戏剧化的倾向显然要更早,例如朱自清、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人就在诗歌中运用戏剧性情节、场景、对话。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新诗戏剧化》《谈戏剧主义》以及《对于诗的迷信》的系列文章中则从学理上具体阐释了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在以袁可嘉为首的新诗戏剧化的理论倡导中,“九叶”诗人进行了最先的写作实践,将戏剧性结构、戏剧性情境、戏剧性对白等融入诗歌写作当中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对于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提出,其历史背景、诗坛状貌、知识场阈的转换以及现实的针对性显然相当重要。新诗戏剧化在20世纪40年代克服和反拨了新诗“感伤”和“说教”的不良倾向,对前此的象征派、现代派强调“玄学”而忽视日常经验予以反思。
尽管袁可嘉关于新诗戏剧化的理论主张是在1946年到1948年间提出的,但实际上早在1942年的时候,袁可嘉的兴趣已经由浪漫主义转向了现代主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以及新诗现代化的倡导除了针对中国诗歌的具体现状之外,还有着对普泛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诗歌的批判与反拨。当时校园里强劲的“现代风”使得袁可嘉放弃了自己曾经钟情的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并且对中国的浪漫主义诗风开始反思。换言之,在正式提出新诗戏剧化理论之前袁可嘉更多是从个人美学趣味出发的,还并未结合当时中国诗坛的现状甚至弊端。
袁可嘉1946年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在1946年年底到1948年间提出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的主张,这显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新诗创作的实践以及相应的诗歌观念的转换密不可分。再有,袁可嘉的西南联大时期的知识背景显然对他建构新诗现代化的理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所提出的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都明显地受到了瑞恰慈、艾略特和英美新批评的启发”①。在战时的语境之下,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极端化的强调。据此,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的提出和倡导其意义非常重大。针对当时的诗歌写作的主导性弊端,袁可嘉强调当时诗歌无外乎两类,“一类是说明自己强烈的意志或信仰,希望通过诗篇有效地影响别人的意志或信仰的;另一类是表现自己某一种狂热的感情,同样希望通过诗作来感染别人的”②。然而这两类诗歌实际上本质上是一样的,即诗人的急于表达和急功近利尤其是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使得这些诗作因为艺术转换过程的缺失而成了抽象的说教和干瘪的口号,所以在袁可嘉看来新诗沾染了“说教”与“感伤”的时代病。而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尤其是新诗戏剧化的提出显然是反拨了当时的题材决定论和文学工具论,搁置了诗歌的社会和政治文化,而是强调诗歌艺术的转化和生成过程,强调诗歌的本体性和艺术品质。“批评的标准是内在的,而不依赖诗篇以外的任何因素”①,这显然与新批评的强调文学性,以文本为中心的诗学立场一致。
基于瑞恰慈把语义学方法引入新批评的理论,袁可嘉认为新诗戏剧化还要在语言的韧性和弹性中间接地表现情智。在《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诗与意义》《诗与晦涩》《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谈戏剧主义》等文章中,袁可嘉对诗歌的意象以及诗歌语言的象征功能、隐喻、反讽、悖论等修辞技巧进行了系统论述。袁可嘉强调新诗戏剧化就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强调客观对应物、想象逻辑、意象比喻、文字的弹性与韧性,强调对话性、复调性以及戏剧冲突、场景、细节和事件在诗歌中的重要性。而认为诗人作为创作主体应该从文本中退场,这在强调智性的同时就相应地批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诗歌表现上的主体性、情感性和直接性,诗歌的抒情、独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排斥。袁可嘉的这种观念与艾略特所鼓吹的“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②的“非个人化”思想同构。无可否认,无论是当年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还是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的主张都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但是我们在今天同样应该对其中的观点进行反思。是否艾略特的以文本为中心而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贬抑诗歌与社会历史、时代背景的关系就是完全正确的?是否经验诗学就一定要优于情感诗学?
二
1915年,休姆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宣布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束,而在中国工业化的语境下来考量,似乎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一个有着古老的抒情诗传统的国度已经终结,诗歌的抒情性遭到空前放逐。新诗戏剧化在诗歌中的实践也呈现出诗人的精神状态,在日常、口语、细节、对话、事件的所谓复调性的时代美学驱动面前,诗歌的戏剧化、叙事性、复调、张力、戏谑、反讽、冲突、悖论成了新诗现代化甚至新诗后现代主义的必经之途。而新诗和戏剧甚至电影的共同作战成了诗人写作的必要常识和思维模式,诗人在普遍的欣快症中迫不及待地加入到日常经验和琐屑的身边事物的旋涡之中,这使得无深度的生活仿写开始泛滥。这种大多带有口语倾向的戏剧化的写作景观显然更为符合当下读者的阅读期待和趣味。在调侃、反讽、幽默、戏剧性甚至带有色情性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现代人的白日梦和高度紧张的神经得到暂时的抚慰,力比多得到刺激与释放。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初的诗歌批评中,评论者几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叙事性作为新诗戏剧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成为了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标签和检验证明。不管在何种程度上谈论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性,这对于反拨以往诗歌写作的运动性、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写作技法的狭隘性和滥情易感而言其意义已不必多说,但是反过来当智性追求下的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和狭隘化并成为唯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无形中诗歌写作的多元化这一说法是需要重新过滤和打量的。应该意识到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看似已经相当繁复和多元,诗歌写作也是在差异和多个向度展开,诗歌的技艺也似乎达到了新诗发展以来较为乐观的时期,但是在近些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大是大非的问题,已经揭示出诗歌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自身的问题,商业、传媒、大众文化、话语权力、诗歌趣味、诗人身份都和诗歌极其含混、暖昧而又不容分说地纠缠在一起。当我们再次提到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戏剧化、叙事性并为此而津津乐道时,人们实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这种类型化写作大面积涌起的时候应该予以重估和反思。当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和戏剧化重新在诗歌的现代之途上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之后,诗歌的抒情性反而反复得到遮蔽甚至被看作诗歌的歧途。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中,诗歌的“叙事性”以及其对“抒情性”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反拨“意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诗歌区别于以往时代诗歌的重要标志和显著性成果。但是当我们已经共睹了诗歌写作的叙事性的诸多益处和“战绩”时,更多的人也因此忽视了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远非如此简单。当朦胧诗(今天诗派)在第三代诗人的呐喊声中湮没于另一种集体狂欢的时候,诗歌写作的精英性和代言身份似乎多少显得不合时宜,这在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论争中仍有显豁的重现。当大众文化和商业媒体的浪潮在更换受众的审美趣味的同时,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也沾染上不可避免的时代症候。“叙事性”作为新诗戏剧化的重要维度在20世纪90年代乃至当下的诗歌批评中成为相当含混和暖昧的诗学概念,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已经成为圭臬甚至唯一的评价诗歌的尺度,而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则被视为畏途和歧途,甚至被讥讽为弱智低能的“小儿科”的智障把戏。在当下的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叙事性是一个合宜的时髦说法和托词,甚至指认海子自杀之后中国诗歌的抒情时代就已宣告结束。实际上,回到诗歌的源头反观诗歌的本体特征,抒情诗才是其真正的底色,任何所谓的叙事性和戏剧化都要以抒情为前提,反之,诗就会走向反面成为“非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心存芥蒂和偏见,相反,合理地使用叙事性会增强诗歌的容纳能力和张力。但是,当在每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翻开各个年度诗歌选本和评论集,我们就会发现相当多的诗人在误解新诗戏剧化和叙事性的前提下滥用了这个看似屡试不爽的灵丹妙方。自90年代后期以来,诗人和批评者对诗歌的“叙事性”的理解是充满歧见的,实际上作为新诗戏剧化的重要方面,“叙事性”已不是单纯的诗歌技巧,更大程度上是在强行转换的时代语境中诗人写作观念和态度的转变。当一些诗人毫无节制并自以为“先锋”地将电影、戏剧、小说、日记、歌曲、随笔、广告掺入诗歌写作中,综合了“现实、象征、玄学”的跨文体性质的诗歌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因为“过度”而成为诗歌写作的阑尾或盲肠。基于此,当我们在看到袁可嘉先生当年倡导的“新诗戏剧化”的历史价值和当时的现实意义的同时,应该提醒在一个普泛的对诗歌写作的抒情性“不齿”的时代,必须重估“叙事性”和“抒情性”,在看到新诗戏剧化在90年代的诗歌写作意义的同时洞察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二元对立情绪的危害性。
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坛,袁可嘉和其他的“九叶”诗人从理论和实践中倡导新诗戏剧化无论是对于现实诗坛的意义,还是对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建构都是有非常重要和富有启示性意义的。而当新诗的戏剧化尤其是“叙事性”成为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口号甚至是唯一的圭臬的时候,诗人和评论者实际上已经忽略了袁可嘉当年的新诗戏剧化主张的时代意义和诗学价值。当然,不可否认袁可嘉先生的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主张很容易让人对诗歌的抒情性和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在诗歌中的张扬报以嗤之以鼻的不屑与偏颇。诗歌写作从来都是多元的,以抒情为主和以客观、间接的戏剧化为主都会生成出优异的诗歌文本,但是在90年代后期以来戏剧化显然以绝对的压倒性优势放逐和排挤了“抒情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的时期,新诗戏剧化并非是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研究的唯一“圭臬”,有时候一种理论倡导在种种时代和诗歌多重因素合力作用下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偏差性的误度和阐释,所以今天必须正确认识和重估新诗的戏剧性。
一
显然,新诗的戏剧化从诗歌写作的层面考量并非始自袁可嘉的倡导,作为新诗实践的一个方面,新诗戏剧化的倾向显然要更早,例如朱自清、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人就在诗歌中运用戏剧性情节、场景、对话。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新诗戏剧化》《谈戏剧主义》以及《对于诗的迷信》的系列文章中则从学理上具体阐释了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在以袁可嘉为首的新诗戏剧化的理论倡导中,“九叶”诗人进行了最先的写作实践,将戏剧性结构、戏剧性情境、戏剧性对白等融入诗歌写作当中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对于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提出,其历史背景、诗坛状貌、知识场阈的转换以及现实的针对性显然相当重要。新诗戏剧化在20世纪40年代克服和反拨了新诗“感伤”和“说教”的不良倾向,对前此的象征派、现代派强调“玄学”而忽视日常经验予以反思。
尽管袁可嘉关于新诗戏剧化的理论主张是在1946年到1948年间提出的,但实际上早在1942年的时候,袁可嘉的兴趣已经由浪漫主义转向了现代主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以及新诗现代化的倡导除了针对中国诗歌的具体现状之外,还有着对普泛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诗歌的批判与反拨。当时校园里强劲的“现代风”使得袁可嘉放弃了自己曾经钟情的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并且对中国的浪漫主义诗风开始反思。换言之,在正式提出新诗戏剧化理论之前袁可嘉更多是从个人美学趣味出发的,还并未结合当时中国诗坛的现状甚至弊端。
袁可嘉1946年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在1946年年底到1948年间提出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的主张,这显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新诗创作的实践以及相应的诗歌观念的转换密不可分。再有,袁可嘉的西南联大时期的知识背景显然对他建构新诗现代化的理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所提出的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艺术转化论、诗的戏剧化论都明显地受到了瑞恰慈、艾略特和英美新批评的启发”①。在战时的语境之下,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极端化的强调。据此,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的提出和倡导其意义非常重大。针对当时的诗歌写作的主导性弊端,袁可嘉强调当时诗歌无外乎两类,“一类是说明自己强烈的意志或信仰,希望通过诗篇有效地影响别人的意志或信仰的;另一类是表现自己某一种狂热的感情,同样希望通过诗作来感染别人的”②。然而这两类诗歌实际上本质上是一样的,即诗人的急于表达和急功近利尤其是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使得这些诗作因为艺术转换过程的缺失而成了抽象的说教和干瘪的口号,所以在袁可嘉看来新诗沾染了“说教”与“感伤”的时代病。而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尤其是新诗戏剧化的提出显然是反拨了当时的题材决定论和文学工具论,搁置了诗歌的社会和政治文化,而是强调诗歌艺术的转化和生成过程,强调诗歌的本体性和艺术品质。“批评的标准是内在的,而不依赖诗篇以外的任何因素”①,这显然与新批评的强调文学性,以文本为中心的诗学立场一致。
基于瑞恰慈把语义学方法引入新批评的理论,袁可嘉认为新诗戏剧化还要在语言的韧性和弹性中间接地表现情智。在《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诗与意义》《诗与晦涩》《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谈戏剧主义》等文章中,袁可嘉对诗歌的意象以及诗歌语言的象征功能、隐喻、反讽、悖论等修辞技巧进行了系统论述。袁可嘉强调新诗戏剧化就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强调客观对应物、想象逻辑、意象比喻、文字的弹性与韧性,强调对话性、复调性以及戏剧冲突、场景、细节和事件在诗歌中的重要性。而认为诗人作为创作主体应该从文本中退场,这在强调智性的同时就相应地批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诗歌表现上的主体性、情感性和直接性,诗歌的抒情、独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排斥。袁可嘉的这种观念与艾略特所鼓吹的“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②的“非个人化”思想同构。无可否认,无论是当年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还是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的主张都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但是我们在今天同样应该对其中的观点进行反思。是否艾略特的以文本为中心而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贬抑诗歌与社会历史、时代背景的关系就是完全正确的?是否经验诗学就一定要优于情感诗学?
二
1915年,休姆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宣布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束,而在中国工业化的语境下来考量,似乎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一个有着古老的抒情诗传统的国度已经终结,诗歌的抒情性遭到空前放逐。新诗戏剧化在诗歌中的实践也呈现出诗人的精神状态,在日常、口语、细节、对话、事件的所谓复调性的时代美学驱动面前,诗歌的戏剧化、叙事性、复调、张力、戏谑、反讽、冲突、悖论成了新诗现代化甚至新诗后现代主义的必经之途。而新诗和戏剧甚至电影的共同作战成了诗人写作的必要常识和思维模式,诗人在普遍的欣快症中迫不及待地加入到日常经验和琐屑的身边事物的旋涡之中,这使得无深度的生活仿写开始泛滥。这种大多带有口语倾向的戏剧化的写作景观显然更为符合当下读者的阅读期待和趣味。在调侃、反讽、幽默、戏剧性甚至带有色情性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现代人的白日梦和高度紧张的神经得到暂时的抚慰,力比多得到刺激与释放。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初的诗歌批评中,评论者几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叙事性作为新诗戏剧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成为了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标签和检验证明。不管在何种程度上谈论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性,这对于反拨以往诗歌写作的运动性、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写作技法的狭隘性和滥情易感而言其意义已不必多说,但是反过来当智性追求下的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和狭隘化并成为唯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无形中诗歌写作的多元化这一说法是需要重新过滤和打量的。应该意识到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看似已经相当繁复和多元,诗歌写作也是在差异和多个向度展开,诗歌的技艺也似乎达到了新诗发展以来较为乐观的时期,但是在近些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大是大非的问题,已经揭示出诗歌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自身的问题,商业、传媒、大众文化、话语权力、诗歌趣味、诗人身份都和诗歌极其含混、暖昧而又不容分说地纠缠在一起。当我们再次提到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戏剧化、叙事性并为此而津津乐道时,人们实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这种类型化写作大面积涌起的时候应该予以重估和反思。当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和戏剧化重新在诗歌的现代之途上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之后,诗歌的抒情性反而反复得到遮蔽甚至被看作诗歌的歧途。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中,诗歌的“叙事性”以及其对“抒情性”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反拨“意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诗歌区别于以往时代诗歌的重要标志和显著性成果。但是当我们已经共睹了诗歌写作的叙事性的诸多益处和“战绩”时,更多的人也因此忽视了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远非如此简单。当朦胧诗(今天诗派)在第三代诗人的呐喊声中湮没于另一种集体狂欢的时候,诗歌写作的精英性和代言身份似乎多少显得不合时宜,这在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论争中仍有显豁的重现。当大众文化和商业媒体的浪潮在更换受众的审美趣味的同时,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也沾染上不可避免的时代症候。“叙事性”作为新诗戏剧化的重要维度在20世纪90年代乃至当下的诗歌批评中成为相当含混和暖昧的诗学概念,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已经成为圭臬甚至唯一的评价诗歌的尺度,而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则被视为畏途和歧途,甚至被讥讽为弱智低能的“小儿科”的智障把戏。在当下的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叙事性是一个合宜的时髦说法和托词,甚至指认海子自杀之后中国诗歌的抒情时代就已宣告结束。实际上,回到诗歌的源头反观诗歌的本体特征,抒情诗才是其真正的底色,任何所谓的叙事性和戏剧化都要以抒情为前提,反之,诗就会走向反面成为“非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心存芥蒂和偏见,相反,合理地使用叙事性会增强诗歌的容纳能力和张力。但是,当在每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翻开各个年度诗歌选本和评论集,我们就会发现相当多的诗人在误解新诗戏剧化和叙事性的前提下滥用了这个看似屡试不爽的灵丹妙方。自90年代后期以来,诗人和批评者对诗歌的“叙事性”的理解是充满歧见的,实际上作为新诗戏剧化的重要方面,“叙事性”已不是单纯的诗歌技巧,更大程度上是在强行转换的时代语境中诗人写作观念和态度的转变。当一些诗人毫无节制并自以为“先锋”地将电影、戏剧、小说、日记、歌曲、随笔、广告掺入诗歌写作中,综合了“现实、象征、玄学”的跨文体性质的诗歌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因为“过度”而成为诗歌写作的阑尾或盲肠。基于此,当我们在看到袁可嘉先生当年倡导的“新诗戏剧化”的历史价值和当时的现实意义的同时,应该提醒在一个普泛的对诗歌写作的抒情性“不齿”的时代,必须重估“叙事性”和“抒情性”,在看到新诗戏剧化在90年代的诗歌写作意义的同时洞察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二元对立情绪的危害性。
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坛,袁可嘉和其他的“九叶”诗人从理论和实践中倡导新诗戏剧化无论是对于现实诗坛的意义,还是对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建构都是有非常重要和富有启示性意义的。而当新诗的戏剧化尤其是“叙事性”成为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口号甚至是唯一的圭臬的时候,诗人和评论者实际上已经忽略了袁可嘉当年的新诗戏剧化主张的时代意义和诗学价值。当然,不可否认袁可嘉先生的新诗现代化和新诗戏剧化主张很容易让人对诗歌的抒情性和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在诗歌中的张扬报以嗤之以鼻的不屑与偏颇。诗歌写作从来都是多元的,以抒情为主和以客观、间接的戏剧化为主都会生成出优异的诗歌文本,但是在90年代后期以来戏剧化显然以绝对的压倒性优势放逐和排挤了“抒情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的时期,新诗戏剧化并非是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研究的唯一“圭臬”,有时候一种理论倡导在种种时代和诗歌多重因素合力作用下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偏差性的误度和阐释,所以今天必须正确认识和重估新诗的戏剧性。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