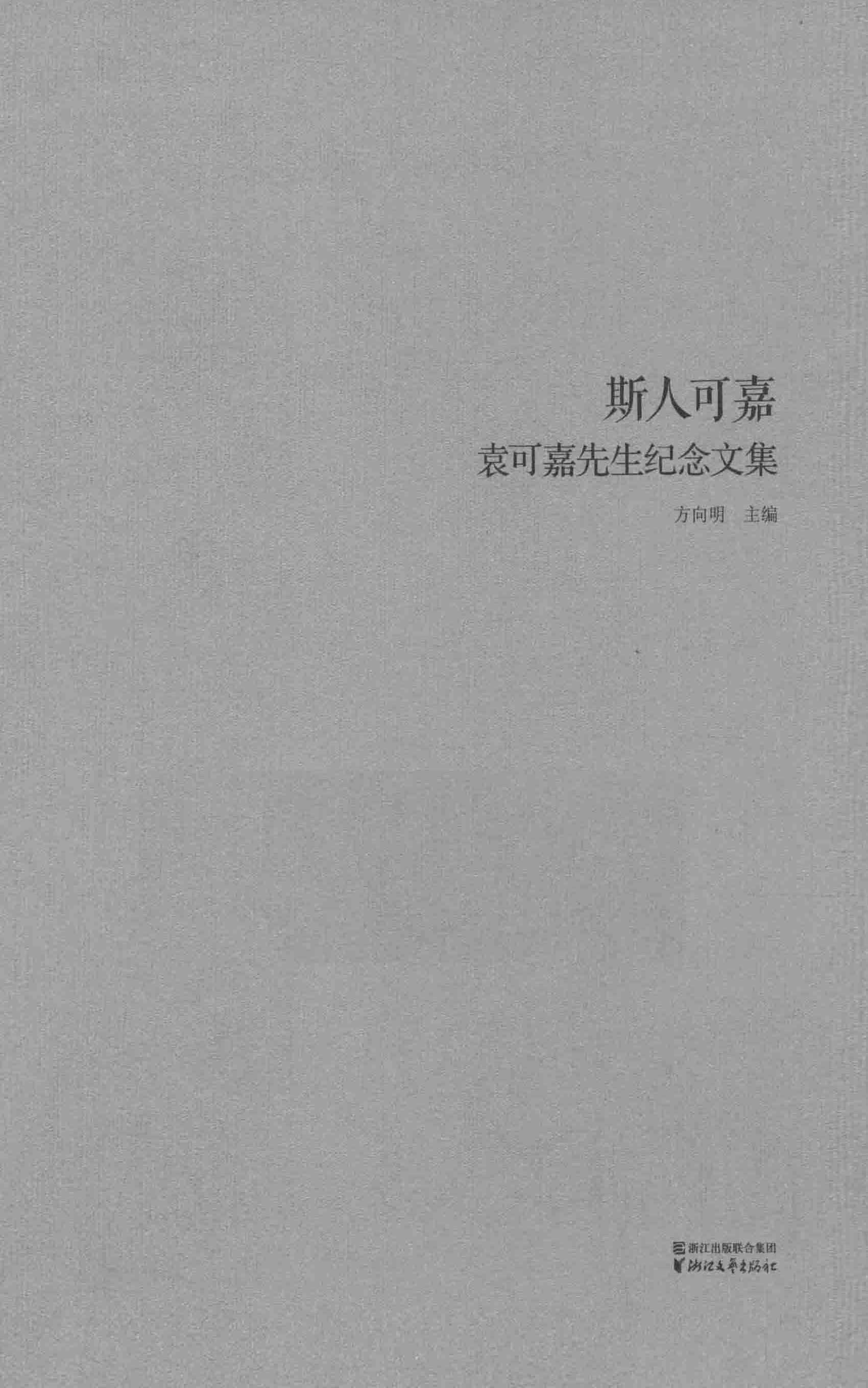永远的老袁——回忆我的忘年交
| 内容出处: | 《斯人可嘉 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 图书 |
| 唯一号: | 112320020220004251 |
| 颗粒名称: | 永远的老袁——回忆我的忘年交 |
| 分类号: | K825.6-53 |
| 页数: | 7 |
| 页码: | 120-126 |
| 摘要: | 亲爱的老袁,离我们而去已五年整,作为他的忘年交,他在生活和学术上给予我种种帮助、支持与教海,至今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怀。1960年7月,我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回国,正经历我国三年经济困难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时期,教育部为了使我们刚归国的留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组织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集中学习了好几个月,直到11月初才分配我们工作。同年11月7日,我们十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同学,相约一起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办理报到手续,我被分配在苏联文学研究组。在寿县工作了将近一年,常常在会议期间或休息日,和卞先生这些“烟民”聚在一起“吞云吐雾”和聊天。 |
| 关键词: | 回忆录 文学研究 袁可嘉 |
内容
往事悠悠。亲爱的老袁,离我们而去已五年整,作为他的忘年交,他在生活和学术上给予我种种帮助、支持与教海,至今历历在目,我永远不会忘怀。
1960年7月,我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回国,正经历我国三年经济困难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时期,教育部为了使我们刚归国的留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组织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集中学习了好几个月,直到11月初才分配我们工作。同年11月7日,我们十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同学,相约一起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办理报到手续,我被分配在苏联文学研究组。
与老袁的相识
常言说:隔行如隔山。很长时间,我同老袁虽在一个单位,只是见面点头,并无实际性交往。老袁大我十三四岁,他在西方文学研究组,虽然没有卞之琳、罗大冈和李健吾等西方文学研究组的成员著名,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已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学者。60年代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我常常读到老袁的大作。当时全国学术刊物屈指可数,可是老袁在学术刊物上,特别是在《文学评论》上一再发表文章。我刚刚走上科研岗位,还没有入门,但在学术上也不甘寂寞,不时写些东西投稿,大多数稿件都被编辑部退回,要不就是石沉大海,后来听到一个当编辑的人说:当编辑的主要时间和工作就是处理“退稿”。这一下子使我意识到,发表文章并非易事。
我同老袁的老师和领导(西方文学研究组组长)——卞先生相识,要比老袁早许多。那时无论是在文学研究所还是在后来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时间并不是搞科研,而是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于我们年轻人,还有一项必修课,即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劳动锻炼。1964年,我是在安徽寿县那次“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四清运动”中,同卞先生相遇的。在寿县工作了将近一年,常常在会议期间或休息日,和卞先生这些“烟民”聚在一起“吞云吐雾”和聊天。卞先生是二级研究员,有牡丹牌这样的高级香烟供应,不时也给我们年轻人一支分享。有一次,卞先生说:你们不知道,我常常收到来信或来电,称我老卡同志或卡之琳先生。我听后说:好啊,老卡比老卞好听。现在想起来,在进行“阶级斗争”的紧张日子里,还能在抽香烟的片刻,不分老少,不分级别,漫无边际地聊天和开玩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老袁不抽烟,没有机会在这种场合相遇。今天回忆起这一幕,不禁感慨系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生活了数十年,对包括老袁在内的一批驰名海内外的老专家老学者及其历史贡献,当年并不真正知道,而是日后逐渐地认识和了解到的。
同老袁的相识,与卞先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的那种相识,则完全不同。1970年5月7日,外国文学所响应中央号召,在军宣队的领导下,奔赴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我们的干校,和全国其他干校有所不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1971年3月,干校转移到河南明港一个部队旧军营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便成为它唯一任务。我那时就是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审查的。
1970年的一个晚上,息县干校广场放电影,我和老袁刚好挨着坐在一起,正片开始放映前,加放新闻片。当时老袁突然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看,那个给埃塞俄比亚皇帝献花的女孩是我的大女儿。”我说:“她好漂亮好聪明啊!在哪个学校学习?”老袁答:“北京一一九中学。”我接着说:“老袁,你真是好福气!”这是我和老袁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的对话和交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的一天,老袁一家三口从美国回北京办事,并到外国文学研究所来,也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老袁大女儿晓敏一走进门便叫吴叔叔,我激动地对她说:“我很早就见过你了,只不过是在二十年前的银幕上。”下一次和老袁一家相逢,则是在美国纽约了。1998年11月,我们夫妇去美国芝加哥探亲,同年12月前往纽约访问一周,住在外文所理论室过去的同事王齐建家,他当时在纽约大学当教授。我多次到距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老袁家做客。老袁一家每次都是热情接待,他已经请我们吃过一次中餐,后来老袁两个可爱的女儿又以自己名义做东,请我们在纽约中心公园对面一家西餐馆共进晚餐。对于姐妹俩出自内心的款待,我们盛情难却。
在纽约五光十色的夜晚,我们一边走一边聊。晓敏谈起她那非同寻常的赴美求学之路,如何艰难地离别北京某学院,又如何艰难地进入美国大学……她所碰到的问题、挑战和困难,是我难以想象的。我听后对她说:“你年纪轻轻,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经历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艰辛,真是命运多舛,幸好都挺过来了,很不简单。你说的像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多层次多情节的长篇小说,如果有机会不妨写出来。”
在干校同老袁的第二次交流,是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所里一些年纪大的老同志开始回北京探亲,老袁也在其中。记得老袁探亲回明港的那一天,吃过晚饭后,春光无限好,大家三三两两地到山上林间散步去了,我们十几个人住的部队大宿舍,只留下我和老袁两个还没有走。老袁说:“这次从北京带来一些点心,你好久没有吃到北京点心了,多吃点。”我吃了几块,道了声谢谢,彼此都没有说别的话。那是我的困难时刻,一切尽在不言中。1972年7月31日,我们告别明港,结束河南干校生活,返回北京。
“时间会治理一切”。1974年,我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案”得到平反。此后,我同老袁的对话交流主要在学术方面。
与老袁的学术交流
在外国文学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中,有不少人既写诗又译诗、评诗,而且每个方面均做得十分出色,例如老一辈中的冯至、卞之琳、罗大冈等,而袁可嘉则是那时中年一辈的佼佼者,仿佛是外国文学所的学术传统和接力棒之一。
老袁在诗歌领域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他既是我国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家和翻译家,也是我国现代派文学的创作者和欧美现代派文论的专门研究家。
我直接评论老袁文学研究的文字很少,唯一的一次是我执笔撰写的《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五十年》(《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第534—56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文集的缘起是,1998年7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五十年,我院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忍之为主编的课题组,并规定每个一级学科均须有五十年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文章。之后,我在所里如法炮制,成立了由我担任组长的课题组,来完成这一任务。由于规定的字数有限,文章不可能很长,因此没有把编辑翻译工作包括在其中。这同各研究所的十五篇文章的体例一致。
外国文学研究课题组的文章共二十一页,涉及十几个外国文学二级学科半个世纪的研究状况和历程。我在1949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里,把英美文学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肯定”的,文章写道:“如范存忠的《论拜伦与雪莱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袁可嘉的《谈雪莱的〈西风颂〉》等,他们一致赞扬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诗人雪莱,特别是他作为‘天才的预言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说,英国宪章派文学,特别是它的诗歌日益引起重视,如袁可嘉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曲战歌》。同时,对袁可嘉关于英国诗人彭斯的评论,则肯定了他注重诗人的政治性,同时指出其不足之处在于“较少触及和研究诗中的宗教思想和象征主义内容”(《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第5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我们在文章的第二类“否定”中,主要是谈论老袁在60年代对待现代派文学的否定态度。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叙述。此外,课题组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期(1977—1999)”中写道:“这一时期对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思潮和流派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且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出现了一大批著述。”其中就列举到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一书。
在老袁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同现代主义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可是,众所周知,现代主义文学或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我国的遭遇和命运,十分复杂,跌宕起伏,两头较热,而中期阶段被批判,走了一个“之”字,即从二三十年代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我国持续翻译传播,并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主义创作,例如李金发和施蛰存等的作品,老袁也于40年代发表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诸如《沉钟》等,并成为著名的“九叶派”诗人之一。但从这个阶段我国文学发展的总体状况看,现代派文学并非主要流派。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我国文艺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文论,持一种完全格格不入的批判态度,往往把现代主义文学同颓废派相提并论,似乎两者是同义词。这不仅在中国和苏联是如此,而且在西方的左翼文学中也是如此。事情的转变发生在1963年。这一年,法国共产党文论家加罗第的著名代表作《论无边现实主义》发表,它明确反对把现代文艺大师卡夫卡和毕加索的创作列入颓废派,认为它们同西方现实息息相关。这引起了全球文艺界的巨大反响,而其“无边现实主义”的定义却受到苏联学者的质疑。但不管怎么样,双方均认为文论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和发展的。这是世界文学领域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正是在60年代中期前这种国际的大气候和我国的大环境的影响下,老袁发表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作家出版社,1961)等著述,在今天看来,不可能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地评论现代派文学,相反,他认为英美“新批评”是反动的文化;艾略特是美帝国主义御用文人等。显然,这在当时是不难理解和难以避免的。斗转星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随着世界文论的变化和发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派再次成为我国20世纪一次真正的热潮。在这种新形势下,老袁轻车熟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40年代初期就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了……新时期以来又重理旧业。”此时,老袁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见地和分量的著述,诸如《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和《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以及他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四位同事共同编选的两卷本《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他和外国文学研究所两位同事编选的四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正是这些著作和编选奠定了老袁改革开放文学新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之所以做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三个阶段的考察,乃是因为老袁均以自己的著述参与了其中。现在就让我们返回90年代初期历史之“现场”。老袁在发表了一系列现代主义文学的新著之后,在一些座谈会和研讨会上,我听到一些同事和朋友的意见,特别是文学研究所一位老袁很熟悉的老同志说的话:如果老袁在现代派文学问题上不作反思,他不买他的新书。这种意见的合理性,无可厚非。但老袁并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否则与他一贯的人品和学品相悖。其实,他在自己的书中,已做了反思和自我批评,只是这些同志和朋友未能看到。1994年,我有幸参加国家图书出版评审委员会外国文学评审会议,会议于一天上午举行,我因为有事,是下午去参加的。我翻了很多书籍,怎么也找不到老袁的那本现代派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有人说,上午大家已经把它摆到另一类去了。我心里明白个中原因。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把老袁的这本书翻到第九十七页,给与会者读了他那段反思文字:“进入60年代,由于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需要,在大批判的旗号下,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派进行了抨击。我在60年代初发表的《托·史·艾略特——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新批评派述评》和《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严厉批判其思想意识,进而抹煞其艺术成就,显然是做得过分了……这在当时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应引为前车之鉴。”又说:“卞之琳的《布莱希特的印象记》是这时期介绍现代派的少数可读的文字之一。”我认为,这无异于说,老袁自己那时关于现代派的文章是不可读的。我在读完老袁这段话后,接着发表意见说:既然袁先生做了公开的自我反思和批评,认识到了过去的不对,表示这是前车之鉴。对于老袁的这种态度,不仅应该欢迎和支持,而且应加以鼓励。为了倡导学术研究上有过能改的好学风,我建议给他的书评奖。经过大家的认真讨论,这本书最后被评为1994年国家图书奖外国文学一等奖。我以为自己仅仅做了应该做的。
这的确是一部实事求是评价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好书,我们知道当时在我国的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中,几乎它的每一点都引起争论和不同意见,在国外也不例外。现代派文学是一个众说纷纭、十分复杂的问题。老袁在书中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和局限,从四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入系统的阐述,而且是那样的实事求是和条分缕析,在国内是我第一次见到,它也的确在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至于老袁对20世纪所谓的科学主义理论即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的评论“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更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既十分到位又十分精到。其理论思维和理论分析之准确,令我十分佩服,并常常运用他的这一至理名言。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1993年底或1994年初,文学研究所的钱中文和我准备召开“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成立会议”,我们两人商量聘请儿个学会顾问,最后决定四个学者为顾问,即季羡林、汝信、蒋孔阳、袁可嘉。几年后,不知是在北京还是在纽约,老袁的大女儿同我聊天,并开玩笑地说:你给我爸的官最大。一时间,我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想了想,大概是我们学会聘请老袁担任顾问之事。她一笑了之。我说,你爸的理论成就,特别是西方文论方面的成就很大,当之无愧,值得我和大家好好学习。其实,1991年或1992年春节,我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不久,便去老袁家拜年,并请他谈谈在目前的全球形势下,外国文学所应该如何搞科研,近期应做哪些项目等等。老袁热情地发表了很多精辟意见。
同老袁一起参加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不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次去天津外国语学院参加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的国际研讨会,那时中国刚刚出版中文译本。我一般不参加俄文作品以外的其他国家具体作品的研讨会。这次邀请我去,可能是我在《译林》上发表了《〈尤利西斯〉在苏联的历史命运》一文。研讨会上,一位美国学者在发言中没有按传统意见说这部作品是意识流小说,却认为它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新观点。当我感到困惑时,老袁在发言中认为,小说中虽然有很多细节描述,甚至还有自然主义的东西,但从总体上看,它属于意识流作品。我觉得老袁说得有道理。在老袁发言后,我进一步向他请教:随着时代和艺术的变化,据我所知,今天的西方有人反而认为它是现实主义小说。老袁接着表示: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理解,才需要人们开会讨论,如果看法和见解一致,就不需要开这样的会了。看得出来,老袁在学术探讨上持一种开放、学习借鉴、讨论争鸣的态度,而且一贯如此,这正如他在40年代的诗中所云:“收容八方的野风。”
总之,老袁于我,是永远的,永远的。
1960年7月,我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回国,正经历我国三年经济困难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时期,教育部为了使我们刚归国的留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组织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集中学习了好几个月,直到11月初才分配我们工作。同年11月7日,我们十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同学,相约一起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办理报到手续,我被分配在苏联文学研究组。
与老袁的相识
常言说:隔行如隔山。很长时间,我同老袁虽在一个单位,只是见面点头,并无实际性交往。老袁大我十三四岁,他在西方文学研究组,虽然没有卞之琳、罗大冈和李健吾等西方文学研究组的成员著名,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已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学者。60年代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我常常读到老袁的大作。当时全国学术刊物屈指可数,可是老袁在学术刊物上,特别是在《文学评论》上一再发表文章。我刚刚走上科研岗位,还没有入门,但在学术上也不甘寂寞,不时写些东西投稿,大多数稿件都被编辑部退回,要不就是石沉大海,后来听到一个当编辑的人说:当编辑的主要时间和工作就是处理“退稿”。这一下子使我意识到,发表文章并非易事。
我同老袁的老师和领导(西方文学研究组组长)——卞先生相识,要比老袁早许多。那时无论是在文学研究所还是在后来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时间并不是搞科研,而是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于我们年轻人,还有一项必修课,即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劳动锻炼。1964年,我是在安徽寿县那次“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四清运动”中,同卞先生相遇的。在寿县工作了将近一年,常常在会议期间或休息日,和卞先生这些“烟民”聚在一起“吞云吐雾”和聊天。卞先生是二级研究员,有牡丹牌这样的高级香烟供应,不时也给我们年轻人一支分享。有一次,卞先生说:你们不知道,我常常收到来信或来电,称我老卡同志或卡之琳先生。我听后说:好啊,老卡比老卞好听。现在想起来,在进行“阶级斗争”的紧张日子里,还能在抽香烟的片刻,不分老少,不分级别,漫无边际地聊天和开玩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老袁不抽烟,没有机会在这种场合相遇。今天回忆起这一幕,不禁感慨系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生活了数十年,对包括老袁在内的一批驰名海内外的老专家老学者及其历史贡献,当年并不真正知道,而是日后逐渐地认识和了解到的。
同老袁的相识,与卞先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的那种相识,则完全不同。1970年5月7日,外国文学所响应中央号召,在军宣队的领导下,奔赴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我们的干校,和全国其他干校有所不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1971年3月,干校转移到河南明港一个部队旧军营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便成为它唯一任务。我那时就是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审查的。
1970年的一个晚上,息县干校广场放电影,我和老袁刚好挨着坐在一起,正片开始放映前,加放新闻片。当时老袁突然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看,那个给埃塞俄比亚皇帝献花的女孩是我的大女儿。”我说:“她好漂亮好聪明啊!在哪个学校学习?”老袁答:“北京一一九中学。”我接着说:“老袁,你真是好福气!”这是我和老袁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的对话和交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的一天,老袁一家三口从美国回北京办事,并到外国文学研究所来,也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老袁大女儿晓敏一走进门便叫吴叔叔,我激动地对她说:“我很早就见过你了,只不过是在二十年前的银幕上。”下一次和老袁一家相逢,则是在美国纽约了。1998年11月,我们夫妇去美国芝加哥探亲,同年12月前往纽约访问一周,住在外文所理论室过去的同事王齐建家,他当时在纽约大学当教授。我多次到距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老袁家做客。老袁一家每次都是热情接待,他已经请我们吃过一次中餐,后来老袁两个可爱的女儿又以自己名义做东,请我们在纽约中心公园对面一家西餐馆共进晚餐。对于姐妹俩出自内心的款待,我们盛情难却。
在纽约五光十色的夜晚,我们一边走一边聊。晓敏谈起她那非同寻常的赴美求学之路,如何艰难地离别北京某学院,又如何艰难地进入美国大学……她所碰到的问题、挑战和困难,是我难以想象的。我听后对她说:“你年纪轻轻,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经历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艰辛,真是命运多舛,幸好都挺过来了,很不简单。你说的像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多层次多情节的长篇小说,如果有机会不妨写出来。”
在干校同老袁的第二次交流,是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所里一些年纪大的老同志开始回北京探亲,老袁也在其中。记得老袁探亲回明港的那一天,吃过晚饭后,春光无限好,大家三三两两地到山上林间散步去了,我们十几个人住的部队大宿舍,只留下我和老袁两个还没有走。老袁说:“这次从北京带来一些点心,你好久没有吃到北京点心了,多吃点。”我吃了几块,道了声谢谢,彼此都没有说别的话。那是我的困难时刻,一切尽在不言中。1972年7月31日,我们告别明港,结束河南干校生活,返回北京。
“时间会治理一切”。1974年,我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案”得到平反。此后,我同老袁的对话交流主要在学术方面。
与老袁的学术交流
在外国文学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中,有不少人既写诗又译诗、评诗,而且每个方面均做得十分出色,例如老一辈中的冯至、卞之琳、罗大冈等,而袁可嘉则是那时中年一辈的佼佼者,仿佛是外国文学所的学术传统和接力棒之一。
老袁在诗歌领域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他既是我国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家和翻译家,也是我国现代派文学的创作者和欧美现代派文论的专门研究家。
我直接评论老袁文学研究的文字很少,唯一的一次是我执笔撰写的《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五十年》(《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第534—56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文集的缘起是,1998年7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五十年,我院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忍之为主编的课题组,并规定每个一级学科均须有五十年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文章。之后,我在所里如法炮制,成立了由我担任组长的课题组,来完成这一任务。由于规定的字数有限,文章不可能很长,因此没有把编辑翻译工作包括在其中。这同各研究所的十五篇文章的体例一致。
外国文学研究课题组的文章共二十一页,涉及十几个外国文学二级学科半个世纪的研究状况和历程。我在1949年至1965年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里,把英美文学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肯定”的,文章写道:“如范存忠的《论拜伦与雪莱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袁可嘉的《谈雪莱的〈西风颂〉》等,他们一致赞扬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诗人雪莱,特别是他作为‘天才的预言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说,英国宪章派文学,特别是它的诗歌日益引起重视,如袁可嘉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曲战歌》。同时,对袁可嘉关于英国诗人彭斯的评论,则肯定了他注重诗人的政治性,同时指出其不足之处在于“较少触及和研究诗中的宗教思想和象征主义内容”(《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第5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我们在文章的第二类“否定”中,主要是谈论老袁在60年代对待现代派文学的否定态度。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叙述。此外,课题组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期(1977—1999)”中写道:“这一时期对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思潮和流派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并且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出现了一大批著述。”其中就列举到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一书。
在老袁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同现代主义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可是,众所周知,现代主义文学或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我国的遭遇和命运,十分复杂,跌宕起伏,两头较热,而中期阶段被批判,走了一个“之”字,即从二三十年代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我国持续翻译传播,并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主义创作,例如李金发和施蛰存等的作品,老袁也于40年代发表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诸如《沉钟》等,并成为著名的“九叶派”诗人之一。但从这个阶段我国文学发展的总体状况看,现代派文学并非主要流派。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我国文艺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文论,持一种完全格格不入的批判态度,往往把现代主义文学同颓废派相提并论,似乎两者是同义词。这不仅在中国和苏联是如此,而且在西方的左翼文学中也是如此。事情的转变发生在1963年。这一年,法国共产党文论家加罗第的著名代表作《论无边现实主义》发表,它明确反对把现代文艺大师卡夫卡和毕加索的创作列入颓废派,认为它们同西方现实息息相关。这引起了全球文艺界的巨大反响,而其“无边现实主义”的定义却受到苏联学者的质疑。但不管怎么样,双方均认为文论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和发展的。这是世界文学领域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正是在60年代中期前这种国际的大气候和我国的大环境的影响下,老袁发表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作家出版社,1961)等著述,在今天看来,不可能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地评论现代派文学,相反,他认为英美“新批评”是反动的文化;艾略特是美帝国主义御用文人等。显然,这在当时是不难理解和难以避免的。斗转星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随着世界文论的变化和发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派再次成为我国20世纪一次真正的热潮。在这种新形势下,老袁轻车熟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40年代初期就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了……新时期以来又重理旧业。”此时,老袁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见地和分量的著述,诸如《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和《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以及他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四位同事共同编选的两卷本《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他和外国文学研究所两位同事编选的四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正是这些著作和编选奠定了老袁改革开放文学新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之所以做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三个阶段的考察,乃是因为老袁均以自己的著述参与了其中。现在就让我们返回90年代初期历史之“现场”。老袁在发表了一系列现代主义文学的新著之后,在一些座谈会和研讨会上,我听到一些同事和朋友的意见,特别是文学研究所一位老袁很熟悉的老同志说的话:如果老袁在现代派文学问题上不作反思,他不买他的新书。这种意见的合理性,无可厚非。但老袁并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否则与他一贯的人品和学品相悖。其实,他在自己的书中,已做了反思和自我批评,只是这些同志和朋友未能看到。1994年,我有幸参加国家图书出版评审委员会外国文学评审会议,会议于一天上午举行,我因为有事,是下午去参加的。我翻了很多书籍,怎么也找不到老袁的那本现代派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有人说,上午大家已经把它摆到另一类去了。我心里明白个中原因。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把老袁的这本书翻到第九十七页,给与会者读了他那段反思文字:“进入60年代,由于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需要,在大批判的旗号下,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派进行了抨击。我在60年代初发表的《托·史·艾略特——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新批评派述评》和《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严厉批判其思想意识,进而抹煞其艺术成就,显然是做得过分了……这在当时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应引为前车之鉴。”又说:“卞之琳的《布莱希特的印象记》是这时期介绍现代派的少数可读的文字之一。”我认为,这无异于说,老袁自己那时关于现代派的文章是不可读的。我在读完老袁这段话后,接着发表意见说:既然袁先生做了公开的自我反思和批评,认识到了过去的不对,表示这是前车之鉴。对于老袁的这种态度,不仅应该欢迎和支持,而且应加以鼓励。为了倡导学术研究上有过能改的好学风,我建议给他的书评奖。经过大家的认真讨论,这本书最后被评为1994年国家图书奖外国文学一等奖。我以为自己仅仅做了应该做的。
这的确是一部实事求是评价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好书,我们知道当时在我国的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中,几乎它的每一点都引起争论和不同意见,在国外也不例外。现代派文学是一个众说纷纭、十分复杂的问题。老袁在书中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和局限,从四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入系统的阐述,而且是那样的实事求是和条分缕析,在国内是我第一次见到,它也的确在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至于老袁对20世纪所谓的科学主义理论即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的评论“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更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既十分到位又十分精到。其理论思维和理论分析之准确,令我十分佩服,并常常运用他的这一至理名言。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1993年底或1994年初,文学研究所的钱中文和我准备召开“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成立会议”,我们两人商量聘请儿个学会顾问,最后决定四个学者为顾问,即季羡林、汝信、蒋孔阳、袁可嘉。几年后,不知是在北京还是在纽约,老袁的大女儿同我聊天,并开玩笑地说:你给我爸的官最大。一时间,我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想了想,大概是我们学会聘请老袁担任顾问之事。她一笑了之。我说,你爸的理论成就,特别是西方文论方面的成就很大,当之无愧,值得我和大家好好学习。其实,1991年或1992年春节,我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不久,便去老袁家拜年,并请他谈谈在目前的全球形势下,外国文学所应该如何搞科研,近期应做哪些项目等等。老袁热情地发表了很多精辟意见。
同老袁一起参加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不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次去天津外国语学院参加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的国际研讨会,那时中国刚刚出版中文译本。我一般不参加俄文作品以外的其他国家具体作品的研讨会。这次邀请我去,可能是我在《译林》上发表了《〈尤利西斯〉在苏联的历史命运》一文。研讨会上,一位美国学者在发言中没有按传统意见说这部作品是意识流小说,却认为它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新观点。当我感到困惑时,老袁在发言中认为,小说中虽然有很多细节描述,甚至还有自然主义的东西,但从总体上看,它属于意识流作品。我觉得老袁说得有道理。在老袁发言后,我进一步向他请教:随着时代和艺术的变化,据我所知,今天的西方有人反而认为它是现实主义小说。老袁接着表示: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理解,才需要人们开会讨论,如果看法和见解一致,就不需要开这样的会了。看得出来,老袁在学术探讨上持一种开放、学习借鉴、讨论争鸣的态度,而且一贯如此,这正如他在40年代的诗中所云:“收容八方的野风。”
总之,老袁于我,是永远的,永远的。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