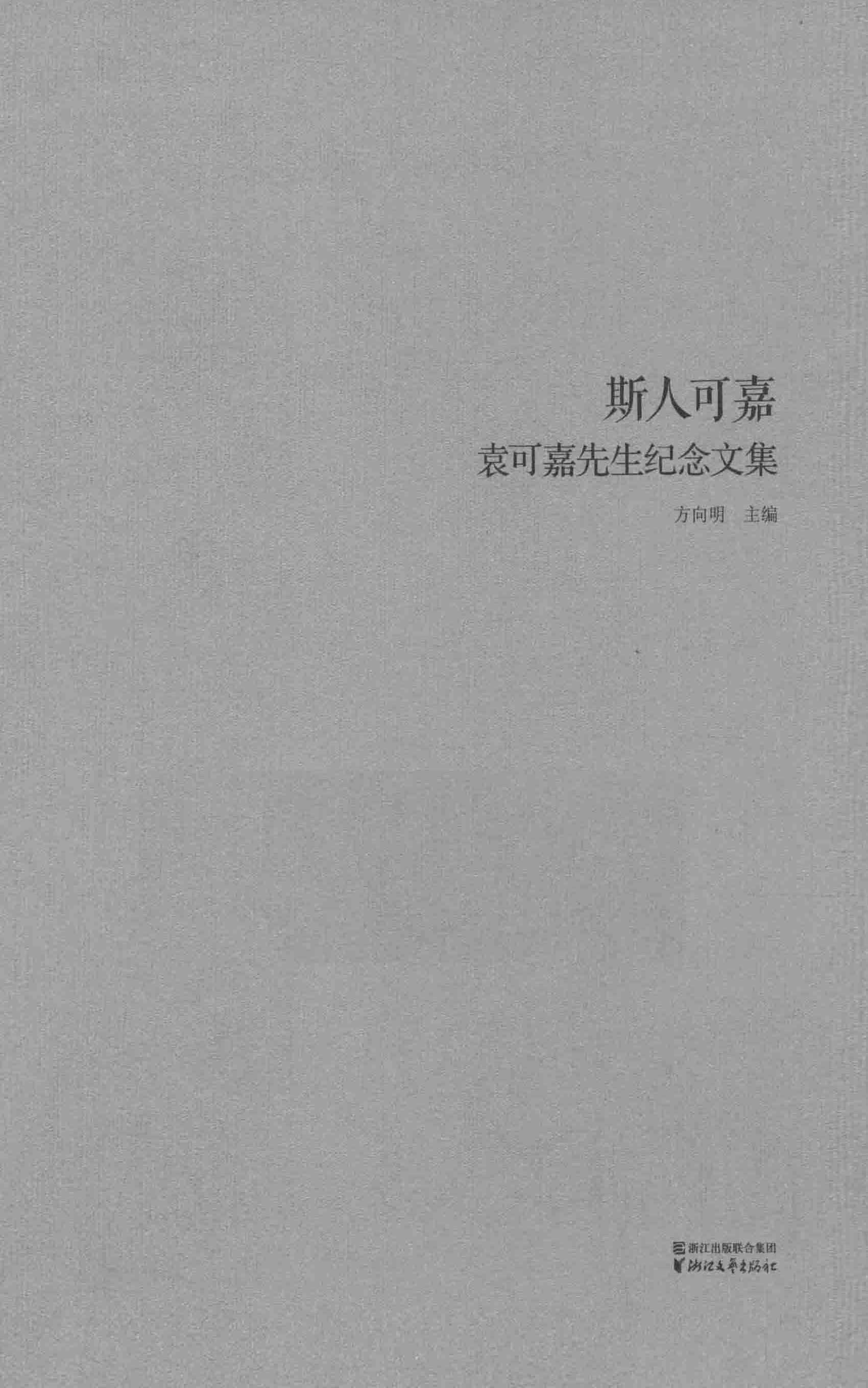盗火者和播火者袁可嘉
| 内容出处: | 《斯人可嘉 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 图书 |
| 唯一号: | 112320020220004239 |
| 颗粒名称: | 盗火者和播火者袁可嘉 |
| 分类号: | K825.6-53 |
| 页数: | 8 |
| 页码: | 050-057 |
| 摘要: | 在今天,谈起“文革”后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引进、介绍、研究和发展,您绕不开一个在这个领域里贡献卓著的学者,他就是袁可嘉。袁可嘉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但他对中国当代文化史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其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介。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文学欣赏习惯是喜欢有故事喜欢情节甚至喜欢大团圆结局的。这种欣赏模式和美学风范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态度和文艺趣味。在中国“文革”以前甚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读惯了西方19世纪小说、看惯了宏大叙事和完整史诗般现实主义描述的读者非常不喜欢西方现代派文学。也就是这时候,我幸运地遭遇了袁可嘉。而他,也无私地将这把钥匙递给了一个 |
| 关键词: | 现代派 文学研究 袁可嘉 |
内容
一
在今天,谈起“文革”后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引进、介绍、研究和发展,您绕不开一个在这个领域里贡献卓著的学者,他就是袁可嘉。
袁可嘉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但他对中国当代文化史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其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介。
袁可嘉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关心西方现代派文学并大量地研究、介绍和引入它们,从现代派诗歌研究的滥觞发端,一直到其后各种流派和各家见解的推介,可以说在这方面竖起了大纛,他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在大陆的执牛耳者。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入在中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介绍和引入过程中始终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风风雨雨。这些阻力中有的是美学的原因暨文学学科内部的争议和理解问题,但更多的却是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羁绊。因此,在那段岁月里,玩现代派文学无异于玩火。它充满了惊异、危险和奇幻甚至厄运,而袁可嘉就是儿个最早敢于玩火的人之一;他乐此不疲,居然玩到了最后。
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文学欣赏习惯是喜欢有故事喜欢情节甚至喜欢大团圆结局的。这种欣赏模式和美学风范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态度和文艺趣味。在中国“文革”以前甚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读惯了西方19世纪小说、看惯了宏大叙事和完整史诗般现实主义描述的读者非常不喜欢西方现代派文学。
可以想见,耽溺于巴尔扎克、热爱莫泊桑和梅里美小说的读者很难读懂卡夫卡,更不易喜欢加缪、贝克特那种既缺少情节又不注重读者喜欢的细节描写,而靠主观的心灵倾诉或者充满了苦难和晦涩的象征寓意之类的小说。你很难想象平日里享受读《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或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甚或《牛虻》的人能够喜欢或欣赏《荒原》《尤利西斯》《城堡》《等待戈多》这类让人读后常常感到郁闷、一头雾水而不得要领的作品。特别是现代派文学表现的那种心理折射的鸡零狗碎、个人化、潜意识及其在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上的那种刻意追求的阴郁、隐喻、晦涩和不合逻辑,处处都给人以尖利、嘈杂、无理、壅塞、硌硬而不舒服的阅读体验。
读者对这类表达不适应,岂不知这些却正是现代派作家和艺术家刻意的追求!他们正是用这种不和谐、凌乱、有违章法和反逻辑的手段制造一种新的美学范式。
现代派之所以深刻,是它的主观意识、反社会性和反传统性;它表现手法的荒诞,影射着人生的荒诞——人生本身就未可知,人生本身就不圆满。既然人生不像一个故事更不像一首史诗,我们为什么又刻意造作地把它粉饰或表现得像牧歌那样呢?现代派艺术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真实。如果荒诞成了我们生命或者是我们的宿命本身,又为什么不能把这种荒诞用文学手段表现出来呢?惯于长夜过春时,长夜的颜色就是春天。这种美学新理念,我认为,是袁可嘉先生给我们揭示出来的。这可以被看作是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切入点。
有什么样的读者就造就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观众就培养什么样的演员。正如看惯了达·芬奇、拉斐尔和列宾、苏里柯夫的欣赏者很难适应毕加索、达利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画作;同样,西方现代派的音乐也跟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外古典音乐大相径庭。艺术欣赏的模式和现代派的矛盾同时发生在中外艺术的几乎每个领域,这是现代主义文艺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它需要突围,它呼唤一个突破点。
除了民族的欣赏趣味和习惯外,另一个理解西方现代派的阻力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因素。
20世纪中叶,不知从何时起,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特别是主流思想趣味范畴兴起了一种反现代派的观念。那时的主流思想都认为西方的现代派是反理性的、颓废的、阴郁的和反社会的。这种认知也许基于对现代派艺术美学上的体验,也许是基于对现代派思想所表达出的那种混乱、混沌和迷茫躁动情绪的一种反动。总而言之,这种结合了意识形态、政治好恶以及美学批判的庙堂观念却成了当时的一种正宗的论断。要想给西方的现代主义翻案甚至想正常地、客观地介绍一下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理念,是需要一种非凡的勇气的。袁可嘉就是这样敢于反潮流、逆主流思想与钦定美学趣味而动的一个人。
二
我们不禁要问,袁可嘉为什么?他出于什么目的要介绍、推荐和身体力行地为现代主义文艺在中国的推广高歌呐喊呢?
这些都跟他的美学理念和其个人人生阅历有着不可剥离的内在关联。
袁可嘉是个诗人。他早年的第一个文学情人是诗,这个缪斯启迪了他的诗情,让他一生不能忘情于斯。诗的训练使他敏感和耽溺于体悟,我想,这是他喜欢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徘徊甚至不谙世事、迷失归途的一个原因。诗神引导他,让他变成了一个不合时俗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候,他是在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
袁可嘉早年赶上了中国大灾难的年代,疲于逃命,耽于奔波,但是在战火和灾难中他仍然看着天边草地上的小花,憧憬着诗。他是以一个诗人的姿态走上文坛的。其后他一生命运坎坷,从诗到翻译、再到理论探索,最后归于体悟和天凉好个秋,一生中深悟人生荒诞。这种生命的契合,跟西方现代派表达的主题有一种天然的共鸣,西方现代派文艺产生的土壤其实就是他思考生命的土壤或者说是他一生阅历的原点。
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钟情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谜底之一。
笔者在读了袁可嘉的书多年以后,在纽约曾听到袁可嘉儿十年前的朋友夏志清先生提起他跟袁可嘉在北大红楼时期的友谊、往还以及袁可嘉的文学个性,印证了他们在北大任教的青涩岁月里袁可嘉的某些心路历程契合了上述推断。
可是,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学跟西方的现代文学却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夏志清曾经谈起,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不论在理念、表现手法还是主题等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文学传统是“五四”以来的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主题,其表现手法大多是遵循西方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传统揭露现实的丑恶并唤醒民众,它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文学更像是西方的19世纪古典文学,它的集中表现是批判现实主义,更要紧的任务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再现和解释苦难。而西方的现代文学则与此大相径庭:由于西方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化内容跟中国不同,西方的现代文学的使命更在于表现人性异化,人的潜意识,人生荒诞,人与社会现实,人与科技、制度、机器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对“五四”后处于民族生死存亡危机面前的中国文坛来说是有些超前的“富贵病”,因之对这类“重口味”的西方先锋文学中国的劳苦大众和一般读者是不能欣赏和喜欢的。
那么,为什么袁可嘉之流的学者却能够欣赏这类怪诞佻脱的作品呢?——因为他们超前,因为他们敏感,也因为他们遭历的独特荒诞经历。
犹记得当年从知青考上大学,笔者还耽溺在唐诗宋词和英、法、德、意、西、俄19世纪文学的岁月,遇到欧美现代派文学就感到焦虑读不懂。觉得那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泥淖、一片魔域,非常令人头疼。不幸的是,我毕业后又被分配在中文系讲授欧美文学,现代派文学是我躲不掉的一个冤家。
也就是这时候,我幸运地遭遇了袁可嘉。他的书里坦诚地告诉读者他在“文革”前也读不懂现代派。是“文革”的不幸遭历,是蹲牛棚,是朝不保夕,是大祸当头妻离子散人人自危,是人间的种种背叛、卖友、出卖人格自轻自贱,是人世中的种种无常让他一下子体味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那种绝望、异化、黑暗和警醒人心的力量。这是一把钥匙,像暗夜里的一团火,让他找到了路径。而他,也无私地将这把钥匙递给了一个个的后来者。
我的少小经历其实也是一个懵懂者的经历。“文革”前我的童年曾经生活优渥,突然在十七岁上“失乐园”,被“上山下乡”从城市生生拔起送到了农村当知青,在乡下的儿年里遍历世态炎凉,痛感人生无常。1977年从农村考到大学中文系,开始把读诗读小说作为终生事业,其间白云苍狗世事变幻令人目不暇接;虽然我的阅读习惯仍然是遵循着中外古典文学的那种喜欢读故事讲情节的习惯模式,但是已能逐渐接受欧美现当代文学暴露人生荒诞和错位、无理的沧桑感。虽然懵懂中我仍然不喜欢现代派文学,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因缘和契机,我有了理解袁可嘉理论的基础。
袁可嘉的这种提示让我顺利地读懂了西方现代文学。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也可以设身处地、也可以体味近似的人生经验去补足文学中的启示和象征。就这样,一声“芝麻开门”,我也进入了这片奇幻的土地领略了其中的堂奥。
窃以为,不仅我,当年教授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后生们都欠着袁可嘉先生的一分私淑的情意,因为他给了大家解谜之钥,给阅读这类题材和体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读法和视角,从而丰富了大家的阅读经验。这样,原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支离破碎、晦涩甚至古怪荒诞的象寓和表述就都有了支点,读者在这种阅读中也融入了自己的个体经验;那样,这种种荒唐就不再扰人而成了深刻与精湛,成了无可替代的新技巧和表现手法。理解了语言与技巧,西方现代文学也就陡然变得可以欣赏,甚至虽然其不必可口却也如苦茶和咖啡般隽永深挚了。
三
有趣的是,袁可嘉生命轨迹的启示虽然让我们看到了老一代学人的坎坷和不幸,也引起了笔者关于学术和成就定位间的不期而然的遐想。
在国内学术圈子里,袁可嘉有自己的领地,他像是一个特定圈子里的国王,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比如说,在那时的中国,说到西方美学,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光潜。说到史学,不期而然地,大家共同想到陈寅恪。说到逻辑学当然是金岳霖,说到中国古代哲学有冯友兰,说到希腊文学有罗念生,说到莎士比亚翻译有朱生豪,说到巴尔扎克或者法国文学翻译有傅雷,等等。
自然,说到对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介,非袁可嘉莫属。
术业有专攻或者扎扎实实地占有一席之地是踏实的治学态度。一个人的一生精力毕竟有限,能在一个领域有所突破就很不容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袁可嘉数十年如一日,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精神攻克最难啃的欧美现代派文学而且泽被后人,这是值得肯定和效法的。
值得肯定的还有,他自量其力,没有逞才使气而是吭哧吭哧地筚路蓝缕,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有理论有实践,主持翻译和整理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文献读本,撰写了理论著作,在这个学科里作出了很平实而可贵的贡献。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里倾注了袁可嘉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我以为,这正是袁可嘉成功的基础。由于这种非凡的刻苦,他成了这个领域里的一个里程碑、一个绕不开的指路标。
他们那一代人里其实不缺少这样聪明的文人甚或更有才华的学者,但是有人不屑或不愿意做这样的苦工或者愿意掉书袋逞才使气展现更亮眼炫目的东西,其艳丽若七宝楼台,华饰若珠宝遍地,但唯缺乏一根线索和红绳把散碎的珠玉穿缀成首饰。这样,有的名士虽学问被公认好,贡献却是几希无。美轮美奂似乎玄妙无边,但是论到具体实用处却使人生疑。结果一肚子好学问却因没有或者不屑于找一个学术支点或领地而被作为图腾供奉着,却对学界缺少实际的指导意义。璀璨委地不可收拾,处处闪闪发光却处处零碎,像一个高级杂货铺,即使再高级,卖的东西却还是杂货。这也许是那些所谓的才子和专家间的区别吧?才子或者通才往往不屑囿于一域,他们喜欢高蹈而不甘于选定一个学科奋斗。拣尽寒枝不愿栖,最后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和冷落。窃以为,像袁可嘉这样的专家、这样咬定青山不放松地献身于一个领域而且踏踏实实出成绩的学者,对学科、对普通读者更实惠更有助益。虽然,在今天的后人看来,才子和专家都逃不脱最后的归宿,他们都已并肩走入了不朽。
而今天,我们回顾先贤们治学的历史和路途的目的并非着意褒贬学科臧否人物,而是希望从前辈的经验和挫折里寻到一些启示。
其实,袁可嘉也是个一直探索、不甘心局限于一隅者。他没有像文艺少年那样终生追梦,当一个纯粹的诗人,也没有立志坐定当一个翻译家或者理论工作者。他的成功还由于他有实践、有理论,又有外语这个利器。这些学术积淀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那个突然到来的春水潺潺、百鸟啁啾的日子一时间成了国内那个百废待兴的荒原上的一只领头羊,他带着大伙儿疯狂地拥抱春天、拥抱阳光、拥抱以前捞不到拥抱的东西,那种如饥似渴,今天回想起来有些让人可怜,让人动容。
只有真正经历过大寒的人才能体悟那时那一缕透过寒窗的半米阳光之可贵和诱惑——也许跟今天的年轻人说起这些,他们往往觉得挺寒碜、挺好笑。但这,其实真的是我们的青春,也是袁可嘉先生的青春。或许,他的青春比我们的更蹉跎:少年时历经离乱和战祸,青年时噤若寒蝉动辄得咎,壮年时被迟到的阳光刺得眼睛有些不适应有些睁不开,而到了能够不惧黑暗拍着良心说话的时候却感到垂垂老矣时日无多。对于袁先生,人生不是一场荒诞又能是什么呢!
所以他理解荒诞派,用他的血肉去理解,用他的灵魂去身受,用他的不屈和倔强人格去体悟;在血水里泡三生,在碱水里煮三生,再在人生的铁砧上被无数次甚至永无休止地敲打和残酷地锤锻、再铸,遍历人生凄惶、世态炎凉、政治高压和时局动荡、朝不保夕的日子,从“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到人生中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背叛、出卖、告密和阴谋,他不可能不理解人生的荒诞、黑色幽默和迷茫。袁可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理解不是读出来的,他是身受、历练和体悟出来的。
当然,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也不容假设。可是如果容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比如说,在中国大动荡大革命的年代,青年时期的袁可嘉出了国,如果他到了港台,如果他到了欧美,他也许会比在国内的朋辈更幸运?他也许能在国外的大学尽情发挥,像他当年流落海外的同学、友人以及他几十年后在纽约相遇的那些功成名就的同侪一样?也许。也许他能因远离祖国政治和动荡少受些波折和坎坷,也许他能够养尊处优因为有安全感而对故国指手画脚,也许他能有更多说话的自由和权利,等等等等。
但是有一点我却隐约地觉得,他或许绝不会有他在今天中国的影响力,因为他现在的资格和尊严是以他受的苦、受的磨难换来的。这是血泊中的花朵,格外艳丽。袁可嘉在今天中国几代学人眼里的地位,是他用受难的尊严博得的——虽然如果能够再生一次,或许他并不愿刻意选择为此去受难。
历史老人在这儿停顿了一下或者说叹息了一声。有时候,人生命运的终极结果并不印证原因;而在更多的时候,原因却并不一定确保最后结果。受磨难最多的人往往不敢不相信宿命这冥冥之中纠缠我们的无赖。在迷茫的人生中,虽然有时候我们播种龙种却收获跳蚤,而有时候我们种瓜却得豆。种豆呢?收获的却可能是苞米。人的生存,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场大荒诞、大浩叹。这些,都已经不是古典的悲剧理论甚至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所能解释的了。袁可嘉治了一辈子理论,或许他的理论都不能告诉他自己一生经历悲剧性的原因。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历史有时候无情却也有时候多情。它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对你微笑。文章憎命达,现实中命运的多蹇也淬炼了不少文学史上的杰出英才。一生惴惴却凄惶在追求纯美或者纯真道路上的袁可嘉遭逢离乱,遭际堪伤,但他对文学使命的追求,他那不懈前行的身影却定格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甚或现代思想史的画面上,渐渐融入了永恒……
在古希腊的传说中有个普罗米修斯,他盗火给人间,照亮了入世却受到了众神的惩罚。在近代,鲁迅先生把从事翻译和介绍外国文明、文化和文学的译者称为传递文明火种的盗火者。借外国的火,来照耀中国的黑暗,以便寻出路把中国引向光明。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袁可嘉也是普罗米修斯。他盗来的火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他不仅盗火,而且播火,这就是那个时代赋予袁可嘉的使命。
【后记】2014年1月18日,在夏志清先生追思会上,笔者巧遇袁可嘉先生的女公子袁晓敏女士。忆起袁先生往事,袁女士索文纪念。次日,得袁女士书申约稿函,此时离袁可嘉纪念册结集截稿期只有十日,此二日恰又适逢本校开学,冗事不少,但思及袁先生及他那一代人的遭际,不胜唏嘘。三十年前的旧事联袂袭来,遂捉笔记写遐思以表达这迟到的感谢。唯笔者人在海外欠缺资料,时间又较紧;此匆匆急就章中一些片段和引言多是据过去记忆书写,未及核对原文,如有不能传递袁先生初始意思之处,是我之失,敬请原宥。
在今天,谈起“文革”后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引进、介绍、研究和发展,您绕不开一个在这个领域里贡献卓著的学者,他就是袁可嘉。
袁可嘉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但他对中国当代文化史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其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介。
袁可嘉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关心西方现代派文学并大量地研究、介绍和引入它们,从现代派诗歌研究的滥觞发端,一直到其后各种流派和各家见解的推介,可以说在这方面竖起了大纛,他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在大陆的执牛耳者。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入在中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介绍和引入过程中始终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风风雨雨。这些阻力中有的是美学的原因暨文学学科内部的争议和理解问题,但更多的却是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羁绊。因此,在那段岁月里,玩现代派文学无异于玩火。它充满了惊异、危险和奇幻甚至厄运,而袁可嘉就是儿个最早敢于玩火的人之一;他乐此不疲,居然玩到了最后。
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文学欣赏习惯是喜欢有故事喜欢情节甚至喜欢大团圆结局的。这种欣赏模式和美学风范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态度和文艺趣味。在中国“文革”以前甚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读惯了西方19世纪小说、看惯了宏大叙事和完整史诗般现实主义描述的读者非常不喜欢西方现代派文学。
可以想见,耽溺于巴尔扎克、热爱莫泊桑和梅里美小说的读者很难读懂卡夫卡,更不易喜欢加缪、贝克特那种既缺少情节又不注重读者喜欢的细节描写,而靠主观的心灵倾诉或者充满了苦难和晦涩的象征寓意之类的小说。你很难想象平日里享受读《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或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甚或《牛虻》的人能够喜欢或欣赏《荒原》《尤利西斯》《城堡》《等待戈多》这类让人读后常常感到郁闷、一头雾水而不得要领的作品。特别是现代派文学表现的那种心理折射的鸡零狗碎、个人化、潜意识及其在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上的那种刻意追求的阴郁、隐喻、晦涩和不合逻辑,处处都给人以尖利、嘈杂、无理、壅塞、硌硬而不舒服的阅读体验。
读者对这类表达不适应,岂不知这些却正是现代派作家和艺术家刻意的追求!他们正是用这种不和谐、凌乱、有违章法和反逻辑的手段制造一种新的美学范式。
现代派之所以深刻,是它的主观意识、反社会性和反传统性;它表现手法的荒诞,影射着人生的荒诞——人生本身就未可知,人生本身就不圆满。既然人生不像一个故事更不像一首史诗,我们为什么又刻意造作地把它粉饰或表现得像牧歌那样呢?现代派艺术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真实。如果荒诞成了我们生命或者是我们的宿命本身,又为什么不能把这种荒诞用文学手段表现出来呢?惯于长夜过春时,长夜的颜色就是春天。这种美学新理念,我认为,是袁可嘉先生给我们揭示出来的。这可以被看作是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切入点。
有什么样的读者就造就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观众就培养什么样的演员。正如看惯了达·芬奇、拉斐尔和列宾、苏里柯夫的欣赏者很难适应毕加索、达利和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画作;同样,西方现代派的音乐也跟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外古典音乐大相径庭。艺术欣赏的模式和现代派的矛盾同时发生在中外艺术的几乎每个领域,这是现代主义文艺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它需要突围,它呼唤一个突破点。
除了民族的欣赏趣味和习惯外,另一个理解西方现代派的阻力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因素。
20世纪中叶,不知从何时起,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特别是主流思想趣味范畴兴起了一种反现代派的观念。那时的主流思想都认为西方的现代派是反理性的、颓废的、阴郁的和反社会的。这种认知也许基于对现代派艺术美学上的体验,也许是基于对现代派思想所表达出的那种混乱、混沌和迷茫躁动情绪的一种反动。总而言之,这种结合了意识形态、政治好恶以及美学批判的庙堂观念却成了当时的一种正宗的论断。要想给西方的现代主义翻案甚至想正常地、客观地介绍一下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理念,是需要一种非凡的勇气的。袁可嘉就是这样敢于反潮流、逆主流思想与钦定美学趣味而动的一个人。
二
我们不禁要问,袁可嘉为什么?他出于什么目的要介绍、推荐和身体力行地为现代主义文艺在中国的推广高歌呐喊呢?
这些都跟他的美学理念和其个人人生阅历有着不可剥离的内在关联。
袁可嘉是个诗人。他早年的第一个文学情人是诗,这个缪斯启迪了他的诗情,让他一生不能忘情于斯。诗的训练使他敏感和耽溺于体悟,我想,这是他喜欢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徘徊甚至不谙世事、迷失归途的一个原因。诗神引导他,让他变成了一个不合时俗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候,他是在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
袁可嘉早年赶上了中国大灾难的年代,疲于逃命,耽于奔波,但是在战火和灾难中他仍然看着天边草地上的小花,憧憬着诗。他是以一个诗人的姿态走上文坛的。其后他一生命运坎坷,从诗到翻译、再到理论探索,最后归于体悟和天凉好个秋,一生中深悟人生荒诞。这种生命的契合,跟西方现代派表达的主题有一种天然的共鸣,西方现代派文艺产生的土壤其实就是他思考生命的土壤或者说是他一生阅历的原点。
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钟情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谜底之一。
笔者在读了袁可嘉的书多年以后,在纽约曾听到袁可嘉儿十年前的朋友夏志清先生提起他跟袁可嘉在北大红楼时期的友谊、往还以及袁可嘉的文学个性,印证了他们在北大任教的青涩岁月里袁可嘉的某些心路历程契合了上述推断。
可是,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学跟西方的现代文学却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夏志清曾经谈起,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不论在理念、表现手法还是主题等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文学传统是“五四”以来的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主题,其表现手法大多是遵循西方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传统揭露现实的丑恶并唤醒民众,它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文学更像是西方的19世纪古典文学,它的集中表现是批判现实主义,更要紧的任务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再现和解释苦难。而西方的现代文学则与此大相径庭:由于西方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化内容跟中国不同,西方的现代文学的使命更在于表现人性异化,人的潜意识,人生荒诞,人与社会现实,人与科技、制度、机器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对“五四”后处于民族生死存亡危机面前的中国文坛来说是有些超前的“富贵病”,因之对这类“重口味”的西方先锋文学中国的劳苦大众和一般读者是不能欣赏和喜欢的。
那么,为什么袁可嘉之流的学者却能够欣赏这类怪诞佻脱的作品呢?——因为他们超前,因为他们敏感,也因为他们遭历的独特荒诞经历。
犹记得当年从知青考上大学,笔者还耽溺在唐诗宋词和英、法、德、意、西、俄19世纪文学的岁月,遇到欧美现代派文学就感到焦虑读不懂。觉得那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泥淖、一片魔域,非常令人头疼。不幸的是,我毕业后又被分配在中文系讲授欧美文学,现代派文学是我躲不掉的一个冤家。
也就是这时候,我幸运地遭遇了袁可嘉。他的书里坦诚地告诉读者他在“文革”前也读不懂现代派。是“文革”的不幸遭历,是蹲牛棚,是朝不保夕,是大祸当头妻离子散人人自危,是人间的种种背叛、卖友、出卖人格自轻自贱,是人世中的种种无常让他一下子体味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那种绝望、异化、黑暗和警醒人心的力量。这是一把钥匙,像暗夜里的一团火,让他找到了路径。而他,也无私地将这把钥匙递给了一个个的后来者。
我的少小经历其实也是一个懵懂者的经历。“文革”前我的童年曾经生活优渥,突然在十七岁上“失乐园”,被“上山下乡”从城市生生拔起送到了农村当知青,在乡下的儿年里遍历世态炎凉,痛感人生无常。1977年从农村考到大学中文系,开始把读诗读小说作为终生事业,其间白云苍狗世事变幻令人目不暇接;虽然我的阅读习惯仍然是遵循着中外古典文学的那种喜欢读故事讲情节的习惯模式,但是已能逐渐接受欧美现当代文学暴露人生荒诞和错位、无理的沧桑感。虽然懵懂中我仍然不喜欢现代派文学,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因缘和契机,我有了理解袁可嘉理论的基础。
袁可嘉的这种提示让我顺利地读懂了西方现代文学。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也可以设身处地、也可以体味近似的人生经验去补足文学中的启示和象征。就这样,一声“芝麻开门”,我也进入了这片奇幻的土地领略了其中的堂奥。
窃以为,不仅我,当年教授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后生们都欠着袁可嘉先生的一分私淑的情意,因为他给了大家解谜之钥,给阅读这类题材和体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读法和视角,从而丰富了大家的阅读经验。这样,原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支离破碎、晦涩甚至古怪荒诞的象寓和表述就都有了支点,读者在这种阅读中也融入了自己的个体经验;那样,这种种荒唐就不再扰人而成了深刻与精湛,成了无可替代的新技巧和表现手法。理解了语言与技巧,西方现代文学也就陡然变得可以欣赏,甚至虽然其不必可口却也如苦茶和咖啡般隽永深挚了。
三
有趣的是,袁可嘉生命轨迹的启示虽然让我们看到了老一代学人的坎坷和不幸,也引起了笔者关于学术和成就定位间的不期而然的遐想。
在国内学术圈子里,袁可嘉有自己的领地,他像是一个特定圈子里的国王,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比如说,在那时的中国,说到西方美学,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光潜。说到史学,不期而然地,大家共同想到陈寅恪。说到逻辑学当然是金岳霖,说到中国古代哲学有冯友兰,说到希腊文学有罗念生,说到莎士比亚翻译有朱生豪,说到巴尔扎克或者法国文学翻译有傅雷,等等。
自然,说到对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引介,非袁可嘉莫属。
术业有专攻或者扎扎实实地占有一席之地是踏实的治学态度。一个人的一生精力毕竟有限,能在一个领域有所突破就很不容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袁可嘉数十年如一日,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精神攻克最难啃的欧美现代派文学而且泽被后人,这是值得肯定和效法的。
值得肯定的还有,他自量其力,没有逞才使气而是吭哧吭哧地筚路蓝缕,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有理论有实践,主持翻译和整理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文献读本,撰写了理论著作,在这个学科里作出了很平实而可贵的贡献。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作里倾注了袁可嘉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我以为,这正是袁可嘉成功的基础。由于这种非凡的刻苦,他成了这个领域里的一个里程碑、一个绕不开的指路标。
他们那一代人里其实不缺少这样聪明的文人甚或更有才华的学者,但是有人不屑或不愿意做这样的苦工或者愿意掉书袋逞才使气展现更亮眼炫目的东西,其艳丽若七宝楼台,华饰若珠宝遍地,但唯缺乏一根线索和红绳把散碎的珠玉穿缀成首饰。这样,有的名士虽学问被公认好,贡献却是几希无。美轮美奂似乎玄妙无边,但是论到具体实用处却使人生疑。结果一肚子好学问却因没有或者不屑于找一个学术支点或领地而被作为图腾供奉着,却对学界缺少实际的指导意义。璀璨委地不可收拾,处处闪闪发光却处处零碎,像一个高级杂货铺,即使再高级,卖的东西却还是杂货。这也许是那些所谓的才子和专家间的区别吧?才子或者通才往往不屑囿于一域,他们喜欢高蹈而不甘于选定一个学科奋斗。拣尽寒枝不愿栖,最后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和冷落。窃以为,像袁可嘉这样的专家、这样咬定青山不放松地献身于一个领域而且踏踏实实出成绩的学者,对学科、对普通读者更实惠更有助益。虽然,在今天的后人看来,才子和专家都逃不脱最后的归宿,他们都已并肩走入了不朽。
而今天,我们回顾先贤们治学的历史和路途的目的并非着意褒贬学科臧否人物,而是希望从前辈的经验和挫折里寻到一些启示。
其实,袁可嘉也是个一直探索、不甘心局限于一隅者。他没有像文艺少年那样终生追梦,当一个纯粹的诗人,也没有立志坐定当一个翻译家或者理论工作者。他的成功还由于他有实践、有理论,又有外语这个利器。这些学术积淀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那个突然到来的春水潺潺、百鸟啁啾的日子一时间成了国内那个百废待兴的荒原上的一只领头羊,他带着大伙儿疯狂地拥抱春天、拥抱阳光、拥抱以前捞不到拥抱的东西,那种如饥似渴,今天回想起来有些让人可怜,让人动容。
只有真正经历过大寒的人才能体悟那时那一缕透过寒窗的半米阳光之可贵和诱惑——也许跟今天的年轻人说起这些,他们往往觉得挺寒碜、挺好笑。但这,其实真的是我们的青春,也是袁可嘉先生的青春。或许,他的青春比我们的更蹉跎:少年时历经离乱和战祸,青年时噤若寒蝉动辄得咎,壮年时被迟到的阳光刺得眼睛有些不适应有些睁不开,而到了能够不惧黑暗拍着良心说话的时候却感到垂垂老矣时日无多。对于袁先生,人生不是一场荒诞又能是什么呢!
所以他理解荒诞派,用他的血肉去理解,用他的灵魂去身受,用他的不屈和倔强人格去体悟;在血水里泡三生,在碱水里煮三生,再在人生的铁砧上被无数次甚至永无休止地敲打和残酷地锤锻、再铸,遍历人生凄惶、世态炎凉、政治高压和时局动荡、朝不保夕的日子,从“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到人生中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背叛、出卖、告密和阴谋,他不可能不理解人生的荒诞、黑色幽默和迷茫。袁可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理解不是读出来的,他是身受、历练和体悟出来的。
当然,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也不容假设。可是如果容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比如说,在中国大动荡大革命的年代,青年时期的袁可嘉出了国,如果他到了港台,如果他到了欧美,他也许会比在国内的朋辈更幸运?他也许能在国外的大学尽情发挥,像他当年流落海外的同学、友人以及他几十年后在纽约相遇的那些功成名就的同侪一样?也许。也许他能因远离祖国政治和动荡少受些波折和坎坷,也许他能够养尊处优因为有安全感而对故国指手画脚,也许他能有更多说话的自由和权利,等等等等。
但是有一点我却隐约地觉得,他或许绝不会有他在今天中国的影响力,因为他现在的资格和尊严是以他受的苦、受的磨难换来的。这是血泊中的花朵,格外艳丽。袁可嘉在今天中国几代学人眼里的地位,是他用受难的尊严博得的——虽然如果能够再生一次,或许他并不愿刻意选择为此去受难。
历史老人在这儿停顿了一下或者说叹息了一声。有时候,人生命运的终极结果并不印证原因;而在更多的时候,原因却并不一定确保最后结果。受磨难最多的人往往不敢不相信宿命这冥冥之中纠缠我们的无赖。在迷茫的人生中,虽然有时候我们播种龙种却收获跳蚤,而有时候我们种瓜却得豆。种豆呢?收获的却可能是苞米。人的生存,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场大荒诞、大浩叹。这些,都已经不是古典的悲剧理论甚至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所能解释的了。袁可嘉治了一辈子理论,或许他的理论都不能告诉他自己一生经历悲剧性的原因。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历史有时候无情却也有时候多情。它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对你微笑。文章憎命达,现实中命运的多蹇也淬炼了不少文学史上的杰出英才。一生惴惴却凄惶在追求纯美或者纯真道路上的袁可嘉遭逢离乱,遭际堪伤,但他对文学使命的追求,他那不懈前行的身影却定格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甚或现代思想史的画面上,渐渐融入了永恒……
在古希腊的传说中有个普罗米修斯,他盗火给人间,照亮了入世却受到了众神的惩罚。在近代,鲁迅先生把从事翻译和介绍外国文明、文化和文学的译者称为传递文明火种的盗火者。借外国的火,来照耀中国的黑暗,以便寻出路把中国引向光明。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袁可嘉也是普罗米修斯。他盗来的火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他不仅盗火,而且播火,这就是那个时代赋予袁可嘉的使命。
【后记】2014年1月18日,在夏志清先生追思会上,笔者巧遇袁可嘉先生的女公子袁晓敏女士。忆起袁先生往事,袁女士索文纪念。次日,得袁女士书申约稿函,此时离袁可嘉纪念册结集截稿期只有十日,此二日恰又适逢本校开学,冗事不少,但思及袁先生及他那一代人的遭际,不胜唏嘘。三十年前的旧事联袂袭来,遂捉笔记写遐思以表达这迟到的感谢。唯笔者人在海外欠缺资料,时间又较紧;此匆匆急就章中一些片段和引言多是据过去记忆书写,未及核对原文,如有不能传递袁先生初始意思之处,是我之失,敬请原宥。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