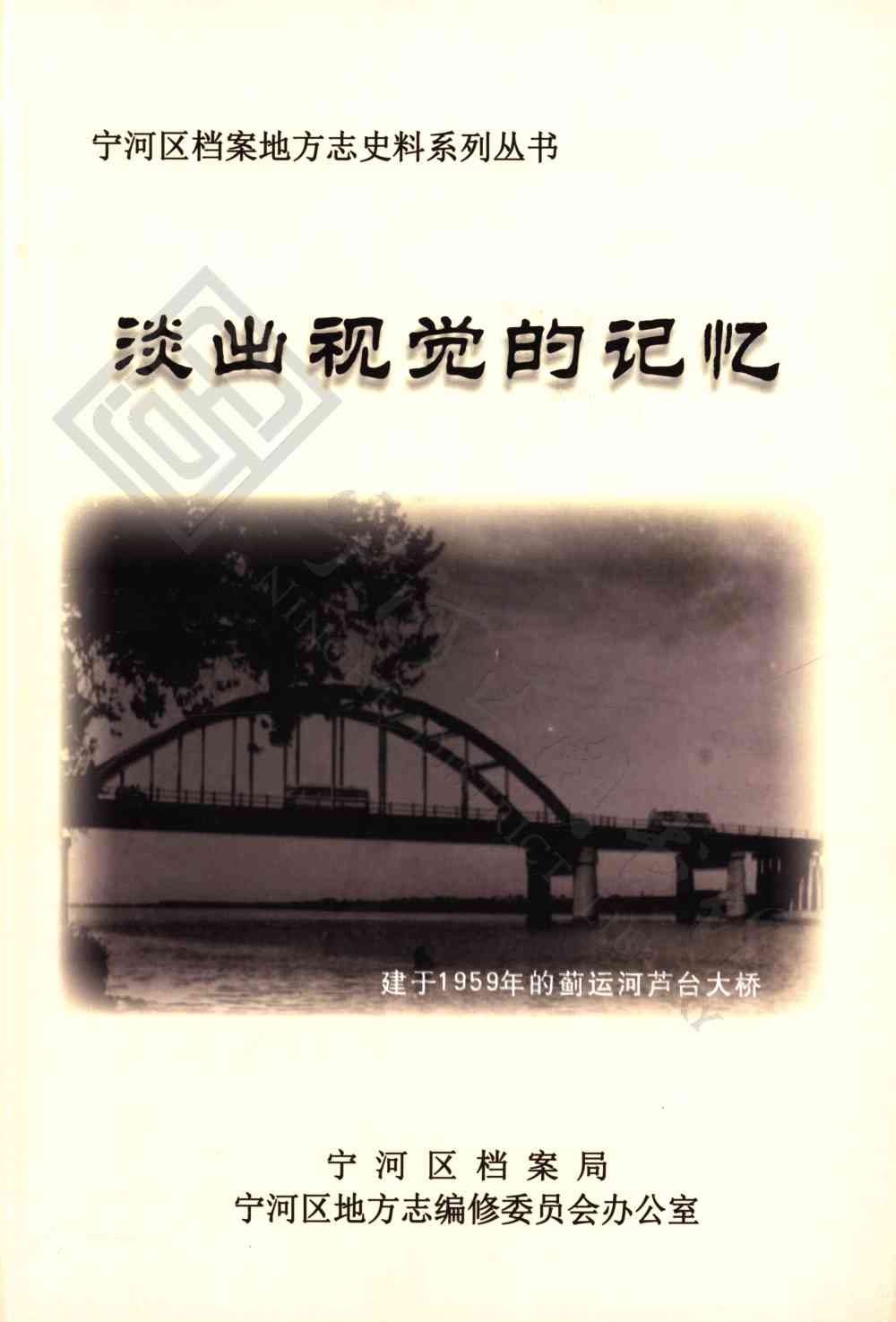内容
我心中的茅草屋
时过境迁,记忆中曾装着我梦想的茅草屋已经被历史的风烟湮没了,无处寻觅。但我依然怀念它,那门、那窗、那微微向内倾斜的墙体,特别是那墙面上用泥巴沾贴上去一排排稻草,好像那一切都在深深吸引着我怀念它,留给我无法忘却的温暖、憧憬与忧伤。
茅草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大多数农村人的栖息、安身、繁衍后代的地方。村村落落都能看得到土坯墙,枯黄稻草顶下的农舍,或连排,或七零八落的伫立在街道两旁。远远望去像土堆、像草垛、像蘑菇,沉寂于大地上,为农人撑起一片生存的天空。
我家的茅草屋坐落在南沽村前街的最南端,它像一条深入绿海里极不协调枯黄的草船。高不过一丈四尺,便是这原始简陋的草坯建筑主体,可它却是我们一家五口人唯一挡风避雨生活的空间,逢年过节的时侯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园。
茅草屋最怕大雨,狂风。可春、夏二季的风雨又特别的多,强劲时狂风夹裹着暴雨,冰雹,像一头头怪兽,猛猛扑向茅草屋,将房顶,墙壁上的稻草一块块,一片片地掀起,甚至洞穿。此时屋外大下,屋内小下,滴嗒、滴嗒,漏雨声弹奏出忧伤烦人的旋律,不由的人人心头涌出一种痛。这个时候的妈妈忙不迭地寻找盆盆罐罐、器皿容器接着从屋顶渗下的雨水。有时依然无济于事,滴嗒的漏雨声和屋外狂风骤雨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一阵紧似一阵,叫人胆战心惊,生怕这风雨飘摇中的茅草屋进一步被风雨摧残吹毁而无处安身。每每这一时刻,我的心揪得特别的紧,也特别的害怕,幼小的心灵过早的品尝了生活的艰难。一场暴风雨过后,茅草屋被掀得四处透风支离破碎,令人十分痛心,回想起凄凉的场景,家家户户相同的遭遇,不禁让人想起了,那位千古流芳的诗人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写到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对诗人的当时处境多了几分理解。尽管俗辈,没有诗人心系天下的胸怀,此时此刻,多么希望我家以及周边的农人都能早日离开这不堪风雨吹打的茅草屋。
其实,草泥垒起的建筑难以抵遇强劲的风雨,周而复始的侵蚀,多少辛劳也换不来理想的住所和长久的安宁,农人们的心中依然在做着“广厦”的梦……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到了我们的小村。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土地经营三十年不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收入也成倍增长。进入八十年代初期,家里积攒下一定积蓄,一九八二年建起砖瓦结构住房四间,改善居住条件,从此告别了住茅草屋的历史。虽然,茅草屋作为一个地区贫穷的标志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它每时每刻都在激励我们发奋图强、拼搏进取,告诫我们在心灵深处要学会感恩和满足。
土炕
谈“炕”离不开“火”。《说文解字》中“炕”的解释是干也从火。炕必须接灶,灶中火、烟、热量,是通过土炕的几条孔道的入炕内进行循环,再通过烟道将其排出室外。天冷的时往灶里添加点一些柴草,一晚上便可以倚仗热炕的余温安然入眠。三伏天,适当烧炕,又能排除一些潮气使人睡起来舒服。同时还可以利用土灶烧水,做饭,炒菜,煲汤……
“炕头”紧挨灶口的地方,这儿最暖和,一般多留给老人,孩子和病人。青壮年人则多睡在炕梢,有“傻小子睡凉炕”的笑谈,就出自这儿。
在小农经济时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广为流传,成为农民辛苦奔波而幸福生活写照。好的日子都化在炕上,好的盼头也都挂在炕上。炕,在北方农村人们心中,就是美好与神圣象征。
对家乡人来说,炕是人生的一个主要舞台,一个人在炕上完成角色的转换,人就像庄稼一样在土炕上,长了一茬,又一茬,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从容地走过一生。
对于老家人来说,炕并不只简单作为自家人睡觉和休息的地方,炕还是会客、吃饭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老家东屋炕梢,总有一些,母亲义务为街坊邻居裁剪,制作大人、孩子的服装,特别是接近年关,那里有干不忘的活。夜里我们常常在土炕上,伴着妈妈的缝纫机的哒哒、哒哒声入睡。
无数次夜里醒来,炕上做活的妈妈都笼罩在暖暖的光晕里,有人说,母亲是孩子心里的佛,端坐在炕上油灯下,光芒之中的妈妈就是我们心里的佛。
除此之外,炕还是孩子们学习、写作业,老人讲故事、邻居传播新闻的地方。如果家里有喜欢唱几口的,炕就是唱念做打的舞台。到了天冷季节,炕也是发馒头、包饺子的地方。尤其在冬天,家里来客人,一般都是先招呼到炕上,把暖和炕头让出来,留给尊贵的客人。炕外边沿上有一道起保护作用的木板,叫“炕沿”,我家的炕沿是椿木做的。有时候客人有急事,就不脱鞋上炕,在炕沿上胯着坐一会,说几句话。
若用现代意义上的家庭空间划分,老家的炕兼具了客厅、餐厅、起居、工作间等全部功能,完全是家里暖人心窝的一处多功能厅。
土灶,包容了世间的悲喜与欢泪也接纳了人们的生命与生活,无论我离它多远多久,都是梦中渴望回到的地方。
如今,砌炕的“土坯”已经没有人做了,人们开始用砖,水泥板或石板代替,却完全没有土坯那样冷热宜人,太热时烙人,太凉时瘆人,太硬时硌人。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最传统的老土炕,土炕上铺苇席,苇席上铺被褥,喜欢土炕的土腥味里混合着世事伦常的味道和人间烟火的气息。
现在,我每次回老家,一定要住土炕。世界再大,奔波的空间再无止境,但真正属于我的或许就是这老家的土炕。
奶奶的纺车
在我很小的时候,躺在被窝里,耳边听着坑上奶奶的纺车发出蜜蜂一样,嗡嗡、嗡嗡的声音,心里就踏实,有无数个夜晚,就是伴着奶奶的纺车声进入梦乡。
奶奶的身影在灯光下放大许多倍以后再投射到墙壁上异常生动耀眼。墙壁上的纺车影像欢快地转动着,转动着……一条细细的长线从奶奶左手指尖的棉絮里缓缓流出,然后缠绕到纺锭上,银白色的线团越缠越大,越缠越粗,最后形成一个橄榄形状,并达一定粗细时,才从纺车上取下来。取下来的线轴干吗?经过浆洗,漂染,织成粗布,再经过裁剪,制作成衣服,被褥……好像我们祖祖辈辈的纺车就是这样转过来的。
奶奶是解放脚(即缠足以后又放开的)。小时候躺在奶奶的纺车边,听着奶奶讲“罗成对花枪”的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哪吒闹海”的故事,还有还有《岳飞传》,那时候我不知道奶奶的故事咋就那么多,取之不尽。现在回想起来,奶奶讲的故事,并不完整,有时候,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不过那时候我们听起来非常认真,性趣十足。
有的时候,一觉醒来,奶奶的纺车还在转动着。那声音像梦,也像绕梁的音乐,它让我童年生活特别踏实,梦也特别地甜。故乡的炊烟,老家用篱笆围起的后院,后院的枣树、杏树、桃树,广阔的田野以及田间的羊肠小道,鸭鹅成群的池塘,门前的小石桥……奶奶的身影和永远不停转动着的纺车重重叠叠在一起,形成了我美妙的童年风景在奶奶不停转动的纺车声中,在奶奶慈祥的笑容里,在奶奶那一段段古老的故事城堡,我度过了美好幸福的童年。
长大以后,我一直没有远离故乡,没有离开奶奶。可后来故乡的人早已不用纺车了,纺车成了历史,成了人们追忆的过去,而奶奶的纺车经常转动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听见纺车的嗡嗡声。它好像在激励、鞭策、感动着我们这些晚辈发愤图强,也好像在冥冥之中,送给我许多温暖而又美好的回忆……
锄地
锄地,是一项单调而又艰辛的劳动,锄地也是那个时代农民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劳动技能。
锄头是农村最普通的农具。一根光滑且笔直的圆木长柄,深深地镶入一个像鸭脖子一样勾回来的铁裤里,鸭脖子那头衔接着一块薄薄锄板。锄板根据用途又可分为两种,一种叫平板锄,适用于锄高粱、玉米、棉花,宽垄农作物,而另一种类似月牙状锄板打磨的光亮如镜,锋利无比,适用于小垄沟密植的农田,或菜地的锄草。
在烈日高悬的“三伏”雨季,是用锄频繁的季节。夏天雨量充沛,一场连阴雨之后,庄稼幼苗,郁郁葱葱,拔着节儿似地生长。然而,周围的那些杂草,也不甘落后,日益茁壮,与禾苗争水,争肥,争光,争营养……此时,锄草是决定一年庄稼丰歉的最关健环节。
这时,锄头便可以大显神威了。雨后人们就会急急忙忙扛着锄头,顶着烈日,下地去锄草。出此之外,锄地兼有疏松土壤,抗旱保墒作用。
锄地也是一个技术性很高的农活儿。锄头入地太深,拉着费劲,杂草也不会立时干枯,入地太浅,锄头贴着地皮飞,锄不断杂草的根系。只有,深浅适度,保持与禾苗的最近距离,又不伤害其根系为宜。锄头入地时,需要聚精会神,锄头绕过苗苗根系,找准切入点,“左右开弓”,手起锄落,干净利索,锄草留苗,又叫“揣锄”,也叫“开苗”,深度适宜。然后,平起锄板,弓步塌腰,怀里揽月,杂草“咔嚓,咔嚓”被一一锄翻!每一根苗都是如此,不多不少,“三锄一苗”,杂草纷纷倒在幼苗周围,烈日之下,锄完一个来回,杂草立刻枯萎。偶有大意之人,也有锄断幼苗的,往往心疼地啧啧咂嘴,后悔不迭。记得,我第一次在生产队锄草,掌握不准,接二连三锄断幼苗,吓得我急忙蹲下身去把苗儿摁进泥土里,生怕队长发现……腰在反复一直一弯中,像折断的柳枝一样,浑身麻木,筋疲力尽。
直到立秋,寸草结籽,稼穑渐熟,锄头,基本完成了一年的使命。闲置下来,不再被打磨的锋芒毕露,悬挂在下房屋的屋梁上,有人把这个过程叫挂锄。挂锄意味着杂草灭迹,庄稼成熟,人们稍作休息,为秋收做好准备。
自从有了除草剂,锄头基本下岗,偶尔派上用场,大多时间,隐匿在一个角落里。
挖鼠洞
挖鼠洞,少时一段趣事,回味起来,记忆犹新。
在我们家乡常见的鼠,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田鼠,它生活在田间地头,尾巴短短,身体胖胖,在田埂,渠埝高处打洞,一来防止雨水倒灌,二是保持鼠洞干燥清爽;还有一种是老鼠,俗称耗子,嘴巴尖尖,尾巴长长,颜色稍黑。
田鼠与老鼠,生活习性不同。虽然,统称为鼠科动物,但却不一样。田鼠的嘴里有两个储存袋,食物充足时,它会把食物放在袋里,带回窝里,储存起来,已备冬天和食物匮乏时享用,这种鼠大都生活在田地里。老鼠嘴巴两侧没有囊,也没有储存食物的习性,它们一般生活在人类住宅角落的鼠洞里,与人们分享入仓粮食和食物。人们非常讨厌它,自古便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臭名,所以这种动物异常怕人,警惕性很高,夜间觅食。
挖鼠洞,当然就是要挖田鼠的洞,把田鼠储存起来的粮食取出来。挖鼠洞始于何年何代,我无从考证,由来已久吧!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特别匮乏,为了解决食物问题,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向鼠口夺粮,挖鼠洞盛行。在我小时候,每到秋天,孩子都要去寻找鼠洞,有时候大人也在其中。
挖鼠洞一般扛上铁锹,带上口袋到收割完庄稼地里去寻找鼠洞和鼠山,所谓的鼠山,就是田鼠挖洞时挖出的土,往往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土堆,称为鼠山。找鼠山有技巧,一般要到豆子、玉米、高粱地里去找,鼠洞周围地里种啥庄稼,鼠窝里定会有啥粮食,我喜欢到黄豆地里去寻找。
看到的鼠山比较大,则老鼠比较大,鼠洞亦比较大,储存的粮食亦比较多。若鼠山土质新鲜潮湿,说明近期田鼠仍在活动,收获便有八九成希望。当找到了鼠山,可以在它的附近寻找另外一个洞口了,而这个洞口必须是直上直下的,无比光滑,还要有田鼠爬行的痕迹,否则你不用去挖,一定是个笨鼠,或废弃的鼠洞,洞中不会有粮食。找到洞口,顺着洞口一直挖下去,这时的鼠洞往往会分成几个分支,分别通往它专用的卧室、活动区和仓库。所以遇到分支,可分头去挖,一般情况,我们会用杂草把各分支的洞口堵上,作为标记,先挖其中的一个,待挖完后再挖其他的。
田鼠的粮仓,为了安全,往往把洞从里面堵死。所以我们在挖掘的过程中一旦不见洞了,必须仔细的寻找,从土的颜色和土的硬度判断,一般它堵的土比四周的土要松软一点,而且颜色也会有所不同。就这样一直挖下去,如找到粮仓,大家会高兴万分,免不了要手舞足蹈的高兴一阵子。然后争抢着小心翼翼地把粮食抠出来,装入袋子。多时可以一二十斤,当然也可能一无所获。有人说,正在哺乳的母鼠洞,一般食物很少,挖到它,算你运气不佳,只能是空手而归了。如挖到田鼠的活动室或卧室,且田鼠也在窝里,它会突然的窜出来,吓人一跳,也会给同伴们带来一点刺激,大家会满地的追逐它,尽情的嬉戏,直至把它整死,少有逃生的,回想起来,有些“残忍”。
实际上有些田鼠把粮食保存很好,用水淘一淘,大多可充作人的口粮了,不好的也可以喂猪和鸡鸭鹅,当然这是大人们考虑的事情。我们只知道挖鼠洞,找粮食,一天好的时候可以收获二三十斤,有收获,心情可想而知。少年这样的一段经历,回想起来感慨颇多……
听蟹
“听蟹”,是祖辈遗传下来的传统捕蟹方法。听蟹最好的季节是秋末冬初,也是河蟹的繁殖季节,一般这个时侯听蟹收获颇丰。
我第一次听蟹是在一九六七年,一个月清风高的晚上,与老九、小安子一起准备好工具。在家里简单地把小提灯用抹布擦拭一番,小提灯是听蟹的主要工具,呈园桶状,上边有一个伞状盖,周围玻璃罩,可防风吹,上下可以排烟通风,在当时国营商店里有销售,如今差不多已成文物了。一个月前应马振得邀请参观兴家坨“天津兴家民俗博物馆”时见过这些东西。
因为,听蟹一般都是在晚上,出发前我们也必须简单装束一下。穿起满是补丁的老棉袄防寒,各自便提起小提灯,带着小方凳,拿起小网兜,腋下夹两捆稻草,在家里提前点亮了小提灯,说说笑笑,亮堂堂出去了。出门后,一直往南走不远,便来到一个小木桥上,小木桥不是很大,终年流水,村里人都叫它“看青桥”。
天尚未黑透,一轮明月已高高地悬在深蓝色的夜空中。水稻已收割完,田里光光秃秃的,仅剩下矮矮的稻茬和咸水沟几根芦苇。不远处是两个生产队集中存放打轧稻草垛与粮食的场院。每一个场院都有一排小房子,那是护场人员休息和存放工具的地方,因为有人看管,小屋里发出微弱的光。深秋的西北风冷飕飕的,我们站在桥头,禁不住寒战连连。
仔细观察一下地形,预测出螃蟹可能出水行走的路线,选择好位置,安放好小凳子,又将小提灯稳稳放在上面,待一切安顿好,我们便躲在暗处,簇拥在一起,或爬、或蹲在铺有稻草土坡上,一动不动,静静地期待着螃蟹自己爬上来……那时的老壕沟,长满厚厚的芦苇,水沟挺深,下游与蓟运河相连,上游是六百亩水稻田。这个沟的水质好,鱼虾肥,螃蟹较多。
“螃蟹能上来吗?”我问,老九说“不着急,不要说话,慢慢听……”静默中,不知又过了多久,忽听得流水中“咕咚咕咚、哗啦啦”响,“有了。”我急忙欠起身跑过去在沟坡上,抓到一只,忙拿到灯光下观看,一只黑背白肚两螯长满茸毛的大蟹,拿在手上还张牙舞爪,这边才放入网兜里,水沟里又有响动,老九又从水边抓起一只,也是大蟹,毛却不多。
“螃蟹真是呆子,这么好抓”。其实不然,那一日晚上,再也没有一个螃蟹爬上来。后来,老人们告诉,先上来的螃蟹是“探子”,是“侦察兵”,不能捕捉。否则,后边的河蟹就不会上来了;你若不抓它们自然会源源不断,成群结队,涌上岸来。
这些年,我慢慢揣摩这其中的奥妙,大约是这灯光诱惑、流水和生活习性的缘故吧,也未可知。
(王来峰)
时过境迁,记忆中曾装着我梦想的茅草屋已经被历史的风烟湮没了,无处寻觅。但我依然怀念它,那门、那窗、那微微向内倾斜的墙体,特别是那墙面上用泥巴沾贴上去一排排稻草,好像那一切都在深深吸引着我怀念它,留给我无法忘却的温暖、憧憬与忧伤。
茅草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大多数农村人的栖息、安身、繁衍后代的地方。村村落落都能看得到土坯墙,枯黄稻草顶下的农舍,或连排,或七零八落的伫立在街道两旁。远远望去像土堆、像草垛、像蘑菇,沉寂于大地上,为农人撑起一片生存的天空。
我家的茅草屋坐落在南沽村前街的最南端,它像一条深入绿海里极不协调枯黄的草船。高不过一丈四尺,便是这原始简陋的草坯建筑主体,可它却是我们一家五口人唯一挡风避雨生活的空间,逢年过节的时侯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园。
茅草屋最怕大雨,狂风。可春、夏二季的风雨又特别的多,强劲时狂风夹裹着暴雨,冰雹,像一头头怪兽,猛猛扑向茅草屋,将房顶,墙壁上的稻草一块块,一片片地掀起,甚至洞穿。此时屋外大下,屋内小下,滴嗒、滴嗒,漏雨声弹奏出忧伤烦人的旋律,不由的人人心头涌出一种痛。这个时候的妈妈忙不迭地寻找盆盆罐罐、器皿容器接着从屋顶渗下的雨水。有时依然无济于事,滴嗒的漏雨声和屋外狂风骤雨的呼啸声交织在一起,一阵紧似一阵,叫人胆战心惊,生怕这风雨飘摇中的茅草屋进一步被风雨摧残吹毁而无处安身。每每这一时刻,我的心揪得特别的紧,也特别的害怕,幼小的心灵过早的品尝了生活的艰难。一场暴风雨过后,茅草屋被掀得四处透风支离破碎,令人十分痛心,回想起凄凉的场景,家家户户相同的遭遇,不禁让人想起了,那位千古流芳的诗人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写到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对诗人的当时处境多了几分理解。尽管俗辈,没有诗人心系天下的胸怀,此时此刻,多么希望我家以及周边的农人都能早日离开这不堪风雨吹打的茅草屋。
其实,草泥垒起的建筑难以抵遇强劲的风雨,周而复始的侵蚀,多少辛劳也换不来理想的住所和长久的安宁,农人们的心中依然在做着“广厦”的梦……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到了我们的小村。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土地经营三十年不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收入也成倍增长。进入八十年代初期,家里积攒下一定积蓄,一九八二年建起砖瓦结构住房四间,改善居住条件,从此告别了住茅草屋的历史。虽然,茅草屋作为一个地区贫穷的标志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它每时每刻都在激励我们发奋图强、拼搏进取,告诫我们在心灵深处要学会感恩和满足。
土炕
谈“炕”离不开“火”。《说文解字》中“炕”的解释是干也从火。炕必须接灶,灶中火、烟、热量,是通过土炕的几条孔道的入炕内进行循环,再通过烟道将其排出室外。天冷的时往灶里添加点一些柴草,一晚上便可以倚仗热炕的余温安然入眠。三伏天,适当烧炕,又能排除一些潮气使人睡起来舒服。同时还可以利用土灶烧水,做饭,炒菜,煲汤……
“炕头”紧挨灶口的地方,这儿最暖和,一般多留给老人,孩子和病人。青壮年人则多睡在炕梢,有“傻小子睡凉炕”的笑谈,就出自这儿。
在小农经济时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广为流传,成为农民辛苦奔波而幸福生活写照。好的日子都化在炕上,好的盼头也都挂在炕上。炕,在北方农村人们心中,就是美好与神圣象征。
对家乡人来说,炕是人生的一个主要舞台,一个人在炕上完成角色的转换,人就像庄稼一样在土炕上,长了一茬,又一茬,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从容地走过一生。
对于老家人来说,炕并不只简单作为自家人睡觉和休息的地方,炕还是会客、吃饭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老家东屋炕梢,总有一些,母亲义务为街坊邻居裁剪,制作大人、孩子的服装,特别是接近年关,那里有干不忘的活。夜里我们常常在土炕上,伴着妈妈的缝纫机的哒哒、哒哒声入睡。
无数次夜里醒来,炕上做活的妈妈都笼罩在暖暖的光晕里,有人说,母亲是孩子心里的佛,端坐在炕上油灯下,光芒之中的妈妈就是我们心里的佛。
除此之外,炕还是孩子们学习、写作业,老人讲故事、邻居传播新闻的地方。如果家里有喜欢唱几口的,炕就是唱念做打的舞台。到了天冷季节,炕也是发馒头、包饺子的地方。尤其在冬天,家里来客人,一般都是先招呼到炕上,把暖和炕头让出来,留给尊贵的客人。炕外边沿上有一道起保护作用的木板,叫“炕沿”,我家的炕沿是椿木做的。有时候客人有急事,就不脱鞋上炕,在炕沿上胯着坐一会,说几句话。
若用现代意义上的家庭空间划分,老家的炕兼具了客厅、餐厅、起居、工作间等全部功能,完全是家里暖人心窝的一处多功能厅。
土灶,包容了世间的悲喜与欢泪也接纳了人们的生命与生活,无论我离它多远多久,都是梦中渴望回到的地方。
如今,砌炕的“土坯”已经没有人做了,人们开始用砖,水泥板或石板代替,却完全没有土坯那样冷热宜人,太热时烙人,太凉时瘆人,太硬时硌人。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最传统的老土炕,土炕上铺苇席,苇席上铺被褥,喜欢土炕的土腥味里混合着世事伦常的味道和人间烟火的气息。
现在,我每次回老家,一定要住土炕。世界再大,奔波的空间再无止境,但真正属于我的或许就是这老家的土炕。
奶奶的纺车
在我很小的时候,躺在被窝里,耳边听着坑上奶奶的纺车发出蜜蜂一样,嗡嗡、嗡嗡的声音,心里就踏实,有无数个夜晚,就是伴着奶奶的纺车声进入梦乡。
奶奶的身影在灯光下放大许多倍以后再投射到墙壁上异常生动耀眼。墙壁上的纺车影像欢快地转动着,转动着……一条细细的长线从奶奶左手指尖的棉絮里缓缓流出,然后缠绕到纺锭上,银白色的线团越缠越大,越缠越粗,最后形成一个橄榄形状,并达一定粗细时,才从纺车上取下来。取下来的线轴干吗?经过浆洗,漂染,织成粗布,再经过裁剪,制作成衣服,被褥……好像我们祖祖辈辈的纺车就是这样转过来的。
奶奶是解放脚(即缠足以后又放开的)。小时候躺在奶奶的纺车边,听着奶奶讲“罗成对花枪”的故事,“牛郎织女”的故事,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哪吒闹海”的故事,还有还有《岳飞传》,那时候我不知道奶奶的故事咋就那么多,取之不尽。现在回想起来,奶奶讲的故事,并不完整,有时候,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不过那时候我们听起来非常认真,性趣十足。
有的时候,一觉醒来,奶奶的纺车还在转动着。那声音像梦,也像绕梁的音乐,它让我童年生活特别踏实,梦也特别地甜。故乡的炊烟,老家用篱笆围起的后院,后院的枣树、杏树、桃树,广阔的田野以及田间的羊肠小道,鸭鹅成群的池塘,门前的小石桥……奶奶的身影和永远不停转动着的纺车重重叠叠在一起,形成了我美妙的童年风景在奶奶不停转动的纺车声中,在奶奶慈祥的笑容里,在奶奶那一段段古老的故事城堡,我度过了美好幸福的童年。
长大以后,我一直没有远离故乡,没有离开奶奶。可后来故乡的人早已不用纺车了,纺车成了历史,成了人们追忆的过去,而奶奶的纺车经常转动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听见纺车的嗡嗡声。它好像在激励、鞭策、感动着我们这些晚辈发愤图强,也好像在冥冥之中,送给我许多温暖而又美好的回忆……
锄地
锄地,是一项单调而又艰辛的劳动,锄地也是那个时代农民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劳动技能。
锄头是农村最普通的农具。一根光滑且笔直的圆木长柄,深深地镶入一个像鸭脖子一样勾回来的铁裤里,鸭脖子那头衔接着一块薄薄锄板。锄板根据用途又可分为两种,一种叫平板锄,适用于锄高粱、玉米、棉花,宽垄农作物,而另一种类似月牙状锄板打磨的光亮如镜,锋利无比,适用于小垄沟密植的农田,或菜地的锄草。
在烈日高悬的“三伏”雨季,是用锄频繁的季节。夏天雨量充沛,一场连阴雨之后,庄稼幼苗,郁郁葱葱,拔着节儿似地生长。然而,周围的那些杂草,也不甘落后,日益茁壮,与禾苗争水,争肥,争光,争营养……此时,锄草是决定一年庄稼丰歉的最关健环节。
这时,锄头便可以大显神威了。雨后人们就会急急忙忙扛着锄头,顶着烈日,下地去锄草。出此之外,锄地兼有疏松土壤,抗旱保墒作用。
锄地也是一个技术性很高的农活儿。锄头入地太深,拉着费劲,杂草也不会立时干枯,入地太浅,锄头贴着地皮飞,锄不断杂草的根系。只有,深浅适度,保持与禾苗的最近距离,又不伤害其根系为宜。锄头入地时,需要聚精会神,锄头绕过苗苗根系,找准切入点,“左右开弓”,手起锄落,干净利索,锄草留苗,又叫“揣锄”,也叫“开苗”,深度适宜。然后,平起锄板,弓步塌腰,怀里揽月,杂草“咔嚓,咔嚓”被一一锄翻!每一根苗都是如此,不多不少,“三锄一苗”,杂草纷纷倒在幼苗周围,烈日之下,锄完一个来回,杂草立刻枯萎。偶有大意之人,也有锄断幼苗的,往往心疼地啧啧咂嘴,后悔不迭。记得,我第一次在生产队锄草,掌握不准,接二连三锄断幼苗,吓得我急忙蹲下身去把苗儿摁进泥土里,生怕队长发现……腰在反复一直一弯中,像折断的柳枝一样,浑身麻木,筋疲力尽。
直到立秋,寸草结籽,稼穑渐熟,锄头,基本完成了一年的使命。闲置下来,不再被打磨的锋芒毕露,悬挂在下房屋的屋梁上,有人把这个过程叫挂锄。挂锄意味着杂草灭迹,庄稼成熟,人们稍作休息,为秋收做好准备。
自从有了除草剂,锄头基本下岗,偶尔派上用场,大多时间,隐匿在一个角落里。
挖鼠洞
挖鼠洞,少时一段趣事,回味起来,记忆犹新。
在我们家乡常见的鼠,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田鼠,它生活在田间地头,尾巴短短,身体胖胖,在田埂,渠埝高处打洞,一来防止雨水倒灌,二是保持鼠洞干燥清爽;还有一种是老鼠,俗称耗子,嘴巴尖尖,尾巴长长,颜色稍黑。
田鼠与老鼠,生活习性不同。虽然,统称为鼠科动物,但却不一样。田鼠的嘴里有两个储存袋,食物充足时,它会把食物放在袋里,带回窝里,储存起来,已备冬天和食物匮乏时享用,这种鼠大都生活在田地里。老鼠嘴巴两侧没有囊,也没有储存食物的习性,它们一般生活在人类住宅角落的鼠洞里,与人们分享入仓粮食和食物。人们非常讨厌它,自古便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臭名,所以这种动物异常怕人,警惕性很高,夜间觅食。
挖鼠洞,当然就是要挖田鼠的洞,把田鼠储存起来的粮食取出来。挖鼠洞始于何年何代,我无从考证,由来已久吧!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特别匮乏,为了解决食物问题,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向鼠口夺粮,挖鼠洞盛行。在我小时候,每到秋天,孩子都要去寻找鼠洞,有时候大人也在其中。
挖鼠洞一般扛上铁锹,带上口袋到收割完庄稼地里去寻找鼠洞和鼠山,所谓的鼠山,就是田鼠挖洞时挖出的土,往往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土堆,称为鼠山。找鼠山有技巧,一般要到豆子、玉米、高粱地里去找,鼠洞周围地里种啥庄稼,鼠窝里定会有啥粮食,我喜欢到黄豆地里去寻找。
看到的鼠山比较大,则老鼠比较大,鼠洞亦比较大,储存的粮食亦比较多。若鼠山土质新鲜潮湿,说明近期田鼠仍在活动,收获便有八九成希望。当找到了鼠山,可以在它的附近寻找另外一个洞口了,而这个洞口必须是直上直下的,无比光滑,还要有田鼠爬行的痕迹,否则你不用去挖,一定是个笨鼠,或废弃的鼠洞,洞中不会有粮食。找到洞口,顺着洞口一直挖下去,这时的鼠洞往往会分成几个分支,分别通往它专用的卧室、活动区和仓库。所以遇到分支,可分头去挖,一般情况,我们会用杂草把各分支的洞口堵上,作为标记,先挖其中的一个,待挖完后再挖其他的。
田鼠的粮仓,为了安全,往往把洞从里面堵死。所以我们在挖掘的过程中一旦不见洞了,必须仔细的寻找,从土的颜色和土的硬度判断,一般它堵的土比四周的土要松软一点,而且颜色也会有所不同。就这样一直挖下去,如找到粮仓,大家会高兴万分,免不了要手舞足蹈的高兴一阵子。然后争抢着小心翼翼地把粮食抠出来,装入袋子。多时可以一二十斤,当然也可能一无所获。有人说,正在哺乳的母鼠洞,一般食物很少,挖到它,算你运气不佳,只能是空手而归了。如挖到田鼠的活动室或卧室,且田鼠也在窝里,它会突然的窜出来,吓人一跳,也会给同伴们带来一点刺激,大家会满地的追逐它,尽情的嬉戏,直至把它整死,少有逃生的,回想起来,有些“残忍”。
实际上有些田鼠把粮食保存很好,用水淘一淘,大多可充作人的口粮了,不好的也可以喂猪和鸡鸭鹅,当然这是大人们考虑的事情。我们只知道挖鼠洞,找粮食,一天好的时候可以收获二三十斤,有收获,心情可想而知。少年这样的一段经历,回想起来感慨颇多……
听蟹
“听蟹”,是祖辈遗传下来的传统捕蟹方法。听蟹最好的季节是秋末冬初,也是河蟹的繁殖季节,一般这个时侯听蟹收获颇丰。
我第一次听蟹是在一九六七年,一个月清风高的晚上,与老九、小安子一起准备好工具。在家里简单地把小提灯用抹布擦拭一番,小提灯是听蟹的主要工具,呈园桶状,上边有一个伞状盖,周围玻璃罩,可防风吹,上下可以排烟通风,在当时国营商店里有销售,如今差不多已成文物了。一个月前应马振得邀请参观兴家坨“天津兴家民俗博物馆”时见过这些东西。
因为,听蟹一般都是在晚上,出发前我们也必须简单装束一下。穿起满是补丁的老棉袄防寒,各自便提起小提灯,带着小方凳,拿起小网兜,腋下夹两捆稻草,在家里提前点亮了小提灯,说说笑笑,亮堂堂出去了。出门后,一直往南走不远,便来到一个小木桥上,小木桥不是很大,终年流水,村里人都叫它“看青桥”。
天尚未黑透,一轮明月已高高地悬在深蓝色的夜空中。水稻已收割完,田里光光秃秃的,仅剩下矮矮的稻茬和咸水沟几根芦苇。不远处是两个生产队集中存放打轧稻草垛与粮食的场院。每一个场院都有一排小房子,那是护场人员休息和存放工具的地方,因为有人看管,小屋里发出微弱的光。深秋的西北风冷飕飕的,我们站在桥头,禁不住寒战连连。
仔细观察一下地形,预测出螃蟹可能出水行走的路线,选择好位置,安放好小凳子,又将小提灯稳稳放在上面,待一切安顿好,我们便躲在暗处,簇拥在一起,或爬、或蹲在铺有稻草土坡上,一动不动,静静地期待着螃蟹自己爬上来……那时的老壕沟,长满厚厚的芦苇,水沟挺深,下游与蓟运河相连,上游是六百亩水稻田。这个沟的水质好,鱼虾肥,螃蟹较多。
“螃蟹能上来吗?”我问,老九说“不着急,不要说话,慢慢听……”静默中,不知又过了多久,忽听得流水中“咕咚咕咚、哗啦啦”响,“有了。”我急忙欠起身跑过去在沟坡上,抓到一只,忙拿到灯光下观看,一只黑背白肚两螯长满茸毛的大蟹,拿在手上还张牙舞爪,这边才放入网兜里,水沟里又有响动,老九又从水边抓起一只,也是大蟹,毛却不多。
“螃蟹真是呆子,这么好抓”。其实不然,那一日晚上,再也没有一个螃蟹爬上来。后来,老人们告诉,先上来的螃蟹是“探子”,是“侦察兵”,不能捕捉。否则,后边的河蟹就不会上来了;你若不抓它们自然会源源不断,成群结队,涌上岸来。
这些年,我慢慢揣摩这其中的奥妙,大约是这灯光诱惑、流水和生活习性的缘故吧,也未可知。
(王来峰)
相关人物
王来峰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宁河区
相关地名
相关专题
锄头
相关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