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庆云
| 内容出处: | 《天津第一座發電厂》 图书 |
| 唯一号: | 020020020230026129 |
| 颗粒名称: | 于庆云 |
| 分类号: | K82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141-151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于庆云在电厂附近长大,先是作为油匠的儿子进入电厂工作,然后因为工作努力被工头嫉妒并被开除出厂。后来,他通过练武和保护工会,展现了工人的勇气和决心。在冲突中,他虽受了伤,但最终他和他的同伴们通过群体力量成功抵抗了工贼的攻击。 |
| 关键词: | 于庆云 人物传略 天津市 |
内容
我們是道地的天津人。而且就是电厂左近,獅子外一带的老住戶,我父亲是眼瞅着电厂盖起来的人。他是油匠,后来經人介紹便到电車厂做长工了。我小的时候,順着河垻找生活之路,撿馬鬃,打“小闊”。后来大些了,便由父亲煩人,也把我带进电車厂来了。子傳父业,也是干油匠,帮着擦車。我由小儿就爱惜父亲的那几把油刷子,刷出来,要紅便紅,要白就白,任怎么髒啊,旧啊,破啊的东西都能变得漂漂亮亮,看着心里痛快,特別喜欢。干起活来眞入迷。要是干得“草鷄”一些,不用人說,自己先憋得慌。又受我父亲的影响,懂得做活的不怕出汗这个道理,凡是上岁数的师付們,有个登梯爬高的地方,我总是搶着来。大伙也說:“这孩子是好样的。”那年月,咱們工人是給比国佬干,誰肯卖力气啊?都是比划比划,点到即止。特別是打夜班,有几个睜眼干到底的。我那年才十四岁,熬一宵也够嗆。有天,擦着擦着車,我在上面打盹儿了。偏也巧,讓工头瞧見。这小子心里早憋着碴儿呢,嫌我楞头楞腦,不懂得巴結他,不給他送礼。于是悄悄跑到洋人那里,給我上了个报吿,借刀杀人,竟把我开革出厂!大伙一听我被革了,都和工头鬧騰起来,說他:“这么好的孩子,你这么办,太缺了!”工头也会裝蒜,說是原来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那曉得眞給开革了呢!鬧也白鬧,再搭上那年月腦子里有这么一种思想,凭手艺吃飯,不低头不求人。走就走吧。
可是,过了一年,我又回来了。是大伙說的,“活重,叫老大回来吧,那是个好孩子。”我父亲当然乐意,我就又来擦車了。見天見擦車完了,一下班,年輕輕的工人們,专有一帮子坏人勾引,出电車厂不远就是六合市場,那儿有下等娼窑,有人就到那里打茶围,寻欢逐乐。有些才十七八、二十上下来岁的工人,居然鬧上花柳病,把一生都糟塌了,旧社会那眞是到处安排陷阱,除了剝削、压榨工人之外,还給开这么一条腐爛人們的坏道。来来去去的熟了,有住在厂子里修閘瓦的孙师付,他就嘱咐我:“可別跟他們一道混。一走那条道,这一輩子就完啦。要爱惜身体。来,跟我侄子練武吧!”他侄子練杠子很有名,还出过国。从这儿起,我也跟着練上了,那时候还眞不含糊,十八般武艺,那样都能来兩下子。可惜,沒有練长。这倒不是我沒恒心,是生活条件不允許。要鍛煉身体,在那年月,沒錢沒閑功夫怎么能行?
不过,就凭这点不到家的拳脚,居然給咱們工人做了点事。1929年鬧罢工的时候,領着一撥糾察队,截住围城电車的便是我。我那时的名字叫于世淸。二一次,1932年鬧罢工,复工以后,我們工人里,选了一撥人保护张广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惜那次我沒遇上暗害广兴的那撥子地痞流氓,要不的話,可是有热鬧瞧了,兴許出了人命。
給大伙出气的是这么一回事。张广兴不是遇刺了么?好哇,工賊刘治倫就派他手下的那些腿子們,車厂电厂到处吹風,說张广兴是蛤蟆伸腿强撑劲儿,不行啦。說要搞工会得跟着他們。乘这机会,要倒我們的工会。我們就和他們理論开了。大伙支持我們,不支持他們。这些小子們有官面势力,有买办林子香給撑腰,于是就买通了門口的警察注意我們,刁难我們。
这天,我們正擦車呢,警察上来了,繞处检查。我心里納悶,这怎么啦?就問:“你上車找什么?”
“說你們藏着刀子,要打群架。”
“誰报吿的?你翻吧!”
沒翻着。警察下車了,斜眼和我們說:“你們可老实点。”
我們一寻思,这准是工賊刘治倫他們給使的坏。倒提我們个醒儿,我們就留神了。晌午在喝茶的地方,这些小子們又在吹風:“张广兴完蛋了,誰跟着他,誰倒霉呀。”
我們十八个人一忽拉子把他們十二个人围上了。我揪住一个問:“你說什么?誰要倒霉!”
这小子喊了一声,“你要倒霉!”过来就揍架。打架他們不是个。我一冒火,抄起一个斧把,照那小子就砍。砍起来的时候,我心里一动,这一斧子下去还有他的命哪?临时換腕子,斧把改做刃背了。就这一下也够嗆,这小子腦袋开花,鲜血直冒,立时暈倒在地上。
吓得这些工賊狗腿子們就要跑。跑,跑哪去?我們抄起火筷子,抄起什么合手就抄什么。砍来砍去的,直到有个穿黃衣服的来拉架。我也沒看淸他是誰,伸手搧了亠个嘴巴子,竟从这边把他搧到那头去。他这才喊:“你們怎么連我也打,我是巡长,我是拉架的。”
一怔神的工夫,兩个警察把我揪住。我說,“你揪什么?跑的了和尙,跑不了庙,打官司咱們走。”
厂里厂外,好哇,称得起是人山人海,到底官面儿相着他們,把我們十八个人用绳牽着,他們十二个人空着手,到派出所去了。捆也白捆,那些家伙們头破血出,反正是吃了亏。
在派出所里,那个狗官更是买卖人的秤砣,一头沉。和我瞪眼珠拍桌子嚷:“你們要造反哪!我要重办你們!”想唬着我們,把事了啦。
我說:“去你一边的吧!办不办,你管不着!我們打官司去。”
“你們犯大罪了,你知道知道?”
我說:“犯多大罪,你尽管写。你越写得狠越好。我們不在乎。事情你管不了,你別吹胡子瞪眼的,少給我們来这一套!”巡长吃了一个大窩脖,这家伙把我們送公安局了。用卡車裝我們走的,五个警察拿盒子槍押車。到公安局里却变了个样,把他們几个头破血出的伤号倒撂在外边了,我們却到屋里坐着歇凉。看监的警察还直說,“吓,这么大热天,小哥几个怎么干这事呀?你們为嘛呀?”
我們就怎么长怎么短的,从打电車罢工那儿一直說到今天的事儿。一提电車罢工,那是全天津市沒人不知道的事儿。連警察也挑大拇哥,說:“你們哥几个是好样的,喝水不?我給你們弄点去。”他还出主意,“要是喝水,就得吃东西,吃足喝飽了,好頂足劲打官司呀!”我們也說对。可是那来的錢呢?这倒不用操心,我們工会早把錢使过了。一布袋子的燒餅跟着就送过来。怪不得警察偏向着我們呢。
那几个工賊狗腿子倒是搗邪霉了。事情鬧到这份上,比国佬跟林子香不肯大把儿使錢、沒有我們来的快。看着我們又吃又喝,他們在外面晒太阳,又是头破血出的,格外口渴,就凑到自来水管子底下,喝凉水。喝凉水也不行,警察就駡他們:“他媽旳,那水是給你們喝的?”順手就抽了孙××兩鞭子。这条狗当时嘆了口气,和那几个人說:“咱們这是何苦来呢?到处挨駡,受这份洋罪,刘治倫跟林子香也不管不問了。”哈哈,这小子也后悔了呢!
从公安局又把我們解到法院。临上車的时候,司机也說:“你們哥几个是好样的,我給你們开快車,五分鐘准到法浣。那几个小子,讓他們坐悶子車,大热天的,烤着这些兎崽子們。”我們明白,連司机这儿,錢也花到了。
到了法院,法官問了几句,来个当場取保釋放。司法警跟我們出来,扯着大嗓門就喊:“你們可找保呀,找不着,押监!”
我們就悄悄和他們說:“辛苦一趟吧,您們老兩位。取了保,我們得謝謝您。不能讓您白跑道。”
司法警一看我們这些工人懂行,也就不嚷了,只是說:“快走,快走。”
那年月,全天津市干电料行,做修理电灯电綫业务的,沒有一家本和电車电灯公司职工勾着。而且有不少职員、工头在外面就开着小电料行。他們都干偸电的业务。所以我們找电料行打保,一找一个准。我們坐車奔南市了。就在我們一位同事开的电料行里取了鋪保,又借了四塊錢,一个法警兩塊,算是把事情了啦。
从这起,我們可失业了。公司以聚众斗歐为名,把我們兩边三十多号人全开革了。这是我二一次被开除。其实,开除事小,比国佬跟林子香搗鬼,那才是大事呢。他們暗含着把那十二不打手养起来了,还叫他們出头吿我們,打算用这个办法,連张广兴在內,一起都咬进去。我們也不含糊,工会暗中支持我們,也和他們沒完沒散,到法院傳訊的时候,我們就找了个开业的大夫,开个有病的証明,这次他們几个有病,下回我們几个又不舒坦,泡来泡去,官司也就不了了之。旧社会的事就是这样。买办林子香一看咬我們咬不住,他就另出花招,叫那十二个工賊打手上班复工。事机不密,早有人給我們送信来了。預先商量好,工人們在里面往外打,我們由外面向里打。反正他們不能上工。这些小子們讓我們打怕了。一瞧見我們在厂子外面等他們,扭头就跑,复工沒复成。后来在电厂、公司都讓我們堵过。这些小子想換个地方复工,也不行。我們只咬定一句,只要他們复工,我們就得复工。
这节骨眼上,国民党市党部又出头了。調解的人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員邵华(这人在1946年做过天津国民党市党部主委),由他出名,由林子香付賬,在登瀛;楼飯庄大摆筵席,給我們兩方調解。有道是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我們十八个人为了防备一手,特地坐膠皮車去的。进这么大的飯館子是头一遭。連站崗的法租界巡捕都看着扎眼,竟問:“你們是干什么来的?”倒是飯庄子人摸底,說道:“是給他們了事的。有市党部的人。”这才算沒干涉我們。
坐在飯桌前面,又是淸蒸白鴨,又是紅燒魚翅,可我們兩只眼却尽着搜索,生怕他們有埋伏,到时候再給我們下了手。这工夫,邵华站起来了,把酒杯一举,开言道:“看我邵华的面子,得啦,你們都是工人,自家兄弟嘛,也別說誰挨了打,誰打了人,我給双方調解。我喝你們大家一杯喜酒吧。”說罢,腦袋一揚,一飲而尽。
跟着,林三林子香也站起来,假門假氏的,他也举着洒杯,說道:“邵委員,我不能駁你的面子。都听你的啦。”也是咕嘟一口,一飮而尽。
那边也說了話,他們有人养着,自然乐意和解。我的十八个人一看,这是硬打鴨子上架。不哼声,光在下面用手你〓我,我〓你的。
邵华以为这么大的飯庄子,这么豪华的酒席,特別是他这么个人物在这儿一摆,把我們唬住了呢。就說:“要是听我的,我給出个主意,你們兩边都不要爭竞,讓公司尽最准許你們复工,挑誰就是誰。”
我二虎头的脾气,这时候忍不住了。霍地一下子站起来。原来也想說几句客气的話,可是舌头不受使,一說話就倔他老大一塊的。“要是这样,你調解不調解不吃紧。
要复工都复工。由公司挑,他們一个也不挑我們。我們还是法院解决。
气得邵华把桌子一拍。嚷道:“到法院你們就能解决嗎?你們有罪,你們明白不明白?”
“有靠法院治罪,你不用操这份心!”
这时候,我們又有一位站起来說話了,就講:“我們都是工人,粗魯人,不会說話。你別生气。今夫承邵委員出来和我們岀面調解,你这么大的面子……”
我嫌他这話太軟,登时插了几句,“別忘啦,有句老話,露多大的臉,現多大的眼!”
气的邵华又一拍桌子。他叫起来:“我不管你們的事了!”小臉儿鉄靑,酒沒再喝,菜也沒吃。
活該。我們哥几个是魚啦,肉啦,風卷殘云,吃完了赶紧都溜了。
不过,跟他們干到底,我們就不行了。刀把攥在人家手里,我們那儿講理,那儿說話去呢?张广兴被捕的当天,一早晨,我們見天見碰头的那个工会秘密所在也讓警察和便衣抄了!恰巧我守在那儿。在網的难逃,本来也要带我們走的,有个便衣說了这么句話:“他們大字不識,共产党不够資格;都他媽的穷光棍,逮他們干嘛呀!”算是網开一面,只把我們赶出来,把房子封了。
沒了头儿,沒了工会,也不好斂会費了,我們靠工会那倆錢活不下去了。大伙儿就說:“咱們也各奔西东,找自己的飯路去吧!”
飯路哪那么好找?我一想,找公司去,跟买办林三要养老金去。林子香听說是我来啦。居然把我叫进他屋,請我在沙發上坐下,笑嘻嘻的說:“你要回来,还可以呀。你要早听我的,够多好。”
我懂得他話里有話,就說:“我是个工人,拉大伙的肉貼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討愧呀。我不能那么办。你給我养老金吧!”
看收买不了我。他还嘆口气:“你是傻子。我留不住你啦。这倆养老金够你吃几天的?”
我吃养老金干什么?我还是耍手艺啊。在外边干零活,干来干去的,瓦匠头王四把我找到电厂来了,在这儿干包工活。一进厂,大伙都認識我:“这不是糾察队的于世淸嗎?这不是斧劈工賊的于老大嗎?”都說:“你在这儿干不长。”
可不,馬上讓比国佬知道了,把包工的王四找了去,說:“他要是在厂里鬧事,你可得負責任。”
王四一拍胸脯,“我使喚的人,你放心,不好的我不要。”
我又不是在厂里做长工和短工,是跟王四来做包活。比国佬也管不了。也就不問了。
由这开的头,电厂里有什么油活,浆活,經常的王四就派我去,我里头净是熟人,干起活来方便。有回,是給新来的总办家油葡萄架,我一个人連踢带打。那个总办看我干活認眞,又叫我到公司去刷房子,刷浆的时候,他經常去看,哪时看哪时我都在工作。这天他竟在下面喊:“木須赵!”①吓我一跳,还以为是那儿活做的不称洋鬼子的心了呢。后来赵翻譯进来把总办的話和我說了:“看你很眼熟。你工作做的不錯,你在那里做过活儿?”我連忙順梯子下来,实話实說。
剛說了兩句,赵翻譯便把話接过去了。他給圓了几句謊。还說:“外国人想补你长工,你得改个名字。”人家这是給我开道。我当然連忙点头。从这儿起,我改名叫于庆云了。
一晃在电厂里干了小三十年。这三十年,說起来慚愧,我沒做什么事。只是因为干油漆活,和木厂子熟,遇①法文赵先生的意思。上电厂里的工人有办白事的,我就热情地去給他們張罗。也就因为做这些事做多了,解放后,成立我們工人自己的工会时,居然把我选做了工会劳保委員。我一听,头大了,党委書記曹化一和我說;“老于,你給大家办点福利事吧。这不比先前好办多了嘛?”是呀,好办自然是好办多了。不过,我常想一个老工人对国家难道就只这么点貢献么?說起来,我实在覚着討愧呀!
可是,过了一年,我又回来了。是大伙說的,“活重,叫老大回来吧,那是个好孩子。”我父亲当然乐意,我就又来擦車了。見天見擦車完了,一下班,年輕輕的工人們,专有一帮子坏人勾引,出电車厂不远就是六合市場,那儿有下等娼窑,有人就到那里打茶围,寻欢逐乐。有些才十七八、二十上下来岁的工人,居然鬧上花柳病,把一生都糟塌了,旧社会那眞是到处安排陷阱,除了剝削、压榨工人之外,还給开这么一条腐爛人們的坏道。来来去去的熟了,有住在厂子里修閘瓦的孙师付,他就嘱咐我:“可別跟他們一道混。一走那条道,这一輩子就完啦。要爱惜身体。来,跟我侄子練武吧!”他侄子練杠子很有名,还出过国。从这儿起,我也跟着練上了,那时候还眞不含糊,十八般武艺,那样都能来兩下子。可惜,沒有練长。这倒不是我沒恒心,是生活条件不允許。要鍛煉身体,在那年月,沒錢沒閑功夫怎么能行?
不过,就凭这点不到家的拳脚,居然給咱們工人做了点事。1929年鬧罢工的时候,領着一撥糾察队,截住围城电車的便是我。我那时的名字叫于世淸。二一次,1932年鬧罢工,复工以后,我們工人里,选了一撥人保护张广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惜那次我沒遇上暗害广兴的那撥子地痞流氓,要不的話,可是有热鬧瞧了,兴許出了人命。
給大伙出气的是这么一回事。张广兴不是遇刺了么?好哇,工賊刘治倫就派他手下的那些腿子們,車厂电厂到处吹風,說张广兴是蛤蟆伸腿强撑劲儿,不行啦。說要搞工会得跟着他們。乘这机会,要倒我們的工会。我們就和他們理論开了。大伙支持我們,不支持他們。这些小子們有官面势力,有买办林子香給撑腰,于是就买通了門口的警察注意我們,刁难我們。
这天,我們正擦車呢,警察上来了,繞处检查。我心里納悶,这怎么啦?就問:“你上車找什么?”
“說你們藏着刀子,要打群架。”
“誰报吿的?你翻吧!”
沒翻着。警察下車了,斜眼和我們說:“你們可老实点。”
我們一寻思,这准是工賊刘治倫他們給使的坏。倒提我們个醒儿,我們就留神了。晌午在喝茶的地方,这些小子們又在吹風:“张广兴完蛋了,誰跟着他,誰倒霉呀。”
我們十八个人一忽拉子把他們十二个人围上了。我揪住一个問:“你說什么?誰要倒霉!”
这小子喊了一声,“你要倒霉!”过来就揍架。打架他們不是个。我一冒火,抄起一个斧把,照那小子就砍。砍起来的时候,我心里一动,这一斧子下去还有他的命哪?临时換腕子,斧把改做刃背了。就这一下也够嗆,这小子腦袋开花,鲜血直冒,立时暈倒在地上。
吓得这些工賊狗腿子們就要跑。跑,跑哪去?我們抄起火筷子,抄起什么合手就抄什么。砍来砍去的,直到有个穿黃衣服的来拉架。我也沒看淸他是誰,伸手搧了亠个嘴巴子,竟从这边把他搧到那头去。他这才喊:“你們怎么連我也打,我是巡长,我是拉架的。”
一怔神的工夫,兩个警察把我揪住。我說,“你揪什么?跑的了和尙,跑不了庙,打官司咱們走。”
厂里厂外,好哇,称得起是人山人海,到底官面儿相着他們,把我們十八个人用绳牽着,他們十二个人空着手,到派出所去了。捆也白捆,那些家伙們头破血出,反正是吃了亏。
在派出所里,那个狗官更是买卖人的秤砣,一头沉。和我瞪眼珠拍桌子嚷:“你們要造反哪!我要重办你們!”想唬着我們,把事了啦。
我說:“去你一边的吧!办不办,你管不着!我們打官司去。”
“你們犯大罪了,你知道知道?”
我說:“犯多大罪,你尽管写。你越写得狠越好。我們不在乎。事情你管不了,你別吹胡子瞪眼的,少給我們来这一套!”巡长吃了一个大窩脖,这家伙把我們送公安局了。用卡車裝我們走的,五个警察拿盒子槍押車。到公安局里却变了个样,把他們几个头破血出的伤号倒撂在外边了,我們却到屋里坐着歇凉。看监的警察还直說,“吓,这么大热天,小哥几个怎么干这事呀?你們为嘛呀?”
我們就怎么长怎么短的,从打电車罢工那儿一直說到今天的事儿。一提电車罢工,那是全天津市沒人不知道的事儿。連警察也挑大拇哥,說:“你們哥几个是好样的,喝水不?我給你們弄点去。”他还出主意,“要是喝水,就得吃东西,吃足喝飽了,好頂足劲打官司呀!”我們也說对。可是那来的錢呢?这倒不用操心,我們工会早把錢使过了。一布袋子的燒餅跟着就送过来。怪不得警察偏向着我們呢。
那几个工賊狗腿子倒是搗邪霉了。事情鬧到这份上,比国佬跟林子香不肯大把儿使錢、沒有我們来的快。看着我們又吃又喝,他們在外面晒太阳,又是头破血出的,格外口渴,就凑到自来水管子底下,喝凉水。喝凉水也不行,警察就駡他們:“他媽旳,那水是給你們喝的?”順手就抽了孙××兩鞭子。这条狗当时嘆了口气,和那几个人說:“咱們这是何苦来呢?到处挨駡,受这份洋罪,刘治倫跟林子香也不管不問了。”哈哈,这小子也后悔了呢!
从公安局又把我們解到法院。临上車的时候,司机也說:“你們哥几个是好样的,我給你們开快車,五分鐘准到法浣。那几个小子,讓他們坐悶子車,大热天的,烤着这些兎崽子們。”我們明白,連司机这儿,錢也花到了。
到了法院,法官問了几句,来个当場取保釋放。司法警跟我們出来,扯着大嗓門就喊:“你們可找保呀,找不着,押监!”
我們就悄悄和他們說:“辛苦一趟吧,您們老兩位。取了保,我們得謝謝您。不能讓您白跑道。”
司法警一看我們这些工人懂行,也就不嚷了,只是說:“快走,快走。”
那年月,全天津市干电料行,做修理电灯电綫业务的,沒有一家本和电車电灯公司职工勾着。而且有不少职員、工头在外面就开着小电料行。他們都干偸电的业务。所以我們找电料行打保,一找一个准。我們坐車奔南市了。就在我們一位同事开的电料行里取了鋪保,又借了四塊錢,一个法警兩塊,算是把事情了啦。
从这起,我們可失业了。公司以聚众斗歐为名,把我們兩边三十多号人全开革了。这是我二一次被开除。其实,开除事小,比国佬跟林子香搗鬼,那才是大事呢。他們暗含着把那十二不打手养起来了,还叫他們出头吿我們,打算用这个办法,連张广兴在內,一起都咬进去。我們也不含糊,工会暗中支持我們,也和他們沒完沒散,到法院傳訊的时候,我們就找了个开业的大夫,开个有病的証明,这次他們几个有病,下回我們几个又不舒坦,泡来泡去,官司也就不了了之。旧社会的事就是这样。买办林子香一看咬我們咬不住,他就另出花招,叫那十二个工賊打手上班复工。事机不密,早有人給我們送信来了。預先商量好,工人們在里面往外打,我們由外面向里打。反正他們不能上工。这些小子們讓我們打怕了。一瞧見我們在厂子外面等他們,扭头就跑,复工沒复成。后来在电厂、公司都讓我們堵过。这些小子想換个地方复工,也不行。我們只咬定一句,只要他們复工,我們就得复工。
这节骨眼上,国民党市党部又出头了。調解的人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員邵华(这人在1946年做过天津国民党市党部主委),由他出名,由林子香付賬,在登瀛;楼飯庄大摆筵席,給我們兩方調解。有道是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我們十八个人为了防备一手,特地坐膠皮車去的。进这么大的飯館子是头一遭。連站崗的法租界巡捕都看着扎眼,竟問:“你們是干什么来的?”倒是飯庄子人摸底,說道:“是給他們了事的。有市党部的人。”这才算沒干涉我們。
坐在飯桌前面,又是淸蒸白鴨,又是紅燒魚翅,可我們兩只眼却尽着搜索,生怕他們有埋伏,到时候再給我們下了手。这工夫,邵华站起来了,把酒杯一举,开言道:“看我邵华的面子,得啦,你們都是工人,自家兄弟嘛,也別說誰挨了打,誰打了人,我給双方調解。我喝你們大家一杯喜酒吧。”說罢,腦袋一揚,一飲而尽。
跟着,林三林子香也站起来,假門假氏的,他也举着洒杯,說道:“邵委員,我不能駁你的面子。都听你的啦。”也是咕嘟一口,一飮而尽。
那边也說了話,他們有人养着,自然乐意和解。我的十八个人一看,这是硬打鴨子上架。不哼声,光在下面用手你〓我,我〓你的。
邵华以为这么大的飯庄子,这么豪华的酒席,特別是他这么个人物在这儿一摆,把我們唬住了呢。就說:“要是听我的,我給出个主意,你們兩边都不要爭竞,讓公司尽最准許你們复工,挑誰就是誰。”
我二虎头的脾气,这时候忍不住了。霍地一下子站起来。原来也想說几句客气的話,可是舌头不受使,一說話就倔他老大一塊的。“要是这样,你調解不調解不吃紧。
要复工都复工。由公司挑,他們一个也不挑我們。我們还是法院解决。
气得邵华把桌子一拍。嚷道:“到法院你們就能解决嗎?你們有罪,你們明白不明白?”
“有靠法院治罪,你不用操这份心!”
这时候,我們又有一位站起来說話了,就講:“我們都是工人,粗魯人,不会說話。你別生气。今夫承邵委員出来和我們岀面調解,你这么大的面子……”
我嫌他这話太軟,登时插了几句,“別忘啦,有句老話,露多大的臉,現多大的眼!”
气的邵华又一拍桌子。他叫起来:“我不管你們的事了!”小臉儿鉄靑,酒沒再喝,菜也沒吃。
活該。我們哥几个是魚啦,肉啦,風卷殘云,吃完了赶紧都溜了。
不过,跟他們干到底,我們就不行了。刀把攥在人家手里,我們那儿講理,那儿說話去呢?张广兴被捕的当天,一早晨,我們見天見碰头的那个工会秘密所在也讓警察和便衣抄了!恰巧我守在那儿。在網的难逃,本来也要带我們走的,有个便衣說了这么句話:“他們大字不識,共产党不够資格;都他媽的穷光棍,逮他們干嘛呀!”算是網开一面,只把我們赶出来,把房子封了。
沒了头儿,沒了工会,也不好斂会費了,我們靠工会那倆錢活不下去了。大伙儿就說:“咱們也各奔西东,找自己的飯路去吧!”
飯路哪那么好找?我一想,找公司去,跟买办林三要养老金去。林子香听說是我来啦。居然把我叫进他屋,請我在沙發上坐下,笑嘻嘻的說:“你要回来,还可以呀。你要早听我的,够多好。”
我懂得他話里有話,就說:“我是个工人,拉大伙的肉貼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討愧呀。我不能那么办。你給我养老金吧!”
看收买不了我。他还嘆口气:“你是傻子。我留不住你啦。这倆养老金够你吃几天的?”
我吃养老金干什么?我还是耍手艺啊。在外边干零活,干来干去的,瓦匠头王四把我找到电厂来了,在这儿干包工活。一进厂,大伙都認識我:“这不是糾察队的于世淸嗎?这不是斧劈工賊的于老大嗎?”都說:“你在这儿干不长。”
可不,馬上讓比国佬知道了,把包工的王四找了去,說:“他要是在厂里鬧事,你可得負責任。”
王四一拍胸脯,“我使喚的人,你放心,不好的我不要。”
我又不是在厂里做长工和短工,是跟王四来做包活。比国佬也管不了。也就不問了。
由这开的头,电厂里有什么油活,浆活,經常的王四就派我去,我里头净是熟人,干起活来方便。有回,是給新来的总办家油葡萄架,我一个人連踢带打。那个总办看我干活認眞,又叫我到公司去刷房子,刷浆的时候,他經常去看,哪时看哪时我都在工作。这天他竟在下面喊:“木須赵!”①吓我一跳,还以为是那儿活做的不称洋鬼子的心了呢。后来赵翻譯进来把总办的話和我說了:“看你很眼熟。你工作做的不錯,你在那里做过活儿?”我連忙順梯子下来,实話实說。
剛說了兩句,赵翻譯便把話接过去了。他給圓了几句謊。还說:“外国人想补你长工,你得改个名字。”人家这是給我开道。我当然連忙点头。从这儿起,我改名叫于庆云了。
一晃在电厂里干了小三十年。这三十年,說起来慚愧,我沒做什么事。只是因为干油漆活,和木厂子熟,遇①法文赵先生的意思。上电厂里的工人有办白事的,我就热情地去給他們張罗。也就因为做这些事做多了,解放后,成立我們工人自己的工会时,居然把我选做了工会劳保委員。我一听,头大了,党委書記曹化一和我說;“老于,你給大家办点福利事吧。这不比先前好办多了嘛?”是呀,好办自然是好办多了。不过,我常想一个老工人对国家难道就只这么点貢献么?說起来,我实在覚着討愧呀!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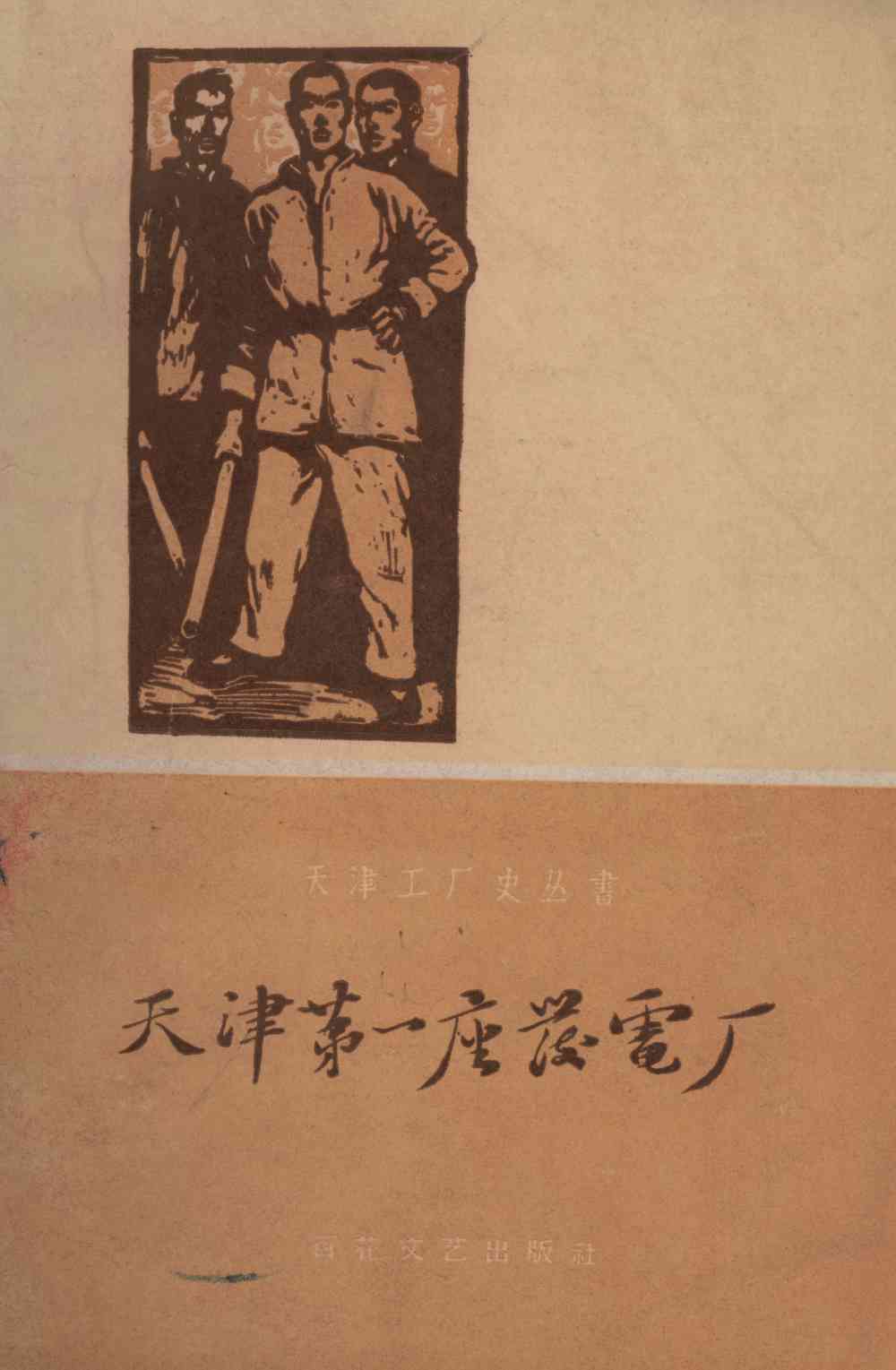
《天津第一座發電厂》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天津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和背景。该活动受到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鼓足了工人的干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阅读
相关机构
天津市电車电灯公司
相关机构
天津国民党市党部主委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天津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