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
| 内容出处: | 《天津第一座發電厂》 图书 |
| 唯一号: | 020020020230026123 |
| 颗粒名称: | 包身工 |
| 分类号: | F246 |
| 页数: | 20 |
| 页码: | 87-106 |
| 摘要: | 该文主要讲述了包身工制度和工人与“棚杨”的斗争。 |
| 关键词: | 压迫 旧中国 工人阶级 |
内容
国民党接收大員“五子登科”唱的这么热鬧,难道工人們眼巴巴的光瞧着嗎?把头工賊任意橫行,难道工人們蔫搭搭的就任他們摆布嗎?沒那个事!工人們有話,“就凭你們这群腦袋呀!你們这些料貨呀!哼,瞧着吧!”偸、磨、泡、蹭几手絕活都照样来着。跟他們斗!
斗得最复杂,最綿长的要屬包身工这档子事了。
提起包身工来,电厂里流行着一首歌謠:“推煤推灰活像鬼,烟熏火燎趟着水,餓着肚皮跑細腿!”就說推煤推灰工人有多苦吧。原先,灰煤部的工人也是长工居多。到日本鬼子来了,因为大伙不給鬼子干,光見人不見活。鬼子沒轍了,于是想出了一个絕招,把活儿能包的全包出去,就这么多錢办这么多事,越省工越多拿錢,賠賺是包活的。推煤推灰的便也包出来,倒了几次手,最后这事儿,讓干棚匠包活的楊恩元悄悄花錢买动到手上。这小子可逮住發財的机会了。騎在推煤推灰的哥儿們头上,这小子里吃外拐,心黑手辣,又扣工錢,又放高利貸,眞是比狼都狠。包工大柜才干了几年哪,到国民党統治时期,这小子家里雇着老媽子,使喚着听差的,交結了一帮狐群狗友,吃吃喝喝,居然也是个財主了。就說他剝削了工人多少錢吧。恨得工人們直搓牙,管他叫“棚楊”。
可巧,这天“棚楊”来监工的时候發生了一件事。有个穿破袄的工人不小心,叫倒下来的殘火苗儿給燒伤了,不能干活。少一个人不行啊,一个蘿卜一个坑。“棚楊”沒法儿,把袖口一挽,大爷也玩一宵票,跟着推了一夜的軲轆馬。这一夜不吃紧,他是酒色掏空了的身子,架不住这点劳累,回家就倒在炕头,爬不起来了。包身工是現錢現卖,干一天領一天的工錢,他一連兩天沒露面儿,大伙可吃不住劲了,一合計,讓班长赵志淸上他家里要錢去。
老赵到了“棚楊”家里,由使喚老媽把他領进正屋。他还歪在炕上,哼唧着腰酸腿痛呢。赵志淸道了来意,說是:“你得給錢,我們包身工沒錢吃飯啦。”“棚揚”心里直嘀咕,生怕包子露了餡,可他又病的起不来,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个便条,讓赵志淸拿了他的圖章到厂里取錢。临完,他千嘱咐万嘱咐的說:“你就凭条領錢,領多少是多少,任嘛事不用問。你明白啦嗎?”
赵志淸兩眼一碼儿黑,認不得半个大字。可他心里豁亮,准知道“棚楊”这里头有鬼。你不是不讓問么,他偏要找个識字的問問。拿回来,讓哥儿們里喝过一点墨水的孙志欽看看。老孙綽号“算天星”,他就朝大伙念叨:“看啊,‘棚楊’吃咱們吃的太狠啦!”大伙一听那个数,火苗儿一窜老高。眞是,狼吃人还得剩堆骨头呢,他这小子吃人,居然連骨头渣子也一塊呑哪!包工錢是三七分,白袖口一卷,先剝三成去,这且不提,怎么大伙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只領八个鐘点的錢呢?那四个小时都讓他昧起来了。这还行,大伙决定吿他去。
头一状吿到厂长张景泰那里去。张景泰倒干脆,說了一句話:“胡鬧!”
哥儿們里头还有一位会出主意的魯克恭,就由他煩人写了一个呈子,遞到伪社会局去。厂里不管,咱們是厂外折騰。伪社会局派一个戴金絲眼鏡,穿洋服的人見的魯克恭,一臉不耐煩的神气,不等魯克恭話說完,这小子就截住問:“你們到底要干什么吧?”
“我們要求取消包工制!”
想不到他倒应家下来,叫过三兩天来听信儿。过了三兩天,魯克恭又去了,这位戴眼鏡的又叫再过三兩天,一来二去的跑了十几趟。他們的事情沒有办出眉目,倒是社会局这儿和张景泰,和“棚楊把事儿办好。戴眼鏡的拿到了他能拿到的那一份儿,也就不再照面了。連再过三兩天的話也沒了。魯克恭他們明白,这是給人家做飯吃,他們白跑这冤枉路了。
可是,他們还不知道,“棚楊”朝他們領头的下毒手了。这天,付班长肖景泉領班,垫手的破麻袋片沒有了。一推車,手上就得燙几个大燎泡。肖景泉就找“棚楊”要麻袋片,“棚楊”正抓碴儿呢,一看送上門来了,张口就駡:“你他媽的拿麻袋片当飯吃呀!三天兩头的要。沒有,沒有!”
肖景泉也窩着火呢,就嚷:“你不給不行!”
“我就不給,你敢怎么样?”說着兩人支巴起来了。
这时候,特务狗腿子张七来了。这小子在日本鬼子統治的时候,拿棍子抽人,到了国民党派儿,他还是拿棍子抽人,还是交报吿,轄制工人。他当然和“棚楊”是一头的,喊喝一声,叫腿子們一拥而上,把老肖,还有跟老肖一塊儿来的老王給按住,往大門外面一推。倒也干脆,开除了!
这能完嗎?当然不能完。老肖和老王就去吿“棚楊”俗話說的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吿来吿去,他們不光沒吿了“棚楊”,反倒被伪法院給他倆扣了个扰乱厂方的罪名,白白压了好几天监獄才放出来。案子就这样算完啦。哥儿們在里面使不上劲,只好嘆口气,先忍着。眼睜睜地看他們到別处去找飯路。
包身工的哥儿們里,有一位叫刘少波的,他是城里住家。这天下午剛迈大門,要去厂里接班。就見斜对門的閻大律师正往外送客。他眼睛尖,看那客人坐的三輪有点儿像“棚楊”的,連忙閃到一旁。从門縫里往外偸看,可不嗎,閻律师送的正是“棚楊”这小子。老刘登时心里犯了嘀咕,“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官司不是已經打完了嗎。干嘛还找律师呢?这小子还安着什么毒計啊?”
随后,他踱到律师的院里,喊了一声,“四爷在家嗎?”
“里边坐,里边坐。”閻律师和老刘是十多年的老鄰居,再搭上他这律师沒有干起来,所以对鄰居有个面。
进屋以后,老刘不用客气照直就問。閻律师也就实話实說。好呀,原来肖景泉他們官司打不过,低头算完啦;他“棚楊”可不算完,斬草要除根,买通律师想把赵志淸也給咬进去,也給押上一陣子,来个一脚踢。
是这么一計啊!刘少波連忙央吿律师:“您可不能这么办呀!‘棚楊’这小子可不是东西。我們班长赵志淸可是好人,人家‘扛着刀’,給我們大伙儿办事。您要这么一来,不把我們都毁了嗎?”
閻律师一想也对。一来是“棚楊”手紧,只〓了几盒烟錢,値不当的去缺德,二来是和刘少波十多年相識,知道他們这伙卖苦力气的哥儿們火气大,犯不上惹人,再給自己〓了大包。就說:“好吧,瞧咱們老街坊的面子,依你。我明天不給他出庭。”事情揭过去了。
刘少波一口气跑到厂子。赶紧給大伙送信。大伙一听,这份气大啦。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大伙抱团,跟他干到底啦。七嘴八舌的說:“給他挂队!罢工!”
有人就摆手不贊成。說道:“这是什么年月?找着讓‘棚楊’把咱們当成共产党八路送終啊!再說,他正巴不得把咱們踢开,另換一撥新人好使喚呢。”
有人就提:“咱們給他来个明着不擱暗里擱。上市政府找杜建时請願去。”又有人摆手:“杜建时是哪一头的?能向着咱們嗎?”
又有人贊成:“嗨,杜建时跟他一鼻孔出气也好,兩鼻孔出气也好;反正这小子得花錢买动!”
“对!”大伙劲头都上来了,“請願不准,咱們不掉肉,‘棚楊’可把錢包丢光了。对,对,哥儿們折騰光这小子!”
要請願就得有說辞,于是煩人写了八項条件。主要的条件是:从比商直至現在,灰煤部工人一向在厂內工作,且为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份。因之灰煤部工人应改为长工;取消一切包工制;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間应改为每天八小时;不許把头虐待、打駡工人。
遞上請願書,沒多久,国民党市政府批下来了,含含糊糊的一句話:“候飭查核办!”以后便石沉大海,渺无音信。大家等得怪悶气的,不办不离奇,准知道他們不給办,可是“棚楊”究竟花多少錢,出多大的血呢?怎么連这个动靜也沒有。
沒有不透風的篱笆,事情讓經常向电厂运煤的把头,张禿张亭善知道了。他說:“我給你們大伙出个主意吧,你們找安靑帮的头目人张逊之,拜师入帮,靠他的势力,国民党不說,連軍統中統也都有个面儿,准把‘棚楊’給拱下去。”
狗拿耗子,怎么他多管起閑事来了呢?把头攆把头,其实这小子也沒安好心眼,他是眼紅嘴饞,想夺“棚楊”的食,挤下“棚楊”,他好当包工头儿。
大伙一硏究,跟“棚楊”斗到这份上,沒路可走了。要是靠安靑帮的势力压下“棚楊”倒也不錯。死馬当作活馬医,每人凑了几个錢,給张逊之送礼,摆香堂,認师付,求他帮忙斗“棚楊”。
一晃,十天半拉月过去了。“棚楊”还是那股子牛劲,斜眼看人,恨不得把誰盯死。大伙儿一想,这不成啊,香堂白摆了是怎么的?哥儿捫凑了三十多个人找张逊之去了。別提有多巧,正碰上张逊之要出門。一見大伙,他在台阶上一站,撇着京腔,倒数叨了大伙一頓:“你們請回吧,原来你們是运焦子的。我这儿也是你們来的地方!”
說完走下台阶,揚着脖子,鑽进汽車里,开路了。大伙駡駡咧咧地不知怎么出这口恶气才好。
这时候,张逊之的办事人,穿着长袍、緞鞋踱了过来,朝大伙伸出四个手指,說道:“人家‘棚楊’使錢,买死啦,你們要想把事扭过来,得这个数。”
这四个手指头就是西十袋面錢的意思。大伙一听,唧唧嚷嚷开了鍋:“要是有四十袋面,誰来你这儿啊!”
“这不是拿我們穷哥儿們炸肉醬玩嘛!”……
大伙沒有搬动“棚楊”,“棚楊”可不饒大伙啊。事情全是班长赵志淸出的头。他成了“棚楊”眼中的毒刺了。
这天晚上,赵志淸剛进鍋爐房,就見一个叫李文杰的拿着油壶,劈头朝他砸下来。赵志淸閃过去,这小子还抓住赵志淸要打。人們上来,把李文杰吆喝住:“喂,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看他有順眼!”李文杰还逞能耍橫。
“是你看着不順眼啊,还是‘棚楊’看着他不順眼?你小子喝他几兩酒,抽了他几支烟哪?”
这一揭底不吃紧,李文杰夹尾巴狗,赶紧溜号了。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沒过几天,老赵下班回家,正走着呢,猛然間从金家窑包子鋪里跳出几个人来,攔住老赵就要揍架;但剛喊了一声,立刻又把拳头縮了回去,原来大家彼此都認識,全是家門口摔跤,練把式的熟人。哥儿几个一甩手。說道:“我們当是誰哪,原来是赵大哥。算他‘棚楊’倒霉,白吃他小子一頓包子。老赵,往后要加小心啊,你走吧!”
赵志淸几次险遭暗算,不能不想个对策。大伙一商量,哥儿們里头,屬魯克恭来得机灵。就讓他假裝投降,到“棚楊”那儿臥底去。
当天晚上,魯克恭晃晃悠悠的到“棚楊”家来了。一张嘴,先借錢:“掌柜的,費您心吧,接济我几个。”
“不借。你們有本事,到处吿我去吧。倒瞧我姓楊的行,还是你們穷小子行。靑天白日旗挂着,大太阳晒着,你們要造反哪?”
“瞧您說的。我跟他們不一道啦。我过您这边来了。胳膊擰不过大腿去。我是吃飯要紧。”
“你这是眞話,假話?”
还沒等魯克恭回答,坐在“棚楊”身边的狗头軍师閻同生开腔了:
“咳,掌柜的,您問这个干嘛。来,开柜子拿錢。”这小子是个机灵鬼,想买动魯克恭,就塞了一把錢給他。其实呀,这也正中了魯克恭的計。
魯克恭回来了,就把錢交給大伙。大伙就拿这錢垫补了菜錢。以后,魯克恭不断的到“棚楊”家送消息去,編方造魔,净是讓他听了心跳的話。一回来,准带一把鈔票回来。就这样,一晃过了兩个月。
日子长了,“棚楊”以为魯克恭可靠了,就出坏招儿說:“克恭,旣然你过我这边来了,你就得給我办点事。这事嘛,你要是办好了。嘿嘿,我給你新打的三輪一輛,三季衣裳都是里表新的。”
“头儿,您說办嘛吧。办得到的一定办。”
“你扒哪个爐子?”
“11号爐子呀。”
“好,你这么办,明天黑夜,你偸偸把爐条扒了,造成事故。嘿嘿,东西可就全到手了。”
“头儿,行是行,可是得缓几天,找着下手的机会,要是讓大伙瞧見,我吃不了得兜着走啊。”
“这样吧,七天,一言为定。”
別說七天了,十天也沒信儿。魯克恭还是到“棚楊”家去要錢。“棚楊”琢磨着不大是味儿。手指縫綳紧,不大相信小魯了。他另憋了新招子。
有天晚上,算天星孙志欽去胡同口买烟卷儿,正好有个人拿着张紙条間摆糖攤的彭老头(你还記得最初爭双月搞罢工的那位彭头嗎?):“我打听一声,有个叫苏德林的在哪儿住?”
彭老头一看这人有点邪行,耍胳膊根的派头,就問:“你找他干什嚒?”
苏德林是外面的包工头儿,經常做电厂的外活。孙志欽就留上心眼了。就說:“苏德林哪,他就住这塊。”随后把紙条要过来扫了兩眼。好啊,正是为他們包身工的事。又是“棚陽”的主意,由苏德林另招了一批工人,打算今天乘他們下班,全換了!
孙志欽沒动声色,吿訴他門牌地址以后,一扭身跑回厂子来了。
大伙一听,反倒心平气和。說是“棚楊”朝大伙来,棍打一片这倒好,省得他算計这个那个的,大伙悬着心。
赵志淸出了个主意:“哥儿們,下了班,咱們別走,預备家伙,干哪!”
天一亮,他們就把队伍拉到門口来了,有拿通条的,有拿鉄銑的,全是鉄器,净等着苏德林带人来了。
苏德林沒来,特务张俊臣却来了。一看这架势,吓了他一跳:“喂喂,你們这是怎么啦?”
赵志淸还有这股机灵劲,馬上給他戴高帽子,說道:“理事长,你們工会管这事不管吧?‘棚楊’找苏德林另招新人,要把我們都下了!”
张俊臣一乐,說道:“不是你們工会,是咱們工会。工会是給大家办事的嘛,怎么不管?这事交我啦!”
“交你怎么样?”大伙嚷道,“你有嘛保証?”
张俊臣是笑面虎,专去拉攏人的角色。这是买好的事,他还能放过?眉毛一揚,鼻子一翹,給看門房的了命令:“今天生人一槪不准进厂。有嘛事先通过我。”
随后,张俊臣把“棚楊”叫来,板着面孔,一通好熊。
过去見面总是乐嘿嘿的,今天这是怎么啦?“棚楊”呆在张俊臣面前,像掉在烤爐里一样,燒得臉紅筋粗,嘴皮子不停。一連声儿“是的,是的!”他心里却暗暗罵道:“沒給你这道衙門口使錢,你小子給我来这一套的!”
其实,张俊臣倒还不是錢不錢的。他是看上这几十号人了。要是能改长工,这就都可以加入他的工会了。那会給他增加多大势力呀?包身工斗爭的事儿,可是复杂透了,八下子都使劲儿。……
这时节,厂里来了一位新的工程师,这人名姓都特別,叫来杰。他是从昆明来的。一进厂,大伙就知道了,都駡駡咧咧的說:“又飞来了一个!”
不过,这位工程师可有些不同,穿着一件藍布半截大褂,一来就下地窖了。到了地窖就和大伙招呼,大伙給他个爱答不理的。这还不算,給他来了个外号,叫来大褂!暗含着这是損他的意思,穿大褂的,不劳而食,是光会指手动嘴的一塊廢料。不,来杰还眞有兩下子,推煤部有个机器坏了,誰也收拾不上。他給出主意,找着老工人一齐对付上了。工人們傳出来了,說道:“来大褂,好家伙呀!有把刷子。”
来杰看地窖里的工人光用斜眼飞他,問什么总是哼哼唧唧的,腔儿不亮,碴儿不对。他就扯着赵志淸說:“你們別这样对我呀。我是好人,你們有什么困难朝我說。瞧你們这个工作条件太差啦。”
大伙围上来了。一听来杰說的是人話,敢情飞来的也不一样,有好有坏,这比先前那位錢串子工程师强太多了。于是大伙就把“棚楊”剝削的事儿,如此这般的一說。
来杰一听,滿臉同情的顏色。自己个往身上攬。就說:“居然还有这样的事。你們听信吧。我給办。”
没过几天,来杰搭拉着腦袋捎回信来:“咳,我办不了呀,厂长不同意,說我是公司的制度。你們好好干吧,我很同情你們。”
要說同情,来杰倒的确是同情。有回,他瞧見工人推着火苗冒着老高的爐灰,連个麻袋片也沒有。这要是濺上火星,登时就是一身潦泡。就問:“麻袋片呢?”
“用坏啦。新的不給呀。說这是制度。”
“老赵,跟我来,我給要兩塊去。”
等着赵志淸到了厂长办公室,好啊,来杰跟张景泰吵起来了。一看他进来,兩个人赶紧改用南边話吵。好讓老赵听不出来。可是老赵兩只眼睛看出来了,张景泰这小子眞狠,連兩塊麻袋片也不給。那意思是,不能把工人寵坏了。他們沒有麻袋,怎么你做工程师的也管这事!最后,来杰气哼哼的把赵志淸扯出来,和他說:“以后要东西的事别找我。我办不了。这又是公司的制度。”
其实,按制度的規定,到日期,也該領麻袋了,这是张景泰故意刁难大伙。过不几天,赵志淸直接找厂长去了,話挺硬:“你还是得給麻袋呀。有日子口管着昵。”
朝他要,这倒可以。张景泰一声不哼,盖了圖章。就說他这里下了多大心計吧!
別瞧兩条麻袋片,事儿不大,風可吹出去了。都說来大褂为包身工的事跟厂长干了一架。你傳我,我傳你的,加油加醋,傳到“棚楊”耳朵里,这小子一泡坏水,多了好几个心眼,未免心里發凉。“怎么这群穷小子,卖苦力的跟工程师搭合上了?还能少給我上眼藥啊?”折騰来,折騰去的,“棚楊”倒开窍了。反正怎么也是花錢,何必花了錢还慪气呢?干脆輸这口气吧。于是他派狗头軍师閻同生到赵志淸家来。
正最吃飯的当口。老赵把狗头軍师迎进屋去。这小子瞟了一眼桌子上摆的窩头咸菜,故意找話:“吃了嗎?”
老赵說話嗆喳的。“这不是正吃着哪嗎?”
“沒福气嘛!吃这么难咽的玩艺儿!人活着为嘛呀!志淸,你是明白人,一轉腦筋,別說不吃这么苦的东西,唔,少不得还要弄个二掌柜的干干。”
老赵准知道他是为嘛来的。就压住气說:“有什么事,你直說吧!”
“老兄弟,楊头很器重你,想和你交个朋友,磕头拜把子。往后是,伙燒一爐香,伙坐一只船,有福同享,有患同当。都是自家哥們弟兄。嘿嘿,你这回可是一步登天啦。”
老赵也嘿嘿了兩声,眼珠子一瞪,大喇叭嗓子嚷开了:“你回去吿訴‘棚楊’,咱是工人,穷光蛋一个,为大伙儿办事。姓赵的不卖朋友!”
“老兄弟,凡事三思而行。干飯燉肉,窩头咸菜;掌拒的,推灰的;这个分量,一天一地,你可掂掂!”
“你給我滾!”赵志淸“砰”的一声把門推开。
閻同生的圓臉变长臉。臉上罩上一層冰霜,冷冷地說道:“好,好呀!姓赵的,你也太不識抬举了,把道都走絕了。走着瞧吧,看我拿錢买不了你这条小命!”
赵志淸把袖子一挽,也說:“好,咱們走着瞧吧。”
这一鬧,等于是硬弓又拉上一扣。包身工的哥儿們都格外加了小心,有今个沒明个的,走着瞧吧。
瞧着,瞧着,“棚楊”的毒計还沒容使出来,倒是大时代已經来到。海河岸边响起隐隐約約的炮声,这些声音在人們心弦上激起了莫大的震动。哥儿們都暗地使劲,悄悄念叨着:“国民党要完蛋了!”
越来越紧了,紧到輪船不通,飞机不飞,天津像一口大瓮似的,被解放軍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张景泰表面上还根据国民党的布置,安排了工厂职工五人联保,保証不是共产党。可是心里却直打鼓,渾身毛毛咕咕,屁股像坐在針毡上一样。走吧,沒法走;不走吧,共产党来了,要怎么整他呢?这小子心神不定,倒經常把来杰找到屋里来聊天,讓来杰启發他。
来杰是共产党嗎?不是。张景泰很知道他。找他談的原因是这样:来杰的老婆前些时候坐船到南边去,走到山东半島地面,船触礁了,停在海面上。一船上好几百人,都是行裝累累,滿是金銀珠宝的有錢的人們,大部份都是从天津走的。这事当时很轟动,謠言很多,都說讓解放軍給他們俘了,杀了,东西都搶光了。事实却是当地的民兵駕着小船,把一船的人都接走,把他們的行李都搬到海灘上,等船修好,又把他們送走了。来杰老婆听当地的工作人員給他們講过話,对政策有些理解,又亲眼看見过解放軍,所以回来以后,就把所聞所見全說給来杰了,来杰把这事当做海外奇談,到处去講,到处去說。张景泰也灌了一耳朵。因此他就来打听来杰:“你說万一……如果,假設他們进城以后,对咱們怎么个看法呢?咱們是技术人員,他捫連工商业都保护,自然咱們更沒什么問題了吧?他們一定要用电,要用电就得靠我們。是不是?你說呀。”
来杰偏不給他打保票,不給他吃舒心丸,倒說:“厂长,有些事,厂长,我覚得嘛……”
听着“厂长”这兩个字儿忌諱。张景泰連忙攔住他說:“来工程师,你就不必繞弯子吧,有話直說吧!”
“地窖子包身工鬧得很厉害。現在他們还到处吿状,罢工,打架呢。将来局面一变,那还了得?依我看,应該取消包工制。”
“这是公司制度,不光天津一处这样。”“到那时候,恐怕很难这样說了。他們几次請求,都說厂长很不同情他們呢。”
张景泰的臉上一陣發靑發白。这小子吓傻眼了。只是拚命吐烟圈儿。
事情决定得很快。轉天,赵志淸被叫进厂长办公室。张景泰决心要买好。可是一瞧老赵那淸瘦的臉儿,由不得的气往上撞,劈头竟說了这么一句:“你們呀,給我找的麻煩太多了!头一个就是你呀。我眞該不要你。”
老赵勉强舌头打弯,說兩句好的:“得啦,您多維持吧。我們穷人总得吃飯,不活反正不行。”
来杰連忙摆手,对赵志淸說:“少說兩句吧!給你們办好事,提升长工啦。”
赵志淸連忙說:“那太好了,我先謝謝吧!”
沒等他乐出来,张景泰却念了个名单,魯克恭他們八个人不留。“調皮搗蛋,厂里不能留。”
“他們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啊!”
张景泰还挺嘴硬,咬定这三个字儿了,“不能留!”
赵志淸从厂长办公室回来,大伙一听,都炸了。这不是拆大伙的台嗎?要好都好,要賴都賴,哥儿們不能有甜有辣呀!”
还是那老招子,給他擱車,罢工!为了罢出点眉目来,讓张景泰一槪全收,赵志淸找张俊臣去了。他不是暗送秋波,想拉攏大家嗎?这回大伙正利用得着他。那曉得张俊臣因为上回那事,后来挨了特务头子一頓申斥。在当时那么紧张的情况下,电厂是很重要的地方。又不同于一般工厂,在特务的工运組,防奸組控制之下是絕对不許有絲毫罢工活动的。张俊臣拉攏工人,想扩张他的势力,那叫因小失大,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引火燒身。把张俊臣駡的够嗆。現在怎么个碴,要罢工!张俊臣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伸手从腰里掏出一把手槍,乒的一声,放在桌子上。这小子母狗眼一立,嚷起来了:“你們敢罢工!你們誰罢工,誰就是共产党八路,破坏电厂,我就槍斃誰!”
这手儿很厉害,国民党正抓人呢,讓张俊臣他們特务咬上,槍斃倒未必,可是裝在麻袋里扔下海河这可是寻常的事。何必找这个牺牲呢?赵志淸就赶紧溜回来了。倒是魯克恭他們哥几个把大伙攔住。劝道:“哥儿們,咱們只要斗了‘棚楊’,不再受他剝皮,这就是大胜利。現在炮都响了,有今天沒明天的日子,留着腦袋,以后跟他們斗吧!走我們几个沒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哥儿們,咱們后会有期呀!”
人們一寻思,这話有理。已經到了这份上了,还跟他們硬拚什么啊。
停了几天,张景泰在院里召集全体工人开了个会,說了几句刷油涂色的門面話,随后念了个名单,果然是魯克恭他們八个都下了。可是“棚楊”却沒踢开,他也补了个职員,还是負責推煤推灰部的工作!哥們儿里有位石宝林,忍不住气,当时冷笑一声,插了一句:“哼,这他媽的是相着‘棚楊’,給他解套,穿一条褲子!”就这一句話不大緊,张景泰所見了,眼睛一斜,这小子所有的工人都認識,立刻找补一句,“还有石宝林,厂子也不留!”
大伙乱哄哄的,这算怎么回事呀?张俊臣把工会的一张布吿貼出来了。字眼用的踉槍弾差不多。“如有工人聚众鬧事者,斟酌情况,或开除,或送警备司会部……”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伙只好駡駡咧咧地走开。包身工的斗爭,到此也就吿一結束。
斗得最复杂,最綿长的要屬包身工这档子事了。
提起包身工来,电厂里流行着一首歌謠:“推煤推灰活像鬼,烟熏火燎趟着水,餓着肚皮跑細腿!”就說推煤推灰工人有多苦吧。原先,灰煤部的工人也是长工居多。到日本鬼子来了,因为大伙不給鬼子干,光見人不見活。鬼子沒轍了,于是想出了一个絕招,把活儿能包的全包出去,就这么多錢办这么多事,越省工越多拿錢,賠賺是包活的。推煤推灰的便也包出来,倒了几次手,最后这事儿,讓干棚匠包活的楊恩元悄悄花錢买动到手上。这小子可逮住發財的机会了。騎在推煤推灰的哥儿們头上,这小子里吃外拐,心黑手辣,又扣工錢,又放高利貸,眞是比狼都狠。包工大柜才干了几年哪,到国民党統治时期,这小子家里雇着老媽子,使喚着听差的,交結了一帮狐群狗友,吃吃喝喝,居然也是个財主了。就說他剝削了工人多少錢吧。恨得工人們直搓牙,管他叫“棚楊”。
可巧,这天“棚楊”来监工的时候發生了一件事。有个穿破袄的工人不小心,叫倒下来的殘火苗儿給燒伤了,不能干活。少一个人不行啊,一个蘿卜一个坑。“棚楊”沒法儿,把袖口一挽,大爷也玩一宵票,跟着推了一夜的軲轆馬。这一夜不吃紧,他是酒色掏空了的身子,架不住这点劳累,回家就倒在炕头,爬不起来了。包身工是現錢現卖,干一天領一天的工錢,他一連兩天沒露面儿,大伙可吃不住劲了,一合計,讓班长赵志淸上他家里要錢去。
老赵到了“棚楊”家里,由使喚老媽把他領进正屋。他还歪在炕上,哼唧着腰酸腿痛呢。赵志淸道了来意,說是:“你得給錢,我們包身工沒錢吃飯啦。”“棚揚”心里直嘀咕,生怕包子露了餡,可他又病的起不来,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个便条,讓赵志淸拿了他的圖章到厂里取錢。临完,他千嘱咐万嘱咐的說:“你就凭条領錢,領多少是多少,任嘛事不用問。你明白啦嗎?”
赵志淸兩眼一碼儿黑,認不得半个大字。可他心里豁亮,准知道“棚楊”这里头有鬼。你不是不讓問么,他偏要找个識字的問問。拿回来,讓哥儿們里喝过一点墨水的孙志欽看看。老孙綽号“算天星”,他就朝大伙念叨:“看啊,‘棚楊’吃咱們吃的太狠啦!”大伙一听那个数,火苗儿一窜老高。眞是,狼吃人还得剩堆骨头呢,他这小子吃人,居然連骨头渣子也一塊呑哪!包工錢是三七分,白袖口一卷,先剝三成去,这且不提,怎么大伙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只領八个鐘点的錢呢?那四个小时都讓他昧起来了。这还行,大伙决定吿他去。
头一状吿到厂长张景泰那里去。张景泰倒干脆,說了一句話:“胡鬧!”
哥儿們里头还有一位会出主意的魯克恭,就由他煩人写了一个呈子,遞到伪社会局去。厂里不管,咱們是厂外折騰。伪社会局派一个戴金絲眼鏡,穿洋服的人見的魯克恭,一臉不耐煩的神气,不等魯克恭話說完,这小子就截住問:“你們到底要干什么吧?”
“我們要求取消包工制!”
想不到他倒应家下来,叫过三兩天来听信儿。过了三兩天,魯克恭又去了,这位戴眼鏡的又叫再过三兩天,一来二去的跑了十几趟。他們的事情沒有办出眉目,倒是社会局这儿和张景泰,和“棚楊把事儿办好。戴眼鏡的拿到了他能拿到的那一份儿,也就不再照面了。連再过三兩天的話也沒了。魯克恭他們明白,这是給人家做飯吃,他們白跑这冤枉路了。
可是,他們还不知道,“棚楊”朝他們領头的下毒手了。这天,付班长肖景泉領班,垫手的破麻袋片沒有了。一推車,手上就得燙几个大燎泡。肖景泉就找“棚楊”要麻袋片,“棚楊”正抓碴儿呢,一看送上門来了,张口就駡:“你他媽的拿麻袋片当飯吃呀!三天兩头的要。沒有,沒有!”
肖景泉也窩着火呢,就嚷:“你不給不行!”
“我就不給,你敢怎么样?”說着兩人支巴起来了。
这时候,特务狗腿子张七来了。这小子在日本鬼子統治的时候,拿棍子抽人,到了国民党派儿,他还是拿棍子抽人,还是交报吿,轄制工人。他当然和“棚楊”是一头的,喊喝一声,叫腿子們一拥而上,把老肖,还有跟老肖一塊儿来的老王給按住,往大門外面一推。倒也干脆,开除了!
这能完嗎?当然不能完。老肖和老王就去吿“棚楊”俗話說的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吿来吿去,他們不光沒吿了“棚楊”,反倒被伪法院給他倆扣了个扰乱厂方的罪名,白白压了好几天监獄才放出来。案子就这样算完啦。哥儿們在里面使不上劲,只好嘆口气,先忍着。眼睜睜地看他們到別处去找飯路。
包身工的哥儿們里,有一位叫刘少波的,他是城里住家。这天下午剛迈大門,要去厂里接班。就見斜对門的閻大律师正往外送客。他眼睛尖,看那客人坐的三輪有点儿像“棚楊”的,連忙閃到一旁。从門縫里往外偸看,可不嗎,閻律师送的正是“棚楊”这小子。老刘登时心里犯了嘀咕,“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官司不是已經打完了嗎。干嘛还找律师呢?这小子还安着什么毒計啊?”
随后,他踱到律师的院里,喊了一声,“四爷在家嗎?”
“里边坐,里边坐。”閻律师和老刘是十多年的老鄰居,再搭上他这律师沒有干起来,所以对鄰居有个面。
进屋以后,老刘不用客气照直就問。閻律师也就实話实說。好呀,原来肖景泉他們官司打不过,低头算完啦;他“棚楊”可不算完,斬草要除根,买通律师想把赵志淸也給咬进去,也給押上一陣子,来个一脚踢。
是这么一計啊!刘少波連忙央吿律师:“您可不能这么办呀!‘棚楊’这小子可不是东西。我們班长赵志淸可是好人,人家‘扛着刀’,給我們大伙儿办事。您要这么一来,不把我們都毁了嗎?”
閻律师一想也对。一来是“棚楊”手紧,只〓了几盒烟錢,値不当的去缺德,二来是和刘少波十多年相識,知道他們这伙卖苦力气的哥儿們火气大,犯不上惹人,再給自己〓了大包。就說:“好吧,瞧咱們老街坊的面子,依你。我明天不給他出庭。”事情揭过去了。
刘少波一口气跑到厂子。赶紧給大伙送信。大伙一听,这份气大啦。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大伙抱团,跟他干到底啦。七嘴八舌的說:“給他挂队!罢工!”
有人就摆手不贊成。說道:“这是什么年月?找着讓‘棚楊’把咱們当成共产党八路送終啊!再說,他正巴不得把咱們踢开,另換一撥新人好使喚呢。”
有人就提:“咱們給他来个明着不擱暗里擱。上市政府找杜建时請願去。”又有人摆手:“杜建时是哪一头的?能向着咱們嗎?”
又有人贊成:“嗨,杜建时跟他一鼻孔出气也好,兩鼻孔出气也好;反正这小子得花錢买动!”
“对!”大伙劲头都上来了,“請願不准,咱們不掉肉,‘棚楊’可把錢包丢光了。对,对,哥儿們折騰光这小子!”
要請願就得有說辞,于是煩人写了八項条件。主要的条件是:从比商直至現在,灰煤部工人一向在厂內工作,且为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份。因之灰煤部工人应改为长工;取消一切包工制;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間应改为每天八小时;不許把头虐待、打駡工人。
遞上請願書,沒多久,国民党市政府批下来了,含含糊糊的一句話:“候飭查核办!”以后便石沉大海,渺无音信。大家等得怪悶气的,不办不离奇,准知道他們不給办,可是“棚楊”究竟花多少錢,出多大的血呢?怎么連这个动靜也沒有。
沒有不透風的篱笆,事情讓經常向电厂运煤的把头,张禿张亭善知道了。他說:“我給你們大伙出个主意吧,你們找安靑帮的头目人张逊之,拜师入帮,靠他的势力,国民党不說,連軍統中統也都有个面儿,准把‘棚楊’給拱下去。”
狗拿耗子,怎么他多管起閑事来了呢?把头攆把头,其实这小子也沒安好心眼,他是眼紅嘴饞,想夺“棚楊”的食,挤下“棚楊”,他好当包工头儿。
大伙一硏究,跟“棚楊”斗到这份上,沒路可走了。要是靠安靑帮的势力压下“棚楊”倒也不錯。死馬当作活馬医,每人凑了几个錢,給张逊之送礼,摆香堂,認师付,求他帮忙斗“棚楊”。
一晃,十天半拉月过去了。“棚楊”还是那股子牛劲,斜眼看人,恨不得把誰盯死。大伙儿一想,这不成啊,香堂白摆了是怎么的?哥儿捫凑了三十多个人找张逊之去了。別提有多巧,正碰上张逊之要出門。一見大伙,他在台阶上一站,撇着京腔,倒数叨了大伙一頓:“你們請回吧,原来你們是运焦子的。我这儿也是你們来的地方!”
說完走下台阶,揚着脖子,鑽进汽車里,开路了。大伙駡駡咧咧地不知怎么出这口恶气才好。
这时候,张逊之的办事人,穿着长袍、緞鞋踱了过来,朝大伙伸出四个手指,說道:“人家‘棚楊’使錢,买死啦,你們要想把事扭过来,得这个数。”
这四个手指头就是西十袋面錢的意思。大伙一听,唧唧嚷嚷开了鍋:“要是有四十袋面,誰来你这儿啊!”
“这不是拿我們穷哥儿們炸肉醬玩嘛!”……
大伙沒有搬动“棚楊”,“棚楊”可不饒大伙啊。事情全是班长赵志淸出的头。他成了“棚楊”眼中的毒刺了。
这天晚上,赵志淸剛进鍋爐房,就見一个叫李文杰的拿着油壶,劈头朝他砸下来。赵志淸閃过去,这小子还抓住赵志淸要打。人們上来,把李文杰吆喝住:“喂,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看他有順眼!”李文杰还逞能耍橫。
“是你看着不順眼啊,还是‘棚楊’看着他不順眼?你小子喝他几兩酒,抽了他几支烟哪?”
这一揭底不吃紧,李文杰夹尾巴狗,赶紧溜号了。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沒过几天,老赵下班回家,正走着呢,猛然間从金家窑包子鋪里跳出几个人来,攔住老赵就要揍架;但剛喊了一声,立刻又把拳头縮了回去,原来大家彼此都認識,全是家門口摔跤,練把式的熟人。哥儿几个一甩手。說道:“我們当是誰哪,原来是赵大哥。算他‘棚楊’倒霉,白吃他小子一頓包子。老赵,往后要加小心啊,你走吧!”
赵志淸几次险遭暗算,不能不想个对策。大伙一商量,哥儿們里头,屬魯克恭来得机灵。就讓他假裝投降,到“棚楊”那儿臥底去。
当天晚上,魯克恭晃晃悠悠的到“棚楊”家来了。一张嘴,先借錢:“掌柜的,費您心吧,接济我几个。”
“不借。你們有本事,到处吿我去吧。倒瞧我姓楊的行,还是你們穷小子行。靑天白日旗挂着,大太阳晒着,你們要造反哪?”
“瞧您說的。我跟他們不一道啦。我过您这边来了。胳膊擰不过大腿去。我是吃飯要紧。”
“你这是眞話,假話?”
还沒等魯克恭回答,坐在“棚楊”身边的狗头軍师閻同生开腔了:
“咳,掌柜的,您問这个干嘛。来,开柜子拿錢。”这小子是个机灵鬼,想买动魯克恭,就塞了一把錢給他。其实呀,这也正中了魯克恭的計。
魯克恭回来了,就把錢交給大伙。大伙就拿这錢垫补了菜錢。以后,魯克恭不断的到“棚楊”家送消息去,編方造魔,净是讓他听了心跳的話。一回来,准带一把鈔票回来。就这样,一晃过了兩个月。
日子长了,“棚楊”以为魯克恭可靠了,就出坏招儿說:“克恭,旣然你过我这边来了,你就得給我办点事。这事嘛,你要是办好了。嘿嘿,我給你新打的三輪一輛,三季衣裳都是里表新的。”
“头儿,您說办嘛吧。办得到的一定办。”
“你扒哪个爐子?”
“11号爐子呀。”
“好,你这么办,明天黑夜,你偸偸把爐条扒了,造成事故。嘿嘿,东西可就全到手了。”
“头儿,行是行,可是得缓几天,找着下手的机会,要是讓大伙瞧見,我吃不了得兜着走啊。”
“这样吧,七天,一言为定。”
別說七天了,十天也沒信儿。魯克恭还是到“棚楊”家去要錢。“棚楊”琢磨着不大是味儿。手指縫綳紧,不大相信小魯了。他另憋了新招子。
有天晚上,算天星孙志欽去胡同口买烟卷儿,正好有个人拿着张紙条間摆糖攤的彭老头(你还記得最初爭双月搞罢工的那位彭头嗎?):“我打听一声,有个叫苏德林的在哪儿住?”
彭老头一看这人有点邪行,耍胳膊根的派头,就問:“你找他干什嚒?”
苏德林是外面的包工头儿,經常做电厂的外活。孙志欽就留上心眼了。就說:“苏德林哪,他就住这塊。”随后把紙条要过来扫了兩眼。好啊,正是为他們包身工的事。又是“棚陽”的主意,由苏德林另招了一批工人,打算今天乘他們下班,全換了!
孙志欽沒动声色,吿訴他門牌地址以后,一扭身跑回厂子来了。
大伙一听,反倒心平气和。說是“棚楊”朝大伙来,棍打一片这倒好,省得他算計这个那个的,大伙悬着心。
赵志淸出了个主意:“哥儿們,下了班,咱們別走,預备家伙,干哪!”
天一亮,他們就把队伍拉到門口来了,有拿通条的,有拿鉄銑的,全是鉄器,净等着苏德林带人来了。
苏德林沒来,特务张俊臣却来了。一看这架势,吓了他一跳:“喂喂,你們这是怎么啦?”
赵志淸还有这股机灵劲,馬上給他戴高帽子,說道:“理事长,你們工会管这事不管吧?‘棚楊’找苏德林另招新人,要把我們都下了!”
张俊臣一乐,說道:“不是你們工会,是咱們工会。工会是給大家办事的嘛,怎么不管?这事交我啦!”
“交你怎么样?”大伙嚷道,“你有嘛保証?”
张俊臣是笑面虎,专去拉攏人的角色。这是买好的事,他还能放过?眉毛一揚,鼻子一翹,給看門房的了命令:“今天生人一槪不准进厂。有嘛事先通过我。”
随后,张俊臣把“棚楊”叫来,板着面孔,一通好熊。
过去見面总是乐嘿嘿的,今天这是怎么啦?“棚楊”呆在张俊臣面前,像掉在烤爐里一样,燒得臉紅筋粗,嘴皮子不停。一連声儿“是的,是的!”他心里却暗暗罵道:“沒給你这道衙門口使錢,你小子給我来这一套的!”
其实,张俊臣倒还不是錢不錢的。他是看上这几十号人了。要是能改长工,这就都可以加入他的工会了。那会給他增加多大势力呀?包身工斗爭的事儿,可是复杂透了,八下子都使劲儿。……
这时节,厂里来了一位新的工程师,这人名姓都特別,叫来杰。他是从昆明来的。一进厂,大伙就知道了,都駡駡咧咧的說:“又飞来了一个!”
不过,这位工程师可有些不同,穿着一件藍布半截大褂,一来就下地窖了。到了地窖就和大伙招呼,大伙給他个爱答不理的。这还不算,給他来了个外号,叫来大褂!暗含着这是損他的意思,穿大褂的,不劳而食,是光会指手动嘴的一塊廢料。不,来杰还眞有兩下子,推煤部有个机器坏了,誰也收拾不上。他給出主意,找着老工人一齐对付上了。工人們傳出来了,說道:“来大褂,好家伙呀!有把刷子。”
来杰看地窖里的工人光用斜眼飞他,問什么总是哼哼唧唧的,腔儿不亮,碴儿不对。他就扯着赵志淸說:“你們別这样对我呀。我是好人,你們有什么困难朝我說。瞧你們这个工作条件太差啦。”
大伙围上来了。一听来杰說的是人話,敢情飞来的也不一样,有好有坏,这比先前那位錢串子工程师强太多了。于是大伙就把“棚楊”剝削的事儿,如此这般的一說。
来杰一听,滿臉同情的顏色。自己个往身上攬。就說:“居然还有这样的事。你們听信吧。我給办。”
没过几天,来杰搭拉着腦袋捎回信来:“咳,我办不了呀,厂长不同意,說我是公司的制度。你們好好干吧,我很同情你們。”
要說同情,来杰倒的确是同情。有回,他瞧見工人推着火苗冒着老高的爐灰,連个麻袋片也沒有。这要是濺上火星,登时就是一身潦泡。就問:“麻袋片呢?”
“用坏啦。新的不給呀。說这是制度。”
“老赵,跟我来,我給要兩塊去。”
等着赵志淸到了厂长办公室,好啊,来杰跟张景泰吵起来了。一看他进来,兩个人赶紧改用南边話吵。好讓老赵听不出来。可是老赵兩只眼睛看出来了,张景泰这小子眞狠,連兩塊麻袋片也不給。那意思是,不能把工人寵坏了。他們沒有麻袋,怎么你做工程师的也管这事!最后,来杰气哼哼的把赵志淸扯出来,和他說:“以后要东西的事别找我。我办不了。这又是公司的制度。”
其实,按制度的規定,到日期,也該領麻袋了,这是张景泰故意刁难大伙。过不几天,赵志淸直接找厂长去了,話挺硬:“你还是得給麻袋呀。有日子口管着昵。”
朝他要,这倒可以。张景泰一声不哼,盖了圖章。就說他这里下了多大心計吧!
別瞧兩条麻袋片,事儿不大,風可吹出去了。都說来大褂为包身工的事跟厂长干了一架。你傳我,我傳你的,加油加醋,傳到“棚楊”耳朵里,这小子一泡坏水,多了好几个心眼,未免心里發凉。“怎么这群穷小子,卖苦力的跟工程师搭合上了?还能少給我上眼藥啊?”折騰来,折騰去的,“棚楊”倒开窍了。反正怎么也是花錢,何必花了錢还慪气呢?干脆輸这口气吧。于是他派狗头軍师閻同生到赵志淸家来。
正最吃飯的当口。老赵把狗头軍师迎进屋去。这小子瞟了一眼桌子上摆的窩头咸菜,故意找話:“吃了嗎?”
老赵說話嗆喳的。“这不是正吃着哪嗎?”
“沒福气嘛!吃这么难咽的玩艺儿!人活着为嘛呀!志淸,你是明白人,一轉腦筋,別說不吃这么苦的东西,唔,少不得还要弄个二掌柜的干干。”
老赵准知道他是为嘛来的。就压住气說:“有什么事,你直說吧!”
“老兄弟,楊头很器重你,想和你交个朋友,磕头拜把子。往后是,伙燒一爐香,伙坐一只船,有福同享,有患同当。都是自家哥們弟兄。嘿嘿,你这回可是一步登天啦。”
老赵也嘿嘿了兩声,眼珠子一瞪,大喇叭嗓子嚷开了:“你回去吿訴‘棚楊’,咱是工人,穷光蛋一个,为大伙儿办事。姓赵的不卖朋友!”
“老兄弟,凡事三思而行。干飯燉肉,窩头咸菜;掌拒的,推灰的;这个分量,一天一地,你可掂掂!”
“你給我滾!”赵志淸“砰”的一声把門推开。
閻同生的圓臉变长臉。臉上罩上一層冰霜,冷冷地說道:“好,好呀!姓赵的,你也太不識抬举了,把道都走絕了。走着瞧吧,看我拿錢买不了你这条小命!”
赵志淸把袖子一挽,也說:“好,咱們走着瞧吧。”
这一鬧,等于是硬弓又拉上一扣。包身工的哥儿們都格外加了小心,有今个沒明个的,走着瞧吧。
瞧着,瞧着,“棚楊”的毒計还沒容使出来,倒是大时代已經来到。海河岸边响起隐隐約約的炮声,这些声音在人們心弦上激起了莫大的震动。哥儿們都暗地使劲,悄悄念叨着:“国民党要完蛋了!”
越来越紧了,紧到輪船不通,飞机不飞,天津像一口大瓮似的,被解放軍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张景泰表面上还根据国民党的布置,安排了工厂职工五人联保,保証不是共产党。可是心里却直打鼓,渾身毛毛咕咕,屁股像坐在針毡上一样。走吧,沒法走;不走吧,共产党来了,要怎么整他呢?这小子心神不定,倒經常把来杰找到屋里来聊天,讓来杰启發他。
来杰是共产党嗎?不是。张景泰很知道他。找他談的原因是这样:来杰的老婆前些时候坐船到南边去,走到山东半島地面,船触礁了,停在海面上。一船上好几百人,都是行裝累累,滿是金銀珠宝的有錢的人們,大部份都是从天津走的。这事当时很轟动,謠言很多,都說讓解放軍給他們俘了,杀了,东西都搶光了。事实却是当地的民兵駕着小船,把一船的人都接走,把他們的行李都搬到海灘上,等船修好,又把他們送走了。来杰老婆听当地的工作人員給他們講过話,对政策有些理解,又亲眼看見过解放軍,所以回来以后,就把所聞所見全說給来杰了,来杰把这事当做海外奇談,到处去講,到处去說。张景泰也灌了一耳朵。因此他就来打听来杰:“你說万一……如果,假設他們进城以后,对咱們怎么个看法呢?咱們是技术人員,他捫連工商业都保护,自然咱們更沒什么問題了吧?他們一定要用电,要用电就得靠我們。是不是?你說呀。”
来杰偏不給他打保票,不給他吃舒心丸,倒說:“厂长,有些事,厂长,我覚得嘛……”
听着“厂长”这兩个字儿忌諱。张景泰連忙攔住他說:“来工程师,你就不必繞弯子吧,有話直說吧!”
“地窖子包身工鬧得很厉害。現在他們还到处吿状,罢工,打架呢。将来局面一变,那还了得?依我看,应該取消包工制。”
“这是公司制度,不光天津一处这样。”“到那时候,恐怕很难这样說了。他們几次請求,都說厂长很不同情他們呢。”
张景泰的臉上一陣發靑發白。这小子吓傻眼了。只是拚命吐烟圈儿。
事情决定得很快。轉天,赵志淸被叫进厂长办公室。张景泰决心要买好。可是一瞧老赵那淸瘦的臉儿,由不得的气往上撞,劈头竟說了这么一句:“你們呀,給我找的麻煩太多了!头一个就是你呀。我眞該不要你。”
老赵勉强舌头打弯,說兩句好的:“得啦,您多維持吧。我們穷人总得吃飯,不活反正不行。”
来杰連忙摆手,对赵志淸說:“少說兩句吧!給你們办好事,提升长工啦。”
赵志淸連忙說:“那太好了,我先謝謝吧!”
沒等他乐出来,张景泰却念了个名单,魯克恭他們八个人不留。“調皮搗蛋,厂里不能留。”
“他們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啊!”
张景泰还挺嘴硬,咬定这三个字儿了,“不能留!”
赵志淸从厂长办公室回来,大伙一听,都炸了。这不是拆大伙的台嗎?要好都好,要賴都賴,哥儿們不能有甜有辣呀!”
还是那老招子,給他擱車,罢工!为了罢出点眉目来,讓张景泰一槪全收,赵志淸找张俊臣去了。他不是暗送秋波,想拉攏大家嗎?这回大伙正利用得着他。那曉得张俊臣因为上回那事,后来挨了特务头子一頓申斥。在当时那么紧张的情况下,电厂是很重要的地方。又不同于一般工厂,在特务的工运組,防奸組控制之下是絕对不許有絲毫罢工活动的。张俊臣拉攏工人,想扩张他的势力,那叫因小失大,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引火燒身。把张俊臣駡的够嗆。現在怎么个碴,要罢工!张俊臣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伸手从腰里掏出一把手槍,乒的一声,放在桌子上。这小子母狗眼一立,嚷起来了:“你們敢罢工!你們誰罢工,誰就是共产党八路,破坏电厂,我就槍斃誰!”
这手儿很厉害,国民党正抓人呢,讓张俊臣他們特务咬上,槍斃倒未必,可是裝在麻袋里扔下海河这可是寻常的事。何必找这个牺牲呢?赵志淸就赶紧溜回来了。倒是魯克恭他們哥几个把大伙攔住。劝道:“哥儿們,咱們只要斗了‘棚楊’,不再受他剝皮,这就是大胜利。現在炮都响了,有今天沒明天的日子,留着腦袋,以后跟他們斗吧!走我們几个沒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哥儿們,咱們后会有期呀!”
人們一寻思,这話有理。已經到了这份上了,还跟他們硬拚什么啊。
停了几天,张景泰在院里召集全体工人开了个会,說了几句刷油涂色的門面話,随后念了个名单,果然是魯克恭他們八个都下了。可是“棚楊”却沒踢开,他也补了个职員,还是負責推煤推灰部的工作!哥們儿里有位石宝林,忍不住气,当时冷笑一声,插了一句:“哼,这他媽的是相着‘棚楊’,給他解套,穿一条褲子!”就这一句話不大緊,张景泰所見了,眼睛一斜,这小子所有的工人都認識,立刻找补一句,“还有石宝林,厂子也不留!”
大伙乱哄哄的,这算怎么回事呀?张俊臣把工会的一张布吿貼出来了。字眼用的踉槍弾差不多。“如有工人聚众鬧事者,斟酌情况,或开除,或送警备司会部……”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伙只好駡駡咧咧地走开。包身工的斗爭,到此也就吿一結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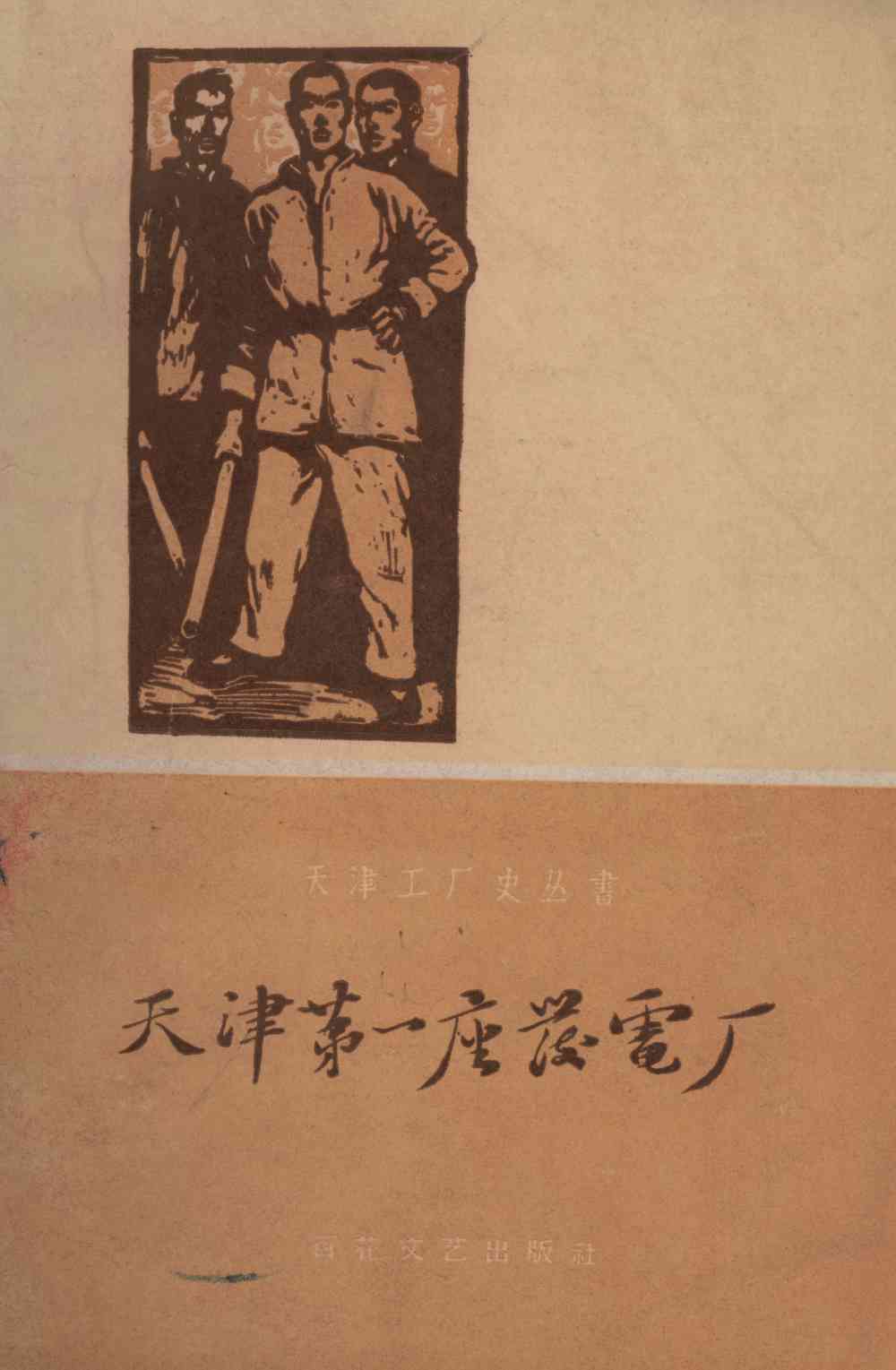
《天津第一座發電厂》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天津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和背景。该活动受到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鼓足了工人的干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阅读
相关地名
天津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