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罢工
| 内容出处: | 《天津第一座發電厂》 图书 |
| 唯一号: | 020020020230026118 |
| 颗粒名称: | 第三次罢工 |
| 分类号: | F246 |
| 页数: | 23 |
| 页码: | 34-56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比国佬在对待工人的态度上越来越强硬,工会为了争取工人权益与比国佬进行斗争。然而比国佬继续加强镇压,打算解雇所有老工人并停止增薪。最终在1932年10月14日,工人们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并提出了十项条件,但比国佬对此不予理睬。 |
| 关键词: | 罢工斗争 旧中国 工人阶级 |
内容
比国佬和实办林三自以为鬼計得逞,連国民党的一条小尾巴都給排挤得一命哀哉了,天下还不是他們洋人的!工会由刘治倫把持,更是从此太平无事。所以比国佬对待工人的威風就抖得更足。什么条件,楞来了个推翻不算,沒有一条实行的!
工人服这一套嗎!当然不服。誰也是窩着一肚子火气,嘟嘟囔囔,等时机爆發。后来事情發生在这个出缺的常务理事职位的問題上了。工人們坚持要补上一个新的来,資本家不同意。拉了很长时期的鋸,才由一个叫张广兴的补上来。张广兴是个俊俏的小伙子,那年才24岁,是公司的一个抄表員。原来文化水平也很低,滄县人,在乡下念过几年小学,后来便通过一位本家叔叔托情到“比商电灯电車公司”来了。这个年輕人很有雄心大志,白天抄表,晩上还到法汉中学夜校去学習,很懂得用功。而且他为人刻苦朴实,不吃喝玩乐,有点儿富裕錢便去买一点杂志新書看。懂得思索一些什么事情。如今老工人們回忆起他来,还說:“人家张广兴是好样的,能說能道,又是赤胆侠骨,好交朋友,好联系群众。”自然,像他这人物要被大家推选上台了。
他所以能够代替陈澤林,自然还另有原因。因为他也是国民党員。經常把这个身份挂在他的嘴皮子上。他上台以后,常务理事是三头为大,沒有一个总干事了。什么事全得三个常务理事联銜盖圖章。所以开初先拖了个时期,称得起是相安无事。
但是,比国佬却心狠手辣,毒計一招跟着一招来,打算把所有的老工人,特別是参加过1929年罢工的那些工人,都抓碴开革。另外一着便是只出人不进人,要职工越来越少。比国佬是懂得人多浪大这条道理的,兩个厂子合在一起一千来人,委实是受不了呀。活忙的时候,比国佬就找工头外包,这样一来,他就不怕牛么罢工的威胁了,因为干活的人和公司沒有什么雇佣关系。但这样还不算,还要停止增薪(按公司旧例每年增薪一次,一次可增几分錢),还要取消已有的福利。比国佬的面孔越来越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是把中国工人当做亡国奴看。
工人吃这一套么?不行,干柴烈火,越着越高,最后在1932年10月14日,召开了“比商电灯电車公司工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12人,张广兴被推选做大会主席,当場向比国資本家提出十項条件。条件的内容是:
一、設立工人子弟学校,月增敎育費200元;
二、給职工免費乘电車,免費用电的待遇;
三、年終發花紅;
四、工人在工作时一律發給官衣;
五、工友有死亡者發給葬埋費200元;
六、每个工人由公司代买兩袋牌价面;
七、职工工龄达22年的加發一年工薪做为养老金;
八、在定額以內节約用煤,發給职工煤賞;
九、病假不扣工資;
十、給工人解决宿舍住房;
比国佬接到工会的意見書,恨得直啄牙花子。心里罵道:“你們这群臭工人忘記自己是老几了,你們要上天哪!”如出一轍,洋鬼子表面不露声色,摆出洋大人高高在上的嘴臉,又来了个不答不理!
就跟上一次罢工一样,国民党市党部聞着腥味,党棍子們又来伸手了。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地面上換了一撥子新的地头蛇而已。如今已非南北大战那时局面,正是奉系坐天下的时代,市长是周荣光,市党部里有邵华和时子周,省委里面有张厉生、严智怡,这些錢串子們早就耳聞上次罢工,如何炸醬的事儿了。这回是机会凑手,如何肯輕輕放过?于是假惺惺地代工人們办起交涉来了。
比国佬跟买办林三一合計,这笔款子有上回的数目摆着,能多不能少呀。这錢挖的未免心痛。洋鬼子这回鬼头多了,慪气挡不住多花錢,这是何苦来?便由林三出头,悄悄把张广兴約来。在他办公室里密談一番。
林子香和张广兴一碰面,这小子先笑唧卿的朝他一竪大拇哥,說道:“广兴,你眞是好样的,我眞佩服你,这手儿搞的多漂亮啊。”
张广兴已經料出几分来了。他也会不动声色,只是說:“到底什么时候答复工人呢?老这么拖下去要出事哩!”
“咳,出事不出事,都在老弟你啦。”林三說到这儿,干笑兩声,随后又講:“咱們有錢花在自己人身上。这事只要你不管,抽手走,兄弟,你發洋財了,这个数!”林三把話打住,朝他眼前伸出兩个大手指来。
张广兴看也沒看,不做声儿。
“好吧,咱們剃头圖凉快,我給您再添个数!”林三又伸了一个手指出来。
张广兴这人可有計謀,还是不声不响。
林三干咳了兩声,又笑了兩笑,点点头。“好哇,你年輕輕的眞辣啊。行,我佩服你,我成全你。这样吧,再加个碼儿,四万塊。”林三把四个手指直晃到他鼻子跟前,嚷起来:“广兴,見好就收。可以啦,太可以啦。你算算吧,你一个月才拿三十几塊錢,你一年才拿三百多塊錢,十年才拿三千来塊錢,你就是活一百年也拿不到这四万塊錢。你算算吧,拿回去置房子买地做卖卖,干什么不够啊?”
逼到这儿。张广兴忍无可忍,这才頂了他一句:“我謝謝你的好意,你給我算的挺好,錢也給的不在少数。拿这錢發財做买卖嘛,那自然是够折騰一气的了。可惜我不想發財,不做买卖,我是替工人大伙办事,我是人,不是狗!”
这一嚷不吃紧,把个林三嚷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万沒想到鼻子碰在城墙上了!他把笑臉收住,冷笑兩声,說道:“你可別不識好歹,我要买你的命,花不了几个錢!”
张广兴也不含忽,說道:“你也別不識好歹,工人們干起来,够你瞧的。你不是有錢能买人么?好,你就拿錢花去吧!”說完,他扭头走了出来。
不敢怠慢,张广兴連忙跑到国民党市党部来。把这情况和头目人一說。把这几头饞狼餓狗都气坏了。他們咬牙切齿地說道:“好哇,好哇,比国佬也太錢狠了。这倆錢說什么也不放啊。拿四万塊錢就想把事情压下去呀,沒那么便宜的事!广兴同志你做的太对了。”
广兴便也裝做“同志”的样儿,乘机献策:“我們得大搞,得支持工人們罢工啊!”
“罢工?”几个头目人有点害怕。半晌才有誰喃喃地說了一句:“万一要是讓共产党利用上,点起火来呢?”
“不会,不会!有我,有我哪!”张广兴一拍胸脯。
这几个头目人一想,广兴是国民党党員,他能掌握住,便不会出大漏子,还是炸比国佬的肉醬,發洋財的事儿要紧。就說:“罢工事情太大,得問一下市长啊。”
那时候,国民党党部和国民党市政府总是碟儿碗儿的碰得叮当乱响。要步驟一致,还得协商,就由张广兴以工会代表的身份跑去見市长周荣光。这位周市长上得台来,兩袖正嫌風淸,急着要大把抓錢呢。听张广兴来請求支持他們电厂車厂工人罢工的事儿,正中下怀,这不是肥猪拱門么?这不是給他市长送大洋錢来了么?登时眉开眼笑,反倒給张广兴打气。說道:“比国資本家这样压迫我們工人,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人要求罢工是正当的,政府一定支持,兄弟我嘛也一定帮忙。哈哈……”这一关也打通了。
这天,九月士二日,天剛蒙蒙亮。深秋的早晨格外淸凉,一群群工人往电車厂子走来。这里由工会临时召集了一个大会。
人們黑鴉鴉的围了一片。从人群中直立起来,张广兴举起喇叭筒朝大家喊道:
“弟兄們!公司資本家拖了又拖,結果是十項条件,一項也不接受。好吧,我們給他一个厉害看看。从今天起,我們罢工了。但咱們罢工不能影响社会秩序,咱們电車还是照样开,只有一样,随便坐車不要錢。讓咱們中国老百姓也沾点光。他們帝国主义賺咱們中国洋錢賺的太多了,也讓他們吐点儿出来吧!”
黑鴉鴉的人群里爆起一片笑声。这个办法太好了,大家都拥护,一来不誤大家坐車办事,二来比国資本家还得往外貼本,比不干活还讓洋人难受,这簡直是拉他們的肉呀!张广兴又一揮手,喊道:“咱們电厂的哥儿們也照常燒鍋爐送电,可就是查电表的不查表,收电費的不收电錢,讓中国人白用电灯吧!”
大家又是一陣哄笑。笑声中,人群蠕动了,罢工开始了!
这一着可房害!电車还像往常一样,車輪子格楞格楞地在鉄軌上滾着,可是白花花的大洋錢却随着声音扔掉了。电灯还照样儿净光冒亮,可是那些电錢却一个也不見!比国佬一下子急傻眼了。
但是,他們还不肯和工人講条件。这口气那能輸啊?于是又由林三布下他的党羽,打算和工人們斗一斗。他們有句話:“我們洋人的买卖,不能受拿捏。”
如今不比先前,林三的手下人也多多了。又約来了兩名专門破坏工人运动,对付工人的大流氓、大走狗錢伯骥和王彩南。这些人的手法又毒又辣,比刘治倫这一群嘎杂子的本領自是高出一筹。不来硬碰,却来个軟泡,他們想撒下迷魂陣,专一的勾引那些不坚定的分子掉入陷阱中去。他們在“日租界”鴻义棧租了間房,大烟白面足这么一供应,另外是酒肉,金錢,女人明摆在那里,把一些他們認为可以腐化、拉下水来的工人叫到这儿来,然后問:“跟我們,你看見了沒有?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人一輩子倒是圖个么呀?”
不頂用,工人們臭卷他們一通,一个个火气都不小。这一着沒有使上。不光这一着沒使上,相反的倒听說张广兴他們另外搞了个秘密办公地点。这地点在那儿,他們不知道!
比国佬一看,想用分化工人的手段,內部自行解决是办不到了。得認头花錢。于是由比国佬出面,在××飯店摆了一桌洋餐。虽說洋餐,但也上了很多精致的中菜,要吃什么有什么。因为是請市长吃飯,怕不对这位周荣光的胃口。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比国佬这回自动开了腔。說道:“我們公司工人又鬧風潮了,这事还得請市长維持、制止。”
周荣光假裝不明白的:“哦!怎么他們鬧事了?不是电車还照样开着嗎?电灯也很亮嘛?”
“要命的是他們不收錢呀!”
“哦!怎么他們不收錢呢。这还了得。”这时候,通过林三的手,一张三万元的支票遞过去了。周荣光用眼一扫,臉子一搭拉,眼角上挂着冰霜。立刻把支票退回去。打着官腔說:“总办先生,你們劳資之間的事,我嘛,也很不便于插手,因为他們工人还是照样开車,照样供电,从維持社会治安角度来看,我也不便說什么。”說着,他立了起来,撢了撢屁股,說是还有飯局,端着个官架子走了。
总办也明白自己下的注小。于是轉天又是一場酒席,把支票换成了五万。五万?周荣光心里的話,我的价碼沒这么賤的,吃完了飯一抹嘴,又走了。总办只好又咬牙,又請客,又加碼儿。直到怠工的第十五天头上,支票換到廿万元的大数,周荣光一合計:“好啊,廿万!廿万能买多少所楼房了呢?弓也拉得够份儿了,老这么抗着洋鬼子,回头再惹岀別的事来。”赶紧唔了一声,把支票掖在腰包里,立时話鋒就改了。他气气哼哼地,說道:“这帮工人眞是可恶,老是搗乱。我看这里面一定有共产党的人操縱。”
“一定是有共产党分子搧动!”比国佬連忙点头。
周荣光就問:“你們有凭据么?”
“凭据沒抓住,可是影影綽綽的。”
就凭影影綽綽的这四个字,当然还不行。周荣光做官的人講究四面圓,八面光,便說:“要是这样的話,你們还得和市党部啦、省党部啦交涉。兄弟我是要严办这群搗乱工人的。”他眞滑,还替党部攬了点儿买卖。
其实,买卖不用他給攬。林三是拜八方的买办,过去他在煤矿上干过,这一套自然駕輕就熟,另外几张为数不小的支票也早已經开过去了。
就在这天晚上,深夜一点鐘的时候,省府委員张厉生忽然用电話将工人代表张广兴,还有印刷工会的陶子明,一共四个人叫到时子周的私室作最后的談判。連周荣光也在座。张厉生扯了一套官面儿話,滿应滿許的:“咱們明天立即复工,这样鬧下去,有碍覌瞻,违背邦交。怠工期間的工資嘛,照發!年終双薪嘛,兄弟我拿人格来担保。你們总信得过我张某人吧?”
张广兴他們早料到这一着了。他們不从这一面和党棍子頂牛,而是抬出几个問題来:“这样一来,是不是要影响党国威信呀?”“哎呀,这样可是不好向工人交代呀。”
“以后的事情很难办了。”
几个党棍子不好說話,周荣光却摆出市长的威風,指着张广兴橫眉立目地問道:“今天怠工第几天了?”
“第十六天。”
“你們老这样鬧下去还行呀!”周荣光紧接着把帽子扣下来,“当初我跟你有言在先,叫你們必須团結一致,不扰乱治安,一切合理合法,我才能帮忙,可是現在……”
张广兴忍不住了,紧盯一句:“現在又怎么样?”
“現在,現在你們里面出了共产党,撒傅单,煽动工人,破坏治安,你知道不知道?”
“沒有的事。我們十五天,一点事儿也沒出。”
沒料想,张广兴居然敢頂撞他市长兩句。正好借这机会冒火儿。张开他那血盆大口,狼一样叫起来:
“张广兴,我命令你通知他們。今天午后三点以前,全体必須复工。誰不服从,就按共产党分子煽动罢工論罪。有一个斃一个,有一对斃一对!”
有去黑臉的,也有去白臉的。那几个便一口一个“广兴”叫着。說道:“大家都要从大局着想,正是国难当头,剿“匪”紧急的时候,我們一定要顧全邦交,別讓共产党利用了。現在从很多迹象看,有共产党操縱的可能。广兴,我們要注意啊。广兴,据說还發現了一些小册子!”
张广兴一口回絕:“那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不能不防止喲!”几个党棍子抓住这頂紅帽子了,就說:“馬上复工,一定要馬上复工!”
几个小时之后,天边剛剛挂出半堵阳光,电厂車厂的工人們便三三兩兩的向南市庆云戏院走来。今天召开临时大会。許多工人还蒙在鼓里,以为是比国佬斗不过,低头講条件了呢。瞧会場上这个热鬧劲儿呀。
人声忽然靜止。原来是张广兴站到台上来了。他声音不大自然,連連喊了几声:“工友們,工友們!”話梗住。底下是一陣唧唧喳喳。“怎么啦?张广兴!”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他。
张广兴下决心了,就把晚上交涉的話,一五一十端了个底掉。工人一听,这还了得!像火山崩开了口子,像热水煮开了鍋,正这儿人声鼎沸,喊喝成一片呢。张广兴却兩手大张,急忙叫大家靜住。他說:“我和兄弟們一样,眞是不願意复工啊,可是逼到这儿,不复工不行啦。再不复工,我們就不单是和比国資本家斗,也是和市党部,和公安局保安队斗了。咱們工人們赤手空拳,劲头再大,心气再齐,却总不能这样对付政府的槍啊,炮啊?咱們为了把眼光放远,把力量保存得足足的,不在刺刀跟前做沒价値的牺牲,我們只好先复工了。复工幷不算是咱們的失敗,咱們团結得很好呀,咱們到底狠狠敎訓了一下比国資本家呀,到底明白了誰才是眞正帮助咱們工人的呀……”张广兴越說越激动,激动得他話都講不下去了,嗓音哽咽了,終于放声大哭起来。
会場上是死一样的寂靜。个个把眼睛瞪得鼓鼓的,像是一团炸藥,簡直的就要炸呀,这时刻,看到情势不妙,周荣光手下的一員干将,市府第三科科长穆道厚晃着腦袋走到前边来。他张开尿盆似的大嘴,嚷道:“我吿訴你們,你們听眞了!市长有命令,命令你們今天下午立即复工,免受共产党分子的利用!你們不就是想多要錢嗎?市长已經給你們办妥,你們要求买兩袋牌价面,多剩倆錢,已經办到啦。人家比国人已經答应了。你們要官衣,人家看周市长的面子,也答应了,給二百件冬季皮衣。行啦,要求差不多啦,你們要立即复工,不复工就是破坏社会治安,破坏社会治安就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就得槍斃!”……
大伙听得几乎气炸了肺,誰都是头暈腦漲的。有人想出去。嗬呀,不行!保安队已經堵上門了,大伙都低下头来。有人喊着:“我們听张广兴的。我們信得过张广兴。”罢工終于又被压下去了。
下午,各部門的工人低着腦袋进厂来了。剛一到电厂門口,不由得人們一怔,門口上把滿了保安队,个个槍上插着刺刀,把母狗眼瞪了个賊圓,就差用槍刺子戳人了。进厂一看,里面还貼着布吿。工人們一边看一边叨咕:
“怎么?罢工十七天的工資一槪不發!来年年終欢薪取消!三年不漲薪!”好啊,比国佬是倒打一耙,嗆上火儿了。这还不算,还把工人包汉文等五个名列黑榜,宣布开除!
大伙一看,这是騎在腦袋上拉屎,故意跟工人們做对。你說我講的,誰也不再往里迈步了。吵嚷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大家放明白点,可別再鬧事呀!保安队是眞槍实弹,鬧哄着要抓共产党哪!”工会里的这批工賊、流氓打手就足这么一煽風,把大伙說的沒了主张。
“不要紧!不要紧!”刘治倫他們又出头了,从另一面攻。說道:“已經請示过市党部了。大家还是先复工呀!市党部保証包汉文他們可以复工。由党部办交涉。”
花說柳說的,工人只好低头走进車間。車間里怎么多了这么些人啊?好啊,一个人屁膜后面跟着一个保安队,他們拿着槍,刺刀也就离后背尺来长。工人們簡直和和罪犯一个样!
包汉文他們五个人就連忙跑到国民党市党部。在門口等了半天,这才有个小职員出来講話,說道:“你們不是被开革,是停职。停职嘛是公司的权利,市党部也不便过多干涉。你們先忍耐一下,等着复职吧。”
“那我們肚子餓了朝誰說去呢?”包汉文他們就問。
“忍耐嘛!自己想想法子嘛!”这位小职員把臉子一摔,走进去了。
这几个人整天随在张广兴的身后,到处交渉,到处沒有結果。于是乘这机会,借这几个人做幌子,大工賊錢伯慶、王彩南派人下到各車間,到处宣傳:“张广兴惹了比国总办,讓咱們大家跟着倒霉。咱們大伙齐心哪,把张广兴赶走哪!”
听說是要把张广兴赶走,大伙喊喝連声,誰听这一套的,硬把狗腿子給攆出来了。
一計未成,又生一計。偏也凑巧,有个电車車守胡宝山卖車票的当儿,誤将車票画錯了一张。被稽查查出,于是硬把芝麻大的事儿当成黃豆,报吿給公司了。公司里的工賊錢伯驥、王彩南正抓碴儿要破坏工会里的这批斗爭人物呢,覚着是个坎儿,就把胡宝山找到日租界鴻义棧里来。指着他說:“姓胡的,摆在你眼前头兩条路,你走哪一条吧!”
胡宝山說:“我犯了什么錯?要你給我摆路。”
“你画錯了車票,这事不小呀。一条道,你承認这是张广兴敎你們搞的,說是要一律吃票营私,自己到公司自首,随后到法院吿张广兴去。吿下来,你明白吧,比国人在职位上,薪金上还要照顧照顧你哪。算你命里該着,要走洋运,我姓錢的帮你这个忙,哈哈。”
胡宝山冷眼問:“另外那一条呢?”
“怎么,你还問那一条?那一条路,你想也想得明白,犯了这么大的錯誤,洋人来一张黃条,就把你开革了。这碗飯你就吃不成了。你想想,心里怕不怕?”
胡宝山反倒嘿嘿一笑:“不就是开革么?我姓胡的領着。张广兴是好人,为工人大伙办事,我姓胡的不能陷害好人。你小子借刀杀人,放心吧,你沒个好!”錢伯驥抹了一鼻子灰不說,而且这事嚷嚷开去,工人們团結的心气更足了。胡宝山虽然被开革了,但是倒更使工賊們难以下手了。
二計不成,又生三計。这一計可毒辣。林三林子香又去找市长去了,他問:“张广兴味儿不对,他这人到底是怎么一个国民党員呢?你們保险么?”
周荣光是做官来的,凡事不担肩儿,于是連忙和党部的几个头目人叨咕。原本,这几个党棍子就有些照影子,张广兴年輕輕的,这么联系群众,这么任劳任怨,到底为了什么啊?”明摆着給他白花花四万塊現洋,他都不眼暈,不伸手啊!察其言覌其行,也覚着不大对味儿,莫不是张广兴別有什么来路?不过疑心归疑心,証据归証据,张广兴明明是国民党員嘛!再一說,如果在国民党員里查出一个潜伏的共产党員,这事情不小,而且对他們头目人都有些不大方便,抓住小辮子就許讓人家給来一下子。兩下子一碰头,还是周荣光出了个主意,他是“事岀有因,査无实据”,不好下手,爽性把人情送給比国佬,請比国資本家看着办,办对了自是很好,办錯了也沒什么自己的責任,眞是再妙沒有了。无声无息地干掉。来个悄悄地失踪,也就算了。
比国佬把这項任务交給了林三。林三在日租界开着大烟館,吃八方的买办,和地痞流氓一向勾勾搭搭,就花錢买通了几个人。有天,乘张广兴他們过老鉄桥的时候,从暗中打了一槍。幸好沒有打中。
张广兴早就提防这一手了,出出进进,他向来不落单。特地找一些工人保护他。包汉文他們不是不能复职嗎?这五个人整天輪班跟着他。这样,地痞流氓也就更下心了,而且另有內綫帮忙他們。后来又有一天,正好是十月一日,广兴他們要到伪社会局去办交涉,走到××路口上,忽拉一下子从看报牌子后边,街道的角落里涌来了几个打手,他們照直奔广兴来了,有的动拳,有的动脚,还有一个从小腿肚子上拔出一把匕首,照广兴的腿胯骨就是一下子!虽然有人护着广兴,可是架不住那边的人多,广兴挨了这一刀子,立时倒了下来。可他能沉得住气,他喊:“抓住流氓,他們是凶杀!抓住他們!”
过路的人从前后左右一齐拥过来。流氓們一看事儿不妙,呼嘯一声,扭头便跑。广兴他們看准那个动刀的了,把那小子按住。連凶器带人,算是抓住一个活口。这事情可就好办了。
忍着鑽心痛的刀伤,张广兴和凶手一齐归警局了。警局里的人認識这些流氓,官面儿不惹地头蛇,光說和,了事无。广兴他們一看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这还成?就要求轉解法院打官司。
法官坐在上面,指着凶手問张广兴:“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张广兴捂着伤口,血又順褲角流了一大片。
法官又指着张广兴問凶手:“你認識他嗎?”流氓橫眉竪目,脖子一歪,胸脯一挺,咧着个大嘴就喊:“認識,我他娘的認識他不少日子了,刺手貨,今天可讓我逮上了。他欠我錢不还。”
法官倒是沉得住气,就又指着凶手問张广兴:“你是該他的錢嗎?”
张广兴痛得順腦門子滴溚汗珠,臉色都变了。但是話却說得有条有理。“咳,这是謀杀。我不跟他說,他是讓人花錢雇的,我跟林子香打官司。請法院傳他吧。他在比商电灯电車公司呢。他是买办。”
法官一听,心里明白这是和發动全市的电車电灯工人大罢工有关。不是明伙路劫,这里还有外国人的事。吓得他暗自叫奶奶,“我这是碰了那股子邪霉了,这么难歪歪的事讓我歪上了。”法官便也要了个三推六拖,烏云遮月的办法。指着张广兴的大腿說:“哎呀呀,你这伤口不淺,流血过多,你看臉白成什么了。赶快送医院吧,养伤要紧。伤好了再过堂。”話說完,他退堂了。
走出审訊室,广兴一看,車厂、电厂和公司的工人,都有人赶来了。而且叫了汽車来。广兴被人們連扶带抱地送上車去。
汽車开到大街上。广兴痛得眼前直發黑。这时候,同車的于世淸便喚他:“广兴,广兴,你睜眼看看!”
张广兴把眼睛强睜开来。嗬呀,街上的电車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停了下来。原来是电車工人听設张广兴遇刺了,准知道这是比国佬下的毒手,馬上来了个全綫停車罢工。看到这光景,张广兴激动得兩行眼泪滾了下来。斬釘截鉄的吐了几句話:“大家眞对的起我;我张广兴死了也甘心!我是坚决干到底呀,决不能辜負大家。”
工人們对他也是关心到極点了。把他送到馬大夫医院。这个医院是外国人办的买卖,病多重先擱一边,拿錢来。同去的工人就拍胸脯,把医藥費都攬在自己身上。张广兴这才被抬进急救室去。
张广兴年紀很輕,又是外伤,养了些日子,病也就逐漸好了。这天,大夫查过病房,看过他的伤口,忽然又回来了。瞪着眼睛和他說:“我看你是个好人。”
张广兴不免有些奇怪,就說:“大夫,您怎么說这話呀?我看您也是个好人。”
沒想到大夫紧接着来了这么一句:“我几乎成了坏人。成了犯罪的人!”
张广兴再一打量大夫的臉色,心里一动,便盯着問:“是不是有人要逮我?害我?我为什么被刺,这事情您也全知道?”
大夫唔了一声,望着广兴:“我要不是看你这人朝气勃勃,敢說散干,我也就不說給你了。吿訴你,你千万不要声张。声张出去,你沒有好,我也沒有好。你可不能連累我呀?”
张广兴笑笑,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們工人,赤胆紅心,无牽无挂。你放心吧,有什么尽管說。”
大夫是眼珠子轉了兩轉,嘴巴扁了几扁,含糊地說着:“有人打算买,买通我,用毒藥,你知道,或是用錯了藥把你害死。我不能干这事。吿訴你,你也別再問了,你赶快偸偸地走吧。”
“好,我明白了。謝謝大夫你呀。”张广兴的腦袋里登时閃过林子香的影子。他明白这又是林三的毒計。
张广兴不敢怠慢,悄悄从医院里搬出来。他沒有回家,躱到他姨的家里。連一般的工人也找不着他到那儿去了。但是,张广兴幷沒有停止工作,經常叫一些人到他姨家去。
去的人很多。如今还能找到的一个是丁××。他被广兴叫去,进屋一看,病床上放着書报杂志,这不算新鮮,新鮮的是还有几本油印的小册子。弄得老丁一怔,这不都是共产党的小册子嗎?
广兴便說:“老丁,咱們要干到底,这样斗不行。咱們必須革命。要革命就得有革命的党領导咱們。你願意参加革命的党嗎?”
老丁明白了八成,这是讓他参加共产党呀。怪不得广兴这样积極呢,这样善于联系群众呢,敢情他是地下共产党員呀!他光顧楞神儿了,沒有馬上答腔。张广兴是話里留話,十分謹愼,也就把这一段話遮过去了。
另外一个便是张广兴的本家叔叔张巨明了。他去看他。张广兴就直接和他說:“咱們要搞革命,叔,你决心怎么样?”
张巨明指着鼻子說:“別人信不过,你本家叔叔总信的过吧?”
沉思片刻,張广兴照直問:“那么,你願意加入共产党嗎?”
“願意!你怎么干,我就跟你怎么干。”
“叔,你写个入党申請書吧。”
张巨明回来以后,馬上便考虑写入党申請書的事儿。当然,写这么一份申請書幷不簡单,张巨明总得准备准备,于是自然而然的便过了几天。就这几天的工夫,张巨明的机会便錯过了,他再也看不到张广兴了。畢竟他沒有逃开敌人的魔掌,被捕了!
被捕的情况,据广兴的爱人回忆,当时情况是这样:
深夜,他家突然有一陣紧急的敲門声音。广兴的爱人早有預料,算計到禍事要来了,好在张广光幷不在家里住,已經从他姨家移到別处去了。 ,.
这时张广兴的本家大爷在院里問:“找誰呀?”
“找人!”
“找誰?”
“开門吧,你!”
門打开。一群特务闖了进来。手电光乱射一陣,屋里屋外翻了个过。只是幷沒有张广兴的踪影。只有他老娘和他老婆,有人就喝問:“张广兴藏到哪儿去了?”
他輕易不回家住。”
“我問你他躱在哪儿啦?”
娘倆吓得說不上話来了,光是哭。广兴的本家大爷看不过,就說:“我們确实不知道他在那儿啊。老总!”
“好,那你跟我們辛苦一趟吧。”这几个家伙話到手到,竟給老人家上了手銬带走!
等到天光破曉。广兴的老婆急忙閃了出来。到扶輪中学一位严姓敎員家里找他。那曉得半路上正碰上姓严的老婆。她也是一臉失神的顏色。
“喂,嫂子。我們广兴在你家不?”
她也問她:“晚上到我們家抓他們来啦。我还以为在你家里呢。”
兩头都落了空。那么他們都藏到那里去了?这个謎沒有等多久,到中午就揭开了。因为特务机关把张家大爷放回来了。他吿訴了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广兴和姓严的躱在陶子明的家里。夜間国民党特务是几处一齐下手,他們同时被捕了去!……
七七事变前一兩个月,张广兴这才从北平的陆軍监獄被釋放了出来。他回来以后,馬上又取得联系,在鉄路工会工作起来。七七事变一起,他和几十个鉄路工人一起到蚌埠去。后来又回来,把家眷也接走。在蚌埠落戶。不过,他却沒有在蚌埠呆住,連他老婆也不知道他又跑到那里去了。一年多以后,他回来了,腿部受了槍伤。只有这一件事他沒瞞着他老婆,說是在新四軍的游击战役中,他們那部份游击队被日寇全部堵击,同志們全都牺牲了。他伤在腿上,当时也暈迷过去。等鬼子兵撤走,他这才醒了逃出来。他也吿訴了老婆,自己是共产党員。其实,他幷不是逃回来的。随后便在明光县开了一家魚粮店,經常人来人往的,成为地下工作的一个据点。这个点坚持了好几年,一直到1948年解放前夕。他在监獄中染下的肺病,这时候再也拖不住了,竟悄悄地死在魚店中。他斗爭了一生,遺憾的是畢竟沒有看到解放!
工人服这一套嗎!当然不服。誰也是窩着一肚子火气,嘟嘟囔囔,等时机爆發。后来事情發生在这个出缺的常务理事职位的問題上了。工人們坚持要补上一个新的来,資本家不同意。拉了很长时期的鋸,才由一个叫张广兴的补上来。张广兴是个俊俏的小伙子,那年才24岁,是公司的一个抄表員。原来文化水平也很低,滄县人,在乡下念过几年小学,后来便通过一位本家叔叔托情到“比商电灯电車公司”来了。这个年輕人很有雄心大志,白天抄表,晩上还到法汉中学夜校去学習,很懂得用功。而且他为人刻苦朴实,不吃喝玩乐,有点儿富裕錢便去买一点杂志新書看。懂得思索一些什么事情。如今老工人們回忆起他来,还說:“人家张广兴是好样的,能說能道,又是赤胆侠骨,好交朋友,好联系群众。”自然,像他这人物要被大家推选上台了。
他所以能够代替陈澤林,自然还另有原因。因为他也是国民党員。經常把这个身份挂在他的嘴皮子上。他上台以后,常务理事是三头为大,沒有一个总干事了。什么事全得三个常务理事联銜盖圖章。所以开初先拖了个时期,称得起是相安无事。
但是,比国佬却心狠手辣,毒計一招跟着一招来,打算把所有的老工人,特別是参加过1929年罢工的那些工人,都抓碴开革。另外一着便是只出人不进人,要职工越来越少。比国佬是懂得人多浪大这条道理的,兩个厂子合在一起一千来人,委实是受不了呀。活忙的时候,比国佬就找工头外包,这样一来,他就不怕牛么罢工的威胁了,因为干活的人和公司沒有什么雇佣关系。但这样还不算,还要停止增薪(按公司旧例每年增薪一次,一次可增几分錢),还要取消已有的福利。比国佬的面孔越来越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是把中国工人当做亡国奴看。
工人吃这一套么?不行,干柴烈火,越着越高,最后在1932年10月14日,召开了“比商电灯电車公司工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12人,张广兴被推选做大会主席,当場向比国資本家提出十項条件。条件的内容是:
一、設立工人子弟学校,月增敎育費200元;
二、給职工免費乘电車,免費用电的待遇;
三、年終發花紅;
四、工人在工作时一律發給官衣;
五、工友有死亡者發給葬埋費200元;
六、每个工人由公司代买兩袋牌价面;
七、职工工龄达22年的加發一年工薪做为养老金;
八、在定額以內节約用煤,發給职工煤賞;
九、病假不扣工資;
十、給工人解决宿舍住房;
比国佬接到工会的意見書,恨得直啄牙花子。心里罵道:“你們这群臭工人忘記自己是老几了,你們要上天哪!”如出一轍,洋鬼子表面不露声色,摆出洋大人高高在上的嘴臉,又来了个不答不理!
就跟上一次罢工一样,国民党市党部聞着腥味,党棍子們又来伸手了。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地面上換了一撥子新的地头蛇而已。如今已非南北大战那时局面,正是奉系坐天下的时代,市长是周荣光,市党部里有邵华和时子周,省委里面有张厉生、严智怡,这些錢串子們早就耳聞上次罢工,如何炸醬的事儿了。这回是机会凑手,如何肯輕輕放过?于是假惺惺地代工人們办起交涉来了。
比国佬跟买办林三一合計,这笔款子有上回的数目摆着,能多不能少呀。这錢挖的未免心痛。洋鬼子这回鬼头多了,慪气挡不住多花錢,这是何苦来?便由林三出头,悄悄把张广兴約来。在他办公室里密談一番。
林子香和张广兴一碰面,这小子先笑唧卿的朝他一竪大拇哥,說道:“广兴,你眞是好样的,我眞佩服你,这手儿搞的多漂亮啊。”
张广兴已經料出几分来了。他也会不动声色,只是說:“到底什么时候答复工人呢?老这么拖下去要出事哩!”
“咳,出事不出事,都在老弟你啦。”林三說到这儿,干笑兩声,随后又講:“咱們有錢花在自己人身上。这事只要你不管,抽手走,兄弟,你發洋財了,这个数!”林三把話打住,朝他眼前伸出兩个大手指来。
张广兴看也沒看,不做声儿。
“好吧,咱們剃头圖凉快,我給您再添个数!”林三又伸了一个手指出来。
张广兴这人可有計謀,还是不声不响。
林三干咳了兩声,又笑了兩笑,点点头。“好哇,你年輕輕的眞辣啊。行,我佩服你,我成全你。这样吧,再加个碼儿,四万塊。”林三把四个手指直晃到他鼻子跟前,嚷起来:“广兴,見好就收。可以啦,太可以啦。你算算吧,你一个月才拿三十几塊錢,你一年才拿三百多塊錢,十年才拿三千来塊錢,你就是活一百年也拿不到这四万塊錢。你算算吧,拿回去置房子买地做卖卖,干什么不够啊?”
逼到这儿。张广兴忍无可忍,这才頂了他一句:“我謝謝你的好意,你給我算的挺好,錢也給的不在少数。拿这錢發財做买卖嘛,那自然是够折騰一气的了。可惜我不想發財,不做买卖,我是替工人大伙办事,我是人,不是狗!”
这一嚷不吃紧,把个林三嚷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万沒想到鼻子碰在城墙上了!他把笑臉收住,冷笑兩声,說道:“你可別不識好歹,我要买你的命,花不了几个錢!”
张广兴也不含忽,說道:“你也別不識好歹,工人們干起来,够你瞧的。你不是有錢能买人么?好,你就拿錢花去吧!”說完,他扭头走了出来。
不敢怠慢,张广兴連忙跑到国民党市党部来。把这情况和头目人一說。把这几头饞狼餓狗都气坏了。他們咬牙切齿地說道:“好哇,好哇,比国佬也太錢狠了。这倆錢說什么也不放啊。拿四万塊錢就想把事情压下去呀,沒那么便宜的事!广兴同志你做的太对了。”
广兴便也裝做“同志”的样儿,乘机献策:“我們得大搞,得支持工人們罢工啊!”
“罢工?”几个头目人有点害怕。半晌才有誰喃喃地說了一句:“万一要是讓共产党利用上,点起火来呢?”
“不会,不会!有我,有我哪!”张广兴一拍胸脯。
这几个头目人一想,广兴是国民党党員,他能掌握住,便不会出大漏子,还是炸比国佬的肉醬,發洋財的事儿要紧。就說:“罢工事情太大,得問一下市长啊。”
那时候,国民党党部和国民党市政府总是碟儿碗儿的碰得叮当乱响。要步驟一致,还得协商,就由张广兴以工会代表的身份跑去見市长周荣光。这位周市长上得台来,兩袖正嫌風淸,急着要大把抓錢呢。听张广兴来請求支持他們电厂車厂工人罢工的事儿,正中下怀,这不是肥猪拱門么?这不是給他市长送大洋錢来了么?登时眉开眼笑,反倒給张广兴打气。說道:“比国資本家这样压迫我們工人,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人要求罢工是正当的,政府一定支持,兄弟我嘛也一定帮忙。哈哈……”这一关也打通了。
这天,九月士二日,天剛蒙蒙亮。深秋的早晨格外淸凉,一群群工人往电車厂子走来。这里由工会临时召集了一个大会。
人們黑鴉鴉的围了一片。从人群中直立起来,张广兴举起喇叭筒朝大家喊道:
“弟兄們!公司資本家拖了又拖,結果是十項条件,一項也不接受。好吧,我們給他一个厉害看看。从今天起,我們罢工了。但咱們罢工不能影响社会秩序,咱們电車还是照样开,只有一样,随便坐車不要錢。讓咱們中国老百姓也沾点光。他們帝国主义賺咱們中国洋錢賺的太多了,也讓他們吐点儿出来吧!”
黑鴉鴉的人群里爆起一片笑声。这个办法太好了,大家都拥护,一来不誤大家坐車办事,二来比国資本家还得往外貼本,比不干活还讓洋人难受,这簡直是拉他們的肉呀!张广兴又一揮手,喊道:“咱們电厂的哥儿們也照常燒鍋爐送电,可就是查电表的不查表,收电費的不收电錢,讓中国人白用电灯吧!”
大家又是一陣哄笑。笑声中,人群蠕动了,罢工开始了!
这一着可房害!电車还像往常一样,車輪子格楞格楞地在鉄軌上滾着,可是白花花的大洋錢却随着声音扔掉了。电灯还照样儿净光冒亮,可是那些电錢却一个也不見!比国佬一下子急傻眼了。
但是,他們还不肯和工人講条件。这口气那能輸啊?于是又由林三布下他的党羽,打算和工人們斗一斗。他們有句話:“我們洋人的买卖,不能受拿捏。”
如今不比先前,林三的手下人也多多了。又約来了兩名专門破坏工人运动,对付工人的大流氓、大走狗錢伯骥和王彩南。这些人的手法又毒又辣,比刘治倫这一群嘎杂子的本領自是高出一筹。不来硬碰,却来个軟泡,他們想撒下迷魂陣,专一的勾引那些不坚定的分子掉入陷阱中去。他們在“日租界”鴻义棧租了間房,大烟白面足这么一供应,另外是酒肉,金錢,女人明摆在那里,把一些他們認为可以腐化、拉下水来的工人叫到这儿来,然后問:“跟我們,你看見了沒有?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人一輩子倒是圖个么呀?”
不頂用,工人們臭卷他們一通,一个个火气都不小。这一着沒有使上。不光这一着沒使上,相反的倒听說张广兴他們另外搞了个秘密办公地点。这地点在那儿,他們不知道!
比国佬一看,想用分化工人的手段,內部自行解决是办不到了。得認头花錢。于是由比国佬出面,在××飯店摆了一桌洋餐。虽說洋餐,但也上了很多精致的中菜,要吃什么有什么。因为是請市长吃飯,怕不对这位周荣光的胃口。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比国佬这回自动开了腔。說道:“我們公司工人又鬧風潮了,这事还得請市长維持、制止。”
周荣光假裝不明白的:“哦!怎么他們鬧事了?不是电車还照样开着嗎?电灯也很亮嘛?”
“要命的是他們不收錢呀!”
“哦!怎么他們不收錢呢。这还了得。”这时候,通过林三的手,一张三万元的支票遞过去了。周荣光用眼一扫,臉子一搭拉,眼角上挂着冰霜。立刻把支票退回去。打着官腔說:“总办先生,你們劳資之間的事,我嘛,也很不便于插手,因为他們工人还是照样开車,照样供电,从維持社会治安角度来看,我也不便說什么。”說着,他立了起来,撢了撢屁股,說是还有飯局,端着个官架子走了。
总办也明白自己下的注小。于是轉天又是一場酒席,把支票换成了五万。五万?周荣光心里的話,我的价碼沒这么賤的,吃完了飯一抹嘴,又走了。总办只好又咬牙,又請客,又加碼儿。直到怠工的第十五天头上,支票換到廿万元的大数,周荣光一合計:“好啊,廿万!廿万能买多少所楼房了呢?弓也拉得够份儿了,老这么抗着洋鬼子,回头再惹岀別的事来。”赶紧唔了一声,把支票掖在腰包里,立时話鋒就改了。他气气哼哼地,說道:“这帮工人眞是可恶,老是搗乱。我看这里面一定有共产党的人操縱。”
“一定是有共产党分子搧动!”比国佬連忙点头。
周荣光就問:“你們有凭据么?”
“凭据沒抓住,可是影影綽綽的。”
就凭影影綽綽的这四个字,当然还不行。周荣光做官的人講究四面圓,八面光,便說:“要是这样的話,你們还得和市党部啦、省党部啦交涉。兄弟我是要严办这群搗乱工人的。”他眞滑,还替党部攬了点儿买卖。
其实,买卖不用他給攬。林三是拜八方的买办,过去他在煤矿上干过,这一套自然駕輕就熟,另外几张为数不小的支票也早已經开过去了。
就在这天晚上,深夜一点鐘的时候,省府委員张厉生忽然用电話将工人代表张广兴,还有印刷工会的陶子明,一共四个人叫到时子周的私室作最后的談判。連周荣光也在座。张厉生扯了一套官面儿話,滿应滿許的:“咱們明天立即复工,这样鬧下去,有碍覌瞻,违背邦交。怠工期間的工資嘛,照發!年終双薪嘛,兄弟我拿人格来担保。你們总信得过我张某人吧?”
张广兴他們早料到这一着了。他們不从这一面和党棍子頂牛,而是抬出几个問題来:“这样一来,是不是要影响党国威信呀?”“哎呀,这样可是不好向工人交代呀。”
“以后的事情很难办了。”
几个党棍子不好說話,周荣光却摆出市长的威風,指着张广兴橫眉立目地問道:“今天怠工第几天了?”
“第十六天。”
“你們老这样鬧下去还行呀!”周荣光紧接着把帽子扣下来,“当初我跟你有言在先,叫你們必須团結一致,不扰乱治安,一切合理合法,我才能帮忙,可是現在……”
张广兴忍不住了,紧盯一句:“現在又怎么样?”
“現在,現在你們里面出了共产党,撒傅单,煽动工人,破坏治安,你知道不知道?”
“沒有的事。我們十五天,一点事儿也沒出。”
沒料想,张广兴居然敢頂撞他市长兩句。正好借这机会冒火儿。张开他那血盆大口,狼一样叫起来:
“张广兴,我命令你通知他們。今天午后三点以前,全体必須复工。誰不服从,就按共产党分子煽动罢工論罪。有一个斃一个,有一对斃一对!”
有去黑臉的,也有去白臉的。那几个便一口一个“广兴”叫着。說道:“大家都要从大局着想,正是国难当头,剿“匪”紧急的时候,我們一定要顧全邦交,別讓共产党利用了。現在从很多迹象看,有共产党操縱的可能。广兴,我們要注意啊。广兴,据說还發現了一些小册子!”
张广兴一口回絕:“那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不能不防止喲!”几个党棍子抓住这頂紅帽子了,就說:“馬上复工,一定要馬上复工!”
几个小时之后,天边剛剛挂出半堵阳光,电厂車厂的工人們便三三兩兩的向南市庆云戏院走来。今天召开临时大会。許多工人还蒙在鼓里,以为是比国佬斗不过,低头講条件了呢。瞧会場上这个热鬧劲儿呀。
人声忽然靜止。原来是张广兴站到台上来了。他声音不大自然,連連喊了几声:“工友們,工友們!”話梗住。底下是一陣唧唧喳喳。“怎么啦?张广兴!”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他。
张广兴下决心了,就把晚上交涉的話,一五一十端了个底掉。工人一听,这还了得!像火山崩开了口子,像热水煮开了鍋,正这儿人声鼎沸,喊喝成一片呢。张广兴却兩手大张,急忙叫大家靜住。他說:“我和兄弟們一样,眞是不願意复工啊,可是逼到这儿,不复工不行啦。再不复工,我們就不单是和比国資本家斗,也是和市党部,和公安局保安队斗了。咱們工人們赤手空拳,劲头再大,心气再齐,却总不能这样对付政府的槍啊,炮啊?咱們为了把眼光放远,把力量保存得足足的,不在刺刀跟前做沒价値的牺牲,我們只好先复工了。复工幷不算是咱們的失敗,咱們团結得很好呀,咱們到底狠狠敎訓了一下比国資本家呀,到底明白了誰才是眞正帮助咱們工人的呀……”张广兴越說越激动,激动得他話都講不下去了,嗓音哽咽了,終于放声大哭起来。
会場上是死一样的寂靜。个个把眼睛瞪得鼓鼓的,像是一团炸藥,簡直的就要炸呀,这时刻,看到情势不妙,周荣光手下的一員干将,市府第三科科长穆道厚晃着腦袋走到前边来。他张开尿盆似的大嘴,嚷道:“我吿訴你們,你們听眞了!市长有命令,命令你們今天下午立即复工,免受共产党分子的利用!你們不就是想多要錢嗎?市长已經給你們办妥,你們要求买兩袋牌价面,多剩倆錢,已經办到啦。人家比国人已經答应了。你們要官衣,人家看周市长的面子,也答应了,給二百件冬季皮衣。行啦,要求差不多啦,你們要立即复工,不复工就是破坏社会治安,破坏社会治安就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就得槍斃!”……
大伙听得几乎气炸了肺,誰都是头暈腦漲的。有人想出去。嗬呀,不行!保安队已經堵上門了,大伙都低下头来。有人喊着:“我們听张广兴的。我們信得过张广兴。”罢工終于又被压下去了。
下午,各部門的工人低着腦袋进厂来了。剛一到电厂門口,不由得人們一怔,門口上把滿了保安队,个个槍上插着刺刀,把母狗眼瞪了个賊圓,就差用槍刺子戳人了。进厂一看,里面还貼着布吿。工人們一边看一边叨咕:
“怎么?罢工十七天的工資一槪不發!来年年終欢薪取消!三年不漲薪!”好啊,比国佬是倒打一耙,嗆上火儿了。这还不算,还把工人包汉文等五个名列黑榜,宣布开除!
大伙一看,这是騎在腦袋上拉屎,故意跟工人們做对。你說我講的,誰也不再往里迈步了。吵嚷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大家放明白点,可別再鬧事呀!保安队是眞槍实弹,鬧哄着要抓共产党哪!”工会里的这批工賊、流氓打手就足这么一煽風,把大伙說的沒了主张。
“不要紧!不要紧!”刘治倫他們又出头了,从另一面攻。說道:“已經請示过市党部了。大家还是先复工呀!市党部保証包汉文他們可以复工。由党部办交涉。”
花說柳說的,工人只好低头走进車間。車間里怎么多了这么些人啊?好啊,一个人屁膜后面跟着一个保安队,他們拿着槍,刺刀也就离后背尺来长。工人們簡直和和罪犯一个样!
包汉文他們五个人就連忙跑到国民党市党部。在門口等了半天,这才有个小职員出来講話,說道:“你們不是被开革,是停职。停职嘛是公司的权利,市党部也不便过多干涉。你們先忍耐一下,等着复职吧。”
“那我們肚子餓了朝誰說去呢?”包汉文他們就問。
“忍耐嘛!自己想想法子嘛!”这位小职員把臉子一摔,走进去了。
这几个人整天随在张广兴的身后,到处交渉,到处沒有結果。于是乘这机会,借这几个人做幌子,大工賊錢伯慶、王彩南派人下到各車間,到处宣傳:“张广兴惹了比国总办,讓咱們大家跟着倒霉。咱們大伙齐心哪,把张广兴赶走哪!”
听說是要把张广兴赶走,大伙喊喝連声,誰听这一套的,硬把狗腿子給攆出来了。
一計未成,又生一計。偏也凑巧,有个电車車守胡宝山卖車票的当儿,誤将車票画錯了一张。被稽查查出,于是硬把芝麻大的事儿当成黃豆,报吿給公司了。公司里的工賊錢伯驥、王彩南正抓碴儿要破坏工会里的这批斗爭人物呢,覚着是个坎儿,就把胡宝山找到日租界鴻义棧里来。指着他說:“姓胡的,摆在你眼前头兩条路,你走哪一条吧!”
胡宝山說:“我犯了什么錯?要你給我摆路。”
“你画錯了車票,这事不小呀。一条道,你承認这是张广兴敎你們搞的,說是要一律吃票营私,自己到公司自首,随后到法院吿张广兴去。吿下来,你明白吧,比国人在职位上,薪金上还要照顧照顧你哪。算你命里該着,要走洋运,我姓錢的帮你这个忙,哈哈。”
胡宝山冷眼問:“另外那一条呢?”
“怎么,你还問那一条?那一条路,你想也想得明白,犯了这么大的錯誤,洋人来一张黃条,就把你开革了。这碗飯你就吃不成了。你想想,心里怕不怕?”
胡宝山反倒嘿嘿一笑:“不就是开革么?我姓胡的領着。张广兴是好人,为工人大伙办事,我姓胡的不能陷害好人。你小子借刀杀人,放心吧,你沒个好!”錢伯驥抹了一鼻子灰不說,而且这事嚷嚷开去,工人們团結的心气更足了。胡宝山虽然被开革了,但是倒更使工賊們难以下手了。
二計不成,又生三計。这一計可毒辣。林三林子香又去找市长去了,他問:“张广兴味儿不对,他这人到底是怎么一个国民党員呢?你們保险么?”
周荣光是做官来的,凡事不担肩儿,于是連忙和党部的几个头目人叨咕。原本,这几个党棍子就有些照影子,张广兴年輕輕的,这么联系群众,这么任劳任怨,到底为了什么啊?”明摆着給他白花花四万塊現洋,他都不眼暈,不伸手啊!察其言覌其行,也覚着不大对味儿,莫不是张广兴別有什么来路?不过疑心归疑心,証据归証据,张广兴明明是国民党員嘛!再一說,如果在国民党員里查出一个潜伏的共产党員,这事情不小,而且对他們头目人都有些不大方便,抓住小辮子就許讓人家給来一下子。兩下子一碰头,还是周荣光出了个主意,他是“事岀有因,査无实据”,不好下手,爽性把人情送給比国佬,請比国資本家看着办,办对了自是很好,办錯了也沒什么自己的責任,眞是再妙沒有了。无声无息地干掉。来个悄悄地失踪,也就算了。
比国佬把这項任务交給了林三。林三在日租界开着大烟館,吃八方的买办,和地痞流氓一向勾勾搭搭,就花錢买通了几个人。有天,乘张广兴他們过老鉄桥的时候,从暗中打了一槍。幸好沒有打中。
张广兴早就提防这一手了,出出进进,他向来不落单。特地找一些工人保护他。包汉文他們不是不能复职嗎?这五个人整天輪班跟着他。这样,地痞流氓也就更下心了,而且另有內綫帮忙他們。后来又有一天,正好是十月一日,广兴他們要到伪社会局去办交涉,走到××路口上,忽拉一下子从看报牌子后边,街道的角落里涌来了几个打手,他們照直奔广兴来了,有的动拳,有的动脚,还有一个从小腿肚子上拔出一把匕首,照广兴的腿胯骨就是一下子!虽然有人护着广兴,可是架不住那边的人多,广兴挨了这一刀子,立时倒了下来。可他能沉得住气,他喊:“抓住流氓,他們是凶杀!抓住他們!”
过路的人从前后左右一齐拥过来。流氓們一看事儿不妙,呼嘯一声,扭头便跑。广兴他們看准那个动刀的了,把那小子按住。連凶器带人,算是抓住一个活口。这事情可就好办了。
忍着鑽心痛的刀伤,张广兴和凶手一齐归警局了。警局里的人認識这些流氓,官面儿不惹地头蛇,光說和,了事无。广兴他們一看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这还成?就要求轉解法院打官司。
法官坐在上面,指着凶手問张广兴:“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张广兴捂着伤口,血又順褲角流了一大片。
法官又指着张广兴問凶手:“你認識他嗎?”流氓橫眉竪目,脖子一歪,胸脯一挺,咧着个大嘴就喊:“認識,我他娘的認識他不少日子了,刺手貨,今天可讓我逮上了。他欠我錢不还。”
法官倒是沉得住气,就又指着凶手問张广兴:“你是該他的錢嗎?”
张广兴痛得順腦門子滴溚汗珠,臉色都变了。但是話却說得有条有理。“咳,这是謀杀。我不跟他說,他是讓人花錢雇的,我跟林子香打官司。請法院傳他吧。他在比商电灯电車公司呢。他是买办。”
法官一听,心里明白这是和發动全市的电車电灯工人大罢工有关。不是明伙路劫,这里还有外国人的事。吓得他暗自叫奶奶,“我这是碰了那股子邪霉了,这么难歪歪的事讓我歪上了。”法官便也要了个三推六拖,烏云遮月的办法。指着张广兴的大腿說:“哎呀呀,你这伤口不淺,流血过多,你看臉白成什么了。赶快送医院吧,养伤要紧。伤好了再过堂。”話說完,他退堂了。
走出审訊室,广兴一看,車厂、电厂和公司的工人,都有人赶来了。而且叫了汽車来。广兴被人們連扶带抱地送上車去。
汽車开到大街上。广兴痛得眼前直發黑。这时候,同車的于世淸便喚他:“广兴,广兴,你睜眼看看!”
张广兴把眼睛强睜开来。嗬呀,街上的电車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停了下来。原来是电車工人听設张广兴遇刺了,准知道这是比国佬下的毒手,馬上来了个全綫停車罢工。看到这光景,张广兴激动得兩行眼泪滾了下来。斬釘截鉄的吐了几句話:“大家眞对的起我;我张广兴死了也甘心!我是坚决干到底呀,决不能辜負大家。”
工人們对他也是关心到極点了。把他送到馬大夫医院。这个医院是外国人办的买卖,病多重先擱一边,拿錢来。同去的工人就拍胸脯,把医藥費都攬在自己身上。张广兴这才被抬进急救室去。
张广兴年紀很輕,又是外伤,养了些日子,病也就逐漸好了。这天,大夫查过病房,看过他的伤口,忽然又回来了。瞪着眼睛和他說:“我看你是个好人。”
张广兴不免有些奇怪,就說:“大夫,您怎么說这話呀?我看您也是个好人。”
沒想到大夫紧接着来了这么一句:“我几乎成了坏人。成了犯罪的人!”
张广兴再一打量大夫的臉色,心里一动,便盯着問:“是不是有人要逮我?害我?我为什么被刺,这事情您也全知道?”
大夫唔了一声,望着广兴:“我要不是看你这人朝气勃勃,敢說散干,我也就不說給你了。吿訴你,你千万不要声张。声张出去,你沒有好,我也沒有好。你可不能連累我呀?”
张广兴笑笑,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們工人,赤胆紅心,无牽无挂。你放心吧,有什么尽管說。”
大夫是眼珠子轉了兩轉,嘴巴扁了几扁,含糊地說着:“有人打算买,买通我,用毒藥,你知道,或是用錯了藥把你害死。我不能干这事。吿訴你,你也別再問了,你赶快偸偸地走吧。”
“好,我明白了。謝謝大夫你呀。”张广兴的腦袋里登时閃过林子香的影子。他明白这又是林三的毒計。
张广兴不敢怠慢,悄悄从医院里搬出来。他沒有回家,躱到他姨的家里。連一般的工人也找不着他到那儿去了。但是,张广兴幷沒有停止工作,經常叫一些人到他姨家去。
去的人很多。如今还能找到的一个是丁××。他被广兴叫去,进屋一看,病床上放着書报杂志,这不算新鮮,新鮮的是还有几本油印的小册子。弄得老丁一怔,这不都是共产党的小册子嗎?
广兴便說:“老丁,咱們要干到底,这样斗不行。咱們必須革命。要革命就得有革命的党領导咱們。你願意参加革命的党嗎?”
老丁明白了八成,这是讓他参加共产党呀。怪不得广兴这样积極呢,这样善于联系群众呢,敢情他是地下共产党員呀!他光顧楞神儿了,沒有馬上答腔。张广兴是話里留話,十分謹愼,也就把这一段話遮过去了。
另外一个便是张广兴的本家叔叔张巨明了。他去看他。张广兴就直接和他說:“咱們要搞革命,叔,你决心怎么样?”
张巨明指着鼻子說:“別人信不过,你本家叔叔总信的过吧?”
沉思片刻,張广兴照直問:“那么,你願意加入共产党嗎?”
“願意!你怎么干,我就跟你怎么干。”
“叔,你写个入党申請書吧。”
张巨明回来以后,馬上便考虑写入党申請書的事儿。当然,写这么一份申請書幷不簡单,张巨明总得准备准备,于是自然而然的便过了几天。就这几天的工夫,张巨明的机会便錯过了,他再也看不到张广兴了。畢竟他沒有逃开敌人的魔掌,被捕了!
被捕的情况,据广兴的爱人回忆,当时情况是这样:
深夜,他家突然有一陣紧急的敲門声音。广兴的爱人早有預料,算計到禍事要来了,好在张广光幷不在家里住,已經从他姨家移到別处去了。 ,.
这时张广兴的本家大爷在院里問:“找誰呀?”
“找人!”
“找誰?”
“开門吧,你!”
門打开。一群特务闖了进来。手电光乱射一陣,屋里屋外翻了个过。只是幷沒有张广兴的踪影。只有他老娘和他老婆,有人就喝問:“张广兴藏到哪儿去了?”
他輕易不回家住。”
“我問你他躱在哪儿啦?”
娘倆吓得說不上話来了,光是哭。广兴的本家大爷看不过,就說:“我們确实不知道他在那儿啊。老总!”
“好,那你跟我們辛苦一趟吧。”这几个家伙話到手到,竟給老人家上了手銬带走!
等到天光破曉。广兴的老婆急忙閃了出来。到扶輪中学一位严姓敎員家里找他。那曉得半路上正碰上姓严的老婆。她也是一臉失神的顏色。
“喂,嫂子。我們广兴在你家不?”
她也問她:“晚上到我們家抓他們来啦。我还以为在你家里呢。”
兩头都落了空。那么他們都藏到那里去了?这个謎沒有等多久,到中午就揭开了。因为特务机关把张家大爷放回来了。他吿訴了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广兴和姓严的躱在陶子明的家里。夜間国民党特务是几处一齐下手,他們同时被捕了去!……
七七事变前一兩个月,张广兴这才从北平的陆軍监獄被釋放了出来。他回来以后,馬上又取得联系,在鉄路工会工作起来。七七事变一起,他和几十个鉄路工人一起到蚌埠去。后来又回来,把家眷也接走。在蚌埠落戶。不过,他却沒有在蚌埠呆住,連他老婆也不知道他又跑到那里去了。一年多以后,他回来了,腿部受了槍伤。只有这一件事他沒瞞着他老婆,說是在新四軍的游击战役中,他們那部份游击队被日寇全部堵击,同志們全都牺牲了。他伤在腿上,当时也暈迷过去。等鬼子兵撤走,他这才醒了逃出来。他也吿訴了老婆,自己是共产党員。其实,他幷不是逃回来的。随后便在明光县开了一家魚粮店,經常人来人往的,成为地下工作的一个据点。这个点坚持了好几年,一直到1948年解放前夕。他在监獄中染下的肺病,这时候再也拖不住了,竟悄悄地死在魚店中。他斗爭了一生,遺憾的是畢竟沒有看到解放!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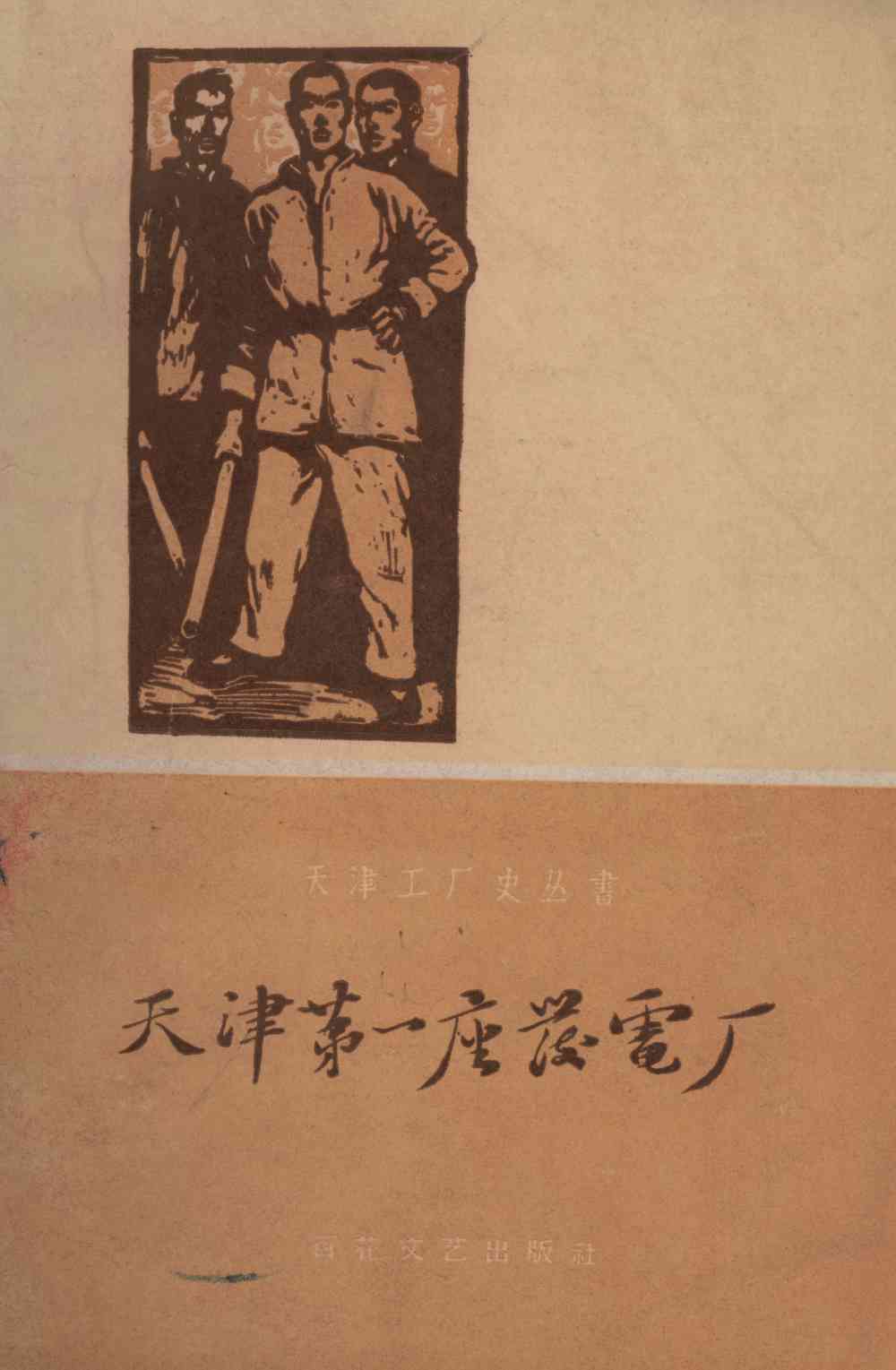
《天津第一座發電厂》
出版者: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天津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和背景。该活动受到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鼓足了工人的干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阅读
相关地名
天津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