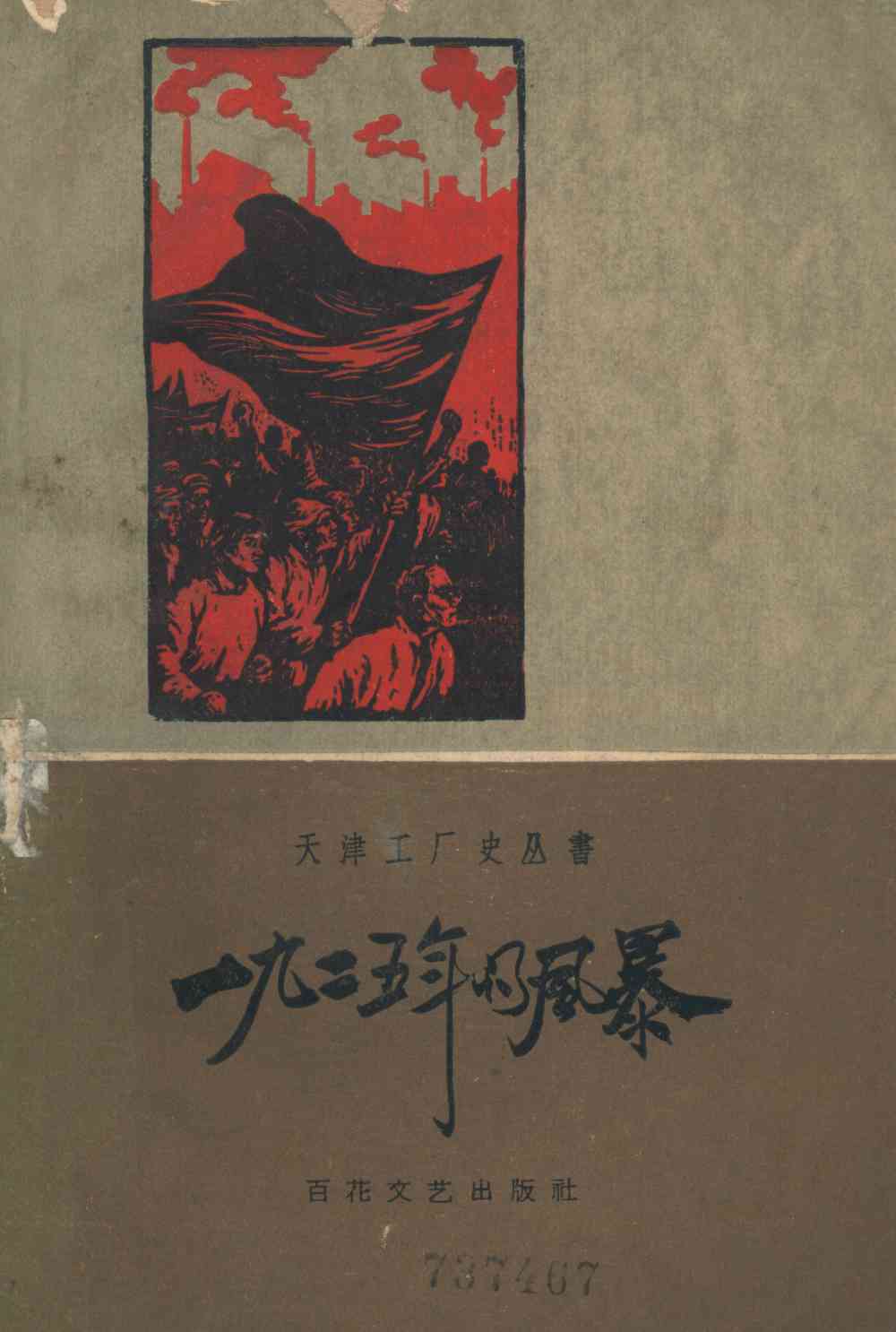内容
模范就有模范样,
英雄就有英雄胆,
不怕难来不怕苦,
外行硬把內行专,
晝夜苦战二年整,
砸断化学神秘栓,
化学梭子制成功,
振动全国美名傳。
要問此人他是誰,
就是劳模孙宝魁,
要問他文化有多高?
初中还沒有上完。
迫出家門
早在三十多年以前,那时孙宝魁还是个小孩子,父亲为了养活这家人,忍受着痛苦,用高价租种了地主四亩地,一年到头不够吃,父亲每逢別人紅白喜事时去帮帮忙,給人家扛个活,做做飯,再要不够了,就把他娘几个送到老娘家表。天长日久还是不行,父亲一賭气,就离开了家乡——香河,跑到了天津衞。
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怎么办呢?只好流浪在街头上,給人家扛活当苦力。慢慢的熟習了,就拉膠皮,逐漸求人吿友找个地方做飯。母亲在家也过不下去了,就带着宝魁和妹妹找到父亲这里。在那个年月里,他父亲就是餓着肚子,也养活不了他娘几个呀,宝魁沒办法,上街去拾煤核,母亲給人做点零活,再拾点菜叶,就这样将就活着。苦难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压着他們,父亲因为日以繼夜的劳累,又沒东西吃,慢慢的就病倒下了。眼看着家里老小挨餓,急的宝魁直哭。沒有办法就求人找了个事,到楊庄子裕大秒厂(現在天津国棉三厂前身)学徒。
宝魁剛十六岁,听說有地方吃飯了,就高兴的說:“这回我可能养活爹了”。誰想到满不是那么回事。进厂以后,日本人就把他送到木管去学徒,剛一进厂工資是一毛八分錢,別說养爹,就是自己吃咸菜也不够呀。一天譲他干十二个小时活,不好就是一頓板子,打的他头上大疙瘩套小疙瘩,自己还不敢言語。这样鬼子还不解气,又讓他去掄压力。一个小孩子,,那能揄得了呢,不掄就是一頓板子,沒有办法,他只得哭着找来一条一尺多长的板凳,这才利压力一样高,狠心的鬼子就讓这么小的孩子掄了三年压力。他个子小,力气又不足,哪能受得住呢?累的宝魁回家趴在炕上起不来,每回一听上工笛响,就吓的倒在媽媽怀里哭。可是媽媽又有什么办法,只好哄着說:“孩子,沒办法,沒有吃的,咱家又沒房子沒有地的,等你长大就好了!”可是自己却偸偸的落泪,每天領着妹妹出去拾菜叶吃,有时逢上好点的,就拿回来給宝魁留着,大家都瘦的象干柴似的。
最惨的还是在民国二十八年,那正是天津閙大水的时候。父亲由于劳累过度,沒錢医治,几天就死了。父亲的死給宝魁更增加了痛苦,家里要錢沒有錢,要东西沒有东西,大水象凶神似的四面八方包围着楊庄子,有誰来管呢?实在沒有办法了,他找到一个什么于九爷,好話說了八車,这才借了一塊門板。宝魁把它釘了一个盒子,把父亲的尸首裝殮起来,由鄰居帮忙,抬在砖堆上放了二个月,水下去了才埋葬。这时家里更加困难了,自己一看沒有办法,只得下班后再到新倉庫一带給人扛草做苦力。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晚間再去扛草,日夜折騰,一个小孩子那受得了呢?經常干着干着活就暈倒了。母亲一看实在沒有办法,整天哭的兩眼肿肿的,忍受着痛苦,又把自己的千四岁的閨女送到了裕大紗厂。就这样一年年还穿不上衣服,媽媽常說;“几时才能熬到头呢?”
換湯不換葯
日本投降以后,孙宝魁心里很高兴,他想这回可好了,再也不用受气了。誰想滿不是那么回事,正象有的工人形容的那样:
日本授了降,
出来个国民党,
把头爪牙眞猖狂,
有事无事車間轉,
工人眞是遭了殃,
一年当中三大节,
节节都得把礼上,
要不就別想进厂。
宝魁說:“这眞是換湯不換藥”。日本剛剛走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又耀武揚威的跑来了。他們象瘋狗一样,进厂就咬上了工人。在那个时候,哪有穷人走的路呢?他不来还好,这一来,狗腿子、爪牙、流氓可猖狂起来了。进厂就成立所謂“工会”。这哪是工会,实际就是把头爪牙的聚集所。他們在这里时时刻刻算計着工人,一个不好,不是打来就是駡,开除成了家常便飯。每逢三大节——五月节、八月节和春节,他們还要在工人身上作买卖,用低价买来的东西高价售給工人,誰要不买,可就成了对头。到了一定时間,你还得給工头打点“人情”,要不就別想吃这碗飯。
一次宝魁在木管部里正干着活,伪工会主席李滨君嘻皮笑臉的拿着文明棍走进来說:
“孙宝魁干嘛呢!”
“涮油漆啦!”宝魁随声应着。李洪君得寸进尺的走到他的跟前小声說:“唉,有油漆嗎,給我来点!”孙宝魁一时轉不过劲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就问他說“你要它干嘛用?”他說:“嘿!你不知道我娶媳妇嗎”宝魁一听就楞啦,接着說:“你娶媳妇用厂里油漆干嘛?”李洪君一听事不对,苦笑着臉說:“哎,我不是問問嗎,你当是眞要啦!”他說完轉身走出来,从那天起他就盯上了孙宝魁。一天下午剛下班,一群爪牙跟上了孙宝魁,等他一出厂,就給包围了,一个人上手就把孙宝魁揪住,随手就要打他,这时一个人攔住說;“先別打他,李主席喜日子快到了,还用他呢!”那人說:“好,今天讓你多活会,你心里要放明白点,李主席喜日子快到了,誤了事我再找你算賬!”这群爪牙轉身走了。孙宝魁第二天一上班,李洪君装着一本正經的,走到他眼前說:“晚上有空給我油油門去!”就这样,孙宝魁白天上班,晚上到李洪君家給油漆門窗,一連干了好几天,不但分文不給,还得賠上油漆,事后又給他送了点礼道了歉才算完事。气得孙宝魁說:“这和小日本在的时候有什么兩样啊?我們受气还有个头嗎?”
解放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了。孙宝魁高兴的說:“这总算熬到头了!”
解放,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裕大紗厂随着社会的改变,也改变了过去的面貌。在共产党筑导下,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接着就取消了几十年来的万恶搜腰制度。工人們可以自由的出入了,再由不受任何人的限制。厂里为了照顧工人,建立了疗养院、保健食堂、职工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圖書館、俱乐部……等等,显著的提高了工人阶級的地位和生活水平。
孙宝魁当上了工会組长和技术員,亲自参加了工厂的管理,生活得到了改善,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他亲身感到了党的温暖。他总說:“党对我这么好,我用什么报答党呢?只有好好的工作了。”
創造洗槽机
一九五一年的三月間,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孙宝魁吃完飯,松心地向原动部澡塘走来,他剛走进鍋爐房門口,突然發現一堆木管(粗紗管),他奇怪的过去看了一眼,幷向工友問了一声:“这是干嘛用的?”“生火!”一个人不怎么在意地回答。孙宝魁一听又接上了一句說:“这不可惜了嗎?”那人粗声粗气的說:“可惜也沒办法,大房標子还燒火呢,別說一些破木管了!”宝魁一听不对劲,紧走一步,拿了个管子看了看說:“別燒,这东西修修还能用!”那个人不耐煩的說:“修嘛!这破玩艺还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日本在时都修不了,別說咱啦。宝魁一听这話心里象被石头堵住似的,一声不响气呼呼的走出厂来,到家把手巾一甩,趴在桌子上象受了委屈似的,利那間在他思想里出現了日本鬼子野田的凶象:一个张牙舞爪的日本人,站在他的眼前,指着宝魁鼻子說:“我們日本人在时,你們可以进厂干活,我們要是走了,你們別說織布、造梭,就是連綫也紡不出来。”宝魁想着想着掉下眼泪,拳头敲打着桌子激动的說:“难道我們中国人永远这样嗎?不!我們一定要造管,要織布!”他情不自禁的喊出来,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又向厂里走去。他走到那堆木管旁边,伸手拿出个管来,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左思右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他看呀看呀,發現粗紗管底部槽有点毛病,如果經过洗刷和修理还可以用。第二天一早,他就找到了工程师,把自己的看法細細的說了一遍,誰想这位黑鬍子的胖老头沒有听入耳,只給了宝魁一句話:“坏了就坏了吧,还修嘛?”宝魁一想能这样算了嗎?不,我是工会組长,应該管这事。于是他轉过身来,奔向工会,找到了主席、共产党員邢可愼,把事一說,主席馬上大力支持說:“你这想法太好了,如果用人工修可就費事了,你硏究硏究是否可以用机器操作?你只管大胆的想、大胆的做吧,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孙宝魁一听,得到了領导的支持,信心可就更足了。
从那天起,宝魁就算琢磨上廢紗管了。他自己也想:要用人工,这六千多管子几时才能修好?如果能够想出个洗槽机来可就好了。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象入了迷,天天夜里独自一人,趴在桌子上画圖,常常一夜一夜地也搞不出个名堂。日子久了,老婆可就煩啦,他要开灯,老婆就要关灯,有时造成口角。老婆說:“你一天穷画嘛?还想怎么着宝魁有时气的也說“反正你早晚会知道!”你一言我一語,閙的不太合适。
几个月之后,宝魁把洗槽机模型想好了,可是解决不了管子內堂起毛的間題,为这愁的他几天吃不下飯去。一天的下午,他下班回家,路过理髮室門口,看見理髮师的推子来回移动,收縮力很强,他就联想到自己的洗槽机,如果能根据这个道理,不就可以解决槽內堂起毛的問題嗎?他高兴的又返回了工厂,重新改制了模型。自己一試,左右收縮間題倒是解决了,可是前后不能移动,这怎么办呢?这可又把孙宝魁难住了。他飯也沒顧得吃,又进了車間,看着师付們鏇管。不知怎么,他冷丁發現师付們在做活时,脚前后有节奏的移动,他象發現了什么宝貝东西似的,聚精会神的看着,自己又想:如果根据这个道理,在洗槽机上按裝一个轉床卡子不就解决了嗎?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工人一說,大伙很高兴的說:“能行,咱們試試看!”工人們連夜为他赶做洗槽机,第二天一試驗,果然成功了。大伙高兴的說:“这回可节約多了!”六千多管子,几天就修理好啦。孙宝魁和大伙一样,高兴的睡不着覚,看看自己修好的管子想道:“中国人現在不但能紡紗織布,这回还能造管呢?”
打这之后,孙宝魁确是在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后来他又連連不断的創造了許多种新工具。
創造中国白色大漆
早在一九五六年,厂里任务非常紧张,可是車間里經常發生錯紗的現象,由于錯紗造成不少浪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經过查对,發現很多錯紗是由于錯管造成的。原来紗管顏色不显,大小一样,工人一忙就容易造成錯紗。孙宝魁一看,造成这么大的浪費,就覚得做木管的也应負責。是他就想:要是顏色明显容易区分不就好了嗎?可是自己又一想:本来大漆色种就很少,中国大漆只能配紅的,日本大漆虽說比中国好,可是也只能配些黃、綠以及其他淺色的。要想配成多种色,就必須要有白色大漆,可是白色大漆到哪儿去找呢?日本在时也曾研究过,但是沒有成功。自己又想,这东西要长期用进口貨也不行,难道我們就不能造点好的嗎?于是孙宝魁就琢磨上了大漆。
一天的晚上,木管部里靜悄悄的,只剩下孙宝魁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拿着中国大漆和日本大漆对比着看,他越看越入神,一时想起日本鬼子在时野田曾說过的一句話:“日本造的大漆,也是用的中国料,不过你們中国人可就造不了。”孙宝魁也曾問过他这是为什么,他說:“沒什么,可就是不能吿訴你們。”宝魁越想越生气,發誓說:“我非搞出来不可!”
当天晚上,他就把兩种大漆做了試驗,在他第一次加热时,發現中国大漆發混,經过过滤找出許多杂質。他把这种漆漆出后,發現光度不好,接着他又做第二次第三次……經过兩个月之后,他發現中国大漆加热到一定程度,就出現了水,把水过濾后,再加10度到40度的热量以后,大漆又逐渐变为金黃色,而且慢慢發出光来,把它漆出以后,不但光好,而且胜过日本大漆。
中国大漆試驗成功以后,使他信心就更大了,他又想起了白色大漆。开始他把立德粉配在大漆里,一試虽然起了一点变化,可是沒亮光。他就想怎样能讓它發亮呢?一次他看見玻璃,感到这玩艺不錯,就把它搞冰磨成粉末摻在大漆里,試驗后光虽好点,可是粗得沒法用。自己有点灰心,就把它放下了。党支部書記知道以后,对他說:“白色大漆对我們来說很有用处,有了它咱們就不至于造成这么多的錯紗,一个人作事总有失敗和成功,只要用心鑽,什么事都能成。”宝魁說:“我的文化低呀!”党支部書記又給比例子說:“高玉宝文化比你也不高,人家还能写書呢。只要肯干就行!”这些話象給了宝魁新的血液一样,使他的信心更足了。这时正赶上他老婆坐月子,他發現很多蛋皮堆在土箱里。他想:用玻璃太粗,这玩艺不行嗎?他就把丢下的鷄蛋皮一个个拾起来,把它硒干,磨成粉末,配在大漆里,經过試驗一看不行,不但是漆軟,而且光度还沒有加玻璃的好。这可怎么办呢?可把宝魁难坏了,一天天愁的飯也吃不下去,覚也睡不好,老婆看他逐漸削瘦,心里也痛他,每天回来都要买好的給他吃,一次他吃着飯,發現桌子上有个細磁茶碗,他一看它的光和色都很好,順手把它放进口袋里。飯后他又回到厂子里,把它砸碎,也磨成粉末,配在大漆里,一試驗不行,他又摻上一点蛋淸,結果倒是出現了一些白色,但是效果不大。自己一生气,走出工厂,正好路过第二工人文化宮,他順脚走进了圖書館,在那里翻閱着画报,接着就找一些化学書看了看。在一本書里,他突然看見有这样記載“……立德粉和硫化碱加上太白粉可以制造白色球鞋。”他一想:可不是,太白粉是专門提白的呀!于是他象懂得了什么新鮮事一样,飞快的跑进了工厂里,把黑色大漆拿出来,配上太白粉……一試驗效果很好,經过攪拌以后,出現了漂白的大漆;他把它漆在木管上;發現又有点渣滓,他随手又摻上一点磁土,他知道磁土是坚固的东西,經过一夜的試驗,就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正式試驗成功了。消息傳出以后,全国各地都来参現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国白色大漆”。他为我們国家又一次增加了光彩。
創造化学梭子
一九五八年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工农业都在大躍进,紡織业当然也不能例外,它要給全国人民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棉紗棉布,来适应人民的需要。生产的高速發展,生产中机物料的消耗也就大起来。梭子,是在紡織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市面上是供不应求的情况。怎么办呢?这就必須自己想办法。厂子里搞几把梭子倒还可以,可就是沒有原料。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一般木料可以作的。所以厂子里一再号召大伙技术革新,孙宝魁当然也不落后,就积極的响应了。开始他琢磨这种东西是否可以用化学原料代替呢?自己虽然是有了这种想法,可是不好意思說出来,怕搞不成讓人笑話,所以自己就不声不响的悶着干。干了一个时期,也沒搞出个名堂来,自己也很別扭。一天厂里买来了一批化学板,他就跑到材料科問这是从那买来的,人家吿訴他說是从北京买来的,他又追問材料員說:“这是用什么原料作的呢?”材料員說:“是用尿素和福而加林作的。”孙宝魁听了之后,就拿錢买些尿素和福而加林,試驗了二十多次,也沒有成功。不但如此,而且还不能溶在一起,自己实在沒有办法了,就买一些化学
書,一点点琢磨,一碰生字就問問別人,后来看到書里說石炭酸可以做塑料,他經过几次試驗还是不行。沒有办法了,他又找到了材料科,問人家那有作料的,人家吿訴他說,天津电木行做,他就开了一封介紹信,找到了天津电木行。
这个电木行,是一个剛剛公私合营不久的厂子,他拿介紹信一問,誰想人家一句也沒有告訴他,他扫兴的又走回厂子里。过几天他愁的沒有什么好办法,就下定决心再去看看,这次他碰見一位妇女,据說是經理的太太,她或多或少懂得点化学原料,人都称她为郭太太。她虽然懂点塑料,可是誰也不吿訴。孙宝魁問她說:“化学板是怎么做的?”她說“很簡单!”要問她塑料怎样配的,她只說一句“火候”,你要再問她多大火候,他只說“凭經驗!”除此以外,你再也問不出任何材料来。为了解她这一点材料,宝魁每逢星期都到这里来,不是帮人家干点活,就是和人家搞好团結,天长日久,这位郭太太也就不耐煩了。
一次,孙宝魁和这厂里采購員錢福林打上了交道,兩人說厂长道短的慢慢就扯起他买材料的事来,孙宝魁問他:“你經常买什么材料呀?”他說:“我过去买些石炭酸、福而加林还有安母尼亞。”宝魁一听有安母尼亞,心里就暗暗的記住它,再問他对到什么比例,他可就不知道了。宝魁回来以后,前后化了五十来塊錢,买来各种化学材料,一点点的配着。时間长了,老婆就問他說:“你最近总要当家,錢你把着,为什么总吃不到好菜呢?”宝魁一听,就支吾着說:“我不是留錢給你买新衣服穿嗎?”她一听这个也就不追了,可是她那知道宝魁用这錢搞試驗了呢。日子一长,党組織發現了,为这事还說过他,給了一些补貼,幷且还給他找来大批材料,从物質上精神上給了他很大支持,甚至看时讓他脫产来搞硏究,这对他革新起到重要作用。在一次試驗压力时,党支部書記李长荣常常跟他干到深夜,具体指导,亲自动手帮助他安装,这对他起到很大的鼓午,他感动地說:“要是沒有党的支持,我早就不搞了。”党就这样日夜帮助他,終于找到了配塑料的規津。一天,他把自己配好的料,拿到天津电木行,郭太太一看吃了一惊說:“你們工人可眞行呀!到底叫你搞成了。”他一边看着一边問:“你是怎样配的呢?”孙宝魁毫无保留的說:“我是用1:1的石炭酸和福而加林,用1/10的安母尼亞配的。”郭太太說:“我們过去用的安母尼亞比你們少,看起来还得向你們学習呢!”宝魁說:“这倒不然,你們有經驗,我們不过才摸索着于呀!”郭太太接着說:“不見得,你看我們的貿量还不如你們的好哪!”从此以后,她們就更客气的来对待宝魁了。孙宝魁找到这原理之后,就用厂里的破布碎紙綫头等,經过压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創造了空前未有的第一把“化学梭子。这样一来,可以給国家节省大批木材,而且还保証了質量。随后他又創造了塑料的大理石。他这种苦鑽苦干的精神,启發了厂里很多工人,成了职工們的一面旗帜。几年来由于党的敎育,他的覚悟也大大提高了,今年11月間他被光荣的批准了火綫入党。現在他日夜不倦地在工作着。不久的将来,他还会發明創造出更多新的东西来。
英雄就有英雄胆,
不怕难来不怕苦,
外行硬把內行专,
晝夜苦战二年整,
砸断化学神秘栓,
化学梭子制成功,
振动全国美名傳。
要問此人他是誰,
就是劳模孙宝魁,
要問他文化有多高?
初中还沒有上完。
迫出家門
早在三十多年以前,那时孙宝魁还是个小孩子,父亲为了养活这家人,忍受着痛苦,用高价租种了地主四亩地,一年到头不够吃,父亲每逢別人紅白喜事时去帮帮忙,給人家扛个活,做做飯,再要不够了,就把他娘几个送到老娘家表。天长日久还是不行,父亲一賭气,就离开了家乡——香河,跑到了天津衞。
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怎么办呢?只好流浪在街头上,給人家扛活当苦力。慢慢的熟習了,就拉膠皮,逐漸求人吿友找个地方做飯。母亲在家也过不下去了,就带着宝魁和妹妹找到父亲这里。在那个年月里,他父亲就是餓着肚子,也养活不了他娘几个呀,宝魁沒办法,上街去拾煤核,母亲給人做点零活,再拾点菜叶,就这样将就活着。苦难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压着他們,父亲因为日以繼夜的劳累,又沒东西吃,慢慢的就病倒下了。眼看着家里老小挨餓,急的宝魁直哭。沒有办法就求人找了个事,到楊庄子裕大秒厂(現在天津国棉三厂前身)学徒。
宝魁剛十六岁,听說有地方吃飯了,就高兴的說:“这回我可能养活爹了”。誰想到满不是那么回事。进厂以后,日本人就把他送到木管去学徒,剛一进厂工資是一毛八分錢,別說养爹,就是自己吃咸菜也不够呀。一天譲他干十二个小时活,不好就是一頓板子,打的他头上大疙瘩套小疙瘩,自己还不敢言語。这样鬼子还不解气,又讓他去掄压力。一个小孩子,,那能揄得了呢,不掄就是一頓板子,沒有办法,他只得哭着找来一条一尺多长的板凳,这才利压力一样高,狠心的鬼子就讓这么小的孩子掄了三年压力。他个子小,力气又不足,哪能受得住呢?累的宝魁回家趴在炕上起不来,每回一听上工笛响,就吓的倒在媽媽怀里哭。可是媽媽又有什么办法,只好哄着說:“孩子,沒办法,沒有吃的,咱家又沒房子沒有地的,等你长大就好了!”可是自己却偸偸的落泪,每天領着妹妹出去拾菜叶吃,有时逢上好点的,就拿回来給宝魁留着,大家都瘦的象干柴似的。
最惨的还是在民国二十八年,那正是天津閙大水的时候。父亲由于劳累过度,沒錢医治,几天就死了。父亲的死給宝魁更增加了痛苦,家里要錢沒有錢,要东西沒有东西,大水象凶神似的四面八方包围着楊庄子,有誰来管呢?实在沒有办法了,他找到一个什么于九爷,好話說了八車,这才借了一塊門板。宝魁把它釘了一个盒子,把父亲的尸首裝殮起来,由鄰居帮忙,抬在砖堆上放了二个月,水下去了才埋葬。这时家里更加困难了,自己一看沒有办法,只得下班后再到新倉庫一带給人扛草做苦力。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晚間再去扛草,日夜折騰,一个小孩子那受得了呢?經常干着干着活就暈倒了。母亲一看实在沒有办法,整天哭的兩眼肿肿的,忍受着痛苦,又把自己的千四岁的閨女送到了裕大紗厂。就这样一年年还穿不上衣服,媽媽常說;“几时才能熬到头呢?”
換湯不換葯
日本投降以后,孙宝魁心里很高兴,他想这回可好了,再也不用受气了。誰想滿不是那么回事,正象有的工人形容的那样:
日本授了降,
出来个国民党,
把头爪牙眞猖狂,
有事无事車間轉,
工人眞是遭了殃,
一年当中三大节,
节节都得把礼上,
要不就別想进厂。
宝魁說:“这眞是換湯不換藥”。日本剛剛走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又耀武揚威的跑来了。他們象瘋狗一样,进厂就咬上了工人。在那个时候,哪有穷人走的路呢?他不来还好,这一来,狗腿子、爪牙、流氓可猖狂起来了。进厂就成立所謂“工会”。这哪是工会,实际就是把头爪牙的聚集所。他們在这里时时刻刻算計着工人,一个不好,不是打来就是駡,开除成了家常便飯。每逢三大节——五月节、八月节和春节,他們还要在工人身上作买卖,用低价买来的东西高价售給工人,誰要不买,可就成了对头。到了一定时間,你还得給工头打点“人情”,要不就別想吃这碗飯。
一次宝魁在木管部里正干着活,伪工会主席李滨君嘻皮笑臉的拿着文明棍走进来說:
“孙宝魁干嘛呢!”
“涮油漆啦!”宝魁随声应着。李洪君得寸进尺的走到他的跟前小声說:“唉,有油漆嗎,給我来点!”孙宝魁一时轉不过劲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就问他說“你要它干嘛用?”他說:“嘿!你不知道我娶媳妇嗎”宝魁一听就楞啦,接着說:“你娶媳妇用厂里油漆干嘛?”李洪君一听事不对,苦笑着臉說:“哎,我不是問問嗎,你当是眞要啦!”他說完轉身走出来,从那天起他就盯上了孙宝魁。一天下午剛下班,一群爪牙跟上了孙宝魁,等他一出厂,就給包围了,一个人上手就把孙宝魁揪住,随手就要打他,这时一个人攔住說;“先別打他,李主席喜日子快到了,还用他呢!”那人說:“好,今天讓你多活会,你心里要放明白点,李主席喜日子快到了,誤了事我再找你算賬!”这群爪牙轉身走了。孙宝魁第二天一上班,李洪君装着一本正經的,走到他眼前說:“晚上有空給我油油門去!”就这样,孙宝魁白天上班,晚上到李洪君家給油漆門窗,一連干了好几天,不但分文不給,还得賠上油漆,事后又給他送了点礼道了歉才算完事。气得孙宝魁說:“这和小日本在的时候有什么兩样啊?我們受气还有个头嗎?”
解放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了。孙宝魁高兴的說:“这总算熬到头了!”
解放,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裕大紗厂随着社会的改变,也改变了过去的面貌。在共产党筑导下,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接着就取消了几十年来的万恶搜腰制度。工人們可以自由的出入了,再由不受任何人的限制。厂里为了照顧工人,建立了疗养院、保健食堂、职工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圖書館、俱乐部……等等,显著的提高了工人阶級的地位和生活水平。
孙宝魁当上了工会組长和技术員,亲自参加了工厂的管理,生活得到了改善,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他亲身感到了党的温暖。他总說:“党对我这么好,我用什么报答党呢?只有好好的工作了。”
創造洗槽机
一九五一年的三月間,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孙宝魁吃完飯,松心地向原动部澡塘走来,他剛走进鍋爐房門口,突然發現一堆木管(粗紗管),他奇怪的过去看了一眼,幷向工友問了一声:“这是干嘛用的?”“生火!”一个人不怎么在意地回答。孙宝魁一听又接上了一句說:“这不可惜了嗎?”那人粗声粗气的說:“可惜也沒办法,大房標子还燒火呢,別說一些破木管了!”宝魁一听不对劲,紧走一步,拿了个管子看了看說:“別燒,这东西修修还能用!”那个人不耐煩的說:“修嘛!这破玩艺还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日本在时都修不了,別說咱啦。宝魁一听这話心里象被石头堵住似的,一声不响气呼呼的走出厂来,到家把手巾一甩,趴在桌子上象受了委屈似的,利那間在他思想里出現了日本鬼子野田的凶象:一个张牙舞爪的日本人,站在他的眼前,指着宝魁鼻子說:“我們日本人在时,你們可以进厂干活,我們要是走了,你們別說織布、造梭,就是連綫也紡不出来。”宝魁想着想着掉下眼泪,拳头敲打着桌子激动的說:“难道我們中国人永远这样嗎?不!我們一定要造管,要織布!”他情不自禁的喊出来,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又向厂里走去。他走到那堆木管旁边,伸手拿出个管来,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左思右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他看呀看呀,發現粗紗管底部槽有点毛病,如果經过洗刷和修理还可以用。第二天一早,他就找到了工程师,把自己的看法細細的說了一遍,誰想这位黑鬍子的胖老头沒有听入耳,只給了宝魁一句話:“坏了就坏了吧,还修嘛?”宝魁一想能这样算了嗎?不,我是工会組长,应該管这事。于是他轉过身来,奔向工会,找到了主席、共产党員邢可愼,把事一說,主席馬上大力支持說:“你这想法太好了,如果用人工修可就費事了,你硏究硏究是否可以用机器操作?你只管大胆的想、大胆的做吧,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孙宝魁一听,得到了領导的支持,信心可就更足了。
从那天起,宝魁就算琢磨上廢紗管了。他自己也想:要用人工,这六千多管子几时才能修好?如果能够想出个洗槽机来可就好了。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象入了迷,天天夜里独自一人,趴在桌子上画圖,常常一夜一夜地也搞不出个名堂。日子久了,老婆可就煩啦,他要开灯,老婆就要关灯,有时造成口角。老婆說:“你一天穷画嘛?还想怎么着宝魁有时气的也說“反正你早晚会知道!”你一言我一語,閙的不太合适。
几个月之后,宝魁把洗槽机模型想好了,可是解决不了管子內堂起毛的間題,为这愁的他几天吃不下飯去。一天的下午,他下班回家,路过理髮室門口,看見理髮师的推子来回移动,收縮力很强,他就联想到自己的洗槽机,如果能根据这个道理,不就可以解决槽內堂起毛的問題嗎?他高兴的又返回了工厂,重新改制了模型。自己一試,左右收縮間題倒是解决了,可是前后不能移动,这怎么办呢?这可又把孙宝魁难住了。他飯也沒顧得吃,又进了車間,看着师付們鏇管。不知怎么,他冷丁發現师付們在做活时,脚前后有节奏的移动,他象發現了什么宝貝东西似的,聚精会神的看着,自己又想:如果根据这个道理,在洗槽机上按裝一个轉床卡子不就解决了嗎?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工人一說,大伙很高兴的說:“能行,咱們試試看!”工人們連夜为他赶做洗槽机,第二天一試驗,果然成功了。大伙高兴的說:“这回可节約多了!”六千多管子,几天就修理好啦。孙宝魁和大伙一样,高兴的睡不着覚,看看自己修好的管子想道:“中国人現在不但能紡紗織布,这回还能造管呢?”
打这之后,孙宝魁确是在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后来他又連連不断的創造了許多种新工具。
創造中国白色大漆
早在一九五六年,厂里任务非常紧张,可是車間里經常發生錯紗的現象,由于錯紗造成不少浪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經过查对,發現很多錯紗是由于錯管造成的。原来紗管顏色不显,大小一样,工人一忙就容易造成錯紗。孙宝魁一看,造成这么大的浪費,就覚得做木管的也应負責。是他就想:要是顏色明显容易区分不就好了嗎?可是自己又一想:本来大漆色种就很少,中国大漆只能配紅的,日本大漆虽說比中国好,可是也只能配些黃、綠以及其他淺色的。要想配成多种色,就必須要有白色大漆,可是白色大漆到哪儿去找呢?日本在时也曾研究过,但是沒有成功。自己又想,这东西要长期用进口貨也不行,难道我們就不能造点好的嗎?于是孙宝魁就琢磨上了大漆。
一天的晚上,木管部里靜悄悄的,只剩下孙宝魁一个人。他坐在椅子上,拿着中国大漆和日本大漆对比着看,他越看越入神,一时想起日本鬼子在时野田曾說过的一句話:“日本造的大漆,也是用的中国料,不过你們中国人可就造不了。”孙宝魁也曾問过他这是为什么,他說:“沒什么,可就是不能吿訴你們。”宝魁越想越生气,發誓說:“我非搞出来不可!”
当天晚上,他就把兩种大漆做了試驗,在他第一次加热时,發現中国大漆發混,經过过滤找出許多杂質。他把这种漆漆出后,發現光度不好,接着他又做第二次第三次……經过兩个月之后,他發現中国大漆加热到一定程度,就出現了水,把水过濾后,再加10度到40度的热量以后,大漆又逐渐变为金黃色,而且慢慢發出光来,把它漆出以后,不但光好,而且胜过日本大漆。
中国大漆試驗成功以后,使他信心就更大了,他又想起了白色大漆。开始他把立德粉配在大漆里,一試虽然起了一点变化,可是沒亮光。他就想怎样能讓它發亮呢?一次他看見玻璃,感到这玩艺不錯,就把它搞冰磨成粉末摻在大漆里,試驗后光虽好点,可是粗得沒法用。自己有点灰心,就把它放下了。党支部書記知道以后,对他說:“白色大漆对我們来說很有用处,有了它咱們就不至于造成这么多的錯紗,一个人作事总有失敗和成功,只要用心鑽,什么事都能成。”宝魁說:“我的文化低呀!”党支部書記又給比例子說:“高玉宝文化比你也不高,人家还能写書呢。只要肯干就行!”这些話象給了宝魁新的血液一样,使他的信心更足了。这时正赶上他老婆坐月子,他發現很多蛋皮堆在土箱里。他想:用玻璃太粗,这玩艺不行嗎?他就把丢下的鷄蛋皮一个个拾起来,把它硒干,磨成粉末,配在大漆里,經过試驗一看不行,不但是漆軟,而且光度还沒有加玻璃的好。这可怎么办呢?可把宝魁难坏了,一天天愁的飯也吃不下去,覚也睡不好,老婆看他逐漸削瘦,心里也痛他,每天回来都要买好的給他吃,一次他吃着飯,發現桌子上有个細磁茶碗,他一看它的光和色都很好,順手把它放进口袋里。飯后他又回到厂子里,把它砸碎,也磨成粉末,配在大漆里,一試驗不行,他又摻上一点蛋淸,結果倒是出現了一些白色,但是效果不大。自己一生气,走出工厂,正好路过第二工人文化宮,他順脚走进了圖書館,在那里翻閱着画报,接着就找一些化学書看了看。在一本書里,他突然看見有这样記載“……立德粉和硫化碱加上太白粉可以制造白色球鞋。”他一想:可不是,太白粉是专門提白的呀!于是他象懂得了什么新鮮事一样,飞快的跑进了工厂里,把黑色大漆拿出来,配上太白粉……一試驗效果很好,經过攪拌以后,出現了漂白的大漆;他把它漆在木管上;發現又有点渣滓,他随手又摻上一点磁土,他知道磁土是坚固的东西,經过一夜的試驗,就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正式試驗成功了。消息傳出以后,全国各地都来参現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国白色大漆”。他为我們国家又一次增加了光彩。
創造化学梭子
一九五八年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工农业都在大躍进,紡織业当然也不能例外,它要給全国人民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棉紗棉布,来适应人民的需要。生产的高速發展,生产中机物料的消耗也就大起来。梭子,是在紡織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市面上是供不应求的情况。怎么办呢?这就必須自己想办法。厂子里搞几把梭子倒还可以,可就是沒有原料。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一般木料可以作的。所以厂子里一再号召大伙技术革新,孙宝魁当然也不落后,就积極的响应了。开始他琢磨这种东西是否可以用化学原料代替呢?自己虽然是有了这种想法,可是不好意思說出来,怕搞不成讓人笑話,所以自己就不声不响的悶着干。干了一个时期,也沒搞出个名堂来,自己也很別扭。一天厂里买来了一批化学板,他就跑到材料科問这是从那买来的,人家吿訴他說是从北京买来的,他又追問材料員說:“这是用什么原料作的呢?”材料員說:“是用尿素和福而加林作的。”孙宝魁听了之后,就拿錢买些尿素和福而加林,試驗了二十多次,也沒有成功。不但如此,而且还不能溶在一起,自己实在沒有办法了,就买一些化学
書,一点点琢磨,一碰生字就問問別人,后来看到書里說石炭酸可以做塑料,他經过几次試驗还是不行。沒有办法了,他又找到了材料科,問人家那有作料的,人家吿訴他說,天津电木行做,他就开了一封介紹信,找到了天津电木行。
这个电木行,是一个剛剛公私合营不久的厂子,他拿介紹信一問,誰想人家一句也沒有告訴他,他扫兴的又走回厂子里。过几天他愁的沒有什么好办法,就下定决心再去看看,这次他碰見一位妇女,据說是經理的太太,她或多或少懂得点化学原料,人都称她为郭太太。她虽然懂点塑料,可是誰也不吿訴。孙宝魁問她說:“化学板是怎么做的?”她說“很簡单!”要問她塑料怎样配的,她只說一句“火候”,你要再問她多大火候,他只說“凭經驗!”除此以外,你再也問不出任何材料来。为了解她这一点材料,宝魁每逢星期都到这里来,不是帮人家干点活,就是和人家搞好团結,天长日久,这位郭太太也就不耐煩了。
一次,孙宝魁和这厂里采購員錢福林打上了交道,兩人說厂长道短的慢慢就扯起他买材料的事来,孙宝魁問他:“你經常买什么材料呀?”他說:“我过去买些石炭酸、福而加林还有安母尼亞。”宝魁一听有安母尼亞,心里就暗暗的記住它,再問他对到什么比例,他可就不知道了。宝魁回来以后,前后化了五十来塊錢,买来各种化学材料,一点点的配着。时間长了,老婆就問他說:“你最近总要当家,錢你把着,为什么总吃不到好菜呢?”宝魁一听,就支吾着說:“我不是留錢給你买新衣服穿嗎?”她一听这个也就不追了,可是她那知道宝魁用这錢搞試驗了呢。日子一长,党組織發現了,为这事还說过他,給了一些补貼,幷且还給他找来大批材料,从物質上精神上給了他很大支持,甚至看时讓他脫产来搞硏究,这对他革新起到重要作用。在一次試驗压力时,党支部書記李长荣常常跟他干到深夜,具体指导,亲自动手帮助他安装,这对他起到很大的鼓午,他感动地說:“要是沒有党的支持,我早就不搞了。”党就这样日夜帮助他,終于找到了配塑料的規津。一天,他把自己配好的料,拿到天津电木行,郭太太一看吃了一惊說:“你們工人可眞行呀!到底叫你搞成了。”他一边看着一边問:“你是怎样配的呢?”孙宝魁毫无保留的說:“我是用1:1的石炭酸和福而加林,用1/10的安母尼亞配的。”郭太太說:“我們过去用的安母尼亞比你們少,看起来还得向你們学習呢!”宝魁說:“这倒不然,你們有經驗,我們不过才摸索着于呀!”郭太太接着說:“不見得,你看我們的貿量还不如你們的好哪!”从此以后,她們就更客气的来对待宝魁了。孙宝魁找到这原理之后,就用厂里的破布碎紙綫头等,經过压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創造了空前未有的第一把“化学梭子。这样一来,可以給国家节省大批木材,而且还保証了質量。随后他又創造了塑料的大理石。他这种苦鑽苦干的精神,启發了厂里很多工人,成了职工們的一面旗帜。几年来由于党的敎育,他的覚悟也大大提高了,今年11月間他被光荣的批准了火綫入党。現在他日夜不倦地在工作着。不久的将来,他还会發明創造出更多新的东西来。
相关机构
天津国棉三厂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天津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