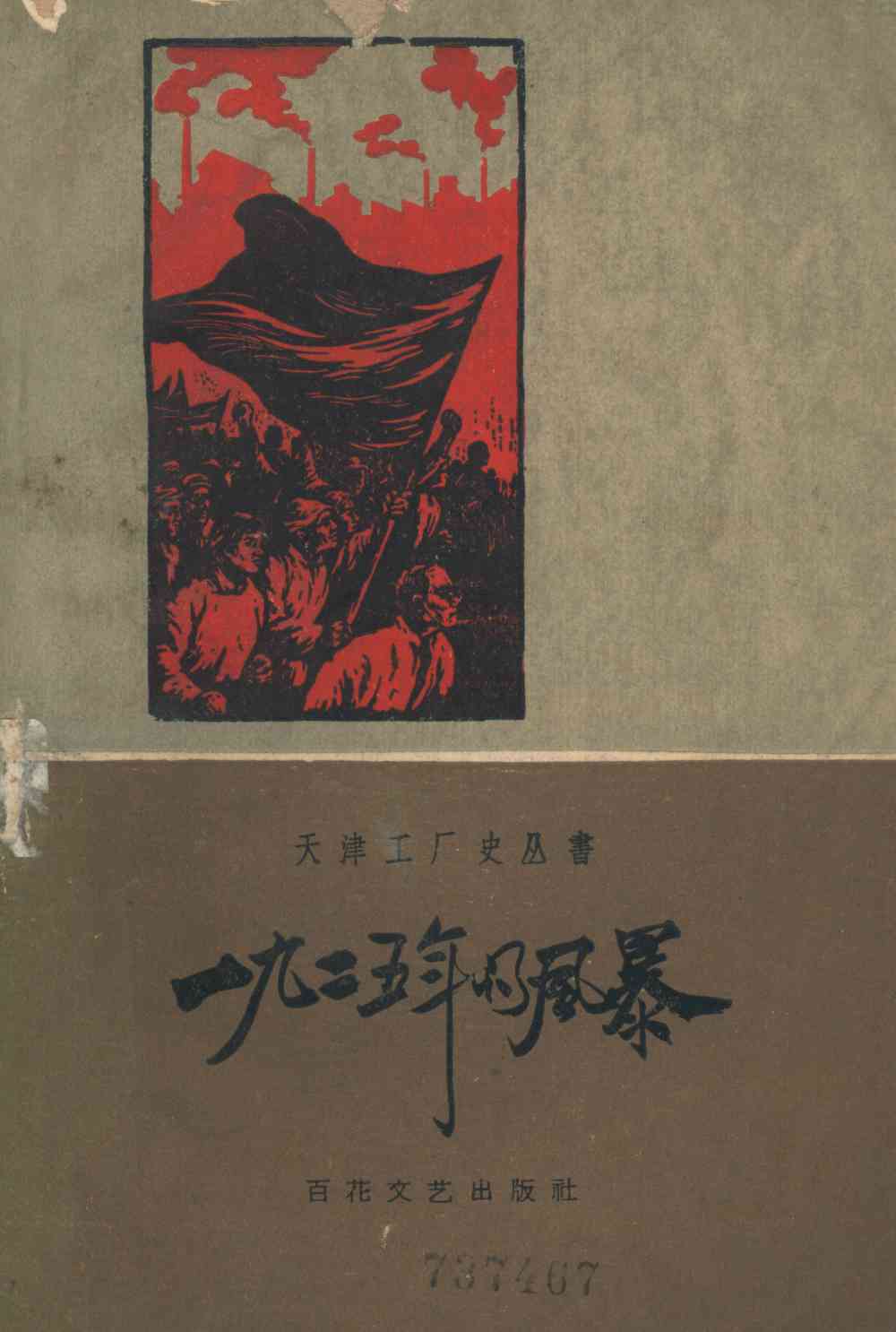内容
王佩玉說:在旧社会我沒有名儿,人家都叫我李王氏。1937年,我才十八岁,就进了裕大紗厂,在摇紗当养成工。
那时候我公公和丈夫也在厂子里上班。全家六口人,三个做工的。按理說,生活应該富裕吧,可是日本统治时期,工人們賺錢太少了,我們家总是穷得叮当乱响,•吃了上頓,下頓还不知往哪儿弄去。在那个世道,当个穷工人也得鑽門子,挖窗戶,隔长补短給当头的送送礼,要不哇,你就活該倒霉。我們家連飯都吃不上,哪有送礼的錢?这一下,我可遭殃啦,那个搖紗的大头赵奎高眞是凶,净在我的車上一根綫一根綫地找毛病,不是說我錯了绺,就説少了根数;上趟厠所也嫌时間长,还要罰三四毛錢。不光罰錢,还寒蠢人哪,把挨罰的原因用大布吿貼在車上边的暖汽管子上叫人們瞧。哪月我都要挨几次罰,貼几次布吿,把肚子气得鼓鼓的也不敢吱声。給头們送礼的人,情况就不大相同啦,干輕閑活,每月还比不送礼的人多关六七塊錢。有些工人怕走背字,就扎紧褲腰带挤出錢来給当头的送礼。这一来可把这些王八羔子喂肥啦,就拿猪肉来說吧,他們从工人手中收了肉条子,就在肉鋪里存着,願意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取。簡直是喝工人的血,吃工人的肉哇!
“閻王好見,小鬼难搪!”大头厉害,还离得远点,小头查車工,整天在弄档里逛蕩,最是难纏。有一个外号叫武大郞的查車工,对工人可坏啦,經常偸偸地瞟着工人干活,只要叫他抓着小辫,馬上到車头上,把皮带打到活輪上去,叫車停下来,紧接着就把赵奎高他們找来,給出錯的工人下結論。我們受的这一層一層的气眞是說不尽。
那工夫,邪道門在厂里也閙得挺凶。大头赵奎高,他本人就是一貫道坛主,象个臭綠豆蝇似的,到处拉人参加他的道門儿。他找到我家劝我:“李王氏,在道門儿可好哩,大水来了,老娘娘派法船接咱,不挨淹;打起仗来,槍子儿参不透,炸弹炸不开,在嘍吧!”我說:“在道門儿管吃还是管穿?我不在!”赵奎高說:“这是好事啊,为嘛不在?”我說:“不作那分好事,我們沒有那分在道門儿的錢!”我这么頂撞他,赵奎高看着我更不順眼啦!
这年,宝成紗厂的东家小老板,把宝成卖給了裕大的日本鬼子,裕大和宝成就合成一个厂子了。日本人把裕大一部份机器新工人搬到宝成,我也就跟着过亲了,这时管,搖紗的总头是小日本橫川。
不久,我就怀了大女儿惠云。这时候我眞害怕極了,好多女工因为怀孩子都被开除了,我家穷得稀里嘩啦,眞要开除了可吃嘛呀!哪个女人不爱自己的小孩?哪个女人不疼自己身上的肉?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却瞞着人,用布做了一个围腰子,狠着心把肚子勒得紧紧的,只怕別人看出我怀了小孩。后来婆婆知道了,就發愁地吿訴弄档里別的老太太們。老太太們就七嘴八舌的劝婆婆:“快别叫媳妇勒了,把小手小脚勒坏了,怎么添哪!赶快劝劝她吧!别出勤啦!”婆婆听了大家的話,就一个劲地劝我,唉!这个理我也不是不懂啊!孩子犯了嘛罪?为嘛在娘肚子里就受折磨!又一想,不勒可不行,前几天陈刘氏因为怀孩子被橫川看見开除的嗎!不能听婆婆的話,还得狠心地勒啊!怀孕的日期一天比一天多,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孩子出了怀,用围腰勒也不中用了。寃家路窄,有一天上夜班,我正在車头落紗,橫川走过来了,我赶紧假裝弯腰拾东西,可也沒瞞过橫川的眼睛,他立刻把赵奎高叫来,叫赵奎高吿訴我:“小孩的有了,要回家休息休息的。”説完就带我去賬桌算賬,我說:“我还能干活儿,晩走几天成么?赵奎高說“人家橫川是关心你呀,叫你回家休息。”我急了,說:“回家去吃什么呀?”赵奎高把眼一瞪說“別对付了,干脆走吧!”我也生气地說“好吧,我走!請你吿訴横川吧,我不用他关心!”这时候赵奎高早把女搜腰的叫来了。半夜一点鐘我械他們赶出工厂,厂外一片漆黑,連个灯亮都沒有,从厂子的大門口到工房,是很长的一段路,西北風刮的刺骨,我又是害怕又是难过,晃晃悠悠地回了家。
管工房的大老崔,消息眞灵通,第二天一早,就催命似地逼我搬家。我苦苦地哀求也白搭,大老崔这条老狗嘴张得天大的,要噬人哪!和丈夫商量了半天,只好含着泪,把我結婚时候的兩件麻綫衣裳和一根銀鏈子当了,买了五斤点心送了去,才算把老狗的嘴堵上了。
房子的問題解决了,吃的上哪弄去呀?这个年月,大家都穷得沒轍,可不能求亲吿友,我就每天带着六七个月的重身子,到杜庄子、吳嘴那一带去拾白菜帮子煮着吃。好歹地把冬天熬过来啦,第二年四月孩子生了,当时家里連个米粒也沒有,婆婆走进走出地偸着掉泪,把一只空面袋扫了又扫,扫出二小撮老棒子面,打了点糊塗給我下奶,唉!那个难哪,簡直不能提!
我正在月子里,新中山开工了,那里賺錢多,好多裕大的工人都跑到那去干活,厂子里怕工人到新中山去,就把工房的大門了鎖。虽然这样,工人們走的还是不少,我趁这个工厂缺人的机会,沒出满月又上班了。
日伪时期,工人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平常厂子的大門总是鎖着,只有上下理和吃飯的时間开一会門。那时候那有喂奶的时間?只有趁給大人送飯的时候,把小孩捎进来在娘怀里吃口奶。日本鬼子防工人象防賊一样,不叫工人出大門,也不叫送飯的人进厂子。送飯的人象探监似的把飯和小孩隔着木欄杆遞进来,不到一刻鐘,工人就得象囚犯似的把飯盒和小孩遞出去,这样,孩子怎能吃足奶?这是上白天班,无論怎样,孩子还可以在娘怀里偎会,要是上夜班,就更惨了,工厂門上了鎖,孩子不能进厂,只好在家中哭一宿。又沒錢給她买代奶的东西吃,孩子剛生下来还水灵,慢慢地就餓的又瘦又干了。可我这兩个奶呀,漲的生痛,干着活奶水滴滴搭搭地往下流,我的眼泪也和奶水一样,把干活的走道洒成河!我隐隐約約地老听見孩子“呱啦”“呱啦”地哭,孩子哭的声音把机器的声音都压下去了!一心惦着孩子,干活哪能不出錯;挨罰的次数就更多啦,挨罰的大布吿也净挂出来。因为揪心,难过,我的身体就一天一天地垮了。
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天津發大水,厂子里停工了。停工不給錢,就更沒有吃。我抱着孩子在厂子大楼的楼梯上避水,大人肚里沒食,奶不够吃,孩子餓得哇哇哭,正哭得我心焦,赵奎高大搖大摆地从前面走过来,我就叫他:“赵头,發大水了,老娘娘怎沒派法船把你接走哇?”赵奎高知道这是損他,白眼珠翻了翻,气哼哼逃走了。我这人就是这么招大头的恨!
惠云剛断奶,又怀了二女儿惠文。开除的滋味尝过了,这次就更害怕!听老太太們說,可以打胎。我反来复去的想,打胎好比生摘瓜,身子骨槽踐了呢?果眞有个三长兩短,全家人怎么办哪?不!不能打胎!可是不打胎开除了也是沒有飯吃呀,唉!千难万承难死人!自己拿不定主意,我就找娘商量去了。娘一听就刷刷地掉泪,説:“惠云媽,你不能这样作呀!人嘛,都是为了生儿养女,咱們不能办这样的缺德事!”娘的話还沒說完,我就扑在娘怀里哭了起来。从娘家回来之后,只得又使老法子,拿布围腰勒肚子,到了五个多月又被开除了。
生了惠文之后,我的身子就更弱了,也許是日本鬼子快要垮台的緣故,果仁餅山芋面也不好买了,每天吃半飽上班干活,下班回家累的老是喘不上气来。就是这样也得不到休息,每天撑着干活,很快地就把我折磨的不成人样了。我常想,这是哪世造下的孽呀?即便我自己前世作了坏事,难道說孩子也和我一样的命嗎?不可能,这純粹是世道造成的!这些时候,布場的男工們净閙罢正,有些大胆的还“偸”紗,“偸”布,叫日本人逮住了就綁在大門、那灌凉水,压杠子,这些人眞硬气,挨打也不含糊。我心里說:“本来嘛,大男爷們,誰受得了这分窩囊罪,可惜我是女人,沒他們那么大的胆字。”有錢的求儿盼女,盼不到手;穷苦人家多儿多女是累贅。惠文才断奶,我又怀了三女儿。这时候我的想法忽然变了:难道穷人就沒有生孩子的自由嗎?穷人的孩子就沒有生存的权利嗎?为嘛叫孩子在媽肚子里受委屈?这回我不勒肚子了,叫孩子舒舒坦坦地躺在娘的肚子里,叫孩子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生了三女儿不久,日本鬼子就投降了,全厂的工人,全工房的家屬都欢騰起来,大家都以为胜利啦,再不受日本鬼子的气啦。哪知道国民党来了,換湯不換藥,把头还是騎在工,人头上。物价更是一天漲几次,錢一个劲的毛,穷人还是連棒子面也混不上。
老家宝坻县来的人常学說八路軍的事情:怎样平分土地啦,怎样斗爭地主啦,穷人們怎样分东西啦,我听了就心里想:天津多咱也象宝坻一个样啊,宝坻离天津只隔一古多里地,可是兩个天下。一九四八年的秋天,工房里就有人偸偸地說,这回国民党可快要完蛋啦,国民党在东北打敗仗啦,咱天津快要来八路軍啦!我們天天盼着。冬天,八路軍眞的把天津包围了,大炮轟轟的响,沒过兩三天,天津就解放了,全厂的工人个个欢喜,大家进厂修机器,搞淸潔。軍代表給我們講話,叫我們“同志”,說工人是厂子的主人,叫我們管好工厂。果眞不久,当头的都撤下来了。工人們干活儿更起劲啦!有一个同志說:“李王氏,現在工人当家作主了,你也起个名儿吧!”于是,他給我起起个名儿叫王佩玉。当时我的心气也很高,心說:“这回可順气啦,也不挨餓啦,一定要好好干。”那時候,工厂里开嘛会我也参加,虽然我嘴笨,說不好話,可就是別人講我也听得入迷。业余学校招生,我如赶紧去参加,为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当睜眼瞎。誰知心劲足,身体不給我作主,十几年忍飢受累的日子叫我作了一身的病。最痛苦的是,出不上气来,一个劲地喘,还直吐血。我是个剛强人,就硬挺着干,跟誰也不說我这病。要是旧社会,誰管你呀,累死了算!現在可不同啦,尽管我不声张,領导上还是注意了我的健康問題,叫老姐妹动員我休养。
我說:“国民党那咱还拚命給他們干啦,現在解放了还歇班!”,話是这祥說,病可越来越重。一九五二年四月,我就病的不能上班了。我在家养病,厂子里的領导和老姐妹常来看我。有一次,工会領导說:“王佩玉,你这病得徹底养,不是三天兩天能好的,干脆退休吧。”一听領导这样說:我心里又嘀咕了,退休?家里怎么过呀?孩子們还小。其实領导早看出我的顧虑来了,就說:“王佩玉,你放心吧!你是厂子里的老工人,一定要照顧你的困难,退休以后可以叫你的大女儿替你上班啊!”我一听,領导上給我想的这么周到,我自己还打的嘛算盤?就按照領导上的意見,在家养病了。这些年,因为生活很好,我的健康恢复得很快,就是这喘病去不了根,这病是日本和国民党統治时期挨飢作成的。因为这病使我失去了工作能力,所以,我再也忘本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
現在我一心盼望我的女儿們好好干,好好地建設咱們的社会主义社会。想想我年輕时候受的苦和难,再看看孩子們現在的幸福生活,我常常感激地流眼泪,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的孩子們还不是和我从前一样?最近,領导上因为我的大女儿在生产上表現的好叫她到北戴河去休养”。以前只有当头的象赵奎高这种人才能去北戴河,現在一个不満二十岁的孩子,才作了一点儿成績,就受到这么大的奖励,在旧社会作梦也梦不到啊!
李惠云說:我是媽媽的大女儿,在旧社会虽然跟着媽媽过了不少苦日子,但是对媽媽的痛苦遭遇知道的少,媽媽为什么受苦更不理解,因为那时我年紀很小,不懂事;媽媽又性情剛强,輕易不肯向人談她过去的經历,她总說:“过去的就过去了吧。一个人应該向前看。”一直到現在,媽媽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敎育我們靑年人,才把她年輕时候的遭遇談出来,这使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
媽媽因为生我們姐妹,把身体糟踏坏了,在我記事的时候,她就是个病人。那时,她还很年輕,可是喘起来就象老年人一样,她很瘦,簡直是皮包着骨头。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时候,她的病已經作成了,每天还是干十二个小时的活,下班回来,累得拾不起个来,仍要强掙扎着洗衣服、作飯。她很慈爱,无論自己怎样痛苦,在外头受了什么委屈,从来沒有象有的媽媽那样,打罵孩子撒气。我很小,不能帮她干什么,可是我常常看着媽那焦黃的臉耽心地想:可別惹媽媽生气啊!我要是淘气,媽媽大声一喊我,她就更累坏啦!”所以我总是听媽媽的話,奶奶和媽媽都說我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长到六七岁,我就学会了看妹妹,到大埝上抬柴禾,撿煤渣儿,我总是努力地拾柴禾,撿煤渣儿。从不怕累。因为家里多存点燒的,就省得媽媽發愁啦。
因为媽媽退休,我十三岁就代替媽媽上班了。临进厂媽媽嘱咐我:“要听領导的話,要听姨啊、嬸們的話,你小孩子家啥也不懂。”我岁数小,个儿又瘦又矮,比搖紗車还矮一戳呢。一进車間,姨啊、嬸啊都疼爱地叫我“小不点儿”。她們都是媽媽的老姐妹,对我格外关心,誰走到我跟前都耐心地敎我干活儿,不到半个月,我就把幷筒的技术学会了,成了棉紡三厂的正式工人。
一連好几年,我都老老实实地干活儿,每月都能完成生产計划。我常想:我不过是个小毛孩子,姨和嬸們不比我强?我干或这样也就可以啦!对自己就沒有更高的要求。每月發了工資,我就赶快把錢拿回家去,交到媽媽手中。看見媽媽不为过日子为难受窄,我就暗暗地高兴。前几年,我很怕开会,很怕叫我搞什么社会活动,因为我总覚得干那些事耗精神,怕影响生产計划的完成。媽媽看出我的缺点,就說:“小云啊!剛解放那時候,我閙着病,弄孩子、作飯,还总参加会,还上业余学校。現在家里的事样样不用你操心,你为嘛不爭取先进呢?生在这个时代,你們年輕人多么幸福啊!”听了媽的話,我受到很大的感动,可是对媽應的意思还沒懂透。这时候,咱們全中国的六亿人口都投到大躍进的浪潮里,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喊得山响,特别是靑年人干劲可眞足啊!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輕人要都象我这样,我們的国家多咱才能赶上英国啊!再說我們祖孙三代都是工人,媽媽在旧社会受尽千辛万苦,是新社会扌把她救活的,我是她的女儿,难道不爱新社会嗎?这些日子,工厂里搞工厂史,媽媽想起以前的事,更时常对我說:“小云啊!要不是共产党,你早成了沒娘的孩儿啦!瞧你多美啊,我象你这个岁数,是在活地獄里过的啊!那功夫,我的眼泪一缸一缸地流。”这时候,团也抓紧对我的敎育,吿訴我不要光爱小家庭,最重要的是爱我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沒有大家庭,就沒有小家庭。我从思想上对这些問題有了新的詔識。
紧接着,又是双反运动,橫扫五气。經过学習,我非常吃惊,別看我是个年輕的女孩子,身上可有暮气,要不引火燒身,我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我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向团作了,徹底的交待,狠狠地給自己貼了张大字报。把这些事情办完了,我忽然覚得渾身都是劲儿。这时候,我們工段的生产关鍵是回絲的浪費問題。我就想:我們每个幷筒工人每天要接多少头儿啊,要是把我們車間的回絲接在一塊量量,还不繞它地球几遭儿,可眞是个大的浪費!我旣然反了自己的暮气,就应該在生产上有个新的表現,年輕人可不能放突炮!于是我就在縮短回絲上打主意。
从前我們接头为了快,总是把紗拉过来就接,回絲往往是一大团。現在我每一接头就把紗比齐了才接,剩卡的回絲总不叫它超过0.5寸(我們的計划是2寸),起初动作慢些,習慣了也同样快。这件事被我們的副工长發現了,就跟我說:“李惠云,你这回絲短得很,这很好,可是只剩下这么一点毛絨絨,別影响質量啊!”我一想,副工长說的有理,应該好好驗驗节。可是当我驗节的时候,不光知道了对質量沒影响,还發現我們这不工序上的紗接头的地方捻度很大,还可以縮短回絲。一試驗,又成功了,又节省了不少紗。这一来,可把我們的团总支書記乐坏了,他逢人便說:“李惠云在双反里的表現可眞突出啊!主要是她在思想上躍进了一大步!”立刻在我們工段的靑年工人里掀起了一个“追云运动”。各班的姐妹們都要求我把操作法表演給她們看。
表演这天,我眞是又惊又喜。我的周围围了很多姐妹,她們不錯眼珠儿盯着我兩只手怎样动作。我剛表演完了,一抬头,忽然發現姨啊、嬸啊也都站在旁边瞅着我呢,我不由得一陣惊慌,心里說:“姨啊!嬸啊!姐姐們!我这一切述是你們給的呢!今后我还要向你們好好地学習!”可是我被感动得嘛話也說不出来。
最近領导上要送一批先进工作者到北戴河去休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我在家中收拾行装的时候,媽媽又向我唠叨起老話来。媽媽啊!現在我完全懂得你的思想了!我一定要努力地干,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劳动中,把你的劲儿也使上!
(袁鶴嗚記、 夏燁整理)
那时候我公公和丈夫也在厂子里上班。全家六口人,三个做工的。按理說,生活应該富裕吧,可是日本统治时期,工人們賺錢太少了,我們家总是穷得叮当乱响,•吃了上頓,下頓还不知往哪儿弄去。在那个世道,当个穷工人也得鑽門子,挖窗戶,隔长补短給当头的送送礼,要不哇,你就活該倒霉。我們家連飯都吃不上,哪有送礼的錢?这一下,我可遭殃啦,那个搖紗的大头赵奎高眞是凶,净在我的車上一根綫一根綫地找毛病,不是說我錯了绺,就説少了根数;上趟厠所也嫌时間长,还要罰三四毛錢。不光罰錢,还寒蠢人哪,把挨罰的原因用大布吿貼在車上边的暖汽管子上叫人們瞧。哪月我都要挨几次罰,貼几次布吿,把肚子气得鼓鼓的也不敢吱声。給头們送礼的人,情况就不大相同啦,干輕閑活,每月还比不送礼的人多关六七塊錢。有些工人怕走背字,就扎紧褲腰带挤出錢来給当头的送礼。这一来可把这些王八羔子喂肥啦,就拿猪肉来說吧,他們从工人手中收了肉条子,就在肉鋪里存着,願意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取。簡直是喝工人的血,吃工人的肉哇!
“閻王好見,小鬼难搪!”大头厉害,还离得远点,小头查車工,整天在弄档里逛蕩,最是难纏。有一个外号叫武大郞的查車工,对工人可坏啦,經常偸偸地瞟着工人干活,只要叫他抓着小辫,馬上到車头上,把皮带打到活輪上去,叫車停下来,紧接着就把赵奎高他們找来,給出錯的工人下結論。我們受的这一層一層的气眞是說不尽。
那工夫,邪道門在厂里也閙得挺凶。大头赵奎高,他本人就是一貫道坛主,象个臭綠豆蝇似的,到处拉人参加他的道門儿。他找到我家劝我:“李王氏,在道門儿可好哩,大水来了,老娘娘派法船接咱,不挨淹;打起仗来,槍子儿参不透,炸弹炸不开,在嘍吧!”我說:“在道門儿管吃还是管穿?我不在!”赵奎高說:“这是好事啊,为嘛不在?”我說:“不作那分好事,我們沒有那分在道門儿的錢!”我这么頂撞他,赵奎高看着我更不順眼啦!
这年,宝成紗厂的东家小老板,把宝成卖給了裕大的日本鬼子,裕大和宝成就合成一个厂子了。日本人把裕大一部份机器新工人搬到宝成,我也就跟着过亲了,这时管,搖紗的总头是小日本橫川。
不久,我就怀了大女儿惠云。这时候我眞害怕極了,好多女工因为怀孩子都被开除了,我家穷得稀里嘩啦,眞要开除了可吃嘛呀!哪个女人不爱自己的小孩?哪个女人不疼自己身上的肉?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却瞞着人,用布做了一个围腰子,狠着心把肚子勒得紧紧的,只怕別人看出我怀了小孩。后来婆婆知道了,就發愁地吿訴弄档里別的老太太們。老太太們就七嘴八舌的劝婆婆:“快别叫媳妇勒了,把小手小脚勒坏了,怎么添哪!赶快劝劝她吧!别出勤啦!”婆婆听了大家的話,就一个劲地劝我,唉!这个理我也不是不懂啊!孩子犯了嘛罪?为嘛在娘肚子里就受折磨!又一想,不勒可不行,前几天陈刘氏因为怀孩子被橫川看見开除的嗎!不能听婆婆的話,还得狠心地勒啊!怀孕的日期一天比一天多,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孩子出了怀,用围腰勒也不中用了。寃家路窄,有一天上夜班,我正在車头落紗,橫川走过来了,我赶紧假裝弯腰拾东西,可也沒瞞过橫川的眼睛,他立刻把赵奎高叫来,叫赵奎高吿訴我:“小孩的有了,要回家休息休息的。”説完就带我去賬桌算賬,我說:“我还能干活儿,晩走几天成么?赵奎高說“人家橫川是关心你呀,叫你回家休息。”我急了,說:“回家去吃什么呀?”赵奎高把眼一瞪說“別对付了,干脆走吧!”我也生气地說“好吧,我走!請你吿訴横川吧,我不用他关心!”这时候赵奎高早把女搜腰的叫来了。半夜一点鐘我械他們赶出工厂,厂外一片漆黑,連个灯亮都沒有,从厂子的大門口到工房,是很长的一段路,西北風刮的刺骨,我又是害怕又是难过,晃晃悠悠地回了家。
管工房的大老崔,消息眞灵通,第二天一早,就催命似地逼我搬家。我苦苦地哀求也白搭,大老崔这条老狗嘴张得天大的,要噬人哪!和丈夫商量了半天,只好含着泪,把我結婚时候的兩件麻綫衣裳和一根銀鏈子当了,买了五斤点心送了去,才算把老狗的嘴堵上了。
房子的問題解决了,吃的上哪弄去呀?这个年月,大家都穷得沒轍,可不能求亲吿友,我就每天带着六七个月的重身子,到杜庄子、吳嘴那一带去拾白菜帮子煮着吃。好歹地把冬天熬过来啦,第二年四月孩子生了,当时家里連个米粒也沒有,婆婆走进走出地偸着掉泪,把一只空面袋扫了又扫,扫出二小撮老棒子面,打了点糊塗給我下奶,唉!那个难哪,簡直不能提!
我正在月子里,新中山开工了,那里賺錢多,好多裕大的工人都跑到那去干活,厂子里怕工人到新中山去,就把工房的大門了鎖。虽然这样,工人們走的还是不少,我趁这个工厂缺人的机会,沒出满月又上班了。
日伪时期,工人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平常厂子的大門总是鎖着,只有上下理和吃飯的时間开一会門。那时候那有喂奶的时間?只有趁給大人送飯的时候,把小孩捎进来在娘怀里吃口奶。日本鬼子防工人象防賊一样,不叫工人出大門,也不叫送飯的人进厂子。送飯的人象探监似的把飯和小孩隔着木欄杆遞进来,不到一刻鐘,工人就得象囚犯似的把飯盒和小孩遞出去,这样,孩子怎能吃足奶?这是上白天班,无論怎样,孩子还可以在娘怀里偎会,要是上夜班,就更惨了,工厂門上了鎖,孩子不能进厂,只好在家中哭一宿。又沒錢給她买代奶的东西吃,孩子剛生下来还水灵,慢慢地就餓的又瘦又干了。可我这兩个奶呀,漲的生痛,干着活奶水滴滴搭搭地往下流,我的眼泪也和奶水一样,把干活的走道洒成河!我隐隐約約地老听見孩子“呱啦”“呱啦”地哭,孩子哭的声音把机器的声音都压下去了!一心惦着孩子,干活哪能不出錯;挨罰的次数就更多啦,挨罰的大布吿也净挂出来。因为揪心,难过,我的身体就一天一天地垮了。
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天津發大水,厂子里停工了。停工不給錢,就更沒有吃。我抱着孩子在厂子大楼的楼梯上避水,大人肚里沒食,奶不够吃,孩子餓得哇哇哭,正哭得我心焦,赵奎高大搖大摆地从前面走过来,我就叫他:“赵头,發大水了,老娘娘怎沒派法船把你接走哇?”赵奎高知道这是損他,白眼珠翻了翻,气哼哼逃走了。我这人就是这么招大头的恨!
惠云剛断奶,又怀了二女儿惠文。开除的滋味尝过了,这次就更害怕!听老太太們說,可以打胎。我反来复去的想,打胎好比生摘瓜,身子骨槽踐了呢?果眞有个三长兩短,全家人怎么办哪?不!不能打胎!可是不打胎开除了也是沒有飯吃呀,唉!千难万承难死人!自己拿不定主意,我就找娘商量去了。娘一听就刷刷地掉泪,説:“惠云媽,你不能这样作呀!人嘛,都是为了生儿养女,咱們不能办这样的缺德事!”娘的話还沒說完,我就扑在娘怀里哭了起来。从娘家回来之后,只得又使老法子,拿布围腰勒肚子,到了五个多月又被开除了。
生了惠文之后,我的身子就更弱了,也許是日本鬼子快要垮台的緣故,果仁餅山芋面也不好买了,每天吃半飽上班干活,下班回家累的老是喘不上气来。就是这样也得不到休息,每天撑着干活,很快地就把我折磨的不成人样了。我常想,这是哪世造下的孽呀?即便我自己前世作了坏事,难道說孩子也和我一样的命嗎?不可能,这純粹是世道造成的!这些时候,布場的男工們净閙罢正,有些大胆的还“偸”紗,“偸”布,叫日本人逮住了就綁在大門、那灌凉水,压杠子,这些人眞硬气,挨打也不含糊。我心里說:“本来嘛,大男爷們,誰受得了这分窩囊罪,可惜我是女人,沒他們那么大的胆字。”有錢的求儿盼女,盼不到手;穷苦人家多儿多女是累贅。惠文才断奶,我又怀了三女儿。这时候我的想法忽然变了:难道穷人就沒有生孩子的自由嗎?穷人的孩子就沒有生存的权利嗎?为嘛叫孩子在媽肚子里受委屈?这回我不勒肚子了,叫孩子舒舒坦坦地躺在娘的肚子里,叫孩子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生了三女儿不久,日本鬼子就投降了,全厂的工人,全工房的家屬都欢騰起来,大家都以为胜利啦,再不受日本鬼子的气啦。哪知道国民党来了,換湯不換藥,把头还是騎在工,人头上。物价更是一天漲几次,錢一个劲的毛,穷人还是連棒子面也混不上。
老家宝坻县来的人常学說八路軍的事情:怎样平分土地啦,怎样斗爭地主啦,穷人們怎样分东西啦,我听了就心里想:天津多咱也象宝坻一个样啊,宝坻离天津只隔一古多里地,可是兩个天下。一九四八年的秋天,工房里就有人偸偸地說,这回国民党可快要完蛋啦,国民党在东北打敗仗啦,咱天津快要来八路軍啦!我們天天盼着。冬天,八路軍眞的把天津包围了,大炮轟轟的响,沒过兩三天,天津就解放了,全厂的工人个个欢喜,大家进厂修机器,搞淸潔。軍代表給我們講話,叫我們“同志”,說工人是厂子的主人,叫我們管好工厂。果眞不久,当头的都撤下来了。工人們干活儿更起劲啦!有一个同志說:“李王氏,現在工人当家作主了,你也起个名儿吧!”于是,他給我起起个名儿叫王佩玉。当时我的心气也很高,心說:“这回可順气啦,也不挨餓啦,一定要好好干。”那時候,工厂里开嘛会我也参加,虽然我嘴笨,說不好話,可就是別人講我也听得入迷。业余学校招生,我如赶紧去参加,为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当睜眼瞎。誰知心劲足,身体不給我作主,十几年忍飢受累的日子叫我作了一身的病。最痛苦的是,出不上气来,一个劲地喘,还直吐血。我是个剛强人,就硬挺着干,跟誰也不說我这病。要是旧社会,誰管你呀,累死了算!現在可不同啦,尽管我不声张,領导上还是注意了我的健康問題,叫老姐妹动員我休养。
我說:“国民党那咱还拚命給他們干啦,現在解放了还歇班!”,話是这祥說,病可越来越重。一九五二年四月,我就病的不能上班了。我在家养病,厂子里的領导和老姐妹常来看我。有一次,工会領导說:“王佩玉,你这病得徹底养,不是三天兩天能好的,干脆退休吧。”一听領导这样說:我心里又嘀咕了,退休?家里怎么过呀?孩子們还小。其实領导早看出我的顧虑来了,就說:“王佩玉,你放心吧!你是厂子里的老工人,一定要照顧你的困难,退休以后可以叫你的大女儿替你上班啊!”我一听,領导上給我想的这么周到,我自己还打的嘛算盤?就按照領导上的意見,在家养病了。这些年,因为生活很好,我的健康恢复得很快,就是这喘病去不了根,这病是日本和国民党統治时期挨飢作成的。因为这病使我失去了工作能力,所以,我再也忘本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
現在我一心盼望我的女儿們好好干,好好地建設咱們的社会主义社会。想想我年輕时候受的苦和难,再看看孩子們現在的幸福生活,我常常感激地流眼泪,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的孩子們还不是和我从前一样?最近,領导上因为我的大女儿在生产上表現的好叫她到北戴河去休养”。以前只有当头的象赵奎高这种人才能去北戴河,現在一个不満二十岁的孩子,才作了一点儿成績,就受到这么大的奖励,在旧社会作梦也梦不到啊!
李惠云說:我是媽媽的大女儿,在旧社会虽然跟着媽媽过了不少苦日子,但是对媽媽的痛苦遭遇知道的少,媽媽为什么受苦更不理解,因为那时我年紀很小,不懂事;媽媽又性情剛强,輕易不肯向人談她过去的經历,她总說:“过去的就过去了吧。一个人应該向前看。”一直到現在,媽媽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敎育我們靑年人,才把她年輕时候的遭遇談出来,这使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
媽媽因为生我們姐妹,把身体糟踏坏了,在我記事的时候,她就是个病人。那时,她还很年輕,可是喘起来就象老年人一样,她很瘦,簡直是皮包着骨头。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时候,她的病已經作成了,每天还是干十二个小时的活,下班回来,累得拾不起个来,仍要强掙扎着洗衣服、作飯。她很慈爱,无論自己怎样痛苦,在外头受了什么委屈,从来沒有象有的媽媽那样,打罵孩子撒气。我很小,不能帮她干什么,可是我常常看着媽那焦黃的臉耽心地想:可別惹媽媽生气啊!我要是淘气,媽媽大声一喊我,她就更累坏啦!”所以我总是听媽媽的話,奶奶和媽媽都說我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长到六七岁,我就学会了看妹妹,到大埝上抬柴禾,撿煤渣儿,我总是努力地拾柴禾,撿煤渣儿。从不怕累。因为家里多存点燒的,就省得媽媽發愁啦。
因为媽媽退休,我十三岁就代替媽媽上班了。临进厂媽媽嘱咐我:“要听領导的話,要听姨啊、嬸們的話,你小孩子家啥也不懂。”我岁数小,个儿又瘦又矮,比搖紗車还矮一戳呢。一进車間,姨啊、嬸啊都疼爱地叫我“小不点儿”。她們都是媽媽的老姐妹,对我格外关心,誰走到我跟前都耐心地敎我干活儿,不到半个月,我就把幷筒的技术学会了,成了棉紡三厂的正式工人。
一連好几年,我都老老实实地干活儿,每月都能完成生产計划。我常想:我不过是个小毛孩子,姨和嬸們不比我强?我干或这样也就可以啦!对自己就沒有更高的要求。每月發了工資,我就赶快把錢拿回家去,交到媽媽手中。看見媽媽不为过日子为难受窄,我就暗暗地高兴。前几年,我很怕开会,很怕叫我搞什么社会活动,因为我总覚得干那些事耗精神,怕影响生产計划的完成。媽媽看出我的缺点,就說:“小云啊!剛解放那時候,我閙着病,弄孩子、作飯,还总参加会,还上业余学校。現在家里的事样样不用你操心,你为嘛不爭取先进呢?生在这个时代,你們年輕人多么幸福啊!”听了媽的話,我受到很大的感动,可是对媽應的意思还沒懂透。这时候,咱們全中国的六亿人口都投到大躍进的浪潮里,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喊得山响,特别是靑年人干劲可眞足啊!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輕人要都象我这样,我們的国家多咱才能赶上英国啊!再說我們祖孙三代都是工人,媽媽在旧社会受尽千辛万苦,是新社会扌把她救活的,我是她的女儿,难道不爱新社会嗎?这些日子,工厂里搞工厂史,媽媽想起以前的事,更时常对我說:“小云啊!要不是共产党,你早成了沒娘的孩儿啦!瞧你多美啊,我象你这个岁数,是在活地獄里过的啊!那功夫,我的眼泪一缸一缸地流。”这时候,团也抓紧对我的敎育,吿訴我不要光爱小家庭,最重要的是爱我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沒有大家庭,就沒有小家庭。我从思想上对这些問題有了新的詔識。
紧接着,又是双反运动,橫扫五气。經过学習,我非常吃惊,別看我是个年輕的女孩子,身上可有暮气,要不引火燒身,我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我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向团作了,徹底的交待,狠狠地給自己貼了张大字报。把这些事情办完了,我忽然覚得渾身都是劲儿。这时候,我們工段的生产关鍵是回絲的浪費問題。我就想:我們每个幷筒工人每天要接多少头儿啊,要是把我們車間的回絲接在一塊量量,还不繞它地球几遭儿,可眞是个大的浪費!我旣然反了自己的暮气,就应該在生产上有个新的表現,年輕人可不能放突炮!于是我就在縮短回絲上打主意。
从前我們接头为了快,总是把紗拉过来就接,回絲往往是一大团。現在我每一接头就把紗比齐了才接,剩卡的回絲总不叫它超过0.5寸(我們的計划是2寸),起初动作慢些,習慣了也同样快。这件事被我們的副工长發現了,就跟我說:“李惠云,你这回絲短得很,这很好,可是只剩下这么一点毛絨絨,別影响質量啊!”我一想,副工长說的有理,应該好好驗驗节。可是当我驗节的时候,不光知道了对質量沒影响,还發現我們这不工序上的紗接头的地方捻度很大,还可以縮短回絲。一試驗,又成功了,又节省了不少紗。这一来,可把我們的团总支書記乐坏了,他逢人便說:“李惠云在双反里的表現可眞突出啊!主要是她在思想上躍进了一大步!”立刻在我們工段的靑年工人里掀起了一个“追云运动”。各班的姐妹們都要求我把操作法表演給她們看。
表演这天,我眞是又惊又喜。我的周围围了很多姐妹,她們不錯眼珠儿盯着我兩只手怎样动作。我剛表演完了,一抬头,忽然發現姨啊、嬸啊也都站在旁边瞅着我呢,我不由得一陣惊慌,心里說:“姨啊!嬸啊!姐姐們!我这一切述是你們給的呢!今后我还要向你們好好地学習!”可是我被感动得嘛話也說不出来。
最近領导上要送一批先进工作者到北戴河去休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我在家中收拾行装的时候,媽媽又向我唠叨起老話来。媽媽啊!現在我完全懂得你的思想了!我一定要努力地干,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劳动中,把你的劲儿也使上!
(袁鶴嗚記、 夏燁整理)
相关地名
天津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