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明对话之路上的《华夷译语》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5844 |
| 颗粒名称: | 丝绸之路:文明对话之路上的《华夷译语》 |
| 分类号: | K928.6 |
| 页数: | 18 |
| 页码: | 386-403 |
| 摘要: | 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是以西安为起点,经过河西四郡,出玉门关进入西域。中国与域外文明的对话有一个随着时间延伸,从而在空间上不断拓展的过程。从时间序列上考察,从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后,正式开辟了从中原内地到西域各地的交通要道,并逐渐将东西两段获得沟通,这条道路的东段可以认为经过陆路和海路经朝鲜一直延伸到日本,整个丝绸之路同样有一个随着时间延伸,从单线到多线,至15世纪郑和下西洋标志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面开通。 |
| 关键词: | 阿克苏 丝绸之路 文明对话 |
内容
从秦汉到明清千余年间,中国与外国与周边少数民族有着频繁的交往,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年)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第一卷中曾经以“丝绸之路”一词来命名这一中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交通之道,这一充满诗意的历史术语得到了一些欧洲汉学家的支持和阐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以及日本的一些探险家、考古学家和旅行家陆续到中国的西北边疆地区进行考察,找到了古代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各国交往的许多遗址,纷纷著书立说来证明这一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存在。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是以西安为起点,经过河西四郡,出玉门关进入西域。一般认为汉朝的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有南北两道,可以视为今天所说的“狭义”的丝绸之路;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中外交流的商贸通道在中国与亚欧之间是呈网状形的分布,既有陆路,也有海路,此即“广义”的丝绸之路。中国与域外文明的对话有一个随着时间延伸,从而在空间上不断拓展的过程。从时间序列上考察,从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后,正式开辟了从中原内地到西域各地的交通要道,并逐渐将东西两段获得沟通,这条道路的东段可以认为经过陆路和海路经朝鲜一直延伸到日本,整个丝绸之路同样有一个随着时间延伸,从单线到多线,至15世纪郑和下西洋标志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面开通。
丝绸之路是文明对话之路,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就离不开语言的接触。本文关注的是在网状形分布的丝绸之路上,中外交往所需的外语人才,如民间的通事和官方的译员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培养的,他们依据着什么样的文献来完成语言学习的过程。关于上述问题,史料上往往语焉不详,只有一些零星的少数民族地区学习汉语,或少数民族赴汉地学习汉语的记录。据《周书·异域传·高昌》记载:高昌地区“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即少数民族文字——作者注),有《毛诗》、《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①又据《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唐代公主入藏后,吐蕃“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②可见当时即使在学习少数民族文字方面,虽已有若干有组织的教育形式以学习汉文化,但尚未建立起双语体制的教学和专门双语内容的学校,早期也找不到有关的双语教学的读本。本文尝试以《华夷译语》为中心来讨论丝绸之路上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学习的若干问题。
一、“回回国子学”、四夷馆与会同四译馆
付克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一书中认为,我国最古老的外国语文学校是元朝的“回回国子学”。③这是元朝政府为培养译员设立的专门学校。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世祖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新元史·选举志》中记载:“是年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弟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从之。八月,遂置国子学。”①在回回国子学和回回监内教习一种称为“亦思替非”的文字。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认为:“‘亦思替非’为波斯古代都城之名,‘仪思替非’文字者,波斯文字也。回回国子学者,教习波斯文字者也。元时所谓回回文字,实波斯文字。”由此付克得出结论:元朝的“回回国子学”是一所教授波斯语言文字的学校。②但日本学者岩村忍认为,“亦思替非”可能是Istanbuli“伊斯坦布”语,即拜占庭语的音译。邵循正在《剌失德丁〈集史·蒙哥汗纪〉译释》中提出,“亦思替非”应为阿拉伯文istafa的对音,意为穆罕默德之文字。③这也反映出元代与中亚各国密切的经济往来,培养懂得“亦思替非”语言文字的人才,实在是当时社会之急需。
国子学可能不久就解散了,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按世祖旧制“笃意领教”。至泰定二年(1325年),入回回国子监学习波斯文的“公卿答复子弟与夫凡民之子”日渐增多,其学官及生员总数共50余人。其中受元政府资助的“饮膳者”有27人。元政府遂下令,对未能享受供给的一名助教和24名生员也提供饮膳。当时政府“百司庶府所设译史”,都从回回国子监内选取生员充任。④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内教习波斯语的教材,至今不存。元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称:“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刘迎胜认为这份回回字母表,与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的教材或许有一点关系。⑤
明清时期海道大通,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交通的主要通道。明朝政府继续与周边各国和各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明太祖洪武二年到三十年,单入贡者,高丽和暹罗各为18次,占城16次,安南13次,琉球12次,爪哇和乌斯藏各为9次,真腊8次,三佛齐6次,日本5次,撒马儿罕和朵甘各3次,撒里和哈梅里各2次,西洋、勃泥、琐里、须文达那、墨剌、打箭炉、西蕃、百花、彭亨、览邦、缅等各1次。①频繁的与邻邦外蕃和海外国家的交往,使明朝政府深感翻译人才的缺乏,于是明初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正式成立,设在翰林院内,分蒙古、女直(即女真)、西藩、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主要是一个官方的语言文字的翻译机构和外语教习馆,②明代丘濬曾阐述过四夷馆的作用:“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如今设立八馆,“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使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史之。通者冠带,授以官,盖重其选也”。③西方和日本的学者有认为四夷馆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刘迎胜认为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在明代或清初属翰林院,拿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一所‘亚洲研究院’”④。正德中,增设八百馆。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⑤外来朝贡觐见者,来去必须有通事等陪同,如果有意摆脱通事擅自进京则以违法论处。若出事故,通事及随伴人员将受到连带处分。如正德三年(1508年),(哈密卫)写亦虎仙入贞,“不与通事偕行,自携边臣文牒投进。大通事王永怒,疏请治究。”弘治八年(1495年)乌斯藏阐化王遣使来贡,在扬州“杀牲纵酒”发生殴斗,结果通事及伴随者都被治罪。①
《明史·职官志》称宣德元年(1426年)四夷馆“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课程”。②教授“四夷语言”的教师在设馆之初,多为通晓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士,也有部分外籍教师。最先聘任外籍教师的是缅甸馆,大约在正统年间(1436~1449年),缅甸人当内、云清、班思杰、康剌改、潘达速、已扯盼六人作为缅甸阿瓦王朝的使者来明朝进贡,经明廷要求,他们便留在四夷馆任教。景泰二年(1451年),缅甸派人请求遣返当内六人,明廷以“译字生王陈等习学未成”为由,继续留任。天顺二年(1458年)缅甸再次派人请求,明廷仍旧强留。当内等六人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缅语翻译人才。明廷曾授予他们“序班”的职衔。死后均葬于南京。弘治十七年(1504年)缅甸阿瓦王朝又应明廷的要求,派遣陶孟(缅语为“头目”)思完、通事李瓒入访,选送孟香、的洒、香牛三位来四夷馆教授缅语,明廷也授予他们“鸿胪寺序班”(从九品)的职衔。孟香(汉名德馨)、的洒(汉名靖之)任教时间较长,后被授予“光禄寺署丞”官衔(从七品)。八百馆的首席教师兰者歌,是八百媳妇国人,也是随本国使者访明时被留下长期任教的。万历五年(1577年)八月,暹罗国派遣贡使渥闷(五等官)辣、渥文(六等官)铁、渥文贴通事渥文源入访明朝,四人均被留下。次年十月增设暹罗馆,即由他们四人任教。③四夷馆内也有中国教师,如缅甸馆中就有安徽县人方英和腾冲入刘迪,他们是1490年入馆任教的,为光禄寺署正教师和通政司知事教师。缅甸馆1509年留任的中国教师多达10人。从1490~1604年先后在缅甸馆任教的中国教师有28人。教师有父死子继的惯例,如缅甸馆序班教师夏凤朝病故,即由其子夏继恩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由神宗准其在四夷馆内缅甸馆“作养继习”。这种父死子继的在缅甸馆内称为“继业生”,据记载有姓名的继业生先后有赵继隆等共10人。①
人馆学习的称为“译字生”,多为官僚子弟,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38人隶属翰林院学译书,学生待遇是“人月给米一石”。学成后“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②后政府决定让四夷馆教师的子弟入馆学习,继承父业。据不完全统计,1508年选收译字生107名;1537年选收译字生120名;1604年有译字生94名;1607年有36名;1625年有44名,1628年有68名。③译字生分班由老师带领学习。例如教师序班:吴嘉胤、许辑瑞两人带领的译字生共计12名。译字生的课程,起初主要是专攻翻译杂字,学习一般文字翻译的技能,但明朝政府设四夷馆原是为了“习译夷字以通朝贡”,提督四夷馆少卿郭鋆于1542年提出:“专攻番译杂字,不及诰敕
、来文,恐非急务,今后萨那着并行肄业。”从此,翻译杂字、译写来文、回答敕谕成了译字生的三门主要课程。④明朝永乐年间,由于郑和、侯显相继出洋,外语教学备受重视。不但“四夷馆”中学习成绩优秀的可以委以官职,连民间精通外语者也可被荐举任用。因此私学外语之风一度兴起。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年)揭发:四夷馆教师马铭除教授官生154名外,又违例私授弟子136名。⑤
明朝政府的涉外机构除四夷馆外,还有专门接待政府使节的会同馆,这里的接待人员也要求掌握外语。清统治者入关后,顺治初年设立会同馆以待外国贡使,管理回回、缅甸、百夷、西蕃、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顺治初年所谓外国贡使只有朝鲜一家。及至顺治十一年(1654年)以后,琉球、荷兰、安南、暹罗等国相继入朝。会同馆馆址初设在内城,“以便监督稽查,周其日用,官兵看守,严其出入”。会同馆由礼部主客司派满汉主事各一人主管馆事,称提督。凡贡使到京之日,提督据督抚报文,稽查正从人数申报礼部,咨光禄寺支送饭食等物,咨工部应付铺垫什物,计到馆马数,咨户部给发草料,咨兵部拨送官兵到馆看守。次日,率贡使赍送该国王表文,至礼部呈递。清朝同时还继承明代“四夷馆”的全套制度,改名为“四译馆”。①清顺治元年(1644年)改名为四译馆,可能因为清朝统治者也是外来民族,对“夷”字比较敏感,于是采用中性的“四译馆”名称。乾隆十三年(1748年)又将会同馆与四译馆合并,于满汉郎中内拣选一人,令其兼理,兼理之人,加以提督会同四译馆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下设太使一人。会同四译馆同时是一个外语教学的机构,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会同四译馆设立朝鲜译学,于下五旗朝鲜子弟内,各咨取四人,令在馆通官二人教习,凡通官员缺,由礼部当堂考试,于应补旗分内,择精熟者充补。②
中外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字需要通过个体翻译的中介来实现文化与文明的对话,于是除了民间的私习外,官方的回回国子学、四夷馆和四译馆等就成了语言文字传习的重要场所。这些机构虽然招收译字生很有限,教授的内容和教学方式也相对比较狭隘,特别是到了近代,这些译字生受到知识结构的局限,无法适应鸦片战争前后的世界翻译格局的变化,如林则徐南下广州时曾经带了一位四译馆的译员,结果发现无法应对日益变化的局面,于是不得不另外出资雇佣了海外留学归来的袁德辉、梁进德等。但我们还是要肯定四译馆曾经为当时的丝绸之路上的外交活动和文明对话交流提供了翻译人才,四译馆等外语教学为后来的外语教育提供了若干经验。
二、《华夷译语》的版本与分类
会同馆、四译馆或会同四译馆究竟采用何种教材来教授外语的呢?不少学者都认为《华夷译语》是明清两代的四夷馆、会同馆和会同四译馆等所编纂的一大批汉语和其他非汉族语言对译词汇(称“杂字”)与公文(称“来文”)的总称。①国外一些学者一般依时代先后对《华夷译语》加以分类,有甲、乙、丙三种或甲、乙、丙、丁四种分类,②本文采用四种分类法:
1.甲种《华夷译语》(又称为洪武《华夷译语》):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诏名翰林侍讲火源洁。③等奉敕编写的《华夷译语》称为“甲种本”,又称洪武《华夷译语》,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刊行。前有刘三吾序,“华夷译语凡例”,分类为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衣服、饮食、珍宝、人物、人事、声色、数日、身体、方隅、通用十七门。后有《诏阿札失里》、《敕僧亦邻真臧卜》、《诰文》、《敕礼部行移应昌卫》、《敕礼部行移安答纳哈出》、《撒蛮答失里等书》、《纳门驸马书》、《脱儿豁察儿书》、《失列门书》、《捏怯来书》、《曩加思千户状》等。明朝郑晓在《今言》一书中指出:“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讲火源洁等类编《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行天下。乃命源洁与编修马懿赤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谐其声音。既成,诏刊布。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得其精。”①该书实际上是一部汉字拼切蒙文读音,同时译成汉文,分类排列的蒙汉词典。商务印书馆版《华夷译语》、上海书店版《丛书集成续编》收录的刻本和齐鲁书社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本均为甲种本,但三者存词汇内容和排列先后略有差别。
2.乙种《华夷译语》(又称永乐《华夷译语》):永乐五年(1407年)设四夷馆后,各馆教习番语开始大规模编修的《华夷译语》称为“乙种本各馆“译语”一般都分成杂字、来文两部分。有本民族的文字,不同抄本很多,有个别刻本行世。如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高昌馆杂字》既有抄本,也有刻本,又名《高昌馆译语》、《高昌馆译书》。它是明代高昌馆编纂的汉文、回鹘文对照分类词汇表,成书于永乐年间(约1403~1424年)。所收词语分为17门类,共1000多条,均从高昌、哈密等地朝贡表文中摘出。抄写格式为半页4个单词,分上下两排,每个回鹘文单词及其汉义和标音从右至左分三行竖写。用回鹘文楷书体书写,共使用18个字母,表示28个音,反映出明代吐鲁番、,”哈密一带维吾尔的特点。①由于部分散失,因此永乐年间的《华夷译语》究竟有多少种,目前尚难定论。
3.
丙种《华夷译语》(又称会同馆《华夷译语》):一般认为丙种本为明代会同馆所编,学术界大多认为编者为明末茅瑞征。②所辑的《华夷译语》只写出汉义和汉字注音,没有番文原文。计有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剌加、女贞、白夷等十三馆译语。此种文本只有抄本没有刻本,国外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丙种本均已经在解放前流到国外,国内已经没有藏本。但冯蒸经过调查,认为国内仍有丙种本的收藏,所发现的最早的丙种本《华夷译语》的《河西译语》成书于1370年,可见并非茅瑞征所纂辑。③丙种本火源洁译、茅伯符辑《华夷译语》有台北珪庭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该书收录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剌加、女真、百夷13种语言。
4.
丁种《华夷译语》(又称会同四译馆《华夷译语》):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会同四译馆设立后编撰。共有42种71册,均是杂字,没有来文,除《琉球语》一种外,均有民族文字。④清高宗《实录》中记载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曾上谕礼部:“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虽分类译名物,朕所识者,西番一种,已不无讹误”因此他要求傅恒、陈大受、那延泰等人,在原来《华夷译语》的基础上“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所有西天及
①该书版本很多,除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明抄本《华夷译语·高昌馆杂字》外,还有清抄本《高昌馆杂字》和清刻本《高昌馆译书》,其中收词最多的有942个词语。胡振华、黄润华整理的《高昌馆杂字》,民族出版社1984年;参见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79~380页。
②茅瑞征(1597~1636年),字伯符,系茅坤之重孙,号苕上愚公,又号澹泊居士。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书室日“浣花馆,著有《虞书笺》、《禹贡汇疏》、《象胥录》、《澹泊斋集》等书。参见《明人小传·四》、《明诗综·五十九》、《静志居诗话·十六》,参见冯蒸《(河西译语)初探》,载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第一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③冯蒸《〈河西译语〉初探》,载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第一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④冯蒸《〈河西译语〉初探》,载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第一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参见闻宥《国外对于〈华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七。
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其暹罗、白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著交该国附近省份之督抚,令其采集补正。此外,如海外诸夷并苗疆等处,有各成书体者,一并访录,亦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以昭同文盛治。”杨玉良认为现在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42种71册本《华夷译语》与乾隆十五年上谕和十五年策楞摺奏的内容基本相符,说明此书正是乾隆十五年前后由傅恒、陈大受等人奉敕采集、编校和缮写的。墨6框栏,框高21.5厘米、宽15.5厘米、四周双边、无行格、白口、无鱼尾。汉字均用墨笔楷书,番、夷字中,间有行书和楷书。每半页四组单词,横写,仅西天一种竖写。各种译语都首列本文,再以汉字注音、义于本文之下。书写整齐流畅,番、夷字形特点鲜明,易于辨认,体势生动。其中法文一种,还能辨认出竹笔书写的特征。故宫藏版的《华夷译语》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英、法、拉丁、意、葡、德及西天等译语7种28册。除西天以《西天真实名经》单辟一种外,其余六种都依照西番书例,列天文、地理等二十门,分类编次。收字730个至2094个不等。各种译语封面签题和册数分别为:“〓咭唎国译语”(英语),2册730字;“弗安喇西雅语”(法语),5册2074字;“拉氐诺语”(拉丁语),5册2094字;“伊达礼雅语”(意语),5册2094字;“播哹都噶礼雅语”(葡语),5册2094字;“额哷马尼雅语”(德语)5册2071字;“西天真实名经”1册267字。二是缅甸、暹罗、苏禄、琉球译语4种8册,其中“琉球土语”列11门1册282字;“苏禄译语”列19门1册403字,末附贡物三种名称;“暹罗译语”20门2册953字;“缅甸译语”20门4册1232字。三是西番译语1种5册,分20门2123字,是各种译语中收字最多的一种。四是川番译语9种9册,主要是四川境内所辖西番字语。各种译语都依照西番书例,列二十门编次,辑杂字726至751不等。五是东川府属倮倮译语5种5册,16至20门,288至740字不等。六为云南省境内17个地区形成的译语13种13册。七为广西境内译语3种3册,分别列11至16门,收杂字71至170个不等。乾隆时期形成的这一《华夷译语》共收录了11种外国译语,还辑录了西藏、四川、云南、广西四省所居住的少数民族语言31种,就语种来说,在传世的各种《华夷译语》中居首位。①
《华夷译语》所包涵的内容很广,属于四夷馆的,最初有鞑靼(蒙古)语、女真语、西番(藏)语、西天(印度)语、回回语、百夷(傣语)、高昌(回鹘)语、缅甸语,后来又增加了八百语、暹罗语,以及川滇桂一带各土司,如倮倮(彝)、壮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属于会同馆的,还有朝鲜语、日本语、琉球语、安南语、占城语、满喇加语等,后来又增加了真腊语、爪哇语等。若按地区划分,属于亚洲西南及南方民族语文有缅甸译语、暹罗译语、八百译语、猛卯译语、湾甸译语;属于亚洲西部及中部民族语文的有回回译语、高昌译语、蒙古译语、汉回(土耳其)译语;属于亚洲东部民族语文者有女真译语、朝鲜译语、日本译语等。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译馆和会同馆合并,称为会同四译馆,又增设了西洋馆,有弗安喇西雅语(法语)、额哷马尼雅语(德语)、伊达礼雅语(意语)、拉氐诺语(拉丁语)、播哷都噶礼雅语(葡语)五种。这些译语一般都是写本,流传不广,在国内未受到学者的充分重视。②
明、清两代总称为《华夷译语》的各种抄本、刻本数量很大,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尚无法将所有抄本和刻本包罗无遗。上述四种本子之外的其他写本还不断有所发现,流传于国外的抄本数量也很多,因此如今仍不能提供一份《华夷译语》的完整目录。国内刊印的早期有《涵芬楼秘笈》本,其中第四集(八册)收录《华夷译语》二册:目前收录较多的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所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其中收录的明钞本有《华夷译语》一卷、《续增华夷译语》一卷、《增定华夷译语残》二卷;所收《华夷译语》包含有《高昌馆课》(明钞本)、《高昌馆译书》一卷(清初刊本)、《高昌馆杂字》一卷(清初同文堂钞本)、《回回馆杂字》一卷(清初同文堂钞本)、《回回馆译语》一卷(清初刊本)、《译语》一卷(袁氏贞节堂钞本)、《百译馆译语》一卷(清初同文堂钞本)、《西天馆译语》一卷(清初刊本)、《西番译语》一卷(清初刊本)、《暹罗馆译语》一卷(清钞本)、《八馆馆考》一卷(清初同文堂钞本)等。
当时此类《华夷译语》的词汇书尚不懂得按词汇拼写的字母顺序来排列语汇,而采用中国传统的词义分类编排法,将汉语与周边地区和域外的词汇分成各种门类,每类中一般都列出分类词语,外语发音,汉文发音。如《鞑靼译语》分成天文、人物、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衣服、饮食、珍宝、人事、声色、数目、身体、方隅、通用,类似今天的分类字典。各种译语在分类上也会略有差别,如《日本馆译语》有“文史”;《朝鲜馆译语》有“干支”、“卦名”;《西番译语》有“彩色”、“香药”;《畏兀儿馆译语》有“朝仪”;《河西译语》有“珍宝”等若干门类。如以《朝鲜馆译语》的“地理门”为例,共收词64个:江——把剌——刚;路——吉二——落;桥——得屡——角;果园——刮世把——刮完;村里——吞阿奈——角歪。①大部分的《华夷译语》所收语汇多数是词,但也有收录一些短句,如《河西译语》的“人事门”中出现了一些语句:如“敬顺天道”、“尊待朝廷”、“明日入朝早起”、“好生摆着”、“跪”、“起来”、“这边来”、“那边去”、“领敕”、“明日领赏”、“谢恩”等,并有汉字的注音;“这边来”:印圆必牙;“那边去”:翁送答纳;“敬天顺道”:倘格因吉达麻的;“明日领赏”:法他迭米秃;“明
日入朝早起”:法他哈那母喇替。这些语句显然是礼部官员对前来“朝贡”的外族使节发出的指令。②《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两份文献中还包括大量的阿拉伯语借词和少量突厥、蒙古和汉语的借词。③这些杂字和译语颇类似今天的分类双语词典,同时它不仅起着翻译词典的作用,这些译语在当时的民族语言和外语的教学中,也有着某种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的作用。
三、《华夷译语》的价值和影响
以平原、山区、沙漠、绿洲、戈壁、草原和海洋组成的亚欧内陆和海洋的丝绸之路,接受过复杂繁多的人口、商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这些广泛的区域内并存着差异巨大的语言接触。就新疆地区出土例如大约20种文字24种语言的大量古代文献和文物。其中文字有汉文、佉卢文、梵文、吐火罗文、婆罗米文、粟特文、于阗文、波斯文、希伯莱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希腊文、叙利亚文、摩尼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察合台文、八思巴文、蒙古文等。其中语言有汉语、健陀罗语、梵语、吐火罗语、于阗塞语、月氏语、图木舒克语、粟特语、大夏语、婆罗钵语、希伯莱语、波斯语、帕提亚语、叙利亚语、突厥—回鹘语、乌孜别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吉克语等。①而海上丝绸之路还包含了朝鲜语、日语、越南语、满剌加语,以及后来地理大发现之后进入中国的葡萄牙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等,《华夷译语》的编纂过程反映了网络状态分布的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对话日益扩大的过程,是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史的最好见证。
《华夷译语》是汉语以及有关语种的历史语言学的重要资料,很多《译语》都是该语系中最早的分类字典,如1403年编纂、1549年由中国通事杨林校订的《满剌加译语》就是历史上第一部马来语汉语词典。②它们无疑是研究这些中外语言接触的最佳范本,明代严从简的《殊域周资录》是一部全面论述外国和它们与中国的陆上和海上关系的专著,其中第四部分论述海外国家安南、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柬埔寨和欧洲国家(佛郎机)。除去描述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制度和习俗外,该书还增加了简短的词汇汇编,包括日语、琉球语、蒙古语、阿拉伯语、越南语和其他语种,这些词汇汇编很有可能也是参照了《华夷译语》。《华夷译语》在18世纪以来就深受西方学者的注意,18世纪耶稣会士钱德明曾最早将若干《华夷译语》康熙年间的抄本带到欧洲,19世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曾将自己收集的《华夷译语》13卷明抄本遗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艾约瑟(J.Edkjns)携带回英国的十种明刻本,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原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曾将若干会同四译馆本《华夷译语》带回英国,藏剑桥大学。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鄂卢梭也曾收集《华夷译语》,现存法国远东博古学院。柏林图书馆藏有夏德收集的24册明抄本最为完整。日本东洋文库收有八种明抄本。①为了再现一度消失了的那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国内外学者利用《华夷译语》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1896年德国学者葛鲁贝公布了柏林图书馆所藏的明永乐年间的《华夷译语》,根据其中《女真译语》写出了《女真语言文字考》一书,该书1936年由北京文殿阁重新影印出版。该书可以视为研究女真文字的开始。在《女真语言文字考》中,葛鲁贝把《华夷译语》中的女真字拆开,按单笔字划排列,共得698个字,逐字定音、释义,又将“来文二十通”中的女真字转写翻译,分为十九门,共收女真语基本词汇871条,做到字、音、义并举,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女真语言文字汉译的工具书。1933年日本的渡边薰太郎把柏林图书馆藏的《女真译语》和日本东洋文库收藏的东洋文库本《女真译语》中的来文共四十通,用女真语和汉语对照加以解释,列有详细的女真语汇的注解,完成了《女真馆来文通解》一书。同年中国学者罗福成出版了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女真译语》正续编。②日本西田龙雄在研究《华夷译语》的基础上,自1964~1980年先后完成了《缅甸语与倮倮诸语——其声调语系的比较研究》(1964年)、《倮倮·缅甸语的研究》(1979年)、《中国西南的倮倮文字》(1980年)、《倮倮译语的研究——倮倮语的结构与体系》(1980年)等,为古代彝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现在正在计划出版一部《华夷译语研究丛书》,涉及西番馆译语、缅甸馆译语、暹罗馆译语、女真馆译语、多续馆译语等。①古蒙古语学家乌·满达夫潜心研究、整理、校勘、注释了13~16世纪汉文音译蒙古语的五种“译语”,并在此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继出版了《蒙古译语词典》、《音译注释〈华夷译语〉》、《蒙古语言研究》等一系列文献研究专著,填补了中国蒙古学界没有汉字音译蒙语文献的现代蒙文资料的空白。
《华夷译语》也成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中亚和西亚一些国家、地区民族生活和地方物产等的宝贵文献。如研究《回回馆译语》,对我们了解回族在明、清两代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在当时多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甲种本《华夷译语》中所记载的蒙古语词汇可以知道,当时已有小麦、大麦、粟、粳米、韭菜、豆、葱、蒜、芥、茄子、萝卜、葫芦等作物;水果有甜瓜、西瓜、葡萄、梨、杏、桃等。在“鸟兽门”中不仅列出了常见的牛、羊、猪、狗、马、狼、狐、猴等,还有一些至今很少知道的羝羖〓、白项鸭、海青、鸦鹘、兔鹘、龙朵、百雄等。②“倒喇舞”乃是元代蒙古族所创造的一种综合性歌舞表演形式,甲种本《华夷译语》中所述“唱——倒喇”、“唱的——倒喇黑赤”,表明所谓“倒喇”,即蒙语“歌唱”之意,强调了其特点是将歌曲与舞蹈的结合,现在我们知道倒喇舞是在蒙古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以歌唱为主的歌舞形式。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长处,变成一种内容丰富,灵活多样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将唱歌与器乐、插科打诨乃至杂技熔于一炉的艺术表演。
《华夷译语》的编纂也对后来晚清早期外语读本的编写产生了影响。如1883年林衡南所编《华夷通语》,在形式上几乎完全模仿《华夷译语》,用汉字拼切南洋一带国家外文读音,同时译成汉文,分类天文、地理、数目、时令、房屋、器用、人伦、工匠、身体、疾病、药材、绸布、颜料、国宝、律例、瓜菜、食物、滋味、果子、花木、禽兽、昆虫、鱼虾、埠头、船政、单字、二字、三字、四字、长句等三十类加以编排。这种分类结构上的影响在很多外语读本上有所表现,如1855年署名子卿的中国人编有《华英通语》,咸丰乙卯(1855年)香港协德堂藏版。子卿曾在英国人所办的书塾中学习过多年。《华英通语》全书分上下两卷,一是按事物分类的词汇,共分36类。有天文、地理、人伦、职分、国宝、五金、玉石、数目、时节、刑法、绸缎、布匹、首饰、颜色、瓜菜、药材、疾病、茶叶、通商、食物、酒名、飞禽、走兽、鱼虾、器用、房屋、百工、果子、身体、草木、各埠、船只、炮制、写字·房什、装扮、房内·用物类。二是不便分类的单词和简单会话,分单字、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长句、单式类等,所有单字、句语都附有英文原文。第一部分的分类显然是对《华夷译语》分类的模仿。唐廷枢(1832~1892年)所著的《英语集全》正文分六卷。卷之一天文(天、日、月、星、风、云、雨露)、地理(山、川、河、海、地名)、时令(年、月、日、时)、帝治(宗室、内阁、六部、五爵、朝臣、品级、士、农、工商、各国人、游民、人伦)、人体(头、五官、四支[肢]、五腑、六脏)、宫室(楼台、房铺、亭、园、池)、音乐、武备(弓箭、刀枪、炮火)。卷之二舟楫(船、艇、船上什物、桅、篷、索)、马车、器用(铺中器具、家中器具、玻璃器、刀叉器具)、器用(文房、书、牌照、单式)、器用(农器、工器)、工作、服饰(衣服、首饰)、食物(内附酒名、茶名)、花木(乔木、果子、五谷、菜蔬、花、草)。卷之三生物百体(鸟音、走兽、飞禽、鳞介、鱼、蚌、虫)、玉石、五金(内附外国银钱和中国银两图式)、通商税则(进口)、通商税则(出口)、通商税则(免税违禁货物)、杂货、各色铜、漆器、牙器、丝货、疋头(绒、呢、各色羽毛、布)。卷之四数目、颜色、一字门、尺寸、斤两、茶价、官讼、句语(短句)、句语(长句)。卷之五人事(一字句至四字句)。卷之六主要是各类商贸英语的句语问答。疋头问答门、孖毯入行问答门、卖茶问答门、肉台问答门、卖鸡鸭问答门、卖杂货问答门、租船问答、早辰讲话、早膳类、问大餐门、小食门、大餐门、饮茶门、请事仔(雇人问答)、晚头吩咐(晚间嘱咐)、买办、看银、管仓、管店、探友问答、百病类、医治等。尽管《英语集全》在分类上有很多适应时代变化的内容变化,但多少仍留下了《华夷译语》的分类痕迹。
不仅英语读本,其他语种的辞典和读本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如1878年由巴达维亚华人林采达编刊的马来语汉语辞典《通语津梁》上下两卷,收录1500个词汇,共分口头套语、日用常谈、数目、时令、天文、地理山水、身体举动、病症医药、宫室房屋、器用、仕宦人事、地理名胜、布帛、宝贝、衙门讼狱、五谷蔬菜、花草果木、禽兽、鱼虫等十八类。1887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龚渭琳编译的《法字入门》,全书分单字门、拼法门、天文门、地理门、人身门、饮食门、杂物门、走兽门、飞鸟门(虫附)、草木门、花果门、味料门、言语门、数目门、算法门、五金宝石门、男女服饰门、点句勾股考、初学文法门。与《法字人门》同年出版的《德字初桄》是由蒋煦编著的,德国施弥德校音。全书分上下两卷,卷上分学字、辨音、拼法门、文法门、记号备考、称谓门、短语门、问答门;卷下分总类门和杂语门两部分,总类门又分天文、地理、时令、邦国(都城附)、人伦、官职、身体、技艺、屋宇(店铺附)、服饰、器用、货物(进口货、出口货)、饮食(食物附)、花木(果品附)、禽兽、鳞虫、金石(珍宝附)、讼狱、舟车、疾病。1900年由广州同文馆出版的广州同文馆东文教习长谷川雄太郎(1865~1904年)编纂的《日语入门》一书,分别列出数目、月日、时刻、七曜日、四季、方角、天文、地理、人伦、身体、宫室、家具、化妆道具、食事道具、文具、服饰、饮食、果物、草木、鱼贝类、鸟、兽、虫、职业、舟车类、金石类、药、贸易品。不难看出,上述《通语津梁》、《法字入门》、《德字初桄》和《日语入门》等尽管在分类上有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但在大类划分上,仍然留有《华夷译语》的影子。
丝绸之路是文明对话之路,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就离不开语言的接触。本文关注的是在网状形分布的丝绸之路上,中外交往所需的外语人才,如民间的通事和官方的译员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培养的,他们依据着什么样的文献来完成语言学习的过程。关于上述问题,史料上往往语焉不详,只有一些零星的少数民族地区学习汉语,或少数民族赴汉地学习汉语的记录。据《周书·异域传·高昌》记载:高昌地区“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即少数民族文字——作者注),有《毛诗》、《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①又据《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唐代公主入藏后,吐蕃“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②可见当时即使在学习少数民族文字方面,虽已有若干有组织的教育形式以学习汉文化,但尚未建立起双语体制的教学和专门双语内容的学校,早期也找不到有关的双语教学的读本。本文尝试以《华夷译语》为中心来讨论丝绸之路上的语言接触和语言学习的若干问题。
一、“回回国子学”、四夷馆与会同四译馆
付克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一书中认为,我国最古老的外国语文学校是元朝的“回回国子学”。③这是元朝政府为培养译员设立的专门学校。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世祖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新元史·选举志》中记载:“是年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弟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从之。八月,遂置国子学。”①在回回国子学和回回监内教习一种称为“亦思替非”的文字。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认为:“‘亦思替非’为波斯古代都城之名,‘仪思替非’文字者,波斯文字也。回回国子学者,教习波斯文字者也。元时所谓回回文字,实波斯文字。”由此付克得出结论:元朝的“回回国子学”是一所教授波斯语言文字的学校。②但日本学者岩村忍认为,“亦思替非”可能是Istanbuli“伊斯坦布”语,即拜占庭语的音译。邵循正在《剌失德丁〈集史·蒙哥汗纪〉译释》中提出,“亦思替非”应为阿拉伯文istafa的对音,意为穆罕默德之文字。③这也反映出元代与中亚各国密切的经济往来,培养懂得“亦思替非”语言文字的人才,实在是当时社会之急需。
国子学可能不久就解散了,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按世祖旧制“笃意领教”。至泰定二年(1325年),入回回国子监学习波斯文的“公卿答复子弟与夫凡民之子”日渐增多,其学官及生员总数共50余人。其中受元政府资助的“饮膳者”有27人。元政府遂下令,对未能享受供给的一名助教和24名生员也提供饮膳。当时政府“百司庶府所设译史”,都从回回国子监内选取生员充任。④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内教习波斯语的教材,至今不存。元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称:“回回字,其母凡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向后,复归于前。”刘迎胜认为这份回回字母表,与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的教材或许有一点关系。⑤
明清时期海道大通,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交通的主要通道。明朝政府继续与周边各国和各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明太祖洪武二年到三十年,单入贡者,高丽和暹罗各为18次,占城16次,安南13次,琉球12次,爪哇和乌斯藏各为9次,真腊8次,三佛齐6次,日本5次,撒马儿罕和朵甘各3次,撒里和哈梅里各2次,西洋、勃泥、琐里、须文达那、墨剌、打箭炉、西蕃、百花、彭亨、览邦、缅等各1次。①频繁的与邻邦外蕃和海外国家的交往,使明朝政府深感翻译人才的缺乏,于是明初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正式成立,设在翰林院内,分蒙古、女直(即女真)、西藩、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主要是一个官方的语言文字的翻译机构和外语教习馆,②明代丘濬曾阐述过四夷馆的作用:“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如今设立八馆,“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使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史之。通者冠带,授以官,盖重其选也”。③西方和日本的学者有认为四夷馆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刘迎胜认为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在明代或清初属翰林院,拿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一所‘亚洲研究院’”④。正德中,增设八百馆。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⑤外来朝贡觐见者,来去必须有通事等陪同,如果有意摆脱通事擅自进京则以违法论处。若出事故,通事及随伴人员将受到连带处分。如正德三年(1508年),(哈密卫)写亦虎仙入贞,“不与通事偕行,自携边臣文牒投进。大通事王永怒,疏请治究。”弘治八年(1495年)乌斯藏阐化王遣使来贡,在扬州“杀牲纵酒”发生殴斗,结果通事及伴随者都被治罪。①
《明史·职官志》称宣德元年(1426年)四夷馆“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课程”。②教授“四夷语言”的教师在设馆之初,多为通晓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士,也有部分外籍教师。最先聘任外籍教师的是缅甸馆,大约在正统年间(1436~1449年),缅甸人当内、云清、班思杰、康剌改、潘达速、已扯盼六人作为缅甸阿瓦王朝的使者来明朝进贡,经明廷要求,他们便留在四夷馆任教。景泰二年(1451年),缅甸派人请求遣返当内六人,明廷以“译字生王陈等习学未成”为由,继续留任。天顺二年(1458年)缅甸再次派人请求,明廷仍旧强留。当内等六人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缅语翻译人才。明廷曾授予他们“序班”的职衔。死后均葬于南京。弘治十七年(1504年)缅甸阿瓦王朝又应明廷的要求,派遣陶孟(缅语为“头目”)思完、通事李瓒入访,选送孟香、的洒、香牛三位来四夷馆教授缅语,明廷也授予他们“鸿胪寺序班”(从九品)的职衔。孟香(汉名德馨)、的洒(汉名靖之)任教时间较长,后被授予“光禄寺署丞”官衔(从七品)。八百馆的首席教师兰者歌,是八百媳妇国人,也是随本国使者访明时被留下长期任教的。万历五年(1577年)八月,暹罗国派遣贡使渥闷(五等官)辣、渥文(六等官)铁、渥文贴通事渥文源入访明朝,四人均被留下。次年十月增设暹罗馆,即由他们四人任教。③四夷馆内也有中国教师,如缅甸馆中就有安徽县人方英和腾冲入刘迪,他们是1490年入馆任教的,为光禄寺署正教师和通政司知事教师。缅甸馆1509年留任的中国教师多达10人。从1490~1604年先后在缅甸馆任教的中国教师有28人。教师有父死子继的惯例,如缅甸馆序班教师夏凤朝病故,即由其子夏继恩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由神宗准其在四夷馆内缅甸馆“作养继习”。这种父死子继的在缅甸馆内称为“继业生”,据记载有姓名的继业生先后有赵继隆等共10人。①
人馆学习的称为“译字生”,多为官僚子弟,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38人隶属翰林院学译书,学生待遇是“人月给米一石”。学成后“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②后政府决定让四夷馆教师的子弟入馆学习,继承父业。据不完全统计,1508年选收译字生107名;1537年选收译字生120名;1604年有译字生94名;1607年有36名;1625年有44名,1628年有68名。③译字生分班由老师带领学习。例如教师序班:吴嘉胤、许辑瑞两人带领的译字生共计12名。译字生的课程,起初主要是专攻翻译杂字,学习一般文字翻译的技能,但明朝政府设四夷馆原是为了“习译夷字以通朝贡”,提督四夷馆少卿郭鋆于1542年提出:“专攻番译杂字,不及诰敕
、来文,恐非急务,今后萨那着并行肄业。”从此,翻译杂字、译写来文、回答敕谕成了译字生的三门主要课程。④明朝永乐年间,由于郑和、侯显相继出洋,外语教学备受重视。不但“四夷馆”中学习成绩优秀的可以委以官职,连民间精通外语者也可被荐举任用。因此私学外语之风一度兴起。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年)揭发:四夷馆教师马铭除教授官生154名外,又违例私授弟子136名。⑤
明朝政府的涉外机构除四夷馆外,还有专门接待政府使节的会同馆,这里的接待人员也要求掌握外语。清统治者入关后,顺治初年设立会同馆以待外国贡使,管理回回、缅甸、百夷、西蕃、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顺治初年所谓外国贡使只有朝鲜一家。及至顺治十一年(1654年)以后,琉球、荷兰、安南、暹罗等国相继入朝。会同馆馆址初设在内城,“以便监督稽查,周其日用,官兵看守,严其出入”。会同馆由礼部主客司派满汉主事各一人主管馆事,称提督。凡贡使到京之日,提督据督抚报文,稽查正从人数申报礼部,咨光禄寺支送饭食等物,咨工部应付铺垫什物,计到馆马数,咨户部给发草料,咨兵部拨送官兵到馆看守。次日,率贡使赍送该国王表文,至礼部呈递。清朝同时还继承明代“四夷馆”的全套制度,改名为“四译馆”。①清顺治元年(1644年)改名为四译馆,可能因为清朝统治者也是外来民族,对“夷”字比较敏感,于是采用中性的“四译馆”名称。乾隆十三年(1748年)又将会同馆与四译馆合并,于满汉郎中内拣选一人,令其兼理,兼理之人,加以提督会同四译馆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下设太使一人。会同四译馆同时是一个外语教学的机构,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在会同四译馆设立朝鲜译学,于下五旗朝鲜子弟内,各咨取四人,令在馆通官二人教习,凡通官员缺,由礼部当堂考试,于应补旗分内,择精熟者充补。②
中外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字需要通过个体翻译的中介来实现文化与文明的对话,于是除了民间的私习外,官方的回回国子学、四夷馆和四译馆等就成了语言文字传习的重要场所。这些机构虽然招收译字生很有限,教授的内容和教学方式也相对比较狭隘,特别是到了近代,这些译字生受到知识结构的局限,无法适应鸦片战争前后的世界翻译格局的变化,如林则徐南下广州时曾经带了一位四译馆的译员,结果发现无法应对日益变化的局面,于是不得不另外出资雇佣了海外留学归来的袁德辉、梁进德等。但我们还是要肯定四译馆曾经为当时的丝绸之路上的外交活动和文明对话交流提供了翻译人才,四译馆等外语教学为后来的外语教育提供了若干经验。
二、《华夷译语》的版本与分类
会同馆、四译馆或会同四译馆究竟采用何种教材来教授外语的呢?不少学者都认为《华夷译语》是明清两代的四夷馆、会同馆和会同四译馆等所编纂的一大批汉语和其他非汉族语言对译词汇(称“杂字”)与公文(称“来文”)的总称。①国外一些学者一般依时代先后对《华夷译语》加以分类,有甲、乙、丙三种或甲、乙、丙、丁四种分类,②本文采用四种分类法:
1.甲种《华夷译语》(又称为洪武《华夷译语》):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诏名翰林侍讲火源洁。③等奉敕编写的《华夷译语》称为“甲种本”,又称洪武《华夷译语》,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刊行。前有刘三吾序,“华夷译语凡例”,分类为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衣服、饮食、珍宝、人物、人事、声色、数日、身体、方隅、通用十七门。后有《诏阿札失里》、《敕僧亦邻真臧卜》、《诰文》、《敕礼部行移应昌卫》、《敕礼部行移安答纳哈出》、《撒蛮答失里等书》、《纳门驸马书》、《脱儿豁察儿书》、《失列门书》、《捏怯来书》、《曩加思千户状》等。明朝郑晓在《今言》一书中指出:“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讲火源洁等类编《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行天下。乃命源洁与编修马懿赤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谐其声音。既成,诏刊布。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得其精。”①该书实际上是一部汉字拼切蒙文读音,同时译成汉文,分类排列的蒙汉词典。商务印书馆版《华夷译语》、上海书店版《丛书集成续编》收录的刻本和齐鲁书社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清钞本均为甲种本,但三者存词汇内容和排列先后略有差别。
2.乙种《华夷译语》(又称永乐《华夷译语》):永乐五年(1407年)设四夷馆后,各馆教习番语开始大规模编修的《华夷译语》称为“乙种本各馆“译语”一般都分成杂字、来文两部分。有本民族的文字,不同抄本很多,有个别刻本行世。如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高昌馆杂字》既有抄本,也有刻本,又名《高昌馆译语》、《高昌馆译书》。它是明代高昌馆编纂的汉文、回鹘文对照分类词汇表,成书于永乐年间(约1403~1424年)。所收词语分为17门类,共1000多条,均从高昌、哈密等地朝贡表文中摘出。抄写格式为半页4个单词,分上下两排,每个回鹘文单词及其汉义和标音从右至左分三行竖写。用回鹘文楷书体书写,共使用18个字母,表示28个音,反映出明代吐鲁番、,”哈密一带维吾尔的特点。①由于部分散失,因此永乐年间的《华夷译语》究竟有多少种,目前尚难定论。
3.
丙种《华夷译语》(又称会同馆《华夷译语》):一般认为丙种本为明代会同馆所编,学术界大多认为编者为明末茅瑞征。②所辑的《华夷译语》只写出汉义和汉字注音,没有番文原文。计有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剌加、女贞、白夷等十三馆译语。此种文本只有抄本没有刻本,国外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丙种本均已经在解放前流到国外,国内已经没有藏本。但冯蒸经过调查,认为国内仍有丙种本的收藏,所发现的最早的丙种本《华夷译语》的《河西译语》成书于1370年,可见并非茅瑞征所纂辑。③丙种本火源洁译、茅伯符辑《华夷译语》有台北珪庭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该书收录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剌加、女真、百夷13种语言。
4.
丁种《华夷译语》(又称会同四译馆《华夷译语》):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会同四译馆设立后编撰。共有42种71册,均是杂字,没有来文,除《琉球语》一种外,均有民族文字。④清高宗《实录》中记载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曾上谕礼部:“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虽分类译名物,朕所识者,西番一种,已不无讹误”因此他要求傅恒、陈大受、那延泰等人,在原来《华夷译语》的基础上“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所有西天及
①该书版本很多,除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明抄本《华夷译语·高昌馆杂字》外,还有清抄本《高昌馆杂字》和清刻本《高昌馆译书》,其中收词最多的有942个词语。胡振华、黄润华整理的《高昌馆杂字》,民族出版社1984年;参见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79~380页。
②茅瑞征(1597~1636年),字伯符,系茅坤之重孙,号苕上愚公,又号澹泊居士。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书室日“浣花馆,著有《虞书笺》、《禹贡汇疏》、《象胥录》、《澹泊斋集》等书。参见《明人小传·四》、《明诗综·五十九》、《静志居诗话·十六》,参见冯蒸《(河西译语)初探》,载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第一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③冯蒸《〈河西译语〉初探》,载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第一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④冯蒸《〈河西译语〉初探》,载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第一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参见闻宥《国外对于〈华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七。
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其暹罗、白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著交该国附近省份之督抚,令其采集补正。此外,如海外诸夷并苗疆等处,有各成书体者,一并访录,亦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以昭同文盛治。”杨玉良认为现在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42种71册本《华夷译语》与乾隆十五年上谕和十五年策楞摺奏的内容基本相符,说明此书正是乾隆十五年前后由傅恒、陈大受等人奉敕采集、编校和缮写的。墨6框栏,框高21.5厘米、宽15.5厘米、四周双边、无行格、白口、无鱼尾。汉字均用墨笔楷书,番、夷字中,间有行书和楷书。每半页四组单词,横写,仅西天一种竖写。各种译语都首列本文,再以汉字注音、义于本文之下。书写整齐流畅,番、夷字形特点鲜明,易于辨认,体势生动。其中法文一种,还能辨认出竹笔书写的特征。故宫藏版的《华夷译语》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英、法、拉丁、意、葡、德及西天等译语7种28册。除西天以《西天真实名经》单辟一种外,其余六种都依照西番书例,列天文、地理等二十门,分类编次。收字730个至2094个不等。各种译语封面签题和册数分别为:“〓咭唎国译语”(英语),2册730字;“弗安喇西雅语”(法语),5册2074字;“拉氐诺语”(拉丁语),5册2094字;“伊达礼雅语”(意语),5册2094字;“播哹都噶礼雅语”(葡语),5册2094字;“额哷马尼雅语”(德语)5册2071字;“西天真实名经”1册267字。二是缅甸、暹罗、苏禄、琉球译语4种8册,其中“琉球土语”列11门1册282字;“苏禄译语”列19门1册403字,末附贡物三种名称;“暹罗译语”20门2册953字;“缅甸译语”20门4册1232字。三是西番译语1种5册,分20门2123字,是各种译语中收字最多的一种。四是川番译语9种9册,主要是四川境内所辖西番字语。各种译语都依照西番书例,列二十门编次,辑杂字726至751不等。五是东川府属倮倮译语5种5册,16至20门,288至740字不等。六为云南省境内17个地区形成的译语13种13册。七为广西境内译语3种3册,分别列11至16门,收杂字71至170个不等。乾隆时期形成的这一《华夷译语》共收录了11种外国译语,还辑录了西藏、四川、云南、广西四省所居住的少数民族语言31种,就语种来说,在传世的各种《华夷译语》中居首位。①
《华夷译语》所包涵的内容很广,属于四夷馆的,最初有鞑靼(蒙古)语、女真语、西番(藏)语、西天(印度)语、回回语、百夷(傣语)、高昌(回鹘)语、缅甸语,后来又增加了八百语、暹罗语,以及川滇桂一带各土司,如倮倮(彝)、壮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属于会同馆的,还有朝鲜语、日本语、琉球语、安南语、占城语、满喇加语等,后来又增加了真腊语、爪哇语等。若按地区划分,属于亚洲西南及南方民族语文有缅甸译语、暹罗译语、八百译语、猛卯译语、湾甸译语;属于亚洲西部及中部民族语文的有回回译语、高昌译语、蒙古译语、汉回(土耳其)译语;属于亚洲东部民族语文者有女真译语、朝鲜译语、日本译语等。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译馆和会同馆合并,称为会同四译馆,又增设了西洋馆,有弗安喇西雅语(法语)、额哷马尼雅语(德语)、伊达礼雅语(意语)、拉氐诺语(拉丁语)、播哷都噶礼雅语(葡语)五种。这些译语一般都是写本,流传不广,在国内未受到学者的充分重视。②
明、清两代总称为《华夷译语》的各种抄本、刻本数量很大,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尚无法将所有抄本和刻本包罗无遗。上述四种本子之外的其他写本还不断有所发现,流传于国外的抄本数量也很多,因此如今仍不能提供一份《华夷译语》的完整目录。国内刊印的早期有《涵芬楼秘笈》本,其中第四集(八册)收录《华夷译语》二册:目前收录较多的为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所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其中收录的明钞本有《华夷译语》一卷、《续增华夷译语》一卷、《增定华夷译语残》二卷;所收《华夷译语》包含有《高昌馆课》(明钞本)、《高昌馆译书》一卷(清初刊本)、《高昌馆杂字》一卷(清初同文堂钞本)、《回回馆杂字》一卷(清初同文堂钞本)、《回回馆译语》一卷(清初刊本)、《译语》一卷(袁氏贞节堂钞本)、《百译馆译语》一卷(清初同文堂钞本)、《西天馆译语》一卷(清初刊本)、《西番译语》一卷(清初刊本)、《暹罗馆译语》一卷(清钞本)、《八馆馆考》一卷(清初同文堂钞本)等。
当时此类《华夷译语》的词汇书尚不懂得按词汇拼写的字母顺序来排列语汇,而采用中国传统的词义分类编排法,将汉语与周边地区和域外的词汇分成各种门类,每类中一般都列出分类词语,外语发音,汉文发音。如《鞑靼译语》分成天文、人物、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衣服、饮食、珍宝、人事、声色、数目、身体、方隅、通用,类似今天的分类字典。各种译语在分类上也会略有差别,如《日本馆译语》有“文史”;《朝鲜馆译语》有“干支”、“卦名”;《西番译语》有“彩色”、“香药”;《畏兀儿馆译语》有“朝仪”;《河西译语》有“珍宝”等若干门类。如以《朝鲜馆译语》的“地理门”为例,共收词64个:江——把剌——刚;路——吉二——落;桥——得屡——角;果园——刮世把——刮完;村里——吞阿奈——角歪。①大部分的《华夷译语》所收语汇多数是词,但也有收录一些短句,如《河西译语》的“人事门”中出现了一些语句:如“敬顺天道”、“尊待朝廷”、“明日入朝早起”、“好生摆着”、“跪”、“起来”、“这边来”、“那边去”、“领敕”、“明日领赏”、“谢恩”等,并有汉字的注音;“这边来”:印圆必牙;“那边去”:翁送答纳;“敬天顺道”:倘格因吉达麻的;“明日领赏”:法他迭米秃;“明
日入朝早起”:法他哈那母喇替。这些语句显然是礼部官员对前来“朝贡”的外族使节发出的指令。②《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两份文献中还包括大量的阿拉伯语借词和少量突厥、蒙古和汉语的借词。③这些杂字和译语颇类似今天的分类双语词典,同时它不仅起着翻译词典的作用,这些译语在当时的民族语言和外语的教学中,也有着某种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的作用。
三、《华夷译语》的价值和影响
以平原、山区、沙漠、绿洲、戈壁、草原和海洋组成的亚欧内陆和海洋的丝绸之路,接受过复杂繁多的人口、商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这些广泛的区域内并存着差异巨大的语言接触。就新疆地区出土例如大约20种文字24种语言的大量古代文献和文物。其中文字有汉文、佉卢文、梵文、吐火罗文、婆罗米文、粟特文、于阗文、波斯文、希伯莱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希腊文、叙利亚文、摩尼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察合台文、八思巴文、蒙古文等。其中语言有汉语、健陀罗语、梵语、吐火罗语、于阗塞语、月氏语、图木舒克语、粟特语、大夏语、婆罗钵语、希伯莱语、波斯语、帕提亚语、叙利亚语、突厥—回鹘语、乌孜别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吉克语等。①而海上丝绸之路还包含了朝鲜语、日语、越南语、满剌加语,以及后来地理大发现之后进入中国的葡萄牙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等,《华夷译语》的编纂过程反映了网络状态分布的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对话日益扩大的过程,是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史的最好见证。
《华夷译语》是汉语以及有关语种的历史语言学的重要资料,很多《译语》都是该语系中最早的分类字典,如1403年编纂、1549年由中国通事杨林校订的《满剌加译语》就是历史上第一部马来语汉语词典。②它们无疑是研究这些中外语言接触的最佳范本,明代严从简的《殊域周资录》是一部全面论述外国和它们与中国的陆上和海上关系的专著,其中第四部分论述海外国家安南、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柬埔寨和欧洲国家(佛郎机)。除去描述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制度和习俗外,该书还增加了简短的词汇汇编,包括日语、琉球语、蒙古语、阿拉伯语、越南语和其他语种,这些词汇汇编很有可能也是参照了《华夷译语》。《华夷译语》在18世纪以来就深受西方学者的注意,18世纪耶稣会士钱德明曾最早将若干《华夷译语》康熙年间的抄本带到欧洲,19世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曾将自己收集的《华夷译语》13卷明抄本遗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艾约瑟(J.Edkjns)携带回英国的十种明刻本,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原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曾将若干会同四译馆本《华夷译语》带回英国,藏剑桥大学。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鄂卢梭也曾收集《华夷译语》,现存法国远东博古学院。柏林图书馆藏有夏德收集的24册明抄本最为完整。日本东洋文库收有八种明抄本。①为了再现一度消失了的那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国内外学者利用《华夷译语》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1896年德国学者葛鲁贝公布了柏林图书馆所藏的明永乐年间的《华夷译语》,根据其中《女真译语》写出了《女真语言文字考》一书,该书1936年由北京文殿阁重新影印出版。该书可以视为研究女真文字的开始。在《女真语言文字考》中,葛鲁贝把《华夷译语》中的女真字拆开,按单笔字划排列,共得698个字,逐字定音、释义,又将“来文二十通”中的女真字转写翻译,分为十九门,共收女真语基本词汇871条,做到字、音、义并举,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女真语言文字汉译的工具书。1933年日本的渡边薰太郎把柏林图书馆藏的《女真译语》和日本东洋文库收藏的东洋文库本《女真译语》中的来文共四十通,用女真语和汉语对照加以解释,列有详细的女真语汇的注解,完成了《女真馆来文通解》一书。同年中国学者罗福成出版了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女真译语》正续编。②日本西田龙雄在研究《华夷译语》的基础上,自1964~1980年先后完成了《缅甸语与倮倮诸语——其声调语系的比较研究》(1964年)、《倮倮·缅甸语的研究》(1979年)、《中国西南的倮倮文字》(1980年)、《倮倮译语的研究——倮倮语的结构与体系》(1980年)等,为古代彝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现在正在计划出版一部《华夷译语研究丛书》,涉及西番馆译语、缅甸馆译语、暹罗馆译语、女真馆译语、多续馆译语等。①古蒙古语学家乌·满达夫潜心研究、整理、校勘、注释了13~16世纪汉文音译蒙古语的五种“译语”,并在此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继出版了《蒙古译语词典》、《音译注释〈华夷译语〉》、《蒙古语言研究》等一系列文献研究专著,填补了中国蒙古学界没有汉字音译蒙语文献的现代蒙文资料的空白。
《华夷译语》也成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中亚和西亚一些国家、地区民族生活和地方物产等的宝贵文献。如研究《回回馆译语》,对我们了解回族在明、清两代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在当时多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甲种本《华夷译语》中所记载的蒙古语词汇可以知道,当时已有小麦、大麦、粟、粳米、韭菜、豆、葱、蒜、芥、茄子、萝卜、葫芦等作物;水果有甜瓜、西瓜、葡萄、梨、杏、桃等。在“鸟兽门”中不仅列出了常见的牛、羊、猪、狗、马、狼、狐、猴等,还有一些至今很少知道的羝羖〓、白项鸭、海青、鸦鹘、兔鹘、龙朵、百雄等。②“倒喇舞”乃是元代蒙古族所创造的一种综合性歌舞表演形式,甲种本《华夷译语》中所述“唱——倒喇”、“唱的——倒喇黑赤”,表明所谓“倒喇”,即蒙语“歌唱”之意,强调了其特点是将歌曲与舞蹈的结合,现在我们知道倒喇舞是在蒙古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以歌唱为主的歌舞形式。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其他艺术形式的长处,变成一种内容丰富,灵活多样的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将唱歌与器乐、插科打诨乃至杂技熔于一炉的艺术表演。
《华夷译语》的编纂也对后来晚清早期外语读本的编写产生了影响。如1883年林衡南所编《华夷通语》,在形式上几乎完全模仿《华夷译语》,用汉字拼切南洋一带国家外文读音,同时译成汉文,分类天文、地理、数目、时令、房屋、器用、人伦、工匠、身体、疾病、药材、绸布、颜料、国宝、律例、瓜菜、食物、滋味、果子、花木、禽兽、昆虫、鱼虾、埠头、船政、单字、二字、三字、四字、长句等三十类加以编排。这种分类结构上的影响在很多外语读本上有所表现,如1855年署名子卿的中国人编有《华英通语》,咸丰乙卯(1855年)香港协德堂藏版。子卿曾在英国人所办的书塾中学习过多年。《华英通语》全书分上下两卷,一是按事物分类的词汇,共分36类。有天文、地理、人伦、职分、国宝、五金、玉石、数目、时节、刑法、绸缎、布匹、首饰、颜色、瓜菜、药材、疾病、茶叶、通商、食物、酒名、飞禽、走兽、鱼虾、器用、房屋、百工、果子、身体、草木、各埠、船只、炮制、写字·房什、装扮、房内·用物类。二是不便分类的单词和简单会话,分单字、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长句、单式类等,所有单字、句语都附有英文原文。第一部分的分类显然是对《华夷译语》分类的模仿。唐廷枢(1832~1892年)所著的《英语集全》正文分六卷。卷之一天文(天、日、月、星、风、云、雨露)、地理(山、川、河、海、地名)、时令(年、月、日、时)、帝治(宗室、内阁、六部、五爵、朝臣、品级、士、农、工商、各国人、游民、人伦)、人体(头、五官、四支[肢]、五腑、六脏)、宫室(楼台、房铺、亭、园、池)、音乐、武备(弓箭、刀枪、炮火)。卷之二舟楫(船、艇、船上什物、桅、篷、索)、马车、器用(铺中器具、家中器具、玻璃器、刀叉器具)、器用(文房、书、牌照、单式)、器用(农器、工器)、工作、服饰(衣服、首饰)、食物(内附酒名、茶名)、花木(乔木、果子、五谷、菜蔬、花、草)。卷之三生物百体(鸟音、走兽、飞禽、鳞介、鱼、蚌、虫)、玉石、五金(内附外国银钱和中国银两图式)、通商税则(进口)、通商税则(出口)、通商税则(免税违禁货物)、杂货、各色铜、漆器、牙器、丝货、疋头(绒、呢、各色羽毛、布)。卷之四数目、颜色、一字门、尺寸、斤两、茶价、官讼、句语(短句)、句语(长句)。卷之五人事(一字句至四字句)。卷之六主要是各类商贸英语的句语问答。疋头问答门、孖毯入行问答门、卖茶问答门、肉台问答门、卖鸡鸭问答门、卖杂货问答门、租船问答、早辰讲话、早膳类、问大餐门、小食门、大餐门、饮茶门、请事仔(雇人问答)、晚头吩咐(晚间嘱咐)、买办、看银、管仓、管店、探友问答、百病类、医治等。尽管《英语集全》在分类上有很多适应时代变化的内容变化,但多少仍留下了《华夷译语》的分类痕迹。
不仅英语读本,其他语种的辞典和读本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如1878年由巴达维亚华人林采达编刊的马来语汉语辞典《通语津梁》上下两卷,收录1500个词汇,共分口头套语、日用常谈、数目、时令、天文、地理山水、身体举动、病症医药、宫室房屋、器用、仕宦人事、地理名胜、布帛、宝贝、衙门讼狱、五谷蔬菜、花草果木、禽兽、鱼虫等十八类。1887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龚渭琳编译的《法字入门》,全书分单字门、拼法门、天文门、地理门、人身门、饮食门、杂物门、走兽门、飞鸟门(虫附)、草木门、花果门、味料门、言语门、数目门、算法门、五金宝石门、男女服饰门、点句勾股考、初学文法门。与《法字人门》同年出版的《德字初桄》是由蒋煦编著的,德国施弥德校音。全书分上下两卷,卷上分学字、辨音、拼法门、文法门、记号备考、称谓门、短语门、问答门;卷下分总类门和杂语门两部分,总类门又分天文、地理、时令、邦国(都城附)、人伦、官职、身体、技艺、屋宇(店铺附)、服饰、器用、货物(进口货、出口货)、饮食(食物附)、花木(果品附)、禽兽、鳞虫、金石(珍宝附)、讼狱、舟车、疾病。1900年由广州同文馆出版的广州同文馆东文教习长谷川雄太郎(1865~1904年)编纂的《日语入门》一书,分别列出数目、月日、时刻、七曜日、四季、方角、天文、地理、人伦、身体、宫室、家具、化妆道具、食事道具、文具、服饰、饮食、果物、草木、鱼贝类、鸟、兽、虫、职业、舟车类、金石类、药、贸易品。不难看出,上述《通语津梁》、《法字入门》、《德字初桄》和《日语入门》等尽管在分类上有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但在大类划分上,仍然留有《华夷译语》的影子。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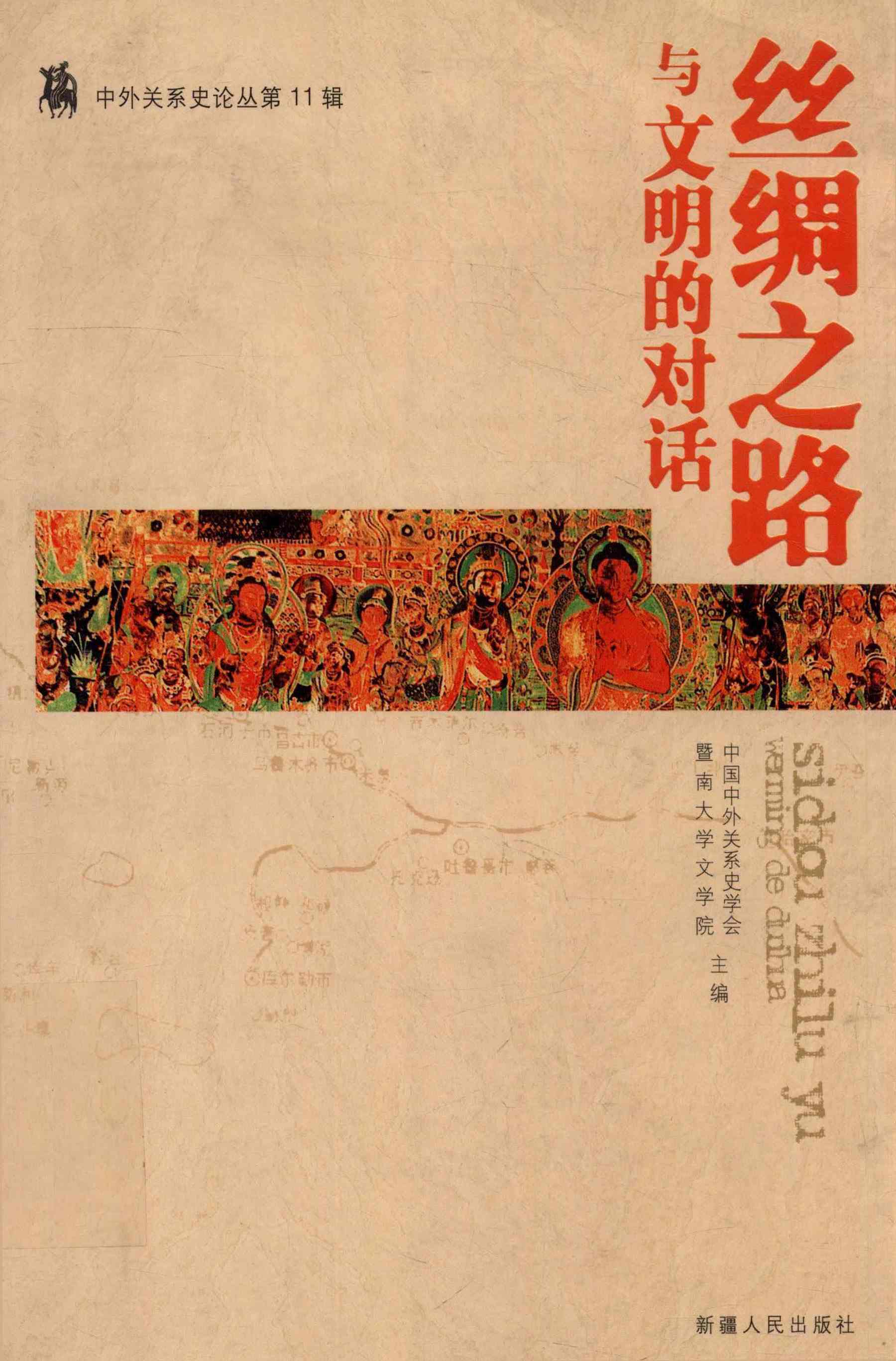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发展与作用》、《丝绸之路上的新和》、《古代新疆与阿拉伯文化》、《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21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喀什“香妃墓”辨误》、《19世纪西方国家对新疆的认知渠道》、《丝绸之路上的英国驻新疆领事馆考述》、《20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从丝绸文化传播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回流》等二十余篇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邹振环
责任者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