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5819 |
| 颗粒名称: | 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 |
| 分类号: | K928.6 |
| 页数: | 21 |
| 页码: | 284-304 |
| 摘要: | 巴蜀古代文明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巴蜀为重心的中国西南古代文明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及其通道,不论在中国文明史还是中外关系史上都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往往只上溯到汉代并且以西北丝绸之路为唯一重心。但是,近年考古学上中国西南特别是巴蜀地区大量外来文化因素的发现,以及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一些地区中国文物尤其是巴蜀文化遗迹的发现,使得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古代巴蜀在早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 关键词: | 巴蜀 古代文明 丝绸之路 |
内容
巴蜀古代文明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巴蜀为重心的中国西南古代文明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及其通道(即南方丝绸之路),不论在中国文明史还是中外关系史上都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往往只上溯到汉代并且以西北丝绸之路为唯一重心。但是,近年考古学上中国西南特别是巴蜀地区大量外来文化因素的发现,以及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一些地区中国文物尤其是巴蜀文化遗迹的发现,使得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古代巴蜀在早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入系统地探索这些文化因素的来龙去脉,并对中外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梳理、钩沉,加以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先秦汉晋时期巴蜀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进而延伸到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其历史意义,已成为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大新课题。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外文献、考古和人类学资料的分析,对大量相关文化因素及其组合方式和演变关系等进行比较,初步揭示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供学术界同行参考。
一、巴蜀文化与滇文化
滇文化是分布在云南东部地区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地方文化,其创造者为滇人。滇文化的年代,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学材料,上限约在公元前5世纪,下限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相续400余年。
史书有关滇文化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言之极为简略。《华阳国志·南中志》对滇文化的记载,也是语焉未详。由于史籍的阙如,前人总以滇王国为蛮荒之国,滇人为后进民族,而滇文化也还徘徊在文明之外。可是,历史事实却完全相反。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滇文化原来是一支灿烂的青铜文化,它具有极为发达的青铜器农业,进步的青铜器手工业,有着异常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它不仅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占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而且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支青铜文化相媲美。
(一)青铜文化的交流遗迹
不论从考古学还是历史文献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青铜文化,诞生年代较之滇文化古远,持续时期也比滇池区域青铜文化长久。固然这两种青铜文化各有优长之处,互有影响,但成都平原青铜文化较早地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却是考古学上的事实。
20世纪50~90年代先后发掘的滇文化墓葬——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群中,有较为明显的成都平原早、中期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晋宁在汉代是滇池县,为故滇国之所在。①这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铸有若干人物和动物的立雕像。这类风格完全不同于华北和楚文化,却与三星堆青铜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造型艺术也较接近。
晋宁石寨山青铜雕像人物中,有椎髻、辫发、穿耳等各种形式,与三星堆青铜雕像人物不乏某些共同之点。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长方形铜片上刻画的符号当中,有一柄短杖的图像,杖身有四个人首纹。这种杖,虽无实物发现,但杖首铜饰在滇文化中却是一突出特点,表明曾经有过发达的用杖制度。有学者认为上刻四个人首纹的杖,可能是某种宗教用物或代表权力的节杖。①这种用杖之制与三星堆青铜文化中的金杖极其相似,而且杖身刻画人首纹,也正是三星堆金杖的显著特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铜鼓,上刻伎乐图像,其中的人、鱼、鸟图像,也与三星堆金杖图案以人、鱼、鸟为主题相同。从蜀、滇相邻,民族、民俗有若干近似等情况出发,两地青铜文化的近似,自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完全有文化交流传播的可能。三星堆青铜文化早于滇文化,滇文化从蜀文化中采借了这些文化因素,并不是没有可能。②
滇文化青铜兵器也有浓厚的蜀文化色彩。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都发现了无格式青铜剑,这种剑与巴蜀式扁茎无格柳叶形青铜剑相比,主要区别仅在于滇式无格剑为圆茎,巴蜀式剑则为扁茎,两种剑实际上属于同一风格,没有本质区别。滇文化的无格式剑与巴蜀文化,显然存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关系。③滇文化的青铜戈,最大特点是以无胡戈为主,占总数的3/4以上,这一特点与蜀文化也很近似。其基本形制只有四种,除前锋平齐的一种外,都是戈援呈三角形,这正是蜀式戈最具特色之处。这种形制的蜀式戈,起源甚早,商代便已开始流行,而在滇文化中出现的年代是在战国早、中期。并且,滇文化青铜戈上的“太阳纹”或“人形纹”,在蜀戈上也是早已有之。固然,滇文化无胡戈具有自身的风格特点,也都制作于当地,但显然在它的发展演变中受到了蜀式戈的重要影响,这与商周时期古蜀王国对南中的文化和政治扩张有关。①
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年代较早,原因复杂,不过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蜀早于滇进入文明时代。在紧相毗邻的两种文化中,文明的波光总会自然而然地波及文明尚未出现的社会,这是文化史上的规律。
然而,绝大多数文化交流总是互动的、双向的,巴蜀文化与滇文化的青铜文化交流也是如此。晚期巴蜀青铜文化中常见各种形式的异形钺,就明显地受到滇文化的影响。滇文化常见的尖嘴式青铜锄,近年在成都市也有发现,表明滇文化中的精华,同样被蜀文化加以吸收采借。
云南自古富产铜矿、锡矿。早在商代,中原商王朝就已经大量地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青铜器制作的原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部分青铜器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取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②金正耀教授的研究成果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③蜀与滇相紧邻,蜀地固然有其铜矿,但商代开采不多,而锡却必须仰给于蜀境以外。除了东方的长江中游地区可能是蜀国青铜矿料的供应地之一外,云南的铜矿、锡矿,当是古蜀王国青铜原料的最大来源。据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三星堆青铜器中所含铅,就是取之于云南的。古蜀国青铜器合金成分与滇文化青铜器比较接近,显然与其矿产地和矿料来源有关。蜀、滇两地都曾使用贝币,为大宗的金锡交易提供了相同的等价物,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④可见,滇文化对巴蜀青铜文化的发展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积极作用不可低估。
(二)古蜀与南中
南中主要指四川凉山州和云南等地。在南中广袤的土地上,很早便有蜀文化的足迹。西汉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引《谱记》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历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唐时姚、巂二州分别治今云南姚安和四川西昌,均属古代南中地域范围。这说明,蚕丛后世中的某些支系,曾长期活动在南中地区,从先秦到汉代,未曾断绝,并且成为当地的土著先民之一。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周时代①,“(蜀王)杜宇称帝..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园苑即指势力范围;《华阳国志·蜀志》又说南中“有蜀王兵栏”,兵栏实指武库。这就意味着,包括滇池区域在内的南中地区,都受到了古蜀的文化和政治影响。方国瑜认为,南中是蜀的附庸②,是有根据的。到战国晚期,蜀王后世选择南中为避难生息之地,便与其先王同南中的政治与文化联系有关。《水经·叶榆水注》所载蜀王子安阳王南迁的史迹,便确切反映了这种关系。
南中的古代居民,《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是“盖夷、越之地”,而滇人又是“滇濮”或“滇越”,即滇地之濮或滇地之越。濮、越属于一个大的民族系统。在南中地区,随处可见濮人的风俗民情,比如干栏式建筑,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上,便有这类图像。这与蜀文化居民居干栏的风俗十分相近,而西周以后蜀文化的主体民族之一,便是濮人。③
百濮民族多居水边,长于操舟。巴蜀文化的船棺葬,是主人生前交通的主要工具。巴蜀青铜器上,也常见操舟作战等图像。滇文化的居民也长于操舟,青铜器上有不少这类图像。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铜鼓上的船纹,就是一种竞渡船。
云南古代曾大量使用贝币,这些贝币主要来源于印度洋,不是云南土产。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白色海贝,背部穿孔,为齿贝,也来源于印度洋,显然是经由南中地区获取的。
古蜀文化与滇文化在政治上的最相近似之处,是它们都不用鼎象征王权、神权和经济特权,两者的国家政权象征系统,都是杖。广汉三星堆商代蜀文化的金杖和滇文化出土的大量杖首,形制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以杖来标志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文化内涵却完全一致。从年代早晚进行时空对照,滇文化的这种风习当与古蜀文化的南传有关。而这种文化的南传,也正与史籍所述古蜀对南中的政治和文化扩张相一致,绝不是偶然的。
(三)古蜀与南方丝绸之路
先秦时代,由于蜀、滇以及两者对外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蜀入滇,经南中西出中国至缅、印的陆上国际交通线便初步开辟出来。蜀文化与滇文化的联系,蜀王后世从蜀至滇,蜀文化从南亚、中亚以至西亚引进而入的某些文化因素,都是经由这条道路往来进行的。这条国际商道,学术界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经今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西折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南行至今乐山、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两道在大理会为一道,又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八莫,跨入外域。
另外还有一条从蜀入滇至外域的国际交通线,在蜀文化与滇文化以及缅、印文化和越南北部红河地区的文化交流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条国际线路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从缅甸八莫至印度阿萨姆地区,这条道路其实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延伸。中路是一条水路,利用红河下航越南,水陆分程的起点为步头。《蛮书》卷6载:“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从云南通海北至晋宁,再北至昆明,即步入滇、蜀之间的五尺道,可直抵成都。东路,从蜀入滇,至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隅,经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清水河),直抵河内。
从云南至西亚的交通线,则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这是历史上的“蜀身毒道”,又称为“滇缅道”。再由中亚入西亚,就不困难了。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
以上从蜀入滇再分别伸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西亚的国际交通线,早在先秦时代已初步开通。蜀、滇之间的五尺道,《史记》记为秦时才开辟的官道,但《汉书》则记为秦以前开通,秦代仅为“常破”而整修。其实早在殷周之际,杜宇即从这条道路从朱提(云南昭通)北上入蜀,立为蜀王。从蜀至云南昆明,南行至通海之南的步头,下红河,入越南的水陆通道,是战国末蜀王子安阳王率众三万人南人交趾、雄长北越的通道。从蜀至滇,西行出八莫,人缅、印,经巴基斯坦至中亚,再抵西亚的远程国际线路,近年来也以蜀文化和滇文化中的中亚、西亚文物或风格近似的文化因素的大量发现,证明早在商代已初步开辟,到春秋战国时代则更加繁荣。
由这些线路所共同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起点均在成都,均由成都南行至南中,再分别伸入外域。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蜀与中国以外其他文明地区的交流传播历史悠远,另一方面则说明蜀与南中各地保有持久而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联系。由此也可看出,古代蜀文化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它是致使古蜀文明形成为一个拥有世界文明特点的重要原因。
二、巴蜀文化与东南亚文明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与东南亚就发生了若干文化联系。在相互间的各种交往中,中国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而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受到中国影响的某些重要因素,其发源地或表现得相当集中的地区,
就是古代巴蜀,云南则是传播的重要通道。
(一)巴蜀文化南传东南亚的几点原因
据童恩正先生研究,古代东南亚的若干文化因素来源于巴蜀,大致有:农作物中的粟米种植,葬俗中的岩葬、船棺葬、石棺葬,大石文化遗迹,以及一些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等等。①巴蜀文化的若干因素向南传播并影响到东南亚相关文化的发生、发展,绝非偶然,它导源于地理的、民族的、历史的各种因素。
东南亚地区分为几个部分,除海岛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是同东亚大陆连为一体的。它们与中国大陆,地域与共,江河相通,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地理条件的优越性,为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中国南方青铜时代中,最有可能实现同东南亚文化交往的地区是云南。可是云南青铜文化发生较迟,不足以给东南亚以太大的影响。紧邻云南北部的巴蜀地区,则不仅青铜文化发祥很早,而且十分辉煌灿烂,辐射力也相当强劲。巴蜀青铜时代不仅青铜文化,而且其他方面的若干因素也很发达,优于南面的滇文化。滇国青铜时代从巴蜀文化中采借吸收了若干因素,就是很好的证据。在这种情形下,巴蜀文化通过滇文化及其再往南面的交流孔道,南向传播于东南亚地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是完全可能的。而上文所列的若干证据,则说明了这种可能性完完全全是历史事实。当然,巴蜀文化向东南亚的传播,传播方式有所不同,有的是直接传播,有的是间接传播,不可一概而论。
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考古学材料证明,两地的古代民族存在若干共性,有着某种共同的渊源关系。云南南部的古代民族,从史籍记述可见,属于百越或百濮系统。而古代巴蜀地区各族中,百濮民族系统为其荦荦大者。民族源流的相近,民风民俗的相类,无疑是文化联系的有利条件,使得较进步的文化容易向较后进的文化进行播染,这在文化史上是不变的规律。
在古代,国界的概念往往并不十分清晰,尤其对于民间来说,所认定的界限主要不是国界,而是民族,是文化认同。所以,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东南亚这一大片广阔的空间内,巴蜀文化若干因素的连续分布是一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对其诸多原因,由于资料的限制,当前还不能够给予一一判明。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更多的地下材料重见天日。
(二)蜀王子安阳王的南迁
在巴蜀文化对东南亚的直接传播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国末蜀王子安阳王的南迁,和在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王朝的历史事件。
公元前4世纪末叶蜀亡于秦后,蜀王的群公子大多降秦,先后封于蜀,贬为蜀侯。然而号为安阳王的蜀王子并未降秦,他率其部众辗转南迁至交趾之地,称雄数代,达百余年之久。
在《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以及其他一些史籍中,保存了蜀王子安阳王南迁的珍贵史料。《交州外域记》记载道:
交趾(按:指今越南北部红河地区)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绥。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眉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晋大康地记》县属交趾。越遂服诸雒将。……
据越籍《大越史记》、《安南志略》、《越史略》诸书所说,蜀王子安阳王名泮,巴蜀人。他显然就是蜀王开明氏后代。
蜀王子安阳王从蜀人越的路线,是沿南方丝绸之路的旄牛道,南下至今四川凉山州西昌后,再出云南的仆水(今礼社江)、劳水(今元江),抵红河地区,即古交趾之地。安阳王在北越地区的治所,据越南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在今河内正北,桥江之南的永福省东英县古螺村。
安阳王在红河地区建立的王朝,前后维持了大约130年,公元前180年为南越王赵佗所灭。这时,上距安阳王初入北越,已不止一两代人。
据蒙文通先生研究,安阳王率兵三万人讨雒王,其实是一支民族的大迁徙,当中不胜兵者不下三万,如此,南迁的蜀人略有六万,同当地雒越民族九万人的比例为2∶3。这表明,南迁的蜀人对于后世越南民族的形成,关系至为重大。越南旧史尊称蜀泮为“蜀朝”,蜀泮在越南民间长期享有崇高威望,不是偶然的。①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安阳王入越也是文化传播与融化的一种最典型的事例。
蜀王子安阳王入越的历史,在考古学上可以找到若干例证。川、滇之间许多地点曾发现巴蜀墓葬和文物,年代为战国晚期,它们正是安阳王所率蜀人南迁时所遗留。北越东山文化中的无胡式青铜戈,同安阳王入越的年代相一致,恰好证实了安阳王征服当地雒王、雒侯、雒将,建立蜀朝的史实。考古学证据同文献记载的一致性,充分表明了古蜀文化对越南东山文化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三、巴蜀文化与南亚文明
以古蜀文明为重心的中国西南文化,同印巴次大陆之间,早有交流道路可通。由蜀入滇,经缅甸达于印度、巴基斯坦的“蜀身毒(印度)道”,是沟通其间各种联系的主要通道。这条线路在殷商时代就已初步开辟,到战国时代愈益发挥出重要作用。
(一)三星堆文化与南亚文明
三星堆文化是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复合型文明。在它的非土著文化因素中,南亚文明因素颇为引人注目。①
在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海贝中,有一种齿货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中间有齿形沟槽,这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显然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入的。据史载,印度地区自古富产齿贝,当地居民交易常用齿贝为货币。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齿贝,大多数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以便于串系,用作货币进行交易。这种用贝币作为商品交换等价物的情形,同南亚次大陆和古代南中,以及商周贝币的功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中国西南地区出土来自于印度洋的海贝之地,并不只有三星堆一处,在云南大理、禄丰、昆明、晋宁、楚雄、曲靖以及四川凉山、茂县等地多有发现。这些地区没有一处出产海贝,都是从印度地区引入的。把这些出土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恰是中国西南与古印度地区的陆上交通线——蜀身毒道,亦即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这表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相当于商代中期),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之间已有了文化交流关系。
饶有兴味的是,在三星堆还出土不少青铜制的海洋生物雕像,全部用平雕方法制成。虽然这些青铜制品多已锈蚀,但仍可清楚地分辨出数枚铜贝和其他海洋生物形象。假如古蜀人没有亲临印度洋地区并在那里获得深刻的海洋生物印象和丰富的知识,就绝不可能制作出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雕像来。这表明,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冲出狭隘的内陆盆地,走向蔚蓝的海洋,并以主动积极、朝气蓬勃的意气和姿态,迎接了来自印度洋的文明因素的碰撞。这比起汉文史书的记载,足足早出了一千多年。
此外,三星堆城市文明、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从而可知,早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经由中国西南出缅甸至印度、巴基斯坦的广阔空间内,存在着一条绵亘万里的经济文化交流纽带,它的一头向着中亚和西亚乃至欧洲大陆延伸,另一头向着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延伸;而这条纽带的中心或枢纽,正是地处横断山脉东侧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古蜀地。
(二)“支那”与成都
“支那”(Cina)是古代印度地区对中国的称呼,最初见于梵文,出现年代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过去人们通常以为,支那一词指的是秦国,或者楚国,很少有人把这个名称同成都联系在一起。
指认支那为秦国或楚国,其实是没有什么可靠的材料为依据的。从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iot)以为,支那是印度对秦始皇所建立的秦王朝的称呼。但是秦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21年,而支那名称在印度的出现却可早到公元前4世纪,可见伯希和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有的学者以为,支那是印度对春秋时代秦国的称呼,由于秦国的屡代赫赫武功,使秦的国名远播西方。但是,春秋时代秦对陇西、北地诸戎并没有形成霸权,秦穆公虽然“开地千里,并国十二”,却得而复失,仅有三百里之地。①而且,诸戎从西、北、东三面形成对秦的重重包围,阻隔着秦的北上西进道路,秦不能越西戎一步,何谈将其声威远播西方?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秦在西北地区才最终获胜,而此时“支那”一名早已在印度出现。显然,支那名称的起源与秦国无关。至于指认支那为荆,由于其立论基础不可靠,同样难以成立。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古蜀文化从商代以来就对南中地区保有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已同印度地区存在以贝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和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这就为古蜀名称远播于古印度提供了条件。另据《史记》和《汉书》,蜀人商贾很早就“南贾滇、僰僮”,并进一步到达“滇越”从事贸易,还到身毒销售蜀布、邛竹杖等蜀物。滇越,即今天东印度阿萨姆地区①,身毒即印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古籍《政事论》也提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所说蚕丝和织皮纽带恰是蜀地的特产。表明了战国时期蜀人在印度频繁的贸易活动,而这又是同商代以来三星堆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流一脉相承的。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印度必然会对古蜀产生较之中国其他地区更多的印象和认识,对于古蜀的名称也绝不会不知道。
成都这个名称,产生很早,已于见《山海经》,春秋时期的四川荥经曾家沟漆器上还刻有“成造”(成都制造)的烙印戳记。“成”这个字,过去学者按中原中心论模式,用北方话来复原它的古音,以为是耕部禅纽字。但是,从南方语音来考虑,它却是真部从纽字,读音正是“支”。按照西方语言的双音节来读,也就读作“支那”。这表明,支那其实是成都的对音。②
梵语里的Cina,在古伊朗语、波斯语、粟特语以及古希腊语里的相对字③均与“成”的古音相同,证实Cina的确是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他地,区的相对字则均与成都的转生语Cina同源。从语音研究上看,这是应有的结论。而其他诸种语言里支那一词的相对字都从梵语Cina转生而去,也恰同成都丝绸经印度播至其他西方文明区的传播方向一致,则从历史方面对此给予了证实。因此,从历史研究上看,支那一词源出成都,也是应有的结论。
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这个湮没已久并一再为人误解的事实,揭示出中国西南在早期中西交通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证明以巴蜀为重心的中国西南古代文明曾经对包括东西方在内的世界古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当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四、巴蜀文化与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
近东,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大致包括西亚、中亚和埃及,也部分地包括爱琴海诸岛。①古代近东文明,主要指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②欧洲古代文明,是指继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希腊、罗马文明,也称欧洲古典文明。由于以欧洲大陆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中有若干因素渊源于近东文明,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也把近东文明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研究。③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联系和交流,在中国史籍里出现较晚,到两汉才见诸记载,但从考古资料分析,其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却要早得多,在先秦时期即已颇见端倪。当时中国与近东的文化联系有三条主要线路:一条是经河西走廊西行出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一条是经北方草原西行的草原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从成都南行经云南至印度再至中亚和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考古学证据表明,巴蜀文化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纪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就是经由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④
(一)三星堆文化与近东文明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在巴蜀本土也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不仅如此,即令在殷商时代的全中国范围内,同样也是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的。
那么,这类文化形式究竟从何而来呢?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所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这三个证据,就是前面提到的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
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开始形成了青铜雕像文化传统。在乌尔(Ur),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青铜人头像。①在尼尼微(Nineveh),发现了阿卡德·萨尔贡一世(Sargon1ofAkkad,2800B.C.)的大型青铜人头雕像②小型工人全身雕像③还出土各种
青铜人物和动物雕像。④在埃及,1896,年发现了古王国第六,王朝法老佩比一世(PepiI,2200B.C)及其子的大小两件一组的全身青铜雕像。⑤古埃及文献所载这类雕像,其铸造年代还可早到公元前2900年。⑥中王国以后,埃及利用青铜制作各类雕像的风气愈益普遍,在卡纳克(Karnak)遗址就曾发现大量青铜雕像残片。在印度河文明中,摩亨佐·达罗城址(CitySiteofMohenjo-daro2500~2000or
1750B.C)也发现了若干青铜雕像,包括人物雕像、动物,雕像和青铜车,其中以一件戴着手镯臂钏的青铜舞女雕像驰名于世。权杖起源于西亚欧贝德文化第4期(UbaidⅣ),年代约为公元前
四千年代前半叶。⑦在以色列的比尔谢巴(Beersheba)发现了公元前3300年的铜权杖首,在死海西岸以南恩格迪(Engedi)的,一个洞穴窖藏中发现铜权杖首240枚、杖首80枚。⑧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用权杖标志神权和王权的传统,在当时的石刻、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品中
比比可见。
古埃及也有权杖传统,早王朝初期埃及文字中的形,便是权杖的象形。①埃及考古中发现过大量各式权杖,既有黄金的,也有青铜的,有学者认为与西亚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关系。后来全世界许多文化都用权杖标志权力,其最初根源即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至于黄金面罩,西亚乌鲁克(Uruk)文化时期娜娜女神庙出土的大理石头像,据说曾复以金箔或铜箔。叙利亚毕布勒神庙地面下发现的一尊青铜雕像,亦覆盖着金箔。②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都饰以金箔,如乌尔王陵中的牛头竖琴,牛头即以金箔包卷而成③,另外的几尊金公牛雕像也以1/2~2毫米的金箔包卷。埃及的黄金面罩,最著名的是图坦哈蒙王陵内发现的葬殓面具。迈锡尼文明中也屡见覆盖在死者头部的黄金面罩,有学者指出这种文化并非当地的文化形式,是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④
从青铜雕像、权杖、金面罩以及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上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的集结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这一点早为国际文化史学界所公认。
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在雕像人物面部形态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中除开那些西南夷的形象外,高鼻、深目的若干面部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类人物,阔眉、杏叶大眼,颧骨低平,高鼻梁,挺直的鼻尖,大嘴两角下勾,下颌一道直达双耳后面的胡须。这些面部特征,与同出的各式西南夷形象以及华北、长江中下游商周之际的各种人面像明显不同,也与成都指挥街发现的华南人扁宽鼻型的人头骨不同。很明显,如此风格的人物面部形态造型,来源于外域文化。
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的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缺乏动感和变化,尤其是双眉入鬓,眼睛大睁,在整个面部处于突出地位,这同西亚雕像艺术的风格十分接近。眼睛的艺术处理,多在脸孔平面上铸成较浅的浮雕,以突出的双眉和下眼眶来显示其深目,这也是西亚雕像常见的艺术手法。对于人物雕像的现实主义和对神祇雕像的夸张表现,也同西亚近东早、中期的艺术特点有相近之处。而对于神树的崇拜,则反映了这种文化形式从近东向南连续分布的情景。
在功能体系上,不论西亚、埃及还是爱琴海文明中的青铜雕像群,大多出于神庙和王陵,普遍属于礼器,起着祭祀和纪念的作用。三星堆雕像群也出于祭祀坑内,无一不是礼器,无一不具宗教礼仪功能。它们与近东雕像的意义完全相同,如出一辙,而与华北所出雕像主要充作装饰的情况相去甚远。至于用金杖代表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特权,就更与华北用“九鼎”代表这些权力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而与近东文明却完全一致。
三星堆青铜雕像、金杖、金面罩与近东文明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说明,古蜀文明是一个善于开放、容纳、改造和多元、多方位地对待世界文化的古文明,是一个富于世界特征的古文明。
(二)“瑟瑟”来路觅踪
唐代诗圣杜甫寓居成都时,曾写过一首《石笋行》诗,诗中说道: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是恐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尚存……
杜工部的疑问,导出了一个千古之谜:“瑟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
原来,瑟瑟(sit-sit)是古代波斯的宝石名称,是示格南语或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中国古书关于瑟瑟的性质有不同说法,主要指宝石,又称“真珠”,明以后主要指人工制造的有色玻璃珠或烧料珠之类。①唐时成都西门一带,先秦曾是蜀王国墓区所在,近年不断发现大批墓葬。杜甫说这里雨多往往得瑟瑟,足见当年随葬之多,又足见蜀人佩戴这种瑟瑟串珠之普遍。既称瑟瑟,当然就是来自于中亚、西亚地区,并且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而来。
杜甫提出的疑问,曾经有人试为之解,宋人吴曾就是其中之一。他说:
杜《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遭火,烧数千家,楼亦以烬。今人往往于砂土上获真珠。又赵清献《蜀郡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今谓石笋非为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盖大秦国多谬琳琅歼,明珠夜光碧,水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②
按照吴曾的看法,杜甫所说石笋街大雨冲刷出来的瑟瑟,不是蜀王国公卿将相墓中的随葬品,也不是开明氏七宝楼真珠帘坠散后的遗存,而是大秦寺门楼珠帘摧毁后坠地所遗。他的说法有一定根据,但同杜甫之说实为两事,不能混为一谈。
据李膺《成都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珍珠为帘,其后蜀郡火,民家数千与七宝楼俱毁。”③《通志》:“双石笋在兴义门内,即真珠楼基也。”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2:“西门,王建武成谓之兴义门矣。”据此,真珠楼与杜甫所说石笋不在一处,真珠楼在西门内,石笋街则在西门外。况且,石笋既为蜀王开明氏墓志,开明王又如何可能以此为楼基?可见吴曾驳杜甫,是“以其昏昏,令人昭昭”,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大秦国胡人曾在真珠楼故地立寺,倒是事实,《蜀中名胜记》引赵清献之说,也提到此事。大秦,是中国古代对古罗马帝国的称呼,①其国多出各种真珠、琉璃、谬琳、琅歼等宝物,“又有水道通益州”,早与蜀文化有交流往来,其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几个世纪。至于成都出土的古罗马瑟瑟,由大秦寺的建立可知,则为唐朝时。
上面征引的各种文献还说明,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为帘。这真珠大概也属瑟瑟一类“舶”来品,原产于西亚和中亚。
这些古代诗文和史籍记载的在成都发现的瑟瑟,数量如此之多,说明古巴蜀与中亚、西亚有着大量的经济文化往来。
除了瑟瑟之外,古代巴蜀还从西亚地区输入琉璃珠和蚀花肉红石髓珠。从1978在重庆发现的两颗蚀花琉璃珠的形态和纹饰看,极似于西亚的早期同类品。在茂县的早期石棺葬中,曾出土产于西亚的不含钡的钙钠玻璃。在理塘县,也曾发现琉璃珠。而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亦出土西亚的早期肉红蚀花石髓珠和琉璃珠②。在云南昭通发掘的巴蜀墓葬内也出土有蚀花石髓珠。巴蜀和滇文化地区西亚石髓珠和琉璃珠的发现,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
蚀花肉红石髓珠和不含钡的钙钠玻璃(琉璃)原产地均在西亚,有悠久的历史,后来传播于中亚和印度河地区。这些人工宝石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一般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从西亚、中亚到南亚再到中国西南这一广阔的连续空间内,出现的文化因素连续分布现象,恰好表明一条文化交流纽带的存在。这条纽带,就是南方丝绸之路。
巴蜀文化中的西亚因素,便是通过这条古老的文化纽带而来的。①
(三)巴蜀丝绸的西传
巴蜀丝绸织锦,自古称奇。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蜀锦的生产年代很早,大约在商周时代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②
西方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蜀国生产的丝。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力丝”(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据考证,Seres是指古代蜀国。③《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古罗马)“又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以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有可能就是以蜀丝加工为胡绫再出口于波斯的。考古学家曾于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亚历山大城(约建成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时,在一处城堡中发现许多中国丝绸。④考虑到西汉前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及剽悍的月氏曾多次遮断了沿河西走廊西行的“丝绸之路”,那么这些丝绸(至少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从成都经滇缅道运至印巴次大陆,再到达中亚的。⑤这些说明,古代巴蜀的丝绸对于西方古典文明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西域西行至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古代进行的大宗丝绸贸易中,也有不少巴蜀织锦。不久前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中发现的大批精美丝织品,其中便有驰名中外的蜀锦,从南北朝到唐代的无不俱备⑥,表明蜀锦是西域丝绸贸易的主要品种之一。再从战国时代蜀锦已远销楚国的两湖地区,并饮誉于希腊、罗马的情况来看,西汉时蜀锦也应是内地同西域诸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古代巴蜀丝绸文化的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并使南方丝绸之路向欧洲延伸。从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巴蜀文化是一个开放型的文化体系,对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外文献、考古和人类学资料的分析,对大量相关文化因素及其组合方式和演变关系等进行比较,初步揭示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供学术界同行参考。
一、巴蜀文化与滇文化
滇文化是分布在云南东部地区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地方文化,其创造者为滇人。滇文化的年代,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学材料,上限约在公元前5世纪,下限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相续400余年。
史书有关滇文化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言之极为简略。《华阳国志·南中志》对滇文化的记载,也是语焉未详。由于史籍的阙如,前人总以滇王国为蛮荒之国,滇人为后进民族,而滇文化也还徘徊在文明之外。可是,历史事实却完全相反。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滇文化原来是一支灿烂的青铜文化,它具有极为发达的青铜器农业,进步的青铜器手工业,有着异常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它不仅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占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而且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支青铜文化相媲美。
(一)青铜文化的交流遗迹
不论从考古学还是历史文献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青铜文化,诞生年代较之滇文化古远,持续时期也比滇池区域青铜文化长久。固然这两种青铜文化各有优长之处,互有影响,但成都平原青铜文化较早地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却是考古学上的事实。
20世纪50~90年代先后发掘的滇文化墓葬——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群中,有较为明显的成都平原早、中期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晋宁在汉代是滇池县,为故滇国之所在。①这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铸有若干人物和动物的立雕像。这类风格完全不同于华北和楚文化,却与三星堆青铜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造型艺术也较接近。
晋宁石寨山青铜雕像人物中,有椎髻、辫发、穿耳等各种形式,与三星堆青铜雕像人物不乏某些共同之点。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长方形铜片上刻画的符号当中,有一柄短杖的图像,杖身有四个人首纹。这种杖,虽无实物发现,但杖首铜饰在滇文化中却是一突出特点,表明曾经有过发达的用杖制度。有学者认为上刻四个人首纹的杖,可能是某种宗教用物或代表权力的节杖。①这种用杖之制与三星堆青铜文化中的金杖极其相似,而且杖身刻画人首纹,也正是三星堆金杖的显著特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铜鼓,上刻伎乐图像,其中的人、鱼、鸟图像,也与三星堆金杖图案以人、鱼、鸟为主题相同。从蜀、滇相邻,民族、民俗有若干近似等情况出发,两地青铜文化的近似,自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完全有文化交流传播的可能。三星堆青铜文化早于滇文化,滇文化从蜀文化中采借了这些文化因素,并不是没有可能。②
滇文化青铜兵器也有浓厚的蜀文化色彩。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都发现了无格式青铜剑,这种剑与巴蜀式扁茎无格柳叶形青铜剑相比,主要区别仅在于滇式无格剑为圆茎,巴蜀式剑则为扁茎,两种剑实际上属于同一风格,没有本质区别。滇文化的无格式剑与巴蜀文化,显然存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关系。③滇文化的青铜戈,最大特点是以无胡戈为主,占总数的3/4以上,这一特点与蜀文化也很近似。其基本形制只有四种,除前锋平齐的一种外,都是戈援呈三角形,这正是蜀式戈最具特色之处。这种形制的蜀式戈,起源甚早,商代便已开始流行,而在滇文化中出现的年代是在战国早、中期。并且,滇文化青铜戈上的“太阳纹”或“人形纹”,在蜀戈上也是早已有之。固然,滇文化无胡戈具有自身的风格特点,也都制作于当地,但显然在它的发展演变中受到了蜀式戈的重要影响,这与商周时期古蜀王国对南中的文化和政治扩张有关。①
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年代较早,原因复杂,不过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蜀早于滇进入文明时代。在紧相毗邻的两种文化中,文明的波光总会自然而然地波及文明尚未出现的社会,这是文化史上的规律。
然而,绝大多数文化交流总是互动的、双向的,巴蜀文化与滇文化的青铜文化交流也是如此。晚期巴蜀青铜文化中常见各种形式的异形钺,就明显地受到滇文化的影响。滇文化常见的尖嘴式青铜锄,近年在成都市也有发现,表明滇文化中的精华,同样被蜀文化加以吸收采借。
云南自古富产铜矿、锡矿。早在商代,中原商王朝就已经大量地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青铜器制作的原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部分青铜器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取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②金正耀教授的研究成果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③蜀与滇相紧邻,蜀地固然有其铜矿,但商代开采不多,而锡却必须仰给于蜀境以外。除了东方的长江中游地区可能是蜀国青铜矿料的供应地之一外,云南的铜矿、锡矿,当是古蜀王国青铜原料的最大来源。据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三星堆青铜器中所含铅,就是取之于云南的。古蜀国青铜器合金成分与滇文化青铜器比较接近,显然与其矿产地和矿料来源有关。蜀、滇两地都曾使用贝币,为大宗的金锡交易提供了相同的等价物,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④可见,滇文化对巴蜀青铜文化的发展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积极作用不可低估。
(二)古蜀与南中
南中主要指四川凉山州和云南等地。在南中广袤的土地上,很早便有蜀文化的足迹。西汉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引《谱记》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历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唐时姚、巂二州分别治今云南姚安和四川西昌,均属古代南中地域范围。这说明,蚕丛后世中的某些支系,曾长期活动在南中地区,从先秦到汉代,未曾断绝,并且成为当地的土著先民之一。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周时代①,“(蜀王)杜宇称帝..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园苑即指势力范围;《华阳国志·蜀志》又说南中“有蜀王兵栏”,兵栏实指武库。这就意味着,包括滇池区域在内的南中地区,都受到了古蜀的文化和政治影响。方国瑜认为,南中是蜀的附庸②,是有根据的。到战国晚期,蜀王后世选择南中为避难生息之地,便与其先王同南中的政治与文化联系有关。《水经·叶榆水注》所载蜀王子安阳王南迁的史迹,便确切反映了这种关系。
南中的古代居民,《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是“盖夷、越之地”,而滇人又是“滇濮”或“滇越”,即滇地之濮或滇地之越。濮、越属于一个大的民族系统。在南中地区,随处可见濮人的风俗民情,比如干栏式建筑,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上,便有这类图像。这与蜀文化居民居干栏的风俗十分相近,而西周以后蜀文化的主体民族之一,便是濮人。③
百濮民族多居水边,长于操舟。巴蜀文化的船棺葬,是主人生前交通的主要工具。巴蜀青铜器上,也常见操舟作战等图像。滇文化的居民也长于操舟,青铜器上有不少这类图像。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铜鼓上的船纹,就是一种竞渡船。
云南古代曾大量使用贝币,这些贝币主要来源于印度洋,不是云南土产。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白色海贝,背部穿孔,为齿贝,也来源于印度洋,显然是经由南中地区获取的。
古蜀文化与滇文化在政治上的最相近似之处,是它们都不用鼎象征王权、神权和经济特权,两者的国家政权象征系统,都是杖。广汉三星堆商代蜀文化的金杖和滇文化出土的大量杖首,形制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以杖来标志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文化内涵却完全一致。从年代早晚进行时空对照,滇文化的这种风习当与古蜀文化的南传有关。而这种文化的南传,也正与史籍所述古蜀对南中的政治和文化扩张相一致,绝不是偶然的。
(三)古蜀与南方丝绸之路
先秦时代,由于蜀、滇以及两者对外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蜀入滇,经南中西出中国至缅、印的陆上国际交通线便初步开辟出来。蜀文化与滇文化的联系,蜀王后世从蜀至滇,蜀文化从南亚、中亚以至西亚引进而入的某些文化因素,都是经由这条道路往来进行的。这条国际商道,学术界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经今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西折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南行至今乐山、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两道在大理会为一道,又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八莫,跨入外域。
另外还有一条从蜀入滇至外域的国际交通线,在蜀文化与滇文化以及缅、印文化和越南北部红河地区的文化交流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条国际线路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从缅甸八莫至印度阿萨姆地区,这条道路其实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延伸。中路是一条水路,利用红河下航越南,水陆分程的起点为步头。《蛮书》卷6载:“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从云南通海北至晋宁,再北至昆明,即步入滇、蜀之间的五尺道,可直抵成都。东路,从蜀入滇,至昆明,经弥勒,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隅,经河江、宣光,循盘龙江(清水河),直抵河内。
从云南至西亚的交通线,则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这是历史上的“蜀身毒道”,又称为“滇缅道”。再由中亚入西亚,就不困难了。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
以上从蜀入滇再分别伸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西亚的国际交通线,早在先秦时代已初步开通。蜀、滇之间的五尺道,《史记》记为秦时才开辟的官道,但《汉书》则记为秦以前开通,秦代仅为“常破”而整修。其实早在殷周之际,杜宇即从这条道路从朱提(云南昭通)北上入蜀,立为蜀王。从蜀至云南昆明,南行至通海之南的步头,下红河,入越南的水陆通道,是战国末蜀王子安阳王率众三万人南人交趾、雄长北越的通道。从蜀至滇,西行出八莫,人缅、印,经巴基斯坦至中亚,再抵西亚的远程国际线路,近年来也以蜀文化和滇文化中的中亚、西亚文物或风格近似的文化因素的大量发现,证明早在商代已初步开辟,到春秋战国时代则更加繁荣。
由这些线路所共同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起点均在成都,均由成都南行至南中,再分别伸入外域。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蜀与中国以外其他文明地区的交流传播历史悠远,另一方面则说明蜀与南中各地保有持久而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联系。由此也可看出,古代蜀文化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它是致使古蜀文明形成为一个拥有世界文明特点的重要原因。
二、巴蜀文化与东南亚文明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与东南亚就发生了若干文化联系。在相互间的各种交往中,中国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而东南亚古文化中明显受到中国影响的某些重要因素,其发源地或表现得相当集中的地区,
就是古代巴蜀,云南则是传播的重要通道。
(一)巴蜀文化南传东南亚的几点原因
据童恩正先生研究,古代东南亚的若干文化因素来源于巴蜀,大致有:农作物中的粟米种植,葬俗中的岩葬、船棺葬、石棺葬,大石文化遗迹,以及一些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等等。①巴蜀文化的若干因素向南传播并影响到东南亚相关文化的发生、发展,绝非偶然,它导源于地理的、民族的、历史的各种因素。
东南亚地区分为几个部分,除海岛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是同东亚大陆连为一体的。它们与中国大陆,地域与共,江河相通,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地理条件的优越性,为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中国南方青铜时代中,最有可能实现同东南亚文化交往的地区是云南。可是云南青铜文化发生较迟,不足以给东南亚以太大的影响。紧邻云南北部的巴蜀地区,则不仅青铜文化发祥很早,而且十分辉煌灿烂,辐射力也相当强劲。巴蜀青铜时代不仅青铜文化,而且其他方面的若干因素也很发达,优于南面的滇文化。滇国青铜时代从巴蜀文化中采借吸收了若干因素,就是很好的证据。在这种情形下,巴蜀文化通过滇文化及其再往南面的交流孔道,南向传播于东南亚地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是完全可能的。而上文所列的若干证据,则说明了这种可能性完完全全是历史事实。当然,巴蜀文化向东南亚的传播,传播方式有所不同,有的是直接传播,有的是间接传播,不可一概而论。
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考古学材料证明,两地的古代民族存在若干共性,有着某种共同的渊源关系。云南南部的古代民族,从史籍记述可见,属于百越或百濮系统。而古代巴蜀地区各族中,百濮民族系统为其荦荦大者。民族源流的相近,民风民俗的相类,无疑是文化联系的有利条件,使得较进步的文化容易向较后进的文化进行播染,这在文化史上是不变的规律。
在古代,国界的概念往往并不十分清晰,尤其对于民间来说,所认定的界限主要不是国界,而是民族,是文化认同。所以,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东南亚这一大片广阔的空间内,巴蜀文化若干因素的连续分布是一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对其诸多原因,由于资料的限制,当前还不能够给予一一判明。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更多的地下材料重见天日。
(二)蜀王子安阳王的南迁
在巴蜀文化对东南亚的直接传播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国末蜀王子安阳王的南迁,和在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王朝的历史事件。
公元前4世纪末叶蜀亡于秦后,蜀王的群公子大多降秦,先后封于蜀,贬为蜀侯。然而号为安阳王的蜀王子并未降秦,他率其部众辗转南迁至交趾之地,称雄数代,达百余年之久。
在《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以及其他一些史籍中,保存了蜀王子安阳王南迁的珍贵史料。《交州外域记》记载道:
交趾(按:指今越南北部红河地区)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绥。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眉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晋大康地记》县属交趾。越遂服诸雒将。……
据越籍《大越史记》、《安南志略》、《越史略》诸书所说,蜀王子安阳王名泮,巴蜀人。他显然就是蜀王开明氏后代。
蜀王子安阳王从蜀人越的路线,是沿南方丝绸之路的旄牛道,南下至今四川凉山州西昌后,再出云南的仆水(今礼社江)、劳水(今元江),抵红河地区,即古交趾之地。安阳王在北越地区的治所,据越南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在今河内正北,桥江之南的永福省东英县古螺村。
安阳王在红河地区建立的王朝,前后维持了大约130年,公元前180年为南越王赵佗所灭。这时,上距安阳王初入北越,已不止一两代人。
据蒙文通先生研究,安阳王率兵三万人讨雒王,其实是一支民族的大迁徙,当中不胜兵者不下三万,如此,南迁的蜀人略有六万,同当地雒越民族九万人的比例为2∶3。这表明,南迁的蜀人对于后世越南民族的形成,关系至为重大。越南旧史尊称蜀泮为“蜀朝”,蜀泮在越南民间长期享有崇高威望,不是偶然的。①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安阳王入越也是文化传播与融化的一种最典型的事例。
蜀王子安阳王入越的历史,在考古学上可以找到若干例证。川、滇之间许多地点曾发现巴蜀墓葬和文物,年代为战国晚期,它们正是安阳王所率蜀人南迁时所遗留。北越东山文化中的无胡式青铜戈,同安阳王入越的年代相一致,恰好证实了安阳王征服当地雒王、雒侯、雒将,建立蜀朝的史实。考古学证据同文献记载的一致性,充分表明了古蜀文化对越南东山文化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三、巴蜀文化与南亚文明
以古蜀文明为重心的中国西南文化,同印巴次大陆之间,早有交流道路可通。由蜀入滇,经缅甸达于印度、巴基斯坦的“蜀身毒(印度)道”,是沟通其间各种联系的主要通道。这条线路在殷商时代就已初步开辟,到战国时代愈益发挥出重要作用。
(一)三星堆文化与南亚文明
三星堆文化是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复合型文明。在它的非土著文化因素中,南亚文明因素颇为引人注目。①
在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海贝中,有一种齿货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中间有齿形沟槽,这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显然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入的。据史载,印度地区自古富产齿贝,当地居民交易常用齿贝为货币。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齿贝,大多数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以便于串系,用作货币进行交易。这种用贝币作为商品交换等价物的情形,同南亚次大陆和古代南中,以及商周贝币的功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中国西南地区出土来自于印度洋的海贝之地,并不只有三星堆一处,在云南大理、禄丰、昆明、晋宁、楚雄、曲靖以及四川凉山、茂县等地多有发现。这些地区没有一处出产海贝,都是从印度地区引入的。把这些出土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恰是中国西南与古印度地区的陆上交通线——蜀身毒道,亦即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这表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相当于商代中期),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之间已有了文化交流关系。
饶有兴味的是,在三星堆还出土不少青铜制的海洋生物雕像,全部用平雕方法制成。虽然这些青铜制品多已锈蚀,但仍可清楚地分辨出数枚铜贝和其他海洋生物形象。假如古蜀人没有亲临印度洋地区并在那里获得深刻的海洋生物印象和丰富的知识,就绝不可能制作出如此众多的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雕像来。这表明,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冲出狭隘的内陆盆地,走向蔚蓝的海洋,并以主动积极、朝气蓬勃的意气和姿态,迎接了来自印度洋的文明因素的碰撞。这比起汉文史书的记载,足足早出了一千多年。
此外,三星堆城市文明、人体装饰艺术、神树崇拜,以及象征南亚热带丛林文化的大量象牙,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关系。从而可知,早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经由中国西南出缅甸至印度、巴基斯坦的广阔空间内,存在着一条绵亘万里的经济文化交流纽带,它的一头向着中亚和西亚乃至欧洲大陆延伸,另一头向着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延伸;而这条纽带的中心或枢纽,正是地处横断山脉东侧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古蜀地。
(二)“支那”与成都
“支那”(Cina)是古代印度地区对中国的称呼,最初见于梵文,出现年代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过去人们通常以为,支那一词指的是秦国,或者楚国,很少有人把这个名称同成都联系在一起。
指认支那为秦国或楚国,其实是没有什么可靠的材料为依据的。从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iot)以为,支那是印度对秦始皇所建立的秦王朝的称呼。但是秦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21年,而支那名称在印度的出现却可早到公元前4世纪,可见伯希和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有的学者以为,支那是印度对春秋时代秦国的称呼,由于秦国的屡代赫赫武功,使秦的国名远播西方。但是,春秋时代秦对陇西、北地诸戎并没有形成霸权,秦穆公虽然“开地千里,并国十二”,却得而复失,仅有三百里之地。①而且,诸戎从西、北、东三面形成对秦的重重包围,阻隔着秦的北上西进道路,秦不能越西戎一步,何谈将其声威远播西方?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秦在西北地区才最终获胜,而此时“支那”一名早已在印度出现。显然,支那名称的起源与秦国无关。至于指认支那为荆,由于其立论基础不可靠,同样难以成立。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古蜀文化从商代以来就对南中地区保有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已同印度地区存在以贝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和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这就为古蜀名称远播于古印度提供了条件。另据《史记》和《汉书》,蜀人商贾很早就“南贾滇、僰僮”,并进一步到达“滇越”从事贸易,还到身毒销售蜀布、邛竹杖等蜀物。滇越,即今天东印度阿萨姆地区①,身毒即印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古籍《政事论》也提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所说蚕丝和织皮纽带恰是蜀地的特产。表明了战国时期蜀人在印度频繁的贸易活动,而这又是同商代以来三星堆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流一脉相承的。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印度必然会对古蜀产生较之中国其他地区更多的印象和认识,对于古蜀的名称也绝不会不知道。
成都这个名称,产生很早,已于见《山海经》,春秋时期的四川荥经曾家沟漆器上还刻有“成造”(成都制造)的烙印戳记。“成”这个字,过去学者按中原中心论模式,用北方话来复原它的古音,以为是耕部禅纽字。但是,从南方语音来考虑,它却是真部从纽字,读音正是“支”。按照西方语言的双音节来读,也就读作“支那”。这表明,支那其实是成都的对音。②
梵语里的Cina,在古伊朗语、波斯语、粟特语以及古希腊语里的相对字③均与“成”的古音相同,证实Cina的确是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他地,区的相对字则均与成都的转生语Cina同源。从语音研究上看,这是应有的结论。而其他诸种语言里支那一词的相对字都从梵语Cina转生而去,也恰同成都丝绸经印度播至其他西方文明区的传播方向一致,则从历史方面对此给予了证实。因此,从历史研究上看,支那一词源出成都,也是应有的结论。
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这个湮没已久并一再为人误解的事实,揭示出中国西南在早期中西交通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证明以巴蜀为重心的中国西南古代文明曾经对包括东西方在内的世界古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当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四、巴蜀文化与近东和欧洲古代文明
近东,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大致包括西亚、中亚和埃及,也部分地包括爱琴海诸岛。①古代近东文明,主要指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②欧洲古代文明,是指继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希腊、罗马文明,也称欧洲古典文明。由于以欧洲大陆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中有若干因素渊源于近东文明,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也把近东文明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研究。③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联系和交流,在中国史籍里出现较晚,到两汉才见诸记载,但从考古资料分析,其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却要早得多,在先秦时期即已颇见端倪。当时中国与近东的文化联系有三条主要线路:一条是经河西走廊西行出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一条是经北方草原西行的草原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从成都南行经云南至印度再至中亚和西亚的南方丝绸之路。考古学证据表明,巴蜀文化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纪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就是经由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④
(一)三星堆文化与近东文明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在巴蜀本土也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不仅如此,即令在殷商时代的全中国范围内,同样也是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的。
那么,这类文化形式究竟从何而来呢?考古学上,至少有三个证据所构成的文化丛,可以表明这些文化因素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这三个证据,就是前面提到的青铜人物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
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开始形成了青铜雕像文化传统。在乌尔(Ur),发现了这个时期的青铜人头像。①在尼尼微(Nineveh),发现了阿卡德·萨尔贡一世(Sargon1ofAkkad,2800B.C.)的大型青铜人头雕像②小型工人全身雕像③还出土各种
青铜人物和动物雕像。④在埃及,1896,年发现了古王国第六,王朝法老佩比一世(PepiI,2200B.C)及其子的大小两件一组的全身青铜雕像。⑤古埃及文献所载这类雕像,其铸造年代还可早到公元前2900年。⑥中王国以后,埃及利用青铜制作各类雕像的风气愈益普遍,在卡纳克(Karnak)遗址就曾发现大量青铜雕像残片。在印度河文明中,摩亨佐·达罗城址(CitySiteofMohenjo-daro2500~2000or
1750B.C)也发现了若干青铜雕像,包括人物雕像、动物,雕像和青铜车,其中以一件戴着手镯臂钏的青铜舞女雕像驰名于世。权杖起源于西亚欧贝德文化第4期(UbaidⅣ),年代约为公元前
四千年代前半叶。⑦在以色列的比尔谢巴(Beersheba)发现了公元前3300年的铜权杖首,在死海西岸以南恩格迪(Engedi)的,一个洞穴窖藏中发现铜权杖首240枚、杖首80枚。⑧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用权杖标志神权和王权的传统,在当时的石刻、雕塑和绘画等艺术品中
比比可见。
古埃及也有权杖传统,早王朝初期埃及文字中的形,便是权杖的象形。①埃及考古中发现过大量各式权杖,既有黄金的,也有青铜的,有学者认为与西亚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关系。后来全世界许多文化都用权杖标志权力,其最初根源即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至于黄金面罩,西亚乌鲁克(Uruk)文化时期娜娜女神庙出土的大理石头像,据说曾复以金箔或铜箔。叙利亚毕布勒神庙地面下发现的一尊青铜雕像,亦覆盖着金箔。②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都饰以金箔,如乌尔王陵中的牛头竖琴,牛头即以金箔包卷而成③,另外的几尊金公牛雕像也以1/2~2毫米的金箔包卷。埃及的黄金面罩,最著名的是图坦哈蒙王陵内发现的葬殓面具。迈锡尼文明中也屡见覆盖在死者头部的黄金面罩,有学者指出这种文化并非当地的文化形式,是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④
从青铜雕像、权杖、金面罩以及相关文化因素的起源和发展上看,近东文明这些文化因素的集结相继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具有传播学上的意义,这一点早为国际文化史学界所公认。
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在雕像人物面部形态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中除开那些西南夷的形象外,高鼻、深目的若干面部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类人物,阔眉、杏叶大眼,颧骨低平,高鼻梁,挺直的鼻尖,大嘴两角下勾,下颌一道直达双耳后面的胡须。这些面部特征,与同出的各式西南夷形象以及华北、长江中下游商周之际的各种人面像明显不同,也与成都指挥街发现的华南人扁宽鼻型的人头骨不同。很明显,如此风格的人物面部形态造型,来源于外域文化。
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的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缺乏动感和变化,尤其是双眉入鬓,眼睛大睁,在整个面部处于突出地位,这同西亚雕像艺术的风格十分接近。眼睛的艺术处理,多在脸孔平面上铸成较浅的浮雕,以突出的双眉和下眼眶来显示其深目,这也是西亚雕像常见的艺术手法。对于人物雕像的现实主义和对神祇雕像的夸张表现,也同西亚近东早、中期的艺术特点有相近之处。而对于神树的崇拜,则反映了这种文化形式从近东向南连续分布的情景。
在功能体系上,不论西亚、埃及还是爱琴海文明中的青铜雕像群,大多出于神庙和王陵,普遍属于礼器,起着祭祀和纪念的作用。三星堆雕像群也出于祭祀坑内,无一不是礼器,无一不具宗教礼仪功能。它们与近东雕像的意义完全相同,如出一辙,而与华北所出雕像主要充作装饰的情况相去甚远。至于用金杖代表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特权,就更与华北用“九鼎”代表这些权力的传统有着明显差异,而与近东文明却完全一致。
三星堆青铜雕像、金杖、金面罩与近东文明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说明,古蜀文明是一个善于开放、容纳、改造和多元、多方位地对待世界文化的古文明,是一个富于世界特征的古文明。
(二)“瑟瑟”来路觅踪
唐代诗圣杜甫寓居成都时,曾写过一首《石笋行》诗,诗中说道: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是恐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尚存……
杜工部的疑问,导出了一个千古之谜:“瑟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
原来,瑟瑟(sit-sit)是古代波斯的宝石名称,是示格南语或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中国古书关于瑟瑟的性质有不同说法,主要指宝石,又称“真珠”,明以后主要指人工制造的有色玻璃珠或烧料珠之类。①唐时成都西门一带,先秦曾是蜀王国墓区所在,近年不断发现大批墓葬。杜甫说这里雨多往往得瑟瑟,足见当年随葬之多,又足见蜀人佩戴这种瑟瑟串珠之普遍。既称瑟瑟,当然就是来自于中亚、西亚地区,并且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而来。
杜甫提出的疑问,曾经有人试为之解,宋人吴曾就是其中之一。他说:
杜《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遭火,烧数千家,楼亦以烬。今人往往于砂土上获真珠。又赵清献《蜀郡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今谓石笋非为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盖大秦国多谬琳琅歼,明珠夜光碧,水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②
按照吴曾的看法,杜甫所说石笋街大雨冲刷出来的瑟瑟,不是蜀王国公卿将相墓中的随葬品,也不是开明氏七宝楼真珠帘坠散后的遗存,而是大秦寺门楼珠帘摧毁后坠地所遗。他的说法有一定根据,但同杜甫之说实为两事,不能混为一谈。
据李膺《成都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珍珠为帘,其后蜀郡火,民家数千与七宝楼俱毁。”③《通志》:“双石笋在兴义门内,即真珠楼基也。”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2:“西门,王建武成谓之兴义门矣。”据此,真珠楼与杜甫所说石笋不在一处,真珠楼在西门内,石笋街则在西门外。况且,石笋既为蜀王开明氏墓志,开明王又如何可能以此为楼基?可见吴曾驳杜甫,是“以其昏昏,令人昭昭”,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大秦国胡人曾在真珠楼故地立寺,倒是事实,《蜀中名胜记》引赵清献之说,也提到此事。大秦,是中国古代对古罗马帝国的称呼,①其国多出各种真珠、琉璃、谬琳、琅歼等宝物,“又有水道通益州”,早与蜀文化有交流往来,其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几个世纪。至于成都出土的古罗马瑟瑟,由大秦寺的建立可知,则为唐朝时。
上面征引的各种文献还说明,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为帘。这真珠大概也属瑟瑟一类“舶”来品,原产于西亚和中亚。
这些古代诗文和史籍记载的在成都发现的瑟瑟,数量如此之多,说明古巴蜀与中亚、西亚有着大量的经济文化往来。
除了瑟瑟之外,古代巴蜀还从西亚地区输入琉璃珠和蚀花肉红石髓珠。从1978在重庆发现的两颗蚀花琉璃珠的形态和纹饰看,极似于西亚的早期同类品。在茂县的早期石棺葬中,曾出土产于西亚的不含钡的钙钠玻璃。在理塘县,也曾发现琉璃珠。而在云南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亦出土西亚的早期肉红蚀花石髓珠和琉璃珠②。在云南昭通发掘的巴蜀墓葬内也出土有蚀花石髓珠。巴蜀和滇文化地区西亚石髓珠和琉璃珠的发现,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
蚀花肉红石髓珠和不含钡的钙钠玻璃(琉璃)原产地均在西亚,有悠久的历史,后来传播于中亚和印度河地区。这些人工宝石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一般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从西亚、中亚到南亚再到中国西南这一广阔的连续空间内,出现的文化因素连续分布现象,恰好表明一条文化交流纽带的存在。这条纽带,就是南方丝绸之路。
巴蜀文化中的西亚因素,便是通过这条古老的文化纽带而来的。①
(三)巴蜀丝绸的西传
巴蜀丝绸织锦,自古称奇。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蜀锦的生产年代很早,大约在商周时代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②
西方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蜀国生产的丝。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力丝”(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据考证,Seres是指古代蜀国。③《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古罗马)“又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以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有可能就是以蜀丝加工为胡绫再出口于波斯的。考古学家曾于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亚历山大城(约建成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时,在一处城堡中发现许多中国丝绸。④考虑到西汉前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及剽悍的月氏曾多次遮断了沿河西走廊西行的“丝绸之路”,那么这些丝绸(至少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从成都经滇缅道运至印巴次大陆,再到达中亚的。⑤这些说明,古代巴蜀的丝绸对于西方古典文明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西域西行至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古代进行的大宗丝绸贸易中,也有不少巴蜀织锦。不久前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中发现的大批精美丝织品,其中便有驰名中外的蜀锦,从南北朝到唐代的无不俱备⑥,表明蜀锦是西域丝绸贸易的主要品种之一。再从战国时代蜀锦已远销楚国的两湖地区,并饮誉于希腊、罗马的情况来看,西汉时蜀锦也应是内地同西域诸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古代巴蜀丝绸文化的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并使南方丝绸之路向欧洲延伸。从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巴蜀文化是一个开放型的文化体系,对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附注
①《华阳国志·南中志》。
①林声:《试释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72页。
②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成都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③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云南青铜器论丛》第168页;张增棋:《滇西青铜文化初探》,《云南青铜器论丛》第94页。
①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
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处:《科研情况简报》第6期,1983年5月14日。
③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5年第2期。
④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①原书作“七国称王”时,指战国中叶时代明显错误。考之史实,应为西周时代。
②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6页。
③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①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文物》1983年第9期。
①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77页。
①参阅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0~554页。
①《汉书·韩安国传》。
①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②参阅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162页。
③B.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04页。
①H.R.Hall,TheAncientHistoryoftheNearEast,1947.
②H.Frankfort,TheBirthoftheCivilizationintheNearEast,1954.
③R.Willis,WesternCivilization:AnUrbanPerspectiveVol.1,1981.
④参阅段渝:《古代巴蜀与近东文明》,《历史月刊》(台北)1993年第2期;《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93页,第532~555页。
①尼·伊·阿拉姆:《中东艺术史》,上海美术出版社1985年。
②R.Willis,WesternCivilization,Vol.1,p.18,1981.
③R.Willis,WesternCivilization,Vol.1,p.16,1981.
④罗塞娃等:《古代西亚埃及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⑤J.E.Quibell,Hierakonpolis,11,Plate1,1902.Mosso,DawnofMediterraneanCivilization,p.56.seeH.R.Hall,TheAncientHistoryoftheNearEast,1947,p.136.
⑥G.Mokhtared,GeneralHistoryofAfrica,Vol.11,1981,p.158.
⑦Strommenger,5000YearsoftheArtofMesopotamia,1964,p.12.
⑧R.F.Tylecote,AHistoryofMetallurgy,1976.
①A.Gardiner,EgyptionGrammar,1957,p.510.
②尼·伊·阿拉姆:《中东艺术史》。
③R.Willis,WesternCivilization,Vol.1,p.19.
④雷·H·肯拜尔等:《世界雕塑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3~24页。
①B.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45~347页。
②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杜〈石笋行〉》。
③《蜀中名胜记》卷二引。
①《三国志》卷三〇杜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②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
①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②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19~371页。
③杨益宪《释支那》,《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第147页。
④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69页。
⑤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
⑥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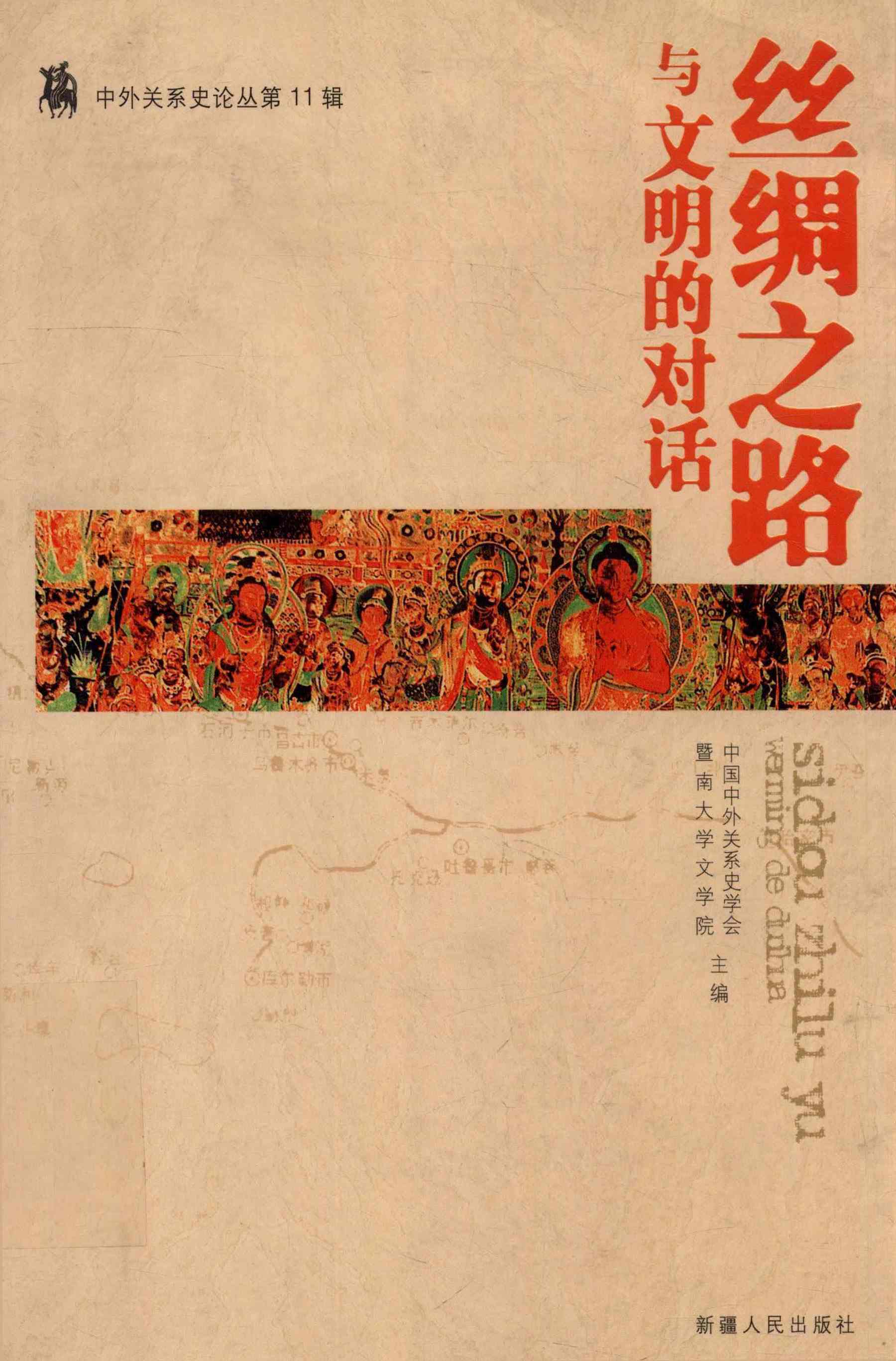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发展与作用》、《丝绸之路上的新和》、《古代新疆与阿拉伯文化》、《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21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喀什“香妃墓”辨误》、《19世纪西方国家对新疆的认知渠道》、《丝绸之路上的英国驻新疆领事馆考述》、《20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从丝绸文化传播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回流》等二十余篇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