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广州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5813 |
| 颗粒名称: | 论唐代广州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 |
| 分类号: | K928.6 |
| 页数: | 17 |
| 页码: | 261-277 |
| 摘要: | 唐开元以前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的唯一机构——市舶使。这一机构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广州港海上交通的发展。唐代广州港分为外港和内港:扶胥港和屯门港为外港;广州城港为内港。内外港在对外贸易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当时广州联系中外贸易的重要桥梁。广州港内联外接,不仅把国内的大量货物运到国外,而且把国外的物品通过贸易和朝贡等形式而运到国内各地。有关唐代与朝贡国家的关系,周伟洲先生已发表《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一文,对此问题有精辟的论述。本文拟就唐代广州内外港与海上交通的关系作以探讨,还请方家指正。其供奉的南海神成为人们海上航行的保护神。 |
| 关键词: | 阿克苏 丝绸文化 结论 |
内容
唐开元以前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的唯一机构——市舶使。这一机构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广州港海上交通的发展。唐代广州港分为外港和内港:扶胥港和屯门港为外港;广州城港为内港。内外港在对外贸易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当时广州联系中外贸易的重要桥梁。广州港内联外接,不仅把国内的大量货物运到国外,而且把国外的物品通过贸易和朝贡等形式而运到国内各地。有关唐代与朝贡国家的关系,周伟洲先生已发表《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对此问题有精辟的论述。本文拟就唐代广州内外港与海上交通的关系作以探讨,还请方家指正。
一、广州外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
扼珠江口内要塞的扶胥(今广州黄埔庙头及以东地区),与其南居于珠江口外东南角的屯门港(今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青山湾)一样,是屏蔽广州的两个重要据点,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广州的外港。
唐广州治所在南海县,即今广州老城区所在的荔湾区、越秀区一部分。由此“正南至大海七十里”,而顺珠江“水路百里”即至“南海”。“自州东八十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浩淼无际。”①此古斗村“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②扶胥和黄木湾依山面海,樵汲充足,扶胥镇因扶胥江得名。而黄木之湾正如倒置斗形,古斗村即在斗形的底部。此湾正是今狮子洋和广州珠江接连地点,东西向珠江漏斗湾到此转南北向的狮子洋大漏斗湾。珠江漏斗湾由广州“小海”阔1500米,到扶胥口扩为2500米,称为“大海”。珠江口内,洪潮急紧,而由扶胥口转南,江面骤宽,洪潮转弱。加上南面的市桥台地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台风的侵袭③。从广州南海县治向东的八十里水道,是由受地质构造和海潮共同影响所形成的广州溺谷湾逐渐发展而来。随着河南、市桥台地逐渐被附近泥沙淤积而扩大,珠江不断东进,加上海水涨潮和退潮的影响,至宋时,广州南海县以东的江道,既受潮水影响,又受珠江影响,故这段漏斗状河道处于内河与海洋的交汇地段,而在唐时,这段水道为海水作用,海舶可以直接航至广州城下④。
扶胥镇位于珠江口北,其南有黄木湾,可以停泊船只,港湾的便利使扶胥镇成为广州城东歇息和中转之地,加之镇西南的南海神庙,是人们出海和归航的祭祀场所。正是便利的交通和著名的神庙,扶胥港成为南海县乃至岭南的一方名镇。南海神庙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同时设立的还有五镇、四渎、东海、吴山等祠①,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唐代开元、天宝时,南海神祭祀日隆。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四海并封为王”,南海神封为“广利王”②;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就有二十三次下诏祭祀岳镇海渎、名山大川③。什么原因?这与玄宗笃信神灵,不断加封诸岳镇海渎有关;也与早灾不断,中央和地方官员借祭祀南海神等岳镇海渎弭灾有关。因此,南海神庙香火日隆主要与国家礼制不断完善有关。正是南海神位高,神职管辖南海交通和岭南安定,有人便在南海神庙附近另辟寺院,宣传佛法,灵化寺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自圆其说,还编造出天宝十二载(753年)南海王与灵化寺住持休咎禅师的故事。这则故事实际上是佛家借助人神对话,利用南海神而炫耀自己,宣传佛法无边。将南海神收归为自己属下弟子。一方面,时南海神成为国家与五岳齐肩的神灵,威名远播岭南,佛家藉此可以抬高身价;另一方面,休咎既想占据南海神庙为佛家寺院,只有将南海神收归佛门弟子,其寺院自然而然成为佛寺。借助此传说,退而求其次,在南海神庙附近建伽蓝,为其建寺寻找借口。如此完美的传说,使南海神脱去了“严急”的性格,皈依佛门,性情温顺,南海再不起波澜;同样他也使休咎在扶胥名正言顺建立寺院,两者互不侵扰,相互利用。北宋蒋之奇写这篇《灵化寺记》是元代二年(1087年),灵化寺取“灵通广化之义”。从唐天宝至北宋,应是灵化寺繁荣之时,“今广利受休咎大师之戒,而南海舟楫遂无飘覆,则佛之慈悲,护持众生如此,神且听之,而况于人乎”④。道出了真正的缘由。当然,宋时南海风波宁静,海上交通畅通,这与造船业的发达,人们的航海技术提高等有联系,才使船毁人亡的现象应有所缓解,而非南海王性情变得温和所致。不过,唐朝南海神尚且如《灵化寺记》所言,“大王威灵,性复严急,”“窃闻大王为性严急,往来舟楫遭风波溺死者甚多”,海上交通仍然有一定风险。究其原因,南海神庙位于珠江口北,风大浪急,特别是每年一度立夏日祭祀时,东南季风盛行,波涛汹涌,由广州城乘船水路东行,逆风而进,又多遇台风,常常船毁人亡,历来广州刺史多畏于风波,“多令从事代祠”。①沿江近海航行尚且如此,远海航行还有诸如风向转换、航线、近海地貌等诸多因素,这些都为航行带来了不便。而珠江口、七洲洋、甚或更远的昆仑岛等处,也常常是船只易覆之地。
唐代扶胥港的繁荣与对内外交通紧密相连。这其中也离不开掌管地方治安与交通安危的南海神。南海神庙被列为国家祭祀之列,并肩五岳,有极高的地位,不仅被国家官员祭祀,就连当地老百姓,甚至域外的海商也来顶礼膜拜。南海神庙所在的扶胥镇一时热闹无比,其他佛教等寺院也接踵沓来,使这一岭南小镇成为中外客商、僧人、官员、士人、民众的汇聚之地。也正是如此,唐代对南海神庙有多次的整修。诸如开元九年(721年)五月,“因诸州水早时有,诏有司遣使祭五岳四渎,自余名山大川等宜令附近州县长官司致祭,并各修饰洒扫。”②天宝十二载(751年)二月,“诏五岳四渎及名山大川并灵迹之处,各委郡县致祭,其祠宇颇毁者,量事修葺”。③南海广利王庙亦应有所修饰。元和十四年(819年),广州刺史孔戣“又广庙宫而大之,治其廷坛,改作东西两序,斋庖之房,百用具修”④。这次修整扩充殿宇,增加斋庖之房,修饰庙内各种器具,应是唐代较大规模的修整。
扶胥港古斗村一带地理位置优越,南通大海,西连扶胥江,北倚山冈,是海上航行出海或归来必经之地。而就在扶胥镇西南南海神庙西今名为“码头园”的鱼塘中,1973年发现了整排的枕木,枕木条每根长2米,延伸20米以上,经C14测定,该枕木系晚唐遗物,木材为海
南紫荆木,坚硬异常。专家逐步推断此枕木为唐时扶胥港遗物,当时南海神庙正在江边,港口在靠近丘陵的内侧。1984年,又在码头园出土唐代陶制壁饰一批,可能是浴日亭附近建筑物上残件①。唐扶胥港既在扶胥镇西南,为广州出海祈求南海神保佑泊船之所,也是归航回来答谢南海神停留之所。当然,有些船在停泊广州城外后,另择时来祈求或报谢南海神亦多从水路而来,码头园附近所在的扶胥港,自然成为理想的抛锚之地。南海神庙“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②。扶胥港正处于出海口南海神庙侧旁,交通方便,堪称广州的外港③,为中外人士参拜神庙停船之所。
南海神庙为扶胥最重要的建筑,是扶胥镇最为亮丽的风景。其供奉的南海神成为人们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南海神不仅是国家神祀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外贸易形成过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由于海舶体积大,海上航行安全难以预料,故在进出港口和海上航行时,人们都希望得到南海神的庇护。不仅是中国沿海的民众,就是外国的“蕃商”和船员也祈佑航运顺利和贸易兴旺。因此,这一中国祭祀文化固有的神祇,随着中外商贸交往的日益频繁,逐渐被“海客”所接受,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外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见证。扶胥镇后来也因是南海庙的所在而名传岭南。镇西南神庙侧旁的扶胥港,成为唐代广州外港的组成部分,人们在此歇息和参拜神庙,扶胥镇北的灵化寺(也称花果院),成为僧徒和香客们趋之若鹜的另一场所。一南一北,一庙一寺,为扶胥镇增色不少。而扶胥港成为人们修佛拜神的停泊之地,在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既然扶胥港是中处商舶进出广州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都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当然,在没有到达广州内港也就是没有履行“纳舶脚”、“收市”和“进奉”等手续以前,是不能在扶胥港进行商贸活动的。出广州东行经扶胥港也一般是货物充足而扬帆的。因此,扶胥港的中外商贸活动是十分有限的,但作为广州的外港,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礼仪文化等方面,与海上丝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唐前期南海神庙与中外贸易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不言而喻,南海神得名“广利王”,与广取货利有关。这种国家的官方神由于有庇护南海航海安全,防止诸如万安州(治今海南陵水东北)豪酋冯若芳等沿海盗匪的掠夺①,有镇海功能,无疑应是岭南民间渔民、商人崇拜的偶像。域外商人或在广州城中的佛寺、婆罗门寺、波斯寺等到祈求各自宗教神灵的保护,亦或出发、归航协同官方共同祈报南海神的保佑,南海神亦间或也是域外商人顶礼膜拜的对象。除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只信真主安拉外,相信南海神成为部分域外商人的崇拜对象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其间这一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逐渐被外商所接受的。因此,唐前期,南海神庙的地位日益提升主要与国家礼制有关,与海上贸易有一定联系,但关系不大,只是两者都处于日益兴隆的同一阶段而已。
扶胥港以南,居于珠江口外东南角的屯门港是屏蔽广州的另外一个重要据点。屯门设有镇兵防守,广州南海郡“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②扶胥与屯门一样,地理位置重要,是防止海寇,稽查来往海船,保护中外商路畅通的交通要冲,屯门既设有镇兵,扶胥的军事地位虽稍逊于屯门,但亦是广州东部的重要据点和港口,再加上为南海神庙所在,亦应有少量士兵驻守。因此,广州稍东的扶胥和屯门,成为广州外围重要的前哨,它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的畅通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唐代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
唐以前,没有设置专门的航海贸易管理机构,而是将航海贸易事务交由沿海州郡地方长官兼管,“前后刺史皆多黩货”①,地方长官由此富甲一方。“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②唐初,贸易仍多由地方官掌管,“显庆六年(661年)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③至迟到开元二年(714年),唐已在广州设立市舶使。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④。至开元十年(722年),市舶使韦某“至于广州,琛赆纳贡,宝贝委积”⑤广州成为“异域殊乡,往来
辐辏,金贝惟错,齿革实繁”之地⑥。天宝,七载(748年),高僧鉴真在广州城外“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有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⑦李庆新先生认为从武德元年(618年)至天宝十四载(754年)为广州对外贸易勃然而兴的时代,亦即日趋兴盛阶段①。开元天宝时,岭南对外贸易兴盛,诱使地方官吏巧取豪夺,为官多贪暴无厌,“以为自开元以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及(卢)奂”。天宝“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环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巨万而死。”卢奂为南海太守,“贪吏敛迹,人用安之”,“中使市舶,亦不干法”②,像卢奂这样为官清廉的地方官少见。这从侧面亦证明唐朝前期繁荣时对外贸易的发达。
天宝十五载(755年),安禄山叛军与来自岭南、黔中、荆襄五万唐军对峙于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唐军大败,“岭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军,多怀金银为资粮,军资、器械尽弃于路,如山积,至是贼徒不胜其富。”③这一方面增强了安禄山叛军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可知岭南等地以金银为货币。这种用金银的传统当追溯至六朝时期。南朝至隋,岭南产银量较前增加,而且通过对外贸易,有进口银源源流入④。唐代亦应如此。乾元元年(758年)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⑤。大食国、波斯国兵众之所以攻城,恐怕与刺史韦利见强取豪夺有关,不然何以“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呢?⑥此后,广德元年(763年),又发生宦官市舶使吕太一叛乱,逐岭南节度使,“纵下大掠广州”⑦。胡三省注《通鉴》曰:“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市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⑧吕太一作乱广州,应以外贸作为其雄厚的经济资本。大历三年(768年),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使原来每年四五艘海舶增加到每岁“至者四十余”①。但好景不常,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叛,攻杀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平叛,“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②。路嗣恭贡献缴获物品,只是上缴其中价值较低且数量较少的商人财产而已。“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代宗)以为至宝,及破(元)载家,得嗣恭所遗琉璃盘径尺”③,大量价值不菲的域外珍宝进贡给诸如权贵元载以及杨炎等朝中重臣。不过,两次平叛,使对外贸易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打击。
此后,从贞元至天祐间(785~907年),广州对外贸易平稳发展④。历任岭南节度使和市舶使在其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贞元初年,杜佑在“商久阻绝”的情况下,“乃导其善利,推以信诚,万船继至,百货错出”⑤。继任的李复虽“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⑥,但亦“久典方面,积聚财货颇甚,为时所讥”⑦。以“廉”、“简”、“肃”闻名的薛珏继其任⑧,亦应廉洁自律。贞元十一年(795年),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⑨。“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广人“多牟利于市”⑩。如此,官民重商,私人贸易兴盛,成为官方贸易之外的又一贸易形式。随着私人贸易的兴盛,居外贸必经之途且又为海上贸易保护神的南海神广利王自然而然香火旺盛,南海神庙及附近地区一派繁荣景象。
贞元时,“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梯山航海,岁来中国”。广州临江建有海阳旧馆,“陆海珍藏”,“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①。贞元末,“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瑇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②,时任岭南节度使的徐申“于常贡之外,未尝腾索,商贾饶盈”③,才使“外蕃岁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④。元和初,岭南节度使杨于陵“奉公洁己”,监军许遂振“好货戾强”,“悍戾贪恣”,为饱己欲,诽谤于陵,朝廷偏信,罢归于陵,“遂振领留事,答吏剔抉其凡赃”⑤,危害岭南。不过,不久遂振终得罪。继任岭南节度使的郑絪“以廉政称”⑥,其后的马总“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僚便之”⑦。岭南“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马总“且专二使,增德以来远人”,于广州城西北修节度使堂,款待“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蜒、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⑧。对外贸易发达,岭南富庶,修建官府军堂,应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修建府馆堂舍之时,岭南“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记,故选帅常重于他镇”⑨。郑权“以家人数多,俸入不足,求为镇守”,贿通中官王守澄,长庆中出任岭南节度使,“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指中官),大为朝士所嗤”①。谢廷老上书言郑权“悉盗公库宝货输注家”有罪,引起接受贿赂中官的憎恨②。宝历二年(726年)胡证出任广州刺史,“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③。如此敛财积聚,富甲天下。因此,“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④。岭南节度使多暴富,从另一方面说明对外贸易的利润丰厚。当然,与此相反,亦有少数廉洁的地方官员。开成时,卢钧出任岭南节度使,“不取商舶珍货,时人
称其廉洁”⑤。会昌中岭南节度使崔龟从亦有“(吴)隐之清节,无愧贪泉”之风,“江革归资,惟闻单舸”⑥。大中时岭南节度使韦正贯改革以往“帅与监舶使必搂其(海货)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旧俗,“一无所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赢犀、象、贝、珠而至者”渐多,“交易其物,海客大至”⑦。继任的纥干〓,宣宗勉励其以李勉为榜样,“不挹于贪泉,无使珠玑,独还于合浦可”⑧。大中末咸通初(859~860年),萧仿“拜岭南节度使,南方珍贿丛夥,不以入门”⑨。咸通间郑愚“扬历清显,声称赫然”⑩。但这种廉洁的官员仍是少数。号称江陵“积谷尚有
七千堆”的“足谷翁”韦宙在咸通中出任岭南节度使,“宣(应作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清廉之戒”⑪。但韦宙在广州任上,还是有所贪婪的。其女为李峣妻,“宙常资之金帛,不可胜记”⑫。即使“以清净为理”的刘崇龟①,“以清俭自居”,后卒于岭表,“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②,“由是名损”③。因此,“门下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苟非令人难著清节,列圣睠念必求贤良”④。
“唐置市舶司于广州,以招来海中蕃舶。”⑤广州的富庶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对外贸易的繁荣。唐廷之所以重视对历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以及市舶使的任命,劝诫历任官员廉洁自律,就是因为其中对外贸易有丰厚收入。黄巢起义军兵临广州城下,欲求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右仆射于琮以“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而予以拒绝⑥。南海的对外贸易与广州的繁荣,王建有《送郑权尚书南海》为证:“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敕设薰炉出,蛮辞呪节开,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白〓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已将身报国,莫起望乡台。”⑦直到唐末天祐元年(904年)十二月,“佛哲国(疑为‘佛誓国’一作佛逝国)、诃陵国、罗越国所贡香药”,广州刺史刘隐进之朝廷⑧,朝贡贸易仍然进行。
安史之乱后,中央直接控制的藩镇为数不多,岭南之所以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应与岭南财富的富足有关。历任岭南节度使或市舶使,或贪或廉,“既贵且富”,对中外贸易或多或少产生一定影响,但都能使这种贸易活动基本上维持下去,上缴国库的财赋也能基本上得以保证。正是因为这种对外贸易的存在,加之作为国家礼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南海神广利王在唐后期香火旺盛,也才出现韩愈所言,“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的局面。⑨
三、广州城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
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港在广州城南,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海潮还可直入港内,“向郡海潮迎”①,“春城海水边”②,兼有河港与海港之利。“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广州“州城三重”,“紫绯满城,邑居逼侧”③,城港相连。“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④,民间外贸活动十分频繁。“海郡雄蛮落,津亭壮越台。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里树桄榔出,时禽翡翠来”⑤,广州城水环曲绕,内地与海外物品皆汇聚于此,“大抵珠江、玳瑁之所聚”⑥。城南濒临珠江(亦称海),上述主管对外贸易的海阳馆即因在海的北面而得名。“岁贡随重译,年芳遍四时”⑦,“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⑧,“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⑨。如此琳琅满目,价值连城的宝货,“人来皆望珠玑去”⑩;“此乡多宝玉”⑪,豪侈重商之风尤盛,“厥俗多豪侈,古来难致礼”⑫。由于招待蕃商有“阅货之宴”和送行之宴,“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①,多在海阳馆设宴。“江上粤王台”②,今越秀山上,亦应是登高宴请场所,真可谓“楼台重蜃气,邑里杂鲛人”③;“波心涌楼阁,规外布星辰”。域外的“鲛人”、“蕃客”成为广州城内外一道亮丽的风景。“冠冕中华客,梯航异域臣,”“贡兼蛟女绢,俗重语儿巾。舶主腰藏宝,黄家砦起臣”④。海阳馆、粤王台之外,广江驿亦成为款待客商、达官贵人的津亭,李群玉有《中秋广江驿示韦益》⑤、《广江驿饯筵留别》,后者有“别筵欲尽秋,一醉海西楼”⑥。广江驿应在广州城偏西,不然何以称其楼为“海西楼”?不过,此驿多为官员来往送别场所,“楼台笼海色”⑦,沿海楼台亭榭不绝于岸,这与商贸活动和政客的往来有关。
新近考古发现也证明了唐代广州城对外贸易的发达。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儿童公园的南越宫署遗址之上的唐地层中,出土了一批高级手工艺的原料和成品,有水晶、玻璃、象牙等,其中一件象牙印章,通高2.8厘米,印钮为外国人头像,曲发后梳,眼帘微垂,鼻梁宽挺,嘴唇厚实,实为唐时来自西域的胡人形象⑧。而唐代珠江边还在今广州市内文明路附近。而就在今广州文明路与北京路交汇处的丽都酒店的建筑工地,以及德政路担杆巷宿舍工地,分别发现了唐代的码头。而在今广州市一宫门前建人行天桥,钻柱孔时又发现了护岸的大木桩和木板⑨。因此,今广州文明路、德政路担杆巷一带,唐时为对外贸易港口所在,“当令输贡赋,不使外夷骄”⑩,贡舶贸易发达。
早在元和之前的贞元十四年(798年)王虔休任岭南节度使时,对原来建于广州城南、珠江滨畔的海阳馆作进一步修整,“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物,陆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戴天捧日,见圣人一家之为贵;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面貌焕然一新。海阳馆不仅是“百宝丛货”汇聚、“天子万方之司存”的宝库之所①,而且因临珠江,交通便利,“始至有阅货之宴”②,归有送别之宴,招款外国使节、客商的客馆,亦称“岭南王馆”,此为市舶使代表中央行使对外贸易之所,也号“市舶使院”。岑仲勉先生以朱彧《萍洲可谈》、王象之《舆地纪胜》、黄佐嘉靖《广东通志》认为:“(宋)海山楼或即(唐)贞元时代临江之‘海阳旧馆’,宋盖承唐制而建设也。其地可能在今邮政总局至十三行附近,此处正对五洲,即今河南之鳌洲,‘鳌’‘五’双声,方音之转变也”③,当为正确。唐市舶使院的地理位置,为以后宋元海山楼及明市舶提举司署、清十三行等外贸商馆、办事机构皆设在城南沿江一带打下基础。虽然贞元、元和时,外贸发达,市舶使院一派繁荣景象,但官方祭祀南海神因夏季珠江风大浪急,加之台风时常发生,故广州刺史祭祀南海神多令副使代之,从元和后期孔戮任广州刺史始,以改往日副使祭祀之惯例,亲至南海神庙祭祀,为后代刺史仿效的榜样。民间祭祀因史料缺乏,难穷究竟,但不能说“海客”(域外客商)、当地商人和渔民,就没有祭祀南海神之举。从一般常理来说,保佑海上交通平安,期求商贸正常进行,应是南海神神职庇护范围之内,因此,唐代中后期,南海神亦随着商贸活动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兴盛,官吏和渔商士民应继续崇祀这一神灵,不断修整和扩建,前引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对南海神庙的扩建即是例证。
就在港口与广州城西南部一带,唐时外商多居住于此,时称“蕃坊”。蕃坊设立“蕃长”、“蕃酋”①,处理蕃商内部事务。蕃坊范围大体在今广州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带,中心在今光塔街及其附近②。唐开成以前,广州“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开成时,岭南节度使卢钧立法,“俾华蛮异处,婚聚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③,加强蕃商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商舶的到来和回航,唐政府设宴款待,“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④,沿江(海)有诸如龙舟的竞赛活动。海商平安到达与龙舟竞渡,都应以祭祀南海神为要。唐时这种风气已经形成。“瓦樽留海客,铜鼓赛江神”⑤,白居易、许浑皆有诗为证。皮日休“铜鼓夜敲溪上月,布帆晴照海边霞”⑥,亦应是岭南的写照。当然,岭南“岛夷徐市种,庙觋赵佗神”⑦,“北与南殊俗,身将货孰亲”⑧,“事事皆殊异”⑨,重鬼信巫风俗相沿,加之,“吾闻近南海,乃是魑魅乡”⑩,“水庙蛟龙集”⑪,“鲸吞洗钵水,犀触点灯船”⑫,赛神与对外贸易交通、岭南民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小结
扶胥港是中外商舶进出广州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都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故其在中外商贸活动中的作用有限。但作为广州的外港,它与屯门是广州外围重要的前哨,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礼仪文化等方面,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的畅通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港在广州城南,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海潮还可直人港内,“向郡海潮迎”。广州城内外的相关官署和海阳等馆驿都在沿城南和城西的水滨,这与海外贸易交通有关。唐代中后期历任广州地方官员的贪廉都对外贸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广州外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
扼珠江口内要塞的扶胥(今广州黄埔庙头及以东地区),与其南居于珠江口外东南角的屯门港(今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青山湾)一样,是屏蔽广州的两个重要据点,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广州的外港。
唐广州治所在南海县,即今广州老城区所在的荔湾区、越秀区一部分。由此“正南至大海七十里”,而顺珠江“水路百里”即至“南海”。“自州东八十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浩淼无际。”①此古斗村“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②扶胥和黄木湾依山面海,樵汲充足,扶胥镇因扶胥江得名。而黄木之湾正如倒置斗形,古斗村即在斗形的底部。此湾正是今狮子洋和广州珠江接连地点,东西向珠江漏斗湾到此转南北向的狮子洋大漏斗湾。珠江漏斗湾由广州“小海”阔1500米,到扶胥口扩为2500米,称为“大海”。珠江口内,洪潮急紧,而由扶胥口转南,江面骤宽,洪潮转弱。加上南面的市桥台地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台风的侵袭③。从广州南海县治向东的八十里水道,是由受地质构造和海潮共同影响所形成的广州溺谷湾逐渐发展而来。随着河南、市桥台地逐渐被附近泥沙淤积而扩大,珠江不断东进,加上海水涨潮和退潮的影响,至宋时,广州南海县以东的江道,既受潮水影响,又受珠江影响,故这段漏斗状河道处于内河与海洋的交汇地段,而在唐时,这段水道为海水作用,海舶可以直接航至广州城下④。
扶胥镇位于珠江口北,其南有黄木湾,可以停泊船只,港湾的便利使扶胥镇成为广州城东歇息和中转之地,加之镇西南的南海神庙,是人们出海和归航的祭祀场所。正是便利的交通和著名的神庙,扶胥港成为南海县乃至岭南的一方名镇。南海神庙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同时设立的还有五镇、四渎、东海、吴山等祠①,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唐代开元、天宝时,南海神祭祀日隆。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四海并封为王”,南海神封为“广利王”②;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就有二十三次下诏祭祀岳镇海渎、名山大川③。什么原因?这与玄宗笃信神灵,不断加封诸岳镇海渎有关;也与早灾不断,中央和地方官员借祭祀南海神等岳镇海渎弭灾有关。因此,南海神庙香火日隆主要与国家礼制不断完善有关。正是南海神位高,神职管辖南海交通和岭南安定,有人便在南海神庙附近另辟寺院,宣传佛法,灵化寺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自圆其说,还编造出天宝十二载(753年)南海王与灵化寺住持休咎禅师的故事。这则故事实际上是佛家借助人神对话,利用南海神而炫耀自己,宣传佛法无边。将南海神收归为自己属下弟子。一方面,时南海神成为国家与五岳齐肩的神灵,威名远播岭南,佛家藉此可以抬高身价;另一方面,休咎既想占据南海神庙为佛家寺院,只有将南海神收归佛门弟子,其寺院自然而然成为佛寺。借助此传说,退而求其次,在南海神庙附近建伽蓝,为其建寺寻找借口。如此完美的传说,使南海神脱去了“严急”的性格,皈依佛门,性情温顺,南海再不起波澜;同样他也使休咎在扶胥名正言顺建立寺院,两者互不侵扰,相互利用。北宋蒋之奇写这篇《灵化寺记》是元代二年(1087年),灵化寺取“灵通广化之义”。从唐天宝至北宋,应是灵化寺繁荣之时,“今广利受休咎大师之戒,而南海舟楫遂无飘覆,则佛之慈悲,护持众生如此,神且听之,而况于人乎”④。道出了真正的缘由。当然,宋时南海风波宁静,海上交通畅通,这与造船业的发达,人们的航海技术提高等有联系,才使船毁人亡的现象应有所缓解,而非南海王性情变得温和所致。不过,唐朝南海神尚且如《灵化寺记》所言,“大王威灵,性复严急,”“窃闻大王为性严急,往来舟楫遭风波溺死者甚多”,海上交通仍然有一定风险。究其原因,南海神庙位于珠江口北,风大浪急,特别是每年一度立夏日祭祀时,东南季风盛行,波涛汹涌,由广州城乘船水路东行,逆风而进,又多遇台风,常常船毁人亡,历来广州刺史多畏于风波,“多令从事代祠”。①沿江近海航行尚且如此,远海航行还有诸如风向转换、航线、近海地貌等诸多因素,这些都为航行带来了不便。而珠江口、七洲洋、甚或更远的昆仑岛等处,也常常是船只易覆之地。
唐代扶胥港的繁荣与对内外交通紧密相连。这其中也离不开掌管地方治安与交通安危的南海神。南海神庙被列为国家祭祀之列,并肩五岳,有极高的地位,不仅被国家官员祭祀,就连当地老百姓,甚至域外的海商也来顶礼膜拜。南海神庙所在的扶胥镇一时热闹无比,其他佛教等寺院也接踵沓来,使这一岭南小镇成为中外客商、僧人、官员、士人、民众的汇聚之地。也正是如此,唐代对南海神庙有多次的整修。诸如开元九年(721年)五月,“因诸州水早时有,诏有司遣使祭五岳四渎,自余名山大川等宜令附近州县长官司致祭,并各修饰洒扫。”②天宝十二载(751年)二月,“诏五岳四渎及名山大川并灵迹之处,各委郡县致祭,其祠宇颇毁者,量事修葺”。③南海广利王庙亦应有所修饰。元和十四年(819年),广州刺史孔戣“又广庙宫而大之,治其廷坛,改作东西两序,斋庖之房,百用具修”④。这次修整扩充殿宇,增加斋庖之房,修饰庙内各种器具,应是唐代较大规模的修整。
扶胥港古斗村一带地理位置优越,南通大海,西连扶胥江,北倚山冈,是海上航行出海或归来必经之地。而就在扶胥镇西南南海神庙西今名为“码头园”的鱼塘中,1973年发现了整排的枕木,枕木条每根长2米,延伸20米以上,经C14测定,该枕木系晚唐遗物,木材为海
南紫荆木,坚硬异常。专家逐步推断此枕木为唐时扶胥港遗物,当时南海神庙正在江边,港口在靠近丘陵的内侧。1984年,又在码头园出土唐代陶制壁饰一批,可能是浴日亭附近建筑物上残件①。唐扶胥港既在扶胥镇西南,为广州出海祈求南海神保佑泊船之所,也是归航回来答谢南海神停留之所。当然,有些船在停泊广州城外后,另择时来祈求或报谢南海神亦多从水路而来,码头园附近所在的扶胥港,自然成为理想的抛锚之地。南海神庙“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②。扶胥港正处于出海口南海神庙侧旁,交通方便,堪称广州的外港③,为中外人士参拜神庙停船之所。
南海神庙为扶胥最重要的建筑,是扶胥镇最为亮丽的风景。其供奉的南海神成为人们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南海神不仅是国家神祀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外贸易形成过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由于海舶体积大,海上航行安全难以预料,故在进出港口和海上航行时,人们都希望得到南海神的庇护。不仅是中国沿海的民众,就是外国的“蕃商”和船员也祈佑航运顺利和贸易兴旺。因此,这一中国祭祀文化固有的神祇,随着中外商贸交往的日益频繁,逐渐被“海客”所接受,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外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见证。扶胥镇后来也因是南海庙的所在而名传岭南。镇西南神庙侧旁的扶胥港,成为唐代广州外港的组成部分,人们在此歇息和参拜神庙,扶胥镇北的灵化寺(也称花果院),成为僧徒和香客们趋之若鹜的另一场所。一南一北,一庙一寺,为扶胥镇增色不少。而扶胥港成为人们修佛拜神的停泊之地,在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既然扶胥港是中处商舶进出广州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都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当然,在没有到达广州内港也就是没有履行“纳舶脚”、“收市”和“进奉”等手续以前,是不能在扶胥港进行商贸活动的。出广州东行经扶胥港也一般是货物充足而扬帆的。因此,扶胥港的中外商贸活动是十分有限的,但作为广州的外港,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礼仪文化等方面,与海上丝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唐前期南海神庙与中外贸易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不言而喻,南海神得名“广利王”,与广取货利有关。这种国家的官方神由于有庇护南海航海安全,防止诸如万安州(治今海南陵水东北)豪酋冯若芳等沿海盗匪的掠夺①,有镇海功能,无疑应是岭南民间渔民、商人崇拜的偶像。域外商人或在广州城中的佛寺、婆罗门寺、波斯寺等到祈求各自宗教神灵的保护,亦或出发、归航协同官方共同祈报南海神的保佑,南海神亦间或也是域外商人顶礼膜拜的对象。除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只信真主安拉外,相信南海神成为部分域外商人的崇拜对象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其间这一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逐渐被外商所接受的。因此,唐前期,南海神庙的地位日益提升主要与国家礼制有关,与海上贸易有一定联系,但关系不大,只是两者都处于日益兴隆的同一阶段而已。
扶胥港以南,居于珠江口外东南角的屯门港是屏蔽广州的另外一个重要据点。屯门设有镇兵防守,广州南海郡“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②扶胥与屯门一样,地理位置重要,是防止海寇,稽查来往海船,保护中外商路畅通的交通要冲,屯门既设有镇兵,扶胥的军事地位虽稍逊于屯门,但亦是广州东部的重要据点和港口,再加上为南海神庙所在,亦应有少量士兵驻守。因此,广州稍东的扶胥和屯门,成为广州外围重要的前哨,它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的畅通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唐代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
唐以前,没有设置专门的航海贸易管理机构,而是将航海贸易事务交由沿海州郡地方长官兼管,“前后刺史皆多黩货”①,地方长官由此富甲一方。“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②唐初,贸易仍多由地方官掌管,“显庆六年(661年)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③至迟到开元二年(714年),唐已在广州设立市舶使。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④。至开元十年(722年),市舶使韦某“至于广州,琛赆纳贡,宝贝委积”⑤广州成为“异域殊乡,往来
辐辏,金贝惟错,齿革实繁”之地⑥。天宝,七载(748年),高僧鉴真在广州城外“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有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⑦李庆新先生认为从武德元年(618年)至天宝十四载(754年)为广州对外贸易勃然而兴的时代,亦即日趋兴盛阶段①。开元天宝时,岭南对外贸易兴盛,诱使地方官吏巧取豪夺,为官多贪暴无厌,“以为自开元以来四十年,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谓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及(卢)奂”。天宝“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环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巨万而死。”卢奂为南海太守,“贪吏敛迹,人用安之”,“中使市舶,亦不干法”②,像卢奂这样为官清廉的地方官少见。这从侧面亦证明唐朝前期繁荣时对外贸易的发达。
天宝十五载(755年),安禄山叛军与来自岭南、黔中、荆襄五万唐军对峙于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唐军大败,“岭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军,多怀金银为资粮,军资、器械尽弃于路,如山积,至是贼徒不胜其富。”③这一方面增强了安禄山叛军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可知岭南等地以金银为货币。这种用金银的传统当追溯至六朝时期。南朝至隋,岭南产银量较前增加,而且通过对外贸易,有进口银源源流入④。唐代亦应如此。乾元元年(758年)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⑤。大食国、波斯国兵众之所以攻城,恐怕与刺史韦利见强取豪夺有关,不然何以“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呢?⑥此后,广德元年(763年),又发生宦官市舶使吕太一叛乱,逐岭南节度使,“纵下大掠广州”⑦。胡三省注《通鉴》曰:“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市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⑧吕太一作乱广州,应以外贸作为其雄厚的经济资本。大历三年(768年),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使原来每年四五艘海舶增加到每岁“至者四十余”①。但好景不常,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叛,攻杀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平叛,“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②。路嗣恭贡献缴获物品,只是上缴其中价值较低且数量较少的商人财产而已。“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代宗)以为至宝,及破(元)载家,得嗣恭所遗琉璃盘径尺”③,大量价值不菲的域外珍宝进贡给诸如权贵元载以及杨炎等朝中重臣。不过,两次平叛,使对外贸易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打击。
此后,从贞元至天祐间(785~907年),广州对外贸易平稳发展④。历任岭南节度使和市舶使在其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贞元初年,杜佑在“商久阻绝”的情况下,“乃导其善利,推以信诚,万船继至,百货错出”⑤。继任的李复虽“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⑥,但亦“久典方面,积聚财货颇甚,为时所讥”⑦。以“廉”、“简”、“肃”闻名的薛珏继其任⑧,亦应廉洁自律。贞元十一年(795年),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⑨。“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广人“多牟利于市”⑩。如此,官民重商,私人贸易兴盛,成为官方贸易之外的又一贸易形式。随着私人贸易的兴盛,居外贸必经之途且又为海上贸易保护神的南海神广利王自然而然香火旺盛,南海神庙及附近地区一派繁荣景象。
贞元时,“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梯山航海,岁来中国”。广州临江建有海阳旧馆,“陆海珍藏”,“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①。贞元末,“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瑇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②,时任岭南节度使的徐申“于常贡之外,未尝腾索,商贾饶盈”③,才使“外蕃岁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④。元和初,岭南节度使杨于陵“奉公洁己”,监军许遂振“好货戾强”,“悍戾贪恣”,为饱己欲,诽谤于陵,朝廷偏信,罢归于陵,“遂振领留事,答吏剔抉其凡赃”⑤,危害岭南。不过,不久遂振终得罪。继任岭南节度使的郑絪“以廉政称”⑥,其后的马总“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僚便之”⑦。岭南“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马总“且专二使,增德以来远人”,于广州城西北修节度使堂,款待“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蜒、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⑧。对外贸易发达,岭南富庶,修建官府军堂,应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修建府馆堂舍之时,岭南“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记,故选帅常重于他镇”⑨。郑权“以家人数多,俸入不足,求为镇守”,贿通中官王守澄,长庆中出任岭南节度使,“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指中官),大为朝士所嗤”①。谢廷老上书言郑权“悉盗公库宝货输注家”有罪,引起接受贿赂中官的憎恨②。宝历二年(726年)胡证出任广州刺史,“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③。如此敛财积聚,富甲天下。因此,“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④。岭南节度使多暴富,从另一方面说明对外贸易的利润丰厚。当然,与此相反,亦有少数廉洁的地方官员。开成时,卢钧出任岭南节度使,“不取商舶珍货,时人
称其廉洁”⑤。会昌中岭南节度使崔龟从亦有“(吴)隐之清节,无愧贪泉”之风,“江革归资,惟闻单舸”⑥。大中时岭南节度使韦正贯改革以往“帅与监舶使必搂其(海货)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旧俗,“一无所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赢犀、象、贝、珠而至者”渐多,“交易其物,海客大至”⑦。继任的纥干〓,宣宗勉励其以李勉为榜样,“不挹于贪泉,无使珠玑,独还于合浦可”⑧。大中末咸通初(859~860年),萧仿“拜岭南节度使,南方珍贿丛夥,不以入门”⑨。咸通间郑愚“扬历清显,声称赫然”⑩。但这种廉洁的官员仍是少数。号称江陵“积谷尚有
七千堆”的“足谷翁”韦宙在咸通中出任岭南节度使,“宣(应作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清廉之戒”⑪。但韦宙在广州任上,还是有所贪婪的。其女为李峣妻,“宙常资之金帛,不可胜记”⑫。即使“以清净为理”的刘崇龟①,“以清俭自居”,后卒于岭表,“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②,“由是名损”③。因此,“门下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苟非令人难著清节,列圣睠念必求贤良”④。
“唐置市舶司于广州,以招来海中蕃舶。”⑤广州的富庶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对外贸易的繁荣。唐廷之所以重视对历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以及市舶使的任命,劝诫历任官员廉洁自律,就是因为其中对外贸易有丰厚收入。黄巢起义军兵临广州城下,欲求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右仆射于琮以“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而予以拒绝⑥。南海的对外贸易与广州的繁荣,王建有《送郑权尚书南海》为证:“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敕设薰炉出,蛮辞呪节开,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白〓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已将身报国,莫起望乡台。”⑦直到唐末天祐元年(904年)十二月,“佛哲国(疑为‘佛誓国’一作佛逝国)、诃陵国、罗越国所贡香药”,广州刺史刘隐进之朝廷⑧,朝贡贸易仍然进行。
安史之乱后,中央直接控制的藩镇为数不多,岭南之所以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应与岭南财富的富足有关。历任岭南节度使或市舶使,或贪或廉,“既贵且富”,对中外贸易或多或少产生一定影响,但都能使这种贸易活动基本上维持下去,上缴国库的财赋也能基本上得以保证。正是因为这种对外贸易的存在,加之作为国家礼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南海神广利王在唐后期香火旺盛,也才出现韩愈所言,“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的局面。⑨
三、广州城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
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港在广州城南,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海潮还可直入港内,“向郡海潮迎”①,“春城海水边”②,兼有河港与海港之利。“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广州“州城三重”,“紫绯满城,邑居逼侧”③,城港相连。“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④,民间外贸活动十分频繁。“海郡雄蛮落,津亭壮越台。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里树桄榔出,时禽翡翠来”⑤,广州城水环曲绕,内地与海外物品皆汇聚于此,“大抵珠江、玳瑁之所聚”⑥。城南濒临珠江(亦称海),上述主管对外贸易的海阳馆即因在海的北面而得名。“岁贡随重译,年芳遍四时”⑦,“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⑧,“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⑨。如此琳琅满目,价值连城的宝货,“人来皆望珠玑去”⑩;“此乡多宝玉”⑪,豪侈重商之风尤盛,“厥俗多豪侈,古来难致礼”⑫。由于招待蕃商有“阅货之宴”和送行之宴,“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①,多在海阳馆设宴。“江上粤王台”②,今越秀山上,亦应是登高宴请场所,真可谓“楼台重蜃气,邑里杂鲛人”③;“波心涌楼阁,规外布星辰”。域外的“鲛人”、“蕃客”成为广州城内外一道亮丽的风景。“冠冕中华客,梯航异域臣,”“贡兼蛟女绢,俗重语儿巾。舶主腰藏宝,黄家砦起臣”④。海阳馆、粤王台之外,广江驿亦成为款待客商、达官贵人的津亭,李群玉有《中秋广江驿示韦益》⑤、《广江驿饯筵留别》,后者有“别筵欲尽秋,一醉海西楼”⑥。广江驿应在广州城偏西,不然何以称其楼为“海西楼”?不过,此驿多为官员来往送别场所,“楼台笼海色”⑦,沿海楼台亭榭不绝于岸,这与商贸活动和政客的往来有关。
新近考古发现也证明了唐代广州城对外贸易的发达。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儿童公园的南越宫署遗址之上的唐地层中,出土了一批高级手工艺的原料和成品,有水晶、玻璃、象牙等,其中一件象牙印章,通高2.8厘米,印钮为外国人头像,曲发后梳,眼帘微垂,鼻梁宽挺,嘴唇厚实,实为唐时来自西域的胡人形象⑧。而唐代珠江边还在今广州市内文明路附近。而就在今广州文明路与北京路交汇处的丽都酒店的建筑工地,以及德政路担杆巷宿舍工地,分别发现了唐代的码头。而在今广州市一宫门前建人行天桥,钻柱孔时又发现了护岸的大木桩和木板⑨。因此,今广州文明路、德政路担杆巷一带,唐时为对外贸易港口所在,“当令输贡赋,不使外夷骄”⑩,贡舶贸易发达。
早在元和之前的贞元十四年(798年)王虔休任岭南节度使时,对原来建于广州城南、珠江滨畔的海阳馆作进一步修整,“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物,陆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戴天捧日,见圣人一家之为贵;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面貌焕然一新。海阳馆不仅是“百宝丛货”汇聚、“天子万方之司存”的宝库之所①,而且因临珠江,交通便利,“始至有阅货之宴”②,归有送别之宴,招款外国使节、客商的客馆,亦称“岭南王馆”,此为市舶使代表中央行使对外贸易之所,也号“市舶使院”。岑仲勉先生以朱彧《萍洲可谈》、王象之《舆地纪胜》、黄佐嘉靖《广东通志》认为:“(宋)海山楼或即(唐)贞元时代临江之‘海阳旧馆’,宋盖承唐制而建设也。其地可能在今邮政总局至十三行附近,此处正对五洲,即今河南之鳌洲,‘鳌’‘五’双声,方音之转变也”③,当为正确。唐市舶使院的地理位置,为以后宋元海山楼及明市舶提举司署、清十三行等外贸商馆、办事机构皆设在城南沿江一带打下基础。虽然贞元、元和时,外贸发达,市舶使院一派繁荣景象,但官方祭祀南海神因夏季珠江风大浪急,加之台风时常发生,故广州刺史祭祀南海神多令副使代之,从元和后期孔戮任广州刺史始,以改往日副使祭祀之惯例,亲至南海神庙祭祀,为后代刺史仿效的榜样。民间祭祀因史料缺乏,难穷究竟,但不能说“海客”(域外客商)、当地商人和渔民,就没有祭祀南海神之举。从一般常理来说,保佑海上交通平安,期求商贸正常进行,应是南海神神职庇护范围之内,因此,唐代中后期,南海神亦随着商贸活动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兴盛,官吏和渔商士民应继续崇祀这一神灵,不断修整和扩建,前引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对南海神庙的扩建即是例证。
就在港口与广州城西南部一带,唐时外商多居住于此,时称“蕃坊”。蕃坊设立“蕃长”、“蕃酋”①,处理蕃商内部事务。蕃坊范围大体在今广州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带,中心在今光塔街及其附近②。唐开成以前,广州“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开成时,岭南节度使卢钧立法,“俾华蛮异处,婚聚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③,加强蕃商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商舶的到来和回航,唐政府设宴款待,“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④,沿江(海)有诸如龙舟的竞赛活动。海商平安到达与龙舟竞渡,都应以祭祀南海神为要。唐时这种风气已经形成。“瓦樽留海客,铜鼓赛江神”⑤,白居易、许浑皆有诗为证。皮日休“铜鼓夜敲溪上月,布帆晴照海边霞”⑥,亦应是岭南的写照。当然,岭南“岛夷徐市种,庙觋赵佗神”⑦,“北与南殊俗,身将货孰亲”⑧,“事事皆殊异”⑨,重鬼信巫风俗相沿,加之,“吾闻近南海,乃是魑魅乡”⑩,“水庙蛟龙集”⑪,“鲸吞洗钵水,犀触点灯船”⑫,赛神与对外贸易交通、岭南民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小结
扶胥港是中外商舶进出广州必经之地,人们在此停泊,一般都与参拜南海神庙有关,故其在中外商贸活动中的作用有限。但作为广州的外港,它与屯门是广州外围重要的前哨,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礼仪文化等方面,在护卫中外商贸交通,保证海上丝路的畅通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港在广州城南,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海潮还可直人港内,“向郡海潮迎”。广州城内外的相关官署和海阳等馆驿都在沿城南和城西的水滨,这与海外贸易交通有关。唐代中后期历任广州地方官员的贪廉都对外贸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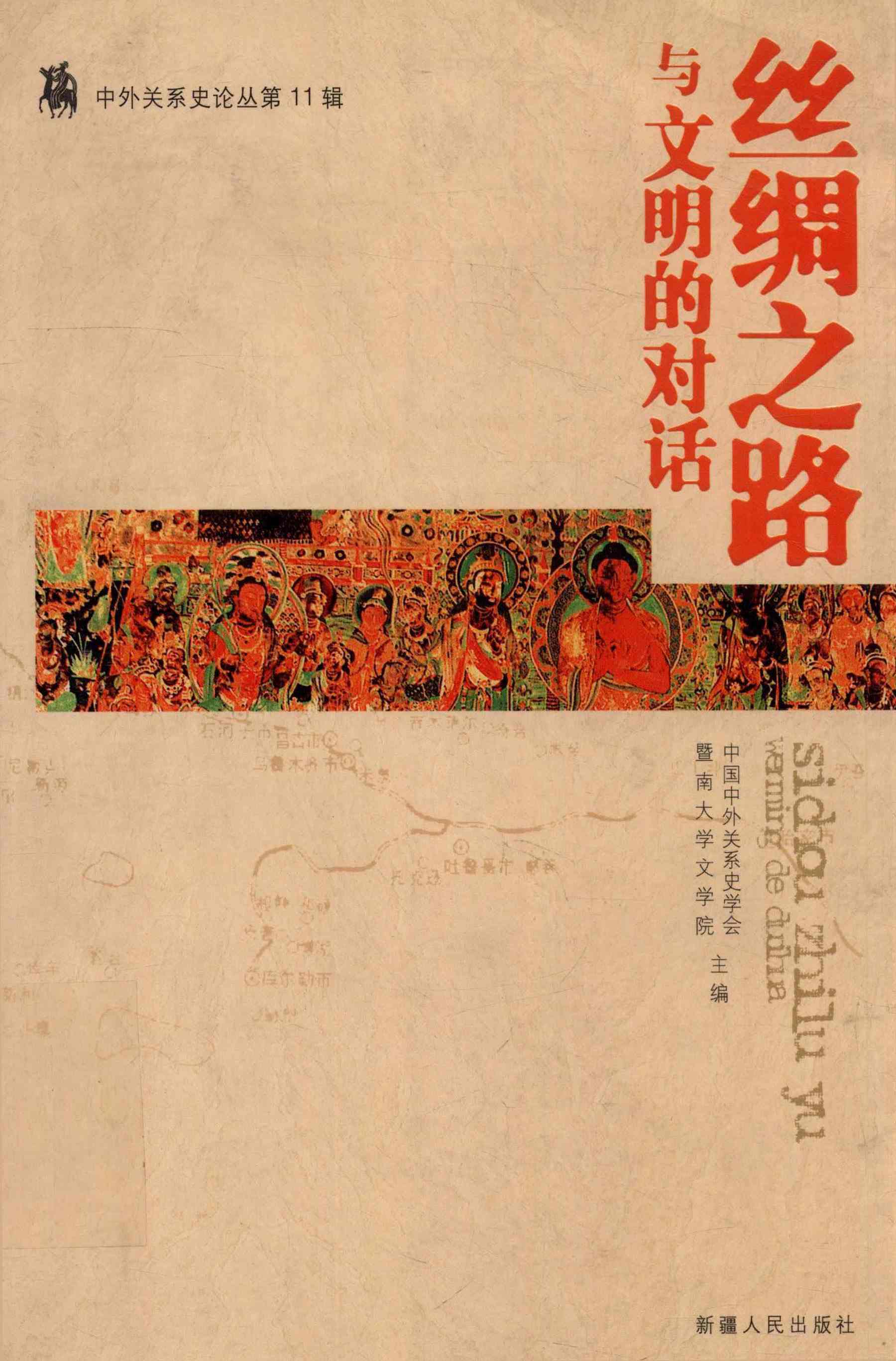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发展与作用》、《丝绸之路上的新和》、《古代新疆与阿拉伯文化》、《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21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喀什“香妃墓”辨误》、《19世纪西方国家对新疆的认知渠道》、《丝绸之路上的英国驻新疆领事馆考述》、《20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从丝绸文化传播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回流》等二十余篇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王元林
责任者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