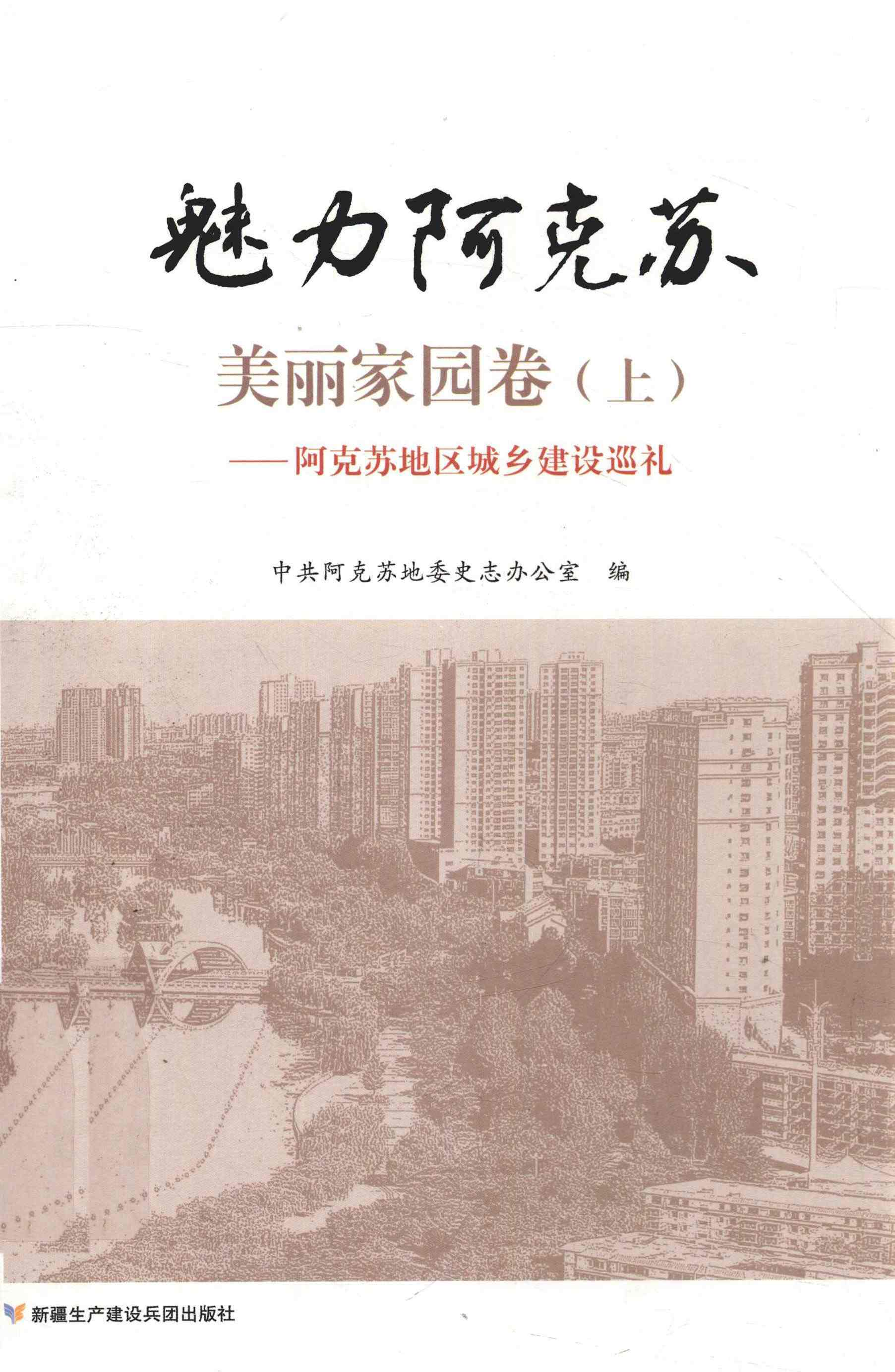内容
玉奇喀特古城,当地人称之为“玉什喀提”,维吾尔语的意思是“三重城”之意。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国内外考古学者以及地区文物部门对该古城进行考古调查以来,出土文物极其丰富,有铜质“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两枚,并出土有耳环、项饰、帽缨等各种饰物。
“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等文物的出土,确定了古城与西域都护府、龟兹等古代盛极一时的大都市之间的关系,也证明新和县在历史上一度曾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
同时,这座古城对于研究古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等,都具有极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对于新和县政府正在致力打造的“汉唐重镇”“龟兹故里”“班超府治”更具有现实意义。
6月,记者在新和县史志办副主任刘金明——对古西域历史文化研究颇有造诣的长者陪伴下,探访了这座古城。
古城距新和县城西南约22千米,呈内城、中城、外城三重形制,属西汉军事戍堡。古城规模宏大,占地近两千亩,是目前阿克苏地区最大的一处汉代军事戍堡。如今的玉奇喀特古城,由于自然与人为因素,其原貌已荡然无存,古城墙、建筑物也早已灰飞烟灭,仅剩下几堵断壁残垣,孤寂地伫立在车来车往的现代公路旁。漫步在昔日的古城废墟中,虽尘沙不语,但依旧能感受到它曾有的繁华和辉煌。
守望在麦田旁
在刘金明的陪同下,我们走进了玉奇喀特古城遗址。
来之前,我们已对古城的现状有所了解,但当古城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时,仍让人顿生伤怀之情。弃车步行数米,刘金明告诉我们:“中城的古城墙就在这里,对面是古城的外城。”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注意到,公路的对面,在白杨的映衬下,还隐约有一段段古城的遗迹。显然,我们的脚下就是玉奇喀特古城的内城和中城。
中城和内城虽还有相对完整的墙基,但和外城一样,大部分地方,已被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所占据,几位维吾尔族农民正在中城里弯身劳作着。
站立在残留的城墙上,放眼望去,那依稀可辨的三层城郭,因岁月的侵蚀,早已看不出丝毫昔日古城的风韵。
一条通往玉奇喀特乡的公路将整个古城一分为二,内城中,红柳、沙棘、小麦丛生,这让人很难想像出古城曾有的繁华,只有地上那些零星散布着的细小红色陶片,才能让人把它与古迹联系起来⋯⋯
关于“衙门”的传闻
内城的城墙边,一个简易的草棚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这是附近老乡的羊圈,县里正在想办法将这些东西迁置,包括公路改道、农田退耕、古城墙的修补与加固、修建观光道路等。”刘金明说。
他说,新和县委、县政府在加大研究地域文化和古城历史文化的力度。“我们已筹资修建班超广场、龟兹文化博物馆、新和龟兹书画院等一系列保护龟兹文化古迹的机构。不久,汉唐重镇、龟兹故里、班超府治的新貌将展现在世人面前。”谈及新和县的未来,刘金明充满信心。
绕过草棚,我们来到了三位正在劳作的维吾尔族老乡面前。
“你好!”一位40多岁的老乡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和我们打着招呼。
“老乡,你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吗?”在刘金明老师的翻译下记者问道。“不知道!”老乡很干脆地回答。“村里有人知道吗?”老乡憨厚地笑着摇了摇头。
刘金明说,现在的农民都不知道有关古城的历史了,只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还会把中城和内城这片地方称为“衙门”。
如此看来,这应该与古城的历史传闻有很大关系。
两枚印章,一地烽火
来到内城,站在两三米高的城墙上,一个长约400米、宽约200米的城池映入眼帘。
“就在这附近,1928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此考察时,发现了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私人印章——‘李崇之印’。1953年,人们又在此发现了‘汉归义羌长印’,随后又有‘常公之印’的铜质印章出土。除此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各种饰物:如耳环、项饰、帽缨等,均为1-6世纪的遗物。”指着内城这个丝毫不起眼的小土坑,刘金明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尤其是‘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印’的相继发现,确定了玉奇喀特古城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的所在地。”
听着刘金明的讲述,记者的思绪回到了2000年前的“汉武大帝”时期。
西域——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从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出现以后,直到2000年后的清末,才被“新疆”这个名称所替代。
在西汉王朝统一西域之前,包括玉奇喀特古城在内的天山南北大多数地区,一直处在匈奴人的铁蹄之下。
历史不会忘记,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一代雄主汉武大帝派遣大英雄张骞曾两度出使西域,完成了与西域的交流。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西域地区终于投入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设立,郑吉成为第一位西域都护。
有史为证:“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它形象地说明了西域都护府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张骞和郑吉等人在维护祖国统一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西汉时期,曾担任过西域都护职位的就有18位,李崇是最后一任西域都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刘金明说。
“为了祖国的统一,李崇战死在这里。”顺着刘金明的话语,记者再次置身于龟兹——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公元16年,王莽新制时期,龟兹各地受到匈奴侵犯,新任都护李崇率军进入西域,亲自带兵攻打匈奴,可惜战败,并战死疆场。”
“按古代‘印随官行’的规则,作为李崇印章的‘李崇之印’出土在玉奇喀特古城,这充分说明李崇保卫龟兹各地时是以玉奇喀特古城为都护府的。”刘金明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无论如何,作为最后一任西域都护的李崇,他将自己的印章留在了玉奇喀特古城,也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龟兹。
也许,他就在我们脚下⋯⋯
古城:风之交响
“汉归义羌长印”和“常公之印”又是怎么回事?环视眼前这个几乎看不到的“城池”,记者感到很好奇。
“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包括龟兹、姑墨、温宿等城郭在内,便成为汉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自此,天山南北各地便在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汉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汉归义羌长印’就说明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
刘金明的话语让记者联想到历史学家陈世良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汉归义羌长印”应该是与李崇共进退的龟兹王所拥有。因此,王莽末年(约公元17年),当时的龟兹王为了躲避匈奴,曾迁龟兹都城于玉奇喀特古城。
对于龟兹的历史变迁,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但无论哪一位历史学家,对“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其中佛塔庙千所”的记载都没有疑义。所以,谈及龟兹变迁的这一话题,就得涉及“三重城”这一字眼,也就不得不提及玉奇喀特古城。只不过,我们还得耐心地等待历史学家的定论。
然而,无论如何,玉奇喀特古城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和新和县境内遗存的42处古城、石窟、佛寺、烽隧、关隘一起,记录着曾经有过的硝烟战火,传递若千年之前的历史信息。
它们的存在,见证了一段段英雄壮举,抒写着一页页英雄史诗,对它们远隔千年的倾诉,需要我们静心地倾听。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国内外考古学者以及地区文物部门对该古城进行考古调查以来,出土文物极其丰富,有铜质“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两枚,并出土有耳环、项饰、帽缨等各种饰物。
“李崇之印”“汉归义羌长印”等文物的出土,确定了古城与西域都护府、龟兹等古代盛极一时的大都市之间的关系,也证明新和县在历史上一度曾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
同时,这座古城对于研究古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等,都具有极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对于新和县政府正在致力打造的“汉唐重镇”“龟兹故里”“班超府治”更具有现实意义。
6月,记者在新和县史志办副主任刘金明——对古西域历史文化研究颇有造诣的长者陪伴下,探访了这座古城。
古城距新和县城西南约22千米,呈内城、中城、外城三重形制,属西汉军事戍堡。古城规模宏大,占地近两千亩,是目前阿克苏地区最大的一处汉代军事戍堡。如今的玉奇喀特古城,由于自然与人为因素,其原貌已荡然无存,古城墙、建筑物也早已灰飞烟灭,仅剩下几堵断壁残垣,孤寂地伫立在车来车往的现代公路旁。漫步在昔日的古城废墟中,虽尘沙不语,但依旧能感受到它曾有的繁华和辉煌。
守望在麦田旁
在刘金明的陪同下,我们走进了玉奇喀特古城遗址。
来之前,我们已对古城的现状有所了解,但当古城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时,仍让人顿生伤怀之情。弃车步行数米,刘金明告诉我们:“中城的古城墙就在这里,对面是古城的外城。”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注意到,公路的对面,在白杨的映衬下,还隐约有一段段古城的遗迹。显然,我们的脚下就是玉奇喀特古城的内城和中城。
中城和内城虽还有相对完整的墙基,但和外城一样,大部分地方,已被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所占据,几位维吾尔族农民正在中城里弯身劳作着。
站立在残留的城墙上,放眼望去,那依稀可辨的三层城郭,因岁月的侵蚀,早已看不出丝毫昔日古城的风韵。
一条通往玉奇喀特乡的公路将整个古城一分为二,内城中,红柳、沙棘、小麦丛生,这让人很难想像出古城曾有的繁华,只有地上那些零星散布着的细小红色陶片,才能让人把它与古迹联系起来⋯⋯
关于“衙门”的传闻
内城的城墙边,一个简易的草棚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这是附近老乡的羊圈,县里正在想办法将这些东西迁置,包括公路改道、农田退耕、古城墙的修补与加固、修建观光道路等。”刘金明说。
他说,新和县委、县政府在加大研究地域文化和古城历史文化的力度。“我们已筹资修建班超广场、龟兹文化博物馆、新和龟兹书画院等一系列保护龟兹文化古迹的机构。不久,汉唐重镇、龟兹故里、班超府治的新貌将展现在世人面前。”谈及新和县的未来,刘金明充满信心。
绕过草棚,我们来到了三位正在劳作的维吾尔族老乡面前。
“你好!”一位40多岁的老乡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和我们打着招呼。
“老乡,你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吗?”在刘金明老师的翻译下记者问道。“不知道!”老乡很干脆地回答。“村里有人知道吗?”老乡憨厚地笑着摇了摇头。
刘金明说,现在的农民都不知道有关古城的历史了,只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还会把中城和内城这片地方称为“衙门”。
如此看来,这应该与古城的历史传闻有很大关系。
两枚印章,一地烽火
来到内城,站在两三米高的城墙上,一个长约400米、宽约200米的城池映入眼帘。
“就在这附近,1928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此考察时,发现了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私人印章——‘李崇之印’。1953年,人们又在此发现了‘汉归义羌长印’,随后又有‘常公之印’的铜质印章出土。除此之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各种饰物:如耳环、项饰、帽缨等,均为1-6世纪的遗物。”指着内城这个丝毫不起眼的小土坑,刘金明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尤其是‘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印’的相继发现,确定了玉奇喀特古城是西域政治军事中心的所在地。”
听着刘金明的讲述,记者的思绪回到了2000年前的“汉武大帝”时期。
西域——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从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出现以后,直到2000年后的清末,才被“新疆”这个名称所替代。
在西汉王朝统一西域之前,包括玉奇喀特古城在内的天山南北大多数地区,一直处在匈奴人的铁蹄之下。
历史不会忘记,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一代雄主汉武大帝派遣大英雄张骞曾两度出使西域,完成了与西域的交流。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西域地区终于投入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设立,郑吉成为第一位西域都护。
有史为证:“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它形象地说明了西域都护府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张骞和郑吉等人在维护祖国统一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西汉时期,曾担任过西域都护职位的就有18位,李崇是最后一任西域都护,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刘金明说。
“为了祖国的统一,李崇战死在这里。”顺着刘金明的话语,记者再次置身于龟兹——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公元16年,王莽新制时期,龟兹各地受到匈奴侵犯,新任都护李崇率军进入西域,亲自带兵攻打匈奴,可惜战败,并战死疆场。”
“按古代‘印随官行’的规则,作为李崇印章的‘李崇之印’出土在玉奇喀特古城,这充分说明李崇保卫龟兹各地时是以玉奇喀特古城为都护府的。”刘金明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无论如何,作为最后一任西域都护的李崇,他将自己的印章留在了玉奇喀特古城,也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龟兹。
也许,他就在我们脚下⋯⋯
古城:风之交响
“汉归义羌长印”和“常公之印”又是怎么回事?环视眼前这个几乎看不到的“城池”,记者感到很好奇。
“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包括龟兹、姑墨、温宿等城郭在内,便成为汉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自此,天山南北各地便在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汉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西域都护,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让其管理地方日常事务,‘汉归义羌长印’就说明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
刘金明的话语让记者联想到历史学家陈世良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汉归义羌长印”应该是与李崇共进退的龟兹王所拥有。因此,王莽末年(约公元17年),当时的龟兹王为了躲避匈奴,曾迁龟兹都城于玉奇喀特古城。
对于龟兹的历史变迁,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但无论哪一位历史学家,对“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其中佛塔庙千所”的记载都没有疑义。所以,谈及龟兹变迁的这一话题,就得涉及“三重城”这一字眼,也就不得不提及玉奇喀特古城。只不过,我们还得耐心地等待历史学家的定论。
然而,无论如何,玉奇喀特古城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和新和县境内遗存的42处古城、石窟、佛寺、烽隧、关隘一起,记录着曾经有过的硝烟战火,传递若千年之前的历史信息。
它们的存在,见证了一段段英雄壮举,抒写着一页页英雄史诗,对它们远隔千年的倾诉,需要我们静心地倾听。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