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和“龙马纹”陶器及相关问题
| 内容出处: |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4876 |
| 颗粒名称: | 新和“龙马纹”陶器及相关问题 |
| 分类号: | K876.3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06-115 |
| 摘要: | 1980年7月,新和县挖掘排碱大渠,于通古孜巴西古城东城墙外出土了一件“龙马纹”的陶器。这件失落于古城之外的陶器,其制作工艺、纹饰的艺术美引起学者的关注。但是有的学者曾撰文称之“马纹陶钵范,外壁和底部均刻S形纹饰,中部有带翼的马纹,背面线刻一立人,时代为唐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曾数次来到通古孜巴西古城及周边的戍堡、烽燧等遗址调查并多次触摸过出土的这件稍微破损的器物。对前人所认定的器物名称、纹饰图案、工艺制作及断代等相关问题有所质疑,不揣粗陋草成此文提出一管之见,以开思路。古城现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关键词: | 新和县 “龙马纹” 陶器 |
内容
1980年7月,新和县挖掘排碱大渠,于通古孜巴西古城东城墙外出土了一件“龙马纹”的陶器。这件失落于古城之外的陶器,其制作工艺、纹饰的艺术美引起学者的关注。但是有的学者曾撰文称之“马纹陶钵范,外壁和底部均刻S形纹饰,中部有带翼的马纹,背面线刻一立人,时代为唐代”。另有学者在引用上述资料后撰文是“模制陶碗的内范,主要图案为希腊飞马(Pegasus),上下两边装饰有浪尖纹等古典艺术纹饰,年代或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是“中亚希腊化时代的艺术品在丝绸之路北道的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曾数次来到通古孜巴西古城及周边的戍堡、烽燧等遗址调查并多次触摸过出土的这件稍微破损的器物。对前人所认定的器物名称、纹饰图案、工艺制作及断代等相关问题有所质疑,不揣粗陋草成此文提出一管之见,以开思路。
一、新和县的通古孜巴西古城
新和“龙马纹”陶器出自通古孜巴西古城的遗址,故此要不厌其烦地简述一下古城及周边相关遗址的概况,借以确定“龙马纹”陶器的相对年代。
1928年,我国学者黄文弼先生首先调查了通古孜巴西古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又曾多次到古城及周边地区的遗址作进一步的文物调查。古城现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处渭干河下游西岸古灌溉区,现已沦为盐渍荒漠。位于新和县城西南约44公里。
从现存遗迹观测,古城建筑平面呈方形,东西城墙长约250米,南北宽约230米,周长约960米,城墙厚约3米,残高约6米。城墙基本上是以夯土、土坯和垛泥的垒砌方法为主。夯层厚50~60厘米。土坯规格有45×24×10或35×10×7厘米。其中古城的南部城墙尚有红柳夹土坯的建筑结构,即一层红柳枝一层土坯的垒叠。这种因地制宜的筑法,省工又省料,而且经久耐用。
紧靠城墙及四角的外缘都筑有向外凸出的垛台,也称为“马面”。垛台是处于防御而设置的军事建筑的“敌台”,同时也起到墙体的加固的保护作用。城墙四角向外伸出的垛台长和宽约6米,残高约6米。四周城墙外的垛台数量和间距皆不相同,东、西墙外的垛台各置有4座,南墙因建城门面置有3座垛台,北墙则建有2座垛台。垛台台面长约5米,宽约4米;顶部长约3米,宽约2.5米,残高约6米。南北城墙的中部各置有瓮城门一座。北瓮城门的大门朝西开,瓮城长约30米,宽约12米。瓮城内的高台上残存有房屋的建筑基址,以及铺地方砖等建筑材料,是古城的最显要遗址区。南瓮城门的大门朝东开,瓮城为土坯垒建,其规模要小于北瓮城门。
古城内泛碱,有多座红柳沙丘的遗迹。地表散露着大量的夹砂红陶质地的罐、钵、盆、瓮、铺地方砖等器物碎片、残铁器、炼铁和炼铜残渣和碎块,以及棉、毛、麻、丝织物残片等文化遗物。历年曾出土可供断代的文物主要有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和大历元宝等钱币;大历年间的“将军妣闺奴烽子钱残纸”、“白苏毕梨领屯米状”、“李明达借粮契残纸”等汉文书;“龙马纹”陶灯;石磨盘、铺地方砖等,凸显了古城文化内涵的时代特征。
通古孜巴西古城周缘尚分布有众多的小型戍堡、烽燧、聚落渠道等唐代遗址和遗迹。结合史籍文献的综合考量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通古孜巴西古城为重心的驻屯史迹,印证了唐代龟兹作为安西大都护府驻节之地,以四镇为前沿基地,依靠屯戍的汉军和西域诸国的各族民众的“务农备战”所创造的物质基础在守边卫土抵御吐蕃的军事围剿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通古孜巴西古城即是唐代安西四镇中的军事基地,对拱卫安西的防卫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其遗址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
二、新和“龙马纹”陶器
这件失落于历史岁月中的陶器偶然出现,它可能涉及龟兹历史的一时一事,更可能涉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例证,充实龟兹文明的研究内容和范围。
通古孜巴西古城出土这件陶器模制,夹砂灰褐陶,火候较低。第一,它不是钵,也不是件范。钵形器呈圜底状,而这件陶器呈平底状的撇形碗,稍残的陶碗经观察,有使用的痕迹表明是件陶灯。夹砂灰陶,模制。敞口,小方(平)沿,弧形壁腹,平底。碗形陶灯口径20、底径10、通高8厘米。灯(碗)内阴线刻划一背影似人,圆形头颅,辫发,双手臂高举过头,着长袍、长靴,(后刻划)。其陶灯的外壁饰一周模制的浮雕式的植物和动物纹饰图案。大体分三层:第一层,即口沿下至上腹之间为一周连续的“S”(绳纹)形纹饰;第二层,腹部的主题图案展翅腾空的“飞马”与“蛇身(龙)”有机组合的“龙马”纹饰为主题,蛇(龙)身起伏,并附4朵云纹;第三层,即腹下至底上之间“海浪”纹(林氏称“浪尖纹”)。陶灯外壁模制的浮雕纹饰,凸起的线条简洁、圆润而流畅,尤其是主题图案中的马首前身的双蹄、翅膀和蛇身(龙)的有机结合,以及蛇(龙)身点缀的4朵祥云都很传神,给人以腾云万里行空的动感的艺术之美,这件出自唐代龟兹绿洲沃土的艺术陶器,它应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即是中国西域龟兹龙马文化中的一类造型艺术。
三、龟兹另类模制陶灯
同龟兹“龙马”纹陶灯模制工艺和纹饰、造型、质地相接近者还有一类陶灯。这类陶灯曾在库车、新和、沙雅、拜城都有发现,主要出自唐代龟兹范围内的古城、佛寺和石窟寺遗址。为便于引起讨论,介绍如次:
1.沙雅县唐代羊达克协海尔城堡出土一件,《新疆文物大观》载文称之“卷草水波纹陶钵范,口径14厘米、底径5.5厘米、高4.4厘米。夹砂灰陶,是模制陶钵的内范”。笔者曾触摸过这件陶器,这并不是一件“模制陶钵的内范”,而是一件实在的“碗型”陶灯。这件陶灯为夹砂灰陶,火候较低,模制,向外撇形的敞口,内浅腹,陶灯外壁呈弧形,小平底,外壁和平底都饰有模制的“浮雕”纹饰。外壁的口沿至腹部有三部分纹饰组成,自沿下依次为“S”形纹,“卷草”纹和向右的“浪花”纹,三组纹饰间有上下两条凸起的弦纹一周为隔断。器底为模制的呈圜状旋涡纹转的“放射”纹。陶灯内附着烟炱。
值得述及的是羊达克协海尔城堡曾发现大陶瓮和唐代开元通宝钱币等。其中有一件陶瓮腹部从左至右竖行墨书有“薛行军”、“监军”,经学者研究认为这是一座唐代驻军城堡。
库车县唐遗址也曾出土一件与沙雅县相同工艺和纹饰的碗形陶灯。陶灯为夹砂灰陶,火候较低,模制工艺,向外撇形敞口,内浅腹;灯外壁呈弧形接小平底。外壁自口沿到器底均饰有一周模制的“浮雕”风格纹饰。自沿下依次有“S”形(绳形)纹,腹中部主体为“卷草”纹,腹下部饰连续右向的“浪花”纹(水涡)。上下三组纹饰之间有两条凸起的弦纹作为隔断,器底为模制呈型的莲花纹。陶灯内附着烟炱。
相同类型的陶灯在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1989—1990年的窟前堆积物清理工程中也发现有三件模制呈“浮雕”纹饰的残损灯具。如K89-4F:12,陶灯残破,“泥质红陶,轮制,圆形敞口,浅底,径约16厘米,胎厚约1.2厘米”。腹底残缺,“外壁模印阳纹二方连续卷草纹和弦纹图案,破失部分为连珠纹圆圈。内壁一侧有烟炱,似灯捻烧过的痕迹。
标本K90-60:2“夹细砂红陶,模制。敞口、平沿、弧壁,小平底。器内外壁施一层土黄色泛白的陶衣,外壁通体模印花纹。花纹分四部分:口沿处饰一周绳纹,腹部饰一周卷草纹,下腹饰‘S’纹带,底部饰以圆形七瓣莲花(只残剩三瓣)。每部分纹饰以一周凸旋纹作间隔,整个纹样凸起,十分清晰,显然是以陶范模印制成,内壁用手抹光,表面布满烟炱迹。此件可能是作为油灯碗使用的陶器。口径16厘米、高5.4厘米、底?厘米。”
标本K90-90-3:5“泥质红陶,轮制,器形规整。微敞口,宽平沿,斜方唇,弧壁。内外壁均施土黄泛白陶衣。口径15厘米。
标本K90-3:25夹细砂红陶,模制。微敞口,平沿,弧壁。内外壁均施土黄泛白陶衣。外壁模印连珠纹、绳纹、卷草纹。口沿和内壁有刮平修整痕迹,内壁有成片的烟炱迹,此件可能是作为油灯碗使用的陶器。口径15.6
厘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陶灯具的主体纹饰中的“卷草纹”,几何图案中的“S”形(绳纹),“浪花纹”(波浪纹),都是克孜尔石窟寺中67、114、206、171、83、14、219、72、123等洞窟壁画普遍出现的边饰图案。
综上所述,新和县通古孜巴西古城发现的模制呈“龙马”艺术纹饰(“飞马”与“龙蛇”的造像是经过切割与组合原理而产生的夸张艺术形象)陶器,以及沙雅、库车、拜城所发现的模制的陶器,从其敞口、弧腹、小平底的自身器型特点看,并不是钵形器,这类陶器应属于“碗”类。其一,所发现的类似陶器的腹内均有灯捻燃烧过的烟炱痕迹,发掘者都一致认为是作为油灯碗使用的陶器,决不是什么“模制陶碗的内范”。其工艺制作和形制皆不同类。其二,出土上述类型陶灯的遗址时代都还有其它可断代的遗物相印证。如新和通古孜巴西古城,沙雅羊达克协海尔古城均为唐安西都护府治下的重要驻军屯戍遗址,库车发现的陶灯则出自安西府治的龟兹故城遗址。克孜尔千佛洞西区窟前出土的陶灯,“其年代约当在公元9世纪上半叶”。如是,这类工艺陶灯的流行时代约为公元7—9世纪上半叶。换言之,即流行的时代皆为唐代。其三,这类模制呈“浮雕”纹饰,马鬃后部的展翅,前蹄跳跃的奔腾,以及龙身(蛇)曲折于云纹之中,其协调的动感,形象而生动。这种“飞马”与“龙”(蛇)采用切割与组合原理的艺术造型为什么能出自于唐代的龟兹沃土,这是我们仍要探讨的原因之一(是希腊化,还是波斯萨珊化,还是本土化?)。
林梅村先生在《中亚的希腊化时代》一讲中谈到希腊艺术的东传时列举到新和县和沙雅县曾出土的两件模制陶器,该文提到:“中亚希腊化时代的艺术品在丝绸之路北道亦有发现。一件为通古斯巴什古城(新和县西南44公里)出土的模制陶碗的内范,口径22厘米,高8厘米,灰褐陶,主要图案为希腊飞马(Pegasus),上下两边装饰有浪尖纹等古典艺术纹饰。另一件为羊达克协海尔古城(新疆沙雅县英买里力乡阔什科瑞克村附近)出土的模制陶碗内范,口径14厘米、底径5.5厘米、高4.4厘米,主要图案为忍冬纹,边饰采用古典艺术浪尖纹。在塔里木盆地,在和田山普拉墓地和楼兰古墓发现过古典艺术的浪尖纹毛织物,皆为汉代之物。而丝绸之路北道发现的两个模制碗的内范都有浪尖纹,年代或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
“希腊飞马是古典艺术马赛克和希腊古钱流行图案,在古罗马时代一个希腊石棺内发现过一个飞马纹铜牌饰,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四、龟兹龙马文化史迹
龟兹史料与考古实例对照的相互勘合表明龟兹龙马文化是西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这一悠久的文化内涵均已渗透于世俗神话传说和宗教之中。
1.龟兹龙马的神话传说
《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中载:“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橇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闻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王欲终没,鞭触其耳,因即潜隐,以至于今。城中无井,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饶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城今荒芜,人烟断绝。”这个龟兹城北大龙池的传说是以神话色彩的方式而诠释龟兹是良马,即“龙马”的产生源地;其二,龟兹国人(土著)自认为是“龙种”来自“龙的传人”。
2.龙文化的形象例证
龟兹考古发现的有关龙的资料主要有木雕的龙首及陶制的龙首等。主要有:
(1)苏巴什西区塔庙墓葬
地处库车河口东西两岸的苏巴什佛寺遗址久负盛名。墓葬则位于西区高耸的塔庙北侧。1978年秋发现时已被盗扰过。停放彩棺的木结构中有一件木雕的龙首构件。圆木雕刻的龙首,“颈部是锯出来的平面,眼眶后顶有一方孔,目、鼻、唇、口分明,眼珠突出,上唇外翻,上下各有尖牙一排,形象生动,并饰以红色,通长约15.7厘米”。
(2)唐王城出土的木雕龙首
库车县唐王城地处县城东南约80公里的荒漠中。古城建筑平面呈方形,墙垣为土坯和夯筑,周长约1074米,城墙高约8米,四面皆有马面及四隅筑角楼,城门置于西城墙的中部并有瓮城门建筑。城内有大型土台基,散露木建筑构件,如木雕龙首、木雕狮首、忍冬纹柱头等。城内曾出土陶、铜、铁、石器、龟兹小铜钱和唐代开元通宝等钱币。龙首式柱头,直径10厘米,通长15厘米。
尚有一件出土于克孜尔石窟寺的另类龙首陶祖,唐代,泥质红陶。龙的双眼怒睁,吻部大张而含一男根。陶祖通长21.6、宽8.8、厚7.9厘米。夸张的艺术形象已表现出对龙的崇拜已是荒诞至极。
以上所举例的资料表明,龟兹龙马文化的传说与考古发现的实物例证相互得到了印证,龟兹龙文化的传说已根植、渗透到社会埋葬习俗和宗教文化的领域之中。
结语
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和融合曾起到过重要作用。我国的龙文化崇拜渊源久远,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如红山文化,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玉龙,河南濮阳出土的仰韶文化的“蚌壳龙”,山西陶寺出土的陶寺文化的“蟠龙纹”彩陶盘,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龙首玉镯”等等,充分证明龙崇拜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十分普遍,同时也证明了龙文化是中华本土文化而不是外来文化。
我国的龙文化自形成之后,不仅在中华大地传播,而且很快与周邻国家交流。尤其是通过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迁徙,辗转传播到中亚、印度及西亚地区。新和“龙马纹”陶器的造型艺术即是丝绸之路与龟兹文化交流、融汇的例证。
一、新和县的通古孜巴西古城
新和“龙马纹”陶器出自通古孜巴西古城的遗址,故此要不厌其烦地简述一下古城及周边相关遗址的概况,借以确定“龙马纹”陶器的相对年代。
1928年,我国学者黄文弼先生首先调查了通古孜巴西古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又曾多次到古城及周边地区的遗址作进一步的文物调查。古城现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处渭干河下游西岸古灌溉区,现已沦为盐渍荒漠。位于新和县城西南约44公里。
从现存遗迹观测,古城建筑平面呈方形,东西城墙长约250米,南北宽约230米,周长约960米,城墙厚约3米,残高约6米。城墙基本上是以夯土、土坯和垛泥的垒砌方法为主。夯层厚50~60厘米。土坯规格有45×24×10或35×10×7厘米。其中古城的南部城墙尚有红柳夹土坯的建筑结构,即一层红柳枝一层土坯的垒叠。这种因地制宜的筑法,省工又省料,而且经久耐用。
紧靠城墙及四角的外缘都筑有向外凸出的垛台,也称为“马面”。垛台是处于防御而设置的军事建筑的“敌台”,同时也起到墙体的加固的保护作用。城墙四角向外伸出的垛台长和宽约6米,残高约6米。四周城墙外的垛台数量和间距皆不相同,东、西墙外的垛台各置有4座,南墙因建城门面置有3座垛台,北墙则建有2座垛台。垛台台面长约5米,宽约4米;顶部长约3米,宽约2.5米,残高约6米。南北城墙的中部各置有瓮城门一座。北瓮城门的大门朝西开,瓮城长约30米,宽约12米。瓮城内的高台上残存有房屋的建筑基址,以及铺地方砖等建筑材料,是古城的最显要遗址区。南瓮城门的大门朝东开,瓮城为土坯垒建,其规模要小于北瓮城门。
古城内泛碱,有多座红柳沙丘的遗迹。地表散露着大量的夹砂红陶质地的罐、钵、盆、瓮、铺地方砖等器物碎片、残铁器、炼铁和炼铜残渣和碎块,以及棉、毛、麻、丝织物残片等文化遗物。历年曾出土可供断代的文物主要有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和大历元宝等钱币;大历年间的“将军妣闺奴烽子钱残纸”、“白苏毕梨领屯米状”、“李明达借粮契残纸”等汉文书;“龙马纹”陶灯;石磨盘、铺地方砖等,凸显了古城文化内涵的时代特征。
通古孜巴西古城周缘尚分布有众多的小型戍堡、烽燧、聚落渠道等唐代遗址和遗迹。结合史籍文献的综合考量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通古孜巴西古城为重心的驻屯史迹,印证了唐代龟兹作为安西大都护府驻节之地,以四镇为前沿基地,依靠屯戍的汉军和西域诸国的各族民众的“务农备战”所创造的物质基础在守边卫土抵御吐蕃的军事围剿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通古孜巴西古城即是唐代安西四镇中的军事基地,对拱卫安西的防卫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其遗址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
二、新和“龙马纹”陶器
这件失落于历史岁月中的陶器偶然出现,它可能涉及龟兹历史的一时一事,更可能涉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例证,充实龟兹文明的研究内容和范围。
通古孜巴西古城出土这件陶器模制,夹砂灰褐陶,火候较低。第一,它不是钵,也不是件范。钵形器呈圜底状,而这件陶器呈平底状的撇形碗,稍残的陶碗经观察,有使用的痕迹表明是件陶灯。夹砂灰陶,模制。敞口,小方(平)沿,弧形壁腹,平底。碗形陶灯口径20、底径10、通高8厘米。灯(碗)内阴线刻划一背影似人,圆形头颅,辫发,双手臂高举过头,着长袍、长靴,(后刻划)。其陶灯的外壁饰一周模制的浮雕式的植物和动物纹饰图案。大体分三层:第一层,即口沿下至上腹之间为一周连续的“S”(绳纹)形纹饰;第二层,腹部的主题图案展翅腾空的“飞马”与“蛇身(龙)”有机组合的“龙马”纹饰为主题,蛇(龙)身起伏,并附4朵云纹;第三层,即腹下至底上之间“海浪”纹(林氏称“浪尖纹”)。陶灯外壁模制的浮雕纹饰,凸起的线条简洁、圆润而流畅,尤其是主题图案中的马首前身的双蹄、翅膀和蛇身(龙)的有机结合,以及蛇(龙)身点缀的4朵祥云都很传神,给人以腾云万里行空的动感的艺术之美,这件出自唐代龟兹绿洲沃土的艺术陶器,它应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即是中国西域龟兹龙马文化中的一类造型艺术。
三、龟兹另类模制陶灯
同龟兹“龙马”纹陶灯模制工艺和纹饰、造型、质地相接近者还有一类陶灯。这类陶灯曾在库车、新和、沙雅、拜城都有发现,主要出自唐代龟兹范围内的古城、佛寺和石窟寺遗址。为便于引起讨论,介绍如次:
1.沙雅县唐代羊达克协海尔城堡出土一件,《新疆文物大观》载文称之“卷草水波纹陶钵范,口径14厘米、底径5.5厘米、高4.4厘米。夹砂灰陶,是模制陶钵的内范”。笔者曾触摸过这件陶器,这并不是一件“模制陶钵的内范”,而是一件实在的“碗型”陶灯。这件陶灯为夹砂灰陶,火候较低,模制,向外撇形的敞口,内浅腹,陶灯外壁呈弧形,小平底,外壁和平底都饰有模制的“浮雕”纹饰。外壁的口沿至腹部有三部分纹饰组成,自沿下依次为“S”形纹,“卷草”纹和向右的“浪花”纹,三组纹饰间有上下两条凸起的弦纹一周为隔断。器底为模制的呈圜状旋涡纹转的“放射”纹。陶灯内附着烟炱。
值得述及的是羊达克协海尔城堡曾发现大陶瓮和唐代开元通宝钱币等。其中有一件陶瓮腹部从左至右竖行墨书有“薛行军”、“监军”,经学者研究认为这是一座唐代驻军城堡。
库车县唐遗址也曾出土一件与沙雅县相同工艺和纹饰的碗形陶灯。陶灯为夹砂灰陶,火候较低,模制工艺,向外撇形敞口,内浅腹;灯外壁呈弧形接小平底。外壁自口沿到器底均饰有一周模制的“浮雕”风格纹饰。自沿下依次有“S”形(绳形)纹,腹中部主体为“卷草”纹,腹下部饰连续右向的“浪花”纹(水涡)。上下三组纹饰之间有两条凸起的弦纹作为隔断,器底为模制呈型的莲花纹。陶灯内附着烟炱。
相同类型的陶灯在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1989—1990年的窟前堆积物清理工程中也发现有三件模制呈“浮雕”纹饰的残损灯具。如K89-4F:12,陶灯残破,“泥质红陶,轮制,圆形敞口,浅底,径约16厘米,胎厚约1.2厘米”。腹底残缺,“外壁模印阳纹二方连续卷草纹和弦纹图案,破失部分为连珠纹圆圈。内壁一侧有烟炱,似灯捻烧过的痕迹。
标本K90-60:2“夹细砂红陶,模制。敞口、平沿、弧壁,小平底。器内外壁施一层土黄色泛白的陶衣,外壁通体模印花纹。花纹分四部分:口沿处饰一周绳纹,腹部饰一周卷草纹,下腹饰‘S’纹带,底部饰以圆形七瓣莲花(只残剩三瓣)。每部分纹饰以一周凸旋纹作间隔,整个纹样凸起,十分清晰,显然是以陶范模印制成,内壁用手抹光,表面布满烟炱迹。此件可能是作为油灯碗使用的陶器。口径16厘米、高5.4厘米、底?厘米。”
标本K90-90-3:5“泥质红陶,轮制,器形规整。微敞口,宽平沿,斜方唇,弧壁。内外壁均施土黄泛白陶衣。口径15厘米。
标本K90-3:25夹细砂红陶,模制。微敞口,平沿,弧壁。内外壁均施土黄泛白陶衣。外壁模印连珠纹、绳纹、卷草纹。口沿和内壁有刮平修整痕迹,内壁有成片的烟炱迹,此件可能是作为油灯碗使用的陶器。口径15.6
厘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陶灯具的主体纹饰中的“卷草纹”,几何图案中的“S”形(绳纹),“浪花纹”(波浪纹),都是克孜尔石窟寺中67、114、206、171、83、14、219、72、123等洞窟壁画普遍出现的边饰图案。
综上所述,新和县通古孜巴西古城发现的模制呈“龙马”艺术纹饰(“飞马”与“龙蛇”的造像是经过切割与组合原理而产生的夸张艺术形象)陶器,以及沙雅、库车、拜城所发现的模制的陶器,从其敞口、弧腹、小平底的自身器型特点看,并不是钵形器,这类陶器应属于“碗”类。其一,所发现的类似陶器的腹内均有灯捻燃烧过的烟炱痕迹,发掘者都一致认为是作为油灯碗使用的陶器,决不是什么“模制陶碗的内范”。其工艺制作和形制皆不同类。其二,出土上述类型陶灯的遗址时代都还有其它可断代的遗物相印证。如新和通古孜巴西古城,沙雅羊达克协海尔古城均为唐安西都护府治下的重要驻军屯戍遗址,库车发现的陶灯则出自安西府治的龟兹故城遗址。克孜尔千佛洞西区窟前出土的陶灯,“其年代约当在公元9世纪上半叶”。如是,这类工艺陶灯的流行时代约为公元7—9世纪上半叶。换言之,即流行的时代皆为唐代。其三,这类模制呈“浮雕”纹饰,马鬃后部的展翅,前蹄跳跃的奔腾,以及龙身(蛇)曲折于云纹之中,其协调的动感,形象而生动。这种“飞马”与“龙”(蛇)采用切割与组合原理的艺术造型为什么能出自于唐代的龟兹沃土,这是我们仍要探讨的原因之一(是希腊化,还是波斯萨珊化,还是本土化?)。
林梅村先生在《中亚的希腊化时代》一讲中谈到希腊艺术的东传时列举到新和县和沙雅县曾出土的两件模制陶器,该文提到:“中亚希腊化时代的艺术品在丝绸之路北道亦有发现。一件为通古斯巴什古城(新和县西南44公里)出土的模制陶碗的内范,口径22厘米,高8厘米,灰褐陶,主要图案为希腊飞马(Pegasus),上下两边装饰有浪尖纹等古典艺术纹饰。另一件为羊达克协海尔古城(新疆沙雅县英买里力乡阔什科瑞克村附近)出土的模制陶碗内范,口径14厘米、底径5.5厘米、高4.4厘米,主要图案为忍冬纹,边饰采用古典艺术浪尖纹。在塔里木盆地,在和田山普拉墓地和楼兰古墓发现过古典艺术的浪尖纹毛织物,皆为汉代之物。而丝绸之路北道发现的两个模制碗的内范都有浪尖纹,年代或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
“希腊飞马是古典艺术马赛克和希腊古钱流行图案,在古罗马时代一个希腊石棺内发现过一个飞马纹铜牌饰,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
四、龟兹龙马文化史迹
龟兹史料与考古实例对照的相互勘合表明龟兹龙马文化是西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这一悠久的文化内涵均已渗透于世俗神话传说和宗教之中。
1.龟兹龙马的神话传说
《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中载:“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橇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闻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王欲终没,鞭触其耳,因即潜隐,以至于今。城中无井,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饶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城今荒芜,人烟断绝。”这个龟兹城北大龙池的传说是以神话色彩的方式而诠释龟兹是良马,即“龙马”的产生源地;其二,龟兹国人(土著)自认为是“龙种”来自“龙的传人”。
2.龙文化的形象例证
龟兹考古发现的有关龙的资料主要有木雕的龙首及陶制的龙首等。主要有:
(1)苏巴什西区塔庙墓葬
地处库车河口东西两岸的苏巴什佛寺遗址久负盛名。墓葬则位于西区高耸的塔庙北侧。1978年秋发现时已被盗扰过。停放彩棺的木结构中有一件木雕的龙首构件。圆木雕刻的龙首,“颈部是锯出来的平面,眼眶后顶有一方孔,目、鼻、唇、口分明,眼珠突出,上唇外翻,上下各有尖牙一排,形象生动,并饰以红色,通长约15.7厘米”。
(2)唐王城出土的木雕龙首
库车县唐王城地处县城东南约80公里的荒漠中。古城建筑平面呈方形,墙垣为土坯和夯筑,周长约1074米,城墙高约8米,四面皆有马面及四隅筑角楼,城门置于西城墙的中部并有瓮城门建筑。城内有大型土台基,散露木建筑构件,如木雕龙首、木雕狮首、忍冬纹柱头等。城内曾出土陶、铜、铁、石器、龟兹小铜钱和唐代开元通宝等钱币。龙首式柱头,直径10厘米,通长15厘米。
尚有一件出土于克孜尔石窟寺的另类龙首陶祖,唐代,泥质红陶。龙的双眼怒睁,吻部大张而含一男根。陶祖通长21.6、宽8.8、厚7.9厘米。夸张的艺术形象已表现出对龙的崇拜已是荒诞至极。
以上所举例的资料表明,龟兹龙马文化的传说与考古发现的实物例证相互得到了印证,龟兹龙文化的传说已根植、渗透到社会埋葬习俗和宗教文化的领域之中。
结语
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和融合曾起到过重要作用。我国的龙文化崇拜渊源久远,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如红山文化,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玉龙,河南濮阳出土的仰韶文化的“蚌壳龙”,山西陶寺出土的陶寺文化的“蟠龙纹”彩陶盘,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龙首玉镯”等等,充分证明龙崇拜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十分普遍,同时也证明了龙文化是中华本土文化而不是外来文化。
我国的龙文化自形成之后,不仅在中华大地传播,而且很快与周邻国家交流。尤其是通过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迁徙,辗转传播到中亚、印度及西亚地区。新和“龙马纹”陶器的造型艺术即是丝绸之路与龟兹文化交流、融汇的例证。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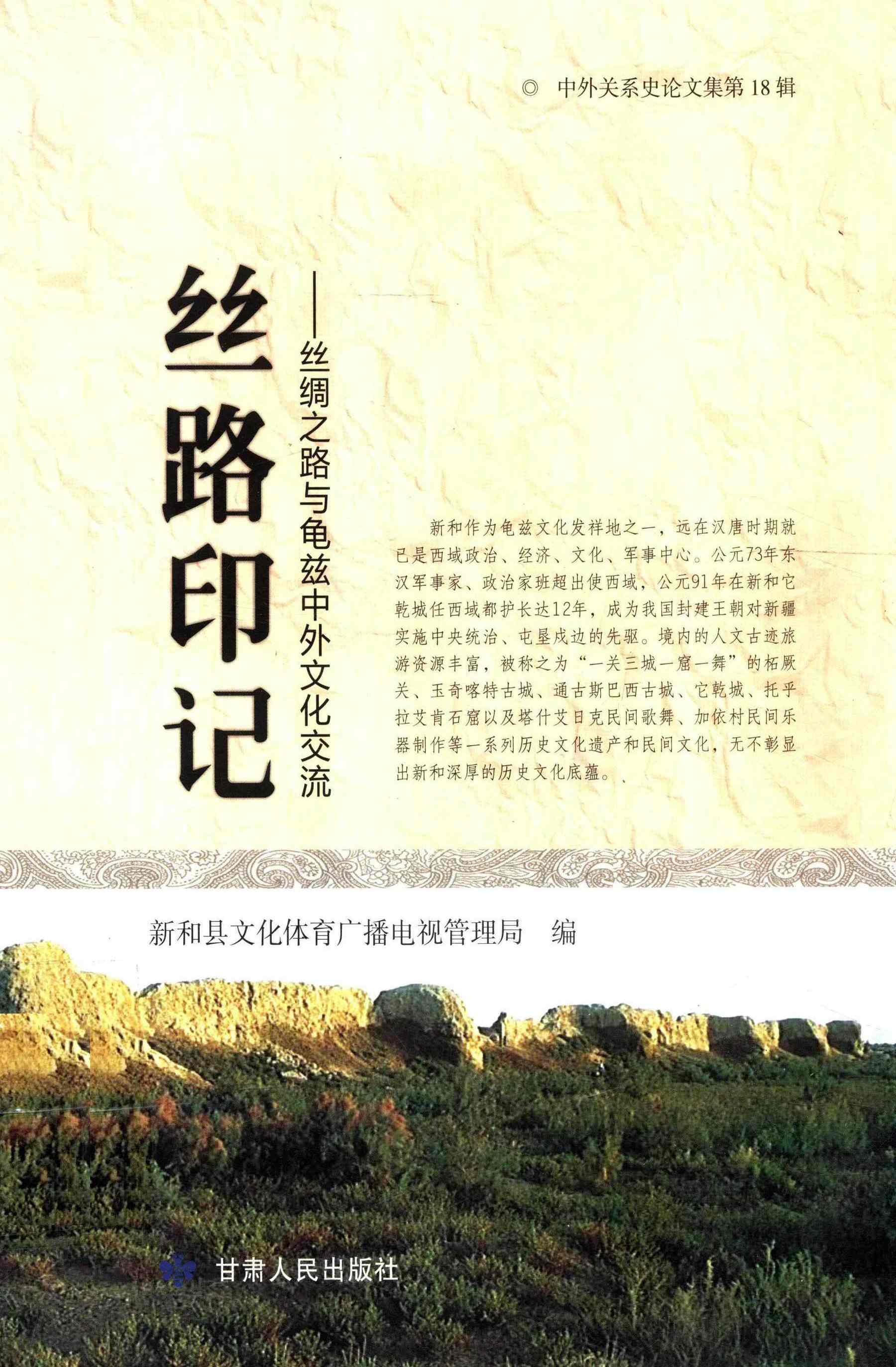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的24篇优秀论文,主要围绕古龟兹文化传统、龟兹文化与丝绸之路、汉唐屯田文化等课题展开论述,探讨了龟兹文化在中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并为进一步研究和发掘古龟兹文化,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阅读
相关人物
张平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新和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