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的概况
| 内容出处: |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4846 |
| 颗粒名称: | 四、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的概况 |
| 分类号: | K203 |
| 页数: | 4 |
| 页码: | 24-27 |
| 摘要: | 童丕先生整理、刊布和译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汉文写本。这实际上是在我国学者张广达先生的帮助下才完成的。伯希和自库车携归的汉文写本特藏由249个号的212件文书组成,从而形成了DA·M,即“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这样一来,全部特藏中总共有214件文书,其中18件已被断代或拥有能令人作出断代的明确标志。其中年代最早者可上溯到690—705年,因为武后新字行用于这段时间。其最晚的时代为784年。其早期有五六件;其晚期,也有同样的数目,其中期,有5件。由此可见,这批写本所覆盖的时代,恰恰是唐军驻扎龟兹的时代,即介于唐军于692年大破吐蕃兵和790—791年左右之间的时代。在这批写本中,军事机构无所不在。 |
| 关键词: | 新和县 丝绸之路 西域探险团 |
内容
童丕先生整理、刊布和译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汉文写本。这实际上是在我国学者张广达先生的帮助下才完成的。
伯希和自库车携归的汉文写本特藏由249个号的212件文书(1-156、157.1-7、201-249号,有些文书后来被撕破成数片)组成,从而形成了DA·M,即“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另外有两件文书则被编入了“伯希和龟兹文特藏”中,尽管它们是用汉文写成的,这是一组总共为44件文书[编号为DA·M(即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507号]中的第31和32号。这样一来,全部特藏中总共有214件文书,其中18件已被断代或拥有能令人作出断代的明确标志。其中年代最早者可上溯到690—705年(DA·M52号文书),因为武后新字行用于这段时间。其最晚的时代为784年(建中五年,DA·M104-106号)。在这两个上下限时间之间,写本的分布很规则。其早期(开元年间,713—741)有五六件;其晚期(760—784),也有同样的数目,其中期(742—759),有5件。由此可见,这批写本所覆盖的时代,恰恰是唐军驻扎龟兹的时代,即介于唐军于692年大破吐蕃兵和790—791年左右之间的时代。
在这批汉文写本中,只有很少的主文献纸叶背面写有与主文献没有任何关系的文字者。这说明它们在写成不久就被失散了。如果它们如同敦煌写本那样被收藏在档案处或藏经处,那么它们的背面就肯定会被重新利用,被用于书写其他内容。
在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中,除了少数12件出自苏巴什之外,其种类非常纷繁,明显出自多个不同的收藏点,遍布于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整片遗址上。但那些佛经和其他寺院文书(僧侣们的书信和账目等),却只占很少数量。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DA·M)中的宗教文献的稀见性,形成了它与出自库车地区的大谷文书之间的高度反差,因为大谷文书中有许多佛经和教义疏注文。为什么在一个伯希和认为是古寺的地方,却很少会出土佛教文献呢?考古发掘已经清楚证明,都勒都尔—阿乎尔确为一座佛寺,但其中居住的都是龟兹人而不是汉族僧众,于现场发现的那些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龟兹文写本,便充分证明了其寺院的周边和生活环境。生活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汉人主要是世俗人,大部分汉文文献均出自官府,其中有许多甚至出自于官吏们本人之手。一批为数不多的私人文书也都往往与官府有关,如某些书信(第131号)、契约(第4号)和殡葬文书(第28-30号),涉及了军镇的驻兵。很明显,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存在着一个官府和一个军镇,居住在其中的汉人是负责管理军队和来自中原的屯边戍民。
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特藏(DA·M)的另一特征,是缺乏商务文书,也没有被用于交易的商品目录;其中更没有旅行文书,如骆驼队的“过所”之类文书。这批文书中只有少数契约,而且似乎也只涉及农民之间的交易,如租地和借粮等(DA·M62号文书背面)。DA·M122号文书涉及了一次“西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龟兹人或粟特人与操汉语的人之间的交易关系。DA·M123号、130号和131号文书是由官吏或者由不以商业谋生的人书写的信件。其中提到的唯一一支骆驼队并不是商队,而是“屯家人”。龟兹城本来是一个商业很发达的地区,但DA·M中的商务文书却极其稀缺,这很可能是由于商人都居住在城内,并且在城内交易,或者是那些沙漠商队客栈均位于城市的四周。
在多种文书(如DA·M33号、47号和86号)中经常出现的“行客”一词,现在尚难以确定其义。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唐代文学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经常出现的“远行商客”。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DA·M134号文书中出现的“行军”(“行军司马”)一词,在DA·M58号和115号写本中还出现过“行客营”。这也可能与商人经常随作战部队远行有关。
在DA·M的大量的行政文书中,只有一件可以被考证为出自龟兹都督府或安西都护府最高当局(DA·M134号):“摄副使行军司马秘书少监薛”。另外至少有3件是通过各级渠道而呈奏龟兹最高当局的,两件是致安西都护府的(DA·M91号和135号):“伏望都护详察”和“都护九郎(?)阁下”;一件是致“龟兹都督府”的(DA·M83号文书残卷5)。其他的文书则向我们揭示了某些高官的尊号,却又无法使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文书的作者,还是仅仅是其收启人(DA·M37号、39号、48号、109号文书)。这些文书其实只涉及到某些琐事,却又要上奏最高当局(DA·M91号和100号文书):对粮食和食物仓库的日常管理、完成工程等。文书中经常提到马匹(DA·M
91号、101号、121号、126等号文书),以及对它们的饲养、统计、采购,而且主要是向突厥人出售(DA·M129号文书)。这些马匹大都属于地方部队(折冲府),但也被用于馆驿。它们不仅仅是中国战略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整个官府的基础(DA·M41号、76号、91号和129号文书)。其中提到的事件完全反映了驻扎在大唐帝国边陲上的那些军事机构的活动。甚至某些佛教文书,它们似乎也涉及了军人(DA·M5号文书,“因军阵损害众生”)。
在这批写本中,军事机构无所不在。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各种级别的军事单位:军镇、城、守捉、开府、镇使、游弈官、孔目官等。但当时那里似乎存在着两种结构:行军(野战军)和折冲(团练)。驻龟兹的军队似乎具有比在中国内地更为广泛的功能。他们当然负责“屯”(DA·M19和88号文书),其中的一处叫作伊利屯(DA·M19号文书背面);他们更要负责在其他地方应该属于行政职权(DA·M57号、90号、104-106号等文书)的事务。其时间最晚的一件文书是DA·M104-106号的请状。它证明,直到784年,唐朝的行政机构在龟兹的某些地区,尚在军队的控制下正常运行。
由于这些文献更多地是涉及地方事务,所以经常提到基层地区单位,如“村”(DA·M12号、95号、121号和127号)、“坊”(DA·M93号、96号、103号、134号文书)。在唐代,“村”与“坊”属于同一级别,“村”位于城市的城墙郭外;“坊”则位于城内,却又不一定具有城市的特征。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中提到了“坊”,这说明在当地就存在着与都城有别的“城”。除了“王子村”之外,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中所提到的村名,均为龟兹语的汉文译音字:“移伐姟(孩?)村”、“伊禄梅村”、“无寻苏射堤村”、“都野提黎伏陀村”和“萨波村”等。那些“坊”却相反都是汉名:“怀柔坊”、“安仁坊”与“和众坊”。这就证明,当时在坊中比在村中具有更高的汉化程度。中原人主要是集中城内,在农村则比较分散。这些坊和村中的居民,似乎更密切地依靠城市当局(DA·M93号、104号-106和134号文书)。我们由此便可以从中管见军屯的迹象,至少是有许多士兵都与其家庭生活在一起。
总之,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提供了许多方面的详细资料。它们对于研究唐代龟兹地区的历史、地理、军事、人口、语言文字、经济和行政组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伯希和自库车携归的汉文写本特藏由249个号的212件文书(1-156、157.1-7、201-249号,有些文书后来被撕破成数片)组成,从而形成了DA·M,即“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另外有两件文书则被编入了“伯希和龟兹文特藏”中,尽管它们是用汉文写成的,这是一组总共为44件文书[编号为DA·M(即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507号]中的第31和32号。这样一来,全部特藏中总共有214件文书,其中18件已被断代或拥有能令人作出断代的明确标志。其中年代最早者可上溯到690—705年(DA·M52号文书),因为武后新字行用于这段时间。其最晚的时代为784年(建中五年,DA·M104-106号)。在这两个上下限时间之间,写本的分布很规则。其早期(开元年间,713—741)有五六件;其晚期(760—784),也有同样的数目,其中期(742—759),有5件。由此可见,这批写本所覆盖的时代,恰恰是唐军驻扎龟兹的时代,即介于唐军于692年大破吐蕃兵和790—791年左右之间的时代。
在这批汉文写本中,只有很少的主文献纸叶背面写有与主文献没有任何关系的文字者。这说明它们在写成不久就被失散了。如果它们如同敦煌写本那样被收藏在档案处或藏经处,那么它们的背面就肯定会被重新利用,被用于书写其他内容。
在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中,除了少数12件出自苏巴什之外,其种类非常纷繁,明显出自多个不同的收藏点,遍布于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整片遗址上。但那些佛经和其他寺院文书(僧侣们的书信和账目等),却只占很少数量。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DA·M)中的宗教文献的稀见性,形成了它与出自库车地区的大谷文书之间的高度反差,因为大谷文书中有许多佛经和教义疏注文。为什么在一个伯希和认为是古寺的地方,却很少会出土佛教文献呢?考古发掘已经清楚证明,都勒都尔—阿乎尔确为一座佛寺,但其中居住的都是龟兹人而不是汉族僧众,于现场发现的那些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龟兹文写本,便充分证明了其寺院的周边和生活环境。生活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汉人主要是世俗人,大部分汉文文献均出自官府,其中有许多甚至出自于官吏们本人之手。一批为数不多的私人文书也都往往与官府有关,如某些书信(第131号)、契约(第4号)和殡葬文书(第28-30号),涉及了军镇的驻兵。很明显,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存在着一个官府和一个军镇,居住在其中的汉人是负责管理军队和来自中原的屯边戍民。
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特藏(DA·M)的另一特征,是缺乏商务文书,也没有被用于交易的商品目录;其中更没有旅行文书,如骆驼队的“过所”之类文书。这批文书中只有少数契约,而且似乎也只涉及农民之间的交易,如租地和借粮等(DA·M62号文书背面)。DA·M122号文书涉及了一次“西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龟兹人或粟特人与操汉语的人之间的交易关系。DA·M123号、130号和131号文书是由官吏或者由不以商业谋生的人书写的信件。其中提到的唯一一支骆驼队并不是商队,而是“屯家人”。龟兹城本来是一个商业很发达的地区,但DA·M中的商务文书却极其稀缺,这很可能是由于商人都居住在城内,并且在城内交易,或者是那些沙漠商队客栈均位于城市的四周。
在多种文书(如DA·M33号、47号和86号)中经常出现的“行客”一词,现在尚难以确定其义。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唐代文学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经常出现的“远行商客”。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DA·M134号文书中出现的“行军”(“行军司马”)一词,在DA·M58号和115号写本中还出现过“行客营”。这也可能与商人经常随作战部队远行有关。
在DA·M的大量的行政文书中,只有一件可以被考证为出自龟兹都督府或安西都护府最高当局(DA·M134号):“摄副使行军司马秘书少监薛”。另外至少有3件是通过各级渠道而呈奏龟兹最高当局的,两件是致安西都护府的(DA·M91号和135号):“伏望都护详察”和“都护九郎(?)阁下”;一件是致“龟兹都督府”的(DA·M83号文书残卷5)。其他的文书则向我们揭示了某些高官的尊号,却又无法使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文书的作者,还是仅仅是其收启人(DA·M37号、39号、48号、109号文书)。这些文书其实只涉及到某些琐事,却又要上奏最高当局(DA·M91号和100号文书):对粮食和食物仓库的日常管理、完成工程等。文书中经常提到马匹(DA·M
91号、101号、121号、126等号文书),以及对它们的饲养、统计、采购,而且主要是向突厥人出售(DA·M129号文书)。这些马匹大都属于地方部队(折冲府),但也被用于馆驿。它们不仅仅是中国战略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整个官府的基础(DA·M41号、76号、91号和129号文书)。其中提到的事件完全反映了驻扎在大唐帝国边陲上的那些军事机构的活动。甚至某些佛教文书,它们似乎也涉及了军人(DA·M5号文书,“因军阵损害众生”)。
在这批写本中,军事机构无所不在。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各种级别的军事单位:军镇、城、守捉、开府、镇使、游弈官、孔目官等。但当时那里似乎存在着两种结构:行军(野战军)和折冲(团练)。驻龟兹的军队似乎具有比在中国内地更为广泛的功能。他们当然负责“屯”(DA·M19和88号文书),其中的一处叫作伊利屯(DA·M19号文书背面);他们更要负责在其他地方应该属于行政职权(DA·M57号、90号、104-106号等文书)的事务。其时间最晚的一件文书是DA·M104-106号的请状。它证明,直到784年,唐朝的行政机构在龟兹的某些地区,尚在军队的控制下正常运行。
由于这些文献更多地是涉及地方事务,所以经常提到基层地区单位,如“村”(DA·M12号、95号、121号和127号)、“坊”(DA·M93号、96号、103号、134号文书)。在唐代,“村”与“坊”属于同一级别,“村”位于城市的城墙郭外;“坊”则位于城内,却又不一定具有城市的特征。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中提到了“坊”,这说明在当地就存在着与都城有别的“城”。除了“王子村”之外,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中所提到的村名,均为龟兹语的汉文译音字:“移伐姟(孩?)村”、“伊禄梅村”、“无寻苏射堤村”、“都野提黎伏陀村”和“萨波村”等。那些“坊”却相反都是汉名:“怀柔坊”、“安仁坊”与“和众坊”。这就证明,当时在坊中比在村中具有更高的汉化程度。中原人主要是集中城内,在农村则比较分散。这些坊和村中的居民,似乎更密切地依靠城市当局(DA·M93号、104号-106和134号文书)。我们由此便可以从中管见军屯的迹象,至少是有许多士兵都与其家庭生活在一起。
总之,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提供了许多方面的详细资料。它们对于研究唐代龟兹地区的历史、地理、军事、人口、语言文字、经济和行政组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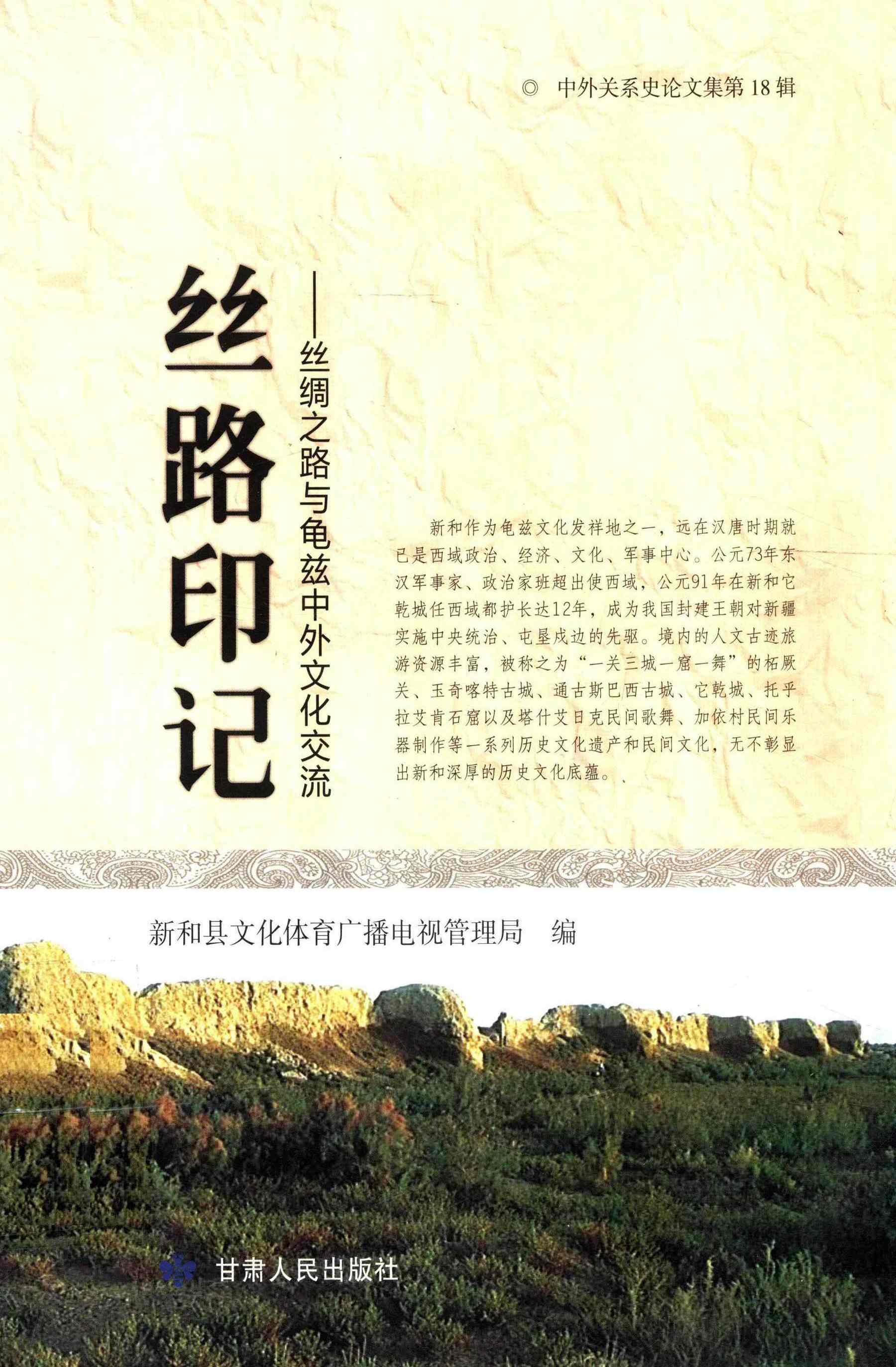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的24篇优秀论文,主要围绕古龟兹文化传统、龟兹文化与丝绸之路、汉唐屯田文化等课题展开论述,探讨了龟兹文化在中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并为进一步研究和发掘古龟兹文化,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阅读
相关地名
新和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