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希和西域探险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古发掘
| 内容出处: |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4844 |
| 颗粒名称: | 二、伯希和西域探险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古发掘 |
| 分类号: | K203 |
| 页数: | 9 |
| 页码: | 14-22 |
| 摘要: | 德国考古学家们主要是在克孜尔和吐木库拉作了考古发掘,伯希和一行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进行发掘时,伯希和的考古发掘日记已经摘录发表于由哈拉德等人编辑的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以一书中了,他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出土了大批文书残卷。主要是用婆罗谜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龟兹文)文书与汉文文书。伯希和最早的发掘主要是集中在围绕着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东北跨院的住宅一带展开的,伯希和于4月25日的考古日记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部分解释”伯希和探险团在库车发掘到的汉文文书。 |
| 关键词: | 新和县 丝绸之路 西域探险团 |
内容
德国考古学家们主要是在克孜尔和吐木库拉作了考古发掘。伯希和一行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进行发掘时,在一个月期间,曾与俄国考古学家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y)同时相伴为邻地工作。
当伯希和探险团将其大本营扎在库木吐拉后,便于4月17日开始对都勒都尔—阿乎尔进行发掘。伯希和的考古发掘日记已经摘录发表于由哈拉德等人编辑的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以一书中了。
资深史语学家伯希和觉得,虽然图木舒克的出土文物甚多,不过开始时文字文献却甚少,但都勒都尔—阿乎尔却未使他失望。他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出土了大批文书残卷,主要是用婆罗谜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龟兹文)文书与汉文文书。伯希和最早的发掘主要是集中在围绕着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东北跨院的住宅一带展开的。
伯希和4月17日至25日的考古笔记,详细记述了他们的发现:梵文和婆罗谜文写本、五铢钱、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直到4月25日,他们才首次发掘了一批写本,但“几乎所有写本都是婆罗谜文字母写成的,没有一行汉字”②。同一天,他却从“其他发掘点上”(应为萨玛克村,Samaq)发掘到了一卷重要文书,其中出现了“明威镇”和“凉州”这样的历史地名。这就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特藏DA·M第114号文书。
5月28日,星期二,伯希和于其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度过自己29岁的生日。我们已完成了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6月4日,星期二,伯希和对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作了初步总结:“我们于此(都勒都尔—阿乎尔)度过的时间基本与在图木舒克的停留期相同。我们的收获物不算很丰富,但总的来说,我对此仍深表满意,因为我们获得了丰富的写本文献。我们可能会在苏巴什对我至今无法解决的一个谜找到答案:为什么在图木舒克会有那样多保存完好的塑像,却没有写本呢?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我们却发现了如此之多的写本,却仅有少许破碎的塑像残片呢?①”
事实上,伯希和于4月25日的考古日记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部分解释。在图木舒克,熊熊大火可能烧得很旺盛,并且过火面很广。其结果是烧焦了许多用粘土模制成的浅浮雕,从而使它们得以留传下来了。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有些完整的住宅区都幸免了火灾,或者是火势不旺,既未使塑像和线浮雕被烧成烧陶制品,又使许多写本被部分地保存下来了。因为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出土的许多纸片上,都带有被火烧焦的痕迹。
伯希和探险团在库车发掘到的汉文文书,与他们在敦煌或吐鲁番发现的那些文书大相径庭。敦煌文书是经人精心地藏匿在藏经洞中的,内容杂乱,自封洞之后再未遭人为翻动和破坏。吐鲁番文书是在墓葬中发现的,每个墓中出土的文书断代和来源一目了然,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家族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相吻合,而且有墓砖为证。都勒都尔—阿乎尔文献的保存状态却甚为恶劣,它们既未被封存在石窟寺中,也未被陪葬于墓葬内,而是在探方中被挖掘出土的。它们在公元8世纪末叶或9世纪初叶被遗弃之前,曾经遭受抢劫和焚烧,又曾遭到先于伯希和到达库车地区的其他外国考古探险团的大肆劫掠。这批文书残损严重,难觅完整的写本,极其稀见完整的文书。此外,这批文书来源复杂,不同时代与不同主人的文书,互相混杂在一起,从而使人考证起来甚难。
至于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写本的断代问题,它们与同时发掘到的钱币的时代大体相一致。这一切都证明了伯希和从其发掘一开始,就曾作出的假定:“我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所获文物的平均时代为8世纪。①那些文书(大都为用婆罗谜文字母写成的)是分别于多处不同地点发掘到的,虽然分散地面很广,却也大都集中在“寺院藏经楼”附近。写本的这种分散性说明,所谓寺院被焚烧之前曾遭抢劫,并非致因的唯一的解释。伯希和主要发掘的地点有“寺院藏经楼”、“西北部的窣堵坡”、门口和垃圾堆,它们彼此距离都相当远,我们很难想象这批文书是出自遭抢劫之前的同一地点,更应该认为它们原来就是被化整为零地收藏的。这批文书的内容纷繁:既有宗教文献,又有私人书信,特别是具有原始籍账与行政文书;世俗文书也不像在敦煌那样抄在写经的背面,而所有文书基本上都是单面抄写,并未被两面使用。
1907年4月17日至22日,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地区的发掘,主要集中在围绕东北跨院的僧房一线。他于其中的一座建筑中,发现了一批明显是非宗教文献的婆罗谜文写本,而且很可能是寺院籍账,其中只有一叶汉文的宗教文书。其他所有汉文宗教写本,大都是由伯氏等从5月23日起,在北部窣堵波大院中发掘出土的。其实,从4月17日起,伯希和一行同时于多处展开发掘,其汉文文书残叶大都为账目,而且都是世俗人的账目,发掘自“混合有厩肥的垃圾堆中”。属于军事机构的DA·M第119号(或DA·M132号)文书是于4月24日在西北段,于一个与外院墙相毗邻的房子中发掘到的。另一件军事文书(DA·M114号)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是于4月25日,当伯希和等集中力量清理“藏经楼”时,才被发现的,但它却出自另一片探方。他们于4月26日之后,所发掘到的非宗教婆罗谜文与汉文文书,也不是出自其主要发掘点,而是出自对萨玛克村的发掘,地处主要发掘点的东端。一份呈西域都护的请状(DA·M91号文书)出自一座建筑物内,该建筑虽紧傍窣堵波北部的建筑群,却又不属于该建筑群。在伯希和于其考古笔记中未加具体确定的一个发掘点上,出土了大批汉文文书,但其地点必然位于大门口附近。汉文文书不会出自伯希和的主要发掘点——宗建设施中,如精舍、窣堵波和其他宗教崇拜地,虽然这些遗址由于其中的艺术作品而特别吸引考古学家们的目光。那些汉文写本主要出土于佛寺群的周边地带。这一切必然会使人联想到,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不仅是僧侣们举行仪轨法事的建筑,而且还是由文职官府机构占据的设施。世俗建筑一般均建于佛寺的周围,也有两类建筑互相交错的例证。世俗文书的时代几乎覆盖了整个8世纪,而没有任何一件宗教文献载有确切的时间。它们也很有可能是于佛寺不复存在之后,由中原士兵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军镇的原因所造成的。现在基本可以肯定,都勒都尔—阿乎尔的佛寺与行政官衙毗邻而居,并于同一时代行使各自的功能①。但我们尚不能充分肯定,这里就是悟空师(法界)当年入竺时所经过的地方。因为悟空当年曾经由耶婆瑟鸡寺②、东西拓(柘)厥寺和阿遮哩贰寺。伯希和当年特别倾向将都勒都尔—阿乎尔考证为玄奘法师所提到的阿奢理贰(阿遮哩贰)伽蓝。他于193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的《吐火罗语和龟兹语》一文中,烈维(S、Lévi)于1913年于《亚细亚学报》发表的《乙种吐火罗语—龟兹语》中,都曾作过类似考证③。季羡林先生等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也采用了此说④。据悟空的记载,东西拓(柘)厥寺与阿遮哩贰明显为两地。玄奘认为阿奢理贰伽蓝“位于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式旌美迹,传芳后叶”。伯希和认为“阿奢理贰”应为“阿奢理腻”之误,因为“贰”字的古音可能为“ni”(腻)⑤。
《新唐书》卷43记载有:“安西西出柘厥关。”其他中文史料中也作“柘厥”,西方汉学家一般均拼音作Zhejue。悟空作“拓厥寺”。“拓”与“柘”号字形相似,而又绝不通假。况且,“拓厥”或“柘厥”是龟兹语的汉文对音。伯希和探险团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到的汉文文书DA·M80号是一份报告(其录文略)。所以,伯希和在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地望作考证时,更多地是坚持“阿奢理腻伽蓝”,从未将此地考证为“柘厥关”。
尽管伯希和在库车地区的考古笔记本中,包括6月19日至7月末的一册早已丢失。但伯希和于其1934年发表的《吐火罗语和龟兹语》①一文中,他尚记得自己发掘到的一卷写本,即DA·M27号文书:“我于1907年曾发掘到一片残纸,可现在已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了,但我很准确地记得于其中读到了‘至柘橛(厥)’的记载。非常遗憾的是再无其他说明,但我于苏巴什西部废墟中搜罗到了其中提到‘柘厥’的这件残卷,也就是说是在西柘厥寺的遗址上发现的。这种巧合令人费解。”因为伯希和似乎将苏巴什西部考证为柘厥寺了,故而他认为不可能从“柘厥”再到柘厥了。但文书中只残存“柘厥”二字,未明确指出是“关”还是“寺”。但从其前后文来看,似乎是指“柘厥寺”。
伯希和的记忆也绝非是永远准确无误的。他在发掘某一残卷时,偶然将都勒都尔—阿乎尔与苏巴什相混淆,也完全在情理之中。首先是在自库车发现的大批匿名文书中,这卷文书完全有理由引起那位考古学家的高度注意,因为其中含有一个史学家们所熟悉的地名“柘厥”。此外,伯氏是一个高水平的考古学家,若发掘地有误,他立即就会想起来,绝不会使他感到“令人费解”。伯希和在苏巴什和都勒都尔—阿乎尔两个遗址的考古发掘是相继于不同时间完成的。他于苏巴什首次发现汉文写本是在6月17日,也就是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工地的发掘工程结束3周之后。对苏巴什的发掘一直是在某种很单调气氛中展开的,其发现物实在不算太多,故而伯希和才会牢固地记住了这份带有“柘厥”字样的文书。
我国新疆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将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考证为唐安西柘厥关。其重要论据之一就是伯希和发掘到的DA·M27号文书,他认为伯希和的记忆力出现了差错,误将在都勒都尔发掘到的这卷文书,归于了苏巴什名下,因而才出现了伯希和考证中的自相矛盾。我国学者有不少人也都同意王先生的观点,甚至包括某些老一辈学者在内。
童丕先生在刊布伯希和库车文书时,依据伯希和当年的观点,对于王炳华先生的考证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苏巴什出土的这卷记载“柘厥关”的汉文写本,已被多人用于为柘厥关确定地望了。王炳华先生认为伯希和将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出土的文书,记在了苏巴什的名下,从而证明伯氏将柘厥关旧址确定在苏巴什,而不是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证。《新唐书》卷43下记载:“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白马河似乎已被比定为木札提河。但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因为古代从龟兹到姑墨曾有多条道路,如其北道沿雀离塔克山麓行进;另一条是经由木扎提河南岸的路,现已被遗弃。悟空提到的东西拓(柘)厥寺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伯希和以其坚实可靠的语言学和地理学论据为基础,将柘厥关与另外两个更为古老的地名作了比较。据伯希和认为,苏巴什双寺(二伽蓝)的遗址位于今城之北的库车河两岸,分别相当于鸠摩罗什(Kumārajiva)时代的雀梨寺(C〓kri)、玄奘于630年提到的昭怙釐(Cogüri)和悟空于788年提到的柘厥。伯希和也没有忽略将悟空提到的柘厥寺与柘厥关相比较,尽管《新唐书》将柘厥关置于了龟兹绿洲的西出口。伯希和于其在苏巴什发现的纸片上读到了“至柘厥”的字样,使他茫然不知所措。尽管这次发现具有棘手的巧合,但伯希和仍极力避免将柘厥关绝对地置于了苏巴什地区,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成立的假设才提出来的。在8世纪时,于库车以北存在着一座柘厥寺,于城西存在着一座同名的关②。伯希和的结论是“不想将任何解释定为最终性的”。他仅满足于“权宜性地”接受,C〓küir的不同相近形式在龟兹语和吐火罗语中均指一关和一寺、一座窣堵波、可能还有一座烽燧。他于其论证时既未表现得专断,也绝不肤浅。伯希和在考古发掘期间,始终都认为都勒都尔—阿乎尔寺是阿奢理贰或阿遮哩贰(意为“奇迹寺”,佛教中的“奇迹”具有“化现”之意),但他也未敢最后确定。直到1934年,他仍建议将两名取经僧人提到的建筑或确定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或确定在库车河以西。
童丕先生认为,即使夏克吐尔确实位于渭干河东岸,即与都勒都尔—阿乎尔遥遥相对,那也很难像王炳华先生那样应将此地考证为柘厥关。因为该地距唐龟兹都城以西23公里处,不足于做为从龟兹都城西行(至姑墨)的第一站。夏克吐尔并不位于绿洲的出口处,而是位于向渭干河右岸深度延伸的农耕区的中心。无论DA·M27号文书是出自苏巴什,还是出自都勒都尔—阿乎尔,都无法证明在某地发现记载某一地名的文书,就断定它就是此地的名称。此外,文书中只有“柘厥”而没有具体注明是“关”还是“寺”,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王炳华先生认为,苏巴什并非是在渭干河两岸建起的唯一建筑群,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情况也应大致如此。位于渭干河西岸者,主要是宗教建筑;位于东岸者,主要是军事—行政机构,但也有宗教崇拜地点。当地的考古学家们分别称这两个遗址中的前者为夏克吐尔(爱克吐尔),后者为玉其吐尔(“吐尔”系突厥文tura的对音,指烽燧和窣堵坡,也可能是指山口)。其实,这两个建筑群具有混合用途,各自都包括行政设施和宗教建筑。这一切与许多人根据出土文书和文物而针对都勒都尔—阿乎尔提出的观点相吻合。但这种考证也并不与伯希和的观点相悖。伯希和在对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时,确实于库车河对岸发现了两个遗址,他分别称之为Hicar(爱克吐尔或夏克吐尔)和Sara〓tam(色乃当)。他仅为色乃当留下了一幅照片。伯希和对爱克吐尔作了简单的记述:“工程量很大。”城堡内部有许多小坯房。伯希和从中发现了许多壁画残片和彩塑残余:“至少有一尊菩萨像,佩戴数量多而较大的首饰。”他还在那里发现了婆罗谜文的木简与一枚建中通宝,却未提到任何汉文写本①。但在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DA·M15号文书的边缘,写有Hicar(爱克吐尔)。
伯希和在开始发掘都勒都尔—阿乎尔时,有些失望。他于4月25日在致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与地理学会主席、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首倡人和鼎力推荐伯希和的塞纳尔(E.Sénart,1847—1928)的信中,流露出了他对最初12天发掘的失望情绪:“至于我们的发掘,至今尚未向我们揭示玄奘所描绘的那种辉煌。数日期间,在所清理的僧房中,没有任何塑像或祭坛的踪迹。我一直在思考,真正的寺院到底在哪里。但在四五天之前,我们最终发现了柴泥制成的祭坛和塑像。尽管它们残损严重,但至少仍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该问题的解释。”“那些在麦秸和杏核中心间堆满了各种垃圾的僧房和小房间,向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布帛、便鞋、芦苇笔、灯盏和陶瓷片。与在图木舒克搜集到的那些文物相比较,它们的数量和品种都要丰富得多。”“我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物的平均时代,确为8世纪⋯⋯如五铢钱(汉代之后)、带有年号(开元和大历,8世纪中叶和末叶)的中国铜钱等。”①
伯希和于5月2日致塞纳尔的书信中,可以更好地解释他对玄奘法师的看法:“我开始理解了这种昔日曾使玄奘感到兴奋的豪华装饰。这里的塑像很多。如果说我们搜集到的大头佛像的风格已纯粹是某种学派的作品了。那么在次要人物的身上,却呈现更多的新奇特征。我在对一间僧房的清理时,于一个祭坛的角落中,发现了一个几乎是全裸的青年美男子彩塑。其半身已残损,很优雅地倚在右胯之上,浸透着一种希腊文化的特征。”“实在说,这种豪华多少有些粗犷,至少从我们现代人的鉴赏观点来看,正是这样的。黄金大量地闪烁,人们到处都使用了黄金,如在壁画上、彩塑上、铜器和木器上,一概如此。尽管那些皈依了伊斯兰教信仰的当地居民,曾大肆地搜刮过这些金叶,现在仍残留有大量的痕迹。即那些经过巧妙设计、精心雕刻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木雕像,它们也身穿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我们在8天便找到了数躯这样的雕像。”②
伯希和探险团对于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地点:佛寺、院子和大门、中心院、宗教圣址、僧房的跨院和第二道门口、主塔和后部小院、木版印刷的雕板处、东北建筑及其宗教设施、大甬道与西北的窣堵坡等。
通过伯希和探险团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现的汉文文书及古钱币,促使伯希和对它们作出了8世纪的断代。该遗址可能是于9世纪时突然停止了活动,因为在许多发掘点都发现了火灾的痕迹。某些绘画的涂金层已被人为刮去,说明在火灾之前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抢劫,“藏经楼”中的写本也因此而四处失散。尽管遗址中出土了许多五铢钱,但我们却很难为这些建筑群的形成期作出准确断代,因为五铢钱于西域至少一直流通到唐初。从公元4世纪起,佛教的宗教功能于龟兹日益多样化。那里出现了带有中心大院、跨院和相继装修的佛寺,而且其数量也都会很多。都勒都尔—阿乎尔的佛寺布局,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犍陀罗佛寺很相似。都勒都尔—阿乎尔的窣堵坡和主要僧伽蓝,都是经过院子的中门而与大院相通。僧伽蓝跨院四周均由僧房簇拥。
总之,都勒都尔—阿乎尔佛寺的最早核心,可能属于一组具有相当规模的佛教建筑,其扩大是随着佛教在龟兹的神奇发展而逐渐完成的。
当伯希和探险团将其大本营扎在库木吐拉后,便于4月17日开始对都勒都尔—阿乎尔进行发掘。伯希和的考古发掘日记已经摘录发表于由哈拉德等人编辑的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以一书中了。
资深史语学家伯希和觉得,虽然图木舒克的出土文物甚多,不过开始时文字文献却甚少,但都勒都尔—阿乎尔却未使他失望。他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出土了大批文书残卷,主要是用婆罗谜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龟兹文)文书与汉文文书。伯希和最早的发掘主要是集中在围绕着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东北跨院的住宅一带展开的。
伯希和4月17日至25日的考古笔记,详细记述了他们的发现:梵文和婆罗谜文写本、五铢钱、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直到4月25日,他们才首次发掘了一批写本,但“几乎所有写本都是婆罗谜文字母写成的,没有一行汉字”②。同一天,他却从“其他发掘点上”(应为萨玛克村,Samaq)发掘到了一卷重要文书,其中出现了“明威镇”和“凉州”这样的历史地名。这就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特藏DA·M第114号文书。
5月28日,星期二,伯希和于其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度过自己29岁的生日。我们已完成了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6月4日,星期二,伯希和对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作了初步总结:“我们于此(都勒都尔—阿乎尔)度过的时间基本与在图木舒克的停留期相同。我们的收获物不算很丰富,但总的来说,我对此仍深表满意,因为我们获得了丰富的写本文献。我们可能会在苏巴什对我至今无法解决的一个谜找到答案:为什么在图木舒克会有那样多保存完好的塑像,却没有写本呢?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我们却发现了如此之多的写本,却仅有少许破碎的塑像残片呢?①”
事实上,伯希和于4月25日的考古日记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部分解释。在图木舒克,熊熊大火可能烧得很旺盛,并且过火面很广。其结果是烧焦了许多用粘土模制成的浅浮雕,从而使它们得以留传下来了。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有些完整的住宅区都幸免了火灾,或者是火势不旺,既未使塑像和线浮雕被烧成烧陶制品,又使许多写本被部分地保存下来了。因为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出土的许多纸片上,都带有被火烧焦的痕迹。
伯希和探险团在库车发掘到的汉文文书,与他们在敦煌或吐鲁番发现的那些文书大相径庭。敦煌文书是经人精心地藏匿在藏经洞中的,内容杂乱,自封洞之后再未遭人为翻动和破坏。吐鲁番文书是在墓葬中发现的,每个墓中出土的文书断代和来源一目了然,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家族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相吻合,而且有墓砖为证。都勒都尔—阿乎尔文献的保存状态却甚为恶劣,它们既未被封存在石窟寺中,也未被陪葬于墓葬内,而是在探方中被挖掘出土的。它们在公元8世纪末叶或9世纪初叶被遗弃之前,曾经遭受抢劫和焚烧,又曾遭到先于伯希和到达库车地区的其他外国考古探险团的大肆劫掠。这批文书残损严重,难觅完整的写本,极其稀见完整的文书。此外,这批文书来源复杂,不同时代与不同主人的文书,互相混杂在一起,从而使人考证起来甚难。
至于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写本的断代问题,它们与同时发掘到的钱币的时代大体相一致。这一切都证明了伯希和从其发掘一开始,就曾作出的假定:“我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所获文物的平均时代为8世纪。①那些文书(大都为用婆罗谜文字母写成的)是分别于多处不同地点发掘到的,虽然分散地面很广,却也大都集中在“寺院藏经楼”附近。写本的这种分散性说明,所谓寺院被焚烧之前曾遭抢劫,并非致因的唯一的解释。伯希和主要发掘的地点有“寺院藏经楼”、“西北部的窣堵坡”、门口和垃圾堆,它们彼此距离都相当远,我们很难想象这批文书是出自遭抢劫之前的同一地点,更应该认为它们原来就是被化整为零地收藏的。这批文书的内容纷繁:既有宗教文献,又有私人书信,特别是具有原始籍账与行政文书;世俗文书也不像在敦煌那样抄在写经的背面,而所有文书基本上都是单面抄写,并未被两面使用。
1907年4月17日至22日,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地区的发掘,主要集中在围绕东北跨院的僧房一线。他于其中的一座建筑中,发现了一批明显是非宗教文献的婆罗谜文写本,而且很可能是寺院籍账,其中只有一叶汉文的宗教文书。其他所有汉文宗教写本,大都是由伯氏等从5月23日起,在北部窣堵波大院中发掘出土的。其实,从4月17日起,伯希和一行同时于多处展开发掘,其汉文文书残叶大都为账目,而且都是世俗人的账目,发掘自“混合有厩肥的垃圾堆中”。属于军事机构的DA·M第119号(或DA·M132号)文书是于4月24日在西北段,于一个与外院墙相毗邻的房子中发掘到的。另一件军事文书(DA·M114号)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是于4月25日,当伯希和等集中力量清理“藏经楼”时,才被发现的,但它却出自另一片探方。他们于4月26日之后,所发掘到的非宗教婆罗谜文与汉文文书,也不是出自其主要发掘点,而是出自对萨玛克村的发掘,地处主要发掘点的东端。一份呈西域都护的请状(DA·M91号文书)出自一座建筑物内,该建筑虽紧傍窣堵波北部的建筑群,却又不属于该建筑群。在伯希和于其考古笔记中未加具体确定的一个发掘点上,出土了大批汉文文书,但其地点必然位于大门口附近。汉文文书不会出自伯希和的主要发掘点——宗建设施中,如精舍、窣堵波和其他宗教崇拜地,虽然这些遗址由于其中的艺术作品而特别吸引考古学家们的目光。那些汉文写本主要出土于佛寺群的周边地带。这一切必然会使人联想到,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不仅是僧侣们举行仪轨法事的建筑,而且还是由文职官府机构占据的设施。世俗建筑一般均建于佛寺的周围,也有两类建筑互相交错的例证。世俗文书的时代几乎覆盖了整个8世纪,而没有任何一件宗教文献载有确切的时间。它们也很有可能是于佛寺不复存在之后,由中原士兵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军镇的原因所造成的。现在基本可以肯定,都勒都尔—阿乎尔的佛寺与行政官衙毗邻而居,并于同一时代行使各自的功能①。但我们尚不能充分肯定,这里就是悟空师(法界)当年入竺时所经过的地方。因为悟空当年曾经由耶婆瑟鸡寺②、东西拓(柘)厥寺和阿遮哩贰寺。伯希和当年特别倾向将都勒都尔—阿乎尔考证为玄奘法师所提到的阿奢理贰(阿遮哩贰)伽蓝。他于193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的《吐火罗语和龟兹语》一文中,烈维(S、Lévi)于1913年于《亚细亚学报》发表的《乙种吐火罗语—龟兹语》中,都曾作过类似考证③。季羡林先生等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也采用了此说④。据悟空的记载,东西拓(柘)厥寺与阿遮哩贰明显为两地。玄奘认为阿奢理贰伽蓝“位于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式旌美迹,传芳后叶”。伯希和认为“阿奢理贰”应为“阿奢理腻”之误,因为“贰”字的古音可能为“ni”(腻)⑤。
《新唐书》卷43记载有:“安西西出柘厥关。”其他中文史料中也作“柘厥”,西方汉学家一般均拼音作Zhejue。悟空作“拓厥寺”。“拓”与“柘”号字形相似,而又绝不通假。况且,“拓厥”或“柘厥”是龟兹语的汉文对音。伯希和探险团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到的汉文文书DA·M80号是一份报告(其录文略)。所以,伯希和在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地望作考证时,更多地是坚持“阿奢理腻伽蓝”,从未将此地考证为“柘厥关”。
尽管伯希和在库车地区的考古笔记本中,包括6月19日至7月末的一册早已丢失。但伯希和于其1934年发表的《吐火罗语和龟兹语》①一文中,他尚记得自己发掘到的一卷写本,即DA·M27号文书:“我于1907年曾发掘到一片残纸,可现在已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了,但我很准确地记得于其中读到了‘至柘橛(厥)’的记载。非常遗憾的是再无其他说明,但我于苏巴什西部废墟中搜罗到了其中提到‘柘厥’的这件残卷,也就是说是在西柘厥寺的遗址上发现的。这种巧合令人费解。”因为伯希和似乎将苏巴什西部考证为柘厥寺了,故而他认为不可能从“柘厥”再到柘厥了。但文书中只残存“柘厥”二字,未明确指出是“关”还是“寺”。但从其前后文来看,似乎是指“柘厥寺”。
伯希和的记忆也绝非是永远准确无误的。他在发掘某一残卷时,偶然将都勒都尔—阿乎尔与苏巴什相混淆,也完全在情理之中。首先是在自库车发现的大批匿名文书中,这卷文书完全有理由引起那位考古学家的高度注意,因为其中含有一个史学家们所熟悉的地名“柘厥”。此外,伯氏是一个高水平的考古学家,若发掘地有误,他立即就会想起来,绝不会使他感到“令人费解”。伯希和在苏巴什和都勒都尔—阿乎尔两个遗址的考古发掘是相继于不同时间完成的。他于苏巴什首次发现汉文写本是在6月17日,也就是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工地的发掘工程结束3周之后。对苏巴什的发掘一直是在某种很单调气氛中展开的,其发现物实在不算太多,故而伯希和才会牢固地记住了这份带有“柘厥”字样的文书。
我国新疆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将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考证为唐安西柘厥关。其重要论据之一就是伯希和发掘到的DA·M27号文书,他认为伯希和的记忆力出现了差错,误将在都勒都尔发掘到的这卷文书,归于了苏巴什名下,因而才出现了伯希和考证中的自相矛盾。我国学者有不少人也都同意王先生的观点,甚至包括某些老一辈学者在内。
童丕先生在刊布伯希和库车文书时,依据伯希和当年的观点,对于王炳华先生的考证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苏巴什出土的这卷记载“柘厥关”的汉文写本,已被多人用于为柘厥关确定地望了。王炳华先生认为伯希和将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出土的文书,记在了苏巴什的名下,从而证明伯氏将柘厥关旧址确定在苏巴什,而不是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证。《新唐书》卷43下记载:“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白马河似乎已被比定为木札提河。但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因为古代从龟兹到姑墨曾有多条道路,如其北道沿雀离塔克山麓行进;另一条是经由木扎提河南岸的路,现已被遗弃。悟空提到的东西拓(柘)厥寺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伯希和以其坚实可靠的语言学和地理学论据为基础,将柘厥关与另外两个更为古老的地名作了比较。据伯希和认为,苏巴什双寺(二伽蓝)的遗址位于今城之北的库车河两岸,分别相当于鸠摩罗什(Kumārajiva)时代的雀梨寺(C〓kri)、玄奘于630年提到的昭怙釐(Cogüri)和悟空于788年提到的柘厥。伯希和也没有忽略将悟空提到的柘厥寺与柘厥关相比较,尽管《新唐书》将柘厥关置于了龟兹绿洲的西出口。伯希和于其在苏巴什发现的纸片上读到了“至柘厥”的字样,使他茫然不知所措。尽管这次发现具有棘手的巧合,但伯希和仍极力避免将柘厥关绝对地置于了苏巴什地区,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成立的假设才提出来的。在8世纪时,于库车以北存在着一座柘厥寺,于城西存在着一座同名的关②。伯希和的结论是“不想将任何解释定为最终性的”。他仅满足于“权宜性地”接受,C〓küir的不同相近形式在龟兹语和吐火罗语中均指一关和一寺、一座窣堵波、可能还有一座烽燧。他于其论证时既未表现得专断,也绝不肤浅。伯希和在考古发掘期间,始终都认为都勒都尔—阿乎尔寺是阿奢理贰或阿遮哩贰(意为“奇迹寺”,佛教中的“奇迹”具有“化现”之意),但他也未敢最后确定。直到1934年,他仍建议将两名取经僧人提到的建筑或确定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或确定在库车河以西。
童丕先生认为,即使夏克吐尔确实位于渭干河东岸,即与都勒都尔—阿乎尔遥遥相对,那也很难像王炳华先生那样应将此地考证为柘厥关。因为该地距唐龟兹都城以西23公里处,不足于做为从龟兹都城西行(至姑墨)的第一站。夏克吐尔并不位于绿洲的出口处,而是位于向渭干河右岸深度延伸的农耕区的中心。无论DA·M27号文书是出自苏巴什,还是出自都勒都尔—阿乎尔,都无法证明在某地发现记载某一地名的文书,就断定它就是此地的名称。此外,文书中只有“柘厥”而没有具体注明是“关”还是“寺”,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王炳华先生认为,苏巴什并非是在渭干河两岸建起的唯一建筑群,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情况也应大致如此。位于渭干河西岸者,主要是宗教建筑;位于东岸者,主要是军事—行政机构,但也有宗教崇拜地点。当地的考古学家们分别称这两个遗址中的前者为夏克吐尔(爱克吐尔),后者为玉其吐尔(“吐尔”系突厥文tura的对音,指烽燧和窣堵坡,也可能是指山口)。其实,这两个建筑群具有混合用途,各自都包括行政设施和宗教建筑。这一切与许多人根据出土文书和文物而针对都勒都尔—阿乎尔提出的观点相吻合。但这种考证也并不与伯希和的观点相悖。伯希和在对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时,确实于库车河对岸发现了两个遗址,他分别称之为Hicar(爱克吐尔或夏克吐尔)和Sara〓tam(色乃当)。他仅为色乃当留下了一幅照片。伯希和对爱克吐尔作了简单的记述:“工程量很大。”城堡内部有许多小坯房。伯希和从中发现了许多壁画残片和彩塑残余:“至少有一尊菩萨像,佩戴数量多而较大的首饰。”他还在那里发现了婆罗谜文的木简与一枚建中通宝,却未提到任何汉文写本①。但在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DA·M15号文书的边缘,写有Hicar(爱克吐尔)。
伯希和在开始发掘都勒都尔—阿乎尔时,有些失望。他于4月25日在致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与地理学会主席、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首倡人和鼎力推荐伯希和的塞纳尔(E.Sénart,1847—1928)的信中,流露出了他对最初12天发掘的失望情绪:“至于我们的发掘,至今尚未向我们揭示玄奘所描绘的那种辉煌。数日期间,在所清理的僧房中,没有任何塑像或祭坛的踪迹。我一直在思考,真正的寺院到底在哪里。但在四五天之前,我们最终发现了柴泥制成的祭坛和塑像。尽管它们残损严重,但至少仍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该问题的解释。”“那些在麦秸和杏核中心间堆满了各种垃圾的僧房和小房间,向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布帛、便鞋、芦苇笔、灯盏和陶瓷片。与在图木舒克搜集到的那些文物相比较,它们的数量和品种都要丰富得多。”“我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物的平均时代,确为8世纪⋯⋯如五铢钱(汉代之后)、带有年号(开元和大历,8世纪中叶和末叶)的中国铜钱等。”①
伯希和于5月2日致塞纳尔的书信中,可以更好地解释他对玄奘法师的看法:“我开始理解了这种昔日曾使玄奘感到兴奋的豪华装饰。这里的塑像很多。如果说我们搜集到的大头佛像的风格已纯粹是某种学派的作品了。那么在次要人物的身上,却呈现更多的新奇特征。我在对一间僧房的清理时,于一个祭坛的角落中,发现了一个几乎是全裸的青年美男子彩塑。其半身已残损,很优雅地倚在右胯之上,浸透着一种希腊文化的特征。”“实在说,这种豪华多少有些粗犷,至少从我们现代人的鉴赏观点来看,正是这样的。黄金大量地闪烁,人们到处都使用了黄金,如在壁画上、彩塑上、铜器和木器上,一概如此。尽管那些皈依了伊斯兰教信仰的当地居民,曾大肆地搜刮过这些金叶,现在仍残留有大量的痕迹。即那些经过巧妙设计、精心雕刻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木雕像,它们也身穿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我们在8天便找到了数躯这样的雕像。”②
伯希和探险团对于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地点:佛寺、院子和大门、中心院、宗教圣址、僧房的跨院和第二道门口、主塔和后部小院、木版印刷的雕板处、东北建筑及其宗教设施、大甬道与西北的窣堵坡等。
通过伯希和探险团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现的汉文文书及古钱币,促使伯希和对它们作出了8世纪的断代。该遗址可能是于9世纪时突然停止了活动,因为在许多发掘点都发现了火灾的痕迹。某些绘画的涂金层已被人为刮去,说明在火灾之前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抢劫,“藏经楼”中的写本也因此而四处失散。尽管遗址中出土了许多五铢钱,但我们却很难为这些建筑群的形成期作出准确断代,因为五铢钱于西域至少一直流通到唐初。从公元4世纪起,佛教的宗教功能于龟兹日益多样化。那里出现了带有中心大院、跨院和相继装修的佛寺,而且其数量也都会很多。都勒都尔—阿乎尔的佛寺布局,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犍陀罗佛寺很相似。都勒都尔—阿乎尔的窣堵坡和主要僧伽蓝,都是经过院子的中门而与大院相通。僧伽蓝跨院四周均由僧房簇拥。
总之,都勒都尔—阿乎尔佛寺的最早核心,可能属于一组具有相当规模的佛教建筑,其扩大是随着佛教在龟兹的神奇发展而逐渐完成的。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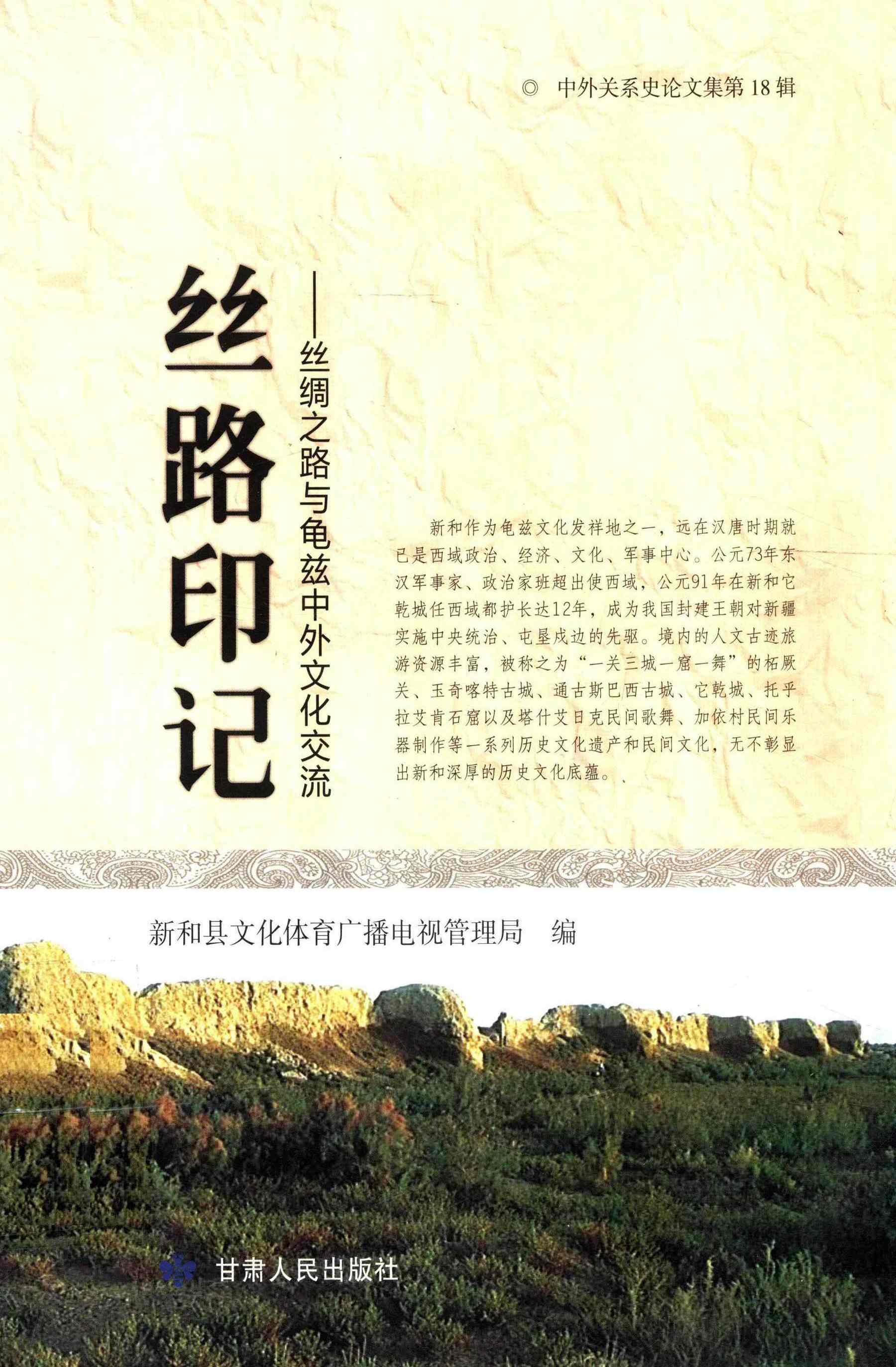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的24篇优秀论文,主要围绕古龟兹文化传统、龟兹文化与丝绸之路、汉唐屯田文化等课题展开论述,探讨了龟兹文化在中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并为进一步研究和发掘古龟兹文化,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阅读
相关地名
新和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