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对库车地区的考察成果
| 内容出处: |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4842 |
| 颗粒名称: | 伯希和对库车地区的考察成果 |
| 分类号: | K203 |
| 页数: | 20 |
| 页码: | 8-27 |
| 摘要: |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殖民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大行分割的同时,又掀起一场赴西域探险考古的热潮。伯希和探险团于1906年6月15日离开巴黎,踏上了漫长的3年西域探险考察之路。殊知这次考察,竟成了外国人在西域探险考察的重大事件。伯希和西域探险团于1906年9月6日到达喀什,在喀什及其附近地区停留了大约6周左右的时间。他们一行于6月10日至7月25日,又对苏巴什作了发掘,也获得了彩绘木盒、雕塑供像与壁画残片等。它们至今仍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巴黎。 |
| 关键词: | 新和县 丝绸之路 考察成果 |
内容
一、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库车地区考古发掘概况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殖民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大行分割的同时,又掀起一场赴西域探险考古的热潮。法国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科学院和公共教育部的资助下,由法国商业地理学会、法国亚洲委员会和自然史博物馆等单位的赞助,也派出了由伯希和率领的西域探险团,赴西域探宝、掠物、调查资料、查访民情、绘制地图、考察地理和气象测量。伯希和探险团于1906年6月15日离开巴黎,踏上了漫长的3年西域探险考察之路。殊知这次考察,竟成了外国人在西域探险考察的重大事件。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于1906年9月6日到达喀什,在喀什及其附近地区停留了大约6周左右的时间。由于成果不尽人意,他们一行于同年10月17日出发赴库车地区,1907年1月2日到达库车。他们的计划是首先考察库木吐拉(Kumtura)千佛洞,然后是考察位于渭干河以西平原中的都勒都尔-阿乎尔(Douldour-Aqour),最后再前往苏巴什(Soubachi)。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3月16日至5月22日在库木吐拉停留,然后又前后交叉地发掘了都勒都尔-阿乎尔(4月17日至8月5日),绘制了一幅考古遗址平面图,发掘出土了各种文字的写本,特别是9世纪之前的梵文和婆罗谜文写本或木简。此外还有供像遗物和木雕像、各种钱币、各类装饰物。但伯希和在这里获得的最令他满意的发掘成果,还是那些死文字的写本,特别是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龟兹文写本。他们一行于6月10日至7月25日,又对苏巴什作了发掘,也获得了彩绘木盒、雕塑供像与壁画残片等。它们至今仍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巴黎。
伯希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我国新疆的西方探险家中的资深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精通西域的几乎所有语言文字。他随身携带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刚出版不久的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在敦煌还专门利用县衙中收藏的雕版而亲自印制了一套《敦煌县志》。他以这些汉文史籍为其作地理、文献和民族学考证的依据,从而保证了其科考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玄奘于630年经过屈支(库车)国,并对昭怙釐二伽蓝作了描述。伯希和根据玄奘的生动记述,曾对该地区的考古发掘寄托了很大希望。伯氏将都勒都尔—阿乎尔寺和苏巴什宗教双城分别比定为阿奢理贰(屈支语,意为“奇迹”。但伯希和认为应读作“阿奢理腻”)大寺和昭怙釐二伽蓝。历史证明,其考证是正确的。
1907年5月28日星期二,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度过了其29岁的生日。正如他于1908年5月28日在敦煌度过其30岁的生日一样。这一天,他们基本完成了对该遗址的发掘,清理了最后一个垃圾坑,获得了一大批文书残卷。
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6月10日到达苏巴什,一直逗留到7月24日。这个考古点位于库车以北15公里左右的地方,地处雀离塔格山脚下和库车河出口处。各占地近一公里的昭怙釐寺二伽蓝便分别位于该河的两岸。在西域,于一条河两岸建同一寺,似为惯例。
伯希和为我们留下了分别写于1907年4月17日至6月4日和6月6日至18日的两部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的考古笔记,详细记载了他们每天的发掘工作和所获文物的情况①,它为后人研究这批文物和文书,提供了时间和地点坐标。
伯希和一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每天平均雇佣25名民工,在苏巴什最多时每天要动用67名民工(6月12日星期三),对所有遗址都作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伯希和根据所发掘到的文书和钱币铭文,而将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断代为初建于公元4世纪,活跃于8世纪,废弃于11世纪。在苏巴什的“壁画屋”中,伯希和对于壁画各部分的人物姿态、服饰、发型、首饰、头冠、飘带、乐器、金刚与钵瓶、装饰图案、建筑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
伯希和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带回法国的物品,现在均收藏于巴黎集美博物馆。其中主要有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壁画、粘土和陶土塑像残片、木制品、建筑木材、活动木制装饰品、金属品、玻璃制品、印鉴、陶器和杂物。属于苏巴什的则有木制品、金属和其他原料的制品、陶器和骨灰盒等。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于库车地区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发掘到的中国考古文物,已经由阿拉德等人公布,收入1982年出版的《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②(法兰西学院版)一书中了。其中公布和研究的壁画有22个号、粘土—陶土—柴泥雕塑38个号、木雕品31个号、考古木料7个号、活动装饰木制品55个号、玻璃和钱币等杂物7个号、印鉴6个号、金属物品15个号、陶器37个号、骨灰盒(瓮)5个号。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库车周围诸遗址所发掘到的文物,已由玛雅尔夫人(MoniqueMaillard)和彼诺(GeorgesPinault)等人,于1987年发表在《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文题记》(法兰西学院版)③一书中了,它们基本上是以克孜尔尕哈(Qyzyl-Qargha)为中心地区的资料。书中公布并研究了壁画残片5个号、柴泥和烧陶雕塑2个号、杂物20个号、柴泥碑2个号、浮雕2个号、土木建筑寺庙和岩窟千佛洞内物品12个号、各小遗址中的物品6个号、金属品26个号、各种材料的物品9个号。
伯希和在库车地区获得了所谓“吐火罗文(龟兹文)”文书,即被他称为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文书,另外还有这种文字的某些木简和题记等。它们主要出自库车地区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和图木舒克。事实上,这其中主要是“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语,特别是P.35339文书。法国早期东方学家烈维、菲利奥札以及德国吐火罗语专家西格等人都曾对它们作过研究。近年来,法国的新一代优秀吐火罗语学家彼诺陆续而又比较系统地刊布和研究了这批写本。伯希和特藏中的龟兹文写本共2000件左右。旧日编ASI-19,共14件文书126个编号;新编1-508和某些残卷,共527件文书;此外还有某些只有数平方厘米的极小残卷,即新编509-1166号,共658件文书;还有些被粘贴在卡片上的文书小残片393个编号。
伯希和在库车地区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到的汉文文书,已于2000年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童丕先生发表,共发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特藏DA·M中的249个号,共212件文书,其中只有12卷文书出自苏巴什,其余均出自都勒都尔—阿乎尔。此外还有收入伯希和龟兹文特藏中的两件文书。这就是童丕于2000年出版的《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法国国家图书馆特藏》一书①。本文正是根据童丕先生公布的文献和所作的背景介绍,而作评介论述的。
当然,伯希和西域探险团还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档案,绝大部分尚有待于整理刊布。伯希和的大弟子韩百诗(LouisHambis,1906—1978)在世时,曾雄心勃勃地制订规划,打算共出版27卷伯希和西域探险团档案。但在实际运作中,这项浩大工程进展缓慢,近40年间,才出版廖廖数卷。但在已出版的9卷中,库车及其附近地区,却占据了6卷之多。由此可见库车地区在伯希和西域探险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由此便可以看到,库车地区是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点重点考察的目标,其成果虽不及在敦煌那样丰硕和影响深远,却也格外令人瞩目,成了“龟兹学”的源头之一。
伯希和为什么会对库车地区如此感兴趣呢?作为一名资深汉学家,伯氏深知,库车地区历史上就是新疆自然资源最丰富和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之一。其地域由南至北为200公里左右,由东至西约100多公里。这里具有海拔7000多米高的巍巍山峰(阿克苏以北的天山);既有冰川和常年积雪(海拔4500多米)的天山山麓,又有热浪滚滚的“沙漠大火炉”(最南部的沙雅,海拔仅950米)。这种稀见的地势、地貌造就了该地区风景的多样化和资源的丰富化。首先是其丰富的矿藏资源,包括铜、铁、铅、氯化铵、硫、雄黄、铅白,特别是天燃气与石油。《魏书》和《北史》等中国史籍都对这一切有详细记述①。但最重要的是龟兹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它雄踞于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地带,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这里在历史上虽然也使用中国中原铜钱,而更多地是使用金银币,由此可见其富裕程度。虽然伯希和一行到达库车要晚于德国人,但他始终坚信会在库车有重大发现,事实也证明了其预感。
当伯希和携其同伴——地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专家路易瓦杨(LouisVaillant)与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Nouette)于1907年1月2日抵达库车时,发掘考察了克孜尔与库木吐拉的德国探险团刚刚满载而去。此后,伯希和一行便于库车地区停留8个月,是历时3年多的法国西域探险团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敦煌停留的时间——4个月,尽管他们在敦煌的所获远远超过了库车。伯希和等考察发掘的重点,当然是都勒都尔—阿尔乎和苏巴什。在1906—1907年的“窝冬”期间,伯希和希望通过实地考察,而印证自郦道元《水经注》和当时刚出版的李光廷《汉西域图考》中对此地的记载;他特别对玄奘法师于630年经由屈支时留下的记述感兴趣。经过仔细斟酌之后,伯希和等在库车地区的考察方案
才最终确定下来:“我们将首先前往库木吐拉,那里有装饰着壁画的石窟,开凿于俯瞰木扎提河(渭干河,Mouzart)即将流出雀离塔克山(Tch〓l-tagh)山口左岸的山崖上。那里同时还有都勒都尔—阿乎尔大寺的遗址。此后,我们将前往苏巴什(Soubachi,本意为“水流的发源地”),那里位于库车河两岸,同样也有两座大寺的遗址。其后,我们将前往深山旷野之中,考察库车以北那蕴藏量丰富的矿区。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我们还将考察使该地区通向裕勒都斯河流域的道路。在该河谷的天山脚下,居住着蒙古部族的人。①”此外,伯希和还希望拥有一幅从库车绿洲和沙雅绿洲直达塔里木盆地的尽可能详尽的地图。
从1907年开春起,伯希和探险团便将其大本营设立在库木吐拉,以便对该绿洲西部进行发掘考察,也就是木扎提河(渭干河)流域的部分地带。他们于3月16日至5月22日逗留在该地区,首先考察该河东岸的石窟寺,尽管德国考察团已经在那里捷足先登了,接着才考察位于库车河彼岸的都勒都尔—阿乎尔佛寺群遗址。德国人在那里只作过草率的考察,伯希和决定于此作系统的发掘,从4月17日一直持续到5月28日。6月初,探险团移师于苏巴什,并在那里一直停留到7月24日。苏巴什位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库车地区的另一端,地处库车东北约15公里处,出自雀离塔克山的库车河正流经那里。
同年7月24日,伯希和与瓦杨离开了苏巴什,沿库车河逆流而上,进入了深山中。他们考察了位于天山、雀离塔克山和北部的阿尔金山的支脉。瓦杨统计到了大批金、铜、煤、石油和氯化铵等珍贵矿藏的矿脉,它们很久以来就被当地人粗放地开采。伯希和继续向北前进,通过那些羊肠小道而直抵裕勒都斯河上游,蒙古牧民们占据了这片遍布湖泊、牧场和森林的地域,那里对于库车的防卫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伯希和又从渭干河的支流克孜勒河上游河谷出发,考察了通向科克苏河(K〓k-SOU,清水河)流域的两条道路,也就是将塔里木盆地与伊犁河流域连接起来的道路。他发现那些灌溉库车绿洲的河流——木扎提河与库车河均流向了塔里木盆地,而作为伊犁河小支流的科克苏河则注入了巴尔喀什湖。伯氏在第二条道路上发现了东汉永寿四年(158年)的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的刻石。在离开大本营整个一个月之后,即8月24日,伯希和终于返回了库车。他在图木舒克和库车发掘到的文物,已经装满了整整的14大车①,准备取道运回巴黎。
二、伯希和西域探险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古发掘
德国考古学家们主要是在克孜尔和吐木库拉作了考古发掘。伯希和一行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进行发掘时,在一个月期间,曾与俄国考古学家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y)同时相伴为邻地工作。
当伯希和探险团将其大本营扎在库木吐拉后,便于4月17日开始对都勒都尔—阿乎尔进行发掘。伯希和的考古发掘日记已经摘录发表于由哈拉德等人编辑的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以一书中了。
资深史语学家伯希和觉得,虽然图木舒克的出土文物甚多,不过开始时文字文献却甚少,但都勒都尔—阿乎尔却未使他失望。他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出土了大批文书残卷,主要是用婆罗谜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龟兹文)文书与汉文文书。伯希和最早的发掘主要是集中在围绕着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东北跨院的住宅一带展开的。
伯希和4月17日至25日的考古笔记,详细记述了他们的发现:梵文和婆罗谜文写本、五铢钱、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直到4月25日,他们才首次发掘了一批写本,但“几乎所有写本都是婆罗谜文字母写成的,没有一行汉字”②。同一天,他却从“其他发掘点上”(应为萨玛克村,Samaq)发掘到了一卷重要文书,其中出现了“明威镇”和“凉州”这样的历史地名。这就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特藏DA·M第114号文书。
5月28日,星期二,伯希和于其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度过自己29岁的生日。我们已完成了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6月4日,星期二,伯希和对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作了初步总结:“我们于此(都勒都尔—阿乎尔)度过的时间基本与在图木舒克的停留期相同。我们的收获物不算很丰富,但总的来说,我对此仍深表满意,因为我们获得了丰富的写本文献。我们可能会在苏巴什对我至今无法解决的一个谜找到答案:为什么在图木舒克会有那样多保存完好的塑像,却没有写本呢?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我们却发现了如此之多的写本,却仅有少许破碎的塑像残片呢?①”
事实上,伯希和于4月25日的考古日记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部分解释。在图木舒克,熊熊大火可能烧得很旺盛,并且过火面很广。其结果是烧焦了许多用粘土模制成的浅浮雕,从而使它们得以留传下来了。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有些完整的住宅区都幸免了火灾,或者是火势不旺,既未使塑像和线浮雕被烧成烧陶制品,又使许多写本被部分地保存下来了。因为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出土的许多纸片上,都带有被火烧焦的痕迹。
伯希和探险团在库车发掘到的汉文文书,与他们在敦煌或吐鲁番发现的那些文书大相径庭。敦煌文书是经人精心地藏匿在藏经洞中的,内容杂乱,自封洞之后再未遭人为翻动和破坏。吐鲁番文书是在墓葬中发现的,每个墓中出土的文书断代和来源一目了然,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家族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相吻合,而且有墓砖为证。都勒都尔—阿乎尔文献的保存状态却甚为恶劣,它们既未被封存在石窟寺中,也未被陪葬于墓葬内,而是在探方中被挖掘出土的。它们在公元8世纪末叶或9世纪初叶被遗弃之前,曾经遭受抢劫和焚烧,又曾遭到先于伯希和到达库车地区的其他外国考古探险团的大肆劫掠。这批文书残损严重,难觅完整的写本,极其稀见完整的文书。此外,这批文书来源复杂,不同时代与不同主人的文书,互相混杂在一起,从而使人考证起来甚难。
至于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写本的断代问题,它们与同时发掘到的钱币的时代大体相一致。这一切都证明了伯希和从其发掘一开始,就曾作出的假定:“我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所获文物的平均时代为8世纪。①那些文书(大都为用婆罗谜文字母写成的)是分别于多处不同地点发掘到的,虽然分散地面很广,却也大都集中在“寺院藏经楼”附近。写本的这种分散性说明,所谓寺院被焚烧之前曾遭抢劫,并非致因的唯一的解释。伯希和主要发掘的地点有“寺院藏经楼”、“西北部的窣堵坡”、门口和垃圾堆,它们彼此距离都相当远,我们很难想象这批文书是出自遭抢劫之前的同一地点,更应该认为它们原来就是被化整为零地收藏的。这批文书的内容纷繁:既有宗教文献,又有私人书信,特别是具有原始籍账与行政文书;世俗文书也不像在敦煌那样抄在写经的背面,而所有文书基本上都是单面抄写,并未被两面使用。
1907年4月17日至22日,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地区的发掘,主要集中在围绕东北跨院的僧房一线。他于其中的一座建筑中,发现了一批明显是非宗教文献的婆罗谜文写本,而且很可能是寺院籍账,其中只有一叶汉文的宗教文书。其他所有汉文宗教写本,大都是由伯氏等从5月23日起,在北部窣堵波大院中发掘出土的。其实,从4月17日起,伯希和一行同时于多处展开发掘,其汉文文书残叶大都为账目,而且都是世俗人的账目,发掘自“混合有厩肥的垃圾堆中”。属于军事机构的DA·M第119号(或DA·M132号)文书是于4月24日在西北段,于一个与外院墙相毗邻的房子中发掘到的。另一件军事文书(DA·M114号)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是于4月25日,当伯希和等集中力量清理“藏经楼”时,才被发现的,但它却出自另一片探方。他们于4月26日之后,所发掘到的非宗教婆罗谜文与汉文文书,也不是出自其主要发掘点,而是出自对萨玛克村的发掘,地处主要发掘点的东端。一份呈西域都护的请状(DA·M91号文书)出自一座建筑物内,该建筑虽紧傍窣堵波北部的建筑群,却又不属于该建筑群。在伯希和于其考古笔记中未加具体确定的一个发掘点上,出土了大批汉文文书,但其地点必然位于大门口附近。汉文文书不会出自伯希和的主要发掘点——宗建设施中,如精舍、窣堵波和其他宗教崇拜地,虽然这些遗址由于其中的艺术作品而特别吸引考古学家们的目光。那些汉文写本主要出土于佛寺群的周边地带。这一切必然会使人联想到,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不仅是僧侣们举行仪轨法事的建筑,而且还是由文职官府机构占据的设施。世俗建筑一般均建于佛寺的周围,也有两类建筑互相交错的例证。世俗文书的时代几乎覆盖了整个8世纪,而没有任何一件宗教文献载有确切的时间。它们也很有可能是于佛寺不复存在之后,由中原士兵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军镇的原因所造成的。现在基本可以肯定,都勒都尔—阿乎尔的佛寺与行政官衙毗邻而居,并于同一时代行使各自的功能①。但我们尚不能充分肯定,这里就是悟空师(法界)当年入竺时所经过的地方。因为悟空当年曾经由耶婆瑟鸡寺②、东西拓(柘)厥寺和阿遮哩贰寺。伯希和当年特别倾向将都勒都尔—阿乎尔考证为玄奘法师所提到的阿奢理贰(阿遮哩贰)伽蓝。他于193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的《吐火罗语和龟兹语》一文中,烈维(S、Lévi)于1913年于《亚细亚学报》发表的《乙种吐火罗语—龟兹语》中,都曾作过类似考证③。季羡林先生等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也采用了此说④。据悟空的记载,东西拓(柘)厥寺与阿遮哩贰明显为两地。玄奘认为阿奢理贰伽蓝“位于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式旌美迹,传芳后叶”。伯希和认为“阿奢理贰”应为“阿奢理腻”之误,因为“贰”字的古音可能为“ni”(腻)⑤。
《新唐书》卷43记载有:“安西西出柘厥关。”其他中文史料中也作“柘厥”,西方汉学家一般均拼音作Zhejue。悟空作“拓厥寺”。“拓”与“柘”号字形相似,而又绝不通假。况且,“拓厥”或“柘厥”是龟兹语的汉文对音。伯希和探险团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到的汉文文书DA·M80号是一份报告(其录文略)。所以,伯希和在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地望作考证时,更多地是坚持“阿奢理腻伽蓝”,从未将此地考证为“柘厥关”。
尽管伯希和在库车地区的考古笔记本中,包括6月19日至7月末的一册早已丢失。但伯希和于其1934年发表的《吐火罗语和龟兹语》①一文中,他尚记得自己发掘到的一卷写本,即DA·M27号文书:“我于1907年曾发掘到一片残纸,可现在已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了,但我很准确地记得于其中读到了‘至柘橛(厥)’的记载。非常遗憾的是再无其他说明,但我于苏巴什西部废墟中搜罗到了其中提到‘柘厥’的这件残卷,也就是说是在西柘厥寺的遗址上发现的。这种巧合令人费解。”因为伯希和似乎将苏巴什西部考证为柘厥寺了,故而他认为不可能从“柘厥”再到柘厥了。但文书中只残存“柘厥”二字,未明确指出是“关”还是“寺”。但从其前后文来看,似乎是指“柘厥寺”。
伯希和的记忆也绝非是永远准确无误的。他在发掘某一残卷时,偶然将都勒都尔—阿乎尔与苏巴什相混淆,也完全在情理之中。首先是在自库车发现的大批匿名文书中,这卷文书完全有理由引起那位考古学家的高度注意,因为其中含有一个史学家们所熟悉的地名“柘厥”。此外,伯氏是一个高水平的考古学家,若发掘地有误,他立即就会想起来,绝不会使他感到“令人费解”。伯希和在苏巴什和都勒都尔—阿乎尔两个遗址的考古发掘是相继于不同时间完成的。他于苏巴什首次发现汉文写本是在6月17日,也就是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工地的发掘工程结束3周之后。对苏巴什的发掘一直是在某种很单调气氛中展开的,其发现物实在不算太多,故而伯希和才会牢固地记住了这份带有“柘厥”字样的文书。
我国新疆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将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考证为唐安西柘厥关。其重要论据之一就是伯希和发掘到的DA·M27号文书,他认为伯希和的记忆力出现了差错,误将在都勒都尔发掘到的这卷文书,归于了苏巴什名下,因而才出现了伯希和考证中的自相矛盾。我国学者有不少人也都同意王先生的观点,甚至包括某些老一辈学者在内。
童丕先生在刊布伯希和库车文书时,依据伯希和当年的观点,对于王炳华先生的考证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苏巴什出土的这卷记载“柘厥关”的汉文写本,已被多人用于为柘厥关确定地望了。王炳华先生认为伯希和将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出土的文书,记在了苏巴什的名下,从而证明伯氏将柘厥关旧址确定在苏巴什,而不是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证。《新唐书》卷43下记载:“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白马河似乎已被比定为木札提河。但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因为古代从龟兹到姑墨曾有多条道路,如其北道沿雀离塔克山麓行进;另一条是经由木扎提河南岸的路,现已被遗弃。悟空提到的东西拓(柘)厥寺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伯希和以其坚实可靠的语言学和地理学论据为基础,将柘厥关与另外两个更为古老的地名作了比较。据伯希和认为,苏巴什双寺(二伽蓝)的遗址位于今城之北的库车河两岸,分别相当于鸠摩罗什(Kumārajiva)时代的雀梨寺(C〓kri)、玄奘于630年提到的昭怙釐(Cogüri)和悟空于788年提到的柘厥。伯希和也没有忽略将悟空提到的柘厥寺与柘厥关相比较,尽管《新唐书》将柘厥关置于了龟兹绿洲的西出口。伯希和于其在苏巴什发现的纸片上读到了“至柘厥”的字样,使他茫然不知所措。尽管这次发现具有棘手的巧合,但伯希和仍极力避免将柘厥关绝对地置于了苏巴什地区,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成立的假设才提出来的。在8世纪时,于库车以北存在着一座柘厥寺,于城西存在着一座同名的关②。伯希和的结论是“不想将任何解释定为最终性的”。他仅满足于“权宜性地”接受,C〓küir的不同相近形式在龟兹语和吐火罗语中均指一关和一寺、一座窣堵波、可能还有一座烽燧。他于其论证时既未表现得专断,也绝不肤浅。伯希和在考古发掘期间,始终都认为都勒都尔—阿乎尔寺是阿奢理贰或阿遮哩贰(意为“奇迹寺”,佛教中的“奇迹”具有“化现”之意),但他也未敢最后确定。直到1934年,他仍建议将两名取经僧人提到的建筑或确定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或确定在库车河以西。
童丕先生认为,即使夏克吐尔确实位于渭干河东岸,即与都勒都尔—阿乎尔遥遥相对,那也很难像王炳华先生那样应将此地考证为柘厥关。因为该地距唐龟兹都城以西23公里处,不足于做为从龟兹都城西行(至姑墨)的第一站。夏克吐尔并不位于绿洲的出口处,而是位于向渭干河右岸深度延伸的农耕区的中心。无论DA·M27号文书是出自苏巴什,还是出自都勒都尔—阿乎尔,都无法证明在某地发现记载某一地名的文书,就断定它就是此地的名称。此外,文书中只有“柘厥”而没有具体注明是“关”还是“寺”,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王炳华先生认为,苏巴什并非是在渭干河两岸建起的唯一建筑群,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情况也应大致如此。位于渭干河西岸者,主要是宗教建筑;位于东岸者,主要是军事—行政机构,但也有宗教崇拜地点。当地的考古学家们分别称这两个遗址中的前者为夏克吐尔(爱克吐尔),后者为玉其吐尔(“吐尔”系突厥文tura的对音,指烽燧和窣堵坡,也可能是指山口)。其实,这两个建筑群具有混合用途,各自都包括行政设施和宗教建筑。这一切与许多人根据出土文书和文物而针对都勒都尔—阿乎尔提出的观点相吻合。但这种考证也并不与伯希和的观点相悖。伯希和在对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时,确实于库车河对岸发现了两个遗址,他分别称之为Hicar(爱克吐尔或夏克吐尔)和Sara〓tam(色乃当)。他仅为色乃当留下了一幅照片。伯希和对爱克吐尔作了简单的记述:“工程量很大。”城堡内部有许多小坯房。伯希和从中发现了许多壁画残片和彩塑残余:“至少有一尊菩萨像,佩戴数量多而较大的首饰。”他还在那里发现了婆罗谜文的木简与一枚建中通宝,却未提到任何汉文写本①。但在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DA·M15号文书的边缘,写有Hicar(爱克吐尔)。
伯希和在开始发掘都勒都尔—阿乎尔时,有些失望。他于4月25日在致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与地理学会主席、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首倡人和鼎力推荐伯希和的塞纳尔(E.Sénart,1847—1928)的信中,流露出了他对最初12天发掘的失望情绪:“至于我们的发掘,至今尚未向我们揭示玄奘所描绘的那种辉煌。数日期间,在所清理的僧房中,没有任何塑像或祭坛的踪迹。我一直在思考,真正的寺院到底在哪里。但在四五天之前,我们最终发现了柴泥制成的祭坛和塑像。尽管它们残损严重,但至少仍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该问题的解释。”“那些在麦秸和杏核中心间堆满了各种垃圾的僧房和小房间,向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布帛、便鞋、芦苇笔、灯盏和陶瓷片。与在图木舒克搜集到的那些文物相比较,它们的数量和品种都要丰富得多。”“我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物的平均时代,确为8世纪⋯⋯如五铢钱(汉代之后)、带有年号(开元和大历,8世纪中叶和末叶)的中国铜钱等。”①
伯希和于5月2日致塞纳尔的书信中,可以更好地解释他对玄奘法师的看法:“我开始理解了这种昔日曾使玄奘感到兴奋的豪华装饰。这里的塑像很多。如果说我们搜集到的大头佛像的风格已纯粹是某种学派的作品了。那么在次要人物的身上,却呈现更多的新奇特征。我在对一间僧房的清理时,于一个祭坛的角落中,发现了一个几乎是全裸的青年美男子彩塑。其半身已残损,很优雅地倚在右胯之上,浸透着一种希腊文化的特征。”“实在说,这种豪华多少有些粗犷,至少从我们现代人的鉴赏观点来看,正是这样的。黄金大量地闪烁,人们到处都使用了黄金,如在壁画上、彩塑上、铜器和木器上,一概如此。尽管那些皈依了伊斯兰教信仰的当地居民,曾大肆地搜刮过这些金叶,现在仍残留有大量的痕迹。即那些经过巧妙设计、精心雕刻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木雕像,它们也身穿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我们在8天便找到了数躯这样的雕像。”②
伯希和探险团对于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地点:佛寺、院子和大门、中心院、宗教圣址、僧房的跨院和第二道门口、主塔和后部小院、木版印刷的雕板处、东北建筑及其宗教设施、大甬道与西北的窣堵坡等。
通过伯希和探险团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现的汉文文书及古钱币,促使伯希和对它们作出了8世纪的断代。该遗址可能是于9世纪时突然停止了活动,因为在许多发掘点都发现了火灾的痕迹。某些绘画的涂金层已被人为刮去,说明在火灾之前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抢劫,“藏经楼”中的写本也因此而四处失散。尽管遗址中出土了许多五铢钱,但我们却很难为这些建筑群的形成期作出准确断代,因为五铢钱于西域至少一直流通到唐初。从公元4世纪起,佛教的宗教功能于龟兹日益多样化。那里出现了带有中心大院、跨院和相继装修的佛寺,而且其数量也都会很多。都勒都尔—阿乎尔的佛寺布局,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犍陀罗佛寺很相似。都勒都尔—阿乎尔的窣堵坡和主要僧伽蓝,都是经过院子的中门而与大院相通。僧伽蓝跨院四周均由僧房簇拥。
总之,都勒都尔—阿乎尔佛寺的最早核心,可能属于一组具有相当规模的佛教建筑,其扩大是随着佛教在龟兹的神奇发展而逐渐完成的。
三、伯希和探险团对苏巴什的考古发掘
伯希和探险团从1907年6月17日开始,对苏巴什宗教双城(二伽蓝)作了一次考古发掘,整整持续1个月的时间。由于这片遗址面积辽阔,所以这样的期限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伯希和从1907年春季起,也就是当他尚滞留于库车时,便对苏巴什周围环境作了仔细考察和测量。从而使他得出结论认为,从其地望来看,苏巴什宗教(寺院)双城只能是玄奘于《西域记》中记载的“昭怙釐二伽蓝”。昭怙釐应为梵文Coriot的汉译,此名可能借鉴自自沙瓦附近著名的迦腻色迦时代之佛寺“雀离”大寺的名称。此寺也就是《水经》中所引证的释氏《西域记》中的雀离大清净寺。伯希和一行刚开始时的工作也并不太顺利。他于1907年1月29日致塞纳尔的信中,列举了自己到达库车后的初步调查结果。他针对苏巴什废墟而写道:“仅仅瞥去一眼,便使我坚信,这里确为玄奘所熟悉并作过生动描述的地方,即昭怙釐大寺。该寺院很古老了,因为在玄奘之前很久,《水经注》中就已经提到该寺了。事实上,位于苏巴什河两岸的这两座寺院留下的废墟,是我自到什喀尔地区之后,所见到的规模最宏伟者。东昭怙釐寺与西昭怙釐寺各自延伸于近一公里长的地方,拥有有时会达到10米高的建筑物,尚且不讲那些仍在多处未曾遭损地保持着其原状的窣堵波。全部建筑均以土坯筑成,最多见的是使用生土坯,当然都露天,现已看不到绘画和涂层的踪迹了。”日本人曾先于伯氏而于此地发掘,但只找到一双便鞋。伯希和本来希望测绘一幅详细的平面图①。伯希和当时已经获知,当时在库车市场上出售的所有印鉴和钱币,均是自这里流散出去的。
伯希和等人的发掘,于7月10日之后仅仅持续两三天,他于7月10日致塞纳尔的信中更流露出了其失望情绪:“对昭怙釐寺的发掘刚刚基本结束,未能提供我本来所期待得到的东西。我于此搜集到的几件木雕,大致属于都勒都尔—阿乎尔那些同类文物的类别,远不如图木舒克的那些精致。至于写本,我们仅获得几种婆罗谜文、汉文,甚至是回鹘文的小片残卷。②”伯希和等共有3次发现了藏钱的钱窑,每次都有数千枚五铢钱出土。他们在大河的西部和北部大山最前面的几条支脉中,又发现了许多写本残卷和洞窟中的游人题记。因为伯希和的考察笔记本遗失了一册,所以其记述只到6月18日便中断了,从而使人无法解释瓦杨的测绘图了。由于苏巴什遗址面积广阔,伯希和探险团人手很少,而且时间又紧迫,所以他们只能零散地进行发掘,其重点就在于搜寻写本。伯希和等人对大河东西两岸,均未测绘出完整的平面图。
苏巴什的佛教遗址与伯希和过去考察过的图木舒克和都勒都尔—阿乎尔完全不同。苏巴什是一种具有某种整体性的建筑。那里的日常居舍、僧房及其附属设施,似乎都属于一个原有的中心,围绕着它而逐渐扩展。苏巴什的宗教双城位于库车河的东西两岸。其建筑物的种类、规模和布局,都会使人联想到于其城墙内集中了不同的建筑,而又能使其中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彼此独立地生活。在东部主体建筑的周围,现在尚可以辨认出庞大的军镇遗址,沿山麓于遥远的地方就能清晰地看到它们。
伯希和探险团在苏巴什西部的地基上,分别考察了大院子、大墓葬、北部窣堵波、僧房、烟囱房和西部大窣堵波;于东部的地基上,他们考察了院子遗址、西南窣堵波和东北窣堵波;
在库车河西岸的石窟中,他们又发现了某些婆罗谜文写本;在宗教双城中,他们特别考察了“壁画屋”。
四、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的概况
童丕先生整理、刊布和译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汉文写本。这实际上是在我国学者张广达先生的帮助下才完成的。
伯希和自库车携归的汉文写本特藏由249个号的212件文书(1-156、157.1-7、201-249号,有些文书后来被撕破成数片)组成,从而形成了DA·M,即“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另外有两件文书则被编入了“伯希和龟兹文特藏”中,尽管它们是用汉文写成的,这是一组总共为44件文书[编号为DA·M(即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507号]中的第31和32号。这样一来,全部特藏中总共有214件文书,其中18件已被断代或拥有能令人作出断代的明确标志。其中年代最早者可上溯到690—705年(DA·M52号文书),因为武后新字行用于这段时间。其最晚的时代为784年(建中五年,DA·M104-106号)。在这两个上下限时间之间,写本的分布很规则。其早期(开元年间,713—741)有五六件;其晚期(760—784),也有同样的数目,其中期(742—759),有5件。由此可见,这批写本所覆盖的时代,恰恰是唐军驻扎龟兹的时代,即介于唐军于692年大破吐蕃兵和790—791年左右之间的时代。
在这批汉文写本中,只有很少的主文献纸叶背面写有与主文献没有任何关系的文字者。这说明它们在写成不久就被失散了。如果它们如同敦煌写本那样被收藏在档案处或藏经处,那么它们的背面就肯定会被重新利用,被用于书写其他内容。
在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中,除了少数12件出自苏巴什之外,其种类非常纷繁,明显出自多个不同的收藏点,遍布于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整片遗址上。但那些佛经和其他寺院文书(僧侣们的书信和账目等),却只占很少数量。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DA·M)中的宗教文献的稀见性,形成了它与出自库车地区的大谷文书之间的高度反差,因为大谷文书中有许多佛经和教义疏注文。为什么在一个伯希和认为是古寺的地方,却很少会出土佛教文献呢?考古发掘已经清楚证明,都勒都尔—阿乎尔确为一座佛寺,但其中居住的都是龟兹人而不是汉族僧众,于现场发现的那些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龟兹文写本,便充分证明了其寺院的周边和生活环境。生活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汉人主要是世俗人,大部分汉文文献均出自官府,其中有许多甚至出自于官吏们本人之手。一批为数不多的私人文书也都往往与官府有关,如某些书信(第131号)、契约(第4号)和殡葬文书(第28-30号),涉及了军镇的驻兵。很明显,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存在着一个官府和一个军镇,居住在其中的汉人是负责管理军队和来自中原的屯边戍民。
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特藏(DA·M)的另一特征,是缺乏商务文书,也没有被用于交易的商品目录;其中更没有旅行文书,如骆驼队的“过所”之类文书。这批文书中只有少数契约,而且似乎也只涉及农民之间的交易,如租地和借粮等(DA·M62号文书背面)。DA·M122号文书涉及了一次“西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龟兹人或粟特人与操汉语的人之间的交易关系。DA·M123号、130号和131号文书是由官吏或者由不以商业谋生的人书写的信件。其中提到的唯一一支骆驼队并不是商队,而是“屯家人”。龟兹城本来是一个商业很发达的地区,但DA·M中的商务文书却极其稀缺,这很可能是由于商人都居住在城内,并且在城内交易,或者是那些沙漠商队客栈均位于城市的四周。
在多种文书(如DA·M33号、47号和86号)中经常出现的“行客”一词,现在尚难以确定其义。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唐代文学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经常出现的“远行商客”。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DA·M134号文书中出现的“行军”(“行军司马”)一词,在DA·M58号和115号写本中还出现过“行客营”。这也可能与商人经常随作战部队远行有关。
在DA·M的大量的行政文书中,只有一件可以被考证为出自龟兹都督府或安西都护府最高当局(DA·M134号):“摄副使行军司马秘书少监薛”。另外至少有3件是通过各级渠道而呈奏龟兹最高当局的,两件是致安西都护府的(DA·M91号和135号):“伏望都护详察”和“都护九郎(?)阁下”;一件是致“龟兹都督府”的(DA·M83号文书残卷5)。其他的文书则向我们揭示了某些高官的尊号,却又无法使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文书的作者,还是仅仅是其收启人(DA·M37号、39号、48号、109号文书)。这些文书其实只涉及到某些琐事,却又要上奏最高当局(DA·M91号和100号文书):对粮食和食物仓库的日常管理、完成工程等。文书中经常提到马匹(DA·M
91号、101号、121号、126等号文书),以及对它们的饲养、统计、采购,而且主要是向突厥人出售(DA·M129号文书)。这些马匹大都属于地方部队(折冲府),但也被用于馆驿。它们不仅仅是中国战略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整个官府的基础(DA·M41号、76号、91号和129号文书)。其中提到的事件完全反映了驻扎在大唐帝国边陲上的那些军事机构的活动。甚至某些佛教文书,它们似乎也涉及了军人(DA·M5号文书,“因军阵损害众生”)。
在这批写本中,军事机构无所不在。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各种级别的军事单位:军镇、城、守捉、开府、镇使、游弈官、孔目官等。但当时那里似乎存在着两种结构:行军(野战军)和折冲(团练)。驻龟兹的军队似乎具有比在中国内地更为广泛的功能。他们当然负责“屯”(DA·M19和88号文书),其中的一处叫作伊利屯(DA·M19号文书背面);他们更要负责在其他地方应该属于行政职权(DA·M57号、90号、104-106号等文书)的事务。其时间最晚的一件文书是DA·M104-106号的请状。它证明,直到784年,唐朝的行政机构在龟兹的某些地区,尚在军队的控制下正常运行。
由于这些文献更多地是涉及地方事务,所以经常提到基层地区单位,如“村”(DA·M12号、95号、121号和127号)、“坊”(DA·M93号、96号、103号、134号文书)。在唐代,“村”与“坊”属于同一级别,“村”位于城市的城墙郭外;“坊”则位于城内,却又不一定具有城市的特征。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中提到了“坊”,这说明在当地就存在着与都城有别的“城”。除了“王子村”之外,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中所提到的村名,均为龟兹语的汉文译音字:“移伐姟(孩?)村”、“伊禄梅村”、“无寻苏射堤村”、“都野提黎伏陀村”和“萨波村”等。那些“坊”却相反都是汉名:“怀柔坊”、“安仁坊”与“和众坊”。这就证明,当时在坊中比在村中具有更高的汉化程度。中原人主要是集中城内,在农村则比较分散。这些坊和村中的居民,似乎更密切地依靠城市当局(DA·M93号、104号-106和134号文书)。我们由此便可以从中管见军屯的迹象,至少是有许多士兵都与其家庭生活在一起。
总之,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提供了许多方面的详细资料。它们对于研究唐代龟兹地区的历史、地理、军事、人口、语言文字、经济和行政组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殖民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大行分割的同时,又掀起一场赴西域探险考古的热潮。法国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科学院和公共教育部的资助下,由法国商业地理学会、法国亚洲委员会和自然史博物馆等单位的赞助,也派出了由伯希和率领的西域探险团,赴西域探宝、掠物、调查资料、查访民情、绘制地图、考察地理和气象测量。伯希和探险团于1906年6月15日离开巴黎,踏上了漫长的3年西域探险考察之路。殊知这次考察,竟成了外国人在西域探险考察的重大事件。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于1906年9月6日到达喀什,在喀什及其附近地区停留了大约6周左右的时间。由于成果不尽人意,他们一行于同年10月17日出发赴库车地区,1907年1月2日到达库车。他们的计划是首先考察库木吐拉(Kumtura)千佛洞,然后是考察位于渭干河以西平原中的都勒都尔-阿乎尔(Douldour-Aqour),最后再前往苏巴什(Soubachi)。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3月16日至5月22日在库木吐拉停留,然后又前后交叉地发掘了都勒都尔-阿乎尔(4月17日至8月5日),绘制了一幅考古遗址平面图,发掘出土了各种文字的写本,特别是9世纪之前的梵文和婆罗谜文写本或木简。此外还有供像遗物和木雕像、各种钱币、各类装饰物。但伯希和在这里获得的最令他满意的发掘成果,还是那些死文字的写本,特别是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龟兹文写本。他们一行于6月10日至7月25日,又对苏巴什作了发掘,也获得了彩绘木盒、雕塑供像与壁画残片等。它们至今仍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巴黎。
伯希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我国新疆的西方探险家中的资深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精通西域的几乎所有语言文字。他随身携带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刚出版不久的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在敦煌还专门利用县衙中收藏的雕版而亲自印制了一套《敦煌县志》。他以这些汉文史籍为其作地理、文献和民族学考证的依据,从而保证了其科考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玄奘于630年经过屈支(库车)国,并对昭怙釐二伽蓝作了描述。伯希和根据玄奘的生动记述,曾对该地区的考古发掘寄托了很大希望。伯氏将都勒都尔—阿乎尔寺和苏巴什宗教双城分别比定为阿奢理贰(屈支语,意为“奇迹”。但伯希和认为应读作“阿奢理腻”)大寺和昭怙釐二伽蓝。历史证明,其考证是正确的。
1907年5月28日星期二,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度过了其29岁的生日。正如他于1908年5月28日在敦煌度过其30岁的生日一样。这一天,他们基本完成了对该遗址的发掘,清理了最后一个垃圾坑,获得了一大批文书残卷。
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6月10日到达苏巴什,一直逗留到7月24日。这个考古点位于库车以北15公里左右的地方,地处雀离塔格山脚下和库车河出口处。各占地近一公里的昭怙釐寺二伽蓝便分别位于该河的两岸。在西域,于一条河两岸建同一寺,似为惯例。
伯希和为我们留下了分别写于1907年4月17日至6月4日和6月6日至18日的两部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的考古笔记,详细记载了他们每天的发掘工作和所获文物的情况①,它为后人研究这批文物和文书,提供了时间和地点坐标。
伯希和一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每天平均雇佣25名民工,在苏巴什最多时每天要动用67名民工(6月12日星期三),对所有遗址都作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伯希和根据所发掘到的文书和钱币铭文,而将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断代为初建于公元4世纪,活跃于8世纪,废弃于11世纪。在苏巴什的“壁画屋”中,伯希和对于壁画各部分的人物姿态、服饰、发型、首饰、头冠、飘带、乐器、金刚与钵瓶、装饰图案、建筑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
伯希和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带回法国的物品,现在均收藏于巴黎集美博物馆。其中主要有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壁画、粘土和陶土塑像残片、木制品、建筑木材、活动木制装饰品、金属品、玻璃制品、印鉴、陶器和杂物。属于苏巴什的则有木制品、金属和其他原料的制品、陶器和骨灰盒等。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于库车地区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发掘到的中国考古文物,已经由阿拉德等人公布,收入1982年出版的《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②(法兰西学院版)一书中了。其中公布和研究的壁画有22个号、粘土—陶土—柴泥雕塑38个号、木雕品31个号、考古木料7个号、活动装饰木制品55个号、玻璃和钱币等杂物7个号、印鉴6个号、金属物品15个号、陶器37个号、骨灰盒(瓮)5个号。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库车周围诸遗址所发掘到的文物,已由玛雅尔夫人(MoniqueMaillard)和彼诺(GeorgesPinault)等人,于1987年发表在《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文题记》(法兰西学院版)③一书中了,它们基本上是以克孜尔尕哈(Qyzyl-Qargha)为中心地区的资料。书中公布并研究了壁画残片5个号、柴泥和烧陶雕塑2个号、杂物20个号、柴泥碑2个号、浮雕2个号、土木建筑寺庙和岩窟千佛洞内物品12个号、各小遗址中的物品6个号、金属品26个号、各种材料的物品9个号。
伯希和在库车地区获得了所谓“吐火罗文(龟兹文)”文书,即被他称为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文书,另外还有这种文字的某些木简和题记等。它们主要出自库车地区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和图木舒克。事实上,这其中主要是“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语,特别是P.35339文书。法国早期东方学家烈维、菲利奥札以及德国吐火罗语专家西格等人都曾对它们作过研究。近年来,法国的新一代优秀吐火罗语学家彼诺陆续而又比较系统地刊布和研究了这批写本。伯希和特藏中的龟兹文写本共2000件左右。旧日编ASI-19,共14件文书126个编号;新编1-508和某些残卷,共527件文书;此外还有某些只有数平方厘米的极小残卷,即新编509-1166号,共658件文书;还有些被粘贴在卡片上的文书小残片393个编号。
伯希和在库车地区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到的汉文文书,已于2000年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童丕先生发表,共发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特藏DA·M中的249个号,共212件文书,其中只有12卷文书出自苏巴什,其余均出自都勒都尔—阿乎尔。此外还有收入伯希和龟兹文特藏中的两件文书。这就是童丕于2000年出版的《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法国国家图书馆特藏》一书①。本文正是根据童丕先生公布的文献和所作的背景介绍,而作评介论述的。
当然,伯希和西域探险团还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档案,绝大部分尚有待于整理刊布。伯希和的大弟子韩百诗(LouisHambis,1906—1978)在世时,曾雄心勃勃地制订规划,打算共出版27卷伯希和西域探险团档案。但在实际运作中,这项浩大工程进展缓慢,近40年间,才出版廖廖数卷。但在已出版的9卷中,库车及其附近地区,却占据了6卷之多。由此可见库车地区在伯希和西域探险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由此便可以看到,库车地区是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点重点考察的目标,其成果虽不及在敦煌那样丰硕和影响深远,却也格外令人瞩目,成了“龟兹学”的源头之一。
伯希和为什么会对库车地区如此感兴趣呢?作为一名资深汉学家,伯氏深知,库车地区历史上就是新疆自然资源最丰富和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之一。其地域由南至北为200公里左右,由东至西约100多公里。这里具有海拔7000多米高的巍巍山峰(阿克苏以北的天山);既有冰川和常年积雪(海拔4500多米)的天山山麓,又有热浪滚滚的“沙漠大火炉”(最南部的沙雅,海拔仅950米)。这种稀见的地势、地貌造就了该地区风景的多样化和资源的丰富化。首先是其丰富的矿藏资源,包括铜、铁、铅、氯化铵、硫、雄黄、铅白,特别是天燃气与石油。《魏书》和《北史》等中国史籍都对这一切有详细记述①。但最重要的是龟兹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它雄踞于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地带,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这里在历史上虽然也使用中国中原铜钱,而更多地是使用金银币,由此可见其富裕程度。虽然伯希和一行到达库车要晚于德国人,但他始终坚信会在库车有重大发现,事实也证明了其预感。
当伯希和携其同伴——地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专家路易瓦杨(LouisVaillant)与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Nouette)于1907年1月2日抵达库车时,发掘考察了克孜尔与库木吐拉的德国探险团刚刚满载而去。此后,伯希和一行便于库车地区停留8个月,是历时3年多的法国西域探险团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站,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敦煌停留的时间——4个月,尽管他们在敦煌的所获远远超过了库车。伯希和等考察发掘的重点,当然是都勒都尔—阿尔乎和苏巴什。在1906—1907年的“窝冬”期间,伯希和希望通过实地考察,而印证自郦道元《水经注》和当时刚出版的李光廷《汉西域图考》中对此地的记载;他特别对玄奘法师于630年经由屈支时留下的记述感兴趣。经过仔细斟酌之后,伯希和等在库车地区的考察方案
才最终确定下来:“我们将首先前往库木吐拉,那里有装饰着壁画的石窟,开凿于俯瞰木扎提河(渭干河,Mouzart)即将流出雀离塔克山(Tch〓l-tagh)山口左岸的山崖上。那里同时还有都勒都尔—阿乎尔大寺的遗址。此后,我们将前往苏巴什(Soubachi,本意为“水流的发源地”),那里位于库车河两岸,同样也有两座大寺的遗址。其后,我们将前往深山旷野之中,考察库车以北那蕴藏量丰富的矿区。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我们还将考察使该地区通向裕勒都斯河流域的道路。在该河谷的天山脚下,居住着蒙古部族的人。①”此外,伯希和还希望拥有一幅从库车绿洲和沙雅绿洲直达塔里木盆地的尽可能详尽的地图。
从1907年开春起,伯希和探险团便将其大本营设立在库木吐拉,以便对该绿洲西部进行发掘考察,也就是木扎提河(渭干河)流域的部分地带。他们于3月16日至5月22日逗留在该地区,首先考察该河东岸的石窟寺,尽管德国考察团已经在那里捷足先登了,接着才考察位于库车河彼岸的都勒都尔—阿乎尔佛寺群遗址。德国人在那里只作过草率的考察,伯希和决定于此作系统的发掘,从4月17日一直持续到5月28日。6月初,探险团移师于苏巴什,并在那里一直停留到7月24日。苏巴什位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库车地区的另一端,地处库车东北约15公里处,出自雀离塔克山的库车河正流经那里。
同年7月24日,伯希和与瓦杨离开了苏巴什,沿库车河逆流而上,进入了深山中。他们考察了位于天山、雀离塔克山和北部的阿尔金山的支脉。瓦杨统计到了大批金、铜、煤、石油和氯化铵等珍贵矿藏的矿脉,它们很久以来就被当地人粗放地开采。伯希和继续向北前进,通过那些羊肠小道而直抵裕勒都斯河上游,蒙古牧民们占据了这片遍布湖泊、牧场和森林的地域,那里对于库车的防卫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伯希和又从渭干河的支流克孜勒河上游河谷出发,考察了通向科克苏河(K〓k-SOU,清水河)流域的两条道路,也就是将塔里木盆地与伊犁河流域连接起来的道路。他发现那些灌溉库车绿洲的河流——木扎提河与库车河均流向了塔里木盆地,而作为伊犁河小支流的科克苏河则注入了巴尔喀什湖。伯氏在第二条道路上发现了东汉永寿四年(158年)的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的刻石。在离开大本营整个一个月之后,即8月24日,伯希和终于返回了库车。他在图木舒克和库车发掘到的文物,已经装满了整整的14大车①,准备取道运回巴黎。
二、伯希和西域探险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古发掘
德国考古学家们主要是在克孜尔和吐木库拉作了考古发掘。伯希和一行于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进行发掘时,在一个月期间,曾与俄国考古学家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y)同时相伴为邻地工作。
当伯希和探险团将其大本营扎在库木吐拉后,便于4月17日开始对都勒都尔—阿乎尔进行发掘。伯希和的考古发掘日记已经摘录发表于由哈拉德等人编辑的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以一书中了。
资深史语学家伯希和觉得,虽然图木舒克的出土文物甚多,不过开始时文字文献却甚少,但都勒都尔—阿乎尔却未使他失望。他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出土了大批文书残卷,主要是用婆罗谜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龟兹文)文书与汉文文书。伯希和最早的发掘主要是集中在围绕着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东北跨院的住宅一带展开的。
伯希和4月17日至25日的考古笔记,详细记述了他们的发现:梵文和婆罗谜文写本、五铢钱、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直到4月25日,他们才首次发掘了一批写本,但“几乎所有写本都是婆罗谜文字母写成的,没有一行汉字”②。同一天,他却从“其他发掘点上”(应为萨玛克村,Samaq)发掘到了一卷重要文书,其中出现了“明威镇”和“凉州”这样的历史地名。这就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特藏DA·M第114号文书。
5月28日,星期二,伯希和于其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度过自己29岁的生日。我们已完成了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6月4日,星期二,伯希和对他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作了初步总结:“我们于此(都勒都尔—阿乎尔)度过的时间基本与在图木舒克的停留期相同。我们的收获物不算很丰富,但总的来说,我对此仍深表满意,因为我们获得了丰富的写本文献。我们可能会在苏巴什对我至今无法解决的一个谜找到答案:为什么在图木舒克会有那样多保存完好的塑像,却没有写本呢?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我们却发现了如此之多的写本,却仅有少许破碎的塑像残片呢?①”
事实上,伯希和于4月25日的考古日记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部分解释。在图木舒克,熊熊大火可能烧得很旺盛,并且过火面很广。其结果是烧焦了许多用粘土模制成的浅浮雕,从而使它们得以留传下来了。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有些完整的住宅区都幸免了火灾,或者是火势不旺,既未使塑像和线浮雕被烧成烧陶制品,又使许多写本被部分地保存下来了。因为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出土的许多纸片上,都带有被火烧焦的痕迹。
伯希和探险团在库车发掘到的汉文文书,与他们在敦煌或吐鲁番发现的那些文书大相径庭。敦煌文书是经人精心地藏匿在藏经洞中的,内容杂乱,自封洞之后再未遭人为翻动和破坏。吐鲁番文书是在墓葬中发现的,每个墓中出土的文书断代和来源一目了然,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家族及其所生活的时代相吻合,而且有墓砖为证。都勒都尔—阿乎尔文献的保存状态却甚为恶劣,它们既未被封存在石窟寺中,也未被陪葬于墓葬内,而是在探方中被挖掘出土的。它们在公元8世纪末叶或9世纪初叶被遗弃之前,曾经遭受抢劫和焚烧,又曾遭到先于伯希和到达库车地区的其他外国考古探险团的大肆劫掠。这批文书残损严重,难觅完整的写本,极其稀见完整的文书。此外,这批文书来源复杂,不同时代与不同主人的文书,互相混杂在一起,从而使人考证起来甚难。
至于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写本的断代问题,它们与同时发掘到的钱币的时代大体相一致。这一切都证明了伯希和从其发掘一开始,就曾作出的假定:“我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所获文物的平均时代为8世纪。①那些文书(大都为用婆罗谜文字母写成的)是分别于多处不同地点发掘到的,虽然分散地面很广,却也大都集中在“寺院藏经楼”附近。写本的这种分散性说明,所谓寺院被焚烧之前曾遭抢劫,并非致因的唯一的解释。伯希和主要发掘的地点有“寺院藏经楼”、“西北部的窣堵坡”、门口和垃圾堆,它们彼此距离都相当远,我们很难想象这批文书是出自遭抢劫之前的同一地点,更应该认为它们原来就是被化整为零地收藏的。这批文书的内容纷繁:既有宗教文献,又有私人书信,特别是具有原始籍账与行政文书;世俗文书也不像在敦煌那样抄在写经的背面,而所有文书基本上都是单面抄写,并未被两面使用。
1907年4月17日至22日,伯希和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地区的发掘,主要集中在围绕东北跨院的僧房一线。他于其中的一座建筑中,发现了一批明显是非宗教文献的婆罗谜文写本,而且很可能是寺院籍账,其中只有一叶汉文的宗教文书。其他所有汉文宗教写本,大都是由伯氏等从5月23日起,在北部窣堵波大院中发掘出土的。其实,从4月17日起,伯希和一行同时于多处展开发掘,其汉文文书残叶大都为账目,而且都是世俗人的账目,发掘自“混合有厩肥的垃圾堆中”。属于军事机构的DA·M第119号(或DA·M132号)文书是于4月24日在西北段,于一个与外院墙相毗邻的房子中发掘到的。另一件军事文书(DA·M114号)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是于4月25日,当伯希和等集中力量清理“藏经楼”时,才被发现的,但它却出自另一片探方。他们于4月26日之后,所发掘到的非宗教婆罗谜文与汉文文书,也不是出自其主要发掘点,而是出自对萨玛克村的发掘,地处主要发掘点的东端。一份呈西域都护的请状(DA·M91号文书)出自一座建筑物内,该建筑虽紧傍窣堵波北部的建筑群,却又不属于该建筑群。在伯希和于其考古笔记中未加具体确定的一个发掘点上,出土了大批汉文文书,但其地点必然位于大门口附近。汉文文书不会出自伯希和的主要发掘点——宗建设施中,如精舍、窣堵波和其他宗教崇拜地,虽然这些遗址由于其中的艺术作品而特别吸引考古学家们的目光。那些汉文写本主要出土于佛寺群的周边地带。这一切必然会使人联想到,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不仅是僧侣们举行仪轨法事的建筑,而且还是由文职官府机构占据的设施。世俗建筑一般均建于佛寺的周围,也有两类建筑互相交错的例证。世俗文书的时代几乎覆盖了整个8世纪,而没有任何一件宗教文献载有确切的时间。它们也很有可能是于佛寺不复存在之后,由中原士兵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军镇的原因所造成的。现在基本可以肯定,都勒都尔—阿乎尔的佛寺与行政官衙毗邻而居,并于同一时代行使各自的功能①。但我们尚不能充分肯定,这里就是悟空师(法界)当年入竺时所经过的地方。因为悟空当年曾经由耶婆瑟鸡寺②、东西拓(柘)厥寺和阿遮哩贰寺。伯希和当年特别倾向将都勒都尔—阿乎尔考证为玄奘法师所提到的阿奢理贰(阿遮哩贰)伽蓝。他于193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的《吐火罗语和龟兹语》一文中,烈维(S、Lévi)于1913年于《亚细亚学报》发表的《乙种吐火罗语—龟兹语》中,都曾作过类似考证③。季羡林先生等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也采用了此说④。据悟空的记载,东西拓(柘)厥寺与阿遮哩贰明显为两地。玄奘认为阿奢理贰伽蓝“位于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式旌美迹,传芳后叶”。伯希和认为“阿奢理贰”应为“阿奢理腻”之误,因为“贰”字的古音可能为“ni”(腻)⑤。
《新唐书》卷43记载有:“安西西出柘厥关。”其他中文史料中也作“柘厥”,西方汉学家一般均拼音作Zhejue。悟空作“拓厥寺”。“拓”与“柘”号字形相似,而又绝不通假。况且,“拓厥”或“柘厥”是龟兹语的汉文对音。伯希和探险团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到的汉文文书DA·M80号是一份报告(其录文略)。所以,伯希和在对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地望作考证时,更多地是坚持“阿奢理腻伽蓝”,从未将此地考证为“柘厥关”。
尽管伯希和在库车地区的考古笔记本中,包括6月19日至7月末的一册早已丢失。但伯希和于其1934年发表的《吐火罗语和龟兹语》①一文中,他尚记得自己发掘到的一卷写本,即DA·M27号文书:“我于1907年曾发掘到一片残纸,可现在已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了,但我很准确地记得于其中读到了‘至柘橛(厥)’的记载。非常遗憾的是再无其他说明,但我于苏巴什西部废墟中搜罗到了其中提到‘柘厥’的这件残卷,也就是说是在西柘厥寺的遗址上发现的。这种巧合令人费解。”因为伯希和似乎将苏巴什西部考证为柘厥寺了,故而他认为不可能从“柘厥”再到柘厥了。但文书中只残存“柘厥”二字,未明确指出是“关”还是“寺”。但从其前后文来看,似乎是指“柘厥寺”。
伯希和的记忆也绝非是永远准确无误的。他在发掘某一残卷时,偶然将都勒都尔—阿乎尔与苏巴什相混淆,也完全在情理之中。首先是在自库车发现的大批匿名文书中,这卷文书完全有理由引起那位考古学家的高度注意,因为其中含有一个史学家们所熟悉的地名“柘厥”。此外,伯氏是一个高水平的考古学家,若发掘地有误,他立即就会想起来,绝不会使他感到“令人费解”。伯希和在苏巴什和都勒都尔—阿乎尔两个遗址的考古发掘是相继于不同时间完成的。他于苏巴什首次发现汉文写本是在6月17日,也就是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工地的发掘工程结束3周之后。对苏巴什的发掘一直是在某种很单调气氛中展开的,其发现物实在不算太多,故而伯希和才会牢固地记住了这份带有“柘厥”字样的文书。
我国新疆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将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考证为唐安西柘厥关。其重要论据之一就是伯希和发掘到的DA·M27号文书,他认为伯希和的记忆力出现了差错,误将在都勒都尔发掘到的这卷文书,归于了苏巴什名下,因而才出现了伯希和考证中的自相矛盾。我国学者有不少人也都同意王先生的观点,甚至包括某些老一辈学者在内。
童丕先生在刊布伯希和库车文书时,依据伯希和当年的观点,对于王炳华先生的考证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苏巴什出土的这卷记载“柘厥关”的汉文写本,已被多人用于为柘厥关确定地望了。王炳华先生认为伯希和将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出土的文书,记在了苏巴什的名下,从而证明伯氏将柘厥关旧址确定在苏巴什,而不是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证。《新唐书》卷43下记载:“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白马河似乎已被比定为木札提河。但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因为古代从龟兹到姑墨曾有多条道路,如其北道沿雀离塔克山麓行进;另一条是经由木扎提河南岸的路,现已被遗弃。悟空提到的东西拓(柘)厥寺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伯希和以其坚实可靠的语言学和地理学论据为基础,将柘厥关与另外两个更为古老的地名作了比较。据伯希和认为,苏巴什双寺(二伽蓝)的遗址位于今城之北的库车河两岸,分别相当于鸠摩罗什(Kumārajiva)时代的雀梨寺(C〓kri)、玄奘于630年提到的昭怙釐(Cogüri)和悟空于788年提到的柘厥。伯希和也没有忽略将悟空提到的柘厥寺与柘厥关相比较,尽管《新唐书》将柘厥关置于了龟兹绿洲的西出口。伯希和于其在苏巴什发现的纸片上读到了“至柘厥”的字样,使他茫然不知所措。尽管这次发现具有棘手的巧合,但伯希和仍极力避免将柘厥关绝对地置于了苏巴什地区,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成立的假设才提出来的。在8世纪时,于库车以北存在着一座柘厥寺,于城西存在着一座同名的关②。伯希和的结论是“不想将任何解释定为最终性的”。他仅满足于“权宜性地”接受,C〓küir的不同相近形式在龟兹语和吐火罗语中均指一关和一寺、一座窣堵波、可能还有一座烽燧。他于其论证时既未表现得专断,也绝不肤浅。伯希和在考古发掘期间,始终都认为都勒都尔—阿乎尔寺是阿奢理贰或阿遮哩贰(意为“奇迹寺”,佛教中的“奇迹”具有“化现”之意),但他也未敢最后确定。直到1934年,他仍建议将两名取经僧人提到的建筑或确定在都勒都尔—阿乎尔,或确定在库车河以西。
童丕先生认为,即使夏克吐尔确实位于渭干河东岸,即与都勒都尔—阿乎尔遥遥相对,那也很难像王炳华先生那样应将此地考证为柘厥关。因为该地距唐龟兹都城以西23公里处,不足于做为从龟兹都城西行(至姑墨)的第一站。夏克吐尔并不位于绿洲的出口处,而是位于向渭干河右岸深度延伸的农耕区的中心。无论DA·M27号文书是出自苏巴什,还是出自都勒都尔—阿乎尔,都无法证明在某地发现记载某一地名的文书,就断定它就是此地的名称。此外,文书中只有“柘厥”而没有具体注明是“关”还是“寺”,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王炳华先生认为,苏巴什并非是在渭干河两岸建起的唯一建筑群,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情况也应大致如此。位于渭干河西岸者,主要是宗教建筑;位于东岸者,主要是军事—行政机构,但也有宗教崇拜地点。当地的考古学家们分别称这两个遗址中的前者为夏克吐尔(爱克吐尔),后者为玉其吐尔(“吐尔”系突厥文tura的对音,指烽燧和窣堵坡,也可能是指山口)。其实,这两个建筑群具有混合用途,各自都包括行政设施和宗教建筑。这一切与许多人根据出土文书和文物而针对都勒都尔—阿乎尔提出的观点相吻合。但这种考证也并不与伯希和的观点相悖。伯希和在对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时,确实于库车河对岸发现了两个遗址,他分别称之为Hicar(爱克吐尔或夏克吐尔)和Sara〓tam(色乃当)。他仅为色乃当留下了一幅照片。伯希和对爱克吐尔作了简单的记述:“工程量很大。”城堡内部有许多小坯房。伯希和从中发现了许多壁画残片和彩塑残余:“至少有一尊菩萨像,佩戴数量多而较大的首饰。”他还在那里发现了婆罗谜文的木简与一枚建中通宝,却未提到任何汉文写本①。但在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DA·M15号文书的边缘,写有Hicar(爱克吐尔)。
伯希和在开始发掘都勒都尔—阿乎尔时,有些失望。他于4月25日在致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与地理学会主席、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首倡人和鼎力推荐伯希和的塞纳尔(E.Sénart,1847—1928)的信中,流露出了他对最初12天发掘的失望情绪:“至于我们的发掘,至今尚未向我们揭示玄奘所描绘的那种辉煌。数日期间,在所清理的僧房中,没有任何塑像或祭坛的踪迹。我一直在思考,真正的寺院到底在哪里。但在四五天之前,我们最终发现了柴泥制成的祭坛和塑像。尽管它们残损严重,但至少仍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该问题的解释。”“那些在麦秸和杏核中心间堆满了各种垃圾的僧房和小房间,向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布帛、便鞋、芦苇笔、灯盏和陶瓷片。与在图木舒克搜集到的那些文物相比较,它们的数量和品种都要丰富得多。”“我们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发掘物的平均时代,确为8世纪⋯⋯如五铢钱(汉代之后)、带有年号(开元和大历,8世纪中叶和末叶)的中国铜钱等。”①
伯希和于5月2日致塞纳尔的书信中,可以更好地解释他对玄奘法师的看法:“我开始理解了这种昔日曾使玄奘感到兴奋的豪华装饰。这里的塑像很多。如果说我们搜集到的大头佛像的风格已纯粹是某种学派的作品了。那么在次要人物的身上,却呈现更多的新奇特征。我在对一间僧房的清理时,于一个祭坛的角落中,发现了一个几乎是全裸的青年美男子彩塑。其半身已残损,很优雅地倚在右胯之上,浸透着一种希腊文化的特征。”“实在说,这种豪华多少有些粗犷,至少从我们现代人的鉴赏观点来看,正是这样的。黄金大量地闪烁,人们到处都使用了黄金,如在壁画上、彩塑上、铜器和木器上,一概如此。尽管那些皈依了伊斯兰教信仰的当地居民,曾大肆地搜刮过这些金叶,现在仍残留有大量的痕迹。即那些经过巧妙设计、精心雕刻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木雕像,它们也身穿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我们在8天便找到了数躯这样的雕像。”②
伯希和探险团对于都勒都尔—阿乎尔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地点:佛寺、院子和大门、中心院、宗教圣址、僧房的跨院和第二道门口、主塔和后部小院、木版印刷的雕板处、东北建筑及其宗教设施、大甬道与西北的窣堵坡等。
通过伯希和探险团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现的汉文文书及古钱币,促使伯希和对它们作出了8世纪的断代。该遗址可能是于9世纪时突然停止了活动,因为在许多发掘点都发现了火灾的痕迹。某些绘画的涂金层已被人为刮去,说明在火灾之前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抢劫,“藏经楼”中的写本也因此而四处失散。尽管遗址中出土了许多五铢钱,但我们却很难为这些建筑群的形成期作出准确断代,因为五铢钱于西域至少一直流通到唐初。从公元4世纪起,佛教的宗教功能于龟兹日益多样化。那里出现了带有中心大院、跨院和相继装修的佛寺,而且其数量也都会很多。都勒都尔—阿乎尔的佛寺布局,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犍陀罗佛寺很相似。都勒都尔—阿乎尔的窣堵坡和主要僧伽蓝,都是经过院子的中门而与大院相通。僧伽蓝跨院四周均由僧房簇拥。
总之,都勒都尔—阿乎尔佛寺的最早核心,可能属于一组具有相当规模的佛教建筑,其扩大是随着佛教在龟兹的神奇发展而逐渐完成的。
三、伯希和探险团对苏巴什的考古发掘
伯希和探险团从1907年6月17日开始,对苏巴什宗教双城(二伽蓝)作了一次考古发掘,整整持续1个月的时间。由于这片遗址面积辽阔,所以这样的期限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伯希和从1907年春季起,也就是当他尚滞留于库车时,便对苏巴什周围环境作了仔细考察和测量。从而使他得出结论认为,从其地望来看,苏巴什宗教(寺院)双城只能是玄奘于《西域记》中记载的“昭怙釐二伽蓝”。昭怙釐应为梵文Coriot的汉译,此名可能借鉴自自沙瓦附近著名的迦腻色迦时代之佛寺“雀离”大寺的名称。此寺也就是《水经》中所引证的释氏《西域记》中的雀离大清净寺。伯希和一行刚开始时的工作也并不太顺利。他于1907年1月29日致塞纳尔的信中,列举了自己到达库车后的初步调查结果。他针对苏巴什废墟而写道:“仅仅瞥去一眼,便使我坚信,这里确为玄奘所熟悉并作过生动描述的地方,即昭怙釐大寺。该寺院很古老了,因为在玄奘之前很久,《水经注》中就已经提到该寺了。事实上,位于苏巴什河两岸的这两座寺院留下的废墟,是我自到什喀尔地区之后,所见到的规模最宏伟者。东昭怙釐寺与西昭怙釐寺各自延伸于近一公里长的地方,拥有有时会达到10米高的建筑物,尚且不讲那些仍在多处未曾遭损地保持着其原状的窣堵波。全部建筑均以土坯筑成,最多见的是使用生土坯,当然都露天,现已看不到绘画和涂层的踪迹了。”日本人曾先于伯氏而于此地发掘,但只找到一双便鞋。伯希和本来希望测绘一幅详细的平面图①。伯希和当时已经获知,当时在库车市场上出售的所有印鉴和钱币,均是自这里流散出去的。
伯希和等人的发掘,于7月10日之后仅仅持续两三天,他于7月10日致塞纳尔的信中更流露出了其失望情绪:“对昭怙釐寺的发掘刚刚基本结束,未能提供我本来所期待得到的东西。我于此搜集到的几件木雕,大致属于都勒都尔—阿乎尔那些同类文物的类别,远不如图木舒克的那些精致。至于写本,我们仅获得几种婆罗谜文、汉文,甚至是回鹘文的小片残卷。②”伯希和等共有3次发现了藏钱的钱窑,每次都有数千枚五铢钱出土。他们在大河的西部和北部大山最前面的几条支脉中,又发现了许多写本残卷和洞窟中的游人题记。因为伯希和的考察笔记本遗失了一册,所以其记述只到6月18日便中断了,从而使人无法解释瓦杨的测绘图了。由于苏巴什遗址面积广阔,伯希和探险团人手很少,而且时间又紧迫,所以他们只能零散地进行发掘,其重点就在于搜寻写本。伯希和等人对大河东西两岸,均未测绘出完整的平面图。
苏巴什的佛教遗址与伯希和过去考察过的图木舒克和都勒都尔—阿乎尔完全不同。苏巴什是一种具有某种整体性的建筑。那里的日常居舍、僧房及其附属设施,似乎都属于一个原有的中心,围绕着它而逐渐扩展。苏巴什的宗教双城位于库车河的东西两岸。其建筑物的种类、规模和布局,都会使人联想到于其城墙内集中了不同的建筑,而又能使其中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彼此独立地生活。在东部主体建筑的周围,现在尚可以辨认出庞大的军镇遗址,沿山麓于遥远的地方就能清晰地看到它们。
伯希和探险团在苏巴什西部的地基上,分别考察了大院子、大墓葬、北部窣堵波、僧房、烟囱房和西部大窣堵波;于东部的地基上,他们考察了院子遗址、西南窣堵波和东北窣堵波;
在库车河西岸的石窟中,他们又发现了某些婆罗谜文写本;在宗教双城中,他们特别考察了“壁画屋”。
四、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的概况
童丕先生整理、刊布和译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汉文写本。这实际上是在我国学者张广达先生的帮助下才完成的。
伯希和自库车携归的汉文写本特藏由249个号的212件文书(1-156、157.1-7、201-249号,有些文书后来被撕破成数片)组成,从而形成了DA·M,即“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另外有两件文书则被编入了“伯希和龟兹文特藏”中,尽管它们是用汉文写成的,这是一组总共为44件文书[编号为DA·M(即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507号]中的第31和32号。这样一来,全部特藏中总共有214件文书,其中18件已被断代或拥有能令人作出断代的明确标志。其中年代最早者可上溯到690—705年(DA·M52号文书),因为武后新字行用于这段时间。其最晚的时代为784年(建中五年,DA·M104-106号)。在这两个上下限时间之间,写本的分布很规则。其早期(开元年间,713—741)有五六件;其晚期(760—784),也有同样的数目,其中期(742—759),有5件。由此可见,这批写本所覆盖的时代,恰恰是唐军驻扎龟兹的时代,即介于唐军于692年大破吐蕃兵和790—791年左右之间的时代。
在这批汉文写本中,只有很少的主文献纸叶背面写有与主文献没有任何关系的文字者。这说明它们在写成不久就被失散了。如果它们如同敦煌写本那样被收藏在档案处或藏经处,那么它们的背面就肯定会被重新利用,被用于书写其他内容。
在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中,除了少数12件出自苏巴什之外,其种类非常纷繁,明显出自多个不同的收藏点,遍布于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整片遗址上。但那些佛经和其他寺院文书(僧侣们的书信和账目等),却只占很少数量。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DA·M)中的宗教文献的稀见性,形成了它与出自库车地区的大谷文书之间的高度反差,因为大谷文书中有许多佛经和教义疏注文。为什么在一个伯希和认为是古寺的地方,却很少会出土佛教文献呢?考古发掘已经清楚证明,都勒都尔—阿乎尔确为一座佛寺,但其中居住的都是龟兹人而不是汉族僧众,于现场发现的那些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龟兹文写本,便充分证明了其寺院的周边和生活环境。生活在都勒都尔—阿乎尔的汉人主要是世俗人,大部分汉文文献均出自官府,其中有许多甚至出自于官吏们本人之手。一批为数不多的私人文书也都往往与官府有关,如某些书信(第131号)、契约(第4号)和殡葬文书(第28-30号),涉及了军镇的驻兵。很明显,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存在着一个官府和一个军镇,居住在其中的汉人是负责管理军队和来自中原的屯边戍民。
伯希和都勒都尔—阿乎尔汉文特藏(DA·M)的另一特征,是缺乏商务文书,也没有被用于交易的商品目录;其中更没有旅行文书,如骆驼队的“过所”之类文书。这批文书中只有少数契约,而且似乎也只涉及农民之间的交易,如租地和借粮等(DA·M62号文书背面)。DA·M122号文书涉及了一次“西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龟兹人或粟特人与操汉语的人之间的交易关系。DA·M123号、130号和131号文书是由官吏或者由不以商业谋生的人书写的信件。其中提到的唯一一支骆驼队并不是商队,而是“屯家人”。龟兹城本来是一个商业很发达的地区,但DA·M中的商务文书却极其稀缺,这很可能是由于商人都居住在城内,并且在城内交易,或者是那些沙漠商队客栈均位于城市的四周。
在多种文书(如DA·M33号、47号和86号)中经常出现的“行客”一词,现在尚难以确定其义。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唐代文学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经常出现的“远行商客”。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DA·M134号文书中出现的“行军”(“行军司马”)一词,在DA·M58号和115号写本中还出现过“行客营”。这也可能与商人经常随作战部队远行有关。
在DA·M的大量的行政文书中,只有一件可以被考证为出自龟兹都督府或安西都护府最高当局(DA·M134号):“摄副使行军司马秘书少监薛”。另外至少有3件是通过各级渠道而呈奏龟兹最高当局的,两件是致安西都护府的(DA·M91号和135号):“伏望都护详察”和“都护九郎(?)阁下”;一件是致“龟兹都督府”的(DA·M83号文书残卷5)。其他的文书则向我们揭示了某些高官的尊号,却又无法使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文书的作者,还是仅仅是其收启人(DA·M37号、39号、48号、109号文书)。这些文书其实只涉及到某些琐事,却又要上奏最高当局(DA·M91号和100号文书):对粮食和食物仓库的日常管理、完成工程等。文书中经常提到马匹(DA·M
91号、101号、121号、126等号文书),以及对它们的饲养、统计、采购,而且主要是向突厥人出售(DA·M129号文书)。这些马匹大都属于地方部队(折冲府),但也被用于馆驿。它们不仅仅是中国战略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整个官府的基础(DA·M41号、76号、91号和129号文书)。其中提到的事件完全反映了驻扎在大唐帝国边陲上的那些军事机构的活动。甚至某些佛教文书,它们似乎也涉及了军人(DA·M5号文书,“因军阵损害众生”)。
在这批写本中,军事机构无所不在。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各种级别的军事单位:军镇、城、守捉、开府、镇使、游弈官、孔目官等。但当时那里似乎存在着两种结构:行军(野战军)和折冲(团练)。驻龟兹的军队似乎具有比在中国内地更为广泛的功能。他们当然负责“屯”(DA·M19和88号文书),其中的一处叫作伊利屯(DA·M19号文书背面);他们更要负责在其他地方应该属于行政职权(DA·M57号、90号、104-106号等文书)的事务。其时间最晚的一件文书是DA·M104-106号的请状。它证明,直到784年,唐朝的行政机构在龟兹的某些地区,尚在军队的控制下正常运行。
由于这些文献更多地是涉及地方事务,所以经常提到基层地区单位,如“村”(DA·M12号、95号、121号和127号)、“坊”(DA·M93号、96号、103号、134号文书)。在唐代,“村”与“坊”属于同一级别,“村”位于城市的城墙郭外;“坊”则位于城内,却又不一定具有城市的特征。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中提到了“坊”,这说明在当地就存在着与都城有别的“城”。除了“王子村”之外,都勒都尔—阿乎尔写本中所提到的村名,均为龟兹语的汉文译音字:“移伐姟(孩?)村”、“伊禄梅村”、“无寻苏射堤村”、“都野提黎伏陀村”和“萨波村”等。那些“坊”却相反都是汉名:“怀柔坊”、“安仁坊”与“和众坊”。这就证明,当时在坊中比在村中具有更高的汉化程度。中原人主要是集中城内,在农村则比较分散。这些坊和村中的居民,似乎更密切地依靠城市当局(DA·M93号、104号-106和134号文书)。我们由此便可以从中管见军屯的迹象,至少是有许多士兵都与其家庭生活在一起。
总之,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提供了许多方面的详细资料。它们对于研究唐代龟兹地区的历史、地理、军事、人口、语言文字、经济和行政组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附注
①玛德玲·哈拉德、西蒙娜·高狄埃:《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1982年巴黎版,第31-38页(MadeleineHallade,SimoneGauthier.Douldour-?qouretSoubachi;MissionPaulPelliot.ⅣV.Paris,1982)。
①玛德玲·哈拉德、西蒙娜·高狄埃:《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4卷,1982年巴黎版,第31-38页(MadeleineHallade,SimoneGauthier,Douldour-?qouretSoubachi;MissionPaulPelliot.ⅣV,Paris,1982)。
②MadeleineHallad:Douldour-?qouretSoubachi,MissionPaulPelliotⅣV,Paris,1982.
③MoniqueMaillard:SitesdiversdelarégiondeKoutcha,EpigrapheKoutchenne,Paris,1987.
①EricTrombert,LesManuscritsChinoisdeKoutcha,FondsPelliotdeLaBibliothequenationaledeFrnce,Paris,2000.
①《魏书》卷102,第2267页;《北史》卷97,第3218页
①路易·瓦杨:《中国西域地理考察报告》(RapportsurlestravauxgeographiquesFaitsparlaMissionarchéologiquedeLAsieCentrale,MissionPaulPelliot(1906—1909),载1955年的《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地理分部学报》(BulletindelaSectiondeCéographieduComnitédeTravauxhistoriquesetScientifiques,Paris,1955)。中译文见: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①上引瓦杨文,第86—90页;上引童丕文,第23页。
②MadeleineHallade:Douldour-〓qouretSoubaehi,MissionPaulPelliotⅣV,巴黎1982年版。中
译文见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第222页以下。
②MadeleineHallade:Douldour-〓qouretSoubachi,第33-36页,耿昇译文,见同上引书,第222页以下。
①上引哈拉德书,第36页;耿昇译本,第241页。
①伯希和于1907年4月25日致塞纳尔的书信,由上引阿拉德书第43页引证;上引童丕书,第27页。
①上引量丕书,第27—28页。
②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判断,耶婆舍鸡寺很可能就是今新疆拜城县境内的克孜尔千佛洞。
③P.Pelliot,TokharienetKouchéen,JA1934,1,P75;S.Lévi,TokharienB,LanguedeKoucha,JA,1913,Ⅱ,P358.
④〔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
⑤同上引伯希和:《吐火罗语与龟兹语》,第75页。
①PaulPelliot,TokharienetKoutchéen,JA,CCXXⅣV,1934年1月—3月,第23—106页。
②王炳华:《唐安西柘厥关故址并有关问题研究》,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新库车玉其吐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①伯希和,1934年文,第75-93页
②同上引伯希和文,第96页。
①同上引莫尼克·玛稚尔等:《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文题记》第8页;上引童丕书,第30页
①上引阿拉德等:《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第43-44页
②上引阿拉德等:《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第45页。
①同上引,第41页。
②上引哈拉德等人书,第50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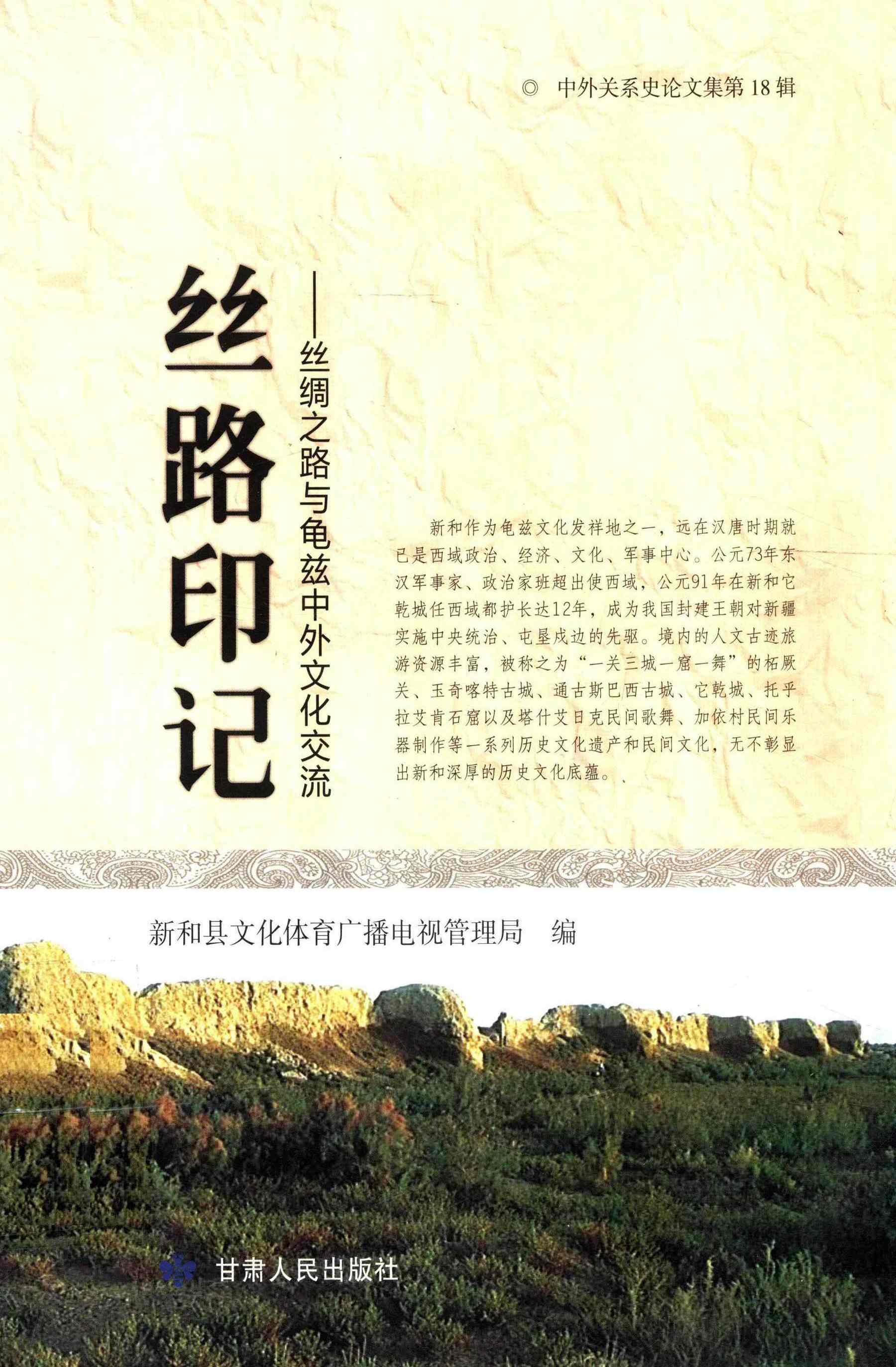
《丝路印记: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的24篇优秀论文,主要围绕古龟兹文化传统、龟兹文化与丝绸之路、汉唐屯田文化等课题展开论述,探讨了龟兹文化在中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并为进一步研究和发掘古龟兹文化,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阅读
相关人物
耿昇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新和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