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妆
| 内容出处: | 《新疆古代服饰艺术》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3833 |
| 颗粒名称: | 化妆 |
| 分类号: | TS974.12 |
| 页数: | 9 |
| 页码: | 22-3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新疆古代居民化妆的的基本情况。汉代西域女子的化妆主要表现在眉毛和面部两个部位。 |
| 关键词: | 新疆 古代 化妆 |
内容
考古资料表明,新疆古代居民十分重视面部的化妆,而且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且末扎滚鲁克墓葬中发现了2800年前的男女干尸,面部上都有用雄黄、雌黄、赤铁粉及铅黄等染料,围绕眼、鼻、额、颧精心绘出的羊角纹、涡纹等纹饰(图1),表现出原始的化妆习俗。1989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在且末扎滚鲁克另一座墓葬中发现的时代与上面相同的一具老年妇女的尸体,我们在她的面部看到,双眉如柳叶,色彩如初描,在额中部还有一个黑色颜料描绘的圆圈纹[1],与南北朝及唐朝时期西域和中原地区宫廷仕女中流行的额黄十分相似。据史料记载,位于吐蕃西、于阗国以南的女儿国,有与扎滚鲁人相似的化妆习俗,《隋书·西域传》记载:“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改变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人有“以赭涂面”的习俗。考古工作者在和静察吾呼沟古墓和鄯善苏贝稀古墓发现了距今2500年左右的眉石和眉笔,特别是苏贝稀古墓还出土有黑、白、红等色的矿物染料,均为化妆品。
化妆也是当时汉代西域居民追求美好的重要表现,特别是女子对化妆十分重视,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汉代西域女子的化妆主要表现在眉毛和面部两个部位。
(1)眉毛的化妆。眉笔和眉石是古代西域女子用于修饰眉毛的主要用具。考古工作者在先秦时期的和静县察吾呼沟古墓、鄯善县苏贝希古墓、洛浦县汉晋时期的山普拉古墓、且末县的扎滚鲁克古墓都发现了用来描眉的眉笔和黑色眉石,其中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眉笔和眉石最为典型。眉笔主要有石质和木质两种类型,眉石是一种黑色颜料。
石眉笔以细沙岩质为主,根据器型的不同分为A、B、C三种。
A型 圆锥体型84LSM28:1-1,残长7.7厘米,直径0.8厘米。
B型 棱锥体型84LSM02:128,尖头部呈两面刃状,长5.2厘米,宽1.3厘米。
C型 双尖头型,两头尖中宽粗,截面三角形,长4厘米,中部宽1.3厘米。
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木眉笔为圆锥体,尖头有黑色染料,根据尾部的差异,分为钻孔系绳型和刻颈系绳型两种,长7~8厘米左右,宽0.8厘米[2]。
眉石为化妆颜料,与石眉笔为一组合,呈不规则形,有明显的磨取颜色留下的凹槽,长7~8厘米左右,宽2.2厘米,厚2.5厘米。
山普拉古墓出土的黑色眉石(图2),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女子画眉的主要颜料——黛。《楚辞·大招》中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的句子。《释名·释首饰》曰“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与中原内地相比,西域女子更喜欢自然之美,就是不用拨去原有的眉毛,而是在眉毛上用眉笔进行修饰。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木眉笔尖头有黑色染料,说明墓主人在2000多年前曾使用过这件木眉笔。现在南疆农村中,常见到维吾尔族年轻女子把眉描的很细很长,描眉的原料是从一种叫“奥斯曼”的植物叶子中榨取的汁,用细木棍缠上棉花,醮其汁描眉。这与汉晋时期西域妇女,用笔尖涂有黑色染料的木眉笔描眉的习俗有一定的相同之处,说明2000多年来新疆和田地区的妇女仍保持着用木眉笔描眉这一传统习俗。
(2)面部的化妆。汉代西域女子化妆时,一般使用胭脂,据史料记载,匈奴妇女对胭脂情有独钟。晋崔豹《古今注》记载:“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国人谓之红蓝,以染粉为面,为燕支粉。”《太平御览》卷719引河西旧事:“祁连山,焉支山,宜畜养,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胭脂原料的主要产地,可能就是甘肃省境内的祁连山。唐张泌《妆楼记》中说“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烟支也”。《汉书·匈奴传》颜师古亦注:“阏氏(胭脂),匈奴皇后号也。”因匈奴贵族常以“阏氏”(胭脂)妆饰脸面,所以“阏氏”成了她们的代称,可见胭脂在匈奴贵族中的地位。据说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胭脂和葡萄、石榴等物一起传入中原地区[3],成为中原妇女主要的化妆品。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出土整盒的胭脂包。汉代西域胭脂的实物见于1959年尼雅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胭脂包内(图3),此包用黄色细绢包裹,内装少许朱色粉末,用白色丝绵扎袋口,袋口边放着残存的棉花,已被染成酱紫色,大约是墓主人化妆的时候使用过的涂抹妆饰用的胭脂包[4]。这座墓还出土了用白绢缝制的绣有叶草纹的刺绣粉袋,高7厘米,宽4厘米,用红色菱形纹的花绮做边缘缀饰。粉袋内装少许由铅粉变质板结成的黑色块状物。铅粉对人皮肤是有害的,但为了使自己的面部白皙起来,古代妇女十分喜欢用铅粉敷面。实物的出土印证了当时西域女子同样以白皙为美的审美时尚。此外,1995年民丰县尼雅1号墓地也出土了一些化妆品。
尼雅1号墓地3号墓出土的漆奁内,装着用于化妆的两小团丝绵,已浸染成紫红色。
尼雅1号墓地4号墓出土了两件将牛角劈开加工而成的化妆盒,呈蚌壳状,一件内装黑色染料,长9.8厘米、宽2.8厘米、深1.4厘米。另一件装红色染料,长7.2厘米、宽4.2厘米、深1.1厘米。
尼雅1号墓地5号墓出土的一位青年女性干尸,腰部随葬木叉,上挂化妆袋,内装铜镜、胭脂粉袋、丝线等。
尼雅1号墓地5号墓出土的虎斑纹锦袋,内装有铜镜、胭脂粉包、绕线轴、线团绢卷等女红用具[5]。
以上民丰县尼雅古墓出土的考古资料表明,精绝国妇女十分重视面部的化妆,尼雅古墓出土的已染成紫红色的丝绵团,牛角化妆盒内储放的红色颜料和黑色颜料,还有出土的胭脂粉包、化妆袋、铜镜等化妆用品,一应俱全,这些都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了西域女子在汉晋时期,已经掌握了比较完备的化妆和美容的方法。黑色颜料用于描眉,红色颜料用于脸部的化妆,红色颜料的使用,说明当时西域女子还喜欢彩妆。
唐代的服饰文化博采众长,特别是女子服饰是有史以来最艳丽的装束。当时以吐鲁番高昌为代表的西域女子的装束,一方面保持着本地区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她们的服装样式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唐代西域妇女对化妆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仕女图》绢画,女舞俑、仕女俑、劳动俑等(图4),再现了唐代西域妇女五彩缤纷的化妆习俗。唐代西域女子的化妆,一般可分为画眉、抹胭脂、贴花钿、点面靥、描斜红等几个步骤。
画眉
眉毛是人们表达感情的重要部位,新疆各民族饰眉的历史源远流长,早期是用石笔磨粉或是用树枝烧成炭条描绘眉毛。考古人员还在鄯善县2500年前的苏贝希古墓、温宿县汉代的包孜东古墓、洛浦县山普拉古墓都发现了用于描眉的眉石和石眉笔,说明西域画眉的历史十分悠久。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画眉的风气日盛,就连八岁的女孩,都能像大人一样描起眉毛。如李商隐《无题》诗:“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据史籍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兴趣广泛,不仅喜欢吟诗作曲,还染有“眉癖”,曾令画工画《十眉图》。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西域女子对眉毛的修饰也十分重视。新疆博物馆收藏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组劳动妇女俑的眉毛的十分独特,眉毛细长而弯曲,同新疆龟兹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飞天、菩萨等人物形象的眉毛十分相似,如同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中描绘的那样“青黛点眉眉细长”。现藏于日本的出土于吐鲁番吐峪沟古墓的一幅《乐舞女图》绢画中的女子的眉毛也是细长的柳叶眉,初唐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一诗中“纤纤岁月上鸦黄”形容的就是一种象新月一样又细又弯的眉形。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围棋仕女图》中的那位正在下棋的贵妇人以及旁边站着的侍女们的眉形却描绘的又黑又宽(图5),如同唐代诗人沈全期诗中所云:“拂黛随时广。”反映了当时描绘阔眉的风尚。
彩妆
据文献记载,早在汉代我国西北地区的匈奴贵族妇女就有喜欢用胭脂化妆的习俗。公元前138年和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将西域各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风情介绍到了中原,胭脂也被引进到中原地区,深受中原妇女的喜爱。专家们认为胭脂是一种用名为“红蓝”的花朵制成的,它的花瓣有红色的色素,对于喜欢彩妆的西域居民来说是一种理想的化妆品。考古工作者在民丰县尼雅古墓发现了汉晋时期的用于化妆用的红色颜料。南北朝时期西域女子依然喜欢彩妆,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的“高昌章和十八年(公元548年)光妃随葬衣物疏”中有“.胭脂、胡粉、青黛、墨黛”等物。到了唐代,西域女子对彩妆的偏爱依然不减。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几件劳动妇女俑,白脸上似施了胭脂,涂成圆形,装饰效果十分明显。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围棋仕女图》中的那位正在下棋的贵妇人以及旁边站着的侍女们,个都面如桃花,红润恬静,反映了唐代西域女子施彩妆的习俗。
花钿
花钿是一种额饰,通常用色纸、鱼鳞片、金箔、丝绸等多种材料剪成花样粘贴而成,也有直接用颜料描绘在额头上的。相传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有一次喝了许多酒后,醉卧在一个长椅上,正好有一朵梅花掉在她的额头中间,额上染上了一朵五瓣花的花痕,洗之不去,宫女们见其新异,竞相效仿,她们直接把梅花的形状画在额际间,以后逐渐形成了贴花钿的习惯。五代牛峤《红蔷薇》诗:“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眉妆。”另外,对于花钿之所以在女子中流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借以掩瑕。相传武则天当权时,每次召见宰相时,都令上官昭容卧于床裙记录所奏之事。一日,宰相来奏事,昭容偷偷窥看,被武则天发觉,大怒,用指甲刀将她脸上刺伤,上官昭容便用花钿来掩饰脸上的伤痕。宫女们见了感觉十分新奇,都纷纷效仿,渐渐成了一种时髦的做法。花钿的形状多种多样,有桃花形、梅花形、菱形、宝相花形、圆形等,颜色多有红、黄、绿等。其中,最为精彩的是一种“翠钿”,它是以各种翠鸟羽毛制成,整个饰物呈青绿色,清新别致,极富情趣。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屏风画《仕女图》绢画中的女子服饰华丽、形态端庄、气质高雅,额际间贴的菱形花钿十分醒目(图6)。此外在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几件女舞俑的额际间也有这种妆饰。唐代诗人杜牧诗中曾云:“春阴扑翠钿。”温庭筠诗里也有“眉间翠钿深”的描述,由此可见,绿色花钿在西域确实存在,而且在吐鲁番西州妇女中十分流行。
额黄
女子在前额上涂画黄粉也是唐代西域女子中颇为流行的一种妆饰手段。这是一种南北朝时期兴起的妆饰手段。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进入鼎盛时期,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这一社会现象的生动写照。随着佛教思想的渗入,西域各地的文化艺术及民间风情等也渐渐传入中原,对中原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妇女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启发,在自己的额头涂染上黄色,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黄额的习俗。中原女子在额前涂黄粉的习俗兴起于南北朝,著名的北朝乐府《木兰辞》中就写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前面所说的出土于吐鲁番吐峪沟古墓的那幅唐代绢画《乐舞女图》中的仕女(图7),身穿回鹘式翻领彩金锦窄袖服装,头梳高耸的发髻,额上描绘的黄色圆晕清晰可见。
斜红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藏中出土的屏风画《仕女图》绢画和彩绘女舞俑所表现的仕女和舞女,其面部还有一种十分特殊的面饰,就是在女子太阳穴部位各画一条红色弯弯的新月形,有的还故意描绘成残破状,宛如白净的脸旁平添了两道伤疤,这种妆饰,被称为“斜红”。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十分怪异奇特,但在唐代它是一种十分时髦的妆饰。唐代诗人罗虬云:“一抹浓红傍脸斜,妆成不语独攀花。”元稹的“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说的就是这种妆饰。其俗始于三国。据唐人张泌《妆楼记》记载: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宫中新添了一名叫薛夜来的宫女。一天夜里,文帝在灯下读书,周围用水晶制成七尺高的屏风相隔。薛夜来走近文帝时,不觉一头撞上屏风,顿时鲜血直流,受伤部位像朝霞一样散开,由此留下两道疤痕,事后文帝对她更加怜惜。其他宫女为了得到文帝的宠幸,也模仿起她的莫样,用胭脂在脸部画上这种血痕,名曰“晓霞妆”,后逐渐演变成这种特殊的妆饰——斜红。南朝梁简帝《艳歌篇》中曾云:“分妆间浅靥,绕脸傅(敷)斜红。”便指此妆。唐代妇女脸上的斜红,一般都描绘在太阳穴部位,工整者形如弯月,复杂者状似伤痕。为了造成残破之感,有时还特在其下部,用胭脂晕染成血迹摸样。在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一件唐代女舞俑脸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斜红的妆饰。不过斜红这种面妆终究属于一种缺陷美,因此自晚唐以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面靥
面靥也叫“妆靥”,是施于面颊酒窝处的一种妆饰。它原是宫廷生活中宫女月事来临时,不能接受“御幸”的一种暗示。但宫中舞伎见其红圆可爱,不时仿效一下,拿来作脸妆,以后传到民间,逐渐演变成一种妆饰。据考证,早在汉代中原就有点面靥的习尚,不过那时叫“的”。西汉作家繁钦《耳·愁赋》一文中有“点圜的之荧荧,映双铺而相望”的句子。“双铺”是左右脸颊,圜的就是脸上的圆点。妆靥的通常直接用颜色点染,如《留青日札》所说“古人点朱于额,以示进退之节”。在唐代这种妆饰传入西域的高昌地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几件仕女俑脸上就绘有这种妆饰。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彩绘长裙女舞俑,额间贴菱形花钿(图8),脸颊抹斜红,俏丽的面颊点饰如黄豆大小的红圆点,显得格外楚楚动人。到了晚唐至五代时,妇女的妆饰风气有增无减,敦煌莫高窟壁画《于阗公主像》中的回鹘公主身着色彩鲜艳的翻领回鹘式长袍,圆润的脸上酒窝处就饰有这种独特的面饰,反映西域贵族女子的化妆习俗。
点唇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藏中出土的绢画《仕女图》、女舞俑等女子形象中(图9),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西域女子的口型十分娇小,反映了当时西域高昌女子的审美情趣。这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审美标准有相同之处,如同白居易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诗句,至今仍被用作形容美丽的中国女性的首选佳句。中国古代妇女的唇脂是丹,“丹”即朱砂,它是古代妇女妆唇所用唇脂的主要原料。古人在丹中加入适当的动物脂膏,使其具有防水性能。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围棋仕女图》中旁边站着的侍女们,其唇被画成颤悠悠的花朵状,上下两唇均为鞍形,如四片花瓣,望之极有动感,显得鲜润可爱。
化妆也是当时汉代西域居民追求美好的重要表现,特别是女子对化妆十分重视,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汉代西域女子的化妆主要表现在眉毛和面部两个部位。
(1)眉毛的化妆。眉笔和眉石是古代西域女子用于修饰眉毛的主要用具。考古工作者在先秦时期的和静县察吾呼沟古墓、鄯善县苏贝希古墓、洛浦县汉晋时期的山普拉古墓、且末县的扎滚鲁克古墓都发现了用来描眉的眉笔和黑色眉石,其中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眉笔和眉石最为典型。眉笔主要有石质和木质两种类型,眉石是一种黑色颜料。
石眉笔以细沙岩质为主,根据器型的不同分为A、B、C三种。
A型 圆锥体型84LSM28:1-1,残长7.7厘米,直径0.8厘米。
B型 棱锥体型84LSM02:128,尖头部呈两面刃状,长5.2厘米,宽1.3厘米。
C型 双尖头型,两头尖中宽粗,截面三角形,长4厘米,中部宽1.3厘米。
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木眉笔为圆锥体,尖头有黑色染料,根据尾部的差异,分为钻孔系绳型和刻颈系绳型两种,长7~8厘米左右,宽0.8厘米[2]。
眉石为化妆颜料,与石眉笔为一组合,呈不规则形,有明显的磨取颜色留下的凹槽,长7~8厘米左右,宽2.2厘米,厚2.5厘米。
山普拉古墓出土的黑色眉石(图2),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女子画眉的主要颜料——黛。《楚辞·大招》中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的句子。《释名·释首饰》曰“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与中原内地相比,西域女子更喜欢自然之美,就是不用拨去原有的眉毛,而是在眉毛上用眉笔进行修饰。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木眉笔尖头有黑色染料,说明墓主人在2000多年前曾使用过这件木眉笔。现在南疆农村中,常见到维吾尔族年轻女子把眉描的很细很长,描眉的原料是从一种叫“奥斯曼”的植物叶子中榨取的汁,用细木棍缠上棉花,醮其汁描眉。这与汉晋时期西域妇女,用笔尖涂有黑色染料的木眉笔描眉的习俗有一定的相同之处,说明2000多年来新疆和田地区的妇女仍保持着用木眉笔描眉这一传统习俗。
(2)面部的化妆。汉代西域女子化妆时,一般使用胭脂,据史料记载,匈奴妇女对胭脂情有独钟。晋崔豹《古今注》记载:“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国人谓之红蓝,以染粉为面,为燕支粉。”《太平御览》卷719引河西旧事:“祁连山,焉支山,宜畜养,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胭脂原料的主要产地,可能就是甘肃省境内的祁连山。唐张泌《妆楼记》中说“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烟支也”。《汉书·匈奴传》颜师古亦注:“阏氏(胭脂),匈奴皇后号也。”因匈奴贵族常以“阏氏”(胭脂)妆饰脸面,所以“阏氏”成了她们的代称,可见胭脂在匈奴贵族中的地位。据说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胭脂和葡萄、石榴等物一起传入中原地区[3],成为中原妇女主要的化妆品。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出土整盒的胭脂包。汉代西域胭脂的实物见于1959年尼雅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胭脂包内(图3),此包用黄色细绢包裹,内装少许朱色粉末,用白色丝绵扎袋口,袋口边放着残存的棉花,已被染成酱紫色,大约是墓主人化妆的时候使用过的涂抹妆饰用的胭脂包[4]。这座墓还出土了用白绢缝制的绣有叶草纹的刺绣粉袋,高7厘米,宽4厘米,用红色菱形纹的花绮做边缘缀饰。粉袋内装少许由铅粉变质板结成的黑色块状物。铅粉对人皮肤是有害的,但为了使自己的面部白皙起来,古代妇女十分喜欢用铅粉敷面。实物的出土印证了当时西域女子同样以白皙为美的审美时尚。此外,1995年民丰县尼雅1号墓地也出土了一些化妆品。
尼雅1号墓地3号墓出土的漆奁内,装着用于化妆的两小团丝绵,已浸染成紫红色。
尼雅1号墓地4号墓出土了两件将牛角劈开加工而成的化妆盒,呈蚌壳状,一件内装黑色染料,长9.8厘米、宽2.8厘米、深1.4厘米。另一件装红色染料,长7.2厘米、宽4.2厘米、深1.1厘米。
尼雅1号墓地5号墓出土的一位青年女性干尸,腰部随葬木叉,上挂化妆袋,内装铜镜、胭脂粉袋、丝线等。
尼雅1号墓地5号墓出土的虎斑纹锦袋,内装有铜镜、胭脂粉包、绕线轴、线团绢卷等女红用具[5]。
以上民丰县尼雅古墓出土的考古资料表明,精绝国妇女十分重视面部的化妆,尼雅古墓出土的已染成紫红色的丝绵团,牛角化妆盒内储放的红色颜料和黑色颜料,还有出土的胭脂粉包、化妆袋、铜镜等化妆用品,一应俱全,这些都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了西域女子在汉晋时期,已经掌握了比较完备的化妆和美容的方法。黑色颜料用于描眉,红色颜料用于脸部的化妆,红色颜料的使用,说明当时西域女子还喜欢彩妆。
唐代的服饰文化博采众长,特别是女子服饰是有史以来最艳丽的装束。当时以吐鲁番高昌为代表的西域女子的装束,一方面保持着本地区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她们的服装样式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唐代西域妇女对化妆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仕女图》绢画,女舞俑、仕女俑、劳动俑等(图4),再现了唐代西域妇女五彩缤纷的化妆习俗。唐代西域女子的化妆,一般可分为画眉、抹胭脂、贴花钿、点面靥、描斜红等几个步骤。
画眉
眉毛是人们表达感情的重要部位,新疆各民族饰眉的历史源远流长,早期是用石笔磨粉或是用树枝烧成炭条描绘眉毛。考古人员还在鄯善县2500年前的苏贝希古墓、温宿县汉代的包孜东古墓、洛浦县山普拉古墓都发现了用于描眉的眉石和石眉笔,说明西域画眉的历史十分悠久。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画眉的风气日盛,就连八岁的女孩,都能像大人一样描起眉毛。如李商隐《无题》诗:“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据史籍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兴趣广泛,不仅喜欢吟诗作曲,还染有“眉癖”,曾令画工画《十眉图》。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西域女子对眉毛的修饰也十分重视。新疆博物馆收藏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组劳动妇女俑的眉毛的十分独特,眉毛细长而弯曲,同新疆龟兹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飞天、菩萨等人物形象的眉毛十分相似,如同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中描绘的那样“青黛点眉眉细长”。现藏于日本的出土于吐鲁番吐峪沟古墓的一幅《乐舞女图》绢画中的女子的眉毛也是细长的柳叶眉,初唐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一诗中“纤纤岁月上鸦黄”形容的就是一种象新月一样又细又弯的眉形。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围棋仕女图》中的那位正在下棋的贵妇人以及旁边站着的侍女们的眉形却描绘的又黑又宽(图5),如同唐代诗人沈全期诗中所云:“拂黛随时广。”反映了当时描绘阔眉的风尚。
彩妆
据文献记载,早在汉代我国西北地区的匈奴贵族妇女就有喜欢用胭脂化妆的习俗。公元前138年和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将西域各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风情介绍到了中原,胭脂也被引进到中原地区,深受中原妇女的喜爱。专家们认为胭脂是一种用名为“红蓝”的花朵制成的,它的花瓣有红色的色素,对于喜欢彩妆的西域居民来说是一种理想的化妆品。考古工作者在民丰县尼雅古墓发现了汉晋时期的用于化妆用的红色颜料。南北朝时期西域女子依然喜欢彩妆,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的“高昌章和十八年(公元548年)光妃随葬衣物疏”中有“.胭脂、胡粉、青黛、墨黛”等物。到了唐代,西域女子对彩妆的偏爱依然不减。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几件劳动妇女俑,白脸上似施了胭脂,涂成圆形,装饰效果十分明显。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围棋仕女图》中的那位正在下棋的贵妇人以及旁边站着的侍女们,个都面如桃花,红润恬静,反映了唐代西域女子施彩妆的习俗。
花钿
花钿是一种额饰,通常用色纸、鱼鳞片、金箔、丝绸等多种材料剪成花样粘贴而成,也有直接用颜料描绘在额头上的。相传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有一次喝了许多酒后,醉卧在一个长椅上,正好有一朵梅花掉在她的额头中间,额上染上了一朵五瓣花的花痕,洗之不去,宫女们见其新异,竞相效仿,她们直接把梅花的形状画在额际间,以后逐渐形成了贴花钿的习惯。五代牛峤《红蔷薇》诗:“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眉妆。”另外,对于花钿之所以在女子中流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借以掩瑕。相传武则天当权时,每次召见宰相时,都令上官昭容卧于床裙记录所奏之事。一日,宰相来奏事,昭容偷偷窥看,被武则天发觉,大怒,用指甲刀将她脸上刺伤,上官昭容便用花钿来掩饰脸上的伤痕。宫女们见了感觉十分新奇,都纷纷效仿,渐渐成了一种时髦的做法。花钿的形状多种多样,有桃花形、梅花形、菱形、宝相花形、圆形等,颜色多有红、黄、绿等。其中,最为精彩的是一种“翠钿”,它是以各种翠鸟羽毛制成,整个饰物呈青绿色,清新别致,极富情趣。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屏风画《仕女图》绢画中的女子服饰华丽、形态端庄、气质高雅,额际间贴的菱形花钿十分醒目(图6)。此外在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几件女舞俑的额际间也有这种妆饰。唐代诗人杜牧诗中曾云:“春阴扑翠钿。”温庭筠诗里也有“眉间翠钿深”的描述,由此可见,绿色花钿在西域确实存在,而且在吐鲁番西州妇女中十分流行。
额黄
女子在前额上涂画黄粉也是唐代西域女子中颇为流行的一种妆饰手段。这是一种南北朝时期兴起的妆饰手段。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进入鼎盛时期,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这一社会现象的生动写照。随着佛教思想的渗入,西域各地的文化艺术及民间风情等也渐渐传入中原,对中原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妇女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启发,在自己的额头涂染上黄色,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黄额的习俗。中原女子在额前涂黄粉的习俗兴起于南北朝,著名的北朝乐府《木兰辞》中就写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前面所说的出土于吐鲁番吐峪沟古墓的那幅唐代绢画《乐舞女图》中的仕女(图7),身穿回鹘式翻领彩金锦窄袖服装,头梳高耸的发髻,额上描绘的黄色圆晕清晰可见。
斜红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藏中出土的屏风画《仕女图》绢画和彩绘女舞俑所表现的仕女和舞女,其面部还有一种十分特殊的面饰,就是在女子太阳穴部位各画一条红色弯弯的新月形,有的还故意描绘成残破状,宛如白净的脸旁平添了两道伤疤,这种妆饰,被称为“斜红”。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十分怪异奇特,但在唐代它是一种十分时髦的妆饰。唐代诗人罗虬云:“一抹浓红傍脸斜,妆成不语独攀花。”元稹的“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说的就是这种妆饰。其俗始于三国。据唐人张泌《妆楼记》记载: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宫中新添了一名叫薛夜来的宫女。一天夜里,文帝在灯下读书,周围用水晶制成七尺高的屏风相隔。薛夜来走近文帝时,不觉一头撞上屏风,顿时鲜血直流,受伤部位像朝霞一样散开,由此留下两道疤痕,事后文帝对她更加怜惜。其他宫女为了得到文帝的宠幸,也模仿起她的莫样,用胭脂在脸部画上这种血痕,名曰“晓霞妆”,后逐渐演变成这种特殊的妆饰——斜红。南朝梁简帝《艳歌篇》中曾云:“分妆间浅靥,绕脸傅(敷)斜红。”便指此妆。唐代妇女脸上的斜红,一般都描绘在太阳穴部位,工整者形如弯月,复杂者状似伤痕。为了造成残破之感,有时还特在其下部,用胭脂晕染成血迹摸样。在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一件唐代女舞俑脸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斜红的妆饰。不过斜红这种面妆终究属于一种缺陷美,因此自晚唐以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面靥
面靥也叫“妆靥”,是施于面颊酒窝处的一种妆饰。它原是宫廷生活中宫女月事来临时,不能接受“御幸”的一种暗示。但宫中舞伎见其红圆可爱,不时仿效一下,拿来作脸妆,以后传到民间,逐渐演变成一种妆饰。据考证,早在汉代中原就有点面靥的习尚,不过那时叫“的”。西汉作家繁钦《耳·愁赋》一文中有“点圜的之荧荧,映双铺而相望”的句子。“双铺”是左右脸颊,圜的就是脸上的圆点。妆靥的通常直接用颜色点染,如《留青日札》所说“古人点朱于额,以示进退之节”。在唐代这种妆饰传入西域的高昌地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几件仕女俑脸上就绘有这种妆饰。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彩绘长裙女舞俑,额间贴菱形花钿(图8),脸颊抹斜红,俏丽的面颊点饰如黄豆大小的红圆点,显得格外楚楚动人。到了晚唐至五代时,妇女的妆饰风气有增无减,敦煌莫高窟壁画《于阗公主像》中的回鹘公主身着色彩鲜艳的翻领回鹘式长袍,圆润的脸上酒窝处就饰有这种独特的面饰,反映西域贵族女子的化妆习俗。
点唇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藏中出土的绢画《仕女图》、女舞俑等女子形象中(图9),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西域女子的口型十分娇小,反映了当时西域高昌女子的审美情趣。这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审美标准有相同之处,如同白居易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诗句,至今仍被用作形容美丽的中国女性的首选佳句。中国古代妇女的唇脂是丹,“丹”即朱砂,它是古代妇女妆唇所用唇脂的主要原料。古人在丹中加入适当的动物脂膏,使其具有防水性能。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围棋仕女图》中旁边站着的侍女们,其唇被画成颤悠悠的花朵状,上下两唇均为鞍形,如四片花瓣,望之极有动感,显得鲜润可爱。
附注
注释:
图1:且末扎滚鲁克墓出土的2800年前的脸部化妆的男女干尸(摹绘图)
图2:眉笔和眉石,洛浦县山普拉汉代古墓出土
图3:1959年民丰县尼雅东汉墓出土的刺绣粉袋
图4:化妆示意摹绘图
图5: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围棋仕女图》中侍女的眉形描绘的又黑又宽
图6: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屏风画《仕女图》绢画中的额头贴有菱形花钿的女子
图7:吐鲁番吐峪沟古墓的那幅唐代绢画《乐舞女图》中额头贴有的额黄的仕女
图8: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面颊酒窝处的面靥施有彩绘长裙女舞俑
图9:《围棋仕女图》中的点唇侍女
[1]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1989年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2年第2。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新疆山普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周汛、高春明著:《中国古代服饰大观》第124页,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4]李肖冰编著《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第9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1999年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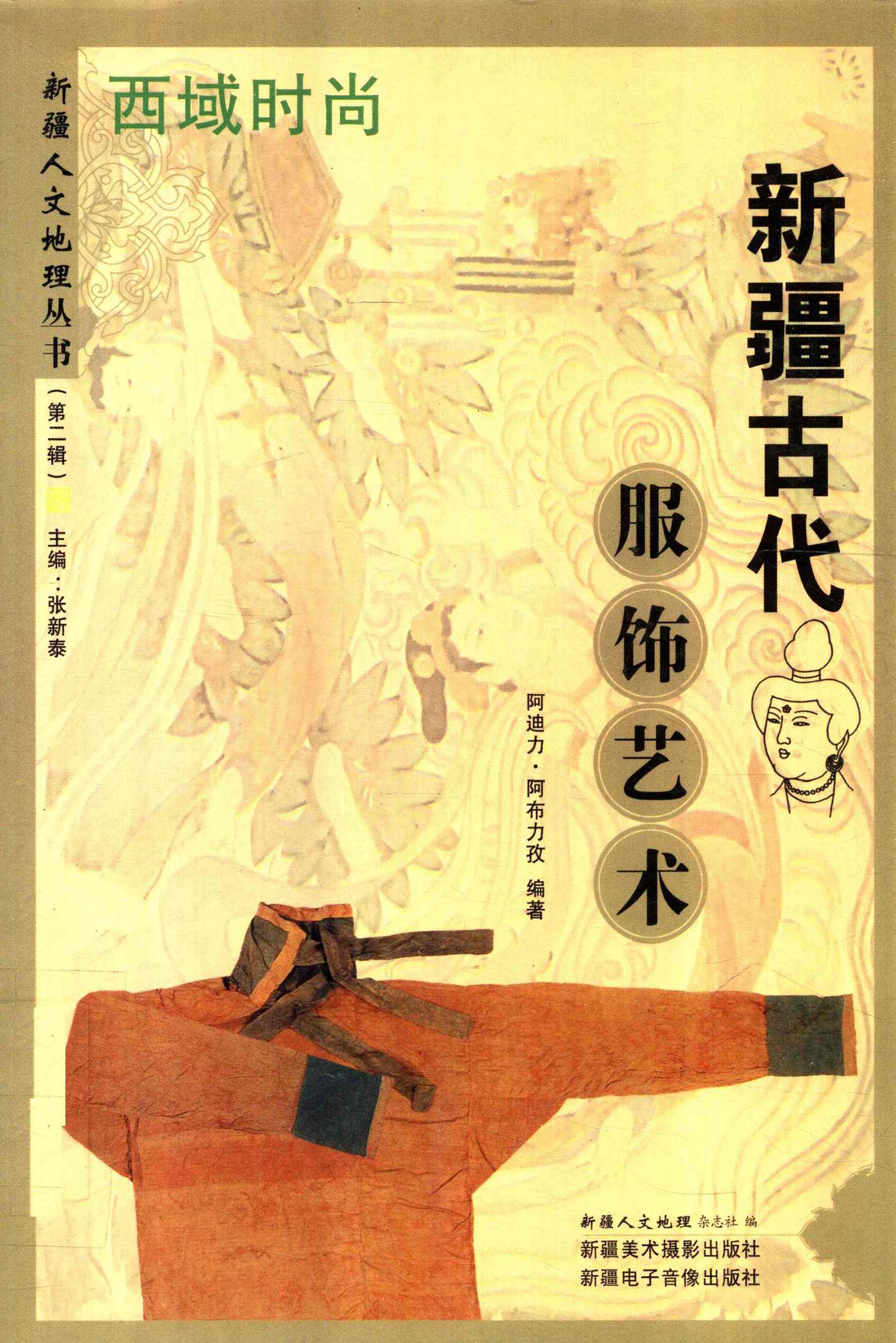
《新疆古代服饰艺术》
出版者: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新疆古代服饰文化,包括新疆古代服饰文化概览、冠冕堂皇新疆古代的帽子、新疆古代居民的发式等内容。我国自古以来就以“衣冠王国”而著称于世。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西域地区,服饰文化发展也源远流长,特别是先秦时期的毛织服饰和汉唐时期的丝绸服装,在中外服饰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阅读
相关地名
新疆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