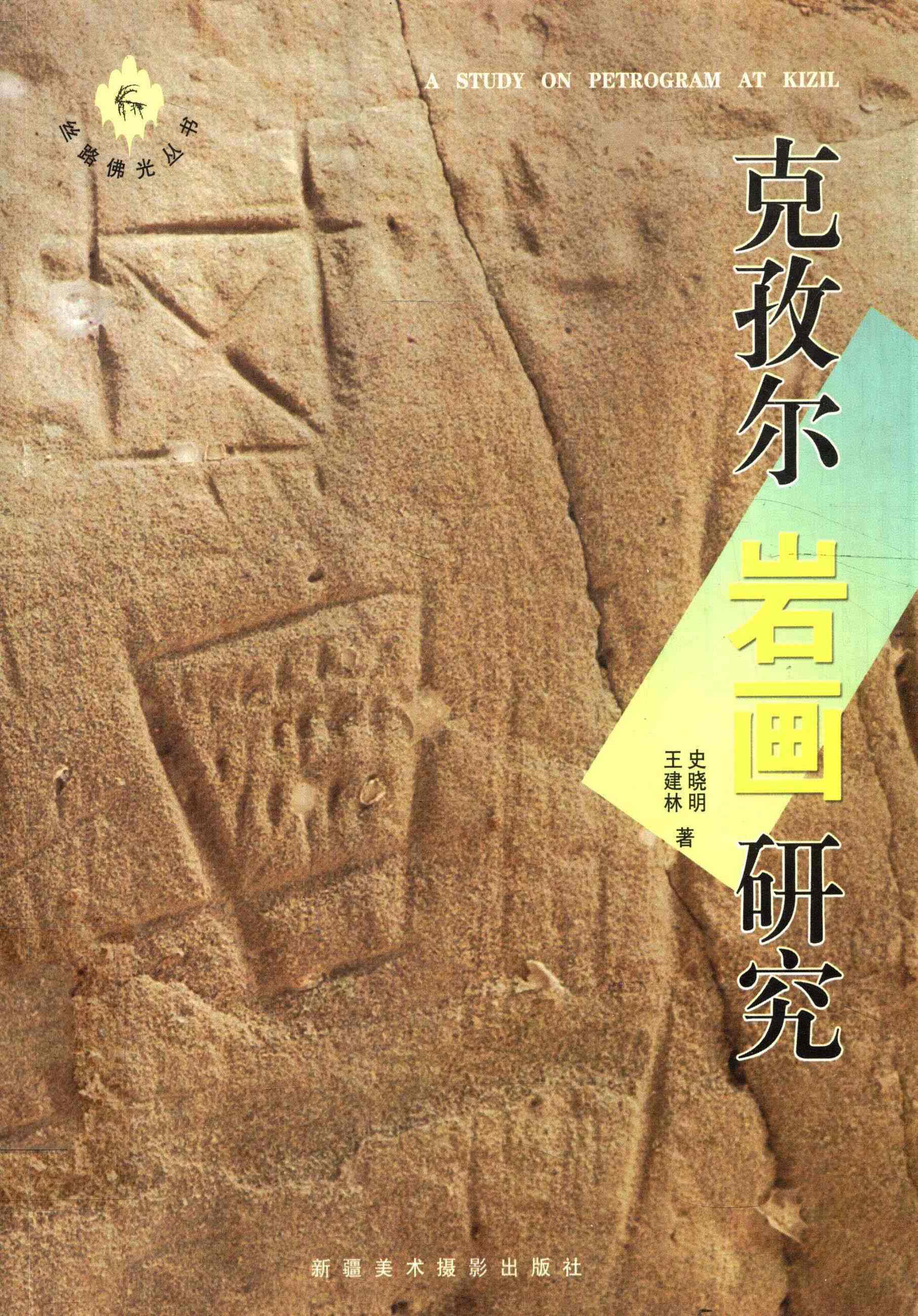内容
岩画断代和作者的归属是岩画研究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年代越久远就越不易把握。况且,岩画的作者与分布区域又多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文化有关,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这个难题。
比起目前岩画断代的一般性方法来说(动物考古法、碳十四测定法、比较学、层位叠压现象、风格题材等),克孜尔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相对而言要明确得多,如年代的上限问题就会相对明朗。可是,眼下依然还有诸多的扑朔迷离之处。如前所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必须首先借助前人对克孜尔岩画年代与族属的观点,然后,再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黄文弼先生1958年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推测克孜尔石窟的三处岩画非近代人手笔。他认为第93窟的刻画“疑为游牧民族走马为之游戏图”,同时根据壁面上的文字和其它洞窟的文字题记,推测此为“仿游牧民族之游戏绘画”,时代为唐之末叶。另外,亦狭克洞中刻画的图像和民族古文字,“即为过此商侣所为”(40)。显然,黄先生的对岩画年代的看法是与他在克孜尔发掘到的文字遗书与题记有关,而且偏重于汉文的年号与史料(41)。由此,他才怀疑作者是“仿”游牧民族的汉人所为。而亦狭克沟没有汉文题字,故可能是过往的非汉人的商侣。黄先生的论点为我们看待克孜尔岩画的年代与作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和分析线索。
北京大学宿白先生1979年在谈及新疆地区的佛教诸问题时曾涉及克孜尔石窟的岩画年代与族属,宿先生以石窟考古类型学和西域历史文化背景为基点,并与当时周邻地区已发现的岩画资料作比较后为克孜尔部分重要洞窟和亦狭克沟的岩画年代和作者给予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克孜尔谷内区和谷东区大约八世纪开凿的某些洞窟和克孜尔东亦狭克沟中的石窟的刻画形象与内容和西藏西部、楼兰地区以及甘肃嘉峪关一带的岩画极为相似。这些都是九世纪吐蕃牧民的遗留。
1985年,史晓明与王建林认为第93、95、131窟是岩画中非常成熟的作品,年代也较晚。考虑到石窟中整体岩画的情况,将这些岩画的年代上限定在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即公元八九世纪,下限时间至少推至十三世纪左右,作者并非只局限于吐蕃游牧民,甚至可能还有回鹘、蒙古时期的遗留(42)。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吴焯先生主要针对第131窟和第93窟这两个洞窟的岩画,将宿白先生提示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学科化,观点也进一步明确。他认为:第93窟的题材是“吐蕃征战图”,作者是吐蕃士兵;131窟的题材是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作者是吐蕃的部民百姓,其年代上限可早到公元七世纪末安西第一次陷于吐蕃的期间之内,下限则晚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前(43)。
北京大学晁华山先生根据第93窟刻画的三游旗、汉字以及石窟内其它洞窟遗留的汉文题记的年号和相关史料,以及公元9世纪后至清代初期这里再没有留下汉人的其他遗迹而断定,该窟的刻画是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唐军士兵所作(4)。
综上所述,研究者之间确实存在有不同观点上的差异,可归纳的共同之处在于:岩画的年代上限应该是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岩画的作者多与游牧民族相关;吐蕃与唐朝在龟兹的争夺战是第93等窟岩画发生的主要线索;不同的见解是作者族属有区别,还有岩画的年代下限不易把握。以下,笔者试图再一次在前人的基础上(45),对克孜尔岩画的整体状况和以上介绍的实际遗存作具体地分析与鉴别,从中找到相应的合适角度与材料来分别看待克孜尔不同洞窟、不同题材、不同造型的岩画现象,进一步地探讨克孜尔石窟岩画的有关问题。
既然岩画年代的上限是与石窟的衰落有关,那么,有必要先弄清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究竟在何时?其实,克孜尔重要的岩画年代与族属焦点可以集中到第93窟的问题上来,该窟特殊的刻画图形与文字题记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国内外学界一般的共识是公元8世纪,这一点无庸质疑。并且可能与当时发生在龟兹的战争有关,而战争又可能是唐王朝与吐蕃在西域的霸权之争,由此才直接影响到克孜尔石窟的衰落,故龟兹学的研究者都将第93窟的刻画归属为争战的题材,只是作者的族属问题意见不一致。黄文弼先生尽管没有明指是哪个民族所为,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明显看出他是指唐军,而晁华山先生也持这种观点,并且理由说得相对合理(2007年8月27日笔者在敦煌学术会期间向马世长先生请教时他也倾向于作者为汉人);然而,宿白和吴焯先生的看法也不无道理。可是,还有一些迹象他们没有注意到或是观察的不细致,如:第93窟的四壁均有刻画,只是大部分的墙皮因该洞窟比较潮湿,尤其正壁与北壁严重脱落,现在只残存个别图像,尽管如此,某些形象还是非常重要,例如正壁残留的两个汉文题字、似大鸟的图形、大角羊、旗帜上的圆形图像,南壁西侧的罐型图像。另外,窗户南壁旗帜上的羊的图示等,这些图像比起其它图形都是供我们分析判断年代和族属的比较直接的特殊研究信息,如罐型的图式在各地的岩画中除了克孜尔这一例之外还有西藏西部日土岩画中也有陶罐出现(图275)(46),如果岩画作者只有吐蕃游牧民有刻画陶罐的习惯的话(47),那么,宿白先生和吴焯先生的立论就有依据可寻,再加之西藏(苏毗)的“鸟卜”习俗确实与克孜尔岩画中出现的鸟的图形相吻合。此外,还有吐蕃有“事羱羝为大神”的图腾习俗(48),如果正壁、窗户南壁旗帜上的羊的标示与此相关的话,这就更增加了吐蕃族属的说服力。不过,虽然有这些旁证,可是,目前第93窟的两处汉字却难以找到对应的、合适的解释理
由,因为,那两处遗留的汉字确实与岩刻是同时所为(49)。然而,如进一步考虑到汉字书写的欠规范化程度和作者特别强调羊图腾因素的话,作者可能更倾向于游牧民族。当然,是否还存在其它偶然性的因素目前仍很难断定。此外,因为要顾及石窟岩画的整体状况,以下再简述六个方面的问题,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1.看待克孜尔岩画的总体状况,不仅要重视本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承关系,而且还要将克孜尔岩画放到整个中亚文化圈的背景中去审视,以此为视野,就不能笼统地把克孜尔不同的83个洞窟的岩画问题概念化,理应区别对待,这样考虑会有利于岩画年代的下限与作者族属等相关问题。同时,又牵扯到研究方法的拓展和图像学的渗入。这些问题的提出至少是基于近些年来国内的岩画发现与研究工作逐步进展,使得龟兹石窟的岩画研究有了相对丰富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在运用图像学的方法论方面也有了多重视角,包括本地区新发现的岩画材料,可以提供直接的近距离的对比。
2.通过本地区普遍存在的岩画现象,使我们首先更加注重,龟兹自古以来就是多个游牧民族定居和不断变迁的地区,龟兹本土的吐火罗民族自不必多言,他们在长期的游牧迁徙的历史长河中在中亚各地均留下了辉煌的足迹(50),虽然吐火罗民族自从来到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定居以来,从来就没有也不会放弃传统的牧业生活方式(51);其次是后来的突厥、吐蕃、回鹘、蒙古族等,他们都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并且都有刻画岩画的文化传统(52)。这些基本的文化背景是我们面对龟兹地区的岩画时所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基础性问题(53)。如拜城县老虎台的岩画中羊的刻画形象与克孜尔第154窟中的羊的表现手法如出一辙(图276)。所以,克孜尔岩画作者的族属问题就不免更复杂化了;再者,看待龟兹地区的岩画,不仅仅是只局限于新疆本地,而且也不能仅限于所谓中国的“半月形岩画圈”或“半月形高地文化传播带”的范围内(54),它应该是与中亚之外更广阔的地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55)。
除了上述的“羊图腾”之外,我们从第7、93、95、100、117、124、131窟均刻有类似“鸟”的图像可以明显感到还可能有“鸟图腾”的相关问题。因为“鸟图腾”的图像在各地的岩画中包括新石器时期的其它艺术中都普遍存在(56),并各有其地方特色(57)。克孜尔岩画属于晚期现象,狩猎、野生动物等题材消失,可是,类鸟图像竟如此突出,而且在不同的洞窟里出现,可见其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相通之处,这至少与刻画者的传统观念与生命意识的潜质有关(58)。这种对鸟的非记事图像的、非自然属性的特殊关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岩画作为一种原始语言的表现,也会有方言”。但是,在世界岩画的范围内,“一些重复的因素出现在所有的大陆,标示出岩画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结构”(59)。由此可见,克孜尔岩画的共同文化内涵并非仅限于周邻地区。
3.关于克孜尔岩画年代的下限,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推至13世纪以后。一个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如果纵观龟兹石窟的整体兴衰史,就可以基本上确定这种看法。因为,以克孜尔为代表的一批龟兹本地风格的石窟大约与克孜尔石窟同时衰落,而惟独库木吐拉石窟延续的时间比其它石窟长得多(60)。所以,当石窟还没有废弃之前,洞窟内的壁画上是不可能随意乱刻乱画的。笔者曾在台台尔、库木吐拉等龟兹石窟也发现有数量不少的岩画迹象(61)。故此,如果以库木吐拉为例证,将该石窟岩画的上限和龟兹其它石窟岩画年代的下限一起来考虑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疑问。
4.结合岩画发生之前的龟兹壁画相关题材与造像,找到间接的可能性的佐证资料。龟兹石窟壁画中大量的动物图像从侧面也反映出游牧文化在佛教造像中的突出地位,特别是羊的造型在壁画中表达的格外精彩(图277-282)。因为,羊不仅是游牧民族日常的主要食物,而且还与游牧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图腾崇拜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仪式上的联系,如突厥汗国就曾经把野山羊作为政权的象征(62)。于是,第93窟窗户南壁的有山羊的旗帜就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同时,问题也愈加微妙起来,因为不仅是古代羌族(63)、突厥民族,而且吐蕃,甚至中亚的游牧民族都同样有这种遗风(64)。
5.手模与印记问题。手模又可称“手印”等(65)。至于说手模这种最古老的、跨地域、跨时代、跨民族的造型艺术观念,尤其是在岩画造像的体裁中显得特别突出,由于手模的文化内涵各不相同(有力量、权威、意志、占有、征服、胜利、祈求、避邪、求援、生产、生殖、兴旺、增多、维持、享受、创造、标志、表现、自豪、礼仪、礼赞、游戏、留念、签名、报道等多种象征寓意的可能性),因而,手模现象是克孜尔岩画中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是由于洞窟废弃之后的上千年的时间内,无数人曾来过此地,或居住、路过、游玩、朝拜等等,既使近代和当代,也有游客在重复古人的“游戏”(66)。按照有些学者的看法,手模往往与其伴生的图形有关联(67)。既有原始思维和宗教巫术的含义,又有现代人玩耍留念的游戏行为。所以,克孜尔手模的表达方式和寓意也应该有所区别。如第93等窟大片的手模,可能就与战争的胜负有关;第95、131、132等窟的可能就与氏族部落的生殖兴旺、宗教礼仪等有联系;而第100窟龛内的带有圆心的手模估计与同时刻画的阿拉伯文字有关系。至于说近年来不少游人的随意刻画又可另当别论了。
岩画中的印记符号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氏族问题(68),但是,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如第131窟等岩刻中的多处符号印记和其它洞窟的不同符号图式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此外,同一个洞窟内存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刻画图形、文字符号等也是正常现象,第95、131、220等比较明显。
6.晚期岩画的普遍性问题。岩画的风格化问题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的共性,由于生产力低下,刻画的质地与材料更接近于自然;因为造型能力所限,形象的塑造更倾向于稚拙;生存信念直接受潜意识控制,故审美判断更接近本能;鉴于思维方式的古朴,表现形式受宗教信仰的迷惑与支配。
克孜尔岩画之所以有多种游牧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史前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间曾经有过漫长的、广泛的接触与交流。这种直接和间接的传承脉络关系会随着当代科技水平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而变得日益清晰起来(69)。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先民们在游牧经济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型的同时,还依然会保留着畜牧业生产的传统观念,这是无可非议的。所以,第95、131窟有意突出畜牧业生产的题材,而野生动物和狩猎的场面消失等与原始岩画的题材有明显差异,包括大量的文字刻画、体裁缺乏原创性等,这些都是克孜尔岩画的基本特点,这显然是游牧民族走向定居生活的文明结果。
比起目前岩画断代的一般性方法来说(动物考古法、碳十四测定法、比较学、层位叠压现象、风格题材等),克孜尔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相对而言要明确得多,如年代的上限问题就会相对明朗。可是,眼下依然还有诸多的扑朔迷离之处。如前所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必须首先借助前人对克孜尔岩画年代与族属的观点,然后,再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黄文弼先生1958年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推测克孜尔石窟的三处岩画非近代人手笔。他认为第93窟的刻画“疑为游牧民族走马为之游戏图”,同时根据壁面上的文字和其它洞窟的文字题记,推测此为“仿游牧民族之游戏绘画”,时代为唐之末叶。另外,亦狭克洞中刻画的图像和民族古文字,“即为过此商侣所为”(40)。显然,黄先生的对岩画年代的看法是与他在克孜尔发掘到的文字遗书与题记有关,而且偏重于汉文的年号与史料(41)。由此,他才怀疑作者是“仿”游牧民族的汉人所为。而亦狭克沟没有汉文题字,故可能是过往的非汉人的商侣。黄先生的论点为我们看待克孜尔岩画的年代与作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和分析线索。
北京大学宿白先生1979年在谈及新疆地区的佛教诸问题时曾涉及克孜尔石窟的岩画年代与族属,宿先生以石窟考古类型学和西域历史文化背景为基点,并与当时周邻地区已发现的岩画资料作比较后为克孜尔部分重要洞窟和亦狭克沟的岩画年代和作者给予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克孜尔谷内区和谷东区大约八世纪开凿的某些洞窟和克孜尔东亦狭克沟中的石窟的刻画形象与内容和西藏西部、楼兰地区以及甘肃嘉峪关一带的岩画极为相似。这些都是九世纪吐蕃牧民的遗留。
1985年,史晓明与王建林认为第93、95、131窟是岩画中非常成熟的作品,年代也较晚。考虑到石窟中整体岩画的情况,将这些岩画的年代上限定在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即公元八九世纪,下限时间至少推至十三世纪左右,作者并非只局限于吐蕃游牧民,甚至可能还有回鹘、蒙古时期的遗留(42)。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吴焯先生主要针对第131窟和第93窟这两个洞窟的岩画,将宿白先生提示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学科化,观点也进一步明确。他认为:第93窟的题材是“吐蕃征战图”,作者是吐蕃士兵;131窟的题材是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作者是吐蕃的部民百姓,其年代上限可早到公元七世纪末安西第一次陷于吐蕃的期间之内,下限则晚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前(43)。
北京大学晁华山先生根据第93窟刻画的三游旗、汉字以及石窟内其它洞窟遗留的汉文题记的年号和相关史料,以及公元9世纪后至清代初期这里再没有留下汉人的其他遗迹而断定,该窟的刻画是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唐军士兵所作(4)。
综上所述,研究者之间确实存在有不同观点上的差异,可归纳的共同之处在于:岩画的年代上限应该是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岩画的作者多与游牧民族相关;吐蕃与唐朝在龟兹的争夺战是第93等窟岩画发生的主要线索;不同的见解是作者族属有区别,还有岩画的年代下限不易把握。以下,笔者试图再一次在前人的基础上(45),对克孜尔岩画的整体状况和以上介绍的实际遗存作具体地分析与鉴别,从中找到相应的合适角度与材料来分别看待克孜尔不同洞窟、不同题材、不同造型的岩画现象,进一步地探讨克孜尔石窟岩画的有关问题。
既然岩画年代的上限是与石窟的衰落有关,那么,有必要先弄清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究竟在何时?其实,克孜尔重要的岩画年代与族属焦点可以集中到第93窟的问题上来,该窟特殊的刻画图形与文字题记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国内外学界一般的共识是公元8世纪,这一点无庸质疑。并且可能与当时发生在龟兹的战争有关,而战争又可能是唐王朝与吐蕃在西域的霸权之争,由此才直接影响到克孜尔石窟的衰落,故龟兹学的研究者都将第93窟的刻画归属为争战的题材,只是作者的族属问题意见不一致。黄文弼先生尽管没有明指是哪个民族所为,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明显看出他是指唐军,而晁华山先生也持这种观点,并且理由说得相对合理(2007年8月27日笔者在敦煌学术会期间向马世长先生请教时他也倾向于作者为汉人);然而,宿白和吴焯先生的看法也不无道理。可是,还有一些迹象他们没有注意到或是观察的不细致,如:第93窟的四壁均有刻画,只是大部分的墙皮因该洞窟比较潮湿,尤其正壁与北壁严重脱落,现在只残存个别图像,尽管如此,某些形象还是非常重要,例如正壁残留的两个汉文题字、似大鸟的图形、大角羊、旗帜上的圆形图像,南壁西侧的罐型图像。另外,窗户南壁旗帜上的羊的图示等,这些图像比起其它图形都是供我们分析判断年代和族属的比较直接的特殊研究信息,如罐型的图式在各地的岩画中除了克孜尔这一例之外还有西藏西部日土岩画中也有陶罐出现(图275)(46),如果岩画作者只有吐蕃游牧民有刻画陶罐的习惯的话(47),那么,宿白先生和吴焯先生的立论就有依据可寻,再加之西藏(苏毗)的“鸟卜”习俗确实与克孜尔岩画中出现的鸟的图形相吻合。此外,还有吐蕃有“事羱羝为大神”的图腾习俗(48),如果正壁、窗户南壁旗帜上的羊的标示与此相关的话,这就更增加了吐蕃族属的说服力。不过,虽然有这些旁证,可是,目前第93窟的两处汉字却难以找到对应的、合适的解释理
由,因为,那两处遗留的汉字确实与岩刻是同时所为(49)。然而,如进一步考虑到汉字书写的欠规范化程度和作者特别强调羊图腾因素的话,作者可能更倾向于游牧民族。当然,是否还存在其它偶然性的因素目前仍很难断定。此外,因为要顾及石窟岩画的整体状况,以下再简述六个方面的问题,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1.看待克孜尔岩画的总体状况,不仅要重视本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承关系,而且还要将克孜尔岩画放到整个中亚文化圈的背景中去审视,以此为视野,就不能笼统地把克孜尔不同的83个洞窟的岩画问题概念化,理应区别对待,这样考虑会有利于岩画年代的下限与作者族属等相关问题。同时,又牵扯到研究方法的拓展和图像学的渗入。这些问题的提出至少是基于近些年来国内的岩画发现与研究工作逐步进展,使得龟兹石窟的岩画研究有了相对丰富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在运用图像学的方法论方面也有了多重视角,包括本地区新发现的岩画材料,可以提供直接的近距离的对比。
2.通过本地区普遍存在的岩画现象,使我们首先更加注重,龟兹自古以来就是多个游牧民族定居和不断变迁的地区,龟兹本土的吐火罗民族自不必多言,他们在长期的游牧迁徙的历史长河中在中亚各地均留下了辉煌的足迹(50),虽然吐火罗民族自从来到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定居以来,从来就没有也不会放弃传统的牧业生活方式(51);其次是后来的突厥、吐蕃、回鹘、蒙古族等,他们都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并且都有刻画岩画的文化传统(52)。这些基本的文化背景是我们面对龟兹地区的岩画时所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基础性问题(53)。如拜城县老虎台的岩画中羊的刻画形象与克孜尔第154窟中的羊的表现手法如出一辙(图276)。所以,克孜尔岩画作者的族属问题就不免更复杂化了;再者,看待龟兹地区的岩画,不仅仅是只局限于新疆本地,而且也不能仅限于所谓中国的“半月形岩画圈”或“半月形高地文化传播带”的范围内(54),它应该是与中亚之外更广阔的地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55)。
除了上述的“羊图腾”之外,我们从第7、93、95、100、117、124、131窟均刻有类似“鸟”的图像可以明显感到还可能有“鸟图腾”的相关问题。因为“鸟图腾”的图像在各地的岩画中包括新石器时期的其它艺术中都普遍存在(56),并各有其地方特色(57)。克孜尔岩画属于晚期现象,狩猎、野生动物等题材消失,可是,类鸟图像竟如此突出,而且在不同的洞窟里出现,可见其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相通之处,这至少与刻画者的传统观念与生命意识的潜质有关(58)。这种对鸟的非记事图像的、非自然属性的特殊关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岩画作为一种原始语言的表现,也会有方言”。但是,在世界岩画的范围内,“一些重复的因素出现在所有的大陆,标示出岩画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结构”(59)。由此可见,克孜尔岩画的共同文化内涵并非仅限于周邻地区。
3.关于克孜尔岩画年代的下限,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推至13世纪以后。一个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如果纵观龟兹石窟的整体兴衰史,就可以基本上确定这种看法。因为,以克孜尔为代表的一批龟兹本地风格的石窟大约与克孜尔石窟同时衰落,而惟独库木吐拉石窟延续的时间比其它石窟长得多(60)。所以,当石窟还没有废弃之前,洞窟内的壁画上是不可能随意乱刻乱画的。笔者曾在台台尔、库木吐拉等龟兹石窟也发现有数量不少的岩画迹象(61)。故此,如果以库木吐拉为例证,将该石窟岩画的上限和龟兹其它石窟岩画年代的下限一起来考虑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疑问。
4.结合岩画发生之前的龟兹壁画相关题材与造像,找到间接的可能性的佐证资料。龟兹石窟壁画中大量的动物图像从侧面也反映出游牧文化在佛教造像中的突出地位,特别是羊的造型在壁画中表达的格外精彩(图277-282)。因为,羊不仅是游牧民族日常的主要食物,而且还与游牧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图腾崇拜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仪式上的联系,如突厥汗国就曾经把野山羊作为政权的象征(62)。于是,第93窟窗户南壁的有山羊的旗帜就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同时,问题也愈加微妙起来,因为不仅是古代羌族(63)、突厥民族,而且吐蕃,甚至中亚的游牧民族都同样有这种遗风(64)。
5.手模与印记问题。手模又可称“手印”等(65)。至于说手模这种最古老的、跨地域、跨时代、跨民族的造型艺术观念,尤其是在岩画造像的体裁中显得特别突出,由于手模的文化内涵各不相同(有力量、权威、意志、占有、征服、胜利、祈求、避邪、求援、生产、生殖、兴旺、增多、维持、享受、创造、标志、表现、自豪、礼仪、礼赞、游戏、留念、签名、报道等多种象征寓意的可能性),因而,手模现象是克孜尔岩画中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是由于洞窟废弃之后的上千年的时间内,无数人曾来过此地,或居住、路过、游玩、朝拜等等,既使近代和当代,也有游客在重复古人的“游戏”(66)。按照有些学者的看法,手模往往与其伴生的图形有关联(67)。既有原始思维和宗教巫术的含义,又有现代人玩耍留念的游戏行为。所以,克孜尔手模的表达方式和寓意也应该有所区别。如第93等窟大片的手模,可能就与战争的胜负有关;第95、131、132等窟的可能就与氏族部落的生殖兴旺、宗教礼仪等有联系;而第100窟龛内的带有圆心的手模估计与同时刻画的阿拉伯文字有关系。至于说近年来不少游人的随意刻画又可另当别论了。
岩画中的印记符号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氏族问题(68),但是,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如第131窟等岩刻中的多处符号印记和其它洞窟的不同符号图式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此外,同一个洞窟内存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刻画图形、文字符号等也是正常现象,第95、131、220等比较明显。
6.晚期岩画的普遍性问题。岩画的风格化问题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的共性,由于生产力低下,刻画的质地与材料更接近于自然;因为造型能力所限,形象的塑造更倾向于稚拙;生存信念直接受潜意识控制,故审美判断更接近本能;鉴于思维方式的古朴,表现形式受宗教信仰的迷惑与支配。
克孜尔岩画之所以有多种游牧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史前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间曾经有过漫长的、广泛的接触与交流。这种直接和间接的传承脉络关系会随着当代科技水平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而变得日益清晰起来(69)。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先民们在游牧经济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型的同时,还依然会保留着畜牧业生产的传统观念,这是无可非议的。所以,第95、131窟有意突出畜牧业生产的题材,而野生动物和狩猎的场面消失等与原始岩画的题材有明显差异,包括大量的文字刻画、体裁缺乏原创性等,这些都是克孜尔岩画的基本特点,这显然是游牧民族走向定居生活的文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