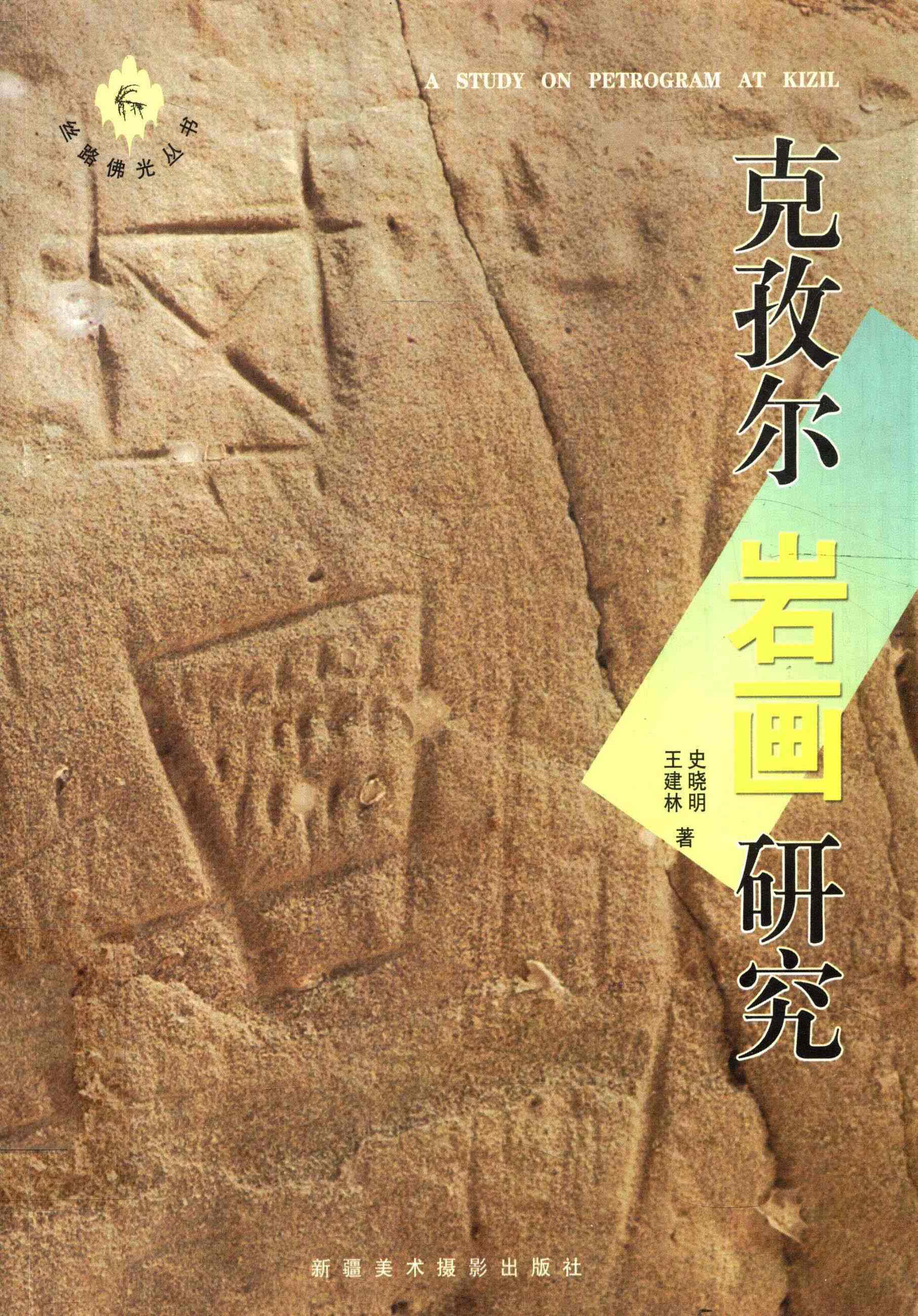内容
引言
1984年5月至1985年5月,我们曾对克孜尔石窟第93、95、131这三个洞窟内所遗存的古代游牧民的刻画图画和符号做过初次试探(1)。此后的20余年间,我们对克孜尔以及龟兹其它石窟普遍存在的这种文化迹象又不断有新的发现。由于那篇文章一直未正式刊出,加之近些年来考古工作在各地大量发现新的岩画“地区”和“地点”(2),与此同时,岩画这门学科在国内的学术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并且还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3),这使得我们对原先的工作结果不免产生新的认识,且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有了可继续探讨的必要性。此外,克孜尔的“岩画”研究本身就有可补充的空间。故此,本文以克孜尔洞窟岩画的多次实地考察为依据,整体地介绍这批晚期的岩画图像资料,并就有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克孜尔石窟的自然地理、人文背景
中国的早期佛教遗址克孜尔石窟,是十九处古龟兹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处(4)。它孤立地坐落在拜城盆地东端东南角的明屋依达格山南麓(5)西北距克孜尔乡政府约9公里(6)。海拔1320米,地理坐标:北纬41°47′、东经82°27′(7)。
克孜尔石窟虽然处在天山以南,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决定了其自然环境显然不同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干旱少雨的绿洲气候(8)。因为石窟前面的小绿洲四面环山,除了东、北、西三面是明屋依达格山高约200米的悬崖峭壁,大部分坐北朝南的洞窟与对面的寸草不生的却勒达格山(主峰高度2131米)隔河相望,两山之间冲积扇低地的交接处,渭干河由西向东蜿蜒流过,给这块神奇的土地又凭添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和滋润的气息。从明屋依达格山中部的峡谷中泻出的冲积扇沙地的形状,犹如一个倒挂的荷叶或横倒平放的、上北下南的菱格形(图1),像一枚绿色宝石镶嵌在荒滩戈壁的边缘深处。所以,克孜尔石窟的自然环境夏季凉爽,冬季温暖,春、夏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秋季水草肥美。难怪古代龟兹佛教僧侣将这块几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作为出家修行首选的理想孤境(9)。
其实,真正给克孜尔石窟这片小绿洲以恩惠的是明屋依达格山体下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特别是山体中部的峡谷中常年流出的滴泉之水(俗称:千泪泉),是灌溉这片绿洲的生命之泉。克孜尔现发现已编号的335个洞窟就是以这个峡谷为中心,并根据山势的走向而分为四个区域(10)。
在公元四至七世纪时,克孜尔石窟是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邦的佛教文化圣地,印度、波斯、西亚、中原文化先后荟萃于此,并且成为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发源地之一,特别是壁画与泥塑彩绘是中世纪早期世界范围内名符其实的造型艺术的新型典范(11)。其石窟形制、佛像样式传播影响到了凉州、敦煌、云岗、长安等中原内地(12),甚至波及朝鲜和日本。
根据古代西域和龟兹的历史文化发展概况来看,龟兹佛教造型艺术的参预者多与游牧民族有关,并不断融合扩展。本土的吐火罗人不必多说,其他的如:突厥、吐蕃、回鹘等民族都先后占领过龟兹(13)。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当佛教在龟兹衰落之后,克孜尔这片土地自然也就成为这些游牧民族后裔生活的天然乐园,尤其是冬季可能更为适合(14)。(图2-49)
二、关于克孜尔岩画的名称问题
在废弃的佛教石窟内,保留的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迹是否属于“岩画”现象,究竟对它们如何称呼?目前尚未有一致的看法(15)。因此,在论述本文的主题之前,有必要对这种遗存现象的名称作一辨识。
先看岩画的定义。辞海岩画辞条认为:“岩画是刻画在洞的壁上或山崖上的图画。”1986年11月,意大利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埃马奴尔·阿纳蒂先生在写给北京中国岩画展览之前的贺词中明确指出:“岩画是绘在或刻在洞穴或露天的岩石上的形象或符号。”
根据这两条定义以及国内岩画专家的共识(16),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将龟兹石窟内的这类文化遗存归属于岩画范畴并称其为“岩画”。其理由如下:那些图画和符号全部都刻在洞的壁上和露天的岩石之上,并且同岩画的主体创造者游牧民族的生活传承与文化性质毫无二致(凡研究者都一致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大部分的刻画质地是画壁画的草泥地仗,洞窟形式也是人为开凿的宗教建筑。然而正是这些废墟和遗留为作画者提供了现成的刻画场地,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图像是直接刻在砂岩之上(17),尤其那些大量的手模印记几乎全都是在砂石岩体上磨搓而成。由此,无论从内容(游牧体裁为主)还是形式上(质地与制作手法)都无法与各地岩画一般性的文化特征区别开来。为避免不必要的歧义,故本文继续沿用“岩画”这个术语。
三、前人成果的概述
1958年,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涉及克孜尔石窟岩画的有三处:“图38洞壁刻画故事画,出拜城克子尔明屋佛洞一组二洞东壁,高34.3,宽62.7厘米,刻画一狮子,张口舞爪,两足前伸,作猛扑状。前有一人危坐,屹然不动,姿势生动活泼,非近代人手笔。又同壁刻有(天宝十三载)年号,故此画亦当为同时所刻”;二是现编号谷内区第93窟的“洞壁刻走马图”,此洞的刻画“疑为游牧民族走马为之游戏图”,黄先生根据壁面上的文字和其它洞窟的文字题记,推测此为“仿游牧民族之游戏绘画”,时代为唐之末叶;三是“石刻兽形图,出克子尔明屋佛洞西二十里,亦狭克洞中,图像有大头羊、骆驼、黄羊和民族古文字。”“此刻画即为过此商侣所为”(18)。
北京大学宿白先生在1979年就新疆地区佛教遗迹调查等诸问题中曾明确提及:“克孜尔谷内和谷东区大约八世纪开凿的某些洞窟和克孜尔东亦狭克沟中的石窟壁面上,都出现了后来刻画的羊、马、驼、禽鸟和人物。这些刻画的形象与内容和西藏西部、楼兰地区以及甘肃嘉峪关一带的岩画极为相似。这些都是九世纪吐蕃牧民的遗留”(19)。
1984年5月,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的史晓明、王建林对克孜尔石窟的岩画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调查整理,并对主要的第93、95和131窟这三个岩画的重要代表性洞窟进行了初步的试探。我们认为第93窟南壁的岩画是一幅征战图,第95窟为牧乐图,第131窟是一幅迁徙图。表现的题材主题鲜明、构图完美,为各地少有,是岩画中非常成熟的作品,年代也比较晚。考虑到石窟中整体岩画的情况,将这些岩画的年代上限定为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即公元八九世纪,下限时间至少推至十三世纪左右,作者并非只局限于吐蕃游牧民,甚至可能还有回鹘、蒙古时期的遗留。这样考虑是因为龟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频繁变迁的地方以及克孜尔石窟约四分之一的洞窟内存有岩画(包括手模)的缘故(20)。
1986年,吴焯先生根据在克孜尔的调查以及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提供的部分照片,在《文物》杂志1986年第10期上刊登了题为《克孜尔石窟刻画图画的内容、作者和时代》的专题研究文章,主要针对第131窟和第93窟这两个洞窟的岩画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第131窟的作者是包括苏毗在内的吐蕃部民,题材表现的是部民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而第93窟则反映的是吐蕃士兵的军事生活和征战活动。两窟均是吐蕃文化在克孜尔佛教石窟开始废弃的同时或以后的体现。它的年代上限可早到公元七世纪末安西第一次陷于吐蕃的期间之内,下限则晚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前。
1993年,晁华山先生在论述克孜尔石窟开始荒废的时间上限时,明确提出第93窟刻画的“攻战图”可能是公元8世纪初驻军士兵所为,表现的是当时的作战情景。但同时又认为这些唐人刻画约作于七八世纪之交(21)。
1993年12月,《克孜尔石窟志》编写组根据史晓明提供的材料,第一次正式的比较完整的刊出克孜尔岩画的洞窟分布与数量统计表,并参照已发表的文章综述了各家的研究论点(22)。
2000年,吴焯先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又重提此事,观点并无大变化,只是在第93窟的作者与题材问题上明显地又考虑了黄文弼先生与晁华山先生的论点(23)。
四、岩画的分布、数量与内容
根据我们多次反复的调查材料统计,克孜尔石窟现有岩画遗存的洞窟83个(不包括亦狭克沟),岩画个体图形总数逾千,其中手模之外各种不同的岩画图形个体374个(见克孜尔岩画数量统计表的34个洞窟)、手模数量约930个(24)。它们分布在石窟的各个区域(主要集中在谷内区),大部分阴刻制作在窟内墙壁的泥皮(25)和砂岩上,也有个别的制作在窟外的砂岩上。位置的高度一般距地面1.5米上下。目前能辨认的形象有:羊、马、鹿、骆驼、禽鸟、狗、驴、战马、骑士、战旗、旗徽、矛、剑、弓箭、人物、陶器、文字、太阳、符号、手模等其它图形符号20余种。鉴于岩画总数百分之七十九的在谷内区,手模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也在谷内区,同时第93、95、131窟又是谷内区最突出的三个重点岩画洞窟,故本文论述的焦点自然也集中于此。为突出主体,以下先介绍这三个方形洞窟和谷内其它洞窟的具体遗留状况,然后再介绍其它区域的部分:
(一)谷内区(23个窟)
第93窟:该窟位于谷内区中段的西侧壁,距离沟口约一百米(26),洞窟坐西向东,位置高度约十余米,前室塌毁,残存南角,窟顶形状不详。西壁尚存,进入主室的门道位于北侧,南侧为主室的窗户(1987年安装门窗并修了进门的台阶),外室存砂岩手模。主室呈方形(图50),室内的所有壁面被烟熏黑。各壁边长约4.5米,壁高约2.8米,顶为穹窿式,从穹4窿顶向下分出17个条幅,穹4窿最大直径约3米,高约1.5米。地面中央部有一坑状。四面墙壁下部约三分之一的墙皮脱落,中部壁面均有岩画遗迹,残存图形、文字等百余个(27)。现结合图片和插图予以逐次描述:
正面壁(西壁):正壁右侧部位高1.5米以下和左侧1.8米以下的墙皮落毁,据估计正壁原先应有不少岩画,可惜仅有个别留存。现在壁面右侧残存岩画及符号个体7幅,形象有旗帜、大角羊、民族古文字,另在旗帜下残留有两个汉字题记,旗帜上还刻有一圆形标识,似人面像(图51-52)。
右侧壁(28)(南壁):右侧壁现存墙皮约6.3平方米,岩画面积约占下部的一半(现存长度3.25米,高度0.9米)(29),是该窟现存岩画的主体部分,个体图形的数量达72幅,所有的形象围绕征战而表现,主要有骑士、战马、战旗、长矛、弓箭为主,整个画面的布局似一场激烈的两阵交战的情景,双方的将领各自持矛跨马,高举大旗,在画面的中部交锋,各方骑兵们冲锋陷阵,短兵相接(图53-60)。从双方的阵势来看,似乎左边的阵容大(现存图形的个体数量也多于右方,再加上窗户的部分就更多),右方的后面可能还遭到攻击(可惜画面损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右方则处于劣势,因为右方的后面明显有两个形体较大的战骑面向后方在护卫防御。此外,双方的阵容中有一些特殊的图形值得关注:如右方的一个侈口、圜底的罐形物、一只类似飞禽的图像比较引人注目(图61-62),而左边阵容的前上方则有一图形似骆驼,上似一骑人(图63,黄文弼、吴焯以为毡房),并且还有两幅母子马比较别致(图64-66);在整个画面中,尤其醒目的还有双方交界的分隔处有三个汉字最让人费解。
左侧壁(北壁):整壁墙面基本毁坏,右(东)侧存有图形5幅,分为旗帜、鹿、人射箭等,其中尤其是半跪状射箭手的姿态异常生动(图67-69),北壁尚有一砂岩手模。
前壁(东壁):左侧残留一旗帜,门道高1.8米、宽1米,门道两侧壁砂岩上留有手模22个;前壁的右侧是窗户,为便于采光,窗户的外口小、边长1米,内口大、边长1.2米,深度为1.1米(30)。在窗户的南侧壁上保留有完整的岩画,面积约1.1平方米,上刻有图形15幅(图70)。画面自左向右铺开,右前下方有两名骑兵在挥舞刀剑,相互拼搏,之间有一马,作惊恐状;周围并有残存物状;画面中上部一人骑马,持大旗,旗帜上有一倒置羊的图形,旗杆顶端刻一圆,圆内泥皮刻空,圈外刻放射状线条;估计这是代表本部族的帅旗或图腾标志;在它的后面也有一人骑马,作奔驰状,这一骑士持一旗与前面的相仿,但无旗徽;后面还有五位骑马者,人物的形式与南壁相同;在帅旗者的前方,刻有一似驴的形象,迎面站立(图71-72)。窗户的北侧壁墙皮几乎脱落,据观察下部也曾有岩画痕迹,现不详。
第95窟:该窟的方位、高度同第93窟,位于第93窟北侧约12余米,中间隔了一个形制为僧房的第94窟(按照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布规律与特点来看,这本该是一排组合型的洞窟,其窟形与功能各有不同,一般来说应有佛殿、讲堂、僧房等基本洞窟形制,可是这一组与一般性的组合稍有不同的是这些洞窟是上下排列。作为佛殿的第97、99、100、101、104却安排在第93、94、95窟的上方)。主室现存南、北、西壁,各边长3.4米,顶为覆斗式(图73),室内积风沙近半;南北两壁和顶部泥皮均脱落,西壁存草泥墙皮上下两层,里层墙皮表面涂过白色,外层稍有烟熏迹象,岩画就刻画在这块面积约5平方米的灰黄色墙面上;由于前壁塌毁,长期风吹日晒,图像多模糊难辨,目前能认清的个体图形约89个(图74-99);画面的主体基本以马、鹿、骑者为主,间有羊、骑者射箭,面向基本朝右,其中比较突出的形体是一鹿、一大角羊、几匹马和右上方的一只似大鸟的形象,大部分的牲畜都悠闲自得地站立,个别作来回奔跑状,另有一母子马和鹿的交配图在右前方;壁面上方从左至右分别有四处似炭色书写的古龟兹文字题记,其中有两处被岩画形象所划破(图100-102);右下部位有一汉字明显为后来所为。此窟与第93窟的兵戎相争的内容截然不同,以突出再现安宁的牧业生活为题材,故可称之为牧乐图(31)。南壁有砂岩手模一个。
第131窟:与第93、95窟相对的是谷内区的东崖壁,东、西两崖壁之间相距50至80米不等,第131窟就在第93、95窟对面崖壁的右前方,洞窟的位置高度略低于第93和95窟,离沟口约30米的距离;该窟坐东朝西,前壁和前室塌毁,主室边长各3.6米,壁高3.2米,顶为五层套斗式,顶高约1米(图103);窟内稍有烟熏迹象,现存所有墙面均未抹泥皮,而是在砂岩壁面上直接刷一层白灰,岩画和多处民族古文字基本都刻画在上面;洞内原先积泥沙半米以上,后清理出窟,因此,现在的岩画位置最高处在2.4米、低处是1.5米;左右两壁有大量手模印记,多达82个,且以左手为多(图104-106)制作手法有磨、刻两种,位置一般在距地面1.5米上下;岩画主要刻画在正壁上,部,从刻绘的痕迹看,不像第93、95窟是用利器工具所为,此窟只须用稍硬的器物便能刻制,这与较松散的砂岩质地有关,因而才会出现有大量的手模岩画(32)。
正壁(东壁):正壁有刻画形象和符号36个,从图像区分有:山羊、鹿、马、骆驼、人物、飞禽和一些图案符号,其中山羊最多,占9幅,人6个、有尾饰,骆驼4匹、鹿3只、马2匹,其它图像12幅,手模2个。从这幅画面的布局安排和内容分析看,这似一幅牧民迁徙图(33)。整个构图呈三角形自右向左展开,各个不同的形象根据游牧生活的经验布置、排列有序。前面似有一形体高大的人开导引路,紧接着是一人骑骆驼者,两手平展,牵二只满负重载的骆驼,还有一禽鸟也被其人牵于手中;中部多为山羊、鹿和马,人物多在后方,并有两人伸开手臂,阻拦两只回头羊。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间一组图案符号古据中心位置,估计应该与本民族的族属和图腾崇拜有内在联系(图107-130)。同时,还有一个十字交叉形符号非常引人注目,正壁右上方存两处古龟兹文字(图131-132)。这不太清晰的题记显然早于岩画,因它们几乎与现墙面融为一体并有被岩画打破关系的迹象,既使一排较清晰的也很难断定是否与岩画同时所为,至少岩画的刻画与文字的书写工具和印痕显然有别(34);还有正壁岩画的上方(鹿的后面)存一处阿拉伯文题记(图133)。此外,正壁下面砂岩上也刻有一羊形象;另外,正壁的几处岩画在刻画之前其质地事先经过打磨平整之后才进行作画。
右壁(北壁):有2幅似马的比较模糊的图形,刻画的痕迹和技法与正壁有别;另存手模18只。左壁(南壁):现存岩画图形5幅,两只羊、一个十字交叉形符号、一个月牙状符号,还有一形状似鹿的造型;并且也有一处古龟兹文字题记。此外,尚有手模58个,其中有些手印的深度达4厘米,且左手多于右手,也有刀刻的手模印记。
此外,外室南壁有砂岩手模7个(1984年调查时只有3只手模)。
以下按序列号介绍谷内区其它洞窟的具体遗存:
第82窟:僧房窟,甬道南壁手模4个,其中左手3个。
第83窟:方形窟,手模1个。
第92窟:方形窟,手模107个(南壁92个、北壁5个、西壁9个、外室1个)。
第94窟:异形窟,主室北壁刻画图形模糊难辨,约4个。
第98窟:中心柱窟,北壁甬道口上方的壁画上用细线轻刻出一鹿(图134)。第99窟:中心柱窟,主室正壁主佛龛内北侧壁刻一似第93窟的旗帜(图135)。
第100窟:中心柱窟,整个窟被烟火熏黑,主室正壁主佛龛内刻不同符号与手模等共26个,其中手模11个(左手9个,南、北侧壁各刻带圆心的手模1双,而且北侧的还用一方框框住,并间有符号(图136-138);南壁还单独刻2个非常规整的圆圈,中心有点;下方刻一不规则的动物;北壁有两处阿拉伯文字题记,北壁下方还残留一禽鸟的躯体(图139-144)。
第107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13个。
第108窟:方形窟,西壁砂岩手模16个、东壁1个。
第117窟:方形窟,泥刻3幅。前室正壁门右面高3米处似有一线刻的家
禽形状;后室左(东)壁高1米处有一线刻山羊,另有一图形符号(图145-147)。
第118窟:方形窟,有岩画9个,手模39个,另有多处刻画的民族古文字及符号。手模的分布为:正壁(北壁)东侧刻画手模1个;右壁(西壁)刻画手模15个(左手10个),其中3个手心(2个右手、1个左手)似有标记,但不清楚;左壁(东壁)刻画手模10个(8个左手);门壁(南壁)东侧刻画手模1个;门壁东窗刻画手模7个(5个左手,另2个不详)、西窗东壁刻画手模5个;(图148-162)
第123窟:中心柱窟,主室右壁的壁画上刻画似弓箭的图形3个、另一似人形。(图163-165)
第124窟:方形窟,东壁残存马、羊、鹿、鸟等,有手模1个(图166-167)(35)。
第126窟:中心柱窟,手模1个。
第126A窟:距第126窟南侧约10米处,龛内似有一山羊的岩刻与手模等(图168-169)。
第127窟:异形窟,南壁可辨羊角等4个图形(图170-171);窟外南侧砂岩手模3个。
第129窟:方形窟,外室南壁砂岩手模2个(左右一双)。
第130窟:僧房窟,室外砂岩手模1个。
第132窟:方形窟,墙皮基本脱落,各种砂岩手模共138个。其中外室右壁3个;前室与主室之间的门道南壁有40个、北壁45个;主室正壁2个(左手)、右壁(北壁)22个、左壁(南壁)27个,并有只磨擦出手指而无手掌的特殊手模指槽现象;另有北壁刻画图形7个,其中似羊、旗帜、弓等(图172-175)。
第135窟:方形窟,东壁的壁画上残存刻画的巨大弓箭、山羊等多幅(图176-177),可辨清形象者4个;手模41个;正壁手模6个,右(北)壁35个(多右手)。
(二)谷西区(33个窟)
第7窟:中心柱窟,右甬道入口处高1.65米处残存数道划痕与不明形体;左甬道外壁残存一似鸟的刻画(图178-179);后甬道后壁壁画上刻一大角羊(图180)。
第8窟:中心柱窟,主室左壁(东壁)中部壁画上有大角羊一个(图181);正
壁手模3个(两个左手)。
第13窟:中心柱窟,主室左壁手模3个。
第18窟:僧房窟,进入主室门道的左壁有右手手模1个。
第19窟:僧房窟,进入主室门道的右壁有右手1个,未完成的手模3个。
第20窟:僧房窟,甬道及主室存刻画图形8个(图182-189)。
第22窟:僧房窟,甬道拐弯处外壁手模1个,左手。
第23窟:中心柱窟,左甬道手模1个,左手。
第27窟:中心柱窟,手模17个,其中左手15个,右手2个(图190-191)。其中有2个刻在主龛内右侧壁的墙皮上(左手),其余在砂岩上(36)。
第28窟:方形窟,正壁两龛之间手模1个。
第29窟:窟外东侧龛存左手手模1个。
第30窟A:砂岩手模1个,左手。
第31窟:北壁砂岩手模2个。
第32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7个。其中正壁6个,东壁1个。
第33窟:方形窟,西壁砂岩手模7个。
第34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30个。其中正壁5个,东壁23个,西壁2个。
第35窟:僧房窟,进入主室门道右侧一刻画似马的图形,两后腿间刻一箭头符号(图192);另有手模4个。第36窟:方形窟,手模25个。第37窟:僧房窟,手模3个。第38窟:中心柱窟,东甬道外壁一个用单线刻画的大角羊(图193);手模
4个,主室西壁1个,东甬道外壁3个,左手(图194-195),为便于刻画,手指叉开。
第39窟:方形窟,正壁高1.4米处刻有一山羊,下边另有一不完整的似羊的图形;右壁高1.9米处,刻有一未完成的羊的图形(图196-198)。
第40窟门外西侧,砂岩手模4个(图199)。
第43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22个。其中东、西壁各11个。多处文字题记,一人形刻画(图200)。第43-47窟的台阶的途中崖壁上,砂岩手模1个(图201)。第46窟:方形窟外东侧,砂岩手模1个。第47窟:大像窟,手模共84个。其中外室正壁高2.5米处1个;外室西壁
42个;高约3米处的壁面(37)6只,还包括两对双手、左手4个,外室东壁10个,其中8个处在高约4米的壁上,也有一对双手;后室、甬道和中心柱上共31个,其中左手5个。(图202-205)
第48窟:大像窟,手模5个。外室2个,正壁高处1个砂岩手模,东壁1个;后室3个,1个砂岩手模,2个刻画手模(左手)。第49窟:方形窟,正壁和左壁岩刻4个。正壁一山羊,轮廓之内的墙皮皆刻去,形象较写实;左壁也有一山羊形象,线刻,前肢残损,还有一形体似未刻完,也似山羊(图206-209);外室西壁砂岩手模4个。
第58窟:中心柱窟,左甬道外壁的壁画上有刻画手模1个(左手)。
第70窟:大像窟,砂岩手模4个。
第71窟:异形窟,手模10个。
第75窟:僧房窟,甬道右(西)壁一形象似羊(图210-211)。
第77窟:大像窟,后室中心柱砂岩手模2个。
第80窟:中心柱窟,手模7个,其中主室正壁龛内南侧壁存一刻画左手手模,甬道6个砂岩手模。
(三)谷东区(21个窟)
第139窟:大像窟,手模9个;其中刻画1个,砂岩手模8个。
第140窟:僧房窟,手模14个;其中在东壁砂岩上刻画1个,北壁砂岩手模13个。第154窟:大像窟,主室门壁右下侧岩刻山羊4个(图212-217);后室有手模1个,另有2个砂岩手指印。第155窟:中心柱窟,主室东壁4个似羊的岩刻;窟外左下4个线刻羊(图218-223);砂岩手模2个。
第156窟:现修门壁窟外砂岩刻画符号8个(图224-226)。
第159窟:中心柱窟,东壁隐约有砂岩手模2个。
第160窟:中心柱窟,西壁有砂岩手模3个(右手),中心柱西甬道内壁有砂岩手模4个(左手)、后甬道正壁有砂岩手模1个。
第161窟:方形窟,窟内壁画烟熏严重,南(门)壁东侧约1.4米高处岩画图形2个,大的显然是一羊,小的也属家畜形状;室外有砂岩手模4个(图227-231)。
第162窟:僧房窟,外室有砂岩手模2个。
第163窟:中心柱窟,主室左壁的壁画上刻画一似鹿的岩画;右壁刻一大角羊(图232-236);正壁砂岩手模1个。第164窟:僧房窟,外室西壁一大角羊(图237),手模3个。第166窟:方形窟,正壁有砂岩手模1个。第167窟:方形窟,正壁手模1个,左(东)壁6个(左手),右(西)壁高3米
处刻左手2个,并有2个图形似鹿。另有2个几何形符号,其中一个十字形(图238-239)。
第168窟:方形窟,砂岩手模3个。
第181窟:中心柱窟,主室墙皮刻画手模2个(左、右手各1个),古民族文字、汉文字题记各一(图240-243)。
第184窟:中心柱窟,主室北壁砂岩手模2个(左手)。
第192窟:中心柱窟,刻画符号一个(图244)。
第194窟:方形窟,北壁砂岩手模2个。
第195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共33个。其中左甬道1个、后甬道正壁11个、后甬道前壁19个、后甬道北壁2个。第196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共8个。其中主室左壁砂岩手模2个、西壁4个、西甬道外壁2个(图245)。
第198窟:中心柱窟,东甬道外壁砂岩手模2个(图246)。
(四)后山区(6个窟)
第201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共24个。其中东壁21个、西壁1个、南壁2个。第206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共24个。其中正壁1个、正壁龛内9个、左壁(东壁)8个、右壁(西壁)6个、。第220窟:长方形窟,东壁刻写民族古文字若干(图247-251)手模7个。其中东壁5个(砂岩手模2个,其一掌内有一大写的汉字“龙”(刻画,3个);南壁龛2个(一左一右);另有一蜘蛛刻画在砂岩上。
第222窟:方形窟,岩画4个(图252-255)。
第232窟:砂岩手模17个。
第233窟:异形窟,砂岩手模1个。
另外,从谷东区往后山区的路途中的岩石上有砂岩手模1个,并有刻画者的姓名(阿不登)及刻画日期(87.9.19)。(五)亦狭克沟(38)(2个窟)亦狭克沟石窟现存四个洞窟,由于其驿站的功能与作用所限,洞窟形制主要为方形或长方形,洞窟凿刻在沟西崖壁上,面朝东。窟内均无壁画。一大窟,长度8.8米,宽度5.3米,壁高2米,券顶高1.3米,前壁一窗户,外口1米,壁厚90厘米,内口1.3米,窗台上抹有草泥,壁面有刻画图画。右壁似有一壁炉,壁面砂岩上涂一层白灰泥,正壁可见6处龟兹文题记,左壁的龟兹文模糊不清,并有6处阿拉伯文字,后壁右角有许多阿拉伯文,窟内至少有四五种不同的文字。一小窟,型制同大窟,横宽3.5米,深3.8米,右壁一壁炉,左壁有龟兹文题记(图256-274)。
五、岩画的制作技法、形式与风格
在论述本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克孜尔石窟的岩石质地再作一个说明。克孜尔石窟的山体属于岩石无可置疑(地质学上称晚第三纪灰白色粉砂岩或泥岩沉积岩石),但是,这种砂岩相对松散,水、风与震动对其危害较大,如果用坚硬的工具敲凿它倒十分结实,可是,直接用手或稍粗糙的物体搓磨其表面,很容易留下痕迹。因此,比起各地岩画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刻物象,可谓事半功倍。其次,在佛教石窟废弃的窟内墙壁的泥皮上刻画图画,也是极为省力的。再则,窟内作画总比露天舒适、方便的多。这些条件和因素都是各地岩画作者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克孜尔岩画的作者可以用非常简陋的工具(利器和钝器均可)在这些无人管理的窟内窟外随心所欲地表达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审美感受。
根据现存岩画的制作痕迹来分析,其表现技法大致有以下几点:
1、单线法:物象的形体结构用阴刻单线来表达,这种方法直接、明确、简易、省事,是克孜尔岩画制作的主要手法。
2、刻面法:把物体的轮廓内部全部或部分刻去,留下一种剪影效果。
3、线面结合法:较典型的是第93窟的旗帜、第95窟的马等。
4、磨搓法:由于砂岩质地的因素,制作者直接用手在砂岩表面上下磨擦,即可成形。克孜尔留下了大量的手印,有的仅限于手指印,或称“指槽”(第47窟主室左壁等)。
侧面轮廓似乎最能表达动物的基本特征,人类原始的洞窟壁画就采用了这种观察方法,这使得各种不同的动物形象一目了然,纵观所有的岩画动物图像都无不如此,克孜尔石窟的岩画同样继承了各地传统的表现技法。
平行透视法(散点式)不必受焦点透视规范的约束,构图平铺直叙反而错落有致、稚拙天真,平面感与装饰效果可以说是古今壁画的一般性特点,第93、95、131和124窟等大场面的画面都运用了这个规律。
简约与抽象从视觉图像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绘画艺术走到了今天,而且还会永远地传承下去(39)。便捷的直觉图形和象征性符号无论是远古的石器时代还是当下的信息社会,都将成为人们不可抗拒或难以回避的视觉文化心理和生存信念的召唤。克孜尔石窟岩画中诸多的有明显寓意的标识性图像都带有这种启蒙文明的余韵。
六、年代、作者族属与相关问题
岩画断代和作者的归属是岩画研究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年代越久远就越不易把握。况且,岩画的作者与分布区域又多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文化有关,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这个难题。
比起目前岩画断代的一般性方法来说(动物考古法、碳十四测定法、比较学、层位叠压现象、风格题材等),克孜尔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相对而言要明确得多,如年代的上限问题就会相对明朗。可是,眼下依然还有诸多的扑朔迷离之处。如前所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必须首先借助前人对克孜尔岩画年代与族属的观点,然后,再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黄文弼先生1958年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推测克孜尔石窟的三处岩画非近代人手笔。他认为第93窟的刻画“疑为游牧民族走马为之游戏图”,同时根据壁面上的文字和其它洞窟的文字题记,推测此为“仿游牧民族之游戏绘画”,时代为唐之末叶。另外,亦狭克洞中刻画的图像和民族古文字,“即为过此商侣所为”(40)。显然,黄先生的对岩画年代的看法是与他在克孜尔发掘到的文字遗书与题记有关,而且偏重于汉文的年号与史料(41)。由此,他才怀疑作者是“仿”游牧民族的汉人所为。而亦狭克沟没有汉文题字,故可能是过往的非汉人的商侣。黄先生的论点为我们看待克孜尔岩画的年代与作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和分析线索。
北京大学宿白先生1979年在谈及新疆地区的佛教诸问题时曾涉及克孜尔石窟的岩画年代与族属,宿先生以石窟考古类型学和西域历史文化背景为基点,并与当时周邻地区已发现的岩画资料作比较后为克孜尔部分重要洞窟和亦狭克沟的岩画年代和作者给予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克孜尔谷内区和谷东区大约八世纪开凿的某些洞窟和克孜尔东亦狭克沟中的石窟的刻画形象与内容和西藏西部、楼兰地区以及甘肃嘉峪关一带的岩画极为相似。这些都是九世纪吐蕃牧民的遗留。
1985年,史晓明与王建林认为第93、95、131窟是岩画中非常成熟的作品,年代也较晚。考虑到石窟中整体岩画的情况,将这些岩画的年代上限定在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即公元八九世纪,下限时间至少推至十三世纪左右,作者并非只局限于吐蕃游牧民,甚至可能还有回鹘、蒙古时期的遗留(42)。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吴焯先生主要针对第131窟和第93窟这两个洞窟的岩画,将宿白先生提示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学科化,观点也进一步明确。他认为:第93窟的题材是“吐蕃征战图”,作者是吐蕃士兵;131窟的题材是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作者是吐蕃的部民百姓,其年代上限可早到公元七世纪末安西第一次陷于吐蕃的期间之内,下限则晚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前(43)。
北京大学晁华山先生根据第93窟刻画的三游旗、汉字以及石窟内其它洞窟遗留的汉文题记的年号和相关史料,以及公元9世纪后至清代初期这里再没有留下汉人的其他遗迹而断定,该窟的刻画是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唐军士兵所作(4)。
综上所述,研究者之间确实存在有不同观点上的差异,可归纳的共同之处在于:岩画的年代上限应该是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岩画的作者多与游牧民族相关;吐蕃与唐朝在龟兹的争夺战是第93等窟岩画发生的主要线索;不同的见解是作者族属有区别,还有岩画的年代下限不易把握。以下,笔者试图再一次在前人的基础上(45),对克孜尔岩画的整体状况和以上介绍的实际遗存作具体地分析与鉴别,从中找到相应的合适角度与材料来分别看待克孜尔不同洞窟、不同题材、不同造型的岩画现象,进一步地探讨克孜尔石窟岩画的有关问题。
既然岩画年代的上限是与石窟的衰落有关,那么,有必要先弄清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究竟在何时?其实,克孜尔重要的岩画年代与族属焦点可以集中到第93窟的问题上来,该窟特殊的刻画图形与文字题记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国内外学界一般的共识是公元8世纪,这一点无庸质疑。并且可能与当时发生在龟兹的战争有关,而战争又可能是唐王朝与吐蕃在西域的霸权之争,由此才直接影响到克孜尔石窟的衰落,故龟兹学的研究者都将第93窟的刻画归属为争战的题材,只是作者的族属问题意见不一致。黄文弼先生尽管没有明指是哪个民族所为,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明显看出他是指唐军,而晁华山先生也持这种观点,并且理由说得相对合理(2007年8月27日笔者在敦煌学术会期间向马世长先生请教时他也倾向于作者为汉人);然而,宿白和吴焯先生的看法也不无道理。可是,还有一些迹象他们没有注意到或是观察的不细致,如:第93窟的四壁均有刻画,只是大部分的墙皮因该洞窟比较潮湿,尤其正壁与北壁严重脱落,现在只残存个别图像,尽管如此,某些形象还是非常重要,例如正壁残留的两个汉文题字、似大鸟的图形、大角羊、旗帜上的圆形图像,南壁西侧的罐型图像。另外,窗户南壁旗帜上的羊的图示等,这些图像比起其它图形都是供我们分析判断年代和族属的比较直接的特殊研究信息,如罐型的图式在各地的岩画中除了克孜尔这一例之外还有西藏西部日土岩画中也有陶罐出现(图275)(46),如果岩画作者只有吐蕃游牧民有刻画陶罐的习惯的话(47),那么,宿白先生和吴焯先生的立论就有依据可寻,再加之西藏(苏毗)的“鸟卜”习俗确实与克孜尔岩画中出现的鸟的图形相吻合。此外,还有吐蕃有“事羱羝为大神”的图腾习俗(48),如果正壁、窗户南壁旗帜上的羊的标示与此相关的话,这就更增加了吐蕃族属的说服力。不过,虽然有这些旁证,可是,目前第93窟的两处汉字却难以找到对应的、合适的解释理
由,因为,那两处遗留的汉字确实与岩刻是同时所为(49)。然而,如进一步考虑到汉字书写的欠规范化程度和作者特别强调羊图腾因素的话,作者可能更倾向于游牧民族。当然,是否还存在其它偶然性的因素目前仍很难断定。此外,因为要顾及石窟岩画的整体状况,以下再简述六个方面的问题,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1.看待克孜尔岩画的总体状况,不仅要重视本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承关系,而且还要将克孜尔岩画放到整个中亚文化圈的背景中去审视,以此为视野,就不能笼统地把克孜尔不同的83个洞窟的岩画问题概念化,理应区别对待,这样考虑会有利于岩画年代的下限与作者族属等相关问题。同时,又牵扯到研究方法的拓展和图像学的渗入。这些问题的提出至少是基于近些年来国内的岩画发现与研究工作逐步进展,使得龟兹石窟的岩画研究有了相对丰富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在运用图像学的方法论方面也有了多重视角,包括本地区新发现的岩画材料,可以提供直接的近距离的对比。
2.通过本地区普遍存在的岩画现象,使我们首先更加注重,龟兹自古以来就是多个游牧民族定居和不断变迁的地区,龟兹本土的吐火罗民族自不必多言,他们在长期的游牧迁徙的历史长河中在中亚各地均留下了辉煌的足迹(50),虽然吐火罗民族自从来到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定居以来,从来就没有也不会放弃传统的牧业生活方式(51);其次是后来的突厥、吐蕃、回鹘、蒙古族等,他们都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并且都有刻画岩画的文化传统(52)。这些基本的文化背景是我们面对龟兹地区的岩画时所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基础性问题(53)。如拜城县老虎台的岩画中羊的刻画形象与克孜尔第154窟中的羊的表现手法如出一辙(图276)。所以,克孜尔岩画作者的族属问题就不免更复杂化了;再者,看待龟兹地区的岩画,不仅仅是只局限于新疆本地,而且也不能仅限于所谓中国的“半月形岩画圈”或“半月形高地文化传播带”的范围内(54),它应该是与中亚之外更广阔的地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55)。
除了上述的“羊图腾”之外,我们从第7、93、95、100、117、124、131窟均刻有类似“鸟”的图像可以明显感到还可能有“鸟图腾”的相关问题。因为“鸟图腾”的图像在各地的岩画中包括新石器时期的其它艺术中都普遍存在(56),并各有其地方特色(57)。克孜尔岩画属于晚期现象,狩猎、野生动物等题材消失,可是,类鸟图像竟如此突出,而且在不同的洞窟里出现,可见其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相通之处,这至少与刻画者的传统观念与生命意识的潜质有关(58)。这种对鸟的非记事图像的、非自然属性的特殊关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岩画作为一种原始语言的表现,也会有方言”。但是,在世界岩画的范围内,“一些重复的因素出现在所有的大陆,标示出岩画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结构”(59)。由此可见,克孜尔岩画的共同文化内涵并非仅限于周邻地区。
3.关于克孜尔岩画年代的下限,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推至13世纪以后。一个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如果纵观龟兹石窟的整体兴衰史,就可以基本上确定这种看法。因为,以克孜尔为代表的一批龟兹本地风格的石窟大约与克孜尔石窟同时衰落,而惟独库木吐拉石窟延续的时间比其它石窟长得多(60)。所以,当石窟还没有废弃之前,洞窟内的壁画上是不可能随意乱刻乱画的。笔者曾在台台尔、库木吐拉等龟兹石窟也发现有数量不少的岩画迹象(61)。故此,如果以库木吐拉为例证,将该石窟岩画的上限和龟兹其它石窟岩画年代的下限一起来考虑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疑问。
4.结合岩画发生之前的龟兹壁画相关题材与造像,找到间接的可能性的佐证资料。龟兹石窟壁画中大量的动物图像从侧面也反映出游牧文化在佛教造像中的突出地位,特别是羊的造型在壁画中表达的格外精彩(图277-282)。因为,羊不仅是游牧民族日常的主要食物,而且还与游牧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图腾崇拜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仪式上的联系,如突厥汗国就曾经把野山羊作为政权的象征(62)。于是,第93窟窗户南壁的有山羊的旗帜就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同时,问题也愈加微妙起来,因为不仅是古代羌族(63)、突厥民族,而且吐蕃,甚至中亚的游牧民族都同样有这种遗风(64)。
5.手模与印记问题。手模又可称“手印”等(65)。至于说手模这种最古老的、跨地域、跨时代、跨民族的造型艺术观念,尤其是在岩画造像的体裁中显得特别突出,由于手模的文化内涵各不相同(有力量、权威、意志、占有、征服、胜利、祈求、避邪、求援、生产、生殖、兴旺、增多、维持、享受、创造、标志、表现、自豪、礼仪、礼赞、游戏、留念、签名、报道等多种象征寓意的可能性),因而,手模现象是克孜尔岩画中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是由于洞窟废弃之后的上千年的时间内,无数人曾来过此地,或居住、路过、游玩、朝拜等等,既使近代和当代,也有游客在重复古人的“游戏”(66)。按照有些学者的看法,手模往往与其伴生的图形有关联(67)。既有原始思维和宗教巫术的含义,又有现代人玩耍留念的游戏行为。所以,克孜尔手模的表达方式和寓意也应该有所区别。如第93等窟大片的手模,可能就与战争的胜负有关;第95、131、132等窟的可能就与氏族部落的生殖兴旺、宗教礼仪等有联系;而第100窟龛内的带有圆心的手模估计与同时刻画的阿拉伯文字有关系。至于说近年来不少游人的随意刻画又可另当别论了。
岩画中的印记符号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氏族问题(68),但是,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如第131窟等岩刻中的多处符号印记和其它洞窟的不同符号图式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此外,同一个洞窟内存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刻画图形、文字符号等也是正常现象,第95、131、220等比较明显。
6.晚期岩画的普遍性问题。岩画的风格化问题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的共性,由于生产力低下,刻画的质地与材料更接近于自然;因为造型能力所限,形象的塑造更倾向于稚拙;生存信念直接受潜意识控制,故审美判断更接近本能;鉴于思维方式的古朴,表现形式受宗教信仰的迷惑与支配。
克孜尔岩画之所以有多种游牧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史前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间曾经有过漫长的、广泛的接触与交流。这种直接和间接的传承脉络关系会随着当代科技水平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而变得日益清晰起来(69)。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先民们在游牧经济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型的同时,还依然会保留着畜牧业生产的传统观念,这是无可非议的。所以,第95、131窟有意突出畜牧业生产的题材,而野生动物和狩猎的场面消失等与原始岩画的题材有明显差异,包括大量的文字刻画、体裁缺乏原创性等,这些都是克孜尔岩画的基本特点,这显然是游牧民族走向定居生活的文明结果。
【余论】
根据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岩画研究的针对性和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建构人类史前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可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析岩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目前正在它的初级阶段”(70)。然而,重新审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早期文明,充分认识原始视觉艺术的人文价值就值得关注。由此,岩画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就显现出其它文献所不能替代的功能与义务。从这个基本的角度出发,岩画无可置疑地为历史考古、民族宗教以及文化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原始图像资料。真可谓是“写在石头上的史书”。但是,文字发明应用以后的岩画现象,其史料的性质与功效就会相应减弱,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佛教石窟废弃之后才出现的岩画就失去了那些基础或早期的文化蕴涵。然而,问题还并不是这么轻易或简率。晚期岩画自有其史前岩画不可替代的功用(71)。各地的农业文明的岩画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在证实着自身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自然原型是造型艺术的图式根源,人类的图像从一开始出现就从没有违背这个基本原则。这种造型意识的生理图式的成熟有专家认为大约在旧、新石器交界时期(72),到公元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除了希腊、罗马的科学造型观念的自觉化之外,原始艺术的模仿、抽象与综合心理素质一直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并各自独立地并行发展。岩画的造型规律可以说从未脱离这个先前的范式,它是上述的模仿与抽象相混合的一种精神意向特征的表达和寄托。至于说公元7、8世纪在塔里木盆地的佛教圣地的出现则是游牧文化对农耕文明审美素质的悖反,因为佛教艺术至少是希腊、罗马造型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在龟兹则是人类造型艺术在中世纪早期的一个辉煌结晶。所以,当游牧民族在废弃的佛教文化殿堂内随意刻画时所体会到的愉悦感与那些辉煌的、五彩缤纷的佛教造像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和疑惑。
不仅仅是克孜尔石窟,龟兹石窟群普遍存在着衰落之后的游牧民族刻画岩画的现象。这的确是一种游牧文化征服农业文明的历史事实。在中世纪宗教艺术的殿堂里随意刻画游牧民族的稚拙图画,比起先前的精美佛教壁画和塑像,无论是艺术的水准还是思想的哲理,可不是一般性地相形见拙。文明确实有时在倒退,就像欧洲的中世纪在很多层面上替代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那样让人沮丧!这种无奈在物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20世纪依旧在重演。这也许会引起对历史直线进步论观点偏见的警觉?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这么让人不可思议!我们从中汲取的文化教训只能是客观地反思历史,更好地呵护人文思想延异的秩序,让人类文明的历史车轮协调前行。
1984年5月至1985年5月,我们曾对克孜尔石窟第93、95、131这三个洞窟内所遗存的古代游牧民的刻画图画和符号做过初次试探(1)。此后的20余年间,我们对克孜尔以及龟兹其它石窟普遍存在的这种文化迹象又不断有新的发现。由于那篇文章一直未正式刊出,加之近些年来考古工作在各地大量发现新的岩画“地区”和“地点”(2),与此同时,岩画这门学科在国内的学术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并且还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3),这使得我们对原先的工作结果不免产生新的认识,且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有了可继续探讨的必要性。此外,克孜尔的“岩画”研究本身就有可补充的空间。故此,本文以克孜尔洞窟岩画的多次实地考察为依据,整体地介绍这批晚期的岩画图像资料,并就有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克孜尔石窟的自然地理、人文背景
中国的早期佛教遗址克孜尔石窟,是十九处古龟兹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处(4)。它孤立地坐落在拜城盆地东端东南角的明屋依达格山南麓(5)西北距克孜尔乡政府约9公里(6)。海拔1320米,地理坐标:北纬41°47′、东经82°27′(7)。
克孜尔石窟虽然处在天山以南,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决定了其自然环境显然不同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干旱少雨的绿洲气候(8)。因为石窟前面的小绿洲四面环山,除了东、北、西三面是明屋依达格山高约200米的悬崖峭壁,大部分坐北朝南的洞窟与对面的寸草不生的却勒达格山(主峰高度2131米)隔河相望,两山之间冲积扇低地的交接处,渭干河由西向东蜿蜒流过,给这块神奇的土地又凭添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和滋润的气息。从明屋依达格山中部的峡谷中泻出的冲积扇沙地的形状,犹如一个倒挂的荷叶或横倒平放的、上北下南的菱格形(图1),像一枚绿色宝石镶嵌在荒滩戈壁的边缘深处。所以,克孜尔石窟的自然环境夏季凉爽,冬季温暖,春、夏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秋季水草肥美。难怪古代龟兹佛教僧侣将这块几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作为出家修行首选的理想孤境(9)。
其实,真正给克孜尔石窟这片小绿洲以恩惠的是明屋依达格山体下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特别是山体中部的峡谷中常年流出的滴泉之水(俗称:千泪泉),是灌溉这片绿洲的生命之泉。克孜尔现发现已编号的335个洞窟就是以这个峡谷为中心,并根据山势的走向而分为四个区域(10)。
在公元四至七世纪时,克孜尔石窟是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邦的佛教文化圣地,印度、波斯、西亚、中原文化先后荟萃于此,并且成为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发源地之一,特别是壁画与泥塑彩绘是中世纪早期世界范围内名符其实的造型艺术的新型典范(11)。其石窟形制、佛像样式传播影响到了凉州、敦煌、云岗、长安等中原内地(12),甚至波及朝鲜和日本。
根据古代西域和龟兹的历史文化发展概况来看,龟兹佛教造型艺术的参预者多与游牧民族有关,并不断融合扩展。本土的吐火罗人不必多说,其他的如:突厥、吐蕃、回鹘等民族都先后占领过龟兹(13)。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当佛教在龟兹衰落之后,克孜尔这片土地自然也就成为这些游牧民族后裔生活的天然乐园,尤其是冬季可能更为适合(14)。(图2-49)
二、关于克孜尔岩画的名称问题
在废弃的佛教石窟内,保留的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迹是否属于“岩画”现象,究竟对它们如何称呼?目前尚未有一致的看法(15)。因此,在论述本文的主题之前,有必要对这种遗存现象的名称作一辨识。
先看岩画的定义。辞海岩画辞条认为:“岩画是刻画在洞的壁上或山崖上的图画。”1986年11月,意大利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埃马奴尔·阿纳蒂先生在写给北京中国岩画展览之前的贺词中明确指出:“岩画是绘在或刻在洞穴或露天的岩石上的形象或符号。”
根据这两条定义以及国内岩画专家的共识(16),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将龟兹石窟内的这类文化遗存归属于岩画范畴并称其为“岩画”。其理由如下:那些图画和符号全部都刻在洞的壁上和露天的岩石之上,并且同岩画的主体创造者游牧民族的生活传承与文化性质毫无二致(凡研究者都一致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大部分的刻画质地是画壁画的草泥地仗,洞窟形式也是人为开凿的宗教建筑。然而正是这些废墟和遗留为作画者提供了现成的刻画场地,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图像是直接刻在砂岩之上(17),尤其那些大量的手模印记几乎全都是在砂石岩体上磨搓而成。由此,无论从内容(游牧体裁为主)还是形式上(质地与制作手法)都无法与各地岩画一般性的文化特征区别开来。为避免不必要的歧义,故本文继续沿用“岩画”这个术语。
三、前人成果的概述
1958年,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涉及克孜尔石窟岩画的有三处:“图38洞壁刻画故事画,出拜城克子尔明屋佛洞一组二洞东壁,高34.3,宽62.7厘米,刻画一狮子,张口舞爪,两足前伸,作猛扑状。前有一人危坐,屹然不动,姿势生动活泼,非近代人手笔。又同壁刻有(天宝十三载)年号,故此画亦当为同时所刻”;二是现编号谷内区第93窟的“洞壁刻走马图”,此洞的刻画“疑为游牧民族走马为之游戏图”,黄先生根据壁面上的文字和其它洞窟的文字题记,推测此为“仿游牧民族之游戏绘画”,时代为唐之末叶;三是“石刻兽形图,出克子尔明屋佛洞西二十里,亦狭克洞中,图像有大头羊、骆驼、黄羊和民族古文字。”“此刻画即为过此商侣所为”(18)。
北京大学宿白先生在1979年就新疆地区佛教遗迹调查等诸问题中曾明确提及:“克孜尔谷内和谷东区大约八世纪开凿的某些洞窟和克孜尔东亦狭克沟中的石窟壁面上,都出现了后来刻画的羊、马、驼、禽鸟和人物。这些刻画的形象与内容和西藏西部、楼兰地区以及甘肃嘉峪关一带的岩画极为相似。这些都是九世纪吐蕃牧民的遗留”(19)。
1984年5月,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的史晓明、王建林对克孜尔石窟的岩画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调查整理,并对主要的第93、95和131窟这三个岩画的重要代表性洞窟进行了初步的试探。我们认为第93窟南壁的岩画是一幅征战图,第95窟为牧乐图,第131窟是一幅迁徙图。表现的题材主题鲜明、构图完美,为各地少有,是岩画中非常成熟的作品,年代也比较晚。考虑到石窟中整体岩画的情况,将这些岩画的年代上限定为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即公元八九世纪,下限时间至少推至十三世纪左右,作者并非只局限于吐蕃游牧民,甚至可能还有回鹘、蒙古时期的遗留。这样考虑是因为龟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频繁变迁的地方以及克孜尔石窟约四分之一的洞窟内存有岩画(包括手模)的缘故(20)。
1986年,吴焯先生根据在克孜尔的调查以及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提供的部分照片,在《文物》杂志1986年第10期上刊登了题为《克孜尔石窟刻画图画的内容、作者和时代》的专题研究文章,主要针对第131窟和第93窟这两个洞窟的岩画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第131窟的作者是包括苏毗在内的吐蕃部民,题材表现的是部民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而第93窟则反映的是吐蕃士兵的军事生活和征战活动。两窟均是吐蕃文化在克孜尔佛教石窟开始废弃的同时或以后的体现。它的年代上限可早到公元七世纪末安西第一次陷于吐蕃的期间之内,下限则晚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前。
1993年,晁华山先生在论述克孜尔石窟开始荒废的时间上限时,明确提出第93窟刻画的“攻战图”可能是公元8世纪初驻军士兵所为,表现的是当时的作战情景。但同时又认为这些唐人刻画约作于七八世纪之交(21)。
1993年12月,《克孜尔石窟志》编写组根据史晓明提供的材料,第一次正式的比较完整的刊出克孜尔岩画的洞窟分布与数量统计表,并参照已发表的文章综述了各家的研究论点(22)。
2000年,吴焯先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又重提此事,观点并无大变化,只是在第93窟的作者与题材问题上明显地又考虑了黄文弼先生与晁华山先生的论点(23)。
四、岩画的分布、数量与内容
根据我们多次反复的调查材料统计,克孜尔石窟现有岩画遗存的洞窟83个(不包括亦狭克沟),岩画个体图形总数逾千,其中手模之外各种不同的岩画图形个体374个(见克孜尔岩画数量统计表的34个洞窟)、手模数量约930个(24)。它们分布在石窟的各个区域(主要集中在谷内区),大部分阴刻制作在窟内墙壁的泥皮(25)和砂岩上,也有个别的制作在窟外的砂岩上。位置的高度一般距地面1.5米上下。目前能辨认的形象有:羊、马、鹿、骆驼、禽鸟、狗、驴、战马、骑士、战旗、旗徽、矛、剑、弓箭、人物、陶器、文字、太阳、符号、手模等其它图形符号20余种。鉴于岩画总数百分之七十九的在谷内区,手模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也在谷内区,同时第93、95、131窟又是谷内区最突出的三个重点岩画洞窟,故本文论述的焦点自然也集中于此。为突出主体,以下先介绍这三个方形洞窟和谷内其它洞窟的具体遗留状况,然后再介绍其它区域的部分:
(一)谷内区(23个窟)
第93窟:该窟位于谷内区中段的西侧壁,距离沟口约一百米(26),洞窟坐西向东,位置高度约十余米,前室塌毁,残存南角,窟顶形状不详。西壁尚存,进入主室的门道位于北侧,南侧为主室的窗户(1987年安装门窗并修了进门的台阶),外室存砂岩手模。主室呈方形(图50),室内的所有壁面被烟熏黑。各壁边长约4.5米,壁高约2.8米,顶为穹窿式,从穹4窿顶向下分出17个条幅,穹4窿最大直径约3米,高约1.5米。地面中央部有一坑状。四面墙壁下部约三分之一的墙皮脱落,中部壁面均有岩画遗迹,残存图形、文字等百余个(27)。现结合图片和插图予以逐次描述:
正面壁(西壁):正壁右侧部位高1.5米以下和左侧1.8米以下的墙皮落毁,据估计正壁原先应有不少岩画,可惜仅有个别留存。现在壁面右侧残存岩画及符号个体7幅,形象有旗帜、大角羊、民族古文字,另在旗帜下残留有两个汉字题记,旗帜上还刻有一圆形标识,似人面像(图51-52)。
右侧壁(28)(南壁):右侧壁现存墙皮约6.3平方米,岩画面积约占下部的一半(现存长度3.25米,高度0.9米)(29),是该窟现存岩画的主体部分,个体图形的数量达72幅,所有的形象围绕征战而表现,主要有骑士、战马、战旗、长矛、弓箭为主,整个画面的布局似一场激烈的两阵交战的情景,双方的将领各自持矛跨马,高举大旗,在画面的中部交锋,各方骑兵们冲锋陷阵,短兵相接(图53-60)。从双方的阵势来看,似乎左边的阵容大(现存图形的个体数量也多于右方,再加上窗户的部分就更多),右方的后面可能还遭到攻击(可惜画面损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右方则处于劣势,因为右方的后面明显有两个形体较大的战骑面向后方在护卫防御。此外,双方的阵容中有一些特殊的图形值得关注:如右方的一个侈口、圜底的罐形物、一只类似飞禽的图像比较引人注目(图61-62),而左边阵容的前上方则有一图形似骆驼,上似一骑人(图63,黄文弼、吴焯以为毡房),并且还有两幅母子马比较别致(图64-66);在整个画面中,尤其醒目的还有双方交界的分隔处有三个汉字最让人费解。
左侧壁(北壁):整壁墙面基本毁坏,右(东)侧存有图形5幅,分为旗帜、鹿、人射箭等,其中尤其是半跪状射箭手的姿态异常生动(图67-69),北壁尚有一砂岩手模。
前壁(东壁):左侧残留一旗帜,门道高1.8米、宽1米,门道两侧壁砂岩上留有手模22个;前壁的右侧是窗户,为便于采光,窗户的外口小、边长1米,内口大、边长1.2米,深度为1.1米(30)。在窗户的南侧壁上保留有完整的岩画,面积约1.1平方米,上刻有图形15幅(图70)。画面自左向右铺开,右前下方有两名骑兵在挥舞刀剑,相互拼搏,之间有一马,作惊恐状;周围并有残存物状;画面中上部一人骑马,持大旗,旗帜上有一倒置羊的图形,旗杆顶端刻一圆,圆内泥皮刻空,圈外刻放射状线条;估计这是代表本部族的帅旗或图腾标志;在它的后面也有一人骑马,作奔驰状,这一骑士持一旗与前面的相仿,但无旗徽;后面还有五位骑马者,人物的形式与南壁相同;在帅旗者的前方,刻有一似驴的形象,迎面站立(图71-72)。窗户的北侧壁墙皮几乎脱落,据观察下部也曾有岩画痕迹,现不详。
第95窟:该窟的方位、高度同第93窟,位于第93窟北侧约12余米,中间隔了一个形制为僧房的第94窟(按照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布规律与特点来看,这本该是一排组合型的洞窟,其窟形与功能各有不同,一般来说应有佛殿、讲堂、僧房等基本洞窟形制,可是这一组与一般性的组合稍有不同的是这些洞窟是上下排列。作为佛殿的第97、99、100、101、104却安排在第93、94、95窟的上方)。主室现存南、北、西壁,各边长3.4米,顶为覆斗式(图73),室内积风沙近半;南北两壁和顶部泥皮均脱落,西壁存草泥墙皮上下两层,里层墙皮表面涂过白色,外层稍有烟熏迹象,岩画就刻画在这块面积约5平方米的灰黄色墙面上;由于前壁塌毁,长期风吹日晒,图像多模糊难辨,目前能认清的个体图形约89个(图74-99);画面的主体基本以马、鹿、骑者为主,间有羊、骑者射箭,面向基本朝右,其中比较突出的形体是一鹿、一大角羊、几匹马和右上方的一只似大鸟的形象,大部分的牲畜都悠闲自得地站立,个别作来回奔跑状,另有一母子马和鹿的交配图在右前方;壁面上方从左至右分别有四处似炭色书写的古龟兹文字题记,其中有两处被岩画形象所划破(图100-102);右下部位有一汉字明显为后来所为。此窟与第93窟的兵戎相争的内容截然不同,以突出再现安宁的牧业生活为题材,故可称之为牧乐图(31)。南壁有砂岩手模一个。
第131窟:与第93、95窟相对的是谷内区的东崖壁,东、西两崖壁之间相距50至80米不等,第131窟就在第93、95窟对面崖壁的右前方,洞窟的位置高度略低于第93和95窟,离沟口约30米的距离;该窟坐东朝西,前壁和前室塌毁,主室边长各3.6米,壁高3.2米,顶为五层套斗式,顶高约1米(图103);窟内稍有烟熏迹象,现存所有墙面均未抹泥皮,而是在砂岩壁面上直接刷一层白灰,岩画和多处民族古文字基本都刻画在上面;洞内原先积泥沙半米以上,后清理出窟,因此,现在的岩画位置最高处在2.4米、低处是1.5米;左右两壁有大量手模印记,多达82个,且以左手为多(图104-106)制作手法有磨、刻两种,位置一般在距地面1.5米上下;岩画主要刻画在正壁上,部,从刻绘的痕迹看,不像第93、95窟是用利器工具所为,此窟只须用稍硬的器物便能刻制,这与较松散的砂岩质地有关,因而才会出现有大量的手模岩画(32)。
正壁(东壁):正壁有刻画形象和符号36个,从图像区分有:山羊、鹿、马、骆驼、人物、飞禽和一些图案符号,其中山羊最多,占9幅,人6个、有尾饰,骆驼4匹、鹿3只、马2匹,其它图像12幅,手模2个。从这幅画面的布局安排和内容分析看,这似一幅牧民迁徙图(33)。整个构图呈三角形自右向左展开,各个不同的形象根据游牧生活的经验布置、排列有序。前面似有一形体高大的人开导引路,紧接着是一人骑骆驼者,两手平展,牵二只满负重载的骆驼,还有一禽鸟也被其人牵于手中;中部多为山羊、鹿和马,人物多在后方,并有两人伸开手臂,阻拦两只回头羊。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间一组图案符号古据中心位置,估计应该与本民族的族属和图腾崇拜有内在联系(图107-130)。同时,还有一个十字交叉形符号非常引人注目,正壁右上方存两处古龟兹文字(图131-132)。这不太清晰的题记显然早于岩画,因它们几乎与现墙面融为一体并有被岩画打破关系的迹象,既使一排较清晰的也很难断定是否与岩画同时所为,至少岩画的刻画与文字的书写工具和印痕显然有别(34);还有正壁岩画的上方(鹿的后面)存一处阿拉伯文题记(图133)。此外,正壁下面砂岩上也刻有一羊形象;另外,正壁的几处岩画在刻画之前其质地事先经过打磨平整之后才进行作画。
右壁(北壁):有2幅似马的比较模糊的图形,刻画的痕迹和技法与正壁有别;另存手模18只。左壁(南壁):现存岩画图形5幅,两只羊、一个十字交叉形符号、一个月牙状符号,还有一形状似鹿的造型;并且也有一处古龟兹文字题记。此外,尚有手模58个,其中有些手印的深度达4厘米,且左手多于右手,也有刀刻的手模印记。
此外,外室南壁有砂岩手模7个(1984年调查时只有3只手模)。
以下按序列号介绍谷内区其它洞窟的具体遗存:
第82窟:僧房窟,甬道南壁手模4个,其中左手3个。
第83窟:方形窟,手模1个。
第92窟:方形窟,手模107个(南壁92个、北壁5个、西壁9个、外室1个)。
第94窟:异形窟,主室北壁刻画图形模糊难辨,约4个。
第98窟:中心柱窟,北壁甬道口上方的壁画上用细线轻刻出一鹿(图134)。第99窟:中心柱窟,主室正壁主佛龛内北侧壁刻一似第93窟的旗帜(图135)。
第100窟:中心柱窟,整个窟被烟火熏黑,主室正壁主佛龛内刻不同符号与手模等共26个,其中手模11个(左手9个,南、北侧壁各刻带圆心的手模1双,而且北侧的还用一方框框住,并间有符号(图136-138);南壁还单独刻2个非常规整的圆圈,中心有点;下方刻一不规则的动物;北壁有两处阿拉伯文字题记,北壁下方还残留一禽鸟的躯体(图139-144)。
第107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13个。
第108窟:方形窟,西壁砂岩手模16个、东壁1个。
第117窟:方形窟,泥刻3幅。前室正壁门右面高3米处似有一线刻的家
禽形状;后室左(东)壁高1米处有一线刻山羊,另有一图形符号(图145-147)。
第118窟:方形窟,有岩画9个,手模39个,另有多处刻画的民族古文字及符号。手模的分布为:正壁(北壁)东侧刻画手模1个;右壁(西壁)刻画手模15个(左手10个),其中3个手心(2个右手、1个左手)似有标记,但不清楚;左壁(东壁)刻画手模10个(8个左手);门壁(南壁)东侧刻画手模1个;门壁东窗刻画手模7个(5个左手,另2个不详)、西窗东壁刻画手模5个;(图148-162)
第123窟:中心柱窟,主室右壁的壁画上刻画似弓箭的图形3个、另一似人形。(图163-165)
第124窟:方形窟,东壁残存马、羊、鹿、鸟等,有手模1个(图166-167)(35)。
第126窟:中心柱窟,手模1个。
第126A窟:距第126窟南侧约10米处,龛内似有一山羊的岩刻与手模等(图168-169)。
第127窟:异形窟,南壁可辨羊角等4个图形(图170-171);窟外南侧砂岩手模3个。
第129窟:方形窟,外室南壁砂岩手模2个(左右一双)。
第130窟:僧房窟,室外砂岩手模1个。
第132窟:方形窟,墙皮基本脱落,各种砂岩手模共138个。其中外室右壁3个;前室与主室之间的门道南壁有40个、北壁45个;主室正壁2个(左手)、右壁(北壁)22个、左壁(南壁)27个,并有只磨擦出手指而无手掌的特殊手模指槽现象;另有北壁刻画图形7个,其中似羊、旗帜、弓等(图172-175)。
第135窟:方形窟,东壁的壁画上残存刻画的巨大弓箭、山羊等多幅(图176-177),可辨清形象者4个;手模41个;正壁手模6个,右(北)壁35个(多右手)。
(二)谷西区(33个窟)
第7窟:中心柱窟,右甬道入口处高1.65米处残存数道划痕与不明形体;左甬道外壁残存一似鸟的刻画(图178-179);后甬道后壁壁画上刻一大角羊(图180)。
第8窟:中心柱窟,主室左壁(东壁)中部壁画上有大角羊一个(图181);正
壁手模3个(两个左手)。
第13窟:中心柱窟,主室左壁手模3个。
第18窟:僧房窟,进入主室门道的左壁有右手手模1个。
第19窟:僧房窟,进入主室门道的右壁有右手1个,未完成的手模3个。
第20窟:僧房窟,甬道及主室存刻画图形8个(图182-189)。
第22窟:僧房窟,甬道拐弯处外壁手模1个,左手。
第23窟:中心柱窟,左甬道手模1个,左手。
第27窟:中心柱窟,手模17个,其中左手15个,右手2个(图190-191)。其中有2个刻在主龛内右侧壁的墙皮上(左手),其余在砂岩上(36)。
第28窟:方形窟,正壁两龛之间手模1个。
第29窟:窟外东侧龛存左手手模1个。
第30窟A:砂岩手模1个,左手。
第31窟:北壁砂岩手模2个。
第32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7个。其中正壁6个,东壁1个。
第33窟:方形窟,西壁砂岩手模7个。
第34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30个。其中正壁5个,东壁23个,西壁2个。
第35窟:僧房窟,进入主室门道右侧一刻画似马的图形,两后腿间刻一箭头符号(图192);另有手模4个。第36窟:方形窟,手模25个。第37窟:僧房窟,手模3个。第38窟:中心柱窟,东甬道外壁一个用单线刻画的大角羊(图193);手模
4个,主室西壁1个,东甬道外壁3个,左手(图194-195),为便于刻画,手指叉开。
第39窟:方形窟,正壁高1.4米处刻有一山羊,下边另有一不完整的似羊的图形;右壁高1.9米处,刻有一未完成的羊的图形(图196-198)。
第40窟门外西侧,砂岩手模4个(图199)。
第43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22个。其中东、西壁各11个。多处文字题记,一人形刻画(图200)。第43-47窟的台阶的途中崖壁上,砂岩手模1个(图201)。第46窟:方形窟外东侧,砂岩手模1个。第47窟:大像窟,手模共84个。其中外室正壁高2.5米处1个;外室西壁
42个;高约3米处的壁面(37)6只,还包括两对双手、左手4个,外室东壁10个,其中8个处在高约4米的壁上,也有一对双手;后室、甬道和中心柱上共31个,其中左手5个。(图202-205)
第48窟:大像窟,手模5个。外室2个,正壁高处1个砂岩手模,东壁1个;后室3个,1个砂岩手模,2个刻画手模(左手)。第49窟:方形窟,正壁和左壁岩刻4个。正壁一山羊,轮廓之内的墙皮皆刻去,形象较写实;左壁也有一山羊形象,线刻,前肢残损,还有一形体似未刻完,也似山羊(图206-209);外室西壁砂岩手模4个。
第58窟:中心柱窟,左甬道外壁的壁画上有刻画手模1个(左手)。
第70窟:大像窟,砂岩手模4个。
第71窟:异形窟,手模10个。
第75窟:僧房窟,甬道右(西)壁一形象似羊(图210-211)。
第77窟:大像窟,后室中心柱砂岩手模2个。
第80窟:中心柱窟,手模7个,其中主室正壁龛内南侧壁存一刻画左手手模,甬道6个砂岩手模。
(三)谷东区(21个窟)
第139窟:大像窟,手模9个;其中刻画1个,砂岩手模8个。
第140窟:僧房窟,手模14个;其中在东壁砂岩上刻画1个,北壁砂岩手模13个。第154窟:大像窟,主室门壁右下侧岩刻山羊4个(图212-217);后室有手模1个,另有2个砂岩手指印。第155窟:中心柱窟,主室东壁4个似羊的岩刻;窟外左下4个线刻羊(图218-223);砂岩手模2个。
第156窟:现修门壁窟外砂岩刻画符号8个(图224-226)。
第159窟:中心柱窟,东壁隐约有砂岩手模2个。
第160窟:中心柱窟,西壁有砂岩手模3个(右手),中心柱西甬道内壁有砂岩手模4个(左手)、后甬道正壁有砂岩手模1个。
第161窟:方形窟,窟内壁画烟熏严重,南(门)壁东侧约1.4米高处岩画图形2个,大的显然是一羊,小的也属家畜形状;室外有砂岩手模4个(图227-231)。
第162窟:僧房窟,外室有砂岩手模2个。
第163窟:中心柱窟,主室左壁的壁画上刻画一似鹿的岩画;右壁刻一大角羊(图232-236);正壁砂岩手模1个。第164窟:僧房窟,外室西壁一大角羊(图237),手模3个。第166窟:方形窟,正壁有砂岩手模1个。第167窟:方形窟,正壁手模1个,左(东)壁6个(左手),右(西)壁高3米
处刻左手2个,并有2个图形似鹿。另有2个几何形符号,其中一个十字形(图238-239)。
第168窟:方形窟,砂岩手模3个。
第181窟:中心柱窟,主室墙皮刻画手模2个(左、右手各1个),古民族文字、汉文字题记各一(图240-243)。
第184窟:中心柱窟,主室北壁砂岩手模2个(左手)。
第192窟:中心柱窟,刻画符号一个(图244)。
第194窟:方形窟,北壁砂岩手模2个。
第195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共33个。其中左甬道1个、后甬道正壁11个、后甬道前壁19个、后甬道北壁2个。第196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共8个。其中主室左壁砂岩手模2个、西壁4个、西甬道外壁2个(图245)。
第198窟:中心柱窟,东甬道外壁砂岩手模2个(图246)。
(四)后山区(6个窟)
第201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共24个。其中东壁21个、西壁1个、南壁2个。第206窟:中心柱窟,砂岩手模共24个。其中正壁1个、正壁龛内9个、左壁(东壁)8个、右壁(西壁)6个、。第220窟:长方形窟,东壁刻写民族古文字若干(图247-251)手模7个。其中东壁5个(砂岩手模2个,其一掌内有一大写的汉字“龙”(刻画,3个);南壁龛2个(一左一右);另有一蜘蛛刻画在砂岩上。
第222窟:方形窟,岩画4个(图252-255)。
第232窟:砂岩手模17个。
第233窟:异形窟,砂岩手模1个。
另外,从谷东区往后山区的路途中的岩石上有砂岩手模1个,并有刻画者的姓名(阿不登)及刻画日期(87.9.19)。(五)亦狭克沟(38)(2个窟)亦狭克沟石窟现存四个洞窟,由于其驿站的功能与作用所限,洞窟形制主要为方形或长方形,洞窟凿刻在沟西崖壁上,面朝东。窟内均无壁画。一大窟,长度8.8米,宽度5.3米,壁高2米,券顶高1.3米,前壁一窗户,外口1米,壁厚90厘米,内口1.3米,窗台上抹有草泥,壁面有刻画图画。右壁似有一壁炉,壁面砂岩上涂一层白灰泥,正壁可见6处龟兹文题记,左壁的龟兹文模糊不清,并有6处阿拉伯文字,后壁右角有许多阿拉伯文,窟内至少有四五种不同的文字。一小窟,型制同大窟,横宽3.5米,深3.8米,右壁一壁炉,左壁有龟兹文题记(图256-274)。
五、岩画的制作技法、形式与风格
在论述本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克孜尔石窟的岩石质地再作一个说明。克孜尔石窟的山体属于岩石无可置疑(地质学上称晚第三纪灰白色粉砂岩或泥岩沉积岩石),但是,这种砂岩相对松散,水、风与震动对其危害较大,如果用坚硬的工具敲凿它倒十分结实,可是,直接用手或稍粗糙的物体搓磨其表面,很容易留下痕迹。因此,比起各地岩画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刻物象,可谓事半功倍。其次,在佛教石窟废弃的窟内墙壁的泥皮上刻画图画,也是极为省力的。再则,窟内作画总比露天舒适、方便的多。这些条件和因素都是各地岩画作者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克孜尔岩画的作者可以用非常简陋的工具(利器和钝器均可)在这些无人管理的窟内窟外随心所欲地表达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审美感受。
根据现存岩画的制作痕迹来分析,其表现技法大致有以下几点:
1、单线法:物象的形体结构用阴刻单线来表达,这种方法直接、明确、简易、省事,是克孜尔岩画制作的主要手法。
2、刻面法:把物体的轮廓内部全部或部分刻去,留下一种剪影效果。
3、线面结合法:较典型的是第93窟的旗帜、第95窟的马等。
4、磨搓法:由于砂岩质地的因素,制作者直接用手在砂岩表面上下磨擦,即可成形。克孜尔留下了大量的手印,有的仅限于手指印,或称“指槽”(第47窟主室左壁等)。
侧面轮廓似乎最能表达动物的基本特征,人类原始的洞窟壁画就采用了这种观察方法,这使得各种不同的动物形象一目了然,纵观所有的岩画动物图像都无不如此,克孜尔石窟的岩画同样继承了各地传统的表现技法。
平行透视法(散点式)不必受焦点透视规范的约束,构图平铺直叙反而错落有致、稚拙天真,平面感与装饰效果可以说是古今壁画的一般性特点,第93、95、131和124窟等大场面的画面都运用了这个规律。
简约与抽象从视觉图像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绘画艺术走到了今天,而且还会永远地传承下去(39)。便捷的直觉图形和象征性符号无论是远古的石器时代还是当下的信息社会,都将成为人们不可抗拒或难以回避的视觉文化心理和生存信念的召唤。克孜尔石窟岩画中诸多的有明显寓意的标识性图像都带有这种启蒙文明的余韵。
六、年代、作者族属与相关问题
岩画断代和作者的归属是岩画研究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年代越久远就越不易把握。况且,岩画的作者与分布区域又多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文化有关,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这个难题。
比起目前岩画断代的一般性方法来说(动物考古法、碳十四测定法、比较学、层位叠压现象、风格题材等),克孜尔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相对而言要明确得多,如年代的上限问题就会相对明朗。可是,眼下依然还有诸多的扑朔迷离之处。如前所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必须首先借助前人对克孜尔岩画年代与族属的观点,然后,再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黄文弼先生1958年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推测克孜尔石窟的三处岩画非近代人手笔。他认为第93窟的刻画“疑为游牧民族走马为之游戏图”,同时根据壁面上的文字和其它洞窟的文字题记,推测此为“仿游牧民族之游戏绘画”,时代为唐之末叶。另外,亦狭克洞中刻画的图像和民族古文字,“即为过此商侣所为”(40)。显然,黄先生的对岩画年代的看法是与他在克孜尔发掘到的文字遗书与题记有关,而且偏重于汉文的年号与史料(41)。由此,他才怀疑作者是“仿”游牧民族的汉人所为。而亦狭克沟没有汉文题字,故可能是过往的非汉人的商侣。黄先生的论点为我们看待克孜尔岩画的年代与作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和分析线索。
北京大学宿白先生1979年在谈及新疆地区的佛教诸问题时曾涉及克孜尔石窟的岩画年代与族属,宿先生以石窟考古类型学和西域历史文化背景为基点,并与当时周邻地区已发现的岩画资料作比较后为克孜尔部分重要洞窟和亦狭克沟的岩画年代和作者给予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克孜尔谷内区和谷东区大约八世纪开凿的某些洞窟和克孜尔东亦狭克沟中的石窟的刻画形象与内容和西藏西部、楼兰地区以及甘肃嘉峪关一带的岩画极为相似。这些都是九世纪吐蕃牧民的遗留。
1985年,史晓明与王建林认为第93、95、131窟是岩画中非常成熟的作品,年代也较晚。考虑到石窟中整体岩画的情况,将这些岩画的年代上限定在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即公元八九世纪,下限时间至少推至十三世纪左右,作者并非只局限于吐蕃游牧民,甚至可能还有回鹘、蒙古时期的遗留(42)。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吴焯先生主要针对第131窟和第93窟这两个洞窟的岩画,将宿白先生提示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学科化,观点也进一步明确。他认为:第93窟的题材是“吐蕃征战图”,作者是吐蕃士兵;131窟的题材是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作者是吐蕃的部民百姓,其年代上限可早到公元七世纪末安西第一次陷于吐蕃的期间之内,下限则晚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前(43)。
北京大学晁华山先生根据第93窟刻画的三游旗、汉字以及石窟内其它洞窟遗留的汉文题记的年号和相关史料,以及公元9世纪后至清代初期这里再没有留下汉人的其他遗迹而断定,该窟的刻画是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唐军士兵所作(4)。
综上所述,研究者之间确实存在有不同观点上的差异,可归纳的共同之处在于:岩画的年代上限应该是佛教在克孜尔石窟衰落之后;岩画的作者多与游牧民族相关;吐蕃与唐朝在龟兹的争夺战是第93等窟岩画发生的主要线索;不同的见解是作者族属有区别,还有岩画的年代下限不易把握。以下,笔者试图再一次在前人的基础上(45),对克孜尔岩画的整体状况和以上介绍的实际遗存作具体地分析与鉴别,从中找到相应的合适角度与材料来分别看待克孜尔不同洞窟、不同题材、不同造型的岩画现象,进一步地探讨克孜尔石窟岩画的有关问题。
既然岩画年代的上限是与石窟的衰落有关,那么,有必要先弄清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究竟在何时?其实,克孜尔重要的岩画年代与族属焦点可以集中到第93窟的问题上来,该窟特殊的刻画图形与文字题记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国内外学界一般的共识是公元8世纪,这一点无庸质疑。并且可能与当时发生在龟兹的战争有关,而战争又可能是唐王朝与吐蕃在西域的霸权之争,由此才直接影响到克孜尔石窟的衰落,故龟兹学的研究者都将第93窟的刻画归属为争战的题材,只是作者的族属问题意见不一致。黄文弼先生尽管没有明指是哪个民族所为,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明显看出他是指唐军,而晁华山先生也持这种观点,并且理由说得相对合理(2007年8月27日笔者在敦煌学术会期间向马世长先生请教时他也倾向于作者为汉人);然而,宿白和吴焯先生的看法也不无道理。可是,还有一些迹象他们没有注意到或是观察的不细致,如:第93窟的四壁均有刻画,只是大部分的墙皮因该洞窟比较潮湿,尤其正壁与北壁严重脱落,现在只残存个别图像,尽管如此,某些形象还是非常重要,例如正壁残留的两个汉文题字、似大鸟的图形、大角羊、旗帜上的圆形图像,南壁西侧的罐型图像。另外,窗户南壁旗帜上的羊的图示等,这些图像比起其它图形都是供我们分析判断年代和族属的比较直接的特殊研究信息,如罐型的图式在各地的岩画中除了克孜尔这一例之外还有西藏西部日土岩画中也有陶罐出现(图275)(46),如果岩画作者只有吐蕃游牧民有刻画陶罐的习惯的话(47),那么,宿白先生和吴焯先生的立论就有依据可寻,再加之西藏(苏毗)的“鸟卜”习俗确实与克孜尔岩画中出现的鸟的图形相吻合。此外,还有吐蕃有“事羱羝为大神”的图腾习俗(48),如果正壁、窗户南壁旗帜上的羊的标示与此相关的话,这就更增加了吐蕃族属的说服力。不过,虽然有这些旁证,可是,目前第93窟的两处汉字却难以找到对应的、合适的解释理
由,因为,那两处遗留的汉字确实与岩刻是同时所为(49)。然而,如进一步考虑到汉字书写的欠规范化程度和作者特别强调羊图腾因素的话,作者可能更倾向于游牧民族。当然,是否还存在其它偶然性的因素目前仍很难断定。此外,因为要顾及石窟岩画的整体状况,以下再简述六个方面的问题,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1.看待克孜尔岩画的总体状况,不仅要重视本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承关系,而且还要将克孜尔岩画放到整个中亚文化圈的背景中去审视,以此为视野,就不能笼统地把克孜尔不同的83个洞窟的岩画问题概念化,理应区别对待,这样考虑会有利于岩画年代的下限与作者族属等相关问题。同时,又牵扯到研究方法的拓展和图像学的渗入。这些问题的提出至少是基于近些年来国内的岩画发现与研究工作逐步进展,使得龟兹石窟的岩画研究有了相对丰富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在运用图像学的方法论方面也有了多重视角,包括本地区新发现的岩画材料,可以提供直接的近距离的对比。
2.通过本地区普遍存在的岩画现象,使我们首先更加注重,龟兹自古以来就是多个游牧民族定居和不断变迁的地区,龟兹本土的吐火罗民族自不必多言,他们在长期的游牧迁徙的历史长河中在中亚各地均留下了辉煌的足迹(50),虽然吐火罗民族自从来到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定居以来,从来就没有也不会放弃传统的牧业生活方式(51);其次是后来的突厥、吐蕃、回鹘、蒙古族等,他们都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并且都有刻画岩画的文化传统(52)。这些基本的文化背景是我们面对龟兹地区的岩画时所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基础性问题(53)。如拜城县老虎台的岩画中羊的刻画形象与克孜尔第154窟中的羊的表现手法如出一辙(图276)。所以,克孜尔岩画作者的族属问题就不免更复杂化了;再者,看待龟兹地区的岩画,不仅仅是只局限于新疆本地,而且也不能仅限于所谓中国的“半月形岩画圈”或“半月形高地文化传播带”的范围内(54),它应该是与中亚之外更广阔的地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55)。
除了上述的“羊图腾”之外,我们从第7、93、95、100、117、124、131窟均刻有类似“鸟”的图像可以明显感到还可能有“鸟图腾”的相关问题。因为“鸟图腾”的图像在各地的岩画中包括新石器时期的其它艺术中都普遍存在(56),并各有其地方特色(57)。克孜尔岩画属于晚期现象,狩猎、野生动物等题材消失,可是,类鸟图像竟如此突出,而且在不同的洞窟里出现,可见其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相通之处,这至少与刻画者的传统观念与生命意识的潜质有关(58)。这种对鸟的非记事图像的、非自然属性的特殊关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岩画作为一种原始语言的表现,也会有方言”。但是,在世界岩画的范围内,“一些重复的因素出现在所有的大陆,标示出岩画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结构”(59)。由此可见,克孜尔岩画的共同文化内涵并非仅限于周邻地区。
3.关于克孜尔岩画年代的下限,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推至13世纪以后。一个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如果纵观龟兹石窟的整体兴衰史,就可以基本上确定这种看法。因为,以克孜尔为代表的一批龟兹本地风格的石窟大约与克孜尔石窟同时衰落,而惟独库木吐拉石窟延续的时间比其它石窟长得多(60)。所以,当石窟还没有废弃之前,洞窟内的壁画上是不可能随意乱刻乱画的。笔者曾在台台尔、库木吐拉等龟兹石窟也发现有数量不少的岩画迹象(61)。故此,如果以库木吐拉为例证,将该石窟岩画的上限和龟兹其它石窟岩画年代的下限一起来考虑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疑问。
4.结合岩画发生之前的龟兹壁画相关题材与造像,找到间接的可能性的佐证资料。龟兹石窟壁画中大量的动物图像从侧面也反映出游牧文化在佛教造像中的突出地位,特别是羊的造型在壁画中表达的格外精彩(图277-282)。因为,羊不仅是游牧民族日常的主要食物,而且还与游牧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图腾崇拜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仪式上的联系,如突厥汗国就曾经把野山羊作为政权的象征(62)。于是,第93窟窗户南壁的有山羊的旗帜就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同时,问题也愈加微妙起来,因为不仅是古代羌族(63)、突厥民族,而且吐蕃,甚至中亚的游牧民族都同样有这种遗风(64)。
5.手模与印记问题。手模又可称“手印”等(65)。至于说手模这种最古老的、跨地域、跨时代、跨民族的造型艺术观念,尤其是在岩画造像的体裁中显得特别突出,由于手模的文化内涵各不相同(有力量、权威、意志、占有、征服、胜利、祈求、避邪、求援、生产、生殖、兴旺、增多、维持、享受、创造、标志、表现、自豪、礼仪、礼赞、游戏、留念、签名、报道等多种象征寓意的可能性),因而,手模现象是克孜尔岩画中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是由于洞窟废弃之后的上千年的时间内,无数人曾来过此地,或居住、路过、游玩、朝拜等等,既使近代和当代,也有游客在重复古人的“游戏”(66)。按照有些学者的看法,手模往往与其伴生的图形有关联(67)。既有原始思维和宗教巫术的含义,又有现代人玩耍留念的游戏行为。所以,克孜尔手模的表达方式和寓意也应该有所区别。如第93等窟大片的手模,可能就与战争的胜负有关;第95、131、132等窟的可能就与氏族部落的生殖兴旺、宗教礼仪等有联系;而第100窟龛内的带有圆心的手模估计与同时刻画的阿拉伯文字有关系。至于说近年来不少游人的随意刻画又可另当别论了。
岩画中的印记符号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氏族问题(68),但是,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如第131窟等岩刻中的多处符号印记和其它洞窟的不同符号图式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此外,同一个洞窟内存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刻画图形、文字符号等也是正常现象,第95、131、220等比较明显。
6.晚期岩画的普遍性问题。岩画的风格化问题无疑是世界范围内的共性,由于生产力低下,刻画的质地与材料更接近于自然;因为造型能力所限,形象的塑造更倾向于稚拙;生存信念直接受潜意识控制,故审美判断更接近本能;鉴于思维方式的古朴,表现形式受宗教信仰的迷惑与支配。
克孜尔岩画之所以有多种游牧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史前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间曾经有过漫长的、广泛的接触与交流。这种直接和间接的传承脉络关系会随着当代科技水平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而变得日益清晰起来(69)。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先民们在游牧经济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型的同时,还依然会保留着畜牧业生产的传统观念,这是无可非议的。所以,第95、131窟有意突出畜牧业生产的题材,而野生动物和狩猎的场面消失等与原始岩画的题材有明显差异,包括大量的文字刻画、体裁缺乏原创性等,这些都是克孜尔岩画的基本特点,这显然是游牧民族走向定居生活的文明结果。
【余论】
根据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岩画研究的针对性和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建构人类史前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可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析岩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目前正在它的初级阶段”(70)。然而,重新审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早期文明,充分认识原始视觉艺术的人文价值就值得关注。由此,岩画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就显现出其它文献所不能替代的功能与义务。从这个基本的角度出发,岩画无可置疑地为历史考古、民族宗教以及文化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原始图像资料。真可谓是“写在石头上的史书”。但是,文字发明应用以后的岩画现象,其史料的性质与功效就会相应减弱,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佛教石窟废弃之后才出现的岩画就失去了那些基础或早期的文化蕴涵。然而,问题还并不是这么轻易或简率。晚期岩画自有其史前岩画不可替代的功用(71)。各地的农业文明的岩画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在证实着自身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自然原型是造型艺术的图式根源,人类的图像从一开始出现就从没有违背这个基本原则。这种造型意识的生理图式的成熟有专家认为大约在旧、新石器交界时期(72),到公元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除了希腊、罗马的科学造型观念的自觉化之外,原始艺术的模仿、抽象与综合心理素质一直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并各自独立地并行发展。岩画的造型规律可以说从未脱离这个先前的范式,它是上述的模仿与抽象相混合的一种精神意向特征的表达和寄托。至于说公元7、8世纪在塔里木盆地的佛教圣地的出现则是游牧文化对农耕文明审美素质的悖反,因为佛教艺术至少是希腊、罗马造型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在龟兹则是人类造型艺术在中世纪早期的一个辉煌结晶。所以,当游牧民族在废弃的佛教文化殿堂内随意刻画时所体会到的愉悦感与那些辉煌的、五彩缤纷的佛教造像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和疑惑。
不仅仅是克孜尔石窟,龟兹石窟群普遍存在着衰落之后的游牧民族刻画岩画的现象。这的确是一种游牧文化征服农业文明的历史事实。在中世纪宗教艺术的殿堂里随意刻画游牧民族的稚拙图画,比起先前的精美佛教壁画和塑像,无论是艺术的水准还是思想的哲理,可不是一般性地相形见拙。文明确实有时在倒退,就像欧洲的中世纪在很多层面上替代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那样让人沮丧!这种无奈在物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20世纪依旧在重演。这也许会引起对历史直线进步论观点偏见的警觉?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这么让人不可思议!我们从中汲取的文化教训只能是客观地反思历史,更好地呵护人文思想延异的秩序,让人类文明的历史车轮协调前行。
附注
注释:
(1)、(20)、(31)、(33)、(42)、(45)、(48)、(64)史晓明、王建林《克孜尔石窟第93、95、131窟“岩画”初探》,新疆首届美术理论年会论文,1986年8月,未刊。(见本书附件1)
(2)关于岩画“地点”和“地区”的区别:“地点”是指有岩画的地方,其边界是要在最靠边的图形以外500米的地方,从各个方向看都没有图形。两组图形之间相隔的距离超过500米,这样的分布可视为两个不同的地点;而“地区”可以包括许多地点,地区与地区之间要相隔20公里以上。一个地区的岩画可能在文化特征、地形地貌等都非常具有代表性。以此而论,龟兹石窟的岩画可称作一个地区,而其中的一个石窟则是一个岩画点。请参阅国际岩画委员会前主席E·阿纳蒂的文章《世界岩画—原始的语言》,载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编《岩画》1,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9—11页。
(3)盖山林,《世界岩画的文化阐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6月,第215页。
(4)龟兹石窟群包括拜城县的克孜尔、台台尔、温巴什、亦狭克、都干、萨喀特克、喀拉苏、玉开都维、阿克塔什石窟;库车县的库木吐拉、克孜尕哈、森木塞姆、玛扎巴赫、阿艾、苏巴什石窟;新和县的吐乎拉克艾肯、塔吉库克、三佛洞石窟;乌什县的沙依拉木石窟。
(5)明屋依,维吾尔语:千间房子;达格是山的意思。
(6)东西狭长形状的拜城盆地是由于北面波澜壮阔的天山山脉中段南麓的冲积洪积扇以及诸河流受到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却勒达格山的阻挡而形成,盆地的西端与温宿县接壤,东端靠库车县的山地,却勒达格山的南坡为新和县、库车县境内,木扎提河从天山汗腾格里峰东麓发源后由北向南流淌,由于受到却勒达格山的阻拦而顺着山脚向东流经拜城县南端边境,在到达克孜尔乡的这一百余公里之间,又分别汇合了天山峡谷流下的四条大的支流(最后的交汇处是1992年建成的克孜尔水库,年流量21.97亿立方米,水库以下的河继续向东流经克孜尔石窟南边,然后再穿过却勒达格山谷流经库木吐拉石窟西崖洞前到沟口区的东方红水电站,下游为库车、新和、沙雅县绿洲)。准确地说克孜尔这个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小山坳是戈壁台地与却勒达格山之间的峡谷,明屋依达格山的山体在地质学上被称作是晚第三纪灰白色粉砂岩或泥岩沉积岩石,本来应该是西南部天山中段南麓喀尔勒克达格山的支脉与却勒达格山之间的山间平地,但却被木扎提河等拜城盆地的11条汇聚的大小河流或天山的洪水冲开了一片河谷。
(7)拜城县志为海拔1225米,地理坐标:北纬41。41′、东经80。31′。
(8)由于克孜尔石窟夹在两山之间,苏格特沟的泪泉之水长流不断,加之夏天的洪水冲出的扇形冲积地,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封闭小山坳,这个安逸的小环境冬季温暖无风,是游牧民十分理想的冬季牧场(冬窝子)。另外,渭干河也是一条天然屏障,使得在这儿过冬的牲畜安全无恙。
(9)1986年之前,克孜尔石窟的现代信息、交通和生活十分不便。
(10)以峡谷沟口为界,西面崖壁有洞窟的区域为谷西区(第1—80、89-1—89-10、新1窟、90-1—90-10),峡谷内东西南北各侧壁的洞窟分布区域称谷内区(第81—135),峡谷沟口的东面为谷东区(136—201、232—235)和后山区(202—231)。关于峡谷的名称,黄文弼先生在1958年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就已称苏格特沟。
(11)它与龟兹另一处重要的石窟库木吐拉有相当数量的汉地风格的壁画雕塑显然有别,拙文《龟兹壁画艺术概述》,未刊。
(12)宿白、金维诺先生都认为龟兹是佛教文化、艺术东传的另一个发源地。笔者的《鸠摩罗什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一文也提出龟兹的造像直接影响了公元五六世纪中原的佛教造像,文章参加1994年鸠摩罗什国际学术研讨会,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3月。
(13)刘锡淦、陈良伟,《龟兹古国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
(14)一个重要因素:游牧民族在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土著化的那一刻也就是向农牧定居生活转型的开始,这种模式在天山以南的地理环境中尤其典型,(参见王博、傅明方《包孜东、麻扎甫塘古墓与龟兹古国文化》,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39-150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龟兹壁画中存在的大量生动的动物形象得到充分应证。
(15)多数文章称其为“刻画”图画。
(16)陈兆复,《古代岩画》,文物出版社,2002年2月。
(17)克孜尔石窟的山体在地质学上被称为晚第三纪灰白色粉砂岩岩石。
(18)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文物出版社,1958年。
(19)宿白,《调查新疆佛教遗迹应予注意的几个问题》,《新疆史学》,1981年第1期。
(21)晁华山,《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分类与寺院》,《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
(22)阿克苏地区史志编篡委员会、拜城县史志编篡委员会、龟兹石窟研究所合作编辑,《克孜尔石窟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12月。
(23)吴焯,《克孜尔石窟兴废与渭干河谷交通》,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6月。
(24)至今尚有29个洞窟未调查(见克孜尔岩画手模数量统计表的70个洞窟);此外,在克孜尔石窟东约10余公里的亦狭克沟石窟也有岩画,1984年6月27日亲往调查,四个洞窟中其中有两个洞内发现岩画图形8幅,民族古文字多处。
(25)这里所说的泥皮是指所有绘制龟兹壁画所准备的壁面,它是在开凿好的石窟内的墙壁上附着的特制的灰泥,但这种泥质的地仗容易脱落。
(26)谷内区中、后段实际上是明屋依达格山上的两道洪水沟汇合后的靠近沟口的约一百余米的狭谷地段。
(27)1990年复查的结果。
(28)本文左、右壁是以主室正壁面对入门方向而划分的。
(29)根据现状分析毁坏的部分应还有一定数量的岩画,并且该壁在1986年夏天又遭到当地老乡的破坏,部分岩画又遭厄运。
(30)克孜尔洞窟窗户的采光形式普遍都采用这种外口小内口大的形制设计。
(32)克孜尔石窟类似情况甚多,只需用手直接按在岩壁上,轻微来回搓磨几下,便可留下清晰痕迹,但也有一定数量的手模是用工具刻画在泥皮和壁画之上,所以,整个石窟手模印痕达930个之多。
(34)吴焯可能将一处文字误作吐蕃文。
(35)1990年4月12日上午12时59分,史晓明独自一人从第125窟前的悬崖绝壁处小心翼翼地靠近第124窟,在离该窟约5米的下方观望东壁和北壁,隐隐约约看到残存的墙皮上有许多图像,由于该窟前半部分塌毁,洞窟基本处于露天状况,墙面日晒风蚀,当时能辨认出的形象东壁约7个,北壁似有手模,故迅速作速写一幅,待退回安全地之后才觉得十分后怕,出了一身冷汗。因此,目前该窟岩画的数量是不确切的。
(36)1990年调查时只有7个。
(37)之所以这些岩画的位置很高是由于从前泥沙堆积在窟内的缘故,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管所时期将其清理,其它洞窟的情况也类似。
(38)1984年6月27日,晨7时半,为专程调查该石窟的岩画,王建林、艾米尔拉、许忠德、笔者一行四人从克孜尔石窟出发,从后山前绕道而行,越无数山峦,徒步跋涉,一鼓作气,于11时20分到达目的地。吃饭后稍作休息,画洞窟外景速写,然后分头对四个洞窟进行考察、记录、测量、绘草图等。中途笔者沿沟壑向北探查,经数公里,两壁并无发现,因时间关系遂后退回。工作完成后返程,一天中行军走路10小时以上,至克孜尔已深夜。连续休养三天,身体才缓慢恢复正常。经地望、方位、距离与周边环境的推测,该石窟为古代交通驿站,东面过盐水沟可去克孜尔尕哈等石窟,南下顺河流可到库木吐拉石窟,北沿沟壑上溯经台木台木、过戈壁跨克孜尔河可到达台台尔石窟,西边溯河而上则是克孜尔石窟,故地理位置四通八达。近日,姚士宏先生寄未刊文章《“坛姆塔木”断想》,文中提及亦狭克沟的功能与作用不仅有同感,而且他还认为亦狭克沟的洞窟可能是龟兹各石窟、寺院之间易寺僧尼频繁往来的临时居舍,是佛教文化传播、繁荣的交通古道。此外,这种情况他曾用书信的方式简略地告知过吴焯先生。
(39)这里是指广义的抽象概念而非指20世纪的现代主义抽象绘画,当然,既是现代的抽象也离不开广义抽象的点、线、面的基本要素。
(40)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6月。
(41)1928年11月30日至12月15日黄文弼先生考察克孜尔时,于12月8日在现在编号的第97号窟清理出:“一汉文文书残纸,上书“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头”,按贞元为唐德宗年号(贞元七年系公元791年),是此地在8世纪末尚在活动。此纸疑为往来人员过此之签证。同地又发现一汉文文书云:“□□节度押牙特进太常卿”等字,节度上疑为“碛西”二字,节上按其笔画痕迹,亦类西字。按《资治通鉴》:“碛西节度使,为开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为有碛西节度使之始。押牙为碛西节度属官。是此纸为开元间所写。在另一佛洞中亦掘拾一残纸,上写“碛西行军押官”,必为同时所书。”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6月,第261页。
(43)吴焯,《克孜尔石窟刻画图画的内容、作者和时代》,《文物》1986年第10期。
(44)晁先生可能参考了黄文弼先生的“仿游牧民族之游戏绘画”的观点。
(46)熊文彬,《汉隋之间的西藏原始宗教本教题材岩画》,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6月。
(47)古代新疆与西藏的文化交流至少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开始,而且其陶器有明确的传承关系,其中带流圜底的罐型仅此两地互存。胡兴军,《新疆与西藏出土带流罐的比较研究》,新疆文物,2006年第2期。
(49)其中研究者们对某些文字的划痕均有误读,如:第93窟南壁的三个汉字中,最上边的那个字的上面一横显然是后来压上去的;还有131窟的民族古文字也有误读现象。关于该窟的岩画与文字的关系问题,笔者经过反复观察,认为文字在先,岩刻在后。131窟能分辨出的文字四处,其中至少有三处是在岩刻之前所为,因为仔细辨认就会发现它们有先后叠压关系。另外,吴焯先生在1986年《文物》杂志上发表的131窟的文字可能有误,如果发表的文字下面一行对应的古藏文字母没有倒置的话,那么上排文字是否是藏文古写法的可能性就值得怀疑了。
(50)林梅村认为著名的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就是吐火罗先民所为。
(51)王博、傅明方《包孜东、麻扎甫塘古墓与龟兹古国文化》,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39-150页。
(52)陈兆复,《中国岩画》,中国现代美术出版社。
(53)温宿县、拜城县、乌什县,龟兹其它石窟内都有发现。
(54)李永宪,《初论西藏岩画》,王邦秀主编,《2000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398页;此外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早已提出“半月形高地文化传播带”的概念。
(55)岳邦湖等,《甘肃岩画的分布及文化内涵》,《岩画及墓葬壁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33页。
(56)孙新周,《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66页。
(57)陈兆复,《古代岩画》,文物出版社,2002年2月,第174—181页;张亚莎,《西藏的岩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第141—166页。
(58)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重庆出版社,2005年4月,第168—172、194页。
(59)[意]E·阿纳蒂的文章《世界岩画—原始的语言》,载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编《岩画》1,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7页。
(60)伊斯兰教占据龟兹的时间在14世纪中叶,参见李进新《额什丁麻扎和伊斯兰教传人库车考》,新疆龟兹学会编,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6月,第308-321页。
(61)1985年4月4日,笔者在台台尔石窟考察时,特意留心那的岩画情况,发现第13窟主室左壁和后室正壁刀刻山羊4只、还有弓箭等符号多处,形式手法同克孜尔;1988年-1990年的夏天,笔者在库木吐拉临摹壁画时,对库木吐拉石窟的岩画遗存也作了调查,其中窟群区的第11、24、36、38、45、46、58、63、68、70、71等窟都发现有手模、羊、马与骑士、射箭、符号等岩画,形式与手法也多同于克孜尔。
(62)巫新华主编,陈弘法编译,《亚欧草原岩画艺术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289页。
(63)梁振华,《桌子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98年9月,第59页。
(65)盖山林,《世界岩画的文化阐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348页。
(66)这种迹象我们可以通过某些被埋在山坡下或高处的洞窟得到证实,如:谷西区第69窟和新1窟分别是1947年和1973年发现的洞窟,窟内没有手模迹象;谷东区第175-190窟的窟内也没有手模现象,第184窟主室北壁有两个砂岩手模,这是由于约一百年前外国探险队揭走壁画之后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181窟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另外,明显的例子还有第27、131、后山等窟内、窟外都有近些年来新增加的手模,笔者1990年调查的结果与现在的数量就显然不同,如第43—47窟之间的手模显然就是十几年前修栈道之后才可能发生。另参见陈麦《再现性与抽象化——岩画艺术漫谈》,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实用美术(31)岩画专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3月,第18页。
(67)张迎胜,《关于岩画中的手图像》,王邦秀主编,《2000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第421页。
(68)苏北海,《新疆岩画》,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1月,第424—434页。
(69)龟兹的先民吐火罗人就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参见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2页。
(70)E·阿纳蒂的文章《世界岩画—原始的语言》,载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编《岩画》1,第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
(71)[蒙古]Д·迈达尔认为中世纪的岩画属于晚期岩画,《蒙古历史文化遗存》,巫新华主编《亚欧草原岩画艺术论集》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72)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重庆出版社,2005年4月,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