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佛教大小乘因素的史料分析
| 内容出处: |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473 |
| 颗粒名称: | 龟兹佛教大小乘因素的史料分析 |
| 分类号: | K294.5 |
| 页数: | 36 |
| 页码: | 317-25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龟兹佛教大小乘因素的史料分析的基本情况。关于龟兹佛教部派的大小乘问题大概也讨论了近一百年。多数学者认为龟兹地区佛教以小乘佛学为主,但也不否认大乘佛教在那里起过作用。这个结论本来不是问题,但当我们需要使用文献资源解读克孜尔石窟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种选择,究竟应该使用大乘典籍还是小乘典籍?不同的选择往往造成对壁画内容完全不同的阐释。 |
| 关键词: | 龟兹佛教 大小乘因素 史料分析 |
内容
关于龟兹佛教部派的大小乘问题大概也讨论了近一百年。多数学者认为龟兹地区佛教以小乘佛学为主,但也不否认大乘佛教在那里起过作用。这个结论本来不是问题,但当我们需要使用文献资源解读克孜尔石窟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种选择,究竟应该使用大乘典籍还是小乘典籍?不同的选择往往造成对壁画内容完全不同的阐释。事实上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也的确存在一些大乘佛教的因素,文献上也能找到不少证据。对龟兹佛教史料的编辑整理要归功于前辈学者的多方努力①,多数史料曾以不同的方式被部分地选择,然后参与对龟兹问题的探讨。史料总数颇多,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对龟兹文化缺乏了解的窘境。正是因为没有龟兹人撰写的本国史料,那些琐碎的片语只言才得以进入学者们疲惫迷惑的视野。本文在前贤工作基础上偏重于史料分析,试图更清楚地呈现龟兹地区佛教的大小乘因素,同时也是笔者在史料使用新方法上的一次尝试。
下述与龟兹佛教有关的资料中多数显示出大乘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者要试图说明龟兹是一个流行大乘佛教的国家,他可以提供比对手更多的证据。但分析下来,这些证据的有效性要相对弱些。其中部分材料,笔者认为对于龟兹佛教的大小乘问题帮助不大,因而将它们逐次作了排除。
一 第一次排除
第一种情况,有学者认为白姓等于帛姓,白氏帛氏皆龟兹人,故将僧人白延、帛法祖、帛法巨(矩)、帛尸梨密多罗、佛图澄(原姓帛)皆作为龟兹高僧①。
白延(帛延),多谓西域沙门,在曹魏时期在洛阳从事译经活动。《佛祖统记》云“甘露元年(256年),天竺沙门白延至洛阳译《无量》”。《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白延者。不知何许人。魏正始之末(约249年)重译出《首楞严》,又《须赖》及《除灾患经》凡三部”。同书卷七又另载有译师帛延于咸和三年(328年)在凉州翻译《首楞严经》,云“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
帛法祖即帛远,据《高僧传》卷一载“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父威达,以儒雅知名”。
帛尸梨密多罗,《高僧传》卷一载“帛尸梨密多罗,此云吉友,西域人。时人呼为高座。传云:国王之子,当承继世,而以国让弟。闇轨太伯,既而悟心天启,遂为沙门”②,现存《佛说灌顶经》则写着译者为“天竺三藏帛尸梨多罗”。
佛图澄,《高僧传》说他本姓帛,西域人。《释氏稽古略》云“佛图澄和尚,天竺国人也。西晋怀帝永嘉四年至洛阳。自言百岁余”。
我们不否认这些僧人来自龟兹的可能,但应该对此保存警惕。①白姓非帛姓,西来者概取读音近似则译,是否所有法名以白、帛二字开头的僧人都来自龟兹呢?还有待讨论②。霍旭初先生曾经指出早期西域僧人常在名前冠以“佛陀”和“帛”,作为对僧人的尊称。①我个人倾向于赞同这个观点。但笔者首先把上述名单排除在有效材料之外,不仅因为他们中或许有人与龟兹无甚关系,更主要因为在他们的传记中确实没有关于龟兹的具体信息。
二 史料总表
剩下来的史料大约可归纳为26项,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将它们排列下表中。
上述资料或多或少都和龟兹有所关联。有的史料包含大乘的信息,有的包含小乘,有的则两者都有。还有少数材料没有关于大小乘的信息,但包含了比较重要的宗教情报。总计大乘信息占14项,小乘信息占10项。
三 第二次排除
上述史料表格中第1、第2、第3、第16、第20、第21号,共六项材料被笔者作为不可靠史料,第二次排除。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如下,以方便以后的研究者。
(1)公元284年,来自于龟兹副使美子侯之《阿惟越致遮经》在敦煌被翻译,此经属大乘法华部。
《出三藏记集》“阿惟越致遮经”记载:“太康五年(西晋284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美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①。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闻知。”
(2)公元286年,龟兹居士帛元信校参大乘《正法华经》和《渐备经》,可能在长安。又参与过大乘《须真天子经》翻译。
《出三藏记集》卷七载:“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共劝助欢喜。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元年二月六日重复。”②
《出三藏记集》卷八载:“《渐备经》护公以元康七年出之。..然出经时人云:聂承远笔受,帛元信、沙门法度,此人皆长安人也。以此推之,略当必在长安出。”
《出三藏记集》载:“《须真天子经》太始二年(按:或许为公元266年之‘泰’始二年)十一月八日于长安青门内白马寺中,天竺菩萨昙摩罗察口授出之,时付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
(3)公元328年(或咸安三年373年),龟兹王世子帛延在凉州翻译大乘经典《首楞严经》及《须赖经》等经。
《出三藏记集》卷七载:“咸和三年①,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支优婆塞支施仑,手执胡本。支博综众经,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业大乘学也。出《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时在凉州州内正听堂湛露轩下集。时译者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受者,常侍西海赵潚、会水令马奕、内侍来恭政,此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德。时在坐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凉州自属辞,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4)公元6世纪晚期,异僧从龟兹至东土,鉴《法华经》。
唐惠详《弘赞法华传》②载:恭(严恭)因发愿造法花百部..于是大起房宇为经之室。庄严清净,供给丰厚,书生常数十人。扬州道俗,共相崇敬..恭甞一时在经堂北,有一异僧,年可八十,来告恭云:闻君造经,愿请一部。又承未有提婆达多品,今留此品,可于宝塔品后安之。贫道,从龟兹国来,今往罗浮山去。得经一部,粗略披寻。仍留金一鉼,重三十斤,用入法花,来岁夏间当附物。又云:向见普贤品内呪少一句语,宜觅足之。言毕而退。恭寻后看,莫知所在。后有捿霞寺禅师宝恭,送零落法花经五十许卷,使恭成就,拟用流通。有一卷第七,是宋元嘉二十九年(452)宋懿所造,校普贤呪,果少婆罗帝三字,是第十六句。自后写经,仍依足之。
这段故事从陈太建初(约569年),严恭年弱冠时经商奇遇故事开始,讲到他信奉“法华”后的种种神迹。此段龟兹异僧故事较奇,关键是他从何处得来经书,文献中并无交代。
(5)公元7世纪下半叶,龟兹国人达磨跋陀(法贤)学习法华经。唐僧详《法华传记》①“龟兹国沙门达磨跋陀十七”载:
达磨跋陀,唐云法贤,龟兹国人也。天性聪明,具通三藏。粗识外国言词,谓小为极,自生贡高,陵辱摩诃衍众。时有巡礼沙门,名曰须梨耶,诵达法华六千偈无脱法,对法贤论所诵幽致。贤识三藏单浅,归心大乘,从须梨耶,诵达法华,每日五遍为业。敬法夜叉,守护此人。又每夜草坊现异光,人谓失火,谘法贤。答曰:“四大天王,番番来护光明。”临终之时,语徒众言:“昔执小典为极,如执瓦石为金宝。今翫法华得真金也,以三年讽诵面见普贤,入正位得不退记。汝等专讽持此经,期正位不过三生。”即注遗书而卒,如入禅定。于遗身骨上起塔。夏雨盛降,雨不能湿塔。鸟类群飞,不近塔边。凡见闻者,礼拜供养如市而已。
同书“浔阳处女十七”故事中记载了法贤到浔阳的时间,云:“唐总章年中(668~670年),外国沙门,名达磨跋陀,唐云法贤,无奈何事,来至浔阳。容仪挺特,色貌端正。诵法华等大乘经凡三万偈也,音声爱(按:当为“受”字)雅众所乐。”
达磨跋陀临终时云:“昔执小典为极,如执瓦石为金宝。今翫法华得真金也。”据此或可推敲,他本来在龟兹所学应是小乘,在东土接触《法华经》后改宗大乘。
(6)唐代,龟兹国僧若那翻译《佛顶尊胜陀罗尼别法》。
《佛顶尊胜陀罗尼别法》卷首写道:“龟兹国僧若那奉诏译。口问笔缀,授与崇福寺僧普能,因即流布。”
虽然上述资料都涉及到龟兹,但使用时需要特别小心。和第一次被排除的情况类似,这些资料本身往往只透露了汉地的相关情报,龟兹的信息非常有限,很难用来说明龟兹问题。比如常见的一种情况佛经译师来自龟兹,但有时译师的翻译活动并不能代表其本人的宗教态度。如霍旭初先生所指出,有时译师来自龟兹,经本却得自汉地①有时甚至译者仅仅是龟兹人,而非僧人。翻译活动的属性要更多归因于发起翻译的功德主。如甘露三年在白马寺翻译《首楞严经》的龟兹王世子帛延应凉州刺史张天锡的要求翻译《首楞严经》,还有太康七年参校《正法华经》的龟兹居士帛元信。翻译书籍的要求可能来自其它人,又或者有学术上的需要,译师仅仅是从事翻译工作而已。中国最大的两个译师,鸠摩罗什和唐玄奘都翻译了大量属于不同派别的佛经。因此汉地译经活动不能用来判断龟兹地区的宗教属性。
另外一种情况是僧人的宗教态度比较明确,并且可能原籍龟兹。但是,除非我们能够明确其所受教育(或资源,如携带入汉地的佛经)来自龟兹,否则也很难用来说明问题。以鸠摩罗什为例,他本来在龟兹接受的是纯粹的小乘教育,直到第二次离开龟兹,在中亚游历才逐渐接受了大乘佛教,最后到汉地传法。我们不能因为鸠摩罗什本身信奉大乘,就简单地推导出其原籍地区也流行相同的宗教。至于他后来回到龟兹传法,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后文会有交代。
我们说上述材料“不可靠”并不是说史料的真实性全部值得怀疑。而是由于上述事件全部发生在汉地,其提供的龟兹情报相当有限,用作龟兹宗教属性研究时可能带有较多主观臆测。在这一点上它们无法成为有效的信息来源。
四 重点史料分析
余下的情报按时间顺序分别排列如下。尽管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依然可能存在于这些材料中,但得益于前辈学者的研究,对一些情报的分析已足够透彻,如鸠摩罗什问题,故只摘录其重要情节;重点对其它一些疑点问题进行讨论。
(1)公元350~352年,鸠摩罗什七至九岁在龟兹随母出家,学习小乘《毗昙》。后出游罽宾、沙勒诸国学习小乘。公元356~363年,鸠摩罗什十三至二十岁,随母返回龟兹,以小乘学识著名。公元363年,鸠摩罗什二十岁,受戒于龟兹王宫,大概经师是佛图舌弥,律师为卑摩罗叉①。当时卑摩罗叉(梵语Vimalaksa)正在龟兹宣讲有部广律《十诵律》。鸠摩罗什在龟兹思想发生转变,开始对大乘佛教感兴趣。
《出三藏记集》卷十四载:“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口诵日得千偈。……诵毘昙……。什年九岁,进到罽宾,遇名德法师盘头达多……遂诵杂藏、中阿含、长阿含,凡四百万言。……至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进到沙勒国。……什于沙勒国,诵阿毘昙、六足诸门、增一阿含。及还龟兹名盖诸国。时龟兹僧众一万余人,疑非凡夫,咸推而敬之,莫敢居上。”
《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传”载:“卑摩罗叉,此云无垢眼,罽宾人。沈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节成务。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及龟兹陷没乃避地焉。顷之闻什在长安大弘经藏,又欲使毘尼胜品复洽东国,于是杖锡流沙冒险东入。以伪秦弘始八年达自关中,什以师礼敬待。”
(2)约公元370~384年,鸠摩罗什在龟兹宣讲大乘。公元370年鸠摩罗什约二十七岁,在第二次旅行学习大乘佛法后回到龟兹,钻研大乘,后在龟兹及周边诸国宣讲大乘。公元384年吕光破龟兹,虏走鸠摩罗什②。
《出三藏记集》载:“后从佛陀耶舍学十诵律,又从须利耶苏摩谘苏禀大乘①。乃叹曰:吾昔学小乘,譬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矣。于是广求义要,诵中百二论。于龟兹帛纯王新寺得放光经,始披读,魔来蔽文,唯见空牒。什知魔所为,誓心逾固。魔去字显,仍习诵之。后于雀梨大寺读大乘经……停住二年,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后往罽宾,为其师盘头达多具说一乘妙义。师感悟心服,即礼什为师,言:我是和上小乘师,和上是我大乘师矣。西域诸国伏什神俊,咸共崇仰,每至讲说,诸王长跪高座之侧,令什践其膝以登焉。”
(3)公元371~372年,中土僧人僧纯自龟兹著名阿含学者佛陀舌弥许得“比丘尼大戒”等戒法,同时也见到大乘僧鸠摩罗什。
《出三藏记集》卷二载:“比丘尼大戒一卷。右一部,凡一卷。晋简文帝时(371~372年),沙门释僧纯于西域拘夷国得胡本。到关中,令竺佛念、昙摩持、慧常共译出。”
同书卷十一记:“……僧纯于丘慈佛陀舌许得戒本。……卷中间尼受大戒法后记云:……。末乃僧纯、昙充拘夷国来,从云慕蓝寺于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剑慕法。遂令佛图卑为译,昙摩侍传之。乃知真是如来所制也。……又授比丘尼大戒,尼三师教授师,更与七尼坛外问内法。”比丘尼大戒卷后又记:“秦建元十五年(379年)十一月五日,岁在鹑尾。比丘僧纯、昙充从丘慈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授大比丘尼戒仪及二岁戒仪”云云。概为僧纯回到汉地开始推行戒法的时间。
《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摘录了《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拘夷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五十僧),剑慕王新蓝(六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
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或易蓝者。未满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
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乃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
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输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
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比丘尼外国法不得独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无师一宿者辄弹之。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舌弥乃不肯令此戒来东,僧纯等求之至勤,每嗟此后出法整唯之斯戒,末乃得之。……
(4)公元393年,龟兹高僧昙摩跋檀应请口头翻译经典。
《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①卷末载:
巍巍十方佛,国土甚清明;七宝为庄严,妙香栴檀馨;悉纯诸菩萨,无有二乘名;惟说不退转,般若道之英;巍巍十方佛,三世道之珍;其闻信乐者,疾成无上真;游于菩萨道,坚住不退还;所生常见佛,遭值诸天尊;巍巍十方佛,三界之导师;至心怀恭敬,信乐无狐疑;所生常端正,颜容甚花晖;辩才慧独,愿礼天人师。
麟嘉六年(393年)六月二十日,于龟兹国金华祠演出此经。译梵音为晋言。昙摩跋檀者,通阿毘昙,畅诸经义,又加究尽摩诃衍事,辩说深法,于龟兹国博解第一。林即请命出此经。檀手自执梵本,衍为龟兹语经。当如是时,道俗欢喜,叹未曾有,竞共讽诵,美其功德。沙门慧海者,通龟兹语,善解晋音。林复命使译龟兹语为晋音。
表面看来这段话好像是在讲《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的翻译过程,其实不然。此经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卷首注明为“元魏天竺三藏吉迦夜译”,可与佛教史籍相关材料吻合。《开元释教录》载:“《称扬诸佛功德经》三卷,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载:“《称扬诸佛功德经》一部三卷。右西晋竺法护译。出长房录。《称扬诸佛功德经》一部三卷,右后魏沙门吉迦夜于北台译。出长房录。《称扬诸佛功德经》一部三卷,右秦弘始七年罗什于长安译,出长房录。”查此经其它同本异译,未见昙摩跋檀所译者。
此经上、中、下三卷,原本目次井然有序。上卷卷首标题“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上”在卷末会重复一次。中卷、下卷亦然。这种编目方法是汉译佛经的惯例。《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下结尾句云“一切大会皆大欢喜,前为佛作礼而去”,整部经书从结构上来说已经完全结束。作为目录使用的语句“《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下”按照正常的格式使用了两次,一次在下卷开头,一次在下卷结尾。但很奇怪,在此经中却使用了三次,即在全书结尾处又多使用了一次,其间插入了上文所摘抄的两段文字①。这两段文字——“巍巍十方佛”之五言偈诵,和“龟兹国金华祠译经故事”都来得异常突兀,且前后矛盾。翻译的“译者”昙摩跋檀、“时间”麟嘉六年(393年)和“地点”龟兹国和正本经文署名之译者“元魏天竺三藏吉迦夜”全无半点关系。这段文字前面的五言偈诵,经笔者检索,系出自《六菩萨亦当诵持经》五言长诵中的一段②,所以后面的两篇文字肯定不属于原经,可能是书籍抄录刊印时被错误加到《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里面来了。则昙摩跋檀所译经典究竟是《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六菩萨名经》还是别的什么经典概莫能知也。但这段文字记录了龟兹高僧应汉人要求翻译经书的情况,仍然有参考价值。
(5)公元400年,法显在丝路中道龟兹焉耆一带旅行,见闻当地小乘佛教。
《高僧法显传》载:“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鄯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法显得符行堂公孙经理,住二月余日。于是还与宝云等共合。乌夷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法显等蒙符公孙供给,遂得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
法显游记中所说的“乌夷”是什么地方?慧琳《一切经音义》谓乌夷即今焉耆,过去之阿耆尼国。云:“阿耆尼国——雨碛之西第一国也,耆音祇,古曰婴夷,或曰乌夷,或曰乌耆,即安西镇之中是其一镇,西去安西七百里。汉时楼阐、善善等城皆此地也,或迁都改叭,或居此城,或住彼城,或随主立名事,互相吞灭,故有多名,皆相邻近,今或丘墟。”但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西方汉学界有过激烈争论。起先是哇特斯考订乌夷为焉耆,列维1913年着文考订乌夷为龟兹,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龟兹有时被称为拘夷,和乌夷有些类似。文曰:“纪元520年刊之《出三藏记集》,载有鸠摩罗什时代龟兹佛教信行之事。所载国名为‘拘夷’。..纪元860年刊《酉阳杂俎》,亦志有‘拘夷’国名。国之北山有陀便水,服之发落,此事与《魏书》所载龟兹国故事,又略相合,故知拘夷为龟兹也..由此拘夷国名,吾人又忆及纪元四百年时法显所经之乌夷。”第二个理由是根据法显所述之行程推算,认为龟兹正好在高昌到于阗的转折处,比较符合龟兹的地理位置。文曰:“考《佛国记》,法显等从鄯善‘西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又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国’。考其行程,乌夷决为今之库车,昔之龟兹。..由焉耆不能‘直进西南行’到今之和阗,古之于阗也。”①后来伯希和1936年撰文反驳列维,考定古,代“焉”字书法与“乌”字相似,容易混淆,导致焉字被误写为乌,遂有焉耆被写作“乌耆”②。
(6)公元400年前后,佛陀耶舍在龟兹传法数年。
《出三藏记集》卷十四“佛陀耶舍传”载:
佛陀耶舍..罽宾人也。..至年十五,诵经日得五六万言。..十九,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乃从其舅学五明诸论,世间法术,多所通习。二十七方受具戒。以读诵为务,手不释牒。..后至沙勒国..太子悦之,仍请宫内供养,待遇隆厚。罗什后至,从其受学阿毘昙、十诵律,甚相尊敬。什随母东归,耶舍留止。..时符坚遣吕光攻龟兹。龟兹王急求救于沙勒,王自率兵救之。..王归,具说罗什为光所执,乃叹曰:我与罗什相遇虽久,未尽怀抱。其忽羁虏,相见何期。停十余年,王薨。因至龟兹,法化甚盛。时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粮欲去,国人请留,复停岁余。语弟子云吾欲寻罗什。..乃取清水一钵,以药投中,咒数千言,与弟子洗足,即便夜发,比至旦行数百里..行达姑臧,而什已入长安。佛陀耶舍在公元384年鸠摩罗什被吕光虏走之后,又在沙勒停了
十多年才去龟兹。故可推测他到达龟兹的时间在公元395年到405年之间。他后来想离开龟兹到姑臧找鸠摩罗什,但到达姑臧时,鸠摩罗什已经去了长安。鸠摩罗什到长安是公元401年,陈世良推测佛陀耶舍到长安时是公元410年③,另一说为公元408年④。故佛陀耶舍在龟兹的时间大约在公元400年前后的几年。佛陀耶舍十九岁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又通法术,看来在大小乘佛学上都有一定造诣。但鸠摩罗什跟随他学习阿毘昙、十诵律,可能是因为他擅长论和律的缘故。尽管后来传说他返回罽宾弄了部《虚空藏经》,但事实上佛陀耶舍到长安后的主要成就是翻译了昙无德部的律藏《四分僧戒本》、《四分律》,此外就是《长阿含经》。应该说佛陀耶舍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小乘方面。至于他在龟兹传法的具体情况,没有直接的文献描述。
(7)约4世纪末5世纪初,罽宾云游禅僧昙摩密多受到龟兹王礼遇。
《高僧传》载:“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博贯群经,特深禅法,所得门户极甚微奥,为人沈邃有慧解,仪轨详正,生而连眉,故世号连眉禅师。少好游方,誓志宣化。周历诸国,遂适龟兹。未至一日,王梦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当入国。汝应供养,明旦即敕外司:‘若有异人入境必驰奏闻’。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延请入宫。遂从禀戒尽四事之礼。蜜多安而能迁,不拘利养,居数载,密有去心。神又降梦曰:‘福德人舍王去矣’。王惕然惊觉。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进到敦煌。……顷之复适凉州。……以宋元嘉元年(424年)展转至蜀,俄而出峡止荆州。……顷之沿流东下至于京师。……初密多之发罽宾也,有迦毘罗神王卫送。遂至龟兹,于中路欲反,乃现形告辞密多曰:汝神力通变自在游处,将不相随共往南方。语毕即收影不现。遂远从至都,即于上寺图像着壁。迄至于今犹有声影之验,洁诚祈福莫不享愿。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
昙摩密多《出三藏记集》谓昙摩蜜多,然传与《高僧传》所载相同。其传曰:以元嘉十九年(442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故可推昙摩密多生于公元356年。又宋元嘉元年(424年)已经从敦煌凉州展转到了四川。大概停留龟兹之数载约在4世纪末5世纪初之际。他进入汉地以后宣讲禅法,翻译了五门禅经要用法,以及《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虚空藏菩萨经》、《禅密要经》等大乘佛经。然其在龟兹作为未见记载。
(8)约公元412年,大乘僧昙无谶至龟兹,不为当地小乘佛教接纳。
《出三藏记集》卷十四载:“昙无谶,中天竺人也。……十岁与同学数人读咒,聪敏出群,诵经日得万余言。初学小乘兼览五明诸论。讲说精辩莫能詶抗。后遇白头禅师共谶论议。……禅师即授以树皮涅槃经本。谶寻读惊悟,方自惭恨,以为坎井之识,久迷大方。于是集众悔过,遂专业大乘。年二十所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谶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王怒捕谶。谶悔惧诛,乃赍大涅槃经本前分十二卷,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奔龟兹。龟兹国多小乘学,不信涅槃,遂至姑臧①,止于传舍。……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请令出其经本。谶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翻为汉言,方共译写。是时沙门慧嵩、道朗独步河西,值其宣出法藏,深相推重,转易梵文,嵩公笔受。”
《涅槃经》大乘有之,小乘亦有之。然中天竺大乘咒师昙无谶所学所译为大乘者也。他本来想持《大涅槃经》、《菩萨戒经》等大乘经卷到龟兹传法,无奈龟兹的情况很不理想,“多小乘学,不信涅槃”,他只能离开龟兹去姑臧,在那里得到蒙逊的支持才呆下来。昙无谶到姑臧后,数次因为经本不全,回到于阗搜寻,而不是更近距离的龟兹,也可应证那里大乘典籍比较缺少的情况。《高僧传》卷二讲到昙无谶被蒙逊谋杀,死时“春秋四十九,是岁宋元嘉十年(433年)也”。可推其生于公元385年,又年二十时为公元404年,他此时尚在中天竺。又据《高僧传》他在姑臧译经,“伪玄始三年(414年)初就翻译”,减去学习汉语之三年,可推昙无谶离开龟兹到姑藏的时间大概在玄始元年①(412年)或略早②。
(9)公元5世纪中后期,高昌法惠往龟兹国求法,醉酒得果。反映小乘观念。梁宝唱撰《比丘尼传》“伪高昌都郎中寺冯尼传”载:
冯尼者,本姓冯,高昌人也,时人敬重,因以姓为号。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菜蔬一食,戒行精苦。烧六指供养,皆悉至掌。诵大般涅槃经,三日一遍。时有法惠法师,精进迈群,为高昌一国尼依止师。冯后忽谓法惠言:‘阿阇梨③未好,冯是阇梨善知识。阇梨可往龟兹国金花帐下直月闻当得胜法。’④法惠闻而从之,往至彼寺见直月。直月欢喜,以蒲萄酒一升与之令饮。法惠惊愕:我来觅胜法,翻然饮我非法之物。不肯饮。直月推背急令出去。法惠退思:我既远来,未达此意,恐不宜违。即顿饮之。醉吐迷闷,无所复识。直月便自他行。法惠酒醒,自知犯戒,追大惭愧,自槌其身,悔责所行,欲自害命。因此思惟得第三果。直月还问曰:已得耶?答曰:然。因还高昌。未至二百里,初无音信。冯呼尼众远出迎候。先知之迹,皆类此也。高昌诸尼莫不师奉。年九十六,梁天监三年(504年)卒。
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5世纪中后期,即冯尼出家的公元438年到其去世的504年之间。同样一段故事也收录在宝唱另外一本着作《名僧传》中。该书在汉地已经不传,但由于其流传到日本,故而在《大日本续藏经》中得以保存。据此书“法惠传”载,法惠去世于齐永元年,比冯尼去世时间略早。
《大般涅槃经》如前所述,有大乘者如北凉昙无谶之译本,凡四十卷;亦有小乘者如东晋法显之译本,凡三卷。高昌冯尼三日一遍,所诵之经属于大乘还是小乘难以判别。不论高昌此时流行大乘还是小乘,冯尼要法惠去龟兹求胜法,终究是对现状不满。有学者根据直月使醉法惠之教法,把直月当作顿悟派禅宗大师。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谈到:“龟兹高僧直月者,其所行之法,即类于中国所谓达磨禅者也,法惠既受其教,当亦于高昌弘扬禅风。”①。
《名僧传》“法惠传”虽然在法惠出家事迹中讲到他“修学禅律”,可是结尾却又讲到他从龟兹返回高昌“大弘经律”,其实许多佛教文献中的“禅”、“律”等词汇往往是虚指,未必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名僧传》中第十九卷专门记录外国禅师,第二十卷专门记录中国禅师,而“法惠传”却被编排在第二十五卷索苦节中,足见这段故事的主题并非宣传禅师。
从名字和行事上看,这位直月的确颇有中国南禅大师呵佛骂祖之风范。但直月可能不是僧人法号,而是寺僧中某种职务称号。如北宋赞宁撰《大宋僧史略》载:“魏孝文以皇舅寺僧义法师为京邑都维那,则勅补也,是乃昭玄都维那耳。今寺中立者,如玄畅勅为总持寺维那是也。次典座者,谓典主床座。凡事举座,一色以摄之,乃通典杂事也。或立直岁则直一年,或直月、直半月、直日,皆悦众也,随方立之。”小乘律藏《摩诃僧祇律》中常常讲到直月负责管理寺院伙食的情况,如云“若比丘为僧作直月,行市买酥油籴米豆麦面麨糒,求一切物时,作不净语者,犯越比尼罪”、“若直月及监食人欲知生熟醎淡甜酢,得着掌中舌舐,无罪”等等。笔者以为前述“法惠”事迹可能与禅宗无关,而仅仅是一个传奇故事,借直月与酒,文学性地嘲讽戒律清规,反映了对禁欲制度的置疑。而法惠经醉酒获得第三果,又正是小乘佛学的概念——声闻四果之“不还果”①故而也折射出龟兹小乘佛教的面貌②。
(10)约公元446~452年兹王礼待法朗。《高僧传》卷十宋高昌释法朗传载:
释法朗③,高昌人。幼而执行精苦,多诸征瑞,韬光蕴德,人莫测其所阶。朗师释法进亦高行沙门,进尝闭户独坐,忽见朗在前,问从何处来。答云:“从户钥中入”。云:“与远僧俱至,日既将中,愿为设食”。进即为设食,唯闻匕钵之声,竟不见人。……至魏虏毁灭佛法,朗西适龟兹。龟兹王与彼国大禅师结约:“若有得道者至,当为我说,我当供养”。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圣礼。后终于龟兹,焚尸之日,两眉涌,龟,泉直上于天。众叹希有,收骨起塔。后西域人来北(金陵本“北”作“此”)土具传此事。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到兴安元年(452年)十二月,文成帝上台才初复佛法。故推法朗赴龟兹的时间大约在此期间。
虽然文字中谈到大禅师,但修禅实在是各个部派的通行法则。又《高僧传》有“习禅”之卷,却把这个故事编在“神异”卷下,用意非常明显,只作为僧人神迹之记载也。这类故事可信度最低,故而宗教方面有用的信息并不太多。
(11)约公元420~479年之刘宋时期,龟兹法丰寺弟子书写《法华经》。疑伪。
唐僧详《法华传记》“宋释法丰”载:“释法丰,姓竺氏。敦煌人,往适龟兹,修理一寺。触事周办,时因号为法丰寺,既久专寺任。稍恃其功力,出内取与,颇乖斟酌,辄减省僧食,令不周足。久之遂亡,生饿鬼中,常在寺院,至初夜后,作饿驰鸣,巡房声叫。弟子宝慧闻而叹曰:是我师声。因问那尔。丰曰:由减僧食料,受饿鬼苦,苦剧难堪,愿见济度。弟子书写《法华经》,广为斋忏,得生清胜”。
《法华传记》大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故事后面注言出自《自镜录》。查唐怀信《释门自镜录》,果有“宋法丰减僧食死作饿鬼事”一篇。载:“释法丰姓竺氏,敦煌人,往适龟兹,修理一寺。触事周辩,时因号为法丰寺,既久专寺任。稍恃其功力,出内取与颇乖斟酌,辄减省僧食,令不周足。久之遂亡,堕饿鬼中,常在寺院,至初夜后,作饿驼鸣,巡房声叫。弟子宝慧闻而叹曰:是我师声。因问那尔。丰曰:由减僧食料,受饿鬼苦。苦剧难堪,愿见济度。弟子广为斋忏,得生清胜”。
这个故事《释门自镜录》所记和《法华传记》几乎完全一致,唯《法华传记》多出关键的“弟子书写《法华经》”一句,概为宣讲法华,所加添笔,殊不可信。
(12)公元540年,汉僧云启和天竺僧那连耶舍相逢于龟兹,合译禅宗《佛祖传法偈》。疑伪。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载:
《佛祖传法偈》,按禹门太守杨衒之《铭系记》云,东魏静帝兴和二年庚申,西魏文帝大统六年,梁武大同六年(540年),高僧云启往西域求法,至龟兹国,遇天竺三藏那连耶舍欲来东土传法。云启曰:佛法未兴,且同止此。遂将梵本译为华言。云启去游印土。那连亲将至西魏,值时多故,乃入高齐,以宣帝礼遇甚厚,廷居石窟寺,以齐方受禅。未暇翻译别经,乃将龟兹与之合所译《祖偈因缘》传居士万天懿。……
此文所云之《佛祖传法偈》应该是指《景德传灯录》所录之诸佛祖偈语。相传继承自唐《宝林传》①,禅宗理论家以记录这些偈语的方式书写了禅宗二十八祖谱系,从“七佛偈”②开始一直到讲到菩提达摩。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成书于至正元年(1341年),叙述释迦法统、禅宗诸祖事迹,以及各朝佛教史实直至元代。该书以禅宗为佛教正统,从“七佛偈”开始,前面数卷关于禅宗二十八祖之内容全部来自《景德传灯录》。故而在“七佛偈”结尾讲到“《佛祖偈》翻译乃高僧云启一同天竺那连耶舍三藏于龟兹国译出。本末载于梁大同六年”。后来又在该年事迹中讲出上述故事,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看似天衣无缝。
那连耶舍(490~589年),又译为那连提黎耶舍,在《续高僧传》中有传,然未题记龟兹又或云启之事。考其事迹,亦与禅宗没有多大关系。他翻译过《月灯三昧经》、《大悲经》、《施灯功德经》、《大集须弥藏经》、《大方等日藏经》、《大方等大集月藏经》、《菩萨见实三昧经》、《阿毗昙心论》等经,后有弟子彦琮(557~610年)为其作传,未见有翻译《祖因缘》之记载。宋景德元年(1004年)道原撰写《景德传灯录》中记载此事则十分含混,云:“禅于唐达磨至中国,今取正宗记为定。盖依梁僧宝唱《续法记》,昔那连耶舍与万天懿,译七佛至二十八祖传法事。梁简文帝,因使臣刘悬运往北齐取其书,诏宝唱编入《续法记》也。”
道原的著作中并无那连耶舍龟兹译经之说。那么比道原晚三百多年,念常为什么要在重新编写《景德传灯录》的时候加入这条信息呢?这和当时中国禅宗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关。自唐成熟的中国禅宗在唐末宋初发展到又一个高峰。但古代中国是一个凡事都要讲法统的社会,类似项羽称楚,刘备彰汉的事迹数不胜数,就连入主中原的北魏鲜卑都要标榜自己是黄帝后人,翻开《魏书》,第一句话就是“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禅宗这个本来是在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宗教,也需要追根溯源,建立一张超级巨大的族谱来显示其“正宗”。他们认为汉地禅宗传统起源于6世纪进入东土的天竺僧人菩提达磨,更通过菩提达磨往前追述,搜罗了其余二十七位古代印度佛教名人作为禅宗的印度血统。这二十八位祖师爷的第一和第二号人物是释迦弟子摩诃迦叶与阿难,这样禅宗也就和释迦佛以及过去诸佛都扯上了关系。但是禅宗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宗派。尽管充分引入了旧有的佛教传法谱系,禅宗的新谱系仍然与过去传入汉地的佛教祖谱谱系相矛盾,因而遭到质疑。如北魏吉迦夜、昙曜合译的《付法藏因缘传》就只讲了二十三祖——释尊入灭后,迦叶、阿难等二十三位印度祖师付法相传,到最后一祖师子尊者结束①,而没有后来被禅宗学者添加的婆须蜜、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和菩提达摩五人。那么这两套谱系究竟哪套能够代表正宗呢?追究这个问题成为后来汉地佛教的一个学术热点,其社会根源其实是禅宗日益繁盛,给其它教派造成很大压力,从而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坚持旧谱系的人很容易找到理由,因为他们所持的经典比《景德传灯录》等书籍古老得多,而《景德传灯录》新建谱系也确实意在自我标榜,难逃造伪之嫌。新谱系的支持者当然都是虔诚的禅宗信徒,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必须找到理由来说明新谱系的合法性,这就要对其翻译过程有所交代,以说明它是来自于印度本土的正宗原典②。这样一来,关于《佛祖传法偈》的流传过程,就有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念常声称,根据北魏杨衒之铭记,此偈是汉僧云启和天竺僧那连耶舍相逢于龟兹时所合译,然后被那连耶舍带到了汉地。云启从汉地出发去西域,那连耶舍是北印度乌场国人,从西往东,或许如念常所云路过龟兹。那么此偈只能是由那连耶舍携带而来。但比念常早约两百年的郑昂却不这么认为。南宋绍兴壬子年(1132年),郑昂在“景德传灯录跋”中讲到:“或者犹疑《佛祖传法偈》无传译之人,此夏虫不知春秋也。佛祖虽曰传无传,至付授之因岂容不知?又达磨具正遍知,华竺之言盖悉通晓。观其答问,安有传译哉?”他当然也是站在《景德传灯录》的立场,认为禅宗初祖达磨通汉语,口授亲传无须翻译。这种说法本来颇为可信。可是如果是菩提达磨把自己编入二十八祖,便少了几分排场,过去诸多演说也就会被其它部派传为笑柄,因而此说在禅宗内部影响不大。又郑昂称《景德传灯录》原为拱辰所著而为道原所获尔,意在攻云门而张临济,遂使其跋文不足为信,已为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四所考①。
11世纪的北宋契嵩对待这个问题比念常和郑昂都显得专业,他为了论证这个问题而完成长篇大着《传法正宗论》二卷,其中也提到那连耶舍,载曰:“又云,有罽宾沙门那连耶舍者,以东魏孝静之世至邺,而专务翻译。及高氏更魏称齐,乃益翻众经,初与处士万天懿译出《尊胜菩萨无量门陀罗尼经》,因谓天懿曰:西土二十七祖亦尊此经。复指达磨其所承于般若多罗,谓此土继其后者法当大传。乃以谶记之。复出已译祖事,与天懿正之。而杨衒之《名系集》亦云:‘耶舍尝会此东僧昙启者,于西天竺共译祖事为汉文。译成而耶舍先持之东来’。然与支疆之所译者,未尝异也。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其出于支疆之所译也。益至乎二十七祖与二十八祖达磨多罗,西域传授之事迹者,盖出于耶舍之所译也。推《宝林》、《传灯》二书,至于昙曜其始单录之者,其本皆承述于支疆耶舍二家之说也。”
契嵩认为,二十八祖的谱系分两次完成,一次是支疆翻译了自七佛开始到二十五祖的谱系,但到那连耶舍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七祖。那连耶舍到东土后,追捧先来汉地传法的菩提达磨,遂自凑成二十八祖。
对比《佛祖历代通载》与《传法正宗论》对同一段历史的记载,念常文献指示那连耶舍同昙启共同翻译佛祖谱系的地点是龟兹,而按照契嵩的引证,则是西天竺。翻译经典的过程也不一样。仅从时间上说,晚期文献的可靠性当然更值得怀疑。然而契嵩的结论是否正确呢?《续高僧传》云那连耶舍为“北天竺乌场国人”(即唐玄奘游历之乌仗那国,契嵩说他是罽宾人也不算错),菩提达磨则是南天竺人。菩提达磨所持的禅法与后来弘忍的东山法门本来大相径庭①,而那连耶舍身上更看不出与禅宗有何关系,他没有动机为也许一个世纪以后才发展成熟的部派代言。根据《续高僧传》,那连耶舍至少在天保七年(556年)已经在邺城定居,而契嵩更提到“以东魏孝静之世至于邺都”他到达中原的时间距离菩提达磨的时代是非常接近的。虽然菩提达磨,于公元535年已经去世,但和那连耶舍仍然是同代中人。就算那连耶舍对菩提达磨欣赏有嘉,也不至于夸张到要将他推上祖谱神坛。事实上一直到唐道宣在《续高僧传》中为菩提达磨作传,故事简略平淡,尚没有什么二十八祖之说。又,契嵩和念常都声称杨衒之对此事有过记载。杨衒之确实在《洛阳伽蓝记》中提到过菩提达磨。在对洛阳永宁寺巨塔极尽赞叹之后,杨衒之写道:“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磨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非常明显,这位被后世禅宗信徒神话般供奉为祖师的菩提达磨,在杨衒之的笔下不过是一个倾倒于我中华文明的移民而已。最后一个疑点,根据契嵩的描述,那连耶舍增加的第二十八祖是“达磨多罗”,而不是“菩提达磨”。事实上是契嵩把把东晋慧远所云萨婆多部达磨多罗与北魏萧梁时代的禅宗达磨多罗混淆了①。至此可知,契嵩之说——那连耶舍立二十八祖菩提达磨,断不可信。而念常所云那连耶舍龟兹译偈之事,以讹传讹,谬之千里矣。
(13)大约公元585年前后,达摩笈多在龟兹王寺停住两年,龟兹王笃好大乘。唐道宣(596~667年)撰《续高僧传》载:
达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贤豆罗啰国人也,刹帝利种,姓弊耶伽啰。..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弟耶(按:依止师)佛驮笈多,此云学密;阿遮利夜(按:轨范师),名旧拏达多,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为普照,通大小乘经论,..笈多受具之后仍住三年。就师学问。师之所得略窥户牖,后以普照师为咤迦国王所请,从师至彼经停一载。..于是历诸大小乘国及以僧寺。..又至沙勒国,同伴一人复还本邑,余有三人停在王寺,谓沙勒王之所造也。经住两载,仍为彼僧讲说破论,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又为讲如实论,亦二千偈,约其文理乃是世间论义之法。又至龟兹国,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系心东夏,无志潜停,密将一僧间行至乌耆国,在阿烂拏寺,讲通前论。又经二年,渐至高昌,客游诸寺。其国僧侣多学汉言,虽停二年,无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载。..延入京城,处之名寺,供给丰渥,即开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华言略悉,又奉别敕,令就翻经。移住兴善,执本对译,允正寔繁,所诵大小乘
论并是深要。
达摩笈多在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十月抵达长安,减去路上停留的五、六年时间,他在龟兹的时间可能在585年左右。达摩笈多传中清楚地讲到当时龟兹国王笃好大乘,达摩笈多达到汉地以后也翻译了不少大乘经典。很早就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时龟兹流行大乘①,但达摩笈多的翻译活动多系奉别敕令。从其传记来看,他原来追随的老师普照通大小乘经论,而他本人到达东土后,所诵大小乘论并是深要,故而笔者认为达摩笈多应当属于那种大小乘兼修的僧人,旅行时随机应变,根据当地需要来宣讲。因此笃好大乘的龟兹国王和龟兹僧众恐怕应该区别对待。
达摩笈多在沙勒、龟兹、焉耆三国连续讲诵《破论》和《如实论》。这三地都长期流行小乘,那么他所讲的经典属性就变得非常关键。《破论》和《如实论》究竟是大乘还是小乘经典呢?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破论》概破对手学说之论,佛教与其它宗教之间、大小乘佛教之间,以及小乘佛教不同部派间都常有这样的破论,仅凭名字难以判别具体属于哪一派。但根据全文“为彼僧讲说破论,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此“二部”破诸外道,可能指上座部和大众部,它们是后来诸部派发端之根本,故而也是小乘佛教之统称。隋吉藏撰《三论玄义》亦云:“十八者,谓十八部异执也,及本二者,根本唯二部,一大众部,二上座部。”
《如实论》同样内容不详,今只有梁真谛之汉译本,全称《如实论反质难品》②,或许与之相当。此书性质和前述《破论》类似,也是反驳外道论师,论证自家学说之如实。关于本论的作者,早期文献均未有记录,但宋、元、明三个本子却题为世亲所造,这当然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世亲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说一切有部论师,撰写了《俱舍论》;另一个是从有部转向大乘的瑜伽行派论师。真谛译《婆薮盘豆法师传》,将二人混同,导致佛教史上一直以此二人为一人,直到现代学者考证才得以澄清①。《如实论反质难品》从内容上看很难说属于说一切有部,其基于因明论的立场,也很有一些大乘的影子。
(14)贞观二年(628年)玄奘到龟兹,见到龟兹等丝路北道三国佛教皆小乘说一切有部。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载:
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翫,人以功竞。
跋禄迦国……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伽蓝数十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15)约公元7世纪,《华严经》传入以小乘为主的龟兹。《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②载:
圣历年中(699~701年),于阗三藏实叉难陀①云:“龟兹国中,唯习小乘,不知释迦分化百亿,现种种身云,示新境界,不信华严大经。有梵僧,从天竺将华严梵本至其国中。小乘师等,皆无信受。梵僧遂留经而归。小乘诸师,乃以经投弃于井,经于井中放光,赫如火聚。夜诸师覩之,疑谓金宝。至明集议,使人漉之。乃是前所弃华严经也。诸师稍为惊异,遂却入归经藏中龛安置。他日忽见梵本在其藏内最上隔。诸师念言:‘此非我释迦所说耶,吾见有少异,乃收入藏中。何人辄将向此上隔?’又以梵本置于下龛。僧众躬锁藏门,自掌钥钩。明日开藏,还见华严在其上隔。诸师方悟一乘大教威灵如此,惭悔过责,信慕渐生矣。”
《华严经感应传》专门收入各类感应灵异之事以宣讲华严,故事的讲述者实叉难陀本身就是华严经的积极传播者,经书撰写的目的性非常明显。而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华严神迹当然也极不可信。所以假设这个故事有什么参考价值的话,只能说它反映了这时龟兹地区仍然流行小乘佛教的情况(和上引昙无谶经历有些类似),并且大乘华严信仰可能在此时传入龟兹地区。文献中未注明故事发生的时间,暂时定在圣历年前一个世纪。
(16)公元671~691年,义净游学印度,记载小乘有部所分之部派在龟兹杂有行者。
《南海寄归内法传》载:
凡此所论,皆依根本说一切有部,不可将余部事见柔于斯。此与十诵大归相似。有部所分,三部之别:一法护、二化地、三迦摄卑。此并不行五天。唯鸟长那国,及龟兹、于阗,杂有行者。然十诵律亦不是根本有部也。
义净于咸亨二年(671年)泛海西行,游学印度。天授二年(691年),他遣人将其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带回汉地。故书中传闻当于此间记录。至于文中说到十诵律与根本有部的关系问题,现代佛学界认为义净所译之有部毗奈耶相当于十诵律之比丘、比丘尼戒法,而内容较十诵律广泛,多载录本生因缘故事。
(17)公元726年前后,龟兹僧利言通学大乘和小乘理论,包括东天竺传来之大乘佛法。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翻译经过时讲到:
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东天竺国人也。游中印度。亦称摩提国人焉。学通三藏,善达医明。利物随缘至龟兹国(正曰屈支),教授门人地战上湿罗(字布那羡,亦称利言①),使令记持梵本《大乘月灯三摩地经》满七千偈,及《历帝记》过一万偈,《瑜伽真言》获五千偈。一闻于耳,恒记在心。开元十四年(726年)受具足戒。自后听习律论、大小乘经、梵书汉书、唐言文字……。
(18)约公元727年,慧超路过作为安西大都护府之龟兹,见证龟兹本地僧人多习小乘,而汉族僧人习大乘。20世纪初,伯希和在敦煌石窟中找到一本失传已久的游记写本《往五天竺国传》①。在游记中,唐代旅行家——新罗僧人慧超如下写道:
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此亦汉军马守促。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韮等。土人着叠布衣也。
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韮等也。汉僧行大乘法。
又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是汉军马领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
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
于阗有一汉寺,名龙兴寺。有一汉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
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崏州人士。又从安西东行□□至乌耆国,是汉军兵□领押。有王,百姓是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
卷末云:“此即安西四镇名..一安西、二于阗、三疏勒、四乌耆”。可知慧超所云安西者,即指龟兹。故秀行、义超等人所驻之大云寺为龟兹大乘汉寺。但是这时龟兹依旧以小乘为主,过去与龟兹宗教属性倾向一致的疏勒和焉耆情况类似。
(19)约公元785~788年,旅行僧人悟空居住龟兹一年,请龟兹高僧勿提提犀鱼翻译他从南天竺携来的《十力经》。
唐圆照之《悟空入竺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载悟空先在北印度犍陀罗地区学习说一切有部,又南游中天竺诸国,求得梵本《十地经》、《回向轮经》和《十力经》,然后取道北路返回大唐,经于阗、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汗国)、据瑟得城之后。次至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捡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①。龟兹国王白环,正曰屈支城。西门外有莲花寺,有三藏沙门名勿提提犀鱼(唐云莲花精进)。至诚祈请,译出《十力经》,可三纸许以成一卷。三藏语通四镇,梵汉兼明。此《十力经》,佛在舍卫国说。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前践寺。复有耶婆瑟鸡山,此山有水滴溜成音,每岁一时采以为曲,故有耶婆瑟鸡寺。东西拓厥寺、阿遮哩贰寺。于此城住一年有余。悟空离开龟兹后在焉耆停留了三个月,然后到达北庭,请当地僧人翻译了《十地经》和《回向轮经》,然后于贞元五年(789年)随同唐北庭宣慰使等官员返朝。推测勿提提犀鱼在龟兹翻译《十力经》的时间应当在此前不久的贞元初期。霍旭初先生对这段事迹有专文考证,最后认为《十力经》属于阿含部(过去通常认为它属于密宗),勿提提犀鱼翻译此经不仅不能证明当地流行密宗,相反还可能为研究当时龟兹小乘佛教提供线索②。
(20)公元16世纪末,西域僧人锁喃嚷结旅行路过龟兹,见证当地佛教凋零。
《西域僧锁喃嚷结传》载其:“至跋禄迦国,名小沙迹,王名碧多。都城高广,人物集盛。唯有一寺,名阿奢理儿寺,宽广僧多,专学禅定,多游天竺。又东三千里,过屈支国,王号木文□多。宫殿整齐,人民男妇赤色,敬重三宝。多幻术。所□诸物华美,衣服精丽。使用金银钱。停住一年。又行东过阿耆尼国,多有银□山,金□山,高可百丈,光气腾曜,不可名状。贼寇极广,其人凶恶,惨杀无忌。”
锁喃嚷结“万历三十年(1602年)五月十五日启奉明肃皇太后命,住万寿庵”,其间在高昌和五台山等地还盘桓了至少四年,故推其路过龟兹的时间在公元16世纪末。尽管提到龟兹人敬重三宝,但描述语气与描述跋禄迦国的佛教情况已大不相同。又云此地多幻术。龟兹佛教这时可能已经大不如前了。
小结
上述名单中有8项史料明确含有小乘信息,另外有一项史料,438~504年龟兹僧直月使人醉酒得果之事,可推测其含有小乘信息(这份材料自羽溪了谛以来常常被当作大乘的证据被使用)。
共有9项史料把龟兹推向大乘。有8项史料明确含有大乘信息,另外有一项史料,4世纪末5世纪初大乘云游禅僧昙摩密多受到龟兹王礼遇,可推测其含有大乘信息。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一些僧人的大小乘都学习,游历的过程中往往根据当地需要讲经说法,例如佛图澄。并且受到礼遇的理由可能是非教派性的,譬如唐玄奘,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他就一路受到小乘高僧的礼遇,在龟兹当然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此说礼遇他的地区一定也流行大乘。
在8项明确含有大乘信息的史料中,刘宋时期龟兹法丰寺弟子书写《法华经》,和公元540年汉僧云启和天竺僧那连耶舍于龟兹合译禅宗《佛祖传法偈》,这两件史料笔者认为有作伪的嫌疑。公元393年,龟兹高僧昙摩跋檀应请口头翻译经典,似乎也应该排除掉大乘信息的因素。这样一来,真正能够体现龟兹大乘信息的就只剩下了5项。其中有3项属于7世纪到8世纪上半叶,大乘佛教在这段时间内突然活动频繁,可能和龟兹地区在被唐朝军队占领有关,一般认为这时汉地流行的大乘佛教随大军西向传入龟兹,这一点在库木吐喇确有清楚的体现。这时克孜尔石窟开始走向式微①。吴焯先生从克孜尔石窟遗存的破坏性题记出发,认为一些题记的上限应该是吐蕃于公元670年攻占安西以后二十二年内所写,这也是克孜尔石窟开始废弃的时间。而开元十四年(726年)到贞元十年(794年)的游人题字大都写在僧房内,说明此时僧房已经空无人住。一系列题记和出土文书表明克孜尔石窟相当一部分洞窟在此时已经废弃,而且作为临时的碛西节度使官方设置的关卡或过所②。笔者同意上述观点,且认为不妨考虑把克孜尔石窟初次遭到破坏的时间推早到公元647年前后③。《法苑珠林》提到唐朝军队攻陷龟兹时有过屠城毁寺之暴行,云:“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征龟兹。有萨孤训者,为行军仓曹参军。及屠龟兹城后,乃于精舍剥佛面取金。”④《法苑珠林》成书于总章元年(668年),说明在吐蕃攻占安西以前已经有破坏龟兹佛寺之传闻了。当然这种破坏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龟兹佛教并没有被完全摧毁,而是继续持续了很长时间。
剩下关于4~7世纪的大乘史料只有2项,公元370~384年鸠摩罗什在龟兹宣讲大乘,公元585年前后达摩笈多在龟兹王寺停住两年,龟兹王笃好大乘。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关于龟兹大乘的虚假情报?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不难发现它们的共性,就是其使用者往往有着共同的立场。它们的来源多是汉地倾向大乘的作家,其写作的立场免不了要向大乘偏移。例如如果能够说明法华经在那些遥远的西域佛国也受到欢迎,无疑能够加强对汉地民众的说服力。与之相比,关于龟兹小乘的史料则大都非常明确。不少来自旅行僧人的直接描述,内容要具体得多,且主角大多也是大乘僧人,事件常常涉及他们在小乘地区并不愉快的经历。看不出里面有夸大或捏造事实的动机。这些小乘史料从4世纪中叶开始延续到8世纪上半叶,它们大体上能够说明龟兹在并置于唐朝安西以前,是一个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地区。这当然也是多数学者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史料分布并不平均。4世纪中到5世纪初的史料,以及7~8世纪的史料略多,而几乎整个6世纪只有585年前后龟兹王好大乘的史料比较可靠。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史料如此之少。说龟兹在6世纪也以小乘为主,恐怕更多是推测其教派属性不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对此,学者们多少应该如履薄冰吧。看来要清楚全面地了解龟兹地区宗教属性,还有待于今后新材料的出现以及多方面的研究。
下述与龟兹佛教有关的资料中多数显示出大乘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者要试图说明龟兹是一个流行大乘佛教的国家,他可以提供比对手更多的证据。但分析下来,这些证据的有效性要相对弱些。其中部分材料,笔者认为对于龟兹佛教的大小乘问题帮助不大,因而将它们逐次作了排除。
一 第一次排除
第一种情况,有学者认为白姓等于帛姓,白氏帛氏皆龟兹人,故将僧人白延、帛法祖、帛法巨(矩)、帛尸梨密多罗、佛图澄(原姓帛)皆作为龟兹高僧①。
白延(帛延),多谓西域沙门,在曹魏时期在洛阳从事译经活动。《佛祖统记》云“甘露元年(256年),天竺沙门白延至洛阳译《无量》”。《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白延者。不知何许人。魏正始之末(约249年)重译出《首楞严》,又《须赖》及《除灾患经》凡三部”。同书卷七又另载有译师帛延于咸和三年(328年)在凉州翻译《首楞严经》,云“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
帛法祖即帛远,据《高僧传》卷一载“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父威达,以儒雅知名”。
帛尸梨密多罗,《高僧传》卷一载“帛尸梨密多罗,此云吉友,西域人。时人呼为高座。传云:国王之子,当承继世,而以国让弟。闇轨太伯,既而悟心天启,遂为沙门”②,现存《佛说灌顶经》则写着译者为“天竺三藏帛尸梨多罗”。
佛图澄,《高僧传》说他本姓帛,西域人。《释氏稽古略》云“佛图澄和尚,天竺国人也。西晋怀帝永嘉四年至洛阳。自言百岁余”。
我们不否认这些僧人来自龟兹的可能,但应该对此保存警惕。①白姓非帛姓,西来者概取读音近似则译,是否所有法名以白、帛二字开头的僧人都来自龟兹呢?还有待讨论②。霍旭初先生曾经指出早期西域僧人常在名前冠以“佛陀”和“帛”,作为对僧人的尊称。①我个人倾向于赞同这个观点。但笔者首先把上述名单排除在有效材料之外,不仅因为他们中或许有人与龟兹无甚关系,更主要因为在他们的传记中确实没有关于龟兹的具体信息。
二 史料总表
剩下来的史料大约可归纳为26项,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将它们排列下表中。
上述资料或多或少都和龟兹有所关联。有的史料包含大乘的信息,有的包含小乘,有的则两者都有。还有少数材料没有关于大小乘的信息,但包含了比较重要的宗教情报。总计大乘信息占14项,小乘信息占10项。
三 第二次排除
上述史料表格中第1、第2、第3、第16、第20、第21号,共六项材料被笔者作为不可靠史料,第二次排除。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如下,以方便以后的研究者。
(1)公元284年,来自于龟兹副使美子侯之《阿惟越致遮经》在敦煌被翻译,此经属大乘法华部。
《出三藏记集》“阿惟越致遮经”记载:“太康五年(西晋284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美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①。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闻知。”
(2)公元286年,龟兹居士帛元信校参大乘《正法华经》和《渐备经》,可能在长安。又参与过大乘《须真天子经》翻译。
《出三藏记集》卷七载:“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共劝助欢喜。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元年二月六日重复。”②
《出三藏记集》卷八载:“《渐备经》护公以元康七年出之。..然出经时人云:聂承远笔受,帛元信、沙门法度,此人皆长安人也。以此推之,略当必在长安出。”
《出三藏记集》载:“《须真天子经》太始二年(按:或许为公元266年之‘泰’始二年)十一月八日于长安青门内白马寺中,天竺菩萨昙摩罗察口授出之,时付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
(3)公元328年(或咸安三年373年),龟兹王世子帛延在凉州翻译大乘经典《首楞严经》及《须赖经》等经。
《出三藏记集》卷七载:“咸和三年①,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支优婆塞支施仑,手执胡本。支博综众经,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业大乘学也。出《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时在凉州州内正听堂湛露轩下集。时译者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受者,常侍西海赵潚、会水令马奕、内侍来恭政,此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德。时在坐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凉州自属辞,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4)公元6世纪晚期,异僧从龟兹至东土,鉴《法华经》。
唐惠详《弘赞法华传》②载:恭(严恭)因发愿造法花百部..于是大起房宇为经之室。庄严清净,供给丰厚,书生常数十人。扬州道俗,共相崇敬..恭甞一时在经堂北,有一异僧,年可八十,来告恭云:闻君造经,愿请一部。又承未有提婆达多品,今留此品,可于宝塔品后安之。贫道,从龟兹国来,今往罗浮山去。得经一部,粗略披寻。仍留金一鉼,重三十斤,用入法花,来岁夏间当附物。又云:向见普贤品内呪少一句语,宜觅足之。言毕而退。恭寻后看,莫知所在。后有捿霞寺禅师宝恭,送零落法花经五十许卷,使恭成就,拟用流通。有一卷第七,是宋元嘉二十九年(452)宋懿所造,校普贤呪,果少婆罗帝三字,是第十六句。自后写经,仍依足之。
这段故事从陈太建初(约569年),严恭年弱冠时经商奇遇故事开始,讲到他信奉“法华”后的种种神迹。此段龟兹异僧故事较奇,关键是他从何处得来经书,文献中并无交代。
(5)公元7世纪下半叶,龟兹国人达磨跋陀(法贤)学习法华经。唐僧详《法华传记》①“龟兹国沙门达磨跋陀十七”载:
达磨跋陀,唐云法贤,龟兹国人也。天性聪明,具通三藏。粗识外国言词,谓小为极,自生贡高,陵辱摩诃衍众。时有巡礼沙门,名曰须梨耶,诵达法华六千偈无脱法,对法贤论所诵幽致。贤识三藏单浅,归心大乘,从须梨耶,诵达法华,每日五遍为业。敬法夜叉,守护此人。又每夜草坊现异光,人谓失火,谘法贤。答曰:“四大天王,番番来护光明。”临终之时,语徒众言:“昔执小典为极,如执瓦石为金宝。今翫法华得真金也,以三年讽诵面见普贤,入正位得不退记。汝等专讽持此经,期正位不过三生。”即注遗书而卒,如入禅定。于遗身骨上起塔。夏雨盛降,雨不能湿塔。鸟类群飞,不近塔边。凡见闻者,礼拜供养如市而已。
同书“浔阳处女十七”故事中记载了法贤到浔阳的时间,云:“唐总章年中(668~670年),外国沙门,名达磨跋陀,唐云法贤,无奈何事,来至浔阳。容仪挺特,色貌端正。诵法华等大乘经凡三万偈也,音声爱(按:当为“受”字)雅众所乐。”
达磨跋陀临终时云:“昔执小典为极,如执瓦石为金宝。今翫法华得真金也。”据此或可推敲,他本来在龟兹所学应是小乘,在东土接触《法华经》后改宗大乘。
(6)唐代,龟兹国僧若那翻译《佛顶尊胜陀罗尼别法》。
《佛顶尊胜陀罗尼别法》卷首写道:“龟兹国僧若那奉诏译。口问笔缀,授与崇福寺僧普能,因即流布。”
虽然上述资料都涉及到龟兹,但使用时需要特别小心。和第一次被排除的情况类似,这些资料本身往往只透露了汉地的相关情报,龟兹的信息非常有限,很难用来说明龟兹问题。比如常见的一种情况佛经译师来自龟兹,但有时译师的翻译活动并不能代表其本人的宗教态度。如霍旭初先生所指出,有时译师来自龟兹,经本却得自汉地①有时甚至译者仅仅是龟兹人,而非僧人。翻译活动的属性要更多归因于发起翻译的功德主。如甘露三年在白马寺翻译《首楞严经》的龟兹王世子帛延应凉州刺史张天锡的要求翻译《首楞严经》,还有太康七年参校《正法华经》的龟兹居士帛元信。翻译书籍的要求可能来自其它人,又或者有学术上的需要,译师仅仅是从事翻译工作而已。中国最大的两个译师,鸠摩罗什和唐玄奘都翻译了大量属于不同派别的佛经。因此汉地译经活动不能用来判断龟兹地区的宗教属性。
另外一种情况是僧人的宗教态度比较明确,并且可能原籍龟兹。但是,除非我们能够明确其所受教育(或资源,如携带入汉地的佛经)来自龟兹,否则也很难用来说明问题。以鸠摩罗什为例,他本来在龟兹接受的是纯粹的小乘教育,直到第二次离开龟兹,在中亚游历才逐渐接受了大乘佛教,最后到汉地传法。我们不能因为鸠摩罗什本身信奉大乘,就简单地推导出其原籍地区也流行相同的宗教。至于他后来回到龟兹传法,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后文会有交代。
我们说上述材料“不可靠”并不是说史料的真实性全部值得怀疑。而是由于上述事件全部发生在汉地,其提供的龟兹情报相当有限,用作龟兹宗教属性研究时可能带有较多主观臆测。在这一点上它们无法成为有效的信息来源。
四 重点史料分析
余下的情报按时间顺序分别排列如下。尽管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依然可能存在于这些材料中,但得益于前辈学者的研究,对一些情报的分析已足够透彻,如鸠摩罗什问题,故只摘录其重要情节;重点对其它一些疑点问题进行讨论。
(1)公元350~352年,鸠摩罗什七至九岁在龟兹随母出家,学习小乘《毗昙》。后出游罽宾、沙勒诸国学习小乘。公元356~363年,鸠摩罗什十三至二十岁,随母返回龟兹,以小乘学识著名。公元363年,鸠摩罗什二十岁,受戒于龟兹王宫,大概经师是佛图舌弥,律师为卑摩罗叉①。当时卑摩罗叉(梵语Vimalaksa)正在龟兹宣讲有部广律《十诵律》。鸠摩罗什在龟兹思想发生转变,开始对大乘佛教感兴趣。
《出三藏记集》卷十四载:“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口诵日得千偈。……诵毘昙……。什年九岁,进到罽宾,遇名德法师盘头达多……遂诵杂藏、中阿含、长阿含,凡四百万言。……至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进到沙勒国。……什于沙勒国,诵阿毘昙、六足诸门、增一阿含。及还龟兹名盖诸国。时龟兹僧众一万余人,疑非凡夫,咸推而敬之,莫敢居上。”
《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传”载:“卑摩罗叉,此云无垢眼,罽宾人。沈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节成务。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及龟兹陷没乃避地焉。顷之闻什在长安大弘经藏,又欲使毘尼胜品复洽东国,于是杖锡流沙冒险东入。以伪秦弘始八年达自关中,什以师礼敬待。”
(2)约公元370~384年,鸠摩罗什在龟兹宣讲大乘。公元370年鸠摩罗什约二十七岁,在第二次旅行学习大乘佛法后回到龟兹,钻研大乘,后在龟兹及周边诸国宣讲大乘。公元384年吕光破龟兹,虏走鸠摩罗什②。
《出三藏记集》载:“后从佛陀耶舍学十诵律,又从须利耶苏摩谘苏禀大乘①。乃叹曰:吾昔学小乘,譬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矣。于是广求义要,诵中百二论。于龟兹帛纯王新寺得放光经,始披读,魔来蔽文,唯见空牒。什知魔所为,誓心逾固。魔去字显,仍习诵之。后于雀梨大寺读大乘经……停住二年,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后往罽宾,为其师盘头达多具说一乘妙义。师感悟心服,即礼什为师,言:我是和上小乘师,和上是我大乘师矣。西域诸国伏什神俊,咸共崇仰,每至讲说,诸王长跪高座之侧,令什践其膝以登焉。”
(3)公元371~372年,中土僧人僧纯自龟兹著名阿含学者佛陀舌弥许得“比丘尼大戒”等戒法,同时也见到大乘僧鸠摩罗什。
《出三藏记集》卷二载:“比丘尼大戒一卷。右一部,凡一卷。晋简文帝时(371~372年),沙门释僧纯于西域拘夷国得胡本。到关中,令竺佛念、昙摩持、慧常共译出。”
同书卷十一记:“……僧纯于丘慈佛陀舌许得戒本。……卷中间尼受大戒法后记云:……。末乃僧纯、昙充拘夷国来,从云慕蓝寺于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剑慕法。遂令佛图卑为译,昙摩侍传之。乃知真是如来所制也。……又授比丘尼大戒,尼三师教授师,更与七尼坛外问内法。”比丘尼大戒卷后又记:“秦建元十五年(379年)十一月五日,岁在鹑尾。比丘僧纯、昙充从丘慈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授大比丘尼戒仪及二岁戒仪”云云。概为僧纯回到汉地开始推行戒法的时间。
《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摘录了《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拘夷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五十僧),剑慕王新蓝(六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
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或易蓝者。未满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
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乃才大高明,大乘学,与舌弥是师徒。而舌弥阿含学者也)。
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输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
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比丘尼外国法不得独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无师一宿者辄弹之。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舌弥乃不肯令此戒来东,僧纯等求之至勤,每嗟此后出法整唯之斯戒,末乃得之。……
(4)公元393年,龟兹高僧昙摩跋檀应请口头翻译经典。
《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①卷末载:
巍巍十方佛,国土甚清明;七宝为庄严,妙香栴檀馨;悉纯诸菩萨,无有二乘名;惟说不退转,般若道之英;巍巍十方佛,三世道之珍;其闻信乐者,疾成无上真;游于菩萨道,坚住不退还;所生常见佛,遭值诸天尊;巍巍十方佛,三界之导师;至心怀恭敬,信乐无狐疑;所生常端正,颜容甚花晖;辩才慧独,愿礼天人师。
麟嘉六年(393年)六月二十日,于龟兹国金华祠演出此经。译梵音为晋言。昙摩跋檀者,通阿毘昙,畅诸经义,又加究尽摩诃衍事,辩说深法,于龟兹国博解第一。林即请命出此经。檀手自执梵本,衍为龟兹语经。当如是时,道俗欢喜,叹未曾有,竞共讽诵,美其功德。沙门慧海者,通龟兹语,善解晋音。林复命使译龟兹语为晋音。
表面看来这段话好像是在讲《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的翻译过程,其实不然。此经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卷首注明为“元魏天竺三藏吉迦夜译”,可与佛教史籍相关材料吻合。《开元释教录》载:“《称扬诸佛功德经》三卷,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载:“《称扬诸佛功德经》一部三卷。右西晋竺法护译。出长房录。《称扬诸佛功德经》一部三卷,右后魏沙门吉迦夜于北台译。出长房录。《称扬诸佛功德经》一部三卷,右秦弘始七年罗什于长安译,出长房录。”查此经其它同本异译,未见昙摩跋檀所译者。
此经上、中、下三卷,原本目次井然有序。上卷卷首标题“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上”在卷末会重复一次。中卷、下卷亦然。这种编目方法是汉译佛经的惯例。《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下结尾句云“一切大会皆大欢喜,前为佛作礼而去”,整部经书从结构上来说已经完全结束。作为目录使用的语句“《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下”按照正常的格式使用了两次,一次在下卷开头,一次在下卷结尾。但很奇怪,在此经中却使用了三次,即在全书结尾处又多使用了一次,其间插入了上文所摘抄的两段文字①。这两段文字——“巍巍十方佛”之五言偈诵,和“龟兹国金华祠译经故事”都来得异常突兀,且前后矛盾。翻译的“译者”昙摩跋檀、“时间”麟嘉六年(393年)和“地点”龟兹国和正本经文署名之译者“元魏天竺三藏吉迦夜”全无半点关系。这段文字前面的五言偈诵,经笔者检索,系出自《六菩萨亦当诵持经》五言长诵中的一段②,所以后面的两篇文字肯定不属于原经,可能是书籍抄录刊印时被错误加到《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里面来了。则昙摩跋檀所译经典究竟是《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六菩萨名经》还是别的什么经典概莫能知也。但这段文字记录了龟兹高僧应汉人要求翻译经书的情况,仍然有参考价值。
(5)公元400年,法显在丝路中道龟兹焉耆一带旅行,见闻当地小乘佛教。
《高僧法显传》载:“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鄯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法显得符行堂公孙经理,住二月余日。于是还与宝云等共合。乌夷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法显等蒙符公孙供给,遂得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
法显游记中所说的“乌夷”是什么地方?慧琳《一切经音义》谓乌夷即今焉耆,过去之阿耆尼国。云:“阿耆尼国——雨碛之西第一国也,耆音祇,古曰婴夷,或曰乌夷,或曰乌耆,即安西镇之中是其一镇,西去安西七百里。汉时楼阐、善善等城皆此地也,或迁都改叭,或居此城,或住彼城,或随主立名事,互相吞灭,故有多名,皆相邻近,今或丘墟。”但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西方汉学界有过激烈争论。起先是哇特斯考订乌夷为焉耆,列维1913年着文考订乌夷为龟兹,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龟兹有时被称为拘夷,和乌夷有些类似。文曰:“纪元520年刊之《出三藏记集》,载有鸠摩罗什时代龟兹佛教信行之事。所载国名为‘拘夷’。..纪元860年刊《酉阳杂俎》,亦志有‘拘夷’国名。国之北山有陀便水,服之发落,此事与《魏书》所载龟兹国故事,又略相合,故知拘夷为龟兹也..由此拘夷国名,吾人又忆及纪元四百年时法显所经之乌夷。”第二个理由是根据法显所述之行程推算,认为龟兹正好在高昌到于阗的转折处,比较符合龟兹的地理位置。文曰:“考《佛国记》,法显等从鄯善‘西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又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国’。考其行程,乌夷决为今之库车,昔之龟兹。..由焉耆不能‘直进西南行’到今之和阗,古之于阗也。”①后来伯希和1936年撰文反驳列维,考定古,代“焉”字书法与“乌”字相似,容易混淆,导致焉字被误写为乌,遂有焉耆被写作“乌耆”②。
(6)公元400年前后,佛陀耶舍在龟兹传法数年。
《出三藏记集》卷十四“佛陀耶舍传”载:
佛陀耶舍..罽宾人也。..至年十五,诵经日得五六万言。..十九,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乃从其舅学五明诸论,世间法术,多所通习。二十七方受具戒。以读诵为务,手不释牒。..后至沙勒国..太子悦之,仍请宫内供养,待遇隆厚。罗什后至,从其受学阿毘昙、十诵律,甚相尊敬。什随母东归,耶舍留止。..时符坚遣吕光攻龟兹。龟兹王急求救于沙勒,王自率兵救之。..王归,具说罗什为光所执,乃叹曰:我与罗什相遇虽久,未尽怀抱。其忽羁虏,相见何期。停十余年,王薨。因至龟兹,法化甚盛。时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粮欲去,国人请留,复停岁余。语弟子云吾欲寻罗什。..乃取清水一钵,以药投中,咒数千言,与弟子洗足,即便夜发,比至旦行数百里..行达姑臧,而什已入长安。佛陀耶舍在公元384年鸠摩罗什被吕光虏走之后,又在沙勒停了
十多年才去龟兹。故可推测他到达龟兹的时间在公元395年到405年之间。他后来想离开龟兹到姑臧找鸠摩罗什,但到达姑臧时,鸠摩罗什已经去了长安。鸠摩罗什到长安是公元401年,陈世良推测佛陀耶舍到长安时是公元410年③,另一说为公元408年④。故佛陀耶舍在龟兹的时间大约在公元400年前后的几年。佛陀耶舍十九岁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又通法术,看来在大小乘佛学上都有一定造诣。但鸠摩罗什跟随他学习阿毘昙、十诵律,可能是因为他擅长论和律的缘故。尽管后来传说他返回罽宾弄了部《虚空藏经》,但事实上佛陀耶舍到长安后的主要成就是翻译了昙无德部的律藏《四分僧戒本》、《四分律》,此外就是《长阿含经》。应该说佛陀耶舍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小乘方面。至于他在龟兹传法的具体情况,没有直接的文献描述。
(7)约4世纪末5世纪初,罽宾云游禅僧昙摩密多受到龟兹王礼遇。
《高僧传》载:“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博贯群经,特深禅法,所得门户极甚微奥,为人沈邃有慧解,仪轨详正,生而连眉,故世号连眉禅师。少好游方,誓志宣化。周历诸国,遂适龟兹。未至一日,王梦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当入国。汝应供养,明旦即敕外司:‘若有异人入境必驰奏闻’。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延请入宫。遂从禀戒尽四事之礼。蜜多安而能迁,不拘利养,居数载,密有去心。神又降梦曰:‘福德人舍王去矣’。王惕然惊觉。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进到敦煌。……顷之复适凉州。……以宋元嘉元年(424年)展转至蜀,俄而出峡止荆州。……顷之沿流东下至于京师。……初密多之发罽宾也,有迦毘罗神王卫送。遂至龟兹,于中路欲反,乃现形告辞密多曰:汝神力通变自在游处,将不相随共往南方。语毕即收影不现。遂远从至都,即于上寺图像着壁。迄至于今犹有声影之验,洁诚祈福莫不享愿。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
昙摩密多《出三藏记集》谓昙摩蜜多,然传与《高僧传》所载相同。其传曰:以元嘉十九年(442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故可推昙摩密多生于公元356年。又宋元嘉元年(424年)已经从敦煌凉州展转到了四川。大概停留龟兹之数载约在4世纪末5世纪初之际。他进入汉地以后宣讲禅法,翻译了五门禅经要用法,以及《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虚空藏菩萨经》、《禅密要经》等大乘佛经。然其在龟兹作为未见记载。
(8)约公元412年,大乘僧昙无谶至龟兹,不为当地小乘佛教接纳。
《出三藏记集》卷十四载:“昙无谶,中天竺人也。……十岁与同学数人读咒,聪敏出群,诵经日得万余言。初学小乘兼览五明诸论。讲说精辩莫能詶抗。后遇白头禅师共谶论议。……禅师即授以树皮涅槃经本。谶寻读惊悟,方自惭恨,以为坎井之识,久迷大方。于是集众悔过,遂专业大乘。年二十所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谶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王怒捕谶。谶悔惧诛,乃赍大涅槃经本前分十二卷,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奔龟兹。龟兹国多小乘学,不信涅槃,遂至姑臧①,止于传舍。……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请令出其经本。谶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翻为汉言,方共译写。是时沙门慧嵩、道朗独步河西,值其宣出法藏,深相推重,转易梵文,嵩公笔受。”
《涅槃经》大乘有之,小乘亦有之。然中天竺大乘咒师昙无谶所学所译为大乘者也。他本来想持《大涅槃经》、《菩萨戒经》等大乘经卷到龟兹传法,无奈龟兹的情况很不理想,“多小乘学,不信涅槃”,他只能离开龟兹去姑臧,在那里得到蒙逊的支持才呆下来。昙无谶到姑臧后,数次因为经本不全,回到于阗搜寻,而不是更近距离的龟兹,也可应证那里大乘典籍比较缺少的情况。《高僧传》卷二讲到昙无谶被蒙逊谋杀,死时“春秋四十九,是岁宋元嘉十年(433年)也”。可推其生于公元385年,又年二十时为公元404年,他此时尚在中天竺。又据《高僧传》他在姑臧译经,“伪玄始三年(414年)初就翻译”,减去学习汉语之三年,可推昙无谶离开龟兹到姑藏的时间大概在玄始元年①(412年)或略早②。
(9)公元5世纪中后期,高昌法惠往龟兹国求法,醉酒得果。反映小乘观念。梁宝唱撰《比丘尼传》“伪高昌都郎中寺冯尼传”载:
冯尼者,本姓冯,高昌人也,时人敬重,因以姓为号。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菜蔬一食,戒行精苦。烧六指供养,皆悉至掌。诵大般涅槃经,三日一遍。时有法惠法师,精进迈群,为高昌一国尼依止师。冯后忽谓法惠言:‘阿阇梨③未好,冯是阇梨善知识。阇梨可往龟兹国金花帐下直月闻当得胜法。’④法惠闻而从之,往至彼寺见直月。直月欢喜,以蒲萄酒一升与之令饮。法惠惊愕:我来觅胜法,翻然饮我非法之物。不肯饮。直月推背急令出去。法惠退思:我既远来,未达此意,恐不宜违。即顿饮之。醉吐迷闷,无所复识。直月便自他行。法惠酒醒,自知犯戒,追大惭愧,自槌其身,悔责所行,欲自害命。因此思惟得第三果。直月还问曰:已得耶?答曰:然。因还高昌。未至二百里,初无音信。冯呼尼众远出迎候。先知之迹,皆类此也。高昌诸尼莫不师奉。年九十六,梁天监三年(504年)卒。
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5世纪中后期,即冯尼出家的公元438年到其去世的504年之间。同样一段故事也收录在宝唱另外一本着作《名僧传》中。该书在汉地已经不传,但由于其流传到日本,故而在《大日本续藏经》中得以保存。据此书“法惠传”载,法惠去世于齐永元年,比冯尼去世时间略早。
《大般涅槃经》如前所述,有大乘者如北凉昙无谶之译本,凡四十卷;亦有小乘者如东晋法显之译本,凡三卷。高昌冯尼三日一遍,所诵之经属于大乘还是小乘难以判别。不论高昌此时流行大乘还是小乘,冯尼要法惠去龟兹求胜法,终究是对现状不满。有学者根据直月使醉法惠之教法,把直月当作顿悟派禅宗大师。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谈到:“龟兹高僧直月者,其所行之法,即类于中国所谓达磨禅者也,法惠既受其教,当亦于高昌弘扬禅风。”①。
《名僧传》“法惠传”虽然在法惠出家事迹中讲到他“修学禅律”,可是结尾却又讲到他从龟兹返回高昌“大弘经律”,其实许多佛教文献中的“禅”、“律”等词汇往往是虚指,未必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名僧传》中第十九卷专门记录外国禅师,第二十卷专门记录中国禅师,而“法惠传”却被编排在第二十五卷索苦节中,足见这段故事的主题并非宣传禅师。
从名字和行事上看,这位直月的确颇有中国南禅大师呵佛骂祖之风范。但直月可能不是僧人法号,而是寺僧中某种职务称号。如北宋赞宁撰《大宋僧史略》载:“魏孝文以皇舅寺僧义法师为京邑都维那,则勅补也,是乃昭玄都维那耳。今寺中立者,如玄畅勅为总持寺维那是也。次典座者,谓典主床座。凡事举座,一色以摄之,乃通典杂事也。或立直岁则直一年,或直月、直半月、直日,皆悦众也,随方立之。”小乘律藏《摩诃僧祇律》中常常讲到直月负责管理寺院伙食的情况,如云“若比丘为僧作直月,行市买酥油籴米豆麦面麨糒,求一切物时,作不净语者,犯越比尼罪”、“若直月及监食人欲知生熟醎淡甜酢,得着掌中舌舐,无罪”等等。笔者以为前述“法惠”事迹可能与禅宗无关,而仅仅是一个传奇故事,借直月与酒,文学性地嘲讽戒律清规,反映了对禁欲制度的置疑。而法惠经醉酒获得第三果,又正是小乘佛学的概念——声闻四果之“不还果”①故而也折射出龟兹小乘佛教的面貌②。
(10)约公元446~452年兹王礼待法朗。《高僧传》卷十宋高昌释法朗传载:
释法朗③,高昌人。幼而执行精苦,多诸征瑞,韬光蕴德,人莫测其所阶。朗师释法进亦高行沙门,进尝闭户独坐,忽见朗在前,问从何处来。答云:“从户钥中入”。云:“与远僧俱至,日既将中,愿为设食”。进即为设食,唯闻匕钵之声,竟不见人。……至魏虏毁灭佛法,朗西适龟兹。龟兹王与彼国大禅师结约:“若有得道者至,当为我说,我当供养”。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圣礼。后终于龟兹,焚尸之日,两眉涌,龟,泉直上于天。众叹希有,收骨起塔。后西域人来北(金陵本“北”作“此”)土具传此事。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到兴安元年(452年)十二月,文成帝上台才初复佛法。故推法朗赴龟兹的时间大约在此期间。
虽然文字中谈到大禅师,但修禅实在是各个部派的通行法则。又《高僧传》有“习禅”之卷,却把这个故事编在“神异”卷下,用意非常明显,只作为僧人神迹之记载也。这类故事可信度最低,故而宗教方面有用的信息并不太多。
(11)约公元420~479年之刘宋时期,龟兹法丰寺弟子书写《法华经》。疑伪。
唐僧详《法华传记》“宋释法丰”载:“释法丰,姓竺氏。敦煌人,往适龟兹,修理一寺。触事周办,时因号为法丰寺,既久专寺任。稍恃其功力,出内取与,颇乖斟酌,辄减省僧食,令不周足。久之遂亡,生饿鬼中,常在寺院,至初夜后,作饿驰鸣,巡房声叫。弟子宝慧闻而叹曰:是我师声。因问那尔。丰曰:由减僧食料,受饿鬼苦,苦剧难堪,愿见济度。弟子书写《法华经》,广为斋忏,得生清胜”。
《法华传记》大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故事后面注言出自《自镜录》。查唐怀信《释门自镜录》,果有“宋法丰减僧食死作饿鬼事”一篇。载:“释法丰姓竺氏,敦煌人,往适龟兹,修理一寺。触事周辩,时因号为法丰寺,既久专寺任。稍恃其功力,出内取与颇乖斟酌,辄减省僧食,令不周足。久之遂亡,堕饿鬼中,常在寺院,至初夜后,作饿驼鸣,巡房声叫。弟子宝慧闻而叹曰:是我师声。因问那尔。丰曰:由减僧食料,受饿鬼苦。苦剧难堪,愿见济度。弟子广为斋忏,得生清胜”。
这个故事《释门自镜录》所记和《法华传记》几乎完全一致,唯《法华传记》多出关键的“弟子书写《法华经》”一句,概为宣讲法华,所加添笔,殊不可信。
(12)公元540年,汉僧云启和天竺僧那连耶舍相逢于龟兹,合译禅宗《佛祖传法偈》。疑伪。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载:
《佛祖传法偈》,按禹门太守杨衒之《铭系记》云,东魏静帝兴和二年庚申,西魏文帝大统六年,梁武大同六年(540年),高僧云启往西域求法,至龟兹国,遇天竺三藏那连耶舍欲来东土传法。云启曰:佛法未兴,且同止此。遂将梵本译为华言。云启去游印土。那连亲将至西魏,值时多故,乃入高齐,以宣帝礼遇甚厚,廷居石窟寺,以齐方受禅。未暇翻译别经,乃将龟兹与之合所译《祖偈因缘》传居士万天懿。……
此文所云之《佛祖传法偈》应该是指《景德传灯录》所录之诸佛祖偈语。相传继承自唐《宝林传》①,禅宗理论家以记录这些偈语的方式书写了禅宗二十八祖谱系,从“七佛偈”②开始一直到讲到菩提达摩。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成书于至正元年(1341年),叙述释迦法统、禅宗诸祖事迹,以及各朝佛教史实直至元代。该书以禅宗为佛教正统,从“七佛偈”开始,前面数卷关于禅宗二十八祖之内容全部来自《景德传灯录》。故而在“七佛偈”结尾讲到“《佛祖偈》翻译乃高僧云启一同天竺那连耶舍三藏于龟兹国译出。本末载于梁大同六年”。后来又在该年事迹中讲出上述故事,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看似天衣无缝。
那连耶舍(490~589年),又译为那连提黎耶舍,在《续高僧传》中有传,然未题记龟兹又或云启之事。考其事迹,亦与禅宗没有多大关系。他翻译过《月灯三昧经》、《大悲经》、《施灯功德经》、《大集须弥藏经》、《大方等日藏经》、《大方等大集月藏经》、《菩萨见实三昧经》、《阿毗昙心论》等经,后有弟子彦琮(557~610年)为其作传,未见有翻译《祖因缘》之记载。宋景德元年(1004年)道原撰写《景德传灯录》中记载此事则十分含混,云:“禅于唐达磨至中国,今取正宗记为定。盖依梁僧宝唱《续法记》,昔那连耶舍与万天懿,译七佛至二十八祖传法事。梁简文帝,因使臣刘悬运往北齐取其书,诏宝唱编入《续法记》也。”
道原的著作中并无那连耶舍龟兹译经之说。那么比道原晚三百多年,念常为什么要在重新编写《景德传灯录》的时候加入这条信息呢?这和当时中国禅宗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关。自唐成熟的中国禅宗在唐末宋初发展到又一个高峰。但古代中国是一个凡事都要讲法统的社会,类似项羽称楚,刘备彰汉的事迹数不胜数,就连入主中原的北魏鲜卑都要标榜自己是黄帝后人,翻开《魏书》,第一句话就是“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禅宗这个本来是在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宗教,也需要追根溯源,建立一张超级巨大的族谱来显示其“正宗”。他们认为汉地禅宗传统起源于6世纪进入东土的天竺僧人菩提达磨,更通过菩提达磨往前追述,搜罗了其余二十七位古代印度佛教名人作为禅宗的印度血统。这二十八位祖师爷的第一和第二号人物是释迦弟子摩诃迦叶与阿难,这样禅宗也就和释迦佛以及过去诸佛都扯上了关系。但是禅宗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宗派。尽管充分引入了旧有的佛教传法谱系,禅宗的新谱系仍然与过去传入汉地的佛教祖谱谱系相矛盾,因而遭到质疑。如北魏吉迦夜、昙曜合译的《付法藏因缘传》就只讲了二十三祖——释尊入灭后,迦叶、阿难等二十三位印度祖师付法相传,到最后一祖师子尊者结束①,而没有后来被禅宗学者添加的婆须蜜、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和菩提达摩五人。那么这两套谱系究竟哪套能够代表正宗呢?追究这个问题成为后来汉地佛教的一个学术热点,其社会根源其实是禅宗日益繁盛,给其它教派造成很大压力,从而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坚持旧谱系的人很容易找到理由,因为他们所持的经典比《景德传灯录》等书籍古老得多,而《景德传灯录》新建谱系也确实意在自我标榜,难逃造伪之嫌。新谱系的支持者当然都是虔诚的禅宗信徒,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必须找到理由来说明新谱系的合法性,这就要对其翻译过程有所交代,以说明它是来自于印度本土的正宗原典②。这样一来,关于《佛祖传法偈》的流传过程,就有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念常声称,根据北魏杨衒之铭记,此偈是汉僧云启和天竺僧那连耶舍相逢于龟兹时所合译,然后被那连耶舍带到了汉地。云启从汉地出发去西域,那连耶舍是北印度乌场国人,从西往东,或许如念常所云路过龟兹。那么此偈只能是由那连耶舍携带而来。但比念常早约两百年的郑昂却不这么认为。南宋绍兴壬子年(1132年),郑昂在“景德传灯录跋”中讲到:“或者犹疑《佛祖传法偈》无传译之人,此夏虫不知春秋也。佛祖虽曰传无传,至付授之因岂容不知?又达磨具正遍知,华竺之言盖悉通晓。观其答问,安有传译哉?”他当然也是站在《景德传灯录》的立场,认为禅宗初祖达磨通汉语,口授亲传无须翻译。这种说法本来颇为可信。可是如果是菩提达磨把自己编入二十八祖,便少了几分排场,过去诸多演说也就会被其它部派传为笑柄,因而此说在禅宗内部影响不大。又郑昂称《景德传灯录》原为拱辰所著而为道原所获尔,意在攻云门而张临济,遂使其跋文不足为信,已为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四所考①。
11世纪的北宋契嵩对待这个问题比念常和郑昂都显得专业,他为了论证这个问题而完成长篇大着《传法正宗论》二卷,其中也提到那连耶舍,载曰:“又云,有罽宾沙门那连耶舍者,以东魏孝静之世至邺,而专务翻译。及高氏更魏称齐,乃益翻众经,初与处士万天懿译出《尊胜菩萨无量门陀罗尼经》,因谓天懿曰:西土二十七祖亦尊此经。复指达磨其所承于般若多罗,谓此土继其后者法当大传。乃以谶记之。复出已译祖事,与天懿正之。而杨衒之《名系集》亦云:‘耶舍尝会此东僧昙启者,于西天竺共译祖事为汉文。译成而耶舍先持之东来’。然与支疆之所译者,未尝异也。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其出于支疆之所译也。益至乎二十七祖与二十八祖达磨多罗,西域传授之事迹者,盖出于耶舍之所译也。推《宝林》、《传灯》二书,至于昙曜其始单录之者,其本皆承述于支疆耶舍二家之说也。”
契嵩认为,二十八祖的谱系分两次完成,一次是支疆翻译了自七佛开始到二十五祖的谱系,但到那连耶舍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七祖。那连耶舍到东土后,追捧先来汉地传法的菩提达磨,遂自凑成二十八祖。
对比《佛祖历代通载》与《传法正宗论》对同一段历史的记载,念常文献指示那连耶舍同昙启共同翻译佛祖谱系的地点是龟兹,而按照契嵩的引证,则是西天竺。翻译经典的过程也不一样。仅从时间上说,晚期文献的可靠性当然更值得怀疑。然而契嵩的结论是否正确呢?《续高僧传》云那连耶舍为“北天竺乌场国人”(即唐玄奘游历之乌仗那国,契嵩说他是罽宾人也不算错),菩提达磨则是南天竺人。菩提达磨所持的禅法与后来弘忍的东山法门本来大相径庭①,而那连耶舍身上更看不出与禅宗有何关系,他没有动机为也许一个世纪以后才发展成熟的部派代言。根据《续高僧传》,那连耶舍至少在天保七年(556年)已经在邺城定居,而契嵩更提到“以东魏孝静之世至于邺都”他到达中原的时间距离菩提达磨的时代是非常接近的。虽然菩提达磨,于公元535年已经去世,但和那连耶舍仍然是同代中人。就算那连耶舍对菩提达磨欣赏有嘉,也不至于夸张到要将他推上祖谱神坛。事实上一直到唐道宣在《续高僧传》中为菩提达磨作传,故事简略平淡,尚没有什么二十八祖之说。又,契嵩和念常都声称杨衒之对此事有过记载。杨衒之确实在《洛阳伽蓝记》中提到过菩提达磨。在对洛阳永宁寺巨塔极尽赞叹之后,杨衒之写道:“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磨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非常明显,这位被后世禅宗信徒神话般供奉为祖师的菩提达磨,在杨衒之的笔下不过是一个倾倒于我中华文明的移民而已。最后一个疑点,根据契嵩的描述,那连耶舍增加的第二十八祖是“达磨多罗”,而不是“菩提达磨”。事实上是契嵩把把东晋慧远所云萨婆多部达磨多罗与北魏萧梁时代的禅宗达磨多罗混淆了①。至此可知,契嵩之说——那连耶舍立二十八祖菩提达磨,断不可信。而念常所云那连耶舍龟兹译偈之事,以讹传讹,谬之千里矣。
(13)大约公元585年前后,达摩笈多在龟兹王寺停住两年,龟兹王笃好大乘。唐道宣(596~667年)撰《续高僧传》载:
达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贤豆罗啰国人也,刹帝利种,姓弊耶伽啰。..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弟耶(按:依止师)佛驮笈多,此云学密;阿遮利夜(按:轨范师),名旧拏达多,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为普照,通大小乘经论,..笈多受具之后仍住三年。就师学问。师之所得略窥户牖,后以普照师为咤迦国王所请,从师至彼经停一载。..于是历诸大小乘国及以僧寺。..又至沙勒国,同伴一人复还本邑,余有三人停在王寺,谓沙勒王之所造也。经住两载,仍为彼僧讲说破论,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又为讲如实论,亦二千偈,约其文理乃是世间论义之法。又至龟兹国,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系心东夏,无志潜停,密将一僧间行至乌耆国,在阿烂拏寺,讲通前论。又经二年,渐至高昌,客游诸寺。其国僧侣多学汉言,虽停二年,无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载。..延入京城,处之名寺,供给丰渥,即开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华言略悉,又奉别敕,令就翻经。移住兴善,执本对译,允正寔繁,所诵大小乘
论并是深要。
达摩笈多在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十月抵达长安,减去路上停留的五、六年时间,他在龟兹的时间可能在585年左右。达摩笈多传中清楚地讲到当时龟兹国王笃好大乘,达摩笈多达到汉地以后也翻译了不少大乘经典。很早就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时龟兹流行大乘①,但达摩笈多的翻译活动多系奉别敕令。从其传记来看,他原来追随的老师普照通大小乘经论,而他本人到达东土后,所诵大小乘论并是深要,故而笔者认为达摩笈多应当属于那种大小乘兼修的僧人,旅行时随机应变,根据当地需要来宣讲。因此笃好大乘的龟兹国王和龟兹僧众恐怕应该区别对待。
达摩笈多在沙勒、龟兹、焉耆三国连续讲诵《破论》和《如实论》。这三地都长期流行小乘,那么他所讲的经典属性就变得非常关键。《破论》和《如实论》究竟是大乘还是小乘经典呢?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破论》概破对手学说之论,佛教与其它宗教之间、大小乘佛教之间,以及小乘佛教不同部派间都常有这样的破论,仅凭名字难以判别具体属于哪一派。但根据全文“为彼僧讲说破论,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此“二部”破诸外道,可能指上座部和大众部,它们是后来诸部派发端之根本,故而也是小乘佛教之统称。隋吉藏撰《三论玄义》亦云:“十八者,谓十八部异执也,及本二者,根本唯二部,一大众部,二上座部。”
《如实论》同样内容不详,今只有梁真谛之汉译本,全称《如实论反质难品》②,或许与之相当。此书性质和前述《破论》类似,也是反驳外道论师,论证自家学说之如实。关于本论的作者,早期文献均未有记录,但宋、元、明三个本子却题为世亲所造,这当然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世亲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说一切有部论师,撰写了《俱舍论》;另一个是从有部转向大乘的瑜伽行派论师。真谛译《婆薮盘豆法师传》,将二人混同,导致佛教史上一直以此二人为一人,直到现代学者考证才得以澄清①。《如实论反质难品》从内容上看很难说属于说一切有部,其基于因明论的立场,也很有一些大乘的影子。
(14)贞观二年(628年)玄奘到龟兹,见到龟兹等丝路北道三国佛教皆小乘说一切有部。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载:
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翫,人以功竞。
跋禄迦国……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伽蓝数十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15)约公元7世纪,《华严经》传入以小乘为主的龟兹。《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②载:
圣历年中(699~701年),于阗三藏实叉难陀①云:“龟兹国中,唯习小乘,不知释迦分化百亿,现种种身云,示新境界,不信华严大经。有梵僧,从天竺将华严梵本至其国中。小乘师等,皆无信受。梵僧遂留经而归。小乘诸师,乃以经投弃于井,经于井中放光,赫如火聚。夜诸师覩之,疑谓金宝。至明集议,使人漉之。乃是前所弃华严经也。诸师稍为惊异,遂却入归经藏中龛安置。他日忽见梵本在其藏内最上隔。诸师念言:‘此非我释迦所说耶,吾见有少异,乃收入藏中。何人辄将向此上隔?’又以梵本置于下龛。僧众躬锁藏门,自掌钥钩。明日开藏,还见华严在其上隔。诸师方悟一乘大教威灵如此,惭悔过责,信慕渐生矣。”
《华严经感应传》专门收入各类感应灵异之事以宣讲华严,故事的讲述者实叉难陀本身就是华严经的积极传播者,经书撰写的目的性非常明显。而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华严神迹当然也极不可信。所以假设这个故事有什么参考价值的话,只能说它反映了这时龟兹地区仍然流行小乘佛教的情况(和上引昙无谶经历有些类似),并且大乘华严信仰可能在此时传入龟兹地区。文献中未注明故事发生的时间,暂时定在圣历年前一个世纪。
(16)公元671~691年,义净游学印度,记载小乘有部所分之部派在龟兹杂有行者。
《南海寄归内法传》载:
凡此所论,皆依根本说一切有部,不可将余部事见柔于斯。此与十诵大归相似。有部所分,三部之别:一法护、二化地、三迦摄卑。此并不行五天。唯鸟长那国,及龟兹、于阗,杂有行者。然十诵律亦不是根本有部也。
义净于咸亨二年(671年)泛海西行,游学印度。天授二年(691年),他遣人将其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带回汉地。故书中传闻当于此间记录。至于文中说到十诵律与根本有部的关系问题,现代佛学界认为义净所译之有部毗奈耶相当于十诵律之比丘、比丘尼戒法,而内容较十诵律广泛,多载录本生因缘故事。
(17)公元726年前后,龟兹僧利言通学大乘和小乘理论,包括东天竺传来之大乘佛法。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翻译经过时讲到:
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东天竺国人也。游中印度。亦称摩提国人焉。学通三藏,善达医明。利物随缘至龟兹国(正曰屈支),教授门人地战上湿罗(字布那羡,亦称利言①),使令记持梵本《大乘月灯三摩地经》满七千偈,及《历帝记》过一万偈,《瑜伽真言》获五千偈。一闻于耳,恒记在心。开元十四年(726年)受具足戒。自后听习律论、大小乘经、梵书汉书、唐言文字……。
(18)约公元727年,慧超路过作为安西大都护府之龟兹,见证龟兹本地僧人多习小乘,而汉族僧人习大乘。20世纪初,伯希和在敦煌石窟中找到一本失传已久的游记写本《往五天竺国传》①。在游记中,唐代旅行家——新罗僧人慧超如下写道:
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祇离国,此亦汉军马守促。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韮等。土人着叠布衣也。
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韮等也。汉僧行大乘法。
又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是汉军马领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
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都)维那,名义超,善解律藏,旧是京中庄严寺僧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
于阗有一汉寺,名龙兴寺。有一汉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
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崏州人士。又从安西东行□□至乌耆国,是汉军兵□领押。有王,百姓是胡。足寺足僧,行小乘法。
卷末云:“此即安西四镇名..一安西、二于阗、三疏勒、四乌耆”。可知慧超所云安西者,即指龟兹。故秀行、义超等人所驻之大云寺为龟兹大乘汉寺。但是这时龟兹依旧以小乘为主,过去与龟兹宗教属性倾向一致的疏勒和焉耆情况类似。
(19)约公元785~788年,旅行僧人悟空居住龟兹一年,请龟兹高僧勿提提犀鱼翻译他从南天竺携来的《十力经》。
唐圆照之《悟空入竺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载悟空先在北印度犍陀罗地区学习说一切有部,又南游中天竺诸国,求得梵本《十地经》、《回向轮经》和《十力经》,然后取道北路返回大唐,经于阗、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曰怖汗国)、据瑟得城之后。次至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捡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①。龟兹国王白环,正曰屈支城。西门外有莲花寺,有三藏沙门名勿提提犀鱼(唐云莲花精进)。至诚祈请,译出《十力经》,可三纸许以成一卷。三藏语通四镇,梵汉兼明。此《十力经》,佛在舍卫国说。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前践寺。复有耶婆瑟鸡山,此山有水滴溜成音,每岁一时采以为曲,故有耶婆瑟鸡寺。东西拓厥寺、阿遮哩贰寺。于此城住一年有余。悟空离开龟兹后在焉耆停留了三个月,然后到达北庭,请当地僧人翻译了《十地经》和《回向轮经》,然后于贞元五年(789年)随同唐北庭宣慰使等官员返朝。推测勿提提犀鱼在龟兹翻译《十力经》的时间应当在此前不久的贞元初期。霍旭初先生对这段事迹有专文考证,最后认为《十力经》属于阿含部(过去通常认为它属于密宗),勿提提犀鱼翻译此经不仅不能证明当地流行密宗,相反还可能为研究当时龟兹小乘佛教提供线索②。
(20)公元16世纪末,西域僧人锁喃嚷结旅行路过龟兹,见证当地佛教凋零。
《西域僧锁喃嚷结传》载其:“至跋禄迦国,名小沙迹,王名碧多。都城高广,人物集盛。唯有一寺,名阿奢理儿寺,宽广僧多,专学禅定,多游天竺。又东三千里,过屈支国,王号木文□多。宫殿整齐,人民男妇赤色,敬重三宝。多幻术。所□诸物华美,衣服精丽。使用金银钱。停住一年。又行东过阿耆尼国,多有银□山,金□山,高可百丈,光气腾曜,不可名状。贼寇极广,其人凶恶,惨杀无忌。”
锁喃嚷结“万历三十年(1602年)五月十五日启奉明肃皇太后命,住万寿庵”,其间在高昌和五台山等地还盘桓了至少四年,故推其路过龟兹的时间在公元16世纪末。尽管提到龟兹人敬重三宝,但描述语气与描述跋禄迦国的佛教情况已大不相同。又云此地多幻术。龟兹佛教这时可能已经大不如前了。
小结
上述名单中有8项史料明确含有小乘信息,另外有一项史料,438~504年龟兹僧直月使人醉酒得果之事,可推测其含有小乘信息(这份材料自羽溪了谛以来常常被当作大乘的证据被使用)。
共有9项史料把龟兹推向大乘。有8项史料明确含有大乘信息,另外有一项史料,4世纪末5世纪初大乘云游禅僧昙摩密多受到龟兹王礼遇,可推测其含有大乘信息。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一些僧人的大小乘都学习,游历的过程中往往根据当地需要讲经说法,例如佛图澄。并且受到礼遇的理由可能是非教派性的,譬如唐玄奘,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他就一路受到小乘高僧的礼遇,在龟兹当然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此说礼遇他的地区一定也流行大乘。
在8项明确含有大乘信息的史料中,刘宋时期龟兹法丰寺弟子书写《法华经》,和公元540年汉僧云启和天竺僧那连耶舍于龟兹合译禅宗《佛祖传法偈》,这两件史料笔者认为有作伪的嫌疑。公元393年,龟兹高僧昙摩跋檀应请口头翻译经典,似乎也应该排除掉大乘信息的因素。这样一来,真正能够体现龟兹大乘信息的就只剩下了5项。其中有3项属于7世纪到8世纪上半叶,大乘佛教在这段时间内突然活动频繁,可能和龟兹地区在被唐朝军队占领有关,一般认为这时汉地流行的大乘佛教随大军西向传入龟兹,这一点在库木吐喇确有清楚的体现。这时克孜尔石窟开始走向式微①。吴焯先生从克孜尔石窟遗存的破坏性题记出发,认为一些题记的上限应该是吐蕃于公元670年攻占安西以后二十二年内所写,这也是克孜尔石窟开始废弃的时间。而开元十四年(726年)到贞元十年(794年)的游人题字大都写在僧房内,说明此时僧房已经空无人住。一系列题记和出土文书表明克孜尔石窟相当一部分洞窟在此时已经废弃,而且作为临时的碛西节度使官方设置的关卡或过所②。笔者同意上述观点,且认为不妨考虑把克孜尔石窟初次遭到破坏的时间推早到公元647年前后③。《法苑珠林》提到唐朝军队攻陷龟兹时有过屠城毁寺之暴行,云:“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征龟兹。有萨孤训者,为行军仓曹参军。及屠龟兹城后,乃于精舍剥佛面取金。”④《法苑珠林》成书于总章元年(668年),说明在吐蕃攻占安西以前已经有破坏龟兹佛寺之传闻了。当然这种破坏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龟兹佛教并没有被完全摧毁,而是继续持续了很长时间。
剩下关于4~7世纪的大乘史料只有2项,公元370~384年鸠摩罗什在龟兹宣讲大乘,公元585年前后达摩笈多在龟兹王寺停住两年,龟兹王笃好大乘。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关于龟兹大乘的虚假情报?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不难发现它们的共性,就是其使用者往往有着共同的立场。它们的来源多是汉地倾向大乘的作家,其写作的立场免不了要向大乘偏移。例如如果能够说明法华经在那些遥远的西域佛国也受到欢迎,无疑能够加强对汉地民众的说服力。与之相比,关于龟兹小乘的史料则大都非常明确。不少来自旅行僧人的直接描述,内容要具体得多,且主角大多也是大乘僧人,事件常常涉及他们在小乘地区并不愉快的经历。看不出里面有夸大或捏造事实的动机。这些小乘史料从4世纪中叶开始延续到8世纪上半叶,它们大体上能够说明龟兹在并置于唐朝安西以前,是一个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地区。这当然也是多数学者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史料分布并不平均。4世纪中到5世纪初的史料,以及7~8世纪的史料略多,而几乎整个6世纪只有585年前后龟兹王好大乘的史料比较可靠。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史料如此之少。说龟兹在6世纪也以小乘为主,恐怕更多是推测其教派属性不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对此,学者们多少应该如履薄冰吧。看来要清楚全面地了解龟兹地区宗教属性,还有待于今后新材料的出现以及多方面的研究。
附注
①参见许宛音《龟兹事辑》(三),《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①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18~420页。
②慧皎着,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①冯承钧《再说龟兹白姓》载《女师大学术季刊》1931年2卷1期,引自《龟兹文化研究(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②白氏历史上有著名唐代诗人白居易。陈寅恪猜测白居易可能有龟兹血统,非谓白居易是龟兹人(陈寅恪《元白诗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7页)。《旧唐书》记载得非常明白,“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从北朝到唐代,其家族七代人都在中原政权作官(《旧唐书》列传第116。“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锽,历酸枣、巩二县令。锽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时李正己据河南十余州叛。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季庚说洧以彭门归国,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历衢州、襄州别驾。自锽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邽,今为下邽人焉”)。即使白氏真的起源于龟兹,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正如我们不能把美国黑人和他们的非洲表亲混为一谈。何况中国更早还有秦昭王帐下名将白起(一说出自姬姓),《史记》记载:“白起者,郿人也”(郿岐州县)(《史记》卷七十三列传十三)。白起担任左庶长的时候是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这个时候龟兹在什么地方?史学界追踪龟兹年,的历史,最早也只能到《汉书·西域传》之“渠犁国”条,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其王名绛宾。此外还有《续高僧传》载“释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帛姓,《汉书》卷九十四下载有侍中谒者帛敞、《后汉书》有渔浦侯帛意(注者引《韩非子》注之曰:“帛,姓也。宋帛产之后,韩非子也”)(《后汉书》列传第二,商务印书馆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第2719页)。《神仙传》还记载了一位道士帛和(葛洪《神仙传》卷七),此人后来被一个道教派别尊为“帛家道”的史祖。僧人方面,有《高僧传》载“帛法桥,中山人”。故白姓非帛姓,西来者概取读音近似则译,未必有一本译名词典作参考。龟兹白氏之译法,起初有向觉明(向达)提出可能渊源于龟兹白山,后冯承钧提出“白”可能是王号“Puspa”之音译。向觉明遂放弃原说,音译说遂为一致意见。然近有陈世良之新说,以为白乃龟兹文Pud—佛之音“”“”—译。(陈世良《龟兹白姓和佛教东传》,载《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公元2世纪下半叶以前,加入僧伽的人通常把自己原来的俗姓改成他们老师的姓,直到公元365~378年道安住在襄阳时,提倡把“释”作为所有僧人的姓氏,才改变这一习惯([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①霍旭初《考证与辩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①《阿惟越致遮经》四卷,西晋竺法护译,与《不退转法轮经》同本异译,摄于法华部。
②《弘赞法华传》载为:元嘉元年(424年)二月六日重复。
①咸和三年为公元328年,然《开元释教录》云咸安三年(373年),此处以早期文献为准。《开元释教录》载:“优婆塞支施仑。须赖经一卷、如幻三昧经二卷、上金光首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右四部六卷。优婆塞支施仑,月支人也,博综众经,特善方等。意存开化,传于未闻。奉经来游,达于凉土,张公见而重之,请令翻译。以咸安三年(373年)癸酉于凉州州内正应堂后,湛露轩下。出‘须赖’等经四部。龟兹王世子帛延传语。常侍西海赵潚、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三人笔受。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同在会证。凉州自属辞不加文饰也。出须赖经后记及首楞严经后记。”
②《弘赞法华传》凡十卷。唐代蓝谷沙门惠详撰。略称法华传。此书备载三国至中唐,有关法华经流传及研学、诵持法华经者所得之灵验事迹,多采传记体。内容分为图像、翻译、讲解、修观、遗身、诵持、转读、书写等八部分,图像系记载寺院、经像、宝塔等建造因缘;翻译乃论述真、伪经之译本及其异同;讲解、修观、遗身、诵持、转读、书写等,皆记述修学法华者之传记或感应。
①《法华传记》凡十卷。唐代僧详撰。本书大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内容大体采集唐玄宗以前有关《法华经》之人、书、事等文字,而汇为一书。
①霍旭初《考证与辩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①陈世良《鸠摩罗什年表考略》,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②陈世良《鸠摩罗什年表考略〉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8页。
①鸠摩罗什生平事迹主要来自《高僧传》和《出三藏记集》,然记载颇有不同。据《高僧传》,鸠摩罗什先在莎车接受了大乘,后回到龟兹。“时有莎车王子参军王子兄弟二人,委国请从,而为沙门。兄字须利耶跋陀,弟字须耶利苏摩。苏摩才伎绝伦,专以大乘为化,其兄及诸学者皆共师焉。什亦宗而奉之。亲好弥至,苏摩后为什说阿耨达经。什闻阴界诸入皆空无相,怪而问曰:此经更有何义而皆破坏诸法?答曰:眼等诸法非真实有。什既执有眼根,彼据因成无实,于是研核大小往复移时。什方知理有所归,遂专务方等,乃叹曰: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因广求义要受诵中百二论及十二门等。顷之随母进到温宿国。即龟兹之北界……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广说诸经”。
①《称扬诸佛功德经》凡三卷。北魏吉迦夜译。又称现在佛名经、诸佛华经、称扬诸佛经、集诸佛华经、集华经。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佛陀于经中自命本经经名为‘称扬诸佛功德法品’或‘集诸佛花’。经中列举诸佛世界及佛名,并赞叹其功德。上卷以东方天神世界之宝海如来为首,赞叹四十九佛之德;中卷赞叹南方真珠世界之日月灯明如来以下三十八佛之德;下卷赞叹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始之三佛及北方阿竭流香世界宝月光明如来为始之三佛,其次为上方宝月世界之金宝光明如来以下二十七佛之功德。
①《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卷下,《大正藏》第十四册,第104~105页。
②《六菩萨亦当诵持经》,《大正藏》第十四册,第752页。
①[法]列维“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1913年亚洲报),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65页。
②[法]伯希和“说吐火罗语”(1936年《通报》),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5页。
③陈世良《鸠摩罗什年表考略》,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④《佛学大词典》中【佛陀耶舍】条。
①《高僧传》载:“顷之王意稍歇待之渐薄,谶以久处致厌,乃辞往罽宾。赍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等。彼国多学小乘,不信涅槃,乃东适龟兹,顷之复进到姑臧,止于传舍。”
①北宋智圆之《涅槃玄义发源机要》卷第四载:“按译经图纪及僧传,并云昙无谶以玄始元年岁次壬子至姑臧,赍涅槃前分十卷,止于俗舍。逊闻谶名,厚遇请译,遂以玄始三年岁次甲寅起首,至玄始十年辛酉译经律,总二十三部,合一百四十八卷,慧嵩笔受。又南山涅槃弘传序云,北凉沮渠氏玄始三年,有天竺三藏昙无谶者,凉言法丰,赍此梵本前分十卷,来达姑臧。伪主蒙逊珍赏隆重,于凉城内闲豫宫中。前后三翻成四十卷,终宋武帝永初二年。”
②李安认为《高僧传》昙无谶纬玄始元年到姑臧之说不可信,其时间大约在北凉玄始十年(421年)——《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③阿阇梨,又作阿舍梨、阿阇梨、阿只利、阿遮利耶,略称阇梨,意译为轨范师、正行、悦众、应可行、应供养、教授、智贤、传授。意即教授弟子,使之行为端正合宜,而自身又堪为弟子楷模之师,故又称导师。据五分律卷十六、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载,阿阇梨有五种:(一)出家阿阇梨,受戒时之授十戒师,故又作十戒阿阇梨。(二)受戒阿阇梨,受具足戒时之羯磨师,故又作羯磨阿阇梨。(三)教授阿阇梨,受具足戒时之授威仪师,故又作威仪阿阇梨。(四)受经阿阇梨,教授经典读法、意义之师。(五)依止阿阇梨,与比丘共居,指导比丘起居之师;或比丘仅依止从学一宿之师,亦可称依止阿阇梨。以上五种加上剃发阿阇梨则为六种阿阇梨。西域另有一种称君持(水瓶、贤瓶)阿阇梨,乃灌顶之师。受具足戒时,须有三师、七证师等十位。三师,指得戒和尚、羯磨阿阇梨、教授阿阇梨。小乘受戒法必须有三师亲临;而大乘受戒法,根据观普贤经,得以释尊、文殊、弥勒像替代。如大乘圆顿戒,即以释尊为戒和尚,以文殊为羯磨阿阇梨,以弥勒为教授阿阇梨。另据大智度论卷十三载,在家众欲出家作沙弥、沙弥尼,必须要有戒和尚及阿阇梨,以此诸师比喻为出家父母。禅宗沙弥之受戒,必定有戒师、作梵阇梨(诵梵呗之师)以及引请阇梨(指导起居之师)参加。
④《大日本续藏经》收入梁宝唱《名僧传抄》卷二十五“齐高昌仙窟寺法惠传”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地点人物为“龟兹国金花寺帐下直月”,多一“寺”字。
①[日]羽西了谛着,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9页。
①四果,指小乘声闻修行所得之四种证果。其阶段依次为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或仅指第四之阿罗汉果。此外,《俱舍论》卷六列举之安立果、加行果、和合果、修习果等,亦称四果。
②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页。
③康法朗另有其人,见高僧传,晋中山康法朗(令韶);又有〈续高僧传〉载二法朗1.[梁]杨都建元寺沙门释僧韶传二(法朗):“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学知名。本姓沈氏。吴兴武康人”;2.[陈]杨都兴皇寺释法朗传二“释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
①后期的禅宗信徒认为《景德传灯录》所传之祖谱参考了唐《大唐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但《宝林传》出现晚于《景德传灯录》,其来源非常可疑,出现之时就已经被非禅宗学者所置疑。《景德传灯录》实际上是第一部禅宗史著作。
②即过去六佛(毘婆尸佛、尸弃佛、毘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所说偈语。
①除释迦外,二十三祖分别是:(1)迦叶、(2)阿难、(3)商那和修、(4)忧波鞠多、(5)提多迦、(6)弥遮迦、(7)佛陀难提、(8)佛陀蜜多、(9)胁比丘、(10)富那奢、(11)马鸣、(12)比罗、(13)龙树、(14)迦那提婆、(15)罗侯罗、(16)僧伽难提、(17)僧伽耶舍、(18)鸠摩罗驮、(19)阇夜多、(20)婆修盘陀、(21)摩奴罗、(22)鹤勒那夜奢、(23)师子比丘。
②宋契嵩《传法正宗论》卷首云:“隋唐来,达磨之宗大劝。而义学者疑之,颇执付法藏传以相发难,谓传所列但二十四世,至师子祖而已矣;以达磨所承者非正出于师子尊者,其所谓二,十八祖者,盖后之人曲说。禅者或引宝林传证之,然宝林亦禅者之书,而难家益不取。如此呶呶,虽累世无以验正。”
①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第777页。
①吕瀓《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8~309页。
①[法]列维“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1913年亚洲报),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7页。
②《如实论》全一卷。陈·真谛译。全称如实论反质难品。本书系以因明论式反驳外道论师之质难,并论证自家所说之如实。计分无道理难品、道理难品、堕负处品等三品。关于本书作者,高丽本不署撰号,诸经录亦缺撰者之名,唯宋、元、明三本题为世亲所造。
①见《佛学大词典》“世亲”条。
②《华严经感应传》全一卷。唐代胡幽贞刊纂。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本书原为法藏之弟子惠英编成二卷。建中四年(783年),四明山胡幽贞重新整理成一卷。内容为华严经信仰者之感应事迹,可作为唐代华严经信仰之研究资料。明代袜宏之华严经感应略记、清代弘璧之华严感应缘起传、清代周克复之华严经持验记,皆为同类著作。
①实叉难陀(652~710年),又作施乞叉难陀,译作学喜、喜学,为唐代译经三藏。于阗(新疆和阗)人。善大、小二乘,旁通异学。证圣元年(695年),持梵本华严经至洛阳,奉则天武后之命,与菩提流志、义净等,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共译成汉文,是即新译华严经八十卷。此外另译有大乘入楞伽经、文殊授记经等,凡十九部,一〇七卷。长安四年(705年)归国,后经再三迎请,于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再度来华,帝亲迎于郊外。未几罹疾,景云元年十月示寂,世寿五十九。
①利言,唐代僧,西域龟兹国人,名地战湿罗(意译真月),字布那羡。东印度沙门法月来游时,师与之相遇,遂从法月修习内外之学,曾闻梵本大乘月灯三摩地经七千偈、历帝纪一万偈、瑜伽真言五千偈,皆能心持不忘。开元十四年(726年)受具足戒,又广研大小乘经、梵书、汉书,乃至石城四镇、护密、战于、吐火罗之语言。开元十八年从其师东游,二十年入长安。为其师作译语,尝入宫中,以方药本草呈玄宗,又参与般若心经之翻译工作。开元二十九年与其师西归,时逢式匿国贼乱,道路壅塞,遂转入于阗。其师示寂后,归至故山。天宝十三年(754年)再度东游,次年二月入武威,住龙兴寺及报恩寺,助不空译经。贞元四年(788年)奉命任职译语,译业告终,进献朝廷而蒙赏赐。翌年又随侍般若三藏,任那罗延力经之翻译。其后不知所终。着有梵语杂名一卷。西明寺圆照集其遗文,作成翻经大德翰林待诏光宅寺利言集二卷。
①《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又名《往五天竺国传》、《慧超传》。系记录新罗僧慧超由唐入天竺之游记。原书三卷,惜早已佚失。现存本系法人伯希和(P.Peliot)于1908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抄写本残简,题名为《周历五天竺行程》。1910年由日人藤,田丰八注释公布,然内容前后均有缺落。
①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二,诏郭昕任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的时间在建中二年(781年)七月。
(②)霍旭初《唐代龟兹僧勿提提犀鱼汉译〈十力经〉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57页。
①VignatoGiuseppe(魏正中)认为石窟的第四期始于7世纪初,终于9世纪初。这也是唐朝位于龟兹的安西都护府始置时期。这一期除了在崖壁上可用的空余位置上开凿新窟外(大多数新寺在后山区开凿),还出现大量的洞窟改建、小窟和龛窟的增建现象。
②吴焯《克孜尔石窟兴废与渭干河谷道交通》,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02页。
③《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八年(644年)安西都护郭孝恪帅师灭焉耆,执其王突骑支送行在所。贞观二十二年(647年),昆山道总管阿史那社尔降处密、处月,破龟兹大拨等五十城,虏数万口,执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以归,龟兹平,西域震骇。二十三年春(649年),俘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等,献于社庙。
④[唐]释道世着,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53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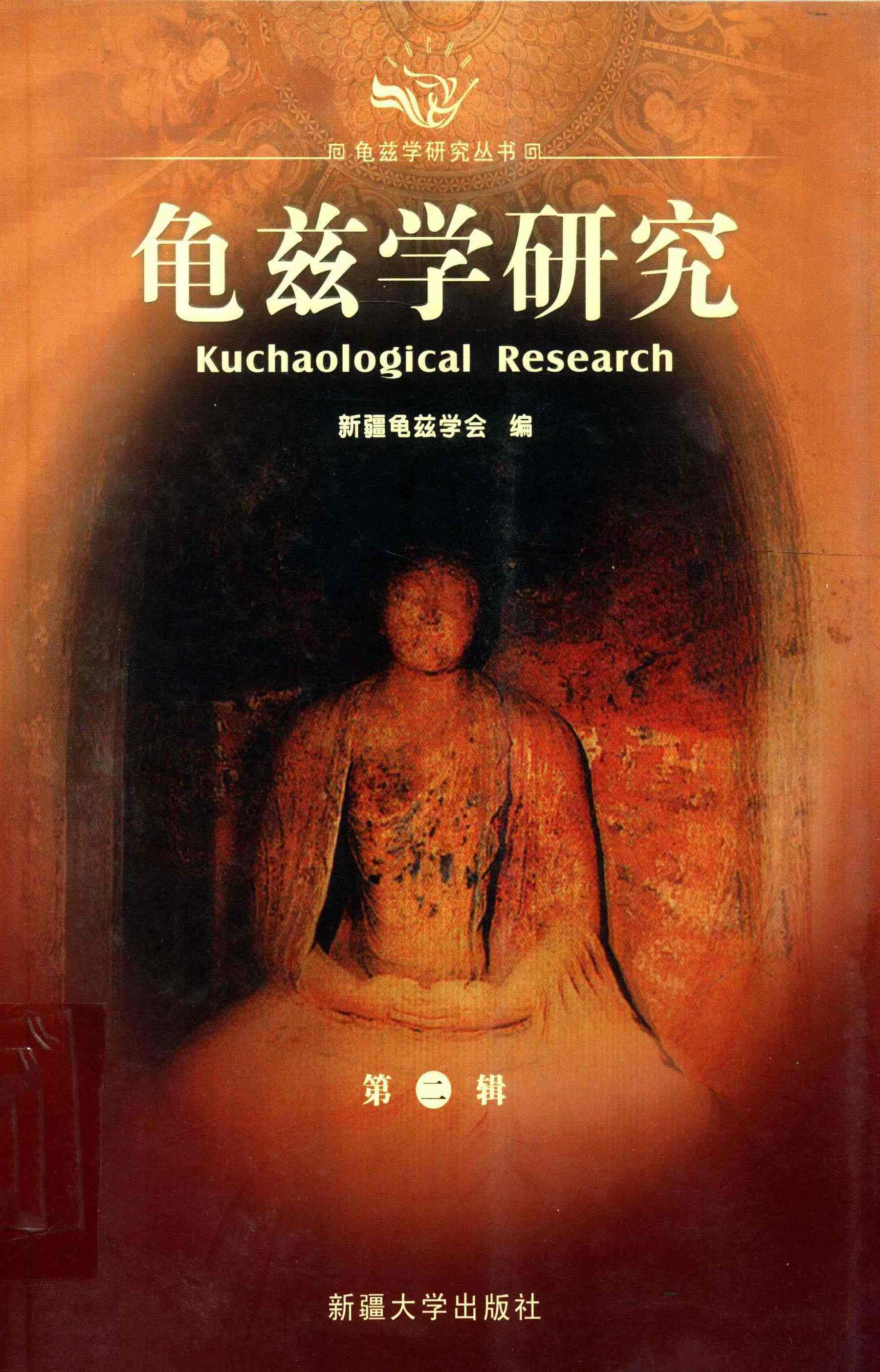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出版者:新疆大学出版社
本书所选论文分为“大家论坛”、“历史研究”、“考古探秘”、“佛教石窟”、“文化艺术”、“史料研究与情报”六个部分。新疆龟兹学会成立已三年有余了。三年来新疆龟兹学会抓了三件事:一是每年召开一次“龟兹学学术研讨会”。二是编辑出版新疆龟兹学会学术刊物《龟兹学研究》。三是进行《龟兹学概论》的编撰工作。
阅读
相关人物
任平山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