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地神
| 内容出处: |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462 |
| 颗粒名称: | 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地神 |
| 分类号: | K879.41 |
| 页数: | 21 |
| 页码: | 186-20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地神的基本情况。其中包含:“降魔成道”图中的地神、供养人脚下的地神。 |
| 关键词: | 龟兹石窟 壁画 地神 |
内容
佛教的地神,名叫坚牢,梵文名Prthivi。因其是佛教所谓的十二天之第十天,故又名地天。在佛教的万神殿中,地神的阶位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由于它曾在一些重大场合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因此在龟兹佛教美术中也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佛教神祗,很有专门研究的必要。目前,龟兹地区所见的地神形象均为壁画材料。依据其题材内容以及所处的位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1)“降魔成道”图中的地神。(2)供养人脚下的地神。关于第一类地神,虽已有前贤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①但笔者在本文中,乐于在基础材料、图像渊源以及图像和佛教典籍的关系诸方面再作一些补充论述,以使读者对本文的主题能够有一个完整全面的认识。至于第二类地神,目前笔者尚未见到专门的论述,因此在本文中拟主要以此为重点,着重就图像及其所反映出的佛教义理和世俗观念作一番探讨。以下就分别论述之,不当之处,请方家斧正。
一
“降魔成道”是记录释迦牟尼生平事迹,即所谓佛传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尽管各种佛传典籍在情节及文字表述上都不尽相同,但是在主要内容上实际是大同小异。其大意说,释迦太子离开王宫,经过六年苦修后,在菩提树下即将成道时,魔王率领魔军前来破坏。先是派妖艳的魔女诱惑不成,又派魔军进攻。释迦仍然无所畏惧。后来,释迦所作无数善行的见证者地神由地涌出作证,魔军溃败。正是经过这一环节,释迦太子才最终成就无上大觉,悟道成佛。因此,在早期佛教美术的佛传表现中,这一题材颇受重视。无论是所谓“四相”图(即树下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槃入灭)还是“八相”图(即降兜率天、乘象入胎、住胎说法、树下诞生、逾城出家、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槃入灭),均包含了这一题材。在龟兹石窟的“降魔成道”图中,出现地神这一要素的,见于克孜尔第76、99、110、175、198和205等窟。以下分别略述之。
第76窟。此窟是一个方形穹窿顶的洞窟。在窟内正壁和左右侧壁原绘连环画式佛传故事。据剥取壁画的“德国探险队”后来发表的资料,在右侧壁有两幅包含降魔题材的壁画。其中一幅,①可见佛陀结跏趺坐于方座上,右手结“触地印”。画面两侧可见奇形怪状的魔众正在向佛陀进攻。佛陀的左侧,魔王之子用双手紧抱其父,劝阻魔王不要破坏释迦成道。在佛座的正下方,可见一带头光的女神露出半身,双手合什。她就是此场面中的地神(见图版八,1)。
第98窟。此窟是一个中心柱纵券顶洞窟。在主室门道上方的半圆形端面上的壁画中,①中间可见释迦结跏跃坐于金刚座上,右手结“触地印”。释迦被魔军包围着。左侧同样可见魔王之子劝阻乃父。在佛座的下方,可见女性地神露出半身,双手合十(见图1)。
第110窟。此窟是一个方形纵券顶窟。在窟内正壁、左右侧壁遍绘佛传故事画,合计达60幅之多。在正壁上方的半圆端面上,绘一幅大型降魔图。据“德国探险队”公布的资料看,②图像部分残失,仅见释迦坐于中间,右手结“触地印”。四周是各种魔军在身着甲胄的魔王率领下,正在向释迦攻击。佛座下方,残存一双手合十的女性地神(见图2)。
第175窟。此窟是一个中心柱纵券顶洞窟。在主室门道上方的半圆形端面上,原有一幅降魔图。③据“德国探险队”公布的资料看,此图的左半部分已残失。现存的右半部分,可见释迦结跏趺坐于方座上,右手结“触地印”。周围可见魔军在魔王率领下,正在向释迦进攻。在佛座下可见露出半身,双手合十的女性地神。
第198窟。此窟是一个中心柱纵券顶洞窟。在其右甬道外侧壁上原存一幅降魔图,据日本学者中川原育子所介绍“德国探险队”的资料看,此画虽已大部分破损,但在释迦座位下,仍可确定有大地女神存在。①
第205窟。此窟是一个中心柱纵券顶洞窟。在该窟右甬道内侧壁上,原存一幅“阿阇世王闻佛涅槃昏厥复苏”的壁画。从“德国探险队”公布的资料看,其中有一个情节是行雨大臣手持一幅帛画向阿阇世王展示。②帛画上绘著名的“四相”图(树下诞生、初转法轮、降魔成道、涅槃入灭)。在“降魔成道”部分,虽然画面较前述的壁画内容更加简略,仅见释迦结跏趺坐于中间,右手结“触地印”。两侧可见几身魔众及一身魔王。即便如此,佛座下仍可见露出上半身双手合十的女性地神(见图3)。
以“降魔成道”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在印度出现较早,如在山奇大塔的第一塔北门横梁上的已出现这一题材的浮雕。但在印度的此类美术品中,真正出现地神的就较少了。两个确定的例子,一个是从萨尔纳特出土的浮雕,另一个是在阿旃陀第1窟的壁画中。这两身地神,均作手持水瓶的姿态,从文献来源看,可以对应《方广大庄严经》中的地神“曲躬恭敬捧七宝瓶,盛满香花以用供养”。①然而从图像看,和前述克孜尔壁画作品比较,显然它们应该出自另外不同的系统。
在犍陀罗,以“降魔成道”为题材的作品约有三十多例。但在这些作品中,地神都没有表现。引人注意的是,在佛传中“降魔成道”之前的另一个场景中却出现了地神。如在喀布尔博物馆所收藏的一块浮雕表现了准备菩提座、走向菩提座的佛陀。菩提座下可见一身女性露出上半身,双手合十。另外在喀拉卡它印度博物馆以及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所收藏的犍陀罗的浮雕作品中,也可见到类似的女性地神。单就图像而言,克孜尔壁画中的地神与犍陀罗浮雕中的同类作品非常相似,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由地面涌出、只露上半身的女性地神,是克孜尔由犍陀罗继承而来,进而成为构成当地降魔成道图的一个图像。①笔者对此也有同感。
关于前述克孜尔6幅“降魔图”所依据的佛教典籍,业经霍旭初和中川原育子两位学者作了非常精细的研究。综合总体画面及主要局部的细节,并参稽汉文佛经,目前已知与南朝宋求那跋陀罗所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中的记载最为接近。在关于魔王询问释迦以及地神由地踊出作证的细节上,该经记载:“魔语菩萨:‘我之果报,是汝所知。汝之果报,谁复知者?’菩萨答言:‘我之果报,唯此地知’。说此语已,于时大地,六种震动。于是地神,持七宝瓶,满中莲花,从地踊出,而语魔言:‘菩萨昔以头目髓脑,以施于人。所出之血,浸润大地。国城妻子象马珍宝,而用布施,不可称计。为求无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应恼乱菩萨。’魔闻是已,心生怖惧,身毛皆竖。时彼地神,礼菩萨足,以花供养,忽然不现。”②
《过去现在因果经》还另有两个异译本,即东汉竺大力与康孟祥合译的《修行本起经》和三国吴支谦所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在这三部关于佛传的典籍中,以《过去现在因果经》的记载,内容最为丰富全面。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将经文与克孜尔壁画对照时,仍然发现一些细节,如魔子劝阻乃父,不见于《过去现在因果经》,反而见于《修行本起经》和《太子瑞应本起经》。个中原因,霍旭初先生认为,西域所用佛经多为胡本,是以当地所用语言文字,即胡语翻译而来的。佛经在被汉译时,从梵译汉,从胡译汉,译经家“作了取舍、增损、改编以至发挥创造”,①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毕竟,用汉译佛经来比对龟兹佛教壁画,以求搜寻壁画绘制所依据的典籍,虽然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方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起到一种参考作用。
上述克孜尔的6幅降魔图所处洞窟开凿年代不同,建筑形制也不尽相类,壁画的位置、布局、表现形式及艺术风格也各异,但都体现出当地信众对这一佛传题材的推崇,反映了龟兹当地小乘佛教“唯礼释迦”的思想理念。尤其是克孜尔第99窟、110窟和175窟,降魔图被单独遴选出来,规划安置于洞窟上方显赫醒目的半圆端面上,须仰视才见,就更能给观者造成一种艺术上的震憾。在纷繁拥杂的画面上地神涌出的这一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如前所述,面对魔王的询问,释迦并未直接回答,而是招请地神出来作证。释迦无数善行的见证者地神的出现,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它“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为释迦牟尼成正觉的必然性作了最好的诠释”。②
二
第二类地神,即出现在供养人脚下的地神图像,见于克孜尔尕哈的第13窟和14窟。以下分别介绍之。
就建筑形制而言,克孜尔尕哈第13窟是一个中心柱窟。主室平面呈方形,纵券顶。主室正壁左右两侧中下方各开一甬道与后甬道相通,甬道纵券顶。主室正壁开龛,其中原来安置有主尊像;左右侧壁残存有佛说法图;前壁左右两侧各绘有4身供养人像;门道上方的半圆端面壁画大部分脱落;券顶绘有菱格因缘故事画;左甬道外侧壁绘本生故事,内侧壁壁画脱落;右甬道外侧壁绘本生故事,内侧壁绘4身供养人像;后甬道前壁绘焚棺场面,正壁壁画大部分脱落。
在第13窟内,仅现存的供养人像即达12身之多,显然这是一个由家族出资建造的洞窟。在本窟众多的供养人像中,尤以右甬道内侧壁前两身供养人像最为引人注目。它们均已残破,仅可见下半身部分。第一身供养人,可见由长袍下沿伸的腿,双腿以脚尖着地,是龟兹供养人常见的供养姿势。在其两腿之间,可见一身形体较小人物的上半身像。这身人物头顶有球形发髻,脸部的两颊有浓密的落腮胡须。他上身裸露,由双肩两侧垂下披帛缠绕在双臂上。这身人物双手曲臂,两手掌托举着上方供养人的双足。结合其脑后所具有圆形头光判定,这是一身男性地神像(见图4)。第二身供养人,仅存下半身的小腿,同样是双腿以脚尖着地的姿势站立。在其两腿之处,也可见一身形体较小人物的上半身像。此像戴头巾,头顶凸起的球形似为发髻,上身着无袖的短衣,自双肩两侧垂下的披帛缠绕在手臂上。这身人物也是双手曲臂托举着上方供养人的双足。此像脑后有圆形头光,从衣着及耸起的胸部特征推断,这是一身女性地神(见图5)。
第14窟位于13窟的右侧,两窟隔墙毗邻,同处于第10至15窟这一组洞窟的中心位置。第14窟也是一个中心柱窟,建筑形制与第13窟大致相同。其主室正壁开龛,其中原来安置有主尊像;左右侧壁残存有佛说法图和本生故事;前壁右侧残存2身供养人像;门道上方的半圆端面绘“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壁画;券顶绘有菱格因缘故事画;左甬道外侧壁绘本生故事,内侧壁绘4身供养人像;右甬道外侧壁绘本生故事,内侧壁绘4身供养人像;后甬道前壁绘焚棺场面,正壁绘“八王争分舍利”壁画。如上所述,本窟的供养人像同样数量不菲,现存的达到12身。在14窟的右甬道内侧壁上残存4身龟兹供养人像中,靠前的两身男性供养人像大部分形体保存较好。它们脑后均具圆形头光,身穿华丽的衣着,系腰带,挎长剑。这两人右手叉腰,左手持香炉,双腿脚尖着地而立。在两身供养人的双腿间,均见一身形体较小人物的上半身像①。无论是从衣着还是从形体姿势看,都与13窟中的女性地神酷似,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两身像也应是女性地神(见图版八,2)。
在西域范围,从图像比对看,与上述地神形象最为接近的当属在于阗地区发现的同类资料。①于阗的地神美术品主要见于以下五个遗址点:(1)热瓦克。在热瓦克大塔四周围墙上塑有多尊佛和菩萨像,在佛像的两脚间另塑有小型地神像,斯坦因说:“离大门再远一点的两尊塑像中,每一尊的双足之间各发现一身较小的女性胸像..它们显然全都相同。”②另外在东墙大门旁所塑四身天王像中,斯坦因编号为ⅩⅩⅤⅡ和ⅩⅩⅤⅢ的两身的双脚间也各见一身塑出的小型地神像。(2)和田县布盖乌于来克佛寺遗址。在该遗址内一个正方形殿堂的壁画中,残存两身大立佛的下半身。其中一身,两脚分立于两朵莲花上。在佛的两脚之间,绘一身跪姿合掌礼敬的女性。该女性脑后放射出十几条波浪式光芒,应是一身地神(见图6)。另一身非常残破,但仍可见跪在佛脚侧的地神。(3)策勒县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在方形平面的遗址中,在正壁泥塑有结跏趺坐于莲台上的佛像。在此塑像左侧又所绘一身立佛的两脚间以及左侧壁所绘另一身立佛的两脚间,各绘出一身地神像。它们双臂伸展,两手托持佛脚。(4)策勒县巴拉瓦斯特佛寺遗址。20世纪初末,德国人特林克勒(Trinkler)在遗址中发现一块壁画。其上绘一地神跪在佛的两脚间,两手托持佛脚(见图7)(5)策勒县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特林克勒在编号为A.4.2的寺院中还发现了一个地神图像。画面虽已十分残破,但我们仍可见在佛两脚间残存了地神胸部以下。它双膝跪地,两臂平举,手托佛脚。2002年,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共同考察丹丹乌里克遗址时,发现一座寺院遗址。在遗址壁画中,又出现了两身地神形像。其一是男性。他身着套头小翻领上衣,脸部有髭,颌下有长须,两颊留络腮胡。此地神仅现上半身,他以双手托举立在莲花上的佛脚;另一身是女性。她身着艳丽有纹饰的外衣,仅现上半身,以双手托举也在莲花上的另一立佛的脚。①
此外,在敦煌也发现地神的壁画、幡画和纸画等多幅作品。②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题材内容均与于阗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莫高窟第98窟的壁画。在此窟的前壁保存有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供养像,在此像的两脚之间赫然可见一身地神。地神脑后有圆形头光,仅现出上半身,双手平伸,托持上方李圣天的双足(见图8)。③
从以上的对比叙述看,即使不算敦煌,就第二类地神图像数量规模及分布地点而言,于阗分见于五处遗址,共有7个,龟兹只见于一处遗址,只有4个,前者多于后者;再就图像的年代而言,于阗诸遗址中的丹丹乌里克早到4~5世纪,④库车克孜尔尕哈的第13、14窟约为6~7世纪建造,①前者也早于后者。由此可见,较之龟兹,第二类地神的美术品在于阗当地出现更早,也更为流行。
龟兹和于阗两地同处天山南路,其间虽有沙漠相隔,但自古即有道路相通。两地又同为西域著名的佛国。小乘说一切有部盛行于龟兹,同时也见于于阗,②所以很早以来,两地的佛教及其艺术就存在相互影响的联系。据《高僧传》的记载,定林寺僧法献在宋元徽三年(475年)由金陵出发,“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观世音灭罪呪及调达品。又得龟兹国金锤鍱像。于是而还”。③唐代高僧玄奘由印度返回中土途中,在于阗王城西南十余里的地迦婆缚那伽蓝中,见寺内“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国而来至止”。④屈支国即龟兹国。唐代不空三藏所译的《毗沙门天王仪轨》中曾记有一个故事:唐天宝元年(742年),大石、康等五国围攻安西城。由于请得了北方毘沙门天王神兵相助,“五国大惧,尽退军。抽兵诸营坠中,并是金鼠咬弓弩弦及器械损断,尽不堪用..反顾城北门楼上有大光明,毘沙门天王见身于楼上,其天王神样”。⑤撇开这则故事中光怪陆离的无稽之处,不去论其可信度,我们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于阗佛教文化对龟兹的影响。因为毗沙门天王信仰和于阗王族有着密切联系,⑥而且,金鼠咬断敌军弓弦及器械之事也来源于于阗当地的鼠壤坟传说。⑦凡此种种,可证两地在佛教文化上有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认定,克孜尔尕哈的地神在图像表现上是受到了于阗同类作品的影响,其源头应在于阗。
三
于阗之盛行地神信仰,决非偶然,乃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大唐西域记》在言及于阗建国时记载了一个传说,“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毘沙门天之祚胤也..其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往毘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
至成立。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自兹已降,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故今神庙多诸珍宝,拜祠享祭,无替于时。地乳所育,因为国号”。①内容大同小异的传说,在8世纪以后的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牛头山授记》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于阗国教法史》中也有记载。②从上述记载看,于阗王族自认毗沙门天是其父系,大地女神是其母系,从中折射出他们对地神的尊崇。虽然佛教的地神信仰出现较早,但在印度和中亚,地神的美术品中并不多见,甚至罕见这种双手托举佛、天王和供养人双足的这类美术品。③在此,我们可以说,佛教的地神信仰传播到于阗后,与当地的民间神话传说相结合后,地神崇拜意外地被发扬光大了。
述及地神的佛教典籍,主要有《佛本行集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方广庄严经》、《观佛三味经》、《禅秘要法经》、《金光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华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据松本文三郎、贾应逸等先生研究,于阗的地神形象主要是根据上述诸经中的《金光明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坚牢地神品》绘制的。①
《金光明经》是北凉时昙无谶所翻译的一部佛经。此经的结构分为四卷,计十八品。在《金光明经》被整部译出前,已有片断的单品被译出。北凉本问世后,先后有真谛、耶舍崛多和阇那崛多对其进行改订或补译。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沙门宝贵又综合各家译本,删同补缺成为《合部金光明经》八卷,计二十四品。武周长安三年(703年)由义净译出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计三十一品,不仅品目义理最为完备,而且译文华质得中,因而后来成为通行的本子。
《金光明经》品目较多,内容庞杂,②据说“是经能灭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百千苦恼”,③故被称为“众经之王”。在此经卷二的《坚牢地神品》中记载,地神坚牢闻佛说《金光明经》后,深感此经的微妙,乃发下大誓愿,“若现在世,若未来世,在在处处。若城邑聚落,若山泽空旷,若王宫民宅..随是经典所流布处,是地分中敷狮子座。令说法者坐其上,广演宣说是妙经典,我当在中常作宿卫,隐蔽其身于法座下,顶戴其足..(使)阎浮提内药草树木根茎枝叶华果滋茂,美我香味,皆悉具足;众生食已,增长寿命”。④从这段记载可知,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演讲《金光明经》者,坚牢地神都愿常作宿卫,顶戴其足。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佛教美术品中,不仅是佛陀,而且还有发愿要“能说正法,修行正法”的天王们,甚至包括人间的君王们,在他们的脚下就自然出现了坚牢地神的形像。就目前所见材料,除布盖乌于来克佛寺所见地神作合掌礼敬姿势外,其余皆作两手托举上方人物双足的姿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巴拉瓦斯特佛寺院的相关壁画可以看出,明显是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绘制的。该经《序品》中的一段偈颂说,佛在王舍城灵鹫山演说此经时,“护世四天众,及大臣眷属,无量诸夜叉,一切皆拥卫。大辩才天女,尼连河水神,诃里底母神,坚牢地神众,梵王帝释主、龙王紧那罗,及金翅鸟王,阿修罗天众,如是天神等,并将其眷属,皆来护是人,昼夜常不离。”①如前所述,从德人特林克勒所拼出的线描图上看,除了两臂平伸,双手托持佛脚,顶戴佛足的坚牢地神外,还残存帝释天的半身像,摩酼首罗天和双手持鱼的尼连河水神等。
关于图像中地神的性别,从形象及衣着上看,绝大多数,包括“降魔变”中由地涌出作证的地神,都是女性。这一现象与《金光明经》中佛称呼坚牢地神为“善女天”②及《金光明最胜王经》中所记“尔时此大地神女,名曰坚牢”③相吻合。但是,如前所述,在于阗丹丹乌里克和克孜尔尕哈第13窟中还各发现一身男性地神。对于这一奇异的文化现象,有学者从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角度,认为丹丹乌里克“借用了民间祭祀的土地神形象..老翁式的地神很可能是受到中原道教的影响。”④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地神分为男女两性的观念或许在古代印度就已有其萌芽了。
玄奘在摩揭陀国曾见一个砖室内绘有两身地神像,“迦叶波佛精舍西北二砖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来将成正觉,一报魔至,一为佛证。后人念功,图形旌德”。⑤由这段文字,可知这两身地神像的来历,乃是后人感念地神在释迦牟尼降魔成道时所立之功而绘。玄奘还生动记载了这段传说故事,“昔如来之将证佛果,天魔来娆,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来告曰:‘汝勿忧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谁为明证?’如来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证’。是时第二地神踊出作证。”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故事与我们常见的佛典中降伏魔众的记录,如南朝宋求那跋陀罗所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差异。后者仅记有一地神涌出作证的情节,在前述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只见一身地神在佛座下现出上半身。与此不同,前者所言地神的数量已是复数的两身了。可惜,玄奘没有对他所见摩揭陀国砖室内的二地神作进一步描述,语焉不详。我揣测,这两身地神像可能并不相同,而是有差异的。从其职能分工不同看,作证的地神,正如我们在前面“降魔图”中所见,会以女性形像表现,而另一助佛降魔的地神,很可能会以男性形像表现。
在发现有众多地神美术品的于阗地区,实际上当地的佛教思想理念中关于地神的类别就不是单一的。集成于于阗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的《世主妙严品》中就列举了多位地神的不同名号,“复有佛世界微尘数主地神,所谓普德净华主地神、坚福庄严主地神、妙华严树主地神、普散众宝主地神、净目观时主地神、妙色胜眼主地神、香毛发光主地神、悦意音声主地神、妙华旋髻主地神、金刚严体主地神。如是等而为上首。”①在此,地神显然已被视为一个群体而非个体了。因此,就总体情况而言,我倾向于男性地神形象的出现最有可能还是肇始于于阗。
四
如前所述,在龟兹、于阗两地不约而同出现了地神由地涌出,双手托持王族供养人的图像,这直观地反映出两地君王对《金光明经》的青睐有加。个中原因,固然与此经宣扬维护镇守国家,救护世间有很大关系,如在《四天王品》中,毘沙门天王、提头赖咤天王、毘留勒叉天王和毘留博叉天王就直白的发愿说:“世尊,如诸国王所有土境,是持经者若至其国,是王应当往是人所听受如是微妙经典。闻已欢喜复当护念恭敬是人。世尊,我等四王,复当勤心拥护是王及国人民,为除衰患令得安隐。世尊,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是经,若诸人王有能供给施其所安,我等四王,亦当令是王及国人民一切安隐,具足无患。世尊,若有四众受持读诵是妙经典,若诸人王有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等四王,亦复当令如是人王于诸王中常得第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令余王钦尚羡慕,称赞其善..世尊,若有人王,欲得自护及王国土多受安乐,欲令国土一切众生悉皆成就具足快乐,欲得摧伏一切外敌,欲得拥护一切国土,欲以正法正治国土,欲得除灭众生怖畏,世尊,是人王等,应当必定听是经典。”①佛也宣教于四天王说:“若有人王能供养恭敬此金光明微妙经典,汝等正应如是护念,灭其苦恼,与其安乐。”②但是,就这些王族供养人自身而言,应有更深层面的缘由。
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曾在库车地区发现大量古文字写本残卷,其中在一份犍陀罗语、龟兹语双语文书上,语言学家发现了龟兹国王有一个“Devaputra”的头衔称呼。③无独有偶,这一称呼还见于于阗文书。④“Devaputra”一词,其词根Deva,在佛教术语中意为“天”,而该词完整意义的直译为“天子”⑤或“天神之子”。在中亚地区,“Devapu-tra”的称号最早出现在贵霜王朝诸王对自己的称呼中。首先是丘就却,随后被迦腻色迦等国王使用。而使用这一称号的诸王们,显然是想神化自我并使王权合法化。但是,如果“Devaputra”仅仅是一种自我称呼,肯定难以令他人心悦诚服。“为了与天子(Devaputra)观念保持一致,贵霜人还建立了神庙(Devakula),把死去的国王即天子们的塑像置于其中”。⑥另外,贵霜钱币上所描绘的国王像,其肩部还向上冒出火焰,“这样做更增加了国王的合法性和神圣性”。⑦然而,真正在理论上使国王权威和权力的来源合法化的,恰恰是大乘佛典《金光明经》中有关“天子”这一概念的系统完整、圆满合理的阐释。据该经《正论品》中的记载,佛为坚牢地神宣讲的故事中,有名为力尊相的国王為其子信相所說的偈言里有如下内容:“云何是人,得名为天?云何人王,复名天子?因集业故,生于人中,王领国土,故称人王;处在胎中,诸天守护,或先守护,然后入胎。虽在人中,生为人王。以天护故,复称天子。三十三天,各以己德,分与是人,故称天子。神力所加,故得自在。”①在这段偈颂中,以问答的方式,虽然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依佛陀之口宣扬了人主身份所具有的“天子”神格。对人主的神化,无形中提供了一种君王们梦寐以求的“王权天授”的政治理念。毫无疑问,《金光明经》中的这段偈颂文字内容,对于身为人主的君王们一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续高僧传》记载,隋大业五年(609年),帝西巡,高僧慧乘陪同前往,“从驾张掖。蕃王毕至。奉勅为高昌王麹氏讲金光明..闻者叹咽”。时为高昌王的麹伯雅听讲后,甚至“布发于地,屈乘践焉”。②《金光明经》对他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龟兹国王看来不仅由贵霜王朝借来了“Devaputra”的称号,而且在佛教石窟中描绘自己供养人像的手法也与后者如出一辙。在已知的龟兹国王供养人像中,③脑后均画出圆形的头光——一种佛教绘画中只有“天”(Deva)及其以上阶位的神祗才具有的图像特征。而前述的克孜尔尕哈的第13、14窟中的供养人像,不仅在脑后画出了头光,而且还在双脚间画上了托持双足的地神,更是极尽神化渲染之能事。
最后探讨一下《金光明经》在龟兹王族中传播、影响的可能性。众所周知,龟兹长期以来盛行小乘说一切有部,而《金光明经》却是一部大乘佛典。此经若能在龟兹的流传,一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认为,主要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大力倡导大乘佛学有密切的关系。据《高僧传》等史籍记载,罗什是初习小乘,后因机缘巧合,又改宗大乘。由于他本人深厚的佛学造诣和崇高的声望,加之龟兹王族又不遗余力地推崇,终使大乘佛教可以在原先小乘佛教占统治地位的龟兹登堂入室,逐渐流传开来。①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前秦将军吕光以兵迎罗什至凉州。但是,此后龟兹本地的大乘佛教并未就此急剧式微。相反,从一些迹象看,它仍保持着一股发展的余势。公元394年,兼通大小乘的龟兹高僧昙摩跋檀在龟兹金华祠译出大乘典籍《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②在北魏太武帝灭佛时,从大乘佛法盛行的高昌避乱至龟兹的沙门法朗就受到龟兹国王之礼遇,后圆寂于此。③公元585年,南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路经龟兹,被当地笃好大乘的国王所挽留,停住两年,为僧众讲说《说(念)破论》,《如实论》。④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就曾据上述记载推断说:“罗什以后达摩笈多时代之龟兹国王,皆寄心大乘教。”⑤近年来,学者对龟兹石窟壁画的研究时也发现其中混杂有反映大乘佛教思想的题材内容,从一个侧面可证此言不虚。⑥克孜尔尕哈第13、14窟中均出现带有头光的王族供养人,而这两个洞窟的开凿年代约为6~7世纪,恰好就在龟兹国王推崇大乘佛教的这一重要时期。
目前,关于《金光明经》的版本,除了前述汉文译本外,在尼泊尔还保存有完整的梵文本,其内容与北凉昙无谶的汉文译本大同小异。另外,《金光明经》尚有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藏文和蒙文等多个语种译本。据《高僧传》的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的中天竺僧人摄摩腾在来华前,就曾“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①可见此经的梵本很早就已在流传。尽管现在还没有发现龟兹文本的《金光明经》,但是考虑到此经的译者昙无谶在河西的姑臧译出此经前曾携带不少佛经在龟兹停留,②而后来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庄严菩提心经》即是《金光明经·最净地陀罗尼品》的异译本,所以还不能完全排除将来有所发现的可能性。何况,龟兹王族中还流行使用梵文,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梵语在当时的西域,以及印度本国,也同法语(在欧洲)一样,被认为是有文化的语言。龟兹,也有焉耆,王廷使用梵语,以显示自己的高贵”。③因此,他们还可能直接阅读梵文本的《金光明经》。
总之,通过对龟兹石窟壁画中地神形象的考察分析,一方面,我们从中可以管窥龟兹佛教美术对外交流互动的一些情形;另一方面,透过一些地神作品的表像,我们还能够发现其中所反映出的龟兹王族神化自我,试图宣扬一种“王权天授”的政治理念。
(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承蒙贾应逸、霍旭初两位先生悉心指点,王志兴为本文绘制了线描图,在此谨致谢意。)
(作者: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
“降魔成道”是记录释迦牟尼生平事迹,即所谓佛传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尽管各种佛传典籍在情节及文字表述上都不尽相同,但是在主要内容上实际是大同小异。其大意说,释迦太子离开王宫,经过六年苦修后,在菩提树下即将成道时,魔王率领魔军前来破坏。先是派妖艳的魔女诱惑不成,又派魔军进攻。释迦仍然无所畏惧。后来,释迦所作无数善行的见证者地神由地涌出作证,魔军溃败。正是经过这一环节,释迦太子才最终成就无上大觉,悟道成佛。因此,在早期佛教美术的佛传表现中,这一题材颇受重视。无论是所谓“四相”图(即树下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槃入灭)还是“八相”图(即降兜率天、乘象入胎、住胎说法、树下诞生、逾城出家、降魔成道、初转法轮、涅槃入灭),均包含了这一题材。在龟兹石窟的“降魔成道”图中,出现地神这一要素的,见于克孜尔第76、99、110、175、198和205等窟。以下分别略述之。
第76窟。此窟是一个方形穹窿顶的洞窟。在窟内正壁和左右侧壁原绘连环画式佛传故事。据剥取壁画的“德国探险队”后来发表的资料,在右侧壁有两幅包含降魔题材的壁画。其中一幅,①可见佛陀结跏趺坐于方座上,右手结“触地印”。画面两侧可见奇形怪状的魔众正在向佛陀进攻。佛陀的左侧,魔王之子用双手紧抱其父,劝阻魔王不要破坏释迦成道。在佛座的正下方,可见一带头光的女神露出半身,双手合什。她就是此场面中的地神(见图版八,1)。
第98窟。此窟是一个中心柱纵券顶洞窟。在主室门道上方的半圆形端面上的壁画中,①中间可见释迦结跏跃坐于金刚座上,右手结“触地印”。释迦被魔军包围着。左侧同样可见魔王之子劝阻乃父。在佛座的下方,可见女性地神露出半身,双手合十(见图1)。
第110窟。此窟是一个方形纵券顶窟。在窟内正壁、左右侧壁遍绘佛传故事画,合计达60幅之多。在正壁上方的半圆端面上,绘一幅大型降魔图。据“德国探险队”公布的资料看,②图像部分残失,仅见释迦坐于中间,右手结“触地印”。四周是各种魔军在身着甲胄的魔王率领下,正在向释迦攻击。佛座下方,残存一双手合十的女性地神(见图2)。
第175窟。此窟是一个中心柱纵券顶洞窟。在主室门道上方的半圆形端面上,原有一幅降魔图。③据“德国探险队”公布的资料看,此图的左半部分已残失。现存的右半部分,可见释迦结跏趺坐于方座上,右手结“触地印”。周围可见魔军在魔王率领下,正在向释迦进攻。在佛座下可见露出半身,双手合十的女性地神。
第198窟。此窟是一个中心柱纵券顶洞窟。在其右甬道外侧壁上原存一幅降魔图,据日本学者中川原育子所介绍“德国探险队”的资料看,此画虽已大部分破损,但在释迦座位下,仍可确定有大地女神存在。①
第205窟。此窟是一个中心柱纵券顶洞窟。在该窟右甬道内侧壁上,原存一幅“阿阇世王闻佛涅槃昏厥复苏”的壁画。从“德国探险队”公布的资料看,其中有一个情节是行雨大臣手持一幅帛画向阿阇世王展示。②帛画上绘著名的“四相”图(树下诞生、初转法轮、降魔成道、涅槃入灭)。在“降魔成道”部分,虽然画面较前述的壁画内容更加简略,仅见释迦结跏趺坐于中间,右手结“触地印”。两侧可见几身魔众及一身魔王。即便如此,佛座下仍可见露出上半身双手合十的女性地神(见图3)。
以“降魔成道”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在印度出现较早,如在山奇大塔的第一塔北门横梁上的已出现这一题材的浮雕。但在印度的此类美术品中,真正出现地神的就较少了。两个确定的例子,一个是从萨尔纳特出土的浮雕,另一个是在阿旃陀第1窟的壁画中。这两身地神,均作手持水瓶的姿态,从文献来源看,可以对应《方广大庄严经》中的地神“曲躬恭敬捧七宝瓶,盛满香花以用供养”。①然而从图像看,和前述克孜尔壁画作品比较,显然它们应该出自另外不同的系统。
在犍陀罗,以“降魔成道”为题材的作品约有三十多例。但在这些作品中,地神都没有表现。引人注意的是,在佛传中“降魔成道”之前的另一个场景中却出现了地神。如在喀布尔博物馆所收藏的一块浮雕表现了准备菩提座、走向菩提座的佛陀。菩提座下可见一身女性露出上半身,双手合十。另外在喀拉卡它印度博物馆以及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所收藏的犍陀罗的浮雕作品中,也可见到类似的女性地神。单就图像而言,克孜尔壁画中的地神与犍陀罗浮雕中的同类作品非常相似,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由地面涌出、只露上半身的女性地神,是克孜尔由犍陀罗继承而来,进而成为构成当地降魔成道图的一个图像。①笔者对此也有同感。
关于前述克孜尔6幅“降魔图”所依据的佛教典籍,业经霍旭初和中川原育子两位学者作了非常精细的研究。综合总体画面及主要局部的细节,并参稽汉文佛经,目前已知与南朝宋求那跋陀罗所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中的记载最为接近。在关于魔王询问释迦以及地神由地踊出作证的细节上,该经记载:“魔语菩萨:‘我之果报,是汝所知。汝之果报,谁复知者?’菩萨答言:‘我之果报,唯此地知’。说此语已,于时大地,六种震动。于是地神,持七宝瓶,满中莲花,从地踊出,而语魔言:‘菩萨昔以头目髓脑,以施于人。所出之血,浸润大地。国城妻子象马珍宝,而用布施,不可称计。为求无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应恼乱菩萨。’魔闻是已,心生怖惧,身毛皆竖。时彼地神,礼菩萨足,以花供养,忽然不现。”②
《过去现在因果经》还另有两个异译本,即东汉竺大力与康孟祥合译的《修行本起经》和三国吴支谦所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在这三部关于佛传的典籍中,以《过去现在因果经》的记载,内容最为丰富全面。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将经文与克孜尔壁画对照时,仍然发现一些细节,如魔子劝阻乃父,不见于《过去现在因果经》,反而见于《修行本起经》和《太子瑞应本起经》。个中原因,霍旭初先生认为,西域所用佛经多为胡本,是以当地所用语言文字,即胡语翻译而来的。佛经在被汉译时,从梵译汉,从胡译汉,译经家“作了取舍、增损、改编以至发挥创造”,①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毕竟,用汉译佛经来比对龟兹佛教壁画,以求搜寻壁画绘制所依据的典籍,虽然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方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起到一种参考作用。
上述克孜尔的6幅降魔图所处洞窟开凿年代不同,建筑形制也不尽相类,壁画的位置、布局、表现形式及艺术风格也各异,但都体现出当地信众对这一佛传题材的推崇,反映了龟兹当地小乘佛教“唯礼释迦”的思想理念。尤其是克孜尔第99窟、110窟和175窟,降魔图被单独遴选出来,规划安置于洞窟上方显赫醒目的半圆端面上,须仰视才见,就更能给观者造成一种艺术上的震憾。在纷繁拥杂的画面上地神涌出的这一细节,非常耐人寻味。如前所述,面对魔王的询问,释迦并未直接回答,而是招请地神出来作证。释迦无数善行的见证者地神的出现,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它“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为释迦牟尼成正觉的必然性作了最好的诠释”。②
二
第二类地神,即出现在供养人脚下的地神图像,见于克孜尔尕哈的第13窟和14窟。以下分别介绍之。
就建筑形制而言,克孜尔尕哈第13窟是一个中心柱窟。主室平面呈方形,纵券顶。主室正壁左右两侧中下方各开一甬道与后甬道相通,甬道纵券顶。主室正壁开龛,其中原来安置有主尊像;左右侧壁残存有佛说法图;前壁左右两侧各绘有4身供养人像;门道上方的半圆端面壁画大部分脱落;券顶绘有菱格因缘故事画;左甬道外侧壁绘本生故事,内侧壁壁画脱落;右甬道外侧壁绘本生故事,内侧壁绘4身供养人像;后甬道前壁绘焚棺场面,正壁壁画大部分脱落。
在第13窟内,仅现存的供养人像即达12身之多,显然这是一个由家族出资建造的洞窟。在本窟众多的供养人像中,尤以右甬道内侧壁前两身供养人像最为引人注目。它们均已残破,仅可见下半身部分。第一身供养人,可见由长袍下沿伸的腿,双腿以脚尖着地,是龟兹供养人常见的供养姿势。在其两腿之间,可见一身形体较小人物的上半身像。这身人物头顶有球形发髻,脸部的两颊有浓密的落腮胡须。他上身裸露,由双肩两侧垂下披帛缠绕在双臂上。这身人物双手曲臂,两手掌托举着上方供养人的双足。结合其脑后所具有圆形头光判定,这是一身男性地神像(见图4)。第二身供养人,仅存下半身的小腿,同样是双腿以脚尖着地的姿势站立。在其两腿之处,也可见一身形体较小人物的上半身像。此像戴头巾,头顶凸起的球形似为发髻,上身着无袖的短衣,自双肩两侧垂下的披帛缠绕在手臂上。这身人物也是双手曲臂托举着上方供养人的双足。此像脑后有圆形头光,从衣着及耸起的胸部特征推断,这是一身女性地神(见图5)。
第14窟位于13窟的右侧,两窟隔墙毗邻,同处于第10至15窟这一组洞窟的中心位置。第14窟也是一个中心柱窟,建筑形制与第13窟大致相同。其主室正壁开龛,其中原来安置有主尊像;左右侧壁残存有佛说法图和本生故事;前壁右侧残存2身供养人像;门道上方的半圆端面绘“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壁画;券顶绘有菱格因缘故事画;左甬道外侧壁绘本生故事,内侧壁绘4身供养人像;右甬道外侧壁绘本生故事,内侧壁绘4身供养人像;后甬道前壁绘焚棺场面,正壁绘“八王争分舍利”壁画。如上所述,本窟的供养人像同样数量不菲,现存的达到12身。在14窟的右甬道内侧壁上残存4身龟兹供养人像中,靠前的两身男性供养人像大部分形体保存较好。它们脑后均具圆形头光,身穿华丽的衣着,系腰带,挎长剑。这两人右手叉腰,左手持香炉,双腿脚尖着地而立。在两身供养人的双腿间,均见一身形体较小人物的上半身像①。无论是从衣着还是从形体姿势看,都与13窟中的女性地神酷似,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两身像也应是女性地神(见图版八,2)。
在西域范围,从图像比对看,与上述地神形象最为接近的当属在于阗地区发现的同类资料。①于阗的地神美术品主要见于以下五个遗址点:(1)热瓦克。在热瓦克大塔四周围墙上塑有多尊佛和菩萨像,在佛像的两脚间另塑有小型地神像,斯坦因说:“离大门再远一点的两尊塑像中,每一尊的双足之间各发现一身较小的女性胸像..它们显然全都相同。”②另外在东墙大门旁所塑四身天王像中,斯坦因编号为ⅩⅩⅤⅡ和ⅩⅩⅤⅢ的两身的双脚间也各见一身塑出的小型地神像。(2)和田县布盖乌于来克佛寺遗址。在该遗址内一个正方形殿堂的壁画中,残存两身大立佛的下半身。其中一身,两脚分立于两朵莲花上。在佛的两脚之间,绘一身跪姿合掌礼敬的女性。该女性脑后放射出十几条波浪式光芒,应是一身地神(见图6)。另一身非常残破,但仍可见跪在佛脚侧的地神。(3)策勒县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在方形平面的遗址中,在正壁泥塑有结跏趺坐于莲台上的佛像。在此塑像左侧又所绘一身立佛的两脚间以及左侧壁所绘另一身立佛的两脚间,各绘出一身地神像。它们双臂伸展,两手托持佛脚。(4)策勒县巴拉瓦斯特佛寺遗址。20世纪初末,德国人特林克勒(Trinkler)在遗址中发现一块壁画。其上绘一地神跪在佛的两脚间,两手托持佛脚(见图7)(5)策勒县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特林克勒在编号为A.4.2的寺院中还发现了一个地神图像。画面虽已十分残破,但我们仍可见在佛两脚间残存了地神胸部以下。它双膝跪地,两臂平举,手托佛脚。2002年,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共同考察丹丹乌里克遗址时,发现一座寺院遗址。在遗址壁画中,又出现了两身地神形像。其一是男性。他身着套头小翻领上衣,脸部有髭,颌下有长须,两颊留络腮胡。此地神仅现上半身,他以双手托举立在莲花上的佛脚;另一身是女性。她身着艳丽有纹饰的外衣,仅现上半身,以双手托举也在莲花上的另一立佛的脚。①
此外,在敦煌也发现地神的壁画、幡画和纸画等多幅作品。②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题材内容均与于阗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莫高窟第98窟的壁画。在此窟的前壁保存有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供养像,在此像的两脚之间赫然可见一身地神。地神脑后有圆形头光,仅现出上半身,双手平伸,托持上方李圣天的双足(见图8)。③
从以上的对比叙述看,即使不算敦煌,就第二类地神图像数量规模及分布地点而言,于阗分见于五处遗址,共有7个,龟兹只见于一处遗址,只有4个,前者多于后者;再就图像的年代而言,于阗诸遗址中的丹丹乌里克早到4~5世纪,④库车克孜尔尕哈的第13、14窟约为6~7世纪建造,①前者也早于后者。由此可见,较之龟兹,第二类地神的美术品在于阗当地出现更早,也更为流行。
龟兹和于阗两地同处天山南路,其间虽有沙漠相隔,但自古即有道路相通。两地又同为西域著名的佛国。小乘说一切有部盛行于龟兹,同时也见于于阗,②所以很早以来,两地的佛教及其艺术就存在相互影响的联系。据《高僧传》的记载,定林寺僧法献在宋元徽三年(475年)由金陵出发,“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观世音灭罪呪及调达品。又得龟兹国金锤鍱像。于是而还”。③唐代高僧玄奘由印度返回中土途中,在于阗王城西南十余里的地迦婆缚那伽蓝中,见寺内“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国而来至止”。④屈支国即龟兹国。唐代不空三藏所译的《毗沙门天王仪轨》中曾记有一个故事:唐天宝元年(742年),大石、康等五国围攻安西城。由于请得了北方毘沙门天王神兵相助,“五国大惧,尽退军。抽兵诸营坠中,并是金鼠咬弓弩弦及器械损断,尽不堪用..反顾城北门楼上有大光明,毘沙门天王见身于楼上,其天王神样”。⑤撇开这则故事中光怪陆离的无稽之处,不去论其可信度,我们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于阗佛教文化对龟兹的影响。因为毗沙门天王信仰和于阗王族有着密切联系,⑥而且,金鼠咬断敌军弓弦及器械之事也来源于于阗当地的鼠壤坟传说。⑦凡此种种,可证两地在佛教文化上有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认定,克孜尔尕哈的地神在图像表现上是受到了于阗同类作品的影响,其源头应在于阗。
三
于阗之盛行地神信仰,决非偶然,乃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大唐西域记》在言及于阗建国时记载了一个传说,“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毘沙门天之祚胤也..其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往毘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
至成立。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自兹已降,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故今神庙多诸珍宝,拜祠享祭,无替于时。地乳所育,因为国号”。①内容大同小异的传说,在8世纪以后的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牛头山授记》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于阗国教法史》中也有记载。②从上述记载看,于阗王族自认毗沙门天是其父系,大地女神是其母系,从中折射出他们对地神的尊崇。虽然佛教的地神信仰出现较早,但在印度和中亚,地神的美术品中并不多见,甚至罕见这种双手托举佛、天王和供养人双足的这类美术品。③在此,我们可以说,佛教的地神信仰传播到于阗后,与当地的民间神话传说相结合后,地神崇拜意外地被发扬光大了。
述及地神的佛教典籍,主要有《佛本行集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方广庄严经》、《观佛三味经》、《禅秘要法经》、《金光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华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据松本文三郎、贾应逸等先生研究,于阗的地神形象主要是根据上述诸经中的《金光明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坚牢地神品》绘制的。①
《金光明经》是北凉时昙无谶所翻译的一部佛经。此经的结构分为四卷,计十八品。在《金光明经》被整部译出前,已有片断的单品被译出。北凉本问世后,先后有真谛、耶舍崛多和阇那崛多对其进行改订或补译。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沙门宝贵又综合各家译本,删同补缺成为《合部金光明经》八卷,计二十四品。武周长安三年(703年)由义净译出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计三十一品,不仅品目义理最为完备,而且译文华质得中,因而后来成为通行的本子。
《金光明经》品目较多,内容庞杂,②据说“是经能灭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百千苦恼”,③故被称为“众经之王”。在此经卷二的《坚牢地神品》中记载,地神坚牢闻佛说《金光明经》后,深感此经的微妙,乃发下大誓愿,“若现在世,若未来世,在在处处。若城邑聚落,若山泽空旷,若王宫民宅..随是经典所流布处,是地分中敷狮子座。令说法者坐其上,广演宣说是妙经典,我当在中常作宿卫,隐蔽其身于法座下,顶戴其足..(使)阎浮提内药草树木根茎枝叶华果滋茂,美我香味,皆悉具足;众生食已,增长寿命”。④从这段记载可知,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演讲《金光明经》者,坚牢地神都愿常作宿卫,顶戴其足。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佛教美术品中,不仅是佛陀,而且还有发愿要“能说正法,修行正法”的天王们,甚至包括人间的君王们,在他们的脚下就自然出现了坚牢地神的形像。就目前所见材料,除布盖乌于来克佛寺所见地神作合掌礼敬姿势外,其余皆作两手托举上方人物双足的姿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巴拉瓦斯特佛寺院的相关壁画可以看出,明显是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绘制的。该经《序品》中的一段偈颂说,佛在王舍城灵鹫山演说此经时,“护世四天众,及大臣眷属,无量诸夜叉,一切皆拥卫。大辩才天女,尼连河水神,诃里底母神,坚牢地神众,梵王帝释主、龙王紧那罗,及金翅鸟王,阿修罗天众,如是天神等,并将其眷属,皆来护是人,昼夜常不离。”①如前所述,从德人特林克勒所拼出的线描图上看,除了两臂平伸,双手托持佛脚,顶戴佛足的坚牢地神外,还残存帝释天的半身像,摩酼首罗天和双手持鱼的尼连河水神等。
关于图像中地神的性别,从形象及衣着上看,绝大多数,包括“降魔变”中由地涌出作证的地神,都是女性。这一现象与《金光明经》中佛称呼坚牢地神为“善女天”②及《金光明最胜王经》中所记“尔时此大地神女,名曰坚牢”③相吻合。但是,如前所述,在于阗丹丹乌里克和克孜尔尕哈第13窟中还各发现一身男性地神。对于这一奇异的文化现象,有学者从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角度,认为丹丹乌里克“借用了民间祭祀的土地神形象..老翁式的地神很可能是受到中原道教的影响。”④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地神分为男女两性的观念或许在古代印度就已有其萌芽了。
玄奘在摩揭陀国曾见一个砖室内绘有两身地神像,“迦叶波佛精舍西北二砖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来将成正觉,一报魔至,一为佛证。后人念功,图形旌德”。⑤由这段文字,可知这两身地神像的来历,乃是后人感念地神在释迦牟尼降魔成道时所立之功而绘。玄奘还生动记载了这段传说故事,“昔如来之将证佛果,天魔来娆,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来告曰:‘汝勿忧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谁为明证?’如来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证’。是时第二地神踊出作证。”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故事与我们常见的佛典中降伏魔众的记录,如南朝宋求那跋陀罗所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差异。后者仅记有一地神涌出作证的情节,在前述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只见一身地神在佛座下现出上半身。与此不同,前者所言地神的数量已是复数的两身了。可惜,玄奘没有对他所见摩揭陀国砖室内的二地神作进一步描述,语焉不详。我揣测,这两身地神像可能并不相同,而是有差异的。从其职能分工不同看,作证的地神,正如我们在前面“降魔图”中所见,会以女性形像表现,而另一助佛降魔的地神,很可能会以男性形像表现。
在发现有众多地神美术品的于阗地区,实际上当地的佛教思想理念中关于地神的类别就不是单一的。集成于于阗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的《世主妙严品》中就列举了多位地神的不同名号,“复有佛世界微尘数主地神,所谓普德净华主地神、坚福庄严主地神、妙华严树主地神、普散众宝主地神、净目观时主地神、妙色胜眼主地神、香毛发光主地神、悦意音声主地神、妙华旋髻主地神、金刚严体主地神。如是等而为上首。”①在此,地神显然已被视为一个群体而非个体了。因此,就总体情况而言,我倾向于男性地神形象的出现最有可能还是肇始于于阗。
四
如前所述,在龟兹、于阗两地不约而同出现了地神由地涌出,双手托持王族供养人的图像,这直观地反映出两地君王对《金光明经》的青睐有加。个中原因,固然与此经宣扬维护镇守国家,救护世间有很大关系,如在《四天王品》中,毘沙门天王、提头赖咤天王、毘留勒叉天王和毘留博叉天王就直白的发愿说:“世尊,如诸国王所有土境,是持经者若至其国,是王应当往是人所听受如是微妙经典。闻已欢喜复当护念恭敬是人。世尊,我等四王,复当勤心拥护是王及国人民,为除衰患令得安隐。世尊,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是经,若诸人王有能供给施其所安,我等四王,亦当令是王及国人民一切安隐,具足无患。世尊,若有四众受持读诵是妙经典,若诸人王有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等四王,亦复当令如是人王于诸王中常得第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令余王钦尚羡慕,称赞其善..世尊,若有人王,欲得自护及王国土多受安乐,欲令国土一切众生悉皆成就具足快乐,欲得摧伏一切外敌,欲得拥护一切国土,欲以正法正治国土,欲得除灭众生怖畏,世尊,是人王等,应当必定听是经典。”①佛也宣教于四天王说:“若有人王能供养恭敬此金光明微妙经典,汝等正应如是护念,灭其苦恼,与其安乐。”②但是,就这些王族供养人自身而言,应有更深层面的缘由。
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曾在库车地区发现大量古文字写本残卷,其中在一份犍陀罗语、龟兹语双语文书上,语言学家发现了龟兹国王有一个“Devaputra”的头衔称呼。③无独有偶,这一称呼还见于于阗文书。④“Devaputra”一词,其词根Deva,在佛教术语中意为“天”,而该词完整意义的直译为“天子”⑤或“天神之子”。在中亚地区,“Devapu-tra”的称号最早出现在贵霜王朝诸王对自己的称呼中。首先是丘就却,随后被迦腻色迦等国王使用。而使用这一称号的诸王们,显然是想神化自我并使王权合法化。但是,如果“Devaputra”仅仅是一种自我称呼,肯定难以令他人心悦诚服。“为了与天子(Devaputra)观念保持一致,贵霜人还建立了神庙(Devakula),把死去的国王即天子们的塑像置于其中”。⑥另外,贵霜钱币上所描绘的国王像,其肩部还向上冒出火焰,“这样做更增加了国王的合法性和神圣性”。⑦然而,真正在理论上使国王权威和权力的来源合法化的,恰恰是大乘佛典《金光明经》中有关“天子”这一概念的系统完整、圆满合理的阐释。据该经《正论品》中的记载,佛为坚牢地神宣讲的故事中,有名为力尊相的国王為其子信相所說的偈言里有如下内容:“云何是人,得名为天?云何人王,复名天子?因集业故,生于人中,王领国土,故称人王;处在胎中,诸天守护,或先守护,然后入胎。虽在人中,生为人王。以天护故,复称天子。三十三天,各以己德,分与是人,故称天子。神力所加,故得自在。”①在这段偈颂中,以问答的方式,虽然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依佛陀之口宣扬了人主身份所具有的“天子”神格。对人主的神化,无形中提供了一种君王们梦寐以求的“王权天授”的政治理念。毫无疑问,《金光明经》中的这段偈颂文字内容,对于身为人主的君王们一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续高僧传》记载,隋大业五年(609年),帝西巡,高僧慧乘陪同前往,“从驾张掖。蕃王毕至。奉勅为高昌王麹氏讲金光明..闻者叹咽”。时为高昌王的麹伯雅听讲后,甚至“布发于地,屈乘践焉”。②《金光明经》对他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龟兹国王看来不仅由贵霜王朝借来了“Devaputra”的称号,而且在佛教石窟中描绘自己供养人像的手法也与后者如出一辙。在已知的龟兹国王供养人像中,③脑后均画出圆形的头光——一种佛教绘画中只有“天”(Deva)及其以上阶位的神祗才具有的图像特征。而前述的克孜尔尕哈的第13、14窟中的供养人像,不仅在脑后画出了头光,而且还在双脚间画上了托持双足的地神,更是极尽神化渲染之能事。
最后探讨一下《金光明经》在龟兹王族中传播、影响的可能性。众所周知,龟兹长期以来盛行小乘说一切有部,而《金光明经》却是一部大乘佛典。此经若能在龟兹的流传,一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认为,主要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大力倡导大乘佛学有密切的关系。据《高僧传》等史籍记载,罗什是初习小乘,后因机缘巧合,又改宗大乘。由于他本人深厚的佛学造诣和崇高的声望,加之龟兹王族又不遗余力地推崇,终使大乘佛教可以在原先小乘佛教占统治地位的龟兹登堂入室,逐渐流传开来。①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前秦将军吕光以兵迎罗什至凉州。但是,此后龟兹本地的大乘佛教并未就此急剧式微。相反,从一些迹象看,它仍保持着一股发展的余势。公元394年,兼通大小乘的龟兹高僧昙摩跋檀在龟兹金华祠译出大乘典籍《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②在北魏太武帝灭佛时,从大乘佛法盛行的高昌避乱至龟兹的沙门法朗就受到龟兹国王之礼遇,后圆寂于此。③公元585年,南天竺沙门达摩笈多路经龟兹,被当地笃好大乘的国王所挽留,停住两年,为僧众讲说《说(念)破论》,《如实论》。④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就曾据上述记载推断说:“罗什以后达摩笈多时代之龟兹国王,皆寄心大乘教。”⑤近年来,学者对龟兹石窟壁画的研究时也发现其中混杂有反映大乘佛教思想的题材内容,从一个侧面可证此言不虚。⑥克孜尔尕哈第13、14窟中均出现带有头光的王族供养人,而这两个洞窟的开凿年代约为6~7世纪,恰好就在龟兹国王推崇大乘佛教的这一重要时期。
目前,关于《金光明经》的版本,除了前述汉文译本外,在尼泊尔还保存有完整的梵文本,其内容与北凉昙无谶的汉文译本大同小异。另外,《金光明经》尚有于阗文、回鹘文、西夏文、藏文和蒙文等多个语种译本。据《高僧传》的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的中天竺僧人摄摩腾在来华前,就曾“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①可见此经的梵本很早就已在流传。尽管现在还没有发现龟兹文本的《金光明经》,但是考虑到此经的译者昙无谶在河西的姑臧译出此经前曾携带不少佛经在龟兹停留,②而后来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庄严菩提心经》即是《金光明经·最净地陀罗尼品》的异译本,所以还不能完全排除将来有所发现的可能性。何况,龟兹王族中还流行使用梵文,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梵语在当时的西域,以及印度本国,也同法语(在欧洲)一样,被认为是有文化的语言。龟兹,也有焉耆,王廷使用梵语,以显示自己的高贵”。③因此,他们还可能直接阅读梵文本的《金光明经》。
总之,通过对龟兹石窟壁画中地神形象的考察分析,一方面,我们从中可以管窥龟兹佛教美术对外交流互动的一些情形;另一方面,透过一些地神作品的表像,我们还能够发现其中所反映出的龟兹王族神化自我,试图宣扬一种“王权天授”的政治理念。
(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承蒙贾应逸、霍旭初两位先生悉心指点,王志兴为本文绘制了线描图,在此谨致谢意。)
(作者: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副研究员)
附注
①霍旭初《克孜尔石窟降魔图考》,载作者所著《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62页;[日]中川原育子《降魔成道图の图像学的考察》,载《密教图像》第六号,第51~73页;《キジルの降魔成道にっいて》,载《宫坂宥腾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法藏馆1993年版,第1315~1348页。
①《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克孜尔1》,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年版,图版一一一。
①《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克孜尔3》,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年版,图版五。
②《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克孜尔2》,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年版,图版二。
③GRANDEXHIBITIONOFSILKROADBUDDHISTART,TOKYO,1996,P139,PL150.
①[日]中川原育子《キジルの降魔成道にっいて》,载《宫坂宥勝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法藏馆,1993年,第1315~1348页。
②《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克孜尔2》,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年版,图版八十。
①《方广大庄严经·降魔品第二十一》,《大正藏》第3册,0594c页。
①[日]中川原育子《キジルの降魔成道にっいて》,载《宫坂宥勝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法藏馆1993年版,第1315~1348页。
②《过去现在因果经》,《大正藏》第3册,0639c页。
①霍旭初《克孜尔石窟降魔图考》,载作者所著《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62页。
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降魔图考》,载作者所著《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162页。
①《中国新疆壁画全集·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图版一二一,一二四。
①关于于阗地区的材料,大部分承贾应逸先生提供。贾先生还馈赠其未刊论文《于阗佛教图像中的地神研究》,谨此致谢。
②A.Stein,AncientKhotan,Oxford,1907.
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丹丹乌里克遗址佛寺清理简报》,载《新疆文物》2005年第3期。在该简报中,仅涉及了清理中所得20余块壁画中被修复的5块壁画。本文中所言及的女性地神像,是2004年我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参加“中日联合保护修复丹丹乌里克佛寺壁画项目”座谈会时有幸得睹。
②如莫高窟154窟的毗沙门天王像,见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图版99;藏经洞所见幡画见东京国立博物馆编集《丝绸之路大美术展》,读卖新闻,1996年,图版178;藏经洞所见P.2322和P.4518号文书上的毗沙门天王像的附图。
③参见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图版13。
④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①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页。
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五记载,玄奘抵达于阗后,被“安置于小乘萨婆多寺”,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1页。萨婆多是梵文Sarv〓stiv〓da的音译,汉译为一切有部。
③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第十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四八八页。
④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十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14~1015页。⑤《毘沙门仪轨》,《大正藏》第21册,0228b页。
⑥古正美《于阗与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载《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第34~66页。⑦《〈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十二,第1017~1018页。
①《〈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十二,第1008页。
②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载作者所著《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191~211页。
③中川原育子《降魔成道图の图像学的考察》。
①[日]松本文三郎著,金申译《兜跋毗沙门天考》,载《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第36~43页。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②关于整部《金光明经》的主要内容介绍,参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三)中“金光明经”的条目,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75~77页。
③《金光明经·四天王品》,《大正藏》第16册,0340c页。
④《金光明经·坚牢地神品》,《大正藏》第16册,0345c页。
①《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大正藏》第16册,0403c页。
②《金光明经·赞叹品》,《大正藏》第16册,0339a页。
③《金光明最胜王经·王法正论品》,《大正藏》第16册,0442a页。
④贾应逸《于阗佛教图像中的地神研究》(未刊稿)。
⑤《〈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八,第681页。
⑥《(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八,第675页。
①《大方广佛华严经·世主妙严品》,《大正藏》第10册,0002c页。
①《金光明经·四天王品》,《大正藏》第16册,0340c~0343a页。
②《金光明经·四天王品》,《大正藏》第16册,0341a页。
③[德]W.Winter著,汤红娟译《吐火罗人与突厥人》(TocharianandTurks),《新疆文物》2001年第1~2期合刊。
④[印]A.K.纳拉因著,王辉云译,杨瑞琳校《贵霜王国初探》,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159~174页。
⑤据A.K.纳拉因的意见,贵霜国王的“天子”称号是受到中国帝号用法的启发。在我看来,这一称号虽然与我国内地王朝统治者所用的“天子”称号形式相同,但是所反映的实质内容却并不完全一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天”是至高无上的,“天子”的位阶仅次于“天”。可是贵霜国王所自称的具有佛教色彩的头衔“天子”中,“天”仅仅是六道轮回中众生的一个最好的归属而已,与最高阶位的佛还有较大差距,“天子”的阶位就更逊一筹了。
⑥[印]A.K纳拉因著,王辉云译,杨瑞琳校《贵霜王国初探》。
⑦[印]A.K.纳拉因著,王辉云译,杨瑞琳校《贵霜王国初探》。
①《金光明经·正论品》,《大正藏》第16册,0346c页。
②道宣撰《续高僧传》卷第二,《大正藏》第50册,0633b页。
③由于国际语言学家的不懈努力,随着克孜尔205窟及69窟的此类男性供养人像旁边所附古文字被先后解读,他们的国王身份被确定。前者是隋末的一位龟兹国王Totika,(见F.H.L〓DERS:WeitereBeitr〓gezurGeschichteundGeographievonOsturkestan(《东突厥故地的历史与地理》).Berlin,1930.)后者则是姓名见于新旧《唐书》的龟兹王苏伐勃驶Swarnapuspa(见中川原育子:《クチャ地域,の供養者像に関する考察》(《关于龟兹供养人像的考察》),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35,1999年,第89~120页)。因此,对于龟兹石窟中那些带头光的世俗供养人,学界一般趋向于他们是历代热心支持佛教的当地国王。
①鸠摩罗什在龟兹弘法的事迹,巳有多位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参见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
②《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大正藏》第14册,0105a页。
③《高僧传》卷第十,第三八七至三八八页。④《续高僧传》卷第二,《大正藏》第50册,0434c页。
⑤[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4页。
⑥朱英荣《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大乘内容》,《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霍旭初《鸠摩罗什大乘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龟兹石窟的影响》,《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①《高僧传》卷第一,第一页。
②《高僧传》卷第二,第七七页。
③季羡林《龟兹研究三题》,载《燕京学报》新十期,又《龟兹学研究》第一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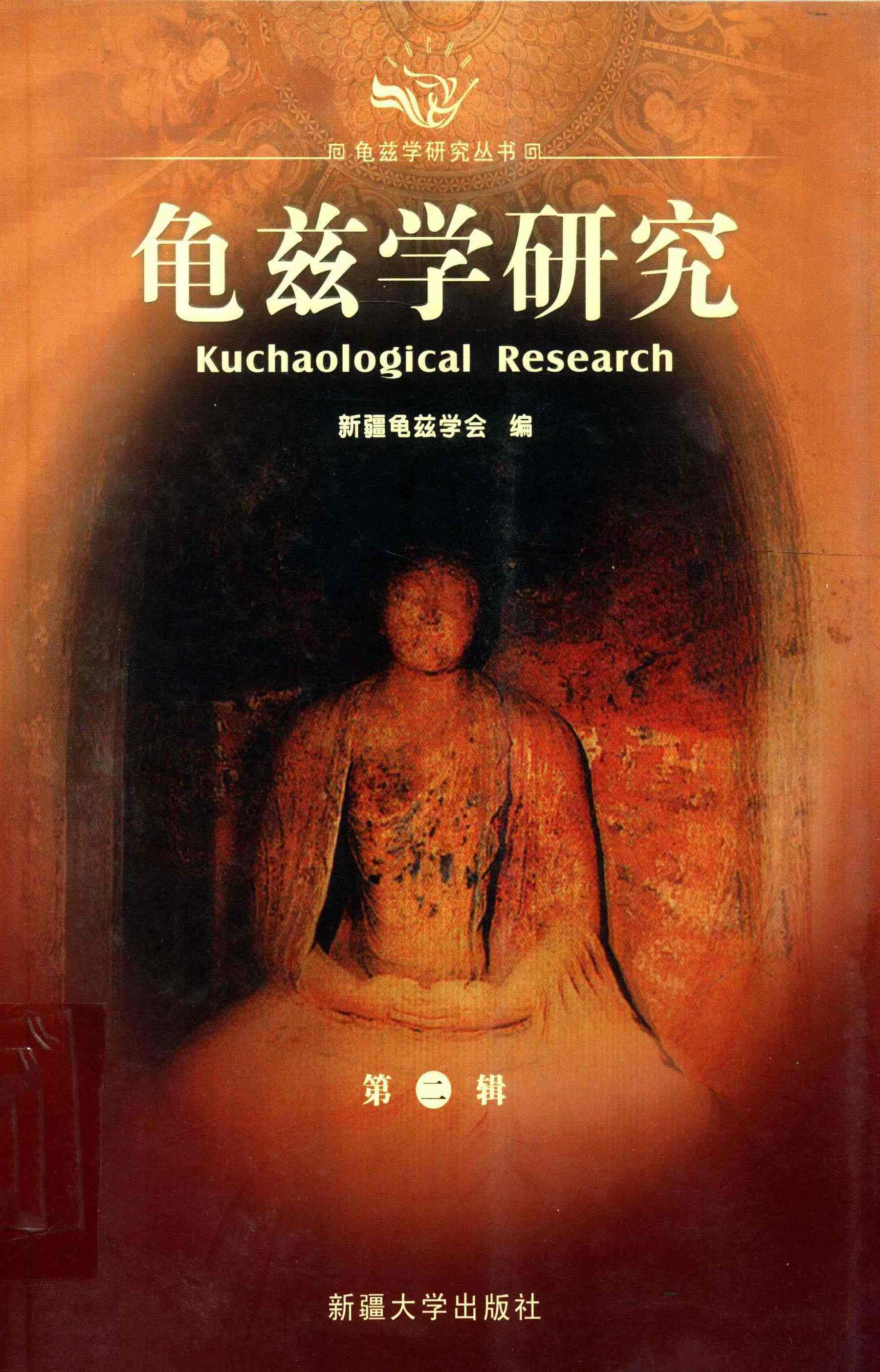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出版者:新疆大学出版社
本书所选论文分为“大家论坛”、“历史研究”、“考古探秘”、“佛教石窟”、“文化艺术”、“史料研究与情报”六个部分。新疆龟兹学会成立已三年有余了。三年来新疆龟兹学会抓了三件事:一是每年召开一次“龟兹学学术研讨会”。二是编辑出版新疆龟兹学会学术刊物《龟兹学研究》。三是进行《龟兹学概论》的编撰工作。
阅读
相关人物
彭杰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