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龟兹文化的几个问题
| 内容出处: |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452 |
| 颗粒名称: | 关于龟兹文化的几个问题 |
| 分类号: | K294.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052-06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关于龟兹文化的几个问题。龟兹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但它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它的核心与主流,却是佛教文化、龟兹文化,从文化类型上说,虽是以龟兹国之名命名的一种地域文化,它的核心区域在龟兹,但它的地域范围不应限于龟兹,即今阿克苏地区,还应包括焉耆、疏勒,也就是整个塔里木盆地北道沿线诸国,即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地区等 |
| 关键词: | 龟兹文化 问题 文化研究 |
内容
近年来,全国兴起地域文化研究热,龟兹文化研究更是持续升温。为此,我也想就龟兹文化的主要内容、地域范围以及研究思路等问题,谈一些肤浅认识。
一
龟兹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但它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它的核心与主流,却是佛教文化。这样说,并非因为我是搞佛教石窟的,有意要抬高它,而是历史事实。当然我说的佛教文化,可不全是印度那样的佛教文化。由于龟兹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富于创造的民族,因此,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它融入了龟兹本土原有文化和民族思想情感。可以说,这里的佛教文化,虽是伴随印度佛教传入而生成发展起来,但却是有着龟兹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我认为,现在说的龟兹文化,应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主要指历史上新疆库车地方政权——龟兹国存在时期的文化。龟兹何时立国,文献未载,不过,《汉书·西域传》已立有龟兹国专传,不仅记载了龟兹都城、人口、兵员、官职,并讲到它的疆界。从传文所记内容看,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之时,龟兹大体上已是完整意义的国家。如果以此算起,到9世纪中虽回鹘民族西迁,龟兹成为西州回鹘领地为止,以今库车为中心,辖境包括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温宿和巴楚等县市的龟兹国历经1000多年。所谓龟兹文化,指的应是这一时期内生息繁衍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当然,也还要算上西州回鹘前期,即龟兹回鹘这一段。龟兹回鹘虽是西州回鹘下属地方政权,但独立性较强,首领自称师子王。后期,龟兹回鹘逐渐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开始伊斯兰化。这以后,就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龟兹文化范畴。也就是说,我们所讨论是11世纪初以前的龟兹历史文化,这是前提。对龟兹文化的概念,我觉得,作一界定是有必要的,它可使我们的讨论有个共识基础。
众所周知,自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时任西域长史班超降服龟兹,废龟兹王尤利多,立龟兹质子白霸为龟兹王,从此,龟兹进入白氏王朝(即龟兹王之名的头一个字基本上都带一个白或帛字。近有学者指出,按惯例,西域诸国通常是王子或王弟为质子,白霸既为尤利多为龟兹王时入侍汉廷的质子,则尤利多与白霸应属同一氏族,亦为白姓龟兹王,龟兹白氏王朝至迟始于龟兹王白建,而这里仍按传统说法叙述)。
白氏王朝有两个突出方面:一是统治龟兹时间长。从白霸开始,一直延续到8世纪末(唐贞元四、五年间,公元788~789年)悟空由印度回国途经龟兹时在位的龟兹王白环,长达近七百年。如此稳定的王朝,出现在当时民族迁徙流动性大、王朝更迭频繁的西域、中亚地区难能可贵,在我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二是白氏王朝历代诸王大多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佛教传入龟兹究竟发生在白氏王朝建立以前,还是在之后,暂且不论,但从文献记载看,他们对佛法的渴求,对高僧(包括外地来龟兹高僧)的敬重,今天仍感到他们那份敬法重人的挚诚。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用习惯的宗教标准作评判,不能完全看作是宗教狂热,或者认为是要利用佛教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理应回归到当时龟兹社会现实来分析考虑。我以为,龟兹白氏王朝诸王带头崇尚佛教,是出于对佛教文化的仰慕,是对当时一种崭新文化的追求。因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以宗教为其表征的。这样认识是否恰当,还可探讨,但在他们倡导和影响之下,龟兹境内佛教长盛不衰,佛教文化空前繁荣。这不仅文献有载,如今遗存在库车、拜城一带众多佛教寺址、石窟,便是当年龟兹佛教兴盛的明证。龟兹回鹘在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前,同样信奉佛教,程度虽不及白氏王朝统治时期那样鼎盛,但其文化仍是以佛教文化为主,开凿在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时期的窟,就是证明。在佛教盛行的同时,龟兹也曾有其他宗教流传,如祆教,在龟兹就建有祭祀场所——天祠。也发现有用龟兹文书写的摩尼教赞美诗卷子。在龟兹文化形成当中,亦吸收融汇了各种外来文化,尤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显示出多元文化的品格,这从龟兹石窟壁画上即可强烈感受到。尽管龟兹文化包含有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异彩纷呈,错综复杂,但佛教始终占据主导地拉,佛教文化无疑是龟兹的主流文化,是龟兹文化的基本形态。这样认为,也许有些过于绝对,但至少从目前揭示的龟兹文化的主要内容来看是这样。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也是一种文化最显著的特征。龟兹为多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流行过多种民族语言文字。龟兹又是中原王朝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汉语言文字曾相当通行,至今还能看到当年用汉文书写的官府文书、借贷契约和摩崖石刻,这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龟兹与内地密切的政治关系。然而,20世纪初以来,经中外语言学家通过研究从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收集到的古文字材料发现,这一带最为通用的语言却是吐火罗语。这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分为两种方言。一种分布于高昌、焉耆等地,称作甲种吐火罗语或焉耆语,记录的全部是佛典,特别是有关弥勒的经典很多。另一种则限于龟兹,称作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语。记录的内容除佛典外,还有世俗文书。虽然焉耆—龟兹语属于吐火罗语甲乙两种方言,但表述这种语言的文字,则是借用印度婆罗谜字母书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记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就是指婆罗谜字母而言。龟兹语即是借用印度婆罗谜文字,显然是伴随佛教而输入龟兹的。熟识情况的人都知道,龟兹佛教与印度贵霜王朝关系密切。20世纪初,在印度马土腊曾出土一尊迦腻色迦雕像,并有用婆罗谜字体镌刻的铭文。而类似用婆罗谜字母拼写自左到右横行书写的龟兹文题记,在龟兹石窟壁画上为数不少,有的时间早到4世纪,这说明,龟兹语文极有可能在佛教传入龟兹伊始即输入龟兹。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窟壁画榜题多用龟兹文、汉文和回鹘文三种文字合壁书写,表明有龟兹回鹘时期,虽然龟兹人种、语言逐渐回鹘化,但龟兹语文仍是通用的语言文字。岁月沧桑,龟兹语文这种古老语言文字虽已在民族融合中消失,无人使用,但应成为我们不可忘却的文化记忆。我国早期汉译佛经有相当部分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由龟兹语文本转译过来,因此,它在佛教传播上作出过贡献,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尤为重要的,它作为龟兹文化的一种载体,为我们记录、保存了大量有关龟兹文化的历史信息,它的学术意义不亚于龟兹石窟壁画。
龟兹乐舞是龟兹文化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也是历年论文著作述介得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内容,几乎成为龟兹文化的标志和代名词。然而龟兹乐舞,是在龟兹本地音乐舞蹈基础上,吸取印度、波斯和中原乐舞长处,尤其是印度乐舞长处而创造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乐舞体系。这自然亦是伴随佛教传入龟兹而逐渐形成完备的。
其他如文学、戏剧、美术也都渗透着佛教文化。尤其是作为龟兹国艺的雕塑、绘画,更是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佛教的传入,使龟兹文化思想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动了龟兹社会发展进程。没有佛教的传人,龟兹不可能如玄奘赞誉那样“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著称于西域;龟兹乐舞也不可能登上隋唐宫廷乐舞的殿堂,风靡中原大地;龟兹更不可能由一个城邦国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国,至今仍受到世人的关注。总之,佛教的传入,使龟兹文化经历一次重构过程,重构就是发展,对龟兹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
曾有研究者谈到龟兹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问题,认为龟兹文化的精神实质就是开放、兼容。的确是这样。龟兹为西域重镇,又位于丝绸之路要道,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这样的地理、人文环境,必然使龟兹文化具有开放、兼容的优势,构成了龟兹文化的一大特色。龟兹文化即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这正是龟兹文化独具魅力和吸引人之处。我们研究龟兹文化,就是要重视发掘其中的积极元素,古为今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服务。也许是巧合,龟兹文化的这种优势、特色,恰恰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佛教自传世2500多年来,一向以和平方式传播,从不用武力或别的什么手段强制别人信仰。也没有排他性,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保有开放接纳的姿态,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少思想禁锢、最有涵容人格精神的一种宗教。而这正是佛教文化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很难想象,若不是佛教的兴盛,佛教文化的浸润,龟兹文化怎能如此繁荣昌盛,为我们留下如此优美的石窟壁画!
二
龟兹文化,从文化类型上说,虽是以龟兹国之名命名的一种地域文化,它的核心区域在龟兹,但它的地域范围不应限于龟兹,即今阿克苏地区,还应包括焉耆、疏勒,也就是整个塔里木盆地北道沿线诸国,即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地区。这样说,并非有意夸大龟兹文化的区域空间,事实根据是不仅因为焉耆、疏勒毗邻龟兹,地域相连,最主要是焉耆、疏勒与龟兹在历史上皆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同属于小乘佛教文化圈带。只要翻阅一个我国三位不同时期西行求法僧行记,即东晋法显《佛国记》、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即可明了。他们都是经西域即今新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前往印度或返回中原内地。在他们的行记里,对南北两道沿线佛教信仰情况均有明确记述。
法显于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后秦弘始元年)从长安出发,次年抵达鄯善(若羌地区),然后转向西北往乌夷(焉耆),再折向西南到于阗,经子合(叶城)、于摩(叶城西南)和竭叉(疏勒,一说塔什库尔干)等国,西越葱岭,于公元402年(东晋元兴元年、后秦弘始三年)进入印度北境。他在《佛国记》里对所经之地佛教,除于摩国外,皆有记述。
鄯善国:
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乌夷国:
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
于阗国:
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
子合国:
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
竭叉国:
有千余僧,尽小乘学。
法显虽未到龟兹,没有记载龟兹情况,但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记载,4世纪中叶前后,龟兹佛教已相当兴盛,尽管大、小乘都有流传,但统辖龟兹佛教领袖佛图舌弥为小乘阿含师,足证龟兹佛教是以小乘为主。从法显所记可以清楚看到,5世纪初(实际年代肯定比这要早),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于阗、子合和北道的焉耆、疏勒等国,虽皆是佛教国家,并各有特点,然而南北两道佛教情况却是泾渭分明。南道于阗一带主要流传大乘佛教,北道沿线诸国则同龟兹,主要信奉小乘佛教。当时形成两个不同的佛教文化区域,即南道以于阗为中心的大乘佛教文化圈带和北道以龟兹为中心的小乘佛教文化圈带。
玄奘于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一说公元639年,唐贞观三年)西行印度求法,途经塔里木盆地北道,归程东越葱岭,从朅盘陀行进到乌铩,再北行到佉沙,然后转向斫句迦,经南道返回长安。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和卷十二分别记述了阿耆尼(焉耆)、屈支(龟兹)、跋禄迦(姑墨,今阿克苏)、朅盘陀(塔什库尔干)、乌铩(莎车)、佉沙(疏勒)、斫句迦(即法显《佛国记》所作子合国)和瞿萨旦那(于阗)等地佛教情况。由于玄奘西行印度求法来回皆取道西域,南北两道主要城邦国都记到,并且更为翔实和具体。
阿耆尼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屈支国:
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
跋禄迦国:
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伽蓝数十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朅盘陀国:
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乌铩国:
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习学小乘教一切有部。
佉沙国:
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斫句迦国:
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淳信三宝,好乐福利。伽蓝数十,毁坏已多。僧徒百余人,习学大乘教。
瞿萨旦那国:
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慧超为朝鲜古国新罗人,赴唐留学僧,也加入当时我国掀起的西行求法热潮,先循海路前往印度(具体时间不明),于公元727年(唐开元十五年)经西域返回内地。他在《往五天竺国传》里对疏勒、于阗、龟兹(安西)和焉耆佛教也作了记述,情况一如法显、玄奘所记,这里不再详细引述。
玄奘、慧超所记分别是7世纪初和8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佛教情况,与法显记之5世纪初相比,虽然南道大乘佛教势力明显削弱,如于阗,尽管这时境内佛寺尚有百余所,可僧徒已从数万减至五千人。子合尤甚,大乘僧由千余减至百余人,近乎衰亡。相对于南道而言,北道小乘佛教却大为增盛,特别是疏勒,小乘僧由过去千余人增至万余人。这种大、小乘之间的消长形势,并未根本改变南北两道佛教基本格局,依旧是:以于阗为中心的南道流传大乘佛教,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信奉小乘佛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玄奘在记述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北道信奉的小乘佛教是为说一切有部,并以文献形式记录下来,使我们对龟兹及其周边地区佛教文化的部派属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通过玄奘、慧超所记也看到,北道沿线诸国,至迟从法显时代5世纪初以来,一直坚持传统的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信仰,在经历多个世纪后,丝毫没有任何变化。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诸国,在佛教文化上,早已形成一个共同的比较稳定的区域,即一个在我国唯一的以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为主体的佛教文化区域,一个比较特殊的与我国其他地区(包括于阗在内)有所不同的佛教文化区域。
正是因为北道沿线国家皆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同属于小乘佛教文化圈带,因此,焉耆、疏勒与龟兹在文化上相同点很多。焉耆与龟兹两地居民不仅为同一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而且在风俗、婚姻、丧葬、物产等方面也大致相同。焉耆与龟兹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就连玄奘记述两地佛教时所使用的词语亦基本相同。疏勒与龟兹在文化上的关系,尽管文献记载没有那么明显,但仅从玄奘所记看,两地相同地方仍有例可举。如语言文字,虽然疏勒与朅盘陀、乌铩比较接近,与龟兹略异,但也是“取则印度”,想必是会通的。僧人则更不是问题。法显在《佛国记》讲到位于南北两道交汇之处的鄯善国时说:“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此(指佛教盛行),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这就是说,西域僧人皆通用梵文,不存在语言文字障阻。在佛事方面,所谓“勤营福利”,“不究其理,多讽其文”,即是指疏勒佛教偏尚修福,追求功利,重视诵读经文,不太深究其中义理,以及持戒较严,却不戒荤腥,食三净肉,等等,与玄奘记龟兹“尚拘渐教,食三净肉。洁清耽玩,人以功竞”相一致,保持了早期佛教的一些特征。特别是生活习俗上,玄奘记龟兹与疏勒两地流行一种“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的奇特做法,大概是在小孩出生后便用木板挤压头颅,使头部扁平。这种人工变形头颅的生活习俗,是受外部文化影响,还是源自本地?是融纳了原始自然宗教的遗绪,还是有着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文化背景?目前尚难论定,但流行于龟兹与疏勒两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是文化心理认同的典型表现。总而言之,尽管焉耆、疏勒与龟兹在政治上不相统属,还时起纷争,但在文化上确实属于一个体系,一个以龟兹为主的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文化体系。学术界在论述西域佛教文化分野时,总是划分成于阗、龟兹和高昌三个区域文化单元,而把焉耆、疏勒与龟兹视为一个区域文化单元,正是这个道理。因此,要进一步丰富我们对龟兹文化的认识,深化对龟兹文化的研究,全面揭示龟兹文化蕴含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就有必要把整个北道沿线地区甚至更大的范围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
三
以上概述了龟兹文化主要内容是佛教文化,龟兹佛教文化主要属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文化以及地域范围,下面再就龟兹佛教文化研究的思路问题,主要是如何看待龟兹大乘佛教和玄奘关于龟兹及周边国家盛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这样两个问题。
据《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收录的《鸠摩罗什传》记载,4世纪中叶,鸠摩罗什由小乘改宗大乘,曾在龟兹大力弘扬大乘佛教。从传文看,声势影响都不小。实际情况是否确如传文描写的那样,需要综合分析。因为这两部传文皆出自内地僧史学家之手,他们偏爱大乘佛教,在行文中不免会加进溢美之词,作些渲染。即使讲的全是实情,也不难看出,尽管罗什大力弘扬,龟兹大乘佛教始终只是停留在龟兹上层社会层面,只是在以龟兹王室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小圈子里流传。佛寺也仅限于罗什居住的王新僧伽蓝(王新寺),寺僧仅有90,在龟兹僧团(当时龟兹僧有1万余人)中所占比例很小,成员估计大多来自王族子弟。可以这样说,龟兹大乘佛教,仅是龟兹王室贵族的佛教,与平民百姓有一定距离。由于缺乏群众基础,随着前秦苻坚派遣吕光率军伐龟兹及焉耆诸国,罗什被劫往凉州,失去了代表人物,龟兹大乘佛教很快便归于沉寂。它对龟兹的影响,包括石窟造像,却很有限,不可估计过高,更谈不上发生龟兹佛教改宗问题。6世纪末,从文献上看,确有西来大乘僧在龟兹弘法,在位龟兹王透溢出对大乘僧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但大乘僧讲的皆是大乘人门性质的内容,龟兹王对大乘佛教仍处于尚未精深阶段,仅是一位诚笃之士而已,因此也很难说6世纪后期龟兹大乘佛教称盛。7世纪后,随着唐王朝重新统一西域,龟兹与中原内地关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迁居龟兹,在中原佛教影响下,龟兹大乘佛教重又活跃起来,库木吐喇石窟中的一批汉风窟便受敦煌壁画深刻影响,而阿艾石窟简直就是敦煌壁画的翻版,属于典型的中原大乘佛教回流龟兹的例证。似如慧超所记,仅是“汉僧行大乘法”,广大民族僧众仍是信奉小乘学说一切有部。正因如此,在龟兹石窟,特别是克孜尔石窟,壁画集中而具体地绘出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特有题材,形象地为我们诠释了小乘有部思想内容。就现存佛教遗迹看,无论是在佛教老家印度,还是我国内地,都是不可多见的。因此,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不仅开凿年代早,在我国石窟史上具有追本溯源意义,而且更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佛学大师玄奘在西行印度求法前,在国内即已遍参名师,穷尽各家学说。在西行求经的17年时间里,接触了当时西域、中亚和印度各地包括说一切有部在内的大、小乘各种派别,观察细致周详。回国后又亲自译出说一切有部论藏中的《异部宗轮论》、《法蕴足论》、《发智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和《顺正理论》等论书。尽人皆知,说一切有部虽是小乘佛教众多部派之一,然而却是思想理论最为丰富、势力与影响较大的一派,主要流传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和迦湿弥罗地区,有自己的经律论三藏。经藏同别的部派一样,以四部阿含经(《长》、《中》、《杂》和《增一》)为根本经典,只是次第有异,将《杂阿含经》置于首位。律藏有两种:一是《十诵律》,主要是在罽宾流传的较为原始的一种律本。另一种即《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包括诸事)。虽然结构、内容与《十诵律》差别不大,但增加不少本生、比喻故事,还掺杂有佛传内容,卷帙也相应增加,因而被称作有部律广本,称《十诵律》为略本。论藏,即是对阐释佛经义理论书的总称,又作《阿毗达磨》、《阿毗昙》、《毗昙》,其论书主要就是上面提到玄奘译出的那些。因为说一切有部最重论藏,喜兴造论释经,不仅为我们留下为数众多的理论著作,而其学说思想就体现在这些论书之中。这一点,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说疏勒僧徒“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来看,从慧立、彦琮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在龟兹参访阿奢理贰伽蓝时,该寺住持(也是当时龟兹佛门领袖)木叉毱多特意向玄奘推荐“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来看,都反映出说一切有部重视论藏情况。玄奘这里说的《毗婆沙》,即《大毗婆沙论》,全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俱舍》,即《俱舍论》,全称《阿毗达磨俱舍论》;《杂心》,即《杂阿毗昙心论》,均为说一切有部3部重要论书。尤其是《毗婆沙》,系统总结论述了说一切有部学说的基本理论,地位最突出,被奉为圭臬。玄奘不仅译出《毗婆沙》,而且翻译了有部几乎所有大论(玄奘所以花大力译出有部论书,恐怕也是考虑到这些论书思想丰富性),应该说,玄奘对有部学说思想深有研究,对有部形成、发展、演变和流传情况不可谓不知,他对龟兹及周边地区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记述是客观可信的。玄奘在记述上述地区情况时,除明确指出是“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外,并且都说到使用的语言文字,可见语言文字之于文化上的意义。而这已从这一带发现的焉耆—龟兹文写本得到认证,证实玄奘的观察是正确的。这也足以说明玄奘记述龟兹及周边流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可信度。在这里,玄奘的记述,不仅仅指出龟兹佛教文化部派属性问题,实为我们研究龟兹佛教文化,解读龟兹石窟壁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思路。在打好历史文献基础的同时,认真研读一下有部经律论三藏,尤其是像《大毗婆沙论》这样的论书,看看究竟说了些什么,是怎样说的,尽可能地掌握有部思想理论和学说主张,弄清一些基本概念,也许会使我们在龟兹佛教文化研究中少走许多弯路,取得更大成果。
(作者:江苏省常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
一
龟兹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但它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它的核心与主流,却是佛教文化。这样说,并非因为我是搞佛教石窟的,有意要抬高它,而是历史事实。当然我说的佛教文化,可不全是印度那样的佛教文化。由于龟兹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富于创造的民族,因此,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它融入了龟兹本土原有文化和民族思想情感。可以说,这里的佛教文化,虽是伴随印度佛教传入而生成发展起来,但却是有着龟兹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我认为,现在说的龟兹文化,应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主要指历史上新疆库车地方政权——龟兹国存在时期的文化。龟兹何时立国,文献未载,不过,《汉书·西域传》已立有龟兹国专传,不仅记载了龟兹都城、人口、兵员、官职,并讲到它的疆界。从传文所记内容看,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之时,龟兹大体上已是完整意义的国家。如果以此算起,到9世纪中虽回鹘民族西迁,龟兹成为西州回鹘领地为止,以今库车为中心,辖境包括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温宿和巴楚等县市的龟兹国历经1000多年。所谓龟兹文化,指的应是这一时期内生息繁衍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当然,也还要算上西州回鹘前期,即龟兹回鹘这一段。龟兹回鹘虽是西州回鹘下属地方政权,但独立性较强,首领自称师子王。后期,龟兹回鹘逐渐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开始伊斯兰化。这以后,就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龟兹文化范畴。也就是说,我们所讨论是11世纪初以前的龟兹历史文化,这是前提。对龟兹文化的概念,我觉得,作一界定是有必要的,它可使我们的讨论有个共识基础。
众所周知,自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时任西域长史班超降服龟兹,废龟兹王尤利多,立龟兹质子白霸为龟兹王,从此,龟兹进入白氏王朝(即龟兹王之名的头一个字基本上都带一个白或帛字。近有学者指出,按惯例,西域诸国通常是王子或王弟为质子,白霸既为尤利多为龟兹王时入侍汉廷的质子,则尤利多与白霸应属同一氏族,亦为白姓龟兹王,龟兹白氏王朝至迟始于龟兹王白建,而这里仍按传统说法叙述)。
白氏王朝有两个突出方面:一是统治龟兹时间长。从白霸开始,一直延续到8世纪末(唐贞元四、五年间,公元788~789年)悟空由印度回国途经龟兹时在位的龟兹王白环,长达近七百年。如此稳定的王朝,出现在当时民族迁徙流动性大、王朝更迭频繁的西域、中亚地区难能可贵,在我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二是白氏王朝历代诸王大多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佛教传入龟兹究竟发生在白氏王朝建立以前,还是在之后,暂且不论,但从文献记载看,他们对佛法的渴求,对高僧(包括外地来龟兹高僧)的敬重,今天仍感到他们那份敬法重人的挚诚。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用习惯的宗教标准作评判,不能完全看作是宗教狂热,或者认为是要利用佛教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理应回归到当时龟兹社会现实来分析考虑。我以为,龟兹白氏王朝诸王带头崇尚佛教,是出于对佛教文化的仰慕,是对当时一种崭新文化的追求。因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以宗教为其表征的。这样认识是否恰当,还可探讨,但在他们倡导和影响之下,龟兹境内佛教长盛不衰,佛教文化空前繁荣。这不仅文献有载,如今遗存在库车、拜城一带众多佛教寺址、石窟,便是当年龟兹佛教兴盛的明证。龟兹回鹘在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前,同样信奉佛教,程度虽不及白氏王朝统治时期那样鼎盛,但其文化仍是以佛教文化为主,开凿在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时期的窟,就是证明。在佛教盛行的同时,龟兹也曾有其他宗教流传,如祆教,在龟兹就建有祭祀场所——天祠。也发现有用龟兹文书写的摩尼教赞美诗卷子。在龟兹文化形成当中,亦吸收融汇了各种外来文化,尤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显示出多元文化的品格,这从龟兹石窟壁画上即可强烈感受到。尽管龟兹文化包含有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异彩纷呈,错综复杂,但佛教始终占据主导地拉,佛教文化无疑是龟兹的主流文化,是龟兹文化的基本形态。这样认为,也许有些过于绝对,但至少从目前揭示的龟兹文化的主要内容来看是这样。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也是一种文化最显著的特征。龟兹为多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流行过多种民族语言文字。龟兹又是中原王朝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汉语言文字曾相当通行,至今还能看到当年用汉文书写的官府文书、借贷契约和摩崖石刻,这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龟兹与内地密切的政治关系。然而,20世纪初以来,经中外语言学家通过研究从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收集到的古文字材料发现,这一带最为通用的语言却是吐火罗语。这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分为两种方言。一种分布于高昌、焉耆等地,称作甲种吐火罗语或焉耆语,记录的全部是佛典,特别是有关弥勒的经典很多。另一种则限于龟兹,称作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语。记录的内容除佛典外,还有世俗文书。虽然焉耆—龟兹语属于吐火罗语甲乙两种方言,但表述这种语言的文字,则是借用印度婆罗谜字母书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记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就是指婆罗谜字母而言。龟兹语即是借用印度婆罗谜文字,显然是伴随佛教而输入龟兹的。熟识情况的人都知道,龟兹佛教与印度贵霜王朝关系密切。20世纪初,在印度马土腊曾出土一尊迦腻色迦雕像,并有用婆罗谜字体镌刻的铭文。而类似用婆罗谜字母拼写自左到右横行书写的龟兹文题记,在龟兹石窟壁画上为数不少,有的时间早到4世纪,这说明,龟兹语文极有可能在佛教传入龟兹伊始即输入龟兹。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窟壁画榜题多用龟兹文、汉文和回鹘文三种文字合壁书写,表明有龟兹回鹘时期,虽然龟兹人种、语言逐渐回鹘化,但龟兹语文仍是通用的语言文字。岁月沧桑,龟兹语文这种古老语言文字虽已在民族融合中消失,无人使用,但应成为我们不可忘却的文化记忆。我国早期汉译佛经有相当部分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由龟兹语文本转译过来,因此,它在佛教传播上作出过贡献,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尤为重要的,它作为龟兹文化的一种载体,为我们记录、保存了大量有关龟兹文化的历史信息,它的学术意义不亚于龟兹石窟壁画。
龟兹乐舞是龟兹文化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也是历年论文著作述介得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内容,几乎成为龟兹文化的标志和代名词。然而龟兹乐舞,是在龟兹本地音乐舞蹈基础上,吸取印度、波斯和中原乐舞长处,尤其是印度乐舞长处而创造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乐舞体系。这自然亦是伴随佛教传入龟兹而逐渐形成完备的。
其他如文学、戏剧、美术也都渗透着佛教文化。尤其是作为龟兹国艺的雕塑、绘画,更是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佛教的传入,使龟兹文化思想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动了龟兹社会发展进程。没有佛教的传人,龟兹不可能如玄奘赞誉那样“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著称于西域;龟兹乐舞也不可能登上隋唐宫廷乐舞的殿堂,风靡中原大地;龟兹更不可能由一个城邦国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国,至今仍受到世人的关注。总之,佛教的传入,使龟兹文化经历一次重构过程,重构就是发展,对龟兹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
曾有研究者谈到龟兹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问题,认为龟兹文化的精神实质就是开放、兼容。的确是这样。龟兹为西域重镇,又位于丝绸之路要道,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这样的地理、人文环境,必然使龟兹文化具有开放、兼容的优势,构成了龟兹文化的一大特色。龟兹文化即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这正是龟兹文化独具魅力和吸引人之处。我们研究龟兹文化,就是要重视发掘其中的积极元素,古为今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服务。也许是巧合,龟兹文化的这种优势、特色,恰恰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佛教自传世2500多年来,一向以和平方式传播,从不用武力或别的什么手段强制别人信仰。也没有排他性,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保有开放接纳的姿态,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少思想禁锢、最有涵容人格精神的一种宗教。而这正是佛教文化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很难想象,若不是佛教的兴盛,佛教文化的浸润,龟兹文化怎能如此繁荣昌盛,为我们留下如此优美的石窟壁画!
二
龟兹文化,从文化类型上说,虽是以龟兹国之名命名的一种地域文化,它的核心区域在龟兹,但它的地域范围不应限于龟兹,即今阿克苏地区,还应包括焉耆、疏勒,也就是整个塔里木盆地北道沿线诸国,即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地区。这样说,并非有意夸大龟兹文化的区域空间,事实根据是不仅因为焉耆、疏勒毗邻龟兹,地域相连,最主要是焉耆、疏勒与龟兹在历史上皆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同属于小乘佛教文化圈带。只要翻阅一个我国三位不同时期西行求法僧行记,即东晋法显《佛国记》、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即可明了。他们都是经西域即今新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前往印度或返回中原内地。在他们的行记里,对南北两道沿线佛教信仰情况均有明确记述。
法显于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后秦弘始元年)从长安出发,次年抵达鄯善(若羌地区),然后转向西北往乌夷(焉耆),再折向西南到于阗,经子合(叶城)、于摩(叶城西南)和竭叉(疏勒,一说塔什库尔干)等国,西越葱岭,于公元402年(东晋元兴元年、后秦弘始三年)进入印度北境。他在《佛国记》里对所经之地佛教,除于摩国外,皆有记述。
鄯善国:
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乌夷国:
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
于阗国:
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
子合国:
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
竭叉国:
有千余僧,尽小乘学。
法显虽未到龟兹,没有记载龟兹情况,但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记载,4世纪中叶前后,龟兹佛教已相当兴盛,尽管大、小乘都有流传,但统辖龟兹佛教领袖佛图舌弥为小乘阿含师,足证龟兹佛教是以小乘为主。从法显所记可以清楚看到,5世纪初(实际年代肯定比这要早),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于阗、子合和北道的焉耆、疏勒等国,虽皆是佛教国家,并各有特点,然而南北两道佛教情况却是泾渭分明。南道于阗一带主要流传大乘佛教,北道沿线诸国则同龟兹,主要信奉小乘佛教。当时形成两个不同的佛教文化区域,即南道以于阗为中心的大乘佛教文化圈带和北道以龟兹为中心的小乘佛教文化圈带。
玄奘于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一说公元639年,唐贞观三年)西行印度求法,途经塔里木盆地北道,归程东越葱岭,从朅盘陀行进到乌铩,再北行到佉沙,然后转向斫句迦,经南道返回长安。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和卷十二分别记述了阿耆尼(焉耆)、屈支(龟兹)、跋禄迦(姑墨,今阿克苏)、朅盘陀(塔什库尔干)、乌铩(莎车)、佉沙(疏勒)、斫句迦(即法显《佛国记》所作子合国)和瞿萨旦那(于阗)等地佛教情况。由于玄奘西行印度求法来回皆取道西域,南北两道主要城邦国都记到,并且更为翔实和具体。
阿耆尼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屈支国:
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
跋禄迦国:
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伽蓝数十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朅盘陀国:
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乌铩国:
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习学小乘教一切有部。
佉沙国:
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斫句迦国:
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淳信三宝,好乐福利。伽蓝数十,毁坏已多。僧徒百余人,习学大乘教。
瞿萨旦那国:
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慧超为朝鲜古国新罗人,赴唐留学僧,也加入当时我国掀起的西行求法热潮,先循海路前往印度(具体时间不明),于公元727年(唐开元十五年)经西域返回内地。他在《往五天竺国传》里对疏勒、于阗、龟兹(安西)和焉耆佛教也作了记述,情况一如法显、玄奘所记,这里不再详细引述。
玄奘、慧超所记分别是7世纪初和8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佛教情况,与法显记之5世纪初相比,虽然南道大乘佛教势力明显削弱,如于阗,尽管这时境内佛寺尚有百余所,可僧徒已从数万减至五千人。子合尤甚,大乘僧由千余减至百余人,近乎衰亡。相对于南道而言,北道小乘佛教却大为增盛,特别是疏勒,小乘僧由过去千余人增至万余人。这种大、小乘之间的消长形势,并未根本改变南北两道佛教基本格局,依旧是:以于阗为中心的南道流传大乘佛教,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信奉小乘佛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玄奘在记述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北道信奉的小乘佛教是为说一切有部,并以文献形式记录下来,使我们对龟兹及其周边地区佛教文化的部派属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通过玄奘、慧超所记也看到,北道沿线诸国,至迟从法显时代5世纪初以来,一直坚持传统的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信仰,在经历多个世纪后,丝毫没有任何变化。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诸国,在佛教文化上,早已形成一个共同的比较稳定的区域,即一个在我国唯一的以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为主体的佛教文化区域,一个比较特殊的与我国其他地区(包括于阗在内)有所不同的佛教文化区域。
正是因为北道沿线国家皆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同属于小乘佛教文化圈带,因此,焉耆、疏勒与龟兹在文化上相同点很多。焉耆与龟兹两地居民不仅为同一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而且在风俗、婚姻、丧葬、物产等方面也大致相同。焉耆与龟兹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就连玄奘记述两地佛教时所使用的词语亦基本相同。疏勒与龟兹在文化上的关系,尽管文献记载没有那么明显,但仅从玄奘所记看,两地相同地方仍有例可举。如语言文字,虽然疏勒与朅盘陀、乌铩比较接近,与龟兹略异,但也是“取则印度”,想必是会通的。僧人则更不是问题。法显在《佛国记》讲到位于南北两道交汇之处的鄯善国时说:“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此(指佛教盛行),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这就是说,西域僧人皆通用梵文,不存在语言文字障阻。在佛事方面,所谓“勤营福利”,“不究其理,多讽其文”,即是指疏勒佛教偏尚修福,追求功利,重视诵读经文,不太深究其中义理,以及持戒较严,却不戒荤腥,食三净肉,等等,与玄奘记龟兹“尚拘渐教,食三净肉。洁清耽玩,人以功竞”相一致,保持了早期佛教的一些特征。特别是生活习俗上,玄奘记龟兹与疏勒两地流行一种“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的奇特做法,大概是在小孩出生后便用木板挤压头颅,使头部扁平。这种人工变形头颅的生活习俗,是受外部文化影响,还是源自本地?是融纳了原始自然宗教的遗绪,还是有着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文化背景?目前尚难论定,但流行于龟兹与疏勒两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是文化心理认同的典型表现。总而言之,尽管焉耆、疏勒与龟兹在政治上不相统属,还时起纷争,但在文化上确实属于一个体系,一个以龟兹为主的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文化体系。学术界在论述西域佛教文化分野时,总是划分成于阗、龟兹和高昌三个区域文化单元,而把焉耆、疏勒与龟兹视为一个区域文化单元,正是这个道理。因此,要进一步丰富我们对龟兹文化的认识,深化对龟兹文化的研究,全面揭示龟兹文化蕴含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就有必要把整个北道沿线地区甚至更大的范围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
三
以上概述了龟兹文化主要内容是佛教文化,龟兹佛教文化主要属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文化以及地域范围,下面再就龟兹佛教文化研究的思路问题,主要是如何看待龟兹大乘佛教和玄奘关于龟兹及周边国家盛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这样两个问题。
据《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收录的《鸠摩罗什传》记载,4世纪中叶,鸠摩罗什由小乘改宗大乘,曾在龟兹大力弘扬大乘佛教。从传文看,声势影响都不小。实际情况是否确如传文描写的那样,需要综合分析。因为这两部传文皆出自内地僧史学家之手,他们偏爱大乘佛教,在行文中不免会加进溢美之词,作些渲染。即使讲的全是实情,也不难看出,尽管罗什大力弘扬,龟兹大乘佛教始终只是停留在龟兹上层社会层面,只是在以龟兹王室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小圈子里流传。佛寺也仅限于罗什居住的王新僧伽蓝(王新寺),寺僧仅有90,在龟兹僧团(当时龟兹僧有1万余人)中所占比例很小,成员估计大多来自王族子弟。可以这样说,龟兹大乘佛教,仅是龟兹王室贵族的佛教,与平民百姓有一定距离。由于缺乏群众基础,随着前秦苻坚派遣吕光率军伐龟兹及焉耆诸国,罗什被劫往凉州,失去了代表人物,龟兹大乘佛教很快便归于沉寂。它对龟兹的影响,包括石窟造像,却很有限,不可估计过高,更谈不上发生龟兹佛教改宗问题。6世纪末,从文献上看,确有西来大乘僧在龟兹弘法,在位龟兹王透溢出对大乘僧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但大乘僧讲的皆是大乘人门性质的内容,龟兹王对大乘佛教仍处于尚未精深阶段,仅是一位诚笃之士而已,因此也很难说6世纪后期龟兹大乘佛教称盛。7世纪后,随着唐王朝重新统一西域,龟兹与中原内地关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迁居龟兹,在中原佛教影响下,龟兹大乘佛教重又活跃起来,库木吐喇石窟中的一批汉风窟便受敦煌壁画深刻影响,而阿艾石窟简直就是敦煌壁画的翻版,属于典型的中原大乘佛教回流龟兹的例证。似如慧超所记,仅是“汉僧行大乘法”,广大民族僧众仍是信奉小乘学说一切有部。正因如此,在龟兹石窟,特别是克孜尔石窟,壁画集中而具体地绘出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特有题材,形象地为我们诠释了小乘有部思想内容。就现存佛教遗迹看,无论是在佛教老家印度,还是我国内地,都是不可多见的。因此,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不仅开凿年代早,在我国石窟史上具有追本溯源意义,而且更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佛学大师玄奘在西行印度求法前,在国内即已遍参名师,穷尽各家学说。在西行求经的17年时间里,接触了当时西域、中亚和印度各地包括说一切有部在内的大、小乘各种派别,观察细致周详。回国后又亲自译出说一切有部论藏中的《异部宗轮论》、《法蕴足论》、《发智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和《顺正理论》等论书。尽人皆知,说一切有部虽是小乘佛教众多部派之一,然而却是思想理论最为丰富、势力与影响较大的一派,主要流传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和迦湿弥罗地区,有自己的经律论三藏。经藏同别的部派一样,以四部阿含经(《长》、《中》、《杂》和《增一》)为根本经典,只是次第有异,将《杂阿含经》置于首位。律藏有两种:一是《十诵律》,主要是在罽宾流传的较为原始的一种律本。另一种即《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包括诸事)。虽然结构、内容与《十诵律》差别不大,但增加不少本生、比喻故事,还掺杂有佛传内容,卷帙也相应增加,因而被称作有部律广本,称《十诵律》为略本。论藏,即是对阐释佛经义理论书的总称,又作《阿毗达磨》、《阿毗昙》、《毗昙》,其论书主要就是上面提到玄奘译出的那些。因为说一切有部最重论藏,喜兴造论释经,不仅为我们留下为数众多的理论著作,而其学说思想就体现在这些论书之中。这一点,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说疏勒僧徒“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来看,从慧立、彦琮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在龟兹参访阿奢理贰伽蓝时,该寺住持(也是当时龟兹佛门领袖)木叉毱多特意向玄奘推荐“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来看,都反映出说一切有部重视论藏情况。玄奘这里说的《毗婆沙》,即《大毗婆沙论》,全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俱舍》,即《俱舍论》,全称《阿毗达磨俱舍论》;《杂心》,即《杂阿毗昙心论》,均为说一切有部3部重要论书。尤其是《毗婆沙》,系统总结论述了说一切有部学说的基本理论,地位最突出,被奉为圭臬。玄奘不仅译出《毗婆沙》,而且翻译了有部几乎所有大论(玄奘所以花大力译出有部论书,恐怕也是考虑到这些论书思想丰富性),应该说,玄奘对有部学说思想深有研究,对有部形成、发展、演变和流传情况不可谓不知,他对龟兹及周边地区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记述是客观可信的。玄奘在记述上述地区情况时,除明确指出是“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外,并且都说到使用的语言文字,可见语言文字之于文化上的意义。而这已从这一带发现的焉耆—龟兹文写本得到认证,证实玄奘的观察是正确的。这也足以说明玄奘记述龟兹及周边流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可信度。在这里,玄奘的记述,不仅仅指出龟兹佛教文化部派属性问题,实为我们研究龟兹佛教文化,解读龟兹石窟壁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思路。在打好历史文献基础的同时,认真研读一下有部经律论三藏,尤其是像《大毗婆沙论》这样的论书,看看究竟说了些什么,是怎样说的,尽可能地掌握有部思想理论和学说主张,弄清一些基本概念,也许会使我们在龟兹佛教文化研究中少走许多弯路,取得更大成果。
(作者:江苏省常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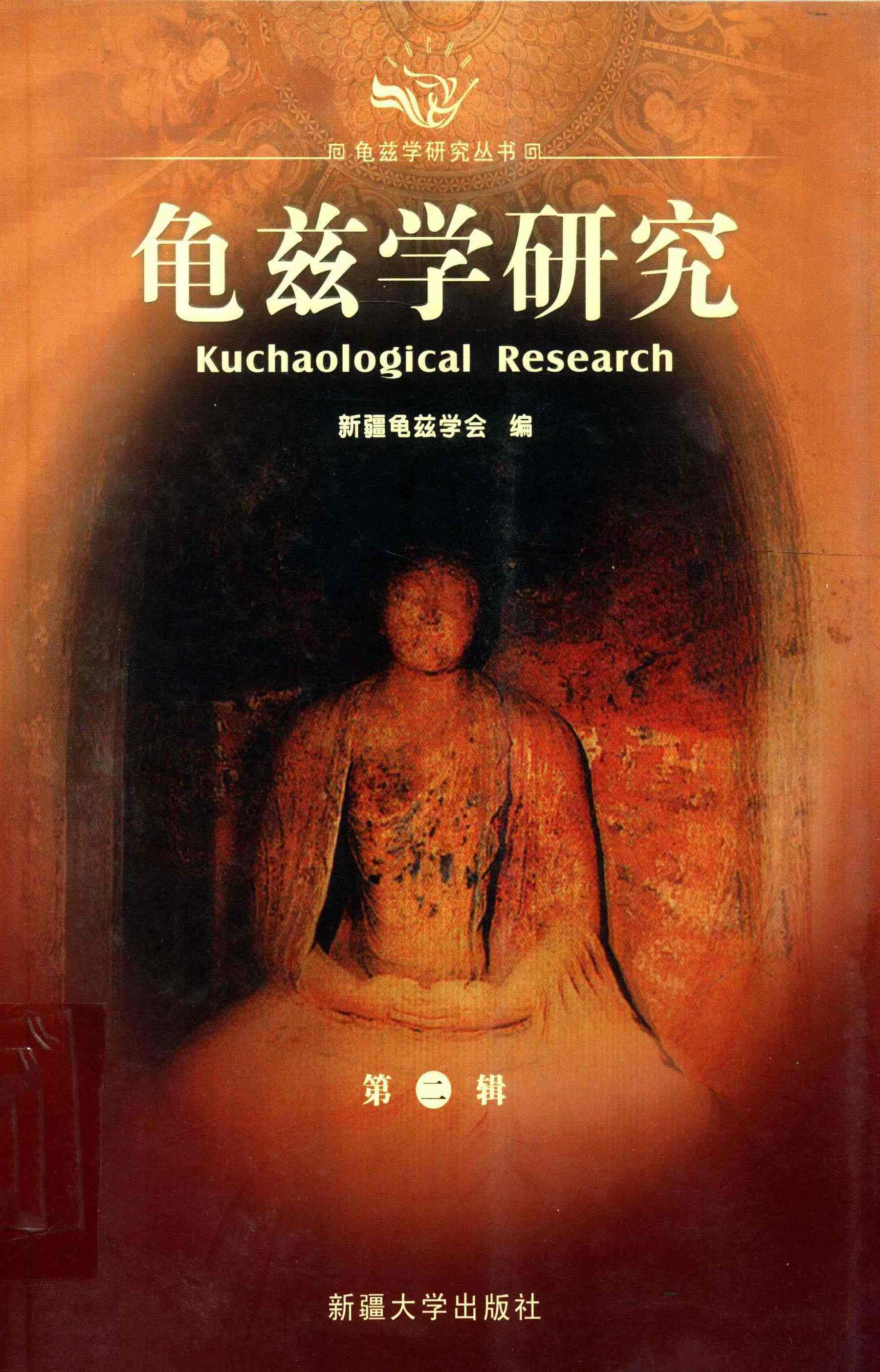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出版者:新疆大学出版社
本书所选论文分为“大家论坛”、“历史研究”、“考古探秘”、“佛教石窟”、“文化艺术”、“史料研究与情报”六个部分。新疆龟兹学会成立已三年有余了。三年来新疆龟兹学会抓了三件事:一是每年召开一次“龟兹学学术研讨会”。二是编辑出版新疆龟兹学会学术刊物《龟兹学研究》。三是进行《龟兹学概论》的编撰工作。
阅读
相关人物
姚士宏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