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 内容出处: |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449 |
| 颗粒名称: | 历史研究 |
| 分类号: | K294.5 |
| 页数: | 87 |
| 页码: | 025-11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龟兹学历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其中包含:塔里木盆地周缘古代居民饮食结构溯源、龟兹文化的研究视域、关于龟兹文化的几个问题、佛教初传龟兹新考、吐火罗与回鹘文化、敦煌晚唐五代中外文化交融与碰撞。 |
| 关键词: | 塔里木盆地 溯源 新疆地区 |
内容
塔里木盆地周缘古代居民饮食结构溯源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 安尼瓦尔·哈斯木
新疆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根据现已掌握的考古资料,在昆仑山北麓的和田河、克里雅河、尼雅河、安迪尔河的河谷及上游地带,罗布淖尔荒漠、孔雀河下游河谷、楼兰故城周围等地均分布有许多细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而且时代延续的比较长。特别是从史前时期遗址在塔里木盆地分布较广的特点看,这里在当时应是古人类出没,采集,捕鱼,狩猎甚至进行简单农业生产的地域。这些因素导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之古代先民们历经数次的迁徙、融合与变迁之后,根据自己的文化底蕴在吸收与融合的基础上,较早就创造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中包括饮食文化。这些均为目前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所证实。因为在这些遗址除发现大量的石核、石球、石镞等石器外,还发现有陶器。谷物类食物的加工与肉食不同,必须要有加工的容器,而陶器的出现则表明当时可能出现了原始农业,同时,这无疑也是人类饮食习俗的形成与饮食结构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环节。
饮食习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进化与确立,与人类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能力,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反差有着密切关系。从塔里木盆地的情况看,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居民虽多,但他们同样也经历了从蒙昧状态时的进食方法到文明进食,结构搭配合理的历史阶段。为使人们对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饮食文化与饮食结构的形成,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与了解,本文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和我国历代文献典籍对其进行溯源。
一 秦汉以前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社会经济与饮食构成
西域由于地处四大文明的交汇处,所受到的文化影响与辐射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看,西域文明仍是由西域远古居民自己最早创造的,在当地土著文化基础上融合四大文明精华而形成的一种多元复合型地域文化。塔里木盆地作为上万年前就存有古人类活动的一个地区,这里所遗留的诸如:和田市南哈因达克以南约10公里的玉龙河右岸①;洛浦县东南约25公里的干河床②;民丰县南尼雅河两主源汇合点以北约15公里的纳格日哈纳西北的干河床③;尉犁县的辛格尔遗址④和喀什西南乌帕尔乡的乌帕尔遗址⑤,以及罗布淖尔周围一带大量反映史前文明的遗址与发现的石核、石锤、各种尖状器、刮削器、切割器、石斧、石刀、石镞、石磨盘、石磨棒及器形,以缸、瓮、壶、钵、碗、碟等为主的陶器残片和有被火烧硬并高出地面的灶址⑥等遗物,说明这里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通过这些,使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与他们用这种极简陋的生产工具过着采集、狩猎生活的现象有初步的透视。石磨盘与石磨棒以及陶器和灶址等的发现,表明当时除了发达的狩猎、捕鱼业与畜牧业外,已出现原始农业。人类的进食习惯也开始发生变化,谷类食品与肉食不同,它不能直接在火上烧烤,必须借助陶器来煮食。
当步入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后,这里的居民又创造出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兼营农业的农牧并重的史前文明。从孔雀河下游的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天山南麓的和硕辛塔拉、阿克苏喀拉玉尔衮和库车喀拉墩等遗址发掘的资料看,当时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居民,虽然出现了小规模的种植业,由于粗放经营,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仍然还是以狩猎、捕渔、采集和游牧为主,日常生活仍以肉类为主食,谷物只是附属食物,饮食结构显得相对单一,下面就考古发现做一些论证。
(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2年在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60公里的小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与发掘距今3800年左右的墓葬4座,获得大量各类珍贵文物。其中,发现最多的当属牛皮、牛头、羽饰、箭杆、木器、毛织物和皮革服饰。虽然在M1出土斗篷边缘捆扎小包内发现麦粒,在M2木雕人像身下、毛织斗篷内发现麦粒与粟粒,普遍随葬的草编篓内发现干结的食物,但没有发现陶器以及与农耕生产有关的生产工具①。从出土弓箭、皮革制品和木器、自地表采集的大量遗物看,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畜牧业与狩猎业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也食用小麦类粮食作物,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的补充。另外,2004~2005年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小河墓地再次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墓葬167座,除获得极为丰富的各类文物外,也获得了部分与饮食文化有关的资料。
(2)1979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发掘了一批距今3800年前后的墓葬,获得大量的遗物,其中,随葬品中以皮毛制品、草编小篓、牛角、角杯和木杯、木盆等居多,不见陶器。这一切表明他们的经济生活仍以畜牧业为主,饲养的牲畜主要是绵羊、山羊、牛和骆驼,日常吃、穿的主要生活资料均取自畜牧业。当时狩猎业居于重要位置,人们通过猎取马鹿、野羊、禽鸟,捞取河鱼来补充着日常生活。虽然他们也种植和食用小麦类粮食作物,但在日常生活中占的比重十分有限①。总体而言其饮食结构还是比较单一,这不仅与当时该地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社会生产低下有关,而且这种以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与罗布淖尔地区荒漠、半荒漠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有关系。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单位,先后于1985年、1989年、1996年和1998年在且末扎滚鲁克墓地进行了清理与发掘,其中一期文化年代距今约有3000年,随葬物多为木器、石器和陶器;距今约2700年的二期文化除了随葬大量的木器、石器、陶器、毛织物,少量的铜器与铁器外,该期墓葬发现有存在放置食物的习惯,主要是羊排骨和羊排骨串,面食较少。墓葬殉牲习俗,一般是羊头(山羊和绵羊)、肩胛骨、牛角、马头、马牙、马下颌和马肩胛骨、狐狸腿等②。从丰富的随葬品看,此时社会经济虽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居民日常生活仍然是以畜牧与狩猎为主,农耕经济没有得到发展,从而使当地居民的饮食结构也还是以肉食为主,粮食类作物占的比例不大。
从对秦汉以前各类遗址、墓葬的发掘清理,以及从中出土的文物与居住遗址的灶址来看,当时人们开始已步入定居的生活阶段,经营有农业,种植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和粟,但种植业的规模极为有限,因而畜牧业和狩猎、捕渔及采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占主要地位,这可从大量随葬的牛、羊、马、驼骨骼、皮毛及毛织物、弓箭等得到见证。至于人们的饮食构成,由于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古代居民在文化与经济形态上有许多共同点,所以人们的饮食主要是烹或烤制的牛、羊肉和各种乳制品,饮食结构相对单一。当然,从用于殉葬的马和骆驼的出现,可以看出马和骆驼与人们的关系较为密切,除了在放牧、狩猎、交通运输和战争中发挥作用外,应该说也开始将其列入了食物的范畴。罗布淖尔地区作为远古人类栖息与活动的重要场所,虽然较早就出现了原始农业,但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低,种植规模也极为有限,根本无法满足人们对饮食的需求,也无法改变人们的饮食结构,所以除了畜牧业,传统经济方式中的狩猎和采集,不仅是当时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还是人们食物重要的来源。
二 从游牧向农耕文化过渡时的饮食构成
西域原始文化带有多元的色彩,秦汉时起西域独特的文化结构已经成型。它大致以天山为界,形成两个相互依存,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在天山以南,凡有水源的地方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绿洲。这些绿洲不仅是当地人类生存繁衍之所,而且还构成了新疆古代农业区。汉代,是新疆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因为不仅使新疆正式划入汉朝版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中出现了“城郭之国”。当然,在秦汉之际,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的经济生活中,虽然畜牧经济仍为主要的经济生产形式和食物来源,畜牧的规模明显大于史前时期,但随着城市的出现,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来自中原地区的屯田士卒进入塔里木盆地周缘,汉族人民开始加入西域多民族大家庭的行列之中,自此中原地区的艺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等开始大量涌入。更重要的是,通过民族的迁徙、融合与发展,促使这里的农业经济也有了飞跃的发展。虽然秦汉时期当地的经济形态仍主要为畜牧业和狩猎业,但由于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方法和生产工具以及先进理念的传入,农业由史前时期的粗放式经营,逐渐开始向规模化的园圃式经营过渡,因而从秦汉时期开始农业经济在塔里木盆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所占比重明显增大。早在距今3000年左右,经昆仑山北麓,到天山南、北麓之山前、河谷台地地带,在广阔的地域内已经出现了种植业。步入秦汉以后,农业的崛兴改变了塔里木盆地居民单一的以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使居民饮食结构趋于完善。
(1)198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洛浦县西南14公里的山普拉墓地进行了发掘,获得了大量各类文物。在出土遗物中除有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外,还有粮食与食物。粮食种类有黍和大麦,在M05、M06、M07、M10、M16、M20和二号马坑中皆有发现。墓葬的粮食主要捆扎在长服的下摆衣角处,有的放在皮口袋或绢布口袋内。食物仅在M06和M20号墓中发现。M06出土一块黍饼,去壳很干净,基本呈粉状。出土时为圆形,饼厚0.25~0.5厘米。M20在尸体上身右侧一兽皮口袋内,内装6个圆饼和一些被加工过的黍粒,圆饼内掺麦壳,饼呈灰黑色,最大径6.5厘米、厚0.6~1厘米;最小径5厘米、厚1厘米,圆饼均为手工捏制。在M06出土一木钵中发现已干化的黍米粥,从M02中还
发现1个核桃。此外,山普拉墓地发现二座马坑,各埋一匹马。一号马坑的坑形保存不太好,但马保存完整,皮毛皆未完全腐烂。马毛色为黄色,葬式为侧身直肢,头向东,面向北。马身上盖有芦苇杆和树枝,额头上插有两根白色羽毛;二号马坑呈不规则“凸”字形,马坑竖穴。坑口距地表35厘米,坑底长241厘米,宽140~198厘米,深110厘米。马保存完好,上部盖有顺长的树枝条。马毛皮大部分都在,毛色呈黄色。葬式亦是侧身直肢,头向北,面向西。颈部和尾部有毛绳,马背上备有鞍具及配件①。从出土遗物看,经济方面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同时也有一定的园林和狩猎。
(2)1996年,且末扎滚鲁克墓地第三期文化墓葬中,除获得陶罐、陶壶、木盘、木碗、木箸、木耜、漆案、铜勺外,还发现食品与谷物。食品均置于漆案上面,有油炸的菊花饼、麻花、桃皮形小油饼、薄饼、葡萄干及连骨肉等,谷物与杂草、棉布一起出土②。
(3)1979年和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孔雀河下游老开屏东汉墓地和楼兰故城东郊两处高台墓地进行了发掘。这些墓葬出土的文物以木器为主,有各种木盆、木盘、木杯、钵、木勺和桶等。木盘是木器中的主要用器,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形制也较丰富,有长方形、椭圆形和圆形3种,均附木腿。这种木盘是当时主要食具。楼兰城郊B高地墓葬出土的木盘中,均见羊头、羊骨,老开屏墓地内也见羊骨。出土木盆与木盘中盛大量羊头、羊骨,这表明当时羊是饲养的主要牲畜,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食物品种①。同时,也说明当时楼兰王国的经济仍是以畜牧业为主。
(4)198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古队在楼兰故城进行考古调查时在孤台墓地清理墓葬两座,获得各类文物170件。其中出土的椭圆形和圆形木盘中均盛有羊头骨和羊骨②。
(5)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尼雅遗址考古调查中,采集和清理的遗物有1千余件,其中除牛羊颈栓、搅拌杆、木桶、铁镰刀、角杯和木碗、木杯等生活与生产器皿外,还有牛、羊、鹿、马和鸡骨等,皮毛有羊毛、骆驼毛、马皮、牛筋和猪鬃,谷物有麦和粟,并采集到一根较完整的麦穗③。此外,在这里还发现过青稞(燕麦)、糜谷、干羊肉、羊蹄、雁爪、干蔓菁等④。
上述这些资料不仅反映了秦至两汉时期塔里木盆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而且还可以看到,当地居民除了畜养羊等家畜之外,马、牛、骆驼等大牲畜的饲养也相应增多。当时,家畜中的羊始终是主体牲畜,羊肉仍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食物。占有羊的多少成为了人们显示财富多寡和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之一,墓葬中发现的整羊、羊头、羊蹄、羊骨、牛筋和殉葬的马匹,明显表明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以肉为食、以酪为浆的日常生活画面。据《汉书·西域传》:“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的记载以及出土的粮食作物、食品与葡萄等,同时也说明了内地种植的麻、菽、麦、稷、黍,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已开始种植。在畜牧业发展的同时,农业与园艺业亦开始发展,尤其是汉王朝派遣的屯田士兵从中原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水利工程技术,更会对塔里木盆地农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塔里木盆地是汉朝在西域屯田的一个重要基地,当时的屯田今天尚有残迹可寻,主要见于轮台、沙雅、若羌和楼兰遗址。驻兵屯田,既是开发建设边疆地区的一项经济措施,同时又是保障边疆安定的一项军事措施,因而汉王朝非常重视在那里的屯田事宜。东汉时期的犁耕、牛耕技术在屯田事务中广泛使用,优良品种不断引入,因此当时这里种植的粮食作物已大体与中原地区相同,在人们的饮食生活中,具有高产潜能的粟开始跃居首位,成为人们饮食构成中的主要粮食品种。同时,园艺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葡萄开始较广泛的种植。
尽管以天山为界,把新疆分成了两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但是不能说绿洲农业为主的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畜牧业不发达。《汉书·西域传》说:诸绿洲国家兼营农业和畜牧业。以农耕为主的国家有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龟兹、温宿、姑墨、焉耆、危须、尉犁等,以畜牧为主的国家有鄯善、若羌等国。这些国家不管是以农耕为主,还是以畜牧业为主,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看,两种经济形态是同时存在的。随着农业、畜牧业和园艺业的发展,当地居民的饮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进食习惯和饮食结构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三 农耕化促进了饮食构成的丰富与完善
汉以后,尤其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新疆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此时随着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畅通,相互往来的不断频繁,民族的迁徙与融合,各种文化的不断碰撞与交流,使得处于丝绸之路重要地段的塔里木盆地周边各绿洲得到高度发展与繁荣,民族文化由分散到聚合,形成异彩纷呈的多元民族文化。同时,经济形态也开始转入以农业和园艺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阶段。当然在发展与变迁过程中,长期以来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先民,历经迁徙、变化、繁衍生息、融合发展,不仅共同创造了辉耀千古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在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饮食构成。正因为塔里木盆地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汇聚与吸收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人群的文化传统,并结合当地实情进行了必要的改进和提炼,从而在饮食种类和习惯等方面既存在差异,也有一定的共性。
从塔里木盆地周缘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和发现情况来看,历史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代居民们,在从事着狩猎、采集和游牧生活时期,基本是将肉类,特别是把饲养的羊作为了主要食物,而将谷类、豆类作物和各种水果作为了附属食品。人类社会步入农业文明进一步发达的历史阶段后,生活在农耕生产占主要位置的绿洲国家古代居民们,开始食用以粮食作物和蔬菜加工的各种食品,特别是将面食作为主要食物,蔬菜与水果的比重也开始增大,而畜牧业虽然也很发达,但肉食及奶制品却相应退居附属地位,合理的饮食结构开始确立。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各种文字类文书的记述看,这个时期塔里木盆地居民饮食构成开始呈现多样化,膳食搭配亦趋于合理与科学,涵盖了农林牧之特点。
(1)粮食作物食品粮食作物包括“五谷”,加工后的食物一般泛称面食。面食是随着农业文明的产生,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发展,逐渐产生和丰富的。从新疆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所获资料来看,大约在公元前8000~2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或距今7000~6000年前,就出现了原始农业①。塔里木盆地作为较早步入农业文明的区域,因而除肉食外,粮食作物也较早就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食物。除《汉书·西域传》的记载,《魏书·西域传》同样有“(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疏勒)土多稻、粟、麻麦..”②。《北史·西域传》有焉耆“土田良沃,谷多稻、粟、菽、麦”③。《洛阳伽蓝记》卷5有“(朱居波)人们山居,五谷甚丰,食则面麦”之记述。由这些史料看,魏晋时期不少绿洲国家已基本改变了史前时期那种“以肉为粮,以酪为浆”的固有生活模式,在饮食构成中开始以粮食作物为主。丰富的考古资料更能对此问题给予足够的证实。楼兰、尼雅出土的汉文简牍保存着大量有关大麦、小麦、粟、米以及麻种植、食用等方面的记录。诸如:“禾一斛七斗六升给禀将尹宜部兵胡支鸾十二人,日食一斗二升起十月十一日尽十一月十日”①;“黑粟三斛六斗禀战车成辅,一人日食一斗二升起二月一尽卅日”②;“将张佥部见兵廿一人,小麦卅七亩已截廿九亩。禾一顷八十五亩溉廿亩莇九十亩”,“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小麦六十二亩溉五十亩,禾一顷七十亩莇五十亩溉五十亩”③等。同时期出土的佉卢文简牍中关于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种植与食用及灌溉等方面均有大量的记述。另外,对于粮食作物,在吐蕃文简牍中就有:“龙年,从种子农户口粮麦子中匀出半克..鲁古,口粮半克。种子一克四升,糌粑二升。分与拉列..价八升,后又十二升,从新谷中给觉卧赞青稞三克,送往若羌二克”④之记载。与文献相互对应的考古发掘资料也极为丰富。诸如:.
1980年,楼兰故城遗址内佛塔东面约30余米处,发现黄灿灿的粮食堆积,堆积层厚约70厘米、宽约100厘米,经鉴定确认为糜和裸大麦⑤;1999年,在汉晋时期的营盘墓地考古发掘时,从M8出土了3件圆形木碗,其中一件内盛羊头和羊肉,上面放有几层薄饼;另一件内盛有沙枣和形状不规则的饼等食物⑥;1958年,焉耆县唐王城清理发掘中发现房屋基址及粮仓遗迹,出土的谷物有小麦、谷子、高粱、胡麻以及磨的很细的面粉⑦。此外,在若羌县米兰古堡还发现有青稞籽实⑧。
(2)肉食制品在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的农业生产虽然得到高度发展,但是作为传统经济手段之一的畜牧业,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经济与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均将肉、奶子、奶皮子、奶疙瘩等作为主要食品,将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作为副食品来食用。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则基本都是将谷物、蔬菜和水果等农作物作为主要食物,将肉和奶制品作为副食来食用的。然而从这一时期的变化看,虽然人们开始大量食用以粮食作物和蔬菜加工的各种食品,特别是将面食作为了主要食物,但是由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畜牧区,以肉为食早已渗入当地居民的生活领域。因这种传统饮食习惯的因素,故肉食在此时不仅仍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更注重了精细处理,食用方法亦开始多样化。此时除传统的烤、煮法之外,对肉食的制作也有了许多创新。
(3)蔬菜、瓜果的种植与食用我国蔬菜瓜果的种植历史,文献上只能追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已经产生了专门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业。但从考古发现看,其历史则要比这早,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就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而言,蔬菜瓜果的栽培与食用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西域的园艺业已相当发展,塔里木盆地各国普遍种植葡萄、杏、核桃等,酿制葡萄酒成为重要的手工业。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园艺业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也就是说,由于汉代以后农业和林果业得到更大的发展因而使蔬菜与瓜果成为当时人们饮食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粮食作物而言,蔬菜和瓜果的遗存发现较少,特别是蔬菜,由于叶茎难以保存,故无实物出土,瓜果多数只为果核,其中发现较多者为葡萄。诸如: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葡萄园遗存②以及涉及葡萄园的佉卢文文书③。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遗址陆续发现葡萄园、葡萄藤以及与葡萄园有关的佉卢文文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共同尼雅遗址联合学术考察队在该遗址内的房屋遗存周围,发现大量的葡萄园遗存和残留的葡萄藤。尤其是分布于编号为95A2和95A7之房屋四周果园中的葡萄种植面积占有相当的比例。其中,编号为95A2中的葡萄园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o米,东西宽约30米,周围有篱笆墙,该葡萄园面积虽说较大,由于大部分已为流沙所掩埋,现所能见到的仅为东西方向的3排和北边的2排葡萄藤;编号为95A7中的葡萄园位于编号为93A24(N44)之西150米处,为至今所发现的葡萄园中面积最大者。其东西长122米,南北宽68.5米,葡萄藤呈东西向排列①。除此,在该遗址北边还发现了长50米,宽30米,四周围有篱笆墙的葡萄园遗址。此遗址现存有9行东西向排列的葡萄藤,其行距大约在2米之间,且每一株葡萄前均残留有用于搭葡萄架的木桩②。另外,从该遗址编号为A39-27的房屋侧房里,还发现了用葡萄藤编织的锅支架③。当然,葡萄在楼兰故城遗址、且末扎滚鲁克墓地、洛浦山普拉墓地等处也有发现,如: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尉犁县营盘汉晋时期墓地考古发掘时,从编号为99BYYM7和99BYYM66两座墓中发现了几串干葡萄④。
除发现大量实物、保存基本完整的葡萄园遗址外,还发现了大量有关葡萄园典当、租赁、买卖以及葡萄酒等方面的佉卢文简牍。其中1959年发现的一件,是“鄯善国精绝州居民苏耆耶、鸠那耶买葡萄园契约”⑤;1991年发现的内容涉及“应该提供贮藏的葡萄酒中有相当于15峰骆驼分的葡萄酒”;编号为91NA20的则涉及用于纳税的谷物和葡萄酒⑥。这些文献对于葡萄园的规模、面积,葡萄及葡萄制品的加工生产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记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葡萄在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变得愈发重要这一点,也给予了一定的反映。由于葡萄在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得到广泛的种植和食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商品化程度亦得到不断的发展。因而在当时人们除了鲜食外,还进行葡萄制品的加工。出土的佉卢文简牍中多见葡萄和葡萄酒字样,以及用于纳税和交换的记载来看,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居民普遍饮酒,而且酿酒的原料则为葡萄。
除了葡萄之外,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栽培和食用的水果种类还有很多,史料记载极为详实。其中成书于公元5世纪的《西京杂记》有:“瀚海梨,出瀚海地,耐寒而不枯”的记载。唐代高僧玄奘于公元7世纪所著《大唐西域记》有:“阿耆尼国,.引水为田。土宜糜、黍、香枣、葡萄、梨、柰(苹果之一种)诸果”;“屈支国..宜糜、麦,有粳稻,出葡萄、石榴,多梨、奈、桃、杏”之记述。同时,有部分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诸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中,在尼雅遗址、楼兰故城、洛浦山普拉墓地、且末扎滚鲁克墓地、营盘墓地、洛浦县阿克斯皮尔故城遗址和巴楚脱库孜沙来古城遗址均发现了杏、核桃壳、梨、苹果、枣、甜瓜籽、桃核、巴旦木、酸梅、桑树、沙枣树等①。虽然还有部分水果没有发现实物,但在出土的各类文字文书及文献典籍中却有记载。
除了尼雅遗址发现的干化蔓菁外,有关蔬菜方面的实物尚未发现,但这并不表明当地没有栽培和食用蔬菜。据史料记载看,张骞通西域之后,产自西域的胡麻、蚕豆、大蒜、洋葱、芫荽(香菜)、黄瓜、红花、胡萝卜和菠菜等农作物纷纷传入我国内地,这些信息都能表明古代新疆蔬菜栽培和食用情况。另外,从楼兰、尼雅等地出土的汉文、佉卢文和吐蕃文书,对当地的蔬菜种植与食用情况均有记述。诸如:《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有:“.加浇种菜,预作冬储”②之内容。米兰戍堡遗址出土的吐蕃文简牍中也有不少反映蔬菜种植方面的信息。如“农田长官多贡之佣奴农户,专种蔬菜的零星地”①。“在小罗布(nob-chun即鄯善)有八畦菜园子,沙弥菩提藏正在耕种时,突然命终”②和“青年与同行的二十人,平均每人食品..(四个)圆饼、发面饼、青菜、腌菜碗”,③。另外,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也有菜园子一词,即“qavlal■r”④。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不仅种植和食用蔬菜,而且也储存和腌制蔬菜。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认定,两汉以后,尤其是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应该是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饮食构成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时期。许多流传至今的食品都是在这个时期趋于完善、发展和定型。正是在这一时期,在人们的饮食生活中,传统的主粮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绿洲地带的居民逐步确立了以麦、粟等粮食为主食,以蔬菜、瓜果和一定量肉食为副食的饮食结构模式。由于此时正处于民族大融合与大发展阶段,故而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地居民的饮食文化,也经历了相互交流、学习和吸收借鉴的历史进程。因而在这一时期不仅初步形成了以蒸、煮、烤、煎、炸、烹等为基本手法,以色、香、味、形为终极效应,具有整体性、完美性和营养性的综合烹饪艺术,而且还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饮食体系与风味。同时,随着文化的交流,胡饼等食品,葡萄酒、奶酪等饮品与奶制品和葡萄、核桃、石榴、洋葱、大蒜、黄
瓜、香菜、菠菜、胡椒等果蔬香料经过丝绸之路纷纷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饮食文化,许多已深深扎根于中华饮食文化之中,成为我国传统饮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此外,在这个时期进一步成熟与成型乃至通过吸收、借鉴而发明创造的食品,至今影响依然至深至巨,历久不衰,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两汉以后塔里木盆地周缘诸绿洲之农业、畜牧业和林果业得到了全面均衡的发展,确立了以粮食作物为主,畜产品、瓜果和蔬菜为辅助食品的合理结构,因而他们所创立的饮食文化,在当地居民以及我国饮食文化史中无疑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总之,从考古发掘资料、文献记载和各种民族文字的古文字文书记述来看,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饮食构成经历了形成、发展和完善这样三个重要时期,而且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当地独特的特点。这里由于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故对于传播、吸收和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民族之间、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推进该地区文明化进程加快之同时,对饮食文化的发展变化也起着促进作用。因而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饮食文化作为新疆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独具特色的西域文化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同时,由于丰富了祖国的饮食文化宝库,对于进一步研究我国饮食文化史有着深远的意义。
(作者:新疆博物馆研究员)
龟兹文化的研究视域
仲高
如果从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新疆库车等地进行掠劫式考古发掘算起,龟兹历史文化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程了。龟兹历史文化研究最初主要在佛教石窟以及佛教壁画、雕塑的考证考释、龟兹古文字的解读、龟兹历史脉络的梳理等方面,且以考古物证与古代文献相互印证,有了二重证据之效。自此,龟兹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延伸,涉及龟兹佛教文化、雕塑和壁画艺术、龟兹乐舞、龟兹风俗、龟兹语文、龟兹文学、建筑和服饰文化、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龟兹文化研究方法也由专题研究和单一学科研究向综合性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跨出了一大步。龟兹历史文化研究最骄人的成果还是龟兹佛教文化的研究,而龟兹世俗文化研究就相对薄弱,不过,研究者都力图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域上进行新的尝试。但是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或中或外、或旧或新),都回避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在追求一种“客观”效果。这种超历史的纯客观研究忽略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这个问题就根本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在龟兹文化研究领域存在着诸多视域的融合,即历史与现实、客体与主体、自我与他者等等,但是根本的是研究者如何对待研究对象——龟兹文化的视域。我们应该努力扩展研究者的视野与传统的诸多视野的“视域融合”效应。由此可见,跨文化研究追求的应是“视域融合”的效应。对此,加达默尔认为:
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把这运用于思维着的意识,我们可以讲到视域的狭窄、视域的可能扩展以及新视域的开辟等等。..一个根本没有视域的人,就是一个不能充分登高远望的人,从而就是过高估价近在咫尺的东西的人。反之,“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东西,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观看。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①
这就是加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在此,理解者和解释者所要做的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之与其他视域融合。加达默尔进而认为:“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融合过程。”②这意味着把理解概念定义为一种“视域融合”,“成功地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本质的看法,从而使过去成为一种永无穷尽的意义可能性的源泉,而不是研究的消极对象”③。显然,加达默尔关于“视域融合”的见解对于诸如龟兹历史文化研究是有启迪意义的。其实,仔细推敲起来,有关龟兹文化研究的文献和考古物证还是捉襟见肘的。汉文及其他文种文献的有限记载和误记,考古物证方面的缺环都无形加大了研究的难度。更何况,当研究者面对历史“流传物”时,往往急功近利,认为只要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并佐之以正确的方法,就能对龟兹文化做出客观结论,并把这些铁定为外在的“事实”,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在龟兹文化研究领域,至少有以下一些做法遮蔽了我们的视域,其结果是,发现不了“问题”,也就不能理解事件的“意义”,结果使我们的研究成了“一种模仿自然科学的陈词滥调”(加达默尔语)。
一是,误认为龟兹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流传至今的僵死“物”,而凭研究者任意宰割。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有史时代的文化研究,也泛滥于史前文化研究。以龟兹乐舞研究为例,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乐舞图、苏巴什遗址出土舍利盒中的乐舞形象,以及汉文文献记载的龟兹乐舞等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是,从文献到文献,从图像到图像,永远无法看到龟兹舞舞动的韵律和听到龟兹乐美妙的旋律。单就客观对象而言,它们只是变成了纯客观的“物”或冷冰冰的“事实”(也根本未抓住“事实”)。这里抽取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其实,研究者与“流传物”之间应该是一种理解与对话的关系,“因为实质上,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眼中或者手中的东西是‘岩画’或‘陶器’,或者用这样的名称去称呼它们时,我们就已经为它赋予了意义”。①我们与历史“流传物”之间呈现出的意义,正是因为我们与龟兹历史文化之间建立了一种交互理解的关系。
二是,误以为以一种超然的客观化态度对待龟兹文化就抓住了龟兹历史文化的“历史事实”。这就存在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龟兹文化的“历史事实”?按照以往一些研究者的理解,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发掘“事实”是他们的职责,以致把历史叙述建立在这种“事实”基础上。这种穷究“历史事实”的做法几乎成了龟兹历史文化研究的“铁律”,以为只有这样才能触摸到西域历史文化的本源。但是,仔细推究起来,这种只对“历史事件”感兴趣的做法是要大打折扣的。且不说龟兹文化是一种逝去的历史文化,我们根本无法触摸到,就是我们赖以研究的文献史料也不过是前人的记载,考古发现提供的是一些历史遗留物而已,“所以,史学家也就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曾经发生过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简单说来,他接触的不是事件,而是证明曾经发生过这一事实的一个记载”①。更何况,记载龟兹历史文化的大多是汉文文献,并不是长期生活在西域的印欧语系语族的文献史料(考古发现表明这类文献也并不多)。即使根据考古发现的物证“复原”龟兹文化的情境(古人当时理解的意义)也是由研究者的中介才呈现出来的意义。这样就出现了第三个问题,对他者文化的理解问题。
三是,误以为像吐火罗人等“他者文化”的文本不是理解的对象。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澄清,首先是对文本的界定。以往的研究者对文本的理解十分狭窄,就是文献史料,且只有汉文文献史料,即汉文正史的记载。其实,广义的文本不仅包括一切文字的记载,还包括口传材料,以及非文字的文物、历史事件等,乃至历史本身。仅以文献史料为例,即使汉文文献对西域历史文化的记载自成体系,相对完整,但是误读,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也时有出现。其次,对古代西域诸民族文化的解读也存在一个语义转换的问题。且不说汉文文献对西域诸民族文化的记载多源于出使者、僧侣、商旅、旅行者的转述,已非第一手材料,就是亲历者的描述也存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语义转换和对话的问题。如若根本不懂塞语、吐火罗语等,那只有靠翻译了,而“翻译者必须克服语言之间的鸿沟,这一例证使得在解释者和本文之间起作用的并与谈话中的相互了解相一致的相互关系显得特别明显”②。当然,这种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因此,对作为文本的“包括整个世界历史本身”的理解,不仅仅是领悟作者意图和考证历史事实来解释文本的意义,而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龟兹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视域融合”效应呢?这是说,研究者自己的视域和作为传统文化的龟兹文化都有诸多视域,比如,研究者把考古发现的诸多器物是当作僵死之物,还是当作会说话的人与之对话,这就是不同的视域;而历史“流传物”也是一种会说话的文本。我们必须承认,研究者(主体)和研究对象(客体)之间是一种开放、交互和相互认识的关系。加达默尔说:“..谁想听取什么,谁就彻底是开放的。彼此相互隶属,同时意指彼此能够相互听取。”①既然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把龟兹文化仅仅当作客观之物,而应把它当作能够说话和提出问题的人,进行平等对话。在此,跨文化研究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同文化类型(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形态)之间的比附和比较,而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理解与对话,追求的是一种“视域融合”的效应。
当然,研究者与龟兹文化之间的对话中的“文化”是已经研究者理解后“给定”的文化,作为研究者理解的文化是“当今”意义的文化,是把文化当作一个整体和综合体去研究的。诚如泰勒所言:“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②笔者正是把龟兹文化视为具有功能性的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这是因为龟兹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复合体。比如,从文化形态看,它是包括绿洲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屯垦文化、城郭文化、宗教文化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就不能顾此失彼。另一方面,笔者的研究旨在追求一种整体效应,这不同于将各种文化形态平列或笼统观照,也非各种具体文化事项的分述。若是这样,就将龟兹文化割裂和肢解了,既反映不出文化的功能,也看不出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龟兹文化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视域融合”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主体和客体、历史和当下、自己和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如果要在龟兹文化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话,正需要这诸多视域之间进行沟通和对话。研究者的视域也在因时因地发生着变化。这本身就说明,超越方法论的局限,扩展视域融合效应是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获得无限广阔视野的必由之路。
在龟兹文化研究的诸多视域中,最主要的是研究者的视域。我们和研究对象的对话,我们倾听他(它)们的诉说,只能在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中才能“听”出来,并发现其意义所在。那么,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视域融合”效应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是加达默尔指出的“效果历史”的原则。他认为: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大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①
加达默尔在“效果历史”中强调的是“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在此,“他者是这样强烈地通过我们自身而呈现出来”②。笔者在龟兹文化研究中不是简单、客观地陈述龟兹文化的各种形态,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而是在进行文化的寻根。比如龟兹文化的生态特征、史前遗物的精神内涵、龟兹文化的符号性特征、民俗生活的精神世界、宗教仪式的文化象征、意象世界的文化阐释等等,无一不是在理解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这些“他者”是通过解释者才呈现出来的。龟兹文化中总是存在许多我们已知和未知的领域,我们必须聆听这些历史的回音。这些回音来自不同的时空,它们不断向我们发问:我们来自何处?我们又向何处去?那些历史遗物,如彩陶、陶祖、塑像、石人、双兽纹铜带扣、马纹陶钵等,呈现在我们面前,看似无言,实则有声。龟兹人正在向我们诉说:我们为什么要制作它们?是如何制作的?这本身就蕴含了文化情境,需要我们仔细聆听,并予以回答。即使直到晚近还在西域普遍存在的拜火仪式,我们的理解也并非全面和深刻,对诸如它的文化象征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可以说是不绝于耳,等待我们的回答。可以这样说,“只有在这些众多的声音中,过去才表现出来”(加达默尔语)。在探究龟兹文化的过程中,效果历史总是在起作用。当然,诚如加达默尔所言:“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里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情况正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具有一种视域。..但是,我们必须也把自身一起带到这个其他的处境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了自我置入的意义。”①
就研究龟兹文化而言,把自身置入龟兹文化的情境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这种自身置入是一个理解的过程。理解就意味着对话与沟通,这样才能明了“他者”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和怎样想,怎样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龟兹文化的意义。
一般来说,研究者在“效果历史”中的理解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在与文本相遇时,理解者已经拥有由他的成见所决定的视域,这两个视域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尚不为理解者所知;第二,理解过程一旦开始,由于两个视域之间必有的差异,彼此会出现一种紧张关系,这时理解者便力图把两者区别开来,策划一个不同于他的视域的文本的视域;第三,当他这样做时,他仍是通过他的视域去区别和策划文本的视域的,所以在区别和策划的同时,他已把他自己的视域融入他所获得的文本的视域中了,因此,了解的结果必是两个视域的融合,被理解的文本的意义必定为文本和理解者所共有,其间的界限事实上不可明确区分。②
这正如加达默尔认为的,成见绝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的前提。正是通过成见,理解者才与传统有了联系,在此,传统也就成了被理解和解释过程中的“效果历史”。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如何消解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紧张,以达到“视域融合”的效应?按照和深刻,对诸如它的文化象征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可以说是不绝于耳,等待我们的回答。可以这样说,“只有在这些众多的声音中,过去才表现出来”(加达默尔语)。在探究龟兹文化的过程中,效果历史总是在起作用。当然,诚如加达默尔所言:“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里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情况正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具有一种视域。..但是,我们必须也把自身一起带到这个其他的处境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了自我置入的意义。”①
就研究龟兹文化而言,把自身置入龟兹文化的情境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这种自身置入是一个理解的过程。理解就意味着对话与沟通,这样才能明了“他者”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和怎样想,怎样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龟兹文化的意义。
一般来说,研究者在“效果历史”中的理解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在与文本相遇时,理解者已经拥有由他的成见所决定的视域,这两个视域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尚不为理解者所知;第二,理解过程一旦开始,由于两个视域之间必有的差异,彼此会出现一种紧张关系,这时理解者便力图把两者区别开来,策划一个不同于他的视域的文本的视域;第三,当他这样做时,他仍是通过他的视域去区别和策划文本的视域的,所以在区别和策划的同时,他已把他自己的视域融入他所获得的文本的视域中了,因此,了解的结果必是两个视域的融合,被理解的文本的意义必定为文本和理解者所共有,其间的界限事实上不可明确区分。②
这正如加达默尔认为的,成见绝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的前提。正是通过成见,理解者才与传统有了联系,在此,传统也就成了被理解和解释过程中的“效果历史”。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如何消解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紧张,以达到“视域融合”的效应?按照加达默尔的观点,那就是调解。调解意味着必须更改所说的东西,以便使这些说出来的东西保持为原来的东西。这是一个进入一种转换的活动过程,在这种活动中过去和当前不断地交互调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解释者的任务仅仅是一个复制过程。每一次新的解释都是在调解,旨在消解“紧张”中进入“效果历史”,这种视域正是文本和理解者共有的。
既然我们承认世界万物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而这一切又是和我们理解的意义与我们发生着关系,那么,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加达默尔关于“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一论断的深意了。在加达默尔看来,语言不是一种符号、一种工具、一种作为手段的装置,而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这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语言理解存在。就解释者和文本的关系而言,“所谓理解了一个文本,也就是理解者和文本在对话引导下就所谈对象取得了共同语言,也就是对象达于语言。正是在这共有的语言中,双方的视域实现了融合,理解者占有和推进了文本的效果历史”。①在此不妨举一例加以说明:《大唐西域记》一向被认为是记载龟兹文化的经典文本,我们正是通过玄奘的话语理解了一个个文化事件的意义,语言作为摹本,被描绘的原型才得以表达和表现。《大唐西域记》在“屈支国”条(即龟兹国)中记载了龟兹国的一种习俗:小孩出生后用木板押头,使头扁阔。对于这种“押头”,玄奘并没有说明是他亲眼所见还是听说的传闻,因此我们(理解者)并不是在与“事实”本身打交道,而是和这一事实的记载发生交互关系。当然,玄奘的记载已被在库车地区出土的唐代人头盖骨和佛教雕塑以及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所证实。我们获得的这个文本正是凭借书写的语言媒介得以流传,并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在理解者面前,理解者和被理解者正是在对话中取得了“共同语言”,也就实现了“视域融合”。“我们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是一个视域不断变化的过程,不仅是玄奘在向“押头”这样习俗的文本提出问题,我们作为理解者也在不断发问:这种“押头”习俗产生于何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习俗?“押头”仪式是怎样进行的?这就是所谓理解者和文本在对话引导下就所谈对象取得了共同语言,以达到新的“视域融合”。
当我们把龟兹文化当作一个文本(其实就是文本)理解时,它给了我们无限的空间,这不仅仅是因为龟兹文化还有许多未解和待解之谜需要我们破译,即使我们熟知的领域也有对意义的不同理解。这既非主观地“自话自说”和“先入为主”,也非客观地陈述历史,而是不断地超越文本的历史视域并与我们的视域相融合。
我们从“历史陈述”走向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的确走出了龟兹文化研究的关犍性一步,但我们仅仅把龟兹文化的跨文化研究当作一种方法论时,我们又走入了一个怪圈——把主体放在对某种方法的使用地位,而忽视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相互理解的关系。只有当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对话、相互理解并进入“视域融合”的境界,我们才能说,龟兹文化研究才真正跨出了一大步,这也是跨文化对话的真正意义。当然,并非所有的理解都是成功的,这里有误记、错位、偏差,这正如一次冒险旅行一样,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危险,不断修正目标,这样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近。龟兹文化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并理解的无限空间,我们对其意义的理解也是无限的。我们不要奢望在这种“视域融合”中会有什么终极结论,因为在理解中,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的视域不断扩大和更新,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在此,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在呈现着不尽的意义,我们追求的不正是这种效果吗?
不可否认,学术研究总会形成一些积习难改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一旦成为顽疾,就会遮蔽我们的视域,固步自封,囿于成说,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偏见就形成了。这种眼光不敞、自我封闭的思维定势作为个体存在也许无所谓,但一旦蔓延,对学术研究的伤害是致命的。不过,我们总能超越自我,在理解与对话中达到“视域融合”的境界。龟兹文化研究的缺憾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研究的领域,还是研究的方法都不能令人满意,至今我们还没有诸如《龟兹文化史》、《龟兹艺术史》之类文化史论方面的著述,即使如龟兹文化通论式著述也鲜能见到,更遑论新视域、新方法论方面启神益智的著述了。这与我们的眼光不敞有关呢,还是和我们的成见有关呢?或许都有。龟兹考古、龟兹佛教、龟兹语文研究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但我们明了如何界定龟兹文化吗?深入探讨过龟兹文化的特征、类型以及起源、演变等问题吗?我们在陶醉于龟兹佛教文化研究和龟兹历史考证取得的成果时,为什么不躬身自问我们对龟兹世俗文化,或者说是龟兹民间文化究竟研究了没有,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以缺乏文献史料和考古物证聊以自慰。假如我们把龟兹文化当作一个会说话的朋友,与他进行互动式的理解与对话,我们就不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了。现在该是我们不断拓展我们的视域,追求“视域融合”的跨文化研究的效应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使龟兹学研究真正成为世人瞩目的国际显学。
(作者: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于龟兹文化的几个问题
姚士宏
近年来,全国兴起地域文化研究热,龟兹文化研究更是持续升温。为此,我也想就龟兹文化的主要内容、地域范围以及研究思路等问题,谈一些肤浅认识。
一
龟兹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但它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它的核心与主流,却是佛教文化。这样说,并非因为我是搞佛教石窟的,有意要抬高它,而是历史事实。当然我说的佛教文化,可不全是印度那样的佛教文化。由于龟兹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富于创造的民族,因此,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它融入了龟兹本土原有文化和民族思想情感。可以说,这里的佛教文化,虽是伴随印度佛教传入而生成发展起来,但却是有着龟兹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我认为,现在说的龟兹文化,应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主要指历史上新疆库车地方政权——龟兹国存在时期的文化。龟兹何时立国,文献未载,不过,《汉书·西域传》已立有龟兹国专传,不仅记载了龟兹都城、人口、兵员、官职,并讲到它的疆界。从传文所记内容看,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之时,龟兹大体上已是完整意义的国家。如果以此算起,到9世纪中虽回鹘民族西迁,龟兹成为西州回鹘领地为止,以今库车为中心,辖境包括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温宿和巴楚等县市的龟兹国历经1000多年。所谓龟兹文化,指的应是这一时期内生息繁衍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当然,也还要算上西州回鹘前期,即龟兹回鹘这一段。龟兹回鹘虽是西州回鹘下属地方政权,但独立性较强,首领自称师子王。后期,龟兹回鹘逐渐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开始伊斯兰化。这以后,就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龟兹文化范畴。也就是说,我们所讨论是11世纪初以前的龟兹历史文化,这是前提。对龟兹文化的概念,我觉得,作一界定是有必要的,它可使我们的讨论有个共识基础。
众所周知,自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时任西域长史班超降服龟兹,废龟兹王尤利多,立龟兹质子白霸为龟兹王,从此,龟兹进入白氏王朝(即龟兹王之名的头一个字基本上都带一个白或帛字。近有学者指出,按惯例,西域诸国通常是王子或王弟为质子,白霸既为尤利多为龟兹王时入侍汉廷的质子,则尤利多与白霸应属同一氏族,亦为白姓龟兹王,龟兹白氏王朝至迟始于龟兹王白建,而这里仍按传统说法叙述)。
白氏王朝有两个突出方面:一是统治龟兹时间长。从白霸开始,一直延续到8世纪末(唐贞元四、五年间,公元788~789年)悟空由印度回国途经龟兹时在位的龟兹王白环,长达近七百年。如此稳定的王朝,出现在当时民族迁徙流动性大、王朝更迭频繁的西域、中亚地区难能可贵,在我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二是白氏王朝历代诸王大多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佛教传入龟兹究竟发生在白氏王朝建立以前,还是在之后,暂且不论,但从文献记载看,他们对佛法的渴求,对高僧(包括外地来龟兹高僧)的敬重,今天仍感到他们那份敬法重人的挚诚。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用习惯的宗教标准作评判,不能完全看作是宗教狂热,或者认为是要利用佛教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理应回归到当时龟兹社会现实来分析考虑。我以为,龟兹白氏王朝诸王带头崇尚佛教,是出于对佛教文化的仰慕,是对当时一种崭新文化的追求。因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以宗教为其表征的。这样认识是否恰当,还可探讨,但在他们倡导和影响之下,龟兹境内佛教长盛不衰,佛教文化空前繁荣。这不仅文献有载,如今遗存在库车、拜城一带众多佛教寺址、石窟,便是当年龟兹佛教兴盛的明证。龟兹回鹘在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前,同样信奉佛教,程度虽不及白氏王朝统治时期那样鼎盛,但其文化仍是以佛教文化为主,开凿在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时期的窟,就是证明。在佛教盛行的同时,龟兹也曾有其他宗教流传,如祆教,在龟兹就建有祭祀场所——天祠。也发现有用龟兹文书写的摩尼教赞美诗卷子。在龟兹文化形成当中,亦吸收融汇了各种外来文化,尤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显示出多元文化的品格,这从龟兹石窟壁画上即可强烈感受到。尽管龟兹文化包含有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异彩纷呈,错综复杂,但佛教始终占据主导地拉,佛教文化无疑是龟兹的主流文化,是龟兹文化的基本形态。这样认为,也许有些过于绝对,但至少从目前揭示的龟兹文化的主要内容来看是这样。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也是一种文化最显著的特征。龟兹为多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流行过多种民族语言文字。龟兹又是中原王朝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汉语言文字曾相当通行,至今还能看到当年用汉文书写的官府文书、借贷契约和摩崖石刻,这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龟兹与内地密切的政治关系。然而,20世纪初以来,经中外语言学家通过研究从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收集到的古文字材料发现,这一带最为通用的语言却是吐火罗语。这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分为两种方言。一种分布于高昌、焉耆等地,称作甲种吐火罗语或焉耆语,记录的全部是佛典,特别是有关弥勒的经典很多。另一种则限于龟兹,称作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语。记录的内容除佛典外,还有世俗文书。虽然焉耆—龟兹语属于吐火罗语甲乙两种方言,但表述这种语言的文字,则是借用印度婆罗谜字母书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记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就是指婆罗谜字母而言。龟兹语即是借用印度婆罗谜文字,显然是伴随佛教而输入龟兹的。熟识情况的人都知道,龟兹佛教与印度贵霜王朝关系密切。20世纪初,在印度马土腊曾出土一尊迦腻色迦雕像,并有用婆罗谜字体镌刻的铭文。而类似用婆罗谜字母拼写自左到右横行书写的龟兹文题记,在龟兹石窟壁画上为数不少,有的时间早到4世纪,这说明,龟兹语文极有可能在佛教传入龟兹伊始即输入龟兹。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窟壁画榜题多用龟兹文、汉文和回鹘文三种文字合壁书写,表明有龟兹回鹘时期,虽然龟兹人种、语言逐渐回鹘化,但龟兹语文仍是通用的语言文字。岁月沧桑,龟兹语文这种古老语言文字虽已在民族融合中消失,无人使用,但应成为我们不可忘却的文化记忆。我国早期汉译佛经有相当部分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由龟兹语文本转译过来,因此,它在佛教传播上作出过贡献,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尤为重要的,它作为龟兹文化的一种载体,为我们记录、保存了大量有关龟兹文化的历史信息,它的学术意义不亚于龟兹石窟壁画。
龟兹乐舞是龟兹文化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也是历年论文著作述介得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内容,几乎成为龟兹文化的标志和代名词。然而龟兹乐舞,是在龟兹本地音乐舞蹈基础上,吸取印度、波斯和中原乐舞长处,尤其是印度乐舞长处而创造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乐舞体系。这自然亦是伴随佛教传入龟兹而逐渐形成完备的。
其他如文学、戏剧、美术也都渗透着佛教文化。尤其是作为龟兹国艺的雕塑、绘画,更是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佛教的传入,使龟兹文化思想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动了龟兹社会发展进程。没有佛教的传人,龟兹不可能如玄奘赞誉那样“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著称于西域;龟兹乐舞也不可能登上隋唐宫廷乐舞的殿堂,风靡中原大地;龟兹更不可能由一个城邦国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国,至今仍受到世人的关注。总之,佛教的传入,使龟兹文化经历一次重构过程,重构就是发展,对龟兹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
曾有研究者谈到龟兹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问题,认为龟兹文化的精神实质就是开放、兼容。的确是这样。龟兹为西域重镇,又位于丝绸之路要道,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这样的地理、人文环境,必然使龟兹文化具有开放、兼容的优势,构成了龟兹文化的一大特色。龟兹文化即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这正是龟兹文化独具魅力和吸引人之处。我们研究龟兹文化,就是要重视发掘其中的积极元素,古为今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服务。也许是巧合,龟兹文化的这种优势、特色,恰恰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佛教自传世2500多年来,一向以和平方式传播,从不用武力或别的什么手段强制别人信仰。也没有排他性,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保有开放接纳的姿态,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少思想禁锢、最有涵容人格精神的一种宗教。而这正是佛教文化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很难想象,若不是佛教的兴盛,佛教文化的浸润,龟兹文化怎能如此繁荣昌盛,为我们留下如此优美的石窟壁画!
二
龟兹文化,从文化类型上说,虽是以龟兹国之名命名的一种地域文化,它的核心区域在龟兹,但它的地域范围不应限于龟兹,即今阿克苏地区,还应包括焉耆、疏勒,也就是整个塔里木盆地北道沿线诸国,即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地区。这样说,并非有意夸大龟兹文化的区域空间,事实根据是不仅因为焉耆、疏勒毗邻龟兹,地域相连,最主要是焉耆、疏勒与龟兹在历史上皆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同属于小乘佛教文化圈带。只要翻阅一个我国三位不同时期西行求法僧行记,即东晋法显《佛国记》、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即可明了。他们都是经西域即今新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前往印度或返回中原内地。在他们的行记里,对南北两道沿线佛教信仰情况均有明确记述。
法显于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后秦弘始元年)从长安出发,次年抵达鄯善(若羌地区),然后转向西北往乌夷(焉耆),再折向西南到于阗,经子合(叶城)、于摩(叶城西南)和竭叉(疏勒,一说塔什库尔干)等国,西越葱岭,于公元402年(东晋元兴元年、后秦弘始三年)进入印度北境。他在《佛国记》里对所经之地佛教,除于摩国外,皆有记述。
鄯善国:
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乌夷国:
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
于阗国:
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
子合国:
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
竭叉国:
有千余僧,尽小乘学。
法显虽未到龟兹,没有记载龟兹情况,但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记载,4世纪中叶前后,龟兹佛教已相当兴盛,尽管大、小乘都有流传,但统辖龟兹佛教领袖佛图舌弥为小乘阿含师,足证龟兹佛教是以小乘为主。从法显所记可以清楚看到,5世纪初(实际年代肯定比这要早),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于阗、子合和北道的焉耆、疏勒等国,虽皆是佛教国家,并各有特点,然而南北两道佛教情况却是泾渭分明。南道于阗一带主要流传大乘佛教,北道沿线诸国则同龟兹,主要信奉小乘佛教。当时形成两个不同的佛教文化区域,即南道以于阗为中心的大乘佛教文化圈带和北道以龟兹为中心的小乘佛教文化圈带。
玄奘于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一说公元639年,唐贞观三年)西行印度求法,途经塔里木盆地北道,归程东越葱岭,从朅盘陀行进到乌铩,再北行到佉沙,然后转向斫句迦,经南道返回长安。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和卷十二分别记述了阿耆尼(焉耆)、屈支(龟兹)、跋禄迦(姑墨,今阿克苏)、朅盘陀(塔什库尔干)、乌铩(莎车)、佉沙(疏勒)、斫句迦(即法显《佛国记》所作子合国)和瞿萨旦那(于阗)等地佛教情况。由于玄奘西行印度求法来回皆取道西域,南北两道主要城邦国都记到,并且更为翔实和具体。
阿耆尼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屈支国:
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
跋禄迦国:
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伽蓝数十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朅盘陀国:
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乌铩国:
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习学小乘教一切有部。
佉沙国:
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斫句迦国:
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淳信三宝,好乐福利。伽蓝数十,毁坏已多。僧徒百余人,习学大乘教。
瞿萨旦那国:
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慧超为朝鲜古国新罗人,赴唐留学僧,也加入当时我国掀起的西行求法热潮,先循海路前往印度(具体时间不明),于公元727年(唐开元十五年)经西域返回内地。他在《往五天竺国传》里对疏勒、于阗、龟兹(安西)和焉耆佛教也作了记述,情况一如法显、玄奘所记,这里不再详细引述。
玄奘、慧超所记分别是7世纪初和8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佛教情况,与法显记之5世纪初相比,虽然南道大乘佛教势力明显削弱,如于阗,尽管这时境内佛寺尚有百余所,可僧徒已从数万减至五千人。子合尤甚,大乘僧由千余减至百余人,近乎衰亡。相对于南道而言,北道小乘佛教却大为增盛,特别是疏勒,小乘僧由过去千余人增至万余人。这种大、小乘之间的消长形势,并未根本改变南北两道佛教基本格局,依旧是:以于阗为中心的南道流传大乘佛教,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信奉小乘佛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玄奘在记述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北道信奉的小乘佛教是为说一切有部,并以文献形式记录下来,使我们对龟兹及其周边地区佛教文化的部派属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通过玄奘、慧超所记也看到,北道沿线诸国,至迟从法显时代5世纪初以来,一直坚持传统的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信仰,在经历多个世纪后,丝毫没有任何变化。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诸国,在佛教文化上,早已形成一个共同的比较稳定的区域,即一个在我国唯一的以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为主体的佛教文化区域,一个比较特殊的与我国其他地区(包括于阗在内)有所不同的佛教文化区域。
正是因为北道沿线国家皆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同属于小乘佛教文化圈带,因此,焉耆、疏勒与龟兹在文化上相同点很多。焉耆与龟兹两地居民不仅为同一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而且在风俗、婚姻、丧葬、物产等方面也大致相同。焉耆与龟兹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就连玄奘记述两地佛教时所使用的词语亦基本相同。疏勒与龟兹在文化上的关系,尽管文献记载没有那么明显,但仅从玄奘所记看,两地相同地方仍有例可举。如语言文字,虽然疏勒与朅盘陀、乌铩比较接近,与龟兹略异,但也是“取则印度”,想必是会通的。僧人则更不是问题。法显在《佛国记》讲到位于南北两道交汇之处的鄯善国时说:“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此(指佛教盛行),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这就是说,西域僧人皆通用梵文,不存在语言文字障阻。在佛事方面,所谓“勤营福利”,“不究其理,多讽其文”,即是指疏勒佛教偏尚修福,追求功利,重视诵读经文,不太深究其中义理,以及持戒较严,却不戒荤腥,食三净肉,等等,与玄奘记龟兹“尚拘渐教,食三净肉。洁清耽玩,人以功竞”相一致,保持了早期佛教的一些特征。特别是生活习俗上,玄奘记龟兹与疏勒两地流行一种“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的奇特做法,大概是在小孩出生后便用木板挤压头颅,使头部扁平。这种人工变形头颅的生活习俗,是受外部文化影响,还是源自本地?是融纳了原始自然宗教的遗绪,还是有着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文化背景?目前尚难论定,但流行于龟兹与疏勒两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是文化心理认同的典型表现。总而言之,尽管焉耆、疏勒与龟兹在政治上不相统属,还时起纷争,但在文化上确实属于一个体系,一个以龟兹为主的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文化体系。学术界在论述西域佛教文化分野时,总是划分成于阗、龟兹和高昌三个区域文化单元,而把焉耆、疏勒与龟兹视为一个区域文化单元,正是这个道理。因此,要进一步丰富我们对龟兹文化的认识,深化对龟兹文化的研究,全面揭示龟兹文化蕴含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就有必要把整个北道沿线地区甚至更大的范围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
三
以上概述了龟兹文化主要内容是佛教文化,龟兹佛教文化主要属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文化以及地域范围,下面再就龟兹佛教文化研究的思路问题,主要是如何看待龟兹大乘佛教和玄奘关于龟兹及周边国家盛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这样两个问题。
据《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收录的《鸠摩罗什传》记载,4世纪中叶,鸠摩罗什由小乘改宗大乘,曾在龟兹大力弘扬大乘佛教。从传文看,声势影响都不小。实际情况是否确如传文描写的那样,需要综合分析。因为这两部传文皆出自内地僧史学家之手,他们偏爱大乘佛教,在行文中不免会加进溢美之词,作些渲染。即使讲的全是实情,也不难看出,尽管罗什大力弘扬,龟兹大乘佛教始终只是停留在龟兹上层社会层面,只是在以龟兹王室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小圈子里流传。佛寺也仅限于罗什居住的王新僧伽蓝(王新寺),寺僧仅有90,在龟兹僧团(当时龟兹僧有1万余人)中所占比例很小,成员估计大多来自王族子弟。可以这样说,龟兹大乘佛教,仅是龟兹王室贵族的佛教,与平民百姓有一定距离。由于缺乏群众基础,随着前秦苻坚派遣吕光率军伐龟兹及焉耆诸国,罗什被劫往凉州,失去了代表人物,龟兹大乘佛教很快便归于沉寂。它对龟兹的影响,包括石窟造像,却很有限,不可估计过高,更谈不上发生龟兹佛教改宗问题。6世纪末,从文献上看,确有西来大乘僧在龟兹弘法,在位龟兹王透溢出对大乘僧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但大乘僧讲的皆是大乘人门性质的内容,龟兹王对大乘佛教仍处于尚未精深阶段,仅是一位诚笃之士而已,因此也很难说6世纪后期龟兹大乘佛教称盛。7世纪后,随着唐王朝重新统一西域,龟兹与中原内地关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迁居龟兹,在中原佛教影响下,龟兹大乘佛教重又活跃起来,库木吐喇石窟中的一批汉风窟便受敦煌壁画深刻影响,而阿艾石窟简直就是敦煌壁画的翻版,属于典型的中原大乘佛教回流龟兹的例证。似如慧超所记,仅是“汉僧行大乘法”,广大民族僧众仍是信奉小乘学说一切有部。正因如此,在龟兹石窟,特别是克孜尔石窟,壁画集中而具体地绘出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特有题材,形象地为我们诠释了小乘有部思想内容。就现存佛教遗迹看,无论是在佛教老家印度,还是我国内地,都是不可多见的。因此,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不仅开凿年代早,在我国石窟史上具有追本溯源意义,而且更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佛学大师玄奘在西行印度求法前,在国内即已遍参名师,穷尽各家学说。在西行求经的17年时间里,接触了当时西域、中亚和印度各地包括说一切有部在内的大、小乘各种派别,观察细致周详。回国后又亲自译出说一切有部论藏中的《异部宗轮论》、《法蕴足论》、《发智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和《顺正理论》等论书。尽人皆知,说一切有部虽是小乘佛教众多部派之一,然而却是思想理论最为丰富、势力与影响较大的一派,主要流传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和迦湿弥罗地区,有自己的经律论三藏。经藏同别的部派一样,以四部阿含经(《长》、《中》、《杂》和《增一》)为根本经典,只是次第有异,将《杂阿含经》置于首位。律藏有两种:一是《十诵律》,主要是在罽宾流传的较为原始的一种律本。另一种即《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包括诸事)。虽然结构、内容与《十诵律》差别不大,但增加不少本生、比喻故事,还掺杂有佛传内容,卷帙也相应增加,因而被称作有部律广本,称《十诵律》为略本。论藏,即是对阐释佛经义理论书的总称,又作《阿毗达磨》、《阿毗昙》、《毗昙》,其论书主要就是上面提到玄奘译出的那些。因为说一切有部最重论藏,喜兴造论释经,不仅为我们留下为数众多的理论著作,而其学说思想就体现在这些论书之中。这一点,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说疏勒僧徒“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来看,从慧立、彦琮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在龟兹参访阿奢理贰伽蓝时,该寺住持(也是当时龟兹佛门领袖)木叉毱多特意向玄奘推荐“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来看,都反映出说一切有部重视论藏情况。玄奘这里说的《毗婆沙》,即《大毗婆沙论》,全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俱舍》,即《俱舍论》,全称《阿毗达磨俱舍论》;《杂心》,即《杂阿毗昙心论》,均为说一切有部3部重要论书。尤其是《毗婆沙》,系统总结论述了说一切有部学说的基本理论,地位最突出,被奉为圭臬。玄奘不仅译出《毗婆沙》,而且翻译了有部几乎所有大论(玄奘所以花大力译出有部论书,恐怕也是考虑到这些论书思想丰富性),应该说,玄奘对有部学说思想深有研究,对有部形成、发展、演变和流传情况不可谓不知,他对龟兹及周边地区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记述是客观可信的。玄奘在记述上述地区情况时,除明确指出是“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外,并且都说到使用的语言文字,可见语言文字之于文化上的意义。而这已从这一带发现的焉耆—龟兹文写本得到认证,证实玄奘的观察是正确的。这也足以说明玄奘记述龟兹及周边流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可信度。在这里,玄奘的记述,不仅仅指出龟兹佛教文化部派属性问题,实为我们研究龟兹佛教文化,解读龟兹石窟壁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思路。在打好历史文献基础的同时,认真研读一下有部经律论三藏,尤其是像《大毗婆沙论》这样的论书,看看究竟说了些什么,是怎样说的,尽可能地掌握有部思想理论和学说主张,弄清一些基本概念,也许会使我们在龟兹佛教文化研究中少走许多弯路,取得更大成果。
(作者:江苏省常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
佛教初传龟兹新考
薛宗正
关于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有两种重要说法。一为《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说,二是西汉武帝时期说,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见解,论述如下:
(一)《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中有如下一段偈颂,兹引录如下:
阿育王闻,喜庆欢悦,和颜悦色,告耶奢曰,“吾获大利,其德实显,法益王子,以理治化,率以礼禁,导以恩和,人民之类,莫不戴奉,今当分此,阎浮利地,吾取一分,一分赐子,使我法益,长生寿考,治化人民,如今无异,新头河表,至娑伽国,干陀越城,乌特村聚、剑浮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至于秦土,此阎浮半,赐与法益,纲理生民,垂名后世。
据此,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乃至“秦土”即我国内地,都已被阿育王赐予其子法益,龟兹、乌孙国名也赫然列入法益受赐领土之内,其说若成立,则龟兹早在阿育王时期就已有佛教传布。案今传《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并非梵文原本,而是前秦苻坚时期印度僧人昙摩难提的译本。参稽《汉书·乌孙传》,乌孙建国始于猎骄靡,上距阿育王时代十分遥远,时间不会早于汉初。足证这一记载必定出自后世僧人自炫性追述,并非信史。其说不能成立。
(二)公元前2世纪说。德籍华人刘茂才始创此说,原文未见,陈世良先生据此发挥①,证据是《梁书·刘之遴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前109年),龟兹国献。”陈先生一再强调这一记载并非孤证,我细查古籍,果然如此,《南史·刘之遴传》也有记载,文字全同,又见于《册府元龟》卷928总录部·好尚条,文字仅略有出入②。并援引《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③所记“大法流此(指龟兹)五百余年”云云,以为佐证。以《比丘尼戒本》译为汉本的晋武帝时期上推五百余年,时间更早于汉武帝时期。其说若成立,则龟兹佛教至迟汉武帝之世已经传入。我初治唐史,近年来逐渐对汉史也初有涉猎,开始对此说发生怀疑,理由是:
(1)公元前2世纪汉与匈奴全面战争爆发之前,西域诸国本臣于匈奴,汉文帝前四年(前176年)匈奴单于遣右贤王率兵西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④,龟兹必包括在此西域二十六国范围之内。早自文帝前四年(前176年)就已臣属匈奴,同汉朝并无任何朝贡关系,西域诸国只知有秦,不知有汉⑤,即使张骞两使西域之后,司马迁据其见闻编写成书的《汉书·大宛列传》中仍无关于龟兹的任何记载,说明碛口丝道,封闭不通,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诸国同汉朝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朝贡关系,直至绛宾之父在位时期犹在奉行亲匈奴政策,所谓元封二年向汉朝贡献佛教法器云云,极少可能。
(2)汉开西域始于元封三年(前108年)赵破奴进军姑师、楼兰之役,《汉书·西域传》记云:
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此役《资治通鉴》卷21系于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十二月。传文中明确记载此前姑师、楼兰受匈奴指使,阻塞碛口,汉与匈奴之间正剑拔弩张,丝路不通,战争一触即发。龟兹偏于此年贡献澡灌,更是绝无可能。
(3)更蹊跷的是这个佛教用器上面居然有汉字铸成的元封二年字样,显然是汉人工匠所为。而当时连汉商出入西域,也属禁绝,龟兹国内根本不可能存在汉人工匠。自东汉末年起,伴随着今、古经学之争,仿古、造古之风盛行,出现了多次伪造古文经的案件,晋鼎倾覆于八王内争,五胡入侵的兵戈乱世,司马氏王室仓皇渡江,南朝真正皇家珍宝已为数无多,这个龟兹澡灌即使存在,也应是宫中珍品,何能流落民间,出现于江南,刘之遴这件收购自民间的皇家法器不可排除其造伪嫌疑。以此为证,未必可信。
(4)《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与《比丘尼戒本》并非完全一回事,在佛典《出三藏记集》中此二书别立名目,《比丘尼戒本》又作《十诵律比丘尼戒本》,总一卷,明确记载是佛教正宗戒典《十诵律》中所设约束比丘尼的律条,今传《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则乃晋武帝时期汉译者所写序言,序中所记“大法流此(指龟兹)五百余年”云云,分明是后世译者口气。自炫其弘法历史悠久,乃是佛教徒的共同心理,同样不足成为科学论据。
(5)佛教是印度文化传播的载体,伴随着佛教的传布必定出现印度音乐、美术的大发展。西汉时期的龟兹音乐舞蹈都非常落后,尚未呈现任何佛教传入的迹象。史载率先归汉的龟兹王是汉昭帝时期继位的绛宾,其父追随匈奴,曾杀害率领汉军屯田于轮台的校尉、扜弥太子赖丹。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长罗侯常惠奉命赴乌孙,取道龟兹,为赖丹复仇,其时绛宾已继位,缚送始建言杀赖丹之龟兹贵族姑翼迎降①,自此绛宾全力附汉,为此,联姻解忧公主之女弟史,偕同弟史一起入朝长安,全面引入以钟鼓琴瑟为代表的汉朝宫廷雅乐,还不会演奏,说明龟兹音乐、舞蹈原极落后,这与以“管弦伎乐特善诸国②”的佛邦龟兹判若两国。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3记前凉张重华在位之“永和四年(348年)天竺国重驿(译)来贡,其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昙、铜钹等九部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这是印度佛教音乐传入我国的最初记录,其乐器组合同后世盛行的龟兹乐非常类似,可见印度佛教音乐乃是龟兹乐舞形成的真正源头。其时已为两晋交替之世,足以说明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绝不会早至西汉中期,最早也只能追溯至汉、晋交替之世。
由于文献无征,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难于准确判定其具体年代,只能推断其大致时间段。主要根据是:
(1)佛教的传播路线必以龟兹所在的地理位置为转移。西域佛教属于陆路扩散的北传佛教,至迟公元前1~2世纪时期,世界佛教已形成为两大中心,一是作为印度本土佛教直接延续的迦湿弥罗(克什米尔)。二是中亚的贵霜王朝。位于昆仑山北麓、独擅地理形胜的于阗同迦湿弥罗(克什米尔)仅隔一山,又有乌弋山离道相连,即今之巴基斯坦的洪札河谷道。于阗佛教的源头必直接渊源于迦湿弥罗,汉文史料《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和藏文史料《于阗教法记》共同印证了这一事实,皆明确记载最早来于阗弘法的高僧名毗卢折那(Vairoca-na,意为遍照)①。最早弘法的地点是距于阗王都不远的杏园,即藏文载籍中的杂沐尔玛局里之园。最早皈依佛教的于阗王名Vijayassmb-hava,法名普胜生。最早兴建的佛寺名赞摩寺。于阗塞人居民同北印度释迦种语言相近,可以直接听法,无须翻译,因而佛教迅速在于阗传布开来。看来,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绝不能更早于于阗,而只能更迟。
西域佛教的第二大策源地乃是中亚的贵霜王朝。龟兹距北印度远而距贵霜近,只能传自中亚贵霜,而龟兹与贵霜之间又隔有疏勒,因此,龟兹佛教传入的时间不但晚于昆仑山北麓的于阗,还必定晚于同贵霜直接毗邻的疏勒,易言之,龟兹佛教还未必是中亚贵霜的直接正传,而必是疏勒佛教东传的历史产物。臣磐(?~170年)则是疏勒佛教的最早倡导者与护法王,国王安国的舅父。汉安帝元初三年(116年)疏勒国内部发生政争,臣磐被国王安国入质于月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二世(78~120年在位),率先皈依佛教。《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贵霜名王迦腻色迦王在位时期(78~120年)曾送疏勒质子“冬居印度诸国,夏居犍陀罗国”学习佛法,还有史料说明这位质子曾在迦毕试国捐资修建了小乘佛寺沙落迦寺,这个“沙落迦”明明就是疏勒的别译,可见这位在迦腻色迦王在位时期皈依佛教的疏勒质子应当就是臣磐。安国卒,无子,贵霜遣兵护送臣磐返国为王,臣磐继承疏勒王位之后大力倡导佛法,定为国教。有人推测,今喀什著名的三仙洞应即臣磐在位或稍后时期开凿的一座石窟寺。随同佛教信仰一起传入疏勒的还有贵霜王朝先进的军政管理制度,因而很快国富兵强,从于阗手中夺回了莎车,独立称雄于喀什噶尔绿洲,国势日盛。龟兹乃疏勒东邻,必定受到了重大影响,佛教初传龟兹或即发生此时。永建二年(127年)遣使贡于汉,顺帝册立为大都尉,因于永建五年(130年)送侍子于汉以为质。阳嘉二年(133年)遣使贡狮子、封牛。阳嘉元年(132年)受敦煌太守徐由征召,发兵二万攻讨檀灭扜弥国的于阗放前,破之,复置扜弥国,扶立成国为扜弥王。西域诸国的传统信仰本是原始巫教,佛教传布必定引起国内激烈的宗教冲突,臣磐之死就同这场宗教斗争有关。《后汉书·西域传》记臣磐建宁元年(168年)狩猎时为侄儿和得射杀。而陕西合阳中平二年(185年)十月所立《曹全碑》则记为:“建宁三年(170)..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得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和得面缚归死。”则臣磐实乃死于建宁三年(170年),时为八旬老翁,断难外出狩猎。曹全时任东汉戊部司马,政变发生后率兵干预,足证《后汉书》所记失实,《曹全碑》所记年代更为可信。政变首领和得夺权后必定实施大规模宗教清洗,此王乃疏勒反佛教势力的首领,死后佛教一度转衰,大批佛教徒必涌向邻国龟兹避难。以此判断,佛教初传龟兹应当发生于臣磐在位时期,至迟也应当发生于建宁三年(170年)和得政变之后。
(2)佛教东传龟兹必定发生于塞人白氏王朝创立之后,绝不可能发生于龟兹前塞人王朝时期。语言是宗教传播的主要媒介,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总是比语系迥异族群之间的传播要容易得多。鲍尔古本的发现和解读证实古龟兹语属B型吐火罗语文,乃古代龟兹塞人所操印欧语系肯通(Kentum)语支的一种方言。B型吐火罗文字则是以古婆罗谜文字拼写的这种印欧语方言,特点是名词有性、数、格的变化,动词变化更为复杂;且有前置词、后置词的区别,更为近似于希腊、拉丁等地中海语言,距于阗塞人所操的印度—伊朗型印欧语存在较大的差别。虽然如此,同操印欧语的塞人总比操汉藏语系的羌人或操其他语系的族群彼此还是相近得多。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实,这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文献都是发现于龟兹白氏王朝建立之后,古代龟兹、焉耆地区人种复杂,虽然塞人早就存在,但种种迹象表明,在塞人白氏王朝创立之前,龟兹曾经存在过一个前塞人王朝。西汉时期则尚不存在这种语文,充分印证佛教传入龟兹乃是白氏王朝建立之后的历史产物。
《魏书·西域传》记龟兹国“其王姓白,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明确记载龟兹历代王统都出自白氏家族,这是我国史书中关于白氏王朝最早的追述。其实,该传中所记后凉时期的白震并非最早见于汉文献的白氏王朝国王,参稽《后汉书》卷47班超传,白氏王朝的历史还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北匈奴册立的龟兹王尤利多为班超击败,被俘,汉朝另立原先送往洛阳的龟兹质子白霸为龟兹王,然白霸既为尤利多任龟兹王时期送往汉朝的质子,尤利多与白霸应属于同一家族,很可能同为北匈奴册立的龟兹王建的后裔,则白氏王朝至迟也可追溯至龟兹王白建。而西汉时期的龟兹王则皆出自绛宾后裔,此系王统传至前、后汉交替之际已不复存在,最后一位绛宾后裔龟兹王弘已被莎车王所杀,全族夷灭。由此足证,龟兹塞人所建的白氏王朝始于东汉初年,至于西汉直至新朝时期的龟兹王统则别出绛宾一系。易言之,西汉时期的龟兹尚属前塞人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发祥印度,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亚洲型(印度—伊朗型)的梵文与巴利文,于阗塞语同这种语言最为接近,《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和藏文文献《于阗教法记》共同证实,迦湿弥罗高僧卢折那(Vairocana)来到于阗杏园(藏文名为杂沐尔玛局里之园)弘法时,于阗居民可以直接听法,无须翻译。因而佛教迅速在于阗传布开来。同理,佛教弘传龟兹绝不可能发生于这一时期,只能发生于塞人白氏王朝建立之后。而且未必发生于白氏王朝建立之初。根据班超、班勇父子相继主政西域时期都未见其有关龟兹佛教的任何记录判断,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必定在西域三通三绝之后,这一时限同前文推算的臣磐被杀、和得政变之后大体相符。
(3)僧徒行纪的记录反映出龟兹佛教初兴的具体时间应是魏末晋初,至东晋时期始蔚为大国。朱士行是我国西行求法第一人,于魏甘露五年(260年)出发西渡流沙,所求法的圣地并非印度,也非龟兹,而是于阗,说明曹魏末年于阗佛教已臻鼎盛,国内已大、小乘经典齐备,龟兹佛教的知名度尚远不如于阗,南梁沙门释慧皎撰《高僧传》卷4义解一记载,其时于阗国内已大、小乘经典齐备,赴于阗访得所求大乘梵书正本凡九十章,因国王与小乘经师的干涉,以“惑乱正典”为名,不许大乘外流,朱士行被迫留于阗为质,换取弟子法饶携经东返洛阳。“至太安二年。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令写为二十卷。士行遂终于于阗。春秋八十。”龟兹佛教的知名度虽不如于阗,然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译经上昙柯迦罗传附有如下文字“又有沙门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后不知所终焉”,按“帛”字乃龟兹王姓,这位帛延应是东赴汉地弘法的龟兹第一人,说明曹魏末的甘露年间(256~259年)龟兹佛教也有了很大发展,乃至有人开始弘法中原了。至西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同名帛延,明确记载为龟兹王世子,也是笃信佛法。见于释僧佑撰《出三藏记集》所收《首楞严后记》①这位兼通胡汉语言文字(“善晋胡音”)的归慈(龟兹)王世子帛延亲自入晋弘法,这两个同名白延(或帛延)是不同的两个人。可见西晋时期龟兹佛教已相当兴盛。西晋时期龟兹高僧、信士入晋弘法者已非一人。如太康七年(286年)法护译《正法华经》时,有天竺沙门竺力与帛元信共同参校。
《须真天子经记》亦记“须真天子经。太始二年十一月八日。于长安青门内白马寺中。天竺菩萨昙摩罗察口授出之。时传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其中提及译经传言者有帛元信,《阿维越遮致经记》(晋言不退转法轮经四卷)附《出经后记》记“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美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闻知”。该经原本属于龟兹副使美子侯,以上帛元信应属龟兹王族,美子侯则属龟兹副使。西晋惠帝时(290~306年)有帛法巨(一作法炬),先与法立共译佛经四部十二卷,又自译四十部五十卷。这些龟兹佛教信徒所译佛经既有大乘,又有小乘,而以小乘居多。最先以弘法为业的龟兹高僧佛图澄(232~348年),《晋书》卷95记云“佛图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学道,妙通玄术。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及洛中寇乱,乃潜草野以观变。”后投奔羯人石勒,石勒父子以胡人应尊胡神,佛是胡神,尊为国教,佛图澄遂被尊为后赵国师,称“大和尚”,特点是不仅在胡人中弘法,而且更重视在汉人中传教。佛教的轮回报应理念迅速得到饱受战乱苦难和变幻莫测风云困惑的汉人广泛认同,从者如归,中原佛教由之崛兴。与佛图澄南北辉映,又有一位白氏王族出身的龟兹高僧帛尸梨蜜(汉语意为吉友),精于咒术,于永嘉年间(307~313年)到达江东,止于建康(南京)建初寺,精于咒术,对江南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大约始自东汉建宁三年(170年)和得政变之后,曹魏时期有了初步发展,虽然仍稍逊于阗,至西晋时期开始蔚为大国。克孜尔等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兴建大约也是始于此时,近年来的C14测定数据也可与此相互印证。
(作者: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吐火罗与回鹘文化
杨富学
一吐火罗人及其语言
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群中的一支,其故乡在今中欧或东欧一带,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便从操印欧语言西北组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向东迁徙,大致于公元前2世纪末到前1世纪初进入新疆天山南北,成为当地最早定居的古代民族之一。学界的研究认为,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都属于吐火罗人。①
关于吐火罗人在历史上的活动情况,由于东西方各种文献史料中的相关记载都非常稀少,而且语焉不详,时隐时现,矛盾牴牾之处比比皆是,故仅靠这些文献资料的零星记载是根本不可能全面认识吐火罗历史与文化的。有幸的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新疆地区考古工作的展开和众多吐火罗语文献的出土、刊布,与吐火罗历史文化有关的史实才逐步揭橥出来。
吐火罗文献都是用婆罗谜(Brahmī)字母写成的。最早的研究者是住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德裔梵文学家霍恩勒(A.F.R.Hoernle)。他在释读文字方面并未遇到困难,但发现其中的一些文献使用的并不是梵语。可究竟是什么语言呢?当时谁也说不清,学界姑且称之为“第一种语言”和“第二种语言”。对于“第二种语言”,学界不久就达成了共识,认为是印欧语系伊兰语族东支的一种语言——塞语,以这种语言写成的文献主要发现于和田地区,故而又被称作“和田塞语”,以区别于其他塞语。对于“第一种语言”的定名,学界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争论,直到今天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学者们都认识到这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从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文献看,吐火罗人尽管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许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前1190年小亚细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古代民族分化迁徙的认识。
1907年,德国著名东方学家缪勒(F.W.K.M〓ller)根据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写本的跋文中讲到回鹘文本译自toxri文本,认为其中的toxri语,其实就是古代东西方文献中提到的吐火罗语(tokhar)。①因为缪勒的定名依据的主要是二者在语音上的近似,而且在论述时对文献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误解,故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次年,德国梵文学家西额(E.Sieg)和西额林(W.Siegling)便撰文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种语言其实属于印度—斯基泰语。①然而,古代希腊人所说的斯基泰人(Skythen)相当于古代波斯人所说的塞人(Saka)这个定名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们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这种语言具有,西部印欧语特点,同时又将其区分为两种方言,即甲种/A方言和乙种/B方言,这些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1913年,法国学者烈维(S.Levi)撰文《乙种吐火罗语为库车语考》,根据文献的记载,证明所谓的乙种吐火罗就是古代龟兹当地的语言。②此说令人信服,至今成为学界通行的说法。相应地,甲种方言遂被确认为焉耆一带使用的方言。
然而,将龟兹、焉耆一带的语言称作吐火罗语,有违于玄奘著《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大唐西域记》曾两次提到睹货逻(吐火罗),其一为卷一提到的睹货逻国,③即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其二为卷十二提到的睹货逻故国,④地当今新疆南部民丰县北部,约即今天的安迪尔(Endere)遗址一带。二者都与龟兹、焉耆无关。那么,回鹘人何以将古代龟兹、焉耆一带使用的这种印欧语称为toxri/吐火罗语呢?这一直是学界难以解决的问题。
经过长期的探索、辩论,近期学界有一种倾向,将吐火罗与大月氏人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这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新思路。首先提出吐火罗就是大月氏这一观点的是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B.Henning)教授。他通过对阿姆河流域出土粟特钱币的研究,认为粟特钱币铭文中提到的“吐火罗人”,其实是粟特人对大月氏的称谓。①贝利(H.Bailey)从伊兰语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指出,Tokhar一名中的to,可解释为“大”,khar可对应“月氏”。②吾人固知,大月氏原居住于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与敦煌之间,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西迁到吐火罗斯坦。其后代建立了著名的贵霜(Kushan)帝国,但汉文史书仍习惯上称之为大月氏。值得注意的是,从河西走廊的姑臧(Kuzan),经新疆吐鲁番的古名姑师/车师(Kushi),到龟兹/库车/曲先(Kuci/Kucha/Kusan),再到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古都贵山(Kusan)城,一直到大月氏人于中亚、印度一带所建立的贵霜(Kushan)帝国,地名、国名、族名的发音非常近似。这种情况的出现当非偶然现象,应与这一区域大月氏人的活动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③易言之,从河西走廊到新疆天山南北,再到中亚以至印度西北部一带,自先秦、秦汉以来都曾是大月氏人/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直到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以后,吐火罗人连同其语言一起销声匿迹了。如是一来,龟兹、焉耆的居民被回鹘人称为吐火罗人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1957年5月,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发现了著名的大苏尔赫—柯塔勒碑(Surkh-Kotal)。三年之后,亨宁成功解读了碑文,知其是一种用草体希腊文字母书写的中古波斯语方言碑铭。由于用这种语文书写的文献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大夏(Bactria)故地,故亨宁建议将其命名为“大夏语”。④一些学者认为这才是大夏人的语言,所以称之为“真正吐火罗语”。⑤言外之意,前文所述的焉耆语、龟兹语也就成了“伪吐火罗语”。此说貌似立论有据,实则失之偏颇。因为在圣彼得堡收藏的一件梵语—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合璧文献中,Kucanne(龟兹)的对应梵文词就直接被写作Tokharika。①在一份回鹘语与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合璧书写的摩尼教赞美诗(编号为U103TⅢD260,19;260,30)中,用k〓is〓n一词来称呼吐火罗语。②(见图1)这些说明,至少在回鹘人于9世纪中叶西迁龟兹前,当地的确被称作吐火罗,其语言也被称为吐火罗语。所以,在我看来,称焉耆语与龟兹语为吐火罗语是实至名归的。古代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相当广大,不可能在语言上整齐划一,包含多种方言是自然的事,所以,不管是大夏语,还是焉耆语、龟兹语,其实都属于吐火罗语,不过都是吐火罗语的方言而已。回鹘人到达新疆时,吐火罗语还在继续流行,回鹘的不少文献都直接从吐火罗语翻译过来,故回鹘人将焉耆、龟兹当地使用的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是可信的,没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二吐火罗人的回鹘化及有关佛事活动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至新疆地区,征服当地部族,建立了以高昌、北庭为中心的民族政权——高昌回鹘王国,龟兹入于回鹘,成为高昌回鹘境内之大都会之一。但《宋史》在《高昌传》之外另列《龟兹传》,称:“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西州回鹘即高昌回鹘,龟兹受其辖制,但何以出现如此混乱的称呼,抑或龟兹具有半独立地位所致也?无从考见。
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控中西交通的咽喉,自古以来佛教文化昌盛。在回鹘统治时期,当地文化持续发展,在原居民吐火罗人逐步融合于回鹘之后,其文化对回鹘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回鹘文化的发展。
我们知道,回鹘本为漠北游牧民族之一。以漠北地区古往今来的自然条件论,古代回鹘的人口是不会很多的。就目前蒙古高原的人口状况推论,唐代回鹘的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00万。经过自然灾害的冲击,尤其是经过黠戛斯人的进攻,回鹘汗国分崩离析,在这种情况下,回鹘人口下降在所难免,随后又因南下、西迁而离散。所以,当时由漠北迁入新疆的实际人口最多不会超过30万。在偌大的高昌回鹘王国,其居民大部分应是被征服的当地各族。如昔日繁盛的龟兹国消失后,其居民都哪里去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回鹘同化了。《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中出现的被称作“西州龟兹回纥白万进”的朝贡使者,就是见诸史册的最为明显的例证。“西州”即高昌,亦即高昌回鹘王国;“龟兹回纥”即龟兹的回鹘人;“白万进”为人名,表明龟兹的白姓居民已归化为回鹘人了。
关于龟兹人的回鹘化,我们还可以西夏国师白法信和白智光为例。
西夏时期佛教盛行,西夏国的缔造者元昊(1038~1048年在位)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一直热心于扶持佛教的发展,并多次向宋朝乞请《大藏经》。1034年,宋刻《开宝藏》传入西夏,元昊遂建高台寺供奉。史载:
[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元昊]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东……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①
从记载知,高台寺建于1047年,当时延纳回鹘僧人讲经说法并译汉文大藏经为西夏文。
元昊殁后,西夏佛教在独揽大权的谅祚(1048~1068年在位)生母没藏氏的支持下继续发展,宋朝于1055年、1058年、1062年又先后三次赐予《大藏经》,故母子动用数万兵民于兴庆府西兴建承天寺,史载:
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②
这一记载表明,谅祚统治时期西夏又从中原地区请得《大藏经》,为储存这些经藏特建立了承天寺,如同元昊一样,也组织回鹘高僧于寺内展开翻译活动,并和其母没藏氏一起常常去寺内听回鹘僧讲法。从西夏统治者皇太后偕皇帝常临寺听回鹘僧人讲经一事看,当时的回鹘高僧在西夏佛教界所拥有的地位当是至高无上的。从西夏文文献看,大凡有皇帝莅临的法事活动,其主持者一般都拥有帝师或国师头衔,而元昊、谅祚时期西夏只有国师而无帝师(帝师在西夏的出现当在夏末仁宗时期)③之设,以理度之,这些回鹘僧的首领应具有国师之位。
通过对西夏佛教文献的进一步检阅,这些国师的身份更为明了。首先是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印本。文献末尾附有撰写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的发愿文,首先叙述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初兴与盛行,经典的翻译与流传,以及“三武灭法”对佛教的迫害等一系列史实,继之讲述了佛教在西夏的流布,以及佛经的翻译情况。载曰:
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蕃译。民安元年,五十三岁,国中先后大小三乘半满教及传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①
其中的“风帝”即西夏王元昊;戊寅年为1038年(即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说明元昊在称帝之初便开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其时比1047年高台寺的建成尚早9年。从是年至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历时53年,终于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12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主持翻译工作的是以国师白法信及其后继者智光等32人为首的一大批人。白法信以国师身份从一开始便参与了译经工作。在他去世后,智光继承了他的国师位及未竟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另一件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印本中,卷首附有一幅木刻版译经图。图中央绘高僧像一身,为主译人,在整幅画卷中图像最大,头部长方形榜题框内有西夏文题名“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两侧绘助译僧侣十六人,后排绘听法俗人八身。在译经图的下部,又绘比较高大的男女画像各一身,分别用西夏文题“母梁氏皇太后”和“子明盛皇帝”。②
同一位被称为“安全国师”的白智光,其名又可见于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序言中:
次始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即惠宗秉常)、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蕃。文华明,天上星月闪闪;义妙澄,海中宝光耀耀。③
这里出现了“智光”和“白智光”两个名字。考虑到二者的身份均为国师,且都在西夏之佛经翻译事业中充当重要角色,活动时代也主要在1037至1090年间,可见二者实为同一人。如序言所称,他翻译的经典,文字优美,表达准确,如“星月闪闪”,光华耀眼,故而在西夏文佛经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那么,上述西夏文文献中出现的白法信、白智光两位国师会不会与上文所述的回鹘高僧有什么关联呢?我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从他们所处的时代、从事的法事活动,尤其是白智光与回鹘僧讲经说法时都有皇太后与皇帝亲聆教诲的场景,使人不由地会做出如此联想,而非完全出自孟浪妄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两位国师的回鹘人身份。
对白法信、白智光民族成分的确认,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史金波先生在80年代初译释上述文献时未论及族属问题,经过数年的深思熟虑,他得出了结论认为白法信、白智光二位著名的译经大师很可能都是来自龟兹地区的回鹘人。①
从姓氏看,白法信和白智光肯定不是党项人。西夏国时期,党项人无以白为姓者。蒙元时代,西夏遗民散布各地,有许多人改行汉姓,但也未闻有以白为姓者。那么,他们会不会是汉人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展开汗牛充栋的中国佛教史册,我们何曾看到有哪一位汉族和尚是俗姓与法号共用?法号的取用本身就意味着与俗姓的决裂。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三国曹魏时被称为“中国出家人中真正沙门的第一人”的朱士行。②由于当时受戒体例尚未完备,故朱士行没有法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特例。东晋道安为增进佛僧的认同意识,首倡以“释”为姓,得到响应,“遂为永式”。③唯来自外国或西域者可有所变通。中原人士为甄别外来僧侣,常以国籍命姓,冠于法号前,如来自印度五天竺者,法号前常冠以“竺”,如竺法兰、竺佛念、竺法雅、竺法乘、竺法义、竺佛调等;来自西域安国者,常以“安”为姓,如安玄、安世高等;来自西域康国者则以“康”为姓,如康僧会、康僧渊、康僧铠、康法朗等;来自印度贵霜国者,则以支或竺命姓,前者表示其为月氏(又作月支)人,后者表示来自天竺。①有的仅用支字,如支娄迦谶、支昙籥、支谦等,有的支、竺共用,如支法护又称竺法护,支佛图澄又称竺佛图澄;而来自龟兹者,则常以其王家姓氏白/帛为姓,如帛尸黎蜜多罗、白延(或帛延)、帛法矩等。
其中,龟兹白(帛)姓尤当注意。自汉至唐700年间,白姓一直是龟兹的大姓。白者,有的史书又写作帛,如《高僧传》及《晋书》之《鸠摩罗什传》中提到的龟兹王白纯,在《晋书·吕光载记》中又被写作帛纯即为明证。据考,白、帛者,均为梵语puspa的音译,意为“云华”。②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汉人在称呼外僧时,既有以姓氏与法号并称者,也有只呼法号者,如竺(支)法护,常略称法护;竺(支)佛图澄呢,则更是以法号行,称姓者反而稀见,这又为白智光何以又被略作智光的问题提供了最佳脚注。
这些说明,白法信和白智光均为来自龟兹的高僧,都是回鹘化了的吐火罗人。二人先后以国师的身份在高台寺和承天寺传经布道,并主持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可以说是古代吐火罗人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因为西夏文大藏经是世界现知的六种大藏经之一。
三 吐火罗与回鹘文佛典翻译
如上所述,当9世纪中叶回鹘人西迁至新疆之前,吐火罗人尚为新疆西部的活跃民族,他们所使用的吐火罗语尚为新疆流行的语言之一。吐火罗人虔信佛教,文化发达,今新疆西部库车、新和一带现存的具有吐火罗风格特点及吐火罗文题记的石窟艺术就是其文化的代表。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库木吐喇石窟第69窟中还可以看到吐火罗文与回鹘文合璧书写的题记(见图2)。二者不存在打破与叠压关系,而且笔法相同,说明为兼通吐火罗文与回鹘文的同一书手所写。吐火罗僧侣接过印度高僧传来的接力棒,把佛教进一步向东方传播。他们是联系印度与中国佛教的纽带,是把佛教由中亚向东方推进的主力。当这些吐火罗人被回鹘同化以后,其佛教文化也被带入回鹘社会之中,对回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吐火罗人在印度佛教传入回鹘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有两部比较重要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就是由吐火罗文本翻译过来的。
其一为《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原名作maitrisimit,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组成。序文的内容主要为一般的佛教教义和回向文;正文主要描绘了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弥勒是未来佛,据《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等载,原出婆罗门家庭,后为佛弟子,先佛入灭,上生于兜率天宫,经四千岁当生于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广为说法。其圆寂及上生兜率天宫的过程在《弥勒会见记》第27幕中有详细描述。这是佛教说一切有部毗婆娑派(Vaibh■sika)的重要著作。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勒柯克(A.vonLeCoq)率领下,于吐鲁番的木头沟和胜金口发现了不少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叶。①1959年4月,在新疆哈密市天山区板房沟乡又发现回鹘文《弥勒会见记》586叶。这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典之一。
这部回鹘文著作,如同其所依的吐火罗语底本一样,常被称作“剧本”。德国学者葛玛丽(A.von.Gabain)②和鲍姆巴奇③经研究后认为,这种本子(或类似的文本)是可以作为街头说唱结合的戏剧演出之底本来使用的。
关于回鹘文本的来源问题,在哈密写本的第一、二、十、十二、十六、廿、廿三、廿五诸幕末尾都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跋文。例如第一幕末尾(第16叶背面)这样写道:精通一切经论的、饮过毗婆娑论甘露的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改编为吐火罗语,智护法师译为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书中跋多利婆罗门做布施第一幕完。①
据此跋文可知,该经回鹘文原名作maitrisimit,它先由圣月大师(Arya〓antr〓)据印度文本改为古代焉耆语,以后又由智护(Patanraksit)大师据之转译为突厥语。据考,圣月大师系三唆里迷国(〓〓Solmi,即焉耆)的著名佛教大师。智护呢?缪勒与西额根据德国所藏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中称智护为Il-bal〓q人的记载,认为他应来自伊犁地区。②葛玛丽教授亦同意此说。③但法国学者伯希和(M.Pelliot)疑之,虽可认定11-bal〓q为突厥语地名,但具体所指已无法知晓。④后来,哈密顿经过研究认为,I1/El-bal〓q不能理解为伊犁,而应为“国都”之意,指的就是回鹘王国的都城——高昌。⑤此说可信。从出土文献看,高昌在古代正属于焉耆语/甲种吐火罗语的流行地。
有幸的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所依据的吐火罗文底本在新疆也有发现。1974年冬,在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个灰坑内出土了一批用婆罗谜文书写的文献,经由季羡林先生研究解读,知其正是用焉耆语/甲种吐火罗语书写的《弥勒会见记》,共44叶,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①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记载的正确,同时也为我们认识西域戏剧的起源、内容与形式及其传播途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通过对回鹘文本与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的比较,学者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有些部分看起来不像是“翻译”出来的,而像是改编甚或是重新创作。②由此之故,古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题记所谓译自吐火罗语的说法是否切合实际,即是否完全按照吐火罗语底本译出,还存在着问题。
其二为《十业道譬喻鬘经》。这是一部大型佛教故事集,性质有些类似于古代印度的《五卷书》和《一千零一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③有关回鹘文写本早在20世纪初就在吐鲁番地区有所发现,回鹘文写作D(a)〓ak(a)rmapata(awdanamal),梵文为Da〓akarmapath〓-vad〓nam〓〓。其中所收故事分门别类地讲述了佛教的十种善业(Kar-mapatha)“十善业”与“十恶业”相对,是佛教的基本道德信条。属于身业的有三:不杀生、不偷窃、不淫邪;属于口业的有四: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属于意业的有三:不贪欲、不嗔忿、不邪见。关于该文献的来源,在德国梅因兹收藏的编号为Mainz864a(TⅢ84-68)中有载(见图3),其跋文称:
精通毗婆沙论、咒法与诗文的僧伽奴将这部伟大的《十业道譬喻鬘经》从uguK〓s〓n语(即龟兹语——引者)译成吐火罗语(即焉耆语——引者),再由尸罗仙那(〓lasena)大师将其重新转译成突厥语。以弘扬“十善业”的利益和十恶行的罪过。①
这一记载说明,《十业道譬喻鬘经》是从由龟兹语翻译成焉耆语,然后再从焉耆语翻译成回鹘语。遗憾的是,该文献之内容既不见于龟兹语、焉耆语文献,也不见于梵文与汉文典籍。除回鹘文文本外,现只发现有粟特语残卷。该残卷的题目似乎是δssyrkrtyh,即“之′十善业”意。②看来,这一粟特文写卷应是一部与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经》类似的著作。
以上两部回鹘文著作都是以焉耆语/甲种吐火罗语为底本的,那么是否有直接译自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的文献呢?我们这里不妨先看缪勒在《吐火罗与贵霜》一文中所提到的如下一段回鹘文题记:
《一切有情..救经》,第三十二分终,原列阿阇梨论师Klianzini(Kaly〓nasena)之idivut中,师从k〓s〓n语译为bar〓uq语,附有大阿梨Srvarak〓ti遗留之idivut经赞..③
题记中所谓的《一切有情..救经》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由于文献断残过甚已无法知晓。其中的“k〓s〓n语”,缪勒解释为与加腻色迦王有关系的人们熟知的“贵霜”之语言,并成为此后欧洲学术界的定说。1931年,羽田亨刊文指出其误,认为应解释为“龟兹语”。④此说得到了伯希和的支持。在羽田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这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k〓s〓n语”实应称“龟兹语”。⑤在笔者看来,就本文献而言,如果将“k〓s〓n语”解释为龟兹语,当更合乎本题记的文意,因为其中所提到的这部佛经是由k〓s〓n语译为bar〓uq语的。Bar〓uq地当今新疆巴楚县,故题记中的bar〓uq语当为古代回鹘语无疑。而回鹘语佛经译本出现之时代,距离贵霜帝国已相当遥远,而龟兹语文却正在流行,而且对回鹘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见下文),故文中的“k〓s〓n语”庶几乎可理解为“龟兹语”。
以上二件文献均译自焉耆文/甲种吐火罗文,那么是否有译自龟兹文/乙种吐火罗文的文献呢?从现知的文献看,尚无法确定。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有这种可能。《阿烂弥王本生》在回鹘文文献中写作〓ranemi-J〓taka,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Ou〓gour1。原写本分为3叶,共存文字119行。其中67行为阿烂弥王本生故事本文,其余52行为题记。该本生故事不见于汉文、梵文与藏文《大藏经》。从译文看,其中大量采用了吐火罗语词汇,如:
人名S〓nt〓r,源自龟兹文sunetra;
人名阿烂弥王〓rnim源自龟兹文aranemi;
地名〓rin〓t〓w,源自龟兹,文arun〓vati;
专有名词a〓ar〓,源自龟兹文a〓ari<梵文〓c〓rya,意为“导师”或“规范师”汉译“阿阇梨”,为佛教僧官称号;复数名,a〓意为“,由am-
词amlar,大臣们”a〓(大臣)加复数后缀-lar构成。其中,ama〓源自龟兹文am〓c<梵文am〓tya。①从这些因素看,该文献有可能来源于龟兹文原典。
四 吐火罗语对回鹘语言的影响
今天发现的吐火罗语文献的时代大多在6~9世纪之间,但吐火罗语在新疆的存在却比这个时期久远得多。佛教大致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地区,然后经由这里而于1世纪左右传入内地。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包括吐火罗人在内的西域诸族曾起过桥梁作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成为梵文佛典译入汉文的媒介。季羡林先生指出:
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我们两国不完全是直接往来,使用吐火罗语的这个部族曾在中间起过桥梁作用……饮水思源,我们不应该忘记曾经沟通中印文化的吐火罗人。①
这个论断,对古代回鹘佛教及其文献语言的形成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是适用的。
回鹘人曾经翻译过大量的佛教经典,纵然不是全部大藏经,至少也是大藏经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都已先后译成了回鹘语。从新疆、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看,这些佛经大多直接译自汉文,另有一部分译自藏文、梵文甚或吐火罗文,不管译自何种文字,我们都可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印度梵语和古回鹘语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语。日本学者庄垣内正弘以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为依据,对回鹘文献语言中存在的借词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回鹘语词尾形式、语音、形态诸方面特征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回鹘语中的借词尽管来源广泛,既有汉语,也有梵语等,但基本上是以吐火罗语为主的,粟特语只是起一些辅助性的作用。②
这里我们先看下列表格(依庄垣内正弘研究成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回鹘语在吸纳梵语词汇的过程,即当梵语词尾为-i/-ī时,在回鹘语中变为-i、-u;-ū则变为-u;-in变为-i;-jit变为-ci,这一演变常常通过了吐火罗语的过渡。在吐火罗语中,元音弱化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古代译师们在用之译经时,按照其语音规律将梵语中的词尾-a改变为-e;当其被译为回鹘语时,又经改造而变成了-i。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梵语词尾到回鹘语词尾的转化都经历了梵语→焉耆—龟兹语(或汉语、藏语)→回鹘语的过程。
除了词尾的变化外,辅音也因受吐火罗语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同时还有回鹘语直接借自吐火罗语,这些情况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也是很常见的。如:
(1)阿鼻狱,梵语原作avīci,但回鹘语却写作avis,究其来源,当源自吐火罗语之avis。
(2)摩竭鱼,梵语原作makara,但在回鹘语中却演变为matar,与梵文相去甚远,显然当借自吐火罗语之matar。
(3)行布施,梵语原作pindapāa,但回鹘语却写作pinvat,究其来源,当源自吐火罗语之pinwāt。在回鹘语中,v、w相通。
这里还应特别提及吐鲁番出土的印度英雄史诗《罗摩衍那》回鹘文写本。《罗摩衍那》本为印度教内容,但被佛教徒借用以宣传佛教。其中有些用词显然受到了吐火罗语的影响。例如,罗摩之妻悉多在梵文本中的对应词是Sita,但在回鹘文本中却变成了siza。同一个词,吐罗语写作Sisā,①于阗文则作Sīysā(ys替代z)。②追寻回鹘文siza之来源,自然应追溯至吐火罗语而非梵语,因为其发音与吐火罗语最为接近而与梵文相距较远。③
还有一些词汇,本为吐火罗语,被回鹘语直接借用。如胡麻,回鹘语作k〓n〓id或ktin〓t,显然借自吐火罗语kuicit;再如小屋,在回鹘语中写作piryan,显然借自吐火罗语pary〓m;大麦回鹘语作ǎrpa,显然借自吐火罗语arpa。
正是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存在,库车居民的语言,直到近世尚存古龟兹之遗风。德国东方学家马丁·哈特曼(MartinHartmann)曾于清末到新疆旅行,在他的著作《中国新疆——历史、行政、宗教和经济(ChinesischTurkestan,Geschichte,Verwaltung,GeisteslebenundWirtschaft)》(哈勒,1908年)一书中记载了他在新疆的见闻,其中提到:
莎车当地人称,库车的语言清纯;说话善用诗,其语言有很多都是我们所不懂的。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现象?法国学者烈维认为,此应是库车维吾尔语受古代吐火罗语影响所致,是值得今人认真研究的。⑤这一结论无疑是有道理的。
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的写本中,还发现有多件用摩尼文或龟兹文字母拼写的龟兹语、回鹘对照摩尼教文献。兹简述于下:
(1)U99(TⅢD259,13)小残片1叶,面积7.6×5.9厘米,存文字10行,内容为用摩尼文书龟兹语、回鹘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①(见图4)
(2)U100(TⅢD260,34/TⅢD259,17),残片1叶,面积20.7×5.6厘米,存文字10行,内容为用龟兹文书写的回鹘语和龟兹语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②
(3)U101(TⅢD260,14,TⅢD260,10),小残片2叶,面积分别为6.4×5.9厘米、10.6×4.7厘米,可拼合。存文字10行,内容为用龟兹文书写的回鹘语和龟兹语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③
(4)U102(TⅢD259,23,TⅢD259,26),小残片2块,面积分别为6.3×5.9厘米、7.3×6厘米,可拼合。存文字10行,内容为用龟兹文书写的回鹘语和龟兹语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④
(5)U103a-c(TⅢD260,19,TⅢD260,30),小残片3叶,面积分别为6.4×5.8厘米、7.4×5.8厘米、3.7×5.6厘米,可拼合。存文字10行,内容为用龟兹文书写的回鹘语和龟兹语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⑤
上述5件写本或用摩尼文书写,或用龟兹文书写,但内容均为回鹘语和龟兹语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以这些因素观之,应为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初的作品。当时吐火罗语尚处于流行阶段,摩尼教也正在吐火罗人和回鹘人中盛行。这些赞美诗无疑体现了吐火罗人、回鹘人与摩尼教间的密切关系。吐火罗人与回鹘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发生在回鹘由摩尼教信仰转归佛教信仰之前,为后来吐火罗语成为印度梵语和回鹘语的媒介语这一现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者: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敦煌:晚唐五代中外文化交融与碰撞
郑炳林
敦煌地区是中原文明、西域文明、藏域文明、草原文明交汇之地,其东界河西诸郡与中原相接,是连接中原西域文明的桥头堡:西临西域,控驭两关与中亚及西方世界连接;南界吐蕃,接受藏文化优秀部分;北御突厥,将草原地区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接纳,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优势。敦煌是古代中国经营西域的基地,汉唐以来中央政府经营西域,都是以敦煌为军屯要塞,因此所谓的吐谷浑道、鄯善道、伊吾道等行军路线,都是以敦煌为起点的,并且派遣敦煌地区民众官员带军出征西域地区。敦煌出土的简牍、文书等大量文献资料和石窟壁画等丰富图像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一 敦煌是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经营西域的基地
自汉武帝置河西四郡设立敦煌郡起,敦煌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都会之地,也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交通道路经由河西走廊往西域,敦煌是其必经之地,有敦煌到伊吾的新开道、由敦煌到高昌的大海道、出敦煌经过玉门关到焉耆的大碛道、出敦煌经阳关到石城的鄯善道、出敦煌到吐蕃的把疾道。①《隋书·裴矩传》说伊吾、高昌、鄯善为西域之门户,而总会敦煌。②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古代的西域主要指敦煌两关以西的地区,而敦煌就成为古代中国的边疆重镇。汉武帝以敦煌为基地经营西域,唐朝贞观年间对吐谷浑的战争、对高昌的战争以及武则天时期对吐蕃和西突厥的战争,都是以敦煌为基地进行。贞观年间唐朝中央政府准备用大量粮食等物资救济居住伊吾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就是以敦煌为中心实施的。
唐朝贞观十四年占领高昌设立西州,相继设立了伊州、庭州,建立安西、北庭两个大都护府,管辖范围一直达到了葱岭以西的地区。以后在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的基础上设置了安西、北庭两个节度使。当时唐朝的认识是西域战乱,河西就受影响,不安定,而河西不保,关中就难以稳定,所以作为唐朝政府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敦煌就显得十分重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得到证实。从吐鲁番地区出土墓志和文书以及敦煌文献记载看,吐鲁番地区的居民很多都是从敦煌地区迁徙而来的,敦煌地区很多人任职吐鲁番地区,担任镇府军将之职。③记载比较明显的是《沙州都督府图经》张芝墨池条和《敦煌名族志》,①有担任唐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阴嗣监,实际就是北庭节度使;有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阴守忠等,还有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摄本卫中郎将充于阗录守使敦煌郡开国公张怀福,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等上柱国张怀立,昭武校尉前西州岸头府左果毅都尉摄本府折冲充墨离军子将张履古,通海镇大将神军索恪,等等。在吐鲁番的汉族居民结构中,源自于敦煌的居民占了主要部分,如敦煌张氏中的清河、南阳、安定等,在吐鲁番出土墓志铭中都有记载。这就使吐鲁番地区的居民结构和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一样,居民中有专门安置胡姓居民的从化乡和崇化乡。经过我们的研究,敦煌胡姓居民大约占了整个居民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或者说,汉姓居民占了敦煌、高昌地区居民的百分之七十左右。②由于这种居民结构特点,因此唐朝政府经营西域,将经营基地放在敦煌,打败高昌的麴文泰和西突厥之后,将管理西域的中心放在汉族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州、庭州。尽管一段时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放在军镇要地龟兹,但是往往是在西州和龟兹之间变换。而敦煌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唐朝政府与吐蕃在西域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唐朝政府为了加强战争的需要,于上元二年将毗邻敦煌的石城镇、播仙镇,划归敦煌地区管辖。敦煌文献《沙州伊州地志》和《寿昌县地境》记载的沙州寿昌县管辖的地域包括了石城镇和播仙镇等。③开元天宝年间,随着吐蕃势力的增强,一度占领毗邻敦煌的石城镇和播仙镇,居住在这里的胡姓居民向敦煌地区迁徙,敦煌县的从化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安史之乱发生之后,边兵内撤,吐蕃乘机占领河西陇右,河西节度使由凉州—张掖—敦煌,在敦煌地区坚持的十一年之后,于786年最后在不要将敦煌地区居民外迁的条件下投降了吐蕃,敦煌开始了将近六十年的吐蕃统治时期。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仍然是吐蕃统治和管理西域地区的中心。经过我们的研究得知,吐蕃统治时期,先后在陇右、河西设立了河州、沙州、凉州和瓜州四个节度使。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州和瓜州节度使,节度使都是由吐蕃宰相来担任的,瓜州节度使管理瓜沙肃及其西域地区,从瓜州节度使衙的任职人员结构看,敦煌地区的大姓成员很多都在瓜州节度使衙中担任各种职务,这在敦煌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同时,瓜州节度使衙的物质供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敦煌。我们从敦煌经济文书记载敦煌百姓服役情况看,记载敦煌地区百姓往瓜州节度使衙送物品,如S.542《戌年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记载敦煌龙兴寺的张善德和史英俊等、莲台寺阴庭圭、灵图寺的史奉仙等往瓜州节度送粳米,护送西州人户往瓜州。①从敦煌文献中的发愿文记载得知,吐蕃时期瓜州节度使曾经带领敦煌地区兵马,前往西域地区平息那里反对吐蕃的少数民族。这些记载表明吐蕃时期,敦煌地区是经营西域的中心。
848年(大中二年),张议潮带领敦煌地区的胡汉民众驱逐了吐蕃统治者,收复瓜沙二州,相继派出十批使节入朝。大中三年,张议潮的军队收复了肃州,大中四年收复了敦煌通往西域的门户之地伊州,大中五年唐朝政府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咸通二年张议潮以七千人收复凉州,追击吐蕃的军队一直到星宿岭南,大概就是今天青海和黄河源一带。②归义军的管辖范围最大时达到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共管辖六个州,一度号称十州。咸通七年前后由于回鹘的归附,名义上就有了西州和庭州。东部因为对吐蕃的战争,归义军政权的管辖范围一度达到了河湟流域。这样归义军的管辖范围名义上就有了鄯州和兰州。①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不归,其兄之子张淮深执掌归义军政权,直到大顺元年(890)被杀为止。②这一时期归义军的疆域处于退缩趋势,最后仅有二州之地,此后敦煌归义军政权经张淮鼎、索勋、张承奉及其曹氏家族,绵延200多年时间,归义军一直没有大的起色。归义军时期在管辖范围上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是:第一,敦煌地区是归义军政权的政治中心,无论是张议潮、张淮深的六州、十州,还是五州、二州八镇,敦煌都是当时的统治中心。唐朝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虽然没有得到唐朝正式任命,但是一直掌握归义军实际事务。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将国都定在东有三危大圣、西有金鞍毒龙,神佛护佑的敦煌,以敦煌为中心经营周边。③第二,从归义军的西部管辖范围变化,可以看出归义军的经营西域用心,将伊吾、西州、石城作为经营的重点。在伊州方面,从大中四年取得伊州,多次用兵攻打盘踞在伊州纳职城的回鹘势力,《张议潮变文》就记载了大中十年~十一年连续对伊州纳职城回鹘势力用兵的情况,并派遣王万清、左公等任伊州刺史,④一直到乾符三年四月回鹘可汗仆固俊打下伊州,归义军对伊吾的控制结束。⑤此后张承奉时期归义军政权曾经一度用兵伊吾,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石城方向,归义军初期,《张议潮变文》记载归义军的军队经过一千余里行军到达吐谷浑国内。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可能是指居住在石城附近的吐蕃政权,根据《沙州图经》记载,阳关至石城的距离是一千五百里左右,和变文记载的历程基本相符合。张承奉时期,归义军派遣罗盈达、张良真出征石城地区的吐蕃,并取得胜利,设立了石城镇。第三,归义军时期积极开展与西域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政治交往,为了加强同西州、伊州回鹘以及于阗、石城仲云(南山)之间关系,归义军政权不断派遣使节、商队前往这些地区。出使某个地区有专门的组织——使团,并且为了加强对使团的管理,专门设立了使头之职,有于阗使驿头、南山使头、西州使头、伊州使头等。①使团的成员有官员、商侣、僧人,也有一般百姓,使团的商业性质很明显,出使前在敦煌地区借贷大量的物品,出使结束之后,以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利润归还。第四,敦煌地区平常接待大量的外来使节,有来自西州、伊州、石城、于阗及其达怛、退浑、吐蕃等区域性政权的,也有来自中亚地区如印度、波斯等地的使节和行僧等,专门设置了宴设司等机构,负责接待工作,开创了敦煌地区又一个繁荣的局面。②
二 敦煌地区居民结构呈现多元化倾向
敦煌地区居民成分复杂,我们曾经研究敦煌县的乡里制度,知道唐代敦煌县有十三乡,其中就有从化乡,主要见载于《天宝十载敦煌县从化乡差科簿》,记载服差役的人有257人,有2人担任市壁师。从化乡是由分布在敦煌城东一里的祆寺周围一带的胡姓居民建立的,他们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市壁师就是专门管理市场贸易的官吏,由胡姓居民担任,表明粟特人是敦煌市场贸易的主体。同时差科簿还记载从化乡有两个里正、四个村正,由于文书残缺,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敦煌从化乡到底有几个里多少村,但是我们起码可以确定,从化乡最少有两个里四个村落。①从化乡的来历,经过陈国灿先生的研究,大约武周时期居住在石城镇一带的粟特人在吐蕃的逼迫之下迁居敦煌,唐朝政府将其安置在敦煌城周围一带,并以之为主建立了从化乡。②
吐蕃统治敦煌之后,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并没有像池田温先生说的那样,粟特外迁到回鹘地区,剩下的都进入寺院变为寺户,从此敦煌地区再也没有粟特人了。经过我们的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粟特人还存在,见于敦煌文书的有,敦煌富商粟特人康秀华,为抄写一部《大般若经》就向佛教教团张金炫和尚施舍了价值600石麦子的银器、胡粉和粟麦等,再敦煌石窟中记载他就是敦煌部落使之一。部落使是由唐代的乡官改变而来的,因此可以肯定,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并没有外迁,而是还保留他原来的面貌。除了部落使康秀华之外,粟特人还担任吐蕃时期敦煌都督之职,都督是吐蕃人之外的汉人及其他民族能够担任的最高官职,但是粟特人也担任这一职位,记载于敦煌文献的就有安都督,实际上粟特人已经成了吐蕃时期敦煌地方政府的实际执政者。③
归义军政权是一个胡汉联合政权,首先从这个政权的建立过程来看,张议潮收复敦煌之后,和副使安景旻、部落使阎英达、都僧统吴洪辩等派出使节入朝,而安景旻就是居住敦煌的粟特人的代表,阎英达是通颊等部落的代表。归义军政权中有瓜州刺史康使君、都知兵马使删丹镇遏使康通信、左都押衙安怀恩等,节度使以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都有粟特人担任,同样都僧统及其以下各级僧官也有粟特人担任,直到曹氏归义军时期。经过荣新江、冯培红等研究认为,曹氏家族就是居住在敦煌的粟特人后裔,归义军政权从张氏时期的以汉人为主的胡汉联合政权,变为曹氏以粟特人为主的胡汉联合政权。①归义军政权从张氏手中转入粟特人曹氏手中,主要是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变化,粟特人在敦煌地区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敦煌地区的粟特人聚落有康家庄、曹家庄、史家庄、石家庄、安家庄、罗家庄等。②经过我们对大量敦煌文书的分析,敦煌地区以胡姓居民为主的外来居民,占了将近百分之三十左右。除了粟特人之外,敦煌地区从武周时期起,就有大量吐谷浑人迁居敦煌,或者他们投唐之后,唐朝将他们安置在敦煌一带;归义军后期,敦煌地区有吐谷浑部落,特别是在瓜州地区,吐谷浑慕容家族势力非常大,五代时期慕容归盈担任瓜州刺史,生前直接派遣使节入朝,死后瓜州官吏还要给归义军节度使上状,要求为慕容归盈修建寺庙纪念。吐蕃统治时期,有大量吐蕃人迁徙到敦煌地区,归义军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的遗迹,特别是在肃州和瓜州之间,就有吐蕃人部落,高居诲出使于阗,图经河西敦煌,看到沿路都有吐蕃聚落。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居住着除了汉族人之外很多民族,居民结构成分复杂,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因此影响到敦煌地区,宗教文化社会风俗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三 敦煌对外交流具有国际化特色
从两汉起敦煌就成为一个国际化商业贸易都会城市,《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敦煌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明确指出敦煌是国际贸易市场城市,敦煌的这种地位一直到唐代中期基本上都没有发生改变。归义军时期敦煌商业贸易市场地位有所衰落,地位远不如以前,但仍然起着国际商业贸易城市的作用。至于这种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是我们探讨的一个主要内容。作为国际贸易城市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具有国际性,二是出现在贸易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商品也要具有国际性,三是贸易市场上使用货币的国际性。
唐代敦煌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他们担任管理市场贸易的市壁师,是敦煌贸易市场的主体。由于粟特人的国际性,对敦煌市场贸易影响很大,使其国际化程度提高,汉唐以来一直保持华夷之交的都会城市特点。此外敦煌商业贸易中还常见有吐蕃、于阗、波斯、印度的商人。敦煌市场上有他们开设的酒店商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时期对外贸易相当频繁,经常向中原地区和西域及周边诸政权派遣使团,这些使团规模大人员庞杂,有官员也有一般随员,还有相当多的商人和僧侣。在一般情况下,使团成员都要携带一些纺织品或其他质轻价高的物品去贩卖,同时将其他地方的物产贩到敦煌市场出售,或经敦煌再转售到其他地方。当时归义军向外派遣使节的记载比较多,为了管理使团事务约束随员纪律等,出使的随团人员中常设了一批使团头目,有甘州使头、西州使头、于阗使头等,这些使团头目中有很多就是由粟特人来担任的。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派往各地的使节非常频繁,这些使节组成复杂,除完成政府的任务而外,还带有商业贸易使团的性质,他们牵驼驮物来往奔走在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及其周边政权之间,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就是通过他们进入的。敦煌文书记载来往使节般次捎带货物比较常见,更多的是出使的目的就是为了商业贸易,出使之前为了筹集足够的商品和运输工具,他们得向人借贷货物和雇佣驼马,出使回来之后用贩运回来的商品偿还利息与雇价。在归义军政权的机构中还专门设立了宴设司,职责是招待来到敦煌的外地使团,这些使团商团有来自回鹘、于阗、南山、鞑靼、波斯、印度等地。这些东来西往的商团尽管经常遭受沿途各个政权的骚扰和劫夺,但是并不因为战争或劫夺而放弃通使和商业贸易。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商品同样也具有国际性。敦煌地区物产贫瘠,地不产珍,献无奇玩。因此敦煌市场上的商品大都靠从外地进口,进行中转贸易。有出产于龟兹的胡粉,中亚的金青和水银,吐蕃地区的石青和石绿,西州出产的棉布,波斯等地出产的胡锦和珠宝,伊州出产的铁器,于阗出产玉石,东罗马的银器,西域印度的药材和香料,高丽出产的高丽锦,达怛和吐蕃出产的畜牧产品和兵器等。产品来源东到中原及朝鲜,南到吐蕃和印度,西到波斯、印度和东罗马。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国际化的程度还决定于市场使用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敦煌文献记载看,金币银币和金银器皿是对外贸易中使用的主要硬通货。金银币等硬通货不但流通,而且数量不小。这些金银币可能就是这些外来胡商带进敦煌贸易市场的。金银器i皿作为流通货币在晚唐五代的敦煌贸易市场比较常见,这些金银器皿有罗马银盏、银盘子、金花银瓶子、银碗等。这些银器表明重量,用于支付物价,其性质显然是货币,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器皿,而是作为货币流通于敦煌等地的贸易市场中。其次在对外贸易中还使用丝绸支付物价。在对内或小宗贸易上多用实物特别是粮食支付物价,进行交换。
四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
(1)多元化宗教流行及其演变:祆教和佛教
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域,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外文化交流都要经过敦煌地区进行,因此敦煌流行的宗教和民间信仰也呈现多元化倾向。汉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盛行,粟特人迁居敦煌之后,祆教也开始流行。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流行的宗教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祆教,如果说将儒家理论学说也归并为教的话,还有儒教,加上各种信仰(如十王信仰、观音信仰、海龙王信仰、毗沙天王信仰、五天山信仰、宾头卢信仰等)那就更多了,主要的是儒、释、道三教。儒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道教是中国原始宗教,二者代表汉文化对外影响的主流。如回鹘、吐蕃等将儒家经典翻译过来,将属于道教的占卜文献翻译成本民族文献,或者在其占卜文献中加以吸纳,是汉文化对其影响的具体方面。更多的是外来宗教进入敦煌地区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戒律清规的演变及其违规现象普遍。其次祆教信仰传播流行日渐盛行,甚至变成归义军的政府行为。
祆教是粟特人信仰的宗教,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就记载了敦煌城东一里有祆寺,所谓的城东水池赛祆,可能就是指祆庙。根据归义军政府支出账的记载,赛祆的时间为每年的正月十一日、正月十三、二月廿一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四月十四日、四月十六日、五月十一日、七月九日、十月五日、十月九日等。祭祀祆神的开支都是由政府负担,表明赛祆是一种政府的行为,祆神被称作安城将军,是敦煌民间信仰的一种神。①《敦煌古迹廿咏》记载有安城祆咏:“板筑安城日,神祠以此兴;州县祈景祚,万类仰休征。频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绳。”②不仅仅粟特人信仰祆教,就是生活在敦煌地区的汉族人也信仰祆教,归义军时期派出的使节带有画纸以备沿途赛祆之用。我们看到张承奉时期及其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支出账都基本上有赛祆的各种支出。祆教流行及其政府出面赛祆,表明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和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粟特人的势力得到加强或者掌握了归义军政权。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违犯戒律现象非常严重,五戒十戒中都规定僧人不能饮酒,但是在晚唐佛教教团中僧人饮酒成风。敦煌籍账文献中很多是寺院或者都司机构的酒账,从这些酒账看,僧人不仅为加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将上好的酒送给归义军政权的有关官员,如每年端午节就送麦酒给节度使或者都押衙等,还自己饮酒,造酒,更有甚者僧人公然开酒店,从事酒制造销售,从中牟利,有的由此成为巨富。③敦煌文献就记载一位叫龙藏的和尚,吐蕃时期因为开酒店,一年营利麦一百三十石、土地七十亩。④归义军时期以僧人命名的酒店很多,很可能就是僧人们出资开的酒店。僧人饮酒不是根本戒,是因为饮酒可以乱性,做出其他违背戒律的事情。敦煌僧人饮酒风气是从吐蕃时期开始的,显然是受了外来风气的影响。
其次,僧人食肉问题,有两点需要我们认识:一是寺院拥有大量牲畜,寺院拥有羊一般数十只,有的达到数百只,专门雇人放牧,每年正月寺院主管与放牧者都要进行算会,新生了多少,死亡了多少,羊皮和羊腔多少,他们将这些羊作什么用途,是出售还是自用。二是,僧人食用臛一类的东西,有人研究是肉汤,如果僧人使用肉汤,那么僧人食肉问题就解决了。目前学术界有的学者坚持僧人食肉,并且有专门论文发表。我们的看法是,按照小乘佛教的要求,僧人可以杂食三净,毗邻敦煌的龟兹等都信仰小乘佛教,这种习俗可能受了他们的影响。
僧人拥有家室可以娶妻生子。这是敦煌文献反映出来的一个特殊问题,敦煌户籍文书记载,晚唐五代的僧人主要是晚唐张议潮时期僧人的户籍都在原来的家里,所谓僧挂俗籍或者僧俗混籍。从这些户籍上看,敦煌的僧人有妻有子女,问题是他们的妻室和子女是出家前所娶,还是出家后所娶,子女是出家前所生,还是出家后所生,目前我们还无法搞清楚。目前学术界有一部分专家认为敦煌佛教教团的僧人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并且专门撰写论文加以论证。从龙藏和尚看,他在出家前娶妻阴二娘,出家之后不久阴二娘就死了,不能证实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可以证实的是龙藏出家后还和其子宣子生活在一起。关于僧人拥有家室主要根据是户籍,就这个问题来说直到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彻底解决。经过杨富学先生的研究,居住在鄯善地区的僧人拥有家室,娶妻生子。开元年间,居住在这里的胡姓居民迁徙敦煌,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教团是否受了他们的影响而允许僧人拥有家室娶妻生子的。也有的专家认为可能与敦煌地区人口问题有关,性比例失调造成的,当时男性少而女性居多,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除了允许一夫多妻、放松女性出家外,就是僧人承担徭役赋税从军打仗,这样僧人就同一般百姓一样了,没有什么特殊优惠条件,那么僧人犯戒娶妻生子就很正常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宋代笔记史料中找到证据。记载广州有僧人娶妻风俗,《鸡肋编》卷中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蕹度乃成礼。市中亦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但欲簪花其上也。”①这与敦煌地区的情况差不多。
僧人从事商业经营,拥有大量田产财物。吐蕃时期龙藏和尚三年间租种土地收入九十驮粮食,合计家里一千驮。至丑年家内羊三百、牛驴三十头,官田租种收入十二车,造酒收入麦一百三十石、土地三十亩,丝绵磑所罗抵价麦粟一百三十石。尽管这些财物与其兄共有,但也足以证明其富有状况。到归义军时期,我们以索崇恩和尚为例,索崇恩是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都教授,从索崇恩的遗嘱得知,索崇恩拥有土地、牲畜、奴婢、磑所、金银、丝绸等财产,②都表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高僧拥有很多资产。这显然与佛教教义相违背,按照佛教教义的要求,僧人三衣之外没有任何资产,僧人不允许穿戴金银和丝织品,敦煌佛教的榜文也是这样规定的,佛教法会及新度僧尼不允许使用金银器皿、不允许穿戴丝织品,一经发现就要当场毁坏,重者要报官处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实行的是两回事,这很可能由于僧人经常不住寺院,生活在家里,所以拥有资产是很平常的事情。佛教戒律清规的要求只是针对寺院活动的僧尼,而对于生活在家庭的僧尼没有什么限制。僧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也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一大特点,从敦煌文书可以看出,僧人出使在晚唐五代是很平常的事情,归义军建立过程中,僧人在入朝通使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唐悟真和尚从大中二年开始一直到咸通十年他担任都僧统期间,多次来往于敦煌与长安之间。此后每次使团中都有僧人参与,特别是出使的僧人都具有商人的职能,他们出使前都要借贷很多东西,回来后以很高的利息归还,僧人从事贸易的结果,使很多僧人成为富商,同时也使佛教戒律破坏。僧人不仅仅从事长途贩运,而且还开店经营,从事有官工商领域的营利活动。
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清规演变最大的是科罚制度与清规出现。在科罚方面,佛教教团将政府的惩罚规定引入佛教教团中,有很多名称都一样,如令、条、式等。科罚内容分实物科罚和身体体罚两种:实物科罚有酒、饮食和粮食,而体罚主要针对年龄比较小的僧尼,他们没有经济来源,实物科罚难以承担,所以采取杖多少下。①我们中国佛教教团的清规——百丈清规(禅门规式)的制定正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影响很难达到敦煌地区。归义军时期,敦煌基本上是一个半独立性的政权,与中原之间的佛教交往受到一定限制,禅门规式不一定能传入敦煌,因此敦煌地区很难看到百丈清规影响的痕迹,但是敦煌地区佛教的发展产生了自己的类似于清规的东西,形成了他们的区域特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虽然没有保留下来成文的清规一类的东西,但是有在榜文中很多与清规有关的规定的记载。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当时清规的大概情况,认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制定有自己的清规。这种清规有很多称呼,所谓规矩、律式、格令等都是指佛教教团的清规。②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教团的清规与禅宗洪州宗关系密切,敦煌佛教教团的很多规定都与淮海禅师的百丈清规有相似的地方,受到洪州宗的禅门规式影响比较大。但是敦煌佛教教团也有其地域特色,有很多方面在洪州宗百丈清规中严加限定的内容,在敦煌相反不加限定或者限定不严格。
(2)敦煌饮食文化的影响——胡食风气
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的饮食资料,敦煌壁画中也有很多形象资料,这些对于我们研究敦煌饮食十分珍贵。首先从种植粮食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的植物主要有:小麦、青稞、大麦、裸麦、荞麦、粟、糜以及豌豆、荜豆、豇豆、小豆子、大豆、黑豆、绿豆等,以麦为主,其次是粟、豆。除了粮食作物之外,还有各种油料作物,如麻、红兰等;蔬菜有萝卜、生菜、葱韭菜、葫芦等,其中南瓜、冬瓜等也称作葫芦。肉类有猪、牛、羊以及各种野生动物。在这种食物原料的基础上产生的敦煌饮食文化,必然具有中外结合的饮食特色。晚唐五代的敦煌饮食文化既是中西文化交流产物,又融合当时西北少数民族的饮食生活内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除了主体民族汉族之外,有粟特为主的胡姓民族,还有龙家、鄯家等西域民族;吐蕃为主的羌姓民族,包括南山人、萨毗、仲云、温末、吐谷浑等在内;回鹘为主的戎姓民族,包括西州回鹘、甘州回鹘、伊州回鹘和达旦等,敦煌文献称之为六蕃,实际上远不止六个少数民族。到了归义军晚期于阗王室在喀喇汗王朝东进形势的逼迫下也迁居敦煌建立了自己的聚落。归义军管辖下的敦煌是多民族混居区,这里有粟特人的聚落,还有管理这些少数民族的机构蕃部落使等,当时敦煌有通颊退浑等十部落,因此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统称为蕃汉百姓,组成的军队也称蕃汉精兵。由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居民是由多民族结构组成,决定了敦煌饮食文化多元化形态,在敦煌地区的饮食结构中少数民族饮食占了很大比重。我们从敦煌文献中看到很多胡食胡风,如“胡饼”频繁见载于敦煌籍账文书之中,不仅仅少数民族食用,汉族也食用,从官府到民间,从一般居民到出家僧众,平时饮食都食用胡饼。胡饼成了晚唐五代敦煌公私宴用、日常生活必备的食品。就胡饼的种类看,除了一般胡饼之外,还有油胡饼和肉胡饼,特别是肉胡饼也是唐代常见的食品,其做法也见载于唐朝笔记史料中。胡饼的传入与粟特等商业民族的迁入关系密切,胡饼的特点是口味好、制作简单、便于携带、易于保存,特别是长途贩运中饮食非常方便。经过有的专家研究胡饼就是今天新疆一带经常食用的食品——馕,也有人说是芝麻饼。很显然胡食是随着胡姓民族进入敦煌地区而形成一种饮食风气,是敦煌地区胡化的一种表现。唐代中原饮食文化不仅仅接受西域及其外来文明,而且很快在各个阶层中普及开来。《唐语林校证》卷七记载马镇西马燧:“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忽为‘古楼子’。”这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肉馕。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经济结构为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归义军政权专门设置官马院管理驼马养牧、设置羊司管理羊的饲养放牧,官府、百姓都养羊等牲畜,就是每个寺院也养数量不等的羊。我们从记载看,寺院还用羊招待为寺院劳动的工匠以及看望寺院的官吏,寺院僧人经常食用“臛”一类东西。“臛”是肉汤一类的食品,经过研究也有用菜做成的藿,今天酒泉食用的特色饮食“胡锅”,是否就是敦煌文献记载的“臛”?不过寺院所养牧的羊的去向一直是敦煌饮食研究的一个谜。其次,晚唐五代归义军诸司机构中有酒司和官酒户,敦煌市场有酒行,从业人员除了汉人还有很多粟特人,他们开了很多酒店,造酒货卖招徕客人。制造的酒有麦酒、粟酒、粟麦酒、清酒、白醪、葡萄酒、胡酒等种类,根据我们研究当时敦煌已经能够制造高浓度的白酒。就是寺院也大量制造存放酒,甚至有的僧人开店买酒、到酒店饮酒。
(3)马的引进及其敦煌地区马文化
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首先是从马开始的。汉武帝取得河西地区建立河西四郡之后,着手经营西域,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以便取得大宛的汗血马。第一次出征不利,又以敦煌为基地修整,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征伐,最后以大宛贡献500匹的条件结束了战争。实际上这是一次争夺马种的战争,这次战争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河西地区成为中国古代马的生产基地,敦煌地区产生了很多关于马的优美传说,由此而产生敦煌地区的马文化。这里我们列举几例,第一是关于敦煌龙勒山的名称来源,《寿昌县地境》记载“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遗其衔勒,故名龙勒山。”根据中国人的传说,马六尺以上称之为龙,因此把行走速度很快的好马被称之为龙,所谓龙勒山就是传说马勒而得名的。第二是关于龙勒泉的传说,《寿昌县地境》记载“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得骏马,愍而放之。既至此泉,饮水鸣喷,辔衔落地,因以为名。”龙勒泉就在龙勒山下,龙勒山的传说应当与龙勒泉的传说是一致的。这些记载一个来自于周,一个来自于西汉,显然是后代附会武周政权所致。《敦煌地志》记载龙勒山因泉得名,龙勒泉是因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得骏马得名,那么龙勒山显然不可能因西周龙马传说得名。第三是龙堆泉,《寿昌县地境》记载:“昔有骏马,来至此泉,饮水嘶鸣,宛转回旋而去。今验池南有土堆,有似龙头,故号为龙堆泉。”第四是寿昌海,《沙州伊州地志》记载“屈曲周回一里,其深浅不测,汉得天马处也。”①《沙州地志》和《汉书·武帝纪》记载最为详细,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池中,作天马之歌。记载南阳暴利长遭刑屯田,见有野马奇异者常来渥洼池饮水,得以进献。为神异此马,说从渥洼池中出。第五是金鞍山,记载“经夏常有雪,山中有神祠,甚灵,人不敢近,每岁土主望祀,献骏马,驱入山中,稍近,立致雷电风雹之患。”①金鞍山经过考证就是龙勒山,②这种祭祀活动,显然与马有很大关系。归义军时期的《龙泉神剑歌》就是由金鞍山展开歌颂祥瑞的。在敦煌壁画有很多马的图案,河西地区出土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文物,如武威雷台出土的铜车马,还有其他墓葬出土的木马,乃至于有前凉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
敦煌地区中外文化交融碰撞的特征不仅仅体现在以上各个方面,而且在石窟艺术、音乐舞蹈、社会风气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外来文明融合到敦煌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产生了一种带有外来文明特征的新的文化特征。从音乐舞蹈上,所谓的胡腾舞③、胡旋舞在敦煌壁画中反映很多,很多净土图像反映天国或者净土境界,都有乐舞场面,所跳之舞基本上都是胡腾舞或者胡旋舞之类。敦煌文献记载到归义军时期敦煌有乐营使,④专门管理从事音乐舞蹈的音声等,布支出账记载作胡腾衣,可见胡腾舞在当时比较普遍。再从琵琶谱看西域来的乐谱在敦煌比较盛行;从石窟艺术方面来看,曹家样在敦煌地区非常流行,同时张家样、吴家样、周家样等都在敦煌壁画中有体现。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敦煌文献找到很多相应的证据,敦煌文献记载归义军时期向伊州、西州、于阗及甘州、南山等地派遣的使节中就有各类工匠,他们中很多与石窟开凿关系密切,这样的交往必然将敦煌地区的石窟艺术风格传播到其他地方,同时将其他各地的艺术风格传播到敦煌地区,促进敦煌地区石窟艺术的发展。
敦煌是中外交通道路的咽喉之地,外来文明通过敦煌传入中原地区,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敦煌传入西域地区,特别是到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更是这样。由于当时敦煌地区居民是胡汉羌回达怛等多民族居住区,居民结构复杂,由他们带来的中原、西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文化,在敦煌地区首先开始接触,碰撞交融,形成了接纳融汇各种文化为特色的敦煌文化。从总的趋势看晚唐五代丝绸之路是衰退了,但是由于归义军政权历任节度使的经营,出现一个区域发展的高峰时期。
(作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伊斯拉菲尔·玉苏甫 安尼瓦尔·哈斯木
新疆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根据现已掌握的考古资料,在昆仑山北麓的和田河、克里雅河、尼雅河、安迪尔河的河谷及上游地带,罗布淖尔荒漠、孔雀河下游河谷、楼兰故城周围等地均分布有许多细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而且时代延续的比较长。特别是从史前时期遗址在塔里木盆地分布较广的特点看,这里在当时应是古人类出没,采集,捕鱼,狩猎甚至进行简单农业生产的地域。这些因素导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之古代先民们历经数次的迁徙、融合与变迁之后,根据自己的文化底蕴在吸收与融合的基础上,较早就创造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中包括饮食文化。这些均为目前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所证实。因为在这些遗址除发现大量的石核、石球、石镞等石器外,还发现有陶器。谷物类食物的加工与肉食不同,必须要有加工的容器,而陶器的出现则表明当时可能出现了原始农业,同时,这无疑也是人类饮食习俗的形成与饮食结构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环节。
饮食习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进化与确立,与人类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能力,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反差有着密切关系。从塔里木盆地的情况看,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居民虽多,但他们同样也经历了从蒙昧状态时的进食方法到文明进食,结构搭配合理的历史阶段。为使人们对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饮食文化与饮食结构的形成,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与了解,本文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和我国历代文献典籍对其进行溯源。
一 秦汉以前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社会经济与饮食构成
西域由于地处四大文明的交汇处,所受到的文化影响与辐射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看,西域文明仍是由西域远古居民自己最早创造的,在当地土著文化基础上融合四大文明精华而形成的一种多元复合型地域文化。塔里木盆地作为上万年前就存有古人类活动的一个地区,这里所遗留的诸如:和田市南哈因达克以南约10公里的玉龙河右岸①;洛浦县东南约25公里的干河床②;民丰县南尼雅河两主源汇合点以北约15公里的纳格日哈纳西北的干河床③;尉犁县的辛格尔遗址④和喀什西南乌帕尔乡的乌帕尔遗址⑤,以及罗布淖尔周围一带大量反映史前文明的遗址与发现的石核、石锤、各种尖状器、刮削器、切割器、石斧、石刀、石镞、石磨盘、石磨棒及器形,以缸、瓮、壶、钵、碗、碟等为主的陶器残片和有被火烧硬并高出地面的灶址⑥等遗物,说明这里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通过这些,使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与他们用这种极简陋的生产工具过着采集、狩猎生活的现象有初步的透视。石磨盘与石磨棒以及陶器和灶址等的发现,表明当时除了发达的狩猎、捕鱼业与畜牧业外,已出现原始农业。人类的进食习惯也开始发生变化,谷类食品与肉食不同,它不能直接在火上烧烤,必须借助陶器来煮食。
当步入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后,这里的居民又创造出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兼营农业的农牧并重的史前文明。从孔雀河下游的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天山南麓的和硕辛塔拉、阿克苏喀拉玉尔衮和库车喀拉墩等遗址发掘的资料看,当时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居民,虽然出现了小规模的种植业,由于粗放经营,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仍然还是以狩猎、捕渔、采集和游牧为主,日常生活仍以肉类为主食,谷物只是附属食物,饮食结构显得相对单一,下面就考古发现做一些论证。
(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2年在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60公里的小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与发掘距今3800年左右的墓葬4座,获得大量各类珍贵文物。其中,发现最多的当属牛皮、牛头、羽饰、箭杆、木器、毛织物和皮革服饰。虽然在M1出土斗篷边缘捆扎小包内发现麦粒,在M2木雕人像身下、毛织斗篷内发现麦粒与粟粒,普遍随葬的草编篓内发现干结的食物,但没有发现陶器以及与农耕生产有关的生产工具①。从出土弓箭、皮革制品和木器、自地表采集的大量遗物看,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畜牧业与狩猎业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也食用小麦类粮食作物,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的补充。另外,2004~2005年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小河墓地再次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墓葬167座,除获得极为丰富的各类文物外,也获得了部分与饮食文化有关的资料。
(2)1979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发掘了一批距今3800年前后的墓葬,获得大量的遗物,其中,随葬品中以皮毛制品、草编小篓、牛角、角杯和木杯、木盆等居多,不见陶器。这一切表明他们的经济生活仍以畜牧业为主,饲养的牲畜主要是绵羊、山羊、牛和骆驼,日常吃、穿的主要生活资料均取自畜牧业。当时狩猎业居于重要位置,人们通过猎取马鹿、野羊、禽鸟,捞取河鱼来补充着日常生活。虽然他们也种植和食用小麦类粮食作物,但在日常生活中占的比重十分有限①。总体而言其饮食结构还是比较单一,这不仅与当时该地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社会生产低下有关,而且这种以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与罗布淖尔地区荒漠、半荒漠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有关系。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单位,先后于1985年、1989年、1996年和1998年在且末扎滚鲁克墓地进行了清理与发掘,其中一期文化年代距今约有3000年,随葬物多为木器、石器和陶器;距今约2700年的二期文化除了随葬大量的木器、石器、陶器、毛织物,少量的铜器与铁器外,该期墓葬发现有存在放置食物的习惯,主要是羊排骨和羊排骨串,面食较少。墓葬殉牲习俗,一般是羊头(山羊和绵羊)、肩胛骨、牛角、马头、马牙、马下颌和马肩胛骨、狐狸腿等②。从丰富的随葬品看,此时社会经济虽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居民日常生活仍然是以畜牧与狩猎为主,农耕经济没有得到发展,从而使当地居民的饮食结构也还是以肉食为主,粮食类作物占的比例不大。
从对秦汉以前各类遗址、墓葬的发掘清理,以及从中出土的文物与居住遗址的灶址来看,当时人们开始已步入定居的生活阶段,经营有农业,种植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和粟,但种植业的规模极为有限,因而畜牧业和狩猎、捕渔及采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占主要地位,这可从大量随葬的牛、羊、马、驼骨骼、皮毛及毛织物、弓箭等得到见证。至于人们的饮食构成,由于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古代居民在文化与经济形态上有许多共同点,所以人们的饮食主要是烹或烤制的牛、羊肉和各种乳制品,饮食结构相对单一。当然,从用于殉葬的马和骆驼的出现,可以看出马和骆驼与人们的关系较为密切,除了在放牧、狩猎、交通运输和战争中发挥作用外,应该说也开始将其列入了食物的范畴。罗布淖尔地区作为远古人类栖息与活动的重要场所,虽然较早就出现了原始农业,但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低,种植规模也极为有限,根本无法满足人们对饮食的需求,也无法改变人们的饮食结构,所以除了畜牧业,传统经济方式中的狩猎和采集,不仅是当时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还是人们食物重要的来源。
二 从游牧向农耕文化过渡时的饮食构成
西域原始文化带有多元的色彩,秦汉时起西域独特的文化结构已经成型。它大致以天山为界,形成两个相互依存,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在天山以南,凡有水源的地方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绿洲。这些绿洲不仅是当地人类生存繁衍之所,而且还构成了新疆古代农业区。汉代,是新疆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因为不仅使新疆正式划入汉朝版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中出现了“城郭之国”。当然,在秦汉之际,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的经济生活中,虽然畜牧经济仍为主要的经济生产形式和食物来源,畜牧的规模明显大于史前时期,但随着城市的出现,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来自中原地区的屯田士卒进入塔里木盆地周缘,汉族人民开始加入西域多民族大家庭的行列之中,自此中原地区的艺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等开始大量涌入。更重要的是,通过民族的迁徙、融合与发展,促使这里的农业经济也有了飞跃的发展。虽然秦汉时期当地的经济形态仍主要为畜牧业和狩猎业,但由于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方法和生产工具以及先进理念的传入,农业由史前时期的粗放式经营,逐渐开始向规模化的园圃式经营过渡,因而从秦汉时期开始农业经济在塔里木盆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所占比重明显增大。早在距今3000年左右,经昆仑山北麓,到天山南、北麓之山前、河谷台地地带,在广阔的地域内已经出现了种植业。步入秦汉以后,农业的崛兴改变了塔里木盆地居民单一的以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使居民饮食结构趋于完善。
(1)198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洛浦县西南14公里的山普拉墓地进行了发掘,获得了大量各类文物。在出土遗物中除有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外,还有粮食与食物。粮食种类有黍和大麦,在M05、M06、M07、M10、M16、M20和二号马坑中皆有发现。墓葬的粮食主要捆扎在长服的下摆衣角处,有的放在皮口袋或绢布口袋内。食物仅在M06和M20号墓中发现。M06出土一块黍饼,去壳很干净,基本呈粉状。出土时为圆形,饼厚0.25~0.5厘米。M20在尸体上身右侧一兽皮口袋内,内装6个圆饼和一些被加工过的黍粒,圆饼内掺麦壳,饼呈灰黑色,最大径6.5厘米、厚0.6~1厘米;最小径5厘米、厚1厘米,圆饼均为手工捏制。在M06出土一木钵中发现已干化的黍米粥,从M02中还
发现1个核桃。此外,山普拉墓地发现二座马坑,各埋一匹马。一号马坑的坑形保存不太好,但马保存完整,皮毛皆未完全腐烂。马毛色为黄色,葬式为侧身直肢,头向东,面向北。马身上盖有芦苇杆和树枝,额头上插有两根白色羽毛;二号马坑呈不规则“凸”字形,马坑竖穴。坑口距地表35厘米,坑底长241厘米,宽140~198厘米,深110厘米。马保存完好,上部盖有顺长的树枝条。马毛皮大部分都在,毛色呈黄色。葬式亦是侧身直肢,头向北,面向西。颈部和尾部有毛绳,马背上备有鞍具及配件①。从出土遗物看,经济方面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同时也有一定的园林和狩猎。
(2)1996年,且末扎滚鲁克墓地第三期文化墓葬中,除获得陶罐、陶壶、木盘、木碗、木箸、木耜、漆案、铜勺外,还发现食品与谷物。食品均置于漆案上面,有油炸的菊花饼、麻花、桃皮形小油饼、薄饼、葡萄干及连骨肉等,谷物与杂草、棉布一起出土②。
(3)1979年和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孔雀河下游老开屏东汉墓地和楼兰故城东郊两处高台墓地进行了发掘。这些墓葬出土的文物以木器为主,有各种木盆、木盘、木杯、钵、木勺和桶等。木盘是木器中的主要用器,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形制也较丰富,有长方形、椭圆形和圆形3种,均附木腿。这种木盘是当时主要食具。楼兰城郊B高地墓葬出土的木盘中,均见羊头、羊骨,老开屏墓地内也见羊骨。出土木盆与木盘中盛大量羊头、羊骨,这表明当时羊是饲养的主要牲畜,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食物品种①。同时,也说明当时楼兰王国的经济仍是以畜牧业为主。
(4)198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古队在楼兰故城进行考古调查时在孤台墓地清理墓葬两座,获得各类文物170件。其中出土的椭圆形和圆形木盘中均盛有羊头骨和羊骨②。
(5)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尼雅遗址考古调查中,采集和清理的遗物有1千余件,其中除牛羊颈栓、搅拌杆、木桶、铁镰刀、角杯和木碗、木杯等生活与生产器皿外,还有牛、羊、鹿、马和鸡骨等,皮毛有羊毛、骆驼毛、马皮、牛筋和猪鬃,谷物有麦和粟,并采集到一根较完整的麦穗③。此外,在这里还发现过青稞(燕麦)、糜谷、干羊肉、羊蹄、雁爪、干蔓菁等④。
上述这些资料不仅反映了秦至两汉时期塔里木盆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而且还可以看到,当地居民除了畜养羊等家畜之外,马、牛、骆驼等大牲畜的饲养也相应增多。当时,家畜中的羊始终是主体牲畜,羊肉仍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食物。占有羊的多少成为了人们显示财富多寡和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之一,墓葬中发现的整羊、羊头、羊蹄、羊骨、牛筋和殉葬的马匹,明显表明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以肉为食、以酪为浆的日常生活画面。据《汉书·西域传》:“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的记载以及出土的粮食作物、食品与葡萄等,同时也说明了内地种植的麻、菽、麦、稷、黍,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已开始种植。在畜牧业发展的同时,农业与园艺业亦开始发展,尤其是汉王朝派遣的屯田士兵从中原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水利工程技术,更会对塔里木盆地农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塔里木盆地是汉朝在西域屯田的一个重要基地,当时的屯田今天尚有残迹可寻,主要见于轮台、沙雅、若羌和楼兰遗址。驻兵屯田,既是开发建设边疆地区的一项经济措施,同时又是保障边疆安定的一项军事措施,因而汉王朝非常重视在那里的屯田事宜。东汉时期的犁耕、牛耕技术在屯田事务中广泛使用,优良品种不断引入,因此当时这里种植的粮食作物已大体与中原地区相同,在人们的饮食生活中,具有高产潜能的粟开始跃居首位,成为人们饮食构成中的主要粮食品种。同时,园艺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葡萄开始较广泛的种植。
尽管以天山为界,把新疆分成了两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但是不能说绿洲农业为主的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畜牧业不发达。《汉书·西域传》说:诸绿洲国家兼营农业和畜牧业。以农耕为主的国家有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龟兹、温宿、姑墨、焉耆、危须、尉犁等,以畜牧为主的国家有鄯善、若羌等国。这些国家不管是以农耕为主,还是以畜牧业为主,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看,两种经济形态是同时存在的。随着农业、畜牧业和园艺业的发展,当地居民的饮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进食习惯和饮食结构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三 农耕化促进了饮食构成的丰富与完善
汉以后,尤其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新疆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此时随着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畅通,相互往来的不断频繁,民族的迁徙与融合,各种文化的不断碰撞与交流,使得处于丝绸之路重要地段的塔里木盆地周边各绿洲得到高度发展与繁荣,民族文化由分散到聚合,形成异彩纷呈的多元民族文化。同时,经济形态也开始转入以农业和园艺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阶段。当然在发展与变迁过程中,长期以来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先民,历经迁徙、变化、繁衍生息、融合发展,不仅共同创造了辉耀千古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在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饮食构成。正因为塔里木盆地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汇聚与吸收了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人群的文化传统,并结合当地实情进行了必要的改进和提炼,从而在饮食种类和习惯等方面既存在差异,也有一定的共性。
从塔里木盆地周缘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和发现情况来看,历史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代居民们,在从事着狩猎、采集和游牧生活时期,基本是将肉类,特别是把饲养的羊作为了主要食物,而将谷类、豆类作物和各种水果作为了附属食品。人类社会步入农业文明进一步发达的历史阶段后,生活在农耕生产占主要位置的绿洲国家古代居民们,开始食用以粮食作物和蔬菜加工的各种食品,特别是将面食作为主要食物,蔬菜与水果的比重也开始增大,而畜牧业虽然也很发达,但肉食及奶制品却相应退居附属地位,合理的饮食结构开始确立。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和各种文字类文书的记述看,这个时期塔里木盆地居民饮食构成开始呈现多样化,膳食搭配亦趋于合理与科学,涵盖了农林牧之特点。
(1)粮食作物食品粮食作物包括“五谷”,加工后的食物一般泛称面食。面食是随着农业文明的产生,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发展,逐渐产生和丰富的。从新疆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所获资料来看,大约在公元前8000~2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或距今7000~6000年前,就出现了原始农业①。塔里木盆地作为较早步入农业文明的区域,因而除肉食外,粮食作物也较早就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食物。除《汉书·西域传》的记载,《魏书·西域传》同样有“(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疏勒)土多稻、粟、麻麦..”②。《北史·西域传》有焉耆“土田良沃,谷多稻、粟、菽、麦”③。《洛阳伽蓝记》卷5有“(朱居波)人们山居,五谷甚丰,食则面麦”之记述。由这些史料看,魏晋时期不少绿洲国家已基本改变了史前时期那种“以肉为粮,以酪为浆”的固有生活模式,在饮食构成中开始以粮食作物为主。丰富的考古资料更能对此问题给予足够的证实。楼兰、尼雅出土的汉文简牍保存着大量有关大麦、小麦、粟、米以及麻种植、食用等方面的记录。诸如:“禾一斛七斗六升给禀将尹宜部兵胡支鸾十二人,日食一斗二升起十月十一日尽十一月十日”①;“黑粟三斛六斗禀战车成辅,一人日食一斗二升起二月一尽卅日”②;“将张佥部见兵廿一人,小麦卅七亩已截廿九亩。禾一顷八十五亩溉廿亩莇九十亩”,“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小麦六十二亩溉五十亩,禾一顷七十亩莇五十亩溉五十亩”③等。同时期出土的佉卢文简牍中关于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种植与食用及灌溉等方面均有大量的记述。另外,对于粮食作物,在吐蕃文简牍中就有:“龙年,从种子农户口粮麦子中匀出半克..鲁古,口粮半克。种子一克四升,糌粑二升。分与拉列..价八升,后又十二升,从新谷中给觉卧赞青稞三克,送往若羌二克”④之记载。与文献相互对应的考古发掘资料也极为丰富。诸如:.
1980年,楼兰故城遗址内佛塔东面约30余米处,发现黄灿灿的粮食堆积,堆积层厚约70厘米、宽约100厘米,经鉴定确认为糜和裸大麦⑤;1999年,在汉晋时期的营盘墓地考古发掘时,从M8出土了3件圆形木碗,其中一件内盛羊头和羊肉,上面放有几层薄饼;另一件内盛有沙枣和形状不规则的饼等食物⑥;1958年,焉耆县唐王城清理发掘中发现房屋基址及粮仓遗迹,出土的谷物有小麦、谷子、高粱、胡麻以及磨的很细的面粉⑦。此外,在若羌县米兰古堡还发现有青稞籽实⑧。
(2)肉食制品在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的农业生产虽然得到高度发展,但是作为传统经济手段之一的畜牧业,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经济与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均将肉、奶子、奶皮子、奶疙瘩等作为主要食品,将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作为副食品来食用。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则基本都是将谷物、蔬菜和水果等农作物作为主要食物,将肉和奶制品作为副食来食用的。然而从这一时期的变化看,虽然人们开始大量食用以粮食作物和蔬菜加工的各种食品,特别是将面食作为了主要食物,但是由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畜牧区,以肉为食早已渗入当地居民的生活领域。因这种传统饮食习惯的因素,故肉食在此时不仅仍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更注重了精细处理,食用方法亦开始多样化。此时除传统的烤、煮法之外,对肉食的制作也有了许多创新。
(3)蔬菜、瓜果的种植与食用我国蔬菜瓜果的种植历史,文献上只能追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已经产生了专门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业。但从考古发现看,其历史则要比这早,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就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而言,蔬菜瓜果的栽培与食用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西域的园艺业已相当发展,塔里木盆地各国普遍种植葡萄、杏、核桃等,酿制葡萄酒成为重要的手工业。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园艺业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也就是说,由于汉代以后农业和林果业得到更大的发展因而使蔬菜与瓜果成为当时人们饮食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粮食作物而言,蔬菜和瓜果的遗存发现较少,特别是蔬菜,由于叶茎难以保存,故无实物出土,瓜果多数只为果核,其中发现较多者为葡萄。诸如: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葡萄园遗存②以及涉及葡萄园的佉卢文文书③。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遗址陆续发现葡萄园、葡萄藤以及与葡萄园有关的佉卢文文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共同尼雅遗址联合学术考察队在该遗址内的房屋遗存周围,发现大量的葡萄园遗存和残留的葡萄藤。尤其是分布于编号为95A2和95A7之房屋四周果园中的葡萄种植面积占有相当的比例。其中,编号为95A2中的葡萄园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o米,东西宽约30米,周围有篱笆墙,该葡萄园面积虽说较大,由于大部分已为流沙所掩埋,现所能见到的仅为东西方向的3排和北边的2排葡萄藤;编号为95A7中的葡萄园位于编号为93A24(N44)之西150米处,为至今所发现的葡萄园中面积最大者。其东西长122米,南北宽68.5米,葡萄藤呈东西向排列①。除此,在该遗址北边还发现了长50米,宽30米,四周围有篱笆墙的葡萄园遗址。此遗址现存有9行东西向排列的葡萄藤,其行距大约在2米之间,且每一株葡萄前均残留有用于搭葡萄架的木桩②。另外,从该遗址编号为A39-27的房屋侧房里,还发现了用葡萄藤编织的锅支架③。当然,葡萄在楼兰故城遗址、且末扎滚鲁克墓地、洛浦山普拉墓地等处也有发现,如: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尉犁县营盘汉晋时期墓地考古发掘时,从编号为99BYYM7和99BYYM66两座墓中发现了几串干葡萄④。
除发现大量实物、保存基本完整的葡萄园遗址外,还发现了大量有关葡萄园典当、租赁、买卖以及葡萄酒等方面的佉卢文简牍。其中1959年发现的一件,是“鄯善国精绝州居民苏耆耶、鸠那耶买葡萄园契约”⑤;1991年发现的内容涉及“应该提供贮藏的葡萄酒中有相当于15峰骆驼分的葡萄酒”;编号为91NA20的则涉及用于纳税的谷物和葡萄酒⑥。这些文献对于葡萄园的规模、面积,葡萄及葡萄制品的加工生产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记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葡萄在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变得愈发重要这一点,也给予了一定的反映。由于葡萄在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得到广泛的种植和食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商品化程度亦得到不断的发展。因而在当时人们除了鲜食外,还进行葡萄制品的加工。出土的佉卢文简牍中多见葡萄和葡萄酒字样,以及用于纳税和交换的记载来看,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居民普遍饮酒,而且酿酒的原料则为葡萄。
除了葡萄之外,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栽培和食用的水果种类还有很多,史料记载极为详实。其中成书于公元5世纪的《西京杂记》有:“瀚海梨,出瀚海地,耐寒而不枯”的记载。唐代高僧玄奘于公元7世纪所著《大唐西域记》有:“阿耆尼国,.引水为田。土宜糜、黍、香枣、葡萄、梨、柰(苹果之一种)诸果”;“屈支国..宜糜、麦,有粳稻,出葡萄、石榴,多梨、奈、桃、杏”之记述。同时,有部分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诸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中,在尼雅遗址、楼兰故城、洛浦山普拉墓地、且末扎滚鲁克墓地、营盘墓地、洛浦县阿克斯皮尔故城遗址和巴楚脱库孜沙来古城遗址均发现了杏、核桃壳、梨、苹果、枣、甜瓜籽、桃核、巴旦木、酸梅、桑树、沙枣树等①。虽然还有部分水果没有发现实物,但在出土的各类文字文书及文献典籍中却有记载。
除了尼雅遗址发现的干化蔓菁外,有关蔬菜方面的实物尚未发现,但这并不表明当地没有栽培和食用蔬菜。据史料记载看,张骞通西域之后,产自西域的胡麻、蚕豆、大蒜、洋葱、芫荽(香菜)、黄瓜、红花、胡萝卜和菠菜等农作物纷纷传入我国内地,这些信息都能表明古代新疆蔬菜栽培和食用情况。另外,从楼兰、尼雅等地出土的汉文、佉卢文和吐蕃文书,对当地的蔬菜种植与食用情况均有记述。诸如:《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有:“.加浇种菜,预作冬储”②之内容。米兰戍堡遗址出土的吐蕃文简牍中也有不少反映蔬菜种植方面的信息。如“农田长官多贡之佣奴农户,专种蔬菜的零星地”①。“在小罗布(nob-chun即鄯善)有八畦菜园子,沙弥菩提藏正在耕种时,突然命终”②和“青年与同行的二十人,平均每人食品..(四个)圆饼、发面饼、青菜、腌菜碗”,③。另外,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也有菜园子一词,即“qavlal■r”④。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不仅种植和食用蔬菜,而且也储存和腌制蔬菜。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认定,两汉以后,尤其是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应该是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饮食构成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时期。许多流传至今的食品都是在这个时期趋于完善、发展和定型。正是在这一时期,在人们的饮食生活中,传统的主粮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绿洲地带的居民逐步确立了以麦、粟等粮食为主食,以蔬菜、瓜果和一定量肉食为副食的饮食结构模式。由于此时正处于民族大融合与大发展阶段,故而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地居民的饮食文化,也经历了相互交流、学习和吸收借鉴的历史进程。因而在这一时期不仅初步形成了以蒸、煮、烤、煎、炸、烹等为基本手法,以色、香、味、形为终极效应,具有整体性、完美性和营养性的综合烹饪艺术,而且还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饮食体系与风味。同时,随着文化的交流,胡饼等食品,葡萄酒、奶酪等饮品与奶制品和葡萄、核桃、石榴、洋葱、大蒜、黄
瓜、香菜、菠菜、胡椒等果蔬香料经过丝绸之路纷纷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饮食文化,许多已深深扎根于中华饮食文化之中,成为我国传统饮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此外,在这个时期进一步成熟与成型乃至通过吸收、借鉴而发明创造的食品,至今影响依然至深至巨,历久不衰,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两汉以后塔里木盆地周缘诸绿洲之农业、畜牧业和林果业得到了全面均衡的发展,确立了以粮食作物为主,畜产品、瓜果和蔬菜为辅助食品的合理结构,因而他们所创立的饮食文化,在当地居民以及我国饮食文化史中无疑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总之,从考古发掘资料、文献记载和各种民族文字的古文字文书记述来看,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饮食构成经历了形成、发展和完善这样三个重要时期,而且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当地独特的特点。这里由于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故对于传播、吸收和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民族之间、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推进该地区文明化进程加快之同时,对饮食文化的发展变化也起着促进作用。因而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饮食文化作为新疆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独具特色的西域文化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同时,由于丰富了祖国的饮食文化宝库,对于进一步研究我国饮食文化史有着深远的意义。
(作者:新疆博物馆研究员)
龟兹文化的研究视域
仲高
如果从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新疆库车等地进行掠劫式考古发掘算起,龟兹历史文化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程了。龟兹历史文化研究最初主要在佛教石窟以及佛教壁画、雕塑的考证考释、龟兹古文字的解读、龟兹历史脉络的梳理等方面,且以考古物证与古代文献相互印证,有了二重证据之效。自此,龟兹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延伸,涉及龟兹佛教文化、雕塑和壁画艺术、龟兹乐舞、龟兹风俗、龟兹语文、龟兹文学、建筑和服饰文化、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龟兹文化研究方法也由专题研究和单一学科研究向综合性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跨出了一大步。龟兹历史文化研究最骄人的成果还是龟兹佛教文化的研究,而龟兹世俗文化研究就相对薄弱,不过,研究者都力图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域上进行新的尝试。但是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或中或外、或旧或新),都回避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在追求一种“客观”效果。这种超历史的纯客观研究忽略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这个问题就根本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在龟兹文化研究领域存在着诸多视域的融合,即历史与现实、客体与主体、自我与他者等等,但是根本的是研究者如何对待研究对象——龟兹文化的视域。我们应该努力扩展研究者的视野与传统的诸多视野的“视域融合”效应。由此可见,跨文化研究追求的应是“视域融合”的效应。对此,加达默尔认为:
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把这运用于思维着的意识,我们可以讲到视域的狭窄、视域的可能扩展以及新视域的开辟等等。..一个根本没有视域的人,就是一个不能充分登高远望的人,从而就是过高估价近在咫尺的东西的人。反之,“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东西,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观看。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①
这就是加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在此,理解者和解释者所要做的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之与其他视域融合。加达默尔进而认为:“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融合过程。”②这意味着把理解概念定义为一种“视域融合”,“成功地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本质的看法,从而使过去成为一种永无穷尽的意义可能性的源泉,而不是研究的消极对象”③。显然,加达默尔关于“视域融合”的见解对于诸如龟兹历史文化研究是有启迪意义的。其实,仔细推敲起来,有关龟兹文化研究的文献和考古物证还是捉襟见肘的。汉文及其他文种文献的有限记载和误记,考古物证方面的缺环都无形加大了研究的难度。更何况,当研究者面对历史“流传物”时,往往急功近利,认为只要掌握了充分的材料并佐之以正确的方法,就能对龟兹文化做出客观结论,并把这些铁定为外在的“事实”,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在龟兹文化研究领域,至少有以下一些做法遮蔽了我们的视域,其结果是,发现不了“问题”,也就不能理解事件的“意义”,结果使我们的研究成了“一种模仿自然科学的陈词滥调”(加达默尔语)。
一是,误认为龟兹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流传至今的僵死“物”,而凭研究者任意宰割。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有史时代的文化研究,也泛滥于史前文化研究。以龟兹乐舞研究为例,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乐舞图、苏巴什遗址出土舍利盒中的乐舞形象,以及汉文文献记载的龟兹乐舞等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是,从文献到文献,从图像到图像,永远无法看到龟兹舞舞动的韵律和听到龟兹乐美妙的旋律。单就客观对象而言,它们只是变成了纯客观的“物”或冷冰冰的“事实”(也根本未抓住“事实”)。这里抽取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其实,研究者与“流传物”之间应该是一种理解与对话的关系,“因为实质上,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眼中或者手中的东西是‘岩画’或‘陶器’,或者用这样的名称去称呼它们时,我们就已经为它赋予了意义”。①我们与历史“流传物”之间呈现出的意义,正是因为我们与龟兹历史文化之间建立了一种交互理解的关系。
二是,误以为以一种超然的客观化态度对待龟兹文化就抓住了龟兹历史文化的“历史事实”。这就存在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龟兹文化的“历史事实”?按照以往一些研究者的理解,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发掘“事实”是他们的职责,以致把历史叙述建立在这种“事实”基础上。这种穷究“历史事实”的做法几乎成了龟兹历史文化研究的“铁律”,以为只有这样才能触摸到西域历史文化的本源。但是,仔细推究起来,这种只对“历史事件”感兴趣的做法是要大打折扣的。且不说龟兹文化是一种逝去的历史文化,我们根本无法触摸到,就是我们赖以研究的文献史料也不过是前人的记载,考古发现提供的是一些历史遗留物而已,“所以,史学家也就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曾经发生过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简单说来,他接触的不是事件,而是证明曾经发生过这一事实的一个记载”①。更何况,记载龟兹历史文化的大多是汉文文献,并不是长期生活在西域的印欧语系语族的文献史料(考古发现表明这类文献也并不多)。即使根据考古发现的物证“复原”龟兹文化的情境(古人当时理解的意义)也是由研究者的中介才呈现出来的意义。这样就出现了第三个问题,对他者文化的理解问题。
三是,误以为像吐火罗人等“他者文化”的文本不是理解的对象。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澄清,首先是对文本的界定。以往的研究者对文本的理解十分狭窄,就是文献史料,且只有汉文文献史料,即汉文正史的记载。其实,广义的文本不仅包括一切文字的记载,还包括口传材料,以及非文字的文物、历史事件等,乃至历史本身。仅以文献史料为例,即使汉文文献对西域历史文化的记载自成体系,相对完整,但是误读,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也时有出现。其次,对古代西域诸民族文化的解读也存在一个语义转换的问题。且不说汉文文献对西域诸民族文化的记载多源于出使者、僧侣、商旅、旅行者的转述,已非第一手材料,就是亲历者的描述也存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语义转换和对话的问题。如若根本不懂塞语、吐火罗语等,那只有靠翻译了,而“翻译者必须克服语言之间的鸿沟,这一例证使得在解释者和本文之间起作用的并与谈话中的相互了解相一致的相互关系显得特别明显”②。当然,这种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因此,对作为文本的“包括整个世界历史本身”的理解,不仅仅是领悟作者意图和考证历史事实来解释文本的意义,而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龟兹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视域融合”效应呢?这是说,研究者自己的视域和作为传统文化的龟兹文化都有诸多视域,比如,研究者把考古发现的诸多器物是当作僵死之物,还是当作会说话的人与之对话,这就是不同的视域;而历史“流传物”也是一种会说话的文本。我们必须承认,研究者(主体)和研究对象(客体)之间是一种开放、交互和相互认识的关系。加达默尔说:“..谁想听取什么,谁就彻底是开放的。彼此相互隶属,同时意指彼此能够相互听取。”①既然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把龟兹文化仅仅当作客观之物,而应把它当作能够说话和提出问题的人,进行平等对话。在此,跨文化研究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同文化类型(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形态)之间的比附和比较,而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理解与对话,追求的是一种“视域融合”的效应。
当然,研究者与龟兹文化之间的对话中的“文化”是已经研究者理解后“给定”的文化,作为研究者理解的文化是“当今”意义的文化,是把文化当作一个整体和综合体去研究的。诚如泰勒所言:“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②笔者正是把龟兹文化视为具有功能性的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这是因为龟兹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复合体。比如,从文化形态看,它是包括绿洲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屯垦文化、城郭文化、宗教文化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就不能顾此失彼。另一方面,笔者的研究旨在追求一种整体效应,这不同于将各种文化形态平列或笼统观照,也非各种具体文化事项的分述。若是这样,就将龟兹文化割裂和肢解了,既反映不出文化的功能,也看不出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龟兹文化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视域融合”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主体和客体、历史和当下、自己和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如果要在龟兹文化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话,正需要这诸多视域之间进行沟通和对话。研究者的视域也在因时因地发生着变化。这本身就说明,超越方法论的局限,扩展视域融合效应是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获得无限广阔视野的必由之路。
在龟兹文化研究的诸多视域中,最主要的是研究者的视域。我们和研究对象的对话,我们倾听他(它)们的诉说,只能在研究者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中才能“听”出来,并发现其意义所在。那么,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视域融合”效应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是加达默尔指出的“效果历史”的原则。他认为: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大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①
加达默尔在“效果历史”中强调的是“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在此,“他者是这样强烈地通过我们自身而呈现出来”②。笔者在龟兹文化研究中不是简单、客观地陈述龟兹文化的各种形态,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而是在进行文化的寻根。比如龟兹文化的生态特征、史前遗物的精神内涵、龟兹文化的符号性特征、民俗生活的精神世界、宗教仪式的文化象征、意象世界的文化阐释等等,无一不是在理解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这些“他者”是通过解释者才呈现出来的。龟兹文化中总是存在许多我们已知和未知的领域,我们必须聆听这些历史的回音。这些回音来自不同的时空,它们不断向我们发问:我们来自何处?我们又向何处去?那些历史遗物,如彩陶、陶祖、塑像、石人、双兽纹铜带扣、马纹陶钵等,呈现在我们面前,看似无言,实则有声。龟兹人正在向我们诉说:我们为什么要制作它们?是如何制作的?这本身就蕴含了文化情境,需要我们仔细聆听,并予以回答。即使直到晚近还在西域普遍存在的拜火仪式,我们的理解也并非全面和深刻,对诸如它的文化象征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可以说是不绝于耳,等待我们的回答。可以这样说,“只有在这些众多的声音中,过去才表现出来”(加达默尔语)。在探究龟兹文化的过程中,效果历史总是在起作用。当然,诚如加达默尔所言:“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里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情况正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具有一种视域。..但是,我们必须也把自身一起带到这个其他的处境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了自我置入的意义。”①
就研究龟兹文化而言,把自身置入龟兹文化的情境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这种自身置入是一个理解的过程。理解就意味着对话与沟通,这样才能明了“他者”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和怎样想,怎样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龟兹文化的意义。
一般来说,研究者在“效果历史”中的理解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在与文本相遇时,理解者已经拥有由他的成见所决定的视域,这两个视域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尚不为理解者所知;第二,理解过程一旦开始,由于两个视域之间必有的差异,彼此会出现一种紧张关系,这时理解者便力图把两者区别开来,策划一个不同于他的视域的文本的视域;第三,当他这样做时,他仍是通过他的视域去区别和策划文本的视域的,所以在区别和策划的同时,他已把他自己的视域融入他所获得的文本的视域中了,因此,了解的结果必是两个视域的融合,被理解的文本的意义必定为文本和理解者所共有,其间的界限事实上不可明确区分。②
这正如加达默尔认为的,成见绝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的前提。正是通过成见,理解者才与传统有了联系,在此,传统也就成了被理解和解释过程中的“效果历史”。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如何消解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紧张,以达到“视域融合”的效应?按照和深刻,对诸如它的文化象征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可以说是不绝于耳,等待我们的回答。可以这样说,“只有在这些众多的声音中,过去才表现出来”(加达默尔语)。在探究龟兹文化的过程中,效果历史总是在起作用。当然,诚如加达默尔所言:“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里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情况正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具有一种视域。..但是,我们必须也把自身一起带到这个其他的处境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了自我置入的意义。”①
就研究龟兹文化而言,把自身置入龟兹文化的情境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这种自身置入是一个理解的过程。理解就意味着对话与沟通,这样才能明了“他者”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和怎样想,怎样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龟兹文化的意义。
一般来说,研究者在“效果历史”中的理解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在与文本相遇时,理解者已经拥有由他的成见所决定的视域,这两个视域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尚不为理解者所知;第二,理解过程一旦开始,由于两个视域之间必有的差异,彼此会出现一种紧张关系,这时理解者便力图把两者区别开来,策划一个不同于他的视域的文本的视域;第三,当他这样做时,他仍是通过他的视域去区别和策划文本的视域的,所以在区别和策划的同时,他已把他自己的视域融入他所获得的文本的视域中了,因此,了解的结果必是两个视域的融合,被理解的文本的意义必定为文本和理解者所共有,其间的界限事实上不可明确区分。②
这正如加达默尔认为的,成见绝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的前提。正是通过成见,理解者才与传统有了联系,在此,传统也就成了被理解和解释过程中的“效果历史”。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如何消解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紧张,以达到“视域融合”的效应?按照加达默尔的观点,那就是调解。调解意味着必须更改所说的东西,以便使这些说出来的东西保持为原来的东西。这是一个进入一种转换的活动过程,在这种活动中过去和当前不断地交互调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解释者的任务仅仅是一个复制过程。每一次新的解释都是在调解,旨在消解“紧张”中进入“效果历史”,这种视域正是文本和理解者共有的。
既然我们承认世界万物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而这一切又是和我们理解的意义与我们发生着关系,那么,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加达默尔关于“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一论断的深意了。在加达默尔看来,语言不是一种符号、一种工具、一种作为手段的装置,而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这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语言理解存在。就解释者和文本的关系而言,“所谓理解了一个文本,也就是理解者和文本在对话引导下就所谈对象取得了共同语言,也就是对象达于语言。正是在这共有的语言中,双方的视域实现了融合,理解者占有和推进了文本的效果历史”。①在此不妨举一例加以说明:《大唐西域记》一向被认为是记载龟兹文化的经典文本,我们正是通过玄奘的话语理解了一个个文化事件的意义,语言作为摹本,被描绘的原型才得以表达和表现。《大唐西域记》在“屈支国”条(即龟兹国)中记载了龟兹国的一种习俗:小孩出生后用木板押头,使头扁阔。对于这种“押头”,玄奘并没有说明是他亲眼所见还是听说的传闻,因此我们(理解者)并不是在与“事实”本身打交道,而是和这一事实的记载发生交互关系。当然,玄奘的记载已被在库车地区出土的唐代人头盖骨和佛教雕塑以及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所证实。我们获得的这个文本正是凭借书写的语言媒介得以流传,并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在理解者面前,理解者和被理解者正是在对话中取得了“共同语言”,也就实现了“视域融合”。“我们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是一个视域不断变化的过程,不仅是玄奘在向“押头”这样习俗的文本提出问题,我们作为理解者也在不断发问:这种“押头”习俗产生于何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习俗?“押头”仪式是怎样进行的?这就是所谓理解者和文本在对话引导下就所谈对象取得了共同语言,以达到新的“视域融合”。
当我们把龟兹文化当作一个文本(其实就是文本)理解时,它给了我们无限的空间,这不仅仅是因为龟兹文化还有许多未解和待解之谜需要我们破译,即使我们熟知的领域也有对意义的不同理解。这既非主观地“自话自说”和“先入为主”,也非客观地陈述历史,而是不断地超越文本的历史视域并与我们的视域相融合。
我们从“历史陈述”走向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的确走出了龟兹文化研究的关犍性一步,但我们仅仅把龟兹文化的跨文化研究当作一种方法论时,我们又走入了一个怪圈——把主体放在对某种方法的使用地位,而忽视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相互理解的关系。只有当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对话、相互理解并进入“视域融合”的境界,我们才能说,龟兹文化研究才真正跨出了一大步,这也是跨文化对话的真正意义。当然,并非所有的理解都是成功的,这里有误记、错位、偏差,这正如一次冒险旅行一样,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危险,不断修正目标,这样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近。龟兹文化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并理解的无限空间,我们对其意义的理解也是无限的。我们不要奢望在这种“视域融合”中会有什么终极结论,因为在理解中,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的视域不断扩大和更新,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在此,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在呈现着不尽的意义,我们追求的不正是这种效果吗?
不可否认,学术研究总会形成一些积习难改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一旦成为顽疾,就会遮蔽我们的视域,固步自封,囿于成说,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偏见就形成了。这种眼光不敞、自我封闭的思维定势作为个体存在也许无所谓,但一旦蔓延,对学术研究的伤害是致命的。不过,我们总能超越自我,在理解与对话中达到“视域融合”的境界。龟兹文化研究的缺憾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研究的领域,还是研究的方法都不能令人满意,至今我们还没有诸如《龟兹文化史》、《龟兹艺术史》之类文化史论方面的著述,即使如龟兹文化通论式著述也鲜能见到,更遑论新视域、新方法论方面启神益智的著述了。这与我们的眼光不敞有关呢,还是和我们的成见有关呢?或许都有。龟兹考古、龟兹佛教、龟兹语文研究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但我们明了如何界定龟兹文化吗?深入探讨过龟兹文化的特征、类型以及起源、演变等问题吗?我们在陶醉于龟兹佛教文化研究和龟兹历史考证取得的成果时,为什么不躬身自问我们对龟兹世俗文化,或者说是龟兹民间文化究竟研究了没有,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以缺乏文献史料和考古物证聊以自慰。假如我们把龟兹文化当作一个会说话的朋友,与他进行互动式的理解与对话,我们就不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了。现在该是我们不断拓展我们的视域,追求“视域融合”的跨文化研究的效应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使龟兹学研究真正成为世人瞩目的国际显学。
(作者: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于龟兹文化的几个问题
姚士宏
近年来,全国兴起地域文化研究热,龟兹文化研究更是持续升温。为此,我也想就龟兹文化的主要内容、地域范围以及研究思路等问题,谈一些肤浅认识。
一
龟兹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但它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它的核心与主流,却是佛教文化。这样说,并非因为我是搞佛教石窟的,有意要抬高它,而是历史事实。当然我说的佛教文化,可不全是印度那样的佛教文化。由于龟兹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富于创造的民族,因此,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它融入了龟兹本土原有文化和民族思想情感。可以说,这里的佛教文化,虽是伴随印度佛教传入而生成发展起来,但却是有着龟兹地域特色的佛教文化。我认为,现在说的龟兹文化,应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主要指历史上新疆库车地方政权——龟兹国存在时期的文化。龟兹何时立国,文献未载,不过,《汉书·西域传》已立有龟兹国专传,不仅记载了龟兹都城、人口、兵员、官职,并讲到它的疆界。从传文所记内容看,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之时,龟兹大体上已是完整意义的国家。如果以此算起,到9世纪中虽回鹘民族西迁,龟兹成为西州回鹘领地为止,以今库车为中心,辖境包括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温宿和巴楚等县市的龟兹国历经1000多年。所谓龟兹文化,指的应是这一时期内生息繁衍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当然,也还要算上西州回鹘前期,即龟兹回鹘这一段。龟兹回鹘虽是西州回鹘下属地方政权,但独立性较强,首领自称师子王。后期,龟兹回鹘逐渐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开始伊斯兰化。这以后,就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龟兹文化范畴。也就是说,我们所讨论是11世纪初以前的龟兹历史文化,这是前提。对龟兹文化的概念,我觉得,作一界定是有必要的,它可使我们的讨论有个共识基础。
众所周知,自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时任西域长史班超降服龟兹,废龟兹王尤利多,立龟兹质子白霸为龟兹王,从此,龟兹进入白氏王朝(即龟兹王之名的头一个字基本上都带一个白或帛字。近有学者指出,按惯例,西域诸国通常是王子或王弟为质子,白霸既为尤利多为龟兹王时入侍汉廷的质子,则尤利多与白霸应属同一氏族,亦为白姓龟兹王,龟兹白氏王朝至迟始于龟兹王白建,而这里仍按传统说法叙述)。
白氏王朝有两个突出方面:一是统治龟兹时间长。从白霸开始,一直延续到8世纪末(唐贞元四、五年间,公元788~789年)悟空由印度回国途经龟兹时在位的龟兹王白环,长达近七百年。如此稳定的王朝,出现在当时民族迁徙流动性大、王朝更迭频繁的西域、中亚地区难能可贵,在我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二是白氏王朝历代诸王大多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佛教传入龟兹究竟发生在白氏王朝建立以前,还是在之后,暂且不论,但从文献记载看,他们对佛法的渴求,对高僧(包括外地来龟兹高僧)的敬重,今天仍感到他们那份敬法重人的挚诚。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用习惯的宗教标准作评判,不能完全看作是宗教狂热,或者认为是要利用佛教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理应回归到当时龟兹社会现实来分析考虑。我以为,龟兹白氏王朝诸王带头崇尚佛教,是出于对佛教文化的仰慕,是对当时一种崭新文化的追求。因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以宗教为其表征的。这样认识是否恰当,还可探讨,但在他们倡导和影响之下,龟兹境内佛教长盛不衰,佛教文化空前繁荣。这不仅文献有载,如今遗存在库车、拜城一带众多佛教寺址、石窟,便是当年龟兹佛教兴盛的明证。龟兹回鹘在脱离西州回鹘、归附喀喇汗王朝前,同样信奉佛教,程度虽不及白氏王朝统治时期那样鼎盛,但其文化仍是以佛教文化为主,开凿在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时期的窟,就是证明。在佛教盛行的同时,龟兹也曾有其他宗教流传,如祆教,在龟兹就建有祭祀场所——天祠。也发现有用龟兹文书写的摩尼教赞美诗卷子。在龟兹文化形成当中,亦吸收融汇了各种外来文化,尤其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显示出多元文化的品格,这从龟兹石窟壁画上即可强烈感受到。尽管龟兹文化包含有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内容,异彩纷呈,错综复杂,但佛教始终占据主导地拉,佛教文化无疑是龟兹的主流文化,是龟兹文化的基本形态。这样认为,也许有些过于绝对,但至少从目前揭示的龟兹文化的主要内容来看是这样。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也是一种文化最显著的特征。龟兹为多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流行过多种民族语言文字。龟兹又是中原王朝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汉语言文字曾相当通行,至今还能看到当年用汉文书写的官府文书、借贷契约和摩崖石刻,这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龟兹与内地密切的政治关系。然而,20世纪初以来,经中外语言学家通过研究从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收集到的古文字材料发现,这一带最为通用的语言却是吐火罗语。这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分为两种方言。一种分布于高昌、焉耆等地,称作甲种吐火罗语或焉耆语,记录的全部是佛典,特别是有关弥勒的经典很多。另一种则限于龟兹,称作乙种吐火罗语或龟兹语。记录的内容除佛典外,还有世俗文书。虽然焉耆—龟兹语属于吐火罗语甲乙两种方言,但表述这种语言的文字,则是借用印度婆罗谜字母书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记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就是指婆罗谜字母而言。龟兹语即是借用印度婆罗谜文字,显然是伴随佛教而输入龟兹的。熟识情况的人都知道,龟兹佛教与印度贵霜王朝关系密切。20世纪初,在印度马土腊曾出土一尊迦腻色迦雕像,并有用婆罗谜字体镌刻的铭文。而类似用婆罗谜字母拼写自左到右横行书写的龟兹文题记,在龟兹石窟壁画上为数不少,有的时间早到4世纪,这说明,龟兹语文极有可能在佛教传入龟兹伊始即输入龟兹。库木吐喇石窟中的龟兹回鹘窟壁画榜题多用龟兹文、汉文和回鹘文三种文字合壁书写,表明有龟兹回鹘时期,虽然龟兹人种、语言逐渐回鹘化,但龟兹语文仍是通用的语言文字。岁月沧桑,龟兹语文这种古老语言文字虽已在民族融合中消失,无人使用,但应成为我们不可忘却的文化记忆。我国早期汉译佛经有相当部分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由龟兹语文本转译过来,因此,它在佛教传播上作出过贡献,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尤为重要的,它作为龟兹文化的一种载体,为我们记录、保存了大量有关龟兹文化的历史信息,它的学术意义不亚于龟兹石窟壁画。
龟兹乐舞是龟兹文化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也是历年论文著作述介得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内容,几乎成为龟兹文化的标志和代名词。然而龟兹乐舞,是在龟兹本地音乐舞蹈基础上,吸取印度、波斯和中原乐舞长处,尤其是印度乐舞长处而创造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乐舞体系。这自然亦是伴随佛教传入龟兹而逐渐形成完备的。
其他如文学、戏剧、美术也都渗透着佛教文化。尤其是作为龟兹国艺的雕塑、绘画,更是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佛教的传入,使龟兹文化思想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动了龟兹社会发展进程。没有佛教的传人,龟兹不可能如玄奘赞誉那样“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著称于西域;龟兹乐舞也不可能登上隋唐宫廷乐舞的殿堂,风靡中原大地;龟兹更不可能由一个城邦国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国,至今仍受到世人的关注。总之,佛教的传入,使龟兹文化经历一次重构过程,重构就是发展,对龟兹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
曾有研究者谈到龟兹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问题,认为龟兹文化的精神实质就是开放、兼容。的确是这样。龟兹为西域重镇,又位于丝绸之路要道,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这样的地理、人文环境,必然使龟兹文化具有开放、兼容的优势,构成了龟兹文化的一大特色。龟兹文化即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这正是龟兹文化独具魅力和吸引人之处。我们研究龟兹文化,就是要重视发掘其中的积极元素,古为今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服务。也许是巧合,龟兹文化的这种优势、特色,恰恰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佛教自传世2500多年来,一向以和平方式传播,从不用武力或别的什么手段强制别人信仰。也没有排他性,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保有开放接纳的姿态,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少思想禁锢、最有涵容人格精神的一种宗教。而这正是佛教文化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很难想象,若不是佛教的兴盛,佛教文化的浸润,龟兹文化怎能如此繁荣昌盛,为我们留下如此优美的石窟壁画!
二
龟兹文化,从文化类型上说,虽是以龟兹国之名命名的一种地域文化,它的核心区域在龟兹,但它的地域范围不应限于龟兹,即今阿克苏地区,还应包括焉耆、疏勒,也就是整个塔里木盆地北道沿线诸国,即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地区。这样说,并非有意夸大龟兹文化的区域空间,事实根据是不仅因为焉耆、疏勒毗邻龟兹,地域相连,最主要是焉耆、疏勒与龟兹在历史上皆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同属于小乘佛教文化圈带。只要翻阅一个我国三位不同时期西行求法僧行记,即东晋法显《佛国记》、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即可明了。他们都是经西域即今新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前往印度或返回中原内地。在他们的行记里,对南北两道沿线佛教信仰情况均有明确记述。
法显于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后秦弘始元年)从长安出发,次年抵达鄯善(若羌地区),然后转向西北往乌夷(焉耆),再折向西南到于阗,经子合(叶城)、于摩(叶城西南)和竭叉(疏勒,一说塔什库尔干)等国,西越葱岭,于公元402年(东晋元兴元年、后秦弘始三年)进入印度北境。他在《佛国记》里对所经之地佛教,除于摩国外,皆有记述。
鄯善国:
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乌夷国:
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
于阗国:
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
子合国:
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
竭叉国:
有千余僧,尽小乘学。
法显虽未到龟兹,没有记载龟兹情况,但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记载,4世纪中叶前后,龟兹佛教已相当兴盛,尽管大、小乘都有流传,但统辖龟兹佛教领袖佛图舌弥为小乘阿含师,足证龟兹佛教是以小乘为主。从法显所记可以清楚看到,5世纪初(实际年代肯定比这要早),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于阗、子合和北道的焉耆、疏勒等国,虽皆是佛教国家,并各有特点,然而南北两道佛教情况却是泾渭分明。南道于阗一带主要流传大乘佛教,北道沿线诸国则同龟兹,主要信奉小乘佛教。当时形成两个不同的佛教文化区域,即南道以于阗为中心的大乘佛教文化圈带和北道以龟兹为中心的小乘佛教文化圈带。
玄奘于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一说公元639年,唐贞观三年)西行印度求法,途经塔里木盆地北道,归程东越葱岭,从朅盘陀行进到乌铩,再北行到佉沙,然后转向斫句迦,经南道返回长安。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一和卷十二分别记述了阿耆尼(焉耆)、屈支(龟兹)、跋禄迦(姑墨,今阿克苏)、朅盘陀(塔什库尔干)、乌铩(莎车)、佉沙(疏勒)、斫句迦(即法显《佛国记》所作子合国)和瞿萨旦那(于阗)等地佛教情况。由于玄奘西行印度求法来回皆取道西域,南北两道主要城邦国都记到,并且更为翔实和具体。
阿耆尼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屈支国:
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
跋禄迦国:
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伽蓝数十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朅盘陀国:
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乌铩国:
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习学小乘教一切有部。
佉沙国:
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淳信佛法,勤营福利。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斫句迦国:
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淳信三宝,好乐福利。伽蓝数十,毁坏已多。僧徒百余人,习学大乘教。
瞿萨旦那国:
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慧超为朝鲜古国新罗人,赴唐留学僧,也加入当时我国掀起的西行求法热潮,先循海路前往印度(具体时间不明),于公元727年(唐开元十五年)经西域返回内地。他在《往五天竺国传》里对疏勒、于阗、龟兹(安西)和焉耆佛教也作了记述,情况一如法显、玄奘所记,这里不再详细引述。
玄奘、慧超所记分别是7世纪初和8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佛教情况,与法显记之5世纪初相比,虽然南道大乘佛教势力明显削弱,如于阗,尽管这时境内佛寺尚有百余所,可僧徒已从数万减至五千人。子合尤甚,大乘僧由千余减至百余人,近乎衰亡。相对于南道而言,北道小乘佛教却大为增盛,特别是疏勒,小乘僧由过去千余人增至万余人。这种大、小乘之间的消长形势,并未根本改变南北两道佛教基本格局,依旧是:以于阗为中心的南道流传大乘佛教,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信奉小乘佛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玄奘在记述中第一次明确指出北道信奉的小乘佛教是为说一切有部,并以文献形式记录下来,使我们对龟兹及其周边地区佛教文化的部派属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通过玄奘、慧超所记也看到,北道沿线诸国,至迟从法显时代5世纪初以来,一直坚持传统的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信仰,在经历多个世纪后,丝毫没有任何变化。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诸国,在佛教文化上,早已形成一个共同的比较稳定的区域,即一个在我国唯一的以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为主体的佛教文化区域,一个比较特殊的与我国其他地区(包括于阗在内)有所不同的佛教文化区域。
正是因为北道沿线国家皆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同属于小乘佛教文化圈带,因此,焉耆、疏勒与龟兹在文化上相同点很多。焉耆与龟兹两地居民不仅为同一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而且在风俗、婚姻、丧葬、物产等方面也大致相同。焉耆与龟兹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就连玄奘记述两地佛教时所使用的词语亦基本相同。疏勒与龟兹在文化上的关系,尽管文献记载没有那么明显,但仅从玄奘所记看,两地相同地方仍有例可举。如语言文字,虽然疏勒与朅盘陀、乌铩比较接近,与龟兹略异,但也是“取则印度”,想必是会通的。僧人则更不是问题。法显在《佛国记》讲到位于南北两道交汇之处的鄯善国时说:“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此(指佛教盛行),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习天竺书、天竺语。”这就是说,西域僧人皆通用梵文,不存在语言文字障阻。在佛事方面,所谓“勤营福利”,“不究其理,多讽其文”,即是指疏勒佛教偏尚修福,追求功利,重视诵读经文,不太深究其中义理,以及持戒较严,却不戒荤腥,食三净肉,等等,与玄奘记龟兹“尚拘渐教,食三净肉。洁清耽玩,人以功竞”相一致,保持了早期佛教的一些特征。特别是生活习俗上,玄奘记龟兹与疏勒两地流行一种“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的奇特做法,大概是在小孩出生后便用木板挤压头颅,使头部扁平。这种人工变形头颅的生活习俗,是受外部文化影响,还是源自本地?是融纳了原始自然宗教的遗绪,还是有着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文化背景?目前尚难论定,但流行于龟兹与疏勒两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是文化心理认同的典型表现。总而言之,尽管焉耆、疏勒与龟兹在政治上不相统属,还时起纷争,但在文化上确实属于一个体系,一个以龟兹为主的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文化体系。学术界在论述西域佛教文化分野时,总是划分成于阗、龟兹和高昌三个区域文化单元,而把焉耆、疏勒与龟兹视为一个区域文化单元,正是这个道理。因此,要进一步丰富我们对龟兹文化的认识,深化对龟兹文化的研究,全面揭示龟兹文化蕴含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就有必要把整个北道沿线地区甚至更大的范围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
三
以上概述了龟兹文化主要内容是佛教文化,龟兹佛教文化主要属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文化以及地域范围,下面再就龟兹佛教文化研究的思路问题,主要是如何看待龟兹大乘佛教和玄奘关于龟兹及周边国家盛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这样两个问题。
据《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收录的《鸠摩罗什传》记载,4世纪中叶,鸠摩罗什由小乘改宗大乘,曾在龟兹大力弘扬大乘佛教。从传文看,声势影响都不小。实际情况是否确如传文描写的那样,需要综合分析。因为这两部传文皆出自内地僧史学家之手,他们偏爱大乘佛教,在行文中不免会加进溢美之词,作些渲染。即使讲的全是实情,也不难看出,尽管罗什大力弘扬,龟兹大乘佛教始终只是停留在龟兹上层社会层面,只是在以龟兹王室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小圈子里流传。佛寺也仅限于罗什居住的王新僧伽蓝(王新寺),寺僧仅有90,在龟兹僧团(当时龟兹僧有1万余人)中所占比例很小,成员估计大多来自王族子弟。可以这样说,龟兹大乘佛教,仅是龟兹王室贵族的佛教,与平民百姓有一定距离。由于缺乏群众基础,随着前秦苻坚派遣吕光率军伐龟兹及焉耆诸国,罗什被劫往凉州,失去了代表人物,龟兹大乘佛教很快便归于沉寂。它对龟兹的影响,包括石窟造像,却很有限,不可估计过高,更谈不上发生龟兹佛教改宗问题。6世纪末,从文献上看,确有西来大乘僧在龟兹弘法,在位龟兹王透溢出对大乘僧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但大乘僧讲的皆是大乘人门性质的内容,龟兹王对大乘佛教仍处于尚未精深阶段,仅是一位诚笃之士而已,因此也很难说6世纪后期龟兹大乘佛教称盛。7世纪后,随着唐王朝重新统一西域,龟兹与中原内地关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迁居龟兹,在中原佛教影响下,龟兹大乘佛教重又活跃起来,库木吐喇石窟中的一批汉风窟便受敦煌壁画深刻影响,而阿艾石窟简直就是敦煌壁画的翻版,属于典型的中原大乘佛教回流龟兹的例证。似如慧超所记,仅是“汉僧行大乘法”,广大民族僧众仍是信奉小乘学说一切有部。正因如此,在龟兹石窟,特别是克孜尔石窟,壁画集中而具体地绘出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特有题材,形象地为我们诠释了小乘有部思想内容。就现存佛教遗迹看,无论是在佛教老家印度,还是我国内地,都是不可多见的。因此,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不仅开凿年代早,在我国石窟史上具有追本溯源意义,而且更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佛学大师玄奘在西行印度求法前,在国内即已遍参名师,穷尽各家学说。在西行求经的17年时间里,接触了当时西域、中亚和印度各地包括说一切有部在内的大、小乘各种派别,观察细致周详。回国后又亲自译出说一切有部论藏中的《异部宗轮论》、《法蕴足论》、《发智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和《顺正理论》等论书。尽人皆知,说一切有部虽是小乘佛教众多部派之一,然而却是思想理论最为丰富、势力与影响较大的一派,主要流传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和迦湿弥罗地区,有自己的经律论三藏。经藏同别的部派一样,以四部阿含经(《长》、《中》、《杂》和《增一》)为根本经典,只是次第有异,将《杂阿含经》置于首位。律藏有两种:一是《十诵律》,主要是在罽宾流传的较为原始的一种律本。另一种即《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包括诸事)。虽然结构、内容与《十诵律》差别不大,但增加不少本生、比喻故事,还掺杂有佛传内容,卷帙也相应增加,因而被称作有部律广本,称《十诵律》为略本。论藏,即是对阐释佛经义理论书的总称,又作《阿毗达磨》、《阿毗昙》、《毗昙》,其论书主要就是上面提到玄奘译出的那些。因为说一切有部最重论藏,喜兴造论释经,不仅为我们留下为数众多的理论著作,而其学说思想就体现在这些论书之中。这一点,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说疏勒僧徒“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来看,从慧立、彦琮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在龟兹参访阿奢理贰伽蓝时,该寺住持(也是当时龟兹佛门领袖)木叉毱多特意向玄奘推荐“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来看,都反映出说一切有部重视论藏情况。玄奘这里说的《毗婆沙》,即《大毗婆沙论》,全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俱舍》,即《俱舍论》,全称《阿毗达磨俱舍论》;《杂心》,即《杂阿毗昙心论》,均为说一切有部3部重要论书。尤其是《毗婆沙》,系统总结论述了说一切有部学说的基本理论,地位最突出,被奉为圭臬。玄奘不仅译出《毗婆沙》,而且翻译了有部几乎所有大论(玄奘所以花大力译出有部论书,恐怕也是考虑到这些论书思想丰富性),应该说,玄奘对有部学说思想深有研究,对有部形成、发展、演变和流传情况不可谓不知,他对龟兹及周边地区信奉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记述是客观可信的。玄奘在记述上述地区情况时,除明确指出是“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外,并且都说到使用的语言文字,可见语言文字之于文化上的意义。而这已从这一带发现的焉耆—龟兹文写本得到认证,证实玄奘的观察是正确的。这也足以说明玄奘记述龟兹及周边流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可信度。在这里,玄奘的记述,不仅仅指出龟兹佛教文化部派属性问题,实为我们研究龟兹佛教文化,解读龟兹石窟壁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思路。在打好历史文献基础的同时,认真研读一下有部经律论三藏,尤其是像《大毗婆沙论》这样的论书,看看究竟说了些什么,是怎样说的,尽可能地掌握有部思想理论和学说主张,弄清一些基本概念,也许会使我们在龟兹佛教文化研究中少走许多弯路,取得更大成果。
(作者:江苏省常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
佛教初传龟兹新考
薛宗正
关于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有两种重要说法。一为《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说,二是西汉武帝时期说,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见解,论述如下:
(一)《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中有如下一段偈颂,兹引录如下:
阿育王闻,喜庆欢悦,和颜悦色,告耶奢曰,“吾获大利,其德实显,法益王子,以理治化,率以礼禁,导以恩和,人民之类,莫不戴奉,今当分此,阎浮利地,吾取一分,一分赐子,使我法益,长生寿考,治化人民,如今无异,新头河表,至娑伽国,干陀越城,乌特村聚、剑浮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至于秦土,此阎浮半,赐与法益,纲理生民,垂名后世。
据此,安息、康居、乌孙、龟兹、于阗,乃至“秦土”即我国内地,都已被阿育王赐予其子法益,龟兹、乌孙国名也赫然列入法益受赐领土之内,其说若成立,则龟兹早在阿育王时期就已有佛教传布。案今传《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并非梵文原本,而是前秦苻坚时期印度僧人昙摩难提的译本。参稽《汉书·乌孙传》,乌孙建国始于猎骄靡,上距阿育王时代十分遥远,时间不会早于汉初。足证这一记载必定出自后世僧人自炫性追述,并非信史。其说不能成立。
(二)公元前2世纪说。德籍华人刘茂才始创此说,原文未见,陈世良先生据此发挥①,证据是《梁书·刘之遴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前109年),龟兹国献。”陈先生一再强调这一记载并非孤证,我细查古籍,果然如此,《南史·刘之遴传》也有记载,文字全同,又见于《册府元龟》卷928总录部·好尚条,文字仅略有出入②。并援引《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③所记“大法流此(指龟兹)五百余年”云云,以为佐证。以《比丘尼戒本》译为汉本的晋武帝时期上推五百余年,时间更早于汉武帝时期。其说若成立,则龟兹佛教至迟汉武帝之世已经传入。我初治唐史,近年来逐渐对汉史也初有涉猎,开始对此说发生怀疑,理由是:
(1)公元前2世纪汉与匈奴全面战争爆发之前,西域诸国本臣于匈奴,汉文帝前四年(前176年)匈奴单于遣右贤王率兵西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④,龟兹必包括在此西域二十六国范围之内。早自文帝前四年(前176年)就已臣属匈奴,同汉朝并无任何朝贡关系,西域诸国只知有秦,不知有汉⑤,即使张骞两使西域之后,司马迁据其见闻编写成书的《汉书·大宛列传》中仍无关于龟兹的任何记载,说明碛口丝道,封闭不通,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诸国同汉朝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朝贡关系,直至绛宾之父在位时期犹在奉行亲匈奴政策,所谓元封二年向汉朝贡献佛教法器云云,极少可能。
(2)汉开西域始于元封三年(前108年)赵破奴进军姑师、楼兰之役,《汉书·西域传》记云:
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此役《资治通鉴》卷21系于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十二月。传文中明确记载此前姑师、楼兰受匈奴指使,阻塞碛口,汉与匈奴之间正剑拔弩张,丝路不通,战争一触即发。龟兹偏于此年贡献澡灌,更是绝无可能。
(3)更蹊跷的是这个佛教用器上面居然有汉字铸成的元封二年字样,显然是汉人工匠所为。而当时连汉商出入西域,也属禁绝,龟兹国内根本不可能存在汉人工匠。自东汉末年起,伴随着今、古经学之争,仿古、造古之风盛行,出现了多次伪造古文经的案件,晋鼎倾覆于八王内争,五胡入侵的兵戈乱世,司马氏王室仓皇渡江,南朝真正皇家珍宝已为数无多,这个龟兹澡灌即使存在,也应是宫中珍品,何能流落民间,出现于江南,刘之遴这件收购自民间的皇家法器不可排除其造伪嫌疑。以此为证,未必可信。
(4)《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与《比丘尼戒本》并非完全一回事,在佛典《出三藏记集》中此二书别立名目,《比丘尼戒本》又作《十诵律比丘尼戒本》,总一卷,明确记载是佛教正宗戒典《十诵律》中所设约束比丘尼的律条,今传《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则乃晋武帝时期汉译者所写序言,序中所记“大法流此(指龟兹)五百余年”云云,分明是后世译者口气。自炫其弘法历史悠久,乃是佛教徒的共同心理,同样不足成为科学论据。
(5)佛教是印度文化传播的载体,伴随着佛教的传布必定出现印度音乐、美术的大发展。西汉时期的龟兹音乐舞蹈都非常落后,尚未呈现任何佛教传入的迹象。史载率先归汉的龟兹王是汉昭帝时期继位的绛宾,其父追随匈奴,曾杀害率领汉军屯田于轮台的校尉、扜弥太子赖丹。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长罗侯常惠奉命赴乌孙,取道龟兹,为赖丹复仇,其时绛宾已继位,缚送始建言杀赖丹之龟兹贵族姑翼迎降①,自此绛宾全力附汉,为此,联姻解忧公主之女弟史,偕同弟史一起入朝长安,全面引入以钟鼓琴瑟为代表的汉朝宫廷雅乐,还不会演奏,说明龟兹音乐、舞蹈原极落后,这与以“管弦伎乐特善诸国②”的佛邦龟兹判若两国。崔鸿《十六国春秋》卷73记前凉张重华在位之“永和四年(348年)天竺国重驿(译)来贡,其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昙、铜钹等九部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这是印度佛教音乐传入我国的最初记录,其乐器组合同后世盛行的龟兹乐非常类似,可见印度佛教音乐乃是龟兹乐舞形成的真正源头。其时已为两晋交替之世,足以说明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绝不会早至西汉中期,最早也只能追溯至汉、晋交替之世。
由于文献无征,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难于准确判定其具体年代,只能推断其大致时间段。主要根据是:
(1)佛教的传播路线必以龟兹所在的地理位置为转移。西域佛教属于陆路扩散的北传佛教,至迟公元前1~2世纪时期,世界佛教已形成为两大中心,一是作为印度本土佛教直接延续的迦湿弥罗(克什米尔)。二是中亚的贵霜王朝。位于昆仑山北麓、独擅地理形胜的于阗同迦湿弥罗(克什米尔)仅隔一山,又有乌弋山离道相连,即今之巴基斯坦的洪札河谷道。于阗佛教的源头必直接渊源于迦湿弥罗,汉文史料《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和藏文史料《于阗教法记》共同印证了这一事实,皆明确记载最早来于阗弘法的高僧名毗卢折那(Vairoca-na,意为遍照)①。最早弘法的地点是距于阗王都不远的杏园,即藏文载籍中的杂沐尔玛局里之园。最早皈依佛教的于阗王名Vijayassmb-hava,法名普胜生。最早兴建的佛寺名赞摩寺。于阗塞人居民同北印度释迦种语言相近,可以直接听法,无须翻译,因而佛教迅速在于阗传布开来。看来,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绝不能更早于于阗,而只能更迟。
西域佛教的第二大策源地乃是中亚的贵霜王朝。龟兹距北印度远而距贵霜近,只能传自中亚贵霜,而龟兹与贵霜之间又隔有疏勒,因此,龟兹佛教传入的时间不但晚于昆仑山北麓的于阗,还必定晚于同贵霜直接毗邻的疏勒,易言之,龟兹佛教还未必是中亚贵霜的直接正传,而必是疏勒佛教东传的历史产物。臣磐(?~170年)则是疏勒佛教的最早倡导者与护法王,国王安国的舅父。汉安帝元初三年(116年)疏勒国内部发生政争,臣磐被国王安国入质于月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二世(78~120年在位),率先皈依佛教。《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贵霜名王迦腻色迦王在位时期(78~120年)曾送疏勒质子“冬居印度诸国,夏居犍陀罗国”学习佛法,还有史料说明这位质子曾在迦毕试国捐资修建了小乘佛寺沙落迦寺,这个“沙落迦”明明就是疏勒的别译,可见这位在迦腻色迦王在位时期皈依佛教的疏勒质子应当就是臣磐。安国卒,无子,贵霜遣兵护送臣磐返国为王,臣磐继承疏勒王位之后大力倡导佛法,定为国教。有人推测,今喀什著名的三仙洞应即臣磐在位或稍后时期开凿的一座石窟寺。随同佛教信仰一起传入疏勒的还有贵霜王朝先进的军政管理制度,因而很快国富兵强,从于阗手中夺回了莎车,独立称雄于喀什噶尔绿洲,国势日盛。龟兹乃疏勒东邻,必定受到了重大影响,佛教初传龟兹或即发生此时。永建二年(127年)遣使贡于汉,顺帝册立为大都尉,因于永建五年(130年)送侍子于汉以为质。阳嘉二年(133年)遣使贡狮子、封牛。阳嘉元年(132年)受敦煌太守徐由征召,发兵二万攻讨檀灭扜弥国的于阗放前,破之,复置扜弥国,扶立成国为扜弥王。西域诸国的传统信仰本是原始巫教,佛教传布必定引起国内激烈的宗教冲突,臣磐之死就同这场宗教斗争有关。《后汉书·西域传》记臣磐建宁元年(168年)狩猎时为侄儿和得射杀。而陕西合阳中平二年(185年)十月所立《曹全碑》则记为:“建宁三年(170)..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得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和得面缚归死。”则臣磐实乃死于建宁三年(170年),时为八旬老翁,断难外出狩猎。曹全时任东汉戊部司马,政变发生后率兵干预,足证《后汉书》所记失实,《曹全碑》所记年代更为可信。政变首领和得夺权后必定实施大规模宗教清洗,此王乃疏勒反佛教势力的首领,死后佛教一度转衰,大批佛教徒必涌向邻国龟兹避难。以此判断,佛教初传龟兹应当发生于臣磐在位时期,至迟也应当发生于建宁三年(170年)和得政变之后。
(2)佛教东传龟兹必定发生于塞人白氏王朝创立之后,绝不可能发生于龟兹前塞人王朝时期。语言是宗教传播的主要媒介,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总是比语系迥异族群之间的传播要容易得多。鲍尔古本的发现和解读证实古龟兹语属B型吐火罗语文,乃古代龟兹塞人所操印欧语系肯通(Kentum)语支的一种方言。B型吐火罗文字则是以古婆罗谜文字拼写的这种印欧语方言,特点是名词有性、数、格的变化,动词变化更为复杂;且有前置词、后置词的区别,更为近似于希腊、拉丁等地中海语言,距于阗塞人所操的印度—伊朗型印欧语存在较大的差别。虽然如此,同操印欧语的塞人总比操汉藏语系的羌人或操其他语系的族群彼此还是相近得多。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实,这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文献都是发现于龟兹白氏王朝建立之后,古代龟兹、焉耆地区人种复杂,虽然塞人早就存在,但种种迹象表明,在塞人白氏王朝创立之前,龟兹曾经存在过一个前塞人王朝。西汉时期则尚不存在这种语文,充分印证佛教传入龟兹乃是白氏王朝建立之后的历史产物。
《魏书·西域传》记龟兹国“其王姓白,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明确记载龟兹历代王统都出自白氏家族,这是我国史书中关于白氏王朝最早的追述。其实,该传中所记后凉时期的白震并非最早见于汉文献的白氏王朝国王,参稽《后汉书》卷47班超传,白氏王朝的历史还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北匈奴册立的龟兹王尤利多为班超击败,被俘,汉朝另立原先送往洛阳的龟兹质子白霸为龟兹王,然白霸既为尤利多任龟兹王时期送往汉朝的质子,尤利多与白霸应属于同一家族,很可能同为北匈奴册立的龟兹王建的后裔,则白氏王朝至迟也可追溯至龟兹王白建。而西汉时期的龟兹王则皆出自绛宾后裔,此系王统传至前、后汉交替之际已不复存在,最后一位绛宾后裔龟兹王弘已被莎车王所杀,全族夷灭。由此足证,龟兹塞人所建的白氏王朝始于东汉初年,至于西汉直至新朝时期的龟兹王统则别出绛宾一系。易言之,西汉时期的龟兹尚属前塞人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发祥印度,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亚洲型(印度—伊朗型)的梵文与巴利文,于阗塞语同这种语言最为接近,《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和藏文文献《于阗教法记》共同证实,迦湿弥罗高僧卢折那(Vairocana)来到于阗杏园(藏文名为杂沐尔玛局里之园)弘法时,于阗居民可以直接听法,无须翻译。因而佛教迅速在于阗传布开来。同理,佛教弘传龟兹绝不可能发生于这一时期,只能发生于塞人白氏王朝建立之后。而且未必发生于白氏王朝建立之初。根据班超、班勇父子相继主政西域时期都未见其有关龟兹佛教的任何记录判断,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必定在西域三通三绝之后,这一时限同前文推算的臣磐被杀、和得政变之后大体相符。
(3)僧徒行纪的记录反映出龟兹佛教初兴的具体时间应是魏末晋初,至东晋时期始蔚为大国。朱士行是我国西行求法第一人,于魏甘露五年(260年)出发西渡流沙,所求法的圣地并非印度,也非龟兹,而是于阗,说明曹魏末年于阗佛教已臻鼎盛,国内已大、小乘经典齐备,龟兹佛教的知名度尚远不如于阗,南梁沙门释慧皎撰《高僧传》卷4义解一记载,其时于阗国内已大、小乘经典齐备,赴于阗访得所求大乘梵书正本凡九十章,因国王与小乘经师的干涉,以“惑乱正典”为名,不许大乘外流,朱士行被迫留于阗为质,换取弟子法饶携经东返洛阳。“至太安二年。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令写为二十卷。士行遂终于于阗。春秋八十。”龟兹佛教的知名度虽不如于阗,然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译经上昙柯迦罗传附有如下文字“又有沙门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后不知所终焉”,按“帛”字乃龟兹王姓,这位帛延应是东赴汉地弘法的龟兹第一人,说明曹魏末的甘露年间(256~259年)龟兹佛教也有了很大发展,乃至有人开始弘法中原了。至西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同名帛延,明确记载为龟兹王世子,也是笃信佛法。见于释僧佑撰《出三藏记集》所收《首楞严后记》①这位兼通胡汉语言文字(“善晋胡音”)的归慈(龟兹)王世子帛延亲自入晋弘法,这两个同名白延(或帛延)是不同的两个人。可见西晋时期龟兹佛教已相当兴盛。西晋时期龟兹高僧、信士入晋弘法者已非一人。如太康七年(286年)法护译《正法华经》时,有天竺沙门竺力与帛元信共同参校。
《须真天子经记》亦记“须真天子经。太始二年十一月八日。于长安青门内白马寺中。天竺菩萨昙摩罗察口授出之。时传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其中提及译经传言者有帛元信,《阿维越遮致经记》(晋言不退转法轮经四卷)附《出经后记》记“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美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闻知”。该经原本属于龟兹副使美子侯,以上帛元信应属龟兹王族,美子侯则属龟兹副使。西晋惠帝时(290~306年)有帛法巨(一作法炬),先与法立共译佛经四部十二卷,又自译四十部五十卷。这些龟兹佛教信徒所译佛经既有大乘,又有小乘,而以小乘居多。最先以弘法为业的龟兹高僧佛图澄(232~348年),《晋书》卷95记云“佛图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学道,妙通玄术。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及洛中寇乱,乃潜草野以观变。”后投奔羯人石勒,石勒父子以胡人应尊胡神,佛是胡神,尊为国教,佛图澄遂被尊为后赵国师,称“大和尚”,特点是不仅在胡人中弘法,而且更重视在汉人中传教。佛教的轮回报应理念迅速得到饱受战乱苦难和变幻莫测风云困惑的汉人广泛认同,从者如归,中原佛教由之崛兴。与佛图澄南北辉映,又有一位白氏王族出身的龟兹高僧帛尸梨蜜(汉语意为吉友),精于咒术,于永嘉年间(307~313年)到达江东,止于建康(南京)建初寺,精于咒术,对江南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佛教初传龟兹的时间大约始自东汉建宁三年(170年)和得政变之后,曹魏时期有了初步发展,虽然仍稍逊于阗,至西晋时期开始蔚为大国。克孜尔等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兴建大约也是始于此时,近年来的C14测定数据也可与此相互印证。
(作者: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吐火罗与回鹘文化
杨富学
一吐火罗人及其语言
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群中的一支,其故乡在今中欧或东欧一带,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便从操印欧语言西北组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向东迁徙,大致于公元前2世纪末到前1世纪初进入新疆天山南北,成为当地最早定居的古代民族之一。学界的研究认为,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都属于吐火罗人。①
关于吐火罗人在历史上的活动情况,由于东西方各种文献史料中的相关记载都非常稀少,而且语焉不详,时隐时现,矛盾牴牾之处比比皆是,故仅靠这些文献资料的零星记载是根本不可能全面认识吐火罗历史与文化的。有幸的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新疆地区考古工作的展开和众多吐火罗语文献的出土、刊布,与吐火罗历史文化有关的史实才逐步揭橥出来。
吐火罗文献都是用婆罗谜(Brahmī)字母写成的。最早的研究者是住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德裔梵文学家霍恩勒(A.F.R.Hoernle)。他在释读文字方面并未遇到困难,但发现其中的一些文献使用的并不是梵语。可究竟是什么语言呢?当时谁也说不清,学界姑且称之为“第一种语言”和“第二种语言”。对于“第二种语言”,学界不久就达成了共识,认为是印欧语系伊兰语族东支的一种语言——塞语,以这种语言写成的文献主要发现于和田地区,故而又被称作“和田塞语”,以区别于其他塞语。对于“第一种语言”的定名,学界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争论,直到今天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学者们都认识到这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从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文献看,吐火罗人尽管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许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前1190年小亚细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吐火罗语的发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欧亚大陆古代民族分化迁徙的认识。
1907年,德国著名东方学家缪勒(F.W.K.M〓ller)根据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写本的跋文中讲到回鹘文本译自toxri文本,认为其中的toxri语,其实就是古代东西方文献中提到的吐火罗语(tokhar)。①因为缪勒的定名依据的主要是二者在语音上的近似,而且在论述时对文献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误解,故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次年,德国梵文学家西额(E.Sieg)和西额林(W.Siegling)便撰文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种语言其实属于印度—斯基泰语。①然而,古代希腊人所说的斯基泰人(Skythen)相当于古代波斯人所说的塞人(Saka)这个定名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他们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这种语言具有,西部印欧语特点,同时又将其区分为两种方言,即甲种/A方言和乙种/B方言,这些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1913年,法国学者烈维(S.Levi)撰文《乙种吐火罗语为库车语考》,根据文献的记载,证明所谓的乙种吐火罗就是古代龟兹当地的语言。②此说令人信服,至今成为学界通行的说法。相应地,甲种方言遂被确认为焉耆一带使用的方言。
然而,将龟兹、焉耆一带的语言称作吐火罗语,有违于玄奘著《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大唐西域记》曾两次提到睹货逻(吐火罗),其一为卷一提到的睹货逻国,③即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其二为卷十二提到的睹货逻故国,④地当今新疆南部民丰县北部,约即今天的安迪尔(Endere)遗址一带。二者都与龟兹、焉耆无关。那么,回鹘人何以将古代龟兹、焉耆一带使用的这种印欧语称为toxri/吐火罗语呢?这一直是学界难以解决的问题。
经过长期的探索、辩论,近期学界有一种倾向,将吐火罗与大月氏人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这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新思路。首先提出吐火罗就是大月氏这一观点的是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B.Henning)教授。他通过对阿姆河流域出土粟特钱币的研究,认为粟特钱币铭文中提到的“吐火罗人”,其实是粟特人对大月氏的称谓。①贝利(H.Bailey)从伊兰语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指出,Tokhar一名中的to,可解释为“大”,khar可对应“月氏”。②吾人固知,大月氏原居住于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与敦煌之间,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被匈奴击败后,西迁到吐火罗斯坦。其后代建立了著名的贵霜(Kushan)帝国,但汉文史书仍习惯上称之为大月氏。值得注意的是,从河西走廊的姑臧(Kuzan),经新疆吐鲁番的古名姑师/车师(Kushi),到龟兹/库车/曲先(Kuci/Kucha/Kusan),再到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古都贵山(Kusan)城,一直到大月氏人于中亚、印度一带所建立的贵霜(Kushan)帝国,地名、国名、族名的发音非常近似。这种情况的出现当非偶然现象,应与这一区域大月氏人的活动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③易言之,从河西走廊到新疆天山南北,再到中亚以至印度西北部一带,自先秦、秦汉以来都曾是大月氏人/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直到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以后,吐火罗人连同其语言一起销声匿迹了。如是一来,龟兹、焉耆的居民被回鹘人称为吐火罗人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1957年5月,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发现了著名的大苏尔赫—柯塔勒碑(Surkh-Kotal)。三年之后,亨宁成功解读了碑文,知其是一种用草体希腊文字母书写的中古波斯语方言碑铭。由于用这种语文书写的文献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大夏(Bactria)故地,故亨宁建议将其命名为“大夏语”。④一些学者认为这才是大夏人的语言,所以称之为“真正吐火罗语”。⑤言外之意,前文所述的焉耆语、龟兹语也就成了“伪吐火罗语”。此说貌似立论有据,实则失之偏颇。因为在圣彼得堡收藏的一件梵语—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合璧文献中,Kucanne(龟兹)的对应梵文词就直接被写作Tokharika。①在一份回鹘语与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合璧书写的摩尼教赞美诗(编号为U103TⅢD260,19;260,30)中,用k〓is〓n一词来称呼吐火罗语。②(见图1)这些说明,至少在回鹘人于9世纪中叶西迁龟兹前,当地的确被称作吐火罗,其语言也被称为吐火罗语。所以,在我看来,称焉耆语与龟兹语为吐火罗语是实至名归的。古代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相当广大,不可能在语言上整齐划一,包含多种方言是自然的事,所以,不管是大夏语,还是焉耆语、龟兹语,其实都属于吐火罗语,不过都是吐火罗语的方言而已。回鹘人到达新疆时,吐火罗语还在继续流行,回鹘的不少文献都直接从吐火罗语翻译过来,故回鹘人将焉耆、龟兹当地使用的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是可信的,没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二吐火罗人的回鹘化及有关佛事活动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至新疆地区,征服当地部族,建立了以高昌、北庭为中心的民族政权——高昌回鹘王国,龟兹入于回鹘,成为高昌回鹘境内之大都会之一。但《宋史》在《高昌传》之外另列《龟兹传》,称:“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西州回鹘即高昌回鹘,龟兹受其辖制,但何以出现如此混乱的称呼,抑或龟兹具有半独立地位所致也?无从考见。
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控中西交通的咽喉,自古以来佛教文化昌盛。在回鹘统治时期,当地文化持续发展,在原居民吐火罗人逐步融合于回鹘之后,其文化对回鹘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回鹘文化的发展。
我们知道,回鹘本为漠北游牧民族之一。以漠北地区古往今来的自然条件论,古代回鹘的人口是不会很多的。就目前蒙古高原的人口状况推论,唐代回鹘的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00万。经过自然灾害的冲击,尤其是经过黠戛斯人的进攻,回鹘汗国分崩离析,在这种情况下,回鹘人口下降在所难免,随后又因南下、西迁而离散。所以,当时由漠北迁入新疆的实际人口最多不会超过30万。在偌大的高昌回鹘王国,其居民大部分应是被征服的当地各族。如昔日繁盛的龟兹国消失后,其居民都哪里去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回鹘同化了。《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中出现的被称作“西州龟兹回纥白万进”的朝贡使者,就是见诸史册的最为明显的例证。“西州”即高昌,亦即高昌回鹘王国;“龟兹回纥”即龟兹的回鹘人;“白万进”为人名,表明龟兹的白姓居民已归化为回鹘人了。
关于龟兹人的回鹘化,我们还可以西夏国师白法信和白智光为例。
西夏时期佛教盛行,西夏国的缔造者元昊(1038~1048年在位)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一直热心于扶持佛教的发展,并多次向宋朝乞请《大藏经》。1034年,宋刻《开宝藏》传入西夏,元昊遂建高台寺供奉。史载:
[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元昊]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东……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①
从记载知,高台寺建于1047年,当时延纳回鹘僧人讲经说法并译汉文大藏经为西夏文。
元昊殁后,西夏佛教在独揽大权的谅祚(1048~1068年在位)生母没藏氏的支持下继续发展,宋朝于1055年、1058年、1062年又先后三次赐予《大藏经》,故母子动用数万兵民于兴庆府西兴建承天寺,史载:
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②
这一记载表明,谅祚统治时期西夏又从中原地区请得《大藏经》,为储存这些经藏特建立了承天寺,如同元昊一样,也组织回鹘高僧于寺内展开翻译活动,并和其母没藏氏一起常常去寺内听回鹘僧讲法。从西夏统治者皇太后偕皇帝常临寺听回鹘僧人讲经一事看,当时的回鹘高僧在西夏佛教界所拥有的地位当是至高无上的。从西夏文文献看,大凡有皇帝莅临的法事活动,其主持者一般都拥有帝师或国师头衔,而元昊、谅祚时期西夏只有国师而无帝师(帝师在西夏的出现当在夏末仁宗时期)③之设,以理度之,这些回鹘僧的首领应具有国师之位。
通过对西夏佛教文献的进一步检阅,这些国师的身份更为明了。首先是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印本。文献末尾附有撰写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的发愿文,首先叙述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初兴与盛行,经典的翻译与流传,以及“三武灭法”对佛教的迫害等一系列史实,继之讲述了佛教在西夏的流布,以及佛经的翻译情况。载曰:
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蕃译。民安元年,五十三岁,国中先后大小三乘半满教及传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①
其中的“风帝”即西夏王元昊;戊寅年为1038年(即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说明元昊在称帝之初便开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其时比1047年高台寺的建成尚早9年。从是年至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历时53年,终于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12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主持翻译工作的是以国师白法信及其后继者智光等32人为首的一大批人。白法信以国师身份从一开始便参与了译经工作。在他去世后,智光继承了他的国师位及未竟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另一件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印本中,卷首附有一幅木刻版译经图。图中央绘高僧像一身,为主译人,在整幅画卷中图像最大,头部长方形榜题框内有西夏文题名“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两侧绘助译僧侣十六人,后排绘听法俗人八身。在译经图的下部,又绘比较高大的男女画像各一身,分别用西夏文题“母梁氏皇太后”和“子明盛皇帝”。②
同一位被称为“安全国师”的白智光,其名又可见于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序言中:
次始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即惠宗秉常)、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蕃。文华明,天上星月闪闪;义妙澄,海中宝光耀耀。③
这里出现了“智光”和“白智光”两个名字。考虑到二者的身份均为国师,且都在西夏之佛经翻译事业中充当重要角色,活动时代也主要在1037至1090年间,可见二者实为同一人。如序言所称,他翻译的经典,文字优美,表达准确,如“星月闪闪”,光华耀眼,故而在西夏文佛经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那么,上述西夏文文献中出现的白法信、白智光两位国师会不会与上文所述的回鹘高僧有什么关联呢?我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从他们所处的时代、从事的法事活动,尤其是白智光与回鹘僧讲经说法时都有皇太后与皇帝亲聆教诲的场景,使人不由地会做出如此联想,而非完全出自孟浪妄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两位国师的回鹘人身份。
对白法信、白智光民族成分的确认,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史金波先生在80年代初译释上述文献时未论及族属问题,经过数年的深思熟虑,他得出了结论认为白法信、白智光二位著名的译经大师很可能都是来自龟兹地区的回鹘人。①
从姓氏看,白法信和白智光肯定不是党项人。西夏国时期,党项人无以白为姓者。蒙元时代,西夏遗民散布各地,有许多人改行汉姓,但也未闻有以白为姓者。那么,他们会不会是汉人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展开汗牛充栋的中国佛教史册,我们何曾看到有哪一位汉族和尚是俗姓与法号共用?法号的取用本身就意味着与俗姓的决裂。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三国曹魏时被称为“中国出家人中真正沙门的第一人”的朱士行。②由于当时受戒体例尚未完备,故朱士行没有法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特例。东晋道安为增进佛僧的认同意识,首倡以“释”为姓,得到响应,“遂为永式”。③唯来自外国或西域者可有所变通。中原人士为甄别外来僧侣,常以国籍命姓,冠于法号前,如来自印度五天竺者,法号前常冠以“竺”,如竺法兰、竺佛念、竺法雅、竺法乘、竺法义、竺佛调等;来自西域安国者,常以“安”为姓,如安玄、安世高等;来自西域康国者则以“康”为姓,如康僧会、康僧渊、康僧铠、康法朗等;来自印度贵霜国者,则以支或竺命姓,前者表示其为月氏(又作月支)人,后者表示来自天竺。①有的仅用支字,如支娄迦谶、支昙籥、支谦等,有的支、竺共用,如支法护又称竺法护,支佛图澄又称竺佛图澄;而来自龟兹者,则常以其王家姓氏白/帛为姓,如帛尸黎蜜多罗、白延(或帛延)、帛法矩等。
其中,龟兹白(帛)姓尤当注意。自汉至唐700年间,白姓一直是龟兹的大姓。白者,有的史书又写作帛,如《高僧传》及《晋书》之《鸠摩罗什传》中提到的龟兹王白纯,在《晋书·吕光载记》中又被写作帛纯即为明证。据考,白、帛者,均为梵语puspa的音译,意为“云华”。②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汉人在称呼外僧时,既有以姓氏与法号并称者,也有只呼法号者,如竺(支)法护,常略称法护;竺(支)佛图澄呢,则更是以法号行,称姓者反而稀见,这又为白智光何以又被略作智光的问题提供了最佳脚注。
这些说明,白法信和白智光均为来自龟兹的高僧,都是回鹘化了的吐火罗人。二人先后以国师的身份在高台寺和承天寺传经布道,并主持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可以说是古代吐火罗人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因为西夏文大藏经是世界现知的六种大藏经之一。
三 吐火罗与回鹘文佛典翻译
如上所述,当9世纪中叶回鹘人西迁至新疆之前,吐火罗人尚为新疆西部的活跃民族,他们所使用的吐火罗语尚为新疆流行的语言之一。吐火罗人虔信佛教,文化发达,今新疆西部库车、新和一带现存的具有吐火罗风格特点及吐火罗文题记的石窟艺术就是其文化的代表。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库木吐喇石窟第69窟中还可以看到吐火罗文与回鹘文合璧书写的题记(见图2)。二者不存在打破与叠压关系,而且笔法相同,说明为兼通吐火罗文与回鹘文的同一书手所写。吐火罗僧侣接过印度高僧传来的接力棒,把佛教进一步向东方传播。他们是联系印度与中国佛教的纽带,是把佛教由中亚向东方推进的主力。当这些吐火罗人被回鹘同化以后,其佛教文化也被带入回鹘社会之中,对回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吐火罗人在印度佛教传入回鹘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有两部比较重要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就是由吐火罗文本翻译过来的。
其一为《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原名作maitrisimit,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组成。序文的内容主要为一般的佛教教义和回向文;正文主要描绘了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弥勒是未来佛,据《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等载,原出婆罗门家庭,后为佛弟子,先佛入灭,上生于兜率天宫,经四千岁当生于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广为说法。其圆寂及上生兜率天宫的过程在《弥勒会见记》第27幕中有详细描述。这是佛教说一切有部毗婆娑派(Vaibh■sika)的重要著作。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勒柯克(A.vonLeCoq)率领下,于吐鲁番的木头沟和胜金口发现了不少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叶。①1959年4月,在新疆哈密市天山区板房沟乡又发现回鹘文《弥勒会见记》586叶。这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典之一。
这部回鹘文著作,如同其所依的吐火罗语底本一样,常被称作“剧本”。德国学者葛玛丽(A.von.Gabain)②和鲍姆巴奇③经研究后认为,这种本子(或类似的文本)是可以作为街头说唱结合的戏剧演出之底本来使用的。
关于回鹘文本的来源问题,在哈密写本的第一、二、十、十二、十六、廿、廿三、廿五诸幕末尾都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跋文。例如第一幕末尾(第16叶背面)这样写道:精通一切经论的、饮过毗婆娑论甘露的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改编为吐火罗语,智护法师译为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书中跋多利婆罗门做布施第一幕完。①
据此跋文可知,该经回鹘文原名作maitrisimit,它先由圣月大师(Arya〓antr〓)据印度文本改为古代焉耆语,以后又由智护(Patanraksit)大师据之转译为突厥语。据考,圣月大师系三唆里迷国(〓〓Solmi,即焉耆)的著名佛教大师。智护呢?缪勒与西额根据德国所藏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中称智护为Il-bal〓q人的记载,认为他应来自伊犁地区。②葛玛丽教授亦同意此说。③但法国学者伯希和(M.Pelliot)疑之,虽可认定11-bal〓q为突厥语地名,但具体所指已无法知晓。④后来,哈密顿经过研究认为,I1/El-bal〓q不能理解为伊犁,而应为“国都”之意,指的就是回鹘王国的都城——高昌。⑤此说可信。从出土文献看,高昌在古代正属于焉耆语/甲种吐火罗语的流行地。
有幸的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所依据的吐火罗文底本在新疆也有发现。1974年冬,在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个灰坑内出土了一批用婆罗谜文书写的文献,经由季羡林先生研究解读,知其正是用焉耆语/甲种吐火罗语书写的《弥勒会见记》,共44叶,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①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记载的正确,同时也为我们认识西域戏剧的起源、内容与形式及其传播途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通过对回鹘文本与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的比较,学者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有些部分看起来不像是“翻译”出来的,而像是改编甚或是重新创作。②由此之故,古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题记所谓译自吐火罗语的说法是否切合实际,即是否完全按照吐火罗语底本译出,还存在着问题。
其二为《十业道譬喻鬘经》。这是一部大型佛教故事集,性质有些类似于古代印度的《五卷书》和《一千零一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③有关回鹘文写本早在20世纪初就在吐鲁番地区有所发现,回鹘文写作D(a)〓ak(a)rmapata(awdanamal),梵文为Da〓akarmapath〓-vad〓nam〓〓。其中所收故事分门别类地讲述了佛教的十种善业(Kar-mapatha)“十善业”与“十恶业”相对,是佛教的基本道德信条。属于身业的有三:不杀生、不偷窃、不淫邪;属于口业的有四: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属于意业的有三:不贪欲、不嗔忿、不邪见。关于该文献的来源,在德国梅因兹收藏的编号为Mainz864a(TⅢ84-68)中有载(见图3),其跋文称:
精通毗婆沙论、咒法与诗文的僧伽奴将这部伟大的《十业道譬喻鬘经》从uguK〓s〓n语(即龟兹语——引者)译成吐火罗语(即焉耆语——引者),再由尸罗仙那(〓lasena)大师将其重新转译成突厥语。以弘扬“十善业”的利益和十恶行的罪过。①
这一记载说明,《十业道譬喻鬘经》是从由龟兹语翻译成焉耆语,然后再从焉耆语翻译成回鹘语。遗憾的是,该文献之内容既不见于龟兹语、焉耆语文献,也不见于梵文与汉文典籍。除回鹘文文本外,现只发现有粟特语残卷。该残卷的题目似乎是δssyrkrtyh,即“之′十善业”意。②看来,这一粟特文写卷应是一部与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经》类似的著作。
以上两部回鹘文著作都是以焉耆语/甲种吐火罗语为底本的,那么是否有直接译自龟兹语/乙种吐火罗语的文献呢?我们这里不妨先看缪勒在《吐火罗与贵霜》一文中所提到的如下一段回鹘文题记:
《一切有情..救经》,第三十二分终,原列阿阇梨论师Klianzini(Kaly〓nasena)之idivut中,师从k〓s〓n语译为bar〓uq语,附有大阿梨Srvarak〓ti遗留之idivut经赞..③
题记中所谓的《一切有情..救经》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由于文献断残过甚已无法知晓。其中的“k〓s〓n语”,缪勒解释为与加腻色迦王有关系的人们熟知的“贵霜”之语言,并成为此后欧洲学术界的定说。1931年,羽田亨刊文指出其误,认为应解释为“龟兹语”。④此说得到了伯希和的支持。在羽田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这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k〓s〓n语”实应称“龟兹语”。⑤在笔者看来,就本文献而言,如果将“k〓s〓n语”解释为龟兹语,当更合乎本题记的文意,因为其中所提到的这部佛经是由k〓s〓n语译为bar〓uq语的。Bar〓uq地当今新疆巴楚县,故题记中的bar〓uq语当为古代回鹘语无疑。而回鹘语佛经译本出现之时代,距离贵霜帝国已相当遥远,而龟兹语文却正在流行,而且对回鹘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见下文),故文中的“k〓s〓n语”庶几乎可理解为“龟兹语”。
以上二件文献均译自焉耆文/甲种吐火罗文,那么是否有译自龟兹文/乙种吐火罗文的文献呢?从现知的文献看,尚无法确定。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有这种可能。《阿烂弥王本生》在回鹘文文献中写作〓ranemi-J〓taka,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Ou〓gour1。原写本分为3叶,共存文字119行。其中67行为阿烂弥王本生故事本文,其余52行为题记。该本生故事不见于汉文、梵文与藏文《大藏经》。从译文看,其中大量采用了吐火罗语词汇,如:
人名S〓nt〓r,源自龟兹文sunetra;
人名阿烂弥王〓rnim源自龟兹文aranemi;
地名〓rin〓t〓w,源自龟兹,文arun〓vati;
专有名词a〓ar〓,源自龟兹文a〓ari<梵文〓c〓rya,意为“导师”或“规范师”汉译“阿阇梨”,为佛教僧官称号;复数名,a〓意为“,由am-
词amlar,大臣们”a〓(大臣)加复数后缀-lar构成。其中,ama〓源自龟兹文am〓c<梵文am〓tya。①从这些因素看,该文献有可能来源于龟兹文原典。
四 吐火罗语对回鹘语言的影响
今天发现的吐火罗语文献的时代大多在6~9世纪之间,但吐火罗语在新疆的存在却比这个时期久远得多。佛教大致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地区,然后经由这里而于1世纪左右传入内地。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包括吐火罗人在内的西域诸族曾起过桥梁作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成为梵文佛典译入汉文的媒介。季羡林先生指出:
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我们两国不完全是直接往来,使用吐火罗语的这个部族曾在中间起过桥梁作用……饮水思源,我们不应该忘记曾经沟通中印文化的吐火罗人。①
这个论断,对古代回鹘佛教及其文献语言的形成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是适用的。
回鹘人曾经翻译过大量的佛教经典,纵然不是全部大藏经,至少也是大藏经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都已先后译成了回鹘语。从新疆、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看,这些佛经大多直接译自汉文,另有一部分译自藏文、梵文甚或吐火罗文,不管译自何种文字,我们都可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印度梵语和古回鹘语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语。日本学者庄垣内正弘以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为依据,对回鹘文献语言中存在的借词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回鹘语词尾形式、语音、形态诸方面特征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回鹘语中的借词尽管来源广泛,既有汉语,也有梵语等,但基本上是以吐火罗语为主的,粟特语只是起一些辅助性的作用。②
这里我们先看下列表格(依庄垣内正弘研究成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回鹘语在吸纳梵语词汇的过程,即当梵语词尾为-i/-ī时,在回鹘语中变为-i、-u;-ū则变为-u;-in变为-i;-jit变为-ci,这一演变常常通过了吐火罗语的过渡。在吐火罗语中,元音弱化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古代译师们在用之译经时,按照其语音规律将梵语中的词尾-a改变为-e;当其被译为回鹘语时,又经改造而变成了-i。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梵语词尾到回鹘语词尾的转化都经历了梵语→焉耆—龟兹语(或汉语、藏语)→回鹘语的过程。
除了词尾的变化外,辅音也因受吐火罗语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同时还有回鹘语直接借自吐火罗语,这些情况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也是很常见的。如:
(1)阿鼻狱,梵语原作avīci,但回鹘语却写作avis,究其来源,当源自吐火罗语之avis。
(2)摩竭鱼,梵语原作makara,但在回鹘语中却演变为matar,与梵文相去甚远,显然当借自吐火罗语之matar。
(3)行布施,梵语原作pindapāa,但回鹘语却写作pinvat,究其来源,当源自吐火罗语之pinwāt。在回鹘语中,v、w相通。
这里还应特别提及吐鲁番出土的印度英雄史诗《罗摩衍那》回鹘文写本。《罗摩衍那》本为印度教内容,但被佛教徒借用以宣传佛教。其中有些用词显然受到了吐火罗语的影响。例如,罗摩之妻悉多在梵文本中的对应词是Sita,但在回鹘文本中却变成了siza。同一个词,吐罗语写作Sisā,①于阗文则作Sīysā(ys替代z)。②追寻回鹘文siza之来源,自然应追溯至吐火罗语而非梵语,因为其发音与吐火罗语最为接近而与梵文相距较远。③
还有一些词汇,本为吐火罗语,被回鹘语直接借用。如胡麻,回鹘语作k〓n〓id或ktin〓t,显然借自吐火罗语kuicit;再如小屋,在回鹘语中写作piryan,显然借自吐火罗语pary〓m;大麦回鹘语作ǎrpa,显然借自吐火罗语arpa。
正是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存在,库车居民的语言,直到近世尚存古龟兹之遗风。德国东方学家马丁·哈特曼(MartinHartmann)曾于清末到新疆旅行,在他的著作《中国新疆——历史、行政、宗教和经济(ChinesischTurkestan,Geschichte,Verwaltung,GeisteslebenundWirtschaft)》(哈勒,1908年)一书中记载了他在新疆的见闻,其中提到:
莎车当地人称,库车的语言清纯;说话善用诗,其语言有很多都是我们所不懂的。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现象?法国学者烈维认为,此应是库车维吾尔语受古代吐火罗语影响所致,是值得今人认真研究的。⑤这一结论无疑是有道理的。
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的写本中,还发现有多件用摩尼文或龟兹文字母拼写的龟兹语、回鹘对照摩尼教文献。兹简述于下:
(1)U99(TⅢD259,13)小残片1叶,面积7.6×5.9厘米,存文字10行,内容为用摩尼文书龟兹语、回鹘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①(见图4)
(2)U100(TⅢD260,34/TⅢD259,17),残片1叶,面积20.7×5.6厘米,存文字10行,内容为用龟兹文书写的回鹘语和龟兹语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②
(3)U101(TⅢD260,14,TⅢD260,10),小残片2叶,面积分别为6.4×5.9厘米、10.6×4.7厘米,可拼合。存文字10行,内容为用龟兹文书写的回鹘语和龟兹语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③
(4)U102(TⅢD259,23,TⅢD259,26),小残片2块,面积分别为6.3×5.9厘米、7.3×6厘米,可拼合。存文字10行,内容为用龟兹文书写的回鹘语和龟兹语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④
(5)U103a-c(TⅢD260,19,TⅢD260,30),小残片3叶,面积分别为6.4×5.8厘米、7.4×5.8厘米、3.7×5.6厘米,可拼合。存文字10行,内容为用龟兹文书写的回鹘语和龟兹语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⑤
上述5件写本或用摩尼文书写,或用龟兹文书写,但内容均为回鹘语和龟兹语双语对照的摩尼教赞美诗,以这些因素观之,应为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之初的作品。当时吐火罗语尚处于流行阶段,摩尼教也正在吐火罗人和回鹘人中盛行。这些赞美诗无疑体现了吐火罗人、回鹘人与摩尼教间的密切关系。吐火罗人与回鹘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发生在回鹘由摩尼教信仰转归佛教信仰之前,为后来吐火罗语成为印度梵语和回鹘语的媒介语这一现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者: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敦煌:晚唐五代中外文化交融与碰撞
郑炳林
敦煌地区是中原文明、西域文明、藏域文明、草原文明交汇之地,其东界河西诸郡与中原相接,是连接中原西域文明的桥头堡:西临西域,控驭两关与中亚及西方世界连接;南界吐蕃,接受藏文化优秀部分;北御突厥,将草原地区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接纳,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优势。敦煌是古代中国经营西域的基地,汉唐以来中央政府经营西域,都是以敦煌为军屯要塞,因此所谓的吐谷浑道、鄯善道、伊吾道等行军路线,都是以敦煌为起点的,并且派遣敦煌地区民众官员带军出征西域地区。敦煌出土的简牍、文书等大量文献资料和石窟壁画等丰富图像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一 敦煌是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经营西域的基地
自汉武帝置河西四郡设立敦煌郡起,敦煌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都会之地,也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交通道路经由河西走廊往西域,敦煌是其必经之地,有敦煌到伊吾的新开道、由敦煌到高昌的大海道、出敦煌经过玉门关到焉耆的大碛道、出敦煌经阳关到石城的鄯善道、出敦煌到吐蕃的把疾道。①《隋书·裴矩传》说伊吾、高昌、鄯善为西域之门户,而总会敦煌。②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古代的西域主要指敦煌两关以西的地区,而敦煌就成为古代中国的边疆重镇。汉武帝以敦煌为基地经营西域,唐朝贞观年间对吐谷浑的战争、对高昌的战争以及武则天时期对吐蕃和西突厥的战争,都是以敦煌为基地进行。贞观年间唐朝中央政府准备用大量粮食等物资救济居住伊吾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就是以敦煌为中心实施的。
唐朝贞观十四年占领高昌设立西州,相继设立了伊州、庭州,建立安西、北庭两个大都护府,管辖范围一直达到了葱岭以西的地区。以后在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的基础上设置了安西、北庭两个节度使。当时唐朝的认识是西域战乱,河西就受影响,不安定,而河西不保,关中就难以稳定,所以作为唐朝政府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敦煌就显得十分重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得到证实。从吐鲁番地区出土墓志和文书以及敦煌文献记载看,吐鲁番地区的居民很多都是从敦煌地区迁徙而来的,敦煌地区很多人任职吐鲁番地区,担任镇府军将之职。③记载比较明显的是《沙州都督府图经》张芝墨池条和《敦煌名族志》,①有担任唐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阴嗣监,实际就是北庭节度使;有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阴守忠等,还有西州蒲昌府折冲都尉摄本卫中郎将充于阗录守使敦煌郡开国公张怀福,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等上柱国张怀立,昭武校尉前西州岸头府左果毅都尉摄本府折冲充墨离军子将张履古,通海镇大将神军索恪,等等。在吐鲁番的汉族居民结构中,源自于敦煌的居民占了主要部分,如敦煌张氏中的清河、南阳、安定等,在吐鲁番出土墓志铭中都有记载。这就使吐鲁番地区的居民结构和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一样,居民中有专门安置胡姓居民的从化乡和崇化乡。经过我们的研究,敦煌胡姓居民大约占了整个居民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或者说,汉姓居民占了敦煌、高昌地区居民的百分之七十左右。②由于这种居民结构特点,因此唐朝政府经营西域,将经营基地放在敦煌,打败高昌的麴文泰和西突厥之后,将管理西域的中心放在汉族居住相对集中的西州、庭州。尽管一段时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放在军镇要地龟兹,但是往往是在西州和龟兹之间变换。而敦煌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唐朝政府与吐蕃在西域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唐朝政府为了加强战争的需要,于上元二年将毗邻敦煌的石城镇、播仙镇,划归敦煌地区管辖。敦煌文献《沙州伊州地志》和《寿昌县地境》记载的沙州寿昌县管辖的地域包括了石城镇和播仙镇等。③开元天宝年间,随着吐蕃势力的增强,一度占领毗邻敦煌的石城镇和播仙镇,居住在这里的胡姓居民向敦煌地区迁徙,敦煌县的从化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安史之乱发生之后,边兵内撤,吐蕃乘机占领河西陇右,河西节度使由凉州—张掖—敦煌,在敦煌地区坚持的十一年之后,于786年最后在不要将敦煌地区居民外迁的条件下投降了吐蕃,敦煌开始了将近六十年的吐蕃统治时期。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仍然是吐蕃统治和管理西域地区的中心。经过我们的研究得知,吐蕃统治时期,先后在陇右、河西设立了河州、沙州、凉州和瓜州四个节度使。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州和瓜州节度使,节度使都是由吐蕃宰相来担任的,瓜州节度使管理瓜沙肃及其西域地区,从瓜州节度使衙的任职人员结构看,敦煌地区的大姓成员很多都在瓜州节度使衙中担任各种职务,这在敦煌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同时,瓜州节度使衙的物质供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敦煌。我们从敦煌经济文书记载敦煌百姓服役情况看,记载敦煌地区百姓往瓜州节度使衙送物品,如S.542《戌年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记载敦煌龙兴寺的张善德和史英俊等、莲台寺阴庭圭、灵图寺的史奉仙等往瓜州节度送粳米,护送西州人户往瓜州。①从敦煌文献中的发愿文记载得知,吐蕃时期瓜州节度使曾经带领敦煌地区兵马,前往西域地区平息那里反对吐蕃的少数民族。这些记载表明吐蕃时期,敦煌地区是经营西域的中心。
848年(大中二年),张议潮带领敦煌地区的胡汉民众驱逐了吐蕃统治者,收复瓜沙二州,相继派出十批使节入朝。大中三年,张议潮的军队收复了肃州,大中四年收复了敦煌通往西域的门户之地伊州,大中五年唐朝政府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咸通二年张议潮以七千人收复凉州,追击吐蕃的军队一直到星宿岭南,大概就是今天青海和黄河源一带。②归义军的管辖范围最大时达到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共管辖六个州,一度号称十州。咸通七年前后由于回鹘的归附,名义上就有了西州和庭州。东部因为对吐蕃的战争,归义军政权的管辖范围一度达到了河湟流域。这样归义军的管辖范围名义上就有了鄯州和兰州。①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不归,其兄之子张淮深执掌归义军政权,直到大顺元年(890)被杀为止。②这一时期归义军的疆域处于退缩趋势,最后仅有二州之地,此后敦煌归义军政权经张淮鼎、索勋、张承奉及其曹氏家族,绵延200多年时间,归义军一直没有大的起色。归义军时期在管辖范围上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是:第一,敦煌地区是归义军政权的政治中心,无论是张议潮、张淮深的六州、十州,还是五州、二州八镇,敦煌都是当时的统治中心。唐朝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虽然没有得到唐朝正式任命,但是一直掌握归义军实际事务。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将国都定在东有三危大圣、西有金鞍毒龙,神佛护佑的敦煌,以敦煌为中心经营周边。③第二,从归义军的西部管辖范围变化,可以看出归义军的经营西域用心,将伊吾、西州、石城作为经营的重点。在伊州方面,从大中四年取得伊州,多次用兵攻打盘踞在伊州纳职城的回鹘势力,《张议潮变文》就记载了大中十年~十一年连续对伊州纳职城回鹘势力用兵的情况,并派遣王万清、左公等任伊州刺史,④一直到乾符三年四月回鹘可汗仆固俊打下伊州,归义军对伊吾的控制结束。⑤此后张承奉时期归义军政权曾经一度用兵伊吾,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石城方向,归义军初期,《张议潮变文》记载归义军的军队经过一千余里行军到达吐谷浑国内。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可能是指居住在石城附近的吐蕃政权,根据《沙州图经》记载,阳关至石城的距离是一千五百里左右,和变文记载的历程基本相符合。张承奉时期,归义军派遣罗盈达、张良真出征石城地区的吐蕃,并取得胜利,设立了石城镇。第三,归义军时期积极开展与西域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政治交往,为了加强同西州、伊州回鹘以及于阗、石城仲云(南山)之间关系,归义军政权不断派遣使节、商队前往这些地区。出使某个地区有专门的组织——使团,并且为了加强对使团的管理,专门设立了使头之职,有于阗使驿头、南山使头、西州使头、伊州使头等。①使团的成员有官员、商侣、僧人,也有一般百姓,使团的商业性质很明显,出使前在敦煌地区借贷大量的物品,出使结束之后,以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利润归还。第四,敦煌地区平常接待大量的外来使节,有来自西州、伊州、石城、于阗及其达怛、退浑、吐蕃等区域性政权的,也有来自中亚地区如印度、波斯等地的使节和行僧等,专门设置了宴设司等机构,负责接待工作,开创了敦煌地区又一个繁荣的局面。②
二 敦煌地区居民结构呈现多元化倾向
敦煌地区居民成分复杂,我们曾经研究敦煌县的乡里制度,知道唐代敦煌县有十三乡,其中就有从化乡,主要见载于《天宝十载敦煌县从化乡差科簿》,记载服差役的人有257人,有2人担任市壁师。从化乡是由分布在敦煌城东一里的祆寺周围一带的胡姓居民建立的,他们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市壁师就是专门管理市场贸易的官吏,由胡姓居民担任,表明粟特人是敦煌市场贸易的主体。同时差科簿还记载从化乡有两个里正、四个村正,由于文书残缺,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敦煌从化乡到底有几个里多少村,但是我们起码可以确定,从化乡最少有两个里四个村落。①从化乡的来历,经过陈国灿先生的研究,大约武周时期居住在石城镇一带的粟特人在吐蕃的逼迫之下迁居敦煌,唐朝政府将其安置在敦煌城周围一带,并以之为主建立了从化乡。②
吐蕃统治敦煌之后,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并没有像池田温先生说的那样,粟特外迁到回鹘地区,剩下的都进入寺院变为寺户,从此敦煌地区再也没有粟特人了。经过我们的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粟特人还存在,见于敦煌文书的有,敦煌富商粟特人康秀华,为抄写一部《大般若经》就向佛教教团张金炫和尚施舍了价值600石麦子的银器、胡粉和粟麦等,再敦煌石窟中记载他就是敦煌部落使之一。部落使是由唐代的乡官改变而来的,因此可以肯定,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并没有外迁,而是还保留他原来的面貌。除了部落使康秀华之外,粟特人还担任吐蕃时期敦煌都督之职,都督是吐蕃人之外的汉人及其他民族能够担任的最高官职,但是粟特人也担任这一职位,记载于敦煌文献的就有安都督,实际上粟特人已经成了吐蕃时期敦煌地方政府的实际执政者。③
归义军政权是一个胡汉联合政权,首先从这个政权的建立过程来看,张议潮收复敦煌之后,和副使安景旻、部落使阎英达、都僧统吴洪辩等派出使节入朝,而安景旻就是居住敦煌的粟特人的代表,阎英达是通颊等部落的代表。归义军政权中有瓜州刺史康使君、都知兵马使删丹镇遏使康通信、左都押衙安怀恩等,节度使以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都有粟特人担任,同样都僧统及其以下各级僧官也有粟特人担任,直到曹氏归义军时期。经过荣新江、冯培红等研究认为,曹氏家族就是居住在敦煌的粟特人后裔,归义军政权从张氏时期的以汉人为主的胡汉联合政权,变为曹氏以粟特人为主的胡汉联合政权。①归义军政权从张氏手中转入粟特人曹氏手中,主要是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变化,粟特人在敦煌地区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敦煌地区的粟特人聚落有康家庄、曹家庄、史家庄、石家庄、安家庄、罗家庄等。②经过我们对大量敦煌文书的分析,敦煌地区以胡姓居民为主的外来居民,占了将近百分之三十左右。除了粟特人之外,敦煌地区从武周时期起,就有大量吐谷浑人迁居敦煌,或者他们投唐之后,唐朝将他们安置在敦煌一带;归义军后期,敦煌地区有吐谷浑部落,特别是在瓜州地区,吐谷浑慕容家族势力非常大,五代时期慕容归盈担任瓜州刺史,生前直接派遣使节入朝,死后瓜州官吏还要给归义军节度使上状,要求为慕容归盈修建寺庙纪念。吐蕃统治时期,有大量吐蕃人迁徙到敦煌地区,归义军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的遗迹,特别是在肃州和瓜州之间,就有吐蕃人部落,高居诲出使于阗,图经河西敦煌,看到沿路都有吐蕃聚落。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居住着除了汉族人之外很多民族,居民结构成分复杂,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因此影响到敦煌地区,宗教文化社会风俗也表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三 敦煌对外交流具有国际化特色
从两汉起敦煌就成为一个国际化商业贸易都会城市,《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敦煌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明确指出敦煌是国际贸易市场城市,敦煌的这种地位一直到唐代中期基本上都没有发生改变。归义军时期敦煌商业贸易市场地位有所衰落,地位远不如以前,但仍然起着国际商业贸易城市的作用。至于这种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是我们探讨的一个主要内容。作为国际贸易城市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具有国际性,二是出现在贸易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商品也要具有国际性,三是贸易市场上使用货币的国际性。
唐代敦煌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他们担任管理市场贸易的市壁师,是敦煌贸易市场的主体。由于粟特人的国际性,对敦煌市场贸易影响很大,使其国际化程度提高,汉唐以来一直保持华夷之交的都会城市特点。此外敦煌商业贸易中还常见有吐蕃、于阗、波斯、印度的商人。敦煌市场上有他们开设的酒店商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时期对外贸易相当频繁,经常向中原地区和西域及周边诸政权派遣使团,这些使团规模大人员庞杂,有官员也有一般随员,还有相当多的商人和僧侣。在一般情况下,使团成员都要携带一些纺织品或其他质轻价高的物品去贩卖,同时将其他地方的物产贩到敦煌市场出售,或经敦煌再转售到其他地方。当时归义军向外派遣使节的记载比较多,为了管理使团事务约束随员纪律等,出使的随团人员中常设了一批使团头目,有甘州使头、西州使头、于阗使头等,这些使团头目中有很多就是由粟特人来担任的。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派往各地的使节非常频繁,这些使节组成复杂,除完成政府的任务而外,还带有商业贸易使团的性质,他们牵驼驮物来往奔走在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及其周边政权之间,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就是通过他们进入的。敦煌文书记载来往使节般次捎带货物比较常见,更多的是出使的目的就是为了商业贸易,出使之前为了筹集足够的商品和运输工具,他们得向人借贷货物和雇佣驼马,出使回来之后用贩运回来的商品偿还利息与雇价。在归义军政权的机构中还专门设立了宴设司,职责是招待来到敦煌的外地使团,这些使团商团有来自回鹘、于阗、南山、鞑靼、波斯、印度等地。这些东来西往的商团尽管经常遭受沿途各个政权的骚扰和劫夺,但是并不因为战争或劫夺而放弃通使和商业贸易。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商品同样也具有国际性。敦煌地区物产贫瘠,地不产珍,献无奇玩。因此敦煌市场上的商品大都靠从外地进口,进行中转贸易。有出产于龟兹的胡粉,中亚的金青和水银,吐蕃地区的石青和石绿,西州出产的棉布,波斯等地出产的胡锦和珠宝,伊州出产的铁器,于阗出产玉石,东罗马的银器,西域印度的药材和香料,高丽出产的高丽锦,达怛和吐蕃出产的畜牧产品和兵器等。产品来源东到中原及朝鲜,南到吐蕃和印度,西到波斯、印度和东罗马。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国际化的程度还决定于市场使用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敦煌文献记载看,金币银币和金银器皿是对外贸易中使用的主要硬通货。金银币等硬通货不但流通,而且数量不小。这些金银币可能就是这些外来胡商带进敦煌贸易市场的。金银器i皿作为流通货币在晚唐五代的敦煌贸易市场比较常见,这些金银器皿有罗马银盏、银盘子、金花银瓶子、银碗等。这些银器表明重量,用于支付物价,其性质显然是货币,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器皿,而是作为货币流通于敦煌等地的贸易市场中。其次在对外贸易中还使用丝绸支付物价。在对内或小宗贸易上多用实物特别是粮食支付物价,进行交换。
四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
(1)多元化宗教流行及其演变:祆教和佛教
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域,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外文化交流都要经过敦煌地区进行,因此敦煌流行的宗教和民间信仰也呈现多元化倾向。汉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盛行,粟特人迁居敦煌之后,祆教也开始流行。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流行的宗教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祆教,如果说将儒家理论学说也归并为教的话,还有儒教,加上各种信仰(如十王信仰、观音信仰、海龙王信仰、毗沙天王信仰、五天山信仰、宾头卢信仰等)那就更多了,主要的是儒、释、道三教。儒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道教是中国原始宗教,二者代表汉文化对外影响的主流。如回鹘、吐蕃等将儒家经典翻译过来,将属于道教的占卜文献翻译成本民族文献,或者在其占卜文献中加以吸纳,是汉文化对其影响的具体方面。更多的是外来宗教进入敦煌地区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戒律清规的演变及其违规现象普遍。其次祆教信仰传播流行日渐盛行,甚至变成归义军的政府行为。
祆教是粟特人信仰的宗教,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就记载了敦煌城东一里有祆寺,所谓的城东水池赛祆,可能就是指祆庙。根据归义军政府支出账的记载,赛祆的时间为每年的正月十一日、正月十三、二月廿一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四月十四日、四月十六日、五月十一日、七月九日、十月五日、十月九日等。祭祀祆神的开支都是由政府负担,表明赛祆是一种政府的行为,祆神被称作安城将军,是敦煌民间信仰的一种神。①《敦煌古迹廿咏》记载有安城祆咏:“板筑安城日,神祠以此兴;州县祈景祚,万类仰休征。频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绳。”②不仅仅粟特人信仰祆教,就是生活在敦煌地区的汉族人也信仰祆教,归义军时期派出的使节带有画纸以备沿途赛祆之用。我们看到张承奉时期及其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支出账都基本上有赛祆的各种支出。祆教流行及其政府出面赛祆,表明敦煌地区的居民结构和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粟特人的势力得到加强或者掌握了归义军政权。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违犯戒律现象非常严重,五戒十戒中都规定僧人不能饮酒,但是在晚唐佛教教团中僧人饮酒成风。敦煌籍账文献中很多是寺院或者都司机构的酒账,从这些酒账看,僧人不仅为加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将上好的酒送给归义军政权的有关官员,如每年端午节就送麦酒给节度使或者都押衙等,还自己饮酒,造酒,更有甚者僧人公然开酒店,从事酒制造销售,从中牟利,有的由此成为巨富。③敦煌文献就记载一位叫龙藏的和尚,吐蕃时期因为开酒店,一年营利麦一百三十石、土地七十亩。④归义军时期以僧人命名的酒店很多,很可能就是僧人们出资开的酒店。僧人饮酒不是根本戒,是因为饮酒可以乱性,做出其他违背戒律的事情。敦煌僧人饮酒风气是从吐蕃时期开始的,显然是受了外来风气的影响。
其次,僧人食肉问题,有两点需要我们认识:一是寺院拥有大量牲畜,寺院拥有羊一般数十只,有的达到数百只,专门雇人放牧,每年正月寺院主管与放牧者都要进行算会,新生了多少,死亡了多少,羊皮和羊腔多少,他们将这些羊作什么用途,是出售还是自用。二是,僧人食用臛一类的东西,有人研究是肉汤,如果僧人使用肉汤,那么僧人食肉问题就解决了。目前学术界有的学者坚持僧人食肉,并且有专门论文发表。我们的看法是,按照小乘佛教的要求,僧人可以杂食三净,毗邻敦煌的龟兹等都信仰小乘佛教,这种习俗可能受了他们的影响。
僧人拥有家室可以娶妻生子。这是敦煌文献反映出来的一个特殊问题,敦煌户籍文书记载,晚唐五代的僧人主要是晚唐张议潮时期僧人的户籍都在原来的家里,所谓僧挂俗籍或者僧俗混籍。从这些户籍上看,敦煌的僧人有妻有子女,问题是他们的妻室和子女是出家前所娶,还是出家后所娶,子女是出家前所生,还是出家后所生,目前我们还无法搞清楚。目前学术界有一部分专家认为敦煌佛教教团的僧人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并且专门撰写论文加以论证。从龙藏和尚看,他在出家前娶妻阴二娘,出家之后不久阴二娘就死了,不能证实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可以证实的是龙藏出家后还和其子宣子生活在一起。关于僧人拥有家室主要根据是户籍,就这个问题来说直到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彻底解决。经过杨富学先生的研究,居住在鄯善地区的僧人拥有家室,娶妻生子。开元年间,居住在这里的胡姓居民迁徙敦煌,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教团是否受了他们的影响而允许僧人拥有家室娶妻生子的。也有的专家认为可能与敦煌地区人口问题有关,性比例失调造成的,当时男性少而女性居多,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除了允许一夫多妻、放松女性出家外,就是僧人承担徭役赋税从军打仗,这样僧人就同一般百姓一样了,没有什么特殊优惠条件,那么僧人犯戒娶妻生子就很正常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宋代笔记史料中找到证据。记载广州有僧人娶妻风俗,《鸡肋编》卷中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蕹度乃成礼。市中亦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但欲簪花其上也。”①这与敦煌地区的情况差不多。
僧人从事商业经营,拥有大量田产财物。吐蕃时期龙藏和尚三年间租种土地收入九十驮粮食,合计家里一千驮。至丑年家内羊三百、牛驴三十头,官田租种收入十二车,造酒收入麦一百三十石、土地三十亩,丝绵磑所罗抵价麦粟一百三十石。尽管这些财物与其兄共有,但也足以证明其富有状况。到归义军时期,我们以索崇恩和尚为例,索崇恩是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都教授,从索崇恩的遗嘱得知,索崇恩拥有土地、牲畜、奴婢、磑所、金银、丝绸等财产,②都表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高僧拥有很多资产。这显然与佛教教义相违背,按照佛教教义的要求,僧人三衣之外没有任何资产,僧人不允许穿戴金银和丝织品,敦煌佛教的榜文也是这样规定的,佛教法会及新度僧尼不允许使用金银器皿、不允许穿戴丝织品,一经发现就要当场毁坏,重者要报官处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实行的是两回事,这很可能由于僧人经常不住寺院,生活在家里,所以拥有资产是很平常的事情。佛教戒律清规的要求只是针对寺院活动的僧尼,而对于生活在家庭的僧尼没有什么限制。僧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也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一大特点,从敦煌文书可以看出,僧人出使在晚唐五代是很平常的事情,归义军建立过程中,僧人在入朝通使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唐悟真和尚从大中二年开始一直到咸通十年他担任都僧统期间,多次来往于敦煌与长安之间。此后每次使团中都有僧人参与,特别是出使的僧人都具有商人的职能,他们出使前都要借贷很多东西,回来后以很高的利息归还,僧人从事贸易的结果,使很多僧人成为富商,同时也使佛教戒律破坏。僧人不仅仅从事长途贩运,而且还开店经营,从事有官工商领域的营利活动。
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清规演变最大的是科罚制度与清规出现。在科罚方面,佛教教团将政府的惩罚规定引入佛教教团中,有很多名称都一样,如令、条、式等。科罚内容分实物科罚和身体体罚两种:实物科罚有酒、饮食和粮食,而体罚主要针对年龄比较小的僧尼,他们没有经济来源,实物科罚难以承担,所以采取杖多少下。①我们中国佛教教团的清规——百丈清规(禅门规式)的制定正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影响很难达到敦煌地区。归义军时期,敦煌基本上是一个半独立性的政权,与中原之间的佛教交往受到一定限制,禅门规式不一定能传入敦煌,因此敦煌地区很难看到百丈清规影响的痕迹,但是敦煌地区佛教的发展产生了自己的类似于清规的东西,形成了他们的区域特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虽然没有保留下来成文的清规一类的东西,但是有在榜文中很多与清规有关的规定的记载。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当时清规的大概情况,认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制定有自己的清规。这种清规有很多称呼,所谓规矩、律式、格令等都是指佛教教团的清规。②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教团的清规与禅宗洪州宗关系密切,敦煌佛教教团的很多规定都与淮海禅师的百丈清规有相似的地方,受到洪州宗的禅门规式影响比较大。但是敦煌佛教教团也有其地域特色,有很多方面在洪州宗百丈清规中严加限定的内容,在敦煌相反不加限定或者限定不严格。
(2)敦煌饮食文化的影响——胡食风气
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的饮食资料,敦煌壁画中也有很多形象资料,这些对于我们研究敦煌饮食十分珍贵。首先从种植粮食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的植物主要有:小麦、青稞、大麦、裸麦、荞麦、粟、糜以及豌豆、荜豆、豇豆、小豆子、大豆、黑豆、绿豆等,以麦为主,其次是粟、豆。除了粮食作物之外,还有各种油料作物,如麻、红兰等;蔬菜有萝卜、生菜、葱韭菜、葫芦等,其中南瓜、冬瓜等也称作葫芦。肉类有猪、牛、羊以及各种野生动物。在这种食物原料的基础上产生的敦煌饮食文化,必然具有中外结合的饮食特色。晚唐五代的敦煌饮食文化既是中西文化交流产物,又融合当时西北少数民族的饮食生活内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除了主体民族汉族之外,有粟特为主的胡姓民族,还有龙家、鄯家等西域民族;吐蕃为主的羌姓民族,包括南山人、萨毗、仲云、温末、吐谷浑等在内;回鹘为主的戎姓民族,包括西州回鹘、甘州回鹘、伊州回鹘和达旦等,敦煌文献称之为六蕃,实际上远不止六个少数民族。到了归义军晚期于阗王室在喀喇汗王朝东进形势的逼迫下也迁居敦煌建立了自己的聚落。归义军管辖下的敦煌是多民族混居区,这里有粟特人的聚落,还有管理这些少数民族的机构蕃部落使等,当时敦煌有通颊退浑等十部落,因此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统称为蕃汉百姓,组成的军队也称蕃汉精兵。由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居民是由多民族结构组成,决定了敦煌饮食文化多元化形态,在敦煌地区的饮食结构中少数民族饮食占了很大比重。我们从敦煌文献中看到很多胡食胡风,如“胡饼”频繁见载于敦煌籍账文书之中,不仅仅少数民族食用,汉族也食用,从官府到民间,从一般居民到出家僧众,平时饮食都食用胡饼。胡饼成了晚唐五代敦煌公私宴用、日常生活必备的食品。就胡饼的种类看,除了一般胡饼之外,还有油胡饼和肉胡饼,特别是肉胡饼也是唐代常见的食品,其做法也见载于唐朝笔记史料中。胡饼的传入与粟特等商业民族的迁入关系密切,胡饼的特点是口味好、制作简单、便于携带、易于保存,特别是长途贩运中饮食非常方便。经过有的专家研究胡饼就是今天新疆一带经常食用的食品——馕,也有人说是芝麻饼。很显然胡食是随着胡姓民族进入敦煌地区而形成一种饮食风气,是敦煌地区胡化的一种表现。唐代中原饮食文化不仅仅接受西域及其外来文明,而且很快在各个阶层中普及开来。《唐语林校证》卷七记载马镇西马燧:“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忽为‘古楼子’。”这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肉馕。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经济结构为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归义军政权专门设置官马院管理驼马养牧、设置羊司管理羊的饲养放牧,官府、百姓都养羊等牲畜,就是每个寺院也养数量不等的羊。我们从记载看,寺院还用羊招待为寺院劳动的工匠以及看望寺院的官吏,寺院僧人经常食用“臛”一类东西。“臛”是肉汤一类的食品,经过研究也有用菜做成的藿,今天酒泉食用的特色饮食“胡锅”,是否就是敦煌文献记载的“臛”?不过寺院所养牧的羊的去向一直是敦煌饮食研究的一个谜。其次,晚唐五代归义军诸司机构中有酒司和官酒户,敦煌市场有酒行,从业人员除了汉人还有很多粟特人,他们开了很多酒店,造酒货卖招徕客人。制造的酒有麦酒、粟酒、粟麦酒、清酒、白醪、葡萄酒、胡酒等种类,根据我们研究当时敦煌已经能够制造高浓度的白酒。就是寺院也大量制造存放酒,甚至有的僧人开店买酒、到酒店饮酒。
(3)马的引进及其敦煌地区马文化
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首先是从马开始的。汉武帝取得河西地区建立河西四郡之后,着手经营西域,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以便取得大宛的汗血马。第一次出征不利,又以敦煌为基地修整,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征伐,最后以大宛贡献500匹的条件结束了战争。实际上这是一次争夺马种的战争,这次战争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河西地区成为中国古代马的生产基地,敦煌地区产生了很多关于马的优美传说,由此而产生敦煌地区的马文化。这里我们列举几例,第一是关于敦煌龙勒山的名称来源,《寿昌县地境》记载“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遗其衔勒,故名龙勒山。”根据中国人的传说,马六尺以上称之为龙,因此把行走速度很快的好马被称之为龙,所谓龙勒山就是传说马勒而得名的。第二是关于龙勒泉的传说,《寿昌县地境》记载“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得骏马,愍而放之。既至此泉,饮水鸣喷,辔衔落地,因以为名。”龙勒泉就在龙勒山下,龙勒山的传说应当与龙勒泉的传说是一致的。这些记载一个来自于周,一个来自于西汉,显然是后代附会武周政权所致。《敦煌地志》记载龙勒山因泉得名,龙勒泉是因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得骏马得名,那么龙勒山显然不可能因西周龙马传说得名。第三是龙堆泉,《寿昌县地境》记载:“昔有骏马,来至此泉,饮水嘶鸣,宛转回旋而去。今验池南有土堆,有似龙头,故号为龙堆泉。”第四是寿昌海,《沙州伊州地志》记载“屈曲周回一里,其深浅不测,汉得天马处也。”①《沙州地志》和《汉书·武帝纪》记载最为详细,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池中,作天马之歌。记载南阳暴利长遭刑屯田,见有野马奇异者常来渥洼池饮水,得以进献。为神异此马,说从渥洼池中出。第五是金鞍山,记载“经夏常有雪,山中有神祠,甚灵,人不敢近,每岁土主望祀,献骏马,驱入山中,稍近,立致雷电风雹之患。”①金鞍山经过考证就是龙勒山,②这种祭祀活动,显然与马有很大关系。归义军时期的《龙泉神剑歌》就是由金鞍山展开歌颂祥瑞的。在敦煌壁画有很多马的图案,河西地区出土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文物,如武威雷台出土的铜车马,还有其他墓葬出土的木马,乃至于有前凉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
敦煌地区中外文化交融碰撞的特征不仅仅体现在以上各个方面,而且在石窟艺术、音乐舞蹈、社会风气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可以说外来文明融合到敦煌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产生了一种带有外来文明特征的新的文化特征。从音乐舞蹈上,所谓的胡腾舞③、胡旋舞在敦煌壁画中反映很多,很多净土图像反映天国或者净土境界,都有乐舞场面,所跳之舞基本上都是胡腾舞或者胡旋舞之类。敦煌文献记载到归义军时期敦煌有乐营使,④专门管理从事音乐舞蹈的音声等,布支出账记载作胡腾衣,可见胡腾舞在当时比较普遍。再从琵琶谱看西域来的乐谱在敦煌比较盛行;从石窟艺术方面来看,曹家样在敦煌地区非常流行,同时张家样、吴家样、周家样等都在敦煌壁画中有体现。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敦煌文献找到很多相应的证据,敦煌文献记载归义军时期向伊州、西州、于阗及甘州、南山等地派遣的使节中就有各类工匠,他们中很多与石窟开凿关系密切,这样的交往必然将敦煌地区的石窟艺术风格传播到其他地方,同时将其他各地的艺术风格传播到敦煌地区,促进敦煌地区石窟艺术的发展。
敦煌是中外交通道路的咽喉之地,外来文明通过敦煌传入中原地区,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敦煌传入西域地区,特别是到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更是这样。由于当时敦煌地区居民是胡汉羌回达怛等多民族居住区,居民结构复杂,由他们带来的中原、西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文化,在敦煌地区首先开始接触,碰撞交融,形成了接纳融汇各种文化为特色的敦煌文化。从总的趋势看晚唐五代丝绸之路是衰退了,但是由于归义军政权历任节度使的经营,出现一个区域发展的高峰时期。
(作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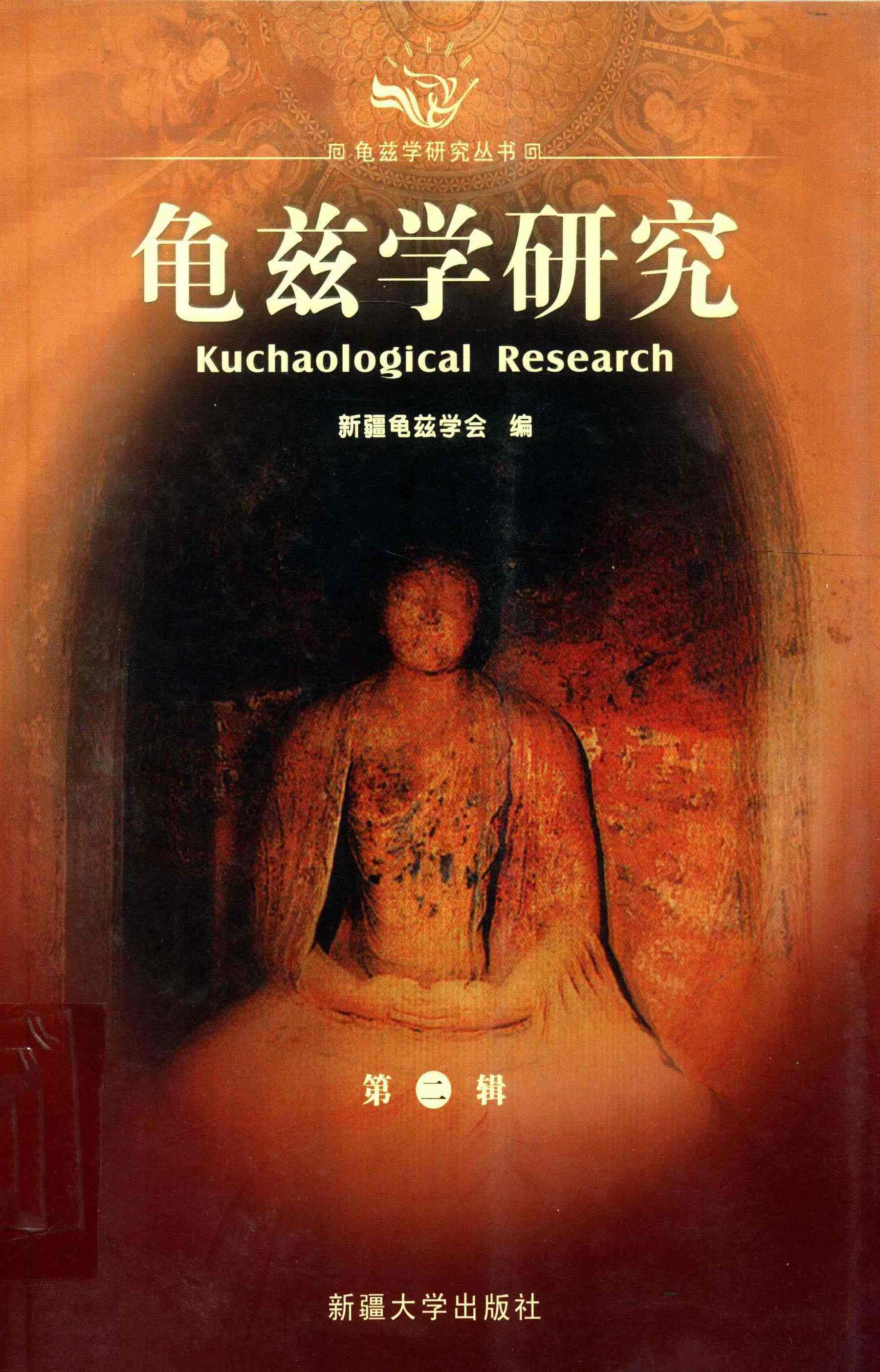
《龟兹学研究 第二辑》
出版者:新疆大学出版社
本书所选论文分为“大家论坛”、“历史研究”、“考古探秘”、“佛教石窟”、“文化艺术”、“史料研究与情报”六个部分。新疆龟兹学会成立已三年有余了。三年来新疆龟兹学会抓了三件事:一是每年召开一次“龟兹学学术研讨会”。二是编辑出版新疆龟兹学会学术刊物《龟兹学研究》。三是进行《龟兹学概论》的编撰工作。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