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疆古代文明的新认识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122 |
| 颗粒名称: | 对新疆古代文明的新认识 |
| 分类号: | K294.5 |
| 页数: | 7 |
| 页码: | 322-32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新疆古代文明的新结论、七角井的证据、古墓沟文化、西汉以前的远古文化遗迹、创新的第一步的研究。 |
| 关键词: | 新疆 古代 史料 |
内容
新疆地区,在中亚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里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亚、欧大陆陆路交通联系的咽喉和桥梁,东西文化曾经在这里交流荟萃,显露过夺目的光采;众多的古代民族,曾以这片广阔的土地为舞台,演出过不少威武雄壮、撼人心魄的历史活剧。至今巍然屹立于地面的不少一两千年前的古代城堡,因特别干燥而得以在地下良好保存的各式遗物,记录着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凝聚着古代各族人民的欢乐和悲辛。这里,是我国有数的考古圣地之一,是我们研究、剖析古代文明的最好现场。而正确把握历史的过去,会使人们更深地理解它的今天,从而也能在迈向未来的征途上,吸取到种种有益的营养。许多人都对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新疆古代文明的具体面目及本质性的特征非常关心。因此,不少国家的学者们,成年累月,就这个课题进行着辛勤的探索。
一、一个新的结论
在遥远的古代,在文献无征的情况下,考古资料是我们认识古代文明最主要、最可靠的手段。A.斯坦因,凭借着他先后三次在新疆地区的考古经历,50年前曾经对新疆地区的古代文明提出过一个深具影响的观点:在伊斯兰文化进入新疆以前,塔里木盆地内“文明上的特征乃是由中国、波斯以及印度三种文化势力混合而成的一种产物”(这里,A.斯坦因将我国与我国境内新疆塔里木盆地并列,当然是明显的错误——引者)。这个观点,贯穿在他卷帙浩繁的有关新疆考古的著述之中。由于A.斯坦因以从事新疆考古著闻于世,又使用着一些考古资料支持
着自己的论点,就使这种观点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一些国外的有关著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个观点影响的存在。
在A.斯坦因的观点中,一个根本的错误是完全无视新疆土著文化的存在,强调文化传播的“外因论”,把邻近地区间自然存在的合理的文化联系因素,夸大到了取代本地区自身文化主体的程度,这就不能不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走到这一步,主要是他在观点上的局限性所致,而考古工作深度、广度的不足,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
通过近四十年新疆地区大量的考古工作实践,使我们有可能对新疆古代文明,作出一个新的结论。
从很遥远的古代起,新疆地区就已经有了古代人类的活动。文物考古工作者,近年已发现了几处可能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的线索。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发现很多,并进行过一定数量的清理和发掘,大量的考古实践,使我们对汉代以前新疆地区的古代文明,有了几个比较明确的概念:新疆地区存在过十分古老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土著文化,它根植在新疆的大地,有着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优点,把它看成某种文化的传播是不正确的;由于新疆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地区自然也存在一定的文化联系,彼此间存在相互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互相的联系和影响日愈扩大而且深入。自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王朝开始,新疆地区进入祖国版图,历代中原王朝或地方性的政权,有效地实行着对这片地区的政治、经济管理,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在这里更是十分广泛而且深入。更早,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它与邻近地区间相类的联系同样存在。从一些具体文化因素分析,与东邻的甘、青、内蒙因地域交通的方便,关系要更加密切一些。这些概念,与A.斯坦因关于新疆古代文明的结论,相去是很远的。
我们引用最近几年中完成的一些工作成果,帮助说明这个问题。
二、七角井的证据
时代可能早到距今9000年上下的七角井细石器文化遗址,是国内外知名的一个所在。遗址位于天山东段七角井盆地内,目前是一片无人的荒漠。红柳、骆驼刺、厉风吹蚀下裸露的沙土,是遗址所在目前的自然景观。2~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光裸发白的沙土地上,我们找到6~7处细石器工具比较集中的地点。在调查中,短短半天,就采集到各类细石器数百件,却绝未见到一小块共生的小陶片。这标示着这个遗址的古老。所见楔状、锥状、柱状石核,大量的细长小石叶,以石叶为基础加工成的小石钻、细石镞,数量不少,型式相当规整,说明当时的细石器加工技术已相当熟练,同类的细石器,新中国成立后在吐鲁番地区、罗布淖尔地区、天山北麓木垒河谷等处也曾有过发现。这些细石器,和我国华北地区所见细石器同属一个类型,在石器制造上有着相同的工艺,表现着在石器加工工艺上确实存在过的彼此交流和影响。从更大的空间范围观察,它仍与蒙古高原、西伯利亚、日本以及阿拉斯加、加拿大的许多遗存有着一定的共性,有力地揭示了从遥远的古代起,包括新疆在内的亚洲广大地区(主要在亚洲东、北部)和美洲西北部之间,存在过相当密切的文化联系。而这种细石叶细石器的起源地就在我国华北地区。
三、古墓沟文化说明什么
近年内,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出土的青铜时代古尸及其所代表的古代文化,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我们认识塔里木盆地东部早期考古文化的具体特点,是一批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古墓沟墓地,东距已经干涸了的罗布淖尔不过70公里,位于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地貌是一片无人的沙丘。在约1600平方米的范围内,我们共发掘得古代墓葬42座。大部分墓葬为竖穴沙室,使用简单的木质葬具。少部分墓葬见七圈环形列木,并有呈辐射状展开的木桩,它们在罗布淖尔盛行的东北季风吹蚀下,地表只留得一个斜向西南的十分光洁的小尖。但在清除积沙后,却如光芒四射的太阳图案,蔚为壮观。两种类型墓葬同属一个文化类型,只是时代早晚有别。
由于特别干燥的自然环境,在这片沙丘上浅埋的竖穴沙室墓葬,都保存得异常完好:木质葬具,盖棺的毛皮、毛布、包裹尸体的毛毯以至人体本身,都还不朽如新。尸体只是因为失水而干缩,形象稍有变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入葬时的穿戴佩饰,以及为死者去到幽冥世界使用而入殉的种种文物,都还基本上保持着入葬时的原状。这就为我们分析罗布荒原上当时土著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历史文化面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一批实物资料。
古墓沟墓地的主人,适应孔雀河谷地带的自然地理特点,经营着以畜牧业为主体的生产。牲畜以羊(包括绵羊、山羊)、牛为主,死者的帽、衣、鞋均以皮、毛为原料,墓内也有表示财富的牛、羊角,可以看到畜牧业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依凭。墓内出土不止一根马鹿骨料制成的锥,骨质致密。禽颊肢骨切割成的小骨珠,串连成人们用为颈部、腕部装饰的骨质项链。加上另一件残破过甚的网,颇为有力地表明了当时狩猎、渔猎的存在,它们是生活资料的一个重要补给源。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里还出土了少量的小麦粒。麦粒均呈深褐色,籽粒形态完整,胚保持完好,麦粒顶端的毛簇尚清楚可见。这些小麦粒,曾经四川农学院颜济教授鉴定,其形态与现代普通小麦无异,是典型的普通小麦。还有一些麦粒,形态虽与此相似,但在其背部紧接胚处,有驼峰状隆起,当为圆锥小麦,它们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小麦实物标本。这一考古资料的发现有力表明近4000年前,我国新疆东部地区已有纯一的普通小麦与普通、圆锥小麦群的存在,这为分析具有中国特色的圆颖多花类型的普通小麦品种的出现,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
古墓沟墓地内没有发现一件陶器,说明他们并没有掌握陶器制作、烧造技术。这样,木器、骨角器、草编器就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用具。不难得到的一段木料,虽木质不一,粗细难均,但只要中部掏挖成空,外表稍经刮削、修整,造型虽然不能划一,盛容液体之目的可达。角杯,只是把角端切断,堵以木塞,其中空的髓腔,就是颇为不错的杯体。此外很好地表现了古墓沟居民们惊人的灵敏和机巧的,是无墓不见的草编器,它们确实可以称得是“化腐朽为神奇”,在罗布荒原上随处可见的野麻、芨芨……这些平淡无奇的禾草类植物,在古墓沟人灵巧的双手下,编制出来各种小巧玲珑的草篓。他们还聪明地利用纬向材料光洁程度的变化,使这些草篓上显示出波状、折曲、菱形等几何形图案,素雅不俗,颇富装饰艺术效果。
古墓沟人的毛纺织工艺,也有值得一说的方面。死者入葬,人人均裸体包覆于毛布或毛毯之中,这些都是以羊绒或羊毛为原料的平纹织物。毛毯,幅宽最大见到有达1.8米的,残长也有1米上下。毛线不算精细,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在6根上下,边缘或饰流苏。这样幅宽的毛织物,明显是用比较原始的竖机所织造。我们在塔里本盆地内及塔什库尔干一些偏僻的农村工作时,曾亲见这类竖机,农民仍以之织毯或毛袋布。古墓沟所见这类毛织物,无疑是我国最古老的毛织物标本,表现了古老传统工艺及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技术水平。关于古墓沟人的毛纺织,还有值得介绍的两点:一是经过检测分析,他们培育的羊绒质量相当好,用现代的概念可纺70支的细毛纱,堪称优良;二是分析表明,这个阶段的古墓沟人,已经大概知道了分等分档使用毛料。粗毛用为搓绳、捻粗线、擀毛毡,细绒捻线,用于织布。这种知识是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毛纺织实践才能总结出来的。
制毡,是古代中亚地区游牧人的又一重大发明,古墓沟所见尖顶毡帽标本,既可有助于认识墓主人的民情风俗,也是难得的毡制品标本:毡色单纯,毡质平匀、厚实,毡帽尖挺,说明制毡水平是相当高的。
在古墓沟人包尸毛织物上,当于死者胸前部位,都见到一小包麻黄碎枝,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例外。这分明是一种信仰崇拜的标志。我们的分析是:麻黄,是罗布荒原随处可见一种药用植物,其化学成分中含生物碱,在一些偶然的机缘中为一些人解除过病痛,经过不知多少次的重复,古墓沟人模模糊糊感到这些罗布荒原上漫生遍布的普通野草竟能对某些病痛有缓解的作用。平淡无奇的麻黄枝于是逐渐具有了一种神圣的地位。这或应是这一原始信仰产生的一种合理物质基础。古墓沟人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老祖母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墓地内出土的五件木雕女性像,说明了这一信息。木雕像比例正确,双乳丰隆、臀部肥硕,显明具有女性特征。这是国内目前所见最早的木质圆雕像,是新疆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留下的艺术杰作。
关于古墓沟墓地的年代,需要在这里稍稍说明。在整个墓地内不见任何汉式文物,而同一地区内的汉代墓葬汉式文物屡见;同时,将这里出土的木器与同一地区内汉墓内出土的木器进行比较,后者型式规整、加工细巧,彼此明显有精粗之别,汉墓中还见到了陶器,可见出早晚之分。因此,可以明确肯定:古墓沟墓地的年代,必然在汉代以前。至于究竟可以早到什么时间,在本地区系统的考古工作很少,还不能从考古学角度做出年代结论的情况下,碳14测定能给我们提供进一步分析的依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碳14实验室曾大力协助将古墓沟墓地内第38号墓葬出土的木棺、毛皮、毛布分别进行测定,年代结论均在距今3800年上下。我们综合分析了其他有关的测定资料,认为这应当是比较可靠的一组数据。如是,古墓沟墓地发掘资料就为我们提供了距今约4000年前后,塔里木盆地内一处古代民族原始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这对我们分析本地区古老的土著文化,研究它们的具体特点,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四、西汉以前的远古文化遗迹
在探讨古代新疆的历史文明这个问题时,较古墓沟墓地时代稍后、在西汉以前,距今3000年前后的哈密五堡原始社会墓地,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鱼儿沟等处自西周晚期到战国阶段的古代墓葬资料、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采掘及冶炼遗址等,都是近年新疆考古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重要成果。
将哈密五堡与古墓沟墓地发掘资料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以五堡为代表的这一物质文化一些十分明显的发展:五堡墓葬的主人,已经普遍使用铜质小刀,它与木器、石器、彩陶器并存,显示了新的特点。由于气候干燥,这里埋葬的古人遗骸,同样形成干尸,穿戴的毡帽、毛布长袍、束腰彩带、彩带绑腿及皮靴,都仍然完好。这些色彩鲜丽的毛织物,已经不是古墓沟那些本色、比较粗糙的平织物所可以比拟的了:它们毛线细匀、织造致密、以斜纹组织为主、色彩仍然新鲜。不论是捻线、织造、染色、图案设计等各个生产环节,均可见出显著的发展与进步。那些致密、厚实的斜纹织物,每平方厘米经纬线达到18根上下。红、褐、蓝、黄等不同色彩,经历数千年的考验,色泽不退。方格、彩条等几何形图案,设计美观大方,见者无不称绝。毛纺织,是新疆地区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一项优秀创造,曾以它的经磨耐用、厚实保暖而为人们所称道。从古墓沟到哈密五堡的出土毛织物标本可以看到,毛纺织工艺在新疆地区具有十分悠久的传统,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发扬的一项优秀文化遗产。
前几年,新疆地区地质科学工作者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尼勒克县奴拉赛战国时期铜矿采掘及冶炼遗址,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发现。古代矿井、坑道、坑木支架都清楚可见。用来采掘的大型石器、炼铜的矿砟、碗形的白冰铜坯,发现不少。初步分析表明,它与我国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水平相去不远,采矿工具形制近同,对于分析当时新疆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与内地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新疆什么时间开始用铁,这也是一个人们十分关心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阿拉沟、鱼儿沟地区,配合南疆铁路工程,笔者曾先后工作三个年头,发掘清理了古代墓葬100多座。在一批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墓葬中,较普遍地发现了小铁刀。足见战国时期,这里已经使用着铁器,至于是否是最早的铁器标本,它们是本地冶造还是交换自邻近地区,只从阿拉沟墓葬一处资料,还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
阿拉沟、鱼儿沟墓地,延续时间相当长。据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经历过一个发展阶段。碳14测定数据,也表明时代早到西周后期,晚到战国末。墓地散布于山谷台地,墓内出土多量羊、骡、马骨及木质牧业生产工具如腿绊、鼻栓等,它们与多量彩陶器共存。说明这里即使是以牧业为主体的经济生活,相对的定居也是明显存在的,在彩陶器的花纹图案中,可以看到甘、青地区古代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这里出土的多量毛织物,水平也远较古墓沟地区为高,发展进步的脉络同样是清楚的。
在阿拉沟发掘的几座规模较大的竖穴木椁墓,墓内大量积石。多量虎纹金饰牌、金箔饰片、双狮铜方座与土质细腻、火候很高的陶器共存。小铁刀穿插羊骨置于木盆内。它们与漆器、绫纹丝罗等明显来自中原的珍品并存于一室,颇为形象地显示了战国时期这一地区内民族文化生活的面貌。据金器、铜器造型及兽纹图案特征分析,应为古代塞人的遗物。塞人,曾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有关发掘资料,对了解我国古代塞人的活动地域及其经济文化面貌,研究古代新疆民族历史,均有重要价值。
五、创新的第一步
汉代以后新疆地区的情况,汉文古籍及其他民族古文字资料中,保留了相当丰富的记录。但在西汉以前,古代新疆地区的民族文化面目,仅从文献就不能得到清楚明白的概念了,要获得这一遥远的古代时期内历史文明的真面目,主要必须凭借考古学资料。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考古实践,我们对新疆地区的古代文明,逐步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对这片地区内具有地区特色、民族特色的考古文化,逐步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前面提到的几个实例多少可以帮助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它们是明显具有新疆地区特色的文化,适应新疆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创造。它们与周围几个古代文明中心,尤其是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联系交往是肯定存在的,在稍后一个历史时期内,这种联系、交往更加明显,其积极意义也不应轻视。汉代新疆统一于中原王朝的版图,这就是一个基础。但即使如此,对于本地区的民族文化,还是要给予足够的认识、充分的研究,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完善,根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对新疆古代文明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与A.斯坦因所代表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同样受考古实践深度、广度的局限,我们今天的认识也只能说是迈出了创新的第一步。随着今后田野考古工作及室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深入,可以预期,我们的这个认识也必然会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对新疆古代文明的认识将会更加深刻,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
一、一个新的结论
在遥远的古代,在文献无征的情况下,考古资料是我们认识古代文明最主要、最可靠的手段。A.斯坦因,凭借着他先后三次在新疆地区的考古经历,50年前曾经对新疆地区的古代文明提出过一个深具影响的观点:在伊斯兰文化进入新疆以前,塔里木盆地内“文明上的特征乃是由中国、波斯以及印度三种文化势力混合而成的一种产物”(这里,A.斯坦因将我国与我国境内新疆塔里木盆地并列,当然是明显的错误——引者)。这个观点,贯穿在他卷帙浩繁的有关新疆考古的著述之中。由于A.斯坦因以从事新疆考古著闻于世,又使用着一些考古资料支持
着自己的论点,就使这种观点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一些国外的有关著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个观点影响的存在。
在A.斯坦因的观点中,一个根本的错误是完全无视新疆土著文化的存在,强调文化传播的“外因论”,把邻近地区间自然存在的合理的文化联系因素,夸大到了取代本地区自身文化主体的程度,这就不能不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走到这一步,主要是他在观点上的局限性所致,而考古工作深度、广度的不足,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
通过近四十年新疆地区大量的考古工作实践,使我们有可能对新疆古代文明,作出一个新的结论。
从很遥远的古代起,新疆地区就已经有了古代人类的活动。文物考古工作者,近年已发现了几处可能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的线索。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发现很多,并进行过一定数量的清理和发掘,大量的考古实践,使我们对汉代以前新疆地区的古代文明,有了几个比较明确的概念:新疆地区存在过十分古老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土著文化,它根植在新疆的大地,有着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优点,把它看成某种文化的传播是不正确的;由于新疆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地区自然也存在一定的文化联系,彼此间存在相互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互相的联系和影响日愈扩大而且深入。自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王朝开始,新疆地区进入祖国版图,历代中原王朝或地方性的政权,有效地实行着对这片地区的政治、经济管理,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在这里更是十分广泛而且深入。更早,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它与邻近地区间相类的联系同样存在。从一些具体文化因素分析,与东邻的甘、青、内蒙因地域交通的方便,关系要更加密切一些。这些概念,与A.斯坦因关于新疆古代文明的结论,相去是很远的。
我们引用最近几年中完成的一些工作成果,帮助说明这个问题。
二、七角井的证据
时代可能早到距今9000年上下的七角井细石器文化遗址,是国内外知名的一个所在。遗址位于天山东段七角井盆地内,目前是一片无人的荒漠。红柳、骆驼刺、厉风吹蚀下裸露的沙土,是遗址所在目前的自然景观。2~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光裸发白的沙土地上,我们找到6~7处细石器工具比较集中的地点。在调查中,短短半天,就采集到各类细石器数百件,却绝未见到一小块共生的小陶片。这标示着这个遗址的古老。所见楔状、锥状、柱状石核,大量的细长小石叶,以石叶为基础加工成的小石钻、细石镞,数量不少,型式相当规整,说明当时的细石器加工技术已相当熟练,同类的细石器,新中国成立后在吐鲁番地区、罗布淖尔地区、天山北麓木垒河谷等处也曾有过发现。这些细石器,和我国华北地区所见细石器同属一个类型,在石器制造上有着相同的工艺,表现着在石器加工工艺上确实存在过的彼此交流和影响。从更大的空间范围观察,它仍与蒙古高原、西伯利亚、日本以及阿拉斯加、加拿大的许多遗存有着一定的共性,有力地揭示了从遥远的古代起,包括新疆在内的亚洲广大地区(主要在亚洲东、北部)和美洲西北部之间,存在过相当密切的文化联系。而这种细石叶细石器的起源地就在我国华北地区。
三、古墓沟文化说明什么
近年内,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出土的青铜时代古尸及其所代表的古代文化,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我们认识塔里木盆地东部早期考古文化的具体特点,是一批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古墓沟墓地,东距已经干涸了的罗布淖尔不过70公里,位于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地貌是一片无人的沙丘。在约1600平方米的范围内,我们共发掘得古代墓葬42座。大部分墓葬为竖穴沙室,使用简单的木质葬具。少部分墓葬见七圈环形列木,并有呈辐射状展开的木桩,它们在罗布淖尔盛行的东北季风吹蚀下,地表只留得一个斜向西南的十分光洁的小尖。但在清除积沙后,却如光芒四射的太阳图案,蔚为壮观。两种类型墓葬同属一个文化类型,只是时代早晚有别。
由于特别干燥的自然环境,在这片沙丘上浅埋的竖穴沙室墓葬,都保存得异常完好:木质葬具,盖棺的毛皮、毛布、包裹尸体的毛毯以至人体本身,都还不朽如新。尸体只是因为失水而干缩,形象稍有变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入葬时的穿戴佩饰,以及为死者去到幽冥世界使用而入殉的种种文物,都还基本上保持着入葬时的原状。这就为我们分析罗布荒原上当时土著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历史文化面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一批实物资料。
古墓沟墓地的主人,适应孔雀河谷地带的自然地理特点,经营着以畜牧业为主体的生产。牲畜以羊(包括绵羊、山羊)、牛为主,死者的帽、衣、鞋均以皮、毛为原料,墓内也有表示财富的牛、羊角,可以看到畜牧业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依凭。墓内出土不止一根马鹿骨料制成的锥,骨质致密。禽颊肢骨切割成的小骨珠,串连成人们用为颈部、腕部装饰的骨质项链。加上另一件残破过甚的网,颇为有力地表明了当时狩猎、渔猎的存在,它们是生活资料的一个重要补给源。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里还出土了少量的小麦粒。麦粒均呈深褐色,籽粒形态完整,胚保持完好,麦粒顶端的毛簇尚清楚可见。这些小麦粒,曾经四川农学院颜济教授鉴定,其形态与现代普通小麦无异,是典型的普通小麦。还有一些麦粒,形态虽与此相似,但在其背部紧接胚处,有驼峰状隆起,当为圆锥小麦,它们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小麦实物标本。这一考古资料的发现有力表明近4000年前,我国新疆东部地区已有纯一的普通小麦与普通、圆锥小麦群的存在,这为分析具有中国特色的圆颖多花类型的普通小麦品种的出现,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
古墓沟墓地内没有发现一件陶器,说明他们并没有掌握陶器制作、烧造技术。这样,木器、骨角器、草编器就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用具。不难得到的一段木料,虽木质不一,粗细难均,但只要中部掏挖成空,外表稍经刮削、修整,造型虽然不能划一,盛容液体之目的可达。角杯,只是把角端切断,堵以木塞,其中空的髓腔,就是颇为不错的杯体。此外很好地表现了古墓沟居民们惊人的灵敏和机巧的,是无墓不见的草编器,它们确实可以称得是“化腐朽为神奇”,在罗布荒原上随处可见的野麻、芨芨……这些平淡无奇的禾草类植物,在古墓沟人灵巧的双手下,编制出来各种小巧玲珑的草篓。他们还聪明地利用纬向材料光洁程度的变化,使这些草篓上显示出波状、折曲、菱形等几何形图案,素雅不俗,颇富装饰艺术效果。
古墓沟人的毛纺织工艺,也有值得一说的方面。死者入葬,人人均裸体包覆于毛布或毛毯之中,这些都是以羊绒或羊毛为原料的平纹织物。毛毯,幅宽最大见到有达1.8米的,残长也有1米上下。毛线不算精细,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在6根上下,边缘或饰流苏。这样幅宽的毛织物,明显是用比较原始的竖机所织造。我们在塔里本盆地内及塔什库尔干一些偏僻的农村工作时,曾亲见这类竖机,农民仍以之织毯或毛袋布。古墓沟所见这类毛织物,无疑是我国最古老的毛织物标本,表现了古老传统工艺及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技术水平。关于古墓沟人的毛纺织,还有值得介绍的两点:一是经过检测分析,他们培育的羊绒质量相当好,用现代的概念可纺70支的细毛纱,堪称优良;二是分析表明,这个阶段的古墓沟人,已经大概知道了分等分档使用毛料。粗毛用为搓绳、捻粗线、擀毛毡,细绒捻线,用于织布。这种知识是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毛纺织实践才能总结出来的。
制毡,是古代中亚地区游牧人的又一重大发明,古墓沟所见尖顶毡帽标本,既可有助于认识墓主人的民情风俗,也是难得的毡制品标本:毡色单纯,毡质平匀、厚实,毡帽尖挺,说明制毡水平是相当高的。
在古墓沟人包尸毛织物上,当于死者胸前部位,都见到一小包麻黄碎枝,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例外。这分明是一种信仰崇拜的标志。我们的分析是:麻黄,是罗布荒原随处可见一种药用植物,其化学成分中含生物碱,在一些偶然的机缘中为一些人解除过病痛,经过不知多少次的重复,古墓沟人模模糊糊感到这些罗布荒原上漫生遍布的普通野草竟能对某些病痛有缓解的作用。平淡无奇的麻黄枝于是逐渐具有了一种神圣的地位。这或应是这一原始信仰产生的一种合理物质基础。古墓沟人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老祖母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墓地内出土的五件木雕女性像,说明了这一信息。木雕像比例正确,双乳丰隆、臀部肥硕,显明具有女性特征。这是国内目前所见最早的木质圆雕像,是新疆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留下的艺术杰作。
关于古墓沟墓地的年代,需要在这里稍稍说明。在整个墓地内不见任何汉式文物,而同一地区内的汉代墓葬汉式文物屡见;同时,将这里出土的木器与同一地区内汉墓内出土的木器进行比较,后者型式规整、加工细巧,彼此明显有精粗之别,汉墓中还见到了陶器,可见出早晚之分。因此,可以明确肯定:古墓沟墓地的年代,必然在汉代以前。至于究竟可以早到什么时间,在本地区系统的考古工作很少,还不能从考古学角度做出年代结论的情况下,碳14测定能给我们提供进一步分析的依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碳14实验室曾大力协助将古墓沟墓地内第38号墓葬出土的木棺、毛皮、毛布分别进行测定,年代结论均在距今3800年上下。我们综合分析了其他有关的测定资料,认为这应当是比较可靠的一组数据。如是,古墓沟墓地发掘资料就为我们提供了距今约4000年前后,塔里木盆地内一处古代民族原始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这对我们分析本地区古老的土著文化,研究它们的具体特点,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四、西汉以前的远古文化遗迹
在探讨古代新疆的历史文明这个问题时,较古墓沟墓地时代稍后、在西汉以前,距今3000年前后的哈密五堡原始社会墓地,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鱼儿沟等处自西周晚期到战国阶段的古代墓葬资料、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采掘及冶炼遗址等,都是近年新疆考古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重要成果。
将哈密五堡与古墓沟墓地发掘资料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以五堡为代表的这一物质文化一些十分明显的发展:五堡墓葬的主人,已经普遍使用铜质小刀,它与木器、石器、彩陶器并存,显示了新的特点。由于气候干燥,这里埋葬的古人遗骸,同样形成干尸,穿戴的毡帽、毛布长袍、束腰彩带、彩带绑腿及皮靴,都仍然完好。这些色彩鲜丽的毛织物,已经不是古墓沟那些本色、比较粗糙的平织物所可以比拟的了:它们毛线细匀、织造致密、以斜纹组织为主、色彩仍然新鲜。不论是捻线、织造、染色、图案设计等各个生产环节,均可见出显著的发展与进步。那些致密、厚实的斜纹织物,每平方厘米经纬线达到18根上下。红、褐、蓝、黄等不同色彩,经历数千年的考验,色泽不退。方格、彩条等几何形图案,设计美观大方,见者无不称绝。毛纺织,是新疆地区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一项优秀创造,曾以它的经磨耐用、厚实保暖而为人们所称道。从古墓沟到哈密五堡的出土毛织物标本可以看到,毛纺织工艺在新疆地区具有十分悠久的传统,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发扬的一项优秀文化遗产。
前几年,新疆地区地质科学工作者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尼勒克县奴拉赛战国时期铜矿采掘及冶炼遗址,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发现。古代矿井、坑道、坑木支架都清楚可见。用来采掘的大型石器、炼铜的矿砟、碗形的白冰铜坯,发现不少。初步分析表明,它与我国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水平相去不远,采矿工具形制近同,对于分析当时新疆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与内地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新疆什么时间开始用铁,这也是一个人们十分关心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阿拉沟、鱼儿沟地区,配合南疆铁路工程,笔者曾先后工作三个年头,发掘清理了古代墓葬100多座。在一批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墓葬中,较普遍地发现了小铁刀。足见战国时期,这里已经使用着铁器,至于是否是最早的铁器标本,它们是本地冶造还是交换自邻近地区,只从阿拉沟墓葬一处资料,还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
阿拉沟、鱼儿沟墓地,延续时间相当长。据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经历过一个发展阶段。碳14测定数据,也表明时代早到西周后期,晚到战国末。墓地散布于山谷台地,墓内出土多量羊、骡、马骨及木质牧业生产工具如腿绊、鼻栓等,它们与多量彩陶器共存。说明这里即使是以牧业为主体的经济生活,相对的定居也是明显存在的,在彩陶器的花纹图案中,可以看到甘、青地区古代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这里出土的多量毛织物,水平也远较古墓沟地区为高,发展进步的脉络同样是清楚的。
在阿拉沟发掘的几座规模较大的竖穴木椁墓,墓内大量积石。多量虎纹金饰牌、金箔饰片、双狮铜方座与土质细腻、火候很高的陶器共存。小铁刀穿插羊骨置于木盆内。它们与漆器、绫纹丝罗等明显来自中原的珍品并存于一室,颇为形象地显示了战国时期这一地区内民族文化生活的面貌。据金器、铜器造型及兽纹图案特征分析,应为古代塞人的遗物。塞人,曾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有关发掘资料,对了解我国古代塞人的活动地域及其经济文化面貌,研究古代新疆民族历史,均有重要价值。
五、创新的第一步
汉代以后新疆地区的情况,汉文古籍及其他民族古文字资料中,保留了相当丰富的记录。但在西汉以前,古代新疆地区的民族文化面目,仅从文献就不能得到清楚明白的概念了,要获得这一遥远的古代时期内历史文明的真面目,主要必须凭借考古学资料。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考古实践,我们对新疆地区的古代文明,逐步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对这片地区内具有地区特色、民族特色的考古文化,逐步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前面提到的几个实例多少可以帮助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它们是明显具有新疆地区特色的文化,适应新疆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创造。它们与周围几个古代文明中心,尤其是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联系交往是肯定存在的,在稍后一个历史时期内,这种联系、交往更加明显,其积极意义也不应轻视。汉代新疆统一于中原王朝的版图,这就是一个基础。但即使如此,对于本地区的民族文化,还是要给予足够的认识、充分的研究,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完善,根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对新疆古代文明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与A.斯坦因所代表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同样受考古实践深度、广度的局限,我们今天的认识也只能说是迈出了创新的第一步。随着今后田野考古工作及室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深入,可以预期,我们的这个认识也必然会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对新疆古代文明的认识将会更加深刻,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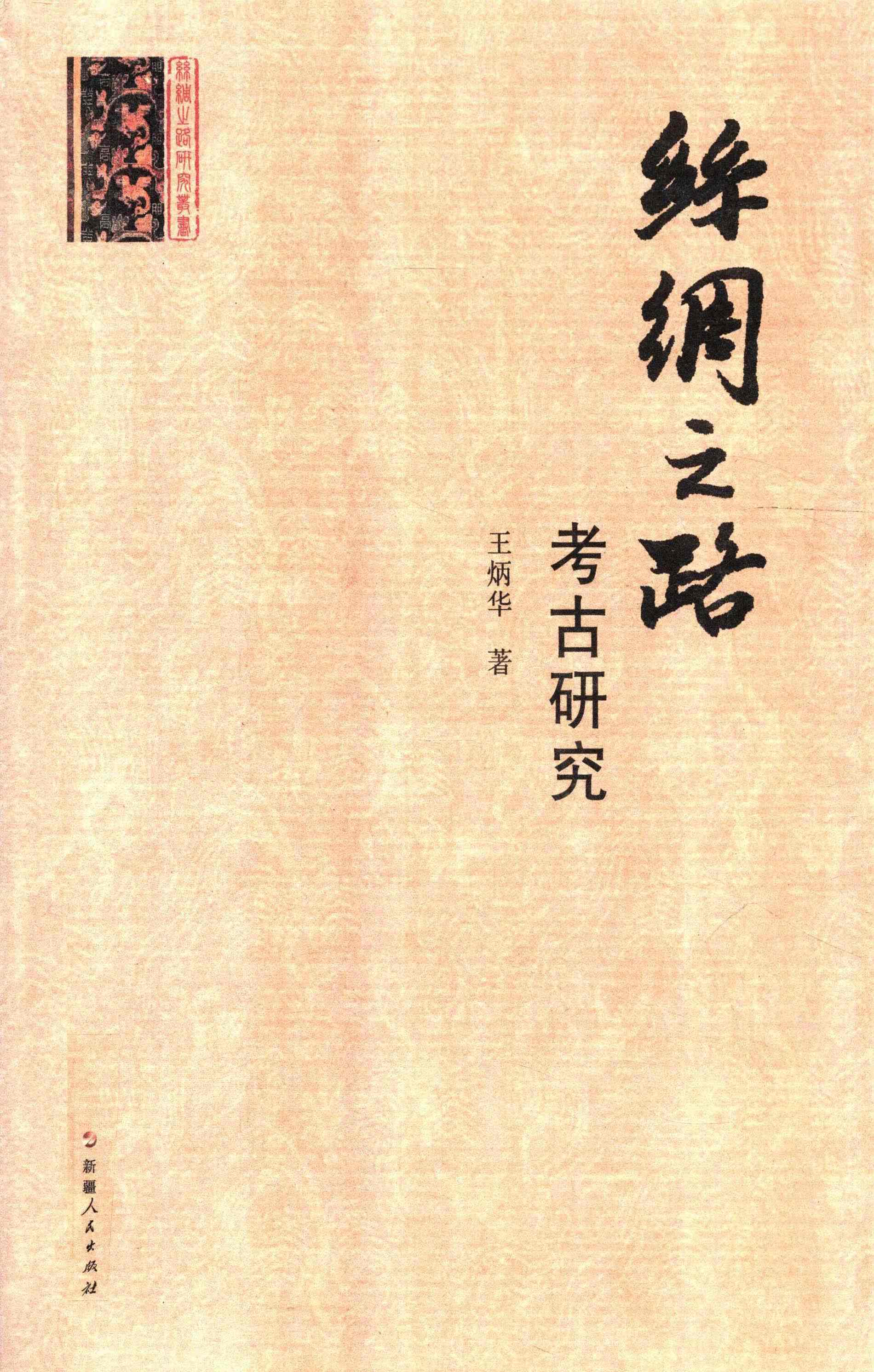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