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105 |
| 颗粒名称: | 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 |
| 分类号: | K879 |
| 页数: | 7 |
| 页码: | 256-26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新疆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包括新地沟石人、苇湖沟石人、牛庄子石人、奇台石人、巴里坤石人等。 |
| 关键词: | 新疆 天山东部 石雕人像 |
内容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从蒙古高原到新疆、中亚哈萨克斯坦广大地区存在一种石雕人像。中外学者,对它们也早有报导及研究,最主要的结论是:这类石刻或石雕人像,是6~9世纪(或说7~12世纪)期间古代突厥人的墓前造像①。
关于新疆地区这类石人造像的分布地域,见于报导的,主要及于阿勒泰地区,尤其是阿勒泰的克尔木齐②;博尔塔拉地区温泉县的乌拉斯台草原、阿尔卡特草原③;伊犁昭苏县的柯达和尔、阿克牙孜④;小洪那海(即昭苏种马场)叶森培孜尔、哈萨克培孜尔⑤;霍城县库鲁斯⑥等处。这些报导,当然是很不完全的,据笔者个人调查记录,阿勒泰地区全境,就是县县皆有石人,凡水草较好的优良牧场所在,一般就可发现石人石棺遗迹。足见,已见的报导资料与实际存在,差距颇大。
天山地带,过去几乎还没见到过有关石人的报导。据李征同志面告,在乌鲁木齐南郊柴窝堡湖畔,曾发现过石人,但始终未见正式文字报告。而对于这类遗迹,进行翔实的调查,附之以准确的地图,对于研究古代突厥人的分布地域,认识其主要的活动中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科学资料。1983年,笔者偕新疆考古所伊弟利斯·阿不都、邢开鼎、伊列·尼加提、祁小山等先生,自乌鲁木齐出发,沿天山北麓向东,经米泉、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直至巴里坤,进行考古调查,见到了一些古代遗址、古城石人、古墓、驿烽等,所获甚丰。其中石人材料,不少是过去所未见。为助于有关“石人”的专题研究,这里略为报导,并草书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石人像遗迹,目前只见于吉木萨尔、奇台和巴里坤三县。
吉木萨尔县,主要分布在天山脚下的新地沟、苇湖沟、贼疙瘩梁等处;奇台县,见于半截沟;巴里坤县,见于石人子乡。都是近山脚一些水草较好,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
一、新地沟石人
新地沟,在今吉木萨尔县西南,县林场所在。山沟内林木苍郁,沟口为白杨,上面生长着松杉。山梁上绿草如茵,沟内水流清澈。目前已垦为耕地的沟谷东岸,林场场部稍南的地方,当地称为“石人滩”,因为这里曾经伫立多个石人,故相沿成俗。据老人回忆,至少有五六个以上,石人多面东,其身后多有土、石堆,我们踏勘遗址时,仅见扑倒的二座。其中之一,即由县文化馆李功仁同志主持运回县城,存县文化馆。石人所在山梁,调查中曾采集到骨片。有关石人的具体情况是:
其一,高152厘米、宽42厘米、厚22厘米,花岗岩质。头部特征刻画较细:宽圆脸型、颧骨较高、浓眉,眼、鼻、嘴轮廓清楚。嘴唇上方,有两撇八字胡。双耳垂饰耳环,颈部,刻圆环一道。衣纹未刻画,也不见一般石人常有持杯、抚剑的特征。脑后,刻斜线两道,环带一道止于耳后,其下,有小刀一把(图116)。
其二,块石高150厘米、宽50厘米、厚16~40厘米,花岗岩质,青色,块石成不规则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块石并未清楚刻画出人物面部形象,只是在相当于人的头部,刻画平行斜线五道,延及块石的两侧面。在其一侧,斜线是复刻一圆环。相当于上身躯干部位,刻划一圆环、一短刀,一条弧线围绕两条平行绕。这在新疆,还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刻石资料(图117)。
二、苇湖沟石人
苇湖沟,居县城西南,近天山脚下,与新地沟东西并列,相距约8公里。自苇湖大队骑马入山,有山道可抵达坂城,算得一处隘道。说是“苇湖”,目前田连阡陌,地面不见苇湖痕迹。石人立于苇湖大队门口一土埂边。但这并不是原来位置,据说最初在一条地势较高的土梁上,目前所见情况是:石质为青灰色花岗岩,较扁平。地面以上的高度为116厘米、宽62厘米、厚20厘米。形象特征是:脸型偏长,下颏稍尖,眼大,鼓突若菱形,鼻准较高。唇上鼻下属两撇唇须,八字展开,尾端上翘,嘴唇紧闭向下,显得神态威严,不可侵犯。唇下垂山羊胡一撮。大耳,耳下垂环。颏下有左右向对称张开的斜线六道,似为须髯。其下衣服、武器、手势及持物等,均未见刻画(图118)。
三、牛庄子石人
牛庄子在吉木萨尔县泉子街乡。其西为贼疙瘩梁,梁上有古城一座。自吉木萨尔越天山到吐鲁番的古代重要交通路线——他地道,就是通过这片地区南入天山。石人原在牛庄子村。石人近旁有大石墓一座,直径20多米,老乡浇地时,发现这里跑水严重,经发掘,见大石棺。后重又掩埋,未开棺清理。
石人,现已移至一马厩墙边。高80厘米(地面以上)、顶宽40厘米、下宽60厘米。花岗岩质,青黑色。面部形象尚清楚,眉、眼、鼻、嘴位置准确。眉弓曲,眼鼓成圆形,鼻直,小嘴,脸型稍圆,头、肩分隔处,稍内收,肩部以下则为自然形状,未经刻画。
四、奇台石人
奇台县内,目前只见石入一躯,原在县城东南,天山北
麓之半截沟。这里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由半截沟入山,有
山道可越天山至鄯善县,石人原在半截沟供销社前,这并
不是原来的位置。现已入藏奇台县文化馆供人观览。石人
以花岗岩为料,通高146厘米、面宽39厘米、石厚20厘
米。刻画较为精细,脸型宽圆,下颏部稍尖凸,似山羊胡。
眼近圆形。鼻下现两撇小须。右手持杯上举至胸前,左手
下抚剑柄。衣饰未刻画(图119)。
五、巴里坤石人
巴里坤县,目前也只见石入一座。原在县城东四十多公里之石人子乡。“石人子”一地之得名,当与此石人遗迹有关,足见清代或清代以前,人们即已注意到这一石人的存在。石人原在石人子村南,天山脚下,后被人移至一渠道边,现存巴里坤县文化馆陈列室。石人用料为细沙岩、青灰色。块石不规整。通宽95厘米、宽34~50厘米、厚20厘米。头部用浅浮雕手法,刻画出人面形象:浓眉、圆眼、鼻隆起、嘴小、无须。头部以下,均为原石,未作任何刻画。巴里坤石人,是天山地区所见地理位置最东的一座。
由于只是地面的一般调查,上述石人资料,自然还难说乌鲁木齐以东天山地区的全部石人材料。因为没有发掘,而且几乎全部石人均已脱离了最初的原始位置,影响了我们对石人像性质的认识。但即使如此,从这点有限的资料,仍可见出不少问题。
第一,国内外历史考古界,有一个差不多一致的观点:从蒙古高原,到新疆广大地区,前苏联的阿尔泰、哈萨克斯坦等,在这么广大的地域内存在的古代石人遗迹,主要是与古代突厥民族有关的一种历史遗存①。而根据古文献记录和突厥人的传说可知,在阿勒泰之南,高昌西北,也就是天山北麓至阿勒泰草原,是古代突厥民族的发祥地②。这片地区,也是后来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主要地域。当然,在这片地区内,保留下来较多的突厥族遗存,是并不令人奇怪的。但在以前发表的资料中,有关石人遗迹,都只见于阿勒泰、博尔塔拉、伊犁地区。乌鲁木齐以东的天山地带,即突厥民族的发祥地却没有见到具体报导。本文的报导,从资料上填补了这一空白,说明在乌鲁木齐以东的天山地区,石人也是同样存在的。目前的资料,虽还只见于吉木萨尔、奇台、巴里坤三县,但今后随着工作的深入,在乌鲁木齐地区、阜康、木垒等县境内,尤其是近天山北麓的山前地带,继续发现这类石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这类石人像的时代、作用,正如前面提到的,一般都认为与隋唐时期突厥人的埋藏制度有关。根据汉文史籍中的有关记录,如《旧唐书》称,阙特勤死,李唐王朝即派金吾将军古逸、都官郎中吕向至突厥王国致祭,由皇帝为之撰写碑文,立祠庙,并“刻石为像”,以致纪念①。另一位芯伽可汗,身死后,也有立像的记录②。这说明,突厥人在死后,确有在墓前立像的习惯。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曾对博尔塔拉温泉县阿尔卡特石人(此石人现在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部陈列。圆脸、大目,颧骨较高、八字胡,身着反领大衣,腰系带,带上佩系小刀。右手持杯至胸前,左手抚刀剑柄。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类型)身后的石棺进行过发掘,除见碎骨、骨灰外,未见其他文物。说明实行火葬。这种火葬习俗,也是见于文献记录的突厥民族曾经实行过的一种葬俗。如《周书·突厥传》提到,突厥在人死后,“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具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旧唐书·突厥传》也记述,7世纪中叶,颉利可汗死,“诏其国人葬之,从其礼俗,焚尸干霸水之东”。将死后立像及火葬这两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说明有一类石人作为石棺火葬墓前的立像标志,是隋唐时期突厥人的象征,大概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另一问题:新疆广大地区内石人形象的特征,彼此差别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如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的石人造型,我们这里介绍的奇台半截沟石人,就属于同一类型;但还有很大部分石人造型,从面部形象到衣服、佩饰等,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不是存在着时代的前后不同?如是,那么石人所代表主人的民族身份是不是也应该有不同?我们前面介绍的6座石人,就清楚显示了这种差异:有的只刻画出面部轮廓,有的在面部形象上清楚显示了不同的特征,对这种差别,看来不应忽略。但是,要求得出明确的结论,必须结合着对石人身后的墓葬进行发掘,并比较研究发掘资料。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太少,进一步分析还有困难。但也有一些发掘资料,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说明。在阿勒泰克尔木齐发掘的一批石棺墓,不少墓前立有石人。这些石入一部分形象就比较简单,甚至只是利用一块椭圆形卵石刻画出人的面部形象。这和阿尔卡特石人所代表的一种类型,明显存在差别,而墓地发掘资料也表明:它们的时代较早。墓前立有石人的墓葬,实行的是土葬,随葬文物,有石镞、石质容器、陶器、铜器①。这和阿尔卡特石人火葬墓,就显示了明显的时代、葬俗上的不同。明确这一点,并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探明、研究这种差异,找出其演变、发展的规律,无疑对于我们认识这类以石人为代表的考古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有很大意义的。
第三,古籍记载突厥民族源起于“金山之阳”。目前,最早见到的汉文史籍是《周书·异域传·突厥》,时代已相当晚,这时期的突厥,作为柔然汗国统治下的一个游牧部落,力量已很强大,这当然不应该是突厥族最初的情况。从隋、唐时期突厥族人的墓葬前立石为像这一习俗看,可以把墓前竖立石人像,作为突厥考古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因此,在阿勒泰草原(金山之阳)发现的、数量相当多的早期石人及墓葬,应该是与突厥考古文化有密切关系,它们是突厥早期文化的一种遗存;或者,可以说,它们是形成后来突厥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无论如何,即使只从石人,或墓前竖立石人像这一重要葬俗看,是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其继承、发展关系的。如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一个逻辑的推论就是:古代突厥人,在阿勒泰地区的居住和活动历史,是十分古老的。它们的时代,远及公元以前。隋、唐时期,影响远布的突厥汗国的传统文化,奠基在一个很深厚的历史基础上。
第四,当突厥兴起以后,势力强大,在东、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下,居民的种族成分大概也是很复杂的。这种情况,应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研究,从考古工作角度,发掘出土的人骨及一些墓葬前的石人立像,就是第一手资料。如前所述,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阿尔卡特石人形象,具有很鲜明的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而吉木萨尔县苇湖沟石人,就表现了完全不同的形象。这是刻画得很有性格特点的一具石人,狭长的面庞上大眼圆睁,高鼻,须髯飞张,这些,都明显具有白种人特点。而石人紧闭的嘴唇,嘴角向下,更十分增强了石人形象的威严,显示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说明了它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可能是某一级的领袖人物。这类资料,集中起来,就足以说明突厥汗国属下相当复杂的居民种族成分。
第五,在吉木萨尔县新地沟(石人滩)所见一件刻石:不见人面形象,但见斜线、圆环、配刀,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新资料。这种刻石,苏联学者称之为“鹿石”①,他们认为这种“鹿石”(石刻上曾见鹿的形象)是一种公式化了的石人形象:在头的部位刻两条或三条斜线,就是代替人面。虽然,它们的含意至今并不完全清楚,但躯干部分的刀或其他刻图案,则表示着武士身上佩系的武器等物。这类石刻,据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前后的一种遗存,而且认为是与古代萨迦人(塞人)有关的一种遗存。它们也是墓葬前面的标志。苏联学者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工作,当然具有参考价值。但结合新疆的发现,究竟是什么情况,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掘才能具体说明。目前应该更深入地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保护或科学发掘工作,使它们的科学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
关于新疆地区这类石人造像的分布地域,见于报导的,主要及于阿勒泰地区,尤其是阿勒泰的克尔木齐②;博尔塔拉地区温泉县的乌拉斯台草原、阿尔卡特草原③;伊犁昭苏县的柯达和尔、阿克牙孜④;小洪那海(即昭苏种马场)叶森培孜尔、哈萨克培孜尔⑤;霍城县库鲁斯⑥等处。这些报导,当然是很不完全的,据笔者个人调查记录,阿勒泰地区全境,就是县县皆有石人,凡水草较好的优良牧场所在,一般就可发现石人石棺遗迹。足见,已见的报导资料与实际存在,差距颇大。
天山地带,过去几乎还没见到过有关石人的报导。据李征同志面告,在乌鲁木齐南郊柴窝堡湖畔,曾发现过石人,但始终未见正式文字报告。而对于这类遗迹,进行翔实的调查,附之以准确的地图,对于研究古代突厥人的分布地域,认识其主要的活动中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科学资料。1983年,笔者偕新疆考古所伊弟利斯·阿不都、邢开鼎、伊列·尼加提、祁小山等先生,自乌鲁木齐出发,沿天山北麓向东,经米泉、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直至巴里坤,进行考古调查,见到了一些古代遗址、古城石人、古墓、驿烽等,所获甚丰。其中石人材料,不少是过去所未见。为助于有关“石人”的专题研究,这里略为报导,并草书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石人像遗迹,目前只见于吉木萨尔、奇台和巴里坤三县。
吉木萨尔县,主要分布在天山脚下的新地沟、苇湖沟、贼疙瘩梁等处;奇台县,见于半截沟;巴里坤县,见于石人子乡。都是近山脚一些水草较好,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
一、新地沟石人
新地沟,在今吉木萨尔县西南,县林场所在。山沟内林木苍郁,沟口为白杨,上面生长着松杉。山梁上绿草如茵,沟内水流清澈。目前已垦为耕地的沟谷东岸,林场场部稍南的地方,当地称为“石人滩”,因为这里曾经伫立多个石人,故相沿成俗。据老人回忆,至少有五六个以上,石人多面东,其身后多有土、石堆,我们踏勘遗址时,仅见扑倒的二座。其中之一,即由县文化馆李功仁同志主持运回县城,存县文化馆。石人所在山梁,调查中曾采集到骨片。有关石人的具体情况是:
其一,高152厘米、宽42厘米、厚22厘米,花岗岩质。头部特征刻画较细:宽圆脸型、颧骨较高、浓眉,眼、鼻、嘴轮廓清楚。嘴唇上方,有两撇八字胡。双耳垂饰耳环,颈部,刻圆环一道。衣纹未刻画,也不见一般石人常有持杯、抚剑的特征。脑后,刻斜线两道,环带一道止于耳后,其下,有小刀一把(图116)。
其二,块石高150厘米、宽50厘米、厚16~40厘米,花岗岩质,青色,块石成不规则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块石并未清楚刻画出人物面部形象,只是在相当于人的头部,刻画平行斜线五道,延及块石的两侧面。在其一侧,斜线是复刻一圆环。相当于上身躯干部位,刻划一圆环、一短刀,一条弧线围绕两条平行绕。这在新疆,还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刻石资料(图117)。
二、苇湖沟石人
苇湖沟,居县城西南,近天山脚下,与新地沟东西并列,相距约8公里。自苇湖大队骑马入山,有山道可抵达坂城,算得一处隘道。说是“苇湖”,目前田连阡陌,地面不见苇湖痕迹。石人立于苇湖大队门口一土埂边。但这并不是原来位置,据说最初在一条地势较高的土梁上,目前所见情况是:石质为青灰色花岗岩,较扁平。地面以上的高度为116厘米、宽62厘米、厚20厘米。形象特征是:脸型偏长,下颏稍尖,眼大,鼓突若菱形,鼻准较高。唇上鼻下属两撇唇须,八字展开,尾端上翘,嘴唇紧闭向下,显得神态威严,不可侵犯。唇下垂山羊胡一撮。大耳,耳下垂环。颏下有左右向对称张开的斜线六道,似为须髯。其下衣服、武器、手势及持物等,均未见刻画(图118)。
三、牛庄子石人
牛庄子在吉木萨尔县泉子街乡。其西为贼疙瘩梁,梁上有古城一座。自吉木萨尔越天山到吐鲁番的古代重要交通路线——他地道,就是通过这片地区南入天山。石人原在牛庄子村。石人近旁有大石墓一座,直径20多米,老乡浇地时,发现这里跑水严重,经发掘,见大石棺。后重又掩埋,未开棺清理。
石人,现已移至一马厩墙边。高80厘米(地面以上)、顶宽40厘米、下宽60厘米。花岗岩质,青黑色。面部形象尚清楚,眉、眼、鼻、嘴位置准确。眉弓曲,眼鼓成圆形,鼻直,小嘴,脸型稍圆,头、肩分隔处,稍内收,肩部以下则为自然形状,未经刻画。
四、奇台石人
奇台县内,目前只见石入一躯,原在县城东南,天山北
麓之半截沟。这里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由半截沟入山,有
山道可越天山至鄯善县,石人原在半截沟供销社前,这并
不是原来的位置。现已入藏奇台县文化馆供人观览。石人
以花岗岩为料,通高146厘米、面宽39厘米、石厚20厘
米。刻画较为精细,脸型宽圆,下颏部稍尖凸,似山羊胡。
眼近圆形。鼻下现两撇小须。右手持杯上举至胸前,左手
下抚剑柄。衣饰未刻画(图119)。
五、巴里坤石人
巴里坤县,目前也只见石入一座。原在县城东四十多公里之石人子乡。“石人子”一地之得名,当与此石人遗迹有关,足见清代或清代以前,人们即已注意到这一石人的存在。石人原在石人子村南,天山脚下,后被人移至一渠道边,现存巴里坤县文化馆陈列室。石人用料为细沙岩、青灰色。块石不规整。通宽95厘米、宽34~50厘米、厚20厘米。头部用浅浮雕手法,刻画出人面形象:浓眉、圆眼、鼻隆起、嘴小、无须。头部以下,均为原石,未作任何刻画。巴里坤石人,是天山地区所见地理位置最东的一座。
由于只是地面的一般调查,上述石人资料,自然还难说乌鲁木齐以东天山地区的全部石人材料。因为没有发掘,而且几乎全部石人均已脱离了最初的原始位置,影响了我们对石人像性质的认识。但即使如此,从这点有限的资料,仍可见出不少问题。
第一,国内外历史考古界,有一个差不多一致的观点:从蒙古高原,到新疆广大地区,前苏联的阿尔泰、哈萨克斯坦等,在这么广大的地域内存在的古代石人遗迹,主要是与古代突厥民族有关的一种历史遗存①。而根据古文献记录和突厥人的传说可知,在阿勒泰之南,高昌西北,也就是天山北麓至阿勒泰草原,是古代突厥民族的发祥地②。这片地区,也是后来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主要地域。当然,在这片地区内,保留下来较多的突厥族遗存,是并不令人奇怪的。但在以前发表的资料中,有关石人遗迹,都只见于阿勒泰、博尔塔拉、伊犁地区。乌鲁木齐以东的天山地带,即突厥民族的发祥地却没有见到具体报导。本文的报导,从资料上填补了这一空白,说明在乌鲁木齐以东的天山地区,石人也是同样存在的。目前的资料,虽还只见于吉木萨尔、奇台、巴里坤三县,但今后随着工作的深入,在乌鲁木齐地区、阜康、木垒等县境内,尤其是近天山北麓的山前地带,继续发现这类石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这类石人像的时代、作用,正如前面提到的,一般都认为与隋唐时期突厥人的埋藏制度有关。根据汉文史籍中的有关记录,如《旧唐书》称,阙特勤死,李唐王朝即派金吾将军古逸、都官郎中吕向至突厥王国致祭,由皇帝为之撰写碑文,立祠庙,并“刻石为像”,以致纪念①。另一位芯伽可汗,身死后,也有立像的记录②。这说明,突厥人在死后,确有在墓前立像的习惯。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曾对博尔塔拉温泉县阿尔卡特石人(此石人现在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部陈列。圆脸、大目,颧骨较高、八字胡,身着反领大衣,腰系带,带上佩系小刀。右手持杯至胸前,左手抚刀剑柄。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类型)身后的石棺进行过发掘,除见碎骨、骨灰外,未见其他文物。说明实行火葬。这种火葬习俗,也是见于文献记录的突厥民族曾经实行过的一种葬俗。如《周书·突厥传》提到,突厥在人死后,“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具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旧唐书·突厥传》也记述,7世纪中叶,颉利可汗死,“诏其国人葬之,从其礼俗,焚尸干霸水之东”。将死后立像及火葬这两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说明有一类石人作为石棺火葬墓前的立像标志,是隋唐时期突厥人的象征,大概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另一问题:新疆广大地区内石人形象的特征,彼此差别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如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的石人造型,我们这里介绍的奇台半截沟石人,就属于同一类型;但还有很大部分石人造型,从面部形象到衣服、佩饰等,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不是存在着时代的前后不同?如是,那么石人所代表主人的民族身份是不是也应该有不同?我们前面介绍的6座石人,就清楚显示了这种差异:有的只刻画出面部轮廓,有的在面部形象上清楚显示了不同的特征,对这种差别,看来不应忽略。但是,要求得出明确的结论,必须结合着对石人身后的墓葬进行发掘,并比较研究发掘资料。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太少,进一步分析还有困难。但也有一些发掘资料,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说明。在阿勒泰克尔木齐发掘的一批石棺墓,不少墓前立有石人。这些石入一部分形象就比较简单,甚至只是利用一块椭圆形卵石刻画出人的面部形象。这和阿尔卡特石人所代表的一种类型,明显存在差别,而墓地发掘资料也表明:它们的时代较早。墓前立有石人的墓葬,实行的是土葬,随葬文物,有石镞、石质容器、陶器、铜器①。这和阿尔卡特石人火葬墓,就显示了明显的时代、葬俗上的不同。明确这一点,并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探明、研究这种差异,找出其演变、发展的规律,无疑对于我们认识这类以石人为代表的考古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有很大意义的。
第三,古籍记载突厥民族源起于“金山之阳”。目前,最早见到的汉文史籍是《周书·异域传·突厥》,时代已相当晚,这时期的突厥,作为柔然汗国统治下的一个游牧部落,力量已很强大,这当然不应该是突厥族最初的情况。从隋、唐时期突厥族人的墓葬前立石为像这一习俗看,可以把墓前竖立石人像,作为突厥考古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因此,在阿勒泰草原(金山之阳)发现的、数量相当多的早期石人及墓葬,应该是与突厥考古文化有密切关系,它们是突厥早期文化的一种遗存;或者,可以说,它们是形成后来突厥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无论如何,即使只从石人,或墓前竖立石人像这一重要葬俗看,是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其继承、发展关系的。如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一个逻辑的推论就是:古代突厥人,在阿勒泰地区的居住和活动历史,是十分古老的。它们的时代,远及公元以前。隋、唐时期,影响远布的突厥汗国的传统文化,奠基在一个很深厚的历史基础上。
第四,当突厥兴起以后,势力强大,在东、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下,居民的种族成分大概也是很复杂的。这种情况,应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研究,从考古工作角度,发掘出土的人骨及一些墓葬前的石人立像,就是第一手资料。如前所述,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阿尔卡特石人形象,具有很鲜明的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而吉木萨尔县苇湖沟石人,就表现了完全不同的形象。这是刻画得很有性格特点的一具石人,狭长的面庞上大眼圆睁,高鼻,须髯飞张,这些,都明显具有白种人特点。而石人紧闭的嘴唇,嘴角向下,更十分增强了石人形象的威严,显示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说明了它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可能是某一级的领袖人物。这类资料,集中起来,就足以说明突厥汗国属下相当复杂的居民种族成分。
第五,在吉木萨尔县新地沟(石人滩)所见一件刻石:不见人面形象,但见斜线、圆环、配刀,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新资料。这种刻石,苏联学者称之为“鹿石”①,他们认为这种“鹿石”(石刻上曾见鹿的形象)是一种公式化了的石人形象:在头的部位刻两条或三条斜线,就是代替人面。虽然,它们的含意至今并不完全清楚,但躯干部分的刀或其他刻图案,则表示着武士身上佩系的武器等物。这类石刻,据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前后的一种遗存,而且认为是与古代萨迦人(塞人)有关的一种遗存。它们也是墓葬前面的标志。苏联学者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工作,当然具有参考价值。但结合新疆的发现,究竟是什么情况,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掘才能具体说明。目前应该更深入地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保护或科学发掘工作,使它们的科学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
附注
①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载《文物》,1962(7~8);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载《考古》,1960(2)。
②《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1);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载《文物》,1962(7~8)。
③李遇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石人墓调查简记》,载《文物》,1962(7~8)。
④⑥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载《考古》,1960(2)。
⑤《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12)。
①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载《文物》,1962(7~8),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载《考古》,1960(2)。
②《周书·异域传·突厥》、《隋书·突厥传》。
①《旧唐书》卷194,《突厥传》。
②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841页。
①《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1);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载《文物》,1962(7~8)。笔者曾参加了这一墓地的发掘,其早期墓,可能远早于战国。
①苏联D.R.萨维诺夫,H.A.契列诺娃:《鹿石分布的西界及其文化民族属性问题》,见《蒙古考古学与民族学》,诺沃西比尔斯克:苏联科学出版社,1978。(苏联)П.Л.奇列诺娃:《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蒙古考古论文集》,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62年。乌恩,陈弘发曾分别翻译为汉文,刊于内蒙古文物队,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1、3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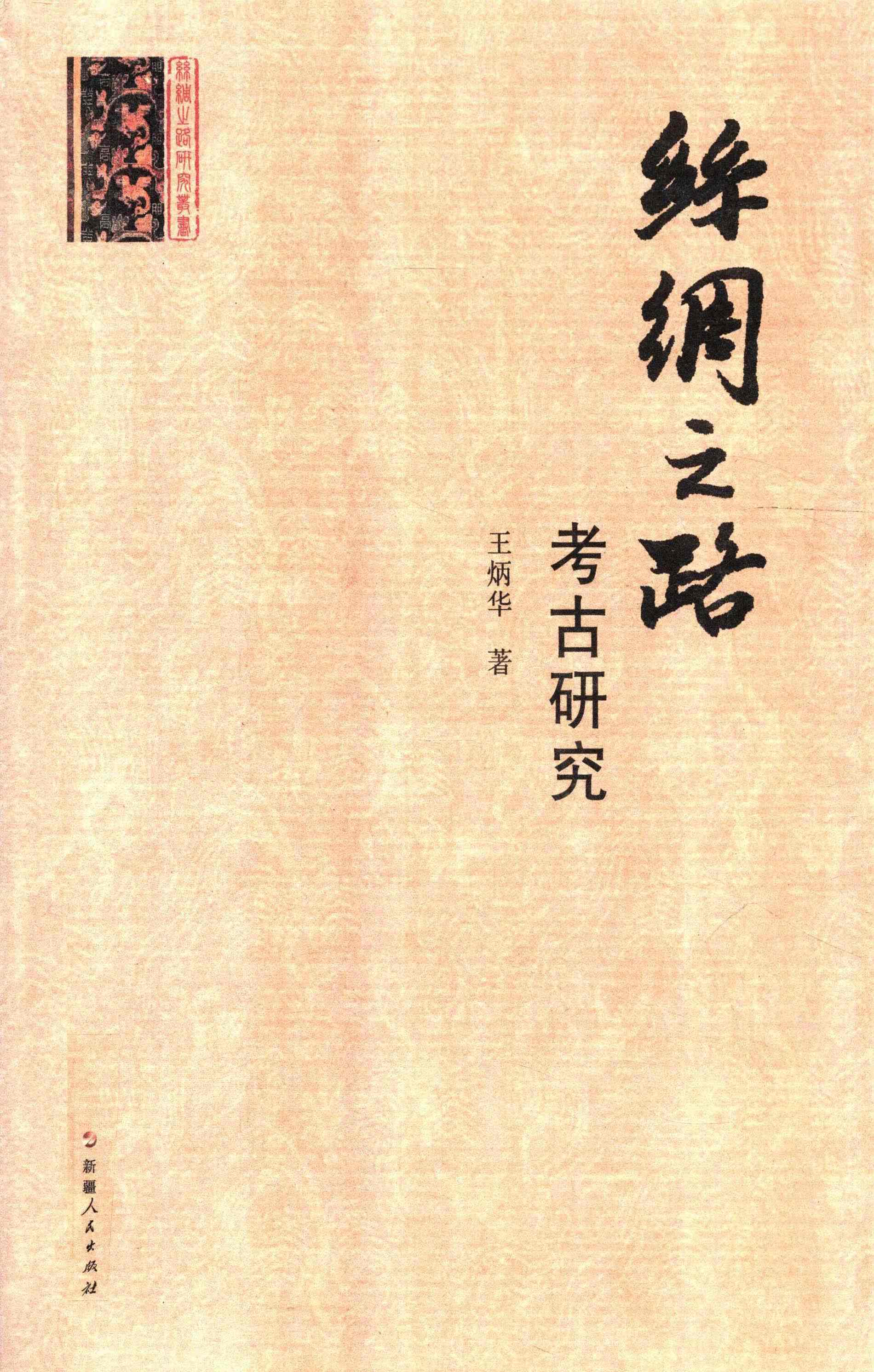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