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犁耕的起源和发展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94 |
| 颗粒名称: | 新疆犁耕的起源和发展 |
| 分类号: | S22 |
| 页数: | 8 |
| 页码: | 234-24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新疆地区什么时候开始掌握犁耕技术,而且使用畜力于犁田耕地,对新疆农业发展史研究是关键性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科学论定,主要必须依凭考古工作的成果。从耜耕转变为犁耕,并使用畜力,是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曾经历过的一次重大革新。 |
| 关键词: | 新疆 起源 发展 |
内容
新疆地区什么时候开始掌握犁耕技术,而且使用畜力于犁田耕地,对新疆农业发展史研究是关键性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科学论定,必须依凭考古工作的成果。
从耜耕转变为犁耕,并使用畜力,是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曾经历过一次重大的革新。它曾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铧的用家畜拉的耕犁。有耕犁以后,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①耜耕,使用人力,一下又一下翻土,是一种断续性劳动操作;犁耕,使用了畜力,断续性动作变成了连续不断的操作。这就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工效,而且使深耕成为可能,地力更好地得到保养,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四川甘洛县藏族人民中有谚语:“十个锄头,顶不上一个脚犁;十个脚犁当得一驾牛犁。”②也是这一意义,形象而又具体、深刻地说明了犁耕在农业生产中的重大作用。
关于新疆开始犁耕的时间,至今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对此,曾有同志表示过观点:其一,认为“汉代在新疆屯田多处,开垦使用铁犁可能性很大”③;其二,认为“大概直到魏晋时期,牛耕技术才开始在屯田地区推广”④。这两个论点,都只是提出见解,并没有具体分析。两种看法都把犁耕技术与屯田事业联系在一起,而没有联系新疆地区本身农业发展情况进行考虑。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是受考古工作成果的局限,缺少能直接说明问题的资料。但这些论点的提出,对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无疑是有利的。
据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一些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勾勒出从耜耕到犁耕的发展轮廓。为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现将有关心得书之于后。
一
两汉之前,新疆地区考古资料中,未见任何犁类实物,无论是木犁、石犁或金属犁。反之,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却发现了木质掘土器、木耜等。这就有力地说明,汉代以前,从目前考古资料可以结论,新疆地区确实尚未用犁。
新疆地区,早在原始社会阶段起,就已经有了农业生产。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乡乌布拉提阿克塔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过石镰、石刀、石砍锄、磨谷器等,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①;孔雀河下游古墓沟青铜时代墓区,出土了小麦,发现了木质挖土工具,其绝对年代在距今3800年左右;哈密五堡公社原始社会墓地中,发现了木质三角形掘土器、木耜、石磨谷器,见到了小米饼、青稞穗壳,时代在距今3000年前;地处吐鲁番盆地西缘的天山阿拉沟中,在原始社会阶段墓地内见到了木质掘土工具、胡麻籽壳,其时代在距今2800~2200年间②;天山北麓木垒县四道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器共80余件,多为生产工具,有石球、磨盘、杵、锄、铲、臼、纺轮,以及石核和片状石器等。而磨制石锄、石铲等明显用于农业生产工具,只见于晚期地层。晚期地层的绝对年代,距今为2345±90年,相当于战国时期③;与此相邻近的巴里坤石人子乡、奎苏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了大型磨盘、石锄、炭化小麦粒等④。在这么多明显以农业为主体或有一定农业经济存在的早期遗址中,没有一处发现过犁类工具。
既都不见犁类工具,早期农业生产中翻土工具是什么?从现有材料看,主要是木耜及木质三角形掘土器等,它们既可用作翻土,也可用于点播,只是效率低下而已。
哈密县五堡公社原始社会墓地,傍近白杨沟(源于天山的一条不大的小河),位于沟旁一处比较高敞的台地上。墓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在1979年试掘的一小片范围内出土墓葬28座。墓内出土木质三角形掘土器2把,木耜1件,共出其他牧业生产工具、砺石、石杵不少,但明显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只有这种三角形掘土器及木耜。三角形掘土器,通长90厘米,木质坚硬,中段微微弓起,成人持握直立可以操作,不必躬腰,其发土部分为比较规整的等腰三角形,恰似当前考古工作中常用的尖头小铲,只是比较厚实,但尖部却相当锐利。我们在当地曾作过掘土试验,入土、发土均相当方便。可证用于发土。点种当无问题。这件三角形掘土器,曾经过长期使用,不仅三角形尖部锐利光洁,而且持握的柄部也因长期把握而相当光滑。共出之木耜,形制如方刃锨铲,通长28.5厘米,厚1厘米,肩部最宽,达16.5厘米,刃部较狭,只13.5厘米。偏耜体上部,居中,对称穿两孔,以便安柄。孔内安柄时使用的毛绳仍部分残存未朽,清楚可见。
这种三角形掘土器及木耜,在《新疆考古》第1期中曾经报道,前者被称为“犁形掘土器,”后者被称为“木锨”,定名均误。
为加深对五堡出土的三角形木质掘土器使用特点的认识,可以少数民族中仍然保留的同类性质的工具进行比较。这类掘土工具在云南独龙族、四川甘洛县藏族中均曾长期使用,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或不久以前,在他们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仍见存在。以这类“活化石”性质的工具作比较,五堡木质掘土器的性质即一目了然。
四川甘洛县藏族(他们自称“耳苏”人),至今耕地还是使用一种“脚犁”。这是以树干或较大的树枝砍削而成,下端安尖状铁犁头。通长2米左右,上部有扶手,在扶手与犁铧之间安一根横木,为踏脚之处。这种脚犁一人操作,手足并用,省力且效率高。
据“耳苏”人自称,他们使用的这种“脚犁”,是从木质掘土棒发展而来:“先是在尖木棍上安装‘扶手’……后来由扶手的启发加上一个脚踏横木,手足并用,遂成木耜。”①(图97)
类似的掘土棒,在云南省独龙族的农业生产中也曾经发现过。民族调查资料表明,在独龙族中,除铁质工具外,还使用着不少木质生产工具。而“在木质工具中,使用最广泛的是‘郭拉’和‘宋姆’……‘宋姆’即点种棒,把小竹棍和小木棒一端削尖或以火炙尖即成。用以挖穴点种,用毕即弃”。“从独龙族各种农具的形制与用途分析……宋姆,当是与石刀、石斧同样古老的工具,它直接从采掘时期的尖头木棒发展而来”②。
“耳苏”入中的掘土棒与独龙族中的“宋姆”,与哈密五堡出土的木质掘土器,形制近同,作用一样。只是哈密之掘土器已较进步,它在选料(木质致密、材质坚硬)、制作(掘土部分呈规整之三角形、端部尖锐易于发土、厚实耐用、刮磨光洁;而且中段弓起,便于起土)、使用(长期使用不弃,已经成了固定的生产工具)与独龙族中随用随弃的尖头木棒“宋姆”比较,确是大不一样的了。
最初使用掘土棒,进而脚犁,而后为犁,似为犁类农具发展曾经历过的过程。在前引民族学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一线索。从王桢《农书》关于脚犁的记述中也可得相同推论:“长镵,踏田器也。镵犁比镵颇窄,制为木柄,谓之长镵……有木为拐,以两手按之,用足踏其镵柄后跟,其锋入土,乃捩柄以起土也。在园圃区田,皆可代耕,比钁省力,得土又多,古谓之跖铧,今谓之踏犁,亦耒耜之遗制也。”如这一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则哈密五堡新石器时代墓地仍以三角形掘土棒、木耜发土,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木垒县四道沟遗址的晚期地层,已相当于战国后期,出土石质农具只见锄、铲、磨盘等,未见犁的痕迹,水平相近。
二
从考古资料分析,新疆犁耕始于西汉。魏晋时期,曾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广牛力犁耕。犁耕开始,即使用铁犁、畜力,其技术水平与同时期的陕、甘相近。当时中央王朝政权关注“丝路”建设、沿途供给,在新疆推行屯田政策,随屯田吏卒带来这一新的耕作方法。这曾对新疆地区的农业生产起过积极影响。
在伊犁地区昭苏县境内,曾发掘了不少古代乌孙墓葬。在其中一座时代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古墓葬封土中,出土了一件铁铧①(图98)。铁铧全重6斤2两,通长35厘米,壁厚1厘米。舌形,铧体中部隆起,尖部及边缘比较钝厚,后部为扁似梭形的銎,銎长15厘米、最宽8厘米、深14厘米。这件铁铧,形制明显具有汉代风格,与陕西关中陇县出土的汉代铁铧形制相同②。在甘肃敦煌还曾出土过一件形制、大小几乎与此完全相同的铜铧,现陈列在敦煌县文化馆,时代同属西汉。
昭苏地区,汉代属乌孙王国。昭苏县境保存的各种巨型乌孙墓冢,至今仍宛若小土山。在乌孙境内,西汉王朝曾派常惠率“三校”士卒,进行屯田③。乌孙王国作为汉王朝的局部,彼此关系十分密切。从这一背景,可以推见汉代铁铧在这里出土,应该与汉代屯田直接有关。军屯,是汉王朝政府主持的生产事业。生产工具、牛畜、籽种等,均由政府供给。使用铁犁、畜力耕田,汉代内地已经普遍。遣士卒到新疆屯田戍守,将这一套农业生产技术带到新疆来,是不言自明的。昭苏铁铧的形制与陕西、甘肃地区同时代出土物相同,正是有力而具体地说明了这一历史事实。限于考古工作规模,同时考虑到这类农业生产工具出土十分不易,汉代铁铧虽只见于伊犁昭苏一地,但它对于说明汉代各个屯田中心的耕地农具情况,却是一件有代表性的实物,具有典型意义。可以预期,随着今后考古工作更大规模、更深入地展开,在古代各屯田中心区域,必将会有更多的、同类性质的工具陆续出土。
在罗布淖尔地区楼兰遗址,新中国成立前曾经出土过不少晋简。其中有一条简文,残存部分文字是:“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晋代,西域长史曾一度驻节于此。从出土的许多木简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楼兰地区是一处重要的屯田中心。简文主要记述的就是有关灌水、管水、种地、锄地、收获等农事工作①,可证。在这样一处屯田中心,出土了上引简文,是并不奇怪的。简文虽并不完整,但文意基本清楚,“大侯”,为官称,可能是西域长史府下的属吏;“谨遣大侯究犁与牛”之“究”,有“穷尽”意。也就是说,命令大侯率属下的全部犁、牛到长更营下“受试”。也有人提出,这里“大侯”一词,可能是指鄯善王,因为鄯善王当时受晋封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王”,而“究”属“王名”但其他地方又未见有如此简称的例子②。然而,不论何种说明为当,全简文意,明显,与推行牛耕技术有关,却是无可怀疑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论:(1)晋代在楼兰地区的屯田,实行以牛为畜力的犁耕;(2)屯田士卒中有的似乎并不熟悉犁田耕地技术,故有训练、“受试”之举;(3)考虑到屯田士卒,其主体无疑是内地的农民。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屯田士兵,对牛耕技术,无疑是早就掌握的。因此,“究犁与牛到营下受试”,也很可能是与推行一种新的耕作方法有关。这几种逻辑推论,不论属于何种情况,都可以肯定一点:晋代楼兰地区,已经使用并相当重视用牛犁地的技术。
魏、晋时期,南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用犁耕地,在佉卢文资料中也有所见。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地区所见700多件佉卢文资料,其绝对年代可“断定为公元3~4世纪”③,主要发现于和田、民丰、且末、若羌等处古遗址。在700多件材料中,涉及农事者不少,主要用“耕地”、“耕种”一词,未明确说耕地或耕种之工具,只一处简文,明确使用了“犁地”的概念:“……关于犁地、大麦、小麦……由汝仔细……照拂。并且来伐罗色摩无论如何对此事一定非常热心……”④可见耕地时使用了犁,这与同一阶段内,前述汉文简牍资料可以统一。
当时犁地是怎样的方法?有一幅壁画可以帮助说明这一问题。在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第175号洞窟中,保留了几幅有关当地世俗生活的画面:如制陶、翻地、犁地等。这一洞窟壁画时代,据阎文儒教授考证,相当于晋①。有关犁耕的画面,以十分简练的笔法,勾勒出了二牛抬杠、合驾一犁、一人在后持物驱牛前行的情景(图99)。犁驾未具体刻画,但对关键性的部件——犁头,作了重点表现:犁作三角形,个体较大。这种二牛抬杠式犁耕方法及犁铧形制,与陕北出土东汉牛耕画像石、江苏睢宁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陕西米脂出土东汉牛耕画像石及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墓壁画、甘肃省酒泉嘉峪关汉魏壁画墓等所见图像,都基本相同,二牛抬杠式的犁耕方法、三角形犁铧,分不出什么差别②。
与这一时代相当,还有一件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的晋墓纸画(图100)。纸画着意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财富,优裕的物质享受生活。画面的三分之一,描绘了墓主人的田园、农具、谷物加工工具、庖厨等③。田亩整齐,禾稼迎风而动;田园旁的农具有木杈、木耙。据不同需要,木杈有双齿、多齿之别(这在今天的南疆农村仍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与木耙等农具置于一道,还有一件工具,其形如
“〓”,见者均不得其解。我认为:这也是一件犁。如将此图平置,其形当是“〓”,这正是一驾犁的侧视示意图。它虽然简单,但却本质地表现了犁梢、犁架、犁辕及系绳等有关部件。这应该是吐鲁番地区晋代用犁情况的直接说明。
不论是伊犁昭苏、罗布淖尔楼兰、库车拜城、吐鲁番,这些地点,在汉晋时期,都是新疆地区比较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当时的屯田重点地区。而铁铧的形制、二牛抬杠的牛耕图像等,又都与内地相同。这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两个概念:(1)新疆古代犁耕技术,深受祖国内地的影响。它们进入新疆地区的过程,与中央王朝在新疆地区大力推行屯田密切相关。这曾经给于新疆古代农业生产以有力推进,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2)从汉晋时期各地出土有关牛耕图像看,当时新疆地区牛耕技术水平与内地相当或相近,差距并不大。这对分析新疆古代农业生产水平,无疑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情况。
三
新疆地区虽早在距今2000年前的西汉即已知犁耕,自汉迄晋,随屯田事业的发展,内地移民(主要为屯田士卒)的不断进入,这一新的耕作技术在新疆地区也逐步得到推广、发展。但其进展是缓慢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耜耕,在犁耕开始一个相当阶段以后,在一些地区仍然保留、沿用。直到新中国成立,犁耕技术仍处于一种相当低下的水平。二牛抬扛,这一犁耕的基本特征,并没有什么显明变化。新疆地区农业生产力获得大的发展、解放,是在成立了新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真正成了生产、生活的主人以后。
在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沿的民丰县,北去100多公里,是现已沦为沙漠的汉、晋尼雅遗址。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后曾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发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次调查中,遗址内曾出土了不少铁、木工具,如铁斧、铁镰、木榔头、“木锨”及多量牧业工具等,但却始终未见过犁类工具①。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因铁犁铧十分珍贵,遗址废弃时随身带走,因此无法发现;再是当时这片地区并未用犁。一个现象支持后一种推测。这就是在报道过的各种工具中,有所谓“木锨”,它“长49厘米、肩宽22.5厘米,也是一件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②。”细审其图版,形制与哈密五堡所出木耜相同,偏近肩部也有对称两孔,明显用作缚绳安柄,应该也是木耜。哈密、民丰地区,土质疏松,这类木耜用于翻土并无困难。从汉、晋尼雅遗址仍然出现木耜而不见犁类工具看,犁耕在尼雅地区似仍未普及,或虽有使用必仍不普遍。因此,木耜未能被排除出历史舞台,而仍然是人们使用的重要农具之一。
与前述晋简中表明的西域长史曾在罗布淖尔楼兰国地区进行牛耕技术相对,同一遗址内,在被斯文·赫定取走,后经康拉德研究的晋简中,曾有一简,简文为“明日之后,便当砍地下种”③。它明白无误地揭示:晋时这片地区,还保留着地”(不是犁地)以种的方法,并未使用犁耕。这也可能正是西域长史要大力推行犁耕的背景。直到公元6世纪初,在宋云、惠生前往印度求经,路过这片地区时,还谈到且末“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①。这是宋云、惠生目睹手记的资料,应该是可靠的。它有力地揭示,在历经500年以后,新疆还有一些地区,仍未能用犁。在封建社会中,一种新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其推广、传播,造福于人民,是十分艰难、十分缓慢的。
考古资料中,汉晋以后,除在焉耆县唐王城发现过一件唐代铁铧外②,笔者再未见有关犁铧资料。
这一缓慢的耕作技术发展过程,直到新中国成立,在新疆农村没有什么变化。不仅牛耕的方法是与2000年前近同的二牛抬杠方式,南疆地区有的偏僻农村,甚至还有以人拉木犁作为耕作手段的。
关于南疆广大农村地区缺乏铁质犁铧的情况,从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调查资料中可以窥见大概。
据南疆农村的农业生产与生产力统计资料:总计916户,有犁143架③。
这就是说,大概平均6户多才能占有1架犁;而犁铧质量也不高,比较容易断裂。因此,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生产效率较低。据同书调查统计,“两头牛拉一架犁,只耕3亩地(一天)”,因为犁头小(3斤),犁身轻,不能进行深耕(约4寸);两牛一人,一天只能犁3亩地,这就使多翻地的耕作方法受到限制”。这种犁耕的实际效率,与人力比较,在当地也有一个估算:“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人工换牛工,一般是五比一,即一架牛对犁地一天,要还5个人工”④,生产力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
这些材料告诉我们,牛耕技术,在经历了2000年的发展以后,在新疆广大农村,仍然处于一个低下水平。它既表现在仍然是二牛抬杠的传统办法,铁犁质量低、轻、薄,耕地效率不高,而且数量极少,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极少数偏僻地区,由于铁铧犁少而价昂,而用木犁,或者用坎土曼翻地,这当然就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经济生活十分贫困。各级封建统治者不关心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广大贫苦农民无力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交通不便、分散、孤立的各绿洲居民点,自成一个天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社会的闭塞、落后更加严重。
从犁耕技术在新疆的起源和发展这一小点进行分析研究,看封建社会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桎梏,可得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近几十年,劳动人民成了生产的主人,新疆农村生产条件的变化是巨大的,拖拉机遍及各地,就是这一巨大变化的特征。
从耜耕转变为犁耕,并使用畜力,是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曾经历过一次重大的革新。它曾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铧的用家畜拉的耕犁。有耕犁以后,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①耜耕,使用人力,一下又一下翻土,是一种断续性劳动操作;犁耕,使用了畜力,断续性动作变成了连续不断的操作。这就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工效,而且使深耕成为可能,地力更好地得到保养,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四川甘洛县藏族人民中有谚语:“十个锄头,顶不上一个脚犁;十个脚犁当得一驾牛犁。”②也是这一意义,形象而又具体、深刻地说明了犁耕在农业生产中的重大作用。
关于新疆开始犁耕的时间,至今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对此,曾有同志表示过观点:其一,认为“汉代在新疆屯田多处,开垦使用铁犁可能性很大”③;其二,认为“大概直到魏晋时期,牛耕技术才开始在屯田地区推广”④。这两个论点,都只是提出见解,并没有具体分析。两种看法都把犁耕技术与屯田事业联系在一起,而没有联系新疆地区本身农业发展情况进行考虑。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是受考古工作成果的局限,缺少能直接说明问题的资料。但这些论点的提出,对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无疑是有利的。
据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一些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勾勒出从耜耕到犁耕的发展轮廓。为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现将有关心得书之于后。
一
两汉之前,新疆地区考古资料中,未见任何犁类实物,无论是木犁、石犁或金属犁。反之,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却发现了木质掘土器、木耜等。这就有力地说明,汉代以前,从目前考古资料可以结论,新疆地区确实尚未用犁。
新疆地区,早在原始社会阶段起,就已经有了农业生产。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乡乌布拉提阿克塔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过石镰、石刀、石砍锄、磨谷器等,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①;孔雀河下游古墓沟青铜时代墓区,出土了小麦,发现了木质挖土工具,其绝对年代在距今3800年左右;哈密五堡公社原始社会墓地中,发现了木质三角形掘土器、木耜、石磨谷器,见到了小米饼、青稞穗壳,时代在距今3000年前;地处吐鲁番盆地西缘的天山阿拉沟中,在原始社会阶段墓地内见到了木质掘土工具、胡麻籽壳,其时代在距今2800~2200年间②;天山北麓木垒县四道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器共80余件,多为生产工具,有石球、磨盘、杵、锄、铲、臼、纺轮,以及石核和片状石器等。而磨制石锄、石铲等明显用于农业生产工具,只见于晚期地层。晚期地层的绝对年代,距今为2345±90年,相当于战国时期③;与此相邻近的巴里坤石人子乡、奎苏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了大型磨盘、石锄、炭化小麦粒等④。在这么多明显以农业为主体或有一定农业经济存在的早期遗址中,没有一处发现过犁类工具。
既都不见犁类工具,早期农业生产中翻土工具是什么?从现有材料看,主要是木耜及木质三角形掘土器等,它们既可用作翻土,也可用于点播,只是效率低下而已。
哈密县五堡公社原始社会墓地,傍近白杨沟(源于天山的一条不大的小河),位于沟旁一处比较高敞的台地上。墓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在1979年试掘的一小片范围内出土墓葬28座。墓内出土木质三角形掘土器2把,木耜1件,共出其他牧业生产工具、砺石、石杵不少,但明显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只有这种三角形掘土器及木耜。三角形掘土器,通长90厘米,木质坚硬,中段微微弓起,成人持握直立可以操作,不必躬腰,其发土部分为比较规整的等腰三角形,恰似当前考古工作中常用的尖头小铲,只是比较厚实,但尖部却相当锐利。我们在当地曾作过掘土试验,入土、发土均相当方便。可证用于发土。点种当无问题。这件三角形掘土器,曾经过长期使用,不仅三角形尖部锐利光洁,而且持握的柄部也因长期把握而相当光滑。共出之木耜,形制如方刃锨铲,通长28.5厘米,厚1厘米,肩部最宽,达16.5厘米,刃部较狭,只13.5厘米。偏耜体上部,居中,对称穿两孔,以便安柄。孔内安柄时使用的毛绳仍部分残存未朽,清楚可见。
这种三角形掘土器及木耜,在《新疆考古》第1期中曾经报道,前者被称为“犁形掘土器,”后者被称为“木锨”,定名均误。
为加深对五堡出土的三角形木质掘土器使用特点的认识,可以少数民族中仍然保留的同类性质的工具进行比较。这类掘土工具在云南独龙族、四川甘洛县藏族中均曾长期使用,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或不久以前,在他们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仍见存在。以这类“活化石”性质的工具作比较,五堡木质掘土器的性质即一目了然。
四川甘洛县藏族(他们自称“耳苏”人),至今耕地还是使用一种“脚犁”。这是以树干或较大的树枝砍削而成,下端安尖状铁犁头。通长2米左右,上部有扶手,在扶手与犁铧之间安一根横木,为踏脚之处。这种脚犁一人操作,手足并用,省力且效率高。
据“耳苏”人自称,他们使用的这种“脚犁”,是从木质掘土棒发展而来:“先是在尖木棍上安装‘扶手’……后来由扶手的启发加上一个脚踏横木,手足并用,遂成木耜。”①(图97)
类似的掘土棒,在云南省独龙族的农业生产中也曾经发现过。民族调查资料表明,在独龙族中,除铁质工具外,还使用着不少木质生产工具。而“在木质工具中,使用最广泛的是‘郭拉’和‘宋姆’……‘宋姆’即点种棒,把小竹棍和小木棒一端削尖或以火炙尖即成。用以挖穴点种,用毕即弃”。“从独龙族各种农具的形制与用途分析……宋姆,当是与石刀、石斧同样古老的工具,它直接从采掘时期的尖头木棒发展而来”②。
“耳苏”入中的掘土棒与独龙族中的“宋姆”,与哈密五堡出土的木质掘土器,形制近同,作用一样。只是哈密之掘土器已较进步,它在选料(木质致密、材质坚硬)、制作(掘土部分呈规整之三角形、端部尖锐易于发土、厚实耐用、刮磨光洁;而且中段弓起,便于起土)、使用(长期使用不弃,已经成了固定的生产工具)与独龙族中随用随弃的尖头木棒“宋姆”比较,确是大不一样的了。
最初使用掘土棒,进而脚犁,而后为犁,似为犁类农具发展曾经历过的过程。在前引民族学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一线索。从王桢《农书》关于脚犁的记述中也可得相同推论:“长镵,踏田器也。镵犁比镵颇窄,制为木柄,谓之长镵……有木为拐,以两手按之,用足踏其镵柄后跟,其锋入土,乃捩柄以起土也。在园圃区田,皆可代耕,比钁省力,得土又多,古谓之跖铧,今谓之踏犁,亦耒耜之遗制也。”如这一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则哈密五堡新石器时代墓地仍以三角形掘土棒、木耜发土,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木垒县四道沟遗址的晚期地层,已相当于战国后期,出土石质农具只见锄、铲、磨盘等,未见犁的痕迹,水平相近。
二
从考古资料分析,新疆犁耕始于西汉。魏晋时期,曾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广牛力犁耕。犁耕开始,即使用铁犁、畜力,其技术水平与同时期的陕、甘相近。当时中央王朝政权关注“丝路”建设、沿途供给,在新疆推行屯田政策,随屯田吏卒带来这一新的耕作方法。这曾对新疆地区的农业生产起过积极影响。
在伊犁地区昭苏县境内,曾发掘了不少古代乌孙墓葬。在其中一座时代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古墓葬封土中,出土了一件铁铧①(图98)。铁铧全重6斤2两,通长35厘米,壁厚1厘米。舌形,铧体中部隆起,尖部及边缘比较钝厚,后部为扁似梭形的銎,銎长15厘米、最宽8厘米、深14厘米。这件铁铧,形制明显具有汉代风格,与陕西关中陇县出土的汉代铁铧形制相同②。在甘肃敦煌还曾出土过一件形制、大小几乎与此完全相同的铜铧,现陈列在敦煌县文化馆,时代同属西汉。
昭苏地区,汉代属乌孙王国。昭苏县境保存的各种巨型乌孙墓冢,至今仍宛若小土山。在乌孙境内,西汉王朝曾派常惠率“三校”士卒,进行屯田③。乌孙王国作为汉王朝的局部,彼此关系十分密切。从这一背景,可以推见汉代铁铧在这里出土,应该与汉代屯田直接有关。军屯,是汉王朝政府主持的生产事业。生产工具、牛畜、籽种等,均由政府供给。使用铁犁、畜力耕田,汉代内地已经普遍。遣士卒到新疆屯田戍守,将这一套农业生产技术带到新疆来,是不言自明的。昭苏铁铧的形制与陕西、甘肃地区同时代出土物相同,正是有力而具体地说明了这一历史事实。限于考古工作规模,同时考虑到这类农业生产工具出土十分不易,汉代铁铧虽只见于伊犁昭苏一地,但它对于说明汉代各个屯田中心的耕地农具情况,却是一件有代表性的实物,具有典型意义。可以预期,随着今后考古工作更大规模、更深入地展开,在古代各屯田中心区域,必将会有更多的、同类性质的工具陆续出土。
在罗布淖尔地区楼兰遗址,新中国成立前曾经出土过不少晋简。其中有一条简文,残存部分文字是:“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晋代,西域长史曾一度驻节于此。从出土的许多木简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楼兰地区是一处重要的屯田中心。简文主要记述的就是有关灌水、管水、种地、锄地、收获等农事工作①,可证。在这样一处屯田中心,出土了上引简文,是并不奇怪的。简文虽并不完整,但文意基本清楚,“大侯”,为官称,可能是西域长史府下的属吏;“谨遣大侯究犁与牛”之“究”,有“穷尽”意。也就是说,命令大侯率属下的全部犁、牛到长更营下“受试”。也有人提出,这里“大侯”一词,可能是指鄯善王,因为鄯善王当时受晋封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王”,而“究”属“王名”但其他地方又未见有如此简称的例子②。然而,不论何种说明为当,全简文意,明显,与推行牛耕技术有关,却是无可怀疑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论:(1)晋代在楼兰地区的屯田,实行以牛为畜力的犁耕;(2)屯田士卒中有的似乎并不熟悉犁田耕地技术,故有训练、“受试”之举;(3)考虑到屯田士卒,其主体无疑是内地的农民。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屯田士兵,对牛耕技术,无疑是早就掌握的。因此,“究犁与牛到营下受试”,也很可能是与推行一种新的耕作方法有关。这几种逻辑推论,不论属于何种情况,都可以肯定一点:晋代楼兰地区,已经使用并相当重视用牛犁地的技术。
魏、晋时期,南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用犁耕地,在佉卢文资料中也有所见。新中国成立前新疆地区所见700多件佉卢文资料,其绝对年代可“断定为公元3~4世纪”③,主要发现于和田、民丰、且末、若羌等处古遗址。在700多件材料中,涉及农事者不少,主要用“耕地”、“耕种”一词,未明确说耕地或耕种之工具,只一处简文,明确使用了“犁地”的概念:“……关于犁地、大麦、小麦……由汝仔细……照拂。并且来伐罗色摩无论如何对此事一定非常热心……”④可见耕地时使用了犁,这与同一阶段内,前述汉文简牍资料可以统一。
当时犁地是怎样的方法?有一幅壁画可以帮助说明这一问题。在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第175号洞窟中,保留了几幅有关当地世俗生活的画面:如制陶、翻地、犁地等。这一洞窟壁画时代,据阎文儒教授考证,相当于晋①。有关犁耕的画面,以十分简练的笔法,勾勒出了二牛抬杠、合驾一犁、一人在后持物驱牛前行的情景(图99)。犁驾未具体刻画,但对关键性的部件——犁头,作了重点表现:犁作三角形,个体较大。这种二牛抬杠式犁耕方法及犁铧形制,与陕北出土东汉牛耕画像石、江苏睢宁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陕西米脂出土东汉牛耕画像石及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墓壁画、甘肃省酒泉嘉峪关汉魏壁画墓等所见图像,都基本相同,二牛抬杠式的犁耕方法、三角形犁铧,分不出什么差别②。
与这一时代相当,还有一件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出土的晋墓纸画(图100)。纸画着意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财富,优裕的物质享受生活。画面的三分之一,描绘了墓主人的田园、农具、谷物加工工具、庖厨等③。田亩整齐,禾稼迎风而动;田园旁的农具有木杈、木耙。据不同需要,木杈有双齿、多齿之别(这在今天的南疆农村仍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与木耙等农具置于一道,还有一件工具,其形如
“〓”,见者均不得其解。我认为:这也是一件犁。如将此图平置,其形当是“〓”,这正是一驾犁的侧视示意图。它虽然简单,但却本质地表现了犁梢、犁架、犁辕及系绳等有关部件。这应该是吐鲁番地区晋代用犁情况的直接说明。
不论是伊犁昭苏、罗布淖尔楼兰、库车拜城、吐鲁番,这些地点,在汉晋时期,都是新疆地区比较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当时的屯田重点地区。而铁铧的形制、二牛抬杠的牛耕图像等,又都与内地相同。这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两个概念:(1)新疆古代犁耕技术,深受祖国内地的影响。它们进入新疆地区的过程,与中央王朝在新疆地区大力推行屯田密切相关。这曾经给于新疆古代农业生产以有力推进,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2)从汉晋时期各地出土有关牛耕图像看,当时新疆地区牛耕技术水平与内地相当或相近,差距并不大。这对分析新疆古代农业生产水平,无疑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情况。
三
新疆地区虽早在距今2000年前的西汉即已知犁耕,自汉迄晋,随屯田事业的发展,内地移民(主要为屯田士卒)的不断进入,这一新的耕作技术在新疆地区也逐步得到推广、发展。但其进展是缓慢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耜耕,在犁耕开始一个相当阶段以后,在一些地区仍然保留、沿用。直到新中国成立,犁耕技术仍处于一种相当低下的水平。二牛抬扛,这一犁耕的基本特征,并没有什么显明变化。新疆地区农业生产力获得大的发展、解放,是在成立了新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真正成了生产、生活的主人以后。
在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沿的民丰县,北去100多公里,是现已沦为沙漠的汉、晋尼雅遗址。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后曾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发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次调查中,遗址内曾出土了不少铁、木工具,如铁斧、铁镰、木榔头、“木锨”及多量牧业工具等,但却始终未见过犁类工具①。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因铁犁铧十分珍贵,遗址废弃时随身带走,因此无法发现;再是当时这片地区并未用犁。一个现象支持后一种推测。这就是在报道过的各种工具中,有所谓“木锨”,它“长49厘米、肩宽22.5厘米,也是一件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②。”细审其图版,形制与哈密五堡所出木耜相同,偏近肩部也有对称两孔,明显用作缚绳安柄,应该也是木耜。哈密、民丰地区,土质疏松,这类木耜用于翻土并无困难。从汉、晋尼雅遗址仍然出现木耜而不见犁类工具看,犁耕在尼雅地区似仍未普及,或虽有使用必仍不普遍。因此,木耜未能被排除出历史舞台,而仍然是人们使用的重要农具之一。
与前述晋简中表明的西域长史曾在罗布淖尔楼兰国地区进行牛耕技术相对,同一遗址内,在被斯文·赫定取走,后经康拉德研究的晋简中,曾有一简,简文为“明日之后,便当砍地下种”③。它明白无误地揭示:晋时这片地区,还保留着地”(不是犁地)以种的方法,并未使用犁耕。这也可能正是西域长史要大力推行犁耕的背景。直到公元6世纪初,在宋云、惠生前往印度求经,路过这片地区时,还谈到且末“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①。这是宋云、惠生目睹手记的资料,应该是可靠的。它有力地揭示,在历经500年以后,新疆还有一些地区,仍未能用犁。在封建社会中,一种新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其推广、传播,造福于人民,是十分艰难、十分缓慢的。
考古资料中,汉晋以后,除在焉耆县唐王城发现过一件唐代铁铧外②,笔者再未见有关犁铧资料。
这一缓慢的耕作技术发展过程,直到新中国成立,在新疆农村没有什么变化。不仅牛耕的方法是与2000年前近同的二牛抬杠方式,南疆地区有的偏僻农村,甚至还有以人拉木犁作为耕作手段的。
关于南疆广大农村地区缺乏铁质犁铧的情况,从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调查资料中可以窥见大概。
据南疆农村的农业生产与生产力统计资料:总计916户,有犁143架③。
这就是说,大概平均6户多才能占有1架犁;而犁铧质量也不高,比较容易断裂。因此,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生产效率较低。据同书调查统计,“两头牛拉一架犁,只耕3亩地(一天)”,因为犁头小(3斤),犁身轻,不能进行深耕(约4寸);两牛一人,一天只能犁3亩地,这就使多翻地的耕作方法受到限制”。这种犁耕的实际效率,与人力比较,在当地也有一个估算:“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人工换牛工,一般是五比一,即一架牛对犁地一天,要还5个人工”④,生产力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
这些材料告诉我们,牛耕技术,在经历了2000年的发展以后,在新疆广大农村,仍然处于一个低下水平。它既表现在仍然是二牛抬杠的传统办法,铁犁质量低、轻、薄,耕地效率不高,而且数量极少,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极少数偏僻地区,由于铁铧犁少而价昂,而用木犁,或者用坎土曼翻地,这当然就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经济生活十分贫困。各级封建统治者不关心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广大贫苦农民无力改善自己的生产条件。交通不便、分散、孤立的各绿洲居民点,自成一个天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社会的闭塞、落后更加严重。
从犁耕技术在新疆的起源和发展这一小点进行分析研究,看封建社会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桎梏,可得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近几十年,劳动人民成了生产的主人,新疆农村生产条件的变化是巨大的,拖拉机遍及各地,就是这一巨大变化的特征。
附注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页。
②严汝娴:《藏族的脚犁及其铸造》,载《农业考古》,1982(1)。
③中国科学院新疆考队、八一农学院、新疆农科所合编:《新疆农业》,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④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载《考古学报》,1977(1)。
①《新疆疏附县阿克塔拉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载《考古》,1977(2)。②④《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③新疆文管会:《新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载《考古》,1982(2)。
①严汝娴:《藏族的脚犁及其铸造》,载《农业考古》,1982(1)。
②卢勋、李根幡:《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载《农业考古》,1981(1)
①《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②陕西博物馆、文管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鐴土》,载《文物》,1966(1)。③《汉书·西域传·乌孙》。
①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
②钱伯泉:《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疆》,见《新疆历史论文续集》,41页。
③关于佉卢文在新疆地区通行的年代,国内、外学者中有各种论点。此从马雍、布腊夫、榎一雄、长泽和俊说。见《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兼论楼兰遗址与魏晋时期的鄯善郡》,见《文史》,第7辑,73~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④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初稿),打印本。据英国皇家亚洲协会1940年英译本译出。此处所引,为第83条简文之分节录。
①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载《文物》,1962(7~8)。
②山西文管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载《考古》,1959(9);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载《文物》,1972(12)。上引材料,《农业考古》,1981(2),封底曾重发图版,可以参考。
③《新疆出土文物》,图版第四十五,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①②新疆博物馆:《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载《考古》,1961(3);史树青:《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载《文物》,1962(7~8)。
③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载《考古学报》,1977(1)。
①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5。
②黄文弼:《新疆考古三个月》,载《考古通讯》,1958(5)。
③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一《南疆农村社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上引有关调查数据,均见此书。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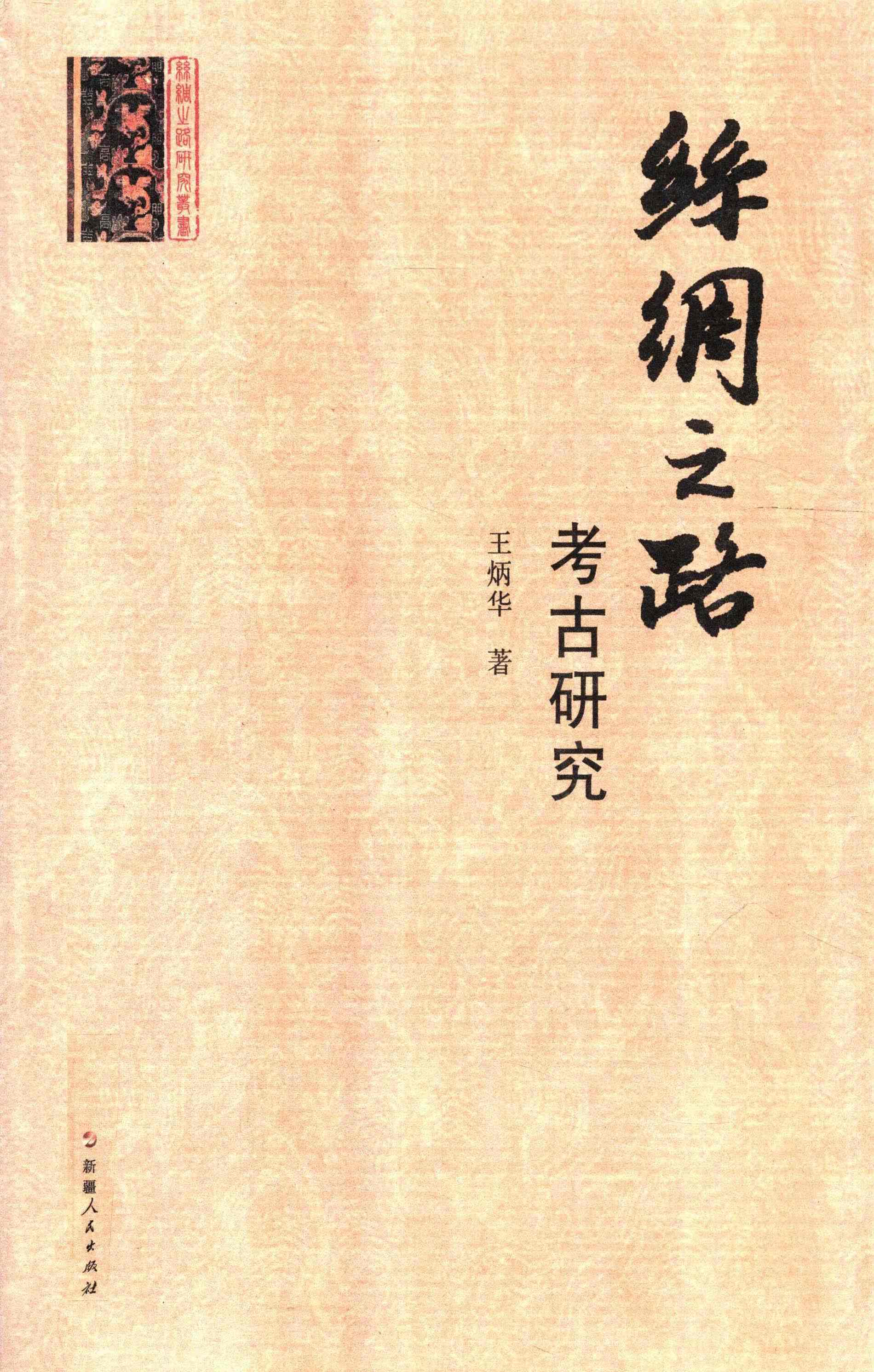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