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农业生产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93 |
| 颗粒名称: | 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农业生产 |
| 分类号: | F321.41 |
| 页数: | 17 |
| 页码: | 217-23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新疆地区农业生产的情况。 |
| 关键词: | 新疆 考古资料 农业生产 |
内容
古代新疆地区,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而且,早自原始社会阶段开始,就存在相当规模的农业生产。对古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汉代以来的我国汉文史籍中曾多少有所反映,保留了一些零散的记录,但从整个情况看,这些记录不仅比较简单,而且多有所缺略。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大大补充这一缺失。
一
新疆原始社会阶段已经有了农业生产。其绝对年代,据已掌握的部分测定数据,当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①。
在原始社会阶段的古遗址或墓地内,明确见到农业生产方面有关材料的,主要有下列几处: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公社乌布拉提大队内的阿克塔拉、温古洛克、德沃勒克、库鲁克塔拉等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们地处帕米尔东麓的山前地带,日前已沦为沙石荒漠,但在遗址中却见到明显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石镰、石砍锄,多量无孔半月形石刀、马鞍形石磨盘等,经济生活“已经以农业生产为主”②;阿克苏县喀拉玉尔衮遗址与此具有相同的特色,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原始社会公共墓地,出土了水质生产工具及小麦③;哈密地区哈密县五堡公社氏族社会墓地,墓葬内尸体、随身衣物均因干燥而不朽,墓葬内不仅出土了小米饼、青稞穗谷,而且发现了三角形木质掘土器、木耜,其时代据碳14测定,距今为3200~2960年左右①;天山中间的阿拉沟,配合南疆铁路工程,曾清理了大批早期墓葬,出土了胡麻籽,这片墓地,据文保所碳14测年结论,距今在2800~2200年左右②;巴音郭楞州和硕县辛塔拉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5米以上,遗址内见彩陶、磨制石器,应该不仅有农业存在,而且在这里古代人们曾经长期定居③;天山北麓,巴里坤县石人子、奎苏、冉家渠等处,彼此地域毗连,曾发现过多处早期遗址、墓葬,出土过炭化小麦粒④、大型磨谷器等。这种大型磨谷器,最大长达114厘米、宽50厘米、厚20~30厘米,一般也都长80厘米、宽50厘米左右。生产规模是不低的。遗址的时代经测定,当在距今2800年左右。
这些早期遗址,存在农业生产,从出土农作物籽实或生产工具特征可以作出肯定结论。我们所以要在这里具体罗列这些资料,是因为过去的论著中,一般都对此缺少比较明确的概念,不是把新疆地区早期考古文化整个列入所谓以狩猎、游牧为主的细石器文化带内,就是把农业生产的时代估计较晚,概念上也有含混不清处⑥。当然,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过去的考古工作做得还少,缺乏准确、科学的发掘资料。从现有的、虽说不上丰富但却稍稍深入分析了的资料,可以明确看到:早到距今4000年上下,从昆仑山北麓,到天山南、北麓,在相当广阔的一片地域内,在山前、河谷台地一带,已经肯定有了农业生产经济;它们开始的时间,当会较此更早。
而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汉代以后,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农业考古资料那就相当丰富多彩了。举其大者,如民丰县汉代精绝王国遗址内,发现过多量农具、农作物标本;伊犁汉代乌孙墓葬中见过铁铧;在轮台、沙雅、若羌等地发现过汉屯田遗址;晋、唐时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内,出土了丰富的农作物标本、农作形象的绘画;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发现自南北朝到宋、元时期的农作物籽实等等,都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新疆地区古代农业经济的具体认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农业考古资料,将为我们对新疆古代农业史的研究开拓一个新天地,在这里人们将发现许多古文献上无法见到的生动素材。
二
可以直接表现新疆地区古代农业生产情况的,莫过于从各处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农作物籽实、穗壳,出土简牍、文书中关于这类作物的直接记录。现据考古资料,按类别、时代条列于下(已作过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则稍予说明)。
(一)粮食作物
1.小麦
首见于距今近4000年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中。由于这里极度干燥,尸体、殉物也大都不朽。出土时均置于墓主人头侧的草编小篓中,十多颗至一百多颗不等。保存良好,外型完整,麦粒显深褐色,籽粒不大、不太饱满。经初步鉴定,其品种有普通小麦和圆锥小麦两种①。较之新疆博物馆所藏、巴里坤石人子乡炭化小麦粒,后者籽粒稍大,比较饱满。在哈密五堡墓地中,也发现过一枝小麦穗。汉代以后的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小麦和麦类加工食品更多。民丰县尼雅汉代遗址中不仅见到小麦实物,还发现过一根麦穗②。罗布淖尔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的汉文简牍中有种植小麦的明确记录③,同一阶段内的佉卢文简牍中也提到小麦种植及灌溉④。若羌县米兰吐蕃族古戍堡中发掘到过唐代的小麦,在同时出土的吐蕃文木简中也涉及分占耕地、种植小麦的内容⑤。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城郊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两处古墓葬地,出土了自晋迄唐代的小麦及麦面加工成的馕、水饺、馄饨、各种点心及麦麸、麦草,同时出土的文书中也有关于小麦租赋、借贷的文契,数量不少⑥。此外,在焉耆县唐代古城“唐王城”内,也发现过小麦及磨得很细的面粉⑦。
小麦是世界最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也是我国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上述并不完全的资料说明,唐代以前,新疆地区已经普遍种植小麦。过去,一般认为它在新疆只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⑧,现在孔雀河出土的小麦标本,把小麦在新疆地区的栽培历史提早到4000年前,而且对新疆小麦的起源也提出了新的见解①,在农学史研究上的意义是很大的。
2,粟
粟即小米,这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物品种,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地区。我国至今还是主要的粟类生产国。由于粟具有高度的抗旱能力,生长季节较短,耐储藏,因此,它也是新疆地区古代栽种比较多的一种粮食作物。最早的粟类标本,见于距今3000年左右的哈密五堡古墓地。主要是一种小米饼,出土颇多。大部分作方形,长约20厘米,厚3~4厘米左右,由于粉碎不好,饼内的卵圆形小米颗粒仍清晰可见。民丰县尼雅遗址,即汉代精绝王国的废墟内,曾在数处房址中见到小米,有的房屋遗址内铺得厚厚一层,因年久而结成了硬块②。楼兰地区,也曾见到粟类遗物③。吐鲁番晋唐时期古墓内,更见到多量瓶装、小五谷袋装小米以及“付麦、粟账”文书残纸,陶碗内盛着的小米饭等。可以看到,小米与小麦一样,是这里人们的主要粮食。焉耆县内:“萨尔墩旧城遗址中有许多圆形坑穴,直径大小不一,小者约1米左右。坑穴内均是粮食……很清楚地可以看到黄米……”④唐王城内也发现过小米。
3.黍
即俗称的糜子,它和粟类似,籽实呈球形,也是生长季短,性耐干旱的一种农作物。民丰尼雅遗址、吐鲁番晋唐时期古墓中均见过不少糜类籽实。在汉晋时期的楼兰古城内,“在古城建筑物上,涂抹着许多草拌泥的墙皮,其中掺杂有大量麦秸、糜秆的碎节和粒壳。同时,在城内距塔东侧约32米处一堆散乱木材下,发现了深达70厘米的糜子堆积层,一粒一粒的糜子至今还是黄灿灿的”,⑤颇可以说明这也是新疆古代大量种植的粮食作物之一。
4.高粱
见于焉耆县萨尔墩旧城遗址之窖穴内,此城的时代可能早到汉;同县唐王城中亦见⑥。高粱在我国也有久远的栽培历史,我国是高粱的原产地之一。这种作物不仅耐旱,而且能适应盐渍较重的土壤。焉耆,就是盐渍较重的一个地区,正是在这里发现了高粱的籽实,可以证明古代新疆各族劳动人民对高粱的特性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5,青稞
哈密五堡墓地内发现过青稞穗壳,这是新疆所见的最早实物,稍后,在民丰尼雅遗址中也见到青稞籽实(原报告中把它括注为“燕麦”)①。吐鲁番晋唐古墓中出土过不少青稞籽实,值得一提的还有在这里出土的一份唐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马料账,逐日登记了马料消耗情况,所用饲料均称“麦”或“青麦”②。“青麦”一词,从冬日马料账上仍然使用分析,可能就是“青稞”的俗称。因为,这时怎么也不可能有未成熟的青麦的;而且,量词都是斛、斗、升、合,这一分析如大致不错,从这份马料账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青稞栽种面积必甚广。此外,在若羌县米兰古堡中也发现过青稞籽实,亦可见其种植地域之广大。
(二)豆类作物
据考古发掘中出土实物统计,新疆古代种植的豆类作物有蚕豆、黑豆,均见于吐鲁番(其他地方未见,当系发掘工作的局限),时代为高昌至唐。蚕豆籽粒椭圆偏平,不大。所谓“黑豆”,细审实物,籽粒不大,呈椭圆形或长椭圆形,当为赤豆之一种,只是外表黑色,故也俗称“黑豆”。这种黑豆,西北地区栽培颇多,因为它耐旱,生长期短,成熟期要求干燥,对于新疆地区的气候条件来讲,是颇为适宜的。
(三)油料作物
胡麻
胡麻至今仍是新疆地区普遍栽培的油料作物之一。在天山阿拉沟古墓地内曾发现胡麻籽,籽粒卵圆形而稍扁,暗褐色,表面光泽。出土后曾请新疆农科院进行鉴定。此外,在吐鲁番晋唐古墓地,焉耆唐王城内也都见过胡麻籽实。
(四)纤维作物
1.棉花
新疆地区种植棉花的历史很早。民丰县出土的东汉墓中已见棉布③,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古墓中,所见棉织物资料更多。在出土的高昌时期的文书中,有借贷棉布的内容,结合文献记录,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地区已经大量植棉并发展起了一定规模的棉纺织业④,在同一时期或稍后的塔里木盆地内,如于田县屋于来克北朝时期遗址中见到了棉织印花布⑤,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晚唐地层内不仅发现了棉花,而且发现了棉籽实物。可见,自南北朝以后,吐鲁番及塔里木盆地各处,已经广泛植棉并发展起了棉纺织业。
对巴楚出土的棉籽,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曾经进行了分析、研究。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色黄等特点,是草棉(即非洲棉)种子①。这种草棉,喜温、喜光、耐旱,在中亚早有种植,也适宜于新疆及甘肃西部地区的气候特点,但纤维短粗、产量低,这又是其弱点。新疆很早即种植这类草棉,表现了这里和中亚地区久远而广泛的联系。
2.大麻
新疆地区出土的麻类织物资料丰富。前引距今约4000年的孔雀河古墓地内,出土的草编织物中,经鉴定,使用了大麻纤维。同时,也使用着罗布麻(亦称野麻)的茎、秆以编织日用器物。可见新疆地区使用麻类纤维是非常早的。后期,则更为普遍。以吐鲁番为例观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的晋、唐时期古墓葬中,没有一墓不见麻类织物。衣服、被褥、鞋袜、谷物袋、麻绳等等,都用着麻。与麻类织物相比较,无论丝,还是棉,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当然,这大量的麻织物中,据资料本身的题款,可以肯定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内地有关省区②,但也同样可以肯定,必有相当部分或大部分是产自本地,墓内有时以麻丝一束随殉,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五)瓜果类
新疆地区瓜果资源非常丰富,是许多瓜果的原产地,素有“瓜果之乡”的美称。有不少珍品、名产,历史上早就传入中原地区,不仅博得了赞誉,而且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是各族人民经济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古文献中,关于西域地区盛产瓜果的记录不少。新疆,尤其是南疆广大地区,各种瓜果的栽培也确有悠久历史,而且具有普遍性。但限于目前考古工作,我们下文所引资料主要来自吐鲁番盆地内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地,这里干燥,墓内人殉的果品实物得以不朽。一斑可以窥豹,从墓中普遍见到的种种果品,多少可以透见古代新疆瓜果生产的概貌。
1.葡萄
这是新疆地区有名的特产。吐鲁番地区又居全疆之冠,这里日照充分、热量丰富,果实含糖量高。除供鲜食外,制干、酿酒,也都是佳品。直到今天,新疆吐鲁番的葡萄及葡萄干仍是驰名中外的上品。这里晋、唐时期古墓葬中,往往以葡萄入殉,可以看到历史上它一直就是人们珍视的果品。其栽植之盛,从墓葬壁画中有葡萄园,出土文书中有“卖”、“租”葡萄园的契纸,有关葡萄酒的记录等,均可透见这一果品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2.甜瓜
甜瓜吐鲁番古墓内,见过甜瓜子、甜瓜皮。较之其他瓜果,发现数量不算多。
3.枣
这是吐鲁番盆地中普遍见到的一种随葬果品,可见当时栽植必多,人民喜食。枣干紫黑色,个体不大。
4.核桃
在吐鲁番古墓中出土也多,最多一墓达数十枚。果核较小。除吐鲁番外,巴楚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亦见①。
5.梨
新疆地区是梨的盛产地,主要品种有白梨、新疆梨、秋子梨、西欧梨、杏叶梨五个品种。而其中的新疆梨,据俞德浚教授研究,认为是“中国梨与西欧梨的自然杂交后裔”。对它的栽培历史,是果树研究人员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的多量梨干中,研究人员曾对唐代墓葬出土的梨干进行了分析鉴定:“果实如梨形,淡黄色,梗细曲,长于果径两倍,无梗洼,萼宿存,开张,基部相连,无萼洼;果心小,石细胞多,果心近萼端,是典型的新疆梨。”②说明新疆梨的双亲——中国梨和西欧梨在新疆地区的栽培历史肯定早在唐代以前。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利用新疆特别干燥的自然条件而得以保存下来的各种作物籽实标本,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当可发掘出许多珍贵的科学结论。
6.李
吐鲁番墓地出土颇多,果实近圆形,黑褐色。从出土较多看,自高昌迄唐,它在这里并不是很稀少的果品。
7.桃
汉晋时期的楼兰城遗址内③,吐鲁番晋唐古墓中均见。汉代尼雅遗址中亦见④,出土物均是桃核。
8.杏尼雅遗址中曾有所见⑤,吐鲁番古墓地内也见到杏核。桃、杏类果品,均来自内地。
此外,据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唐代吐鲁番地区还出土了芝麻、巴旦杏。芝麻原产非洲,巴旦杏原产伊朗。看来,新疆地区引进、栽培的历史也是很久的。
(六)其他作物
在介绍有关新疆考古资料中所涉及的农作物品种时,不应忽视对饲料作物(如苜蓿)的栽培。
新疆地区的经济,畜牧业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对饲料物的栽培、种植,古代曾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吐鲁番地区出土过一件北凉时期的文书①,文内提到所有在学的儿童要从役“芟刈苜蓿”。新中国成立前所见吐鲁番地区出土文书也有关于种植苜蓿的资料②。如高昌故城(原书称哈拉和卓古城)中出土的“伊吾军屯田残籍”,其中有“……苜蓿烽地五亩近屯”字样,诚如黄文弼先生所说:“苜蓿烽为一地名,盖因种苜蓿而得名。”
苜蓿是富有蛋白质的优良饲料,再生能力强,在水肥充足的情况下,年可收获数次,而且管理省工,是经济价值很高的饲料作物。从史籍看,新疆地区很早就有苜蓿的栽培,而且早在汉代,随优良马匹进入内地,苜蓿也被引进到了内地。此外,在吐鲁番晋、唐时期古墓中,还出土了为数极多的葫芦片。葫芦,原产印度,后引入我国,嫩果可作蔬菜,老果可作盛器。又在民丰县汉尼雅遗址中,发现过不少干蔓青。蔓青,即芜菁,干、鲜食用均宜。
这些,都多少反映新疆古代的一点蔬菜情况。可见早在晋、唐以前,新疆既有
苜蓿,也有葫芦和蔓青。
三
在认识、研究新疆地区古代农业生产状况时,各种农业生产工具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应予认真分析。
在整理有关农业生产工具的资料时,我们感到有两个比较显目的特点:一是原始社会阶段或较早期遗址内,木质生产工具占有很大比重,具有重要地位;再是从工具角度,可以十分鲜明地感受到中原地区对这里显著的影响。
在前述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原始社会墓地内,曾出土过一件木质生产工具,长22厘米、宽8厘米,尖端及两侧薄刃锐利,有长期使用的痕迹,如附以木柄,是不错的挖掘沙土的工具。
出土木质工具稍多的是哈密五堡公社内的原始社会墓地。共见两根三角形掘土器、一件木耜③。这是在不见其他任何石质或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出土的,颇可见木质工具当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这种木质掘土器,系选取与人高比例相称、便于直立劳动的硬质木杆,微显弯曲,然后把端部细致加工成三角形,尖部锐利。掘土器曾经过长期使用,不仅尖部光滑锐薄,扶手部分也因长期使用而很光洁。其一通高90厘米。这种木质掘土器,在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中也曾发现过,如云南省独龙族,“铁质工具数量极少,在生产中不占什么地位。在木质工具中,使用最广泛的是‘郭拉’和‘宋姆’。……‘宋姆’即点种棒,把小竹棍或小木棒一端削尖或以火灸尖即成。用于挖穴点种,用毕即弃”①。四川省甘洛县藏族(自称“耳苏”)人也曾使用过这种尖木棍,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成脚犁,在耳苏人古老的传说中“……他们从事过种种原始的生产活动,留下了许多原始工具的名称,如狩猎用的石箭头‘耳买’、骨箭头‘日古买’。农业则用石斧‘吴戳’伐木,用称为‘布’的尖头木棍或尖竹棍发土点种”。“脚犁就是由尖木棍发展而来的,先是在尖木棍上安装‘扶手’……后来由扶手的启发加上一个脚踏横木,手足并用,遂成木耒”②。无论独龙族中的“宋姆”还是耳苏入中的“布”,与五堡所见三角形掘土器都是同一性质的工具,基本形制、功用都同,只是五堡的掘土器已较进步成型,不再随用随弃了。
与这种三角形掘土器共出,在五堡见到木耜(原报道中称其为“方头木锨”),长28.5厘米、宽16.5厘米、厚1厘米,刃部锐薄,偏上部见对称两孔,便于安柄。这种木耜,在民丰县汉代尼雅遗址中也有发现③(原报告中称“木锨”),矩形,长49厘米、肩宽22.5厘米,上部有两孔,便于安柄。同一遗址内,出土铁工具(如斧、铲、镰)不少,但不见犁,而出土了这种木耜,似可以说明这片地区当时木耜仍未退出历史舞台。
这类木质生产工具,在天山阿拉沟古墓区也有所见,有一端磨尖的木器,也有作双叉形,端部经过加工,十分尖锐。
上述汉代尼雅遗址,还曾出土过一柄保存良好的木榔头,通长108厘米,头长46厘米。这种木榔头对于碎土或修堤筑坝等水利工程,都是十分适用的。
汉代以后,由于汉王朝在新疆地区进行屯垦,各种农具及中原地区的农作物,随屯田士卒、应募农民不断进入,给新疆农业生产以重大影响。
汉尼雅遗址中出土的铁镰刀,和“今天陕西关中地区农民使用的镰刀形状相同”④。在伊犁地区的昭苏县,相当于西汉时期的乌孙墓出土一张铁铧,舌形,中部鼓凸,铧体削面近等腰三角形,后部有銎,銎作扁圆形。通体厚重、粗糙。这种形制,与关中礼泉、长安、陇县等地出土的西汉中晚期“舌形大铧”①形制相同。利用这种铁铧发土,效率当然会大大提高一步。
汉代开始在新疆地区屯田,牛耕技术肯定会相应进入新疆地区。在罗布淖尔楼兰地区出土的晋简中,有一支简文是:“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谐营下受试。”②这里是晋西域长史的驻节地,仔细推敲简文文意,可以看到西域长史府至少在屯田部队中曾经有组织地大力推广一种新的驭牛犁耕技术。“大侯”是西域长史的下属,责其“究”(“究”有“穷尽”意)犁与牛到“营下”受试考核,颇见认真。
关于这一阶段犁耕的具体,特点,可由同一时期内龟兹(今库车地区)的一幅牛耕图壁画帮助说明。在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第一百七十五窟(时代约当两晋)中,“在坐佛的周围,画出类似‘二牛抬杠’的牛耕图,有宽刃的镢和锄等工具。从牛耕图中宽大铁铧来看,与发现的汉代铁铧比较接近”③。细审有关画面:一人右手持物,驱赶二牛前行,此二牛合驾一辕,其后为一呈三角形尖刃的宽大犁铧,双牛负驾吃力。这一“二牛抬杠”式耕作画图,与同一阶段内嘉峪关壁画墓中所见牛耕图近似。只是因受穹形洞窟的局限,画面无法展开,对犁的形制没有具体刻画。同一洞窟内,还有一幅表现了砍地、翻土动作的画面:裸身、赤足、戴帽、着短裤的二龟兹人,两腿以丁字步式站立,上身前倾,作奋力劳作状。他们所持镢、锄,略近方形、宽刃。这种形式的砍锄与今天新疆境内普遍使用的“坎土曼”形式酷似。“坎土曼”,新疆广大农村翻土、提土、修渠、筑堤等等工作,均得力于斯,差不多是小件农具中的万能工具,维吾尔族农民使用得心应手,十分灵便。
有关这一阶段农作工具情况的,还有1964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中出土的一幅纸画④,画幅长106.5厘米、宽47厘米。绘画内容表现了统治阶级人物的生活。其中有三分之一画面,表现了墓主人的田园及庖厨。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所以这实际是墓主人财富及享乐生活的写照。在田园生活画面中,可以看到整齐的田亩,茂盛的禾稼,旁侧是草杈、耙等农具,木耙长柄多齿。另有一件农具颇费解,从形象分析,这应当是犁。只要转一角度,正是一架犁的侧视图,有犁辕、犁梢、犁架及系绳等。在庖厨画面内,还有磨、碓的形象,磨以长木杆作联动轴,由人推转;碓是用足踩动。这些谷物加工工具,与内地农村流行形式完全一样,明显可以看到,这是由于接受后者的影响。这一情况,当与吐鲁番地区汉晋时期居民相当一部分来自甘肃等地有关,他们从内地迁居吐鲁番时,同时带来内地一套耕作、谷物加工技术,是毫不足怪的。这对新疆古代农业的发展,曾起过良好作用,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四
新疆是一个干旱地区,除少部分地区或山区外,全年降水量很小,在塔里木盆地及吐鲁番盆地内,基本上全年无雨,这样的降水量是无法“靠天吃饭”的。因此,新疆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其首要前提之一,就是必须解决一个农田水利灌溉问题。公元6世纪初,当宋云、惠生过新疆地区时,看到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地区)“民决水而种”。他们听说中原地区的农田是“待雨而种”时,觉得十分好笑、不可理解:因为“天何由可共期也?”(见《洛阳伽蓝记》)。塔什库尔干地区雨水还是较多的,塔里木盆地内这一差别就见得更大了。这一生动的记录,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新疆地区水利灌溉是农业生产的前提。
汉代以前的水利灌溉遗迹,目前还未发现。那时的农业,规模不大,农田也都选择在引水比较方便的河道下游,这些地方地势比较平缓,引水比较方便。目前发现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哈密五堡古墓地,都有这样的特点。而汉代以后,中央王朝在这片地区推行屯田,水利事业也相应得到进一步发展。
西汉王朝在新疆的屯田,是按桑弘羊的筹划实施的。桑弘羊给汉武帝刘彻的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在轮台地区“通利沟渠”,用部队进行屯田;再是有一定基础后徙民实边,“益垦溉田”①。也就是说,一是强调了在屯垦地区首先要注意做好灌溉事业,这样,农业生产才有可能进行;而针对新疆地区地广人稀的特点,募民实边,发展农业生产也就有了保证。
汉代以来,在新疆地区兴修水利的情况,既见诸文字记录,也有不少遗迹可寻。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篇》中留有一条西域各族人民兴修水利的故事:曾有“敦煌索勘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①、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人,横断注滨河,灌浸沃衍,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凌冒堤……大战三日,水乃迥减。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租粟百万,威服外国”这段记录,除去神话外衣,其实质内容颇可信从。迁酒泉、敦煌人到新疆屯田,是合理的,历史上曾再三实行过。横断注滨河、拦蓄河水,使不入盐湖,则下游沃野可尽得开发。因此,这段记录颇真实地表现了公元6世纪以前西域地区修水利、开屯田的史迹。表现了历史上人们对兴修水利的必要性及有关筑堤坝、蓄洪水的工程知识。反映了要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才能完成较大的工程,而得农业发展之功效。下文介绍的几项较大水利灌溉遗迹,没有这样的组织力量,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沙雅县汉人渠
在库车地区沙雅县、新和县境内,黄文弼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进行考古调查中,曾发现多处遗址及屯田遗迹。其中有“长达二百华里之古渠……在渠旁及遗址中,曾觅出汉代五铢钱及陶片”,“古渠位于(英业)古城之东北”,“维吾尔语称为黑太也拉克,即汉人渠”。“此渠位于喀拉黑炭巴扎之西,地名曲鲁巴哈。由干河分支东行,经英业入戈壁,一直往东,至爱默提草湖遂不见,全长约200余里。附近古城有阿克沁、满玛克沁、黑太也沁、于什格提,皆附于渠旁”。“渠为红土所筑,宽约6米。至于什格提东面,分为三渠至草湖”。对这一长100公里、宽6米的古渠及沿渠的古城废墟,1981年,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伊第列斯等人,曾经再履其地,渠道痕迹仍宛然在目。渠道所经,因沙淤土积,均高于地表,宛若一道逶迤远去的土堤。这次调查中,在傍近古渠的一处古城址“羊达克沁”,群众曾采集到唐代钱币。这些迹象表明:这片地区,自汉迄唐,一直是一片规模宏大的屯田中心,但目前却已是盐化相当严重的荒漠了。
(二)若羌县米兰古堡附近,农垦勘测设计人员曾发现一处古代灌溉渠系统
渠系与古米兰河通联,“干渠全长8.5公里,渠身宽10~20米(包括渠坝),渠高3~10米(自地面算起)……大型支渠7条,总长28.4公里”。“小的毛渠阡陌纵横,密布于各支渠间的灌溉面积上”。灌溉面积实测达1700亩①。这一灌溉遗址,考古工作者李征同志1973年也曾进行过调查。渠道所在,所以会远远高于地表,主要原因是渠内大量淤沙(米兰河含沙量很大,常水期每升含沙3.8~6.6克,洪水期达27.9~52克)。淤沙使渠床不断升高,清淤沙土不断垒积渠道两旁,逐渐形成这种景观。据水利工作者饶瑞符测量分析,这一灌溉系统的“干、支、斗渠,全部沿最大坡度,垂直地形高线布置。7条支渠均匀地顺地形脊岭,采用双向灌溉,有效控制着整个灌区,全灌区没有不能上水的土地”。“整个灌溉系统的布置较为合理,而灌渠渠线的正直、整齐,采用双向灌溉和集中分水的方式,水头控制良好,因地制宜与渠道网的完整性,为其他旧灌区所少见。在无地形测量资料的古代,全凭目测与生产斗争经验的条件下,足以说明汉代在此兴建水利灌溉系统有较高的水平”②。这一渠系的修建年代,目前未得文物直接证明。但据《汉书》,汉立尉屠耆为鄯善王,“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③,冯承钧认为“伊循是今之弥朗”④。若然,这一古代灌溉渠系,应该就是汉代伊循屯田的遗迹。
(三)轮台地区汉代屯田遗址
据黄文弼先生调查,在轮台县克子尔河流域,有古堡及城市遗址多处,如柹木沁、黑太也沁、柯尤克沁、着果特沁等。从调查所得遗物看,除黑太也沁可能为唐城以外,余均汉代遗址。遗址周围,有“干渠;埂界犹存,疑为古时垦殖区域”。“柯尤克沁……可能为汉仑头国故址,城西有古时流水沟渠,盖引克子尔河水灌城中者”。“着果特沁旧城……城中有红底黑花陶片,与柯尤克沁旧城所拾相同,皆为纪元前后之遗物。又拾铁矢镞一,中实有柄,系汉物……疑此城为汉代屯田轮台时所筑。因城有营垒,当为田卒所住,城中有粮食,城南及东皆为红泥滩,古
时沟渠田界痕迹尚显然可见”⑤。这片地区是汉代屯田中心,曾经繁荣一时,但目前已成一片盐渍碱荒漠,渠沙淖泥遍地,盐衣白末到处可见。
其他,为于阗县克里雅故道下游的喀拉墩遗址。据笔者调查,遗址区内渠道纵横,田畦清晰,也是晋南北朝时期凭借人工灌溉事业而发展成功的一片绿洲。
(四)在罗布淖尔地区所出汉晋简牍中,不少筑坝、修水利、管水浇地资料,颇可见当日屯田地区对水利的经营
……本空决六所并乘堤已至大决中……五百一人作……增兵”“将张佥部见兵二十一人大麦二顷已截二十亩下〓九十亩溉七十亩,小麦三四亩已口二十九亩禾一顷八十五亩溉二十亩锄五十亩(简面)将梁襄部见兵二十六人大麦六十六亩已截五十亩下〓八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六十三亩溉五十亩禾一顷七十亩锄五十亩溉五十亩(简背)
“水曹请绳十丈”等①,类似简文还有。从这些断简残牍中可以看到,当时在楼兰地区的屯田,水利是关键,有“水曹”司其事,堤坝有人管理,土地分划成地块,分别由各部负责种植及管理,锄、灌、截之进度均须定期检查、呈报。组织是非常严密的。
(五)关于新疆古代水利灌溉事业的经营建设,吐鲁番出土文书、碑刻资料,也提供了十分具体的记录
吐鲁番盆地内,几乎终年无雨,而气温高,蒸发强。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农业生产,比较完备的水利灌溉工程,是一个前提。自汉代始,这里就是汉王朝、匈奴屯田的所在,对水利灌溉必已有一套办法。有人认为,新疆在汉代已知坎儿井②,但在吐鲁番地区考古调查中,却未见任何可以说明这一问题的资料。相反,从吐鲁番唐代墓葬中出土的文书资料看,显示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水利灌溉系统。有一件唐高昌县“为申修堤堰料工状”③,文书残纸上,钤有“高昌县印”。
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到,每年用水期过后,高昌县必须组织众多人力(从这件文书看,动用人工达1450人),对“新兴谷”内的“堤堰”及县城南的“草泽堤堰”和“箭干渠”进行维修。据此,可以明确肯定:在山区当有水库类性质的设施,盆地内低凹处也有塘坝及干渠,它们构成一个灌溉系统。
吐鲁番盆地的地理特点,决定了盆地内的灌溉用水主要得之于天山雪水。这种雪水年均流量稳定、变化小,农业用水保证率较高,对农业是有利的;但这种雪水,夏日天热时水量集中。因此,在夏日雪水大量下来前,每年都必须对水库、塘坝等蓄水处的堤堰及渠堤进行检查维修加固,保证安全。而这种水库、塘坝对调节用水是十分必要的,看来,这件申修堤堰的状文,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年年如是,故可“准往例”处分。这种关系整个社会命脉的水利系统,工程的兴修、维护、管理,必须有组织、有专人负责,县内是“知水官”主持其事。从这一文书出发,可以大概透见高昌县的水利灌溉组织情况。
在吐鲁番这样的地区,有水才有生命,才有农业。水是十分珍贵的。又一件出土文书就十分形象地表明了这一情况。录文如下:
城南营小水田家 状上
老人董思举
右件人等所营小水田皆用当城四面豪(濠)坑内水,中间亦有口分亦有私种者,非是三家五家。每欲灌溉之晨,漏并无准。
只如家有三人两 人者,重浇三回。
孕独之流,不蒙升合。富者因滋转瞻,贫者转复更穷。总缘无检校人,致使有强欺弱。前件老人性直清平,谙识水利,望差检校,庶得无漏。立一牌牓,水次到转牌看名用水,庶得无漏。
如有不依次第取水用者,请罚车牛一道远使,如无有牛家,罚单功一月日驱使。
即无漏并长安稳。请处分牒件如前谨牒
在浇地的关键时刻,凭靠城濠内水利浇地的各家营小水田者,彼此为水而纠纷,要求官府调理,委定专人管水,保证合理使用。这一状文,十分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吐鲁番盆地内水的珍贵。一个合理的灌溉系统对吐鲁番正常农业生产的绝对必要,从这里可以得到更深的体会。
在结束这节文字前,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历史上那些屯田中心如轮台等地,为什么今天却都成了一片荒漠式盐田碱滩?2000年前的良田沃野成了今天的不毛之地,这一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以轮台地区为例。广泛发育的天山前山地区主要是中生代、新生代的含盐岩系,可溶性盐分极多,高山雪水至此,自然形成为浓度较大的矿化水。流经山前地区后,矿化度当会更高。在河流下游垦殖的荒地,亦即古代的屯田中心,用这种水灌溉,而又没有一套排盐碱措施,就会使盐分不断停积于农田地带,这种积盐过程是十分缓慢的,但经过相当一个历史阶段,就会达到一定浓度,最后使农田荒芜、作物不生。在古代人们对水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盆地内排水又不畅,终至无法逃脱土地盐碱化的惩罚。在其他古代屯田地带,也往往经历过相类的过程。这个问题,在今天新疆地区的农田生产、水利灌溉中,仍是人们必须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五
汉代以来,在新疆地区广泛进行屯田,历唐迄清,这一事业始终不衰,对新疆地区的农业发展,曾发挥过重大作用,无论是士兵还是“累重敢徙”的应募者,主要成分无疑都是中原地区的农民,他们在新疆屯田,自然就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农具、籽种、耕作方法等等,这在上文已经论及。
屯田生产,对新疆地区的开发建设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新疆地广人稀,要靠这里有限的人力、物力维持相当数量的边防部队、各种管理机构,保证“丝绸之路”的需要等,肯定会十分困难,利用部队并募民屯田自养、再上缴国家一定粮食,就可缓和并解决这一矛盾。在论及新疆古代农业生产问题时,屯田是一项必须重点研究的课题。
关于这一问题,上文已有相当涉及。这里将直接打开古代屯田的几件文物收录于后,以利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民丰县汉代尼雅遗址,曾出土“司禾府印”一方,边长2厘米,高1.7厘米①。从印文“司禾府”可以推见,是汉晋时期与屯田事务有关的一个机构。
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许多文书直接表明了当时屯田的情况。
1972年出土的“伊吾军纳粮牒”(长27.5厘米,宽8.5厘米)②,其上钤“伊吾军之印”,表明为正式公文,残留文字有:
敕伊吾军 牒上西庭支度使
合军州应纳北庭粮米肆仟硕 叁仟捌佰伍拾叁硕捌
头叁胜伍合军州前后
纳得
肆拾叁硕壹斗陆胜伍
合前后欠不纳
壹佰玖拾柒硕纳伊州仓讫 叁仟陆佰肆拾陆硕捌
头叁胜伍合纳军仓讫。
从这一文书可以看到伊吾军屯田的规模,每年应纳的粮额。而且,不仅缴纳军仓,以供军需(这是主要部分),还要纳一部分到“州仓”,以供地方行政需要。唐代边防军的屯田,组织、管理是十分严密的。合戍守与生产为一体,虽小到只有两三人的烽燧,其生产任务也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反映这一情况的残文书出土颇多,试举出土的两件残文书为例。其一为“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①,从文书残存文字可以看到,在西州都督府管领下,合诸镇、戍军卒营田总数约十余顷。提到的镇、戍名称有“赤亭镇”、“柳谷镇”、“白水镇”、“银山戍”、“方亭戍”、“维磨戍”等,同墓又一件残文书,内容有:
……田水纵有者去烽卅廿
每烽烽子只有三人两人又属警固近烽不敢不营里数既遥营种不济状上者曹判近烽者即勒营种去地远者不可施功当牒上支度使讫至开十闰五月二十四日被支度营田使留后司五月十八……
分析文意,可以看到部队屯田系归“支度营田使”负责管理。每座烽燧,烽子即使只有两人三人,也有明确的生产任务。如遇特殊情况,屯种任务不能完成,必须逐级申报,“近烽者即勒营种;地远者不可施功,当牒上支度使”。由于文书残缺,不可尽读,但小至两三人的烽燧也有明确的生产任务,确是明白无误的。
这几件文书,虽只涉及伊吾军及西州都督府,即只关系到哈密及吐鲁番地区,但却具有一般性意义。其他地区的屯田情况,与此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在这样严格的管理制度下,生产得到了保证,军资有了着落,人民多少减轻了负担,有利于边防,也有利于新疆地区的社会生产事业,其积极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一
新疆原始社会阶段已经有了农业生产。其绝对年代,据已掌握的部分测定数据,当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①。
在原始社会阶段的古遗址或墓地内,明确见到农业生产方面有关材料的,主要有下列几处: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公社乌布拉提大队内的阿克塔拉、温古洛克、德沃勒克、库鲁克塔拉等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们地处帕米尔东麓的山前地带,日前已沦为沙石荒漠,但在遗址中却见到明显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石镰、石砍锄,多量无孔半月形石刀、马鞍形石磨盘等,经济生活“已经以农业生产为主”②;阿克苏县喀拉玉尔衮遗址与此具有相同的特色,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原始社会公共墓地,出土了水质生产工具及小麦③;哈密地区哈密县五堡公社氏族社会墓地,墓葬内尸体、随身衣物均因干燥而不朽,墓葬内不仅出土了小米饼、青稞穗谷,而且发现了三角形木质掘土器、木耜,其时代据碳14测定,距今为3200~2960年左右①;天山中间的阿拉沟,配合南疆铁路工程,曾清理了大批早期墓葬,出土了胡麻籽,这片墓地,据文保所碳14测年结论,距今在2800~2200年左右②;巴音郭楞州和硕县辛塔拉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5米以上,遗址内见彩陶、磨制石器,应该不仅有农业存在,而且在这里古代人们曾经长期定居③;天山北麓,巴里坤县石人子、奎苏、冉家渠等处,彼此地域毗连,曾发现过多处早期遗址、墓葬,出土过炭化小麦粒④、大型磨谷器等。这种大型磨谷器,最大长达114厘米、宽50厘米、厚20~30厘米,一般也都长80厘米、宽50厘米左右。生产规模是不低的。遗址的时代经测定,当在距今2800年左右。
这些早期遗址,存在农业生产,从出土农作物籽实或生产工具特征可以作出肯定结论。我们所以要在这里具体罗列这些资料,是因为过去的论著中,一般都对此缺少比较明确的概念,不是把新疆地区早期考古文化整个列入所谓以狩猎、游牧为主的细石器文化带内,就是把农业生产的时代估计较晚,概念上也有含混不清处⑥。当然,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过去的考古工作做得还少,缺乏准确、科学的发掘资料。从现有的、虽说不上丰富但却稍稍深入分析了的资料,可以明确看到:早到距今4000年上下,从昆仑山北麓,到天山南、北麓,在相当广阔的一片地域内,在山前、河谷台地一带,已经肯定有了农业生产经济;它们开始的时间,当会较此更早。
而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汉代以后,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农业考古资料那就相当丰富多彩了。举其大者,如民丰县汉代精绝王国遗址内,发现过多量农具、农作物标本;伊犁汉代乌孙墓葬中见过铁铧;在轮台、沙雅、若羌等地发现过汉屯田遗址;晋、唐时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内,出土了丰富的农作物标本、农作形象的绘画;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发现自南北朝到宋、元时期的农作物籽实等等,都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新疆地区古代农业经济的具体认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农业考古资料,将为我们对新疆古代农业史的研究开拓一个新天地,在这里人们将发现许多古文献上无法见到的生动素材。
二
可以直接表现新疆地区古代农业生产情况的,莫过于从各处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农作物籽实、穗壳,出土简牍、文书中关于这类作物的直接记录。现据考古资料,按类别、时代条列于下(已作过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则稍予说明)。
(一)粮食作物
1.小麦
首见于距今近4000年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中。由于这里极度干燥,尸体、殉物也大都不朽。出土时均置于墓主人头侧的草编小篓中,十多颗至一百多颗不等。保存良好,外型完整,麦粒显深褐色,籽粒不大、不太饱满。经初步鉴定,其品种有普通小麦和圆锥小麦两种①。较之新疆博物馆所藏、巴里坤石人子乡炭化小麦粒,后者籽粒稍大,比较饱满。在哈密五堡墓地中,也发现过一枝小麦穗。汉代以后的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小麦和麦类加工食品更多。民丰县尼雅汉代遗址中不仅见到小麦实物,还发现过一根麦穗②。罗布淖尔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的汉文简牍中有种植小麦的明确记录③,同一阶段内的佉卢文简牍中也提到小麦种植及灌溉④。若羌县米兰吐蕃族古戍堡中发掘到过唐代的小麦,在同时出土的吐蕃文木简中也涉及分占耕地、种植小麦的内容⑤。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城郊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两处古墓葬地,出土了自晋迄唐代的小麦及麦面加工成的馕、水饺、馄饨、各种点心及麦麸、麦草,同时出土的文书中也有关于小麦租赋、借贷的文契,数量不少⑥。此外,在焉耆县唐代古城“唐王城”内,也发现过小麦及磨得很细的面粉⑦。
小麦是世界最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也是我国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上述并不完全的资料说明,唐代以前,新疆地区已经普遍种植小麦。过去,一般认为它在新疆只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⑧,现在孔雀河出土的小麦标本,把小麦在新疆地区的栽培历史提早到4000年前,而且对新疆小麦的起源也提出了新的见解①,在农学史研究上的意义是很大的。
2,粟
粟即小米,这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物品种,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地区。我国至今还是主要的粟类生产国。由于粟具有高度的抗旱能力,生长季节较短,耐储藏,因此,它也是新疆地区古代栽种比较多的一种粮食作物。最早的粟类标本,见于距今3000年左右的哈密五堡古墓地。主要是一种小米饼,出土颇多。大部分作方形,长约20厘米,厚3~4厘米左右,由于粉碎不好,饼内的卵圆形小米颗粒仍清晰可见。民丰县尼雅遗址,即汉代精绝王国的废墟内,曾在数处房址中见到小米,有的房屋遗址内铺得厚厚一层,因年久而结成了硬块②。楼兰地区,也曾见到粟类遗物③。吐鲁番晋唐时期古墓内,更见到多量瓶装、小五谷袋装小米以及“付麦、粟账”文书残纸,陶碗内盛着的小米饭等。可以看到,小米与小麦一样,是这里人们的主要粮食。焉耆县内:“萨尔墩旧城遗址中有许多圆形坑穴,直径大小不一,小者约1米左右。坑穴内均是粮食……很清楚地可以看到黄米……”④唐王城内也发现过小米。
3.黍
即俗称的糜子,它和粟类似,籽实呈球形,也是生长季短,性耐干旱的一种农作物。民丰尼雅遗址、吐鲁番晋唐时期古墓中均见过不少糜类籽实。在汉晋时期的楼兰古城内,“在古城建筑物上,涂抹着许多草拌泥的墙皮,其中掺杂有大量麦秸、糜秆的碎节和粒壳。同时,在城内距塔东侧约32米处一堆散乱木材下,发现了深达70厘米的糜子堆积层,一粒一粒的糜子至今还是黄灿灿的”,⑤颇可以说明这也是新疆古代大量种植的粮食作物之一。
4.高粱
见于焉耆县萨尔墩旧城遗址之窖穴内,此城的时代可能早到汉;同县唐王城中亦见⑥。高粱在我国也有久远的栽培历史,我国是高粱的原产地之一。这种作物不仅耐旱,而且能适应盐渍较重的土壤。焉耆,就是盐渍较重的一个地区,正是在这里发现了高粱的籽实,可以证明古代新疆各族劳动人民对高粱的特性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5,青稞
哈密五堡墓地内发现过青稞穗壳,这是新疆所见的最早实物,稍后,在民丰尼雅遗址中也见到青稞籽实(原报告中把它括注为“燕麦”)①。吐鲁番晋唐古墓中出土过不少青稞籽实,值得一提的还有在这里出土的一份唐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马料账,逐日登记了马料消耗情况,所用饲料均称“麦”或“青麦”②。“青麦”一词,从冬日马料账上仍然使用分析,可能就是“青稞”的俗称。因为,这时怎么也不可能有未成熟的青麦的;而且,量词都是斛、斗、升、合,这一分析如大致不错,从这份马料账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青稞栽种面积必甚广。此外,在若羌县米兰古堡中也发现过青稞籽实,亦可见其种植地域之广大。
(二)豆类作物
据考古发掘中出土实物统计,新疆古代种植的豆类作物有蚕豆、黑豆,均见于吐鲁番(其他地方未见,当系发掘工作的局限),时代为高昌至唐。蚕豆籽粒椭圆偏平,不大。所谓“黑豆”,细审实物,籽粒不大,呈椭圆形或长椭圆形,当为赤豆之一种,只是外表黑色,故也俗称“黑豆”。这种黑豆,西北地区栽培颇多,因为它耐旱,生长期短,成熟期要求干燥,对于新疆地区的气候条件来讲,是颇为适宜的。
(三)油料作物
胡麻
胡麻至今仍是新疆地区普遍栽培的油料作物之一。在天山阿拉沟古墓地内曾发现胡麻籽,籽粒卵圆形而稍扁,暗褐色,表面光泽。出土后曾请新疆农科院进行鉴定。此外,在吐鲁番晋唐古墓地,焉耆唐王城内也都见过胡麻籽实。
(四)纤维作物
1.棉花
新疆地区种植棉花的历史很早。民丰县出土的东汉墓中已见棉布③,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古墓中,所见棉织物资料更多。在出土的高昌时期的文书中,有借贷棉布的内容,结合文献记录,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地区已经大量植棉并发展起了一定规模的棉纺织业④,在同一时期或稍后的塔里木盆地内,如于田县屋于来克北朝时期遗址中见到了棉织印花布⑤,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晚唐地层内不仅发现了棉花,而且发现了棉籽实物。可见,自南北朝以后,吐鲁番及塔里木盆地各处,已经广泛植棉并发展起了棉纺织业。
对巴楚出土的棉籽,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曾经进行了分析、研究。根据其种粒小、纤维短、色黄等特点,是草棉(即非洲棉)种子①。这种草棉,喜温、喜光、耐旱,在中亚早有种植,也适宜于新疆及甘肃西部地区的气候特点,但纤维短粗、产量低,这又是其弱点。新疆很早即种植这类草棉,表现了这里和中亚地区久远而广泛的联系。
2.大麻
新疆地区出土的麻类织物资料丰富。前引距今约4000年的孔雀河古墓地内,出土的草编织物中,经鉴定,使用了大麻纤维。同时,也使用着罗布麻(亦称野麻)的茎、秆以编织日用器物。可见新疆地区使用麻类纤维是非常早的。后期,则更为普遍。以吐鲁番为例观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的晋、唐时期古墓葬中,没有一墓不见麻类织物。衣服、被褥、鞋袜、谷物袋、麻绳等等,都用着麻。与麻类织物相比较,无论丝,还是棉,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当然,这大量的麻织物中,据资料本身的题款,可以肯定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内地有关省区②,但也同样可以肯定,必有相当部分或大部分是产自本地,墓内有时以麻丝一束随殉,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五)瓜果类
新疆地区瓜果资源非常丰富,是许多瓜果的原产地,素有“瓜果之乡”的美称。有不少珍品、名产,历史上早就传入中原地区,不仅博得了赞誉,而且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是各族人民经济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古文献中,关于西域地区盛产瓜果的记录不少。新疆,尤其是南疆广大地区,各种瓜果的栽培也确有悠久历史,而且具有普遍性。但限于目前考古工作,我们下文所引资料主要来自吐鲁番盆地内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地,这里干燥,墓内人殉的果品实物得以不朽。一斑可以窥豹,从墓中普遍见到的种种果品,多少可以透见古代新疆瓜果生产的概貌。
1.葡萄
这是新疆地区有名的特产。吐鲁番地区又居全疆之冠,这里日照充分、热量丰富,果实含糖量高。除供鲜食外,制干、酿酒,也都是佳品。直到今天,新疆吐鲁番的葡萄及葡萄干仍是驰名中外的上品。这里晋、唐时期古墓葬中,往往以葡萄入殉,可以看到历史上它一直就是人们珍视的果品。其栽植之盛,从墓葬壁画中有葡萄园,出土文书中有“卖”、“租”葡萄园的契纸,有关葡萄酒的记录等,均可透见这一果品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2.甜瓜
甜瓜吐鲁番古墓内,见过甜瓜子、甜瓜皮。较之其他瓜果,发现数量不算多。
3.枣
这是吐鲁番盆地中普遍见到的一种随葬果品,可见当时栽植必多,人民喜食。枣干紫黑色,个体不大。
4.核桃
在吐鲁番古墓中出土也多,最多一墓达数十枚。果核较小。除吐鲁番外,巴楚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亦见①。
5.梨
新疆地区是梨的盛产地,主要品种有白梨、新疆梨、秋子梨、西欧梨、杏叶梨五个品种。而其中的新疆梨,据俞德浚教授研究,认为是“中国梨与西欧梨的自然杂交后裔”。对它的栽培历史,是果树研究人员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的多量梨干中,研究人员曾对唐代墓葬出土的梨干进行了分析鉴定:“果实如梨形,淡黄色,梗细曲,长于果径两倍,无梗洼,萼宿存,开张,基部相连,无萼洼;果心小,石细胞多,果心近萼端,是典型的新疆梨。”②说明新疆梨的双亲——中国梨和西欧梨在新疆地区的栽培历史肯定早在唐代以前。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利用新疆特别干燥的自然条件而得以保存下来的各种作物籽实标本,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当可发掘出许多珍贵的科学结论。
6.李
吐鲁番墓地出土颇多,果实近圆形,黑褐色。从出土较多看,自高昌迄唐,它在这里并不是很稀少的果品。
7.桃
汉晋时期的楼兰城遗址内③,吐鲁番晋唐古墓中均见。汉代尼雅遗址中亦见④,出土物均是桃核。
8.杏尼雅遗址中曾有所见⑤,吐鲁番古墓地内也见到杏核。桃、杏类果品,均来自内地。
此外,据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唐代吐鲁番地区还出土了芝麻、巴旦杏。芝麻原产非洲,巴旦杏原产伊朗。看来,新疆地区引进、栽培的历史也是很久的。
(六)其他作物
在介绍有关新疆考古资料中所涉及的农作物品种时,不应忽视对饲料作物(如苜蓿)的栽培。
新疆地区的经济,畜牧业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对饲料物的栽培、种植,古代曾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吐鲁番地区出土过一件北凉时期的文书①,文内提到所有在学的儿童要从役“芟刈苜蓿”。新中国成立前所见吐鲁番地区出土文书也有关于种植苜蓿的资料②。如高昌故城(原书称哈拉和卓古城)中出土的“伊吾军屯田残籍”,其中有“……苜蓿烽地五亩近屯”字样,诚如黄文弼先生所说:“苜蓿烽为一地名,盖因种苜蓿而得名。”
苜蓿是富有蛋白质的优良饲料,再生能力强,在水肥充足的情况下,年可收获数次,而且管理省工,是经济价值很高的饲料作物。从史籍看,新疆地区很早就有苜蓿的栽培,而且早在汉代,随优良马匹进入内地,苜蓿也被引进到了内地。此外,在吐鲁番晋、唐时期古墓中,还出土了为数极多的葫芦片。葫芦,原产印度,后引入我国,嫩果可作蔬菜,老果可作盛器。又在民丰县汉尼雅遗址中,发现过不少干蔓青。蔓青,即芜菁,干、鲜食用均宜。
这些,都多少反映新疆古代的一点蔬菜情况。可见早在晋、唐以前,新疆既有
苜蓿,也有葫芦和蔓青。
三
在认识、研究新疆地区古代农业生产状况时,各种农业生产工具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应予认真分析。
在整理有关农业生产工具的资料时,我们感到有两个比较显目的特点:一是原始社会阶段或较早期遗址内,木质生产工具占有很大比重,具有重要地位;再是从工具角度,可以十分鲜明地感受到中原地区对这里显著的影响。
在前述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原始社会墓地内,曾出土过一件木质生产工具,长22厘米、宽8厘米,尖端及两侧薄刃锐利,有长期使用的痕迹,如附以木柄,是不错的挖掘沙土的工具。
出土木质工具稍多的是哈密五堡公社内的原始社会墓地。共见两根三角形掘土器、一件木耜③。这是在不见其他任何石质或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出土的,颇可见木质工具当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这种木质掘土器,系选取与人高比例相称、便于直立劳动的硬质木杆,微显弯曲,然后把端部细致加工成三角形,尖部锐利。掘土器曾经过长期使用,不仅尖部光滑锐薄,扶手部分也因长期使用而很光洁。其一通高90厘米。这种木质掘土器,在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中也曾发现过,如云南省独龙族,“铁质工具数量极少,在生产中不占什么地位。在木质工具中,使用最广泛的是‘郭拉’和‘宋姆’。……‘宋姆’即点种棒,把小竹棍或小木棒一端削尖或以火灸尖即成。用于挖穴点种,用毕即弃”①。四川省甘洛县藏族(自称“耳苏”)人也曾使用过这种尖木棍,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成脚犁,在耳苏人古老的传说中“……他们从事过种种原始的生产活动,留下了许多原始工具的名称,如狩猎用的石箭头‘耳买’、骨箭头‘日古买’。农业则用石斧‘吴戳’伐木,用称为‘布’的尖头木棍或尖竹棍发土点种”。“脚犁就是由尖木棍发展而来的,先是在尖木棍上安装‘扶手’……后来由扶手的启发加上一个脚踏横木,手足并用,遂成木耒”②。无论独龙族中的“宋姆”还是耳苏入中的“布”,与五堡所见三角形掘土器都是同一性质的工具,基本形制、功用都同,只是五堡的掘土器已较进步成型,不再随用随弃了。
与这种三角形掘土器共出,在五堡见到木耜(原报道中称其为“方头木锨”),长28.5厘米、宽16.5厘米、厚1厘米,刃部锐薄,偏上部见对称两孔,便于安柄。这种木耜,在民丰县汉代尼雅遗址中也有发现③(原报告中称“木锨”),矩形,长49厘米、肩宽22.5厘米,上部有两孔,便于安柄。同一遗址内,出土铁工具(如斧、铲、镰)不少,但不见犁,而出土了这种木耜,似可以说明这片地区当时木耜仍未退出历史舞台。
这类木质生产工具,在天山阿拉沟古墓区也有所见,有一端磨尖的木器,也有作双叉形,端部经过加工,十分尖锐。
上述汉代尼雅遗址,还曾出土过一柄保存良好的木榔头,通长108厘米,头长46厘米。这种木榔头对于碎土或修堤筑坝等水利工程,都是十分适用的。
汉代以后,由于汉王朝在新疆地区进行屯垦,各种农具及中原地区的农作物,随屯田士卒、应募农民不断进入,给新疆农业生产以重大影响。
汉尼雅遗址中出土的铁镰刀,和“今天陕西关中地区农民使用的镰刀形状相同”④。在伊犁地区的昭苏县,相当于西汉时期的乌孙墓出土一张铁铧,舌形,中部鼓凸,铧体削面近等腰三角形,后部有銎,銎作扁圆形。通体厚重、粗糙。这种形制,与关中礼泉、长安、陇县等地出土的西汉中晚期“舌形大铧”①形制相同。利用这种铁铧发土,效率当然会大大提高一步。
汉代开始在新疆地区屯田,牛耕技术肯定会相应进入新疆地区。在罗布淖尔楼兰地区出土的晋简中,有一支简文是:“因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谐营下受试。”②这里是晋西域长史的驻节地,仔细推敲简文文意,可以看到西域长史府至少在屯田部队中曾经有组织地大力推广一种新的驭牛犁耕技术。“大侯”是西域长史的下属,责其“究”(“究”有“穷尽”意)犁与牛到“营下”受试考核,颇见认真。
关于这一阶段犁耕的具体,特点,可由同一时期内龟兹(今库车地区)的一幅牛耕图壁画帮助说明。在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第一百七十五窟(时代约当两晋)中,“在坐佛的周围,画出类似‘二牛抬杠’的牛耕图,有宽刃的镢和锄等工具。从牛耕图中宽大铁铧来看,与发现的汉代铁铧比较接近”③。细审有关画面:一人右手持物,驱赶二牛前行,此二牛合驾一辕,其后为一呈三角形尖刃的宽大犁铧,双牛负驾吃力。这一“二牛抬杠”式耕作画图,与同一阶段内嘉峪关壁画墓中所见牛耕图近似。只是因受穹形洞窟的局限,画面无法展开,对犁的形制没有具体刻画。同一洞窟内,还有一幅表现了砍地、翻土动作的画面:裸身、赤足、戴帽、着短裤的二龟兹人,两腿以丁字步式站立,上身前倾,作奋力劳作状。他们所持镢、锄,略近方形、宽刃。这种形式的砍锄与今天新疆境内普遍使用的“坎土曼”形式酷似。“坎土曼”,新疆广大农村翻土、提土、修渠、筑堤等等工作,均得力于斯,差不多是小件农具中的万能工具,维吾尔族农民使用得心应手,十分灵便。
有关这一阶段农作工具情况的,还有1964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中出土的一幅纸画④,画幅长106.5厘米、宽47厘米。绘画内容表现了统治阶级人物的生活。其中有三分之一画面,表现了墓主人的田园及庖厨。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所以这实际是墓主人财富及享乐生活的写照。在田园生活画面中,可以看到整齐的田亩,茂盛的禾稼,旁侧是草杈、耙等农具,木耙长柄多齿。另有一件农具颇费解,从形象分析,这应当是犁。只要转一角度,正是一架犁的侧视图,有犁辕、犁梢、犁架及系绳等。在庖厨画面内,还有磨、碓的形象,磨以长木杆作联动轴,由人推转;碓是用足踩动。这些谷物加工工具,与内地农村流行形式完全一样,明显可以看到,这是由于接受后者的影响。这一情况,当与吐鲁番地区汉晋时期居民相当一部分来自甘肃等地有关,他们从内地迁居吐鲁番时,同时带来内地一套耕作、谷物加工技术,是毫不足怪的。这对新疆古代农业的发展,曾起过良好作用,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四
新疆是一个干旱地区,除少部分地区或山区外,全年降水量很小,在塔里木盆地及吐鲁番盆地内,基本上全年无雨,这样的降水量是无法“靠天吃饭”的。因此,新疆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其首要前提之一,就是必须解决一个农田水利灌溉问题。公元6世纪初,当宋云、惠生过新疆地区时,看到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地区)“民决水而种”。他们听说中原地区的农田是“待雨而种”时,觉得十分好笑、不可理解:因为“天何由可共期也?”(见《洛阳伽蓝记》)。塔什库尔干地区雨水还是较多的,塔里木盆地内这一差别就见得更大了。这一生动的记录,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新疆地区水利灌溉是农业生产的前提。
汉代以前的水利灌溉遗迹,目前还未发现。那时的农业,规模不大,农田也都选择在引水比较方便的河道下游,这些地方地势比较平缓,引水比较方便。目前发现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哈密五堡古墓地,都有这样的特点。而汉代以后,中央王朝在这片地区推行屯田,水利事业也相应得到进一步发展。
西汉王朝在新疆的屯田,是按桑弘羊的筹划实施的。桑弘羊给汉武帝刘彻的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在轮台地区“通利沟渠”,用部队进行屯田;再是有一定基础后徙民实边,“益垦溉田”①。也就是说,一是强调了在屯垦地区首先要注意做好灌溉事业,这样,农业生产才有可能进行;而针对新疆地区地广人稀的特点,募民实边,发展农业生产也就有了保证。
汉代以来,在新疆地区兴修水利的情况,既见诸文字记录,也有不少遗迹可寻。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篇》中留有一条西域各族人民兴修水利的故事:曾有“敦煌索勘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①、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人,横断注滨河,灌浸沃衍,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凌冒堤……大战三日,水乃迥减。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租粟百万,威服外国”这段记录,除去神话外衣,其实质内容颇可信从。迁酒泉、敦煌人到新疆屯田,是合理的,历史上曾再三实行过。横断注滨河、拦蓄河水,使不入盐湖,则下游沃野可尽得开发。因此,这段记录颇真实地表现了公元6世纪以前西域地区修水利、开屯田的史迹。表现了历史上人们对兴修水利的必要性及有关筑堤坝、蓄洪水的工程知识。反映了要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才能完成较大的工程,而得农业发展之功效。下文介绍的几项较大水利灌溉遗迹,没有这样的组织力量,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沙雅县汉人渠
在库车地区沙雅县、新和县境内,黄文弼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进行考古调查中,曾发现多处遗址及屯田遗迹。其中有“长达二百华里之古渠……在渠旁及遗址中,曾觅出汉代五铢钱及陶片”,“古渠位于(英业)古城之东北”,“维吾尔语称为黑太也拉克,即汉人渠”。“此渠位于喀拉黑炭巴扎之西,地名曲鲁巴哈。由干河分支东行,经英业入戈壁,一直往东,至爱默提草湖遂不见,全长约200余里。附近古城有阿克沁、满玛克沁、黑太也沁、于什格提,皆附于渠旁”。“渠为红土所筑,宽约6米。至于什格提东面,分为三渠至草湖”。对这一长100公里、宽6米的古渠及沿渠的古城废墟,1981年,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伊第列斯等人,曾经再履其地,渠道痕迹仍宛然在目。渠道所经,因沙淤土积,均高于地表,宛若一道逶迤远去的土堤。这次调查中,在傍近古渠的一处古城址“羊达克沁”,群众曾采集到唐代钱币。这些迹象表明:这片地区,自汉迄唐,一直是一片规模宏大的屯田中心,但目前却已是盐化相当严重的荒漠了。
(二)若羌县米兰古堡附近,农垦勘测设计人员曾发现一处古代灌溉渠系统
渠系与古米兰河通联,“干渠全长8.5公里,渠身宽10~20米(包括渠坝),渠高3~10米(自地面算起)……大型支渠7条,总长28.4公里”。“小的毛渠阡陌纵横,密布于各支渠间的灌溉面积上”。灌溉面积实测达1700亩①。这一灌溉遗址,考古工作者李征同志1973年也曾进行过调查。渠道所在,所以会远远高于地表,主要原因是渠内大量淤沙(米兰河含沙量很大,常水期每升含沙3.8~6.6克,洪水期达27.9~52克)。淤沙使渠床不断升高,清淤沙土不断垒积渠道两旁,逐渐形成这种景观。据水利工作者饶瑞符测量分析,这一灌溉系统的“干、支、斗渠,全部沿最大坡度,垂直地形高线布置。7条支渠均匀地顺地形脊岭,采用双向灌溉,有效控制着整个灌区,全灌区没有不能上水的土地”。“整个灌溉系统的布置较为合理,而灌渠渠线的正直、整齐,采用双向灌溉和集中分水的方式,水头控制良好,因地制宜与渠道网的完整性,为其他旧灌区所少见。在无地形测量资料的古代,全凭目测与生产斗争经验的条件下,足以说明汉代在此兴建水利灌溉系统有较高的水平”②。这一渠系的修建年代,目前未得文物直接证明。但据《汉书》,汉立尉屠耆为鄯善王,“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③,冯承钧认为“伊循是今之弥朗”④。若然,这一古代灌溉渠系,应该就是汉代伊循屯田的遗迹。
(三)轮台地区汉代屯田遗址
据黄文弼先生调查,在轮台县克子尔河流域,有古堡及城市遗址多处,如柹木沁、黑太也沁、柯尤克沁、着果特沁等。从调查所得遗物看,除黑太也沁可能为唐城以外,余均汉代遗址。遗址周围,有“干渠;埂界犹存,疑为古时垦殖区域”。“柯尤克沁……可能为汉仑头国故址,城西有古时流水沟渠,盖引克子尔河水灌城中者”。“着果特沁旧城……城中有红底黑花陶片,与柯尤克沁旧城所拾相同,皆为纪元前后之遗物。又拾铁矢镞一,中实有柄,系汉物……疑此城为汉代屯田轮台时所筑。因城有营垒,当为田卒所住,城中有粮食,城南及东皆为红泥滩,古
时沟渠田界痕迹尚显然可见”⑤。这片地区是汉代屯田中心,曾经繁荣一时,但目前已成一片盐渍碱荒漠,渠沙淖泥遍地,盐衣白末到处可见。
其他,为于阗县克里雅故道下游的喀拉墩遗址。据笔者调查,遗址区内渠道纵横,田畦清晰,也是晋南北朝时期凭借人工灌溉事业而发展成功的一片绿洲。
(四)在罗布淖尔地区所出汉晋简牍中,不少筑坝、修水利、管水浇地资料,颇可见当日屯田地区对水利的经营
……本空决六所并乘堤已至大决中……五百一人作……增兵”“将张佥部见兵二十一人大麦二顷已截二十亩下〓九十亩溉七十亩,小麦三四亩已口二十九亩禾一顷八十五亩溉二十亩锄五十亩(简面)将梁襄部见兵二十六人大麦六十六亩已截五十亩下〓八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六十三亩溉五十亩禾一顷七十亩锄五十亩溉五十亩(简背)
“水曹请绳十丈”等①,类似简文还有。从这些断简残牍中可以看到,当时在楼兰地区的屯田,水利是关键,有“水曹”司其事,堤坝有人管理,土地分划成地块,分别由各部负责种植及管理,锄、灌、截之进度均须定期检查、呈报。组织是非常严密的。
(五)关于新疆古代水利灌溉事业的经营建设,吐鲁番出土文书、碑刻资料,也提供了十分具体的记录
吐鲁番盆地内,几乎终年无雨,而气温高,蒸发强。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农业生产,比较完备的水利灌溉工程,是一个前提。自汉代始,这里就是汉王朝、匈奴屯田的所在,对水利灌溉必已有一套办法。有人认为,新疆在汉代已知坎儿井②,但在吐鲁番地区考古调查中,却未见任何可以说明这一问题的资料。相反,从吐鲁番唐代墓葬中出土的文书资料看,显示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水利灌溉系统。有一件唐高昌县“为申修堤堰料工状”③,文书残纸上,钤有“高昌县印”。
从这件文书可以看到,每年用水期过后,高昌县必须组织众多人力(从这件文书看,动用人工达1450人),对“新兴谷”内的“堤堰”及县城南的“草泽堤堰”和“箭干渠”进行维修。据此,可以明确肯定:在山区当有水库类性质的设施,盆地内低凹处也有塘坝及干渠,它们构成一个灌溉系统。
吐鲁番盆地的地理特点,决定了盆地内的灌溉用水主要得之于天山雪水。这种雪水年均流量稳定、变化小,农业用水保证率较高,对农业是有利的;但这种雪水,夏日天热时水量集中。因此,在夏日雪水大量下来前,每年都必须对水库、塘坝等蓄水处的堤堰及渠堤进行检查维修加固,保证安全。而这种水库、塘坝对调节用水是十分必要的,看来,这件申修堤堰的状文,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年年如是,故可“准往例”处分。这种关系整个社会命脉的水利系统,工程的兴修、维护、管理,必须有组织、有专人负责,县内是“知水官”主持其事。从这一文书出发,可以大概透见高昌县的水利灌溉组织情况。
在吐鲁番这样的地区,有水才有生命,才有农业。水是十分珍贵的。又一件出土文书就十分形象地表明了这一情况。录文如下:
城南营小水田家 状上
老人董思举
右件人等所营小水田皆用当城四面豪(濠)坑内水,中间亦有口分亦有私种者,非是三家五家。每欲灌溉之晨,漏并无准。
只如家有三人两 人者,重浇三回。
孕独之流,不蒙升合。富者因滋转瞻,贫者转复更穷。总缘无检校人,致使有强欺弱。前件老人性直清平,谙识水利,望差检校,庶得无漏。立一牌牓,水次到转牌看名用水,庶得无漏。
如有不依次第取水用者,请罚车牛一道远使,如无有牛家,罚单功一月日驱使。
即无漏并长安稳。请处分牒件如前谨牒
在浇地的关键时刻,凭靠城濠内水利浇地的各家营小水田者,彼此为水而纠纷,要求官府调理,委定专人管水,保证合理使用。这一状文,十分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吐鲁番盆地内水的珍贵。一个合理的灌溉系统对吐鲁番正常农业生产的绝对必要,从这里可以得到更深的体会。
在结束这节文字前,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历史上那些屯田中心如轮台等地,为什么今天却都成了一片荒漠式盐田碱滩?2000年前的良田沃野成了今天的不毛之地,这一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以轮台地区为例。广泛发育的天山前山地区主要是中生代、新生代的含盐岩系,可溶性盐分极多,高山雪水至此,自然形成为浓度较大的矿化水。流经山前地区后,矿化度当会更高。在河流下游垦殖的荒地,亦即古代的屯田中心,用这种水灌溉,而又没有一套排盐碱措施,就会使盐分不断停积于农田地带,这种积盐过程是十分缓慢的,但经过相当一个历史阶段,就会达到一定浓度,最后使农田荒芜、作物不生。在古代人们对水质缺乏认识的情况下,盆地内排水又不畅,终至无法逃脱土地盐碱化的惩罚。在其他古代屯田地带,也往往经历过相类的过程。这个问题,在今天新疆地区的农田生产、水利灌溉中,仍是人们必须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五
汉代以来,在新疆地区广泛进行屯田,历唐迄清,这一事业始终不衰,对新疆地区的农业发展,曾发挥过重大作用,无论是士兵还是“累重敢徙”的应募者,主要成分无疑都是中原地区的农民,他们在新疆屯田,自然就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农具、籽种、耕作方法等等,这在上文已经论及。
屯田生产,对新疆地区的开发建设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新疆地广人稀,要靠这里有限的人力、物力维持相当数量的边防部队、各种管理机构,保证“丝绸之路”的需要等,肯定会十分困难,利用部队并募民屯田自养、再上缴国家一定粮食,就可缓和并解决这一矛盾。在论及新疆古代农业生产问题时,屯田是一项必须重点研究的课题。
关于这一问题,上文已有相当涉及。这里将直接打开古代屯田的几件文物收录于后,以利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民丰县汉代尼雅遗址,曾出土“司禾府印”一方,边长2厘米,高1.7厘米①。从印文“司禾府”可以推见,是汉晋时期与屯田事务有关的一个机构。
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许多文书直接表明了当时屯田的情况。
1972年出土的“伊吾军纳粮牒”(长27.5厘米,宽8.5厘米)②,其上钤“伊吾军之印”,表明为正式公文,残留文字有:
敕伊吾军 牒上西庭支度使
合军州应纳北庭粮米肆仟硕 叁仟捌佰伍拾叁硕捌
头叁胜伍合军州前后
纳得
肆拾叁硕壹斗陆胜伍
合前后欠不纳
壹佰玖拾柒硕纳伊州仓讫 叁仟陆佰肆拾陆硕捌
头叁胜伍合纳军仓讫。
从这一文书可以看到伊吾军屯田的规模,每年应纳的粮额。而且,不仅缴纳军仓,以供军需(这是主要部分),还要纳一部分到“州仓”,以供地方行政需要。唐代边防军的屯田,组织、管理是十分严密的。合戍守与生产为一体,虽小到只有两三人的烽燧,其生产任务也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反映这一情况的残文书出土颇多,试举出土的两件残文书为例。其一为“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①,从文书残存文字可以看到,在西州都督府管领下,合诸镇、戍军卒营田总数约十余顷。提到的镇、戍名称有“赤亭镇”、“柳谷镇”、“白水镇”、“银山戍”、“方亭戍”、“维磨戍”等,同墓又一件残文书,内容有:
……田水纵有者去烽卅廿
每烽烽子只有三人两人又属警固近烽不敢不营里数既遥营种不济状上者曹判近烽者即勒营种去地远者不可施功当牒上支度使讫至开十闰五月二十四日被支度营田使留后司五月十八……
分析文意,可以看到部队屯田系归“支度营田使”负责管理。每座烽燧,烽子即使只有两人三人,也有明确的生产任务。如遇特殊情况,屯种任务不能完成,必须逐级申报,“近烽者即勒营种;地远者不可施功,当牒上支度使”。由于文书残缺,不可尽读,但小至两三人的烽燧也有明确的生产任务,确是明白无误的。
这几件文书,虽只涉及伊吾军及西州都督府,即只关系到哈密及吐鲁番地区,但却具有一般性意义。其他地区的屯田情况,与此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在这样严格的管理制度下,生产得到了保证,军资有了着落,人民多少减轻了负担,有利于边防,也有利于新疆地区的社会生产事业,其积极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附注
①③1979年冬,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孔雀河下游发掘了一批原始社会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小麦。墓地年代,据北大考古教研室碳14实验室用木材、毛布、皮张等测定,当在距今4000~3700年上下。
②《新疆疏附县阿克塔拉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载《考古》,1977(2)。
①《新疆东疆和南疆地区考古新发现》,载《新疆考古》,1979(1)。
②墓地年代测定结论已在《文物》1978年5月刊布。
③辛塔拉遗址,新疆考古研究所曾进行过调查、试掘。资料刊布于《新疆文物》,1986(1)。
④《新疆东部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64(7)。
⑤《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7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⑥《新疆农业》(第二章),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①鉴定工作是由四川农学院农学系教授颜济先生进行的。
②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载《文物》,1960(6);新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载《考古》,1961(3)。
③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1914。
④转引自汪宁生:《汉晋西域国文明》,载《考古学报》,1977(1);《若羌且末新发现的文物》,载《文物》,1960(8~9)。
⑤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曾在米兰古堡内进行过调查、发掘,这里据这次发掘资料。
⑥有关发掘材料,先后发表于《文物》1960年6月、1972年1月、1973年10月、1975年7月、1978年6月及《考古》1959年12月等期。从中可以窥见各种农作物的出土情况。下文所见吐鲁番资料,均同此,不一一注明。
⑦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载《考古》,1959(2)。
⑧《新疆农业》,10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图93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花式点心,尽显高昌地区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①一般认为,新疆小麦得之于西亚。据颜济教授分析孔雀河小麦品种,结合对新疆现存野生小麦的调查,认为新疆完全有可能是小麦原产地之一。
②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载《文物》,1960(6);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载《考古》,1961(3)。
③转引自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载《考古学报》,1977(1);《若羌且末新发现的文物》,载《文物》,1960(8~9)。46黄文弼:《1957~1958年新疆考古调查附记》,见《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⑤侯灿:《楼兰遗迹考察简报》,载《历史地理》,1981。
①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载《文物》,1960(6)。②《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55年)曾发表了这一马料账的部分细目,见该书图版第98、99“轮台县长行坊马料账”、“草料账之一、之二”。
③《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60(6)。
④《梁书·西北诸戎·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织市用焉。”(《历代各族传记全编》第二编下,1705页)。
⑤《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版二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897。
①沙比提:《从考古发掘材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载《文物》,1973(10)
②王炳华:《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载《文物》,1981(1)
①巴楚核桃,资料现存新疆博物馆。
②新疆农科院农科所、陕西省果树研究所:《新疆的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
③侯灿:《楼兰遗迹考察简报》,载《历史地理》,1981。
④⑤见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
① 文物现存吐鲁番文管所,有关简报最近将发表。这里据李征同志的笔记资料。
②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图版三三,“伊吾军屯田残籍”。
③ 其简单报道见218页①,文物现存新疆考古所,原消息报道中称三角形掘土器为尖状木“犁”,不准确。
①卢勋、李根幡:《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载《农业考古》1981(1)。
②严汝娴:《藏族的脚犁及其铸造》,载《农业考古》,1981(1)
③史树青:《谈新疆民丰尼雅遗址》,载《文物》,1962(7、8)25页第14图。
④李遇春:《从出土文物看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载《团结》,1959(11)。
①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载《文物》,1966(1)。
②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
③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载《文物》,1962(7~8)。
④见《新疆出土文物》,图版第45,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①《汉书·西域传·渠犁》载桑弘羊奏章为:“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方,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可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间。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桑弘羊这一建议,汉武帝刘彻当时没有采纳,但30年后,西汉王朝却是在新疆地区全面实施了这一建议的。
①“鄯善”二字疑误。两汉前期有楼兰无鄯善,后有鄯善而楼兰又在其中故两者不应并立。这里的“鄯善疑为“车师”之误,楼兰与车师邻境,动员车师人支援楼兰的大型水利工程,是说得通的。
①②饶瑞符:《米兰汉唐屯田水利工程查勘——从米兰的灌溉系统遗址看汉唐时代的屯田建设》,载《新疆巴州科技》,1981(1)。
③《汉书·西域传(上)·鄯善国》。
④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北京:中华书局,1957。
⑤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二章,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①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
②王国维:《西域井渠考》,见《观堂集林》。
③《新疆出土文物》图版96,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①《新疆出土文物》图版24,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②《新疆出土文物》图版10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①《新疆出土文物》图版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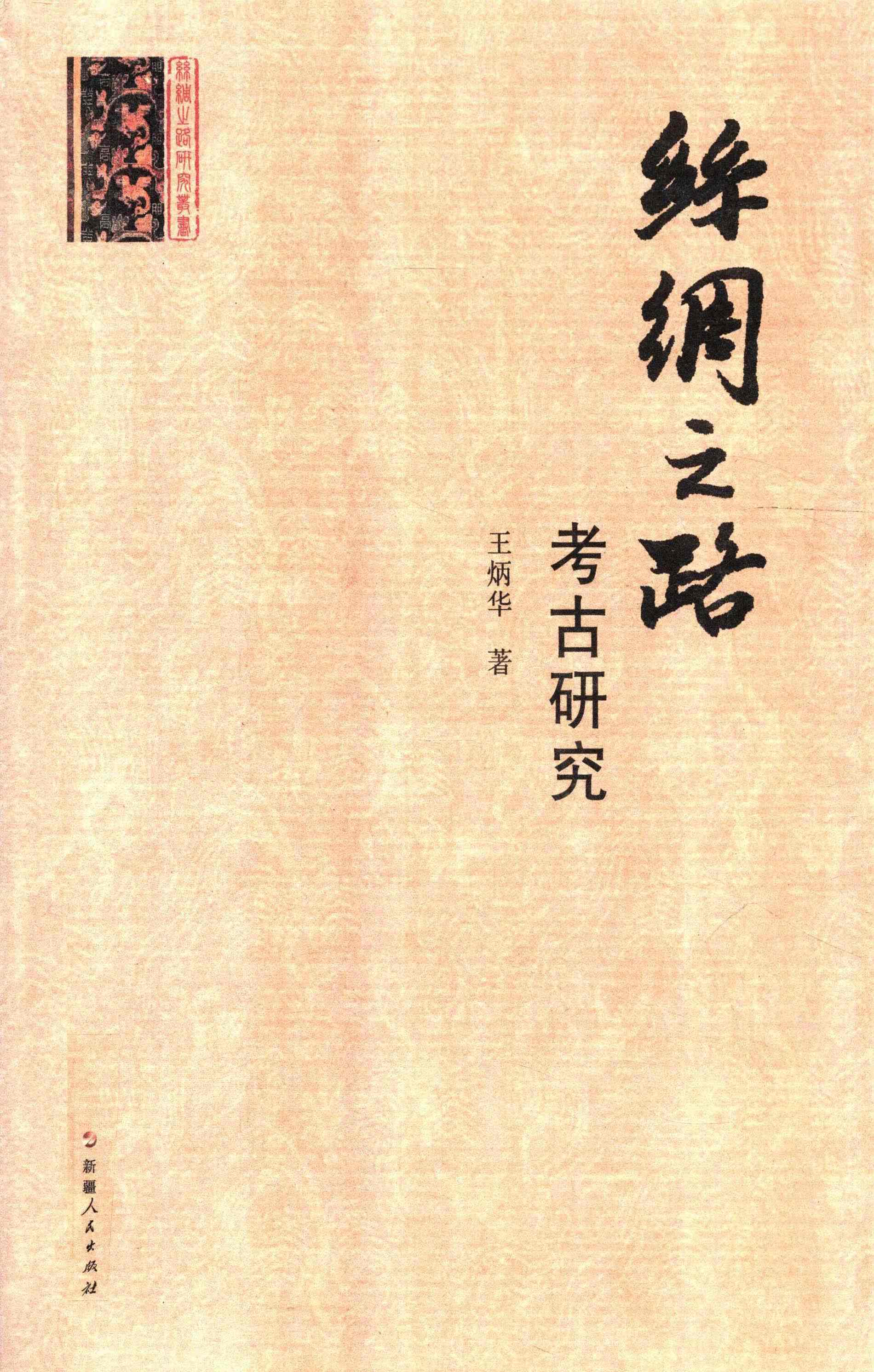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