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伊犁后乌孙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89 |
| 颗粒名称: | 西迁伊犁后乌孙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
| 分类号: | D663 |
| 页数: | 17 |
| 页码: | 167-18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西迁伊犁地区后,国力得到长足进步,曾对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有过重要的建树。 |
| 关键词: | 伊犁后乌孙 社会经济 政治 |
内容
在战国秦汉时期,从河西走廊以至新疆这片广大地区的历史舞台上,乌孙是一个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古代民族。它西迁伊犁地区后,国力得到长足进步,曾对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有过重要的建树。
关于乌孙的历史资料,比较集中地见诸于《史记》、《汉书》等早期史籍,但均非常简略。对乌孙西迁新疆西部地区后的政治、经济状况,与西汉王朝的关系等,也都是语焉不详,都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20世纪60年代初期,新疆考古研究所曾组织力量对天山以北的北疆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并进而在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地区等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发掘。结果,在伊犁河流域发现了乌孙古代文化遗存。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进行了两次工作①,这就为我们研究乌孙历史提供了一批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大大丰富、扩展了历史文献对乌孙的有限记录,加深了我们对乌孙历史,尤其是西迁伊犁地区后乌孙王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状况的认识和了解。
一
乌孙,在汉代的西域地区是一个最大的地方小王国政权。《汉书·西域传》记述:它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不论是人口还是兵力,与汉西域地区其他地方政权相比较,都居于前列。
乌孙,西徙伊犁地区后的活动地域,文献中没有准确、具体的记录。根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在新疆北部地区的考古调查及部分地区的重点发掘资料,我国境内现存的乌孙考古遗存,主要分布在天山到伊犁河之间广阔的草原地带,如昭苏、特克斯、新源、巩留、尼勒克等县,其中昭苏县木扎特草原、萨勒卧堡乡,新源县巩乃斯种羊场和县城附近,特克斯县三乡等地都有规模巨大的乌孙墓葬群,尤其是木扎特草原,正位于唐称为凌山的天山北麓,巨冢成行成列,漫布在山口外草原上,底周一般均在二三百米左右,高达七八米,犹如一座小山,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景色壮观,这些无疑都是乌孙上层贵族的墓冢。
在乌孙墓葬比较集中分布的上述地区内,山多松林,水丰草茂,气温比较低,地理气候特点与《汉书·西域传》中所描写的乌孙地区“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完全一致。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昭苏县与察布查尔县交界的一段天山支脉,至今当地群众尚呼之为“乌孙山”;同时在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活动地域的我国哈萨克族中,新中国成立前就仍然有名为“玉孙”(即乌孙)的部落,表现了乌孙西徙伊犁地区后,在各方面留下的深重历史印痕。
凭借众多的人力资源,加上伊犁河谷十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乌孙在西迁伊犁地区以后,社会经济得到了逐步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公元前1世纪以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乌孙经济是以畜牧业为主体的一种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虽也存在,但并不居于重要地位。
伊犁地区,尤其是伊犁河南至天山山麓这一片草原,天山中间的高山草场是非常优良的牧业基地。在这片地区内,气候湿润、草场辽阔,牧草以禾本科、豆科为主,适饲性强,利用率高,载畜量大。而且雨水较多,山区松林漫布。以昭苏县为例,据县气象站统计资料,年降雨量一般达500毫米,全年日照时间2400多小时,年平均气温较低,只有2.5℃。无霜期只有100天左右。海拔1000~2000米。这种气候地理特点,对农业生产不利,但对畜牧业却非常适宜,真可谓水足草茂。这种地理环境与《汉书·西域传》记录的“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颇相一致。我们在昭苏草原调查中,茂草的高度及于马腹。大家都知道,马对饲草的要求是高草、禾本科、豆科草类,而这正是伊犁河谷、天山山前地带可以满足的条件,它对于马的饲养特别有利。苜蓿也是这片地区广泛种植的优良饲料。而在这大片地区内,山前与山中、山内阳坡与阴坡,随地势变化,气候、牧草也都有相应改变,可适应畜群不同季节的需要。如山中背风面阳的较低处所,冬日基本无雪;即有小雪,并不能全部覆盖牧草。冬日气温较高,牧草可供畜群需要,这些是俗称的“冬窝子”,即冬草场。夏日,牲畜可转至地势较高,气候凉爽,有水有草的高山草场,畜群可以得到充分的营养,避开了山前地势低平处较高的气温,这里是俗称的“夏窝子”,即夏牧场。至于春秋草场,基本在同一地点,大都是山前地带。在畜群转场后,一般都有几个月的间隔,牧草可以得到恢复、生长,下一季节畜群转回时,可以满足需要。这样,在一个小地区内,不论春、夏、秋、冬,可供牲畜饲用、彼此相去也不算太远的四季草场俱备,就为人工放牧,靠天然草场饲畜提供了合适的条件。它和《盐铁论》中对匈奴游牧特点的描述“因水草为仓廪”、“随美草甘水而驱牧”颇为一致。在水草条件合适、有自然游牧的条件时,古代的游牧民族多采取这一经营方式。迄目前为止,在新疆北部广大牧区畜牧业经营与内地多数省区不同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此。它与农业结合很不紧密,依靠天然草场养畜,人工放牧,随季节转换草场。看来这是适应自然地理条件、长期形成的放牧习惯。《汉书》称乌孙的社会经济特点是“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就是这种经营特点的简练概括。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种相对流动的游牧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对的定居。我们认为,在乌孙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居住点,文献中提到乌孙首都赤谷城,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存在定居的直接证明。在考古调查中,我们发现,乌孙土墩墓大量集中的地点往往是出天山山口的河流附近的山前草原,或其他一些水草俱佳的小谷地。这些地点多为春秋牧场所在,也就是地势开阔、气候较温和、牧民活动时间最长的地点。在这些地区内,墓群成行成列,巨型土冢远远可见,蔚为壮观。这些地点应该也是乌孙人生活居住的中心。虽然我们目前还未直接发现当时的居住遗迹,但从墓地特点可以推论:居地与墓地相去不会太远;巨型土冢的营建非一日一时之功,必须动员相当人力、物力,远距住地将无法进行。
当时的住室(除毡幕外)是什么样式?这从考古资料与民族调查中颇有线索可寻。在昭苏等县区,农村中目前仍沿用一种小屋,是以圆木为墙、盖顶。圆木纵横交接处互相凿孔榫卯,屋顶、木墙外均覆土抹泥。室内铺地板,木壁或挂毡毯。障风、避雨雪、保暖,作用均佳。这是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因地制宜而出现的建筑形式。非常有趣的是,这种木屋结构与乌孙古墓内见到的木椁造型,几乎一样。椁室四壁均以圆木叠砌成墙,接头处互相榫卯,保持牢固和水平。椁室内壁曾经挂毡毯,朽灰仍见。毡毯外并钉附“米”字型细木条。椁木顶部盖覆松木二三层。坟墓是生者为死者安排的地下居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图景。而这一墓室形制正是现存木构小屋的形象。我们把它看成是古代乌孙人住室的再现,可以说是言之成理的。
乌孙的牲畜种类,据有关文献,主要有马、牛、羊、骆驼、驴等①,而以养羊、马为主。考古发掘中,曾发现有马、羊、狗的骨架或部分骨骼,而以马、羊骨居多。《汉书·西域传》说其“国多马,富人或至四五千匹”。媒聘细君公主,即“以马千匹”为礼,颇可见养马数量之多。马的质量,在汉代也负有盛名,张骞以后从乌孙选去内地的马匹,因品种优良,被誉称“天马”。在大宛马进入中原后,才更“天马”之名为“西极马”。伊犁河流域,实际上就是当年乌孙的中心地域,至今仍然是全国知名的“伊犁马”生产基地,马体不大,形体俊美,善走,速度亦佳。看来,这是有悠久传统的。
墓葬中殉葬的马、羊、狗等的骨架,形象地反映了牧业生活特点。马,日常骑乘,代步,不论用于生产或作战,都不可稍离,它们是牧民生产和生活中主要的伴侣。羊是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生活资料。细君公主在《黄鹄歌》中咏唱的“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这里的“肉食”,马、牛、羊肉都有,但羊是居于主要地位的。墓葬内出土的羊骨,往往都和一把小铁匕首共见,小铁匕首甚至穿插在羊骨中,形象地表现了当时生者为死者去到另一个世界时安排的肉食资料,而这自然也是生者日常生活的现实写照。操小刀以剔肉,到现在为此,还是牧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乌孙墓葬内,或在封土中,曾见到完整的狗骨架。在牧业生产中,牧羊犬是牧人十分重要的助手,他们能帮助看守羊群,防止狼害。每个牧民家庭,无不有犬,墓室内葬狗,封土中殉狗(应该是祭礼的体现),也自然就是为死者作出的切合牧业生产需要的周到安排。
西汉后期,当雌栗靡为乌孙大昆弥时,颇具权威,贵族翕侯皆畏服之。史籍记载其重要政绩,取得成功的经验是在国内颁布了一条法令:“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①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条记录。“无使入牧”的含义,前人颜师古、徐松曾有注释。颜注为“勿入昆弥牧中,恐其相扰也”。徐松则认为是“入牧、疑当谓人所牧为税”②。我们认为,徐松所注并未得其要领,颜注接近于实际。这里的“无使入牧”四字,应该不仅是包括昆弥,也包括乌孙统治集团各级“贵人”之间。全面地说,应作“无使入昆弥及他人牧地”,这实际上是一项调节生产关系的重大措施。如前所述,畜牧业是乌孙社会经济的主体,而牧放畜群又是依靠四季天然草场。因此,草场就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对它的占有、使用,实际就是对社会最主要财富的占有、使用。一定数量的草场,其载畜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掌握了大量畜群的乌孙昆弥及各级翕侯,亦即是乌孙社会的贵族统治集团,他们对草场的占有要求,尤其是对水质好、水源足、草质优良的草场的占有要求,就是一种经常存在的需要。而这类优良草场总是有限的。这种多量的需求与有限的可能就会形成经常的矛盾,会不可避免地危及乌孙最高统治者昆弥的利益,导致贵族集团之间尖锐的冲突和斗争。雌栗靡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特制法律,明确保护对草场的占有、使用,不允许互相侵夺,这就既保证了昆弥的最高占有权,也可以相对地调节各级贵族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相对安定,“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的兴盛局面才得以出现。汉宣帝时,常惠为长罗侯驻屯于乌孙赤谷城,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靡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③,”颇可见分划地界(分划地域包括有关水源、草场的意义)是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之一大中心任务。
雌栗靡关于划分草场不得互相抢牧的规定,不仅政治上调节了统治集团间的关系,而且对牧业生产来说,也使水草资源得到适当的保护、开发和更合理的使用,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作为畜牧经济的补充,乌孙在西迁伊犁地区后,经过一个阶段,开始了农业的经营,这一发展,与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体的汉族人民的积极影响有关。在《汉书·西域传》中,述及乌孙的社会经济状况时,曾明确记载:它“不田作种树”,树者植也,说明乌孙不经营农业种植。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应指乌孙早期或初迁伊犁时期的情况。徙居伊犁一个阶段后,和汉朝政府的关系有了重大发展。联系致密,其经济生活也产生了相当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农业。《汉书·西域传》记述宣帝刘询为处理乌孙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王位的矛盾,曾派常惠率领“三校”士卒,驻屯赤谷①。具体说明了汉政府当时在乌孙的军队曾屯田自养。前文谈到,乌孙境内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宜牧不宜农;但在一些地势较低,接近河谷的地带,气温高,日照长,水量足,又是宜于农业生产的地段。在昭苏县发掘的一座乌孙墓葬封土中曾出土铁铧一件②。铁铧重3公斤,舌形,其形制类似关中地区出土的所谓“舌形大铧”,只是形体较小、较轻而已。出土时锈蚀较重,制作也较粗糙,铧体中部鼓凸若扁圆状,边缘刃部锐平,锋部稍残,说明曾经使用过。后部为椭圆形銎。这类形制的舌形铁铧,在关中地区的西汉中、晚期遗址中屡有所出③,尤其是与敦煌所出的铜铧④的形制和大小几乎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肯定,昭苏所出铁铧,虽出自墓葬封土中,无疑是汉代遗物,它用于破沟发土,是相当有力的。至于它是乌孙本身制造还是由内地输入,尚需进一步研究。不过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左右以后,乌孙的冶铁业无疑有了重要的进展(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因此这件实物也不能排斥有可能为乌孙所造。无论如何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乌孙农业的存在,而且可以说明在农业技术上吸收了中原地区的经验。乌孙早期农业,本来就与汉朝政府在赤谷的军事屯田有关,而士兵的主要成分又是农民,农业技术上出现这种共同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在中亚有关乌孙考古工作的报告中,也见到有关农业经营的直接材料,如出土了谷物及农作物和粮食加工工具:青铜镰刀、石磨盘、石碾等⑤,这些材料,对于说明乌孙在西迁伊犁地区后已有一定的农业经营是很有力量的。
手工业生产,是乌孙社会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又一生产部类,据考古资料,参照有关文献记录,这时手工业的种类有金属冶炼、
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器物加工等等。
金属冶炼,这是乌孙主要手工业生产部门。据考古资料,在西迁伊犁地区后的早期乌孙墓葬中,出土的金属器物虽有小铁刀、
小铁锥之属,但并不是普遍、大量的出现,而是数量少,仅见于部分墓葬之中;中期以后的墓葬,情况有明显变化。不仅普遍见到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小铁刀、铁锥,而且出土了环首铁刀、铁铧、铁镞。铜器有青铜锥、小铜帽、铜饰物等。从墓室四壁及椁木加工痕迹,明显可见使用了金属铲、凿之类的工具。同时,还见到残朽铜质器物及金戒指、金耳环及各种形式的金箔饰件。一些金箔饰件原来包覆在铜质器物上,绿色铜锈清楚可见①。
铁、钢等金属器物的制造,从前述发展过程分析,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小件铁镞、铁刀等应是本地所产。从早期墓葬中铁器较少,到中期以后铁器增多,质量提高,可以看到技术本身的进步。这一工艺的进步与中原地区先进工艺的影响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汉书·陈汤传》曾有明确的文字记载。陈汤在向汉成帝报告乌孙武备情况时明确说:“夫胡兵五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清楚地表明在西汉后期因“得汉巧”,乌孙的金属冶炼、武器加工技术水平有了重大发展和提高。其中如铁镞,是一种消耗量很大的武器,没有金属冶炼业的发展,是无法保证需求的。
金属的冶炼、金属工具的制造,涉及一系列专门生产工艺。这种生产方式,再不是作为家庭副业的手工业所能包容的,它们必然是独立于畜牧业、农业之外又一新的生产部门。
陶器制造:在乌孙墓葬内,普遍用陶器随葬。早期墓葬出土陶器,多手制的泥质陶,制作粗糙。器形主要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器的壶、钵、碟类等。由于是手制,不同墓葬内,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器皿,也只是基本形制相同,并不规整。大都呈红褐色或土红色,烧制火候也不高。这说明,陶器的制造,这时很可能还是作为一种家庭副业生产而存在,烧造陶器的方法也较原始,还是在露天或封闭不严的土室中烧造,所以火候低。早期陶器中,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相当部分底部穿孔,说明是专为随葬而生产的明器;二是这一阶段的陶器中,还有一种具有特色的茧形壶,小口小直颈,广肩鼓腹,两肩堆砌泥条,通体呈茧形①。这类茧形壶,就其基本形制特征看,与关中地区战国秦墓中常见的同类器相似(但在细部和纹饰上不同)。据研究,战国秦墓中的那种茧形壶是秦文化中具有特征性的器物②。
中期乌孙墓中的陶器,大多仍然是手制的,但经过刮磨加工,陶器较紧实致密,陶质较细,器形较规整,出现前期不见的烛台、盘、深腹钵等。进入后期,变化发展更为显著,陶器均为轮制,陶器形体规整,陶质细,火候高。至此,从陶器的使用及烧造技术的提高,说明制陶业已从家庭副业的生产状态脱离出来,成为社会上一个新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毛纺织业: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衣着除毛皮外,毛纺织物是重要的材料。而穹庐形的毡幕,则是主要的居住形式。细君公主充满哀怨的《黄鹄歌》中说,“穹庐为室兮旃为墙”,正是对这种毡幕的形象写照。这类毡幕障风避雨,搬迁甚易,适宜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具体特点,所以至今仍然是牧区广大人民喜好的居住形式。因此,毛毡的加工、擀制,是每户牧民都必须掌握的一种技术。它是将洗净的羊绒、羊毛,平铺在草席上,加力捶打、压擀。压擀过程中不断添毛、绒并加水,增加毛、绒黏附力。不断擀压,使绒、毛压实成毡。这一工作,因需较大的体力,主要由男子承担。毛布纺织也是每户牧民家庭必须掌握的又一种副业,无论是纺还是织,主要均由妇女承担。将毛、绒捻搓成线,编织成各种毛带,这是毡帐搬迁、固定、骑乘中都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纺织毛布更是一件费工费时的手工劳作。从罗布淖尔、哈密等地出土的早期毛织物看,新疆地区的毛纺织工艺,是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的③。由于气候潮湿多雨,在伊犁地区的乌孙墓葬中,迄今我们虽未直接发现毛织物标本,但却见到了毡毯的朽灰痕迹,或在墓室底部,或见于木椁内壁。乌孙当时存在毛纺织工艺是可以肯定的。
其他如墓葬中出土的三棱形骨镞、编席(印痕)等资料,还可以说明骨器制造、草编工艺等的存在。至于墓葬中出土的漆器残片和丝织物残片等表明丝、漆器存在的资料,应该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赠品或商品。《汉书·乌孙传》中记录了汉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乌孙时曾带来汉政府赠给的大批丝织品。只是由于昭苏雨水甚多,这些文物不易保存下来。
二
关于乌孙的社会性质、政治制度问题,前人著述中少见涉及。近年来,有关研究中对此提出了分析性意见①。但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两汉时期乌孙的社会性质,从文献及考古资料看,是一个宗法性很强的、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奴隶制社会。
乌孙,历史上曾长期受匈奴的统治和奴役,可以算是匈奴统治下的部落奴隶②。这种部落奴隶,实际就是被匈奴征服的部落集团。他们仍然在原居住地按自己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进行各自的生产活动,而按规定向匈奴统治集团缴纳大量贡赋,从事各项劳役义务以至战争义务,政治上朝会拜见以表示归属。《史记·大宛列传》称:“(昆莫)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就是反映了这种情况。这就形成了不同于家内奴隶制的又一种奴隶制剥削方式。被统治部落保持自己的家族、氏族、部落不变,原来的部落领袖或国王,对内仍然居于这一地位;但实质上不过是他族奴隶主上层集团的奴隶总管,是高级奴隶。乌孙在西迁伊犁河流域之初,与新疆其他小国一样,受匈奴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僮仆都尉”管辖。顾名思义,所谓“僮仆都尉”,就是奴隶总管。只是到后来,随着乌孙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日益强大,政治上就力图摆脱匈奴的控制和奴役,抗命“不肯朝会匈奴”。这一努力最后取得了成功。匈奴为维护旧有统治,曾以战争手段进行镇压,“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军事镇压遭到失败后,终于不能不承认了乌孙的相对独立地位。
乌孙社会内部也是实行着一种奴隶制度。
两汉时期,乌孙已明显进入阶级社会,这从文献记录中是清晰可见的。《汉书·西域传·乌孙传》中,称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不仅说明社会财富已积累很多,而且说明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化,贫富不均。因此,在乌孙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是十分尖锐的。所以,前引传文又称:“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这正是社会分化、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情况的反映。
乌孙,这时期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从这些文字记录,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在于,根据什么说它就是处在奴隶社会时期?
在《汉书·西域传·乌孙传》中述及乌孙社会情况时,有一句关键性的总结,“与匈奴同俗”。这种“俗”,决不只是人情习惯,风俗之“俗”,还意味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类同。匈奴,史学界大都认为它在两汉时期是实行着一种奴隶制度的,乌孙与匈奴历史关系十分密切,它是在匈奴的卵翼下成长、复国、发展起来的。乌孙吸收、仿同匈奴的各种制度,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过程。
文献记录中也不乏乌孙掠取人口,掠获大量战争俘虏的资料。这些被掠人口的归宿,只能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这里最显著的一例,就是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对匈奴的战争。乌孙精兵直捣右谷蠡王廷,“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于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乌孙皆自取所获”①。
在考古资料中,也颇有可与这些文献记录互相补充、互相发明的材料,有助于说明乌孙的社会性质。
在昭苏县木扎特山口(亦名夏台),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经三年时间,我们曾发掘了一座较大型的乌孙墓葬,编号为ZSM3。此墓封土呈圆丘形,远看形如小土山。底周有200多米,高达10米。封丘周围为一道浅沟。粗略测算,封堆体积达1万立方米,而且封土曾经局部加夯。这样巨型的封土堆,从挖土、运输、堆封、局部加夯等劳动过程分析,得动用3万左右人工(用比较落后的挖土工具,一人每天挖土以1立方米计;加上运输、堆封、夯实,估计人工得增两倍上下)。
巨型封堆中部是长方形墓室所在。墓室长6米、宽4米、深4米。墓室体积近100立方米。营构这样的墓室,只挖土即需人工200以上(挖这种坑,出土不易,费工较多)。墓室四壁为木椁,以直径20~30厘米的松木横竖叠砌,墓室顶部覆盖木三四层。粗略统计,用木材近达50立方米。这么多木材,砍伐、运输,没有数百工也是无法完成的。
营构这样巨型的大墓,必须组织、奴役大量的社会劳动力。而另一些形制虽近、但规模极小,只是微微隆起于地表的小型墓葬,墓室内既无木椁,殉物也极少或不见一件殉物。与前述大墓构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其社会地位悬殊、阶级身份各异、占有社会财富多寡不均的情况明晰可见。
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大墓墓室内虽曾经盗坑,尚残存一些陶器、骨器、铜铁器、金饰物、漆器残片等各类殉物外,在墓主人棺木旁侧还发现一个形制不太规整的半月形腰坑,坑内埋葬散乱的骨架,仔细区分,可识别出四个个体,他们应是惨遭杀殉的奴隶骸骨。这对于揭示乌孙的奴隶社会性质,是一件更有力的资料①。
两汉时期的乌孙社会,存在一套简单的政权、军事、社会组织。其中,虽还可以多少透见氏族社会阶段的印痕,但却已经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存在超阶级强制的一套全新制度了。
从《汉书·西域传·乌孙传》可以清楚看到,乌孙社会实行以国王为首的专制统治。王位的继承实行长子继承制。但这一继承制度,似乎确立、实行都还未太久,受到旧有习惯的强大干扰,相当严重地影响到乌孙政局的稳定。终西汉之世,因王位继承问题导致的矛盾、产生的祸乱频仍,并导致王国分裂。
从河西走廊西迁到伊犁河流域,败大月氏,并摆脱匈奴的奴役和控制,完成乌孙历史上这一辉煌功业的乌孙名王叫猎骄靡,王号为昆莫。猎骄靡的这种空前成就,使他赢得了在乌孙王国内的崇高权威,无人可以替代。他确定长子为太子,但太子早死。按长子继承法,太子死前要求立长孙为太子,也得到猎骄靡的认可,但这却激起次子的不满,他要求兄终弟及。次子官居大禄,有军事才能,率领局部万余骑谋叛反抗。猎骄靡不得不对之妥协,令长孙率领万余骑“别居”,自己也领万余骑“为备”。于是,名为一国,而实际“国分为三”,只是“大总羁属昆莫”(这种处置,也刻印着匈奴的影响。匈奴单于王廷居中,左右贤王分统左右两部,似为同一形式)。
猎骄靡死后,长孙军须靡继位。军须靡死前,其子泥靡幼小,也希望缓解与叔父的矛盾,决定让王位于大禄之子、其堂兄弟翁归靡,但却声言:“泥靡大,以国归之。”实际可以看成是习惯的兄终弟及法的实施。
翁归靡继承王位后,乌孙归于一统,国力强盛。公元前71年,曾与汉王朝配合,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空前胜利。他在位晚年,曾力图借汉王朝的力量,将他与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立为太子,毁弃由泥靡继位的前言,这得到汉王朝的全力支持。但翁归靡一死,泥靡即在“乌孙贵人”的支持下复位,重又导致乌孙王国分裂。翁归靡匈奴妻所生子乌就屠杀泥靡以自立,旋又在汉王朝的干预下立元贵靡为大昆靡(王)、乌就屠为小昆靡,并由汉王朝为之分别人民、地界。自此,大、小昆靡两部彼此矛盾、争斗不息,终西汉之时,“且无宁岁”。
从乌孙王统继承的矛盾和斗争过程看,长子继承法并未得到彻底确立,使奴隶主上层统治集团之间夺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更加尖锐;其次,从斗争过程看,在乌孙社会内部,似乎还有一种贵族议事会议在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其证明就是,当翁归靡准备凭藉汉王朝的权威决定由元贵靡继承王位,而不是如最初约定的交还政权给泥靡时,“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即军须靡)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翁归靡在位时,颇多建树,乌孙国力至达鼎盛,其在乌孙的权威和影响不可轻估;这时汉王朝对乌孙的重大军事、政治决策,也完全可以控制。但“乌孙贵人”竟仍然能够“共从本约”,不顾汉王朝的反对,扶立泥靡,他们在乌孙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量是不能轻估的。原始氏族社会阶段,氏族、部落领袖通过一定的形式决定部落联盟内的一切重大事务,这种议事会具有无上权威。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们的影响一落千丈。但在刚刚步入文明不久的历史阶段,这种贵族议事会的传统力量还是十分巨大的。这时的乌孙王位的继承当然秉承着国王的意志,但“乌孙贵人”(应该就是贵族议事会的成员)却可施加强大的影响。这可以说明乌孙社会跨入文明新阶段为时并不太久,古老的氏族社会的传统还是深具影响的。
乌孙社会的政权组织是比较简单的。昆莫(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其下为大禄,即相。这是昆莫的最重要的辅佐,是昆莫以下最重要的行政首脑,相当于汉王朝的丞相,故汉语译称“相”。但从实际职能看,它还有军事权力。担任这一职位的往往是高级贵族。猎骄靡为王,长子为太子,作王储,而次子即为“大禄”,可见其地位确实非同一般。
大禄之下,有左、右大将二人。这是王国最重要的军职。乌孙受匈奴影响,以左为贵,左大将位置更重。翁归靡时,三子为左大将;而冯嫽嫁右大将为妻。左、右大将,任重权高,不同于一般。韩宣为西域都护时,因乌孙王星靡“怯弱”,建议汉王朝“可免”其乌孙王号,“更以季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廷未允。但可见左大将权位之隆重。
大将以下有侯。侯的地位、权势亦重。《汉书》中屡见“诸翕侯”、“翕侯”之称,往往也都与军事活动有关。如翁归靡攻匈奴时,就是“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驰驱直进;乌就屠图谋政变,“与诸翕侯俱去”,后终“袭杀狂王”;“大昆弥翕侯难栖杀(小昆弥)末振将”等等,都可为证。
其他还有“大都尉”、“大蓝”、“大吏”、“舍十大吏”,“骑君”、“译导”等等。其中译导,未见明确记录,但在张骞出使中亚时,乌孙曾发译导送之;虑及当时西域地区民族复杂、语音纷殊的情况,司语言翻译、导送的吏员,肯定是存在的。这些大概就是乌孙王国内主要的军、政官吏。汉朝政府曾经接受了西域都护的建议,给“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金印紫绶”,这是汉王朝政府给丞相、列侯以上高官的待遇,于此可见这几种吏员在乌孙王国内地位的尊崇。
在乌孙的律令制度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大昆弥雌栗靡时正式颁布的:“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用法律形式,保护牧草场地的贵族所有,不允许互相侵夺,使草场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使用,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这一措施曾经保证了乌孙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
乌孙社会,诸翕侯各有自己的“民众”。这受到习惯的尊重、法律的保护。这些民众,很可能就是原来各部落的自由民及附属的家内奴隶,而翕侯则是原来的部落领袖,现在的世袭贵族。乌就屠袭杀狂王发动政变时,曾“与诸翕侯俱去”。后经汉王朝政府干预,乌就屠自愿做小昆弥,而由元贵靡为大昆弥,但乌就屠却“不尽归诸翕侯民众”。这导致汉王朝的干预,派常惠率领三校士兵驻屯赤谷,并为大、小昆弥明确分划人民、地界,以排除矛盾。这件事具体反映了自诸翕侯上至昆弥均有自己的地域、人众,说明在乌孙社会中氏族、部落残留的痕迹不小。
乌孙的军事制度,实际是全民皆兵。在“十二万户”的乌孙居民中,有“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可见每户的丁壮均是胜兵。这与匈奴的制度是一样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本性也”①。可见平常生产的组织与战时军事组织是完全合一的。而组织形式,应该就是从氏族社会接受过来的氏族、部落的外壳。所以,翕侯既是原来的部落领袖,又是现在新的军事、生产的领袖,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在乌孙社会的婚姻制度上,同样可以看到浓重的氏族社会习惯。试以解忧公主为例,先嫁军须靡;军须靡死,翁归靡继王位,则转嫁军须靡之堂兄弟翁归靡;翁归靡死后,又成了军须靡匈奴妻所生子泥靡的夫人。这与匈奴实行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②是完全一样的。有人对此提出的解释是“恶种姓之失”,“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实际这是原始社会氏族外婚制的一种遗留。他氏族的女子嫁到本氏族中来,就是本氏族一群兄弟的妻子。进入阶级社会,王位必须以国王的血统为转移,妻子也随着王位的继承而被继承,可以不至因王族血统的混乱而造成对王权的任何干扰。古老传统的外壳这时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
三
乌孙,汉代是西域地区最大的王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它从匈奴的羽盟转变为和西汉王朝结盟,并很快发展到政治上归属西汉王朝统治,可说是经历了巨大的发展。这一发展变化,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历史大厦,曾发挥过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深刻认识这一变化,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矛盾、斗争中加以考察。西汉前期,汉王朝政府与匈奴王国的矛盾和冲突是中国大地上主要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产生了汉王朝对西域及乌孙王国结盟的战略抉择及一系列策略措施,导致了西域及乌孙历史进程的新方向。
乌孙,历史上与匈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当乌孙居住、活动在河西走廊,在与大月氏和匈奴的冲突中国破家亡,难兜靡死于非命,其子猎骄靡在匈奴冒顿单于的救助、扶持下成长复国,这决定了乌孙与匈奴不同于一般的密切关系。猎骄靡幼时“生弃于野,乌衔肉飞其上,狼往乳之”的神话故事,正是曲折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真实。狼,是匈奴的图腾,匈奴的象征。
猎骄靡长大成人,冒顿又“使将兵”,“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使其逐步成长为一支不可轻视的强大力量。无论猎骄靡,还是乌孙各级氏族、部落的领袖人物(也就是以后乌孙王国的各级贵族),对匈奴的依附,自然不同于一般。冒顿时期,乌孙实际是匈奴的属部,承担了经济上贡纳、政治上服从、军事上接受调度的各种强制性义务,实质上是部落奴隶。只是在冒顿死后,关系才疏远了一层。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乌孙“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①,企图摆脱匈奴的奴役和统治,尤其是乌孙西迁伊犁地区以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口增多,国力增强。对匈奴奴隶主集团苛繁的经济掠夺,对自身政治上的屈辱地位更加不满,这自然导致矛盾的进一步发展。
而正是在这样的矛盾面前,西汉王朝的使者张骞带来了西汉政府结盟抗击匈奴的建议和要求:“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拒匈奴。”这对乌孙,是既有一定吸引力,但又是不能贸然决定的重大问题。主要的困难在于:不知汉王朝实力;内部亲依匈奴、恐惧匈奴的势力不小;而且国分为三,猎骄靡一人无法专制。所以只是派人、送马回报,并未明确答应汉王朝要求。
促成猎骄靡改变态度,同意和亲、结盟的,主要是客观形势的急剧变化。虽乌孙态度暧昧,西汉王朝通使西域、断匈奴右臂的决策却在积极执行,汉使大宛、月氏者,“相属不绝”;匈奴了解乌孙曾与汉王朝通使往来后,“怒,欲击之”;再加乌孙使者到内地,“见汉人众富厚”,也增强了信心。这几个因素促使猎骄靡“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希望通过和亲结盟以保证自身政权的安全稳定。最后以马千匹为聘,汉王朝则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主,出嫁猎骄靡,为右夫人。匈奴也闻风而动,“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②。这时的猎骄靡,行动上还是持两端,希望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保持平衡。
乌孙,由这种半心半意与汉王朝结盟到全心全意结盟,以至后来政治上归属西汉王朝,接受汉王朝的统属,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汉王朝政府在对匈奴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匈奴实力不断被严重削弱。
汉武帝刘彻,在汉初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利用富厚的经济力量,对匈奴向中原地区不断的侵扰、掠夺性的战争发起了反击。这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常生产秩序和人民安定生活的保障的。匈奴则由于战争失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自然灾害频仍,军事、经济实力受到极大削弱,逐步失掉了对阴山、河套、河西走廊、西域广大水草肥美地区的控制。汉王朝在实际控制西域广大地区后,于公元前60年(汉神爵二年),正式派出了统管西域地区军政事务的西域都护。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西域地区,包括北疆乌孙,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至此正式列入汉朝版图。这无论在新疆古代历史,还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形成和发展史上都是一次关系重大的事件。设西域都护,标志匈奴对西域控制的瓦解。这一重大进展,与本始三年,汉、乌孙联军对匈奴战争取得的胜利直接有关。此前,匈奴为维护其对西域的统治,以巴里坤草原为前进基地,屯田车师(吐鲁番盆地及吉木萨尔等地),进攻乌孙,以控制、稳定北疆地区,隔断乌孙与汉朝的联系,并以车师为桥头堡,向南疆发展。乌孙王翁归靡与汉解忧公主清楚地分析了有关形势,先后多次上书汉王朝,建议组织联军反击。“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王朝在充分准备以后,“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西域一线,“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密切配合行动。这一仗获得了全胜。乌孙“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廷,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于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骆驼七十余万头”①,这一仗,使匈奴在西域地区的力量、元气大伤。史载,“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转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②。汉、乌孙联军的这一次打击,对匈奴帝国的衰败瓦解,所起作用是相当不小的。
乌孙政治上归属汉王朝统治,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这次联合军事行动到西域都护设立期间的种种情况分析,已经充分完成。我们说,自这一阶段以后,乌孙从政治上看已经是西汉王朝统属下的一个部分,有如下的实质表现。
首先,乌孙王国自国王以下各级官员,均接受汉王朝的册封,佩汉朝政府颁发的印绶,作为其权威的象征,表示其权力的合法性。如大吏、大禄、大监,汉朝政府均视为如汉之最高级吏员,赐金印紫绶;只是在发现他们不能忠于职守,如乌孙王雌栗靡被杀害时不作有力抗争,即收回金印紫绶,另颁铜印墨绶,作为惩处。铜印墨绶,在汉王朝,只是600石以上吏员的级别标志。不仅是这种配戴印绶,更重要的,乌孙王的王位继承、废立,亦均要得到汉王朝的认可,翁归靡希望变动旧议,改立元贵靡为嗣,要报汉王朝;乌就屠杀泥靡,自立为王,西域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只得放弃了大昆弥的地位;西域都护韩宣认为乌孙王“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王朝不批准,就必须维持原状;乌孙小昆弥末振将使人刺杀大昆弥雌栗靡,汉王朝即始终以诛杀末振将为己任,对杀死末振将的难栖升官晋爵,封为“坚守都尉”。凡此种种,均堪足以说明汉王朝对乌孙王国内重大政治事项均有直接处理的权力及责任。
其次,西汉王朝对乌孙军队有征调、节制指挥权。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汉、乌孙联军共讨匈奴,汉政府即“遣校尉使持节护乌孙兵”,实际是掌握了最主要的对乌孙部队的控制、指挥权。汉地节元年(前69年),常惠自乌孙经龟兹返内地,在霍光支持下,自行调发龟兹以东各小国合兵2万余人,乌孙兵7000人,三面围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罪①。类此,均是较大的、有历史影响的军事行动,故史籍有所记载,其他规模较小的军事征发肯定是不会少的,这种军事指挥权是国家权力的主要表现之一。
对危及乌孙王国政权稳定、安全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有处理权力。乌就屠与元贵靡兄弟失和,争位夺权。经汉王朝裁定,元贵靡为大昆靡、乌就屠为小昆靡。但乌就屠仍然“不尽归诸翕侯民众”。为稳定乌孙内部的局势,“汉复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6万余,小昆弥户4万余”②,明确分划清楚地界,分划清楚户口、民众的归属,并派驻部队屯田监守,保证有关决定的实施。汉王朝的统治权力在这里是明确无误的。
在乌孙归属于汉王朝的统治,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犁河流域广大土地进入祖国的版图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进程中,汉王朝政府实行的和亲政策,细君、解忧,其中尤其是解忧公主在乌孙王国的活动,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从西汉王朝与乌孙王国和亲的实践看,实际是一种政治结盟的方式。在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下,这种和亲可以实现很好的政治效果。因为国家政权是一种宗法性的、世袭的王权统治,与国王联姻,利用女主对国王及王室的影响,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会起到特殊的作用。西汉王朝与乌孙和亲,就怀有这样的愿望。这从细君嫁给年迈体衰的猎骄靡,而猎骄靡随后又要求细君再嫁其长孙军须靡时,细君受汉朝传统、礼教的束缚,不从,请示汉王朝。刘彻的决定却是:“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一语道破了这种政治婚姻的实质。细君秉承汉王朝旨意,不仅再嫁了军须靡;而且根据自身使命,广泛进行了活动:“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但终因不多几年即逝,未见出显著成效。而解忧公主,先后在乌孙生活了50年左右,在乌孙的政治生活中就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解忧在乌孙曾先后嫁军须靡、翁归靡、泥靡。她与翁归靡共同生活时间颇长,“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为莎车王。次男大乐,为右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翕侯妻”。这些子女,在乌孙、龟兹、莎车,都曾居于显要地位。
翁归靡,在乌孙历史上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名王。他在位时,王国统一,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西汉后期雌栗靡取得显著政绩,史家即以之和翁归靡这段统治时期相比称,可见不同于一般。翁归靡的这一建树,得到过解忧的有力佐助和支持,翁归靡在汉、乌孙联军重创匈奴这一著名战役中的贡献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为促成这一战役实现,解忧曾多次上书汉廷,力陈利害,终于达到了预想的结果。
综观解忧在乌孙的活动,实际上是西汉王朝派驻乌孙的全权代表。她洞察、分析乌孙的各种情况,提出关键性的建议或运用自己的地位、影响便宜行事。公元前71年扭转了西域地区政治形势,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的重大战役,解忧起过十分显著的作用;狂王泥靡“暴恶失众”,“为乌孙所患苦”,她一手策划、指挥了剪除狂王的宫廷政变。这次政变,因行事者粗疏,未得成功。但于此可见解忧在乌孙的影响、谋略。她不仅运用自身力量影响乌孙政局,而且以乌孙为基地,派心腹“侍者冯嫽”,“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得到“敬信”。冯嫽“能史书、习事”,是一个熟悉西域情况、有相当水平的能干女官,被西域各国尊之为“冯夫人”。她的丈夫是乌孙右大将,她曾运用这一关系,平息、调处了乌就屠发动的又一变乱。原来,在狂王泥靡死后,未得汉王朝同意,乌就屠即擅自继位为王。为此,汉王朝调动了军队,准备了粮食,准备进行征讨。最后,在冯夫人为首的汉朝命使的调解下,乌就屠同意放弃昆莫称号,“为小昆弥”,而由汉王朝册“立元贵靡为大昆弥”。王国一分为二,“使破羌将军不出塞”,一场箭在弦上的战争得以避免。冯夫人在乌孙享有威望,她对乌孙也怀有感情。在解忧公主年老回到中原后,乌孙大昆弥星靡怯弱,她不惮以老年之身,主动向汉王朝要求,愿“使乌孙镇抚星靡”,并得以如愿成行。
从解忧、冯嫽的和亲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其作用是不能轻估的,当然,和亲所以能发挥这样的影响,还在于当时总的斗争形势。在汉与匈奴、汉与乌孙、匈奴与乌孙这几组具体矛盾中:匈奴势力日蹙;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日强;乌孙对匈奴的奴隶制掠夺政策反抗日烈,而自身在汉朝和亲政策实践中也感受到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等等。没有这些基本的条件,无论解忧、冯嫽个人具有怎样超群出众的能力,也是无补于事的。
汉与乌孙的和亲,对乌孙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细君初嫁乌孙时,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其盛”,“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足见,这种动辄数百人的和亲使团,是包含有各方面的人才的;否则,“自治宫室”,哪里得有可能?!解忧在乌孙生活有50年左右,联系更加密切。解忧的女儿弟史至“京师学鼓琴”,弟史丈夫龟兹王绛宾企图在龟兹推行汉王朝的制度;经过不长的时间,乌孙王国的冶金技术得到很大提高,缩短了和中原地区冶炼技术间的差距;在长安,可以学习乌孙的语言……凡此种种,都可以见出彼此关系的深入、密切。这意味着彼此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丰富,在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历史中,它曾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是不应该忽视的。
关于乌孙的历史资料,比较集中地见诸于《史记》、《汉书》等早期史籍,但均非常简略。对乌孙西迁新疆西部地区后的政治、经济状况,与西汉王朝的关系等,也都是语焉不详,都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20世纪60年代初期,新疆考古研究所曾组织力量对天山以北的北疆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并进而在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地区等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发掘。结果,在伊犁河流域发现了乌孙古代文化遗存。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进行了两次工作①,这就为我们研究乌孙历史提供了一批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大大丰富、扩展了历史文献对乌孙的有限记录,加深了我们对乌孙历史,尤其是西迁伊犁地区后乌孙王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状况的认识和了解。
一
乌孙,在汉代的西域地区是一个最大的地方小王国政权。《汉书·西域传》记述:它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不论是人口还是兵力,与汉西域地区其他地方政权相比较,都居于前列。
乌孙,西徙伊犁地区后的活动地域,文献中没有准确、具体的记录。根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在新疆北部地区的考古调查及部分地区的重点发掘资料,我国境内现存的乌孙考古遗存,主要分布在天山到伊犁河之间广阔的草原地带,如昭苏、特克斯、新源、巩留、尼勒克等县,其中昭苏县木扎特草原、萨勒卧堡乡,新源县巩乃斯种羊场和县城附近,特克斯县三乡等地都有规模巨大的乌孙墓葬群,尤其是木扎特草原,正位于唐称为凌山的天山北麓,巨冢成行成列,漫布在山口外草原上,底周一般均在二三百米左右,高达七八米,犹如一座小山,巍然屹立,气势雄伟,景色壮观,这些无疑都是乌孙上层贵族的墓冢。
在乌孙墓葬比较集中分布的上述地区内,山多松林,水丰草茂,气温比较低,地理气候特点与《汉书·西域传》中所描写的乌孙地区“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完全一致。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昭苏县与察布查尔县交界的一段天山支脉,至今当地群众尚呼之为“乌孙山”;同时在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活动地域的我国哈萨克族中,新中国成立前就仍然有名为“玉孙”(即乌孙)的部落,表现了乌孙西徙伊犁地区后,在各方面留下的深重历史印痕。
凭借众多的人力资源,加上伊犁河谷十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乌孙在西迁伊犁地区以后,社会经济得到了逐步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公元前1世纪以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乌孙经济是以畜牧业为主体的一种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虽也存在,但并不居于重要地位。
伊犁地区,尤其是伊犁河南至天山山麓这一片草原,天山中间的高山草场是非常优良的牧业基地。在这片地区内,气候湿润、草场辽阔,牧草以禾本科、豆科为主,适饲性强,利用率高,载畜量大。而且雨水较多,山区松林漫布。以昭苏县为例,据县气象站统计资料,年降雨量一般达500毫米,全年日照时间2400多小时,年平均气温较低,只有2.5℃。无霜期只有100天左右。海拔1000~2000米。这种气候地理特点,对农业生产不利,但对畜牧业却非常适宜,真可谓水足草茂。这种地理环境与《汉书·西域传》记录的“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颇相一致。我们在昭苏草原调查中,茂草的高度及于马腹。大家都知道,马对饲草的要求是高草、禾本科、豆科草类,而这正是伊犁河谷、天山山前地带可以满足的条件,它对于马的饲养特别有利。苜蓿也是这片地区广泛种植的优良饲料。而在这大片地区内,山前与山中、山内阳坡与阴坡,随地势变化,气候、牧草也都有相应改变,可适应畜群不同季节的需要。如山中背风面阳的较低处所,冬日基本无雪;即有小雪,并不能全部覆盖牧草。冬日气温较高,牧草可供畜群需要,这些是俗称的“冬窝子”,即冬草场。夏日,牲畜可转至地势较高,气候凉爽,有水有草的高山草场,畜群可以得到充分的营养,避开了山前地势低平处较高的气温,这里是俗称的“夏窝子”,即夏牧场。至于春秋草场,基本在同一地点,大都是山前地带。在畜群转场后,一般都有几个月的间隔,牧草可以得到恢复、生长,下一季节畜群转回时,可以满足需要。这样,在一个小地区内,不论春、夏、秋、冬,可供牲畜饲用、彼此相去也不算太远的四季草场俱备,就为人工放牧,靠天然草场饲畜提供了合适的条件。它和《盐铁论》中对匈奴游牧特点的描述“因水草为仓廪”、“随美草甘水而驱牧”颇为一致。在水草条件合适、有自然游牧的条件时,古代的游牧民族多采取这一经营方式。迄目前为止,在新疆北部广大牧区畜牧业经营与内地多数省区不同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此。它与农业结合很不紧密,依靠天然草场养畜,人工放牧,随季节转换草场。看来这是适应自然地理条件、长期形成的放牧习惯。《汉书》称乌孙的社会经济特点是“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就是这种经营特点的简练概括。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种相对流动的游牧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对的定居。我们认为,在乌孙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居住点,文献中提到乌孙首都赤谷城,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存在定居的直接证明。在考古调查中,我们发现,乌孙土墩墓大量集中的地点往往是出天山山口的河流附近的山前草原,或其他一些水草俱佳的小谷地。这些地点多为春秋牧场所在,也就是地势开阔、气候较温和、牧民活动时间最长的地点。在这些地区内,墓群成行成列,巨型土冢远远可见,蔚为壮观。这些地点应该也是乌孙人生活居住的中心。虽然我们目前还未直接发现当时的居住遗迹,但从墓地特点可以推论:居地与墓地相去不会太远;巨型土冢的营建非一日一时之功,必须动员相当人力、物力,远距住地将无法进行。
当时的住室(除毡幕外)是什么样式?这从考古资料与民族调查中颇有线索可寻。在昭苏等县区,农村中目前仍沿用一种小屋,是以圆木为墙、盖顶。圆木纵横交接处互相凿孔榫卯,屋顶、木墙外均覆土抹泥。室内铺地板,木壁或挂毡毯。障风、避雨雪、保暖,作用均佳。这是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因地制宜而出现的建筑形式。非常有趣的是,这种木屋结构与乌孙古墓内见到的木椁造型,几乎一样。椁室四壁均以圆木叠砌成墙,接头处互相榫卯,保持牢固和水平。椁室内壁曾经挂毡毯,朽灰仍见。毡毯外并钉附“米”字型细木条。椁木顶部盖覆松木二三层。坟墓是生者为死者安排的地下居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图景。而这一墓室形制正是现存木构小屋的形象。我们把它看成是古代乌孙人住室的再现,可以说是言之成理的。
乌孙的牲畜种类,据有关文献,主要有马、牛、羊、骆驼、驴等①,而以养羊、马为主。考古发掘中,曾发现有马、羊、狗的骨架或部分骨骼,而以马、羊骨居多。《汉书·西域传》说其“国多马,富人或至四五千匹”。媒聘细君公主,即“以马千匹”为礼,颇可见养马数量之多。马的质量,在汉代也负有盛名,张骞以后从乌孙选去内地的马匹,因品种优良,被誉称“天马”。在大宛马进入中原后,才更“天马”之名为“西极马”。伊犁河流域,实际上就是当年乌孙的中心地域,至今仍然是全国知名的“伊犁马”生产基地,马体不大,形体俊美,善走,速度亦佳。看来,这是有悠久传统的。
墓葬中殉葬的马、羊、狗等的骨架,形象地反映了牧业生活特点。马,日常骑乘,代步,不论用于生产或作战,都不可稍离,它们是牧民生产和生活中主要的伴侣。羊是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生活资料。细君公主在《黄鹄歌》中咏唱的“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这里的“肉食”,马、牛、羊肉都有,但羊是居于主要地位的。墓葬内出土的羊骨,往往都和一把小铁匕首共见,小铁匕首甚至穿插在羊骨中,形象地表现了当时生者为死者去到另一个世界时安排的肉食资料,而这自然也是生者日常生活的现实写照。操小刀以剔肉,到现在为此,还是牧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乌孙墓葬内,或在封土中,曾见到完整的狗骨架。在牧业生产中,牧羊犬是牧人十分重要的助手,他们能帮助看守羊群,防止狼害。每个牧民家庭,无不有犬,墓室内葬狗,封土中殉狗(应该是祭礼的体现),也自然就是为死者作出的切合牧业生产需要的周到安排。
西汉后期,当雌栗靡为乌孙大昆弥时,颇具权威,贵族翕侯皆畏服之。史籍记载其重要政绩,取得成功的经验是在国内颁布了一条法令:“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①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条记录。“无使入牧”的含义,前人颜师古、徐松曾有注释。颜注为“勿入昆弥牧中,恐其相扰也”。徐松则认为是“入牧、疑当谓人所牧为税”②。我们认为,徐松所注并未得其要领,颜注接近于实际。这里的“无使入牧”四字,应该不仅是包括昆弥,也包括乌孙统治集团各级“贵人”之间。全面地说,应作“无使入昆弥及他人牧地”,这实际上是一项调节生产关系的重大措施。如前所述,畜牧业是乌孙社会经济的主体,而牧放畜群又是依靠四季天然草场。因此,草场就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对它的占有、使用,实际就是对社会最主要财富的占有、使用。一定数量的草场,其载畜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掌握了大量畜群的乌孙昆弥及各级翕侯,亦即是乌孙社会的贵族统治集团,他们对草场的占有要求,尤其是对水质好、水源足、草质优良的草场的占有要求,就是一种经常存在的需要。而这类优良草场总是有限的。这种多量的需求与有限的可能就会形成经常的矛盾,会不可避免地危及乌孙最高统治者昆弥的利益,导致贵族集团之间尖锐的冲突和斗争。雌栗靡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特制法律,明确保护对草场的占有、使用,不允许互相侵夺,这就既保证了昆弥的最高占有权,也可以相对地调节各级贵族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相对安定,“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的兴盛局面才得以出现。汉宣帝时,常惠为长罗侯驻屯于乌孙赤谷城,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靡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③,”颇可见分划地界(分划地域包括有关水源、草场的意义)是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之一大中心任务。
雌栗靡关于划分草场不得互相抢牧的规定,不仅政治上调节了统治集团间的关系,而且对牧业生产来说,也使水草资源得到适当的保护、开发和更合理的使用,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作为畜牧经济的补充,乌孙在西迁伊犁地区后,经过一个阶段,开始了农业的经营,这一发展,与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体的汉族人民的积极影响有关。在《汉书·西域传》中,述及乌孙的社会经济状况时,曾明确记载:它“不田作种树”,树者植也,说明乌孙不经营农业种植。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应指乌孙早期或初迁伊犁时期的情况。徙居伊犁一个阶段后,和汉朝政府的关系有了重大发展。联系致密,其经济生活也产生了相当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农业。《汉书·西域传》记述宣帝刘询为处理乌孙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王位的矛盾,曾派常惠率领“三校”士卒,驻屯赤谷①。具体说明了汉政府当时在乌孙的军队曾屯田自养。前文谈到,乌孙境内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宜牧不宜农;但在一些地势较低,接近河谷的地带,气温高,日照长,水量足,又是宜于农业生产的地段。在昭苏县发掘的一座乌孙墓葬封土中曾出土铁铧一件②。铁铧重3公斤,舌形,其形制类似关中地区出土的所谓“舌形大铧”,只是形体较小、较轻而已。出土时锈蚀较重,制作也较粗糙,铧体中部鼓凸若扁圆状,边缘刃部锐平,锋部稍残,说明曾经使用过。后部为椭圆形銎。这类形制的舌形铁铧,在关中地区的西汉中、晚期遗址中屡有所出③,尤其是与敦煌所出的铜铧④的形制和大小几乎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肯定,昭苏所出铁铧,虽出自墓葬封土中,无疑是汉代遗物,它用于破沟发土,是相当有力的。至于它是乌孙本身制造还是由内地输入,尚需进一步研究。不过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左右以后,乌孙的冶铁业无疑有了重要的进展(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因此这件实物也不能排斥有可能为乌孙所造。无论如何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乌孙农业的存在,而且可以说明在农业技术上吸收了中原地区的经验。乌孙早期农业,本来就与汉朝政府在赤谷的军事屯田有关,而士兵的主要成分又是农民,农业技术上出现这种共同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在中亚有关乌孙考古工作的报告中,也见到有关农业经营的直接材料,如出土了谷物及农作物和粮食加工工具:青铜镰刀、石磨盘、石碾等⑤,这些材料,对于说明乌孙在西迁伊犁地区后已有一定的农业经营是很有力量的。
手工业生产,是乌孙社会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又一生产部类,据考古资料,参照有关文献记录,这时手工业的种类有金属冶炼、
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器物加工等等。
金属冶炼,这是乌孙主要手工业生产部门。据考古资料,在西迁伊犁地区后的早期乌孙墓葬中,出土的金属器物虽有小铁刀、
小铁锥之属,但并不是普遍、大量的出现,而是数量少,仅见于部分墓葬之中;中期以后的墓葬,情况有明显变化。不仅普遍见到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小铁刀、铁锥,而且出土了环首铁刀、铁铧、铁镞。铜器有青铜锥、小铜帽、铜饰物等。从墓室四壁及椁木加工痕迹,明显可见使用了金属铲、凿之类的工具。同时,还见到残朽铜质器物及金戒指、金耳环及各种形式的金箔饰件。一些金箔饰件原来包覆在铜质器物上,绿色铜锈清楚可见①。
铁、钢等金属器物的制造,从前述发展过程分析,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小件铁镞、铁刀等应是本地所产。从早期墓葬中铁器较少,到中期以后铁器增多,质量提高,可以看到技术本身的进步。这一工艺的进步与中原地区先进工艺的影响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汉书·陈汤传》曾有明确的文字记载。陈汤在向汉成帝报告乌孙武备情况时明确说:“夫胡兵五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清楚地表明在西汉后期因“得汉巧”,乌孙的金属冶炼、武器加工技术水平有了重大发展和提高。其中如铁镞,是一种消耗量很大的武器,没有金属冶炼业的发展,是无法保证需求的。
金属的冶炼、金属工具的制造,涉及一系列专门生产工艺。这种生产方式,再不是作为家庭副业的手工业所能包容的,它们必然是独立于畜牧业、农业之外又一新的生产部门。
陶器制造:在乌孙墓葬内,普遍用陶器随葬。早期墓葬出土陶器,多手制的泥质陶,制作粗糙。器形主要是作为日常生活用器的壶、钵、碟类等。由于是手制,不同墓葬内,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器皿,也只是基本形制相同,并不规整。大都呈红褐色或土红色,烧制火候也不高。这说明,陶器的制造,这时很可能还是作为一种家庭副业生产而存在,烧造陶器的方法也较原始,还是在露天或封闭不严的土室中烧造,所以火候低。早期陶器中,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相当部分底部穿孔,说明是专为随葬而生产的明器;二是这一阶段的陶器中,还有一种具有特色的茧形壶,小口小直颈,广肩鼓腹,两肩堆砌泥条,通体呈茧形①。这类茧形壶,就其基本形制特征看,与关中地区战国秦墓中常见的同类器相似(但在细部和纹饰上不同)。据研究,战国秦墓中的那种茧形壶是秦文化中具有特征性的器物②。
中期乌孙墓中的陶器,大多仍然是手制的,但经过刮磨加工,陶器较紧实致密,陶质较细,器形较规整,出现前期不见的烛台、盘、深腹钵等。进入后期,变化发展更为显著,陶器均为轮制,陶器形体规整,陶质细,火候高。至此,从陶器的使用及烧造技术的提高,说明制陶业已从家庭副业的生产状态脱离出来,成为社会上一个新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毛纺织业: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衣着除毛皮外,毛纺织物是重要的材料。而穹庐形的毡幕,则是主要的居住形式。细君公主充满哀怨的《黄鹄歌》中说,“穹庐为室兮旃为墙”,正是对这种毡幕的形象写照。这类毡幕障风避雨,搬迁甚易,适宜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具体特点,所以至今仍然是牧区广大人民喜好的居住形式。因此,毛毡的加工、擀制,是每户牧民都必须掌握的一种技术。它是将洗净的羊绒、羊毛,平铺在草席上,加力捶打、压擀。压擀过程中不断添毛、绒并加水,增加毛、绒黏附力。不断擀压,使绒、毛压实成毡。这一工作,因需较大的体力,主要由男子承担。毛布纺织也是每户牧民家庭必须掌握的又一种副业,无论是纺还是织,主要均由妇女承担。将毛、绒捻搓成线,编织成各种毛带,这是毡帐搬迁、固定、骑乘中都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纺织毛布更是一件费工费时的手工劳作。从罗布淖尔、哈密等地出土的早期毛织物看,新疆地区的毛纺织工艺,是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的③。由于气候潮湿多雨,在伊犁地区的乌孙墓葬中,迄今我们虽未直接发现毛织物标本,但却见到了毡毯的朽灰痕迹,或在墓室底部,或见于木椁内壁。乌孙当时存在毛纺织工艺是可以肯定的。
其他如墓葬中出土的三棱形骨镞、编席(印痕)等资料,还可以说明骨器制造、草编工艺等的存在。至于墓葬中出土的漆器残片和丝织物残片等表明丝、漆器存在的资料,应该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赠品或商品。《汉书·乌孙传》中记录了汉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嫁乌孙时曾带来汉政府赠给的大批丝织品。只是由于昭苏雨水甚多,这些文物不易保存下来。
二
关于乌孙的社会性质、政治制度问题,前人著述中少见涉及。近年来,有关研究中对此提出了分析性意见①。但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两汉时期乌孙的社会性质,从文献及考古资料看,是一个宗法性很强的、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奴隶制社会。
乌孙,历史上曾长期受匈奴的统治和奴役,可以算是匈奴统治下的部落奴隶②。这种部落奴隶,实际就是被匈奴征服的部落集团。他们仍然在原居住地按自己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进行各自的生产活动,而按规定向匈奴统治集团缴纳大量贡赋,从事各项劳役义务以至战争义务,政治上朝会拜见以表示归属。《史记·大宛列传》称:“(昆莫)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就是反映了这种情况。这就形成了不同于家内奴隶制的又一种奴隶制剥削方式。被统治部落保持自己的家族、氏族、部落不变,原来的部落领袖或国王,对内仍然居于这一地位;但实质上不过是他族奴隶主上层集团的奴隶总管,是高级奴隶。乌孙在西迁伊犁河流域之初,与新疆其他小国一样,受匈奴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僮仆都尉”管辖。顾名思义,所谓“僮仆都尉”,就是奴隶总管。只是到后来,随着乌孙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日益强大,政治上就力图摆脱匈奴的控制和奴役,抗命“不肯朝会匈奴”。这一努力最后取得了成功。匈奴为维护旧有统治,曾以战争手段进行镇压,“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军事镇压遭到失败后,终于不能不承认了乌孙的相对独立地位。
乌孙社会内部也是实行着一种奴隶制度。
两汉时期,乌孙已明显进入阶级社会,这从文献记录中是清晰可见的。《汉书·西域传·乌孙传》中,称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不仅说明社会财富已积累很多,而且说明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化,贫富不均。因此,在乌孙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是十分尖锐的。所以,前引传文又称:“民刚恶贪狠无信,多寇盗”,这正是社会分化、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情况的反映。
乌孙,这时期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从这些文字记录,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在于,根据什么说它就是处在奴隶社会时期?
在《汉书·西域传·乌孙传》中述及乌孙社会情况时,有一句关键性的总结,“与匈奴同俗”。这种“俗”,决不只是人情习惯,风俗之“俗”,还意味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类同。匈奴,史学界大都认为它在两汉时期是实行着一种奴隶制度的,乌孙与匈奴历史关系十分密切,它是在匈奴的卵翼下成长、复国、发展起来的。乌孙吸收、仿同匈奴的各种制度,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过程。
文献记录中也不乏乌孙掠取人口,掠获大量战争俘虏的资料。这些被掠人口的归宿,只能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这里最显著的一例,就是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对匈奴的战争。乌孙精兵直捣右谷蠡王廷,“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于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乌孙皆自取所获”①。
在考古资料中,也颇有可与这些文献记录互相补充、互相发明的材料,有助于说明乌孙的社会性质。
在昭苏县木扎特山口(亦名夏台),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经三年时间,我们曾发掘了一座较大型的乌孙墓葬,编号为ZSM3。此墓封土呈圆丘形,远看形如小土山。底周有200多米,高达10米。封丘周围为一道浅沟。粗略测算,封堆体积达1万立方米,而且封土曾经局部加夯。这样巨型的封土堆,从挖土、运输、堆封、局部加夯等劳动过程分析,得动用3万左右人工(用比较落后的挖土工具,一人每天挖土以1立方米计;加上运输、堆封、夯实,估计人工得增两倍上下)。
巨型封堆中部是长方形墓室所在。墓室长6米、宽4米、深4米。墓室体积近100立方米。营构这样的墓室,只挖土即需人工200以上(挖这种坑,出土不易,费工较多)。墓室四壁为木椁,以直径20~30厘米的松木横竖叠砌,墓室顶部覆盖木三四层。粗略统计,用木材近达50立方米。这么多木材,砍伐、运输,没有数百工也是无法完成的。
营构这样巨型的大墓,必须组织、奴役大量的社会劳动力。而另一些形制虽近、但规模极小,只是微微隆起于地表的小型墓葬,墓室内既无木椁,殉物也极少或不见一件殉物。与前述大墓构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其社会地位悬殊、阶级身份各异、占有社会财富多寡不均的情况明晰可见。
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大墓墓室内虽曾经盗坑,尚残存一些陶器、骨器、铜铁器、金饰物、漆器残片等各类殉物外,在墓主人棺木旁侧还发现一个形制不太规整的半月形腰坑,坑内埋葬散乱的骨架,仔细区分,可识别出四个个体,他们应是惨遭杀殉的奴隶骸骨。这对于揭示乌孙的奴隶社会性质,是一件更有力的资料①。
两汉时期的乌孙社会,存在一套简单的政权、军事、社会组织。其中,虽还可以多少透见氏族社会阶段的印痕,但却已经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存在超阶级强制的一套全新制度了。
从《汉书·西域传·乌孙传》可以清楚看到,乌孙社会实行以国王为首的专制统治。王位的继承实行长子继承制。但这一继承制度,似乎确立、实行都还未太久,受到旧有习惯的强大干扰,相当严重地影响到乌孙政局的稳定。终西汉之世,因王位继承问题导致的矛盾、产生的祸乱频仍,并导致王国分裂。
从河西走廊西迁到伊犁河流域,败大月氏,并摆脱匈奴的奴役和控制,完成乌孙历史上这一辉煌功业的乌孙名王叫猎骄靡,王号为昆莫。猎骄靡的这种空前成就,使他赢得了在乌孙王国内的崇高权威,无人可以替代。他确定长子为太子,但太子早死。按长子继承法,太子死前要求立长孙为太子,也得到猎骄靡的认可,但这却激起次子的不满,他要求兄终弟及。次子官居大禄,有军事才能,率领局部万余骑谋叛反抗。猎骄靡不得不对之妥协,令长孙率领万余骑“别居”,自己也领万余骑“为备”。于是,名为一国,而实际“国分为三”,只是“大总羁属昆莫”(这种处置,也刻印着匈奴的影响。匈奴单于王廷居中,左右贤王分统左右两部,似为同一形式)。
猎骄靡死后,长孙军须靡继位。军须靡死前,其子泥靡幼小,也希望缓解与叔父的矛盾,决定让王位于大禄之子、其堂兄弟翁归靡,但却声言:“泥靡大,以国归之。”实际可以看成是习惯的兄终弟及法的实施。
翁归靡继承王位后,乌孙归于一统,国力强盛。公元前71年,曾与汉王朝配合,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空前胜利。他在位晚年,曾力图借汉王朝的力量,将他与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立为太子,毁弃由泥靡继位的前言,这得到汉王朝的全力支持。但翁归靡一死,泥靡即在“乌孙贵人”的支持下复位,重又导致乌孙王国分裂。翁归靡匈奴妻所生子乌就屠杀泥靡以自立,旋又在汉王朝的干预下立元贵靡为大昆靡(王)、乌就屠为小昆靡,并由汉王朝为之分别人民、地界。自此,大、小昆靡两部彼此矛盾、争斗不息,终西汉之时,“且无宁岁”。
从乌孙王统继承的矛盾和斗争过程看,长子继承法并未得到彻底确立,使奴隶主上层统治集团之间夺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更加尖锐;其次,从斗争过程看,在乌孙社会内部,似乎还有一种贵族议事会议在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其证明就是,当翁归靡准备凭藉汉王朝的权威决定由元贵靡继承王位,而不是如最初约定的交还政权给泥靡时,“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即军须靡)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翁归靡在位时,颇多建树,乌孙国力至达鼎盛,其在乌孙的权威和影响不可轻估;这时汉王朝对乌孙的重大军事、政治决策,也完全可以控制。但“乌孙贵人”竟仍然能够“共从本约”,不顾汉王朝的反对,扶立泥靡,他们在乌孙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量是不能轻估的。原始氏族社会阶段,氏族、部落领袖通过一定的形式决定部落联盟内的一切重大事务,这种议事会具有无上权威。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们的影响一落千丈。但在刚刚步入文明不久的历史阶段,这种贵族议事会的传统力量还是十分巨大的。这时的乌孙王位的继承当然秉承着国王的意志,但“乌孙贵人”(应该就是贵族议事会的成员)却可施加强大的影响。这可以说明乌孙社会跨入文明新阶段为时并不太久,古老的氏族社会的传统还是深具影响的。
乌孙社会的政权组织是比较简单的。昆莫(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其下为大禄,即相。这是昆莫的最重要的辅佐,是昆莫以下最重要的行政首脑,相当于汉王朝的丞相,故汉语译称“相”。但从实际职能看,它还有军事权力。担任这一职位的往往是高级贵族。猎骄靡为王,长子为太子,作王储,而次子即为“大禄”,可见其地位确实非同一般。
大禄之下,有左、右大将二人。这是王国最重要的军职。乌孙受匈奴影响,以左为贵,左大将位置更重。翁归靡时,三子为左大将;而冯嫽嫁右大将为妻。左、右大将,任重权高,不同于一般。韩宣为西域都护时,因乌孙王星靡“怯弱”,建议汉王朝“可免”其乌孙王号,“更以季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廷未允。但可见左大将权位之隆重。
大将以下有侯。侯的地位、权势亦重。《汉书》中屡见“诸翕侯”、“翕侯”之称,往往也都与军事活动有关。如翁归靡攻匈奴时,就是“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驰驱直进;乌就屠图谋政变,“与诸翕侯俱去”,后终“袭杀狂王”;“大昆弥翕侯难栖杀(小昆弥)末振将”等等,都可为证。
其他还有“大都尉”、“大蓝”、“大吏”、“舍十大吏”,“骑君”、“译导”等等。其中译导,未见明确记录,但在张骞出使中亚时,乌孙曾发译导送之;虑及当时西域地区民族复杂、语音纷殊的情况,司语言翻译、导送的吏员,肯定是存在的。这些大概就是乌孙王国内主要的军、政官吏。汉朝政府曾经接受了西域都护的建议,给“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金印紫绶”,这是汉王朝政府给丞相、列侯以上高官的待遇,于此可见这几种吏员在乌孙王国内地位的尊崇。
在乌孙的律令制度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大昆弥雌栗靡时正式颁布的:“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用法律形式,保护牧草场地的贵族所有,不允许互相侵夺,使草场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使用,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这一措施曾经保证了乌孙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
乌孙社会,诸翕侯各有自己的“民众”。这受到习惯的尊重、法律的保护。这些民众,很可能就是原来各部落的自由民及附属的家内奴隶,而翕侯则是原来的部落领袖,现在的世袭贵族。乌就屠袭杀狂王发动政变时,曾“与诸翕侯俱去”。后经汉王朝政府干预,乌就屠自愿做小昆弥,而由元贵靡为大昆弥,但乌就屠却“不尽归诸翕侯民众”。这导致汉王朝的干预,派常惠率领三校士兵驻屯赤谷,并为大、小昆弥明确分划人民、地界,以排除矛盾。这件事具体反映了自诸翕侯上至昆弥均有自己的地域、人众,说明在乌孙社会中氏族、部落残留的痕迹不小。
乌孙的军事制度,实际是全民皆兵。在“十二万户”的乌孙居民中,有“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可见每户的丁壮均是胜兵。这与匈奴的制度是一样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本性也”①。可见平常生产的组织与战时军事组织是完全合一的。而组织形式,应该就是从氏族社会接受过来的氏族、部落的外壳。所以,翕侯既是原来的部落领袖,又是现在新的军事、生产的领袖,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在乌孙社会的婚姻制度上,同样可以看到浓重的氏族社会习惯。试以解忧公主为例,先嫁军须靡;军须靡死,翁归靡继王位,则转嫁军须靡之堂兄弟翁归靡;翁归靡死后,又成了军须靡匈奴妻所生子泥靡的夫人。这与匈奴实行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②是完全一样的。有人对此提出的解释是“恶种姓之失”,“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实际这是原始社会氏族外婚制的一种遗留。他氏族的女子嫁到本氏族中来,就是本氏族一群兄弟的妻子。进入阶级社会,王位必须以国王的血统为转移,妻子也随着王位的继承而被继承,可以不至因王族血统的混乱而造成对王权的任何干扰。古老传统的外壳这时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
三
乌孙,汉代是西域地区最大的王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它从匈奴的羽盟转变为和西汉王朝结盟,并很快发展到政治上归属西汉王朝统治,可说是经历了巨大的发展。这一发展变化,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历史大厦,曾发挥过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深刻认识这一变化,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矛盾、斗争中加以考察。西汉前期,汉王朝政府与匈奴王国的矛盾和冲突是中国大地上主要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产生了汉王朝对西域及乌孙王国结盟的战略抉择及一系列策略措施,导致了西域及乌孙历史进程的新方向。
乌孙,历史上与匈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当乌孙居住、活动在河西走廊,在与大月氏和匈奴的冲突中国破家亡,难兜靡死于非命,其子猎骄靡在匈奴冒顿单于的救助、扶持下成长复国,这决定了乌孙与匈奴不同于一般的密切关系。猎骄靡幼时“生弃于野,乌衔肉飞其上,狼往乳之”的神话故事,正是曲折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真实。狼,是匈奴的图腾,匈奴的象征。
猎骄靡长大成人,冒顿又“使将兵”,“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使其逐步成长为一支不可轻视的强大力量。无论猎骄靡,还是乌孙各级氏族、部落的领袖人物(也就是以后乌孙王国的各级贵族),对匈奴的依附,自然不同于一般。冒顿时期,乌孙实际是匈奴的属部,承担了经济上贡纳、政治上服从、军事上接受调度的各种强制性义务,实质上是部落奴隶。只是在冒顿死后,关系才疏远了一层。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乌孙“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①,企图摆脱匈奴的奴役和统治,尤其是乌孙西迁伊犁地区以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口增多,国力增强。对匈奴奴隶主集团苛繁的经济掠夺,对自身政治上的屈辱地位更加不满,这自然导致矛盾的进一步发展。
而正是在这样的矛盾面前,西汉王朝的使者张骞带来了西汉政府结盟抗击匈奴的建议和要求:“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拒匈奴。”这对乌孙,是既有一定吸引力,但又是不能贸然决定的重大问题。主要的困难在于:不知汉王朝实力;内部亲依匈奴、恐惧匈奴的势力不小;而且国分为三,猎骄靡一人无法专制。所以只是派人、送马回报,并未明确答应汉王朝要求。
促成猎骄靡改变态度,同意和亲、结盟的,主要是客观形势的急剧变化。虽乌孙态度暧昧,西汉王朝通使西域、断匈奴右臂的决策却在积极执行,汉使大宛、月氏者,“相属不绝”;匈奴了解乌孙曾与汉王朝通使往来后,“怒,欲击之”;再加乌孙使者到内地,“见汉人众富厚”,也增强了信心。这几个因素促使猎骄靡“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希望通过和亲结盟以保证自身政权的安全稳定。最后以马千匹为聘,汉王朝则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主,出嫁猎骄靡,为右夫人。匈奴也闻风而动,“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②。这时的猎骄靡,行动上还是持两端,希望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保持平衡。
乌孙,由这种半心半意与汉王朝结盟到全心全意结盟,以至后来政治上归属西汉王朝,接受汉王朝的统属,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汉王朝政府在对匈奴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匈奴实力不断被严重削弱。
汉武帝刘彻,在汉初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利用富厚的经济力量,对匈奴向中原地区不断的侵扰、掠夺性的战争发起了反击。这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常生产秩序和人民安定生活的保障的。匈奴则由于战争失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自然灾害频仍,军事、经济实力受到极大削弱,逐步失掉了对阴山、河套、河西走廊、西域广大水草肥美地区的控制。汉王朝在实际控制西域广大地区后,于公元前60年(汉神爵二年),正式派出了统管西域地区军政事务的西域都护。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西域地区,包括北疆乌孙,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至此正式列入汉朝版图。这无论在新疆古代历史,还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形成和发展史上都是一次关系重大的事件。设西域都护,标志匈奴对西域控制的瓦解。这一重大进展,与本始三年,汉、乌孙联军对匈奴战争取得的胜利直接有关。此前,匈奴为维护其对西域的统治,以巴里坤草原为前进基地,屯田车师(吐鲁番盆地及吉木萨尔等地),进攻乌孙,以控制、稳定北疆地区,隔断乌孙与汉朝的联系,并以车师为桥头堡,向南疆发展。乌孙王翁归靡与汉解忧公主清楚地分析了有关形势,先后多次上书汉王朝,建议组织联军反击。“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王朝在充分准备以后,“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西域一线,“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密切配合行动。这一仗获得了全胜。乌孙“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廷,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于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骆驼七十余万头”①,这一仗,使匈奴在西域地区的力量、元气大伤。史载,“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转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②。汉、乌孙联军的这一次打击,对匈奴帝国的衰败瓦解,所起作用是相当不小的。
乌孙政治上归属汉王朝统治,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这次联合军事行动到西域都护设立期间的种种情况分析,已经充分完成。我们说,自这一阶段以后,乌孙从政治上看已经是西汉王朝统属下的一个部分,有如下的实质表现。
首先,乌孙王国自国王以下各级官员,均接受汉王朝的册封,佩汉朝政府颁发的印绶,作为其权威的象征,表示其权力的合法性。如大吏、大禄、大监,汉朝政府均视为如汉之最高级吏员,赐金印紫绶;只是在发现他们不能忠于职守,如乌孙王雌栗靡被杀害时不作有力抗争,即收回金印紫绶,另颁铜印墨绶,作为惩处。铜印墨绶,在汉王朝,只是600石以上吏员的级别标志。不仅是这种配戴印绶,更重要的,乌孙王的王位继承、废立,亦均要得到汉王朝的认可,翁归靡希望变动旧议,改立元贵靡为嗣,要报汉王朝;乌就屠杀泥靡,自立为王,西域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只得放弃了大昆弥的地位;西域都护韩宣认为乌孙王“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王朝不批准,就必须维持原状;乌孙小昆弥末振将使人刺杀大昆弥雌栗靡,汉王朝即始终以诛杀末振将为己任,对杀死末振将的难栖升官晋爵,封为“坚守都尉”。凡此种种,均堪足以说明汉王朝对乌孙王国内重大政治事项均有直接处理的权力及责任。
其次,西汉王朝对乌孙军队有征调、节制指挥权。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汉、乌孙联军共讨匈奴,汉政府即“遣校尉使持节护乌孙兵”,实际是掌握了最主要的对乌孙部队的控制、指挥权。汉地节元年(前69年),常惠自乌孙经龟兹返内地,在霍光支持下,自行调发龟兹以东各小国合兵2万余人,乌孙兵7000人,三面围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罪①。类此,均是较大的、有历史影响的军事行动,故史籍有所记载,其他规模较小的军事征发肯定是不会少的,这种军事指挥权是国家权力的主要表现之一。
对危及乌孙王国政权稳定、安全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有处理权力。乌就屠与元贵靡兄弟失和,争位夺权。经汉王朝裁定,元贵靡为大昆靡、乌就屠为小昆靡。但乌就屠仍然“不尽归诸翕侯民众”。为稳定乌孙内部的局势,“汉复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6万余,小昆弥户4万余”②,明确分划清楚地界,分划清楚户口、民众的归属,并派驻部队屯田监守,保证有关决定的实施。汉王朝的统治权力在这里是明确无误的。
在乌孙归属于汉王朝的统治,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犁河流域广大土地进入祖国的版图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进程中,汉王朝政府实行的和亲政策,细君、解忧,其中尤其是解忧公主在乌孙王国的活动,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从西汉王朝与乌孙王国和亲的实践看,实际是一种政治结盟的方式。在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下,这种和亲可以实现很好的政治效果。因为国家政权是一种宗法性的、世袭的王权统治,与国王联姻,利用女主对国王及王室的影响,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会起到特殊的作用。西汉王朝与乌孙和亲,就怀有这样的愿望。这从细君嫁给年迈体衰的猎骄靡,而猎骄靡随后又要求细君再嫁其长孙军须靡时,细君受汉朝传统、礼教的束缚,不从,请示汉王朝。刘彻的决定却是:“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一语道破了这种政治婚姻的实质。细君秉承汉王朝旨意,不仅再嫁了军须靡;而且根据自身使命,广泛进行了活动:“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但终因不多几年即逝,未见出显著成效。而解忧公主,先后在乌孙生活了50年左右,在乌孙的政治生活中就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解忧在乌孙曾先后嫁军须靡、翁归靡、泥靡。她与翁归靡共同生活时间颇长,“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为莎车王。次男大乐,为右大将。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翕侯妻”。这些子女,在乌孙、龟兹、莎车,都曾居于显要地位。
翁归靡,在乌孙历史上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名王。他在位时,王国统一,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西汉后期雌栗靡取得显著政绩,史家即以之和翁归靡这段统治时期相比称,可见不同于一般。翁归靡的这一建树,得到过解忧的有力佐助和支持,翁归靡在汉、乌孙联军重创匈奴这一著名战役中的贡献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为促成这一战役实现,解忧曾多次上书汉廷,力陈利害,终于达到了预想的结果。
综观解忧在乌孙的活动,实际上是西汉王朝派驻乌孙的全权代表。她洞察、分析乌孙的各种情况,提出关键性的建议或运用自己的地位、影响便宜行事。公元前71年扭转了西域地区政治形势,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的重大战役,解忧起过十分显著的作用;狂王泥靡“暴恶失众”,“为乌孙所患苦”,她一手策划、指挥了剪除狂王的宫廷政变。这次政变,因行事者粗疏,未得成功。但于此可见解忧在乌孙的影响、谋略。她不仅运用自身力量影响乌孙政局,而且以乌孙为基地,派心腹“侍者冯嫽”,“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得到“敬信”。冯嫽“能史书、习事”,是一个熟悉西域情况、有相当水平的能干女官,被西域各国尊之为“冯夫人”。她的丈夫是乌孙右大将,她曾运用这一关系,平息、调处了乌就屠发动的又一变乱。原来,在狂王泥靡死后,未得汉王朝同意,乌就屠即擅自继位为王。为此,汉王朝调动了军队,准备了粮食,准备进行征讨。最后,在冯夫人为首的汉朝命使的调解下,乌就屠同意放弃昆莫称号,“为小昆弥”,而由汉王朝册“立元贵靡为大昆弥”。王国一分为二,“使破羌将军不出塞”,一场箭在弦上的战争得以避免。冯夫人在乌孙享有威望,她对乌孙也怀有感情。在解忧公主年老回到中原后,乌孙大昆弥星靡怯弱,她不惮以老年之身,主动向汉王朝要求,愿“使乌孙镇抚星靡”,并得以如愿成行。
从解忧、冯嫽的和亲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其作用是不能轻估的,当然,和亲所以能发挥这样的影响,还在于当时总的斗争形势。在汉与匈奴、汉与乌孙、匈奴与乌孙这几组具体矛盾中:匈奴势力日蹙;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日强;乌孙对匈奴的奴隶制掠夺政策反抗日烈,而自身在汉朝和亲政策实践中也感受到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等等。没有这些基本的条件,无论解忧、冯嫽个人具有怎样超群出众的能力,也是无补于事的。
汉与乌孙的和亲,对乌孙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细君初嫁乌孙时,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其盛”,“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足见,这种动辄数百人的和亲使团,是包含有各方面的人才的;否则,“自治宫室”,哪里得有可能?!解忧在乌孙生活有50年左右,联系更加密切。解忧的女儿弟史至“京师学鼓琴”,弟史丈夫龟兹王绛宾企图在龟兹推行汉王朝的制度;经过不长的时间,乌孙王国的冶金技术得到很大提高,缩短了和中原地区冶炼技术间的差距;在长安,可以学习乌孙的语言……凡此种种,都可以见出彼此关系的深入、密切。这意味着彼此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丰富,在缔造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历史中,它曾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是不应该忽视的。
附注
①《昭苏县土墩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62(7~8);《文物考古三十年》;《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
①《汉书·西域传》:公元前71年,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一次即掳获马、牛、羊、骆驼、驴等70余万头。
①③《汉书·西域传·乌孙传》。
②《历代各族传记会编》,第1编,430页。
①《汉书·西域传·乌孙传》。
②《文物考古三十年》,图版十五(4),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③《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鐴土》,载《文物》,1961(1);《秦始皇陵附近新发现文物》,载《文物》,1973(5)。
④该文物陈列于敦煌文化馆展厅中。
⑤阿基耶夫:《1954年伊犁考古考察团工作报告》,见《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著作集》,第1卷,阿拉木图:1956;阿基耶夫、库沙也夫:《伊犁河谷塞克与乌孙的古代文化》,阿拉木图:1963。
①《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①《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84页,图九。
②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战国秦汉考古》(上),33页,1973(6)。
③古墓沟毛织物,时代在去今3800年前。哈密毛织物早到距今3000年前,有平纹、斜纹织物,染色水平亦高。
①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载《疆疆大学学报》,1980(2)
②马长寿:《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载《历史研究》,1954(5)。
①《汉书·西域传·乌孙传》。
①《昭苏县土墩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62(7~8);《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
① 《汉书·匈奴传》上。
② 《史记·匈奴列传》。
①《史记·大宛列传》。
②引文均见《汉书·西域传·乌孙传》
①《汉书·西城传·乌孙传》
②《汉书·匈奴传》上。
①《汉书·常惠传》。
②《汉书·西域传·乌孙传》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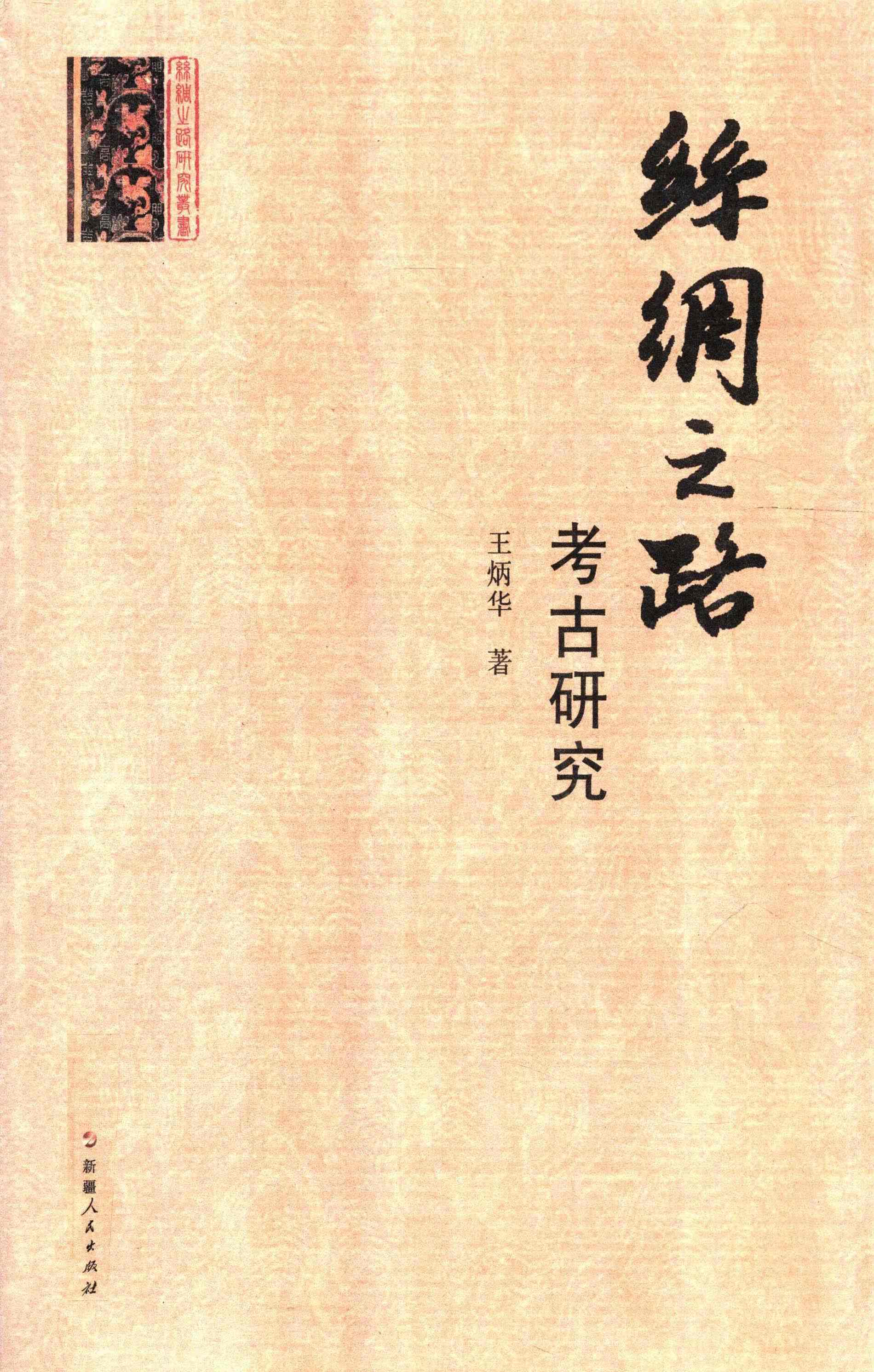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