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83 |
| 颗粒名称: | 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 |
| 分类号: | K878 |
| 页数: | 13 |
| 页码: | 154-16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 近年来在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发现一处古铜矿遗址,并陆续出土了一批铜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对此遗址遗物的时代、族属、考古及历史价值,尚待深入研究。 |
| 关键词: | 古代新疆 伊犁河流域 考古资料 |
内容
“塞人”之“塞,”古音读为“Sak”,同于古代波斯文献中的”萨迦”。在古代中亚历史舞台上,他们曾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新疆古代历史上,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予以认真注意。但在新疆历史研究领域中,受到文献资料的局限,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有关古代塞人在新疆地区的活动,汉文史籍始见于《汉书》,但文字十分简略。近年,新疆考古工作中,一些发现明显涉及塞人的历史和文化,但并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和注意。有鉴于此,这里试对古代新疆塞人历史资料加以搜集,并稍予分析,以供国内外关心这一课题的同仁们进一步研究。
一、《汉书》中有关塞人的历史记录
《汉书》中有关塞人资料,主要见于《西域传》、《张骞李广利传》。试举其例:
“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汉书·西域传·乌孙》)。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汉书·西域传·休循国》)。
“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汉书·西域传·捐毒国》)。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四君大夏。自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汉书·西域传·罽宾国》)。
“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根据《汉书》中有关塞人的记录,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主要的概念:一是塞人在新疆活动的主要地域,就是汉代乌孙、休循、捐毒等国居住活动的地区。汉代乌孙在新疆地区的活动地域,据上引文献并结合乌孙遗迹分布状况,主要在“天山到伊犁河之间”“广阔的草原地带”,“如昭苏、特克斯、新源、巩留、尼勒克等县”,就是乌孙活动的中心地区①。休循,其活动地域大概在帕米尔山中②。捐毒,活动地域大概在塔什库尔干地区③。总体来看,汉代以前,塞人在新疆地区的主要活动地域应在伊犁河流域并及于天山和更南的阿赖岭、东帕米尔等地。二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大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前④,这里本为塞人领地。这时期的塞人,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政权,其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塞王”。至于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生活、宗教、文化艺术及与周围地区的关系等,从这些简单文字记录,难能得其要领。
《汉书》以后,汉文史籍中基本不见有关塞人的记录。但有一条资料,需稍加说明。
唐道宣之《广弘明集》,引荀济上梁武帝肖衍之《论佛教表》,称“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乃讹转以塞种为释种,其实一也”⑤。荀济此文,谓引自《汉书·西域传》,但今本《汉书》中,并无所见。
将“塞种”与“释种”互相比附,还见于(唐)颜师古对《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塞种”一词的注解:“塞音先得反。西域国名。即佛经所谓释种者。塞、释音相近,本一姓耳。”⑥
荀济此文,研究新疆塞人历史者颇多称引。但细作推敲,颇多疑点。谓资料引自《汉书》,但今本《汉书》中并无此文。在南北朝崇佛的潮流中,荀济是肖梁时期抨击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而利用所谓夷夏之别进行反佛宣传,则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现象。在《论佛教表》中,荀济将“释”(佛教)与“塞”等同,则“释”为“夷狄,”使用的就是这个武器。因此,关于“塞”人的这一记录,真实性究竟如何,是需要考虑的。曾有学者揭明过这一问题⑦,此处不赘。
二、有关塞人的考古资料
要将新疆古代塞人的历史研究清楚,关键在于考古工作。目前新疆地区所见考古资料,不少涉及了塞人的历史和文化。一些重要发现,也确实已经给目前的塞人历史研究投射了一束光明。
1976~1978年间,在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天山阿拉沟东口,曾发掘了四座竖穴木椁墓。时代为战国到西汉。根据墓中出土文物特征,笔者曾在执笔的报告中①结论为塞人文化遗存。
从已刊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有关塞人墓葬的基本概念。
墓葬地表见块石封堆,圆形,直径5米多,高不足1米。封堆周围见矩形石垣,东西向,长15米、宽10米左右。墓葬彼此成东北、西南向链线排列。
墓室,均东西向,长方形竖穴,规模较大。其一,长3米、宽2米、深6米多。最大的一座,长6.56米、宽4.22米、深7.1米。墓室内积卵石、巨型块石(较大者长、宽、高均在1米以上)。积石下为木椁,木椁以直径10~24厘米的松木纵横叠置,紧贴墓壁,构成框架,高近1米。尸体置木椁内。葬一人或两人。骨骼粗大。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中,葬青年女性一人,头骨上见一锐利钻孔,孔径0.5厘米。
随葬文物位于墓室西端壁龛、尸体周围。见多量金、银、铜、铁、陶、木、丝、漆器、牛羊骨。
出土文物中,金器量多,纯度很高,且富有特点。大多当为带饰、衣饰。计虎纹圆金牌八块(块径6厘米,重20克上下),图案为老虎形象:头微昂、前腿跃起、躯体卷曲成半圆。或左向,或右向。对虎纹金箔带四件(件长26厘米,重27.75克),图案为相向踞伏的对虎。另外,还有
作奔跃咬啮状的狮形金箔一件。他如兽面纹金饰片,六角形花金饰片,菱形花金饰片,圆形、柳叶形、矩形、树叶形、双十字形、螺旋形金饰片等,品种不少,数量很多,当为衣饰无疑。此外,还见到小金钉、金环等,形式多样。这批墓葬经过盗扰,劫余金器尚且如此,墓葬主人崇尚黄金而且富有黄金的特点,是表现得很清楚的。
银牌,共见七块。有方形、矩形、盾形之别。均模压兽面纹图案,似猫科类野兽形象。这种金属饰牌,成分极为不纯。经光谱分析,其中含银量仅超过10%;其他是铅、铜、铝、钙、钠、矽、镁、铋等。色灰白,质脆易碎。冶炼水平是不高的。
方座承兽铜盘,这也是一件很有特点的器物。器身通高32厘米。下部为喇叭形器座,上部为边长30厘米的方盘。盘中并立二兽,似狮形,鬛毛卷曲成穿孔,似翼。其制作方法是分别铸出兽、盘、器座等,最后焊联成一体。
铁器,有小铁刀、铁镞。铁刀长11.5厘米,与盛羊骨木盘放置一起。镞为三棱形,已锈结成块。
陶器,均手制。细泥红陶,打磨光洁,外表敷酱红色陶衣。计有带流筒形壶、杯、平底盆、三足盆等。漆器、木器,均朽蚀严重。丝质绫纹罗亦朽,但痕迹清晰。此外,还见到珍珠、玛瑙类饰物。
1983年夏,在伊犁新源县境,出土了一批铜器。出土地点在巩乃斯河南岸,新源县东北20多公里处。当地原有一列南北向七墩墓,封土墩在农业生产中已经推平。这次在距地表深1.5米处,见铜器、陶片、人骨、兽骨。报道称,铜器中包括“青铜武士俑一尊,高42厘米”,“青铜大釜一件,重21公斤。青铜铃一件,还有残损的青铜高脚油灯,青铜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和双飞兽相对圆环各一件”。“武士俑的造型端庄、英俊,单跪姿势,头戴高弯勾圆帽,双手好像握着剑或刀……上身裸露,腰间围系着遮身物,赤脚、高鼻梁、大鬓角”。报道认为这是一组“乌孙的遗物”①。
有关文物出土后,承郭文清同志赐函介绍情况,并惠赐文物照片一套。据已刊照片并参照郭文清同志的介绍,得到了更明确、清楚的概念。所称“青铜高脚油灯”,系与阿拉沟出土承兽铜盘为同一类型物。器座已毁,但其上所承方盘仍然完好。盘内两角各蹲一兽,似熊,憨态可掬,造型是很生动的。
“青铜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对虎相向,面、唇相接触,体回曲成圆形。
“双飞兽相对圆环,”造型风格同上。二兽回曲相向,鬣毛上卷成孔,作奔跃状。
铜釜,三兽足,平口深鼓腹。上腹部附四耳,二平二直。腹部弦纹三道。
跪姿武士,头戴高帽,阔檐尖顶,尖顶前弯如钩。
这一组文物,因系推土所得,其埋藏情况、共存关系等,已难究明,是很大的损失。
与巩乃斯河谷出土的这批文物风格类同,1966~1976年期间,新源县城附近亦曾出土一批珍贵铜器,介绍的同志称:同样有承兽铜盘、三足铜釜等物,承兽铜盘上环列异兽,均不幸散失。
在伊犁昭苏地区,近年出土过多件铜盘,矩形,四兽足,也是塞人文化中的典型文物。
还有一批十分重要的资料,是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城附近奴拉赛山上所见古代铜矿遗址。这是一处品位很高的晶质辉铜矿。古代采矿洞口已倒塌,泥石淤塞,但仍可见出十余处。一条“采矿暗洞,洞长30米,最宽3米。洞室大如房舍,局部有横木支护”。“洞内遗留大量石器。由坚硬的河床卵石加工而成。外形大都为一面扁平三面凸起的锥体”一端尖锐,一端钝圆,中腰有凹槽,重3~10多斤。距矿坑不远处的山沟内,为炼铜,遗址所在。炼铜炉砟厚1米,炉砟灰内见木炭、铜锭。铜锭共见5块,外形似碗状,一面圆凸,一面平。锭块重者十余公斤,轻者每块3~5公斤。铜锭块质较纯,含铜量60%以上,性脆,断面银灰色,磨光面银自反光,可鉴人影”①。关于这处铜矿的开采年代,曾经取古矿洞内支架坑木进行碳14测定,经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2650±170年及2440±75年②,相当于春秋早期至战国阶段。
三、有关考古资料辨证、分析
上述三批考古资料,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原简报已说明为塞人文化。巩乃斯河南岸一组青铜器原报道认为是“乌孙的遗物”。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开掘者应属何民族,尚未见涉及这一问题。
结合各方面情况分析,有充分根据可以说明:上述考古资料,应均属塞人文化遗存,是研究新疆古代塞人历史的珍贵资料,应作塞族资料处理。
尼勒克县奴拉赛古铜矿遗址,时代在春秋至战国早期,所在地点是战国时期统治伊犁河流域的塞人王国辖境,开采、冶炼这一铜矿的主人,自然非塞人莫属。说战国时期的尼勒克,在塞人统治之下,这从《汉书》所记“乌孙国..本塞地也”,可以确知。因为据文献、考古资料,已经可以肯定:尼勒克县,在乌孙王国时期,是属于其统治境域中心地带的③。乌孙以前的战国时期,地属塞人,自可明见。
另外两批资料,新源县境巩乃斯河南岸出土青铜器,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出土文物,其风格是一致的。但终非发掘所得,一些具体情况已难明究竟,故着重对阿拉沟竖穴木椁墓资料予以剖析。
阿拉沟木椁墓简报提出了有关墓葬属于塞人遗存的正确结论,但未充分展开。
从葬俗上看,竖穴木椁、封丘成链向排列,在中亚谢米列契地区所见塞种墓葬,同样具有这种特征①。头骨钻孔,这一具有特点的葬俗,在中亚阿尔泰地区所见塞人墓葬中,也有相同的实例②。
从出土文物分析,阿拉沟所见承兽铜盘,方盘中伫立二兽,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所见方盘,对角蹲踞二兽,这类风格的文物,在中亚地区的塞种文化遗址内,是出土不少的。中亚学者称之为“祭祀台”,认为与袄教崇拜有关,是塞人文化的典型文物之图一③。阿拉沟出土不少的虎纹圆金牌,与中亚哈萨克斯坦麦阿密地区出土的塞人文物,卷曲的“豹”形象的圆金牌相同④,从金牌图案造型到作用,实际也是一样的。猫科类猛兽的图案形象,被认为是萨迦—斯基泰装饰艺术中重要的图案主题之一⑤。
这些因素,从不同角度帮助揭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肯定为塞种文化遗存,这是正确的。
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这批铜器,原报告称之为“乌孙文物”,值得斟酌,因为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文化面貌,经过20世纪60~70年代持续二十多年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对乌孙墓葬中出土文物的基本风格、总体特征,人们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⑥。以之对比新源县这批青铜器,基本风格是不同的。因此,视其为乌孙文化系统的文物,缺少充分的根据,这是一。从另外一方面看,如前所述,这批铜器中的承兽铜盘(原报道称为“高脚铜灯”)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所见承兽铜盘,风格一致。这种承兽铜盘,与兽足铜釜,往往共出,被视为塞人文化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在中亚谢米列契、天山地区,常有所见⑦。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这次见到这一文物组合,铜釜的造型、风格,与苏联谢米列契所见,几乎也是完全一样。这就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文化现象。其他如“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双飞兽相对圆环”,这里的“对虎、翼兽”风格、整个圆环的造型,同样是比较典型的塞人艺术特点。在伊朗出土的萨迦文物中,可以找到相同的实例⑧。
四、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塞人历史
这几批考古资料,揭示了多方面的塞人历史内容。
(一)活动地域
这些资料,不仅印证了《汉书》中所记述的,汉代乌孙居地,就是战国时期塞人的故土,伊犁河流域自然条件优良,同样曾是塞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而且告诉我们:沿巩乃斯河谷上行,进入天山,直到阿拉沟东口(包括于尔都斯草原),这片优良的夏牧场地区,十分可能都曾经是古代塞人活动的基地。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铜器与阿拉沟东口竖穴木椁墓中的多量金器,都不是一般塞人平民所能享有。很有可能,这片地区内,曾是伊犁地区塞人王国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
(二)社会经济活动
这是文献记录中缺略、考古资料较为丰富的一个方面。
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发现了小铁刀、三棱形铁镞。战国时期,塞人已经用铁,尤其是使用了消耗量很大的铁镞,这对我们估计当时塞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铁矿的冶炼、铁器的加工,都远较铜金属要困难。铁被用于制作工具、兵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使不少新的生产领域可以得到开发。
同样在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见到了随葬的羊、牛、马骨。随葬木盆中,羊骨与小铁刀并陈,形象地说明了墓主人生前生活中肉食具有重要地位。这可以说明:畜牧业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体。《汉书》称塞人经济为“随畜逐水草”,可谓抓住了要点。
木器制作、毛纺织、制陶等,是主要的家庭手工业。木器主要见到作为盛器的盘,长方形,利用整木加工成型,内外修刮光洁。陶器品种较多,如带流筒形杯、盆、钵、小杯等,均日常用器,较之木器似占更重要地位。陶器手制,形制规正。陶土很细,外施一层酱红色陶衣。毛织物,只见到严重朽烂的小片。此外,阿拉沟木椁墓内还见过草席印痕。草编织物,当也是家庭手工业产品之一。
在谈及战国时期塞人的社会生产时,对当时的矿冶、金属加工业,应特别注意。从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开采、冶炼资料,可以肯定:当时采矿、冶炼生产必然已经越出家庭手工业的范畴,成了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在铜器、金器制作上,应该也是同样的情况。不论是铜矿开采还是冶炼,生产工艺比较复杂,专业性比较强,生产规模较大,需要的劳动力也比较多。每个生产环节,如找矿、坑道掘进、支架防护、采矿、排水通风、提取运输矿石、冶炼、浇铸等,都要求生产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专门技术,必须比较固定或相对稳定地从事这一工作。从奴拉赛所见古代铜矿冶炼遗址看,矿石开采与冶炼集中在一处,这也符合经济的原则,但这更加需要每个生产环节的密切协作,需要比较严密的组织与统一的指挥。这些生产运营本身的要求,使这类矿冶生产必然要独立于畜牧业或农业生产以外,越出家庭手工业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金器、铜器的制作,同样是这个道理,相当复杂的工艺过程,往往都不是附属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所能承担的。
在分析奴拉赛矿冶遗址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矿坑内外,发现相当多数量的卵石制器。它们中部凹腰,端头见到为便于捆缚而加工的凹痕。这类石器,在湖北大冶县铜绿山春秋、战国到汉代的矿冶遗址内,也曾经出土过。被认为是一种提升工具——平衡石锤①。铜绿山矿冶遗址时代早,沿用时间长。这里的石锤与奴拉赛矿冶遗址所出石锤,形制相同,作用应该相当。这当然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古代中原地区矿冶技术对新疆地区的具体影响。
奴拉赛矿冶遗址,对我们认识塞人王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是十分重要的资料。我们目前的分析只是根据已经报道的十分有限的考古调查资料,随发掘工作的展开,对当时的采掘技术、冶炼工艺、生产规模等许多方面的专门问题,必然会提供更多具体、准确的资料,为古代塞人历史研究揭开新页。
(三)崇尚黄金并且积累了较多的黄金财富,是战国时期塞人社会生活中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特点
阿拉沟4座竖穴木椁墓,无墓不见金器。以第30号墓为例:重20克左右的虎纹圆金牌8块(虎头左向的5块,右向3块,不对称,实际当不止此数),重27克多对虎纹金箔带4件,狮形金箔1件,其他有菱形花金饰片3件,较大圆形金泡饰片33片,较小的金泡仅女尸头部傍近,即达数十片,柳叶形金饰片近百片,螺旋形金串饰片33件,其他还有双十字形、树叶形、矩形饰片及金丝等物②。大小合计,数达200件以上。而这些墓葬,都曾经过盗扰,所见金器,不过是盗墓后的劫余。从发掘现场及残余金饰形制分析,这类饰片,主要都是用为冠、衣、带、鞋类服装缀饰,当日情状,肯定是十分辉煌的。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曾经说到塞人王族享用着上天赐予的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有金盏,死后要以黄金制品随葬③,颇可以与我们的考古资料互相印证。
相当富厚、奢侈的随葬品,相当规模的墓室(同样以30号墓为例:竖穴墓室土方量即达一百多立方米,矩形木椁高近1米,厚达2米的填石大小整齐,填沙纯净),也说明这类墓葬的主人,不是一般社会成员。《汉书》记载塞人有“王”,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考古资料与此可以互相证明。
(四)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及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所见塞人遗物,可以窥见其具有特点的艺术风格
各种饰牌、金饰片、铜器,除极少数为植物花纹图案(柳叶形金饰片、六角形金花饰片)外,占统治地位的是各种野兽纹图案,有虎、狮、带角兽、熊等,猫科类猛兽形象具有重要地位。野兽形象基本是写实的,对各种野兽的特点掌握得很准确,造型比例适当,形象很生动。伊犁地区的这支塞人在图案艺术上的这些具体特点,与中亚西部或南亚地区塞人有什么差别,体现了什么具体的历史内核,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这批文物中,图案设计十分讲究对称、平衡,这也是不应忽略的一个方面。
(五)论及伊犁地区这支塞人的历史文化,从文物中体现出来的他们与中亚广大地区(如谢米列契地区)塞人的密切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有关这支塞人和其他地区的关系,如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出土文物也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出土的漆器、丝织物(菱纹链式罗),奴拉赛铜矿出土“或说为采掘工具”的平衡石器。
“平衡石器”(或说为采掘工具)的造型与湖北大冶铜绿山所见石器造型一样,这些,都说明肯定存在相当的经济、文化关系。这是过去文献记录中不见涉及的一个方面,它们填补了文献记录的空白,值得重视。
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铜人,很值得推敲。铜人单腿下跪,半裸体,社会身份似乎不高。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塞人王国属下人民的体形特点。从造型看,其体格十分健壮,双臂肌腱鼓凸,强实有力,粗眉大眼,鼻梁较高,头戴十分显目的高冠,尖顶向前极度弯曲,下身着短裙。
在波斯文献中有萨迦·提格拉豪达(SakaTigrakhanda),意为戴尖帽子的萨迦人(在波斯碑刻中也见到过一种尖帽萨迦人形象①,但与铜人的尖帽形象不尽相同)。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提到“属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高又硬,顶头的一方是尖的”②。联系这一铜人形象,对塞人尖帽特征,可得到一点新的概念。
五、另外两批有关塞人的资料
新疆地区,还有另外两批考古资料,可能也与塞人有关。
其一,1966~1967年,新疆考古研究所陈戈、吕恩国、周金铃等在帕米尔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北约4公里,塔什库尔干河谷西岸第二台地上的香巴拜,曾经发掘过40座墓葬①。
据已刊报告,40座墓葬中,有火葬墓19座、土葬墓21座。除地表堆石或围以石垣,墓室作长圆形或不规则圆形为两类墓葬同时具备的特征外,在其他更主要的一些方面:如墓口盖木,有无葬具,埋葬方式(火葬或土葬),有无殉物或殉葬文物种类、组合等,都明显具有不同的特点。
19座“火葬墓中,除6座出土一件铜耳环和几块碎陶片、残铁块、鸟骨外,余均无随葬品”。
21座土葬墓,随殉了陶器、铜器、铁器、金器、木器及石、骨、玛瑙珠饰等。“每座墓的随葬品不多,除个别的殉人墓和二次葬墓有超过10件以上者外,大部分墓的随葬品只有几件。随葬品中,以装饰品最多,生活用具次之,生产工具最少”。
陶器,陶胎均夹粗沙,手制,烧成温度较低,陶色斑驳不均,基本为素面,少数饰凸弦纹或指甲纹,制陶工艺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陶器种类有釜、罐、碗、钵、杯、纺轮。主要为实用炊器,器表仍附有烟煤。其他为盛器及纺织工具。
铜器,主要为各式装饰品,少数为工具、武器。包括铜镞、各种片饰、镯、耳环、指环、铜管等。其中羊角形饰片,为帕米尔山区常见大角羊头形图案,线条简单,形象真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铁器,很少。除一件环首小刀及镯、指环外,其他小件铁器均因锈蚀严重,难辨其形制。
金器,为一梨形薄金片做成的饰牌。
其他为毛毡、钻木取火器、各种串珠及羊骨、鸟骨等。
两座墓葬中发现殉人。
墓葬时代,根据3座墓内盖木标本的碳14测定结论,结合有关考古文化资料,结论为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左右,属“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经济生活,适应帕米尔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以畜牧和狩猎为主,没有农业。
关于墓葬主人的族属,报告没有作出明确、肯定的结论。一方面说,根据土葬、火葬同时并存,认为“这些墓葬可能与羌族有关”。但同时又提出:(1)根据对墓葬中一个保存稍好的头骨的鉴定,“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2)“在塔什库尔干西边的帕米尔河和阿克苏河流域,过去曾发掘过一些墓葬。这些墓葬的形制、结构和随葬陶器与这批墓葬基本一样”。中亚考古学界认为是“塞克族的遗迹”。所以“这批墓葬……有可能也与塞克族有关”。
在帕米尔地区,发掘工作做得很少,在目前十分有限的资料下,对墓葬主人的族属要作出明确的结论,本身确存在一定困难。但有几个因素,却可以稍作进一步的分析:一是这批土葬墓的主人,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与作为蒙古人种的羌族不能统一;二是邻近的中亚地区,对同类墓葬曾进行过相当工作,研究结论,有关墓葬为塞人遗存①;三是据有关文献(包括前引《汉书》资料),帕米尔地区在战国时期,确曾为塞人活动地域。因此,可以初步肯定,有关土葬墓属古代塞人遗存,是比较合理的。
同一地点出土的火葬墓,显示了相当多的不同特点,把这类墓葬作为另一种考古文化考虑,是比较合理的。它们是否可能与曾在葱岭地区活动过的氐、羌族有关,则确是一个可以分析的问题。从河西地区所见氐、羌资料看,火葬是其基本特点之一。但目前仍是资料太少,结论只能留待以后进一步的工作来做了。
其二,在罗布淖尔地区,新中国成立前曾发掘过一种土著人墓葬。墓室为浅埋的沙穴,葬具为船形木棺或一般木棺,其上盖板,铺覆皮张,内葬一人。因环境干燥,不少成为干尸,随身衣物保存完好。其一般情况是:头戴尖顶毡帽,帽上或插翎羽。裸体,包覆毛毯。足蹬皮鞋。随葬木器,或有弓箭。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之头下胸前,均附一小包麻黄细枝,无一例外。这种古墓,我国学者黄文弼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学者贝格曼,以及斯坦因等,在罗布荒原上均曾有过发现②。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考古所在孔雀河下游也曾发掘过这么一处墓地③。
对这类墓葬主人的族属问题,斯坦因、黄文弼曾有过分析。
斯坦因的观点是:这些人的特点“很近于阿尔卑斯种型”,并认为据掌握的人类学测量资料,“现在塔里木盆地人民的种族组织,还以此为最普通的因素”④。
黄文弼根据出土古尸的形象、服饰,尤其是死者头戴尖状毡帽之特征,认为同于塞人之习俗,“故余疑楼兰土人与塞种人不无关系”⑤。而以麻黄细枝入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习俗。据称,古印度伊兰人有一种信念,认为这种麻黄,可以产生一种“浩玛”或“所玛”(Haoma或Soma),是伊兰人祭祀中的重要物品⑥。若然,则可透见罗布荒原上的这一土著习俗,与古代伊兰人存在密切的关系。
从目前新疆地区所见这三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在论定或初步结论与塞人有关的这三组资料中,伊犁河流域的塞人文化,可能与塞人有关的帕米尔山区香巴拜墓地及罗布荒原上戴尖帽的土著人文化,它们彼此之间明显具有相当不同的文化特点,差别很大。但是,与古代波斯碑刻及古希腊文献提供的有关塞人的概念,却可以互相呼应。
古代波斯的楔形文字刻石,常提及萨迦人。见到的称呼有提格拉豪达·萨迦、豪玛瓦尔格·萨迦、提艾伊·塔拉·达拉伊雅·萨迦,分为三个部分,各有不同地域。提格拉豪达·萨迦,意为戴尖帽子的萨迦人,活动地域在黑海以东,锡尔河东南,包括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南部,帕米尔、阿赖岭以北,塔什干、天山以至巴尔喀什湖以南,楚河、塔拉斯河流域;豪玛瓦尔格·萨迦,意为带着所崇拜的植物叶子的萨迦人,活动地域在费尔干纳盆地、帕米尔及阿赖岭等地;提艾伊·塔拉·达拉伊雅·萨迦,意为海那边的萨迦人,活动地域当在阿姆河以西,黑海、咸海周围①。从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这部巨著中,也可以看到,在中亚大地存在许多不同的萨迦部落。在希罗多德笔下,黑海、黑海以北至锡尔河流域的广大游牧人,都与萨迦人有关。他们或被称为斯奇提亚人(亦译西徐亚人、斯基泰人),或称萨尔马希安人,或称马萨该达伊人,或称萨迦人。萨尔马希安人的语言“是斯希提亚语”。
而“乌萨该达伊人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族..有一些人说他们是斯奇提亚人的一个民族”。“属于斯奇提亚人的萨卡依人(即萨迦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萨卡依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奇提亚人都称为萨卡依人的”②。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在希罗多德当时(前5世纪),对中亚广大地区以至欧洲一些地方的所谓萨迦人,概念还不是十分具体、精确的。这些不同的萨迦人集团,彼此也存在不同特点。我们今天沿用这个概念,会遇到考古文化上呈现出来的不同面貌,当然就不奇怪了,而且还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事。
根据波斯碑刻及古希腊文献,联系我们新疆地区上述所见塞人资料,有几个具体问题,可以着重说明一下:
一是斯特拉波(Strabo)曾经提到,在锡尔河东北,曾有一支塞人,称为萨拉可伊人(Sacaraucae),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这颇可以与我国《汉书》所述伊犁地区塞人相当③。从西方古典作家的记录与我国古文献记录,结合现实考古资料研究,三者似可统一。
二是所谓“带着所崇拜的植物叶子”的萨迦人,他们这一特殊的习俗与罗布荒原上头戴尖帽的土著人习俗,完全一致。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的雷同。而很可能是古代罗布荒原上曾经活动过一支豪玛瓦尔格·萨迦人的生动说明。他们的阿尔卑斯型人种特征,头戴尖顶毡帽的习惯,也都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汉代以后,汉文史籍中少见塞人资料。但在新疆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存在着塞人的活动,有着塞人的影响。乌孙徙居伊犁河流域后,有相当数量的塞人逐渐融合到了乌孙民族之中,所以,《汉书》说“乌孙民有塞种”,在考古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彼此存在过的影响。
塞人的语言,已经确认是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支。帕米尔地区,曾是古代塞人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帕米尔广大地区现在的主要居民,仍操东伊朗语。我国境内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塔吉克族,其语言也是属于东伊朗语支的。其间的历史关系,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和田、巴楚等地发现过不少古于田文书,时在汉代以后,约属公元6~10世纪。据研究,古于阗文字“原出印度波罗米字芨多正体,是于阗地区塞族居民使用的文字”,它所记录的语言“今称于阗语或于阗塞克语”。“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于阗曾是塞族住地,与印度境内的塞族为同支近亲,甚至与远在中亚北部的斯基泰人也有亲属关系,所以贝利(英)也称于阗语为印度—斯基泰语或径称塞克语”①。贝利教授还曾明确提出: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有一支萨迦部落来到于阗定居下来,并形成他们的统治阶级。瞿萨旦那,就是塞人在和田地区曾建立的王国②。
这些例子,多少可以看到古代塞人在新疆地区历史生活中的深重影响。
有关古代塞人在新疆地区的活动,汉文史籍始见于《汉书》,但文字十分简略。近年,新疆考古工作中,一些发现明显涉及塞人的历史和文化,但并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和注意。有鉴于此,这里试对古代新疆塞人历史资料加以搜集,并稍予分析,以供国内外关心这一课题的同仁们进一步研究。
一、《汉书》中有关塞人的历史记录
《汉书》中有关塞人资料,主要见于《西域传》、《张骞李广利传》。试举其例:
“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汉书·西域传·乌孙》)。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汉书·西域传·休循国》)。
“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汉书·西域传·捐毒国》)。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四君大夏。自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汉书·西域传·罽宾国》)。
“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根据《汉书》中有关塞人的记录,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主要的概念:一是塞人在新疆活动的主要地域,就是汉代乌孙、休循、捐毒等国居住活动的地区。汉代乌孙在新疆地区的活动地域,据上引文献并结合乌孙遗迹分布状况,主要在“天山到伊犁河之间”“广阔的草原地带”,“如昭苏、特克斯、新源、巩留、尼勒克等县”,就是乌孙活动的中心地区①。休循,其活动地域大概在帕米尔山中②。捐毒,活动地域大概在塔什库尔干地区③。总体来看,汉代以前,塞人在新疆地区的主要活动地域应在伊犁河流域并及于天山和更南的阿赖岭、东帕米尔等地。二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大月氏西迁伊犁河流域前④,这里本为塞人领地。这时期的塞人,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政权,其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塞王”。至于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生活、宗教、文化艺术及与周围地区的关系等,从这些简单文字记录,难能得其要领。
《汉书》以后,汉文史籍中基本不见有关塞人的记录。但有一条资料,需稍加说明。
唐道宣之《广弘明集》,引荀济上梁武帝肖衍之《论佛教表》,称“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乃讹转以塞种为释种,其实一也”⑤。荀济此文,谓引自《汉书·西域传》,但今本《汉书》中,并无所见。
将“塞种”与“释种”互相比附,还见于(唐)颜师古对《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塞种”一词的注解:“塞音先得反。西域国名。即佛经所谓释种者。塞、释音相近,本一姓耳。”⑥
荀济此文,研究新疆塞人历史者颇多称引。但细作推敲,颇多疑点。谓资料引自《汉书》,但今本《汉书》中并无此文。在南北朝崇佛的潮流中,荀济是肖梁时期抨击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而利用所谓夷夏之别进行反佛宣传,则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现象。在《论佛教表》中,荀济将“释”(佛教)与“塞”等同,则“释”为“夷狄,”使用的就是这个武器。因此,关于“塞”人的这一记录,真实性究竟如何,是需要考虑的。曾有学者揭明过这一问题⑦,此处不赘。
二、有关塞人的考古资料
要将新疆古代塞人的历史研究清楚,关键在于考古工作。目前新疆地区所见考古资料,不少涉及了塞人的历史和文化。一些重要发现,也确实已经给目前的塞人历史研究投射了一束光明。
1976~1978年间,在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天山阿拉沟东口,曾发掘了四座竖穴木椁墓。时代为战国到西汉。根据墓中出土文物特征,笔者曾在执笔的报告中①结论为塞人文化遗存。
从已刊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有关塞人墓葬的基本概念。
墓葬地表见块石封堆,圆形,直径5米多,高不足1米。封堆周围见矩形石垣,东西向,长15米、宽10米左右。墓葬彼此成东北、西南向链线排列。
墓室,均东西向,长方形竖穴,规模较大。其一,长3米、宽2米、深6米多。最大的一座,长6.56米、宽4.22米、深7.1米。墓室内积卵石、巨型块石(较大者长、宽、高均在1米以上)。积石下为木椁,木椁以直径10~24厘米的松木纵横叠置,紧贴墓壁,构成框架,高近1米。尸体置木椁内。葬一人或两人。骨骼粗大。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中,葬青年女性一人,头骨上见一锐利钻孔,孔径0.5厘米。
随葬文物位于墓室西端壁龛、尸体周围。见多量金、银、铜、铁、陶、木、丝、漆器、牛羊骨。
出土文物中,金器量多,纯度很高,且富有特点。大多当为带饰、衣饰。计虎纹圆金牌八块(块径6厘米,重20克上下),图案为老虎形象:头微昂、前腿跃起、躯体卷曲成半圆。或左向,或右向。对虎纹金箔带四件(件长26厘米,重27.75克),图案为相向踞伏的对虎。另外,还有
作奔跃咬啮状的狮形金箔一件。他如兽面纹金饰片,六角形花金饰片,菱形花金饰片,圆形、柳叶形、矩形、树叶形、双十字形、螺旋形金饰片等,品种不少,数量很多,当为衣饰无疑。此外,还见到小金钉、金环等,形式多样。这批墓葬经过盗扰,劫余金器尚且如此,墓葬主人崇尚黄金而且富有黄金的特点,是表现得很清楚的。
银牌,共见七块。有方形、矩形、盾形之别。均模压兽面纹图案,似猫科类野兽形象。这种金属饰牌,成分极为不纯。经光谱分析,其中含银量仅超过10%;其他是铅、铜、铝、钙、钠、矽、镁、铋等。色灰白,质脆易碎。冶炼水平是不高的。
方座承兽铜盘,这也是一件很有特点的器物。器身通高32厘米。下部为喇叭形器座,上部为边长30厘米的方盘。盘中并立二兽,似狮形,鬛毛卷曲成穿孔,似翼。其制作方法是分别铸出兽、盘、器座等,最后焊联成一体。
铁器,有小铁刀、铁镞。铁刀长11.5厘米,与盛羊骨木盘放置一起。镞为三棱形,已锈结成块。
陶器,均手制。细泥红陶,打磨光洁,外表敷酱红色陶衣。计有带流筒形壶、杯、平底盆、三足盆等。漆器、木器,均朽蚀严重。丝质绫纹罗亦朽,但痕迹清晰。此外,还见到珍珠、玛瑙类饰物。
1983年夏,在伊犁新源县境,出土了一批铜器。出土地点在巩乃斯河南岸,新源县东北20多公里处。当地原有一列南北向七墩墓,封土墩在农业生产中已经推平。这次在距地表深1.5米处,见铜器、陶片、人骨、兽骨。报道称,铜器中包括“青铜武士俑一尊,高42厘米”,“青铜大釜一件,重21公斤。青铜铃一件,还有残损的青铜高脚油灯,青铜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和双飞兽相对圆环各一件”。“武士俑的造型端庄、英俊,单跪姿势,头戴高弯勾圆帽,双手好像握着剑或刀……上身裸露,腰间围系着遮身物,赤脚、高鼻梁、大鬓角”。报道认为这是一组“乌孙的遗物”①。
有关文物出土后,承郭文清同志赐函介绍情况,并惠赐文物照片一套。据已刊照片并参照郭文清同志的介绍,得到了更明确、清楚的概念。所称“青铜高脚油灯”,系与阿拉沟出土承兽铜盘为同一类型物。器座已毁,但其上所承方盘仍然完好。盘内两角各蹲一兽,似熊,憨态可掬,造型是很生动的。
“青铜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对虎相向,面、唇相接触,体回曲成圆形。
“双飞兽相对圆环,”造型风格同上。二兽回曲相向,鬣毛上卷成孔,作奔跃状。
铜釜,三兽足,平口深鼓腹。上腹部附四耳,二平二直。腹部弦纹三道。
跪姿武士,头戴高帽,阔檐尖顶,尖顶前弯如钩。
这一组文物,因系推土所得,其埋藏情况、共存关系等,已难究明,是很大的损失。
与巩乃斯河谷出土的这批文物风格类同,1966~1976年期间,新源县城附近亦曾出土一批珍贵铜器,介绍的同志称:同样有承兽铜盘、三足铜釜等物,承兽铜盘上环列异兽,均不幸散失。
在伊犁昭苏地区,近年出土过多件铜盘,矩形,四兽足,也是塞人文化中的典型文物。
还有一批十分重要的资料,是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城附近奴拉赛山上所见古代铜矿遗址。这是一处品位很高的晶质辉铜矿。古代采矿洞口已倒塌,泥石淤塞,但仍可见出十余处。一条“采矿暗洞,洞长30米,最宽3米。洞室大如房舍,局部有横木支护”。“洞内遗留大量石器。由坚硬的河床卵石加工而成。外形大都为一面扁平三面凸起的锥体”一端尖锐,一端钝圆,中腰有凹槽,重3~10多斤。距矿坑不远处的山沟内,为炼铜,遗址所在。炼铜炉砟厚1米,炉砟灰内见木炭、铜锭。铜锭共见5块,外形似碗状,一面圆凸,一面平。锭块重者十余公斤,轻者每块3~5公斤。铜锭块质较纯,含铜量60%以上,性脆,断面银灰色,磨光面银自反光,可鉴人影”①。关于这处铜矿的开采年代,曾经取古矿洞内支架坑木进行碳14测定,经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2650±170年及2440±75年②,相当于春秋早期至战国阶段。
三、有关考古资料辨证、分析
上述三批考古资料,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原简报已说明为塞人文化。巩乃斯河南岸一组青铜器原报道认为是“乌孙的遗物”。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开掘者应属何民族,尚未见涉及这一问题。
结合各方面情况分析,有充分根据可以说明:上述考古资料,应均属塞人文化遗存,是研究新疆古代塞人历史的珍贵资料,应作塞族资料处理。
尼勒克县奴拉赛古铜矿遗址,时代在春秋至战国早期,所在地点是战国时期统治伊犁河流域的塞人王国辖境,开采、冶炼这一铜矿的主人,自然非塞人莫属。说战国时期的尼勒克,在塞人统治之下,这从《汉书》所记“乌孙国..本塞地也”,可以确知。因为据文献、考古资料,已经可以肯定:尼勒克县,在乌孙王国时期,是属于其统治境域中心地带的③。乌孙以前的战国时期,地属塞人,自可明见。
另外两批资料,新源县境巩乃斯河南岸出土青铜器,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出土文物,其风格是一致的。但终非发掘所得,一些具体情况已难明究竟,故着重对阿拉沟竖穴木椁墓资料予以剖析。
阿拉沟木椁墓简报提出了有关墓葬属于塞人遗存的正确结论,但未充分展开。
从葬俗上看,竖穴木椁、封丘成链向排列,在中亚谢米列契地区所见塞种墓葬,同样具有这种特征①。头骨钻孔,这一具有特点的葬俗,在中亚阿尔泰地区所见塞人墓葬中,也有相同的实例②。
从出土文物分析,阿拉沟所见承兽铜盘,方盘中伫立二兽,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所见方盘,对角蹲踞二兽,这类风格的文物,在中亚地区的塞种文化遗址内,是出土不少的。中亚学者称之为“祭祀台”,认为与袄教崇拜有关,是塞人文化的典型文物之图一③。阿拉沟出土不少的虎纹圆金牌,与中亚哈萨克斯坦麦阿密地区出土的塞人文物,卷曲的“豹”形象的圆金牌相同④,从金牌图案造型到作用,实际也是一样的。猫科类猛兽的图案形象,被认为是萨迦—斯基泰装饰艺术中重要的图案主题之一⑤。
这些因素,从不同角度帮助揭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肯定为塞种文化遗存,这是正确的。
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这批铜器,原报告称之为“乌孙文物”,值得斟酌,因为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文化面貌,经过20世纪60~70年代持续二十多年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对乌孙墓葬中出土文物的基本风格、总体特征,人们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⑥。以之对比新源县这批青铜器,基本风格是不同的。因此,视其为乌孙文化系统的文物,缺少充分的根据,这是一。从另外一方面看,如前所述,这批铜器中的承兽铜盘(原报道称为“高脚铜灯”)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所见承兽铜盘,风格一致。这种承兽铜盘,与兽足铜釜,往往共出,被视为塞人文化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在中亚谢米列契、天山地区,常有所见⑦。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这次见到这一文物组合,铜釜的造型、风格,与苏联谢米列契所见,几乎也是完全一样。这就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文化现象。其他如“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双飞兽相对圆环”,这里的“对虎、翼兽”风格、整个圆环的造型,同样是比较典型的塞人艺术特点。在伊朗出土的萨迦文物中,可以找到相同的实例⑧。
四、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塞人历史
这几批考古资料,揭示了多方面的塞人历史内容。
(一)活动地域
这些资料,不仅印证了《汉书》中所记述的,汉代乌孙居地,就是战国时期塞人的故土,伊犁河流域自然条件优良,同样曾是塞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而且告诉我们:沿巩乃斯河谷上行,进入天山,直到阿拉沟东口(包括于尔都斯草原),这片优良的夏牧场地区,十分可能都曾经是古代塞人活动的基地。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铜器与阿拉沟东口竖穴木椁墓中的多量金器,都不是一般塞人平民所能享有。很有可能,这片地区内,曾是伊犁地区塞人王国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
(二)社会经济活动
这是文献记录中缺略、考古资料较为丰富的一个方面。
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发现了小铁刀、三棱形铁镞。战国时期,塞人已经用铁,尤其是使用了消耗量很大的铁镞,这对我们估计当时塞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铁矿的冶炼、铁器的加工,都远较铜金属要困难。铁被用于制作工具、兵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使不少新的生产领域可以得到开发。
同样在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见到了随葬的羊、牛、马骨。随葬木盆中,羊骨与小铁刀并陈,形象地说明了墓主人生前生活中肉食具有重要地位。这可以说明:畜牧业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体。《汉书》称塞人经济为“随畜逐水草”,可谓抓住了要点。
木器制作、毛纺织、制陶等,是主要的家庭手工业。木器主要见到作为盛器的盘,长方形,利用整木加工成型,内外修刮光洁。陶器品种较多,如带流筒形杯、盆、钵、小杯等,均日常用器,较之木器似占更重要地位。陶器手制,形制规正。陶土很细,外施一层酱红色陶衣。毛织物,只见到严重朽烂的小片。此外,阿拉沟木椁墓内还见过草席印痕。草编织物,当也是家庭手工业产品之一。
在谈及战国时期塞人的社会生产时,对当时的矿冶、金属加工业,应特别注意。从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开采、冶炼资料,可以肯定:当时采矿、冶炼生产必然已经越出家庭手工业的范畴,成了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在铜器、金器制作上,应该也是同样的情况。不论是铜矿开采还是冶炼,生产工艺比较复杂,专业性比较强,生产规模较大,需要的劳动力也比较多。每个生产环节,如找矿、坑道掘进、支架防护、采矿、排水通风、提取运输矿石、冶炼、浇铸等,都要求生产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专门技术,必须比较固定或相对稳定地从事这一工作。从奴拉赛所见古代铜矿冶炼遗址看,矿石开采与冶炼集中在一处,这也符合经济的原则,但这更加需要每个生产环节的密切协作,需要比较严密的组织与统一的指挥。这些生产运营本身的要求,使这类矿冶生产必然要独立于畜牧业或农业生产以外,越出家庭手工业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金器、铜器的制作,同样是这个道理,相当复杂的工艺过程,往往都不是附属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所能承担的。
在分析奴拉赛矿冶遗址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矿坑内外,发现相当多数量的卵石制器。它们中部凹腰,端头见到为便于捆缚而加工的凹痕。这类石器,在湖北大冶县铜绿山春秋、战国到汉代的矿冶遗址内,也曾经出土过。被认为是一种提升工具——平衡石锤①。铜绿山矿冶遗址时代早,沿用时间长。这里的石锤与奴拉赛矿冶遗址所出石锤,形制相同,作用应该相当。这当然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从中可以看到古代中原地区矿冶技术对新疆地区的具体影响。
奴拉赛矿冶遗址,对我们认识塞人王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是十分重要的资料。我们目前的分析只是根据已经报道的十分有限的考古调查资料,随发掘工作的展开,对当时的采掘技术、冶炼工艺、生产规模等许多方面的专门问题,必然会提供更多具体、准确的资料,为古代塞人历史研究揭开新页。
(三)崇尚黄金并且积累了较多的黄金财富,是战国时期塞人社会生活中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特点
阿拉沟4座竖穴木椁墓,无墓不见金器。以第30号墓为例:重20克左右的虎纹圆金牌8块(虎头左向的5块,右向3块,不对称,实际当不止此数),重27克多对虎纹金箔带4件,狮形金箔1件,其他有菱形花金饰片3件,较大圆形金泡饰片33片,较小的金泡仅女尸头部傍近,即达数十片,柳叶形金饰片近百片,螺旋形金串饰片33件,其他还有双十字形、树叶形、矩形饰片及金丝等物②。大小合计,数达200件以上。而这些墓葬,都曾经过盗扰,所见金器,不过是盗墓后的劫余。从发掘现场及残余金饰形制分析,这类饰片,主要都是用为冠、衣、带、鞋类服装缀饰,当日情状,肯定是十分辉煌的。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曾经说到塞人王族享用着上天赐予的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有金盏,死后要以黄金制品随葬③,颇可以与我们的考古资料互相印证。
相当富厚、奢侈的随葬品,相当规模的墓室(同样以30号墓为例:竖穴墓室土方量即达一百多立方米,矩形木椁高近1米,厚达2米的填石大小整齐,填沙纯净),也说明这类墓葬的主人,不是一般社会成员。《汉书》记载塞人有“王”,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考古资料与此可以互相证明。
(四)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及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所见塞人遗物,可以窥见其具有特点的艺术风格
各种饰牌、金饰片、铜器,除极少数为植物花纹图案(柳叶形金饰片、六角形金花饰片)外,占统治地位的是各种野兽纹图案,有虎、狮、带角兽、熊等,猫科类猛兽形象具有重要地位。野兽形象基本是写实的,对各种野兽的特点掌握得很准确,造型比例适当,形象很生动。伊犁地区的这支塞人在图案艺术上的这些具体特点,与中亚西部或南亚地区塞人有什么差别,体现了什么具体的历史内核,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这批文物中,图案设计十分讲究对称、平衡,这也是不应忽略的一个方面。
(五)论及伊犁地区这支塞人的历史文化,从文物中体现出来的他们与中亚广大地区(如谢米列契地区)塞人的密切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有关这支塞人和其他地区的关系,如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出土文物也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出土的漆器、丝织物(菱纹链式罗),奴拉赛铜矿出土“或说为采掘工具”的平衡石器。
“平衡石器”(或说为采掘工具)的造型与湖北大冶铜绿山所见石器造型一样,这些,都说明肯定存在相当的经济、文化关系。这是过去文献记录中不见涉及的一个方面,它们填补了文献记录的空白,值得重视。
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铜人,很值得推敲。铜人单腿下跪,半裸体,社会身份似乎不高。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塞人王国属下人民的体形特点。从造型看,其体格十分健壮,双臂肌腱鼓凸,强实有力,粗眉大眼,鼻梁较高,头戴十分显目的高冠,尖顶向前极度弯曲,下身着短裙。
在波斯文献中有萨迦·提格拉豪达(SakaTigrakhanda),意为戴尖帽子的萨迦人(在波斯碑刻中也见到过一种尖帽萨迦人形象①,但与铜人的尖帽形象不尽相同)。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提到“属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高又硬,顶头的一方是尖的”②。联系这一铜人形象,对塞人尖帽特征,可得到一点新的概念。
五、另外两批有关塞人的资料
新疆地区,还有另外两批考古资料,可能也与塞人有关。
其一,1966~1967年,新疆考古研究所陈戈、吕恩国、周金铃等在帕米尔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北约4公里,塔什库尔干河谷西岸第二台地上的香巴拜,曾经发掘过40座墓葬①。
据已刊报告,40座墓葬中,有火葬墓19座、土葬墓21座。除地表堆石或围以石垣,墓室作长圆形或不规则圆形为两类墓葬同时具备的特征外,在其他更主要的一些方面:如墓口盖木,有无葬具,埋葬方式(火葬或土葬),有无殉物或殉葬文物种类、组合等,都明显具有不同的特点。
19座“火葬墓中,除6座出土一件铜耳环和几块碎陶片、残铁块、鸟骨外,余均无随葬品”。
21座土葬墓,随殉了陶器、铜器、铁器、金器、木器及石、骨、玛瑙珠饰等。“每座墓的随葬品不多,除个别的殉人墓和二次葬墓有超过10件以上者外,大部分墓的随葬品只有几件。随葬品中,以装饰品最多,生活用具次之,生产工具最少”。
陶器,陶胎均夹粗沙,手制,烧成温度较低,陶色斑驳不均,基本为素面,少数饰凸弦纹或指甲纹,制陶工艺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陶器种类有釜、罐、碗、钵、杯、纺轮。主要为实用炊器,器表仍附有烟煤。其他为盛器及纺织工具。
铜器,主要为各式装饰品,少数为工具、武器。包括铜镞、各种片饰、镯、耳环、指环、铜管等。其中羊角形饰片,为帕米尔山区常见大角羊头形图案,线条简单,形象真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铁器,很少。除一件环首小刀及镯、指环外,其他小件铁器均因锈蚀严重,难辨其形制。
金器,为一梨形薄金片做成的饰牌。
其他为毛毡、钻木取火器、各种串珠及羊骨、鸟骨等。
两座墓葬中发现殉人。
墓葬时代,根据3座墓内盖木标本的碳14测定结论,结合有关考古文化资料,结论为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左右,属“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经济生活,适应帕米尔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以畜牧和狩猎为主,没有农业。
关于墓葬主人的族属,报告没有作出明确、肯定的结论。一方面说,根据土葬、火葬同时并存,认为“这些墓葬可能与羌族有关”。但同时又提出:(1)根据对墓葬中一个保存稍好的头骨的鉴定,“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2)“在塔什库尔干西边的帕米尔河和阿克苏河流域,过去曾发掘过一些墓葬。这些墓葬的形制、结构和随葬陶器与这批墓葬基本一样”。中亚考古学界认为是“塞克族的遗迹”。所以“这批墓葬……有可能也与塞克族有关”。
在帕米尔地区,发掘工作做得很少,在目前十分有限的资料下,对墓葬主人的族属要作出明确的结论,本身确存在一定困难。但有几个因素,却可以稍作进一步的分析:一是这批土葬墓的主人,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与作为蒙古人种的羌族不能统一;二是邻近的中亚地区,对同类墓葬曾进行过相当工作,研究结论,有关墓葬为塞人遗存①;三是据有关文献(包括前引《汉书》资料),帕米尔地区在战国时期,确曾为塞人活动地域。因此,可以初步肯定,有关土葬墓属古代塞人遗存,是比较合理的。
同一地点出土的火葬墓,显示了相当多的不同特点,把这类墓葬作为另一种考古文化考虑,是比较合理的。它们是否可能与曾在葱岭地区活动过的氐、羌族有关,则确是一个可以分析的问题。从河西地区所见氐、羌资料看,火葬是其基本特点之一。但目前仍是资料太少,结论只能留待以后进一步的工作来做了。
其二,在罗布淖尔地区,新中国成立前曾发掘过一种土著人墓葬。墓室为浅埋的沙穴,葬具为船形木棺或一般木棺,其上盖板,铺覆皮张,内葬一人。因环境干燥,不少成为干尸,随身衣物保存完好。其一般情况是:头戴尖顶毡帽,帽上或插翎羽。裸体,包覆毛毯。足蹬皮鞋。随葬木器,或有弓箭。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之头下胸前,均附一小包麻黄细枝,无一例外。这种古墓,我国学者黄文弼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学者贝格曼,以及斯坦因等,在罗布荒原上均曾有过发现②。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考古所在孔雀河下游也曾发掘过这么一处墓地③。
对这类墓葬主人的族属问题,斯坦因、黄文弼曾有过分析。
斯坦因的观点是:这些人的特点“很近于阿尔卑斯种型”,并认为据掌握的人类学测量资料,“现在塔里木盆地人民的种族组织,还以此为最普通的因素”④。
黄文弼根据出土古尸的形象、服饰,尤其是死者头戴尖状毡帽之特征,认为同于塞人之习俗,“故余疑楼兰土人与塞种人不无关系”⑤。而以麻黄细枝入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习俗。据称,古印度伊兰人有一种信念,认为这种麻黄,可以产生一种“浩玛”或“所玛”(Haoma或Soma),是伊兰人祭祀中的重要物品⑥。若然,则可透见罗布荒原上的这一土著习俗,与古代伊兰人存在密切的关系。
从目前新疆地区所见这三组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在论定或初步结论与塞人有关的这三组资料中,伊犁河流域的塞人文化,可能与塞人有关的帕米尔山区香巴拜墓地及罗布荒原上戴尖帽的土著人文化,它们彼此之间明显具有相当不同的文化特点,差别很大。但是,与古代波斯碑刻及古希腊文献提供的有关塞人的概念,却可以互相呼应。
古代波斯的楔形文字刻石,常提及萨迦人。见到的称呼有提格拉豪达·萨迦、豪玛瓦尔格·萨迦、提艾伊·塔拉·达拉伊雅·萨迦,分为三个部分,各有不同地域。提格拉豪达·萨迦,意为戴尖帽子的萨迦人,活动地域在黑海以东,锡尔河东南,包括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南部,帕米尔、阿赖岭以北,塔什干、天山以至巴尔喀什湖以南,楚河、塔拉斯河流域;豪玛瓦尔格·萨迦,意为带着所崇拜的植物叶子的萨迦人,活动地域在费尔干纳盆地、帕米尔及阿赖岭等地;提艾伊·塔拉·达拉伊雅·萨迦,意为海那边的萨迦人,活动地域当在阿姆河以西,黑海、咸海周围①。从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这部巨著中,也可以看到,在中亚大地存在许多不同的萨迦部落。在希罗多德笔下,黑海、黑海以北至锡尔河流域的广大游牧人,都与萨迦人有关。他们或被称为斯奇提亚人(亦译西徐亚人、斯基泰人),或称萨尔马希安人,或称马萨该达伊人,或称萨迦人。萨尔马希安人的语言“是斯希提亚语”。
而“乌萨该达伊人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族..有一些人说他们是斯奇提亚人的一个民族”。“属于斯奇提亚人的萨卡依人(即萨迦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萨卡依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奇提亚人都称为萨卡依人的”②。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概念,在希罗多德当时(前5世纪),对中亚广大地区以至欧洲一些地方的所谓萨迦人,概念还不是十分具体、精确的。这些不同的萨迦人集团,彼此也存在不同特点。我们今天沿用这个概念,会遇到考古文化上呈现出来的不同面貌,当然就不奇怪了,而且还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事。
根据波斯碑刻及古希腊文献,联系我们新疆地区上述所见塞人资料,有几个具体问题,可以着重说明一下:
一是斯特拉波(Strabo)曾经提到,在锡尔河东北,曾有一支塞人,称为萨拉可伊人(Sacaraucae),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这颇可以与我国《汉书》所述伊犁地区塞人相当③。从西方古典作家的记录与我国古文献记录,结合现实考古资料研究,三者似可统一。
二是所谓“带着所崇拜的植物叶子”的萨迦人,他们这一特殊的习俗与罗布荒原上头戴尖帽的土著人习俗,完全一致。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的雷同。而很可能是古代罗布荒原上曾经活动过一支豪玛瓦尔格·萨迦人的生动说明。他们的阿尔卑斯型人种特征,头戴尖顶毡帽的习惯,也都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汉代以后,汉文史籍中少见塞人资料。但在新疆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存在着塞人的活动,有着塞人的影响。乌孙徙居伊犁河流域后,有相当数量的塞人逐渐融合到了乌孙民族之中,所以,《汉书》说“乌孙民有塞种”,在考古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彼此存在过的影响。
塞人的语言,已经确认是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支。帕米尔地区,曾是古代塞人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帕米尔广大地区现在的主要居民,仍操东伊朗语。我国境内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塔吉克族,其语言也是属于东伊朗语支的。其间的历史关系,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和田、巴楚等地发现过不少古于田文书,时在汉代以后,约属公元6~10世纪。据研究,古于阗文字“原出印度波罗米字芨多正体,是于阗地区塞族居民使用的文字”,它所记录的语言“今称于阗语或于阗塞克语”。“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于阗曾是塞族住地,与印度境内的塞族为同支近亲,甚至与远在中亚北部的斯基泰人也有亲属关系,所以贝利(英)也称于阗语为印度—斯基泰语或径称塞克语”①。贝利教授还曾明确提出: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有一支萨迦部落来到于阗定居下来,并形成他们的统治阶级。瞿萨旦那,就是塞人在和田地区曾建立的王国②。
这些例子,多少可以看到古代塞人在新疆地区历史生活中的深重影响。
附注
①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11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②关于休循国今地,学术界观点分歧,迄无定论。或说即今克什米尔之洪查;或说为帕米尔山中的伊尔克斯坦(Irkeshtam);或说在阿赖山中;或说为喀什至浩罕的山口,等等。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下),310~3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关于捐毒今地,同样是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此从岑仲勉说。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下),318~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④关于大月氏西徙年代,有多种意见。但应以公元前3世纪末即开始西徙较为合理。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64~66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⑤道宣:《广弘明集》卷七。
⑥《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2692页。
⑦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杨炼译,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①《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图版八,载《文物》,1981(1),18~22页。
①巴依达吾列提、郭文清:《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珍贵文物》,载《新疆艺术》,1984(1);《新疆日报》,1983(10.15),第4版。
①探古:《新疆发现东周时代开采的古铜矿》,载《中国地质报》,1983(10.10),第1版;王有标:《尼勒克发现古铜矿遗址》,载《新疆日报》,1984(2.25)
②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14实验室:《碳14年代测定报告(五)》,载《文物》,1984(4)
③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11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①③7H.贝尔什塔姆:《谢米列契和天山历史文化的基本阶段》,载《苏联考古学》,1949(11)。
②G.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载《考古学报》,1957(2)。
④C.N.鲁金科:《阿尔泰斯基泰艺术》,36页,图27。
⑤B.A.伊林斯卡娅:《斯基泰野兽纹问题的研究现状》,见《欧亚民族艺术中的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莫斯科:1976。
⑥《乌孙研究》,见《新疆考古三十年》,8~9页,4751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⑧《波斯艺术大观》(英文)卷7,57页,纽约:1981。
①中国金属学会出版委员会编:《铜绿山——中国古矿冶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②《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1)
③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433、435、4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①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附录,2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王治来:《中亚简史》第二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②希罗多德:《历史》,6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①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载《考古学报》,1981(2)。原报告中,地名译作“香保保”,不尽准确;今据当地习用译称,作“香巴拜”。
①《帕米尔古迹》,见《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俄文版),第26卷,324~325页,1952;《世界屋脊的古代游牧人》(俄文版),26页,1972。
②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56~57页,105页,图12~14;F,贝格曼:《新疆考古调查》(英文版),斯德哥尔摩:1939;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10~114页,图66~67,北京:中华书局,1936。
③《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1)。
④(英)A,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1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36。
⑤⑥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57、100页,北京: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印行,1946。
①在波斯贝希斯敦(Behistum)、波斯波里斯(Bersepolis)、纳克沁·伊·罗斯塔(Nakshi·Rostam)三处刻石,均提到大流士王征服、缴纳贡赋的国家和地区,均提到萨迦(Saka),后者更具体提出萨迦·提格拉豪达、萨迦·豪玛瓦尔格及萨迦·塔拉达拉雅。引自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369页;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附录第三节;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32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王治来《中亚简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②希罗多德:《历史》,第4卷、第7卷,267、476、6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③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252页。
①黄振华:《于阗文》,见《中国民族古文字》,163~170页。
②H.W.贝利:《于阗语文书集》(英文本),剑桥:1960。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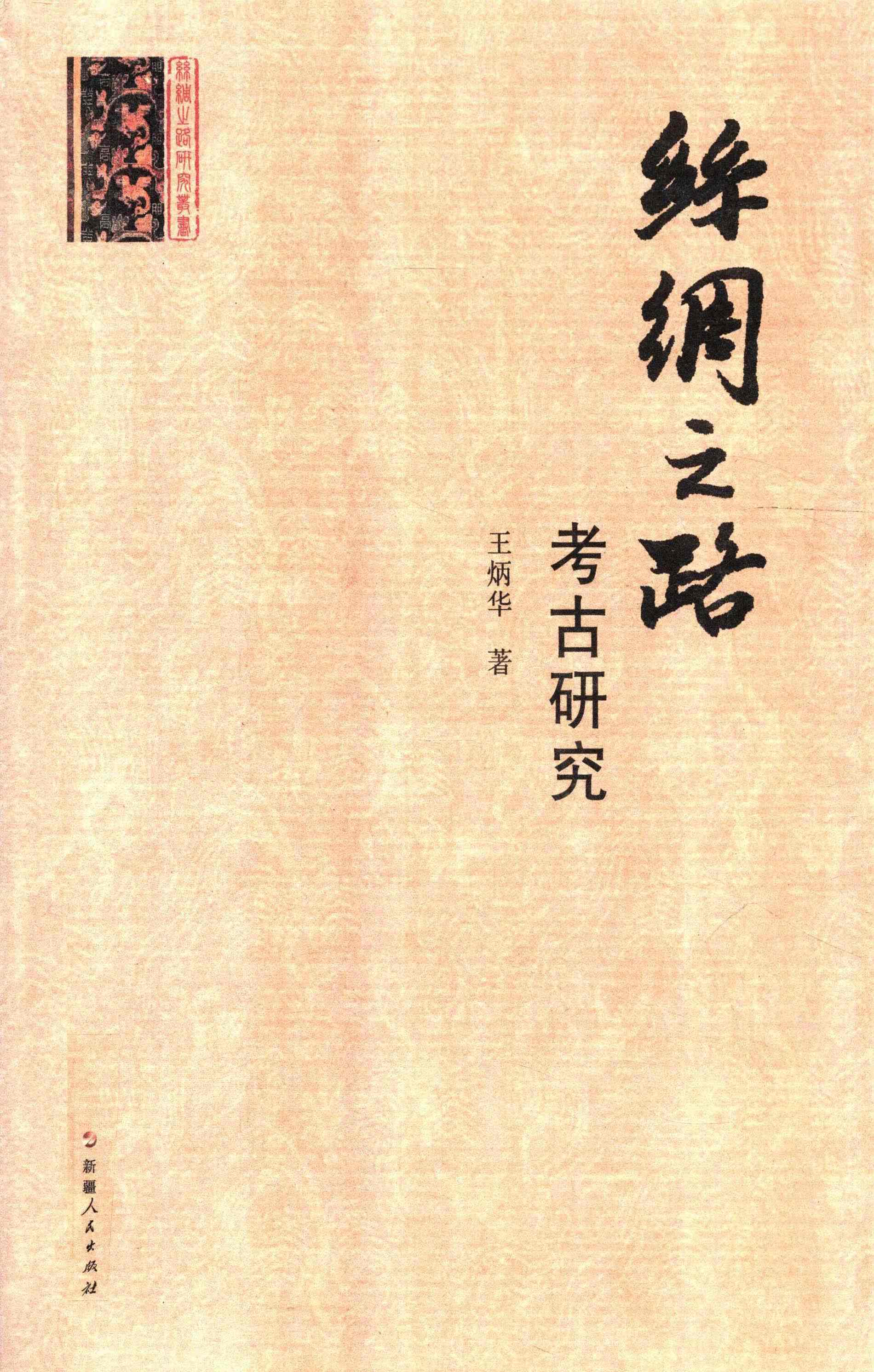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