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72 |
| 颗粒名称: | 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索 |
| 分类号: | K878.9 |
| 页数: | 13 |
| 页码: | 122-13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区和祖国内地存在十分久远的历史关系。在西汉王朝政权统一新疆地区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记录十分丰富,人们认识得也比较深刻。对于此前的历史关系,虽然是大家早就注意、关心的一个问题,不少论著中曾予提及。但终因文献资料舛缺,考古资料零散,所以少见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是目前新疆历史研究中有待加强的一个薄弱环节。 |
| 关键词: | 新疆 中原地区 历史关系 |
内容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区和祖国内地存在十分久远的历史关系。在西汉王朝政权统一新疆地区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记录十分丰富,人们认识得也比较深刻。对于此前的历史关系,虽然是大家早就注意、关心的一个问题,不少论著中曾予提及,但终因文献资料舛缺,考古资料零散,所以少见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这是目前新疆历史研究中有待加强的一个薄弱环节。
这一课题的完成,主要需凭藉考古工作的成果。
因为种种具体条件的局限,已经完成了的各种各类考古工作实际,并不一定能及时被各界人们所接触、了解。把足以说明西汉以前新疆地区与内地历史关系的考古资料,稍予整理、纂辑,并进行一定的分析,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深入,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因主要是考古资料的介绍,文字虽成系统,有材料堆积之疵,但望以此引发人们对这一课题的更大关心,促进这一研究课题的深入。
一
可能早到距今1万年前后的哈密地区七角井细石器遗址,其石器制作工艺,明显受到我国华北地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影响,生动表明了新疆地区和黄河流域十分久远的文化联系。这个问题,早有人们注意,但从未得到较为深入的说明、介绍。
国内外考古学界从宏观的角度,都注意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这就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世界范围内普遍见到采用特定工艺技术所生产的小型细石核、细石叶(长数厘米,宽不到1厘米、厚只1~2毫米的细长石片)和以细石叶为材料进一步加工成的细小石器,分布范围相当广、延续时间也相当长。它标志着当时人类的采集、渔猎生活有了新的发展、进步。而从石器加工技术、器物造型角度,又可据其异同分为两个大的系统:几何形细石器和细石叶细石器。几何形细石器分布于欧洲、北非、西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①,其特点是利用从圆体石核上打下窄长细石叶,并截断加工成规整的三角形、半月形和梯形等石刃。与之相对,细石叶细石器则主要分布于亚洲东、北部和美洲西、北部,包括新疆在内的我国、蒙古、西伯利亚、日本和白令海峡地区,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部分地区。这里的特点是从扁体石核上打剥下窄长细石叶,并用此加工镞、钻、雕刻器等。对这一重大文化现象,国内外不少学者早就注意并揭明过这一事实。称这是“具有世界意后有源于西伯利亚、蒙古、我国华北地区等多种论点③。
经过近20年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这一问题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得到了比较合理的结论。这就是:它们起源在我国华北地区。这么广大的地区内,我国华北地区,最早在山西省许家窑旧石器时代遗址,就见到了细石器。经过测定,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10万年前④。更后,如距今3万年左右的山西朔县峙峪⑤,距今义的考古研究课②,但对细石叶细石器究竟起源在何处?怎样发展、传播?则有不同的看法,国内外先。题”1.8万多年的河南安阳小南海⑥等旧石器晚期遗址中,细石器趋向成型,工艺特征比较清楚。经过长时间发展,形成比较成熟的工艺传统,逐渐流行在黄河流域,并进而影响到我国广大地区及蒙古、西伯利亚、日本、阿拉斯加等处⑦。
地处亚洲腹地的新疆,哈密七角井、三道岭及吐鲁番阿斯塔那、罗布淖尔等处,都发现过细石器遗址。它们的造型特征明显属于我国华北地区类型,而与西南亚、欧洲地区所见细石器风格不同。对这一现象,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和我国学者杨钟健在首次向国内外介绍七角井的有关发现时,就注意到这个情况,稍后并正面作了阐发⑧。
为了对这一问题有较为具体的认识,我们以哈密七角井石器遗址为例,稍作深入说明。
在约3万平方米的范围内,用3天时间,即采集各类石器近1000件。石料主要为燧石,它们出土于距今1万年前后的全新世地层。从非常丰富的扁锥形石核、船底形石核到锥体、柱体石核,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修治石核、打剥石叶都有严格的工艺过程。从这些石核上打剥下来的细石叶与用细石叶加工出来的箭头、钻头、雕刻器等,已见出一定造型。利用拇指盖大小或稍大一点的厚石片,按一定方法压琢修治成有一定造型的刮削器,刃部锐薄。加上共存的以打制石片加工的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砍砸器等,很鲜明地表现了当时人们以采集狩猎为主体的生活内容。这些石器,据其造型、加工工艺特点,都可以看到它们与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期遗址,如山西下川①、河南许昌灵井②、陕西大荔沙苑③、黑龙江海拉尔松山④等处所见同类石器,表现了共同的特征。应该强调一句,选择特定的石料、修坯、制造石核,按一定方法打剥石片,进一步加工成合适的用器,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显示了的共同点,当然不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只能是同一种文化、技术影响下的产物,是新疆地区在距今1万年前后即与黄河流域存在文化交流的有力说明⑤。
在七角井细石器遗址,我们还采集到一件浅红色的珊瑚珠。珊瑚是海产。从七角井细石器工艺与黄河流域相同而与西南亚不同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近乎肯定:这件珊瑚原料,应该也是来自我国东部沿海。
二
时代较此稍后,还有另一件必须引起足够注意的可资说明新疆与中原地区久远联系的考古资料。1976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发掘了一座未经盗扰的殷王室墓葬。据墓内出土甲骨文、铜器铭文可以肯定,墓主人是殷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其死亡、入葬年代可以明确在公元前13世纪末叶至公元前12世纪初⑥也就是在,距今3200年前后。在这座规模不算大的墓葬中,共出土随葬器物1928件,,其中有玉器756件(少量残片未计),玉器占出土器物的39.2%。这批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优美,包括礼器、仪仗、日用器及大量装饰品。埋葬3000多年后出土,多数玉器光泽依然晶莹鲜润,表现了当时在琢玉工艺、抛光技术方面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注意。
有关这批玉料的产地,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为取得比较可靠的结论,曾取各类标本300多件送请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单位进行鉴定。结论是除3件标本外,均属新疆玉。包括“青玉、白玉(内有极少量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糖玉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白玉、青白玉很少,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①。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结论。
我们知道,商、殷王朝使用玉器数量是十分巨大的。《逸周书·世俘解》称:“..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②(清王念孙校读为“凡武王俘商,得获宝玉万四千)证之以妇好墓,一次出土即达750多件,《逸周书》中有关殷王室大量用玉的记录,可能接近于真实。
商,殷王室大量用玉,而玉料又主要取之于新疆地区,这就再一次以有力的考古资料揭明了新疆与中原地区存在的经济联系。
先秦时期的文献如《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对古代中原地区用玉,而且玉取自和田、昆仑,有不少记录。但人们对这些记录,往往是疑信参半。现在有殷墟这批玉器出土,则可以肯定,先秦时期关于内地用新疆玉的记录,去事实绝不会太远。
早到新石器时代,内地不少遗址中即见用玉。可能与夏文化有关的河南省偃师二里头墓葬,玉器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由于玉石的温润光洁,历代统治阶级都以玉德自比,用玉风气有盛无衰,需玉数量也非常大。这一趋势,直至清代不改。而新疆又是全国最主要的、也是玉质最好的一处软玉产地。在玉石东去中原的历史中,凝结着新疆与祖国内地之间密切、久远的经济联系。
三
关于我国中原地区丝织物的西传,是早就被注意,并有不少学者写过文章的。这里的介绍,不多涉及文献,主要以考古资料中所见实物为主。
1976~1978年,配合南疆铁路工程,笔者曾在吐鲁番盆地西缘,天山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段,主持、参与了一大批古代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墓葬出土文物丰富,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特点。墓葬主人主要经营畜牧业,饲养羊、骡、马。衣着材料是各式毛织物。墓内出土的多量彩陶器很有特点。综合分析出土文物特征,结合有关碳14测定资料,墓地延续了相当一个历史阶段,主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最晚到汉③。
测定为春秋阶段的第28号墓(碳14测定结论为距今2620士165年),其中出土了一件凤鸟纹刺绣。在长、宽均20多厘米的素色绢地上,用绿色丝线锁绣出凤鸟图案。由于原件已残破,完整图案形象已难明,但残余部分仍可见到凤鸟的躯体,微曲的腿、爪(原物现在新疆博物馆陈列)。这件文物,不论是丝绢本身,还是其上的凤鸟图案,一目了然,属于中原地区的产品无疑。
在测定为战国至汉代阶段的第30号墓中(测定数据一为距今2345±75年;又一为距今2090±95年),与大量具有战国阶段风格的野兽纹金、银、铜器共存,有一块规规整整的用黄黏土做成的方泥饼,边长15厘米、厚2.5厘米。原来用菱纹链式罗包裹。丝罗已朽,但因为黏土质地致密,菱纹罗痕迹却十分清晰地印存黏土面上。其细密的组织,非丝莫属。这一印纹照片,曾刊布于《文物》1981年第1期图版捌:5。
与新疆地区邻境,苏联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区巴泽雷克古墓葬,是世界知名的一处古代塞人文化遗址①。在结论为公元前1000年中叶的这批墓葬中,出土了不少我国丝绣织物。“某些巨墓中出土的中国织物,有用大量的捻股细丝线织成(每平方厘米为34×50支)的普通平纹织物。这些织物,有小块的,也有整幅的(铺盖在皮衣服的上面)”。“其中图案和制作技术最为特殊的,是巴泽雷克第3号墓出土的一块有花纹的丝织物。这块丝织物,1平方厘米为18×24支纱,由一经两纬织成。丝织物为1/3和3/1斜纹(即三下一上或三上一下的斜纹)”。“巴泽雷克第五号墓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这是一块鞍褥面,制作技术为平纹,1平方厘米为40×52支纱,宽约43厘米。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连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的形象是极其多样化的”。“它的富于表现力的形象和优美的色调,无疑的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品”。“发现有凤凰绣缎的墓葬”,主要可以根据西亚细亚出产的织物——羊毛绒毯和非常细密的羊毛织品——准确地断其为公元前5世纪的墓葬。根据这些资料,苏联学者肯定“中国与苏联阿尔泰居民的最早关系是发生于公元前第一千年的中叶”。
我们需要在这里附带说明的,一是前述阿拉沟第28号墓的凤鸟纹刺绣,其中刺绣技法、凤鸟图案风格,与巴泽雷克古墓中所见凤鸟纹图案风格、刺绣技法,是一致的。再是,邻境的苏联阿尔泰地区与我国中原地区的交往事实,也完全可以帮助我们考虑当日中原与新疆地区联系的实际。
阿拉沟,并非古代通衢要道,也不是由比较大的绿洲构成的古代重要政治、经济中心。但就在这样比较偏僻的山区古墓葬中,同样见到了来自中原的菱纹罗、凤鸟纹刺绣,这个事实对于揭明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已传到新疆,并及于更多的其他地方,是有很大说服力的。
在这一背景下,再去认识印度文献记录,比如憍胝厘耶著的《治国安邦术》,其中提到“憍奢耶和产生在支那的成捆的丝”(憍胝厘耶据说是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月护大王的侍臣),亦即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已经去到印度①,就是完全不难理解的了。
四
与丝绣相类,漆器、铜镜也是我国中原地区的传统产品,汉代以前,新疆地区已见。另外,还见到产自东海、南海的贝类。
(一)漆器
阿拉沟第18号墓葬,时代为战国。这里出土漆盘一件。见于“墓室西头木椁外。径16厘米。木胎,已朽,只余内外漆皮,黑色地,朱红彩,绘弦纹四道,盘底绘流云纹”②。
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阿拉沟第30号墓葬中,也曾见到漆器多件。漆器置与墓室西头,与承兽铜盘、陶器、木盆、兽骨、泥饼等随葬文物并列一起,漆器彼此叠置。清理中,发现这组漆器胎质已朽,只有漆皮,为沙土覆压。当时采取措施,在漆器周围沙土上挖槽,而后灌浇石膏,企图连沙土,并漆皮浇灌一块,运回室内剥离、修复。十分可惜的是这一石膏块灌封未严,在汽车长途运输中沙土散裂,返至室内后未能取得完好漆器标本。部分曾送北京修复,亦未奏功。这里的漆器标本虽已不存,但墓内曾随葬多件漆器,是毫无疑问的。
阿拉沟第23号墓,时代较第18、30号墓要稍早,其中出土残耳环一件,木胎,胎质较厚,黑色漆地,绘朱红色彩,显云纹图案。这一标本,在文物出版社《文物》特刊第40期(1977年12月15日)曾刊发过照片。
阿拉沟墓地的时代,主要在春秋、战国阶段,这么多件漆器标本在阿拉沟墓地出土,说明汉代以前,曾有相当数量的中原地区漆器西来新疆,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
(二)铜镜
1963年,笔者与易漫白、王明哲同志一道,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发掘过32座石人、石棺墓葬。时代上起殷周,下迄隋唐,延续时间相当长。在其中第22号墓葬中,出土铜镜一件,“直径仅六厘米,平素无纹,弓钮无座”。它“是古代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它的形制和大小都与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基本一致”。“这面铜镜的出土,说明新疆,包括北疆在内的古代少数民族,在古远的历史时期,已经和中原的汉族文化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①(就在同一墓地内,第24号墓葬内,曾出土黄色豆形陶器一件,饰几何形划纹,通高7.5厘米。其“形制与中原地区春秋时代出土的陶豆颇有渊源关系”)。
早期铜镜,在前引苏联阿勒泰巴泽雷克墓地中也有所见,“在巴泽雷克第6号墓中,发现白色的金属制的中国镜一面,即所谓秦式镜的变形之一。镜体虽已破损(保存了二分之一强),但我们仍然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因为在阿尔泰山西麓的一个墓葬中,也发现了一面完全相同的镜子”。“这两面镜子的直径,均为11.5厘米。质地薄脆,镜面极为光滑。边缘为素卷边,在镜背稍凸起的方形钮座中心,置一小弦钮。地纹为美丽的、单一的所谓‘羽状’纹。羽状纹地上,沿边缘置以四个‘山’字形雕饰。在山字纹之间,有成对的心状叶形”。“发现上述金属镜的数处墓葬,年代则比较晚,属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②。根据上引C.N.鲁金科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属于我国战国阶段流行的山字纹铜镜,是典型的中原地区产品。
(三)海贝
新中国成立前,在罗布淖尔地区的原始社会阶段墓地中,出土过海菊贝制成的珠饰。海菊贝,是只产于我国东南沿海的贝类。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哈密五堡,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两处墓地,见到了不少海贝。
五堡墓地是距今3000年前后的一处原始社会阶段墓地。这里所见贝类标本,主要用为装饰品,如佩饰于毛织围巾、衣服上。共见标本十多件,经初步鉴定,品种主要属“货贝”。
阿拉沟墓地所见海贝,主要置于死者头侧、臂侧,似作为装饰品。个别海贝含放于死者口中。贝在这里,是作为一种贵重珍品了。死者口中含贝,中原地区,商代有这样的习俗。更晚一点,则口中含钱。吐鲁番晋、唐时期墓葬中,死者口中有含波斯银币的。在阿拉沟发现的海贝数量,较哈密五堡墓地稍多。经鉴定,除货贝外,还有环纹货贝。
货贝、环纹货贝的产地相当广泛。我国东部渤海、黄海以至南海,均见出产。西南亚的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亦见。但联系有关文献资料,含贝以葬的风俗,前述南海海菊贝先例。笔者认为,它们来自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我国古代,对贝十分珍视。“宝”字繁体从“贝”,“宝贝”一词,在汉语文中一直用来形容珍贵物品。商代,曾以贝作货币。考古工作中,曾见到过铜贝。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穆天子传》有关的一部分记录:述及周穆王抵达一地,与当地首领应酬、互相赠礼时,穆王赠礼,几乎都有“贝带”一项。对于《穆天子传》此书,史学界看法、评价不一。但对于此书最晚成于战国之时(或更早),表现了周、秦阶段对祖国西北地区、包括今新疆一带的了解,则基本没有异词。现在,哈密、阿拉沟、罗布淖尔等地,都见到了海贝,有的海贝只产于我国东、南沿海。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可能是异曲同工,从不同角度揭明了同一历史事实:周、秦时期,海贝确曾源源不断从中原地区来到过新疆。
五
前面提到的阿拉沟古代墓葬中,曾出土过多量的虎纹圆金牌、虎纹金箔带、虎纹图案银牌、熊头图案金牌等。虎的形象比较清楚,它们或蹲踞、或伫立、或呼啸奔跃。在出土虎纹金牌比较集中的第30号墓中,共见圆金牌8块,金牌直径6厘米。虎作昂首行进状,张嘴扬鬛,尾卷曲。金箔带长26厘米,其上两虎相向蹲踞,形象凶猛。在第47号墓中,一件虎形金箔,虎作伫立状,头转向一侧斜视,生动有神。在又一些兽纹银牌上,虎头形象已经图案化①。这么多贵金属的虎形牌饰,给人以强烈印象:老虎,在这里具有相当不一般的地位。与阿拉沟属同一地区,吐鲁番盆地中哈拉和卓附近的一处原始社会遗址,还发现过一块铜质虎形饰牌(原物现在新疆博物馆陈列),是同一性质的文化遗物。
对阿拉沟等地出土的多量虎纹金饰牌,应做怎样进一步的分析?结合历史发展分析,这应该是阿拉沟等地古代居民图腾崇拜的表现或遗留。在原始社会阶段曾经盛行过的图腾崇拜,相信人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而对它们保持一种特殊的迷信、崇拜。古代传说、考古发现、国内外民族学调查材料中,都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寻。在原始社会阶段,图腾信仰曾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过重大影响,绘画、雕刻、舞蹈、建筑等方面,都曾留下过这种烙印。
与这一逻辑分析并行不悖,从先秦时期有关西域地区的古文献记录中,我们发现了有关虎、豹类图腾崇拜的痕迹。
在《山海经》、《穆天子传》这两部古籍中,有不少关于“西王母”的描述。如《山海经·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穆天子传》称:“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绵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其他相类的关于西王母的记述尚多。对这些怪诞离奇的文字,正常情况就很难理解。但如果联系原始社会阶段氏族图腾崇拜现象来理解这些文字,我们就会得到一种全新的、生动而形象的原始氏族社会生活图景:所谓“西王母”,它是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一个氏族集团(从原始社会史看,这一阶段正是图腾崇拜的盛行期)。他们劳动、生息在“流沙之滨”、“昆仑之丘”的新疆地区。在这个氏族内,人们披发、戴项链,在氏族集会活动时,因为图腾信仰的关系,人们要戴虎头假面,身拖豹尾,发出虎的啸声,群聚歌舞。他们穴居洞中,是很勇敢的,传说可以制服天上的厉鬼并人间的“五残”。
《山海经》这部书,与《穆天子传》一样,对其成书时代、内容性质,研究者颇多,分歧很大、疑信不一。但是,可以指出一点,即使对它们持怀疑观点,大都也承认:这两部书即或晚出,也肯定包含着不少先秦时期的文字、素材。而持肯定观点者,则认为它们“未被秦以后儒家之润色”,文字的“离奇怪诞,正可窥见初民意识形态之真面目”。总的来看,这类古籍,大概不会是成于一入一时之手,有后期的增益删削,但也肯定保存着不少先秦时期的资料。
我们将阿拉沟、吐鲁番出土的虎形饰牌,结合《山海经》、《穆天子传》,关于西王母的描述,联系原始社会阶段肯定存在过的图腾崇拜,三者可以得到合理的统一。这使我们相信,古籍中有关西王母的描写,在怪诞不经的文字后面,包藏着深刻的新疆地区早期历史的科学内核。表现了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人们对祖国西部地区的认识和了解。
写作态度严谨的司马迁,在他的名著《史记·赵世家》中说:“缪王(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看来,对先秦文献中提到的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的事,2100年前的太史公也是相信的。
六
新中国成立前,在河南省新郑、汲县等地曾出土过一种青铜制造的莲鹤纹壶,壶体或方或圆,时代在春秋中期,或晚到战国初叶。
这种莲鹤纹方壶,有非常值得注意的造型特点。对此,郭沫若同志生前早就注意,并曾予以精辟分析。他说,新郑铜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纹饰,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而于莲瓣之中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脾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
对这件新郑壶及汲县山彪镇战国墓中出土的立鹤方壶,负责发掘工作的我国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生前亦曾有过介绍:新郑“莲鹤方壶为青铜时代转变期的一个代表作品。盖顶一鸟耸立,张翅欲飞,壶侧双龙旁顾,夺器欲出,壶底两螭抗拒,跃跃欲动,全部格局,在庞然大器的附着上,有离心前进动向..立鸟是立在一个长方形平板上,板心铸有爪迹凸起,为鸟与板原为联铸确证..1935年发掘汲县山彪镇,在一座王侯墓中,亦发现立鸟华盖壶两对,铜质银白,花纹精美,鸟立板心,盖中透空..汲、郑既不约而同,东周曾有此制流行,确可互证”。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会出现这么新颖的莲花立鹤形象?郭老的观点是:因为接受了印度文化艺术的影响。他曾明确说“以莲花为艺术创作之动机,且于莲花之中置以人物或它物者,此乃印度艺术中所习见之图案。盖赤道地方之大莲,硕大无朋,其叶若花每可以乘人载物也。此壶盖取材于莲花,覆于花心立一白鹤,与印度艺术之机杼颇相近似。中国自来无此图案,中国自来亦无是大莲。谓作者闭户造车,出门合辙,然必有相当之自然条件为前提,中国之小莲与此夸张之着想不相应。余恐于春秋初年或其前已有印度艺术之输入,故中原艺术家即受其影响也”①。
这一分析、论断,中肯有力,可以信从。不论是新郑或汲县铜壶,都是周代的传统形式,主体花纹也是传统的云纹、回纹等几何图案,龙耳螭足,为传统怪兽形象。现在,传统浓重的旧器上出现了源于现实生活的莲花、立鹤,印度的影响明显,据此自可窥见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与印度间存在思想、文化的交流。而此交流的途径,最大的可能,是取西域一途。
关于我国古代与印度联系的途径,据季羡林先生比较全面的分析,可有“南海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西域道”五条途径。这五条道路中,早期最主要的要算“西域道”,“西域道”是“丝路”干线:新疆和田地区古代居民操“和田塞语”,与印度西北部古代居民语言相同,交往便利;昆仑山北麓古代居民使用的佉卢语,也是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东部、阿富汗地区古代居民使用的俗语,彼此肯定交往频繁。在全面分析以后,季羡林先生结论“西域道”作为我国古代丝及丝织物西传印度的通路,有其特殊便利条件。①印度文化东传我国黄河流域的路线,通过新疆,同样是非常合理的。这一考古资料附着于此,既可以作为中原与新疆地区文化联系古远一例,也可以从这里看出当时中原地区经由新疆与印度交往的历史事实。
七
上述考古资料,可以肯定说明,在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之间,早就有着联系和交往。
这一事实,在先秦文献中,不可能没有反映。
前引《山海经》、《穆天子传》已有涉及,这里,再将一些比较清楚的记录,予以搜集。个别资料,稍予申说。
先秦阶段,文献中见到了有关昆仑、沙海、罗布淖尔、孔雀河等地理概念。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从一些感性的认识到最后形成文字,又有一个过程。实际存在的联系当较文献表明的要更早一些。
关于昆仑、流沙……的记录: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山海经·大荒西经》)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海内四经》)
“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屈原《天问》)
“按古图书,名河所出曰昆仑。”(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这条记录很重要。张骞公元前2世纪30年代,第一次出使西域,从南道过昆仑山返回到长安,对汉武帝刘彻报告所见所闻。刘彻即“按古图书”,名黄河所源之山为昆仑山(汉代,一直认为塔里木河是黄河源)。刘彻有可参考的古图古书,可见前引战国时期有关昆仑的记录,确系新疆境内的昆仑。
“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山海经·西山经》)
“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山东北隅,实唯河源。”(《山海经·北山经》)“泑泽”指罗布淖尔。“敦薨之水”,指孔雀河。直到汉、晋、南北朝阶段,中原地区仍持这一观点。
“魂乎无西!西方流沙,莽洋洋只……”(屈原《大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兮。五谷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兮。”(屈原《招魂》)
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的这些诗作,对没有水、没有生命、没有谷物、莽莽洋洋、无边无际的沙漠的描述,恰似局外人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印象,直如“进去出不来”这句话的注脚。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燃火之山,投物辄燃。”(《山海经·大荒西经》)这是过去未引起重视的一条记录,这很可能是中原地区对新疆昆仑山中存在火山活动的最早记录。在昆仑山中段,确实存在目前已停止活动的火山口。过去火山喷发的岩浆冷凝后形成的火山球,在策勒、于田县境不少地区,都还可以采集到。在尼雅、喀拉墩等古代遗址中,也可以采集到大大小小的火山球。这不仅表明昆仑山中火山的存在,而且表明古代新疆居民很早已注意到这一火山的存在。以这一客观事实对照《山海经》中的记录,说明战国时期的中原人对昆仑山有真实的认识了解。
关于中原用玉及玉石与月氏的关系:
“火燃昆仑,玉石俱焚。”(《尚书·胤征第四》)
“玉起于禺氏。”(《管子·国蓄篇》)
“玉起于禺氏之边山。”(《管子·地数篇》)
“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呼?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干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昆仑之墟可得而朝也。”(《管子·轻重甲篇》)
“禺氏”、“于氏”均月氏的异称,战国时期雄踞于甘肃地区。玉产于昆仑,通过月氏而进入中原。《尚书》、《管子》的这些记录,表现了战国时期的实际①。相类的文字记录还有,不一一具引。上列资料,颇可与前述实物资料互相呼应,增进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八
对汉代以前华北地区与新疆联系的通路,其性质及交通状况试作分析。
在《史记·赵世家》中,保留了一封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信。谈到“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己。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己”①。羊肠,是太行山中的径道。句注、常山,在今山西省北部代县、恒山一带。秦在陕西,如东进,控制了句注、常山这些晋北险要处所,东面可直达于燕(河北北部)。这样,赵国所需要的西北地区的良马、猎犬、昆仑玉就不能到手了。这封信,透露了一个历史信息。赵国(今山西东北部,河北西部地区)对西北地区的马、犬、玉常有所求,其路线是经过山西北部的“句注、常山”,而出句注、常山,即可进入河套地区;更西,可进入河西走廊。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年至前266年在位。因此,这一记录,很有力地说明了公元前3世纪初,华北平原与西北地区联系的大概路线。
战国时期,雄踞甘肃地区的,主要是月氏。上引《管子》一书中,将进入中原的玉均与月氏族联系,可见月氏当时实际控制了这条通道,也控制着这一中间贸易。《穆天子传》所述周穆王西行路线,也是跨太行山,过雁门岭,入河套,经甘肃、青海而入新疆。这与《史记·赵世家》、《管子》中有关记录,可以彼此呼应。
与西汉以后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不同的是,这一通道只是分段运行着的路线,没有汉朝以后那样统一的规制、建设,严密的管理、经营。如前引所见赵国与河套地区、历史文献中多见的秦与西戎(羌、氐)的联系,月氏与新疆及月氏向中原..都是关于这条通道的历史信息。
对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北、新疆地区的交往,张星烺曾有一个逻辑推论:“鄙意秦皇以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汉初执政者,皆丰、沛子弟,悉非秦人。秦国之掌故,鲜能道者,以致秦国与西域之交通事迹,史无详文也。”②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分析,结合上述资料,确可信从。
先秦阶段中原与西域地区间实际存在的经济、交通联系,对祖国西北、中原地区的开发、建设,都曾有过积极的作用。它是人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步开拓的。古代各族人民,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在这一事业中,有重大的历史贡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从河套地区进入甘、青,经河西走廊跨入新疆,实际是自然的、合理的过程,而且是并不困难的。这一历史的基础,就是张骞、甘父“凿空”的前提。
这一课题的完成,主要需凭藉考古工作的成果。
因为种种具体条件的局限,已经完成了的各种各类考古工作实际,并不一定能及时被各界人们所接触、了解。把足以说明西汉以前新疆地区与内地历史关系的考古资料,稍予整理、纂辑,并进行一定的分析,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深入,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因主要是考古资料的介绍,文字虽成系统,有材料堆积之疵,但望以此引发人们对这一课题的更大关心,促进这一研究课题的深入。
一
可能早到距今1万年前后的哈密地区七角井细石器遗址,其石器制作工艺,明显受到我国华北地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影响,生动表明了新疆地区和黄河流域十分久远的文化联系。这个问题,早有人们注意,但从未得到较为深入的说明、介绍。
国内外考古学界从宏观的角度,都注意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这就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世界范围内普遍见到采用特定工艺技术所生产的小型细石核、细石叶(长数厘米,宽不到1厘米、厚只1~2毫米的细长石片)和以细石叶为材料进一步加工成的细小石器,分布范围相当广、延续时间也相当长。它标志着当时人类的采集、渔猎生活有了新的发展、进步。而从石器加工技术、器物造型角度,又可据其异同分为两个大的系统:几何形细石器和细石叶细石器。几何形细石器分布于欧洲、北非、西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①,其特点是利用从圆体石核上打下窄长细石叶,并截断加工成规整的三角形、半月形和梯形等石刃。与之相对,细石叶细石器则主要分布于亚洲东、北部和美洲西、北部,包括新疆在内的我国、蒙古、西伯利亚、日本和白令海峡地区,美国阿拉斯加和加拿大部分地区。这里的特点是从扁体石核上打剥下窄长细石叶,并用此加工镞、钻、雕刻器等。对这一重大文化现象,国内外不少学者早就注意并揭明过这一事实。称这是“具有世界意后有源于西伯利亚、蒙古、我国华北地区等多种论点③。
经过近20年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这一问题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得到了比较合理的结论。这就是:它们起源在我国华北地区。这么广大的地区内,我国华北地区,最早在山西省许家窑旧石器时代遗址,就见到了细石器。经过测定,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10万年前④。更后,如距今3万年左右的山西朔县峙峪⑤,距今义的考古研究课②,但对细石叶细石器究竟起源在何处?怎样发展、传播?则有不同的看法,国内外先。题”1.8万多年的河南安阳小南海⑥等旧石器晚期遗址中,细石器趋向成型,工艺特征比较清楚。经过长时间发展,形成比较成熟的工艺传统,逐渐流行在黄河流域,并进而影响到我国广大地区及蒙古、西伯利亚、日本、阿拉斯加等处⑦。
地处亚洲腹地的新疆,哈密七角井、三道岭及吐鲁番阿斯塔那、罗布淖尔等处,都发现过细石器遗址。它们的造型特征明显属于我国华北地区类型,而与西南亚、欧洲地区所见细石器风格不同。对这一现象,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和我国学者杨钟健在首次向国内外介绍七角井的有关发现时,就注意到这个情况,稍后并正面作了阐发⑧。
为了对这一问题有较为具体的认识,我们以哈密七角井石器遗址为例,稍作深入说明。
在约3万平方米的范围内,用3天时间,即采集各类石器近1000件。石料主要为燧石,它们出土于距今1万年前后的全新世地层。从非常丰富的扁锥形石核、船底形石核到锥体、柱体石核,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修治石核、打剥石叶都有严格的工艺过程。从这些石核上打剥下来的细石叶与用细石叶加工出来的箭头、钻头、雕刻器等,已见出一定造型。利用拇指盖大小或稍大一点的厚石片,按一定方法压琢修治成有一定造型的刮削器,刃部锐薄。加上共存的以打制石片加工的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砍砸器等,很鲜明地表现了当时人们以采集狩猎为主体的生活内容。这些石器,据其造型、加工工艺特点,都可以看到它们与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期遗址,如山西下川①、河南许昌灵井②、陕西大荔沙苑③、黑龙江海拉尔松山④等处所见同类石器,表现了共同的特征。应该强调一句,选择特定的石料、修坯、制造石核,按一定方法打剥石片,进一步加工成合适的用器,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显示了的共同点,当然不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只能是同一种文化、技术影响下的产物,是新疆地区在距今1万年前后即与黄河流域存在文化交流的有力说明⑤。
在七角井细石器遗址,我们还采集到一件浅红色的珊瑚珠。珊瑚是海产。从七角井细石器工艺与黄河流域相同而与西南亚不同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近乎肯定:这件珊瑚原料,应该也是来自我国东部沿海。
二
时代较此稍后,还有另一件必须引起足够注意的可资说明新疆与中原地区久远联系的考古资料。1976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发掘了一座未经盗扰的殷王室墓葬。据墓内出土甲骨文、铜器铭文可以肯定,墓主人是殷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其死亡、入葬年代可以明确在公元前13世纪末叶至公元前12世纪初⑥也就是在,距今3200年前后。在这座规模不算大的墓葬中,共出土随葬器物1928件,,其中有玉器756件(少量残片未计),玉器占出土器物的39.2%。这批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优美,包括礼器、仪仗、日用器及大量装饰品。埋葬3000多年后出土,多数玉器光泽依然晶莹鲜润,表现了当时在琢玉工艺、抛光技术方面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注意。
有关这批玉料的产地,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为取得比较可靠的结论,曾取各类标本300多件送请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单位进行鉴定。结论是除3件标本外,均属新疆玉。包括“青玉、白玉(内有极少量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糖玉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白玉、青白玉很少,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①。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结论。
我们知道,商、殷王朝使用玉器数量是十分巨大的。《逸周书·世俘解》称:“..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②(清王念孙校读为“凡武王俘商,得获宝玉万四千)证之以妇好墓,一次出土即达750多件,《逸周书》中有关殷王室大量用玉的记录,可能接近于真实。
商,殷王室大量用玉,而玉料又主要取之于新疆地区,这就再一次以有力的考古资料揭明了新疆与中原地区存在的经济联系。
先秦时期的文献如《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对古代中原地区用玉,而且玉取自和田、昆仑,有不少记录。但人们对这些记录,往往是疑信参半。现在有殷墟这批玉器出土,则可以肯定,先秦时期关于内地用新疆玉的记录,去事实绝不会太远。
早到新石器时代,内地不少遗址中即见用玉。可能与夏文化有关的河南省偃师二里头墓葬,玉器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由于玉石的温润光洁,历代统治阶级都以玉德自比,用玉风气有盛无衰,需玉数量也非常大。这一趋势,直至清代不改。而新疆又是全国最主要的、也是玉质最好的一处软玉产地。在玉石东去中原的历史中,凝结着新疆与祖国内地之间密切、久远的经济联系。
三
关于我国中原地区丝织物的西传,是早就被注意,并有不少学者写过文章的。这里的介绍,不多涉及文献,主要以考古资料中所见实物为主。
1976~1978年,配合南疆铁路工程,笔者曾在吐鲁番盆地西缘,天山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段,主持、参与了一大批古代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墓葬出土文物丰富,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特点。墓葬主人主要经营畜牧业,饲养羊、骡、马。衣着材料是各式毛织物。墓内出土的多量彩陶器很有特点。综合分析出土文物特征,结合有关碳14测定资料,墓地延续了相当一个历史阶段,主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最晚到汉③。
测定为春秋阶段的第28号墓(碳14测定结论为距今2620士165年),其中出土了一件凤鸟纹刺绣。在长、宽均20多厘米的素色绢地上,用绿色丝线锁绣出凤鸟图案。由于原件已残破,完整图案形象已难明,但残余部分仍可见到凤鸟的躯体,微曲的腿、爪(原物现在新疆博物馆陈列)。这件文物,不论是丝绢本身,还是其上的凤鸟图案,一目了然,属于中原地区的产品无疑。
在测定为战国至汉代阶段的第30号墓中(测定数据一为距今2345±75年;又一为距今2090±95年),与大量具有战国阶段风格的野兽纹金、银、铜器共存,有一块规规整整的用黄黏土做成的方泥饼,边长15厘米、厚2.5厘米。原来用菱纹链式罗包裹。丝罗已朽,但因为黏土质地致密,菱纹罗痕迹却十分清晰地印存黏土面上。其细密的组织,非丝莫属。这一印纹照片,曾刊布于《文物》1981年第1期图版捌:5。
与新疆地区邻境,苏联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区巴泽雷克古墓葬,是世界知名的一处古代塞人文化遗址①。在结论为公元前1000年中叶的这批墓葬中,出土了不少我国丝绣织物。“某些巨墓中出土的中国织物,有用大量的捻股细丝线织成(每平方厘米为34×50支)的普通平纹织物。这些织物,有小块的,也有整幅的(铺盖在皮衣服的上面)”。“其中图案和制作技术最为特殊的,是巴泽雷克第3号墓出土的一块有花纹的丝织物。这块丝织物,1平方厘米为18×24支纱,由一经两纬织成。丝织物为1/3和3/1斜纹(即三下一上或三上一下的斜纹)”。“巴泽雷克第五号墓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这是一块鞍褥面,制作技术为平纹,1平方厘米为40×52支纱,宽约43厘米。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连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的形象是极其多样化的”。“它的富于表现力的形象和优美的色调,无疑的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品”。“发现有凤凰绣缎的墓葬”,主要可以根据西亚细亚出产的织物——羊毛绒毯和非常细密的羊毛织品——准确地断其为公元前5世纪的墓葬。根据这些资料,苏联学者肯定“中国与苏联阿尔泰居民的最早关系是发生于公元前第一千年的中叶”。
我们需要在这里附带说明的,一是前述阿拉沟第28号墓的凤鸟纹刺绣,其中刺绣技法、凤鸟图案风格,与巴泽雷克古墓中所见凤鸟纹图案风格、刺绣技法,是一致的。再是,邻境的苏联阿尔泰地区与我国中原地区的交往事实,也完全可以帮助我们考虑当日中原与新疆地区联系的实际。
阿拉沟,并非古代通衢要道,也不是由比较大的绿洲构成的古代重要政治、经济中心。但就在这样比较偏僻的山区古墓葬中,同样见到了来自中原的菱纹罗、凤鸟纹刺绣,这个事实对于揭明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已传到新疆,并及于更多的其他地方,是有很大说服力的。
在这一背景下,再去认识印度文献记录,比如憍胝厘耶著的《治国安邦术》,其中提到“憍奢耶和产生在支那的成捆的丝”(憍胝厘耶据说是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月护大王的侍臣),亦即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已经去到印度①,就是完全不难理解的了。
四
与丝绣相类,漆器、铜镜也是我国中原地区的传统产品,汉代以前,新疆地区已见。另外,还见到产自东海、南海的贝类。
(一)漆器
阿拉沟第18号墓葬,时代为战国。这里出土漆盘一件。见于“墓室西头木椁外。径16厘米。木胎,已朽,只余内外漆皮,黑色地,朱红彩,绘弦纹四道,盘底绘流云纹”②。
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阿拉沟第30号墓葬中,也曾见到漆器多件。漆器置与墓室西头,与承兽铜盘、陶器、木盆、兽骨、泥饼等随葬文物并列一起,漆器彼此叠置。清理中,发现这组漆器胎质已朽,只有漆皮,为沙土覆压。当时采取措施,在漆器周围沙土上挖槽,而后灌浇石膏,企图连沙土,并漆皮浇灌一块,运回室内剥离、修复。十分可惜的是这一石膏块灌封未严,在汽车长途运输中沙土散裂,返至室内后未能取得完好漆器标本。部分曾送北京修复,亦未奏功。这里的漆器标本虽已不存,但墓内曾随葬多件漆器,是毫无疑问的。
阿拉沟第23号墓,时代较第18、30号墓要稍早,其中出土残耳环一件,木胎,胎质较厚,黑色漆地,绘朱红色彩,显云纹图案。这一标本,在文物出版社《文物》特刊第40期(1977年12月15日)曾刊发过照片。
阿拉沟墓地的时代,主要在春秋、战国阶段,这么多件漆器标本在阿拉沟墓地出土,说明汉代以前,曾有相当数量的中原地区漆器西来新疆,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
(二)铜镜
1963年,笔者与易漫白、王明哲同志一道,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发掘过32座石人、石棺墓葬。时代上起殷周,下迄隋唐,延续时间相当长。在其中第22号墓葬中,出土铜镜一件,“直径仅六厘米,平素无纹,弓钮无座”。它“是古代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它的形制和大小都与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基本一致”。“这面铜镜的出土,说明新疆,包括北疆在内的古代少数民族,在古远的历史时期,已经和中原的汉族文化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①(就在同一墓地内,第24号墓葬内,曾出土黄色豆形陶器一件,饰几何形划纹,通高7.5厘米。其“形制与中原地区春秋时代出土的陶豆颇有渊源关系”)。
早期铜镜,在前引苏联阿勒泰巴泽雷克墓地中也有所见,“在巴泽雷克第6号墓中,发现白色的金属制的中国镜一面,即所谓秦式镜的变形之一。镜体虽已破损(保存了二分之一强),但我们仍然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因为在阿尔泰山西麓的一个墓葬中,也发现了一面完全相同的镜子”。“这两面镜子的直径,均为11.5厘米。质地薄脆,镜面极为光滑。边缘为素卷边,在镜背稍凸起的方形钮座中心,置一小弦钮。地纹为美丽的、单一的所谓‘羽状’纹。羽状纹地上,沿边缘置以四个‘山’字形雕饰。在山字纹之间,有成对的心状叶形”。“发现上述金属镜的数处墓葬,年代则比较晚,属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②。根据上引C.N.鲁金科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属于我国战国阶段流行的山字纹铜镜,是典型的中原地区产品。
(三)海贝
新中国成立前,在罗布淖尔地区的原始社会阶段墓地中,出土过海菊贝制成的珠饰。海菊贝,是只产于我国东南沿海的贝类。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哈密五堡,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两处墓地,见到了不少海贝。
五堡墓地是距今3000年前后的一处原始社会阶段墓地。这里所见贝类标本,主要用为装饰品,如佩饰于毛织围巾、衣服上。共见标本十多件,经初步鉴定,品种主要属“货贝”。
阿拉沟墓地所见海贝,主要置于死者头侧、臂侧,似作为装饰品。个别海贝含放于死者口中。贝在这里,是作为一种贵重珍品了。死者口中含贝,中原地区,商代有这样的习俗。更晚一点,则口中含钱。吐鲁番晋、唐时期墓葬中,死者口中有含波斯银币的。在阿拉沟发现的海贝数量,较哈密五堡墓地稍多。经鉴定,除货贝外,还有环纹货贝。
货贝、环纹货贝的产地相当广泛。我国东部渤海、黄海以至南海,均见出产。西南亚的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亦见。但联系有关文献资料,含贝以葬的风俗,前述南海海菊贝先例。笔者认为,它们来自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我国古代,对贝十分珍视。“宝”字繁体从“贝”,“宝贝”一词,在汉语文中一直用来形容珍贵物品。商代,曾以贝作货币。考古工作中,曾见到过铜贝。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穆天子传》有关的一部分记录:述及周穆王抵达一地,与当地首领应酬、互相赠礼时,穆王赠礼,几乎都有“贝带”一项。对于《穆天子传》此书,史学界看法、评价不一。但对于此书最晚成于战国之时(或更早),表现了周、秦阶段对祖国西北地区、包括今新疆一带的了解,则基本没有异词。现在,哈密、阿拉沟、罗布淖尔等地,都见到了海贝,有的海贝只产于我国东、南沿海。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可能是异曲同工,从不同角度揭明了同一历史事实:周、秦时期,海贝确曾源源不断从中原地区来到过新疆。
五
前面提到的阿拉沟古代墓葬中,曾出土过多量的虎纹圆金牌、虎纹金箔带、虎纹图案银牌、熊头图案金牌等。虎的形象比较清楚,它们或蹲踞、或伫立、或呼啸奔跃。在出土虎纹金牌比较集中的第30号墓中,共见圆金牌8块,金牌直径6厘米。虎作昂首行进状,张嘴扬鬛,尾卷曲。金箔带长26厘米,其上两虎相向蹲踞,形象凶猛。在第47号墓中,一件虎形金箔,虎作伫立状,头转向一侧斜视,生动有神。在又一些兽纹银牌上,虎头形象已经图案化①。这么多贵金属的虎形牌饰,给人以强烈印象:老虎,在这里具有相当不一般的地位。与阿拉沟属同一地区,吐鲁番盆地中哈拉和卓附近的一处原始社会遗址,还发现过一块铜质虎形饰牌(原物现在新疆博物馆陈列),是同一性质的文化遗物。
对阿拉沟等地出土的多量虎纹金饰牌,应做怎样进一步的分析?结合历史发展分析,这应该是阿拉沟等地古代居民图腾崇拜的表现或遗留。在原始社会阶段曾经盛行过的图腾崇拜,相信人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而对它们保持一种特殊的迷信、崇拜。古代传说、考古发现、国内外民族学调查材料中,都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寻。在原始社会阶段,图腾信仰曾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过重大影响,绘画、雕刻、舞蹈、建筑等方面,都曾留下过这种烙印。
与这一逻辑分析并行不悖,从先秦时期有关西域地区的古文献记录中,我们发现了有关虎、豹类图腾崇拜的痕迹。
在《山海经》、《穆天子传》这两部古籍中,有不少关于“西王母”的描述。如《山海经·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穆天子传》称:“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绵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其他相类的关于西王母的记述尚多。对这些怪诞离奇的文字,正常情况就很难理解。但如果联系原始社会阶段氏族图腾崇拜现象来理解这些文字,我们就会得到一种全新的、生动而形象的原始氏族社会生活图景:所谓“西王母”,它是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一个氏族集团(从原始社会史看,这一阶段正是图腾崇拜的盛行期)。他们劳动、生息在“流沙之滨”、“昆仑之丘”的新疆地区。在这个氏族内,人们披发、戴项链,在氏族集会活动时,因为图腾信仰的关系,人们要戴虎头假面,身拖豹尾,发出虎的啸声,群聚歌舞。他们穴居洞中,是很勇敢的,传说可以制服天上的厉鬼并人间的“五残”。
《山海经》这部书,与《穆天子传》一样,对其成书时代、内容性质,研究者颇多,分歧很大、疑信不一。但是,可以指出一点,即使对它们持怀疑观点,大都也承认:这两部书即或晚出,也肯定包含着不少先秦时期的文字、素材。而持肯定观点者,则认为它们“未被秦以后儒家之润色”,文字的“离奇怪诞,正可窥见初民意识形态之真面目”。总的来看,这类古籍,大概不会是成于一入一时之手,有后期的增益删削,但也肯定保存着不少先秦时期的资料。
我们将阿拉沟、吐鲁番出土的虎形饰牌,结合《山海经》、《穆天子传》,关于西王母的描述,联系原始社会阶段肯定存在过的图腾崇拜,三者可以得到合理的统一。这使我们相信,古籍中有关西王母的描写,在怪诞不经的文字后面,包藏着深刻的新疆地区早期历史的科学内核。表现了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人们对祖国西部地区的认识和了解。
写作态度严谨的司马迁,在他的名著《史记·赵世家》中说:“缪王(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看来,对先秦文献中提到的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的事,2100年前的太史公也是相信的。
六
新中国成立前,在河南省新郑、汲县等地曾出土过一种青铜制造的莲鹤纹壶,壶体或方或圆,时代在春秋中期,或晚到战国初叶。
这种莲鹤纹方壶,有非常值得注意的造型特点。对此,郭沫若同志生前早就注意,并曾予以精辟分析。他说,新郑铜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纹饰,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而于莲瓣之中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脾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
对这件新郑壶及汲县山彪镇战国墓中出土的立鹤方壶,负责发掘工作的我国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生前亦曾有过介绍:新郑“莲鹤方壶为青铜时代转变期的一个代表作品。盖顶一鸟耸立,张翅欲飞,壶侧双龙旁顾,夺器欲出,壶底两螭抗拒,跃跃欲动,全部格局,在庞然大器的附着上,有离心前进动向..立鸟是立在一个长方形平板上,板心铸有爪迹凸起,为鸟与板原为联铸确证..1935年发掘汲县山彪镇,在一座王侯墓中,亦发现立鸟华盖壶两对,铜质银白,花纹精美,鸟立板心,盖中透空..汲、郑既不约而同,东周曾有此制流行,确可互证”。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会出现这么新颖的莲花立鹤形象?郭老的观点是:因为接受了印度文化艺术的影响。他曾明确说“以莲花为艺术创作之动机,且于莲花之中置以人物或它物者,此乃印度艺术中所习见之图案。盖赤道地方之大莲,硕大无朋,其叶若花每可以乘人载物也。此壶盖取材于莲花,覆于花心立一白鹤,与印度艺术之机杼颇相近似。中国自来无此图案,中国自来亦无是大莲。谓作者闭户造车,出门合辙,然必有相当之自然条件为前提,中国之小莲与此夸张之着想不相应。余恐于春秋初年或其前已有印度艺术之输入,故中原艺术家即受其影响也”①。
这一分析、论断,中肯有力,可以信从。不论是新郑或汲县铜壶,都是周代的传统形式,主体花纹也是传统的云纹、回纹等几何图案,龙耳螭足,为传统怪兽形象。现在,传统浓重的旧器上出现了源于现实生活的莲花、立鹤,印度的影响明显,据此自可窥见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与印度间存在思想、文化的交流。而此交流的途径,最大的可能,是取西域一途。
关于我国古代与印度联系的途径,据季羡林先生比较全面的分析,可有“南海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西域道”五条途径。这五条道路中,早期最主要的要算“西域道”,“西域道”是“丝路”干线:新疆和田地区古代居民操“和田塞语”,与印度西北部古代居民语言相同,交往便利;昆仑山北麓古代居民使用的佉卢语,也是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东部、阿富汗地区古代居民使用的俗语,彼此肯定交往频繁。在全面分析以后,季羡林先生结论“西域道”作为我国古代丝及丝织物西传印度的通路,有其特殊便利条件。①印度文化东传我国黄河流域的路线,通过新疆,同样是非常合理的。这一考古资料附着于此,既可以作为中原与新疆地区文化联系古远一例,也可以从这里看出当时中原地区经由新疆与印度交往的历史事实。
七
上述考古资料,可以肯定说明,在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之间,早就有着联系和交往。
这一事实,在先秦文献中,不可能没有反映。
前引《山海经》、《穆天子传》已有涉及,这里,再将一些比较清楚的记录,予以搜集。个别资料,稍予申说。
先秦阶段,文献中见到了有关昆仑、沙海、罗布淖尔、孔雀河等地理概念。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从一些感性的认识到最后形成文字,又有一个过程。实际存在的联系当较文献表明的要更早一些。
关于昆仑、流沙……的记录: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山海经·大荒西经》)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海内四经》)
“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屈原《天问》)
“按古图书,名河所出曰昆仑。”(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这条记录很重要。张骞公元前2世纪30年代,第一次出使西域,从南道过昆仑山返回到长安,对汉武帝刘彻报告所见所闻。刘彻即“按古图书”,名黄河所源之山为昆仑山(汉代,一直认为塔里木河是黄河源)。刘彻有可参考的古图古书,可见前引战国时期有关昆仑的记录,确系新疆境内的昆仑。
“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山海经·西山经》)
“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山东北隅,实唯河源。”(《山海经·北山经》)“泑泽”指罗布淖尔。“敦薨之水”,指孔雀河。直到汉、晋、南北朝阶段,中原地区仍持这一观点。
“魂乎无西!西方流沙,莽洋洋只……”(屈原《大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兮。五谷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兮。”(屈原《招魂》)
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的这些诗作,对没有水、没有生命、没有谷物、莽莽洋洋、无边无际的沙漠的描述,恰似局外人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印象,直如“进去出不来”这句话的注脚。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燃火之山,投物辄燃。”(《山海经·大荒西经》)这是过去未引起重视的一条记录,这很可能是中原地区对新疆昆仑山中存在火山活动的最早记录。在昆仑山中段,确实存在目前已停止活动的火山口。过去火山喷发的岩浆冷凝后形成的火山球,在策勒、于田县境不少地区,都还可以采集到。在尼雅、喀拉墩等古代遗址中,也可以采集到大大小小的火山球。这不仅表明昆仑山中火山的存在,而且表明古代新疆居民很早已注意到这一火山的存在。以这一客观事实对照《山海经》中的记录,说明战国时期的中原人对昆仑山有真实的认识了解。
关于中原用玉及玉石与月氏的关系:
“火燃昆仑,玉石俱焚。”(《尚书·胤征第四》)
“玉起于禺氏。”(《管子·国蓄篇》)
“玉起于禺氏之边山。”(《管子·地数篇》)
“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呼?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干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昆仑之墟可得而朝也。”(《管子·轻重甲篇》)
“禺氏”、“于氏”均月氏的异称,战国时期雄踞于甘肃地区。玉产于昆仑,通过月氏而进入中原。《尚书》、《管子》的这些记录,表现了战国时期的实际①。相类的文字记录还有,不一一具引。上列资料,颇可与前述实物资料互相呼应,增进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八
对汉代以前华北地区与新疆联系的通路,其性质及交通状况试作分析。
在《史记·赵世家》中,保留了一封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信。谈到“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己。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己”①。羊肠,是太行山中的径道。句注、常山,在今山西省北部代县、恒山一带。秦在陕西,如东进,控制了句注、常山这些晋北险要处所,东面可直达于燕(河北北部)。这样,赵国所需要的西北地区的良马、猎犬、昆仑玉就不能到手了。这封信,透露了一个历史信息。赵国(今山西东北部,河北西部地区)对西北地区的马、犬、玉常有所求,其路线是经过山西北部的“句注、常山”,而出句注、常山,即可进入河套地区;更西,可进入河西走廊。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年至前266年在位。因此,这一记录,很有力地说明了公元前3世纪初,华北平原与西北地区联系的大概路线。
战国时期,雄踞甘肃地区的,主要是月氏。上引《管子》一书中,将进入中原的玉均与月氏族联系,可见月氏当时实际控制了这条通道,也控制着这一中间贸易。《穆天子传》所述周穆王西行路线,也是跨太行山,过雁门岭,入河套,经甘肃、青海而入新疆。这与《史记·赵世家》、《管子》中有关记录,可以彼此呼应。
与西汉以后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不同的是,这一通道只是分段运行着的路线,没有汉朝以后那样统一的规制、建设,严密的管理、经营。如前引所见赵国与河套地区、历史文献中多见的秦与西戎(羌、氐)的联系,月氏与新疆及月氏向中原..都是关于这条通道的历史信息。
对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北、新疆地区的交往,张星烺曾有一个逻辑推论:“鄙意秦皇以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汉初执政者,皆丰、沛子弟,悉非秦人。秦国之掌故,鲜能道者,以致秦国与西域之交通事迹,史无详文也。”②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分析,结合上述资料,确可信从。
先秦阶段中原与西域地区间实际存在的经济、交通联系,对祖国西北、中原地区的开发、建设,都曾有过积极的作用。它是人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步开拓的。古代各族人民,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在这一事业中,有重大的历史贡献。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从河套地区进入甘、青,经河西走廊跨入新疆,实际是自然的、合理的过程,而且是并不困难的。这一历史的基础,就是张骞、甘父“凿空”的前提。
附注
①安志敏:《南澳大利亚的石器》,载《考古》,1974(6)399~405。
②③⑦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载《考古学报》,1978(3);盖培:《从华北到美洲——关于华北与北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联系》,载《化石》,1972(2)。
④贾兰坡等:《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4)。此文提出:“许家窑的漏斗状石核和原始棱柱状石核,分别是华北以至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普遍使用的锥状石核(或铅笔头型石核)和棱柱状石核的母型。”
⑤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2(1)。
⑥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载《考古学报》,1965(1)。
⑧德日进、杨钟健:《在蒙古、新疆和中国西部地区发现的一些新石器和可能是旧石器时代遗址》,见《中国地质学集刊》,第12卷,92~95页,1933。
①王健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2)。
②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载《考古》,1974(2)。
③安志敏、吴汝祚:《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载《考古学报》,1957(3)
④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载《考古学报》,1978(1)。
⑤关于七角井细石器遗址的性质,前引安志敏在有关陕西朝邑大荔、海拉尔松山的报告均有论及。在安志敏《三十年来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载《考古》,1979年5期)亦有分析。我们对七角井遗址也进行过详细调查,资料现存新疆考古所。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22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11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②《逸周书》卷四。
③有关测定数据,发表于《文物》,1978(5)。
①C.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载《考古学报》,1957(2)
①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76~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②新疆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图八:漆盘出土情况,载《文物》,1981(1)。
①新疆社科院考古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1)。
②C.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载《考古学报》,1957(2)。
①新疆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墓发掘简报》,图八:漆盘出土情况,载《文物》,1981(1)
①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一、二考释》、《新郑古器中“莲鹤壶”的平反》,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①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76~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①《管子》一书,各篇成书时代不一。有人认为这里所引各篇多成书于汉文景时。实则不然。内地用玉,时代很早,战国时期有此类记录是毫不足怪的。
①《史记》卷三十四。②《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上古时代的中外交通》。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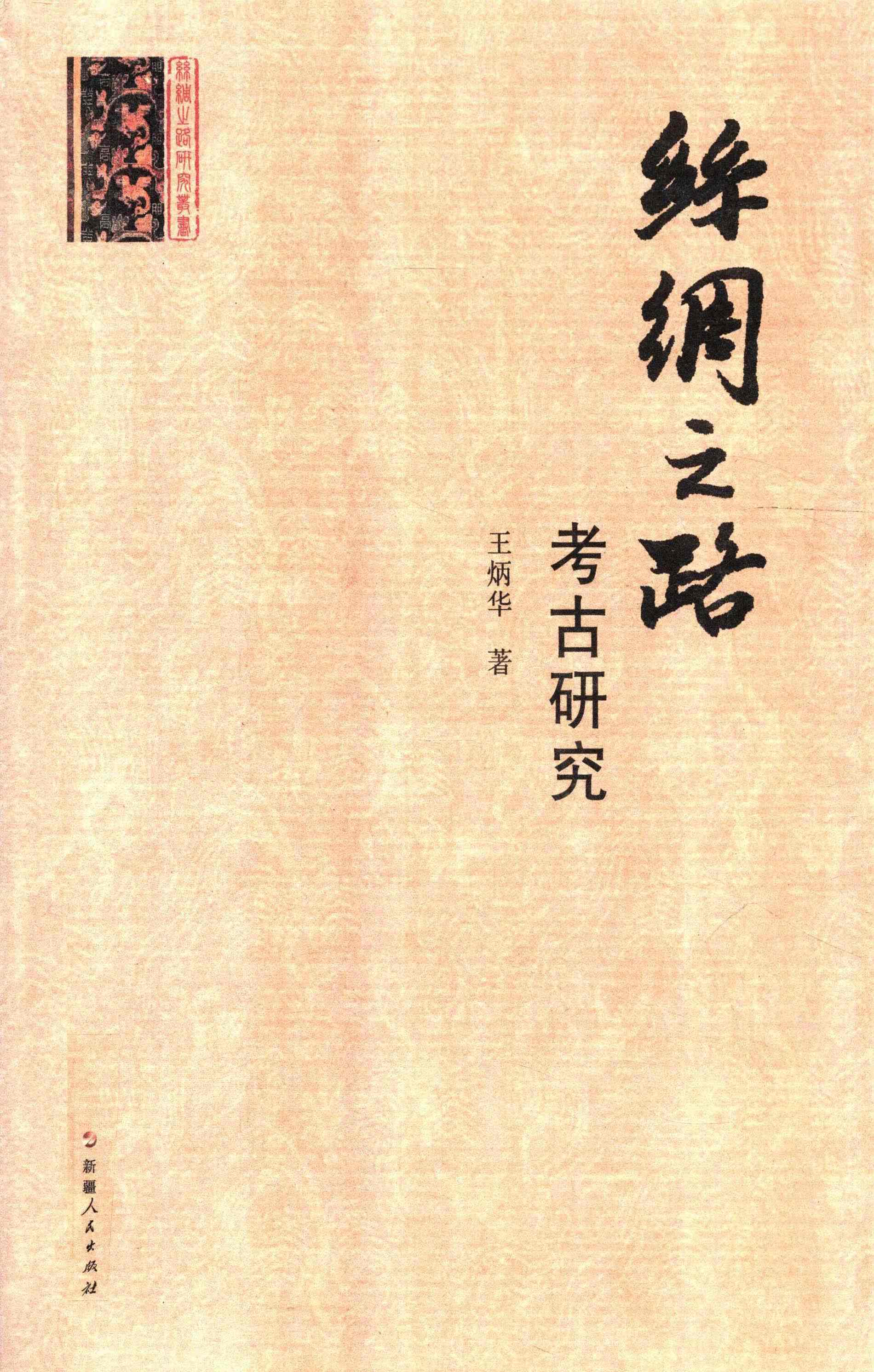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