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71 |
| 颗粒名称: | 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 |
| 分类号: | K878.9 |
| 页数: | 14 |
| 页码: | 108-12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关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不论是其绝对年代,还是具体的文化内涵,都还是一个新的待研究的命题,至今还没有见到从这方面提出分析、进行探索的文章。换一句话说,这还是新疆考古领域中须待填补的空白。在国内先后出版的有关我国青铜器的重要专著,如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 |
| 关键词: | 新疆 青铜 考古 |
内容
关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不论是其绝对年代,还是具体的文化内涵,都还是一个新的待研究的命题,至今还没有见到从这方面提出分析、进行探索的文章。换一句话说,这还是新疆考古领域中需待填补的空白。
在国内先后出版的有关我国青铜器的重要专著,如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成书较早,资料所及多在中原地区,对新疆的青铜器文化没有一字一词涉及。这反映了一个问题,说明了这方面研究十分薄弱。导致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新疆地区考古文化存在什么特殊情况,曾超越过青铜时代这一发展阶段。相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疆地区已发现不少属于这一时代的重要遗址和墓葬,在工农业生产中,也有不少重要的青铜器文物出土。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一是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对这方面的一些重要发现,认识不足,未能及时给予报道;再是对已有的并经报道了的发现,未能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做必要的概括、研究。这些明显的弱点,自然局限了对问题的认识,影响着研究的深入。
在目前这样一个工作基础上,要对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各主要方面作出比较清楚、比较准确的说明,困难是很大的。但对已有的资料进行初步的概括,从一定的理论高度进行分析,也会明显地推动问题的深入。因此,我在这里提出的新疆青铜时代的起始、繁荣阶段,它的基本特征及与周围地区的关系等,都只能是很初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是一个提供讨论的意见。希望在进一步的讨论,尤其是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修正、提高,逐步完善。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我个人的看法是:从公元前2000年前起,新疆地区已陆续步入了青铜时代。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青铜文化呈现了相当的繁荣,铜器使用相当普遍,铜矿开采也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进入战国时代,出现铁器,实现了向铁器时代的转化。由于新疆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从青铜器造型、风格上看,与邻近的中亚地区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同时,与蒙古草原地区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有相当鲜明的地区特点。
一
我之所以提出,在公元前2000年,新疆地区已经步入青铜时代,主要根据有二:一是罗布淖尔地区古墓沟墓地的发掘,二是在伊犁河流域巩留县阿格尔森所采集的一批青铜器。这两批资料,目前虽只是两个点,但却代表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域。
1979年冬,新疆考古研究所派人到罗布淖尔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于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进行了发掘。笔者主持了这一工作。参加这一墓地发掘工作的还有伊弟利斯·阿不都、邢开鼎、刘玉生、常喜恩等。古墓沟墓地,共见古代墓葬42座,全部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可区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为竖穴木棺墓,浅葬,木质葬具保存完好。二类同样为竖穴,但埋葬深,葬具已朽。墓穴外附七圈环形列木,环形木圈外,见放射状四向展开的木桩。曾观察木桩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墓葬,木桩总数达894根。从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分析,第二类型墓葬相对较晚。关于墓地的绝对年代,据第一类墓葬中多组测定数据,为距今3800年前的遗存。在这一墓地的两类墓葬中,均发现过小铜卷、小铜片。这些小件铜器,与木器、石器(细石镞)、骨、玉饰物、小麦籽粒、草编器、毛织物(布、毯、毡)及牲畜皮毛等共存。因所出小件铜器不仅造型过小、形制难辨,而且朽蚀相当严重,既难判明铜器制作工艺,也无法据以分析铜器在当时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当时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①。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对墓地内所出木器及木桩进行仔细观察、分析以后。详细、认真分析了墓地内出土木材及有关器物上保留至今的工具痕迹,不能不予确认:在当时的古墓沟地区,无可怀疑,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着一种相当锐利的金属砍伐工具。其硬度、锐利程度,不是磨制石器或红铜工具所能达到的。这种工具,当以青铜器最为合理。因此,这一墓地,虽无大型青铜器出土,但却同样为我们认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资料。
因地理环境十分干燥,古墓沟墓地内,木、骨、皮等制器,大多均完好如入土之时。未朽之板材,叩击仍铿然作声。当年加工板材遗留的大量工具印痕,也清楚明晰。分析这些痕迹,对于判明所使用工具的性质及其锐利程度,是很有说服力的。
墓地内所用木材,多为胡杨。胡杨本质细密,硬度较大。将直径二三十厘米的胡杨树干,砍断、削平,形成棺木类葬具;或砍削出锐尖,形成木桩,都并非易事。古墓沟墓地内发掘的42座墓葬,第一类型墓葬占36座。墓葬内几乎都见木“棺”。这类木“棺,”是在沙穴上,置厢板、挡板,尸体放人后,覆盖多块小木板。这些板块,都取胡杨木为料,砍削成比较平整的板材,长短、厚薄比较一致,边棱整齐,加工工具,明显是比较得心应手的。第二类墓葬葬具虽朽,但保存完好的木桩、木柱至夥。直径二三十厘米的粗胡杨木,都要砍出锐尖,才能深揳入地下深处。笔者曾观察、记录了一直径23厘米、长110厘米的粗大胡杨木,一端砍削出非常锐利的尖锥。尖锥长28厘米,端部锐尖不到1厘米,尖锐部分砍削痕迹既光洁又整齐。还曾对取回乌鲁木齐的部分葬具、木桩,选择砍削痕迹清楚的进行了分析、统计。在统计的240个数据中,可以看出:砍痕均圆刃工具所致。刃宽一般在3~5厘米,最狭的1.5厘米。一次砍进深度,最深达10.5厘米,一般砍进深度也在3~5厘米。砍削痕迹均相当光洁、干净,不见毛毛糙糙的砍痕。砍进这么深,而且砍痕这么光滑洁净,是一切钝的、轻的非金属类工具所不能达到的。换句话说,只有比较锐利、比较厚重的金属斧类工具,才能造成这样的砍削效果。在古墓沟墓地,还出土了木雕人像、木杯、木盘多件。一些木器,利用一段木料的自然形状掏挖,说不上精致,但也不乏加工精细的标本。如木雕女性人像,经过细致刻削,很形象地表现了人物头戴尖顶毡帽、梳辫、尖下颏、丰满而垂下的双乳。辫形整齐、辫纹清晰、垂于脑后。尖帽、下颏、双乳,削刻均十分匀称,刻削痕迹干净利索。笔者曾有机会观察用石斧砍伐、加工木器的试验。粗大、刃部锐利的石斧,以之砍伐小树,十多分钟可将直径10厘米上下的树杆砍断。遗留痕迹是:砍痕十分粗糙,加工面毛糙不齐,每次用力砍伐,砍进深度不足1厘米,或勉强达到1厘米。这与古墓沟墓地木桩、棺木、木器
上保留至今的砍伐痕迹相比,无论在砍进深度、砍痕光洁程度方面,都判然有别。这么深而且光洁的砍痕,明显是须要刃部锐利,而且相当厚重的斧、斤类金属工具才能奏效的。
还应该说明的一点是:这类砍痕,如果只是个别、少数存在,自然也可以考虑其他可能性。而现在的观察结论是:在任何墓葬,任何一件木器、棺具、木桩上,都随处可以找到多量的、特征一致的砍伐痕迹。这就显示了一种普遍的、一般性现象。笔者取回乌鲁木齐供分析的葬具及木桩标本,与墓地出土木材相比,只是十分小的、可以说是不成比例的一点资料。在这些标本上随意观察、统计砍伐痕迹,明确无误、特征明显的数据即达240组。这足以说明,在当时的古墓沟地区,金属生产工具在社会生产中已占重要地位。而不是一种个别的、孤立的存在。常识告诉我们:因为红铜质软、硬度不够,所以并不能在生产中排除、取代石器。古墓沟墓地所见锐利的砍痕,在砍木上砍进深度一般都达四五厘米,最深可达10厘米以上,是红铜质及石质工具所不能达到的。只有青铜工具,或较青铜硬度更大、更锐利的工具,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从整个历史背景分析,这种金属工具,当然以青铜器为宜。因此,目前虽没有直接见到青铜工具实物,判定当时使用的主要是青铜器,还是比较合理的。既然这样,为什么在全墓地内,一件青铜器工具也没有发现?主要原因可能是:这类金属工具,在当时还是十分珍贵的生产手段,取得它们也很不容易。而且,这类工具,与人们现实的经济生活利益关系重大,所以,一般都不用于殉葬。
既然逻辑推论表明:古墓沟阶段,已经出现了相当锐利,可用于砍伐硬木、加工板材的青铜工具,在社会生产中使用还比较普遍,自然就可以结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已经步入了青铜时代。当然,这个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物资料直接证明。但可以相信,这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与古墓沟墓地年代相近,在北疆伊犁河谷地巩留县境,发现过又一批青铜器。1975年,新疆博物馆王博、成振国同志,在巩留采集得青铜工具12件。铜器出土于阿格尔森。群众在这里开挖水渠,于距地表1米多深的地下,发现3件铜斧,3件铜镰、钲、凿等,共12件①。斧刃圆弧,弯柄圆銎,柄部饰焦叶纹,分大小两种。镰作弯背弧刃,使用痕迹明显,磨损较重。12件铜器,均是实用生产工具,而且农业生产工具占有较大比重。有关铜器出土后,对其金属成分,曾送请北京钢院冶金史研究所进行分析,结论为青铜工具无疑。
对这批铜器资料有关考古文化的具体内容,因非正式发掘,目前还无法提供更多的具体说明。但铜斧、铜镰的形制,与中亚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出土的斧、镰基本一致,蕉叶纹装饰也完全相同。毫无疑问,这为我们认识有关青铜器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线索。所谓安德罗诺沃文化,是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南阿尔泰,西伯利亚地区的一种考古文化,其绝对年代在距今4000~3000年之间。我国境内的这批青铜工具,其绝对年代自当同样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内。而这一时代,与古墓沟墓地的年代是相近的。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批资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说明:从罗布淖尔地区到伊犁河谷地,在这一十分宽广的地域内,自距今4000年以来,已见青铜器物的使用。当然,仅此两例,尚不足以充分说明那时新疆地区青铜器使用的深度、广度,但作为新疆已使用青铜器的说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三
到距今3000年前后,在新疆不少地点,都发现了大型青铜器。少数出土青铜器的遗址、墓葬,曾经过发掘,取得了一定数量的发掘资料。这些考古资料有力表明:在这一历史阶段内,新疆地区青铜文化有了重要发展。定居及农业相当程度地发展,是这一时期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一些地区,可能已进入阶级社会。
试举数例,以为说明。
在天山南麓,和硕县辛塔拉,曾发现并试掘过一处古代居住遗址①。遗址文化层灰土厚达5米以上,表明古代人们在这里曾有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居住。遗址区内,发现过铜器、石斧、玉斧、大型石刀、石镰、磨谷器、多量彩陶及刻画纹陶器及麦、粟类籽实、动物碎骨。陶器中的彩陶器占相当大的比重。遗址在考古工作者进行调查、发掘之前,已经在农民取灰土肥田的过程中遭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挖取灰土过程中,见到了铜斧、铜刀、小件铜饰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件似斧青铜器(库藏号为79HS×∶8),通高17.3厘米。弧刃、空心圆銎。按柄方向,与刃向垂直。銎径3厘米、深8厘米。刃部较宽圆成弧,曾经使用,有较重残损。柄部有三道棱脊,稍残。下两道棱脊间曾外张连续成圈,可垂系附件。从器物外形分析,近同斧,但又有一些明显不同于斧的特征。笔者曾进行称量,残重仍有997克,足见,原器重当在1公斤以上。这是一件实用的生产工具或兵器。发掘中曾取文化层内包含的木炭进行年代测定,据文物局文保所碳14实验室测定结论:这一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640±145年。
巴里坤县兰州湾子,近年曾发掘了一处青铜时代居住遗址。天山北麓,尤其是在巴里坤县境内,如口门子东之盐池、口门子西之伊吾军马场、奎苏、石人子、兰州湾子一线,在天山山前地带,可以见到不少巨型土石堆。老乡俗称这类土石堆为“青疙瘩”、“灰疙瘩”、“白疙瘩”、“黑疙瘩”等。石人子、奎苏等处,因老乡挖土取肥,在这类巨型土石堆中,曾出土过大型磨谷器、彩陶器、小麦粒、铜器等。石人子地区出土文物情况,曾经有过报道②。关于奎苏遗址的出土文物,1978年,笔者在巴里坤工作期间,正是老乡挖土发现一批文物之时,当即至现场观察,并收回了已出土的几件铜器、陶器。文物现存巴里坤县文化馆。奎苏出土文物,除多量大型磨石、彩陶及红陶片、大量烧灰外,还见到几件铜器,包括铜斧、刀、镰等。斧,通长21厘米、宽4~4.6厘米。按柄方向与斧刃方向一致。柄部圆孔,孔径3.7厘米,通体绿锈,相当厚重。其形制特点是:自柄端起,有棱脊三道,向刃部延展,刃部有砍痕。小铜刀已断残,残长8.5厘米、宽2.8厘米。柄部有近三角形环孔,通体铜绿色。铜鐏,通高11厘米。柄部有圆孔,孔径2.2厘米。插地部分呈扁锥状,十分锐利,无使用痕迹。与铜器共出,还有陶泥抹、石质容器等。关于奎苏遗址的绝对年代,曾取土石墩内木炭进行碳14测定,结论是距今2620±70年①。
近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又在巴里坤县城西约6公里的兰州湾子,发掘了一处巨型石堆遗址。地表堆石成圆形,直径达30米,高达3米。地表特征与石人子、奎苏所见堆石一致。发掘结果说明,这类土石堆,实际上是巨石构成的建筑,废弃后为土掩覆。建筑面积近200平方米,周围石墙厚达3米,残高近2米。分隔成前、后室。主室居南,面积达100平方米。底部见柱洞,洞内仍残存木柱残段。附室居北,主、附室彼此有门道通连。由附室向东开门。石墙用材选自山前巨型块石,大者长达1.5米,宽、厚过50~60厘米,非多人不能挪动。但房址内侧墙面十分平整。房址内,见大量烧炭、红烧灰土。并出土了大型圈足铜鍑,环首小铜刀、双耳鼓腹红陶罐、彩陶罐、陶锉、多件大型磨石和石球、碳化小麦粒及马、羊、鹿骨。铜鍑通高54厘米、口径32厘米。平口、双立耳、腹部饰波纹一道,底部为圈足。铜绿色,器表见黑色烟炱。陶器均手制。石构遗址曾经先后三次住人。取底层木炭请文保所碳14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结论为距今3285±75年,表明了遗址最早的时间②。
值得注意的是,与兰州湾子古代居住遗址出土铜鍑形制相同的器物,在巴里坤大河乡、奇台县卡尔孜乡西卡尔孜大队五小队等地亦曾见出土。西卡尔孜出土铜鍑通高40厘米,与划纹灰陶共出。这么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域,时代延续又相当长,说明以兰州湾子为代表的、出土大型铜鍑的考古文化,是一组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化遗址。
克尔木齐发掘资料,相当一部分也是处于青铜时代这一文化阶段的。在阿尔泰山南麓,阿勒泰市克尔木齐发掘的石人石棺、竖穴土坑墓,文化内容比较复杂,延续时间相当长。原简报曾正确地揭明过这一实质。但把这批发掘资料的上限定为最早不过战国时期,却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一个结论①。笔者曾参加了克尔木齐的发掘,在全部32座墓葬中,曾亲自发掘过其中的相当部分。因此,对有关墓葬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这里的石棺墓,具有比较明显的早期特征。它们的基本内容是:石棺、棺前或有石人,棺内多为丛葬,骨架多至20具。随葬文物有石镞,青铜镞,铜刀,石质杯、罐,灰陶器(多圆底、似橄榄形、饰划纹)等。陶器形制及纹饰,与邻近的中亚地区阿凡纳羡沃文化中的陶器,存在明显的联系②。也有观点认为:这里出土的“石容器和橄榄形陶器是这批墓葬带典型性的器物。它们与中亚地区南阿尔泰地区卡拉苏克文化的文物颇为相似,其年代据认为在公元前1200~前700年左右”③。但对这一观点没有具体申述。中亚地区卡拉苏克文化中的陶器,确实也有一种鸭蛋形、饰杉针纹的陶罐,中亚学者同样认为这类陶器“保留了阿凡纳羡沃的传统”④。从这一角度分析,彼此可以统一。但据此,克尔木齐这类墓葬的绝对年代,就要远早于汉代或战国,当是可以明确肯定的。如是,阿勒泰地区进入青铜时代阶段,当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
同属这一时代,在哈密市南郊花园乡茶迄马勒,出土了一批鄂尔多斯式铜器。铜器深埋于距地表4米以下,农民挖窖中出土。共见鹿首铜刀一件(通长36厘米,柄长13.5厘米。柄端为圆雕鹿首。鹿首颜面较长,眼鼓突,耳直立,角后曲成环。柄首与刀背曲成一条谐和的曲线)、环首小铜刀一件(通长14.5厘米,柄长6.5厘米。柄微曲,柄端有三角形环,背部弧曲,刃部微鼓凸)、铜镞(叶形有銎,通长5.8厘米)、砺石等。挖出的陶器为老乡毁弃。这一组铜器具有典型的鄂尔多斯风格。形制相同的铜刀等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及河北省青龙县抄道沟及陕西绥德墕头村商代遗址中都曾经有过发现,在邻境的中亚地区卡拉苏克文化中也有发现。同类鹿首铜刀流行时代据青龙县发掘资料是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①。
哈密地区,还有一些出土铜器的遗址,也处于这一历史时期前后。如哈密县五堡公社古代墓地。在先后发掘的100多座墓葬中,出土文物除死者随身皮、毛织物外,还见到木器、石器、陶器(陶器中包含彩陶)及海贝等物。死者衣、鞋上佩小件铜饰,男性死者腰际佩砺石及小铜刀。铜刀通体铜绿色,单面刃。五堡墓地因气候干燥,织物、木器多不朽。墓穴上盖木同样保存完好。从出土盖木上遗留的工具痕迹可以看到,在相当坚硬的胡杨木上,砍削痕相当光洁,切口非常锐利。盖木大小、长短一致,形制规整。同样的道理,这样的加工效果,非坚硬锐利的青铜金属工具莫属。这一墓地的绝对年代,利用墓穴盖木进行碳14年代测定,结论为公元前1165~前890年之间②。
与五堡墓地时代相当,在哈密四堡拉甫乔克,还发现过一处墓地。一个显明的特征也是:彩陶器与青铜器共存③。
吐鲁番县哈拉和卓,1975年也曾发掘过一处古代遗址。在距地表1米多的深新处,发现了彩陶、红褐色陶、青铜镞。遗址地表,采集得虎形铜饰牌一件。曾取遗址文化层内木炭进行过年代测定,结论为距今2895±100年④。
巴里坤县奎苏乡南湾墓地,新疆博物馆文物队曾在这里发掘古代墓葬100多座。出土文物中,见多件铜斧、小铜刀、彩陶、红褐陶及石器。铜刀的形制与哈密五堡出土铜刀相同。其总的特征,似与巴里坤、奎苏、石人子、哈密五保墓地时代相近①。
其他如木垒县四道沟遗址,早期文化层在距今3000年前,同样已经见到了铜器。这些小件铜器与磨制石器、骨器、陶器共存②。伊吾县卡尔遗址晚期文化层,出土石罐、青铜器③。阿克苏县喀拉玉尔兗古遗址,在距地表深4米的地下,见青铜环,与石斧、石罐、陶器、兽骨共存④。这些遗址外,还有其他一些地点,如巩乃斯河上游查布哈河工地,特克斯县铁里氏盖遗址等处,也都曾采集到过青铜刀、铜斧、牛头形铜饰物等。
从这些古代遗址,可以看到其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一个逻辑的结论是:在距今3000年前后,新疆大地青铜器的使用,已经是比较普遍了。
三
自公元前1000年中期到战国,新疆各地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址更多,而进入战国时期,不少遗址中已见到铁器,如小铁刀、铁镞、铁钉之属。这一现象说明:进入战国时期,新疆地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
为了更进一层地认识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这一历史阶段内的铜矿开采及冶铸事业,是应予注意的重要一环。
从铜、锡矿蕴藏来看,新疆算不得一个很丰富的地区,但铜矿点并不少。只是过去已经开采的点就有伊犁地区特克斯县的菁布拉克、尼勒克县奴拉赛山、乌鲁木齐地区的达坂城、哈密地区的沙泉子;在塔里木盆地周缘,有阿克陶县的卡拉玛、特格里苏曼,拜城县滴水,莎车县的阿尔巴列克,托克逊县的可可乃克等处。在尼勒克县的奴拉赛、圆头山,拜城县的滴水,还曾见到古代采矿痕迹。这些铜矿点,蕴藏量虽不很大,但埋藏不深,开采较易,而且含铜量也较丰富。至于锡,在博尔塔拉地区的图尔贡河谷右支流上游,有相当数量的蕴藏⑤。无疑,这些铜、锡矿藏资源,是新疆地区青铜制造工业发展的有利物质基础。
这些铜矿点中,尼勒克县境的圆头山及奴拉赛山,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采矿及冶炼遗址。
圆头山及奴拉赛山古铜矿遗址,均位于尼勒克县阿晋拉勒山北坡,喀什河南岸的低山丘陵地带。圆头山古代矿坑距县城约5公里,因山形似孤立的钟状山头,故名圆头山。山顶有北西320。走向的两条破碎带,充填含铜石英—方解石脉,部分地方被亚沙土覆盖,但有锅形洼地,可以追索矿体。沿矿脉使用槽探,结果表明:在风成亚沙土覆盖层1米以下,见有大量废矿石堆积,2米以下仍未见基岩。
沿铜矿脉展布的锅形洼地,为古代采矿坑的遗迹。坑口直径2.5米,底径1米,深2米。其上覆亚沙土,丛生灌木。从展布情况分析:当时采矿是间隔采掘,弃贫求富,最深处已采到3米以下。
沿圆头山铜矿脉,在亚沙土覆盖层下,发现了大量废矿石堆积。在废矿石堆中,有很多扁圆形、杏仁形、卵圆形石器,直径多在10~20厘米以上,腰部有宽约2厘米的槽痕,边缘圆滑,局部有破裂脱落缺口,明显为使用痕迹。石料多为花岗岩、石英钠长斑岩、硅质粉沙岩等。石料取自喀什河河床砾石和附近二叠系砾岩的砾石,与石器共存有木炭碎块。将用这些炭块送请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碳14年代测定结论为距今2650±170年,相当于春秋时期。
圆头山铜矿遗址,只见到这种露天采掘矿坑、大型石器。与石器共存,虽见木炭,但未发现进一步的冶炼痕迹①。
去圆头山矿点不远,为奴拉赛古铜矿开采、冶炼遗址。
奴拉赛古铜矿遗址,距尼勒克县3公里。矿井位于奴拉赛沟中游右岸的山腰部位,这里有含量丰富、品位很高的脉状晶质辉铜矿,共见两条矿脉。在一条矿脉上发现一处槽形洼地,洼地局部为一不规则大坑,内有废石及矿石堆积,在这一堆积中,捡到直径达20厘米的卵圆形石器②。
在另一条矿脉上,见到多处采矿洞口。地质工作者在距山顶50米处爆破,发现一暗洞。洞深30米,长20米,最宽处6米。底部积水深达8米。在洞底岩石上,发现了木炭碎块及骨片,骨片上已附着一层孔雀石,说明年代已十分久远。这一竖井的自然洞口,因废石、黄土状岩石覆盖,没有完全探明。其后,考古工作者又在这里进行了调查。报道称:发现了十余处竖井洞口,每个洞口大致5米见方。洞口已塌毁,为碎石、砾砂和丛生的野草所覆盖。各竖井洞口在地下是相通的,形成了网络似的采矿平洞和巷道。有的坑道已遭水淹;进入坑道,尚可见到支撑矿层的坑架。坑架是用原木分为数层揳入坑壁而成,保存完好①。
在采矿竖井内及井外,发现了大量铜矿石及石器。石器形制均作圆或扁圆形大石锤,一头圆钝、一头稍尖锐,最大直径约为20厘米,重1.5~5公斤多。石锤一端大都凿有纵、横向宽条凹槽,以利于绳索捆绑。这类石锤的特征与湖北大冶战国时铜矿遗址内所见石锤一样,似为采掘工具,但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平衡、提升工具。这种造型的一致,为我们分析2000多年前新疆西部地区与湖北大冶地区之间在矿冶技术上的交流,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资料。
距矿井不远的沟谷内,为冶炼遗址。炼砟堆积厚达1米。炼砟灰内见木炭、铜锭,还见到陶片、矿石、动物骨骼等。油黑色炼砟上残留着木炭或木质纤维状印痕②。这表明:奴拉赛古铜矿内所采矿石,只要运送到旁近的山沟内,即可冶炼,冶炼用的燃料,是木炭。
对这里出土的铜坯,曾进行过分析。铜坯似碗形,一面圆凸,一面平。共见五块。锭块重者十余公斤,轻者每块3~5公斤。铜锭块质较纯,含铜量在60%以上。性脆,断面呈银灰色,磨光面银白反光,可鉴人影。
这处矿冶遗址的年代,曾取矿洞内支架坑木进行碳14测定,结论为距今2440±75年,相当于战国早期③。
从圆头山、奴拉赛山这两处采矿及冶炼遗址资料,似可结论,采矿技术从春秋到战国时期,曾经历了一个显明的发展。从地面挖坑采矿到竖井采矿,标志着两个不同技术发展阶段。进入战国时期,在采矿技术上表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在深数十米的地下,从找矿到开掘竖井、掘进坑道、支架防护、采矿、排水通风、提取运输矿石,都须要比较成熟的技术知识,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它绝不是露天挖坑取矿所可比拟的了。
采矿与冶炼集中在一起,这完全符合经济的原则,但也需要更严密的组织。从这些资料可以推论,在战国时期,新疆地区的铜矿开采、冶炼生产,已是社会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生产部门,紧密联系、彼此协作的各个生产环节,要求有相对稳定、并掌握一定专门技术的生产工人,在统一的调度下行动,才能保证生产秩序的正常进行。这些资料,对我们认识公元前4世纪前后,新疆地区的铜矿开采及冶炼生产,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是有说服力的。
铜矿开采、冶炼,是青铜器生产的物质基础。要深入认识新疆地区古代青铜器的生产,离不开对这一基础的了解。对这一基础的认识和了解,会使我们对古代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认识大大深化。
与战国时期铜矿的开采、冶炼事业发展相一致,在这一历史时期,新疆各地出土了更多的铜器,不少是大型铜器。伊犁地区的新源、察布查尔、昭苏县,就陆续有多批铜器出土。新源县内,巩乃斯河谷地带,农业生产中见到了一批铜器,其中包括通高42厘米的青铜武士俑。武士头戴阔檐高帽,帽作尖顶,前弯如钩。武士裸上身,着裙,右腿跪地,双手持物(已断裂遗失),分别置于腿上,长脸,高鼻、肌腱鼓凸,孔武有力。共存承兽铜盘一件,盘作方形,盘内两角各蹲一兽,似熊,憨态可掬。兽足铜釜,三兽足。釜作平口深鼓腹,上腹部附四耳,二平二直,腹饰弦纹三道。其他如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已残。两虎面唇相接,特征明显。对兽圆环,二兽回曲相向,鬣毛上卷成孔,作奔跃状①。据了解,十年动乱期间,在新源县城附近还曾出土过与这一组大型铜器风格相同的青铜文物。据看到的同志介绍,铜器中的大型承兽铜盘,盘上环列异兽一圈。共存铜器中,同样有兽足铜釜等物。此外,在昭苏、察布查尔等县,同样见到大型铜器、兽足盘。铜鍑通高达50厘米上下,深腹饰弦纹,圈足。铜盘,矩形,四兽足。除圈足铜鍑外,伊犁地区陆续出土的这些大型铜器,从器物造型、装饰艺术风格看,一般均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新疆历史舞图台上的塞人文化遗物②。从出土数量多,个体造型巨大,铸造工艺精湛,野兽形象逼真,神气十足等特点,充分表现了这一阶段内青铜工艺臻于成熟。
除了伊犁地区以外,在和静县查布干河口古代墓区、阿拉沟东口及鱼儿沟车站地区古墓葬群、鄯善县苏巴什古墓区等处,这些地点的早期墓葬、出土文物都是青铜器与彩陶器、木器等共存。时代也是在战国或战国以前。自可看作是这一历史阶段中的遗址。这些资料可以说明:到公元前1000年中期,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水平,处于盛期,由此而后,即逐步迈入了铁器时代。
四
关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发生、发展,向铁器时代过渡,它本身的特点及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在新疆考古研究中,还是一些尚待具体建设的新概念。本文即使提到这些方而,充其量说,也只是初步提出了问题。它们都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受到检验,求得发展、提高。
正如本文实际已经说明的,在现有的考古资料基础上,对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这些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一些初步的概念,还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说,由于不少素材只是采集、调查资料,发掘资料比较少;已有的这一部分发掘资料,分布面也不均衡,一些地点比较集中,不少地区可以说还是空白。而且,对这些已经到手的资料,又缺少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最简单的一点,对所有已经入藏的出土铜器,对它们的金属成分进行分析测定统计,这样一个完全应该进行的项目,除少数样品曾经进行以外,大部分就未能完成,而只是就其形体、使用情况进行推理,这就十分不够。不言而喻,这种状况,当然会极大地局限我们认识的深入。
据现有资料,本文明确提出:公元前2000年前,新疆地区已经步入了青铜时代。这当然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和不少同志传统的、感性的认识“新疆地区古代文明发展程度比较低,较之中原地区,要远为落后”这样一种传统的、有影响的概念,是有差别的、相当不同的。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看,新疆地区青铜器的造型、纹饰等,与黄河流域差异较大,具有相当鲜明的自身特点,而与中亚西部、西伯利亚南部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南阿尔泰等地的出土物,存在较多的联系。这可能与彼此地域接近,而在古代往往又是同一居民集团,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有关。
新疆地区,作为亚洲腹心地带,民族迁徙频繁,是交通来去之要冲,黄河流域古老文明在这里投射下光明、产生过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当然也不会例外。起源、发展中心在黄河中游的鄂尔多斯草原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比较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哈密地区同样出土了,就是一个鲜明的、有说服力的实例。目前所见,虽只有一个点,随工作深入,当会有更多资料涌现。这对研究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古代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及联系的具体途径,都是很值得人们注意的。
粗略观察现已出土的铜器,一个印象比较突出:实用器居主、礼器较少。而在实用器中,生产工具(有些是明显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具)又占较大比重。青铜工具,当然代表着一种更进步的生产力。因此,随青铜时代的到来,青铜工具的使用,对新疆的社会生产、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些怎样的具体影响,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这对古代新疆历史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多次强调、重复,关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一些概括,是很粗浅的。这当然不是什么谦虚之辞,而是在这一阶段中难免的局限。这种情况下,公开提出这些观点,除了希望推动有关研究的深入以外,还希望借此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得到指正。希望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使有关研究不断发展、提高,使新疆地区的考古研究事业得到进一步的繁荣。
在国内先后出版的有关我国青铜器的重要专著,如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成书较早,资料所及多在中原地区,对新疆的青铜器文化没有一字一词涉及。这反映了一个问题,说明了这方面研究十分薄弱。导致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新疆地区考古文化存在什么特殊情况,曾超越过青铜时代这一发展阶段。相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疆地区已发现不少属于这一时代的重要遗址和墓葬,在工农业生产中,也有不少重要的青铜器文物出土。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一是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对这方面的一些重要发现,认识不足,未能及时给予报道;再是对已有的并经报道了的发现,未能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做必要的概括、研究。这些明显的弱点,自然局限了对问题的认识,影响着研究的深入。
在目前这样一个工作基础上,要对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各主要方面作出比较清楚、比较准确的说明,困难是很大的。但对已有的资料进行初步的概括,从一定的理论高度进行分析,也会明显地推动问题的深入。因此,我在这里提出的新疆青铜时代的起始、繁荣阶段,它的基本特征及与周围地区的关系等,都只能是很初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是一个提供讨论的意见。希望在进一步的讨论,尤其是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修正、提高,逐步完善。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我个人的看法是:从公元前2000年前起,新疆地区已陆续步入了青铜时代。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青铜文化呈现了相当的繁荣,铜器使用相当普遍,铜矿开采也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进入战国时代,出现铁器,实现了向铁器时代的转化。由于新疆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从青铜器造型、风格上看,与邻近的中亚地区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同时,与蒙古草原地区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有相当鲜明的地区特点。
一
我之所以提出,在公元前2000年,新疆地区已经步入青铜时代,主要根据有二:一是罗布淖尔地区古墓沟墓地的发掘,二是在伊犁河流域巩留县阿格尔森所采集的一批青铜器。这两批资料,目前虽只是两个点,但却代表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域。
1979年冬,新疆考古研究所派人到罗布淖尔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于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进行了发掘。笔者主持了这一工作。参加这一墓地发掘工作的还有伊弟利斯·阿不都、邢开鼎、刘玉生、常喜恩等。古墓沟墓地,共见古代墓葬42座,全部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可区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为竖穴木棺墓,浅葬,木质葬具保存完好。二类同样为竖穴,但埋葬深,葬具已朽。墓穴外附七圈环形列木,环形木圈外,见放射状四向展开的木桩。曾观察木桩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墓葬,木桩总数达894根。从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分析,第二类型墓葬相对较晚。关于墓地的绝对年代,据第一类墓葬中多组测定数据,为距今3800年前的遗存。在这一墓地的两类墓葬中,均发现过小铜卷、小铜片。这些小件铜器,与木器、石器(细石镞)、骨、玉饰物、小麦籽粒、草编器、毛织物(布、毯、毡)及牲畜皮毛等共存。因所出小件铜器不仅造型过小、形制难辨,而且朽蚀相当严重,既难判明铜器制作工艺,也无法据以分析铜器在当时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当时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①。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对墓地内所出木器及木桩进行仔细观察、分析以后。详细、认真分析了墓地内出土木材及有关器物上保留至今的工具痕迹,不能不予确认:在当时的古墓沟地区,无可怀疑,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着一种相当锐利的金属砍伐工具。其硬度、锐利程度,不是磨制石器或红铜工具所能达到的。这种工具,当以青铜器最为合理。因此,这一墓地,虽无大型青铜器出土,但却同样为我们认识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资料。
因地理环境十分干燥,古墓沟墓地内,木、骨、皮等制器,大多均完好如入土之时。未朽之板材,叩击仍铿然作声。当年加工板材遗留的大量工具印痕,也清楚明晰。分析这些痕迹,对于判明所使用工具的性质及其锐利程度,是很有说服力的。
墓地内所用木材,多为胡杨。胡杨本质细密,硬度较大。将直径二三十厘米的胡杨树干,砍断、削平,形成棺木类葬具;或砍削出锐尖,形成木桩,都并非易事。古墓沟墓地内发掘的42座墓葬,第一类型墓葬占36座。墓葬内几乎都见木“棺”。这类木“棺,”是在沙穴上,置厢板、挡板,尸体放人后,覆盖多块小木板。这些板块,都取胡杨木为料,砍削成比较平整的板材,长短、厚薄比较一致,边棱整齐,加工工具,明显是比较得心应手的。第二类墓葬葬具虽朽,但保存完好的木桩、木柱至夥。直径二三十厘米的粗胡杨木,都要砍出锐尖,才能深揳入地下深处。笔者曾观察、记录了一直径23厘米、长110厘米的粗大胡杨木,一端砍削出非常锐利的尖锥。尖锥长28厘米,端部锐尖不到1厘米,尖锐部分砍削痕迹既光洁又整齐。还曾对取回乌鲁木齐的部分葬具、木桩,选择砍削痕迹清楚的进行了分析、统计。在统计的240个数据中,可以看出:砍痕均圆刃工具所致。刃宽一般在3~5厘米,最狭的1.5厘米。一次砍进深度,最深达10.5厘米,一般砍进深度也在3~5厘米。砍削痕迹均相当光洁、干净,不见毛毛糙糙的砍痕。砍进这么深,而且砍痕这么光滑洁净,是一切钝的、轻的非金属类工具所不能达到的。换句话说,只有比较锐利、比较厚重的金属斧类工具,才能造成这样的砍削效果。在古墓沟墓地,还出土了木雕人像、木杯、木盘多件。一些木器,利用一段木料的自然形状掏挖,说不上精致,但也不乏加工精细的标本。如木雕女性人像,经过细致刻削,很形象地表现了人物头戴尖顶毡帽、梳辫、尖下颏、丰满而垂下的双乳。辫形整齐、辫纹清晰、垂于脑后。尖帽、下颏、双乳,削刻均十分匀称,刻削痕迹干净利索。笔者曾有机会观察用石斧砍伐、加工木器的试验。粗大、刃部锐利的石斧,以之砍伐小树,十多分钟可将直径10厘米上下的树杆砍断。遗留痕迹是:砍痕十分粗糙,加工面毛糙不齐,每次用力砍伐,砍进深度不足1厘米,或勉强达到1厘米。这与古墓沟墓地木桩、棺木、木器
上保留至今的砍伐痕迹相比,无论在砍进深度、砍痕光洁程度方面,都判然有别。这么深而且光洁的砍痕,明显是须要刃部锐利,而且相当厚重的斧、斤类金属工具才能奏效的。
还应该说明的一点是:这类砍痕,如果只是个别、少数存在,自然也可以考虑其他可能性。而现在的观察结论是:在任何墓葬,任何一件木器、棺具、木桩上,都随处可以找到多量的、特征一致的砍伐痕迹。这就显示了一种普遍的、一般性现象。笔者取回乌鲁木齐供分析的葬具及木桩标本,与墓地出土木材相比,只是十分小的、可以说是不成比例的一点资料。在这些标本上随意观察、统计砍伐痕迹,明确无误、特征明显的数据即达240组。这足以说明,在当时的古墓沟地区,金属生产工具在社会生产中已占重要地位。而不是一种个别的、孤立的存在。常识告诉我们:因为红铜质软、硬度不够,所以并不能在生产中排除、取代石器。古墓沟墓地所见锐利的砍痕,在砍木上砍进深度一般都达四五厘米,最深可达10厘米以上,是红铜质及石质工具所不能达到的。只有青铜工具,或较青铜硬度更大、更锐利的工具,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从整个历史背景分析,这种金属工具,当然以青铜器为宜。因此,目前虽没有直接见到青铜工具实物,判定当时使用的主要是青铜器,还是比较合理的。既然这样,为什么在全墓地内,一件青铜器工具也没有发现?主要原因可能是:这类金属工具,在当时还是十分珍贵的生产手段,取得它们也很不容易。而且,这类工具,与人们现实的经济生活利益关系重大,所以,一般都不用于殉葬。
既然逻辑推论表明:古墓沟阶段,已经出现了相当锐利,可用于砍伐硬木、加工板材的青铜工具,在社会生产中使用还比较普遍,自然就可以结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已经步入了青铜时代。当然,这个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物资料直接证明。但可以相信,这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与古墓沟墓地年代相近,在北疆伊犁河谷地巩留县境,发现过又一批青铜器。1975年,新疆博物馆王博、成振国同志,在巩留采集得青铜工具12件。铜器出土于阿格尔森。群众在这里开挖水渠,于距地表1米多深的地下,发现3件铜斧,3件铜镰、钲、凿等,共12件①。斧刃圆弧,弯柄圆銎,柄部饰焦叶纹,分大小两种。镰作弯背弧刃,使用痕迹明显,磨损较重。12件铜器,均是实用生产工具,而且农业生产工具占有较大比重。有关铜器出土后,对其金属成分,曾送请北京钢院冶金史研究所进行分析,结论为青铜工具无疑。
对这批铜器资料有关考古文化的具体内容,因非正式发掘,目前还无法提供更多的具体说明。但铜斧、铜镰的形制,与中亚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出土的斧、镰基本一致,蕉叶纹装饰也完全相同。毫无疑问,这为我们认识有关青铜器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线索。所谓安德罗诺沃文化,是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南阿尔泰,西伯利亚地区的一种考古文化,其绝对年代在距今4000~3000年之间。我国境内的这批青铜工具,其绝对年代自当同样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内。而这一时代,与古墓沟墓地的年代是相近的。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批资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说明:从罗布淖尔地区到伊犁河谷地,在这一十分宽广的地域内,自距今4000年以来,已见青铜器物的使用。当然,仅此两例,尚不足以充分说明那时新疆地区青铜器使用的深度、广度,但作为新疆已使用青铜器的说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三
到距今3000年前后,在新疆不少地点,都发现了大型青铜器。少数出土青铜器的遗址、墓葬,曾经过发掘,取得了一定数量的发掘资料。这些考古资料有力表明:在这一历史阶段内,新疆地区青铜文化有了重要发展。定居及农业相当程度地发展,是这一时期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一些地区,可能已进入阶级社会。
试举数例,以为说明。
在天山南麓,和硕县辛塔拉,曾发现并试掘过一处古代居住遗址①。遗址文化层灰土厚达5米以上,表明古代人们在这里曾有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居住。遗址区内,发现过铜器、石斧、玉斧、大型石刀、石镰、磨谷器、多量彩陶及刻画纹陶器及麦、粟类籽实、动物碎骨。陶器中的彩陶器占相当大的比重。遗址在考古工作者进行调查、发掘之前,已经在农民取灰土肥田的过程中遭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挖取灰土过程中,见到了铜斧、铜刀、小件铜饰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件似斧青铜器(库藏号为79HS×∶8),通高17.3厘米。弧刃、空心圆銎。按柄方向,与刃向垂直。銎径3厘米、深8厘米。刃部较宽圆成弧,曾经使用,有较重残损。柄部有三道棱脊,稍残。下两道棱脊间曾外张连续成圈,可垂系附件。从器物外形分析,近同斧,但又有一些明显不同于斧的特征。笔者曾进行称量,残重仍有997克,足见,原器重当在1公斤以上。这是一件实用的生产工具或兵器。发掘中曾取文化层内包含的木炭进行年代测定,据文物局文保所碳14实验室测定结论:这一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640±145年。
巴里坤县兰州湾子,近年曾发掘了一处青铜时代居住遗址。天山北麓,尤其是在巴里坤县境内,如口门子东之盐池、口门子西之伊吾军马场、奎苏、石人子、兰州湾子一线,在天山山前地带,可以见到不少巨型土石堆。老乡俗称这类土石堆为“青疙瘩”、“灰疙瘩”、“白疙瘩”、“黑疙瘩”等。石人子、奎苏等处,因老乡挖土取肥,在这类巨型土石堆中,曾出土过大型磨谷器、彩陶器、小麦粒、铜器等。石人子地区出土文物情况,曾经有过报道②。关于奎苏遗址的出土文物,1978年,笔者在巴里坤工作期间,正是老乡挖土发现一批文物之时,当即至现场观察,并收回了已出土的几件铜器、陶器。文物现存巴里坤县文化馆。奎苏出土文物,除多量大型磨石、彩陶及红陶片、大量烧灰外,还见到几件铜器,包括铜斧、刀、镰等。斧,通长21厘米、宽4~4.6厘米。按柄方向与斧刃方向一致。柄部圆孔,孔径3.7厘米,通体绿锈,相当厚重。其形制特点是:自柄端起,有棱脊三道,向刃部延展,刃部有砍痕。小铜刀已断残,残长8.5厘米、宽2.8厘米。柄部有近三角形环孔,通体铜绿色。铜鐏,通高11厘米。柄部有圆孔,孔径2.2厘米。插地部分呈扁锥状,十分锐利,无使用痕迹。与铜器共出,还有陶泥抹、石质容器等。关于奎苏遗址的绝对年代,曾取土石墩内木炭进行碳14测定,结论是距今2620±70年①。
近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又在巴里坤县城西约6公里的兰州湾子,发掘了一处巨型石堆遗址。地表堆石成圆形,直径达30米,高达3米。地表特征与石人子、奎苏所见堆石一致。发掘结果说明,这类土石堆,实际上是巨石构成的建筑,废弃后为土掩覆。建筑面积近200平方米,周围石墙厚达3米,残高近2米。分隔成前、后室。主室居南,面积达100平方米。底部见柱洞,洞内仍残存木柱残段。附室居北,主、附室彼此有门道通连。由附室向东开门。石墙用材选自山前巨型块石,大者长达1.5米,宽、厚过50~60厘米,非多人不能挪动。但房址内侧墙面十分平整。房址内,见大量烧炭、红烧灰土。并出土了大型圈足铜鍑,环首小铜刀、双耳鼓腹红陶罐、彩陶罐、陶锉、多件大型磨石和石球、碳化小麦粒及马、羊、鹿骨。铜鍑通高54厘米、口径32厘米。平口、双立耳、腹部饰波纹一道,底部为圈足。铜绿色,器表见黑色烟炱。陶器均手制。石构遗址曾经先后三次住人。取底层木炭请文保所碳14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结论为距今3285±75年,表明了遗址最早的时间②。
值得注意的是,与兰州湾子古代居住遗址出土铜鍑形制相同的器物,在巴里坤大河乡、奇台县卡尔孜乡西卡尔孜大队五小队等地亦曾见出土。西卡尔孜出土铜鍑通高40厘米,与划纹灰陶共出。这么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域,时代延续又相当长,说明以兰州湾子为代表的、出土大型铜鍑的考古文化,是一组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化遗址。
克尔木齐发掘资料,相当一部分也是处于青铜时代这一文化阶段的。在阿尔泰山南麓,阿勒泰市克尔木齐发掘的石人石棺、竖穴土坑墓,文化内容比较复杂,延续时间相当长。原简报曾正确地揭明过这一实质。但把这批发掘资料的上限定为最早不过战国时期,却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一个结论①。笔者曾参加了克尔木齐的发掘,在全部32座墓葬中,曾亲自发掘过其中的相当部分。因此,对有关墓葬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这里的石棺墓,具有比较明显的早期特征。它们的基本内容是:石棺、棺前或有石人,棺内多为丛葬,骨架多至20具。随葬文物有石镞,青铜镞,铜刀,石质杯、罐,灰陶器(多圆底、似橄榄形、饰划纹)等。陶器形制及纹饰,与邻近的中亚地区阿凡纳羡沃文化中的陶器,存在明显的联系②。也有观点认为:这里出土的“石容器和橄榄形陶器是这批墓葬带典型性的器物。它们与中亚地区南阿尔泰地区卡拉苏克文化的文物颇为相似,其年代据认为在公元前1200~前700年左右”③。但对这一观点没有具体申述。中亚地区卡拉苏克文化中的陶器,确实也有一种鸭蛋形、饰杉针纹的陶罐,中亚学者同样认为这类陶器“保留了阿凡纳羡沃的传统”④。从这一角度分析,彼此可以统一。但据此,克尔木齐这类墓葬的绝对年代,就要远早于汉代或战国,当是可以明确肯定的。如是,阿勒泰地区进入青铜时代阶段,当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
同属这一时代,在哈密市南郊花园乡茶迄马勒,出土了一批鄂尔多斯式铜器。铜器深埋于距地表4米以下,农民挖窖中出土。共见鹿首铜刀一件(通长36厘米,柄长13.5厘米。柄端为圆雕鹿首。鹿首颜面较长,眼鼓突,耳直立,角后曲成环。柄首与刀背曲成一条谐和的曲线)、环首小铜刀一件(通长14.5厘米,柄长6.5厘米。柄微曲,柄端有三角形环,背部弧曲,刃部微鼓凸)、铜镞(叶形有銎,通长5.8厘米)、砺石等。挖出的陶器为老乡毁弃。这一组铜器具有典型的鄂尔多斯风格。形制相同的铜刀等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及河北省青龙县抄道沟及陕西绥德墕头村商代遗址中都曾经有过发现,在邻境的中亚地区卡拉苏克文化中也有发现。同类鹿首铜刀流行时代据青龙县发掘资料是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①。
哈密地区,还有一些出土铜器的遗址,也处于这一历史时期前后。如哈密县五堡公社古代墓地。在先后发掘的100多座墓葬中,出土文物除死者随身皮、毛织物外,还见到木器、石器、陶器(陶器中包含彩陶)及海贝等物。死者衣、鞋上佩小件铜饰,男性死者腰际佩砺石及小铜刀。铜刀通体铜绿色,单面刃。五堡墓地因气候干燥,织物、木器多不朽。墓穴上盖木同样保存完好。从出土盖木上遗留的工具痕迹可以看到,在相当坚硬的胡杨木上,砍削痕相当光洁,切口非常锐利。盖木大小、长短一致,形制规整。同样的道理,这样的加工效果,非坚硬锐利的青铜金属工具莫属。这一墓地的绝对年代,利用墓穴盖木进行碳14年代测定,结论为公元前1165~前890年之间②。
与五堡墓地时代相当,在哈密四堡拉甫乔克,还发现过一处墓地。一个显明的特征也是:彩陶器与青铜器共存③。
吐鲁番县哈拉和卓,1975年也曾发掘过一处古代遗址。在距地表1米多的深新处,发现了彩陶、红褐色陶、青铜镞。遗址地表,采集得虎形铜饰牌一件。曾取遗址文化层内木炭进行过年代测定,结论为距今2895±100年④。
巴里坤县奎苏乡南湾墓地,新疆博物馆文物队曾在这里发掘古代墓葬100多座。出土文物中,见多件铜斧、小铜刀、彩陶、红褐陶及石器。铜刀的形制与哈密五堡出土铜刀相同。其总的特征,似与巴里坤、奎苏、石人子、哈密五保墓地时代相近①。
其他如木垒县四道沟遗址,早期文化层在距今3000年前,同样已经见到了铜器。这些小件铜器与磨制石器、骨器、陶器共存②。伊吾县卡尔遗址晚期文化层,出土石罐、青铜器③。阿克苏县喀拉玉尔兗古遗址,在距地表深4米的地下,见青铜环,与石斧、石罐、陶器、兽骨共存④。这些遗址外,还有其他一些地点,如巩乃斯河上游查布哈河工地,特克斯县铁里氏盖遗址等处,也都曾采集到过青铜刀、铜斧、牛头形铜饰物等。
从这些古代遗址,可以看到其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一个逻辑的结论是:在距今3000年前后,新疆大地青铜器的使用,已经是比较普遍了。
三
自公元前1000年中期到战国,新疆各地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址更多,而进入战国时期,不少遗址中已见到铁器,如小铁刀、铁镞、铁钉之属。这一现象说明:进入战国时期,新疆地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
为了更进一层地认识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这一历史阶段内的铜矿开采及冶铸事业,是应予注意的重要一环。
从铜、锡矿蕴藏来看,新疆算不得一个很丰富的地区,但铜矿点并不少。只是过去已经开采的点就有伊犁地区特克斯县的菁布拉克、尼勒克县奴拉赛山、乌鲁木齐地区的达坂城、哈密地区的沙泉子;在塔里木盆地周缘,有阿克陶县的卡拉玛、特格里苏曼,拜城县滴水,莎车县的阿尔巴列克,托克逊县的可可乃克等处。在尼勒克县的奴拉赛、圆头山,拜城县的滴水,还曾见到古代采矿痕迹。这些铜矿点,蕴藏量虽不很大,但埋藏不深,开采较易,而且含铜量也较丰富。至于锡,在博尔塔拉地区的图尔贡河谷右支流上游,有相当数量的蕴藏⑤。无疑,这些铜、锡矿藏资源,是新疆地区青铜制造工业发展的有利物质基础。
这些铜矿点中,尼勒克县境的圆头山及奴拉赛山,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采矿及冶炼遗址。
圆头山及奴拉赛山古铜矿遗址,均位于尼勒克县阿晋拉勒山北坡,喀什河南岸的低山丘陵地带。圆头山古代矿坑距县城约5公里,因山形似孤立的钟状山头,故名圆头山。山顶有北西320。走向的两条破碎带,充填含铜石英—方解石脉,部分地方被亚沙土覆盖,但有锅形洼地,可以追索矿体。沿矿脉使用槽探,结果表明:在风成亚沙土覆盖层1米以下,见有大量废矿石堆积,2米以下仍未见基岩。
沿铜矿脉展布的锅形洼地,为古代采矿坑的遗迹。坑口直径2.5米,底径1米,深2米。其上覆亚沙土,丛生灌木。从展布情况分析:当时采矿是间隔采掘,弃贫求富,最深处已采到3米以下。
沿圆头山铜矿脉,在亚沙土覆盖层下,发现了大量废矿石堆积。在废矿石堆中,有很多扁圆形、杏仁形、卵圆形石器,直径多在10~20厘米以上,腰部有宽约2厘米的槽痕,边缘圆滑,局部有破裂脱落缺口,明显为使用痕迹。石料多为花岗岩、石英钠长斑岩、硅质粉沙岩等。石料取自喀什河河床砾石和附近二叠系砾岩的砾石,与石器共存有木炭碎块。将用这些炭块送请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碳14年代测定结论为距今2650±170年,相当于春秋时期。
圆头山铜矿遗址,只见到这种露天采掘矿坑、大型石器。与石器共存,虽见木炭,但未发现进一步的冶炼痕迹①。
去圆头山矿点不远,为奴拉赛古铜矿开采、冶炼遗址。
奴拉赛古铜矿遗址,距尼勒克县3公里。矿井位于奴拉赛沟中游右岸的山腰部位,这里有含量丰富、品位很高的脉状晶质辉铜矿,共见两条矿脉。在一条矿脉上发现一处槽形洼地,洼地局部为一不规则大坑,内有废石及矿石堆积,在这一堆积中,捡到直径达20厘米的卵圆形石器②。
在另一条矿脉上,见到多处采矿洞口。地质工作者在距山顶50米处爆破,发现一暗洞。洞深30米,长20米,最宽处6米。底部积水深达8米。在洞底岩石上,发现了木炭碎块及骨片,骨片上已附着一层孔雀石,说明年代已十分久远。这一竖井的自然洞口,因废石、黄土状岩石覆盖,没有完全探明。其后,考古工作者又在这里进行了调查。报道称:发现了十余处竖井洞口,每个洞口大致5米见方。洞口已塌毁,为碎石、砾砂和丛生的野草所覆盖。各竖井洞口在地下是相通的,形成了网络似的采矿平洞和巷道。有的坑道已遭水淹;进入坑道,尚可见到支撑矿层的坑架。坑架是用原木分为数层揳入坑壁而成,保存完好①。
在采矿竖井内及井外,发现了大量铜矿石及石器。石器形制均作圆或扁圆形大石锤,一头圆钝、一头稍尖锐,最大直径约为20厘米,重1.5~5公斤多。石锤一端大都凿有纵、横向宽条凹槽,以利于绳索捆绑。这类石锤的特征与湖北大冶战国时铜矿遗址内所见石锤一样,似为采掘工具,但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平衡、提升工具。这种造型的一致,为我们分析2000多年前新疆西部地区与湖北大冶地区之间在矿冶技术上的交流,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资料。
距矿井不远的沟谷内,为冶炼遗址。炼砟堆积厚达1米。炼砟灰内见木炭、铜锭,还见到陶片、矿石、动物骨骼等。油黑色炼砟上残留着木炭或木质纤维状印痕②。这表明:奴拉赛古铜矿内所采矿石,只要运送到旁近的山沟内,即可冶炼,冶炼用的燃料,是木炭。
对这里出土的铜坯,曾进行过分析。铜坯似碗形,一面圆凸,一面平。共见五块。锭块重者十余公斤,轻者每块3~5公斤。铜锭块质较纯,含铜量在60%以上。性脆,断面呈银灰色,磨光面银白反光,可鉴人影。
这处矿冶遗址的年代,曾取矿洞内支架坑木进行碳14测定,结论为距今2440±75年,相当于战国早期③。
从圆头山、奴拉赛山这两处采矿及冶炼遗址资料,似可结论,采矿技术从春秋到战国时期,曾经历了一个显明的发展。从地面挖坑采矿到竖井采矿,标志着两个不同技术发展阶段。进入战国时期,在采矿技术上表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在深数十米的地下,从找矿到开掘竖井、掘进坑道、支架防护、采矿、排水通风、提取运输矿石,都须要比较成熟的技术知识,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它绝不是露天挖坑取矿所可比拟的了。
采矿与冶炼集中在一起,这完全符合经济的原则,但也需要更严密的组织。从这些资料可以推论,在战国时期,新疆地区的铜矿开采、冶炼生产,已是社会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生产部门,紧密联系、彼此协作的各个生产环节,要求有相对稳定、并掌握一定专门技术的生产工人,在统一的调度下行动,才能保证生产秩序的正常进行。这些资料,对我们认识公元前4世纪前后,新疆地区的铜矿开采及冶炼生产,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是有说服力的。
铜矿开采、冶炼,是青铜器生产的物质基础。要深入认识新疆地区古代青铜器的生产,离不开对这一基础的了解。对这一基础的认识和了解,会使我们对古代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认识大大深化。
与战国时期铜矿的开采、冶炼事业发展相一致,在这一历史时期,新疆各地出土了更多的铜器,不少是大型铜器。伊犁地区的新源、察布查尔、昭苏县,就陆续有多批铜器出土。新源县内,巩乃斯河谷地带,农业生产中见到了一批铜器,其中包括通高42厘米的青铜武士俑。武士头戴阔檐高帽,帽作尖顶,前弯如钩。武士裸上身,着裙,右腿跪地,双手持物(已断裂遗失),分别置于腿上,长脸,高鼻、肌腱鼓凸,孔武有力。共存承兽铜盘一件,盘作方形,盘内两角各蹲一兽,似熊,憨态可掬。兽足铜釜,三兽足。釜作平口深鼓腹,上腹部附四耳,二平二直,腹饰弦纹三道。其他如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已残。两虎面唇相接,特征明显。对兽圆环,二兽回曲相向,鬣毛上卷成孔,作奔跃状①。据了解,十年动乱期间,在新源县城附近还曾出土过与这一组大型铜器风格相同的青铜文物。据看到的同志介绍,铜器中的大型承兽铜盘,盘上环列异兽一圈。共存铜器中,同样有兽足铜釜等物。此外,在昭苏、察布查尔等县,同样见到大型铜器、兽足盘。铜鍑通高达50厘米上下,深腹饰弦纹,圈足。铜盘,矩形,四兽足。除圈足铜鍑外,伊犁地区陆续出土的这些大型铜器,从器物造型、装饰艺术风格看,一般均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新疆历史舞图台上的塞人文化遗物②。从出土数量多,个体造型巨大,铸造工艺精湛,野兽形象逼真,神气十足等特点,充分表现了这一阶段内青铜工艺臻于成熟。
除了伊犁地区以外,在和静县查布干河口古代墓区、阿拉沟东口及鱼儿沟车站地区古墓葬群、鄯善县苏巴什古墓区等处,这些地点的早期墓葬、出土文物都是青铜器与彩陶器、木器等共存。时代也是在战国或战国以前。自可看作是这一历史阶段中的遗址。这些资料可以说明:到公元前1000年中期,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水平,处于盛期,由此而后,即逐步迈入了铁器时代。
四
关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发生、发展,向铁器时代过渡,它本身的特点及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在新疆考古研究中,还是一些尚待具体建设的新概念。本文即使提到这些方而,充其量说,也只是初步提出了问题。它们都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受到检验,求得发展、提高。
正如本文实际已经说明的,在现有的考古资料基础上,对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这些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一些初步的概念,还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说,由于不少素材只是采集、调查资料,发掘资料比较少;已有的这一部分发掘资料,分布面也不均衡,一些地点比较集中,不少地区可以说还是空白。而且,对这些已经到手的资料,又缺少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最简单的一点,对所有已经入藏的出土铜器,对它们的金属成分进行分析测定统计,这样一个完全应该进行的项目,除少数样品曾经进行以外,大部分就未能完成,而只是就其形体、使用情况进行推理,这就十分不够。不言而喻,这种状况,当然会极大地局限我们认识的深入。
据现有资料,本文明确提出:公元前2000年前,新疆地区已经步入了青铜时代。这当然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和不少同志传统的、感性的认识“新疆地区古代文明发展程度比较低,较之中原地区,要远为落后”这样一种传统的、有影响的概念,是有差别的、相当不同的。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看,新疆地区青铜器的造型、纹饰等,与黄河流域差异较大,具有相当鲜明的自身特点,而与中亚西部、西伯利亚南部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南阿尔泰等地的出土物,存在较多的联系。这可能与彼此地域接近,而在古代往往又是同一居民集团,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有关。
新疆地区,作为亚洲腹心地带,民族迁徙频繁,是交通来去之要冲,黄河流域古老文明在这里投射下光明、产生过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当然也不会例外。起源、发展中心在黄河中游的鄂尔多斯草原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比较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哈密地区同样出土了,就是一个鲜明的、有说服力的实例。目前所见,虽只有一个点,随工作深入,当会有更多资料涌现。这对研究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古代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及联系的具体途径,都是很值得人们注意的。
粗略观察现已出土的铜器,一个印象比较突出:实用器居主、礼器较少。而在实用器中,生产工具(有些是明显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具)又占较大比重。青铜工具,当然代表着一种更进步的生产力。因此,随青铜时代的到来,青铜工具的使用,对新疆的社会生产、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些怎样的具体影响,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这对古代新疆历史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多次强调、重复,关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一些概括,是很粗浅的。这当然不是什么谦虚之辞,而是在这一阶段中难免的局限。这种情况下,公开提出这些观点,除了希望推动有关研究的深入以外,还希望借此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得到指正。希望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使有关研究不断发展、提高,使新疆地区的考古研究事业得到进一步的繁荣。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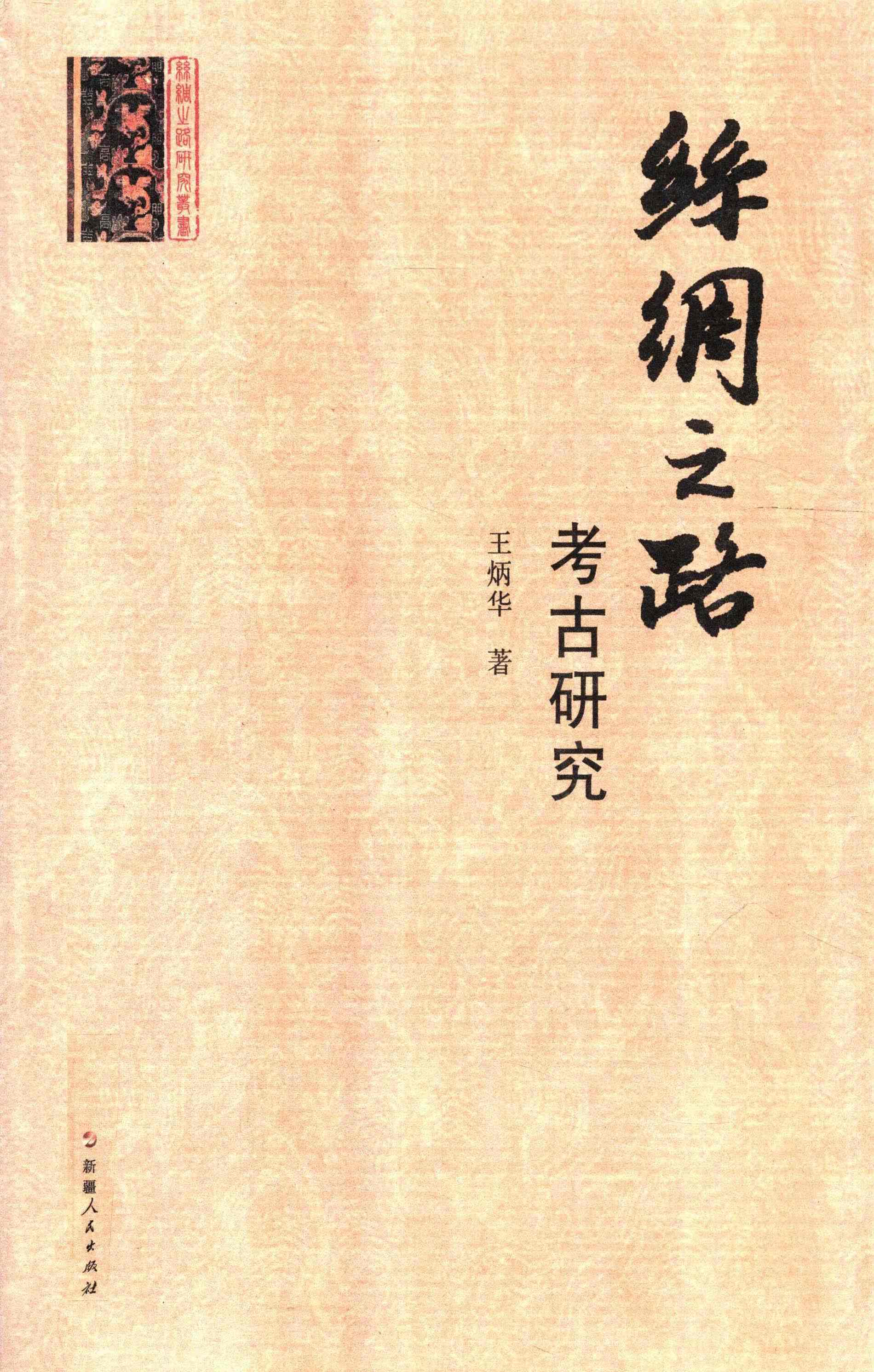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