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70 |
| 颗粒名称: | 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 |
| 分类号: | K878 |
| 页数: | 12 |
| 页码: | 096-10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新疆细石器遗存调查或了解的遗址、细石器类型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操持细石器等类型的生产工具等。 |
| 关键词: | 新疆 细石器 研究 |
内容
细石器遗存,从目前资料看,全国大部分地区差不多都有发现。但是,正北方地区,尤其是从东北到内蒙古以至新疆广大的北方草原地带,它所据有的非常重要的地位,不是其他地方散见的、少量细石器遗物所可比拟的。从新疆地区已有资料分析,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尤其是新疆新石器时代,占主体地位的原始文化内容,就是细石器。换句话说,要认识新疆地区早期原始文化的内涵及基本特征,最主要的,就在于具体研究这片地区内存在的细石器文化遗址。
新疆地区,据现有资料,大概在距今4000年前后,保守一点,或者说,在距今4000年前期,生产中已陆续使用了铜金属工具,步入了青铜时代。而在这以前,当是新石器时代或早于新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阶段。目前已经工作的全部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4000年以前,新疆地区的早期考古文化遗址,主要就是以细石器遗物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这样,在新疆考古研究中一个相当流行的概念就应该特别强调地予以澄清。在过去发表的许多文章里,几乎都是把新疆地区有彩陶器出土的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之间的金石并用期遗存来认识的。笔者过去也曾持有同样的观点,从这一角度认识过问题①。在工作还不深入、掌握资料也不丰富的情况下,有这样的认识,也不奇怪。因为彩陶器,从国内外无数考古资料分析,确曾是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物,出现这样的逻辑联系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根据新疆地区已见的包含彩陶器的全部文化遗址资料,却不得不提出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统计资料说明,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包含彩陶器的文化遗址中,几乎都见到共出铜器。有些遗址中,见到大型铜工具。在孔雀河古墓沟距今3800年上下的一处古代墓地内,虽未见到彩陶器,但却见到小件铜饰,尤其是在墓地内大量出土的棺木、木器上,普遍保留下了锐利的金属工具加工的痕迹。根据这些资料,就不能不得出一个逻辑的结论:新疆地区的彩陶,与邻近的甘肃或中亚地区相比较,时代可以肯定较晚。它们不是作为新石器时代具有特征的代表性文物出现于历史舞台,而主要是在进入青铜时代才见使用的。而且,晚到铁器时代,比如,从绝对年代看,到相当于战国、两汉阶段,这类彩陶器仍在使用之中①。这样,就不能不得出一个新的结论:讨论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或更早石器阶段考古文化,目前所涉及的,只能是细石器文化遗址。换句话说,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或更早的中石器阶段考古文化,除了一定数量的细石器遗址以外,几乎还没有接触到其他类型的考古文化资料。这是一个新的概念。从这个新的概念出发,自然就使我们更深一层地看到了对现存细石器文化遗址进行比较深入的野外工作、室内研究的重大学术意义。舍此,我们就不能对新疆地区原始社会阶段的考古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正是我们进行这一新探索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一
新疆地区,到目前为止,先后调查或工作过的细石器遗址,已见诸报道,或虽无正式报道,但却是笔者直接调查或了解的遗址有:
(1)三道岭。位于哈密市西约80公里的三道岭镇,现为一处大型露天煤矿所在。20世纪30年代,杨钟健、德日进在这里工作时,在第四纪黄土层的最上部及地层表面,发现不少细石器。包括用砾石打制成的刮削器、细长石片、锥形石核等。细石器石料,主要为玛瑙和石髓②。这处遗址,笔者曾两次前往调查,未有所获。看来,已在煤矿建设中消失。
(2)七角井。遗址位于天山中间的七角井盆地内,曾先后发现两处细石器分布点。
其一,在七角井镇西10公里左右。杨钟健、德日进曾在这里采集到砍砸器和扁锥形石核。这类石核,是新疆细石器遗址中比较典型的文化遗物。遗址区所在,除一区土庙遗迹外,是典型的戈壁荒漠景观③。
其二,在七角井镇东北500多米处,位于公路北侧。在约2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见到细石器分布点8小片,彼此同在一个小的地区范围内,但相去数十米或百米之遥。④笔者和新疆考古所东疆队同志一道,在这里工作不到三天,采集到各类细石器标本近700件①。
七角井,是天山中间的一块小盆地。地表无水,植被主要是胡杨、红柳、芨芨、骆驼刺等耐旱、耐盐的植物。文化遗物有石核、石片石器及细石镞、石钻头、大量细石叶、圆头刮削器等。石核有锥体、柱状体等。细石器多见第二步加工,但完全不见陶片共存。根据这一特征,曾有学者提出,它是中石器阶段的一处细石器遗存②。
(3)木垒河。遗址位于木垒县城内约500米,处木垒河东岸草地上。细石器散布在南北约200米、东西约50米的范围内。共采集得石器标本72件,绝大部分为细石叶。石质主要为燧石及矽质板岩、石英岩、石英、玛瑙等,特点是大型打制石器与典型细石器共存。细石器中,除柱状石核外,还见到三角形凹底镞、小镞、石片等③。
(4)四道沟。位于木垒县城西南约10公里。这是一处相当于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古代居住遗址。发掘中见到灰坑、灶址和柱洞,出土小件铜器及磨制石器、陶器。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晚期文化层内,均见到细石核,石质为燧石,石核上有清晰的剥打细石片后留下的斑痕④。
(5)伊尔卡巴克。位于木垒县北38公里。地表为沙窝。但因地下水位稍高,一些地块植被很好。采集得细石器数十件。包括细石核、小石叶、石镞及石片、刮削器等。细石镞通体压修,造型规整,凹底,十分锐利。细石器所在,也见到彩陶片、磨石及小件铜器。彼此关系尚无法确切说明⑤。
(6)阿斯塔那。遗址位于吐鲁番县城东南约40公里,阿斯塔那村西北戈壁滩上,处火焰山南麓。遗址北、西面环有一条干河床,河床以西为沙丘,在南北约七八百米、东西近一千米的地域范围内,地表采得细石器遗物760多件,遗址区内,也采集到粗沙陶。石质以硅质板岩为主,其他还有燧石、石英、玛瑙等。计有打制的石片石器(刮削器、尖状器、敲砸器、锛形器等)、石核石器(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及细石器,包括细长薄石片及小石核。其他还有琢制石器、石磨盘、石砧、石球、穿孔器等。也见到装饰品及玩具。陶器多平底,器形有钵、杯、碗及壶等,或有纹饰,均十分简单,主要为堆纹及压印纹⑥。由于是采集资料,细石器与粗沙陶器是否为同时期遗存,目前还难以作出完全肯定的判断。
(7)辛格尔。在吐鲁番盆地南缘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辛格尔村西沙丘,发现过300多件石器和陶片。细石器中包括锥状细石核、柳叶形石镞、小石镞、细长石片等,陶片呈褐色或红色,制作粗糙,少数陶片上有划纹或堆纹⑦。有人认为,辛格尔出土石器中,有一种鸟喙形的尖状器,与在哈尔滨附近,蒙古及美洲阿拉斯加发现的同类石器是相同的①。
(8)罗布淖尔地区。在罗布淖尔地区,涉及地域范围相当大。在这片地区内,自新中国成立前至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多次,在不少地点发现过细石器遗存。比较集中的地点是在孔雀河进入罗布淖尔湖的三角洲地带、孔雀河下游小河附近、楼兰古城遗址附近。具体情况是:
①1900~1901年,斯文·赫定在罗布淖尔地区采集得细石核和小石片各1件。
②1930~1934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霍诺尔、陈宗器及贝格曼等人,在罗布淖尔湖西北、孔雀河下游、雅丹布列克等处,约八九个地点都采集到了细石器标本,包括细石核、小石英、柳叶形石矛及小石镞等。一些细石器地点共存夹砂粗褐陶。这些地点,目前都是荒漠②。
③20世纪初,斯坦因在罗布淖尔湖西北,包括楼兰古城及古城遗址东北的三个地点,采集到小石叶、石镞。认为是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③。
④20世纪30年代,黄文弼在土垠西北、库鲁克山南麓、孔雀河北岸曾发现几处细石器地点,主要器型有细石核、小石叶;在孔雀河谷地带,也曾发现过几处细石器点,见三角形镞、石斧、玉斧,与晚期铜器及汉代文物共存于一地④。
1979~198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又曾先后三次到罗布淖尔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中也曾发现不少细石器遗址地点。
这些资料,十分有力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在石器时代,在罗布淖尔湖周围,湖西北地区,在孔雀河谷下游,曾经有过不少居民在活动,采集、渔猎经济,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这和当前罗布淖尔荒原上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
(9)英都尔库什。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英都尔库什山沟之南口。这里北距得格尔约100公里,南距阿提米西布拉克约75公里,居得格尔与罗布淖尔之间,是从吐鲁番盆地穿库鲁克山到罗布淖尔的必经之路,也是其间唯一有水草之处,水虽微咸,但驼马仍可饮用。在附近沙阜上,黄文弼曾采集细石核数件,小石叶120多件,叶片上或加工出锐利之尖角,石料主要为石英。其他还见较大型打制石斧两件,半圆形钻孔蛤壳饰物等①。
(10)且末。遗址位于且末县城南80公里,车尔臣河谷,贝格曼曾经在这里发现过细石器遗址。计有细石叶、石核、刮削器等,与篦纹陶片共存。也有与辛格尔所见素陶类同的陶片。这是细石器与陶片共存的又一例②。
(11)克里雅。遗址位于昆仑山西北,皮山县克里雅村东南10公里,居克里阳河左岸,东经77。56′40″、北纬37。14′20″处。这里发现的文化遗物中有一件用硅质岩打制的小石片,明显有刮削使用痕迹。与黄色粗陶片、骨片,烧过的石块和炭屑等共存③。
(12)乌帕尔。遗址位于帕米尔东麓,喀什市疏附县乌帕尔绿洲边缘。近年,在两个地点采集到多量细石器。石质多石英、燧石、硅质岩。见锥状细石核、柱状细石核、小石叶、石片刮削器、圆头刮削器等。遗址所在地区,也见夹沙粗陶片④。
(13)柯坪。位于县城西南,居柯坪塔格山与艾外依塔格山之间的萨尔干盆地的东缘,当乌旦库勒泉水汇合苏巴什河流出口处,古干三角洲阶地表面。阶地高3~5米,表面为草丛沙丘和不定型流沙覆盖。在沙间平地上见大量细石器,共采集标本300多件,有细石核、小石叶、刮削器等。没有陶片共存。石质主要为绿色硅质岩、燧石。值得注意的是,附近并没有这类岩石出露,河谷中也没有此种岩石的转石,石料当是取自较远的处所⑤。
(14)巴楚。1913年,斯坦因在巴楚县附近曾采集得一批细石器标本,计细石核2件、石镞1件、尖状器1件、小石片8片。斯坦因曾认为这可能是旧石器时代遗存,但据有关资料分析,当同样是新石器时代之文物⑥。
(15)焉耆。黄文弼先生在博斯腾湖畔40里城子南沙碛中,曾采集到细石镞1件①。
(16)雅尔崖古城沟西。在吐鲁番县城西北10公里交河沟西土岸上。近年,在这里曾进行过多次调查,采集到相当多量的细石器标本。除石核及石核制器外,打制石片所占比重相当大。石片宽大于长,形制不规整,边刃见再加工及使用痕迹。相对比较,细石叶数量较少,也见到石镞。遗址区内,有早期陶片,但都是地面采集所得,这类细石器与陶片是否共存,很难判定。只从细石器本身进行分析,则明显具有比较原始的特征②。
(17)柴窝堡。遗址在乌鲁木齐市东向40多公里的天山山谷中,居柴窝堡湖畔。共见两区,一处湖之东北,又一处居湖之西南。共采集得细石器标本500多件。细石核有锥状、柱状、船底形等,石片石器占较大比重,有尖状器、刮削器等,多以打制石片加工而成。细石叶或以细石叶为料进一步加工的细石器数量较少。部分制器的工艺特点与山西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的细石器工艺特征一致,显然是早期特征。遗址范围内也见到几块彩陶片。因系地面采集,而且附近又有晚期遗址、墓葬,很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遗存。在这片遗址地区内,也还采集到通体精细压琢、造型规整的柳叶形矛头,虽然是个别标本,但显然具有比较进步的特征。从这一角度看,柴窝堡细石器遗址似乎曾经历了相当长的延续发展过程③。
(18)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在若羌县境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喀尔墩和野牛泉。野牛泉遗址,位于东经87。54′30″,北纬36°53′45″处,海拔4530米。由于地势高寒,空气稀薄,生态环境严酷,不适于人类生存活动,但在1200平方米的范围内,却发现了相当丰富的细石器标本。喀尔墩遗址与此纬度相同,东去约200公里,遗址面积相近。在这两处遗址区内曾经发现并采集了一批细石器标本,有石核、刮削器、小石叶等。石料以燧石和水晶石为主,器物经打制并压修加工,具有明显的早期文化特点④。
(19)克尔木齐。在阿尔泰山南麓阿勒泰克尔木齐村,曾经发掘过一片古代墓地。在相当于战国时期的一批古墓葬内,出土多量细石镞,形制规整,通体经过压修。从出土现场观察,这类细石镞,明显是当时的一种锐利武器⑤。
(20)吉木萨尔等处。袁复礼曾在此地发现过细石器遗址,采集到各类细石器标本,但具体资料至今未见发表。
(21)善县迪坎尔遗址。位于迪坎尔村东南约800米处。遗址范围约3平方公里,采集到细石器标本数百件。主要包括锥状、柱状细石核,小石叶,圆头刮削器。遗址区内不见陶片。石叶宽短,器形稍大,显示了比较原始的特征①。
(22)鄯善连木沁乡克孜尔库木遗址。位于连木沁乡丘旺克尔村尤土克西南约3公里处。在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可以看到大量剥打下来的石片,而只见少量成型的石核及石叶、斧形器。大量石片,不见进一步加工或使用痕迹,应是制作石器过程中的废料②。
(23)善县洋海阿斯喀勒买来遗址。位于吐峪沟乡洋海阿斯喀勒买来村西北约3公里的戈壁上,属吐峪沟口前沿洪积扇地带。在这里采集到细石核、刮削器等,从器形观察,比较原始。
(24)塔西肯艾热克遗址。居鄯善县鲁克沁乡三个桥村南约1.5公里处,采集到柱状细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细石镞、圆刮器、双刃刮器、细石叶及敲砸器等③。
(25)七城子细石器遗址。位于木垒县大石头乡南约20公里处,遗址傍近泉水,在东西约400米、南北近600米范围内,采集到细石器标本160多件。包括石核、石叶、石片石器等,石核多楔形,石叶或经进一步加工。刮削器多用石片进一步加工而成。文化面貌比较原始④。
(26)塔克尔巴斯陶遗址。位于木垒县城东北约32公里处的冲积平原荒漠地带,遗址区内见泉水。采集到细石器40多件。有锥状石核、柱形石核、楔形石核、刮削器、石片石器、细石叶等,不见陶片,文化内涵比较单纯⑤。
这26处细石器遗址,当然不可能是全部遗址资料,但就从这一不尽完整的资料出发,也可以看到:其分布地域差不多遍及新疆大地,从昆仑山北麓至帕米尔高原山前地带,天山南麓,罗布淖尔荒原及吐鲁番盆地,哈密绿洲及天山北麓的木垒、吉木萨尔,以至阿勒泰草原。可以看到:细石器,曾是新疆大地上古代居民普遍使用过的一种工具。这类细石器遗址,因为多是地面调查、采集,没有经过科学的发掘,因而对这类细石器遗址所代表的时代,其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它的发展、变化历程,还不能揭示出更多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就从这类采集资料分析,也明显可以作出结论:它们曾经历了一个漫长发展过程,是我们认识新疆地区古代居民早期历史不可缺少的一批重要资料。
二
根据前述细石器资料,对新疆地区细石器类型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址分类、分期、经济生活类型,以及有关遗址的绝对年代等,都曾有考古学者进行过探讨。
有一种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其要旨是:根据新疆地区现有的细石器遗物(指用间接打片并用压制法进行第二步加工取得的各类细石器),从加工技术及石核形制、石器造型方面看,均和我国东北、内蒙古、陕西等地所见的细石器工具,具有相同的特征。属于细石叶细石器这个系统。
从宏观角度分析,细石器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分布,经历的时间也十分漫长,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器时代以至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的历史阶段,都曾使用过细石器工具。而从细石器的形制差别,又可区分为细石叶细石器和几何形细石器两大系统。前者分布在我国、蒙古、南西伯利亚、日本和白令海峡地区。几何形细石器则分布于欧洲、北非、西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多半月形、三角形、梯形石刃。从现有资料分析,细石叶细石器在我国华北地区发生得早、分布也比较集中,华北地区当是这类细石叶细石器的起源地。新疆地区的细石器,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明显曾经接受过华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影响。
从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遗址如寺峪、小南海,已经可以看到细石器的雏形。时代稍晚的一些遗址,如山西下川,细石器已经十分典型。而晚到金属出现,进入阶级社会,细石器在一些地点,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持续了一个十分长远的历史时期。具体到新疆地区,基本情况也是相类的。在上列经过初步工作的26处遗址点(其中罗布淖尔地区,本身又包含了多处遗址点)里,情况也是各有不同。从总的方面看,确应该强调,新疆地区属于我国细石器这一系统;在细石器工艺上接受过华北地区的影响;同时又应看到,它们还具有不少自身的特点、自身的个性。比如,新疆不少地点,阿斯塔那、罗布淖尔地区等处,细石器遗址点里多见一种桂叶形石矛头,通体压成鱼鳞状,形制规整,制作精细。这种石器在中原地区就几乎没有见到,个别地点见到相同器型,而数量也很少。又如,在阿斯塔那遗址中所见的一件锯齿形刃刮器,也是华北地区少见的器形。
在新疆这么一个广阔的空间地带,时间又延续如此长久的细石器工艺,会在相当程度上显示地区的特点,时代的差别,这是不会令人奇怪的。但是,因为缺少比较深入的工作,尤其是没有一处遗址曾经科学发掘,缺少了地层叠压关系;多数地点因风蚀沙移,也已失去原生地层。虽同样都是地面的采集物,但实际上也可能早晚相杂,并不单纯。这些因素,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我们的认识,影响了问题的深入。
根据现有的采集资料,有关细石器或共存文物所显示的制作工艺的成熟程度,新工艺及新器物的出现等,我们可以将已知的新疆细石器遗址区分几种不同的类型,并试为探讨它们的相对早晚或绝对年代。这一方面,早有文章进行过探索①。本文吸取了这些成果。但从总体观察,本文却是一种新的分类,新的观点。因为没有发掘资料,就笔者言,其中一些遗址点,又是间接的知识。因此,这一分类、分期,只能是初步的认识,须要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接受检验,求得完善。
第一类:可以阿尔金山、雅尔崖古城沟西、柴窝堡湖细石器遗址为代表。这一类型的遗址,除少量细石器,包括石核、小石叶、细石器等外,共存大量打制石片石器,形成文化遗物的主体。这类打制石片较厚,宽往往大于长,形制不规整,取其边刃或尖端用作刮削、锥刺。边刃或尖部见第二步加工或使用痕迹,这是明显的石器制作工艺还比较原始的状况,也是时代比较古老的证明,当属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距今时间可能在万年以前。这里,要附带说明几点。一是着重以石器制作工艺比较原始为根据,来论定时代早晚,是否合适?因为道理很明显,在晚期文化遗址中,往往还存在相当原始的古代工艺及制器。如大型打制石器,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或更晚的文化遗址中都还见使用,就是有力的说明。但笔者在这里所以还持这样的论点,是因为在这类遗址中,具有较为原始形态的打制石片石器占有很大比重,近于主体,这就不是一种残余的形态,而应作为时代古老、工艺原始的特征;二是在部分遗址区内,曾发现过陶片或彩陶片。本文在分析时,对这一文化现象均予剔除了。所以这样做,根据在于:这些细石器遗址所在,都有晚期的墓葬或遗址,出现有关陶片并不令人奇怪;根据对新疆地区的考古文化的全面分析,新疆地区目前所见彩陶,一般都在金石并用时期以后,主要是青铜时代的古代居民生活用器,甚至到两汉阶段,彩陶器仍然还在使用,它们的时代明显要较这类细石器工具为晚。此外,在柴窝堡湖畔的细石器遗址内,还曾采获一件残断的桂叶形石矛,形制规整,通体修琢,工艺相当精致,它是后期新疆细石器遗址中具有特征的典型器物之一。它在柴窝堡出土,或可作为遗址在晚期仍在使用的一个说明。
第二类:可以七角井、三道岭遗址作为代表。遗址地区内,细石器工具比重较大,共见各类石核、细石叶,以小石叶为料进一步加工成的小石镞、石钻、雕刻器等近700件。长数厘米,宽数毫米的细石叶随处可见,最长达7厘米,宽只三四毫米,可见压剥细石器工艺之精。这类细石器,多数未经第二步加工,但锋刃锐利。笔者曾用之于切割羊肉,真可谓得心应手。以细石叶为料进一步加工成的细石镞、石钻头、雕刻器等,两面压琢修整,加工精细,制作工艺是十分成熟的。这类细石叶细石器与石核砍砸器、打制石片及以石片为料加工成的刮削器、尖状器共存。这里出土的指甲形刮削器,不论造型还是制作方法,均与山西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同类器物一致。还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在七角井采集的700件细石器中,没有发现一件磨制石器标本。而且在约20万平方米的遗址地区内,见到细石器遗物分布点共8处,却绝不见一块陶片。这些特点表明:这里有比较成熟的细石器制作工艺,细石器工具比较发达,数量多,这都明显较第一类型遗址前进了一步①。
第三类:可以木垒河细石器遗址为例。所采集的石器标本中,主要为细石器,包括柱状石核、多量细石片。细石片大都截断,表明是作石刀刃片的材料。还有细石镞,镞体作三角形,通体修压精致。更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底部内凹。据考古所邢开鼎同志介绍,在木垒县北伊尔卡巴克细石器遗址中也发现凹底石镞多件。石镞通体压修,形制规整,近树叶形。体薄,尖、刃均极锋利。尾端均凹人。这种凹底石镞,可以看作是木垒地区细石器中具有特点的一种器形。在木垒河细石器遗址中还有一个特点是细石器与打制的较大型石器共存,器型有斧、锛之属,刀口同样未经加磨。在遗址范围内,还见到了十分粗糙的夹沙红灰陶片及细沙质灰陶。不论从石器加工制作的成熟还是陶器的出现,都说明这是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遗址,其时代,较之七角井明显要晚。
第四类:可以吐鲁番阿斯塔那、罗布淖尔地区为代表。无论是阿斯塔那,还是罗布淖尔西、北部地区,一是有关细石器的采集品都十分丰富;再是细石器与打制石器、琢制石器、陶器共存;还出现了装饰品及玩具,如穿孔砾石坠及弹丸。在细石器中,器形比较定型,制作工艺精巧。尤其是桂叶形矛头,通体压修成鱼鳞状,是这两处遗址地区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器形。石镞制作同样精巧,多带铤,这与木垒遗址又形成显目的差别。细石器大多经过第二步加工。在罗布淖尔地区,细石器分布地点,还见到有少量磨制石器。共出陶器,以阿斯塔那为例,均手制,多平底器、多沙质陶。对阿斯塔那遗址,多认为已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其绝对年代或在距今4000年前后①。近年,新疆考古所在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发掘过一处罗布淖尔地区土著人的古墓地,在一座墓葬内曾出土过一件制作精巧的细石镞,形制规整,锋刃锐利,出土时仍穿插一男性骨架的骶骨缝中,看来是当时仍在使用而且有杀伤力的一种武器。这种石镞的造型、工艺,与罗布荒原上曾经采集的细石镞颇多共同之处。这一墓地,绝对年代在距今3800年前后。这一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这类细石器遗址绝对时代时的参考。
至于四道沟、阿勒泰等处的细石器,已与金属器共存,从总体上看,已只能算是一种古老技术的残留。在讨论新石器时代以前的细石器遗址及其分布、分期时,可以不作考虑了。
三
新疆大地,曾经普遍存在细石器遗址。新疆地区土著居民,操持细石器等类型的生产工具,与大自然斗争并索取,求得自身的生存及发展,曾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从细石器及与其共生的石片石器、砾石石器等进行分析,以柴窝堡、七角井等类型的遗址为代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大型砍砸器,可以是生产木器,砸碎兽骨的有力手段。至于细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等,则可以是割剥兽皮,切割兽肉,采集植物籽实、块根的工具。将细石叶经过切断、加工,嵌入骨、木柄缝中,可以成为一柄很锋利的石刀。这种复合的工具——细石刀,在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遗址、青海乐都县柳湾新石器时代墓地中都曾有实物出土,给了我们以有力的启示。这种细石叶,刃部非常锋利,切割羊肉,较之钝铁刀,还要快利。至于石镞、石矛头,当然是更有力的生产工具,从其可用于狩猎野兽,也可以致人殒命看,其杀伤力是很大的。
综观全部细石器遗址资料,可以看到从早期到晚期,这类采集、狩猎经济,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在后期,如木垒河、阿斯塔那、罗布淖尔等处细石器遗址中,可能已经有了农业生产。这方面,除石器中出现了石磨盘、磨棒等可用于谷物加工的用器外,还有使用陶器提供的佐证,淀粉类的谷物籽实,是不能直接用火烧灼的,它的加工、熟制,必须用陶器类可供蒸煮的器具。陶器的出现使用,往往是和农业、定居相联系在一起的。这类文物可以初步结论到距今4000多年以前。这类细石器遗址的主人,已经有了农业的生产。从孔雀河下游到罗布淖尔湖西、北岸,楼兰古城一带,这一阶段的遗址分布相当集中,可以看到,当年在这片地区内,曾有不少氏族部落在生息、繁荣,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在综观新疆地区这些细石器遗址点时,又一个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问题是:在这些遗址中,除个别遗址点(如木垒河)仍是自然环境良好,水草咸备,农牧业皆宜以外,绝大多数遗址点,目前都已是一片荒漠或半荒漠,一些地点(如罗布淖尔地区),甚至成了一片少见生命的世界。没有水、没有树木,基本没有动物。这样的环境,无论是进行采集、狩猎还是农业,当然是完全不行的。七角井细石器遗址,基本也是这样的情况。遗址范围内,除少数胡杨、红柳、骆驼刺等耐盐耐旱植物外,同样是一片荒漠景观。木垒县伊尔卡巴克遗址,现在已沦为一片沙漠。吐鲁番阿斯塔那细石器遗址所在,则是一片不毛之地。这些例子,不能不使我们产生一个逻辑的推论:在1万年以来,或者说是距今4000年以来,这些遗址点所在的自然地理环境,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导致这些变化的因素,是社会的、人的原因呢?还是自然的原因?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随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研究课题需要有关学科专业工作者之间进行密切的配合和自觉的合作。对新疆一些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变化规律的探索,就是这样的课题之一。要使这个课题得到深入,就很需要地理、生物、气象、沙漠、考古等许多学科研究工作者的协同合作。借这篇小文提出这个问题,但愿引起有关学科同志们及科研组织领导部门的注意,使问题得到积极的推动和深入。
新疆地区,据现有资料,大概在距今4000年前后,保守一点,或者说,在距今4000年前期,生产中已陆续使用了铜金属工具,步入了青铜时代。而在这以前,当是新石器时代或早于新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阶段。目前已经工作的全部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4000年以前,新疆地区的早期考古文化遗址,主要就是以细石器遗物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这样,在新疆考古研究中一个相当流行的概念就应该特别强调地予以澄清。在过去发表的许多文章里,几乎都是把新疆地区有彩陶器出土的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之间的金石并用期遗存来认识的。笔者过去也曾持有同样的观点,从这一角度认识过问题①。在工作还不深入、掌握资料也不丰富的情况下,有这样的认识,也不奇怪。因为彩陶器,从国内外无数考古资料分析,确曾是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物,出现这样的逻辑联系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根据新疆地区已见的包含彩陶器的全部文化遗址资料,却不得不提出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统计资料说明,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包含彩陶器的文化遗址中,几乎都见到共出铜器。有些遗址中,见到大型铜工具。在孔雀河古墓沟距今3800年上下的一处古代墓地内,虽未见到彩陶器,但却见到小件铜饰,尤其是在墓地内大量出土的棺木、木器上,普遍保留下了锐利的金属工具加工的痕迹。根据这些资料,就不能不得出一个逻辑的结论:新疆地区的彩陶,与邻近的甘肃或中亚地区相比较,时代可以肯定较晚。它们不是作为新石器时代具有特征的代表性文物出现于历史舞台,而主要是在进入青铜时代才见使用的。而且,晚到铁器时代,比如,从绝对年代看,到相当于战国、两汉阶段,这类彩陶器仍在使用之中①。这样,就不能不得出一个新的结论:讨论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或更早石器阶段考古文化,目前所涉及的,只能是细石器文化遗址。换句话说,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或更早的中石器阶段考古文化,除了一定数量的细石器遗址以外,几乎还没有接触到其他类型的考古文化资料。这是一个新的概念。从这个新的概念出发,自然就使我们更深一层地看到了对现存细石器文化遗址进行比较深入的野外工作、室内研究的重大学术意义。舍此,我们就不能对新疆地区原始社会阶段的考古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正是我们进行这一新探索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一
新疆地区,到目前为止,先后调查或工作过的细石器遗址,已见诸报道,或虽无正式报道,但却是笔者直接调查或了解的遗址有:
(1)三道岭。位于哈密市西约80公里的三道岭镇,现为一处大型露天煤矿所在。20世纪30年代,杨钟健、德日进在这里工作时,在第四纪黄土层的最上部及地层表面,发现不少细石器。包括用砾石打制成的刮削器、细长石片、锥形石核等。细石器石料,主要为玛瑙和石髓②。这处遗址,笔者曾两次前往调查,未有所获。看来,已在煤矿建设中消失。
(2)七角井。遗址位于天山中间的七角井盆地内,曾先后发现两处细石器分布点。
其一,在七角井镇西10公里左右。杨钟健、德日进曾在这里采集到砍砸器和扁锥形石核。这类石核,是新疆细石器遗址中比较典型的文化遗物。遗址区所在,除一区土庙遗迹外,是典型的戈壁荒漠景观③。
其二,在七角井镇东北500多米处,位于公路北侧。在约2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见到细石器分布点8小片,彼此同在一个小的地区范围内,但相去数十米或百米之遥。④笔者和新疆考古所东疆队同志一道,在这里工作不到三天,采集到各类细石器标本近700件①。
七角井,是天山中间的一块小盆地。地表无水,植被主要是胡杨、红柳、芨芨、骆驼刺等耐旱、耐盐的植物。文化遗物有石核、石片石器及细石镞、石钻头、大量细石叶、圆头刮削器等。石核有锥体、柱状体等。细石器多见第二步加工,但完全不见陶片共存。根据这一特征,曾有学者提出,它是中石器阶段的一处细石器遗存②。
(3)木垒河。遗址位于木垒县城内约500米,处木垒河东岸草地上。细石器散布在南北约200米、东西约50米的范围内。共采集得石器标本72件,绝大部分为细石叶。石质主要为燧石及矽质板岩、石英岩、石英、玛瑙等,特点是大型打制石器与典型细石器共存。细石器中,除柱状石核外,还见到三角形凹底镞、小镞、石片等③。
(4)四道沟。位于木垒县城西南约10公里。这是一处相当于西周到战国时期的古代居住遗址。发掘中见到灰坑、灶址和柱洞,出土小件铜器及磨制石器、陶器。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晚期文化层内,均见到细石核,石质为燧石,石核上有清晰的剥打细石片后留下的斑痕④。
(5)伊尔卡巴克。位于木垒县北38公里。地表为沙窝。但因地下水位稍高,一些地块植被很好。采集得细石器数十件。包括细石核、小石叶、石镞及石片、刮削器等。细石镞通体压修,造型规整,凹底,十分锐利。细石器所在,也见到彩陶片、磨石及小件铜器。彼此关系尚无法确切说明⑤。
(6)阿斯塔那。遗址位于吐鲁番县城东南约40公里,阿斯塔那村西北戈壁滩上,处火焰山南麓。遗址北、西面环有一条干河床,河床以西为沙丘,在南北约七八百米、东西近一千米的地域范围内,地表采得细石器遗物760多件,遗址区内,也采集到粗沙陶。石质以硅质板岩为主,其他还有燧石、石英、玛瑙等。计有打制的石片石器(刮削器、尖状器、敲砸器、锛形器等)、石核石器(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及细石器,包括细长薄石片及小石核。其他还有琢制石器、石磨盘、石砧、石球、穿孔器等。也见到装饰品及玩具。陶器多平底,器形有钵、杯、碗及壶等,或有纹饰,均十分简单,主要为堆纹及压印纹⑥。由于是采集资料,细石器与粗沙陶器是否为同时期遗存,目前还难以作出完全肯定的判断。
(7)辛格尔。在吐鲁番盆地南缘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辛格尔村西沙丘,发现过300多件石器和陶片。细石器中包括锥状细石核、柳叶形石镞、小石镞、细长石片等,陶片呈褐色或红色,制作粗糙,少数陶片上有划纹或堆纹⑦。有人认为,辛格尔出土石器中,有一种鸟喙形的尖状器,与在哈尔滨附近,蒙古及美洲阿拉斯加发现的同类石器是相同的①。
(8)罗布淖尔地区。在罗布淖尔地区,涉及地域范围相当大。在这片地区内,自新中国成立前至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多次,在不少地点发现过细石器遗存。比较集中的地点是在孔雀河进入罗布淖尔湖的三角洲地带、孔雀河下游小河附近、楼兰古城遗址附近。具体情况是:
①1900~1901年,斯文·赫定在罗布淖尔地区采集得细石核和小石片各1件。
②1930~1934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霍诺尔、陈宗器及贝格曼等人,在罗布淖尔湖西北、孔雀河下游、雅丹布列克等处,约八九个地点都采集到了细石器标本,包括细石核、小石英、柳叶形石矛及小石镞等。一些细石器地点共存夹砂粗褐陶。这些地点,目前都是荒漠②。
③20世纪初,斯坦因在罗布淖尔湖西北,包括楼兰古城及古城遗址东北的三个地点,采集到小石叶、石镞。认为是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③。
④20世纪30年代,黄文弼在土垠西北、库鲁克山南麓、孔雀河北岸曾发现几处细石器地点,主要器型有细石核、小石叶;在孔雀河谷地带,也曾发现过几处细石器点,见三角形镞、石斧、玉斧,与晚期铜器及汉代文物共存于一地④。
1979~198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又曾先后三次到罗布淖尔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中也曾发现不少细石器遗址地点。
这些资料,十分有力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在石器时代,在罗布淖尔湖周围,湖西北地区,在孔雀河谷下游,曾经有过不少居民在活动,采集、渔猎经济,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这和当前罗布淖尔荒原上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
(9)英都尔库什。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英都尔库什山沟之南口。这里北距得格尔约100公里,南距阿提米西布拉克约75公里,居得格尔与罗布淖尔之间,是从吐鲁番盆地穿库鲁克山到罗布淖尔的必经之路,也是其间唯一有水草之处,水虽微咸,但驼马仍可饮用。在附近沙阜上,黄文弼曾采集细石核数件,小石叶120多件,叶片上或加工出锐利之尖角,石料主要为石英。其他还见较大型打制石斧两件,半圆形钻孔蛤壳饰物等①。
(10)且末。遗址位于且末县城南80公里,车尔臣河谷,贝格曼曾经在这里发现过细石器遗址。计有细石叶、石核、刮削器等,与篦纹陶片共存。也有与辛格尔所见素陶类同的陶片。这是细石器与陶片共存的又一例②。
(11)克里雅。遗址位于昆仑山西北,皮山县克里雅村东南10公里,居克里阳河左岸,东经77。56′40″、北纬37。14′20″处。这里发现的文化遗物中有一件用硅质岩打制的小石片,明显有刮削使用痕迹。与黄色粗陶片、骨片,烧过的石块和炭屑等共存③。
(12)乌帕尔。遗址位于帕米尔东麓,喀什市疏附县乌帕尔绿洲边缘。近年,在两个地点采集到多量细石器。石质多石英、燧石、硅质岩。见锥状细石核、柱状细石核、小石叶、石片刮削器、圆头刮削器等。遗址所在地区,也见夹沙粗陶片④。
(13)柯坪。位于县城西南,居柯坪塔格山与艾外依塔格山之间的萨尔干盆地的东缘,当乌旦库勒泉水汇合苏巴什河流出口处,古干三角洲阶地表面。阶地高3~5米,表面为草丛沙丘和不定型流沙覆盖。在沙间平地上见大量细石器,共采集标本300多件,有细石核、小石叶、刮削器等。没有陶片共存。石质主要为绿色硅质岩、燧石。值得注意的是,附近并没有这类岩石出露,河谷中也没有此种岩石的转石,石料当是取自较远的处所⑤。
(14)巴楚。1913年,斯坦因在巴楚县附近曾采集得一批细石器标本,计细石核2件、石镞1件、尖状器1件、小石片8片。斯坦因曾认为这可能是旧石器时代遗存,但据有关资料分析,当同样是新石器时代之文物⑥。
(15)焉耆。黄文弼先生在博斯腾湖畔40里城子南沙碛中,曾采集到细石镞1件①。
(16)雅尔崖古城沟西。在吐鲁番县城西北10公里交河沟西土岸上。近年,在这里曾进行过多次调查,采集到相当多量的细石器标本。除石核及石核制器外,打制石片所占比重相当大。石片宽大于长,形制不规整,边刃见再加工及使用痕迹。相对比较,细石叶数量较少,也见到石镞。遗址区内,有早期陶片,但都是地面采集所得,这类细石器与陶片是否共存,很难判定。只从细石器本身进行分析,则明显具有比较原始的特征②。
(17)柴窝堡。遗址在乌鲁木齐市东向40多公里的天山山谷中,居柴窝堡湖畔。共见两区,一处湖之东北,又一处居湖之西南。共采集得细石器标本500多件。细石核有锥状、柱状、船底形等,石片石器占较大比重,有尖状器、刮削器等,多以打制石片加工而成。细石叶或以细石叶为料进一步加工的细石器数量较少。部分制器的工艺特点与山西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的细石器工艺特征一致,显然是早期特征。遗址范围内也见到几块彩陶片。因系地面采集,而且附近又有晚期遗址、墓葬,很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遗存。在这片遗址地区内,也还采集到通体精细压琢、造型规整的柳叶形矛头,虽然是个别标本,但显然具有比较进步的特征。从这一角度看,柴窝堡细石器遗址似乎曾经历了相当长的延续发展过程③。
(18)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在若羌县境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喀尔墩和野牛泉。野牛泉遗址,位于东经87。54′30″,北纬36°53′45″处,海拔4530米。由于地势高寒,空气稀薄,生态环境严酷,不适于人类生存活动,但在1200平方米的范围内,却发现了相当丰富的细石器标本。喀尔墩遗址与此纬度相同,东去约200公里,遗址面积相近。在这两处遗址区内曾经发现并采集了一批细石器标本,有石核、刮削器、小石叶等。石料以燧石和水晶石为主,器物经打制并压修加工,具有明显的早期文化特点④。
(19)克尔木齐。在阿尔泰山南麓阿勒泰克尔木齐村,曾经发掘过一片古代墓地。在相当于战国时期的一批古墓葬内,出土多量细石镞,形制规整,通体经过压修。从出土现场观察,这类细石镞,明显是当时的一种锐利武器⑤。
(20)吉木萨尔等处。袁复礼曾在此地发现过细石器遗址,采集到各类细石器标本,但具体资料至今未见发表。
(21)善县迪坎尔遗址。位于迪坎尔村东南约800米处。遗址范围约3平方公里,采集到细石器标本数百件。主要包括锥状、柱状细石核,小石叶,圆头刮削器。遗址区内不见陶片。石叶宽短,器形稍大,显示了比较原始的特征①。
(22)鄯善连木沁乡克孜尔库木遗址。位于连木沁乡丘旺克尔村尤土克西南约3公里处。在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可以看到大量剥打下来的石片,而只见少量成型的石核及石叶、斧形器。大量石片,不见进一步加工或使用痕迹,应是制作石器过程中的废料②。
(23)善县洋海阿斯喀勒买来遗址。位于吐峪沟乡洋海阿斯喀勒买来村西北约3公里的戈壁上,属吐峪沟口前沿洪积扇地带。在这里采集到细石核、刮削器等,从器形观察,比较原始。
(24)塔西肯艾热克遗址。居鄯善县鲁克沁乡三个桥村南约1.5公里处,采集到柱状细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细石镞、圆刮器、双刃刮器、细石叶及敲砸器等③。
(25)七城子细石器遗址。位于木垒县大石头乡南约20公里处,遗址傍近泉水,在东西约400米、南北近600米范围内,采集到细石器标本160多件。包括石核、石叶、石片石器等,石核多楔形,石叶或经进一步加工。刮削器多用石片进一步加工而成。文化面貌比较原始④。
(26)塔克尔巴斯陶遗址。位于木垒县城东北约32公里处的冲积平原荒漠地带,遗址区内见泉水。采集到细石器40多件。有锥状石核、柱形石核、楔形石核、刮削器、石片石器、细石叶等,不见陶片,文化内涵比较单纯⑤。
这26处细石器遗址,当然不可能是全部遗址资料,但就从这一不尽完整的资料出发,也可以看到:其分布地域差不多遍及新疆大地,从昆仑山北麓至帕米尔高原山前地带,天山南麓,罗布淖尔荒原及吐鲁番盆地,哈密绿洲及天山北麓的木垒、吉木萨尔,以至阿勒泰草原。可以看到:细石器,曾是新疆大地上古代居民普遍使用过的一种工具。这类细石器遗址,因为多是地面调查、采集,没有经过科学的发掘,因而对这类细石器遗址所代表的时代,其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它的发展、变化历程,还不能揭示出更多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就从这类采集资料分析,也明显可以作出结论:它们曾经历了一个漫长发展过程,是我们认识新疆地区古代居民早期历史不可缺少的一批重要资料。
二
根据前述细石器资料,对新疆地区细石器类型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址分类、分期、经济生活类型,以及有关遗址的绝对年代等,都曾有考古学者进行过探讨。
有一种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其要旨是:根据新疆地区现有的细石器遗物(指用间接打片并用压制法进行第二步加工取得的各类细石器),从加工技术及石核形制、石器造型方面看,均和我国东北、内蒙古、陕西等地所见的细石器工具,具有相同的特征。属于细石叶细石器这个系统。
从宏观角度分析,细石器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分布,经历的时间也十分漫长,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器时代以至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的历史阶段,都曾使用过细石器工具。而从细石器的形制差别,又可区分为细石叶细石器和几何形细石器两大系统。前者分布在我国、蒙古、南西伯利亚、日本和白令海峡地区。几何形细石器则分布于欧洲、北非、西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多半月形、三角形、梯形石刃。从现有资料分析,细石叶细石器在我国华北地区发生得早、分布也比较集中,华北地区当是这类细石叶细石器的起源地。新疆地区的细石器,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明显曾经接受过华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影响。
从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遗址如寺峪、小南海,已经可以看到细石器的雏形。时代稍晚的一些遗址,如山西下川,细石器已经十分典型。而晚到金属出现,进入阶级社会,细石器在一些地点,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持续了一个十分长远的历史时期。具体到新疆地区,基本情况也是相类的。在上列经过初步工作的26处遗址点(其中罗布淖尔地区,本身又包含了多处遗址点)里,情况也是各有不同。从总的方面看,确应该强调,新疆地区属于我国细石器这一系统;在细石器工艺上接受过华北地区的影响;同时又应看到,它们还具有不少自身的特点、自身的个性。比如,新疆不少地点,阿斯塔那、罗布淖尔地区等处,细石器遗址点里多见一种桂叶形石矛头,通体压成鱼鳞状,形制规整,制作精细。这种石器在中原地区就几乎没有见到,个别地点见到相同器型,而数量也很少。又如,在阿斯塔那遗址中所见的一件锯齿形刃刮器,也是华北地区少见的器形。
在新疆这么一个广阔的空间地带,时间又延续如此长久的细石器工艺,会在相当程度上显示地区的特点,时代的差别,这是不会令人奇怪的。但是,因为缺少比较深入的工作,尤其是没有一处遗址曾经科学发掘,缺少了地层叠压关系;多数地点因风蚀沙移,也已失去原生地层。虽同样都是地面的采集物,但实际上也可能早晚相杂,并不单纯。这些因素,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我们的认识,影响了问题的深入。
根据现有的采集资料,有关细石器或共存文物所显示的制作工艺的成熟程度,新工艺及新器物的出现等,我们可以将已知的新疆细石器遗址区分几种不同的类型,并试为探讨它们的相对早晚或绝对年代。这一方面,早有文章进行过探索①。本文吸取了这些成果。但从总体观察,本文却是一种新的分类,新的观点。因为没有发掘资料,就笔者言,其中一些遗址点,又是间接的知识。因此,这一分类、分期,只能是初步的认识,须要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接受检验,求得完善。
第一类:可以阿尔金山、雅尔崖古城沟西、柴窝堡湖细石器遗址为代表。这一类型的遗址,除少量细石器,包括石核、小石叶、细石器等外,共存大量打制石片石器,形成文化遗物的主体。这类打制石片较厚,宽往往大于长,形制不规整,取其边刃或尖端用作刮削、锥刺。边刃或尖部见第二步加工或使用痕迹,这是明显的石器制作工艺还比较原始的状况,也是时代比较古老的证明,当属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距今时间可能在万年以前。这里,要附带说明几点。一是着重以石器制作工艺比较原始为根据,来论定时代早晚,是否合适?因为道理很明显,在晚期文化遗址中,往往还存在相当原始的古代工艺及制器。如大型打制石器,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或更晚的文化遗址中都还见使用,就是有力的说明。但笔者在这里所以还持这样的论点,是因为在这类遗址中,具有较为原始形态的打制石片石器占有很大比重,近于主体,这就不是一种残余的形态,而应作为时代古老、工艺原始的特征;二是在部分遗址区内,曾发现过陶片或彩陶片。本文在分析时,对这一文化现象均予剔除了。所以这样做,根据在于:这些细石器遗址所在,都有晚期的墓葬或遗址,出现有关陶片并不令人奇怪;根据对新疆地区的考古文化的全面分析,新疆地区目前所见彩陶,一般都在金石并用时期以后,主要是青铜时代的古代居民生活用器,甚至到两汉阶段,彩陶器仍然还在使用,它们的时代明显要较这类细石器工具为晚。此外,在柴窝堡湖畔的细石器遗址内,还曾采获一件残断的桂叶形石矛,形制规整,通体修琢,工艺相当精致,它是后期新疆细石器遗址中具有特征的典型器物之一。它在柴窝堡出土,或可作为遗址在晚期仍在使用的一个说明。
第二类:可以七角井、三道岭遗址作为代表。遗址地区内,细石器工具比重较大,共见各类石核、细石叶,以小石叶为料进一步加工成的小石镞、石钻、雕刻器等近700件。长数厘米,宽数毫米的细石叶随处可见,最长达7厘米,宽只三四毫米,可见压剥细石器工艺之精。这类细石器,多数未经第二步加工,但锋刃锐利。笔者曾用之于切割羊肉,真可谓得心应手。以细石叶为料进一步加工成的细石镞、石钻头、雕刻器等,两面压琢修整,加工精细,制作工艺是十分成熟的。这类细石叶细石器与石核砍砸器、打制石片及以石片为料加工成的刮削器、尖状器共存。这里出土的指甲形刮削器,不论造型还是制作方法,均与山西下川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同类器物一致。还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在七角井采集的700件细石器中,没有发现一件磨制石器标本。而且在约20万平方米的遗址地区内,见到细石器遗物分布点共8处,却绝不见一块陶片。这些特点表明:这里有比较成熟的细石器制作工艺,细石器工具比较发达,数量多,这都明显较第一类型遗址前进了一步①。
第三类:可以木垒河细石器遗址为例。所采集的石器标本中,主要为细石器,包括柱状石核、多量细石片。细石片大都截断,表明是作石刀刃片的材料。还有细石镞,镞体作三角形,通体修压精致。更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底部内凹。据考古所邢开鼎同志介绍,在木垒县北伊尔卡巴克细石器遗址中也发现凹底石镞多件。石镞通体压修,形制规整,近树叶形。体薄,尖、刃均极锋利。尾端均凹人。这种凹底石镞,可以看作是木垒地区细石器中具有特点的一种器形。在木垒河细石器遗址中还有一个特点是细石器与打制的较大型石器共存,器型有斧、锛之属,刀口同样未经加磨。在遗址范围内,还见到了十分粗糙的夹沙红灰陶片及细沙质灰陶。不论从石器加工制作的成熟还是陶器的出现,都说明这是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遗址,其时代,较之七角井明显要晚。
第四类:可以吐鲁番阿斯塔那、罗布淖尔地区为代表。无论是阿斯塔那,还是罗布淖尔西、北部地区,一是有关细石器的采集品都十分丰富;再是细石器与打制石器、琢制石器、陶器共存;还出现了装饰品及玩具,如穿孔砾石坠及弹丸。在细石器中,器形比较定型,制作工艺精巧。尤其是桂叶形矛头,通体压修成鱼鳞状,是这两处遗址地区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器形。石镞制作同样精巧,多带铤,这与木垒遗址又形成显目的差别。细石器大多经过第二步加工。在罗布淖尔地区,细石器分布地点,还见到有少量磨制石器。共出陶器,以阿斯塔那为例,均手制,多平底器、多沙质陶。对阿斯塔那遗址,多认为已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其绝对年代或在距今4000年前后①。近年,新疆考古所在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发掘过一处罗布淖尔地区土著人的古墓地,在一座墓葬内曾出土过一件制作精巧的细石镞,形制规整,锋刃锐利,出土时仍穿插一男性骨架的骶骨缝中,看来是当时仍在使用而且有杀伤力的一种武器。这种石镞的造型、工艺,与罗布荒原上曾经采集的细石镞颇多共同之处。这一墓地,绝对年代在距今3800年前后。这一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这类细石器遗址绝对时代时的参考。
至于四道沟、阿勒泰等处的细石器,已与金属器共存,从总体上看,已只能算是一种古老技术的残留。在讨论新石器时代以前的细石器遗址及其分布、分期时,可以不作考虑了。
三
新疆大地,曾经普遍存在细石器遗址。新疆地区土著居民,操持细石器等类型的生产工具,与大自然斗争并索取,求得自身的生存及发展,曾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从细石器及与其共生的石片石器、砾石石器等进行分析,以柴窝堡、七角井等类型的遗址为代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大型砍砸器,可以是生产木器,砸碎兽骨的有力手段。至于细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等,则可以是割剥兽皮,切割兽肉,采集植物籽实、块根的工具。将细石叶经过切断、加工,嵌入骨、木柄缝中,可以成为一柄很锋利的石刀。这种复合的工具——细石刀,在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遗址、青海乐都县柳湾新石器时代墓地中都曾有实物出土,给了我们以有力的启示。这种细石叶,刃部非常锋利,切割羊肉,较之钝铁刀,还要快利。至于石镞、石矛头,当然是更有力的生产工具,从其可用于狩猎野兽,也可以致人殒命看,其杀伤力是很大的。
综观全部细石器遗址资料,可以看到从早期到晚期,这类采集、狩猎经济,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在后期,如木垒河、阿斯塔那、罗布淖尔等处细石器遗址中,可能已经有了农业生产。这方面,除石器中出现了石磨盘、磨棒等可用于谷物加工的用器外,还有使用陶器提供的佐证,淀粉类的谷物籽实,是不能直接用火烧灼的,它的加工、熟制,必须用陶器类可供蒸煮的器具。陶器的出现使用,往往是和农业、定居相联系在一起的。这类文物可以初步结论到距今4000多年以前。这类细石器遗址的主人,已经有了农业的生产。从孔雀河下游到罗布淖尔湖西、北岸,楼兰古城一带,这一阶段的遗址分布相当集中,可以看到,当年在这片地区内,曾有不少氏族部落在生息、繁荣,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在综观新疆地区这些细石器遗址点时,又一个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问题是:在这些遗址中,除个别遗址点(如木垒河)仍是自然环境良好,水草咸备,农牧业皆宜以外,绝大多数遗址点,目前都已是一片荒漠或半荒漠,一些地点(如罗布淖尔地区),甚至成了一片少见生命的世界。没有水、没有树木,基本没有动物。这样的环境,无论是进行采集、狩猎还是农业,当然是完全不行的。七角井细石器遗址,基本也是这样的情况。遗址范围内,除少数胡杨、红柳、骆驼刺等耐盐耐旱植物外,同样是一片荒漠景观。木垒县伊尔卡巴克遗址,现在已沦为一片沙漠。吐鲁番阿斯塔那细石器遗址所在,则是一片不毛之地。这些例子,不能不使我们产生一个逻辑的推论:在1万年以来,或者说是距今4000年以来,这些遗址点所在的自然地理环境,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导致这些变化的因素,是社会的、人的原因呢?还是自然的原因?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随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研究课题需要有关学科专业工作者之间进行密切的配合和自觉的合作。对新疆一些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变化规律的探索,就是这样的课题之一。要使这个课题得到深入,就很需要地理、生物、气象、沙漠、考古等许多学科研究工作者的协同合作。借这篇小文提出这个问题,但愿引起有关学科同志们及科研组织领导部门的注意,使问题得到积极的推动和深入。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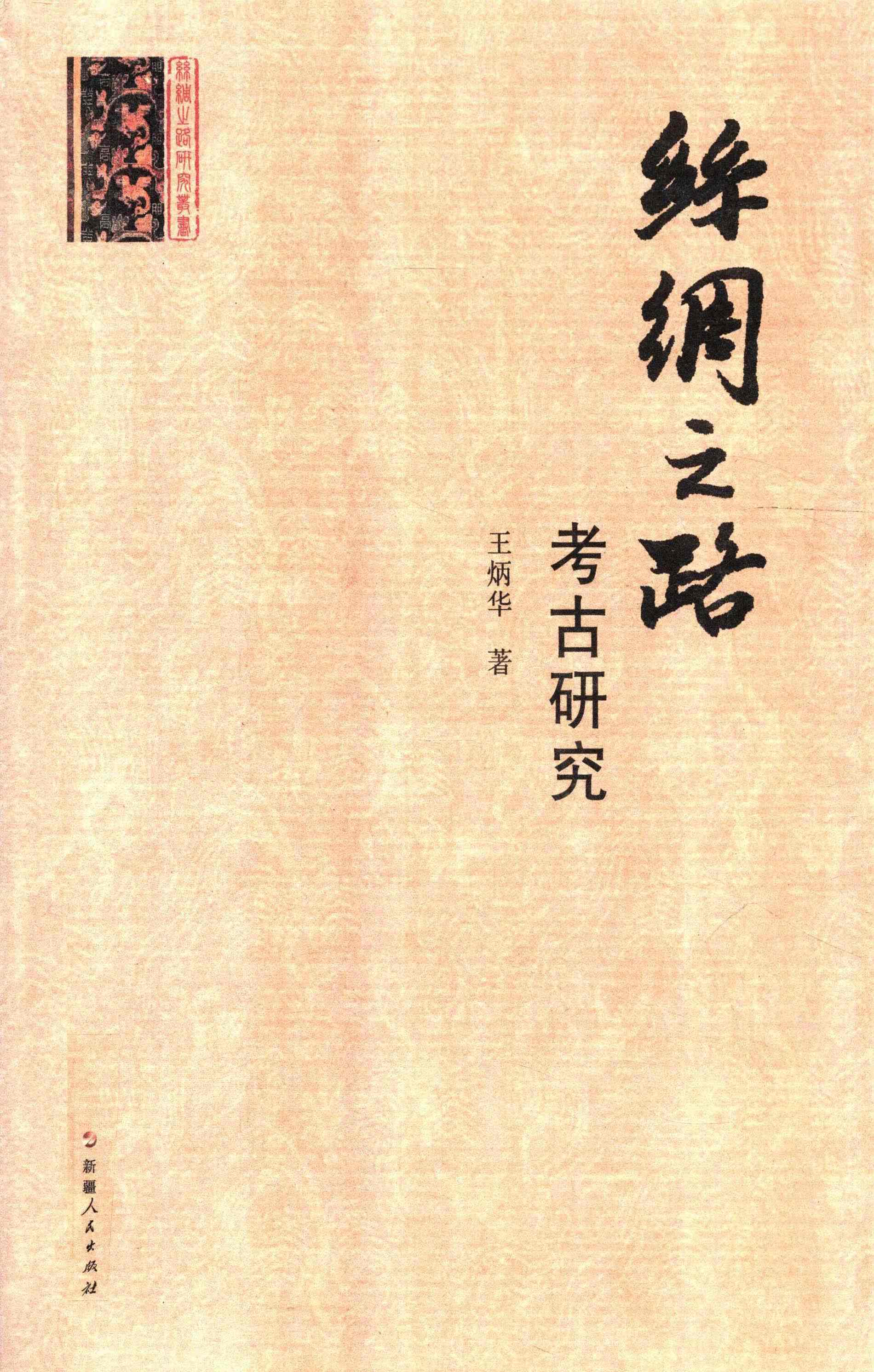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