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国刻石”及有关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68 |
| 颗粒名称: | “刘平国刻石”及有关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 |
| 分类号: | K878 |
| 页数: | 9 |
| 页码: | 079-08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境内的东汉永寿四年(公元一五八年)“刘平国治关亭颂”刻石,是国内外历史考古学界早就注意到的一块重要摩岩石刻。自十九世纪晚期发现以来,国内不少学者曾予著录、研究,如王树柟《新疆访古录》(此书除著录了王树柟自己对刻石文字的分析外,还附录了王仁俊、叶昌炽对刻石文字的记录、分析)、罗振玉《西垂石刻录》王国维《观堂集林》、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书,对刻石均有介绍、分析。 |
| 关键词: | 刘平国 刻石 拜城县 |
内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境内的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刘平国治关亭颂”刻石,是国内外历史考古学界早就注意到的一块重要摩岩石刻。自19世纪晚期发现以来,国内不少学者曾予著录、研究,如王树楠《新疆访古录》(此书除著录了王树楠自己对刻石文字的分析外,还附录了王仁俊、叶昌炽对刻石文字的记录、分析)、罗振玉《西陲石刻录》、王国维《观堂集林》、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书,对刻石均有介绍、分析。
由于刻石所在岩壁凹凸不平,长期暴露山野,风雨浸蚀,清光绪初年发现时,字迹已多漫漶。以后影响渐大,拓录者不乏其人,使过去从不为人注意的山沟刻石成了一处知名所在。随之也出现了不少有意无意的破坏,字迹更加不清。因此,随拓录时间的先后,各家著录文字歧异。1928年,黄文弼先生在拜城考察这一刻石时,已“惜字多剥蚀,不尽可辨”①。但他还是据自己考察,对此前王仁俊、叶昌炽、王树楠、王国维等各家关于该石录文进行了校勘、辨订,并结合附近遗址遗迹对刻石内容作了分析、研究,近乎是进行了一番总结。此后,似未见有不同意见发表。
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有一件“刘平国刻石”拓片,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所拓,时在刻石刚刚发现之后。字迹虽亦漫漶,但大多数文字尚可辨析②。用以校对有关著录,尤其是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的有关结论,在不少重要文字上可作重大补正,并可进而说明新疆古代史上几个具体问题。
一
新疆博物馆藏光绪五年“刘平国刻石”拓本,有乌程施补华题跋,叙述刻石发现的经过。当时清军“过其地”,发现这一摩岩石刻。由于“字漫漶不可识,以告余,疑为汉刻。余请于节帅张公,命总戎王得魁,大令张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得其点划……”①这里的“节帅张公”,是左宗棠部将张曜,《清史稿》中有传。此前刻石似乎并未为世人所知,所以施补华曾“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当时得到拓片的周大烈数年后曾称誉此幅拓片乃当时初拓本,“最为清朗完善。未及数年,其第五行之首,坚固以下残数十字矣!”
拓片上下,除施补华、周大烈外,还有王廉生、戤伯羲等人题跋,名章。后拓片传入陈叔通先生手中,拓片左下角有“隙叔通读碑记”印章。新中国成立后,为利于开展新疆历史、文物研究,陈叔通先生又将此拓片赠予了新疆博物馆。因此,新疆博物馆藏拓本,应是发现时初拓本之一,弥足珍贵。
对这一拓片文字比较清晰的部分,施补华曾经作了记录,直书于拓文之旁,文为: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九日发家
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当卑
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
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 日
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
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
将军所作也“敦煌”
淳于伯
作此诵”
对拓片比较模糊不清处,施补华录文均略过未提。将这一拓片及录文,对照叶昌炽、王二俊、王树楠、王国维及黄文弼的有关结论,可以发现不少歧异。
第一行:“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各家录文一致。下文“廿九日发家”数字,或作“廿六日发家”、“廿六日发众”。据光绪五年拓本,最后“日发家”三字清晰不误。
第二行:“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光绪五年拓本清晰不误,各家录文也基本统一。但“卑”下尚有三字,施补华未录。王国维录文属“万口羌”,王仁俊断为“莫羌”,黄文弼据其手拓本,认为“末行‘羌’字尚可见其仿佛”。细审新疆博物馆藏拓本,末行“羌”字清晰无疑,前二字笔画不清,也是一个人名。
第三行:叶昌炽录文“当”字前有“石”字,“作”字下有“利〓从”三字,王仁俊录文作“口宥车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州亭得”。王国维录文为“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下缺三字)”。黄文弼因拓本“均不清晰”,对有歧异的录文未予置论。今细审光绪五年拓本,王国维录文可以信从。下缺之三字,可见的笔画为“刂亭彳”。第一字只余“刂”,叶、王录文释作“州”或“利”;第二字,笔画基本完整,显明为一“亭”字。联系“亭”字释读前一字,则应该是“列”(说详后);第三字从现存笔画难以定论,王仁俊释为“得”,近似。这样,这一行录文应为“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得”。
第四行:“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各家录文基本一致,“孔”后尚有三字,著录不一。从新疆馆藏本看,此三字为“至艹日”,颇明晰。
第五行:“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除叶、王录文起首多一“以”字外,各家录文均同。
第六行:“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各家录文一致。
第七行:“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各家录文一致。
第八行:“将军所作也”。“也”字下,应还有两字,笔画不清,各家歧见。叶作“亻?披”,王仁俊作“从掖,”王国维作“佐披”,黄文弼作“口披,疑为刻字工人”。“敦煌淳于伯作此诵”。其他各家录文均作:“京兆长安淳于伯隗作此诵”。从光绪五年拓本文字看,似以“京兆长
安”为当。
对照各家录文,细审新疆博物馆所藏光绪五年拓本,文字笔画虽也有缺失,但不失为比较完善的一件早期拓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综观前后各家录文,在下列几个具体问题上也可以统一: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永寿四年在拜城县修筑的关城是“亭”,刻石作诵正是为了表彰、纪念这一工程竣工;跟随刘平国的工人被冠以“秦人”之称;从事施工的六名工匠中有两人名“万口羌”(从王国维说)、“程阿羌”,等。这几条材料,涉及到新疆古代史上几个具体问题,容后申述。
二
“亭”,在汉代有多种意义①。
一种是作为地方行政组织。《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这种乡亭,职能在于维护地方的封建统治秩序,主捕“盗贼”。汉高祖刘邦,曾“为泗上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所谓“求盗”,据应劭注,是为“亭卒。旧时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②。可见亭的组织是比较简单的,但在维护治安上却有大意义。所以,赵充国在加强对羌族控制的有名的“屯田奏”中,把“缮乡亭”③作为一条重要措施。
“亭”之所在,往往有馆舍,可供食宿,起馆驿作用。刘邦作泗上亭长时,送县内徒隶往骊山服劳役,行“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师古注称,“亭谓停留行旅宿食之馆”④,从上例可见,亭舍,可供多人食宿。
“亭”,据人口稠密情况,在一定距离内都有设置。因此,邮驿传递,也往往和“亭”结合在一起,故历史上有“邮亭”之称。前引《汉书·赵充国传》称:“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败坏者。”《后汉书·西羌传》:“滇零遣入寇褒中,燔烧邮亭,大掠百姓。”《后汉书·卫飒传》称:“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亭传与邮驿结合一道,随道路开通而设置。
在汉代,“亭”,往往以“列亭”、“亭侯”、“亭鄣”联称,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设置。汉武帝刘彻击败匈奴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敦煌四郡,为进一步加强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及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于是自敦煌西至临泽(罗布淖尔),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⑤。在桑弘羊给刘彻的有名的屯田戍边建议中,也力陈在轮台、渠犁等处屯田积谷,稍有“畜积”后,“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⑥。对桑弘羊的建议,刘彻没有同意,认为“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⑦。从上下文看,“列亭”与“亭隧”作用等同,军事上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
关于新疆地区这类“亭”的军事职能,《汉书·西域传》曾记述了王莽时期的一件事:戊己校尉刁获属下的陈良、终带等谋叛匈奴,欲杀刁获以邀功,“即将数千骑至校尉府,胁诸亭令燔积薪,分告诸壁曰,匈奴十万骑来入……去校尉府数里止,晨火燃,校尉开门击鼓,收吏士,良等随入,遂杀校尉刁获”。亭起烽燧的作用,可以明见。
“亭燧”连称,《汉书》屡见。侯应在论述汉代边防建设时,说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而汉元帝时“罢外城,省亭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①,亭燧建设是否完备,关系边塞的是否强固。《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匈奴左部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诸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这些记录,说明边塞地区的“亭”,起着候望、烽燧的作用,但它们作为馆舍、邮驿的作用,在居民更少的边境地区,肯定也在发挥着;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处于交通冲要地带的亭燧,它们的馆舍、邮驿作用,是无法被取代的。
无论作为“亭燧”、“亭彰”、“亭邮”,发挥烽燧、驿馆、邮传的作用,“亭”,均须成“列”。所以,前引文字资料中,“列亭”一词屡见。新疆博物馆藏光绪五年拓片第三行文字,“作”下“亭”前的“刂”笔画,应为“列”字无疑。
东汉永寿四年(即延熹元年),刘平国在拜城地区建“列亭”,可以见出正是汉朝政府军政制度在这里的直接实施。
拜城县博孜克日格沟,是库车地区北通伊犁的一条径道。据称,循沟北行,经六站,可抵伊犁地区②。伊犁地区,两汉时期是乌孙活动的中心地带。乌孙与汉朝政府往来,大都通过龟兹地区③。在交通隘口,修建关“亭”,对警备候望、交通安全、邮传往来,都是必要的。
黄文弼先生1928年到拜城县博孜克日格沟口调查刘平国刻石时,“在西壁刻字附近,发现石孔,圆径周约1.6米,深约1.3米;又沟东半山岩,亦凿有石孔,岩下碎石甚多,必为凿岩遗屑”。黄文弼分析是:“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凿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有关遗迹,正好是刘平国刻石文字“斫山石作孔”的注脚④。
三
塔里木盆地内的先秦居民,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认为主要是雅利安人。
“刘平国刻石”提供的明确材料是:东汉时,在库车地区,也有汉人、羌人在那里劳动、生息。
刻石文字第二行,“从秦人”之“秦”字清晰可见,明确无误。
“秦人”,曾是战国、秦王朝时期西域广大地区对中原秦王朝统治下人民的称呼。两汉阶段,仍用以称呼两汉王朝统治下的人民,这是传统习惯的表现。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述李广利攻大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同一件事,在《汉书·李广利传》中,“秦人”一词即写作“汉人”。《史记》、《汉书》之“匈奴传”中,也有这种“秦人”、“汉人”互异的情况。汉武帝刘彻在一件罪已诏中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①这些资料都可以说明,所谓“秦人”,明显即指“汉人”,这在汉代当时,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国内的史学界,对此也一直没有疑义。
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述了上列《史记·大宛列传》那条资料,并申述文内的“秦人”,指的应该是“大秦”人②,即古罗马人,看来并不准确。
汉代西域地区流行的“秦人”一词,指的就是汉朝人,绝非“大秦”,除前述理由外,“刘平国刻石”可以说是同样有力的又一个证据。刻石这一句的全文是“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从孟伯山等人的姓名特征可以肯定无疑地说,是没有任何“大秦”特征的。
刻石中,提到的“秦人”还有“万口羌”、“程阿羌”两人。两汉时期,河西、新疆地区,取名“××羌”、“羌女”等,均为羌族③。这里的“万口羌”、“程阿羌”二人,亦应是古代羌族无疑。
羌族,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一支,他们主要活动、居住在祖国西部地区。
新疆地区,昆仑山南麓,有“婼羌”居住、劳动、生息,在《汉书》中早见记录④。
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汉政府还曾经征调“婼、月氏兵四千人”,参加平定甘、青地区的动乱①。然库车地区却未见有羌族居住的记录。但东汉时期,确见到征发甘、青地区羌族到新疆地区服役的记录,库车地区羌族,或应与此有关。
西汉初,中央王朝即设有获羌校尉,管理甘、青地区羌族事务,代表中央王朝统治羌族人民。东汉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刘秀曾封羌族酋长楼登为“归义君长”,永平元年(58年),汉明帝刘庄曾封羌族首领滇岸为“汉大都尉归义侯”②。羌族人民以畜牧业为主,西汉以来,逐渐与汉族交错杂居,从事农业生产的也逐渐增多。但是羌族劳动人民“其内属者,或控〓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受到汉族地主及本族酋豪的残酷剥削及奴役,也不断被征发为士兵。历史上有名的公元2世纪初历时十多年的羌族劳动人民反对东汉统治的起义斗争,即源于兵役的征发,史载“时诸降羌布住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107)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③。据此可见,在两汉时期对西域的军事活动、屯田生产中,甘、青地区的羌族劳动人民是汉朝政府征发的对象之一,为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奴役,他们也有逃避“出塞”、徙居新疆地区的。这部分羌族劳动人民长期与汉族人民混居共处,接受汉文化影响甚深。他们进入新疆地区以后,对新疆的开发建设起过很好的作用。
联系这一历史背景,东汉时期的龟兹地区,刘平国率领的“秦人”中包含“羌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他们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被汉朝政府征发来到新疆,因而被龟兹同样视为“秦人”,自是情理中事。
曾有羌族劳动人民被汉朝政府征发到龟兹地区执行军事、劳役任务,还得到另一件历史文物的证明。在库车地区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内曾出土一枚“汉归义羌长印”④,铜质方形,卧羊钮,边长2.3厘米,通高35厘米。这方铜印,确切说明汉代曾有一支羌族在本族领袖——汉朝政府敕封的“归义羌长”的率领下,应役到达了库车地区,在开发、建设祖国西部边疆的事业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刘平国刻石”和“汉归义羌长印”,帮助我们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新疆古代史上这一问题的认识。
四
两汉时期,西域广大地区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广、不容轻估的。
“刘平国刻石”文字,是很工整的隶书。龟兹地区,表现出这样的汉文化水平,并不偶然。自西汉前期西域统一于中原王朝以后,龟兹与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关系一直相当密切。公元前1世纪汉宣帝刘询在位时,龟兹国王名绛宾,他的夫人是汉朝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绛宾与弟史曾在长安留居一年,以后并数至中原。深受汉王朝政治制度、中原封建文化的熏陶、影响。绛宾在从长安回龟兹后,曾在国内推行改革,史称其“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①,就反映了这一过程。吕光到龟兹时,“见其宫室壮丽”,“焕若神居”,曾命人作“龟兹宫赋”②,以记其盛。颇可透见汉王朝宫廷建筑艺术在这里的影响。
作为龟兹左将军的刘平国,从其姓名,也可看到汉文化在龟兹贵族上层集团中的巨大影响。关于刘平国,究竟是龟兹人还是汉人,有两种相反意见③。从一般情况看,当时汉人在西域作中央命官者多,担任地方小王国官吏则未见;而刻石文字又明言刘平国率“秦人”孟伯山等六人作亭,则刘平国当非“秦人”。他既非“秦人”,却取名“平国,”寓有深意,不是一般的用汉文标音,可以看出当时龟兹人汉语文造诣颇深。
稍加留意,可以发现,两汉时期,汉文化在西域地区影响相当深入。统治阶级上层取汉名、以汉文作文字工具者颇不乏人。与库车绿洲相对,处塔里木盆地南沿的民丰县尼雅遗址,即汉代精绝国废墟,统治阶级上层人物间互相赠礼、酬答的简扎,人物名号有“君华”、“承德”、“且末夫人”等④,也都是一手很精彩的汉隶,与“刘平国刻石”可以互相辉映。
我们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即汉宣帝刘询神爵二年(前60),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任命将吏,统管西域军政,代表汉王朝在西域广大地区行使国家权力,推行汉朝政令、组织生产、征收贡赋,西域广大地区归属西汉王朝以来,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疆地区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趋紧密。历两汉之世,虽然随中央王朝军政势力的强弱变化,对西域的统治、控制有所谓“三绝三通”,即强弱紧松之别;但新疆地区基本都在中央王朝的统属之下。这时,各地方小王国政权都奉中央王朝的正朔,接受中央王朝的敕封,使用统一的纪年,受中央王朝的军政调遣。东汉后期的刘平国刻石,可为这一情况佐证。在龟兹境内拜城县山区修建的列亭之一,实际体现着汉朝政令的贯彻实施;刻石文字中使用的也是东汉王朝的纪年。虽然,东汉桓帝刘志使用永寿纪年只到四年六月,即因“赦天下,改元”为延熹。所以,永寿四年八月,实际已在改元两个月以后。但因距离遥远,联系不便,这一大事还未通达龟兹地区,所以仍然沿用着“永寿四年”,其自视为中央王朝之属部,是灼然可见的。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在开发、建设祖国的西部边疆,缔造统一祖国历史的过程中,都曾有过自己的贡献。刻石具体说明,2000年前,在新疆地区劳动、生活的除本地少数民族人民外,还有汉族劳动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如古代羌族的劳动人民。这些普通的、名不见经传、也从不为世人所知的手工业工人、劳动农民,曾以自己的智慧、技能、辛勤劳动的汗水,和龟兹地区劳动人民一道,开发、建设了库车地区。在这次博孜克日格沟口斫岩作孔、建设列亭的任务中,他们又作出了优异成绩,受到表彰。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兢兢业业为维护祖国的统一而斗争。刻石为我们留下了孟伯山、程阿羌等6名汉、羌族劳动人民的姓名,他们是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共进的代表,是历史的主人。
“刘平国刻石”,是这一历史的很好的见证。
由于刻石所在岩壁凹凸不平,长期暴露山野,风雨浸蚀,清光绪初年发现时,字迹已多漫漶。以后影响渐大,拓录者不乏其人,使过去从不为人注意的山沟刻石成了一处知名所在。随之也出现了不少有意无意的破坏,字迹更加不清。因此,随拓录时间的先后,各家著录文字歧异。1928年,黄文弼先生在拜城考察这一刻石时,已“惜字多剥蚀,不尽可辨”①。但他还是据自己考察,对此前王仁俊、叶昌炽、王树楠、王国维等各家关于该石录文进行了校勘、辨订,并结合附近遗址遗迹对刻石内容作了分析、研究,近乎是进行了一番总结。此后,似未见有不同意见发表。
新疆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中,有一件“刘平国刻石”拓片,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所拓,时在刻石刚刚发现之后。字迹虽亦漫漶,但大多数文字尚可辨析②。用以校对有关著录,尤其是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的有关结论,在不少重要文字上可作重大补正,并可进而说明新疆古代史上几个具体问题。
一
新疆博物馆藏光绪五年“刘平国刻石”拓本,有乌程施补华题跋,叙述刻石发现的经过。当时清军“过其地”,发现这一摩岩石刻。由于“字漫漶不可识,以告余,疑为汉刻。余请于节帅张公,命总戎王得魁,大令张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得其点划……”①这里的“节帅张公”,是左宗棠部将张曜,《清史稿》中有传。此前刻石似乎并未为世人所知,所以施补华曾“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当时得到拓片的周大烈数年后曾称誉此幅拓片乃当时初拓本,“最为清朗完善。未及数年,其第五行之首,坚固以下残数十字矣!”
拓片上下,除施补华、周大烈外,还有王廉生、戤伯羲等人题跋,名章。后拓片传入陈叔通先生手中,拓片左下角有“隙叔通读碑记”印章。新中国成立后,为利于开展新疆历史、文物研究,陈叔通先生又将此拓片赠予了新疆博物馆。因此,新疆博物馆藏拓本,应是发现时初拓本之一,弥足珍贵。
对这一拓片文字比较清晰的部分,施补华曾经作了记录,直书于拓文之旁,文为: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九日发家
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当卑
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
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 日
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
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
将军所作也“敦煌”
淳于伯
作此诵”
对拓片比较模糊不清处,施补华录文均略过未提。将这一拓片及录文,对照叶昌炽、王二俊、王树楠、王国维及黄文弼的有关结论,可以发现不少歧异。
第一行:“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各家录文一致。下文“廿九日发家”数字,或作“廿六日发家”、“廿六日发众”。据光绪五年拓本,最后“日发家”三字清晰不误。
第二行:“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光绪五年拓本清晰不误,各家录文也基本统一。但“卑”下尚有三字,施补华未录。王国维录文属“万口羌”,王仁俊断为“莫羌”,黄文弼据其手拓本,认为“末行‘羌’字尚可见其仿佛”。细审新疆博物馆藏拓本,末行“羌”字清晰无疑,前二字笔画不清,也是一个人名。
第三行:叶昌炽录文“当”字前有“石”字,“作”字下有“利〓从”三字,王仁俊录文作“口宥车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州亭得”。王国维录文为“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下缺三字)”。黄文弼因拓本“均不清晰”,对有歧异的录文未予置论。今细审光绪五年拓本,王国维录文可以信从。下缺之三字,可见的笔画为“刂亭彳”。第一字只余“刂”,叶、王录文释作“州”或“利”;第二字,笔画基本完整,显明为一“亭”字。联系“亭”字释读前一字,则应该是“列”(说详后);第三字从现存笔画难以定论,王仁俊释为“得”,近似。这样,这一行录文应为“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得”。
第四行:“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各家录文基本一致,“孔”后尚有三字,著录不一。从新疆馆藏本看,此三字为“至艹日”,颇明晰。
第五行:“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除叶、王录文起首多一“以”字外,各家录文均同。
第六行:“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各家录文一致。
第七行:“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各家录文一致。
第八行:“将军所作也”。“也”字下,应还有两字,笔画不清,各家歧见。叶作“亻?披”,王仁俊作“从掖,”王国维作“佐披”,黄文弼作“口披,疑为刻字工人”。“敦煌淳于伯作此诵”。其他各家录文均作:“京兆长安淳于伯隗作此诵”。从光绪五年拓本文字看,似以“京兆长
安”为当。
对照各家录文,细审新疆博物馆所藏光绪五年拓本,文字笔画虽也有缺失,但不失为比较完善的一件早期拓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综观前后各家录文,在下列几个具体问题上也可以统一: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永寿四年在拜城县修筑的关城是“亭”,刻石作诵正是为了表彰、纪念这一工程竣工;跟随刘平国的工人被冠以“秦人”之称;从事施工的六名工匠中有两人名“万口羌”(从王国维说)、“程阿羌”,等。这几条材料,涉及到新疆古代史上几个具体问题,容后申述。
二
“亭”,在汉代有多种意义①。
一种是作为地方行政组织。《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这种乡亭,职能在于维护地方的封建统治秩序,主捕“盗贼”。汉高祖刘邦,曾“为泗上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所谓“求盗”,据应劭注,是为“亭卒。旧时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②。可见亭的组织是比较简单的,但在维护治安上却有大意义。所以,赵充国在加强对羌族控制的有名的“屯田奏”中,把“缮乡亭”③作为一条重要措施。
“亭”之所在,往往有馆舍,可供食宿,起馆驿作用。刘邦作泗上亭长时,送县内徒隶往骊山服劳役,行“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师古注称,“亭谓停留行旅宿食之馆”④,从上例可见,亭舍,可供多人食宿。
“亭”,据人口稠密情况,在一定距离内都有设置。因此,邮驿传递,也往往和“亭”结合在一起,故历史上有“邮亭”之称。前引《汉书·赵充国传》称:“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败坏者。”《后汉书·西羌传》:“滇零遣入寇褒中,燔烧邮亭,大掠百姓。”《后汉书·卫飒传》称:“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亭传与邮驿结合一道,随道路开通而设置。
在汉代,“亭”,往往以“列亭”、“亭侯”、“亭鄣”联称,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设置。汉武帝刘彻击败匈奴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敦煌四郡,为进一步加强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及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于是自敦煌西至临泽(罗布淖尔),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⑤。在桑弘羊给刘彻的有名的屯田戍边建议中,也力陈在轮台、渠犁等处屯田积谷,稍有“畜积”后,“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⑥。对桑弘羊的建议,刘彻没有同意,认为“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⑦。从上下文看,“列亭”与“亭隧”作用等同,军事上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
关于新疆地区这类“亭”的军事职能,《汉书·西域传》曾记述了王莽时期的一件事:戊己校尉刁获属下的陈良、终带等谋叛匈奴,欲杀刁获以邀功,“即将数千骑至校尉府,胁诸亭令燔积薪,分告诸壁曰,匈奴十万骑来入……去校尉府数里止,晨火燃,校尉开门击鼓,收吏士,良等随入,遂杀校尉刁获”。亭起烽燧的作用,可以明见。
“亭燧”连称,《汉书》屡见。侯应在论述汉代边防建设时,说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而汉元帝时“罢外城,省亭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①,亭燧建设是否完备,关系边塞的是否强固。《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说:“匈奴左部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诸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这些记录,说明边塞地区的“亭”,起着候望、烽燧的作用,但它们作为馆舍、邮驿的作用,在居民更少的边境地区,肯定也在发挥着;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处于交通冲要地带的亭燧,它们的馆舍、邮驿作用,是无法被取代的。
无论作为“亭燧”、“亭彰”、“亭邮”,发挥烽燧、驿馆、邮传的作用,“亭”,均须成“列”。所以,前引文字资料中,“列亭”一词屡见。新疆博物馆藏光绪五年拓片第三行文字,“作”下“亭”前的“刂”笔画,应为“列”字无疑。
东汉永寿四年(即延熹元年),刘平国在拜城地区建“列亭”,可以见出正是汉朝政府军政制度在这里的直接实施。
拜城县博孜克日格沟,是库车地区北通伊犁的一条径道。据称,循沟北行,经六站,可抵伊犁地区②。伊犁地区,两汉时期是乌孙活动的中心地带。乌孙与汉朝政府往来,大都通过龟兹地区③。在交通隘口,修建关“亭”,对警备候望、交通安全、邮传往来,都是必要的。
黄文弼先生1928年到拜城县博孜克日格沟口调查刘平国刻石时,“在西壁刻字附近,发现石孔,圆径周约1.6米,深约1.3米;又沟东半山岩,亦凿有石孔,岩下碎石甚多,必为凿岩遗屑”。黄文弼分析是:“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凿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有关遗迹,正好是刘平国刻石文字“斫山石作孔”的注脚④。
三
塔里木盆地内的先秦居民,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认为主要是雅利安人。
“刘平国刻石”提供的明确材料是:东汉时,在库车地区,也有汉人、羌人在那里劳动、生息。
刻石文字第二行,“从秦人”之“秦”字清晰可见,明确无误。
“秦人”,曾是战国、秦王朝时期西域广大地区对中原秦王朝统治下人民的称呼。两汉阶段,仍用以称呼两汉王朝统治下的人民,这是传统习惯的表现。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述李广利攻大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同一件事,在《汉书·李广利传》中,“秦人”一词即写作“汉人”。《史记》、《汉书》之“匈奴传”中,也有这种“秦人”、“汉人”互异的情况。汉武帝刘彻在一件罪已诏中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①这些资料都可以说明,所谓“秦人”,明显即指“汉人”,这在汉代当时,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国内的史学界,对此也一直没有疑义。
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述了上列《史记·大宛列传》那条资料,并申述文内的“秦人”,指的应该是“大秦”人②,即古罗马人,看来并不准确。
汉代西域地区流行的“秦人”一词,指的就是汉朝人,绝非“大秦”,除前述理由外,“刘平国刻石”可以说是同样有力的又一个证据。刻石这一句的全文是“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从孟伯山等人的姓名特征可以肯定无疑地说,是没有任何“大秦”特征的。
刻石中,提到的“秦人”还有“万口羌”、“程阿羌”两人。两汉时期,河西、新疆地区,取名“××羌”、“羌女”等,均为羌族③。这里的“万口羌”、“程阿羌”二人,亦应是古代羌族无疑。
羌族,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一支,他们主要活动、居住在祖国西部地区。
新疆地区,昆仑山南麓,有“婼羌”居住、劳动、生息,在《汉书》中早见记录④。
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汉政府还曾经征调“婼、月氏兵四千人”,参加平定甘、青地区的动乱①。然库车地区却未见有羌族居住的记录。但东汉时期,确见到征发甘、青地区羌族到新疆地区服役的记录,库车地区羌族,或应与此有关。
西汉初,中央王朝即设有获羌校尉,管理甘、青地区羌族事务,代表中央王朝统治羌族人民。东汉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刘秀曾封羌族酋长楼登为“归义君长”,永平元年(58年),汉明帝刘庄曾封羌族首领滇岸为“汉大都尉归义侯”②。羌族人民以畜牧业为主,西汉以来,逐渐与汉族交错杂居,从事农业生产的也逐渐增多。但是羌族劳动人民“其内属者,或控〓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受到汉族地主及本族酋豪的残酷剥削及奴役,也不断被征发为士兵。历史上有名的公元2世纪初历时十多年的羌族劳动人民反对东汉统治的起义斗争,即源于兵役的征发,史载“时诸降羌布住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107)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③。据此可见,在两汉时期对西域的军事活动、屯田生产中,甘、青地区的羌族劳动人民是汉朝政府征发的对象之一,为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奴役,他们也有逃避“出塞”、徙居新疆地区的。这部分羌族劳动人民长期与汉族人民混居共处,接受汉文化影响甚深。他们进入新疆地区以后,对新疆的开发建设起过很好的作用。
联系这一历史背景,东汉时期的龟兹地区,刘平国率领的“秦人”中包含“羌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他们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被汉朝政府征发来到新疆,因而被龟兹同样视为“秦人”,自是情理中事。
曾有羌族劳动人民被汉朝政府征发到龟兹地区执行军事、劳役任务,还得到另一件历史文物的证明。在库车地区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内曾出土一枚“汉归义羌长印”④,铜质方形,卧羊钮,边长2.3厘米,通高35厘米。这方铜印,确切说明汉代曾有一支羌族在本族领袖——汉朝政府敕封的“归义羌长”的率领下,应役到达了库车地区,在开发、建设祖国西部边疆的事业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刘平国刻石”和“汉归义羌长印”,帮助我们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新疆古代史上这一问题的认识。
四
两汉时期,西域广大地区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广、不容轻估的。
“刘平国刻石”文字,是很工整的隶书。龟兹地区,表现出这样的汉文化水平,并不偶然。自西汉前期西域统一于中原王朝以后,龟兹与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关系一直相当密切。公元前1世纪汉宣帝刘询在位时,龟兹国王名绛宾,他的夫人是汉朝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绛宾与弟史曾在长安留居一年,以后并数至中原。深受汉王朝政治制度、中原封建文化的熏陶、影响。绛宾在从长安回龟兹后,曾在国内推行改革,史称其“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①,就反映了这一过程。吕光到龟兹时,“见其宫室壮丽”,“焕若神居”,曾命人作“龟兹宫赋”②,以记其盛。颇可透见汉王朝宫廷建筑艺术在这里的影响。
作为龟兹左将军的刘平国,从其姓名,也可看到汉文化在龟兹贵族上层集团中的巨大影响。关于刘平国,究竟是龟兹人还是汉人,有两种相反意见③。从一般情况看,当时汉人在西域作中央命官者多,担任地方小王国官吏则未见;而刻石文字又明言刘平国率“秦人”孟伯山等六人作亭,则刘平国当非“秦人”。他既非“秦人”,却取名“平国,”寓有深意,不是一般的用汉文标音,可以看出当时龟兹人汉语文造诣颇深。
稍加留意,可以发现,两汉时期,汉文化在西域地区影响相当深入。统治阶级上层取汉名、以汉文作文字工具者颇不乏人。与库车绿洲相对,处塔里木盆地南沿的民丰县尼雅遗址,即汉代精绝国废墟,统治阶级上层人物间互相赠礼、酬答的简扎,人物名号有“君华”、“承德”、“且末夫人”等④,也都是一手很精彩的汉隶,与“刘平国刻石”可以互相辉映。
我们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即汉宣帝刘询神爵二年(前60),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任命将吏,统管西域军政,代表汉王朝在西域广大地区行使国家权力,推行汉朝政令、组织生产、征收贡赋,西域广大地区归属西汉王朝以来,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疆地区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趋紧密。历两汉之世,虽然随中央王朝军政势力的强弱变化,对西域的统治、控制有所谓“三绝三通”,即强弱紧松之别;但新疆地区基本都在中央王朝的统属之下。这时,各地方小王国政权都奉中央王朝的正朔,接受中央王朝的敕封,使用统一的纪年,受中央王朝的军政调遣。东汉后期的刘平国刻石,可为这一情况佐证。在龟兹境内拜城县山区修建的列亭之一,实际体现着汉朝政令的贯彻实施;刻石文字中使用的也是东汉王朝的纪年。虽然,东汉桓帝刘志使用永寿纪年只到四年六月,即因“赦天下,改元”为延熹。所以,永寿四年八月,实际已在改元两个月以后。但因距离遥远,联系不便,这一大事还未通达龟兹地区,所以仍然沿用着“永寿四年”,其自视为中央王朝之属部,是灼然可见的。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在开发、建设祖国的西部边疆,缔造统一祖国历史的过程中,都曾有过自己的贡献。刻石具体说明,2000年前,在新疆地区劳动、生活的除本地少数民族人民外,还有汉族劳动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如古代羌族的劳动人民。这些普通的、名不见经传、也从不为世人所知的手工业工人、劳动农民,曾以自己的智慧、技能、辛勤劳动的汗水,和龟兹地区劳动人民一道,开发、建设了库车地区。在这次博孜克日格沟口斫岩作孔、建设列亭的任务中,他们又作出了优异成绩,受到表彰。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兢兢业业为维护祖国的统一而斗争。刻石为我们留下了孟伯山、程阿羌等6名汉、羌族劳动人民的姓名,他们是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共进的代表,是历史的主人。
“刘平国刻石”,是这一历史的很好的见证。
附注
①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②这一拓本,曾发表于《新疆出土文物》,图四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①关于“刘平国刻石”的发现经过,王树楠《新疆访古录》称是光绪三年刘锦棠部将徐万福发现。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从其说。与这里的施补华题跋不同,似应以施补华题跋为准。
① 贺昌群:《烽燧考》,见《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②④《汉书》卷一《高帝纪第一上》。
③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⑤ 《汉书·西域传》上。
⑥⑦《汉书·西域传》下。
①《汉书·匈奴传》下。
②④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③见《汉书·西域传》《乌孙》。
① 《汉书·西域传》下。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七章。
③ 顾颉刚:《新疆南路之羌》,见《史林杂识初编》。
④《汉书·西域传》:“婼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小宛??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戎卢……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渠勒??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扜弥接”,“于阗……南与婼羌接”,“难兜??南与婼羌接”。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按《通典》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曰葱茈羌,曰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理广狭,盖同为羌种,故传以婼羌目之,刘氏以为误,非也。”
①《汉书·赵充国传》。
②③《后汉书·西羌传》。④《新疆出土文物》图一〇,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①《汉书·西域传》。
②《晋书·西戎传》。
③王树楠认为刘平国“乃汉人为西域官者”,王国维持相反观点,认为既称刘“率秦人劳作,则刘非秦人无疑”。
④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载《文物》,1960(6)。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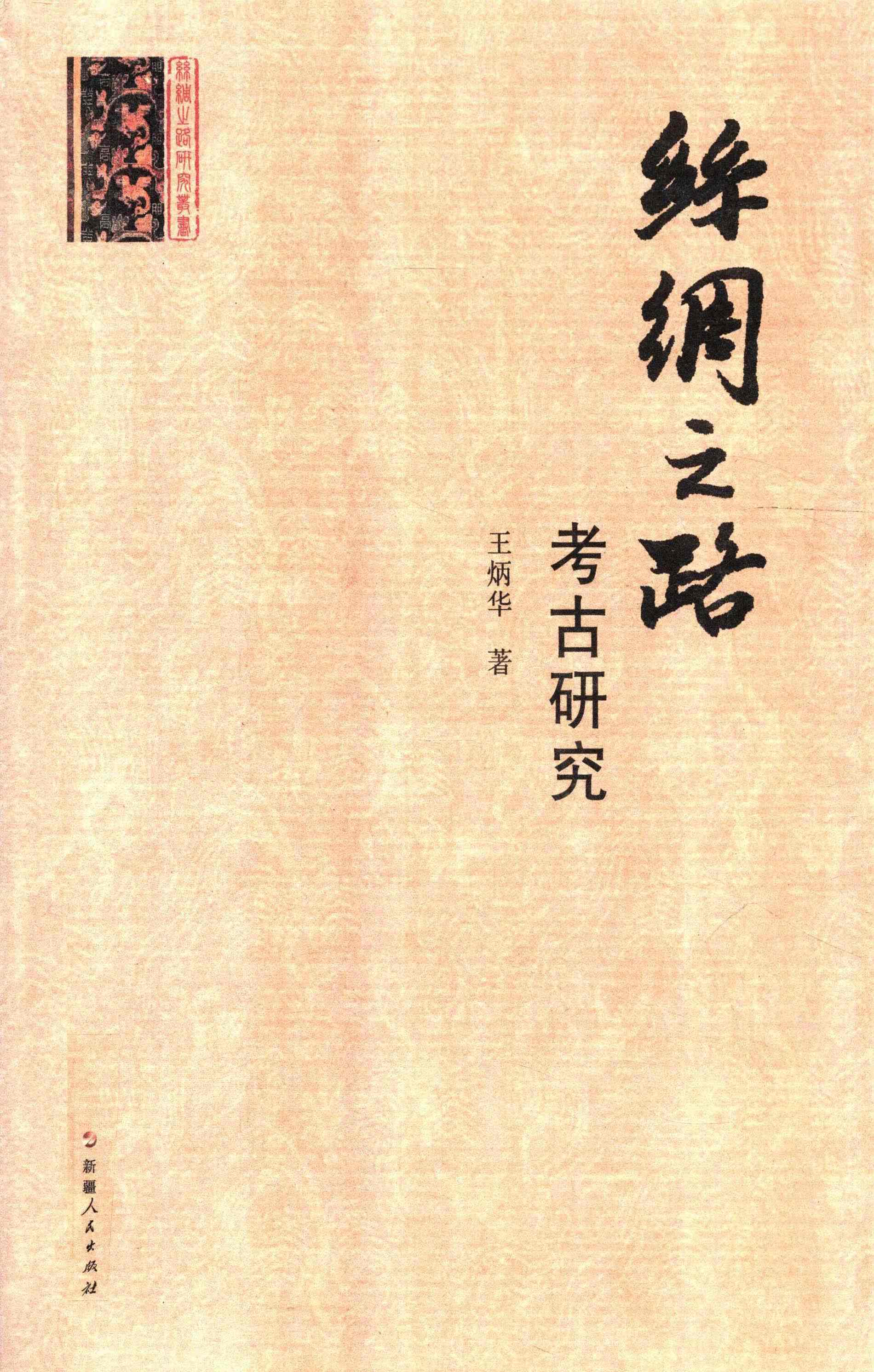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拜城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