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丝路考古发现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61 |
| 颗粒名称: | 四、丝路考古发现 |
| 分类号: | K875.9 |
| 页数: | 7 |
| 页码: | 039-04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丝路考古发现的丝绸、造纸、毛纺织工艺、玻璃珍贵遗物的研究与介绍。 |
| 关键词: | 丝绸 考古 遗物 |
内容
新疆,作为“丝路”干线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路段,留下了许多足以表现当年“丝路”历史的珍贵遗物。近年的新疆考古工作中,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收获。不言而喻,这些有幸出土的“丝路”遗珍,与当年实际存在的社会生活相比,只不过是片鳞只爪,不足以代表全体,但却揭示、反映着一种历史的存在,它所显示的文化交流的精神,更值得今天的人们深刻认识、继承、发扬。现择其主要者,略予介绍。
(一)丝绸
在出土的足以表现“丝路”内容的珍贵文物中,首推丝绸。出土数量大、品种多、地域广,时代延续长,十分有力地表明:在丝绸之路上,轻薄美观的各种“丝绸”织物,深受西亚、欧洲人民的欢迎,是通过“丝路”西向的主要商品。
近几十年来,新疆考古工作中见到丝绸织物的遗址点相当丰富。举其大者,如若羌东部的阿拉尔,楼兰城东北郊的孤台、平台墓地,孔雀河谷老开屏墓地,库鲁克山南麓的营盘古墓,吐鲁番盆地中鄯善县鲁克沁,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天山中阿拉沟、鱼儿沟古墓地,乌鲁木齐南郊盐湖,库车苏巴什,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民丰县尼雅古墓,于田县喀拉墩,洛浦县山普拉古墓,木垒四道沟古墓葬等处,均有所见。尤其是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的阿斯塔那晋唐墓地,差不多可以说,无墓不见丝绸文物,颇为有力地说明当年丝绸织物在高昌地区相当普及的情况。谈及丝织物出土地点,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地点,几乎全部在天山以南地区。所以存在这一现象,应与天山以北地区降水较多,湿度较大,织物类在地下很不容易保存有关。
有关织物的时代,分析表明:早可以到春秋、战国,盛于两汉,大盛于隋唐,迄止于宋元,均有所见。
织物品种,主要为素绢及染色绢,以及各种花纹图案的织锦、暗花绮、绫、缣、纱、罗、轻容、刺绣及染织等。这些文物,出土时多零散、破损,绝对数量虽不算多,但实际却代表着巨大的数字。A.斯坦因在楼兰故城遗址点发掘得一枚简牍,简文称“人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绢四千三百廿六匹”。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提到长安汉商在弓月城胡商处,一次就调剂到绢237匹。将上列出土文物品种与这些出土文字资料结合分析,可以充分肯定,通过“丝路”进行的丝绸缎物贸易,数量曾是相当巨大的。
分析“丝路”织物图案,可以得到的强烈印象是汉代织锦,花纹布局,均成行排列,循环往复。花纹图案,多在变幻的云纹中,出没象征吉祥的瑞兽,并穿插种种吉样用语如“延年益寿”、“富贵且昌”等等,形成显目的时代特点。而南北朝以后,尤其隋唐时期,花纹图案出现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艺术的化生、莲花。其中一些标本,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猪头纹锦等,更明显具有波斯风格。唐代,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联珠禽兽纹锦,数量巨大。其中一些兽纹锦,且织有“胡王”字样。
在丝织物图像上的这种变化、发展,至少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表明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传统的中国丝织物装饰图案,吸收了西亚的营养,显得更为丰富而光彩夺目;第二,可以肯定,丝织物方面的这一发展,与中原王朝推进丝路贸易密切相关。适合波斯等西亚地区人们喜好的联珠禽兽、鸾鸟衔绶等纹饰织锦,会更加受到他们的欢迎。在织锦图像中,织上“胡王”字样,十分明显就是为外销目的而组织的生产。
值得强调一句,在论及“丝路”上的“丝绸”贸易时,一般的概念,都是从丝绸的祖国——中国西去,这当然是正确的结论。但在新疆出土文书及丝织实物中,可以得到另一历史信息,这就是在隋唐以前,在新疆大地上还有来自波斯的织锦。吐鲁番哈拉和卓第90号墓出土文书中,见到“钵斯锦”(此墓同出有永康十七年(480年)文书)。阿斯塔那第170号墓葬中,出土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其中见到“故波斯锦十张”,对这些文字记录,有学者认为,“此‘钵斯锦’……颇似当地所产”(意为当地织工仿波斯图案而生产)。而衣物疏中,“‘波斯锦’只不过表现了一种愿望,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真实”①。但从情理推论,生活中如果没有波斯锦的实际,则仿制无由,占有它们的愿望亦不可能出现。因此,不论多少,流入的途径如何,公元5~6世纪的吐鲁番地区已出现了波斯锦,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这实际上也已得到了出土实物的印证。夏鼐先生曾经考证,在吐鲁番出土的鸾鸟衔绶带纹锦等,就可以作为波斯锦的实物。
通过“丝路”,不仅大量中国丝绸织物西传,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意义更为重大、影响甚为深远的还有育蚕缫丝及丝绸织造工艺的西传,这在新疆出土文物中也有表现。
嘉峪关市东北约20公里的戈壁,有一片魏晋时期古墓,其中八座有壁画、砖画。绘画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其中即有采桑图,表明在公元3、4世纪时,植桑育蚕技术,在邻近新疆的河西走廊西部,已是农家经济生活的一个环节。在新疆,废弃于公元4世纪中叶的尼雅遗址,不仅见到了古代桑树,也见到蚕茧实物。在吐鲁番文书中,也保存着相关的记录。
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文书中,有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的“赁薄蚕桑”文书,表明5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蚕桑业已有相当规模”“并导致缫丝制锦业的发展”。在另几件西凉文书中,表现了为官茧缫丝,领取官银,以为工价的史实,在麹氏高昌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有在茧丝交易中收取“秤钱”的记录,而在高昌地区购买茧丝者颇多胡人,故可推论“当时销往中、西亚的中国茧丝,其中相当一部分产自高昌”②。
在育茧缫丝业发展基础上,根据麴氏高昌时期征收寺院官绢的文书,初唐时期记录绵练价格的文书,反映官属纺织工匠报告因火灾受损的文书,则可肯定麴氏高昌时期吐鲁番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丝织业。文书中还留下了它们织造着“黄地丘慈锦”等。出土实物中,也确实发现了丝、棉混织几何纹锦。
这里,着重说明了吐鲁番地区的情况,而从文书中涉及的“疏勒锦”、“丘慈锦”,则可以推论,与吐鲁番绿洲相类,在南北朝晚期,库车、喀什绿洲丝织业也都有相当水平。这类技术,自新疆进一步远及中亚、西亚,实际已不存在困难。
(二)造纸
纸及造纸技术,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造纸技术传入新疆,并通过新疆进一步西去,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在尼雅东汉墓中,发现过纸。但当时的书写材料,还是纸、木简并行,而且主要均见于木质简牍。说明纸质书写材料,还显得少而珍贵,尼雅、楼兰多见汉文简牍,可以证明。
吐鲁番地区三十多年来,出土文书约3000件。目前所见文书,最早在公元4世纪前期的十六国时期。自此以后,纸质文书是吐鲁番古墓中最常见的出土物;官方文档、私人契约、书信、抄写经典、学生习字,无不用纸。纸,在当年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是一件须臾不可离开的物品。
据此,可以作出一个推论:在十六国时期,尤其是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在这里置高昌郡以后,吐鲁番可能已逐渐地生产纸张。理由是,社会对纸有重大需求;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自西汉开始造纸至此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其技术知识,当已较普及。因此在河西地区进入吐鲁番的大量移民中,会有了解纸作工艺的匠师。本地造纸的主客观条件,是具备的。
这一推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对吐鲁番出土古纸,潘吉星教授曾进行了分析。取北凉到唐代古纸标本26件(其中4件为库车出土),对纸的物理、化学结构进行观察,纸质标本,包括官府文档、私人文书、古籍抄本、佛经等。观察表明: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典籍抄本、官府文档用纸,纤维分散均匀,纤维束少,打浆较细,纸质较好;而一般民间用纸,如民间私契、丸药包装纸,纤维交织不均,打浆不匀,纤维破碎程度较差,杂质或未除尽,纸质明显较次。分析抄纸工艺,可见主要为布纹纸,也有帘文纸。吐鲁番出土建兴三十六年(348)建初十四年(418)用纸,都是用织纹模抄造的布纹纸。其中建初十四年古纸,可以观察到纸模网目约为110孔/厘米2,是我国目前有准确纪年的早期布纹纸标本。
布纹纸是比较古老的产品,表现着传统的工艺,汉、晋、南北朝时期,多为这种技法。值得强调说明的是新疆土法造纸,至今仍保持这一传统。因此,它接受的是中原地区比较古老的一种工艺。因而可以推论,其接受的时代当也是这一工艺在中原、河西地区流行的时代。
帘纹纸,是晋以后始见的抄纸工艺。在潘氏测定的18件隋唐时期古纸中,除少量帘纹不显外,几乎都是帘纹纸。细致分析吐鲁番出土唐“白怀洛借钱契”、“卜老师借钱契”及“卜天寿《论语》郑注”、“宁和才授田户籍”,可以见出纸质有粗帘纹及制作稍精的细帘纹之别。学生习字等平常普通用纸,明显为粗帘纹,官府文档如户籍等,纸质即较精良。帘纹纸与敦煌石室中所见粗横帘纹纸,工艺一致。
唐代吐鲁番地区已有了官办的造纸作坊,这得到阿斯塔那第93号墓中出土唐代文书的证明。文书有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驱使”,可作为唐代已存在“纸坊”的确证。唐代四州既有纸坊,纸质标本显示的工艺与敦煌地区用纸又一样,这说明,当年吐鲁番地区纸张生产工艺得之于河西地区的影响;或者,生产者就直接来之于河西地区。如是,与两汉以后河西地区大量移民进入吐鲁番的历史背景又是可以统一的。
在分析吐鲁番出土古纸标本时,还有一个工艺现象,在纸浆中加入淀粉糊,以使纸质平润、增光、受墨,而这种工艺方法,在今天新疆一些地区,还仍然保留使用。应该说,这一传统,也显示着历史的印痕。
造纸工艺经过新疆传入阿拉伯并进一步及于非洲、欧洲广大地区,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这一工艺西传的中继站,就在新疆。
(三)毛纺织工艺
近四十年的新疆考古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对新疆地区毛纺织生产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对毛纺织生产工艺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些年的考古工作,在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哈密五堡,且末扎洪鲁克墓地,阿拉沟、鱼儿沟墓地,和静察吾乎沟墓地,巴里坤南湾,哈密焉不拉克、哈密火车站附近、洛浦山普拉墓地、鄯善洋海三个桥、楼兰城郊、尼雅、于田屋于勒克、巴楚托库孜萨来、吐鲁番阿斯塔那、米兰吐蕃戍堡等处,都有相当数量而且保存情况很好的古代毛织物出土。从距今4000年前直到唐宋时期,也就是说,前后历时差不多达3000年。
粗略统计一下现有毛织物种类,如提花毛毯、平纹毛织毯、平纹毛布、毛罽、缂毛织物、各种编织毛带等,其中,不能排除少量毛织物(如山普拉出土的人首马身缂毛织物)是来自国外,但绝大多数当为本地自产。
这就为我们总结、认识古代新疆毛织物发展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资料。
对新疆出土毛织物的分析研究,即对毛纺织物的原料,纺纱技术,织造工艺,染色,图案,它们与周围地区的关联等,已取得一定的进展①,但有待深入的空间还是不小的。
目前,可以肯定提出一点:中国中原地区在唐宋时期运用得十分成熟,有过许多惊人产品的缂丝工艺,其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应该是藉丝路联系,吸收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毛纺织生产中早就运用了的一种生产工艺。在新疆出土的毛纺织物中,早在公元前,已见到这类通经断纬的生产技术,出土的公元前后的毛织物中,通经断纬技术运用得十分成熟。其他如毛织物染色,也是一项应该认真分析、总结的技艺。3000年前的毛织物,其色彩至今仍然新鲜而光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四)玻璃
近年的新疆考古,不少古代遗址中见到了玻璃。举其大者,如若羌县瓦石峡、且末县城西南纳勒克、安迪尔牧场东北沙漠中的安迪尔古城(亦称夏然塔格古城)、于田县喀拉墩、墨玉县扎瓦遗址、疏附县英吾斯坦、楼兰古城等,在考古调查中,都发现过数量不等的玻璃器、各种玻璃珠及玻璃碎片。这些资料,目前都保存在新疆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还采集、保存着阿克苏、库车地区一些古遗址中的玻璃片。在若羌瓦石峡,考古工作者发掘过一处烧制玻璃器的土窑,出土了小口细颈凹底瓶、玻璃罐,具有宋、元时期特征。对宋、元时期新疆地区的玻璃生产,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据瓦石峡出土资料,如从玻璃器造型看,与同时期的阿拉伯、波斯玻璃器有相近特点,属钠钙玻璃系统,表明当年新疆玻璃生产接受着阿拉伯、波斯的影响。
在塔里木周缘不少古代废墟中采集的玻璃片,大多是薄壁器,单色素面。部分保存了器口的玻璃器残片,多为圆唇,唇口或有一道淡蓝色的纹道,总体看,玻璃器透明度不好,含有较多小气泡及杂质,熔炼水平不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为标本多是遗址地表采集,在时代判定上存在一定困难,局限了认识的深入。但总体分出析,在公元初始的汉—晋时期(4世纪前),已见玻璃制品(如楼兰古城中的玻璃器),隋唐时期更多,宋、元时期,已见土法烧造的玻璃器,工艺上明显可以见出阿拉伯、波斯影响,但在助熔剂(如用新疆土硝)等配料上,有自身的特点。
玻璃工艺,通过丝路东来中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新疆地区,是深入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地段,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进一步的努力。
除了这几个方面的资料外,其他如古代采矿及金属冶铸工艺,犁耕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如凿井、坎儿井)等方面,也都有相当新的资料,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古代“丝路”上文化技术知识的交流。
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推动过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丝路的历史,表现了全人类在自身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中,需要互相支持、帮助,一个互相联系、积极交流、共同发展与进步的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一积极的文化精神,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随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一)丝绸
在出土的足以表现“丝路”内容的珍贵文物中,首推丝绸。出土数量大、品种多、地域广,时代延续长,十分有力地表明:在丝绸之路上,轻薄美观的各种“丝绸”织物,深受西亚、欧洲人民的欢迎,是通过“丝路”西向的主要商品。
近几十年来,新疆考古工作中见到丝绸织物的遗址点相当丰富。举其大者,如若羌东部的阿拉尔,楼兰城东北郊的孤台、平台墓地,孔雀河谷老开屏墓地,库鲁克山南麓的营盘古墓,吐鲁番盆地中鄯善县鲁克沁,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天山中阿拉沟、鱼儿沟古墓地,乌鲁木齐南郊盐湖,库车苏巴什,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民丰县尼雅古墓,于田县喀拉墩,洛浦县山普拉古墓,木垒四道沟古墓葬等处,均有所见。尤其是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的阿斯塔那晋唐墓地,差不多可以说,无墓不见丝绸文物,颇为有力地说明当年丝绸织物在高昌地区相当普及的情况。谈及丝织物出土地点,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地点,几乎全部在天山以南地区。所以存在这一现象,应与天山以北地区降水较多,湿度较大,织物类在地下很不容易保存有关。
有关织物的时代,分析表明:早可以到春秋、战国,盛于两汉,大盛于隋唐,迄止于宋元,均有所见。
织物品种,主要为素绢及染色绢,以及各种花纹图案的织锦、暗花绮、绫、缣、纱、罗、轻容、刺绣及染织等。这些文物,出土时多零散、破损,绝对数量虽不算多,但实际却代表着巨大的数字。A.斯坦因在楼兰故城遗址点发掘得一枚简牍,简文称“人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绢四千三百廿六匹”。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提到长安汉商在弓月城胡商处,一次就调剂到绢237匹。将上列出土文物品种与这些出土文字资料结合分析,可以充分肯定,通过“丝路”进行的丝绸缎物贸易,数量曾是相当巨大的。
分析“丝路”织物图案,可以得到的强烈印象是汉代织锦,花纹布局,均成行排列,循环往复。花纹图案,多在变幻的云纹中,出没象征吉祥的瑞兽,并穿插种种吉样用语如“延年益寿”、“富贵且昌”等等,形成显目的时代特点。而南北朝以后,尤其隋唐时期,花纹图案出现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艺术的化生、莲花。其中一些标本,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猪头纹锦等,更明显具有波斯风格。唐代,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联珠禽兽纹锦,数量巨大。其中一些兽纹锦,且织有“胡王”字样。
在丝织物图像上的这种变化、发展,至少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表明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传统的中国丝织物装饰图案,吸收了西亚的营养,显得更为丰富而光彩夺目;第二,可以肯定,丝织物方面的这一发展,与中原王朝推进丝路贸易密切相关。适合波斯等西亚地区人们喜好的联珠禽兽、鸾鸟衔绶等纹饰织锦,会更加受到他们的欢迎。在织锦图像中,织上“胡王”字样,十分明显就是为外销目的而组织的生产。
值得强调一句,在论及“丝路”上的“丝绸”贸易时,一般的概念,都是从丝绸的祖国——中国西去,这当然是正确的结论。但在新疆出土文书及丝织实物中,可以得到另一历史信息,这就是在隋唐以前,在新疆大地上还有来自波斯的织锦。吐鲁番哈拉和卓第90号墓出土文书中,见到“钵斯锦”(此墓同出有永康十七年(480年)文书)。阿斯塔那第170号墓葬中,出土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其中见到“故波斯锦十张”,对这些文字记录,有学者认为,“此‘钵斯锦’……颇似当地所产”(意为当地织工仿波斯图案而生产)。而衣物疏中,“‘波斯锦’只不过表现了一种愿望,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真实”①。但从情理推论,生活中如果没有波斯锦的实际,则仿制无由,占有它们的愿望亦不可能出现。因此,不论多少,流入的途径如何,公元5~6世纪的吐鲁番地区已出现了波斯锦,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这实际上也已得到了出土实物的印证。夏鼐先生曾经考证,在吐鲁番出土的鸾鸟衔绶带纹锦等,就可以作为波斯锦的实物。
通过“丝路”,不仅大量中国丝绸织物西传,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意义更为重大、影响甚为深远的还有育蚕缫丝及丝绸织造工艺的西传,这在新疆出土文物中也有表现。
嘉峪关市东北约20公里的戈壁,有一片魏晋时期古墓,其中八座有壁画、砖画。绘画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其中即有采桑图,表明在公元3、4世纪时,植桑育蚕技术,在邻近新疆的河西走廊西部,已是农家经济生活的一个环节。在新疆,废弃于公元4世纪中叶的尼雅遗址,不仅见到了古代桑树,也见到蚕茧实物。在吐鲁番文书中,也保存着相关的记录。
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文书中,有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的“赁薄蚕桑”文书,表明5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蚕桑业已有相当规模”“并导致缫丝制锦业的发展”。在另几件西凉文书中,表现了为官茧缫丝,领取官银,以为工价的史实,在麹氏高昌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有在茧丝交易中收取“秤钱”的记录,而在高昌地区购买茧丝者颇多胡人,故可推论“当时销往中、西亚的中国茧丝,其中相当一部分产自高昌”②。
在育茧缫丝业发展基础上,根据麴氏高昌时期征收寺院官绢的文书,初唐时期记录绵练价格的文书,反映官属纺织工匠报告因火灾受损的文书,则可肯定麴氏高昌时期吐鲁番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丝织业。文书中还留下了它们织造着“黄地丘慈锦”等。出土实物中,也确实发现了丝、棉混织几何纹锦。
这里,着重说明了吐鲁番地区的情况,而从文书中涉及的“疏勒锦”、“丘慈锦”,则可以推论,与吐鲁番绿洲相类,在南北朝晚期,库车、喀什绿洲丝织业也都有相当水平。这类技术,自新疆进一步远及中亚、西亚,实际已不存在困难。
(二)造纸
纸及造纸技术,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造纸技术传入新疆,并通过新疆进一步西去,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在尼雅东汉墓中,发现过纸。但当时的书写材料,还是纸、木简并行,而且主要均见于木质简牍。说明纸质书写材料,还显得少而珍贵,尼雅、楼兰多见汉文简牍,可以证明。
吐鲁番地区三十多年来,出土文书约3000件。目前所见文书,最早在公元4世纪前期的十六国时期。自此以后,纸质文书是吐鲁番古墓中最常见的出土物;官方文档、私人契约、书信、抄写经典、学生习字,无不用纸。纸,在当年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是一件须臾不可离开的物品。
据此,可以作出一个推论:在十六国时期,尤其是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在这里置高昌郡以后,吐鲁番可能已逐渐地生产纸张。理由是,社会对纸有重大需求;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自西汉开始造纸至此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其技术知识,当已较普及。因此在河西地区进入吐鲁番的大量移民中,会有了解纸作工艺的匠师。本地造纸的主客观条件,是具备的。
这一推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对吐鲁番出土古纸,潘吉星教授曾进行了分析。取北凉到唐代古纸标本26件(其中4件为库车出土),对纸的物理、化学结构进行观察,纸质标本,包括官府文档、私人文书、古籍抄本、佛经等。观察表明: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典籍抄本、官府文档用纸,纤维分散均匀,纤维束少,打浆较细,纸质较好;而一般民间用纸,如民间私契、丸药包装纸,纤维交织不均,打浆不匀,纤维破碎程度较差,杂质或未除尽,纸质明显较次。分析抄纸工艺,可见主要为布纹纸,也有帘文纸。吐鲁番出土建兴三十六年(348)建初十四年(418)用纸,都是用织纹模抄造的布纹纸。其中建初十四年古纸,可以观察到纸模网目约为110孔/厘米2,是我国目前有准确纪年的早期布纹纸标本。
布纹纸是比较古老的产品,表现着传统的工艺,汉、晋、南北朝时期,多为这种技法。值得强调说明的是新疆土法造纸,至今仍保持这一传统。因此,它接受的是中原地区比较古老的一种工艺。因而可以推论,其接受的时代当也是这一工艺在中原、河西地区流行的时代。
帘纹纸,是晋以后始见的抄纸工艺。在潘氏测定的18件隋唐时期古纸中,除少量帘纹不显外,几乎都是帘纹纸。细致分析吐鲁番出土唐“白怀洛借钱契”、“卜老师借钱契”及“卜天寿《论语》郑注”、“宁和才授田户籍”,可以见出纸质有粗帘纹及制作稍精的细帘纹之别。学生习字等平常普通用纸,明显为粗帘纹,官府文档如户籍等,纸质即较精良。帘纹纸与敦煌石室中所见粗横帘纹纸,工艺一致。
唐代吐鲁番地区已有了官办的造纸作坊,这得到阿斯塔那第93号墓中出土唐代文书的证明。文书有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驱使”,可作为唐代已存在“纸坊”的确证。唐代四州既有纸坊,纸质标本显示的工艺与敦煌地区用纸又一样,这说明,当年吐鲁番地区纸张生产工艺得之于河西地区的影响;或者,生产者就直接来之于河西地区。如是,与两汉以后河西地区大量移民进入吐鲁番的历史背景又是可以统一的。
在分析吐鲁番出土古纸标本时,还有一个工艺现象,在纸浆中加入淀粉糊,以使纸质平润、增光、受墨,而这种工艺方法,在今天新疆一些地区,还仍然保留使用。应该说,这一传统,也显示着历史的印痕。
造纸工艺经过新疆传入阿拉伯并进一步及于非洲、欧洲广大地区,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这一工艺西传的中继站,就在新疆。
(三)毛纺织工艺
近四十年的新疆考古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对新疆地区毛纺织生产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对毛纺织生产工艺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些年的考古工作,在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哈密五堡,且末扎洪鲁克墓地,阿拉沟、鱼儿沟墓地,和静察吾乎沟墓地,巴里坤南湾,哈密焉不拉克、哈密火车站附近、洛浦山普拉墓地、鄯善洋海三个桥、楼兰城郊、尼雅、于田屋于勒克、巴楚托库孜萨来、吐鲁番阿斯塔那、米兰吐蕃戍堡等处,都有相当数量而且保存情况很好的古代毛织物出土。从距今4000年前直到唐宋时期,也就是说,前后历时差不多达3000年。
粗略统计一下现有毛织物种类,如提花毛毯、平纹毛织毯、平纹毛布、毛罽、缂毛织物、各种编织毛带等,其中,不能排除少量毛织物(如山普拉出土的人首马身缂毛织物)是来自国外,但绝大多数当为本地自产。
这就为我们总结、认识古代新疆毛织物发展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资料。
对新疆出土毛织物的分析研究,即对毛纺织物的原料,纺纱技术,织造工艺,染色,图案,它们与周围地区的关联等,已取得一定的进展①,但有待深入的空间还是不小的。
目前,可以肯定提出一点:中国中原地区在唐宋时期运用得十分成熟,有过许多惊人产品的缂丝工艺,其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应该是藉丝路联系,吸收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毛纺织生产中早就运用了的一种生产工艺。在新疆出土的毛纺织物中,早在公元前,已见到这类通经断纬的生产技术,出土的公元前后的毛织物中,通经断纬技术运用得十分成熟。其他如毛织物染色,也是一项应该认真分析、总结的技艺。3000年前的毛织物,其色彩至今仍然新鲜而光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四)玻璃
近年的新疆考古,不少古代遗址中见到了玻璃。举其大者,如若羌县瓦石峡、且末县城西南纳勒克、安迪尔牧场东北沙漠中的安迪尔古城(亦称夏然塔格古城)、于田县喀拉墩、墨玉县扎瓦遗址、疏附县英吾斯坦、楼兰古城等,在考古调查中,都发现过数量不等的玻璃器、各种玻璃珠及玻璃碎片。这些资料,目前都保存在新疆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还采集、保存着阿克苏、库车地区一些古遗址中的玻璃片。在若羌瓦石峡,考古工作者发掘过一处烧制玻璃器的土窑,出土了小口细颈凹底瓶、玻璃罐,具有宋、元时期特征。对宋、元时期新疆地区的玻璃生产,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据瓦石峡出土资料,如从玻璃器造型看,与同时期的阿拉伯、波斯玻璃器有相近特点,属钠钙玻璃系统,表明当年新疆玻璃生产接受着阿拉伯、波斯的影响。
在塔里木周缘不少古代废墟中采集的玻璃片,大多是薄壁器,单色素面。部分保存了器口的玻璃器残片,多为圆唇,唇口或有一道淡蓝色的纹道,总体看,玻璃器透明度不好,含有较多小气泡及杂质,熔炼水平不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为标本多是遗址地表采集,在时代判定上存在一定困难,局限了认识的深入。但总体分出析,在公元初始的汉—晋时期(4世纪前),已见玻璃制品(如楼兰古城中的玻璃器),隋唐时期更多,宋、元时期,已见土法烧造的玻璃器,工艺上明显可以见出阿拉伯、波斯影响,但在助熔剂(如用新疆土硝)等配料上,有自身的特点。
玻璃工艺,通过丝路东来中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新疆地区,是深入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地段,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进一步的努力。
除了这几个方面的资料外,其他如古代采矿及金属冶铸工艺,犁耕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如凿井、坎儿井)等方面,也都有相当新的资料,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古代“丝路”上文化技术知识的交流。
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推动过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丝路的历史,表现了全人类在自身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中,需要互相支持、帮助,一个互相联系、积极交流、共同发展与进步的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一积极的文化精神,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随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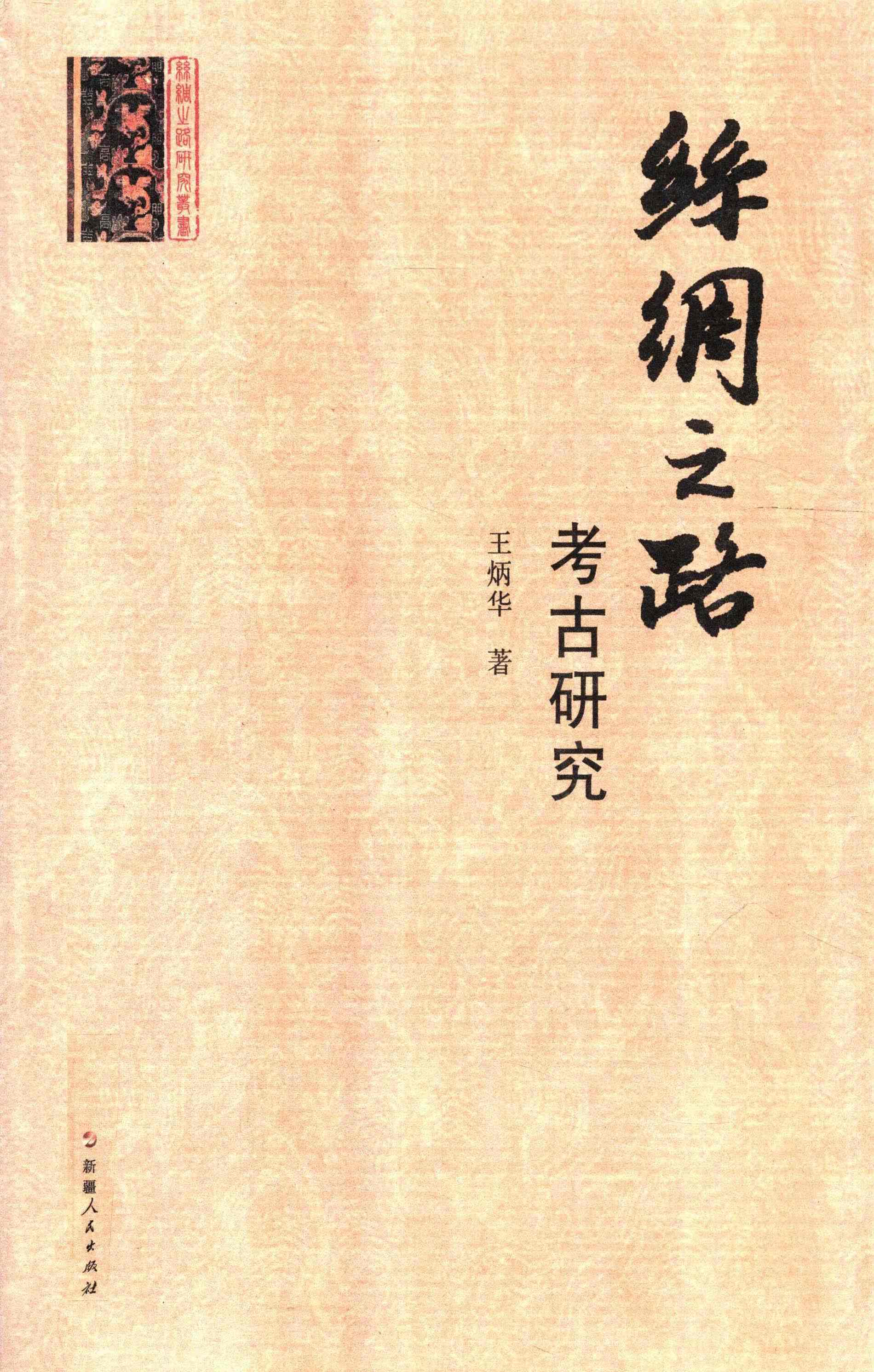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