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道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1059 |
| 颗粒名称: | (二)中道 |
| 分类号: | K875.9 |
| 页数: | 12 |
| 页码: | 023-03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丝路自焉耆傍天山南麓西行,自汉迄唐、以至宋元,变化不大的交通路线沿线的重要遗迹和遗物。 |
| 关键词: | 中道 丝路 沿线 |
内容
这里指出敦煌后沿天山南麓过帕米尔抵大宛、碎叶的交通路线,即《汉书·西域传》中的“北道”,是丝绸之路沙漠道中最主要的交通路线。
这一路线,自焉耆傍天山南麓西行,自汉迄唐、以至宋元,变化不大。关键在于敦煌至焉耆间,变化不小:或经罗布荒漠到楼兰;或经伊吾过高昌;甚至经过库姆塔格沙漠入高昌,颇为复杂。
西出敦煌,沿疏勒河谷入白龙堆,过楼兰,沿孔雀河谷西走,这是两汉时期进入西域的一条主要路线。出玉门关后,仍然耸立着一段西向延伸的汉代长城。黄文弼20世纪30年代在罗布淖尔北岸发掘过的土垠遗址,世界瞩目的古楼兰城,1979年新疆考古所在孔雀河谷老开屏发掘的汉墓,近年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附近发现的汉代墓葬,沿库鲁克山列布的古代烽燧,既清楚表明这一古道的存在,也显示了古道的走向。
从自然地理条件角度分析,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通路。自疏勒河谷进入白龙堆,沿途戈壁、风蚀土丘林、盐渍荒漠,缺水少草,通行十分艰难。所以选择、开拓这条道路,完全是因为存在匈奴对伊吾、车师的控制。因着这一政治形势,西汉王朝才抉择了这一路线,从而也把楼兰推上了中西交通枢纽的宝座。
楼兰依傍罗布淖尔湖,位于罗布泊西北,目前已沉没在无人的荒漠中。根据新疆考古所在1979~1987年对楼兰城的多次调查试掘资料,楼兰古城位于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古城城墙已在强烈的风蚀中破败不堪。城垣原为不规则的方形,周长1316.5米,总面积10.8万多平方米。从残存土垣看,城垣曾经过多次修筑,一条古河道,贯穿全城,城内遗迹尚可见出官署、寺院、居民住宅区的差别,全城建筑规模最大的所谓官署区,留存至今的三间土屋面积只106平方米。城内建筑基本特点,是当前仍在南疆地区沿用的以木材构架,红柳枝作墙,外涂草泥以为墙壁的建筑风格。新疆考古所在楼兰城内,发掘到汉晋时期残木简60多支,在楼兰城郊,清理过一批汉代墓葬,出土最多的是汉代锦绢、漆器、铜镜,它们明显来自中原地区。另有不少土产精致毛毯、斜纹毛织物,平纹毛布、木器、陶器等。表现了汉晋时代楼兰的社会生活。
根据大量的楼兰出土文物,学术界一般都同意,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活跃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楼兰城,在公元4世纪30年代以后,即逐渐废弃,慢慢沦为荒漠。对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研究者们曾经提出过多方面的分析意见。择其大要,如气候趋于干旱,降水趋少,引起地理环境变化说;高山冰川萎缩,导致河流水量减少说;干旱荒漠地区水系和湖泊不稳定,侵蚀和堆积交替作用使水系成周期性变化,导致楼兰环境改变说;人类活动,导致河道水量改变,使楼兰地区环境恶化等等。各种观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认真分析整个情况,我认为,应该说,“楼兰的兴衰是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变化的综合反映”①,而社会政治因素在其中明显起着关键性作用。
第四纪以来,罗布泊地区一直是干旱环境,因此,楼兰在历史时期中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不能简单地归于气候干旱,而必须考虑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干旱的新疆内陆,一个绿洲的形成、维持、发展,不单须有必要的地理条件,而且要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楼兰作为王国的都城,魏晋时期作为西域长史府驻地,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鲜明存在于这一社会背景,存在着政治、经济、丝路交通方面的实际需要。强大有力的组织力量,科学的水利灌溉设施,辛勤的劳动,人类曾限制了这片地区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发展,并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保持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生态环境。而一旦失掉了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努力,恶劣的自然条件就会使无组织的相对软弱的人群束手无策。认真分析楼兰古城废弃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其中社会交通因素可以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因子。楼兰古城在西域历史上发出过夺目光彩光芒,受到当时中原王朝、匈奴王国、西方各国的关心,无非是因为它在从敦煌到天山南麓的交通路线上曾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两三个世纪的努力,匈奴被排除出西域政治舞台,中原王朝经过伊吾、高昌,沿天山南麓西去的交通线逐渐成了坦途。公元327年,北凉在高昌设郡,立田地县,标志柳中、高昌与河西地区早已联成一体的事实,在政治上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这一情况下,通过白龙堆、楼兰一线,交通条件上的不利因素自然使其在丝路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必然要导致楼兰的衰落。
汉晋时期,为支持楼兰运输干线的运转,克服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汉、魏晋王朝曾集中力量在楼兰地区屯田、西域长史府,作为当时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驻节在楼兰,强大的组织力量,使楼兰的自然地理环境虽称恶劣,但还是维持着平衡。从大量出土的具体表现当年屯田事业的文书中,可以看到西域长史府凭藉着强有力的水利灌溉事业,运营着楼兰地区以屯田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丝路供给、丝路安全保障,应该说,都凭藉着这一生产事业的支持。楼兰故址出土文书资料,最晚止于前凉王朝继续使用的(西晋)建兴十八年(330年),不见较其更晚的纪年文字。这说明,在公元330年或其稍后,楼兰古城作为西域长史府的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使得楼兰丧失了它在“丝路”干线上中继站的重要地位,与政治、军事、商业交通、邮传、屯田等有关的一套相应组织会随之撤离、转移,人口会随之大大减少,有组织地对罗布荒漠自然环境的改造努力会随之急剧减弱,这对楼兰绿洲生命的维持,无疑会是严重的一击。没有了人类有组织的努力,风沙侵袭,河流改道,土地积盐等可以克服的自然困难会变得无法克服,楼兰绿洲环境会日益恶化。这一切,无疑会导致楼兰绿洲的最后毁灭。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楼兰古城的兴起、废败,与中原王朝对西域大地政治、经济的控制、管理,与丝路路线的组织、建设密切相关。
可以帮助说明楼兰碛道之废弃绝不是、或主要绝不是自然原因还有一个相反的实例。公元7世纪中叶,割据吐鲁番的高昌王国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结盟,极力阻抑唐王朝进入西域,控制了通过吐鲁番来去的“丝路”大道。焉耆王龙突骑支就曾建议重开通过孔雀河谷经过故楼兰地区、白龙堆入敦煌的“碛路”,这实际是与高昌竞争把握“丝路”权益的措施,曾得到了唐王朝的支持。这一计划,随唐王朝统一高昌而自然放弃,但却表明了一个事实:通过楼兰地区的“碛路”,虽属困难,却并不是不能通行的,而通行与否,社会经济、政治因素,起着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楼兰到天山南麓的路线,是走库鲁克山南麓,孔雀河谷水草丰沛地带。
自楼兰古城西北行,还可以见到几座烽燧遗迹,兀立在荒漠之中。
距楼兰古城约80公里,在孔雀河北岸一道低矮山脊上,俗称老开屏,1979年,笔者曾主持发掘过一座孤立的汉代墓葬,出土过汉锦、汉镜及多量木器①。
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旁,近年发现一区最晚到汉晋的古墓群,出土大量毛毯、毛纺织物、木器,也见到汉代织锦②。
尉犁县西北约60公里,位于库鲁克山南麓一剥蚀土丘上,还保存古烽一座,烽墩约4米见方,高3米左右,土坯叠砌。其下见大量红陶片、烽砟③。
自此更前行,即可抵达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西域都护驻节地乌垒城。
从伊吾方向进入天山南麓,是一条更重要、自然地理条件也稍好的路线。
汉代伊吾城址,至今未得考古确定,估计当在今哈密市附近。这里泉水丰沛,农业生产条件优良。在哈密市内,近年发现不少古代遗址,哈密火车站附近就是一片相当密集的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古代墓地,墓中出土相当丰富的彩陶。
在哈密火车站基建中,也有过出土文物的报道。
自哈密西行,四堡乡,现存拉甫乔克古城,有说为唐“纳职县”所在。
自拉甫乔克过五堡,斜向东南,戈壁中尚存一区古堡遗址,沿白杨沟水,沿途也见古代烽燧断续相继,这显示了自伊州入西州(从哈密绿洲进入吐鲁番盆地)的一条径道。
吐鲁番盆地中,七克台、汉墩、连木沁、煤窑沟、七泉湖、木尔吐克萨依、乌江布拉克、胜金口、交河南北、野木什、阿拉沟口等许多地点,都见到古代烽燧、戍堡,由于欠缺深入的工作,对有关遗迹的准确时代,及通过它们所标示的古代路线及不同历史时期中路线的变化,目前还难以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高昌、交河故城,是这一线路中大家都比较注意的两座古城。
高昌古城是古代新疆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玄奘西去求经,麟德元年(664年),波斯王子泥涅师自长安返国,都曾在这里停息。
高昌古城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可分外、内、宫城三重。这是长时期发展的结果,记录着历史变化的痕迹。
外城略呈方形,周长5000多米,城垣基址厚达12米,城墙残高至今仍有11.5米,夯土版筑,部分地段用土坯修补。有马面,城门从现存遗迹分析,每面至少有两座,在城郊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记录了唐西州城有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可以印证。
内城居外城正中,西、南两面城墙大部分保存下来,北面仅存部分基址,东墙全毁,复原周长约3000多米。
《隋书》称高昌王国“其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隋唐时期一步当于6尺4寸。据出土唐尺,一尺长度为29厘米,6尺4寸当1.856米,1840步,则当于3415米,与现存中城范围相近,故而可以肯定目前中城遗址实际就是高昌王国的都城所在。其建城时间较外城为早。
高昌王国的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俗称“可汗堡”。堡内塔柱至今仍高十多米,其旁,是一组包含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地下庭院、暗燧的大型建筑,燧道宽达3米多。宫城墙基本完好,高达6米,南向开门,门阙地基清晰。其间是宽达3米的门道。宫墙东侧,曾出土“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表明了当年高昌王室寺院的所在。
至于公元9世纪以后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从现存遗迹看,范围已不很明确,南北朝时期高昌王国宫城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是否被继续使用,目前还无充分资料作出明确结论。有的学者提出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是在现存外城的北部,处内、外城北墙之间,即外城北墙为宫城之北墙,而内城北墙即宫城南墙,主要根据是这一范围内目前保留了不少高出地面三四米的高土台,建筑规模宏伟,故可能是回鹘王族的宫廷所在,可以聊备一说。
外城西南部有一大型寺院,寺门东向,东西长约130米、宽85米,占地面积1.1万多平方米,寺院中央台基上有一多层台的土坯塔柱,周围高墙回护,是全寺的主体建筑。两厢和塔庙是高大的重楼建筑。规模十分宏伟。
寺院附近有密集的建筑遗址,建筑物多是夯土为墙,土坯起券,作长筒形纵券顶,这种建筑方法吐鲁番地区至今仍然使用。
外城东南部分也有一小型寺院,土坯砌就的土塔犹存,从壁画风格看,时代较西南大寺为晚。
自高昌建城至公元13世纪中叶海都叛乱(1279),攻灭高昌,古城被毁,前后历时1000年以上,作为高昌回鹘王都,历时也近500年,高昌在新疆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
高昌城外北、西北郊是晋、唐时期的墓区。这里埋葬着同一历史阶段内高昌各种社会身份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发掘古墓葬四百多座,出土过大量古代珍贵文书、丝绸文物等,是研究高昌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及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
自高昌古城斜向西北,距约50公里,是交河故城。不论是高昌、西州,还是高昌回鹘,北向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或西向焉耆,这里均是交通要隘,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历史上一直也是吐鲁番地区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西汉时为车师前国的王都。《汉书·西域传》称:“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域下,故号‘交河’。”交河故城坐落在两河之间的一区土岛上,这段文字,是对古城形势的准确描述,也说清了古城得名的由来。
古城所在土岛南北长1650米,最宽处约300米,古城位于土岛之南半部,建筑遗迹南北长达1000米,宽与岛之宽同。说为古城,因坐落在高数十米(最高30米)的土岛上,四周峭壁悬岩,形势天成,可以凭险据守,所以并无防御性质的城墙。
入城门道有两处:南门是主要进出口,但具体建筑结构已破坏,只存门道豁口;东门保存较好,劈岩而成门道,安设门额的方形榫洞也依然可见,自门道到河底高达20米,陡险曲折。入门处有防御设施,堪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城内建筑遗址总面积,初步测量约22万平方米,大致可见出寺院、民居、衙署和官邸等性质不同的建筑遗迹。
纵贯全城南北方向有一条长约350米,宽约10米的大道。大道直通城北一区大型寺院,建筑面积达5100平方米,在这区重楼建筑的方形大院内,塔柱犹存。城内寺院建筑多为这种方形院落,入室有神坛或塔柱,主要分布在主干道以西。
自这一主干道中部向东为另一干道,通向东门。主干道以东,东西干道以南,这一区域内多大型院落,常是衙署、官邸所在。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全城内唯一见砖、瓦的大型建筑,即是这一区内附有地下室的气势相当宏大的院落。
东西干道以北,建筑相当密集,门庭较小,当是一般居民住宅。
交河故城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古城遗址之一,建筑富有特色:其一,街道两旁是高厚土墙,临街不见门窗,纵横交错的巷道通过土墙将庭院分隔为坊曲,穿过街巷,进入坊墙,才能到达民户大门。
其二,土崖土质致密,所有建筑均挖地为院,隔梁为墙,掏洞成室。街巷也是挖地而成的路沟,高度不足,则以挖地所得泥土夹板夯筑。房顶主要由土墙承重,所用木料不多,这是适应新疆地区干燥少雨的特点而形成的生土建筑风格,极大地减省了木材及能源的消耗,是值得总结、发扬的优良传统。
交河故城始建在西汉以前的车师前部。西汉前期,是车师王都所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汉王朝在吐鲁番地区设戊己校尉管理屯戍,设交河壁,派驻吏卒。晋十六国,吐鲁番地区为高昌王国,交河为王国—郡。由于地位重要,每每派王子驻节交河。公元640年,唐王朝统一高昌,设西州、交河为西州属县。因为这里形势险要、又控制着天山南北交通的一处隘道,在军事上明显具有重要地位。自交河故城南出盐山之阙口,目前仍可见唐代烽墩。自盐山南缘斜向东南,经布干土拉古城可抵高昌;斜向西南,经大墩子、屋威梯木古城堡入托克逊,为唐代丝路“银山道”干线;稍偏西北,入阿拉沟口,也见到唐代古堡,有山道可入巩乃斯河、于尔都斯草原。
交河故城西,存石窟寺一区。足以展示“丝路”文化特色的佛教遗迹,除交河城外石窟外,在吐鲁番地区,还有桃儿沟、吐峪沟、胜金口、柏孜克里克等多处。唯蒙受种种人为的、自然的破坏,保存状况堪忧。柏孜克里克,算是目前保存状况较好的一区,这里稍作介绍。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坐落在高昌城北火焰山中,踞火焰山主峰北坡,下临木头沟水,环境清幽。唐《西州图经》称此为“宁戎窟寺”。现存洞窟83个,可以见出毗诃罗窟、支提窟、隐窟、僧房之别。保存壁画洞窟约只50%,大多残毁比较严重。洞窟始建于高昌王国时,唐、高昌回鹘时期臻于繁荣,是高昌回鹘时期的王室寺院之一。近年维修柏孜克里克,文物工作者曾在早期废窟中发现回鹘文、粟特文、汉文、梵文的残经及世俗文书,如晋人写本《汉书·西域传》残页,写于高昌王国建昌五年(559年)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鸠摩罗什译本),宋刻本《金藏》残帙,回鹘文雕版印刷品残页,西夏文雕刻印本残页,粟特文手写本残卷等。其中一件金箔包装纸,来自宋代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东朝西的一家纸铺,它专门制作、销售“佛经诸般金箔”,希望主顾“辨认不误”,是宋代杭州纸铺的广告商标,也很好地说明了在11、12世纪时,高昌回鹘王朝与宋王朝的商业贸易情况。清理工作中还发现十分宏伟的木构建筑材料,如斗栱等物(其中一件,栱径75厘米、斗长21厘米)。表明唐代,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在依岩开凿的洞窟外面,有十分高大的殿堂、回廊。
柏孜克里克现存壁画,主要属于高昌回鹘时期。在长方形纵券顶的洞窟内,绘佛传故事,展示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第33窟后壁,一幅表现佛涅槃后众弟子举哀的图像,艺术表现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民族的佛弟子,肤色各异,发式、服装不同,可以多少反映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西域大地,人种各异、民族众多的社会生活图景。
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画面完整、色泽鲜丽的高昌回鹘国王、王后供养佛的图像,是壁画中的珍品。主要部分已为勒柯克割剥运往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
“丝路”自吐鲁番沿“银山道”西去,下一站主要为焉耆王国。关于“银山道”的具体线路,据考古调查资料,出托克逊后,应走苏巴什沟,沿途有水草。地理形势、山泉,与玄奘当年留下的记录可以呼应。出沟,至库米什,进入焉耆盆地。唐代在这里设置过焉耆都护府和焉耆镇,目前坐落在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达沁古城,可能就是汉焉耆国都员渠城,也是唐焉耆都督府和焉耆镇城之所在。
博格达沁古城是焉耆盆地内建筑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周长3000多米,城墙基垣完整,保存稍好地段残高4米。城内建筑遗迹多已坍塌。最大一区周长达143米,城内地表采集到汉五铢、唐开元通宝、波斯银币等,其他金银饰物、料珠、陶器亦常见。古城附近见较大型汉唐墓葬,出土过汉代铜镜、包金铁剑、金质龙纹带扣。
与博格达沁古城相去不远的锡克沁、明屋佛寺遗址,曾经出土过多量佛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界,佛教史学者关注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就出土在明屋佛寺之中。
焉耆西去,最重要的站点是轮台。这里是汉轮台国所在,也是汉代为支持、开拓“丝路”进行屯田的主要基地,在经营建设丝绸之路的伟大工程中,屯田戍边是十分成功的一项政策措施。
屯田遗迹主要散布在克孜尔河畔,距现代居民点多在30公里以外,目前均已沦为盐渍荒漠,这片地区内诸如梯木沁、柯尤克沁、着果特沁、黑太也沁等古代遗址,渠道、田埂遗迹广布,粮食、陶器、汉代钱币等物,调查中均有所见。
为汉王朝统一西域,保证“丝路”畅通建立过功勋的这一屯田基地,目前已成盐土。这是灌溉用水含盐,而又没有适当排盐措施,长期屯垦生产而导致的结果。研究这片地区的遗址遗迹,不仅对汉代以来的屯垦生产、“丝路”走向有意义,对认识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土壤盐化,也很有价值。
自轮台西行,越过一片戈壁,即进入库车绿洲,在今天公路的南侧,彼此距离不远,如二八台等处,还可以见到一些唐代烽墩、戍堡,显示了丝路走向。
库车地区居新疆之中,古称龟兹,是古代西域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东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均设置在此,可见其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汉、唐龟兹国都称延城(唐代又名伊罗卢城),其遗址,即今库车县城东郊之皮朗古城。古城破坏比较严重,从残迹追寻,周长约7公里。考古工作者曾在城内喀拉墩进行发掘,文化遗物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青铜时代。出土石器、骨器、彩陶片、部分铜器及一枚汉代五铢,其上叠压成组大陶瓮,以及莲纹铺地砖、蓝纹砖、筒瓦等,砖的纹饰、形制与唐代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铺地砖近同,共出唐代钱币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开元通宝等,明显为唐代遗存。
库车县城西渭干河畔夏克土尔、玉其土尔古址,伯希和名之为“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沿渭干河东西岸分布。据伯希和发掘出土文物,尤其是其中二百多件汉文文书,结合《唐书·地理志》中有关记录,可以结论为唐代东西柘橛关及柘橛寺故址之所在①。是“丝路”上的一座重要关隘,无论西去疏勒,还是西北向碎叶,均必须通过这一关隘。
古代龟兹王国,统治地域主要在库车、新和、沙雅绿洲及拜城盆地,地理位置冲要,自然条件优越,长时间中一直是西域大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境内不仅古代城镇遗址众多,作为佛教文化的主要中心,也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石窟遗址,举其大者,如拜城县境克孜尔、台台尔、温巴什,库车县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玛扎巴哈、森木塞姆石窟及苏巴什佛寺,新和县境的托克拉克埃肯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遗存。粗略统计,全部石窟可有五百多孔,保存壁画可达2万平方米以上,是研究古代西域佛教思想史、佛教艺术史的瑰宝。
研究表明,古代龟兹可能早到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已经接受佛教。克孜尔石窟开凿的早期石窟,可能就在这一历史时期。进入南北朝、唐、高昌回鹘王朝阶段,佛教大盛,不仅克孜尔,而且库木吐拉等处,都普遍凿窟、造像,形成当时西域地区的一区主要佛教中心②。龟兹石窟,不论从窟形、造像、壁画方面去分析,既可以见到古代印度、犍陀罗、伊朗文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吸收当时中原文化的因素,并在吸收邻近地区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消化融合,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窟形、绘画来,有学者称此为佛教艺术中的“龟兹风”①。而唐代晚期以后,随吐蕃政治势力在公元8、9世纪深入西域,在石窟艺术领域,又明显留下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这些特点,不仅生动体现了“丝路”文化的积极精神,也显示了古代龟兹人民博大的胸襟,积极向上的开放精神,从而为我们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瑰宝。
自库车而西,进入中亚“丝路”干线,主要可见两条。自库车西稍偏南行,沿塔里木河、克孜尔河方向过巴楚、入喀什,翻天山谷道进入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这是《汉书》强调指出的“北道”;而从库车过温宿,沿托什干河西行,过乌什越别迭里山口,抵碎叶镇,有学者称此为“热海道”。汉代陈汤、唐高仙芝进入中亚的路线,走的就是后一条路。这两条路线,在唐代都受到重视,沿途也都有驿馆、烽燧。除西向干线外,自沙雅绿洲向南,沿克里雅河南行,可抵扜弥;自龟兹到姑墨,沿和田河南行,过玛扎塔格山,可达古代于阗。在论及新疆丝路时,这是不可忽视的两条支线,它把“丝路”南、北道干线串连在一起,在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自库车至巴楚途中,沿途可以见到唐代烽燧、驿馆。这方面较显目的遗迹,如柯坪亚依德梯木、阿克沁、都埃梯木,巴楚县的穷梯木、玉木拉克梯木、柯西梯木、泽梯木等,绵延连续至托库孜萨来古城。论者根据出土之唐代文物,结合《唐书·地理志》,认为正是唐代“和平铺”(都埃梯木)、“济浊馆”(亚依德梯木)、“译者馆”(穷梯木)等馆驿的故址②。
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位于巴楚县东北柯坪山派生的一座孤立的石岭上,喀什噶尔河流贯其南。喀什噶尔河上游主支称克孜尔河(汉意“红河”),这一地理位置与《唐书·地理志》所记“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洲,在赤河北岸孤行山”的记录,具体特征可以说完全统一。唐“据史德城”故址在此,可无疑义。
托库孜萨来古城,内外两重,依山势而铺展,是疏勒至龟兹间的军事重镇、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经济宗教中心。伯希和曾经在这里发掘,得到了十分丰富的唐代佛教文物,多量富有希腊化风格的佛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疆考古工作者20世纪50年代也曾在这里进行发掘清理,发现了自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多量文物,佛教塑像,唐代汉文文书,古龟兹文书,丝、毛、棉织物,以及五铢钱铸范,显示了这一古城当年作为“丝路”重镇,在经济上曾具有重要地位③。
关于托库孜萨来古城的上限,林梅村提出应早到汉,可能是疏勒王国的盘陀城,班超曾经在这里戍守。据称,有古城出土佉卢文的直接证明④,这拓宽了人们对托库孜萨来古城的历史认识,但目前还未得到汉代文化层的印证,需要考古工作者更深入的工作。
进入喀什绿洲,古代“丝路”遗迹更为丰富。自巴楚过伽师至疏附县,在疏附东部的盐碱荒漠中,沉落着不少古代村镇、农田遗迹,也见到成一线展开的烽燧。这里不断出土过汉代以来的文物,在英吾斯坦乡内一块农田中,曾出土过一块青石浮雕,具有鲜明的中亚艺术特点。疏附县,伯什克拉木乡,有“汗诺依”古城,出土过多量唐宋时期文物。距城址不远,有一区气势宏伟的佛塔,当地俗称摩尔佛塔,表明这片目前荒无人烟的荒漠,唐代前后,也曾是人烟稠密的所在。
喀什市南郊,有艾斯克沙尔古城。喀什西北乌帕尔艾斯热提毛拉山上,保存着古代佛寺遗迹,佛寺依山势而铺展,气势雄伟,这里出土的贝叶经、佛像残体,都引人注目。
自乌帕尔斜向西北,乌布拉提村西,荒漠中有一座已完全沉没在地下的古代城市,古城墙深埋在地下。笔者1972年在这里试掘,发现过古钱币及多量陶器,城毁于火,据出土文物风格及碳14测年结论,古城毁弃在南北朝时期。由古城更西北走,有谷道可入安集延。
自喀什西北走,在乌恰县境一处荒山中,曾出土过700多枚波斯银币及10根金条,埋藏在一条石缝之中。银币铸于萨珊王朝时期,出土情况表明,在当年“丝路”上,交通往往不靖。维护万里“丝路”交通的安全,是当年的封建统治者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自库车、温宿沿托什干河谷到乌什县,斜向西北,为天山险隘别迭里山口,这也是汉唐时期由新疆进入伊塞克湖、古代碎叶、但罗斯的一条重要路线。沿托什干河西走,柯坪县见托木里克古城、沙牙提古城,县城西北郊苏巴什河口的克斯勒塔格佛寺,乌什县旁托什干河谷的古力瓦克古城、沙依拉木石窟,进入别迭里山口,沿途还保存着古代烽燧。这些遗迹,可以说都显示着“丝路”中道通过别迭里山口以出中亚的具体走向①。
这一路线,自焉耆傍天山南麓西行,自汉迄唐、以至宋元,变化不大。关键在于敦煌至焉耆间,变化不小:或经罗布荒漠到楼兰;或经伊吾过高昌;甚至经过库姆塔格沙漠入高昌,颇为复杂。
西出敦煌,沿疏勒河谷入白龙堆,过楼兰,沿孔雀河谷西走,这是两汉时期进入西域的一条主要路线。出玉门关后,仍然耸立着一段西向延伸的汉代长城。黄文弼20世纪30年代在罗布淖尔北岸发掘过的土垠遗址,世界瞩目的古楼兰城,1979年新疆考古所在孔雀河谷老开屏发掘的汉墓,近年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附近发现的汉代墓葬,沿库鲁克山列布的古代烽燧,既清楚表明这一古道的存在,也显示了古道的走向。
从自然地理条件角度分析,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通路。自疏勒河谷进入白龙堆,沿途戈壁、风蚀土丘林、盐渍荒漠,缺水少草,通行十分艰难。所以选择、开拓这条道路,完全是因为存在匈奴对伊吾、车师的控制。因着这一政治形势,西汉王朝才抉择了这一路线,从而也把楼兰推上了中西交通枢纽的宝座。
楼兰依傍罗布淖尔湖,位于罗布泊西北,目前已沉没在无人的荒漠中。根据新疆考古所在1979~1987年对楼兰城的多次调查试掘资料,楼兰古城位于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古城城墙已在强烈的风蚀中破败不堪。城垣原为不规则的方形,周长1316.5米,总面积10.8万多平方米。从残存土垣看,城垣曾经过多次修筑,一条古河道,贯穿全城,城内遗迹尚可见出官署、寺院、居民住宅区的差别,全城建筑规模最大的所谓官署区,留存至今的三间土屋面积只106平方米。城内建筑基本特点,是当前仍在南疆地区沿用的以木材构架,红柳枝作墙,外涂草泥以为墙壁的建筑风格。新疆考古所在楼兰城内,发掘到汉晋时期残木简60多支,在楼兰城郊,清理过一批汉代墓葬,出土最多的是汉代锦绢、漆器、铜镜,它们明显来自中原地区。另有不少土产精致毛毯、斜纹毛织物,平纹毛布、木器、陶器等。表现了汉晋时代楼兰的社会生活。
根据大量的楼兰出土文物,学术界一般都同意,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活跃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楼兰城,在公元4世纪30年代以后,即逐渐废弃,慢慢沦为荒漠。对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研究者们曾经提出过多方面的分析意见。择其大要,如气候趋于干旱,降水趋少,引起地理环境变化说;高山冰川萎缩,导致河流水量减少说;干旱荒漠地区水系和湖泊不稳定,侵蚀和堆积交替作用使水系成周期性变化,导致楼兰环境改变说;人类活动,导致河道水量改变,使楼兰地区环境恶化等等。各种观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认真分析整个情况,我认为,应该说,“楼兰的兴衰是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变化的综合反映”①,而社会政治因素在其中明显起着关键性作用。
第四纪以来,罗布泊地区一直是干旱环境,因此,楼兰在历史时期中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不能简单地归于气候干旱,而必须考虑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干旱的新疆内陆,一个绿洲的形成、维持、发展,不单须有必要的地理条件,而且要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楼兰作为王国的都城,魏晋时期作为西域长史府驻地,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鲜明存在于这一社会背景,存在着政治、经济、丝路交通方面的实际需要。强大有力的组织力量,科学的水利灌溉设施,辛勤的劳动,人类曾限制了这片地区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发展,并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保持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生态环境。而一旦失掉了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努力,恶劣的自然条件就会使无组织的相对软弱的人群束手无策。认真分析楼兰古城废弃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其中社会交通因素可以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因子。楼兰古城在西域历史上发出过夺目光彩光芒,受到当时中原王朝、匈奴王国、西方各国的关心,无非是因为它在从敦煌到天山南麓的交通路线上曾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两三个世纪的努力,匈奴被排除出西域政治舞台,中原王朝经过伊吾、高昌,沿天山南麓西去的交通线逐渐成了坦途。公元327年,北凉在高昌设郡,立田地县,标志柳中、高昌与河西地区早已联成一体的事实,在政治上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这一情况下,通过白龙堆、楼兰一线,交通条件上的不利因素自然使其在丝路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必然要导致楼兰的衰落。
汉晋时期,为支持楼兰运输干线的运转,克服恶劣自然条件的影响,汉、魏晋王朝曾集中力量在楼兰地区屯田、西域长史府,作为当时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驻节在楼兰,强大的组织力量,使楼兰的自然地理环境虽称恶劣,但还是维持着平衡。从大量出土的具体表现当年屯田事业的文书中,可以看到西域长史府凭藉着强有力的水利灌溉事业,运营着楼兰地区以屯田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丝路供给、丝路安全保障,应该说,都凭藉着这一生产事业的支持。楼兰故址出土文书资料,最晚止于前凉王朝继续使用的(西晋)建兴十八年(330年),不见较其更晚的纪年文字。这说明,在公元330年或其稍后,楼兰古城作为西域长史府的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使得楼兰丧失了它在“丝路”干线上中继站的重要地位,与政治、军事、商业交通、邮传、屯田等有关的一套相应组织会随之撤离、转移,人口会随之大大减少,有组织地对罗布荒漠自然环境的改造努力会随之急剧减弱,这对楼兰绿洲生命的维持,无疑会是严重的一击。没有了人类有组织的努力,风沙侵袭,河流改道,土地积盐等可以克服的自然困难会变得无法克服,楼兰绿洲环境会日益恶化。这一切,无疑会导致楼兰绿洲的最后毁灭。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楼兰古城的兴起、废败,与中原王朝对西域大地政治、经济的控制、管理,与丝路路线的组织、建设密切相关。
可以帮助说明楼兰碛道之废弃绝不是、或主要绝不是自然原因还有一个相反的实例。公元7世纪中叶,割据吐鲁番的高昌王国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结盟,极力阻抑唐王朝进入西域,控制了通过吐鲁番来去的“丝路”大道。焉耆王龙突骑支就曾建议重开通过孔雀河谷经过故楼兰地区、白龙堆入敦煌的“碛路”,这实际是与高昌竞争把握“丝路”权益的措施,曾得到了唐王朝的支持。这一计划,随唐王朝统一高昌而自然放弃,但却表明了一个事实:通过楼兰地区的“碛路”,虽属困难,却并不是不能通行的,而通行与否,社会经济、政治因素,起着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楼兰到天山南麓的路线,是走库鲁克山南麓,孔雀河谷水草丰沛地带。
自楼兰古城西北行,还可以见到几座烽燧遗迹,兀立在荒漠之中。
距楼兰古城约80公里,在孔雀河北岸一道低矮山脊上,俗称老开屏,1979年,笔者曾主持发掘过一座孤立的汉代墓葬,出土过汉锦、汉镜及多量木器①。
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旁,近年发现一区最晚到汉晋的古墓群,出土大量毛毯、毛纺织物、木器,也见到汉代织锦②。
尉犁县西北约60公里,位于库鲁克山南麓一剥蚀土丘上,还保存古烽一座,烽墩约4米见方,高3米左右,土坯叠砌。其下见大量红陶片、烽砟③。
自此更前行,即可抵达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西域都护驻节地乌垒城。
从伊吾方向进入天山南麓,是一条更重要、自然地理条件也稍好的路线。
汉代伊吾城址,至今未得考古确定,估计当在今哈密市附近。这里泉水丰沛,农业生产条件优良。在哈密市内,近年发现不少古代遗址,哈密火车站附近就是一片相当密集的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古代墓地,墓中出土相当丰富的彩陶。
在哈密火车站基建中,也有过出土文物的报道。
自哈密西行,四堡乡,现存拉甫乔克古城,有说为唐“纳职县”所在。
自拉甫乔克过五堡,斜向东南,戈壁中尚存一区古堡遗址,沿白杨沟水,沿途也见古代烽燧断续相继,这显示了自伊州入西州(从哈密绿洲进入吐鲁番盆地)的一条径道。
吐鲁番盆地中,七克台、汉墩、连木沁、煤窑沟、七泉湖、木尔吐克萨依、乌江布拉克、胜金口、交河南北、野木什、阿拉沟口等许多地点,都见到古代烽燧、戍堡,由于欠缺深入的工作,对有关遗迹的准确时代,及通过它们所标示的古代路线及不同历史时期中路线的变化,目前还难以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高昌、交河故城,是这一线路中大家都比较注意的两座古城。
高昌古城是古代新疆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玄奘西去求经,麟德元年(664年),波斯王子泥涅师自长安返国,都曾在这里停息。
高昌古城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可分外、内、宫城三重。这是长时期发展的结果,记录着历史变化的痕迹。
外城略呈方形,周长5000多米,城垣基址厚达12米,城墙残高至今仍有11.5米,夯土版筑,部分地段用土坯修补。有马面,城门从现存遗迹分析,每面至少有两座,在城郊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记录了唐西州城有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可以印证。
内城居外城正中,西、南两面城墙大部分保存下来,北面仅存部分基址,东墙全毁,复原周长约3000多米。
《隋书》称高昌王国“其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隋唐时期一步当于6尺4寸。据出土唐尺,一尺长度为29厘米,6尺4寸当1.856米,1840步,则当于3415米,与现存中城范围相近,故而可以肯定目前中城遗址实际就是高昌王国的都城所在。其建城时间较外城为早。
高昌王国的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俗称“可汗堡”。堡内塔柱至今仍高十多米,其旁,是一组包含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地下庭院、暗燧的大型建筑,燧道宽达3米多。宫城墙基本完好,高达6米,南向开门,门阙地基清晰。其间是宽达3米的门道。宫墙东侧,曾出土“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表明了当年高昌王室寺院的所在。
至于公元9世纪以后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从现存遗迹看,范围已不很明确,南北朝时期高昌王国宫城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是否被继续使用,目前还无充分资料作出明确结论。有的学者提出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是在现存外城的北部,处内、外城北墙之间,即外城北墙为宫城之北墙,而内城北墙即宫城南墙,主要根据是这一范围内目前保留了不少高出地面三四米的高土台,建筑规模宏伟,故可能是回鹘王族的宫廷所在,可以聊备一说。
外城西南部有一大型寺院,寺门东向,东西长约130米、宽85米,占地面积1.1万多平方米,寺院中央台基上有一多层台的土坯塔柱,周围高墙回护,是全寺的主体建筑。两厢和塔庙是高大的重楼建筑。规模十分宏伟。
寺院附近有密集的建筑遗址,建筑物多是夯土为墙,土坯起券,作长筒形纵券顶,这种建筑方法吐鲁番地区至今仍然使用。
外城东南部分也有一小型寺院,土坯砌就的土塔犹存,从壁画风格看,时代较西南大寺为晚。
自高昌建城至公元13世纪中叶海都叛乱(1279),攻灭高昌,古城被毁,前后历时1000年以上,作为高昌回鹘王都,历时也近500年,高昌在新疆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
高昌城外北、西北郊是晋、唐时期的墓区。这里埋葬着同一历史阶段内高昌各种社会身份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发掘古墓葬四百多座,出土过大量古代珍贵文书、丝绸文物等,是研究高昌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及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
自高昌古城斜向西北,距约50公里,是交河故城。不论是高昌、西州,还是高昌回鹘,北向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或西向焉耆,这里均是交通要隘,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历史上一直也是吐鲁番地区的重要政治军事中心。西汉时为车师前国的王都。《汉书·西域传》称:“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域下,故号‘交河’。”交河故城坐落在两河之间的一区土岛上,这段文字,是对古城形势的准确描述,也说清了古城得名的由来。
古城所在土岛南北长1650米,最宽处约300米,古城位于土岛之南半部,建筑遗迹南北长达1000米,宽与岛之宽同。说为古城,因坐落在高数十米(最高30米)的土岛上,四周峭壁悬岩,形势天成,可以凭险据守,所以并无防御性质的城墙。
入城门道有两处:南门是主要进出口,但具体建筑结构已破坏,只存门道豁口;东门保存较好,劈岩而成门道,安设门额的方形榫洞也依然可见,自门道到河底高达20米,陡险曲折。入门处有防御设施,堪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城内建筑遗址总面积,初步测量约22万平方米,大致可见出寺院、民居、衙署和官邸等性质不同的建筑遗迹。
纵贯全城南北方向有一条长约350米,宽约10米的大道。大道直通城北一区大型寺院,建筑面积达5100平方米,在这区重楼建筑的方形大院内,塔柱犹存。城内寺院建筑多为这种方形院落,入室有神坛或塔柱,主要分布在主干道以西。
自这一主干道中部向东为另一干道,通向东门。主干道以东,东西干道以南,这一区域内多大型院落,常是衙署、官邸所在。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全城内唯一见砖、瓦的大型建筑,即是这一区内附有地下室的气势相当宏大的院落。
东西干道以北,建筑相当密集,门庭较小,当是一般居民住宅。
交河故城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古城遗址之一,建筑富有特色:其一,街道两旁是高厚土墙,临街不见门窗,纵横交错的巷道通过土墙将庭院分隔为坊曲,穿过街巷,进入坊墙,才能到达民户大门。
其二,土崖土质致密,所有建筑均挖地为院,隔梁为墙,掏洞成室。街巷也是挖地而成的路沟,高度不足,则以挖地所得泥土夹板夯筑。房顶主要由土墙承重,所用木料不多,这是适应新疆地区干燥少雨的特点而形成的生土建筑风格,极大地减省了木材及能源的消耗,是值得总结、发扬的优良传统。
交河故城始建在西汉以前的车师前部。西汉前期,是车师王都所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汉王朝在吐鲁番地区设戊己校尉管理屯戍,设交河壁,派驻吏卒。晋十六国,吐鲁番地区为高昌王国,交河为王国—郡。由于地位重要,每每派王子驻节交河。公元640年,唐王朝统一高昌,设西州、交河为西州属县。因为这里形势险要、又控制着天山南北交通的一处隘道,在军事上明显具有重要地位。自交河故城南出盐山之阙口,目前仍可见唐代烽墩。自盐山南缘斜向东南,经布干土拉古城可抵高昌;斜向西南,经大墩子、屋威梯木古城堡入托克逊,为唐代丝路“银山道”干线;稍偏西北,入阿拉沟口,也见到唐代古堡,有山道可入巩乃斯河、于尔都斯草原。
交河故城西,存石窟寺一区。足以展示“丝路”文化特色的佛教遗迹,除交河城外石窟外,在吐鲁番地区,还有桃儿沟、吐峪沟、胜金口、柏孜克里克等多处。唯蒙受种种人为的、自然的破坏,保存状况堪忧。柏孜克里克,算是目前保存状况较好的一区,这里稍作介绍。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坐落在高昌城北火焰山中,踞火焰山主峰北坡,下临木头沟水,环境清幽。唐《西州图经》称此为“宁戎窟寺”。现存洞窟83个,可以见出毗诃罗窟、支提窟、隐窟、僧房之别。保存壁画洞窟约只50%,大多残毁比较严重。洞窟始建于高昌王国时,唐、高昌回鹘时期臻于繁荣,是高昌回鹘时期的王室寺院之一。近年维修柏孜克里克,文物工作者曾在早期废窟中发现回鹘文、粟特文、汉文、梵文的残经及世俗文书,如晋人写本《汉书·西域传》残页,写于高昌王国建昌五年(559年)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鸠摩罗什译本),宋刻本《金藏》残帙,回鹘文雕版印刷品残页,西夏文雕刻印本残页,粟特文手写本残卷等。其中一件金箔包装纸,来自宋代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东朝西的一家纸铺,它专门制作、销售“佛经诸般金箔”,希望主顾“辨认不误”,是宋代杭州纸铺的广告商标,也很好地说明了在11、12世纪时,高昌回鹘王朝与宋王朝的商业贸易情况。清理工作中还发现十分宏伟的木构建筑材料,如斗栱等物(其中一件,栱径75厘米、斗长21厘米)。表明唐代,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在依岩开凿的洞窟外面,有十分高大的殿堂、回廊。
柏孜克里克现存壁画,主要属于高昌回鹘时期。在长方形纵券顶的洞窟内,绘佛传故事,展示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第33窟后壁,一幅表现佛涅槃后众弟子举哀的图像,艺术表现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民族的佛弟子,肤色各异,发式、服装不同,可以多少反映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西域大地,人种各异、民族众多的社会生活图景。
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画面完整、色泽鲜丽的高昌回鹘国王、王后供养佛的图像,是壁画中的珍品。主要部分已为勒柯克割剥运往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
“丝路”自吐鲁番沿“银山道”西去,下一站主要为焉耆王国。关于“银山道”的具体线路,据考古调查资料,出托克逊后,应走苏巴什沟,沿途有水草。地理形势、山泉,与玄奘当年留下的记录可以呼应。出沟,至库米什,进入焉耆盆地。唐代在这里设置过焉耆都护府和焉耆镇,目前坐落在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达沁古城,可能就是汉焉耆国都员渠城,也是唐焉耆都督府和焉耆镇城之所在。
博格达沁古城是焉耆盆地内建筑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周长3000多米,城墙基垣完整,保存稍好地段残高4米。城内建筑遗迹多已坍塌。最大一区周长达143米,城内地表采集到汉五铢、唐开元通宝、波斯银币等,其他金银饰物、料珠、陶器亦常见。古城附近见较大型汉唐墓葬,出土过汉代铜镜、包金铁剑、金质龙纹带扣。
与博格达沁古城相去不远的锡克沁、明屋佛寺遗址,曾经出土过多量佛像。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界,佛教史学者关注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就出土在明屋佛寺之中。
焉耆西去,最重要的站点是轮台。这里是汉轮台国所在,也是汉代为支持、开拓“丝路”进行屯田的主要基地,在经营建设丝绸之路的伟大工程中,屯田戍边是十分成功的一项政策措施。
屯田遗迹主要散布在克孜尔河畔,距现代居民点多在30公里以外,目前均已沦为盐渍荒漠,这片地区内诸如梯木沁、柯尤克沁、着果特沁、黑太也沁等古代遗址,渠道、田埂遗迹广布,粮食、陶器、汉代钱币等物,调查中均有所见。
为汉王朝统一西域,保证“丝路”畅通建立过功勋的这一屯田基地,目前已成盐土。这是灌溉用水含盐,而又没有适当排盐措施,长期屯垦生产而导致的结果。研究这片地区的遗址遗迹,不仅对汉代以来的屯垦生产、“丝路”走向有意义,对认识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土壤盐化,也很有价值。
自轮台西行,越过一片戈壁,即进入库车绿洲,在今天公路的南侧,彼此距离不远,如二八台等处,还可以见到一些唐代烽墩、戍堡,显示了丝路走向。
库车地区居新疆之中,古称龟兹,是古代西域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东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均设置在此,可见其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汉、唐龟兹国都称延城(唐代又名伊罗卢城),其遗址,即今库车县城东郊之皮朗古城。古城破坏比较严重,从残迹追寻,周长约7公里。考古工作者曾在城内喀拉墩进行发掘,文化遗物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为青铜时代。出土石器、骨器、彩陶片、部分铜器及一枚汉代五铢,其上叠压成组大陶瓮,以及莲纹铺地砖、蓝纹砖、筒瓦等,砖的纹饰、形制与唐代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铺地砖近同,共出唐代钱币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开元通宝等,明显为唐代遗存。
库车县城西渭干河畔夏克土尔、玉其土尔古址,伯希和名之为“都勒杜尔·阿胡尔”遗址沿渭干河东西岸分布。据伯希和发掘出土文物,尤其是其中二百多件汉文文书,结合《唐书·地理志》中有关记录,可以结论为唐代东西柘橛关及柘橛寺故址之所在①。是“丝路”上的一座重要关隘,无论西去疏勒,还是西北向碎叶,均必须通过这一关隘。
古代龟兹王国,统治地域主要在库车、新和、沙雅绿洲及拜城盆地,地理位置冲要,自然条件优越,长时间中一直是西域大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境内不仅古代城镇遗址众多,作为佛教文化的主要中心,也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石窟遗址,举其大者,如拜城县境克孜尔、台台尔、温巴什,库车县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玛扎巴哈、森木塞姆石窟及苏巴什佛寺,新和县境的托克拉克埃肯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遗存。粗略统计,全部石窟可有五百多孔,保存壁画可达2万平方米以上,是研究古代西域佛教思想史、佛教艺术史的瑰宝。
研究表明,古代龟兹可能早到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已经接受佛教。克孜尔石窟开凿的早期石窟,可能就在这一历史时期。进入南北朝、唐、高昌回鹘王朝阶段,佛教大盛,不仅克孜尔,而且库木吐拉等处,都普遍凿窟、造像,形成当时西域地区的一区主要佛教中心②。龟兹石窟,不论从窟形、造像、壁画方面去分析,既可以见到古代印度、犍陀罗、伊朗文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吸收当时中原文化的因素,并在吸收邻近地区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消化融合,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窟形、绘画来,有学者称此为佛教艺术中的“龟兹风”①。而唐代晚期以后,随吐蕃政治势力在公元8、9世纪深入西域,在石窟艺术领域,又明显留下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这些特点,不仅生动体现了“丝路”文化的积极精神,也显示了古代龟兹人民博大的胸襟,积极向上的开放精神,从而为我们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瑰宝。
自库车而西,进入中亚“丝路”干线,主要可见两条。自库车西稍偏南行,沿塔里木河、克孜尔河方向过巴楚、入喀什,翻天山谷道进入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这是《汉书》强调指出的“北道”;而从库车过温宿,沿托什干河西行,过乌什越别迭里山口,抵碎叶镇,有学者称此为“热海道”。汉代陈汤、唐高仙芝进入中亚的路线,走的就是后一条路。这两条路线,在唐代都受到重视,沿途也都有驿馆、烽燧。除西向干线外,自沙雅绿洲向南,沿克里雅河南行,可抵扜弥;自龟兹到姑墨,沿和田河南行,过玛扎塔格山,可达古代于阗。在论及新疆丝路时,这是不可忽视的两条支线,它把“丝路”南、北道干线串连在一起,在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自库车至巴楚途中,沿途可以见到唐代烽燧、驿馆。这方面较显目的遗迹,如柯坪亚依德梯木、阿克沁、都埃梯木,巴楚县的穷梯木、玉木拉克梯木、柯西梯木、泽梯木等,绵延连续至托库孜萨来古城。论者根据出土之唐代文物,结合《唐书·地理志》,认为正是唐代“和平铺”(都埃梯木)、“济浊馆”(亚依德梯木)、“译者馆”(穷梯木)等馆驿的故址②。
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位于巴楚县东北柯坪山派生的一座孤立的石岭上,喀什噶尔河流贯其南。喀什噶尔河上游主支称克孜尔河(汉意“红河”),这一地理位置与《唐书·地理志》所记“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洲,在赤河北岸孤行山”的记录,具体特征可以说完全统一。唐“据史德城”故址在此,可无疑义。
托库孜萨来古城,内外两重,依山势而铺展,是疏勒至龟兹间的军事重镇、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经济宗教中心。伯希和曾经在这里发掘,得到了十分丰富的唐代佛教文物,多量富有希腊化风格的佛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疆考古工作者20世纪50年代也曾在这里进行发掘清理,发现了自南北朝到唐宋时期的多量文物,佛教塑像,唐代汉文文书,古龟兹文书,丝、毛、棉织物,以及五铢钱铸范,显示了这一古城当年作为“丝路”重镇,在经济上曾具有重要地位③。
关于托库孜萨来古城的上限,林梅村提出应早到汉,可能是疏勒王国的盘陀城,班超曾经在这里戍守。据称,有古城出土佉卢文的直接证明④,这拓宽了人们对托库孜萨来古城的历史认识,但目前还未得到汉代文化层的印证,需要考古工作者更深入的工作。
进入喀什绿洲,古代“丝路”遗迹更为丰富。自巴楚过伽师至疏附县,在疏附东部的盐碱荒漠中,沉落着不少古代村镇、农田遗迹,也见到成一线展开的烽燧。这里不断出土过汉代以来的文物,在英吾斯坦乡内一块农田中,曾出土过一块青石浮雕,具有鲜明的中亚艺术特点。疏附县,伯什克拉木乡,有“汗诺依”古城,出土过多量唐宋时期文物。距城址不远,有一区气势宏伟的佛塔,当地俗称摩尔佛塔,表明这片目前荒无人烟的荒漠,唐代前后,也曾是人烟稠密的所在。
喀什市南郊,有艾斯克沙尔古城。喀什西北乌帕尔艾斯热提毛拉山上,保存着古代佛寺遗迹,佛寺依山势而铺展,气势雄伟,这里出土的贝叶经、佛像残体,都引人注目。
自乌帕尔斜向西北,乌布拉提村西,荒漠中有一座已完全沉没在地下的古代城市,古城墙深埋在地下。笔者1972年在这里试掘,发现过古钱币及多量陶器,城毁于火,据出土文物风格及碳14测年结论,古城毁弃在南北朝时期。由古城更西北走,有谷道可入安集延。
自喀什西北走,在乌恰县境一处荒山中,曾出土过700多枚波斯银币及10根金条,埋藏在一条石缝之中。银币铸于萨珊王朝时期,出土情况表明,在当年“丝路”上,交通往往不靖。维护万里“丝路”交通的安全,是当年的封建统治者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自库车、温宿沿托什干河谷到乌什县,斜向西北,为天山险隘别迭里山口,这也是汉唐时期由新疆进入伊塞克湖、古代碎叶、但罗斯的一条重要路线。沿托什干河西走,柯坪县见托木里克古城、沙牙提古城,县城西北郊苏巴什河口的克斯勒塔格佛寺,乌什县旁托什干河谷的古力瓦克古城、沙依拉木石窟,进入别迭里山口,沿途还保存着古代烽燧。这些遗迹,可以说都显示着“丝路”中道通过别迭里山口以出中亚的具体走向①。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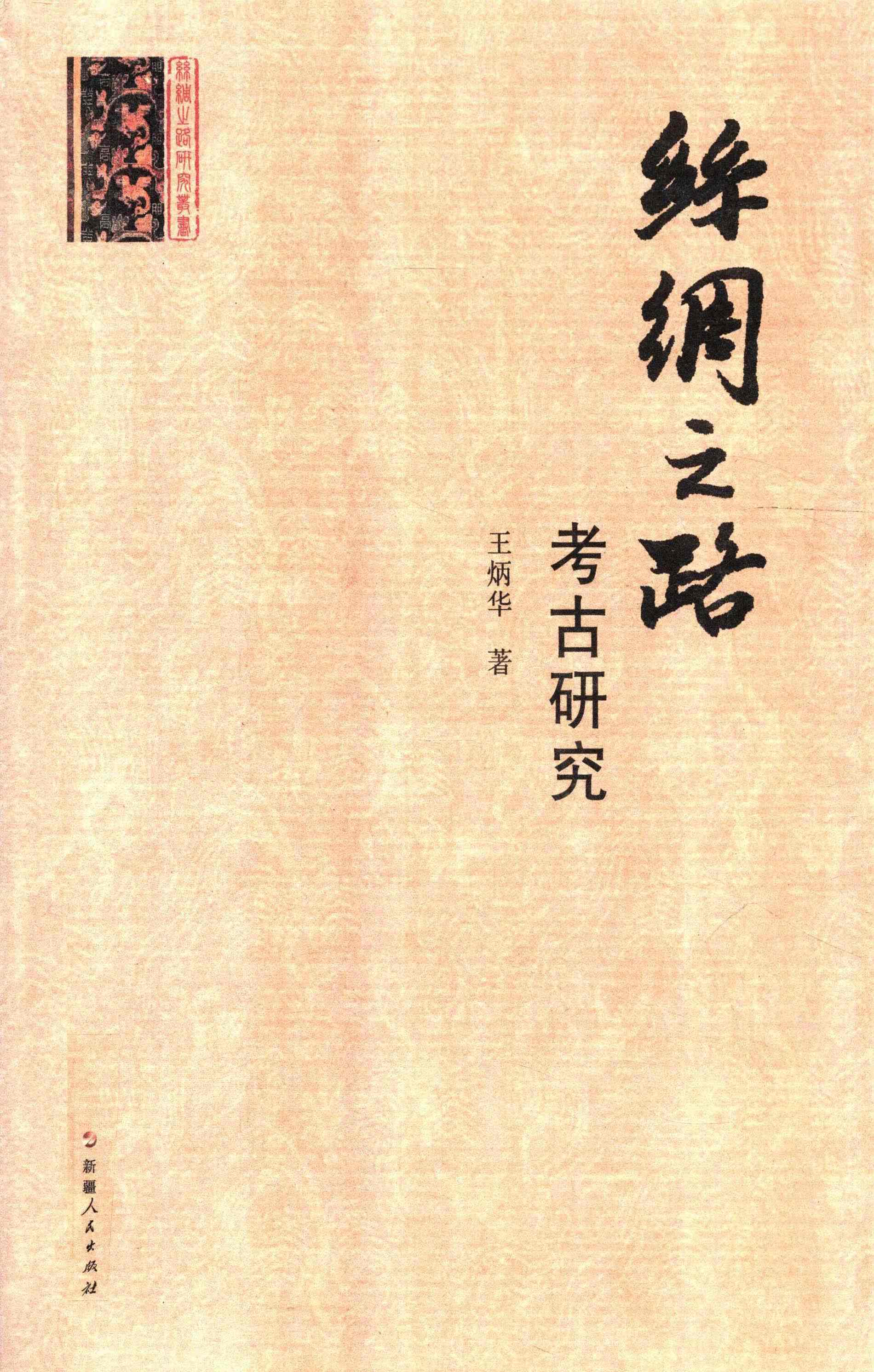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帷幕初揭时,就策划、设计并组织出版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应该说,它在当年,是紧密呼应时代要求而出版的一套好书。在这套丛书中,我应命承担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当年交出的,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只是将手边积淀了丝路文化痕迹的部分论文,编集在一起,交了卷。本书内容包括: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唐西州白水镇初考;尼雅考古与精绝文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