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第一节 西部地区人居生态环境的古今演化
一、石羊河流域古今生态的演化
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是一形胜之地:“天梯亘前,沙河绕后,左有古浪之险,右有西山之固,东控宁夏,南距黄河,西连番部北际沙漠”,是谓重地。在西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开设武威郡,辖区较大。清朝时设凉州府,下辖镇番(今民勤县)、武威、永昌、古浪、平番(今永登县)五县。今日之石羊河流域行政设置与清代相比,有所变动,设有金昌市(辖1区1县即金川区和永昌县)面积9593平方千米,武威市(辖1区3县,即凉州区和民勤县、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面积33000平方千米。总计面积为42593平方千米。
清代的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相当好,特别是山体植被堪称是被松柏,丰草所覆盖,有的是终年积雪下流成川。根据《大清一统志·凉州府志》所记载的十多座山,在清朝还是四季常青,郁郁葱葱。
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河流纵横、水资源丰富、湖泊星罗棋布,在《嘉庆重修一统志》中记载了众多河湖的情况,了解历史上的河湖状况可以使我们的以古察今去认真思考历史变迁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冷静深思生态环境的变化带给我们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什么,人们应该如何科学地处理人与环境的协调问题,因小失大、舍近求远、鼠目寸光会带来难以弥补的生态灾难,在这里我们根据有关古籍的记载,再现石羊河流域昔日风采,天、地、人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和谐的景象。
(一)石羊河流域山体植被状况
青山:其位置在武威县东二百五十里、山多松柏、冬夏常青。
松山:其位置在武威县东三百一十里,上多古松。
天梯山:其位置在武威县南八十里,《魏书》记载太延五年议讨沮渠牧、李顺等言,自围河以西,至于姑臧志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至丈余,春夏消释下流成川,引以灌溉。
青山:其位置在武威县南,《寰宇记》记载山下有湫(大水池)甚广,人触之,立有风雹暴至。看来这个大深潭还十分神秘。
姑臧南山:其位置在武威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西连永昌县界。《汉书·地理志》记载姑臧县南山、在县一百三十里。《寰宇记》记:番和县南山一名天山、又名雪山。山阔千余里,其畜称是、连互数郡界、美水丰草。尤宜畜牧。葱岭以东,无高于此。《引都司志》云:姑臧南山在凉州卫西南一百二十里,又雪山在永昌卫南一百八十里、怀凉州南山相连、夏积雪不消、亦名祁连山,按此山西连山丹甘州台肃之祁连山。以及塞外之雪山脉皆连互。名多互称。故杜佑《通典》曰:自张掖而西至于庭相去三千五六百里。而山皆周编。
西山:其位置在武威县西二十里,县志载,山有乐泉、可以疗病。
第五山:其位置在武威西一百三十里,炭山堡西南,《隋书·地理志》云姑臧县有第五山。《寰宇记》载第五山夏函霜雪,有清尔藏林、悬崖修竹,自古为隐士所居。
苏武山:其位置在镇番县东南三十里。山右有苏武庙,谷传为苏武牧羊处。
燕支山:其位置在永昌县西,西接甘州府山丹县界。《隋书·地理志》载番和(今永昌县)有世支山,即此。《引都司志》载松山在永昌卫西八十里,又名大黄山焉支山,一山而连跨数处,山在高古城北一里,广二十里,山产大苋,又产松木,故以为名。
里松林山:其位置在古浪县东四十五里,山上多松。
柏林山:其位置在古浪县东南七十五里,山上多柏树。
西山:其位置在古浪县西五十里,亦名雪山。
白岭山:其位置在古浪县西。《寰宇记》云在昌松县西南,山顶冬夏积雪,望之皓然,寒气异于余处,深冬人绝引路,鸟飞不下。
万花山:其位置在平番县(今永登县)西南?《庄浪汇》记载山下有泉暖。
棋子山:其位置在平番县(今永登县)西南二百里,相连者为皋子山,道险林密,为番人巢穴。
大松山:其位置在平番县(今永登县)东北一百二十里,接兰州府兰县界,山多大松。其北又有小松山在阿堡十五里。
(二)石羊河流域的河湖分布状况
石羊河流域的河流、湖泊在清代以前水源相当丰富,单单泉水的分布就多达5万多处,水是生命之所在,怪不得人们把武威称为“金张掖,银武威”,在这里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及有关书籍的记载把清朝时期的水系状况作了一概述。
谷水(即石羊河,又称谷水)《嘉庆重修一统志·甘肃》载,在武威县东,该河流“经东北镇番县(今民勤县),东出边海,亦名武始泽,即今三岔河也”。清代的三岔河,也就是今日之石羊河。
《汉书·地理志》记载:“姑臧县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汉时的姑臧,就是今日的武威市。汉代的武威县,在今日之民勤县东北50余公里处。
《魏书·地形志》载:“武威郡襄城县(今民勤县境)有武始泽。”
《水经注》卷40载:“都野泽,上承姑臧武始泽。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迳姑臧县(今武威)故城西,东北流,水侧曰灵渊池。??泽水又东北流迳马城东,谓之马城河。又东北与横水合,水出姑臧(今武威)城下,侧城北流,注马城河,又东北清涧水入焉。又与长泉水合。又东北迳宣威县故城(在今民勤县西南石羊河畔)南,又东北迳平泽、晏然二亭东。又东北迳武威县故城(今民勤县东北约50余公里处)东。届此水流两分,一水北入休屠泽,一水又东迳一百五十里入猪野。”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凉州府》引旧志的说法为:三岔河(今石羊河)在凉州卫东北三十里,上源曰金塔寺山口涧,源出天梯山,北流止南把截堡(今武威市南)西分二流,一支北流经卫城西,又屈经城北,而东流至三岔堡。一支东北流经南把截堡北,又东经卫城东到三岔堡,与西一支合,又合杂木山口涧,是谓三岔河,至镇番卫南分为二小河,经卫之西南溉田,又东此,经卫东三十里,又北汲者为海。
清代的三岔河,是汇诸山涧之水而成,大致有蹇占山口,土弥干山口,金塔寺山口,杂木山口,苋羊川山口。
从汉至清朝,我们可以看到石羊河即历史上的谷水,其危端湖水的变化。根据《汉书·地理志》武威县下注曰:“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野泽”。这里的“古文以为猪野泽”是指《尚书·禹贡》篇所说的“原隰底渍”,至于猪野泽即汉时休屠湖已经一分为二了。上到《水经注》谷水即到武威县后,一入休屠泽,一入猪野泽,可知大湖已经一分为二了。而即到了清代,石羊河的尾端湖由原来的两个现在变成了一个,即清代的鱼海亦名哈喇伯。
以上为清代所述的石羊河的正流,那么,其支流也是不少的。
五涧水,在武威县(今武威市)东。
《水经注》清涧水,俗谓之五涧水,出姑臧(今武威)城东,西北流注马城河,合有杂林涧,工凉州卫东南七十里,源出天梯山,北流经古城堡西,又东北经大河驿东,又北合苋羊川,折而西北流,入三岔河。
苋羊川,东卫东南一百七十里,源出古浪雪山,有灌溉之利。
土弥干川水,在武威县(今武威市)西南五十里。《寰宇记》:番和县(今有弥干川,古匈奴为牧放之地,鲜卑语髓为土弥干,言此川水肥美如髓故名。
《行都司志》:土弥干山涧,在凉州卫西南七十里,即五涧水浴水,又有蹇占山口涧,在卫南一百五十里,土弥干山涧的卫西南大口子,北流经卫西,又东北流,左合蹇占山涧,入三岔河。该山涧出自户为南雪山。
长泉水,在古浪县北,《水经注》:长家水出姑臧(今武威市)东,次县(今古浪县北)西北,历黄河阜而东北,注马城河,《旧志》:今有河,东凉《旧志》州卫东北五十里,源出塞外红泉,西流入边,折而北流入三岔河。
除上述外,当时凉州府的平番县(今永登县、已归兰州市管辖)也有数水发源,但都向东南流入黄河,这里不再赘述。
还需提及的是:还有古浪河和水磨川二水各自渚为海,并非流入石羊河。古浪河在汉代叫松陕水,《汉书·地理志》武威郡苍松县(今武威市东南)南山,松陕水所出,北至揟次(今古浪县北)入海,《旧志》云:今名古浪水,在古浪所南八十里,有二源,一出分水岭,一出所东南山,俱北流至城东合为一。又东北流出边,按此水由土门堡出边,又东北百余里猪为泽,清代谓其泽为白海(在今内蒙古界)。
水磨川水,一名云川,自永昌县西东北流,经新城堡北,水磨堡西,又东流经永昌城北,又东北经凝远堡西,北流出边,经旅界,猪为大泽,蒙古名河喇鄂模(在今内蒙古境)又有考耒河,在县西南八十里,东北流入水磨川,按舆图,此水流二百余里,又五百余里许,猪于泽其长与三岔河相等。
从今天看来,水磨川水和古浪河下游的尾端湖泊已经消失。
牧羊川,在永昌县北三十里,文车泽,在威县东,《元和志》在姑臧东三十里。
叙述了清代时期凉州的山、水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湖泊的状况和分布:
休屠泽,《尚书·禹贡》谓其为猪野泽,《汉书·地理志》言“武威县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野泽”。《水经注》谓武威北有休屠泽,俗谓之西海,其东有猪野泽,俗谓之东海,通谓之都野。到了清代,名称变为白亭海,《引都司志》:白亭海一名小阔端海子、五间涧谷水流入此海,《旧志》白亭海即猪野泽。三岔河自镇番(今民勤县)东北流出边,又三百余里猪为大泽,方广数十里,俗名鱼海子,蒙古名哙嗽鄂模,即古休屠泽、但《水经注》谓其东别有猪野泽、与汉《志》异。
沙喇泊。在休屠泽西二百余里,水磨川自凝无堡北出边,注入其中,方广三四十里。然而这个湖泊已在地图上见不到了,前文方水磨川水与三岔河水的长短不相上下,果不虚言,因为水磨川水发源于冷龙岭东,均向北流去,三岔河之水之泽谓沙喇泊,且方沙喇泊在休屠泽西二百里,就文献记载而言,此湖的纬度起码与镇番县(今民勤县)相同。
昌凝湖,在旅南界,《旧志》直永昌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凝远堡北四十里,东至镇番县(今民勤县)一百五十里,多水草杨木,明季青马都游牧于此。
长草湖,在旅界凝罗山北。
摆方湖,在旅界上平番县(今永登县)东北边外。
马跑泉,在旅界,直永昌县(今永昌县)北三百十里,又高泉、平泉、赤纳泉皆在旅界。
双泉,在旅界,直镇番县(今民勤县)西北三百四十里,泉有三处,又有乱井儿亦在旅界。
查阅地图,小的湖泊且不说,清朝时期还可看到的比较大的湖泊,今日已从地图抹去了。
鸭儿湖,在镇番县(今勤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中多芦草。又天池湖在县北二十里。......
柳树湖,在镇番县(今民勤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共溉田二千四百九十八顷。
昌凝湖,在永昌县(今永昌县)东北一百二十里。绥远堡北四十里。东至镇番县(今民勤县)一百五十里。中多小草杨木。
摆方湖,在平番县(今永登县)东北塞外、庄浪景记湖在河莹迤北二百八十里。
灵泉池:在武威县《水经注》:武始泽迳姑臧城(今武威市)西,东北流,水侧有灵渊池。王隐《晋书》曰:汉末博士敦煌侯瑾,善内学,语弟子曰:凉州城西泉水当竭......寰宇记:灵泉池在姑臧县南城中。
天池,在武威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山上,四时不涸。
鱼池,在武威县东北一里,阔二百里,周围有湖、草树密,为公余游息之地。
小池,在镇番县(今民勤县)东四十里,俗呼龙潭。
龙潭泉,在平番县(今永登县)、水旱无盈缩。
近城泉,在武威县东五里。又黑水林泉在县东三十里、红水泉在县东五十里,水色微红。海藏寺泉,在县北十里,以上四泉皆流入沙河,溉田甚广、又然的泉在县北三十里。
暖泉,在武威县东一百二十里,又有明白泉在永昌县西三十里,二六雾出、四时常温、东北流注水磨川。又一在永昌县(今永昌县)东三里、一在县北一里。
一碗泉,在永昌县西四十里。又鹿泉,在县西北一百里。
双泉,在永昌县(今永昌县)西北二百里,亦名双井。又草茅泉在县北六十里,矮鹿泉在县东北七十里。
马跑泉,在永昌县(今永昌县)北三百一十里,又育梁泉在县北四百三十里,平泉在县东北二百六十里,芝纳泉在县东北五百里,皆在边外。
青羊泉,在平番县(今永登县)东五十里,又四眼泉,在县东南七十里,犁耙泉在县西四十里。
龙泉,在平番县(今永登县)......。
罗锡泉,在平番县(今永登县)北七十里,泉周七里。冬夏不涸。又沙泉,在县东北八十里,又家保界有沟泉,溉田甚广。
河井,在镇番县(今民勤县)西北二十五里、青池西边外,又有井在县西北二百二十里,小白盐池边,甘洌可饮,又腻古井在县西二百里边外。
三井,在镇番县(今民勤县)西北二百四十里边外,有泉三外,又有乱井儿在县西北一百七十里边外,有泉数处,因名。
(三)石羊河流域古今生态变化的若干方面
如今的石羊河与历史上的石羊河相比,发生了令人可怕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猪野泽,休屠泽彻底消失了。早在西汉前期,猪野泽和休屠泽曾经是匈奴休屠王的驻牧地,《禹贡》和《汉书·地理志》均有记载。据说,由石羊河注入的湖泊东西长120公里,南北最宽处达50公里左右(吴晓军:《西北生态启示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32页)——但是,随着历史的变化,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夕:
由于石羊河下游诸湖泊水源缺乏甚至消失,就变成湖荒地和自然绿洲,其中部分荒地被开垦成灌溉农田,有些低洼之地成为蓄洪区。(冯
绝武:《区域地理论文集》,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349页)。距民勤县城北90公里的青土湖,作为石羊河的尾闾湖,到1924年再没有接纳石羊河下泄水量,勉强维持到1953年,湖水完全干涸,(吴晓军,《西北生态启示录》,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33页)。
其二是河进人退,民勤县面临消失的境地。
早在汉代建立的武威县,已经被黄沙所掩埋,它的原址是在今民勤县以北靠近休屠泽的地方。造成全县已有13.5成亩的人工沙枣林枯梢或死亡,10万亩耕地,50万亩耕地沙化。近400万亩天然草场被黄河覆盖(黄茂军:《民勤消失》,刊《经济观察报》2003年9月23日)。如不采取强有力措施,民勤难逃消失的劫难。
其三是河流湖泊干涸,地下水急剧下降,无法生存的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
河水断流,泉眼之奄息,在石羊河的中下游来说是无回天之力。永昌县境内有石羊河支流金川河和清河、原本泉水丰盈,据历史记载,全县共有大小泉眼578万余处,多年平均泉水流量每秒7.006立方米,年径流量2.2091亿立方米,但由于地表水的减少和地下水的开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使许多泉水枯竭,清水河流域原有的17条泉流,除乌牛犋、小河犋梅杞犋尚有少量泉水外,其余泉流全部干涸......1985年全县泉水年径流量降至1.181亿立方米,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减少364.5%(吴晓军:《西部生态度启示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2第1版,35页)。
由于地表无水、迫使为延续生存的百姓向地下索水。民勤县从70年代至今,30年间打井万余口,各类机井每年超采地下水4.62亿立方米,地下水位每年以0.5米~1米的速度下降。
据说,由于生态条件所迫,近年来已有3万多群众背井离乡走上了不归之路。
第二节 难以忍受的承载能力
一、新疆地区人口的古今变化
二、河西走廊地区人口的古今变化
三、汉代塔里木地区的人口分布
《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所载梁景之文章,题目叫《汉代塔里木地区的人口分布与变迁》。论及汉代塔里木盆地人口分布的特点,他提出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其不平衡性表现在:古代沿天山南麓的北道,比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南道,人口分布要稠密,他得出的结论是:北道分布的人口数为189 444 人,南道人口分布的数量是87 596人,南道人口与北道人口之比是1∶2.16 ,这一思考与寻求南北道人口的变化的特征与规律,是值得借鉴的。笔者也进行了统计,与梁先生的数字大致相同但略有出入。具体统计情况如下,梁文云:北道诸国或地区的人口,据《汉书·西城传》记载:山国有众5000,焉耆国32100,尉犁国9600,尉头国2300,危须国4900,姑墨国24500,温宿国8400,龟兹国81317,疏勒国18647,乌垒1200,渠犁1480,各国(地)人口合计为189444人,南道诸国中鄯善国为14100人,若羌国1750人,且末国1610人,小宛国1050人,精绝国3360人,戎卢国1610人,渠勒国2170人,扜弥国20040人,于阗国19300人,皮山国3500人,乌秅国2733人,莎车国16373人,各国人口合计为87596人,两地区的人口总数分别为189444人与87596人,二者之比为2.16∶1。
上面进行的统计与计算有不足的地方,应该把车师地区的人口也算作北道,这是因为《汉书·西域传》中把车师列入北道,如《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所以应该地把车师的人口算入北道,这样加上车师前国人口6050人,加上车师都尉人口960人,北道的总人口为197357人,南道的人口我们计算的数字是104263人,二者之比为1.89∶1,与梁先生的数字有出入,而这个比例与今天南北人口之比基本相同。根据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册统计目前的比例是1.898∶1。这与两千年前南北道人口之比是非常接近。我们不妨把当今的南北道人口具体列出便可看得更加清楚。当今南道的人口是这样的:若羌县2.9万,且末县5.5万,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3.1万,和田市17万,和田县26.2万,墨玉县40.5万,皮山县21.6万,洛浦县23.6万,策勒县13.2万,于田县21.2万,民丰县3.2万,莎车县62.1万,泽普县17万,叶城县36.9万,麦盖提县20.2万,共计314.2万。而北道的人口是这样的:阿图什市20万,阿克陶县6.3万,阿合奇县3.4万,乌恰县4.2万,阿拉尔市17万,图木舒克市12万,喀什市32万,疏附县36万,疏勒县28.7万,英吉沙县21.3万,岳普湖2.9万,伽师县31.1万,巴楚县37.6万,阿克苏市52万,温宿县21.9万,库车县38.9万,沙雅县20.3万,新和县3.9万,拜城县19万,乌什县17.7万,阿瓦提县19万,柯平县3.8万,库尔勒市36万,轮台县9.2万,尉犁县10.3万,和静县17万,和硕县6.3万,博湖县6万,焉耆县11.7万,吐鲁番市14万,鄯善县19.7万,托克逊县10.2万,总计为588.6万,与南道的人口314.2万相比,其比值为1.87∶1。
上面的数据是塔里木盆地在西汉时期南北道人口的分布与南北道人口之比例,计算的结果,我们得出了一个两千年前后南北道人口比例基本不变的惊人结论。历经两千多年南北道的人口由三十来万增长到千万,增长了三十倍,但南北道人口数量的比例不变值得探讨,不变的原因是什么非常值得思考。是不是在一定生态条件下其容量是一个定值,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力的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是均衡的。若以塔里木盆地人口增长的比例看是不低的,西汉时期西域以东的中国人口的总量是6000来万,塔里木盆地的人口是30来万,约占千分之五,而今天塔里木盆地的人口是近千万,约占十三亿人口的千分之七点七。看来经过近二千年的变化,塔里木盆地人口增长的比例要大于塔里木盆地以东人口增长的比例,这说明塔里木盆地在一些方面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内地。
关于塔里木盆地人口分布的地理问题,梁景之先生的文章共讲了四点,讲得很好。他认为有四种类型,这便是荒漠绿洲型,河谷山地型,荒漠草原型,盆地绿洲型。他认为荒漠绿洲型主要是指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以农为主的各国或地区,如且末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自且末以西诸国的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都基本相同。属于荒漠绿洲型的还有精绝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于阗居民从事农牧,多桑麻,龟兹居民主要务农,兼营畜牧,冶铸酿酒也很发达。疏勒居民从事农业,精工艺开采铜铁,姑墨居民以农为主兼营牧业,产铜铁。乌垒土地肥沃,莎车,扜弥,皮山等也是以农为主兼营畜牧,总之这种荒漠绿洲型诸国以农为主,人口较多。第二种类型的诸国是河谷山地型,人口稀少,多分布于天山、昆仑山及帕米尔等地区的河流谷地或高山低地一带,交通不便,多以牧业为主,如乌秅国,山居,田石间出小步马,有驴无牛。山国,民山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休循国,王治飞鸟谷,因畜逐水草。捐毒国,随水草,依葱领。西夜国其种类氐羌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蒲犁国,寄田莎车。依耐国与子合国俗相同,少谷,寄田莎车、疏勒。无雷国俗与子合同,从事游牧。尉头国田畜随水草。温宿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同。小宛,戎卢,渠勒皆处于高山谷地,即便今天也以游牧为主。第三种类型是荒漠草原型,此为人口地理分布诸类型中,人口最稀少的类型之一,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东部荒漠平原或荒漠高山坡地地带,如鄯善若羌等国,这些国家的人口基本以游牧为主,由于自然条件差,植被不好,所以人口也很稀少。第四种类型的是盆地绿洲型,此种类型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天山东部山间盆地,低地地区,水草丰茂土地肥沃,植被好,居民人口多,以农为主兼营畜牧业,如当时焉耆国居民务农捕鱼畜牧,直到今天其分布特点依然十分突出。
第三节 黑河流域古今生态的变化
黑河是我国的第二大内陆河。也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水系中最大的一支,发源于祁连山中,主要流经张掖,临泽,高台,嘉峪关,酒泉,金塔,再向北长途跋涉入内蒙的中外蒙之交处的居延海,全长约1000公里,横贯甘肃、内蒙两省。该地域古属雍州之地,战国秦汉时期此地为大月氏人的游牧地。西汉初年,由于冒顿单于的强大,匈奴人把大月氏人从祁连山逐出,成为匈奴昆邪王的牧地。到了西汉中期,汉王朝经过数十年之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大,为解除匈奴人对北部边防之压力,攘逐匈奴,在河西地区开设四郡,此地置张掖、酒泉二郡。张掖为张国臂掖之意,酒泉取其泉水众多味如美酒之意。清朝时设甘州、肃州直隶州。地当要冲,河山襟带为羌戎通驿之路,南有雪山嵯峨万仞,北有紫塞延袤千里,实为古代羌番入贡之要道,河西保障之咽喉。当今设有张掖市,辖一区五县即甘州区、山丹、民乐、高台,临泽、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以及嘉峪关市、酒泉市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有近10万平方公里。
(一)古代黑河流域的山体植被状况
从文献记载看,黑河流域的山体植被虽不如石羊河流域那么多名木名山,但亦相差不远,山体植被除松柏外,主要是美水茂草,是得天独厚的少有的广袤的牧场。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现根据《大清一统志·甘州府》和《大清一统志·肃州府》志的记载,将此二州所在的植被状况予以简述:
雪山:在张掖县南一百里,多林木箭杆。
临松山:在张掖县南,《隋书·地理志》:张掖有临松山,《寰宇记》:临松山,一名青松山,一名马踢山,又名丹岭山,在张掖县南182里。
祁连山:《西河旧事》言:山在张掖、酒泉二郡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一名天山。亦名白山。
焉支山:在山丹县东南,接凉州府永昌县界?《西河旧事》云: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括地志》: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
金山:在山丹县西南??《汉晋春秋》云:是年氐池县大柳谷口,激波涌溢,有苍石立水中,文曰:大讨曹。《十六国春秋》云:吕光龙飞二年,沮渠蒙逊起兵攻拨临松,屯据金山,沮渠蒙逊元始五年,祀金山,西入苕濯,遣将袭卑和,自率众为继,循海而西,复入金山而归。
龙首山:在山丹县西北二十五里边外??山阴有泉。
文殊山:在州西南三十里,两峰南北对峙,水泉中流??又有滥尼山,一名淖泥山,在西南百余里文殊山南,其山多水泉,地泞泥,故名。
榆木山:在高台县南四十里,上产榆树,故名,东起梨园,西尽暖泉,延长百余里。
白城山:在高台县西南八十里??林泉之胜。
合黎山:其山产茶,(在今高台县北)
以上我们引述的材料虽然不多,但可以看出苍松翠柏的图景。现在我们引述《肃州志·南山》的记述作为黑河流域植被状况的小结:“南山松百里,阴翳车师东,参天拨地如虬龙,合抱岂止数十围,拜爵已受千年封”,其间最古老之树“曾阅汉唐平西戎”。
(二)古代黑河流域的河湖状况
《嘉庆重修一统志·甘州府》记载该府中的两条较大的河流,其一是张掖河,其二是弱水。张掖河就是今日之黑河,汉代的羌谷水。《汉书·地理志》言其行程二千一百里,《括地志》还详细记载了张掖河的不同名称:一名鲜水、一名合黎水、一名复袁水、一名副投河,发源于吐谷浑界,流入居延海。另一条大的河流是弱水(山丹河),源于山丹县南,后与张掖河合。张掖河的支流,志书尚未记载的还有梨园河、洪水河、八宝河等。
除记载大河之外,府《志》还记载了当时州内的一些有名的泉水及宜牧之地所设置的牧马厂,大致有以下多处:
赤泉:张掖县东南。
甘泉:张掖县西一八十里甘峻山下,味甘冽。又城南门内东三十余步,亦有甘泉,北流出城,引以转皑。
蓼泉:在张掖县西??《行都司志》:萼泉在卫西九十里,都渎间在其西。
九眼泉:在张掖县西九十里。
草湖泉:在张掖县张掖河,两岸多生芦苇,每年收草百余万束以饲马。
暖泉:在山丹县东南四十五里,平地涌泉二穴,寒不冻,有大渠一,分闸五,共灌田七百一十八顷。
石井:在山丹县东八十里,其水常满,汲之不竭。《行都司志》:井出石峡口山下。
三十二井:在张掖县北边外,参差并列。
乐得故城:后为甘州,因州东甘峻山为名,或言地多甘草,故名。
昭武故城:在张掖县西北??晋改曰临泽。
删丹故城:本汉旧县,按焉支山一名删丹山,故以县名。
日勒故城:在山丹县东南,汉置,属张掖郡。《汉书·地里志》:日勒都尉治泽索谷,《赵充国传》:武威郡,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
祁连废郡:在张掖县西南??《晋书·地理志》:永和中,张祚置汉阳县以守牧地。
(三)古代肃州所设之牧马厂
永固城,在山丹县境,去府治东南一百八十里,有牧马厂。
洪水堡,在张掖县东南一百四十里,县南山场柏树湾有牧马厂。县东观音口内混泉,有甘州城守营牧马厂。
南古城堡,在张掖县南一百里,柳沟河有牧马厂。
梨园堡,张掖县南一百里,有牧马厂。
石峡口堡,在山丹县东八十里,有牧马厂。又独峰口,有山丹营牧马厂。
(四)《志》书中记载的肃州的具体的河湖
托来河,根据《舆图》所载,今托来河发源于州西南五百余里的番界中,有三大支流,最西者曰托来河,其西又有辉图巴尔呼河,北流百余里,与托来河合。又东北百余里有巴哈额齐讷二河,分流二百里许,合流,又北数十里与托来河混为一,又东北二百余里入边,绕州南至州东北合西来之水,又东北出边过金桥寺,稍折而北。又转东与张掖河合,又北五百余里入居延海。
红水,在州东南三十里,源出南山,北流合白水,入托来河,以水有红色故名。
白水,源出州西南二十里,下合红水。
沙河,在州东四十里,源出雪山,北流入托来河。
清水,在州北五十里,源出州西北清水泉,东流入托来河。
黑水,在州西北120里,源出黑水泉,会清水流。
放驿湖:在州东南一里,周六里余。
铧尖湖:在州东南二十里,有二湖,皆放牧之所。
郑家湖:在州北七里郑家堡前。
花城儿湖:在县北八十里,地属新城堡。
仓儿湖:在州北二十五里,俗谓之大湖场。
五霸湖:在高台县东十二里。
大芦湾湖:在县东北二十里。
黑家站家湖:在县东四十里。
鸳鸯湖:在高台县西十里。
七霸湖:在县西十五里。
月牙湖:在县西北五里。
高台站家湖:在县西北五里。
水磨湖:在县西北十里。
海底湖:在县西北十里。
苇荡湖:在县西北十五里。
狼窝湖:在县西北二十里。
李家湖:在县西北二十里。
官军湖:在高台县镇夷所城东南三里。
局匠湖:在城东南十里,旧为牧放之地。
夜不收湖:在城东北五十里,胭脂堡旁。
大湖:在高台县镇夷所西一里。
乌鲁讷湖:在城北边外五百里。
(五)历史上神秘而美丽的居延海
前面所述的黑河、张掖河就是今日之额济纳河,额济纳河经过周折之后最后注入居延海,古称流沙。《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均有记载。关于居延海在历史上的面积说法不一,但相差无几。杜海斌认为:
历史上的居延面积曾达到800平方公里(杜海斌:《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
而杜弋鹏则认为:
古居延海面积达720平方公里(杜弋鹏:《阿拉善尘暴:你在诉说什么》刊于《光明日报》1996年5月14日)。
总之水域面积相当壮观。古居延海面积的缩小是从宋朝末年开始的,但宋朝末年直到19世纪50年代仍维持在3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不变。杜弋鹏认为:
到宋朝末年,河水(指今之额济纳河)改道,逐渐消失后,形成的新居延海面积还有300多平方公里(见前注)。《人民政协报》记者李宏前往考察并于2001年10月31日发表在该报上的《额济纳绿洲面临消失险境》中指出:
“50年前,东西居延海分别有水面35平方公里和287平方公里”。
从中可以看到从宋朝末年到上午世纪50年代,历时近千年,居延海的面积相当稳定没有变化。居延海及其沿黑河两岸的植被被草丛和密林所覆盖。林学家董正钧早在19世纪40年代考察黑河时指出:
“南由狼心山老树窝起,北至河口,沿东西河及其支流两岸,直达居延海滨,均布满天然森林??红柳高达丈余,密生处,人不可入,一望无际方园数千里,堪称奇观。”对于额济纳旗生态环境的记述,马天鹤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篇幅颇多,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令人十分神往,我们不妨把他的日记摘录数篇於下:
(1926年)十月二十八日:
“起视林源,大数百亩,树数千株,可以说是额济纳的富源??此地水草肥美,草木繁盛??
沿河岸行,西望河边,胡桐树林延亘,一直数十里。”
(1926年)十月二十九日
“早起四望,见西面大林密布,细苇丛生,??十二时行,沿途硬沙,西面林更密,草更茂,一望无际,不知几千百亩??入晚,行数十里,穿林而过,草木益密。”
(1926年)十月三十日:
“下午一时行,沿途芨芨草高三、四尺,细苇杂生,一望皆是,不知几千百亩。”
(1926年)十一月二日:
“早起四望,周围全是树木,深密无际,十二时行,一路在密林茂草中穿过??非披荆斩棘不可,一直数十里,依然草木广茂,胡桐、柽柳等或则大数围抱,或则高五六丈,或则一丛方丈,甚至数丈,想见上古洪荒时代之景况。“(转引自杜海斌:《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刊于《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从马天鹤先生所记载的额济纳之胡桐柽柳竟然能长到粗达数围抱,高则五六丈,可知经历了何等久远的年代,他所记载的这一区域为原始森林区是确定无疑的。
够了,无须我在这里再加总结,我们可以想象到20个世纪40年以前的额济纳是何等的诱人。
(六)额济纳旗绿洲林木面积的减少
据记载,早在50年前额济纳旗的绿洲面积是32万平方公里,而如今只剩下0.3万平方公里??以前额济纳旗入境的两条河流两岸的胡杨林有75万亩,红柳林225万亩,而如今减少到34万亩和150万亩。草本植物有130多种,如今只剩下不到30种(李宏:《额济纳旗绿洲面临消失的险境》,刊于《人民政协报》2001年10月3日)。
另据全国政协委员其仁旺其格的调查,分布于黑河下游额济纳境内以东、西居延海为主体的面积为2488平方公里的湖泊、盐化沼泽、芦苇湿地大幅度萎缩乃至相继消失。6500平方公里的绿洲已退化到3300多平方公里,113万公顷的梭梭林仅剩下38万公顷残林,50万公顷的天然次生林仅剩下294公顷残林,草场退化面积达334万公顷以上,植被覆盖率降低了30%、80%,沙化面积占总面积的85%以上??由于湖泊干涸,绿洲萎缩,植被退化沙漠扩大,沙尘暴发生次数增多,强度增大,危害加重,京津唐地区的扬沙、尘雾天气多源于阿拉善地区。目前其境内的三大沙漠每年以10米~20米的速度(折合约1000平方公里)扩展,人工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沙漠化程度(其仁旺其格:《阿拉善生态建设任重道远》载于《人民政协报》2004年4月6日)。
山丹军马场山坡牧场的灌木林在1964至1984年20年间,因开荒种地和超负荷放牧被毁面积达37600亩以上,祁连山草场现在普遍出现了草原退化,如肃南县草场退化面积已达1068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50%,军马场退化草场达658461亩,占整体可利用草场的38.5%,黑河流域沙漠化发展速度达到年均2.6%~6.8%(程国栋:《论干旱区景观生态特征与景态生态建设》载于《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1期)。
(七)黑河流量减少,湖泊干涸
据《理论研究》1999第1期所载王芳、秋才的《西部各地区间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可知,20世纪50年代黑河水流入额济纳的水量在12亿立方米~13亿立方米左右,60~70年代至少也保持在10亿立方米以上,能基本维持额济纳旗生态平衡和人民生活用水。80年代以后,由于上游用水剧增,黑河入旗水量锐减至4亿立方米,枯水年仅有2亿立方米,1992年再减至1.83亿立方米。据记者李宏观察到情况是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黑河流入额济纳的水量减少了44%,河道断流期由原来的100天延长到200多天,流域内30多条支流先后消失,东,西居延海等12个大小湖泊完全枯竭(西居延海1961年干涸,东居延海于1973年、1980年、1986年三次干涸、变成一个间歇性湖泊,到1992年彻底干涸)。16个泉眼,4个沼泽地完全消失,370万亩的原水域变成了盐碱滩。
河水断流、湖泊之于涸给沿岸居民带来了灾难。据《光明日报》1996年5月14日所载杜弋鹏的《阿拉善尘暴你在诉说什么》一文所载,1988年到1995年间沿河的吉日嘎郎图、苏古淖尔、赛汉桃来三个苏木地下水位平均降低111米,远离河道的地方,水位下降程度可想而知了。有关部门调查发现,沿河牧区1548眼简井中的1018眼干枯了,许多农户只好到十多里外去取水。
居延海干枯之后,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维持生态系统的各种生物的衰竭与死亡,沙漠化急剧发展,特别是在额济纳旗狼心山以北东西两河下游三角洲上,植被退化和沙漠化十分严重,天然生长的乔、灌、草三层结构,逐渐演化为二层,单层,甚至全部枯死,裸露的地面和松散的河流沉积物不断遭受风力的侵蚀,在风力的作用下原先繁茂的河岸植被在一侧堆积成胡杨、红柳沙包。河道干涸后,胡杨、红柳因失去水分供给逐渐枯萎死亡。古老的居延绿洲正面临着一场灭顶的生态灾难,那些半流动、流动的沙包正逐渐吞噬着千百年来人类居住的家园。据兰州沙漠所1986年调查,额济纳旗仅绿洲地带内沙漠化土地就达26362.5平方公里,占绿洲面积的87.2%(见吴晓军:《西北生态启示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42页)。
第四节 准噶尔盆地古今生态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首先把清代方志中所记载的有关情况简述於下:今日之乌鲁木齐,清代名迪化,它当时所管辖的区域内民丁男妇大小共103052名口,统计12028户。其山川河流泉水及植被情况远优于今日。《志》载:阿拉癸山,在州南70里,山深林密险窄难行。
阿察河:在州东,有三泉,出天山北麓,北流50里,汇为一河,余波入于沙碛。
阿勒塔齐河:在州南,源出乌可克岭北麓,分二支,夹州城各北流,入于地,其西南有三水并来入之。
昌吉河:在州西昌吉县南......,有四支合而北流。
罗克伦河:在州西昌吉河之西,有二源,西北流入於呼图克拜河。
呼图克拜河:在州西,当孔道,有五源出天山北麓,会诸河,会于额彬格逊淖尔。
图古里克河:在州西,源出巴颜哈玛尔山。
哈齐克河:在州西,有三源......
玛纳斯河:在州西绥来县治之西境,有五源......入额彬格逊淖尔。
和尔郭斯河:在州西......
安济哈雅河:在州西,凡三源,东北流一百一十里,逾孔道北渚为小泽。
察罕水:在州东。
乌兰水:在州东。
多伦水:在州东。
库里叶图泉:在州东。
纳里特泉:在州东。
铿格尔泉:在州东。
必柳泉:在州东。
多博绰克泉:在州东。
济尔玛台泉:在州东。
乌里雅苏台泉:在州东。
阿克塔斯泉:在州东。
额彬格逊淖尔:在州西北会呼图克拜河、玛纳斯河、乌兰水诸流咸集,周可五十余里,一巨泽也。
鄂伦淖尔:在州西北,亦曰达布苏淖尔,南距城四十里,周十里许,其东别有小池。
以上所引《志》书所载清朝时期迪化州内的山水泉林,有许多今日已不复存在了。中央党校出版社所出版的奚国金先生的著作名为《西部生态》,言及出版于清朝光绪乙未年(1895年)的《皇朝省直地舆全图》,较为清楚地绘制了新疆一百多年前的地理景观。从图上可以看出,当时新疆的河流较今日多、流程也比较长,例如天山北坡的一些河流相互流通,形成了5个主要水系,东部木垒以东的河流都流入巴里坤湖,形成了巴里坤水系,奇台与乌鲁木齐之间的河流汇入乌鲁木齐北部的东道海子,形成了东道海子水系,乌鲁木齐到屯奎之间的河流以及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的河流,都流入玛纳斯湖,形成了玛纳斯水系,屯奎以西的河流汇入艾比湖,形成了艾比湖水系。然而到了今天,这些河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河流流程变短,湖泊缩小或干涸。如天山北坡的第一大河玛纳斯河,比以前缩短了100公里,它的尾闾湖玛纳斯湖已经干涸,天山北坡的原先的五大水系现在已经变成独立的十几条小河。再以艾比湖盆地来说,它位于天山北坡西端,是西来气流进入新疆的最重要的孔道,艾比湖盆地的中心是面积约560平方公里的艾比湖,根据调查,艾比湖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湖水面积是900多平方公里,由于上游地区引水开荒种田,流到湖里的水量很快减少,导致湖水面积缩小。艾比湖盆地西高东低,湖水东深西浅,湖水面积缩小后,西部湖底大量的沉积物盐类裸露在地表,每当大风吹来湖底的盐类物质形成盐尘,飘散在空中,??在天山北麓西段已经形成了一条盐尘污染带。
第五节 塔里木盆地古今生态的变化
塔里木盆地从西到东贯穿一条大河,那就是我国最长的一条内陆河塔里木河。塔里木河的上游有四条主要的河流,那便是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和阿克苏河,这四条河流汇合后向东便进入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干流的总长度约1300多公里。注入罗布泊。罗布泊的水域面积很大,罗布泊向东的延伸处可能与疏勒河的尾涧湖相接近,不然的话,《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均言及玉门关距蒲昌海的距离是300里。如《汉书·西域传》载: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不但《汉书》有这样的记载,而《后汉书·西域传》也认为蒲昌海距玉门三百余里。奚国金的《西部生态启示录》第43页曾言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下游盆地流入神秘的罗布泊的说法。刊于《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上的张莉同志的《西汉楼兰道新考》认为:古代疏勒河河水丰盈,在大灞冲击扇缘洼地内,曾汇集成广阔的河道湖泊,汉代称之谓冥泽,唐代称之谓大泽,其东西长达260里南北宽有60里,唐代疏勒河由此得名为冥水。出冥河,河水继续向西,汇聚疏勒河下游最大的支流党河,党河汉代称为氐置水,党河在敦煌以北冲积扇北缘洼地,有众多泉水出露,与疏勒河下游河道相通,向西一直进入甘新边境的榆树泉,其再向西与罗布泊湖盆向东伸出的一个湖湾阿克奇沟谷相连。我们之所以引用上面那么多资料,目的是想证明古代罗布泊水量之大。不然的话,《汉书》、《后汉书》均言及玉门关距罗布泊只有300里,很有可能它们的水系相通。
以上所引资料足以说明塔里木河在古代水量是相当丰沛的,遗憾的是如今的塔里木河已今非昔比。据奚国金先生所著《西部生态》所载:塔里木河主要源流有三支,这便是和田河,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如今和田河、叶尔羌河已无水汇入塔里木河,阿克苏河成为塔里木河目前唯一的源流。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塔里木河上游每年向下输送的水量约32亿立方米,到达中游时,水量减少到18亿立方米,到下游时水量锐减到约2.4亿立方米,这些水只能向下再流约230公里,到达大西海水库,再向下游,塔里木河已经干涸,下游约200公里河道断流。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之后,使得原本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进一步破坏,区域生态环境趋向恶化,沿塔里木河下游原本生长有大片的胡杨林和其他植物,它形成了分隔塔里木河下游库鲁克库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绿色走廊,绿色走廊有通往新疆东南部的便捷通道218国道,计划中的新疆至青海铁路也将从这里通过,绿色走廊还有效地减少了由强劲东风携带的沙尘,保护了库尔勒等地处下风位置城市的生态环境。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后沿河的胡杨林逐渐衰亡,林下的灌木和草已经全部死光。218许多路段被流沙埋没,通行困难,人们担心,有朝一日,库鲁克库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会连为一体。昆仑山北麓山前绿洲区的变化也是十分巨大的,和田地区是新疆受沙漠化威胁十分严重的地区,据说近百年来这一地区新产生的沙漠土地面积达8600平方千米,近30年来被流沙吞没的农田就达三十万亩。
第六节 祁连山北麓人居生态环境的变化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一二六号发言材料刊登的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慧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加强祁连山北麓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的建议》,文中谈到目前祁连山北麓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天然林缩减,功能削弱。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22.4%下降到现在的13.8%,森林林带由建国初期的1900米退缩至230米,如今浅山区森林已基本消失;灌木生长下限比20世纪50年代上移约60米,30%的灌木已草原化,灌木盖度和高度分别下降了35%和20%。二是草场退化,生产力下降。祁连山北麓445.6万公顷草地,退化面积已达26%、盐碱化面积达4.09%、沙化面积达7.13%;水土流失面积达20.12%。可食牧草比重与1983年相比下降18%,每个羊单位需草面积由1983年的7亩增至目前的8至16亩;一、二等草原面积比重与1983年相比下降22个百分点。三是河道干涸,水源匮乏。由于祁连山水源涵养功能减退,大小河流水量减少,枯水期延长,前山地带部分河流流程缩短,河岸植被稀疏,河道沉积沙石,旱则洞,涝则泛,山洪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下游凹地天然植物枯死,沙漠化趋势加剧。有调查表明河西地区沙化土地面积达到1671.14万公顷,较1999年增加59.24万公顷。四是冰川萎缩,雪线上升。据甘肃省气象科研所冰川考察资料,祁连山现有雪线比古雪线升高500至800米,祁连山冰川融水比20世纪70年代减少了大约10立方米,局部地区的雪线正以年均2米至6.5米的速度上升,导致积雪面积明显减少。据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冰川的平均退缩速度东部为16.8米/年,中部为3.3米/米,西部为2.2米/年,远超过海洋性冰川的一般退缩幅度。有些专家预言,面积在2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型冰川将在2050年前基本消亡。五是生物种类减少,病虫害蔓延。高山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的退化和山区径流的减少,加剧了山区小气候的变化,长时间的干旱少雨,使祁连山森林景观渐呈破碎状,野生动物栖息地遭破坏,导致一些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特别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珍稀野生动物如马麝、雪豹、野牦牛、白唇鹿等处于濒危、灭绝状态;植物中原始的高大乔木植物种类也在逐年减少。20世纪以来,祁连山北麓的青海云杉林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针叶发黄,长势衰弱、病虫害严重等问题,每年发生各类森林病虫害3.4万公顷,占林地面积的30.6%,严重的地段部分林木成片死亡或趋于死亡。
第七节 人与生态的平衡问题
在人对自然的认识上,在生态问题上,人们对其规律还不能全部了解。人们为了生存得拥有和开发资源,有些地方的资源可以开发,有些地方的资源可以适度开发,有些地方的资源是绝对不允许开发,利在当代的工程并不一定都能功在千秋。历史上这些例子太多了,其留下来的恶果我们现在还在品尝,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汉武帝对西北地区的屯田开发,虽然减轻了转输之劳,保障了屯田将士的粮食供给,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屯田破坏了草原植被,肇启了沙漠化的先河。当代中亚地区开发所造成的后果值得我们借鉴:位于中亚地区的咸海周围属于干旱地区,在苏联的农业生产上居于重要地位,其棉花产量占前苏联的95%,水果占1/3,蔬菜占1/4,稻谷占40%,由于气候干旱,90%的农田依靠灌溉。随着生产的发展,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上,挖掘了一系列的运河以引水灌溉。水浇地从50年代的290万公顷发展到750万公顷,引水量大增,入湖水量大量减少,在30年中,使咸海湖面缩减了40%,贮水量减少了67%,湖平面下降了14米。湖水退缩后,使30000平方公里的湖底出露,变为沙漠??当地70%~80%的动物灭绝,随着湖水容量的减少,水中含盐量增加2倍,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本地鱼种已完全绝迹,渔业也随之凋零,干涸湖底的含盐尘土被风吹扬至附近的农田,使作物减产,农民为了维持农作物的产量而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污染地下水,环境质量的恶化,导致许多疾病的流行。据报道:像传染性肝炎,伤寒、黄疸、肠道感染和癌症等病例均明显增多,发育不全和婴儿夭折的比例都很高。大风还把灰尘、盐分和风干了的农药颗粒吹扬至几百公里以外,西达里海,北达北极圈内。(见杨子祥:《冷静看待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刊于《人民政协报》2001年9月4日第6版)。位于我国西部的新疆、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与咸海流域的中亚地区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地理气候条件,苏联的生态灾难——咸海周围开发的前车之鉴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由此看来,荒漠化并非大自然的恩赐,恐怕是人类自酿的一杯苦酒。恩格斯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消失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培育地保护的森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恩格斯的话对我们很有启示,西北地区解放以来所发生的巨大的生态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新疆的最大生态变化莫过于罗布泊的干涸。《水经注》是这样记载罗布泊的:
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故蒲昌海亦有盐泽之称也。《山海经》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者也,东至玉门阳关千三百里,广轮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其中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当其寰流之上,飞禽奋翮于霄中者,无不坠于渊波矣。即河水之所潜,而出于积石也。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大的水面的湖泊却于1972年彻底干涸。无独有偶,就在罗布泊干涸这一年,黄河出现断流,这在黄河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此后黄河几乎年年断流。为什么罗布泊的干涸与黄河的断流发生在同一个年份?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古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黄河的发源地是昆仑山,流到罗布泊汇成一个很大的水面,约有20000平方公里,然后从积石山潜流复出奔向大海。即从罗布泊到积石山是潜流,是无形之河。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
1.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对罗布泊有明确的记载,认为是“河水之所潜也”,即这里的水潜行地下,通过暗流东出形成黄河。如《山海经》云:“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坳泽(即罗布泊),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
2.《尚书·禹贡》篇云:“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3.《史记·夏本纪》是这样记载的:“道九川??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唐朝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这句话是这样注释的:“《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州伊吾县北百二十里’,其黑水源在伊州,从伊州东南三千余里至鄯州,鄯州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河州有小积石山,即《禹贡》‘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者。然黄河源从西南下,出大昆仑东北隅,东北流经于阗,入盐泽,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又东北流,来处极远。其黑水,当洪水时,合从黄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张守节在注释“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这句话时,谈到了河源问题,认为河源是出自昆仑山,流经于阗,入于盐泽,然后潜行地下,经吐谷浑(即今青海地区)而达于大积石山(概指今天的巴颜喀拉山北麓)然后向东北流至于小积石山(概指今日甘肃省东南积石山脉)。
4.唐代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用《尔雅》的说法也认为河源出自昆仑。他在注释《史记·夏本纪》时引用《汉书·西域传》云:“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其水停居,冬夏不减,潜行地中,南出积石为中国河。”是河源发昆仑,禹导河自积石而加工焉。
5.《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河发于昆仑:“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对于《大宛列传》中的这句话,唐朝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唐朝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都分别有注释。《史记正义》云:《汉书》云,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山为中国河。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案:《汉书·西域传》云,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山海经》云,河出昆仑东北隅,郭璞云,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山于阗国,复分流歧出,合而东注坳泽,已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坳泽即盐泽也,一名蒲昌海。
6.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认为是河出昆仑,上面已有引文这里不再赘述。
自郦道元之后,唐代人有考河源者,元代人亦有多次考河源者,到了清代更是如此。康熙帝、乾隆帝都曾多次派人考察河源。如阿弥达受乾隆之命考察河源,从青海到罗布泊,他认为罗布泊的水源来自60多条河流,罗布泊东西长200里,南北宽100多里,他认为该湖是黄河之源的上游(引自《罗布泊》)。徐松是十九世纪人,进士出身,他作了《西域水道记》,在文中言说“昆仑之墟,黄河初源于此焉”。还说“罗布淖尔者,黄河初源所湾畜也”。《大清一统志·黄河》云:“源出清海之极西境,自回部罗布淖尔伏流重发,名阿尔坦河,流入鄂敦他腊,挟扎楞、鄂楞两淖尔水,东南流,折西北又转东北,历二千七百余里,至积石关,入甘肃河州界”。
对河源的认识也有不同的看法,《元史·地理志》载,在元朝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时,任命都实为招讨史,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受命之后,当年到河州,从这里出发,经过四个月才达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后来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临川朱思本又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画,而以华文译之,与昂霄所志,互有详略。总之,他们认为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站在高山往下看,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刺脑儿,这大概就是常说的扎陵湖和鄂陵湖。
以上罗列不同的河源说,《大清一统志》对各家看法给以总结,并得出一个倾向性的结论:“本朝威德远布,幅员广大,边徼荒服,皆隶版图。我圣祖仁皇帝遣使臣,往穷河源,测量地度,绘入舆图,凡河源左右,一山一水,与黄河之形势曲折,道理远近,靡不悉载,较之元人所志又加详焉。今依地理今释,参考舆图,及青海山川册说,著其大略如此。按旧志序述河源,以阿勒坦河,在鄂敦他腊之上,与今日考订情形,颇相吻合。惟未著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及天池上之黄水,又未悉回部和田叶尔羌初发之源,伏于蒲昌海,重复于阿勒坦河。盍其时回部未定,考验靡因,今日西域青海,偏隶版章,大河真源,近在户闼。高宗纯皇帝命我穷考,圣制诗文,详晰指示。汉张骞所之云,二水交流,发葱岭于田,伏盐泽而重发积石者为说是而其文太略。元笃什所穷鄂敦他腊以下,地位近是,而未悉黄水真源及西域之伏流。盖大河原委,至今日而始备其实焉,今并存元史及旧志原文,而考定其说如此。”
上面我们探究了河源的两种不同说法,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大部分人承认无形之河的存在,即暗河的存在,而部分人探明的是有形之河,所存在的分歧究竟是有没有潜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考证从罗布泊到星宿海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潜流,而目前还没有人考证这个问题。但目前有人考证了巴丹吉林沙漠有条地下河。《人民政协报》2004年11月30日刊载一条消息,言说巴丹吉林沙漠惊现地下河,11月25日英国《自然》杂志432卷发表了来自河海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论文指出,中国西北阿拉善高原的巴丹吉林沙漠下隐藏着大量的淡水资源,其与500公里外的祁连山冰川积雪之间,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调水通道——祁连山深大断裂。这件事说明了地下是存在有暗流的,而且里程有500多公里,古人认为从罗布泊到星宿海之间有条暗河。不知有什么根据和理由。从地图上看,罗布泊到星宿海之间的直线距离也不过七百公里,目前还没有文章排除暗流的存在。总之,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牵扯着一个生态的大问题。因为自从罗布泊干涸后,黄河几乎年年断流。如果罗布泊与黄河之间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应当恢复罗布泊即恢复生态系统。(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常剑峤先生的《祖国的奇山异水》一书)。
一、石羊河流域古今生态的演化
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是一形胜之地:“天梯亘前,沙河绕后,左有古浪之险,右有西山之固,东控宁夏,南距黄河,西连番部北际沙漠”,是谓重地。在西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开设武威郡,辖区较大。清朝时设凉州府,下辖镇番(今民勤县)、武威、永昌、古浪、平番(今永登县)五县。今日之石羊河流域行政设置与清代相比,有所变动,设有金昌市(辖1区1县即金川区和永昌县)面积9593平方千米,武威市(辖1区3县,即凉州区和民勤县、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面积33000平方千米。总计面积为42593平方千米。
清代的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相当好,特别是山体植被堪称是被松柏,丰草所覆盖,有的是终年积雪下流成川。根据《大清一统志·凉州府志》所记载的十多座山,在清朝还是四季常青,郁郁葱葱。
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河流纵横、水资源丰富、湖泊星罗棋布,在《嘉庆重修一统志》中记载了众多河湖的情况,了解历史上的河湖状况可以使我们的以古察今去认真思考历史变迁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冷静深思生态环境的变化带给我们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什么,人们应该如何科学地处理人与环境的协调问题,因小失大、舍近求远、鼠目寸光会带来难以弥补的生态灾难,在这里我们根据有关古籍的记载,再现石羊河流域昔日风采,天、地、人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和谐的景象。
(一)石羊河流域山体植被状况
青山:其位置在武威县东二百五十里、山多松柏、冬夏常青。
松山:其位置在武威县东三百一十里,上多古松。
天梯山:其位置在武威县南八十里,《魏书》记载太延五年议讨沮渠牧、李顺等言,自围河以西,至于姑臧志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至丈余,春夏消释下流成川,引以灌溉。
青山:其位置在武威县南,《寰宇记》记载山下有湫(大水池)甚广,人触之,立有风雹暴至。看来这个大深潭还十分神秘。
姑臧南山:其位置在武威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西连永昌县界。《汉书·地理志》记载姑臧县南山、在县一百三十里。《寰宇记》记:番和县南山一名天山、又名雪山。山阔千余里,其畜称是、连互数郡界、美水丰草。尤宜畜牧。葱岭以东,无高于此。《引都司志》云:姑臧南山在凉州卫西南一百二十里,又雪山在永昌卫南一百八十里、怀凉州南山相连、夏积雪不消、亦名祁连山,按此山西连山丹甘州台肃之祁连山。以及塞外之雪山脉皆连互。名多互称。故杜佑《通典》曰:自张掖而西至于庭相去三千五六百里。而山皆周编。
西山:其位置在武威县西二十里,县志载,山有乐泉、可以疗病。
第五山:其位置在武威西一百三十里,炭山堡西南,《隋书·地理志》云姑臧县有第五山。《寰宇记》载第五山夏函霜雪,有清尔藏林、悬崖修竹,自古为隐士所居。
苏武山:其位置在镇番县东南三十里。山右有苏武庙,谷传为苏武牧羊处。
燕支山:其位置在永昌县西,西接甘州府山丹县界。《隋书·地理志》载番和(今永昌县)有世支山,即此。《引都司志》载松山在永昌卫西八十里,又名大黄山焉支山,一山而连跨数处,山在高古城北一里,广二十里,山产大苋,又产松木,故以为名。
里松林山:其位置在古浪县东四十五里,山上多松。
柏林山:其位置在古浪县东南七十五里,山上多柏树。
西山:其位置在古浪县西五十里,亦名雪山。
白岭山:其位置在古浪县西。《寰宇记》云在昌松县西南,山顶冬夏积雪,望之皓然,寒气异于余处,深冬人绝引路,鸟飞不下。
万花山:其位置在平番县(今永登县)西南?《庄浪汇》记载山下有泉暖。
棋子山:其位置在平番县(今永登县)西南二百里,相连者为皋子山,道险林密,为番人巢穴。
大松山:其位置在平番县(今永登县)东北一百二十里,接兰州府兰县界,山多大松。其北又有小松山在阿堡十五里。
(二)石羊河流域的河湖分布状况
石羊河流域的河流、湖泊在清代以前水源相当丰富,单单泉水的分布就多达5万多处,水是生命之所在,怪不得人们把武威称为“金张掖,银武威”,在这里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及有关书籍的记载把清朝时期的水系状况作了一概述。
谷水(即石羊河,又称谷水)《嘉庆重修一统志·甘肃》载,在武威县东,该河流“经东北镇番县(今民勤县),东出边海,亦名武始泽,即今三岔河也”。清代的三岔河,也就是今日之石羊河。
《汉书·地理志》记载:“姑臧县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汉时的姑臧,就是今日的武威市。汉代的武威县,在今日之民勤县东北50余公里处。
《魏书·地形志》载:“武威郡襄城县(今民勤县境)有武始泽。”
《水经注》卷40载:“都野泽,上承姑臧武始泽。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迳姑臧县(今武威)故城西,东北流,水侧曰灵渊池。??泽水又东北流迳马城东,谓之马城河。又东北与横水合,水出姑臧(今武威)城下,侧城北流,注马城河,又东北清涧水入焉。又与长泉水合。又东北迳宣威县故城(在今民勤县西南石羊河畔)南,又东北迳平泽、晏然二亭东。又东北迳武威县故城(今民勤县东北约50余公里处)东。届此水流两分,一水北入休屠泽,一水又东迳一百五十里入猪野。”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凉州府》引旧志的说法为:三岔河(今石羊河)在凉州卫东北三十里,上源曰金塔寺山口涧,源出天梯山,北流止南把截堡(今武威市南)西分二流,一支北流经卫城西,又屈经城北,而东流至三岔堡。一支东北流经南把截堡北,又东经卫城东到三岔堡,与西一支合,又合杂木山口涧,是谓三岔河,至镇番卫南分为二小河,经卫之西南溉田,又东此,经卫东三十里,又北汲者为海。
清代的三岔河,是汇诸山涧之水而成,大致有蹇占山口,土弥干山口,金塔寺山口,杂木山口,苋羊川山口。
从汉至清朝,我们可以看到石羊河即历史上的谷水,其危端湖水的变化。根据《汉书·地理志》武威县下注曰:“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野泽”。这里的“古文以为猪野泽”是指《尚书·禹贡》篇所说的“原隰底渍”,至于猪野泽即汉时休屠湖已经一分为二了。上到《水经注》谷水即到武威县后,一入休屠泽,一入猪野泽,可知大湖已经一分为二了。而即到了清代,石羊河的尾端湖由原来的两个现在变成了一个,即清代的鱼海亦名哈喇伯。
以上为清代所述的石羊河的正流,那么,其支流也是不少的。
五涧水,在武威县(今武威市)东。
《水经注》清涧水,俗谓之五涧水,出姑臧(今武威)城东,西北流注马城河,合有杂林涧,工凉州卫东南七十里,源出天梯山,北流经古城堡西,又东北经大河驿东,又北合苋羊川,折而西北流,入三岔河。
苋羊川,东卫东南一百七十里,源出古浪雪山,有灌溉之利。
土弥干川水,在武威县(今武威市)西南五十里。《寰宇记》:番和县(今有弥干川,古匈奴为牧放之地,鲜卑语髓为土弥干,言此川水肥美如髓故名。
《行都司志》:土弥干山涧,在凉州卫西南七十里,即五涧水浴水,又有蹇占山口涧,在卫南一百五十里,土弥干山涧的卫西南大口子,北流经卫西,又东北流,左合蹇占山涧,入三岔河。该山涧出自户为南雪山。
长泉水,在古浪县北,《水经注》:长家水出姑臧(今武威市)东,次县(今古浪县北)西北,历黄河阜而东北,注马城河,《旧志》:今有河,东凉《旧志》州卫东北五十里,源出塞外红泉,西流入边,折而北流入三岔河。
除上述外,当时凉州府的平番县(今永登县、已归兰州市管辖)也有数水发源,但都向东南流入黄河,这里不再赘述。
还需提及的是:还有古浪河和水磨川二水各自渚为海,并非流入石羊河。古浪河在汉代叫松陕水,《汉书·地理志》武威郡苍松县(今武威市东南)南山,松陕水所出,北至揟次(今古浪县北)入海,《旧志》云:今名古浪水,在古浪所南八十里,有二源,一出分水岭,一出所东南山,俱北流至城东合为一。又东北流出边,按此水由土门堡出边,又东北百余里猪为泽,清代谓其泽为白海(在今内蒙古界)。
水磨川水,一名云川,自永昌县西东北流,经新城堡北,水磨堡西,又东流经永昌城北,又东北经凝远堡西,北流出边,经旅界,猪为大泽,蒙古名河喇鄂模(在今内蒙古境)又有考耒河,在县西南八十里,东北流入水磨川,按舆图,此水流二百余里,又五百余里许,猪于泽其长与三岔河相等。
从今天看来,水磨川水和古浪河下游的尾端湖泊已经消失。
牧羊川,在永昌县北三十里,文车泽,在威县东,《元和志》在姑臧东三十里。
叙述了清代时期凉州的山、水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湖泊的状况和分布:
休屠泽,《尚书·禹贡》谓其为猪野泽,《汉书·地理志》言“武威县休屠泽在东北,古文以为猪野泽”。《水经注》谓武威北有休屠泽,俗谓之西海,其东有猪野泽,俗谓之东海,通谓之都野。到了清代,名称变为白亭海,《引都司志》:白亭海一名小阔端海子、五间涧谷水流入此海,《旧志》白亭海即猪野泽。三岔河自镇番(今民勤县)东北流出边,又三百余里猪为大泽,方广数十里,俗名鱼海子,蒙古名哙嗽鄂模,即古休屠泽、但《水经注》谓其东别有猪野泽、与汉《志》异。
沙喇泊。在休屠泽西二百余里,水磨川自凝无堡北出边,注入其中,方广三四十里。然而这个湖泊已在地图上见不到了,前文方水磨川水与三岔河水的长短不相上下,果不虚言,因为水磨川水发源于冷龙岭东,均向北流去,三岔河之水之泽谓沙喇泊,且方沙喇泊在休屠泽西二百里,就文献记载而言,此湖的纬度起码与镇番县(今民勤县)相同。
昌凝湖,在旅南界,《旧志》直永昌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凝远堡北四十里,东至镇番县(今民勤县)一百五十里,多水草杨木,明季青马都游牧于此。
长草湖,在旅界凝罗山北。
摆方湖,在旅界上平番县(今永登县)东北边外。
马跑泉,在旅界,直永昌县(今永昌县)北三百十里,又高泉、平泉、赤纳泉皆在旅界。
双泉,在旅界,直镇番县(今民勤县)西北三百四十里,泉有三处,又有乱井儿亦在旅界。
查阅地图,小的湖泊且不说,清朝时期还可看到的比较大的湖泊,今日已从地图抹去了。
鸭儿湖,在镇番县(今勤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中多芦草。又天池湖在县北二十里。......
柳树湖,在镇番县(今民勤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共溉田二千四百九十八顷。
昌凝湖,在永昌县(今永昌县)东北一百二十里。绥远堡北四十里。东至镇番县(今民勤县)一百五十里。中多小草杨木。
摆方湖,在平番县(今永登县)东北塞外、庄浪景记湖在河莹迤北二百八十里。
灵泉池:在武威县《水经注》:武始泽迳姑臧城(今武威市)西,东北流,水侧有灵渊池。王隐《晋书》曰:汉末博士敦煌侯瑾,善内学,语弟子曰:凉州城西泉水当竭......寰宇记:灵泉池在姑臧县南城中。
天池,在武威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山上,四时不涸。
鱼池,在武威县东北一里,阔二百里,周围有湖、草树密,为公余游息之地。
小池,在镇番县(今民勤县)东四十里,俗呼龙潭。
龙潭泉,在平番县(今永登县)、水旱无盈缩。
近城泉,在武威县东五里。又黑水林泉在县东三十里、红水泉在县东五十里,水色微红。海藏寺泉,在县北十里,以上四泉皆流入沙河,溉田甚广、又然的泉在县北三十里。
暖泉,在武威县东一百二十里,又有明白泉在永昌县西三十里,二六雾出、四时常温、东北流注水磨川。又一在永昌县(今永昌县)东三里、一在县北一里。
一碗泉,在永昌县西四十里。又鹿泉,在县西北一百里。
双泉,在永昌县(今永昌县)西北二百里,亦名双井。又草茅泉在县北六十里,矮鹿泉在县东北七十里。
马跑泉,在永昌县(今永昌县)北三百一十里,又育梁泉在县北四百三十里,平泉在县东北二百六十里,芝纳泉在县东北五百里,皆在边外。
青羊泉,在平番县(今永登县)东五十里,又四眼泉,在县东南七十里,犁耙泉在县西四十里。
龙泉,在平番县(今永登县)......。
罗锡泉,在平番县(今永登县)北七十里,泉周七里。冬夏不涸。又沙泉,在县东北八十里,又家保界有沟泉,溉田甚广。
河井,在镇番县(今民勤县)西北二十五里、青池西边外,又有井在县西北二百二十里,小白盐池边,甘洌可饮,又腻古井在县西二百里边外。
三井,在镇番县(今民勤县)西北二百四十里边外,有泉三外,又有乱井儿在县西北一百七十里边外,有泉数处,因名。
(三)石羊河流域古今生态变化的若干方面
如今的石羊河与历史上的石羊河相比,发生了令人可怕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猪野泽,休屠泽彻底消失了。早在西汉前期,猪野泽和休屠泽曾经是匈奴休屠王的驻牧地,《禹贡》和《汉书·地理志》均有记载。据说,由石羊河注入的湖泊东西长120公里,南北最宽处达50公里左右(吴晓军:《西北生态启示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32页)——但是,随着历史的变化,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夕:
由于石羊河下游诸湖泊水源缺乏甚至消失,就变成湖荒地和自然绿洲,其中部分荒地被开垦成灌溉农田,有些低洼之地成为蓄洪区。(冯
绝武:《区域地理论文集》,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349页)。距民勤县城北90公里的青土湖,作为石羊河的尾闾湖,到1924年再没有接纳石羊河下泄水量,勉强维持到1953年,湖水完全干涸,(吴晓军,《西北生态启示录》,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33页)。
其二是河进人退,民勤县面临消失的境地。
早在汉代建立的武威县,已经被黄沙所掩埋,它的原址是在今民勤县以北靠近休屠泽的地方。造成全县已有13.5成亩的人工沙枣林枯梢或死亡,10万亩耕地,50万亩耕地沙化。近400万亩天然草场被黄河覆盖(黄茂军:《民勤消失》,刊《经济观察报》2003年9月23日)。如不采取强有力措施,民勤难逃消失的劫难。
其三是河流湖泊干涸,地下水急剧下降,无法生存的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
河水断流,泉眼之奄息,在石羊河的中下游来说是无回天之力。永昌县境内有石羊河支流金川河和清河、原本泉水丰盈,据历史记载,全县共有大小泉眼578万余处,多年平均泉水流量每秒7.006立方米,年径流量2.2091亿立方米,但由于地表水的减少和地下水的开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使许多泉水枯竭,清水河流域原有的17条泉流,除乌牛犋、小河犋梅杞犋尚有少量泉水外,其余泉流全部干涸......1985年全县泉水年径流量降至1.181亿立方米,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减少364.5%(吴晓军:《西部生态度启示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2第1版,35页)。
由于地表无水、迫使为延续生存的百姓向地下索水。民勤县从70年代至今,30年间打井万余口,各类机井每年超采地下水4.62亿立方米,地下水位每年以0.5米~1米的速度下降。
据说,由于生态条件所迫,近年来已有3万多群众背井离乡走上了不归之路。
第二节 难以忍受的承载能力
一、新疆地区人口的古今变化
二、河西走廊地区人口的古今变化
三、汉代塔里木地区的人口分布
《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所载梁景之文章,题目叫《汉代塔里木地区的人口分布与变迁》。论及汉代塔里木盆地人口分布的特点,他提出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其不平衡性表现在:古代沿天山南麓的北道,比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南道,人口分布要稠密,他得出的结论是:北道分布的人口数为189 444 人,南道人口分布的数量是87 596人,南道人口与北道人口之比是1∶2.16 ,这一思考与寻求南北道人口的变化的特征与规律,是值得借鉴的。笔者也进行了统计,与梁先生的数字大致相同但略有出入。具体统计情况如下,梁文云:北道诸国或地区的人口,据《汉书·西城传》记载:山国有众5000,焉耆国32100,尉犁国9600,尉头国2300,危须国4900,姑墨国24500,温宿国8400,龟兹国81317,疏勒国18647,乌垒1200,渠犁1480,各国(地)人口合计为189444人,南道诸国中鄯善国为14100人,若羌国1750人,且末国1610人,小宛国1050人,精绝国3360人,戎卢国1610人,渠勒国2170人,扜弥国20040人,于阗国19300人,皮山国3500人,乌秅国2733人,莎车国16373人,各国人口合计为87596人,两地区的人口总数分别为189444人与87596人,二者之比为2.16∶1。
上面进行的统计与计算有不足的地方,应该把车师地区的人口也算作北道,这是因为《汉书·西域传》中把车师列入北道,如《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所以应该地把车师的人口算入北道,这样加上车师前国人口6050人,加上车师都尉人口960人,北道的总人口为197357人,南道的人口我们计算的数字是104263人,二者之比为1.89∶1,与梁先生的数字有出入,而这个比例与今天南北人口之比基本相同。根据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册统计目前的比例是1.898∶1。这与两千年前南北道人口之比是非常接近。我们不妨把当今的南北道人口具体列出便可看得更加清楚。当今南道的人口是这样的:若羌县2.9万,且末县5.5万,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3.1万,和田市17万,和田县26.2万,墨玉县40.5万,皮山县21.6万,洛浦县23.6万,策勒县13.2万,于田县21.2万,民丰县3.2万,莎车县62.1万,泽普县17万,叶城县36.9万,麦盖提县20.2万,共计314.2万。而北道的人口是这样的:阿图什市20万,阿克陶县6.3万,阿合奇县3.4万,乌恰县4.2万,阿拉尔市17万,图木舒克市12万,喀什市32万,疏附县36万,疏勒县28.7万,英吉沙县21.3万,岳普湖2.9万,伽师县31.1万,巴楚县37.6万,阿克苏市52万,温宿县21.9万,库车县38.9万,沙雅县20.3万,新和县3.9万,拜城县19万,乌什县17.7万,阿瓦提县19万,柯平县3.8万,库尔勒市36万,轮台县9.2万,尉犁县10.3万,和静县17万,和硕县6.3万,博湖县6万,焉耆县11.7万,吐鲁番市14万,鄯善县19.7万,托克逊县10.2万,总计为588.6万,与南道的人口314.2万相比,其比值为1.87∶1。
上面的数据是塔里木盆地在西汉时期南北道人口的分布与南北道人口之比例,计算的结果,我们得出了一个两千年前后南北道人口比例基本不变的惊人结论。历经两千多年南北道的人口由三十来万增长到千万,增长了三十倍,但南北道人口数量的比例不变值得探讨,不变的原因是什么非常值得思考。是不是在一定生态条件下其容量是一个定值,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力的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是均衡的。若以塔里木盆地人口增长的比例看是不低的,西汉时期西域以东的中国人口的总量是6000来万,塔里木盆地的人口是30来万,约占千分之五,而今天塔里木盆地的人口是近千万,约占十三亿人口的千分之七点七。看来经过近二千年的变化,塔里木盆地人口增长的比例要大于塔里木盆地以东人口增长的比例,这说明塔里木盆地在一些方面的发展速度要快于内地。
关于塔里木盆地人口分布的地理问题,梁景之先生的文章共讲了四点,讲得很好。他认为有四种类型,这便是荒漠绿洲型,河谷山地型,荒漠草原型,盆地绿洲型。他认为荒漠绿洲型主要是指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以农为主的各国或地区,如且末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自且末以西诸国的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都基本相同。属于荒漠绿洲型的还有精绝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于阗居民从事农牧,多桑麻,龟兹居民主要务农,兼营畜牧,冶铸酿酒也很发达。疏勒居民从事农业,精工艺开采铜铁,姑墨居民以农为主兼营牧业,产铜铁。乌垒土地肥沃,莎车,扜弥,皮山等也是以农为主兼营畜牧,总之这种荒漠绿洲型诸国以农为主,人口较多。第二种类型的诸国是河谷山地型,人口稀少,多分布于天山、昆仑山及帕米尔等地区的河流谷地或高山低地一带,交通不便,多以牧业为主,如乌秅国,山居,田石间出小步马,有驴无牛。山国,民山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休循国,王治飞鸟谷,因畜逐水草。捐毒国,随水草,依葱领。西夜国其种类氐羌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蒲犁国,寄田莎车。依耐国与子合国俗相同,少谷,寄田莎车、疏勒。无雷国俗与子合同,从事游牧。尉头国田畜随水草。温宿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同。小宛,戎卢,渠勒皆处于高山谷地,即便今天也以游牧为主。第三种类型是荒漠草原型,此为人口地理分布诸类型中,人口最稀少的类型之一,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东部荒漠平原或荒漠高山坡地地带,如鄯善若羌等国,这些国家的人口基本以游牧为主,由于自然条件差,植被不好,所以人口也很稀少。第四种类型的是盆地绿洲型,此种类型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天山东部山间盆地,低地地区,水草丰茂土地肥沃,植被好,居民人口多,以农为主兼营畜牧业,如当时焉耆国居民务农捕鱼畜牧,直到今天其分布特点依然十分突出。
第三节 黑河流域古今生态的变化
黑河是我国的第二大内陆河。也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水系中最大的一支,发源于祁连山中,主要流经张掖,临泽,高台,嘉峪关,酒泉,金塔,再向北长途跋涉入内蒙的中外蒙之交处的居延海,全长约1000公里,横贯甘肃、内蒙两省。该地域古属雍州之地,战国秦汉时期此地为大月氏人的游牧地。西汉初年,由于冒顿单于的强大,匈奴人把大月氏人从祁连山逐出,成为匈奴昆邪王的牧地。到了西汉中期,汉王朝经过数十年之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大,为解除匈奴人对北部边防之压力,攘逐匈奴,在河西地区开设四郡,此地置张掖、酒泉二郡。张掖为张国臂掖之意,酒泉取其泉水众多味如美酒之意。清朝时设甘州、肃州直隶州。地当要冲,河山襟带为羌戎通驿之路,南有雪山嵯峨万仞,北有紫塞延袤千里,实为古代羌番入贡之要道,河西保障之咽喉。当今设有张掖市,辖一区五县即甘州区、山丹、民乐、高台,临泽、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以及嘉峪关市、酒泉市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有近10万平方公里。
(一)古代黑河流域的山体植被状况
从文献记载看,黑河流域的山体植被虽不如石羊河流域那么多名木名山,但亦相差不远,山体植被除松柏外,主要是美水茂草,是得天独厚的少有的广袤的牧场。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现根据《大清一统志·甘州府》和《大清一统志·肃州府》志的记载,将此二州所在的植被状况予以简述:
雪山:在张掖县南一百里,多林木箭杆。
临松山:在张掖县南,《隋书·地理志》:张掖有临松山,《寰宇记》:临松山,一名青松山,一名马踢山,又名丹岭山,在张掖县南182里。
祁连山:《西河旧事》言:山在张掖、酒泉二郡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一名天山。亦名白山。
焉支山:在山丹县东南,接凉州府永昌县界?《西河旧事》云: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括地志》: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
金山:在山丹县西南??《汉晋春秋》云:是年氐池县大柳谷口,激波涌溢,有苍石立水中,文曰:大讨曹。《十六国春秋》云:吕光龙飞二年,沮渠蒙逊起兵攻拨临松,屯据金山,沮渠蒙逊元始五年,祀金山,西入苕濯,遣将袭卑和,自率众为继,循海而西,复入金山而归。
龙首山:在山丹县西北二十五里边外??山阴有泉。
文殊山:在州西南三十里,两峰南北对峙,水泉中流??又有滥尼山,一名淖泥山,在西南百余里文殊山南,其山多水泉,地泞泥,故名。
榆木山:在高台县南四十里,上产榆树,故名,东起梨园,西尽暖泉,延长百余里。
白城山:在高台县西南八十里??林泉之胜。
合黎山:其山产茶,(在今高台县北)
以上我们引述的材料虽然不多,但可以看出苍松翠柏的图景。现在我们引述《肃州志·南山》的记述作为黑河流域植被状况的小结:“南山松百里,阴翳车师东,参天拨地如虬龙,合抱岂止数十围,拜爵已受千年封”,其间最古老之树“曾阅汉唐平西戎”。
(二)古代黑河流域的河湖状况
《嘉庆重修一统志·甘州府》记载该府中的两条较大的河流,其一是张掖河,其二是弱水。张掖河就是今日之黑河,汉代的羌谷水。《汉书·地理志》言其行程二千一百里,《括地志》还详细记载了张掖河的不同名称:一名鲜水、一名合黎水、一名复袁水、一名副投河,发源于吐谷浑界,流入居延海。另一条大的河流是弱水(山丹河),源于山丹县南,后与张掖河合。张掖河的支流,志书尚未记载的还有梨园河、洪水河、八宝河等。
除记载大河之外,府《志》还记载了当时州内的一些有名的泉水及宜牧之地所设置的牧马厂,大致有以下多处:
赤泉:张掖县东南。
甘泉:张掖县西一八十里甘峻山下,味甘冽。又城南门内东三十余步,亦有甘泉,北流出城,引以转皑。
蓼泉:在张掖县西??《行都司志》:萼泉在卫西九十里,都渎间在其西。
九眼泉:在张掖县西九十里。
草湖泉:在张掖县张掖河,两岸多生芦苇,每年收草百余万束以饲马。
暖泉:在山丹县东南四十五里,平地涌泉二穴,寒不冻,有大渠一,分闸五,共灌田七百一十八顷。
石井:在山丹县东八十里,其水常满,汲之不竭。《行都司志》:井出石峡口山下。
三十二井:在张掖县北边外,参差并列。
乐得故城:后为甘州,因州东甘峻山为名,或言地多甘草,故名。
昭武故城:在张掖县西北??晋改曰临泽。
删丹故城:本汉旧县,按焉支山一名删丹山,故以县名。
日勒故城:在山丹县东南,汉置,属张掖郡。《汉书·地里志》:日勒都尉治泽索谷,《赵充国传》:武威郡,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
祁连废郡:在张掖县西南??《晋书·地理志》:永和中,张祚置汉阳县以守牧地。
(三)古代肃州所设之牧马厂
永固城,在山丹县境,去府治东南一百八十里,有牧马厂。
洪水堡,在张掖县东南一百四十里,县南山场柏树湾有牧马厂。县东观音口内混泉,有甘州城守营牧马厂。
南古城堡,在张掖县南一百里,柳沟河有牧马厂。
梨园堡,张掖县南一百里,有牧马厂。
石峡口堡,在山丹县东八十里,有牧马厂。又独峰口,有山丹营牧马厂。
(四)《志》书中记载的肃州的具体的河湖
托来河,根据《舆图》所载,今托来河发源于州西南五百余里的番界中,有三大支流,最西者曰托来河,其西又有辉图巴尔呼河,北流百余里,与托来河合。又东北百余里有巴哈额齐讷二河,分流二百里许,合流,又北数十里与托来河混为一,又东北二百余里入边,绕州南至州东北合西来之水,又东北出边过金桥寺,稍折而北。又转东与张掖河合,又北五百余里入居延海。
红水,在州东南三十里,源出南山,北流合白水,入托来河,以水有红色故名。
白水,源出州西南二十里,下合红水。
沙河,在州东四十里,源出雪山,北流入托来河。
清水,在州北五十里,源出州西北清水泉,东流入托来河。
黑水,在州西北120里,源出黑水泉,会清水流。
放驿湖:在州东南一里,周六里余。
铧尖湖:在州东南二十里,有二湖,皆放牧之所。
郑家湖:在州北七里郑家堡前。
花城儿湖:在县北八十里,地属新城堡。
仓儿湖:在州北二十五里,俗谓之大湖场。
五霸湖:在高台县东十二里。
大芦湾湖:在县东北二十里。
黑家站家湖:在县东四十里。
鸳鸯湖:在高台县西十里。
七霸湖:在县西十五里。
月牙湖:在县西北五里。
高台站家湖:在县西北五里。
水磨湖:在县西北十里。
海底湖:在县西北十里。
苇荡湖:在县西北十五里。
狼窝湖:在县西北二十里。
李家湖:在县西北二十里。
官军湖:在高台县镇夷所城东南三里。
局匠湖:在城东南十里,旧为牧放之地。
夜不收湖:在城东北五十里,胭脂堡旁。
大湖:在高台县镇夷所西一里。
乌鲁讷湖:在城北边外五百里。
(五)历史上神秘而美丽的居延海
前面所述的黑河、张掖河就是今日之额济纳河,额济纳河经过周折之后最后注入居延海,古称流沙。《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均有记载。关于居延海在历史上的面积说法不一,但相差无几。杜海斌认为:
历史上的居延面积曾达到800平方公里(杜海斌:《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
而杜弋鹏则认为:
古居延海面积达720平方公里(杜弋鹏:《阿拉善尘暴:你在诉说什么》刊于《光明日报》1996年5月14日)。
总之水域面积相当壮观。古居延海面积的缩小是从宋朝末年开始的,但宋朝末年直到19世纪50年代仍维持在3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不变。杜弋鹏认为:
到宋朝末年,河水(指今之额济纳河)改道,逐渐消失后,形成的新居延海面积还有300多平方公里(见前注)。《人民政协报》记者李宏前往考察并于2001年10月31日发表在该报上的《额济纳绿洲面临消失险境》中指出:
“50年前,东西居延海分别有水面35平方公里和287平方公里”。
从中可以看到从宋朝末年到上午世纪50年代,历时近千年,居延海的面积相当稳定没有变化。居延海及其沿黑河两岸的植被被草丛和密林所覆盖。林学家董正钧早在19世纪40年代考察黑河时指出:
“南由狼心山老树窝起,北至河口,沿东西河及其支流两岸,直达居延海滨,均布满天然森林??红柳高达丈余,密生处,人不可入,一望无际方园数千里,堪称奇观。”对于额济纳旗生态环境的记述,马天鹤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篇幅颇多,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令人十分神往,我们不妨把他的日记摘录数篇於下:
(1926年)十月二十八日:
“起视林源,大数百亩,树数千株,可以说是额济纳的富源??此地水草肥美,草木繁盛??
沿河岸行,西望河边,胡桐树林延亘,一直数十里。”
(1926年)十月二十九日
“早起四望,见西面大林密布,细苇丛生,??十二时行,沿途硬沙,西面林更密,草更茂,一望无际,不知几千百亩??入晚,行数十里,穿林而过,草木益密。”
(1926年)十月三十日:
“下午一时行,沿途芨芨草高三、四尺,细苇杂生,一望皆是,不知几千百亩。”
(1926年)十一月二日:
“早起四望,周围全是树木,深密无际,十二时行,一路在密林茂草中穿过??非披荆斩棘不可,一直数十里,依然草木广茂,胡桐、柽柳等或则大数围抱,或则高五六丈,或则一丛方丈,甚至数丈,想见上古洪荒时代之景况。“(转引自杜海斌:《居延二千年历史环境的变迁》刊于《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从马天鹤先生所记载的额济纳之胡桐柽柳竟然能长到粗达数围抱,高则五六丈,可知经历了何等久远的年代,他所记载的这一区域为原始森林区是确定无疑的。
够了,无须我在这里再加总结,我们可以想象到20个世纪40年以前的额济纳是何等的诱人。
(六)额济纳旗绿洲林木面积的减少
据记载,早在50年前额济纳旗的绿洲面积是32万平方公里,而如今只剩下0.3万平方公里??以前额济纳旗入境的两条河流两岸的胡杨林有75万亩,红柳林225万亩,而如今减少到34万亩和150万亩。草本植物有130多种,如今只剩下不到30种(李宏:《额济纳旗绿洲面临消失的险境》,刊于《人民政协报》2001年10月3日)。
另据全国政协委员其仁旺其格的调查,分布于黑河下游额济纳境内以东、西居延海为主体的面积为2488平方公里的湖泊、盐化沼泽、芦苇湿地大幅度萎缩乃至相继消失。6500平方公里的绿洲已退化到3300多平方公里,113万公顷的梭梭林仅剩下38万公顷残林,50万公顷的天然次生林仅剩下294公顷残林,草场退化面积达334万公顷以上,植被覆盖率降低了30%、80%,沙化面积占总面积的85%以上??由于湖泊干涸,绿洲萎缩,植被退化沙漠扩大,沙尘暴发生次数增多,强度增大,危害加重,京津唐地区的扬沙、尘雾天气多源于阿拉善地区。目前其境内的三大沙漠每年以10米~20米的速度(折合约1000平方公里)扩展,人工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沙漠化程度(其仁旺其格:《阿拉善生态建设任重道远》载于《人民政协报》2004年4月6日)。
山丹军马场山坡牧场的灌木林在1964至1984年20年间,因开荒种地和超负荷放牧被毁面积达37600亩以上,祁连山草场现在普遍出现了草原退化,如肃南县草场退化面积已达1068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50%,军马场退化草场达658461亩,占整体可利用草场的38.5%,黑河流域沙漠化发展速度达到年均2.6%~6.8%(程国栋:《论干旱区景观生态特征与景态生态建设》载于《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1期)。
(七)黑河流量减少,湖泊干涸
据《理论研究》1999第1期所载王芳、秋才的《西部各地区间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可知,20世纪50年代黑河水流入额济纳的水量在12亿立方米~13亿立方米左右,60~70年代至少也保持在10亿立方米以上,能基本维持额济纳旗生态平衡和人民生活用水。80年代以后,由于上游用水剧增,黑河入旗水量锐减至4亿立方米,枯水年仅有2亿立方米,1992年再减至1.83亿立方米。据记者李宏观察到情况是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黑河流入额济纳的水量减少了44%,河道断流期由原来的100天延长到200多天,流域内30多条支流先后消失,东,西居延海等12个大小湖泊完全枯竭(西居延海1961年干涸,东居延海于1973年、1980年、1986年三次干涸、变成一个间歇性湖泊,到1992年彻底干涸)。16个泉眼,4个沼泽地完全消失,370万亩的原水域变成了盐碱滩。
河水断流、湖泊之于涸给沿岸居民带来了灾难。据《光明日报》1996年5月14日所载杜弋鹏的《阿拉善尘暴你在诉说什么》一文所载,1988年到1995年间沿河的吉日嘎郎图、苏古淖尔、赛汉桃来三个苏木地下水位平均降低111米,远离河道的地方,水位下降程度可想而知了。有关部门调查发现,沿河牧区1548眼简井中的1018眼干枯了,许多农户只好到十多里外去取水。
居延海干枯之后,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维持生态系统的各种生物的衰竭与死亡,沙漠化急剧发展,特别是在额济纳旗狼心山以北东西两河下游三角洲上,植被退化和沙漠化十分严重,天然生长的乔、灌、草三层结构,逐渐演化为二层,单层,甚至全部枯死,裸露的地面和松散的河流沉积物不断遭受风力的侵蚀,在风力的作用下原先繁茂的河岸植被在一侧堆积成胡杨、红柳沙包。河道干涸后,胡杨、红柳因失去水分供给逐渐枯萎死亡。古老的居延绿洲正面临着一场灭顶的生态灾难,那些半流动、流动的沙包正逐渐吞噬着千百年来人类居住的家园。据兰州沙漠所1986年调查,额济纳旗仅绿洲地带内沙漠化土地就达26362.5平方公里,占绿洲面积的87.2%(见吴晓军:《西北生态启示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42页)。
第四节 准噶尔盆地古今生态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首先把清代方志中所记载的有关情况简述於下:今日之乌鲁木齐,清代名迪化,它当时所管辖的区域内民丁男妇大小共103052名口,统计12028户。其山川河流泉水及植被情况远优于今日。《志》载:阿拉癸山,在州南70里,山深林密险窄难行。
阿察河:在州东,有三泉,出天山北麓,北流50里,汇为一河,余波入于沙碛。
阿勒塔齐河:在州南,源出乌可克岭北麓,分二支,夹州城各北流,入于地,其西南有三水并来入之。
昌吉河:在州西昌吉县南......,有四支合而北流。
罗克伦河:在州西昌吉河之西,有二源,西北流入於呼图克拜河。
呼图克拜河:在州西,当孔道,有五源出天山北麓,会诸河,会于额彬格逊淖尔。
图古里克河:在州西,源出巴颜哈玛尔山。
哈齐克河:在州西,有三源......
玛纳斯河:在州西绥来县治之西境,有五源......入额彬格逊淖尔。
和尔郭斯河:在州西......
安济哈雅河:在州西,凡三源,东北流一百一十里,逾孔道北渚为小泽。
察罕水:在州东。
乌兰水:在州东。
多伦水:在州东。
库里叶图泉:在州东。
纳里特泉:在州东。
铿格尔泉:在州东。
必柳泉:在州东。
多博绰克泉:在州东。
济尔玛台泉:在州东。
乌里雅苏台泉:在州东。
阿克塔斯泉:在州东。
额彬格逊淖尔:在州西北会呼图克拜河、玛纳斯河、乌兰水诸流咸集,周可五十余里,一巨泽也。
鄂伦淖尔:在州西北,亦曰达布苏淖尔,南距城四十里,周十里许,其东别有小池。
以上所引《志》书所载清朝时期迪化州内的山水泉林,有许多今日已不复存在了。中央党校出版社所出版的奚国金先生的著作名为《西部生态》,言及出版于清朝光绪乙未年(1895年)的《皇朝省直地舆全图》,较为清楚地绘制了新疆一百多年前的地理景观。从图上可以看出,当时新疆的河流较今日多、流程也比较长,例如天山北坡的一些河流相互流通,形成了5个主要水系,东部木垒以东的河流都流入巴里坤湖,形成了巴里坤水系,奇台与乌鲁木齐之间的河流汇入乌鲁木齐北部的东道海子,形成了东道海子水系,乌鲁木齐到屯奎之间的河流以及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的河流,都流入玛纳斯湖,形成了玛纳斯水系,屯奎以西的河流汇入艾比湖,形成了艾比湖水系。然而到了今天,这些河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河流流程变短,湖泊缩小或干涸。如天山北坡的第一大河玛纳斯河,比以前缩短了100公里,它的尾闾湖玛纳斯湖已经干涸,天山北坡的原先的五大水系现在已经变成独立的十几条小河。再以艾比湖盆地来说,它位于天山北坡西端,是西来气流进入新疆的最重要的孔道,艾比湖盆地的中心是面积约560平方公里的艾比湖,根据调查,艾比湖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湖水面积是900多平方公里,由于上游地区引水开荒种田,流到湖里的水量很快减少,导致湖水面积缩小。艾比湖盆地西高东低,湖水东深西浅,湖水面积缩小后,西部湖底大量的沉积物盐类裸露在地表,每当大风吹来湖底的盐类物质形成盐尘,飘散在空中,??在天山北麓西段已经形成了一条盐尘污染带。
第五节 塔里木盆地古今生态的变化
塔里木盆地从西到东贯穿一条大河,那就是我国最长的一条内陆河塔里木河。塔里木河的上游有四条主要的河流,那便是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和阿克苏河,这四条河流汇合后向东便进入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干流的总长度约1300多公里。注入罗布泊。罗布泊的水域面积很大,罗布泊向东的延伸处可能与疏勒河的尾涧湖相接近,不然的话,《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均言及玉门关距蒲昌海的距离是300里。如《汉书·西域传》载: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不但《汉书》有这样的记载,而《后汉书·西域传》也认为蒲昌海距玉门三百余里。奚国金的《西部生态启示录》第43页曾言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下游盆地流入神秘的罗布泊的说法。刊于《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上的张莉同志的《西汉楼兰道新考》认为:古代疏勒河河水丰盈,在大灞冲击扇缘洼地内,曾汇集成广阔的河道湖泊,汉代称之谓冥泽,唐代称之谓大泽,其东西长达260里南北宽有60里,唐代疏勒河由此得名为冥水。出冥河,河水继续向西,汇聚疏勒河下游最大的支流党河,党河汉代称为氐置水,党河在敦煌以北冲积扇北缘洼地,有众多泉水出露,与疏勒河下游河道相通,向西一直进入甘新边境的榆树泉,其再向西与罗布泊湖盆向东伸出的一个湖湾阿克奇沟谷相连。我们之所以引用上面那么多资料,目的是想证明古代罗布泊水量之大。不然的话,《汉书》、《后汉书》均言及玉门关距罗布泊只有300里,很有可能它们的水系相通。
以上所引资料足以说明塔里木河在古代水量是相当丰沛的,遗憾的是如今的塔里木河已今非昔比。据奚国金先生所著《西部生态》所载:塔里木河主要源流有三支,这便是和田河,叶尔羌河、阿克苏河,如今和田河、叶尔羌河已无水汇入塔里木河,阿克苏河成为塔里木河目前唯一的源流。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塔里木河上游每年向下输送的水量约32亿立方米,到达中游时,水量减少到18亿立方米,到下游时水量锐减到约2.4亿立方米,这些水只能向下再流约230公里,到达大西海水库,再向下游,塔里木河已经干涸,下游约200公里河道断流。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之后,使得原本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进一步破坏,区域生态环境趋向恶化,沿塔里木河下游原本生长有大片的胡杨林和其他植物,它形成了分隔塔里木河下游库鲁克库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绿色走廊,绿色走廊有通往新疆东南部的便捷通道218国道,计划中的新疆至青海铁路也将从这里通过,绿色走廊还有效地减少了由强劲东风携带的沙尘,保护了库尔勒等地处下风位置城市的生态环境。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后沿河的胡杨林逐渐衰亡,林下的灌木和草已经全部死光。218许多路段被流沙埋没,通行困难,人们担心,有朝一日,库鲁克库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会连为一体。昆仑山北麓山前绿洲区的变化也是十分巨大的,和田地区是新疆受沙漠化威胁十分严重的地区,据说近百年来这一地区新产生的沙漠土地面积达8600平方千米,近30年来被流沙吞没的农田就达三十万亩。
第六节 祁连山北麓人居生态环境的变化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一二六号发言材料刊登的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慧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加强祁连山北麓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的建议》,文中谈到目前祁连山北麓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天然林缩减,功能削弱。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22.4%下降到现在的13.8%,森林林带由建国初期的1900米退缩至230米,如今浅山区森林已基本消失;灌木生长下限比20世纪50年代上移约60米,30%的灌木已草原化,灌木盖度和高度分别下降了35%和20%。二是草场退化,生产力下降。祁连山北麓445.6万公顷草地,退化面积已达26%、盐碱化面积达4.09%、沙化面积达7.13%;水土流失面积达20.12%。可食牧草比重与1983年相比下降18%,每个羊单位需草面积由1983年的7亩增至目前的8至16亩;一、二等草原面积比重与1983年相比下降22个百分点。三是河道干涸,水源匮乏。由于祁连山水源涵养功能减退,大小河流水量减少,枯水期延长,前山地带部分河流流程缩短,河岸植被稀疏,河道沉积沙石,旱则洞,涝则泛,山洪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下游凹地天然植物枯死,沙漠化趋势加剧。有调查表明河西地区沙化土地面积达到1671.14万公顷,较1999年增加59.24万公顷。四是冰川萎缩,雪线上升。据甘肃省气象科研所冰川考察资料,祁连山现有雪线比古雪线升高500至800米,祁连山冰川融水比20世纪70年代减少了大约10立方米,局部地区的雪线正以年均2米至6.5米的速度上升,导致积雪面积明显减少。据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冰川的平均退缩速度东部为16.8米/年,中部为3.3米/米,西部为2.2米/年,远超过海洋性冰川的一般退缩幅度。有些专家预言,面积在2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型冰川将在2050年前基本消亡。五是生物种类减少,病虫害蔓延。高山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的退化和山区径流的减少,加剧了山区小气候的变化,长时间的干旱少雨,使祁连山森林景观渐呈破碎状,野生动物栖息地遭破坏,导致一些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特别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珍稀野生动物如马麝、雪豹、野牦牛、白唇鹿等处于濒危、灭绝状态;植物中原始的高大乔木植物种类也在逐年减少。20世纪以来,祁连山北麓的青海云杉林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针叶发黄,长势衰弱、病虫害严重等问题,每年发生各类森林病虫害3.4万公顷,占林地面积的30.6%,严重的地段部分林木成片死亡或趋于死亡。
第七节 人与生态的平衡问题
在人对自然的认识上,在生态问题上,人们对其规律还不能全部了解。人们为了生存得拥有和开发资源,有些地方的资源可以开发,有些地方的资源可以适度开发,有些地方的资源是绝对不允许开发,利在当代的工程并不一定都能功在千秋。历史上这些例子太多了,其留下来的恶果我们现在还在品尝,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汉武帝对西北地区的屯田开发,虽然减轻了转输之劳,保障了屯田将士的粮食供给,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屯田破坏了草原植被,肇启了沙漠化的先河。当代中亚地区开发所造成的后果值得我们借鉴:位于中亚地区的咸海周围属于干旱地区,在苏联的农业生产上居于重要地位,其棉花产量占前苏联的95%,水果占1/3,蔬菜占1/4,稻谷占40%,由于气候干旱,90%的农田依靠灌溉。随着生产的发展,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上,挖掘了一系列的运河以引水灌溉。水浇地从50年代的290万公顷发展到750万公顷,引水量大增,入湖水量大量减少,在30年中,使咸海湖面缩减了40%,贮水量减少了67%,湖平面下降了14米。湖水退缩后,使30000平方公里的湖底出露,变为沙漠??当地70%~80%的动物灭绝,随着湖水容量的减少,水中含盐量增加2倍,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本地鱼种已完全绝迹,渔业也随之凋零,干涸湖底的含盐尘土被风吹扬至附近的农田,使作物减产,农民为了维持农作物的产量而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污染地下水,环境质量的恶化,导致许多疾病的流行。据报道:像传染性肝炎,伤寒、黄疸、肠道感染和癌症等病例均明显增多,发育不全和婴儿夭折的比例都很高。大风还把灰尘、盐分和风干了的农药颗粒吹扬至几百公里以外,西达里海,北达北极圈内。(见杨子祥:《冷静看待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刊于《人民政协报》2001年9月4日第6版)。位于我国西部的新疆、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与咸海流域的中亚地区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地理气候条件,苏联的生态灾难——咸海周围开发的前车之鉴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由此看来,荒漠化并非大自然的恩赐,恐怕是人类自酿的一杯苦酒。恩格斯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消失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培育地保护的森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恩格斯的话对我们很有启示,西北地区解放以来所发生的巨大的生态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新疆的最大生态变化莫过于罗布泊的干涸。《水经注》是这样记载罗布泊的:
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故蒲昌海亦有盐泽之称也。《山海经》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者也,东至玉门阳关千三百里,广轮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其中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当其寰流之上,飞禽奋翮于霄中者,无不坠于渊波矣。即河水之所潜,而出于积石也。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大的水面的湖泊却于1972年彻底干涸。无独有偶,就在罗布泊干涸这一年,黄河出现断流,这在黄河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此后黄河几乎年年断流。为什么罗布泊的干涸与黄河的断流发生在同一个年份?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古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黄河的发源地是昆仑山,流到罗布泊汇成一个很大的水面,约有20000平方公里,然后从积石山潜流复出奔向大海。即从罗布泊到积石山是潜流,是无形之河。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
1.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对罗布泊有明确的记载,认为是“河水之所潜也”,即这里的水潜行地下,通过暗流东出形成黄河。如《山海经》云:“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坳泽(即罗布泊),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
2.《尚书·禹贡》篇云:“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3.《史记·夏本纪》是这样记载的:“道九川??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唐朝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这句话是这样注释的:“《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州伊吾县北百二十里’,其黑水源在伊州,从伊州东南三千余里至鄯州,鄯州东南四百余里至河州,入黄河。河州有小积石山,即《禹贡》‘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者。然黄河源从西南下,出大昆仑东北隅,东北流经于阗,入盐泽,即东南潜行入吐谷浑界大积石山,又东北流,至小积石山,又东北流,来处极远。其黑水,当洪水时,合从黄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张守节在注释“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这句话时,谈到了河源问题,认为河源是出自昆仑山,流经于阗,入于盐泽,然后潜行地下,经吐谷浑(即今青海地区)而达于大积石山(概指今天的巴颜喀拉山北麓)然后向东北流至于小积石山(概指今日甘肃省东南积石山脉)。
4.唐代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用《尔雅》的说法也认为河源出自昆仑。他在注释《史记·夏本纪》时引用《汉书·西域传》云:“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其水停居,冬夏不减,潜行地中,南出积石为中国河。”是河源发昆仑,禹导河自积石而加工焉。
5.《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河发于昆仑:“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对于《大宛列传》中的这句话,唐朝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唐朝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都分别有注释。《史记正义》云:《汉书》云,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山为中国河。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案:《汉书·西域传》云,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山海经》云,河出昆仑东北隅,郭璞云,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山于阗国,复分流歧出,合而东注坳泽,已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坳泽即盐泽也,一名蒲昌海。
6.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认为是河出昆仑,上面已有引文这里不再赘述。
自郦道元之后,唐代人有考河源者,元代人亦有多次考河源者,到了清代更是如此。康熙帝、乾隆帝都曾多次派人考察河源。如阿弥达受乾隆之命考察河源,从青海到罗布泊,他认为罗布泊的水源来自60多条河流,罗布泊东西长200里,南北宽100多里,他认为该湖是黄河之源的上游(引自《罗布泊》)。徐松是十九世纪人,进士出身,他作了《西域水道记》,在文中言说“昆仑之墟,黄河初源于此焉”。还说“罗布淖尔者,黄河初源所湾畜也”。《大清一统志·黄河》云:“源出清海之极西境,自回部罗布淖尔伏流重发,名阿尔坦河,流入鄂敦他腊,挟扎楞、鄂楞两淖尔水,东南流,折西北又转东北,历二千七百余里,至积石关,入甘肃河州界”。
对河源的认识也有不同的看法,《元史·地理志》载,在元朝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时,任命都实为招讨史,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受命之后,当年到河州,从这里出发,经过四个月才达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后来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临川朱思本又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画,而以华文译之,与昂霄所志,互有详略。总之,他们认为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站在高山往下看,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刺脑儿,这大概就是常说的扎陵湖和鄂陵湖。
以上罗列不同的河源说,《大清一统志》对各家看法给以总结,并得出一个倾向性的结论:“本朝威德远布,幅员广大,边徼荒服,皆隶版图。我圣祖仁皇帝遣使臣,往穷河源,测量地度,绘入舆图,凡河源左右,一山一水,与黄河之形势曲折,道理远近,靡不悉载,较之元人所志又加详焉。今依地理今释,参考舆图,及青海山川册说,著其大略如此。按旧志序述河源,以阿勒坦河,在鄂敦他腊之上,与今日考订情形,颇相吻合。惟未著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及天池上之黄水,又未悉回部和田叶尔羌初发之源,伏于蒲昌海,重复于阿勒坦河。盍其时回部未定,考验靡因,今日西域青海,偏隶版章,大河真源,近在户闼。高宗纯皇帝命我穷考,圣制诗文,详晰指示。汉张骞所之云,二水交流,发葱岭于田,伏盐泽而重发积石者为说是而其文太略。元笃什所穷鄂敦他腊以下,地位近是,而未悉黄水真源及西域之伏流。盖大河原委,至今日而始备其实焉,今并存元史及旧志原文,而考定其说如此。”
上面我们探究了河源的两种不同说法,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大部分人承认无形之河的存在,即暗河的存在,而部分人探明的是有形之河,所存在的分歧究竟是有没有潜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考证从罗布泊到星宿海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潜流,而目前还没有人考证这个问题。但目前有人考证了巴丹吉林沙漠有条地下河。《人民政协报》2004年11月30日刊载一条消息,言说巴丹吉林沙漠惊现地下河,11月25日英国《自然》杂志432卷发表了来自河海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论文指出,中国西北阿拉善高原的巴丹吉林沙漠下隐藏着大量的淡水资源,其与500公里外的祁连山冰川积雪之间,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调水通道——祁连山深大断裂。这件事说明了地下是存在有暗流的,而且里程有500多公里,古人认为从罗布泊到星宿海之间有条暗河。不知有什么根据和理由。从地图上看,罗布泊到星宿海之间的直线距离也不过七百公里,目前还没有文章排除暗流的存在。总之,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牵扯着一个生态的大问题。因为自从罗布泊干涸后,黄河几乎年年断流。如果罗布泊与黄河之间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应当恢复罗布泊即恢复生态系统。(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常剑峤先生的《祖国的奇山异水》一书)。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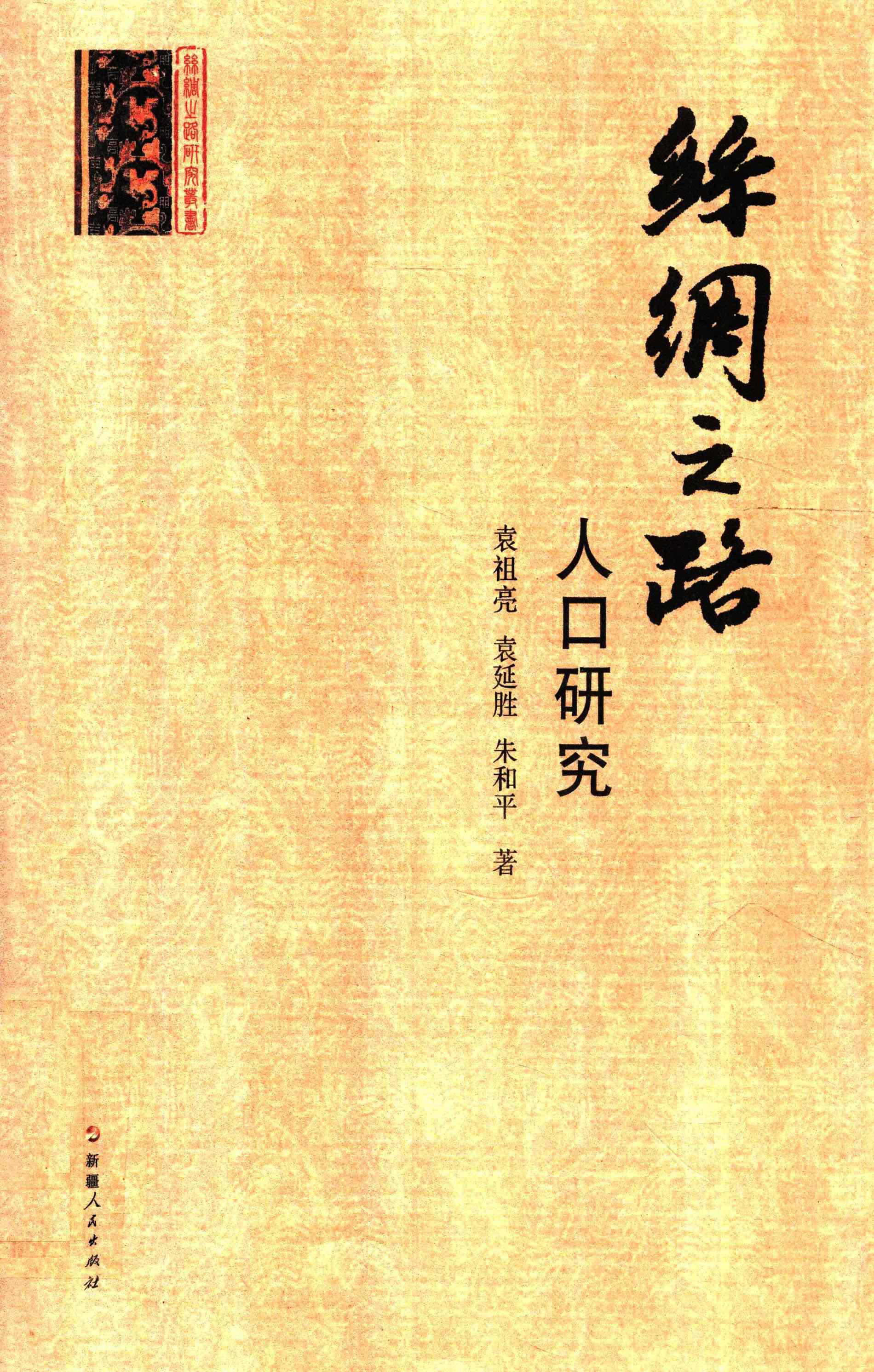
《丝绸之路人口研究》
本书主要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问题,五代、宋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问题,元朝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问题,明朝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口问题,丝绸之路人居生态环境的变迁等内容。“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汇集了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丝绸之路各学科领域研究成果,是国内最权威、最全面、最系统的学术著作。《丝绸之路人口研究》内容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人口、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