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醉圆双媚靥——西域妇女化妆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服饰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921 |
| 颗粒名称: | 第十三节 醉圆双媚靥——西域妇女化妆 |
| 分类号: | K892 |
| 页数: | 5 |
| 页码: | 139-14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西域妇女化妆的情况。其中包括面部的修饰、额面的修饰、眉的修饰等。 |
| 关键词: | 西域 妇女 化妆 |
内容
化妆术的运用,可追溯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的先辈曾用鲜红茜草的汁液涂在动物骨片上来装饰自己,于是渐渐产生爱美的观念。殷纣时期已有燕支(胭脂)。《战国策》曰:“周郑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间之间。”宋玉之《大招》中即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长袂拂面,善留客只”。叙述古人不仅以粉敷面,还用青墨画眉。关于国外化妆术传闻更多,传说古代埃及为了敬奉神明,每天要沐浴,净身后还要梳头染发。
西域妇女爱敷粉、点丹、朱唇、妆靥,艳美不绝,其演变千姿百态,它不同于内地汉妆,有着后世所鲜为人知的化妆术。
西域各族妇女对于化妆特别重视,仅从南北疆出土的各式铜镜,即可说明其重视程度。各种铜镜往往从千万里之遥的内地传入西域,在交通不便的路途中历经了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说明边陲人民对于仪容修饰的迫切需要,反映出当时人们崇美意识的发展情势。铜镜既便于仪容的修饰,又促成化妆术有物可鉴。
素面铜镜发掘于新疆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古墓。镜面直径仅6厘米,重46.9克,呈圆形。这种素面铜镜是我国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一种制作轻巧、镜背面无纹饰的小细钮照镜。战国时期,铜镜作为社会时尚在中原地区盛行,开始由素面向花样纹饰发展,一扫前期古拙质朴之风。铜镜的出土,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汉文化已在边疆西部地区产生影响。
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铜镜,铸刻有铭文“君宜高官”,它造型绝妙,时至今日,铜镜仍光泽如新,好似镀上一层金属。此外,南北疆均出土不少铜镜,在此不一一列举。
下面,本文拟对几种类型,仪容修饰的美的形态,以及饰面、饰额、饰眉的方法与化妆的审美心理与造型作一些介绍和阐释。
面部的修饰
前额与面颊是面部化妆的主要部位。
新疆民丰县尼雅东汉墓中曾出土了内装铅粉的粉袋、胭脂包。实物的出现,印证了当时西域妇女使用铅粉敷面颊,以白皙为美的审美时尚的事实。刘勰《文心雕龙》曰:“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铅粉敷面,不仅增白皮肤,且使姿容貌美、淑丽。
化妆样式,代有更迭。随着社会生活日趋丰富,尚美心理更为强烈,妆面也不断变化,如绢画中的俏丽女子面部不仅施粉,而且两颊侧面施斜红,额间施花钿。如唐代罗虬在《比红儿》中描绘:“一抹浓红傍脸斜。”红扑扑的脸儿令人垂爱。
尚美不仅体现在面颊上,那嘴角两旁的点丹也倩丽多姿,谓之“妆靥”。额间的花钿、两颊斜红与红靥,合称为“花靥”。如元稹诗:“醉圆双媚靥。”少女化妆如鲜花怒放,如醉如痴。司空曙《观妓》曰:“翠蛾红脸不胜情。”古人诗词中都赞颂了追求面颊敷红的形色之美所给予的感官上的审美满足。
《弈棋图》中的那位贵妇与侍女,都施以红粉妆、桃花妆、香扑扑、红艳艳的如鲜花怒放。几位妇女脸颊也施胭脂,颊面两侧只涂上圆圆的红心,没有敷施满面,颇有特色,与朴素淡雅的衣着相衬,自有一种淳朴的美。彩绘女子俑的妆面艳丽俊俏,面额贴花钿,两颊涂斜红,嘴角两侧点妆靥,正如欧阳炯诗中所云:“满面纵横花靥”,脂粉味极浓的妆靥,动人心旌,醒人眼目,反映了西域女性化妆的独特之美。
贴花钿、涂斜红、点红靥在化妆程序中是较为复杂的,但是,俑几乎都是“花靥妆”,反映了当时社会世俗妇女的偏爱。王建《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中描述:“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人初贴,蛱蝶重飞样未传。况复萧郎有情思,可怜春日镜台前。”不仅将妆靥化妆先敷粉的感受,以及色泽的浓艳,质地的轻薄,叙述得既细腻又明白,还将为了化好妆,要耐住性子不厌其烦的心理状态描述得很细致。
脸敷胭脂,红红艳艳,为多数妇女所青睐。胭脂是我国妇女常用的化妆品,一直延续到现今仍受欢迎。
额面的修饰
额面,即指前额部位,它与发型的修饰关系密切,也是面部化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几种西域时期额面化妆的不同样式中,即可窥见西域人独特的面饰艺术。
前额三道彩妆 西域妇女对前额的修饰颇为重视。前额化妆有其鲜明的独到之处。在新疆罗布泊北岸古墓(相当于汉代)出土一具女干尸,她全身裹毡毯,头戴毡帽,足穿皮靴,在前额明显地绘出红绿彩三道,勾勒出古罗布泊女牧民美丽的形象与独特的风韵。前额赋彩鲜明,重视形象的色彩美,从物色美化发展到构形的巧妙。三道彩化妆不失自然,人工天巧,不着痕迹。
前额饰白毫的佛像妆 前额中心饰白毫是佛像化妆。它与头光、头顶发髻一样是一种佛教庄严、神圣的象征。但是,在龟兹库木吐拉新2窟13尊乐舞菩萨造像的前额上,那白皙的眉心中心显现一个红色圆点,好似是对佛像中白毫面饰的一种模仿妆。
前额花钿妆 花钿妆是一种独具韵味的妆式,它又名花子、媚子,施于前额眉心。刘禹锡曾赋诗曰:“安钿当妩眉。”花钿妆呈现出妩媚姿色。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绢画、彩俑的造型,可以清晰地看到前额施花钿妆。花钿的颜色有红、绿、黄三色。红色多为点丹式的,如《酉阳杂俎》曰:“诸嬖人欲要宠,皆以丹脂点颊。”复杂的花钿妆,大都用红纸剪成锥形、菱形、梅花瓣形,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定婚店》中有这样的描述:“眉间常贴一钿花,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说明剪贴的花钿不易退去。
绿色的花钿叫“翠钿”。如《弈棋图》中那位侍女,她前额点一圆形绿色翠钿。唐代杜牧在诗中曾有描绘:“春阴扑翠钿。”温庭筠词中也有“眉间翠钿深”的描绘。唐代诗词中出现花钿的描写,说明当时社会仕女化妆实有其事。以花钿饰面,不仅使面部容光焕发,且呈现鲜丽色调。
前额鹅黄妆 鹅黄妆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北朝诗人江洪赋诗曰:“薄鬓约微黄。”它是一种用黄粉涂于前额的妆式。也有用黄纸剪成星星、月亮、花卉、鸟尾形贴于前额,谓“贴黄”。《木兰辞》中巾帼英雄花木兰解甲回乡后,在闺房中就有化妆的描写:“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就是鹅黄妆。这种妆始自南北朝,盛行于唐代。唐代吴融诗中曰:“眉边金失翠,额畔半留黄。”裴虔余诗中曰:“半额微黄金缕衣。”鹅黄妆彩艳浓华,呈现新美色调。
额前鹅黄妆反映了古人化妆审美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它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而演进。在高昌吐峪沟古遗址发掘的绢画上,那位乐舞仕女,身着彩锦窄袖胡装,头梳回鹘髻,额上饰黄星靥子,这种妆靥是当时流行的鹅黄妆。她那丽质色艳的感性面饰美,同样使人获得一种审美愉悦。
眉的修饰
眉在化妆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似与人的性格有着内在关联。唐代诗人李白曰:“眉语两自笑。”道出了眉的化妆与人的神态、性格相关的真谛。
西域妇女描眉,传说源远流长,但实物资料缺乏,仅从旁证材料中得到线索。吴妍春《民俗与考古》①一文中曾引用原苏联学者B.M.萨里安吉讲述中亚地区盛行描眉习俗的《古代大夏》②一文中,提到过远在公元前2000年的造型优美的化妆瓶。这种阔圆腹、高管颈、扁平环形口的小瓶中,往往插着一根顶端为动物形纹样的小棍。萨里安吉认为,它是用于画眉的化妆瓶。无独有偶,在新疆博物馆现代民俗展厅塔塔尔族展品中,有两个造型类似于大夏一带出土的金属画眉瓶,不同之处仅是画眉棍顶端纹样是花卉形状。文物的发掘说明新疆居民与中亚有着文化交流的往来。
新疆佛教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飞天、乐伎菩萨等人物形象造型,大多是细长的柳叶眉。如同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诗中描绘的那样:“青黛点眉眉细长”,墨黑而细长,柔曲波动,很助眼神。后来发展成一种短而阔的眉形,它浓密而短阔,在李贺诗中也有描写:“添眉桂叶浓。”形容眉如桂叶,作短阔之形。《弈棋图》中那位贵妇与侍女,即描阔叶眉。浓黑短阔衬托那丰腴的圆脸,越显雍容华贵,浓丽艳美。
西域妇女化妆早为世人所瞩目。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胡妆也流传至中原,成为妇女崇尚的世时妆。尚美成为历史流变中反映的一种审美内涵,尚美形式的美感积沉着一定的社会内容,内含时代精神特色。
西域妇女爱敷粉、点丹、朱唇、妆靥,艳美不绝,其演变千姿百态,它不同于内地汉妆,有着后世所鲜为人知的化妆术。
西域各族妇女对于化妆特别重视,仅从南北疆出土的各式铜镜,即可说明其重视程度。各种铜镜往往从千万里之遥的内地传入西域,在交通不便的路途中历经了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说明边陲人民对于仪容修饰的迫切需要,反映出当时人们崇美意识的发展情势。铜镜既便于仪容的修饰,又促成化妆术有物可鉴。
素面铜镜发掘于新疆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古墓。镜面直径仅6厘米,重46.9克,呈圆形。这种素面铜镜是我国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一种制作轻巧、镜背面无纹饰的小细钮照镜。战国时期,铜镜作为社会时尚在中原地区盛行,开始由素面向花样纹饰发展,一扫前期古拙质朴之风。铜镜的出土,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汉文化已在边疆西部地区产生影响。
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铜镜,铸刻有铭文“君宜高官”,它造型绝妙,时至今日,铜镜仍光泽如新,好似镀上一层金属。此外,南北疆均出土不少铜镜,在此不一一列举。
下面,本文拟对几种类型,仪容修饰的美的形态,以及饰面、饰额、饰眉的方法与化妆的审美心理与造型作一些介绍和阐释。
面部的修饰
前额与面颊是面部化妆的主要部位。
新疆民丰县尼雅东汉墓中曾出土了内装铅粉的粉袋、胭脂包。实物的出现,印证了当时西域妇女使用铅粉敷面颊,以白皙为美的审美时尚的事实。刘勰《文心雕龙》曰:“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铅粉敷面,不仅增白皮肤,且使姿容貌美、淑丽。
化妆样式,代有更迭。随着社会生活日趋丰富,尚美心理更为强烈,妆面也不断变化,如绢画中的俏丽女子面部不仅施粉,而且两颊侧面施斜红,额间施花钿。如唐代罗虬在《比红儿》中描绘:“一抹浓红傍脸斜。”红扑扑的脸儿令人垂爱。
尚美不仅体现在面颊上,那嘴角两旁的点丹也倩丽多姿,谓之“妆靥”。额间的花钿、两颊斜红与红靥,合称为“花靥”。如元稹诗:“醉圆双媚靥。”少女化妆如鲜花怒放,如醉如痴。司空曙《观妓》曰:“翠蛾红脸不胜情。”古人诗词中都赞颂了追求面颊敷红的形色之美所给予的感官上的审美满足。
《弈棋图》中的那位贵妇与侍女,都施以红粉妆、桃花妆、香扑扑、红艳艳的如鲜花怒放。几位妇女脸颊也施胭脂,颊面两侧只涂上圆圆的红心,没有敷施满面,颇有特色,与朴素淡雅的衣着相衬,自有一种淳朴的美。彩绘女子俑的妆面艳丽俊俏,面额贴花钿,两颊涂斜红,嘴角两侧点妆靥,正如欧阳炯诗中所云:“满面纵横花靥”,脂粉味极浓的妆靥,动人心旌,醒人眼目,反映了西域女性化妆的独特之美。
贴花钿、涂斜红、点红靥在化妆程序中是较为复杂的,但是,俑几乎都是“花靥妆”,反映了当时社会世俗妇女的偏爱。王建《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中描述:“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人初贴,蛱蝶重飞样未传。况复萧郎有情思,可怜春日镜台前。”不仅将妆靥化妆先敷粉的感受,以及色泽的浓艳,质地的轻薄,叙述得既细腻又明白,还将为了化好妆,要耐住性子不厌其烦的心理状态描述得很细致。
脸敷胭脂,红红艳艳,为多数妇女所青睐。胭脂是我国妇女常用的化妆品,一直延续到现今仍受欢迎。
额面的修饰
额面,即指前额部位,它与发型的修饰关系密切,也是面部化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几种西域时期额面化妆的不同样式中,即可窥见西域人独特的面饰艺术。
前额三道彩妆 西域妇女对前额的修饰颇为重视。前额化妆有其鲜明的独到之处。在新疆罗布泊北岸古墓(相当于汉代)出土一具女干尸,她全身裹毡毯,头戴毡帽,足穿皮靴,在前额明显地绘出红绿彩三道,勾勒出古罗布泊女牧民美丽的形象与独特的风韵。前额赋彩鲜明,重视形象的色彩美,从物色美化发展到构形的巧妙。三道彩化妆不失自然,人工天巧,不着痕迹。
前额饰白毫的佛像妆 前额中心饰白毫是佛像化妆。它与头光、头顶发髻一样是一种佛教庄严、神圣的象征。但是,在龟兹库木吐拉新2窟13尊乐舞菩萨造像的前额上,那白皙的眉心中心显现一个红色圆点,好似是对佛像中白毫面饰的一种模仿妆。
前额花钿妆 花钿妆是一种独具韵味的妆式,它又名花子、媚子,施于前额眉心。刘禹锡曾赋诗曰:“安钿当妩眉。”花钿妆呈现出妩媚姿色。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绢画、彩俑的造型,可以清晰地看到前额施花钿妆。花钿的颜色有红、绿、黄三色。红色多为点丹式的,如《酉阳杂俎》曰:“诸嬖人欲要宠,皆以丹脂点颊。”复杂的花钿妆,大都用红纸剪成锥形、菱形、梅花瓣形,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定婚店》中有这样的描述:“眉间常贴一钿花,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说明剪贴的花钿不易退去。
绿色的花钿叫“翠钿”。如《弈棋图》中那位侍女,她前额点一圆形绿色翠钿。唐代杜牧在诗中曾有描绘:“春阴扑翠钿。”温庭筠词中也有“眉间翠钿深”的描绘。唐代诗词中出现花钿的描写,说明当时社会仕女化妆实有其事。以花钿饰面,不仅使面部容光焕发,且呈现鲜丽色调。
前额鹅黄妆 鹅黄妆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北朝诗人江洪赋诗曰:“薄鬓约微黄。”它是一种用黄粉涂于前额的妆式。也有用黄纸剪成星星、月亮、花卉、鸟尾形贴于前额,谓“贴黄”。《木兰辞》中巾帼英雄花木兰解甲回乡后,在闺房中就有化妆的描写:“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就是鹅黄妆。这种妆始自南北朝,盛行于唐代。唐代吴融诗中曰:“眉边金失翠,额畔半留黄。”裴虔余诗中曰:“半额微黄金缕衣。”鹅黄妆彩艳浓华,呈现新美色调。
额前鹅黄妆反映了古人化妆审美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它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而演进。在高昌吐峪沟古遗址发掘的绢画上,那位乐舞仕女,身着彩锦窄袖胡装,头梳回鹘髻,额上饰黄星靥子,这种妆靥是当时流行的鹅黄妆。她那丽质色艳的感性面饰美,同样使人获得一种审美愉悦。
眉的修饰
眉在化妆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似与人的性格有着内在关联。唐代诗人李白曰:“眉语两自笑。”道出了眉的化妆与人的神态、性格相关的真谛。
西域妇女描眉,传说源远流长,但实物资料缺乏,仅从旁证材料中得到线索。吴妍春《民俗与考古》①一文中曾引用原苏联学者B.M.萨里安吉讲述中亚地区盛行描眉习俗的《古代大夏》②一文中,提到过远在公元前2000年的造型优美的化妆瓶。这种阔圆腹、高管颈、扁平环形口的小瓶中,往往插着一根顶端为动物形纹样的小棍。萨里安吉认为,它是用于画眉的化妆瓶。无独有偶,在新疆博物馆现代民俗展厅塔塔尔族展品中,有两个造型类似于大夏一带出土的金属画眉瓶,不同之处仅是画眉棍顶端纹样是花卉形状。文物的发掘说明新疆居民与中亚有着文化交流的往来。
新疆佛教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飞天、乐伎菩萨等人物形象造型,大多是细长的柳叶眉。如同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诗中描绘的那样:“青黛点眉眉细长”,墨黑而细长,柔曲波动,很助眼神。后来发展成一种短而阔的眉形,它浓密而短阔,在李贺诗中也有描写:“添眉桂叶浓。”形容眉如桂叶,作短阔之形。《弈棋图》中那位贵妇与侍女,即描阔叶眉。浓黑短阔衬托那丰腴的圆脸,越显雍容华贵,浓丽艳美。
西域妇女化妆早为世人所瞩目。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胡妆也流传至中原,成为妇女崇尚的世时妆。尚美成为历史流变中反映的一种审美内涵,尚美形式的美感积沉着一定的社会内容,内含时代精神特色。
附注
①吴妍春:《民俗与考古》,见《新疆文物》,1991(1)。
②《古代大夏》一书系引用其俄文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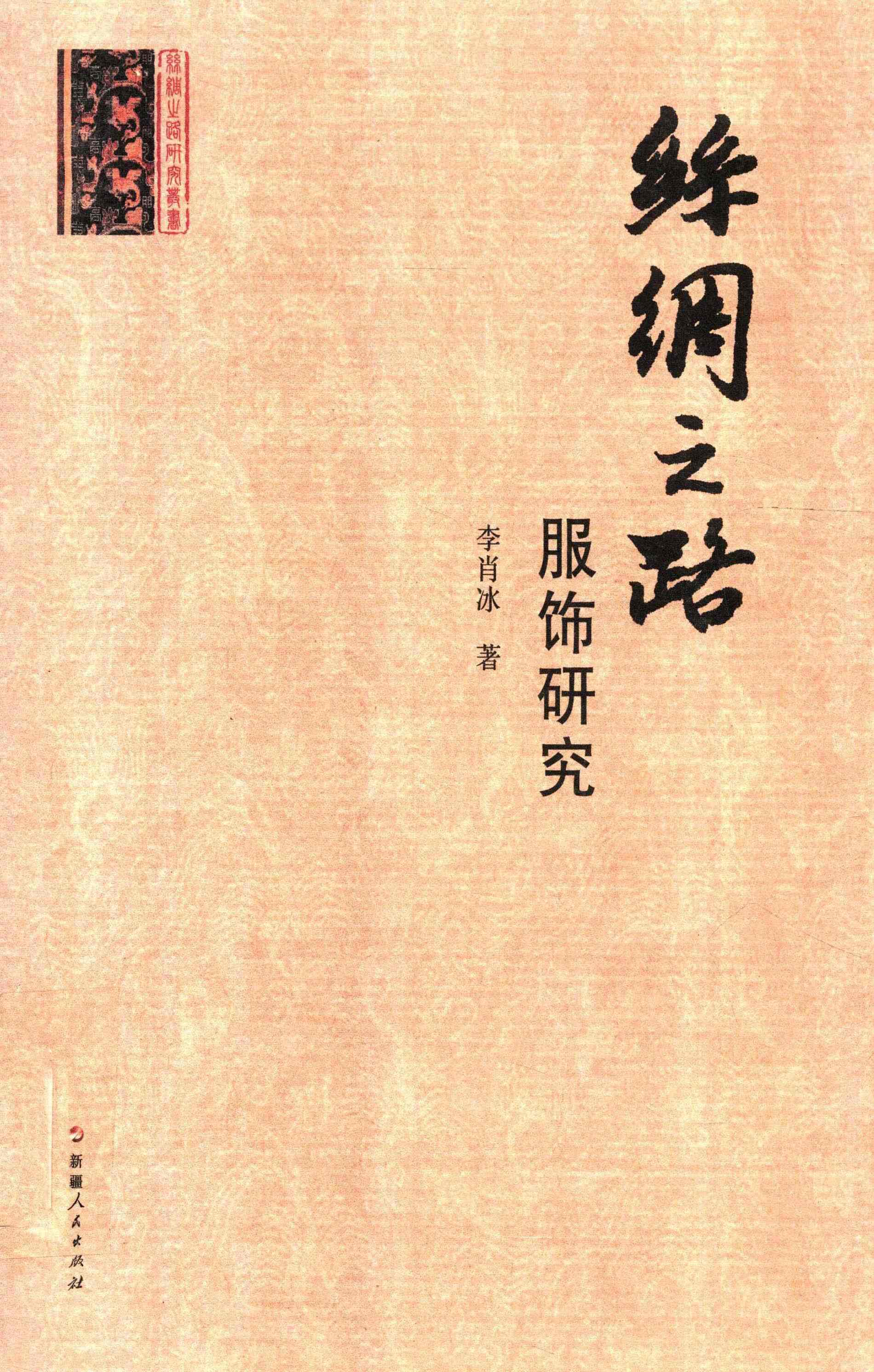
《丝绸之路服饰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正由于它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且展现出浓郁的民族衣饰风格,才使它独树一帜,别具风采。一部西域服饰文化的著成,应涵盖从古代到近代各族人民巨大的创造性。每一处墓葬出土的衣冠服饰珍品,每一幅壁画人物衣饰的穿着,以及雕刻衣装的草原石人、岩画、木雕、泥俑、塑像等人物的衣冠服饰造型,都足以说明西域服饰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载着它的兴衰,凝聚着先民的精魂。诚然,我们难以认定衣饰形式的确切年代,但却可以据此追溯到它的童稚时期,那经历了从人类混沌意识中的原始阶段,逐渐过渡到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