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原始装饰与审美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服饰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836 |
| 颗粒名称: | 第五节 原始装饰与审美 |
| 分类号: | K892.23 |
| 页数: | 10 |
| 页码: | 013-02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原始装饰与审美的情况。其中包括装饰性石器与骨饰件、精美的玉石饰品、古拙的青铜器、金器装饰纹样等。 |
| 关键词: | 服饰 原始装饰 审美 |
内容
远古时期的边疆原始人类,从半兽半人、茹毛饮血的洞穴中走出来,他们既具备与大自然搏斗的能力,又有发展生产的渴求,这就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与生存竞争的结果。粗笨沉重的石器工具使原始人类捕猎了食物,但在生活上却造成许多艰难与不幸。面对严酷的现实,原始人从打制粗糙的石器进而发展到制作精巧的细石器,然后再装上木质或骨质的手柄。经过细致琢凿的工具,不仅外观得到改善,还能较快地处理各种兽类毛皮。装饰性工具的细微变化,孕育、萌发了人类对自然物的审美体验。
装饰性石器与骨饰件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位置,赐予了西域的楼兰等地区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活动。考古学者曾采集到柳叶形、桂月形石镞、石矛。这些细石器不仅使用方便,而且美观大方,有的石器通体被凿成鱼鳞状,其造型与刻纹透出粗野、淳朴的原始美。那饱满的构图,既匀称又变化无穷,予人以独特的美感。一件件装饰化物件的出现,意味着原始初民造型观念的拓展,装饰性造型融入了制作石器之中。
砾石坠 新疆考古队在阿斯塔那细石器文化遗址采集时,发现了发出迷人光彩的砾石坠。“砾石坠”呈桃形,中心部位对穿小孔,对称、均匀,显示了磨钻技艺的熟练。利用坚硬的砾石制作饰物,无论是欣赏或把玩,都充分体现了边疆古代初民在与大自然抗衡中,在游牧渔猎之余,仍然有着美化、装饰自己的情趣,这正是古代人类编织文明发展史的序曲。
心形骨饰件 此件制作巧妙,构思独特,是考古工作者在木垒县四道沟遗址采获的,为铜石并用时代的饰件,即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出现铜石、金石并用,对于生产、生活用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件用骨质制作的装饰品,长约6.2厘米,厚约0.8厘米,形状扁平略呈凸形,上端倒置呈三角形,适中的起着连接作用。边长约2.9厘米。三角形中镂空雕琢成心形,下端另接长约4.8厘米的心形,上下对称,蕴含心心相印。骨饰件的中心是镂空的,最下端还刻成凸形呈椭圆状骨钉,似带钩连结上端。它似项链又像独特的艺术品,在整体艺术结构中发挥得自由活泼,表现出率真的生命力,影射出古代某些生活气息和原始初民对自身创造价值的某种肯定,呈现出人类精神主体和意志相联系的审美愉悦。
考古所曾在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孔雀河古墓沟遗址发现一件件稀有的骨质项链、木质头簪、玉珠、骨针与木针。
骨质项链 其形有筒状、圆珠形之分。造型古朴、原始,由一颗颗骨质筒状、圆珠状连接串成,琢磨均匀、形状奇特,是件不可多得的装饰品瑰宝,其艺术价值并不逊色于现代的珍珠、玛瑙项链。
骨簪、木簪 簪,单股如针,以簪贯发为饰。古有骨簪、玉簪、金簪。此出土骨簪,上端呈椭圆、圆柱形,下端如针。木簪顶部呈长方形,并刻有简洁、朴素的几何纹,优美的曲线与四出菱形图案融会一处,构图均衡疏朗,含有一种韵律的节奏感,予人以活力,具有古朴的原始美。骨簪既精巧又美观,表现了原始初民对仪容美的重视,开始用簪固定发型,求得一种仪容的修饰美。仪容审美不仅是个人的爱好与兴趣,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的表征,它显示了东方民族审美思想的独特性。
骨针、木针 造型别致,纹饰各异。此骨针没有针眼,顶部精细地琢出桂叶形、四菱形、圆锥形、圆珠形等针柄,柄部刻出细纹,针部磨制光滑。“木针”是最原始的“纽扣”,既可别住无扣的上衣,又是一种装饰品。作为实用的装饰性物件,在特定的环境中,构成某种气氛,从而产生特有的审美效果。
原始初民不仅在佩戴装饰物件上讲究美化,而且在日常用具上也精琢细雕。据考古工作者羊毅勇报道:出土于新疆木垒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把骨梳,它的造型呈长方形,扁平而光滑,另一面是稍有麻点的骨质孔,长约8.3厘米,宽2.4厘米,共计6个尖状齿,这种造型的骨梳在新疆是首次发现。按其齿的形状、疏密与间隔的特点,可以看出,此梳主要是用作梳理兽毛,为制作毛纺织物图28骨针。孔雀河古墓沟出土做好了准备。
精美的玉石饰品
新疆盛产玉石,这是大自然赐予的得天独厚的珍贵宝藏,且历史悠久,蕴藏丰富。考古人员在楼兰地区采集到远在新石器时代高5.4厘米,宽5厘米,厚1.4厘米的“玉斧”。斧的刃部较厚,虽有自然裂纹,却闪烁着玉石的晶莹与光洁,以名贵的羊脂玉制成的“玉斧”,反射出古朴的造型情趣。
玉石珠饰出土于孔雀河古墓沟,是随葬品,为年轻女干尸颈部、腕部佩戴,软玉质,较有透明感,呈管状空心、菱形四角形、圆柱形,琢刻巧妙,细润光滑。不久又发现各种玉石珠饰,五光十色,耀眼夺目,象征着原始初民创造的光灿灿彩虹。爱美的心理融入饰物之中,体现出朦胧的人体装饰美感意识,以审美的观点来对待自己身体的完美性。
新疆玉石的开发利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中华民族祖先黄帝时期就有记载。《山海经》曰:“密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黄帝乃取密山之玉,而投于钟山之阳。”《贾子通政语》上篇曰:“黄帝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蚩山”、“密山”、“昆仑”都泛指新疆玉石产地。玉石,是古代西北少数民族装饰自己的佳品,也是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物证。据载: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一座古王府墓葬,出土了举世罕见的文物,而玉器多达700多件,经鉴定绝大多数玉器“基本上是新疆玉”。它的发现证实早在殷商晚期新疆玉已大量输入中原。此后,交往不绝,绵延不息。玉石作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往、传播的枢纽,早于“丝绸之路”,是一条闻名于世的“玉石之路”,它为西域古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疆玉石以和田玉质地最好,有名贵的墨玉、脂玉、翠玉等。墨玉墨而透亮,脂玉光泽如羊脂,翠玉绿如碧玉,翡翠是装饰品中的珍品,流传极广,蜚声中外。杨汉臣等著《新疆宝石和玉石》一书中写着:“商代是我国琢玉工艺发展的重要时期..周的礼器、秦的玉玺、汉的玉衣、唐的玉莲花、宋的玉观音、元的渎山大玉海、明的子冈别子..历代这些玉器大都是由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利用和田玉琢成的玉器,堪称我国玉器的瑰宝,内含东方传统文化装饰性审美意趣,和田美玉可与世界上的精美玉石相媲美,令世人赞叹不已。
古拙的青铜器、金器装饰纹样
青铜器、金器饰物的出现,显示着装饰性饰物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新疆的和静县察吾乎文化曾出土了一面青铜器——为公元前8年至公元前5世纪的一面圆形铜镜。为新疆地区仅见的早期铜镜,镜面中心镶一个弧形的钮,主体纹饰为凶猛的巨兽,它圆目大睁,血盆大口露出巨齿,啮咬着尾部,使丰满的兽尾四散飞扬,与发达的肢体蜷曲于纹饰之中。狞厉威严的兽纹渗透着一种奇拙、怪异的意蕴,犹如原始初民深信的图腾物。野兽纹饰具有雄浑的鄂尔多斯造型风格,在绿洲草原古遗址与岩画中多有发现。野兽纹饰已非常物,它在古代原始初民的观念中,融入的原始宗教渐渐被神化,形成一种带有原始特征的艺术形式,野兽纹饰中怪异的纹饰,具有某种象征符号,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权威神力观念。
据载:“吐鲁番艾丁湖潘坎出土‘虎叼羊纹铜饰牌’,长11.1厘米,宽5.3厘米,厚0.3厘米。正面铸成一只透雕的老虎,睁目竖耳,张口叼着一只羊。猎获物到口后老虎不慌不忙迈步回山林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背面有三个环状钮,头端二个,尾端一个,布局呈三角形,以供附缀于其图33白玉斧。新石器时代于罗布泊采集。此玉斧形似长方形,刃部留有琢磨痕迹,至今仍很锋利、流畅。玉斧质地为名贵的羊脂玉,晶莹洁白,细润光滑,经阳光照映,熠熠生辉。新疆考古所藏他物件..以往,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关系时,很少引用新疆的资料。木垒县收集的野猪搏马纹铜饰牌,与西伯利亚出土的同类饰牌构图,造型非常相似。吐鲁番新发现的虎叼羊纹铜饰牌,与1975年在萨格雷河谷斯基泰时代的古墓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简直雷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新疆地区的广泛分布,填补了区域空白与这一草原文化传播链条上的缺环。”①撰文具体地写着吐鲁番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的造型、质地及与鄂尔多斯纹样的内在联系。
“虎叼羊纹铜饰牌”与上述“野兽纹饰铜镜”都具有鄂尔多斯纹样风格,但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变化。前者纹饰酣畅、饱满,突出它巨大的身躯与明显夸张的口部,呈现出野兽的凶猛与猎获时的种种神态;后者虽张开血盆大口,却首尾摆动,又夸张其肢体,于其动态之中蕴含一种神性的张力,赋予一种神秘力量。实际上,新疆已发现多处鄂尔多斯式纹饰的造型饰物,它反映北方草原文化圈的一种形态特征。在这个文化圈内,由于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彼此相似,草原游牧人之间彼此交流往来的互融性,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亦呈现出一致性和稳定性,西域地区更受中亚文化的影响,因此,纹饰中蕴含着多种文化因素。
金器纹饰的不断发现,显示着西陲边塞进入了文明的黄金时代。考古者在伊犁河流域,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塞人墓葬发现了金簪、金耳环、铜耳环、铜发钗等金、铜饰物,又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古遗址发现了战国时期最富特色的黄金饰物。它色泽纯正,闪闪发亮,制作手艺高超,堪称传世金饰中的代表作。其中一具“虎形金箔腰带饰”,长25.4厘米,宽3.3厘米,金光灿灿,造型构思巧妙,刻画出猛虎奔跑、跃动、张嘴啮咬的雄威与出没山野的巨兽体态。两虎相对,它们的头部、肩与腿部都做了有力地夸张,刻画坚实、粗壮、筋肉凸起,特别突出两虎的蹲伏状,翘起的尾部卷曲而又富有韵律感,创造了一种气焰逼人、奔放不羁的激烈气氛,连同那旋转式的旋纹,刻画得十分流畅。虎形纹样装饰,使观者获得一种生命的活力,反映出远古时代初民们的某种精神需求。
“虎纹圆形金饰牌”也是以猛虎为主体形象的黄金饰牌,突出虎的头部、身躯与四肢蜷曲于圆形饰牌中,并作跳跃奔跑之状,既突出虎的凶猛,又简化其肢体部位,适当地融入旋纹。
上述金属饰物与古代塞人有着密切联系。王炳华著《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书中曾提及这批出土的金器。他举例说:“在那座年仅20多岁的贵族女子墓中,装饰腰带的金牌就见到8块,每块金牌都重20克以下。蓬勃生气的造型,洋溢着生命的流动感,它夺目耀眼,切入动态变异中的熠熠光泽,透出造型迷人的神韵。”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曾经告诉人们:“塞族人王族享用着上天赐予的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有着黄金饰牌,人死后,要用黄金制品入葬……”在阿拉沟东口打开的塞族人贵族墓葬,为我们了解塞族人,了解吐鲁番的开发建设过程,提供了更为丰富详实的实物资料。
塞人是曾经驰骋于中亚草原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足迹也留在了西域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所留下的珍贵遗物可供历史学家补续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载:“塞种人,古代族名。历史上主要分布于中亚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曾散居中国西部。西方古典作家称之为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为塞卡人,中国史地文献称之为塞种、塞人。”塞人崇尚以虎、狮、熊为主体的装饰性图案,视其为表达情感的有生命的实体,创造出显示自己力量的膜拜偶像。一件件出土的表现得酣畅淋漓的装饰化饰物,传达了塞族人的审美倾向与观念。图案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朴拙的气质、奇异诡谲、飞扬流动的神采,绽放出巨大的、摄人心魄的魅力。
独特的造型特征,究其原因出于它的源流与生成,呈现着先民们的思维生存环境与情感的流露。即便是斯基泰风格或鄂尔多斯造型,也都同源于草原游牧文化圈内,是一种超越部族的文化形态,具有共性的特征。
金项链则是出土于阿拉沟古墓,它是古代妇女珍爱的宝物。它不仅璀璨夺目,且制作工艺精细,其金质项链采用极细的金丝编织成链状,相隔一定的距离镶上色泽柔和、温润光洁的白玉、翠绿的孔雀石,显得晶莹璀璨、华丽夺目、玲珑剔透,是件弥足珍贵的金、玉镶嵌首饰。
金耳环造型精致、铸纹流畅,也是一件少为人知的金饰。此耳环金色纯正,黄色中闪透光泽。其长2.5厘米,环径1.5厘米。耳环的上端为圆形金环,下端系着塔锥形坠饰,坠的上端铸出密集如珍珠的珠点纹,下端呈座状式,衬托整体金耳环饰。
葡萄坠金耳环其造型疏密有致,具有一种韵律感。耳环的上端系着一个圆环,直径仅1.3厘米,环的下端以两个小钩相连紧靠金坠。坠饰由8个空心圆形金泡组成,连接为一体,似一串丰硕的葡萄,它的色泽和亮度透出纹饰璀璨而闪烁。
这些金银饰物不是单纯欣赏、美化的装饰物,它所以被誉为珍宝,是因透射出时代的风尚变化,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开端,是古代人类集感情、审美、原始宗教、生活实用等诸多因素的产物,代表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神秘含义。那种对“纹饰”的特殊情感、认知与表达,传递出原始初民内心世界的某些隐秘。“纹饰”以“纹”为核心,它在文字诞生之前,也是一种记录历史与文化的方式。《易经》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晋人干宝注说:“四时之变悬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具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以“文明而化成天下,即所谓的‘文化’,而文明之文指天文、地文、人文,也即天纹、地纹、人纹,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迁变;地文谓地理气脉,山川植被形状;人文是人的文彩装饰,包括纹饰、文章、礼仪等内容①。”阐述了“纹饰”涵盖面的博深,包含着宇宙万物与哲理内容的精髓。一件件珍贵的装饰品使深埋地下数千年的古代宝物终于出世,它使人们从中悟到一个真谛:人类的繁衍生息与文化累积的延续,是靠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进取与实践获得的。实际上,人的生活需求只有靠人类自己,它也包含着人类的审美意识,那附着于金、铜饰上的纹饰与造型,那一串串色彩斑斓、晶莹剔透的装饰品,是原始人类认定的万物精灵,是他们心灵辉映的火花,是最早的精神寄托。同时,玉石、金铜饰物精巧的制作和应用,也表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与水平,反映出边塞城邦诸国、游牧民族时代的文明背景。人们透过感官、视觉,体会到古代人类的文明发展坎坷不平、生生不息地朝前迈进的艰难历程。
面饰的装饰化
文身、文面是人类文化中最原始的肤体装饰,纹样各异的装饰,构成一种无声的语言,其历史几乎和整个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纹饰的古拙或浓艳,多有特定的内涵,在世界某些地区曾流行过,且渐渐形成一种习俗,曾盛行东南亚、东北亚、非洲..我国台湾的高山族、云南的独龙族、傣族、海南的黎族、四川凉山彝族等似有文身、文面之俗。此俗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久远。《汉书·地理志》曰:“越人,文身断发,以辟蚊龙之害。”《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墨子·公孟篇》也有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越,方外之地,断发纹身之民也。”
西域与内地相隔万里之遥,过去与现今在各地居民中很少发现“文身文面”的习俗,然而,近年来,新疆考古人员却在偏远的南疆且末扎洪鲁克乡古墓,发现距今3000年前后的两具男、女古尸。由于当地干旱少雨,古尸保存完好,发现在他们的面部饰有布局对称、纹路清晰的纹饰,画在鼻、眼、额、颧骨部位,似用矿物原料,如雌黄、雄黄、铅黄以及赤铁矿等涂抹。男尸面部太阳穴处(两侧均有)画有卷曲的大羊角纹,它又似太阳,中心稍圆,四周呈放射状。女尸面部眼窝下端左右两侧显出对称的卷云纹。面纹的发现与古人对日月、天宇等大自然崇拜有着紧密关联。李砚祖在《纹样新探》中道:“研究《周易》的学者曾指出,卦爻辞的表现形式是‘假象喻意’,即拟取人们生活中习见常闻的物象..以‘八卦之象’为例,所谓‘八卦之象’,即八卦象八类事物。以自然界八种自然为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自然客观物象是人朝夕可见,其形其性都明白易察,深层的理性规范、哲理,所谓‘道’,一旦与人们所熟悉的自然物象的存在相比较,便能获得很好的传播和接受效应。”
真正见底蕴的是人类运用自然物,给予象征性表现与带有浓重的原始意识和先民对于大自然的认识,渐渐积沉于心灵与思维活动中,并反映在面饰的纹样上,由此又引发某种审美观念或原始宗教意识。面饰赋予人美的丰采,也含有取悦异性的崇美心态。
装饰性石器与骨饰件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位置,赐予了西域的楼兰等地区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活动。考古学者曾采集到柳叶形、桂月形石镞、石矛。这些细石器不仅使用方便,而且美观大方,有的石器通体被凿成鱼鳞状,其造型与刻纹透出粗野、淳朴的原始美。那饱满的构图,既匀称又变化无穷,予人以独特的美感。一件件装饰化物件的出现,意味着原始初民造型观念的拓展,装饰性造型融入了制作石器之中。
砾石坠 新疆考古队在阿斯塔那细石器文化遗址采集时,发现了发出迷人光彩的砾石坠。“砾石坠”呈桃形,中心部位对穿小孔,对称、均匀,显示了磨钻技艺的熟练。利用坚硬的砾石制作饰物,无论是欣赏或把玩,都充分体现了边疆古代初民在与大自然抗衡中,在游牧渔猎之余,仍然有着美化、装饰自己的情趣,这正是古代人类编织文明发展史的序曲。
心形骨饰件 此件制作巧妙,构思独特,是考古工作者在木垒县四道沟遗址采获的,为铜石并用时代的饰件,即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出现铜石、金石并用,对于生产、生活用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件用骨质制作的装饰品,长约6.2厘米,厚约0.8厘米,形状扁平略呈凸形,上端倒置呈三角形,适中的起着连接作用。边长约2.9厘米。三角形中镂空雕琢成心形,下端另接长约4.8厘米的心形,上下对称,蕴含心心相印。骨饰件的中心是镂空的,最下端还刻成凸形呈椭圆状骨钉,似带钩连结上端。它似项链又像独特的艺术品,在整体艺术结构中发挥得自由活泼,表现出率真的生命力,影射出古代某些生活气息和原始初民对自身创造价值的某种肯定,呈现出人类精神主体和意志相联系的审美愉悦。
考古所曾在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孔雀河古墓沟遗址发现一件件稀有的骨质项链、木质头簪、玉珠、骨针与木针。
骨质项链 其形有筒状、圆珠形之分。造型古朴、原始,由一颗颗骨质筒状、圆珠状连接串成,琢磨均匀、形状奇特,是件不可多得的装饰品瑰宝,其艺术价值并不逊色于现代的珍珠、玛瑙项链。
骨簪、木簪 簪,单股如针,以簪贯发为饰。古有骨簪、玉簪、金簪。此出土骨簪,上端呈椭圆、圆柱形,下端如针。木簪顶部呈长方形,并刻有简洁、朴素的几何纹,优美的曲线与四出菱形图案融会一处,构图均衡疏朗,含有一种韵律的节奏感,予人以活力,具有古朴的原始美。骨簪既精巧又美观,表现了原始初民对仪容美的重视,开始用簪固定发型,求得一种仪容的修饰美。仪容审美不仅是个人的爱好与兴趣,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的表征,它显示了东方民族审美思想的独特性。
骨针、木针 造型别致,纹饰各异。此骨针没有针眼,顶部精细地琢出桂叶形、四菱形、圆锥形、圆珠形等针柄,柄部刻出细纹,针部磨制光滑。“木针”是最原始的“纽扣”,既可别住无扣的上衣,又是一种装饰品。作为实用的装饰性物件,在特定的环境中,构成某种气氛,从而产生特有的审美效果。
原始初民不仅在佩戴装饰物件上讲究美化,而且在日常用具上也精琢细雕。据考古工作者羊毅勇报道:出土于新疆木垒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把骨梳,它的造型呈长方形,扁平而光滑,另一面是稍有麻点的骨质孔,长约8.3厘米,宽2.4厘米,共计6个尖状齿,这种造型的骨梳在新疆是首次发现。按其齿的形状、疏密与间隔的特点,可以看出,此梳主要是用作梳理兽毛,为制作毛纺织物图28骨针。孔雀河古墓沟出土做好了准备。
精美的玉石饰品
新疆盛产玉石,这是大自然赐予的得天独厚的珍贵宝藏,且历史悠久,蕴藏丰富。考古人员在楼兰地区采集到远在新石器时代高5.4厘米,宽5厘米,厚1.4厘米的“玉斧”。斧的刃部较厚,虽有自然裂纹,却闪烁着玉石的晶莹与光洁,以名贵的羊脂玉制成的“玉斧”,反射出古朴的造型情趣。
玉石珠饰出土于孔雀河古墓沟,是随葬品,为年轻女干尸颈部、腕部佩戴,软玉质,较有透明感,呈管状空心、菱形四角形、圆柱形,琢刻巧妙,细润光滑。不久又发现各种玉石珠饰,五光十色,耀眼夺目,象征着原始初民创造的光灿灿彩虹。爱美的心理融入饰物之中,体现出朦胧的人体装饰美感意识,以审美的观点来对待自己身体的完美性。
新疆玉石的开发利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中华民族祖先黄帝时期就有记载。《山海经》曰:“密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黄帝乃取密山之玉,而投于钟山之阳。”《贾子通政语》上篇曰:“黄帝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蚩山”、“密山”、“昆仑”都泛指新疆玉石产地。玉石,是古代西北少数民族装饰自己的佳品,也是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物证。据载: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一座古王府墓葬,出土了举世罕见的文物,而玉器多达700多件,经鉴定绝大多数玉器“基本上是新疆玉”。它的发现证实早在殷商晚期新疆玉已大量输入中原。此后,交往不绝,绵延不息。玉石作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往、传播的枢纽,早于“丝绸之路”,是一条闻名于世的“玉石之路”,它为西域古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疆玉石以和田玉质地最好,有名贵的墨玉、脂玉、翠玉等。墨玉墨而透亮,脂玉光泽如羊脂,翠玉绿如碧玉,翡翠是装饰品中的珍品,流传极广,蜚声中外。杨汉臣等著《新疆宝石和玉石》一书中写着:“商代是我国琢玉工艺发展的重要时期..周的礼器、秦的玉玺、汉的玉衣、唐的玉莲花、宋的玉观音、元的渎山大玉海、明的子冈别子..历代这些玉器大都是由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利用和田玉琢成的玉器,堪称我国玉器的瑰宝,内含东方传统文化装饰性审美意趣,和田美玉可与世界上的精美玉石相媲美,令世人赞叹不已。
古拙的青铜器、金器装饰纹样
青铜器、金器饰物的出现,显示着装饰性饰物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新疆的和静县察吾乎文化曾出土了一面青铜器——为公元前8年至公元前5世纪的一面圆形铜镜。为新疆地区仅见的早期铜镜,镜面中心镶一个弧形的钮,主体纹饰为凶猛的巨兽,它圆目大睁,血盆大口露出巨齿,啮咬着尾部,使丰满的兽尾四散飞扬,与发达的肢体蜷曲于纹饰之中。狞厉威严的兽纹渗透着一种奇拙、怪异的意蕴,犹如原始初民深信的图腾物。野兽纹饰具有雄浑的鄂尔多斯造型风格,在绿洲草原古遗址与岩画中多有发现。野兽纹饰已非常物,它在古代原始初民的观念中,融入的原始宗教渐渐被神化,形成一种带有原始特征的艺术形式,野兽纹饰中怪异的纹饰,具有某种象征符号,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权威神力观念。
据载:“吐鲁番艾丁湖潘坎出土‘虎叼羊纹铜饰牌’,长11.1厘米,宽5.3厘米,厚0.3厘米。正面铸成一只透雕的老虎,睁目竖耳,张口叼着一只羊。猎获物到口后老虎不慌不忙迈步回山林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背面有三个环状钮,头端二个,尾端一个,布局呈三角形,以供附缀于其图33白玉斧。新石器时代于罗布泊采集。此玉斧形似长方形,刃部留有琢磨痕迹,至今仍很锋利、流畅。玉斧质地为名贵的羊脂玉,晶莹洁白,细润光滑,经阳光照映,熠熠生辉。新疆考古所藏他物件..以往,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关系时,很少引用新疆的资料。木垒县收集的野猪搏马纹铜饰牌,与西伯利亚出土的同类饰牌构图,造型非常相似。吐鲁番新发现的虎叼羊纹铜饰牌,与1975年在萨格雷河谷斯基泰时代的古墓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简直雷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新疆地区的广泛分布,填补了区域空白与这一草原文化传播链条上的缺环。”①撰文具体地写着吐鲁番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的造型、质地及与鄂尔多斯纹样的内在联系。
“虎叼羊纹铜饰牌”与上述“野兽纹饰铜镜”都具有鄂尔多斯纹样风格,但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变化。前者纹饰酣畅、饱满,突出它巨大的身躯与明显夸张的口部,呈现出野兽的凶猛与猎获时的种种神态;后者虽张开血盆大口,却首尾摆动,又夸张其肢体,于其动态之中蕴含一种神性的张力,赋予一种神秘力量。实际上,新疆已发现多处鄂尔多斯式纹饰的造型饰物,它反映北方草原文化圈的一种形态特征。在这个文化圈内,由于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彼此相似,草原游牧人之间彼此交流往来的互融性,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亦呈现出一致性和稳定性,西域地区更受中亚文化的影响,因此,纹饰中蕴含着多种文化因素。
金器纹饰的不断发现,显示着西陲边塞进入了文明的黄金时代。考古者在伊犁河流域,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塞人墓葬发现了金簪、金耳环、铜耳环、铜发钗等金、铜饰物,又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古遗址发现了战国时期最富特色的黄金饰物。它色泽纯正,闪闪发亮,制作手艺高超,堪称传世金饰中的代表作。其中一具“虎形金箔腰带饰”,长25.4厘米,宽3.3厘米,金光灿灿,造型构思巧妙,刻画出猛虎奔跑、跃动、张嘴啮咬的雄威与出没山野的巨兽体态。两虎相对,它们的头部、肩与腿部都做了有力地夸张,刻画坚实、粗壮、筋肉凸起,特别突出两虎的蹲伏状,翘起的尾部卷曲而又富有韵律感,创造了一种气焰逼人、奔放不羁的激烈气氛,连同那旋转式的旋纹,刻画得十分流畅。虎形纹样装饰,使观者获得一种生命的活力,反映出远古时代初民们的某种精神需求。
“虎纹圆形金饰牌”也是以猛虎为主体形象的黄金饰牌,突出虎的头部、身躯与四肢蜷曲于圆形饰牌中,并作跳跃奔跑之状,既突出虎的凶猛,又简化其肢体部位,适当地融入旋纹。
上述金属饰物与古代塞人有着密切联系。王炳华著《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书中曾提及这批出土的金器。他举例说:“在那座年仅20多岁的贵族女子墓中,装饰腰带的金牌就见到8块,每块金牌都重20克以下。蓬勃生气的造型,洋溢着生命的流动感,它夺目耀眼,切入动态变异中的熠熠光泽,透出造型迷人的神韵。”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曾经告诉人们:“塞族人王族享用着上天赐予的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有着黄金饰牌,人死后,要用黄金制品入葬……”在阿拉沟东口打开的塞族人贵族墓葬,为我们了解塞族人,了解吐鲁番的开发建设过程,提供了更为丰富详实的实物资料。
塞人是曾经驰骋于中亚草原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足迹也留在了西域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所留下的珍贵遗物可供历史学家补续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载:“塞种人,古代族名。历史上主要分布于中亚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曾散居中国西部。西方古典作家称之为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为塞卡人,中国史地文献称之为塞种、塞人。”塞人崇尚以虎、狮、熊为主体的装饰性图案,视其为表达情感的有生命的实体,创造出显示自己力量的膜拜偶像。一件件出土的表现得酣畅淋漓的装饰化饰物,传达了塞族人的审美倾向与观念。图案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朴拙的气质、奇异诡谲、飞扬流动的神采,绽放出巨大的、摄人心魄的魅力。
独特的造型特征,究其原因出于它的源流与生成,呈现着先民们的思维生存环境与情感的流露。即便是斯基泰风格或鄂尔多斯造型,也都同源于草原游牧文化圈内,是一种超越部族的文化形态,具有共性的特征。
金项链则是出土于阿拉沟古墓,它是古代妇女珍爱的宝物。它不仅璀璨夺目,且制作工艺精细,其金质项链采用极细的金丝编织成链状,相隔一定的距离镶上色泽柔和、温润光洁的白玉、翠绿的孔雀石,显得晶莹璀璨、华丽夺目、玲珑剔透,是件弥足珍贵的金、玉镶嵌首饰。
金耳环造型精致、铸纹流畅,也是一件少为人知的金饰。此耳环金色纯正,黄色中闪透光泽。其长2.5厘米,环径1.5厘米。耳环的上端为圆形金环,下端系着塔锥形坠饰,坠的上端铸出密集如珍珠的珠点纹,下端呈座状式,衬托整体金耳环饰。
葡萄坠金耳环其造型疏密有致,具有一种韵律感。耳环的上端系着一个圆环,直径仅1.3厘米,环的下端以两个小钩相连紧靠金坠。坠饰由8个空心圆形金泡组成,连接为一体,似一串丰硕的葡萄,它的色泽和亮度透出纹饰璀璨而闪烁。
这些金银饰物不是单纯欣赏、美化的装饰物,它所以被誉为珍宝,是因透射出时代的风尚变化,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开端,是古代人类集感情、审美、原始宗教、生活实用等诸多因素的产物,代表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神秘含义。那种对“纹饰”的特殊情感、认知与表达,传递出原始初民内心世界的某些隐秘。“纹饰”以“纹”为核心,它在文字诞生之前,也是一种记录历史与文化的方式。《易经》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晋人干宝注说:“四时之变悬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具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以“文明而化成天下,即所谓的‘文化’,而文明之文指天文、地文、人文,也即天纹、地纹、人纹,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迁变;地文谓地理气脉,山川植被形状;人文是人的文彩装饰,包括纹饰、文章、礼仪等内容①。”阐述了“纹饰”涵盖面的博深,包含着宇宙万物与哲理内容的精髓。一件件珍贵的装饰品使深埋地下数千年的古代宝物终于出世,它使人们从中悟到一个真谛:人类的繁衍生息与文化累积的延续,是靠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进取与实践获得的。实际上,人的生活需求只有靠人类自己,它也包含着人类的审美意识,那附着于金、铜饰上的纹饰与造型,那一串串色彩斑斓、晶莹剔透的装饰品,是原始人类认定的万物精灵,是他们心灵辉映的火花,是最早的精神寄托。同时,玉石、金铜饰物精巧的制作和应用,也表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与水平,反映出边塞城邦诸国、游牧民族时代的文明背景。人们透过感官、视觉,体会到古代人类的文明发展坎坷不平、生生不息地朝前迈进的艰难历程。
面饰的装饰化
文身、文面是人类文化中最原始的肤体装饰,纹样各异的装饰,构成一种无声的语言,其历史几乎和整个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纹饰的古拙或浓艳,多有特定的内涵,在世界某些地区曾流行过,且渐渐形成一种习俗,曾盛行东南亚、东北亚、非洲..我国台湾的高山族、云南的独龙族、傣族、海南的黎族、四川凉山彝族等似有文身、文面之俗。此俗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久远。《汉书·地理志》曰:“越人,文身断发,以辟蚊龙之害。”《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墨子·公孟篇》也有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越,方外之地,断发纹身之民也。”
西域与内地相隔万里之遥,过去与现今在各地居民中很少发现“文身文面”的习俗,然而,近年来,新疆考古人员却在偏远的南疆且末扎洪鲁克乡古墓,发现距今3000年前后的两具男、女古尸。由于当地干旱少雨,古尸保存完好,发现在他们的面部饰有布局对称、纹路清晰的纹饰,画在鼻、眼、额、颧骨部位,似用矿物原料,如雌黄、雄黄、铅黄以及赤铁矿等涂抹。男尸面部太阳穴处(两侧均有)画有卷曲的大羊角纹,它又似太阳,中心稍圆,四周呈放射状。女尸面部眼窝下端左右两侧显出对称的卷云纹。面纹的发现与古人对日月、天宇等大自然崇拜有着紧密关联。李砚祖在《纹样新探》中道:“研究《周易》的学者曾指出,卦爻辞的表现形式是‘假象喻意’,即拟取人们生活中习见常闻的物象..以‘八卦之象’为例,所谓‘八卦之象’,即八卦象八类事物。以自然界八种自然为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自然客观物象是人朝夕可见,其形其性都明白易察,深层的理性规范、哲理,所谓‘道’,一旦与人们所熟悉的自然物象的存在相比较,便能获得很好的传播和接受效应。”
真正见底蕴的是人类运用自然物,给予象征性表现与带有浓重的原始意识和先民对于大自然的认识,渐渐积沉于心灵与思维活动中,并反映在面饰的纹样上,由此又引发某种审美观念或原始宗教意识。面饰赋予人美的丰采,也含有取悦异性的崇美心态。
附注
①柳洪亮:《吐鲁番艾丁湖坎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西域的影响》,见《新疆文物》,1992(2)。
①李砚祖:《纹样新探》,见《文艺研究》,1992(6)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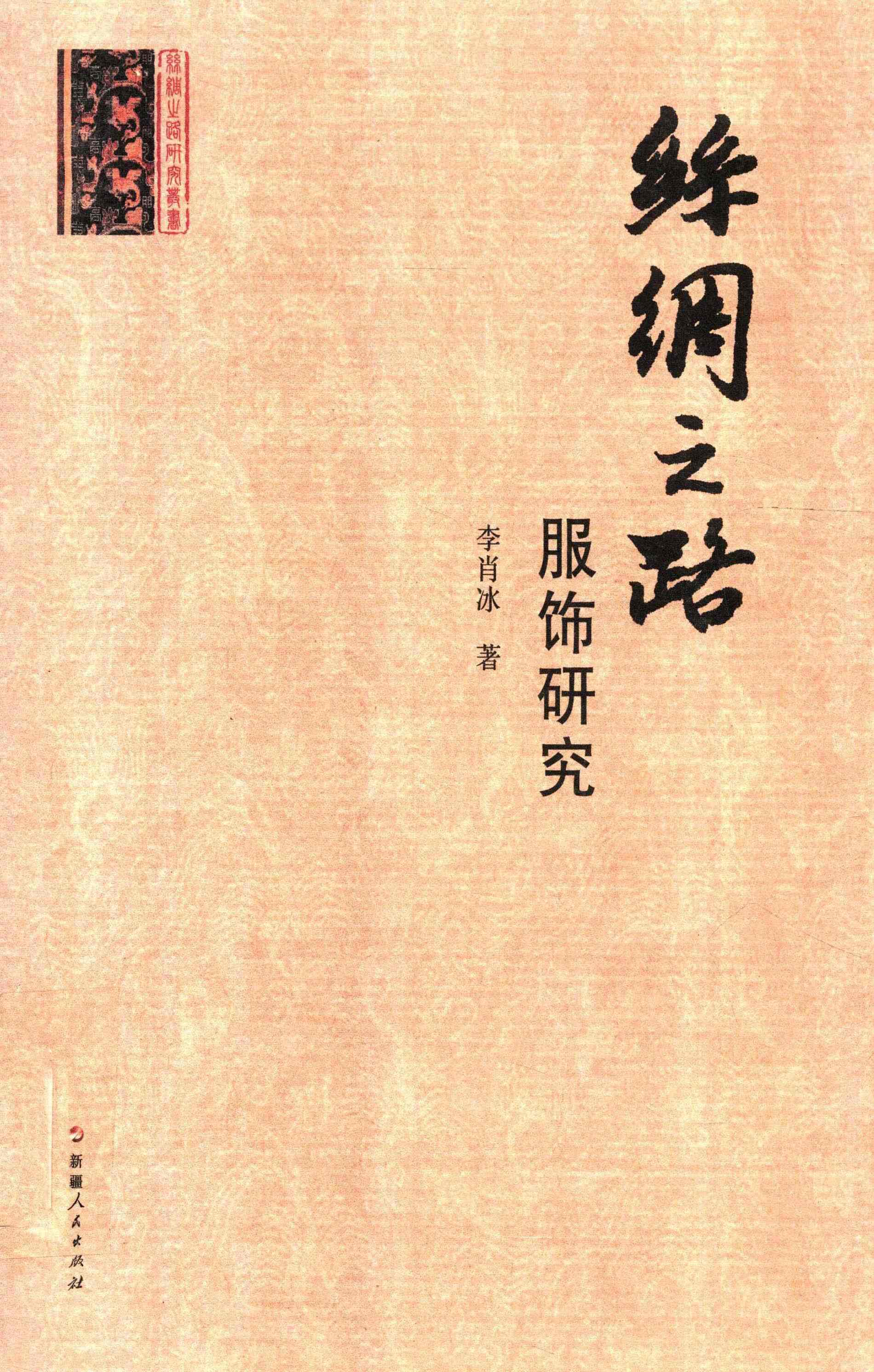
《丝绸之路服饰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正由于它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且展现出浓郁的民族衣饰风格,才使它独树一帜,别具风采。一部西域服饰文化的著成,应涵盖从古代到近代各族人民巨大的创造性。每一处墓葬出土的衣冠服饰珍品,每一幅壁画人物衣饰的穿着,以及雕刻衣装的草原石人、岩画、木雕、泥俑、塑像等人物的衣冠服饰造型,都足以说明西域服饰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载着它的兴衰,凝聚着先民的精魂。诚然,我们难以认定衣饰形式的确切年代,但却可以据此追溯到它的童稚时期,那经历了从人类混沌意识中的原始阶段,逐渐过渡到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