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时期西域服饰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服饰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0832 |
| 颗粒名称: | 第一章 先秦时期西域服饰 |
| 分类号: | K875.2 |
| 页数: | 40 |
| 页码: | 001-04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先秦时期西域服饰的情况。其中包括服饰的缘起与形成、岩画中的原始衣冠、西王母的传说、胡服等。 |
| 关键词: | 先秦 西域 服饰 |
内容
第一节 服饰的缘起与形成
大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地。“人猿揖别”之始,大自然就显示了对于人类无限的威慑力量。当人类在各种物质创造性活动中显出本质力量之时,它只能说明是人类征服了自然,其中蕴藏着人类衣饰穿着意识的萌芽。
宇宙万物千变万化、神奇莫测。据考古、历史、地质学家考证与研究,约在距今5万万年以前,现今新疆的这块宝地,原先是烟波浩渺的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几经地震与火山爆发,海底隆起无数山脉,盆地又渐渐升高,使新疆呈现一片波状大草原、参天大树、绿野丛林..巨大的爬行动物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随着造山运动的更迭,沧海桑田,水去陆现,生态环境的天翻地覆,造成生活在海洋中的“主人”终于葬身海底岩石下。
几经动荡,造山运动促使大自然发生巨变,人类成了大地的主人。“阿图什人头骨”①化石的发现,是新疆考古界发现的第一例古人类化石,填补了古人类化石的空白。据古人类学家鉴定,“阿图什人头骨”是属新石器早期人骨,似为18岁左右男性,距今约1万年。考古的发掘足以说明新疆在1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原始初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十分低劣,在漫长的蒙昧时期不断地劳作和积累原始文化。到了中石器时代,诸多原始石器造型不断出现,并渐渐趋于成熟。从新疆出土的石镞、石叶片等工具,即发现它们可嵌入木质或骨质的刻槽中,制成一把锋利的刮刀、切割器或投掷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工具。将石器再装上骨质、木质的长柄,它们就成为投掷武器,使用于狩猎飞禽或捕捉水中的游鱼,亦可作为原始初民处理各种兽类毛皮和食肉的必需用具。将其获得的兽皮用石器切割刮净,披挂于身上可御寒护体,较之赤身裸体又进了一步。与传说中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即有了文身等肤体装饰行为相比较,披盖原生皮毛,标志着人类衣着的萌芽与缘起。以实用功能为目的,是人类以护体穿着为模式走向文明之滥觞。《说文解字》曰:“衣,依也。”即人类依赖的穿衣护体也。
以生活需求为实用穿着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与动物的分离,而“骨针”的发明,则促成原始初民在穿着上的根本变化。考古工作者在天山北麓木垒县四道沟铜石并用时期遗址,发现与缝制衣服相关的“骨针”其类型有粗长、细短两种。细短的,一枚长5.4厘米,直径0.18厘米,呈肉皮色,带有骨质外露的浅驼色斑纹。粗长的一枚长8.8厘米,直径0.23厘米,通体布满深驼色斑纹。两枚“骨针”磨制精细,表面光滑、细腻。“骨针”的出土,证实了原始初民已经运用它缝缀衣服。这时,衣服才逐渐形成,改变了原始的赤身裸体或披兽皮、树叶的状况。有了骨针,能将兽皮大致缝合起来,肉体被遮盖,蔽体保暖,衣服成了文明的特征。“骨针”是体现人类智慧的“活化石”,是催化衣服雏形走向完善形制的原始珍品。
纺织是人类继穿兽皮之后的重要发明。西域的游牧民族以经营畜牧业为主体,最初的纺织原料是羊、驼等畜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提高了改进生产工具的意识,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原始狩猎人通过这种改变之力逐渐转变为游牧人。由于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提高,在一些绿洲开始有了原始农业,出现了通体凿成鱼鳞状的桂叶形石镞、石磨与石纺轮。
石纺轮不仅磨制平滑,造型别致,呈圆形,且凿有孔眼。孔眼作用很大,可以用骨棱或骨梳穿上手捻的毛纱(纬线)在经线上(纺轮)来回穿梭,纺织成粗质毛布。石纺轮的打磨、钻孔技艺高超,显示了新石器时期人类的伟大创造力,表现了人的生命时空及其制造工具实践活动的时空,就这样交替地被拓展。纺轮的出现,比骨针缝缀兽皮又前进了一步。纺织的毛布是衣服面料的新创造。它可根据人体部位量体裁衣,初具“领、襟、袖”等上衣形制和下身着“褶”,即前后开胯的“裤”装形制,衣服模型逐渐形成,形制也灵活多变,体现着人类衣冠创造活动的生生不息和变换常新。
帽冠的发明是伴随衣服的发展而产生,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原始初民、狩猎人为了捕获猎物,往往把自己扮成野兽模样,他们常戴兽头帽、兽角或系尾,以便靠近狩猎目标,提高狩猎效果,这与帽冠发明有着密切联系。为了防暑、御寒,或戴树叶蔽日,或戴兽皮护卫头顶,这是最原始的帽子。
人类在经过漫长的赤足时期之后才发明了鞋。新疆北部山区严寒地带,鞋的类型较多,起源较早,目的是保护双脚不被冻伤。最原始的是在脚面上覆一块兽皮再用皮绳系住,或穿毛皮窝子。狩猎人为抵御风雪侵袭,又在原有鞋的式样上改进、变化,将兽皮覆盖面加大,做成长筒形,这便是最早期的“靴”。
第二节 岩画中的原始衣冠
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比较,史前史研究最大特点在于其时代久远,缥缈洪荒,既缺实物,更无文字,仅仅靠推理,实难令人信服,而岩画的发现,填补了史前研究的某些空白。岩画是原始人类自我表达的一种形式,以其粗犷的原始意蕴,渗透出强烈的诱人魅力,包含着原始人类生命内在的律动感。在岩画的层面上,那匀称、粗野的凿点,刻画出一幅幅姿态生动、形体逼真的原始生活图录,记载着人类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以及文化积淀的内涵,也是原始先民萌发的原始思维与审美观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生活面貌。
在浩瀚、广袤的新疆大地,天山南北曾出现面积不等、时代不同、内容各异的岩画,是猎牧民的杰作。它作为原始人类在岩壁上的“投影”,记录了从石器时代延续至近代的人类生存活动的历史篇章,向人们展示了人类在宇宙洪荒年代野蛮而壮烈的历史画卷。
岩画形成的因素很多,是与地壳变化更迭有关,致使原先一片汪洋大海、湖泊、沼泽发生巨大变化。于是,昆仑山、阿尔泰山、天山更加雄奇壮观,重峦叠嶂。山崖的增多,为岩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岩画多刻在僻静的岩壁上,四周高山、森林,淙淙泉水流淌,绿色山野幽静,给予原始岩画一个特殊的层面。天山南北发现岩画,它又说明这些地方在远古时期是原始人类繁衍生息的活动场地。从已发现的岩画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原始人类生活与狩猎图像两大类,动物形象占据相当大的数量,展示了由野羊、山鹿、虎、牛、骆驼等组成的动物世界,揭示了新疆古代初民最早的生活方式是狩猎、游牧。岩画中有不少刻画了狩猎游牧民族的形象,以及他们穿着的衣冠,这对于研究游牧人最初的服饰文化是极为重要的依据与参考资料。
新疆岩画多刻在朝东向阳的黑砂岩、花岗岩、板岩、条状岩等岩面上,多采用粗线条的阴刻或浅浮雕的手法,也出现少量的彩色岩画,是以赭红色的砂物质做颜料,涂染显现朱红色,它是游牧人心目中象征生命永恒的色彩。
昆仑山岩画 不仅幅面规模宏伟,且表现人类在蒙昧、荒蛮时代同大自然搏斗的艰苦历程。凿刻朴拙、纯真,是原始初民童稚时代的一面镜子。胡邦铸等曾对新疆岩画做了论述,笔者结合实地考察,摘其要点,作衣冠穿着的赏析。
莫勒恰河谷口岩画 位于昆仑山脚下且末县莫勒恰河出口以南的山腰处,山形蜿蜒曲折,几千幅岩画凿刻在石壁上。据地质工作者考证,山崖的位置处在第四阶地的原始河床上。岩画层面宽阔,以动物图像占多数,羊的形象几乎占一半。它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原始初民居住的生态环境,它是古代羌族人的游牧生活区域。且末、若羌一带是古代羌族人的游牧之地。《汉书·西域传》云:“若羌,‘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这段记述与岩画内容基本相符,也是当时且末羌族人生活的写照。众多的岩画其突出的画面以“征战图”最为气魄宏伟,人物形象逼真,线刻准确,展示了当时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战斗的图像。它负载着一个沉重的、鲜为人知的丰厚文化,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珍贵历史图录。正如《后汉书·西羌传》云:“羌人,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这是它的内蕴含义,是“征战图”岩画刻凿人物形象的内在精神力量。
征战图 刻画写实动人,勾画一幅争战双方骑马互相进击的场面。追击者拉开弓箭,被追击者回首弯弓,神情紧张,预示一场战斗即将开始。画面中一骑士头戴一顶类似塞人的尖顶帽,帽耳至肩,还有一武士戴有“〓”形饰物,覆盖头顶,似其他民族或羌族人特征。双方手持长矛面向立在牛背上的武士猛刺,后者持盾阻挡长矛,盾为心形,上面刻有“升”形纹样。流畅的线条勾画出人物交战时的神态与作战双方的位置,产生了争战双方激战的情景。从一幅写实的、动人心魄的征战图不仅可以窥见羌族人、塞人在昆仑山中的战斗纪实,而且从中还能看出游牧民族帽冠的穿戴方式,那是当时生活衣着的真实写照。《说文解字·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羊的形象在岩画中占据面积很大,岩画中羊的形态、造型各异,想必与当时现实生活相符。羊是游牧人的主要衣食来源。
至于昆仑山岩画断代问题,翦伯赞先生的一段话是中肯的,他引用《秦汉史》中的有关羌族人记载:“以后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西羌之族,又循着天山北麓的天然走廊,徙人这个盆地西南。”
“也就是说,羌人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时间应当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这个时间也就是昆仑山岩画产生的年代,其下限可能延续至隋唐,文献记载着7世纪末武则天时西域的天山南麓还生活着‘群羌’。隋唐以后西域的羌族逐渐融合于吐蕃、回纥、汉族、吐谷浑诸民族之中,不再以独立的民族形象存在了①。”
狩猎人 昆仑山岩画表现狩猎人的形象,刻凿线条明朗,体型强健且富于变化。狩猎者那双有力的手,持弓搭箭瞄准着正在奔跑的野鹿、山羊。狩猎人与鹿和羊的头角、颈部、躯体及腿部之间构成与原型相近的力度感。骑马放牧人的雄伟英姿出现在岩画凿刻的层面上。马的使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岩画中狩猎人骑马放牧,是表现古代游牧骑士放牧、狩猎的情景。
狩猎图 位于温宿县天山林场的小库孜巴依岩画中有一幅颇有生气的狩猎图,狩猎者个个持弓拉箭做射猎状。猎人穿着的衣装非常引人注目:明显地刻出他们穿着宽大的衣袍,下摆大,给人以穿了厚重的毛质衣物的感觉,是岩画中少见的服饰。“袍”为长外衣,《诗经·秦风·无衣》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袍”始创于周,《后汉书·舆服志》云:“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形制多为身宽袖长,覆足及地。古时,西北游牧民族多穿袍,类似现在新疆少数民族穿的“袷袢”,是一种交领式长大衣。岩画刻凿狩猎者穿宽身袍装,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着装创制,袍服是抵御严寒的最好衣饰。
放牧图 此图是北疆富蕴县唐巴塔斯岩画,其中以“放牧图”展现草原生活风貌,具有浓郁北国风貌的情趣。此图的右上方是戴尖顶帽的牧人,他纵马扬鞭,飞奔驰骋,表现出急促的动感,似放牧归来;左下方是位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脚蹬长筒靴的牧人,似他家中的成员,好像在盼望骑马归来的亲人。简洁的刻凿勾勒出人物形象与家人等待、企盼的神态,传递、交流人物之间内在的真挚情感。四周空间浸润了大自然的灵性与活力,草原上奔跑着欢跳的牧羊狗,与天空上飞翔的小鸟,似乎都有“欢迎”主人归来的意思。充满浓厚生活情趣的“放牧图”给辽阔、静寂的大千世界增添了人间的温馨。牧人的穿戴,如长袍、尖顶帽冠、高筒长靴则与记载中的古代塞人穿着颇为相似,它又为塞人曾在此地区游牧、活动提供了证明。
狩猎图 位于温宿北境博孜敦乡,有一幅颇具特征的猎人狩猎的岩画。岩画以阴刻法凸显猎人张弓搭箭,瞄准前方奔跑的猎物。那牛、鹿、大角羊急驰于旷野,那蓄势待发的紧张神态,使观者获得了特定环境中的某种信息。岩画四周的环境赋予了一定的情境氛围,天山群峰、辽阔草原、莽莽林海,大自然赐予岩画创造者以鲜活的生命力。其中,有两位高约40厘米的猎人,他们身上披着似厚实的毡褐,这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披着的衣饰。《大唐西域记》一书中记载着龟兹人的服饰:“服饰锦褐,断发巾帽。”《文献通考》载:“衣毡褐皮氍,以缯缭。”毡褐是由细毡缝制而成,与史书记载龟兹细毡相符。博孜敦古时为姑墨地,与龟兹山水相依,地理位置相近,衣饰习俗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牧归图 则以简明的线条刻画,衬托散落四处的羊群,显出空间大面积的层面,在线与面的交融中,突出牧人一家在主妇的带领下,她双手拦着羊,流出欢庆丰收的喜悦之情。主妇穿着的衣裙呈现一种厚度感,衣服的质地似用细毡制成,那身宽厚的连衣裙装,明显地表示它是当时妇女的家常服。
上述库鲁克山古代岩画是古代游牧民族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人类早期的狩猎、祭祀或巫术礼仪,以及舞蹈、征战等图形,到长房建筑、栏杆式窝棚等刻凿图和意念性的各种图式符号,是记载古代游牧人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历史画廊。
这里岩画的产生年代:“……可以确定库鲁克山区岩画的上限时间应在纪元前5世纪以前。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居民大多系塞族人部落,是与斯基泰人同属的一大游牧文化群体,可认为其主人即创作者是塞族人。”①
争战图 位于哈密沁城岩画的“争战图”,人物刻凿写实逼真,争战双方交锋场面激烈,动人心魄。哈密是古代乌孙、匈奴、车师等民族活动过的地方。沁城距离哈密约7公里,在折腰沟处,横亘着一条流动的季节河,四周山麓崖畔上散堆着形态各异的黑色花岗质的巨石,岩画就刻在巨大的岩石上。“争战图”突出刻画九位骑马武士,轮廓清晰,武士们身着盔甲铁衣,面部刻凿线条明显,能粗略地窥见武士须眉与面部神色的疏密、细微差异。画面宽阔,长约16厘米,刻绘出九位武士鏖战双方精彩的一页。两阵对垒,战斗激烈,交战双方形态各异,特征独具。有的武士持枪跃马威风凛凛,与身边握枪的武士拼杀,刹那间,战马四蹄腾空,鬃尾飘动,虽舍去细部,却准确、清晰。武士穿戴的甲胄体现了盔甲的特征,是记载武士形象、穿着的原始记录。征战的气氛浓郁,与刻画的高度概括、取舍得当、抓取的特征相关,厮杀声犹如回荡在天宇之间。
猎人图 位于裕民县巴尔鲁克山简巴尔达湖的山坡岩壁上。猎人拿着盾牌,准备击中右上方的岩羊,一条狗也跟在羊的身后。猎人赤身裸体,头戴一顶四角状的帽冠,四角的距离相等,形同放射状,好像太阳的光芒普照大地。帽冠形状尚属首例,它象征原始狩猎人心中崇拜的太阳神,给人类带来温暖与光明,是原始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寄托。原始人类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大自然崇拜表现了虔诚的敬仰,在岩画中以头饰表现,阐释了头饰即首服的意义。对于大自然的崇拜,直接影响了新疆的后世子民。正如杨金祥在《宗教与维吾尔古代美术》一文中所说:“远在8世纪前,当东回鹘人还生活在漠北时期,在蒙古高原上建立回鹘汗国的可汗,要在自己名字前面加个‘捆’(Kil,湖泊的意思)字,以示自己是水神之裔。”《乌古斯汗》中的乌古斯可汗,分别取名“日、月、星、天、山、海”。这是先民对于大自然崇拜的延续,表明了他们的心迹。
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大型岩画 地处天山深处的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大型岩画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震惊。它是一幅反映原始人类文化的生动图像,同时也留下了原始人类服饰模式的印记。
岩画特定环境的选择会形成岩画独特的气氛与意境。康家石门子所在地山体色泽赭红,气势雄伟,水草丰盛,环境幽静,生态植被保持良好,是理想的高山牧场。岩画面积很大,它东西长14米,上下高约9米多,属地质史上新第三纪粉沙岩层面,刻画着约300人的男女人像,热烈地表达了各自的狂放、粗野的情感。凿刻技艺简洁、造型浪漫,使原始文化的虚幻性康家石门子岩刻人物特写与写实性融为一体,使神态各异的舞蹈者以及生殖崇拜的图像释放出独特的异彩,观赏者能从中领悟到生命微妙的奥秘。宏伟巨大的人像场面令人惊叹,动人魂魄。那一幅幅占有重要位置的原始生殖崇拜的岩刻,不仅使观者获得一种超越现实的神秘感,而且隐含着人类生存期望的内涵。
康家石门子岩画画风古拙、朴实。以浅浮雕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面部与形体,戴在头上的尖顶高帽或簸箕形帽冠(有的帽顶插有羽毛),显得神气非凡。大部分男女是裸体的,只有画面中心直立着穿着裙装,身高1.05米的女舞人。那简洁而抽象的裙衣,衬着左肩飘动的衣带,使她那宽胸细腰,优美的身姿在空间翩翩起舞,创造出一种空灵的情调与韵律。戴尖顶高帽是古代塞人的帽冠特征,表明古代塞人曾游牧天山一带。头饰羽毛是狩猎英雄的标记,代表光荣、美好。岩画中头饰羽毛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当代,现今的哈萨克族少女爱在帽饰插上羽毛,把它视为吉祥物,寓意“驱邪、消灾”。帽冠同时具有一种礼仪的形式,其历史性与价值取向是鲜明的。裙装则是当今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常服,妇女们在冬季也喜爱穿着裙装,下穿毛裤与长筒皮靴。岩画人物形象的着装与现代的民族装相似,表明它们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贯穿着历史的承袭性与传统习俗。
对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断代,我同意这种观点:“岩刻画,也直接显示出早晚相互叠压的痕迹,晚期的刻画,覆盖了早期的图像,应该是完成最早,也属于画面最上部的一列巨型女像,并显露出不同的思想信仰。因此,康家石门子岩刻的始创时代远比原始社会晚期的战国阶段要早,应是没有疑问的。”①
天山深处周围的岩画与原苏联、中亚一带、内蒙古岩画,从内容到形式表现上都有相似之处,都反映出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特征和相互融合,形成特殊形态的岩画艺术体系。至于断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一部分可能早到铜石并用时期,一部分则可能在公元前后,而也有可能在公元12或13世纪的蒙古时期,甚至更晚,如与元朝喇嘛传布有关的古藏文岩刻也有发现。”①
第三节 西王母的传说
《穆天子传》中记述周穆王巡游天下曾到新疆,会见居住在高原上的一位原始部落首领西王母,互赠礼品,传为千古佳话。神话般的动人传说,显示了秦汉以前我国古代中原和西域各国友好往来的景况。
西王母并非实有其人,迄今为止,尚找不到确凿的依据来说明或引证。周穆王却实有其人,是西周王朝第五代国君,姓姬名满。据《穆天子传》中记载的“昆仑”、“春山”,其地理位置与新疆的昆仑山和葱岭基本相符。著名的敦煌莫高窟第249窟、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以及内地画像石刻中都留有西王母的形象,有关西王母的传说深入而又广泛。
有关书中所指“西王母之邦”和“天子宾于西王母”等传说,在《山海经》中亦有记述。书中云:“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戴胜即指妇女首服,豹尾虎齿即指以虎头图腾为标记的某部落。
西王母的形象与衣冠服饰穿戴多流传各地。在西人著戴岳译的《中国美术史》书中插图即有武梁祠石刻画像,曰:“西王母戴五梁冠,端坐楼上。”梁冠为在朝文官所戴,三品五梁。在汉画石刻中也为贵妇戴冠。武梁祠石刻画像中又刻出五梁冠为西王母所戴,它仅为一种传说。
东汉嘉祥蔡氏园出土的“西王母像”,与山东嘉祥宋山汉画像石颇为相似。原题为西王母戴胜,此“胜”指妇女首饰,与《诗·齐风》中所说:“总角兮”;《礼记·内则》中“男角女羁”及《丧大记》中疏云:“髦者,幼时剪发为之,至年长则垂著两边”大体相近①。
山东两城汉像石,刻画技艺精巧,画像中表现了神话般的浪漫色彩。画像中刻画西王母的衣冠服饰与其造型反映一种神秘的意蕴,呈现了人们的希望与欲求,包含着宇宙万物。
汉代画像风尚流行一时,不仅有画像石,还有画像砖和帛画。题材多取自神话传说,奇禽异兽,也有少数描绘社会现实的。画像构图饱满、匀称,刻画风格为文与野、雅与俗的交汇融合,形成一种富有民俗性文化内涵的独特风韵,受到人们的喜爱。
《西王母》画像石刻怪诞奇特,是一幅装饰性浓郁的肖像画。西王母端坐正中,身着宽袖襦袍,双手拢袖,神态安详。头戴冠,冠顶站立青鸟,表现了《山海经》中的一个情节,即“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与图中下端两鸟对称呼应。
西王母全身披着帛巾,飘拂浮动,形成匀称的云纹,使主体人物似在云彩缭绕之中升腾。异样怪诞的两侧人物造型,是一男一女人首蛇躯,蛇身盘结缠绕,构建成绳纹图案的蛇尾座,勾画出一个总体形象,使神态威严的西王母稳坐蛇尾座上。蛇尾的末端幻化成两只生机盎然、勃勃灵动的青鸟,它似回首顾盼,挺立在神话般的天宇间。奇特的构成方式浸染着西王母的造型更具浓厚的神秘色彩,这是神话传说的魅力,是民间艺术丰富的想象力和工匠的独特手法。
由于历史的变迁,其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差异,西王母的形象由“豹尾虎齿”的凶神变成容貌端庄,戴冠着宽袖襦袍,或帔帛绕身的吉神、女神,揭示了民间对神的不同祈求与愿望,是神画像内涵在外形造像上的巨大变化。
总之,西王母的形象显然脱离了原发性的主体生命律动形式,反映民众主体的心理、情感与不同的文化层面。
第四节 胡服
据史籍记载,我国古代对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区各民族一般都泛称“胡”。《汉书·匈奴传》载:“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辞海》载:匈奴称为胡或北胡。乌桓、鲜卑等在匈奴东,故称东胡..西域各族在匈奴之西,故泛称西胡……
所谓“胡服”,即短衣齐膝、窄袖、左衽(即左边开襟)和紧身窄袖,下着裤装的衣装特征。此服饰轻便灵活,适宜骑马作战、放牧游猎,与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宽衣系带式汉装有较大差异。胡服不仅为作战时武士装束所需要,而且广为流传于民间,影响极大。
“胡服”形式实则是以“上衣下裳”制改下裳为裤装。“裳”即“裙”,呈筒式,上古时期男女都着“裙”,称“上衣下裳”。皆为遮护下身之服。所谓“胡人”,其多数为游牧人与马背民族,习于骑马,善涉水草,驰骋群山峻岭。他们的服饰以衣和裤为主要服装,称曰:“裤褶服。”《急就篇》云:“褶为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衣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左衽多是胡服衣饰的特点,广袖则为适应汉装,胡服则是窄袖。
“裤褶服”名称始见于汉末,但仅从新疆各古墓葬出土的衣冠服饰即可窥见,裤装为主要服饰形式,如且末扎洪鲁克古墓、哈密五堡古墓、墓葬古尸均为3000年前的当地民族。他们都着毛皮大衣,下穿裤装,还有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吐鲁番地区苏贝希古墓,古尸穿着皮衣、皮裤。自纺毛布衣裤、连靴套裤等。笔者从考古实物证实,“裤褶服”始于西域古代,可追溯到距今3000年前新疆哈密五堡古墓、扎洪鲁克古墓,其出土裤制就有合裆与〓裆裤。
以裤装为外服,自裤褶服始。春秋战国之际,奴隶社会溃崩瓦解,战事频繁。正在此时,出现了我国服饰史上最早的改革家——赵武灵王,他积极推广胡服(即裤褶服),因此服便于作战,便于骑射,所以改服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战争方式发展变化所驱使。当时的北方地理环境存在着局限性,战场从平原扩展到山区,形势逼人,作战方式必须改变。当时地处西北的赵国,为适应军事发展需求,采用以弓箭为主要武器,全军上下皆习骑射。“胡服”与骑射关系密切,窄袖、短衣、紧身裤、革靴等服饰便于作战,活动灵便。武灵王推广“胡服”影响极大,许多地区甚至民间皆仿效之。《事物原会》引《舆服杂事》云:“赵武灵王有裤褶之服。”武灵王服饰改革的贡献相当重大,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与胡服密切相关的是“靴”。赵武灵王改屦舄为着靴。《释名》云:“古有舄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事物纪原》云:“履三代皆以皮为之,单底为履,复底曰舄,盖祭服曰舄,朝服曰履。”《中华古今注》云:“靴者,盖古西胡服也,昔赵武灵王作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至马周改制长靿,取便乘骑也,文武百僚皆服之。”
赵武灵王仿效胡人腰带,因其便利骑射系束紧身,可将随身物件附系腰带之间,并附饰若干小环,将携带之物挂扣于革带之上。其仿制腰带曾有记载。《战国策·赵策》云:“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即古人革带镶饰黄金带钩。据周锡保著《中国古代服饰史》中论述:“但带饰之有鞢〓,即有环和加饰金银等,应自赵武灵王始。”
散见于全国各地的古代胡服尚不多见,新疆出土的古代服饰另有文章论述,此处不再重复。现仅举例,以资考证。
据周锡保著《中国古代服饰史》中所画山西省侯马出土陶范,为东周末期春秋时代胡人服饰。所画两人均为窄袖短袍,一为左衽,一为右衽和领,下身穿裤的服饰形式,与“裤褶服”相似。此陶范的出土其时间早于赵武灵王改革服制,证实改制胡服是有所依据的。
胡服流散各地的资料不算多,现列举一二以供观赏。《文物》1955年第1期发表一幅东周时期的“持竿胡女铜像”。此胡女铜像体型丰圆粗壮,身穿短袍窄袖,梳双辫垂于双肩,腰间束带珰的革带,足蹬靴,是古人少女服饰。
“战国铜人”是穿窄袖、短衣装的杂技艺人。原件在美国华府弗里尔美术馆。
“戴冠战国铜人”是穿窄袖齐膝短衣的男子。此件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
“战国银人像”是穿着窄短袍,腰束革带的胡人装。原件在日本。
“当户掌灯铜人”是穿着窄袖对襟短衣的仆从装。此件出土于河北满城。
第五节 原始装饰与审美
远古时期的边疆原始人类,从半兽半人、茹毛饮血的洞穴中走出来,他们既具备与大自然搏斗的能力,又有发展生产的渴求,这就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与生存竞争的结果。粗笨沉重的石器工具使原始人类捕猎了食物,但在生活上却造成许多艰难与不幸。面对严酷的现实,原始人从打制粗糙的石器进而发展到制作精巧的细石器,然后再装上木质或骨质的手柄。经过细致琢凿的工具,不仅外观得到改善,还能较快地处理各种兽类毛皮。装饰性工具的细微变化,孕育、萌发了人类对自然物的审美体验。
装饰性石器与骨饰件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位置,赐予了西域的楼兰等地区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活动。考古学者曾采集到柳叶形、桂月形石镞、石矛。这些细石器不仅使用方便,而且美观大方,有的石器通体被凿成鱼鳞状,其造型与刻纹透出粗野、淳朴的原始美。那饱满的构图,既匀称又变化无穷,予人以独特的美感。一件件装饰化物件的出现,意味着原始初民造型观念的拓展,装饰性造型融入了制作石器之中。
砾石坠 新疆考古队在阿斯塔那细石器文化遗址采集时,发现了发出迷人光彩的砾石坠。“砾石坠”呈桃形,中心部位对穿小孔,对称、均匀,显示了磨钻技艺的熟练。利用坚硬的砾石制作饰物,无论是欣赏或把玩,都充分体现了边疆古代初民在与大自然抗衡中,在游牧渔猎之余,仍然有着美化、装饰自己的情趣,这正是古代人类编织文明发展史的序曲。
心形骨饰件 此件制作巧妙,构思独特,是考古工作者在木垒县四道沟遗址采获的,为铜石并用时代的饰件,即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出现铜石、金石并用,对于生产、生活用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件用骨质制作的装饰品,长约6.2厘米,厚约0.8厘米,形状扁平略呈凸形,上端倒置呈三角形,适中的起着连接作用。边长约2.9厘米。三角形中镂空雕琢成心形,下端另接长约4.8厘米的心形,上下对称,蕴含心心相印。骨饰件的中心是镂空的,最下端还刻成凸形呈椭圆状骨钉,似带钩连结上端。它似项链又像独特的艺术品,在整体艺术结构中发挥得自由活泼,表现出率真的生命力,影射出古代某些生活气息和原始初民对自身创造价值的某种肯定,呈现出人类精神主体和意志相联系的审美愉悦。
考古所曾在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孔雀河古墓沟遗址发现一件件稀有的骨质项链、木质头簪、玉珠、骨针与木针。
骨质项链 其形有筒状、圆珠形之分。造型古朴、原始,由一颗颗骨质筒状、圆珠状连接串成,琢磨均匀、形状奇特,是件不可多得的装饰品瑰宝,其艺术价值并不逊色于现代的珍珠、玛瑙项链。
骨簪、木簪 簪,单股如针,以簪贯发为饰。古有骨簪、玉簪、金簪。此出土骨簪,上端呈椭圆、圆柱形,下端如针。木簪顶部呈长方形,并刻有简洁、朴素的几何纹,优美的曲线与四出菱形图案融会一处,构图均衡疏朗,含有一种韵律的节奏感,予人以活力,具有古朴的原始美。骨簪既精巧又美观,表现了原始初民对仪容美的重视,开始用簪固定发型,求得一种仪容的修饰美。仪容审美不仅是个人的爱好与兴趣,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的表征,它显示了东方民族审美思想的独特性。
骨针、木针 造型别致,纹饰各异。此骨针没有针眼,顶部精细地琢出桂叶形、四菱形、圆锥形、圆珠形等针柄,柄部刻出细纹,针部磨制光滑。“木针”是最原始的“纽扣”,既可别住无扣的上衣,又是一种装饰品。作为实用的装饰性物件,在特定的环境中,构成某种气氛,从而产生特有的审美效果。
原始初民不仅在佩戴装饰物件上讲究美化,而且在日常用具上也精琢细雕。据考古工作者羊毅勇报道:出土于新疆木垒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把骨梳,它的造型呈长方形,扁平而光滑,另一面是稍有麻点的骨质孔,长约8.3厘米,宽2.4厘米,共计6个尖状齿,这种造型的骨梳在新疆是首次发现。按其齿的形状、疏密与间隔的特点,可以看出,此梳主要是用作梳理兽毛,为制作毛纺织物图28骨针。孔雀河古墓沟出土做好了准备。
精美的玉石饰品
新疆盛产玉石,这是大自然赐予的得天独厚的珍贵宝藏,且历史悠久,蕴藏丰富。考古人员在楼兰地区采集到远在新石器时代高5.4厘米,宽5厘米,厚1.4厘米的“玉斧”。斧的刃部较厚,虽有自然裂纹,却闪烁着玉石的晶莹与光洁,以名贵的羊脂玉制成的“玉斧”,反射出古朴的造型情趣。
玉石珠饰出土于孔雀河古墓沟,是随葬品,为年轻女干尸颈部、腕部佩戴,软玉质,较有透明感,呈管状空心、菱形四角形、圆柱形,琢刻巧妙,细润光滑。不久又发现各种玉石珠饰,五光十色,耀眼夺目,象征着原始初民创造的光灿灿彩虹。爱美的心理融入饰物之中,体现出朦胧的人体装饰美感意识,以审美的观点来对待自己身体的完美性。
新疆玉石的开发利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中华民族祖先黄帝时期就有记载。《山海经》曰:“密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黄帝乃取密山之玉,而投于钟山之阳。”《贾子通政语》上篇曰:“黄帝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蚩山”、“密山”、“昆仑”都泛指新疆玉石产地。玉石,是古代西北少数民族装饰自己的佳品,也是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物证。据载: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一座古王府墓葬,出土了举世罕见的文物,而玉器多达700多件,经鉴定绝大多数玉器“基本上是新疆玉”。它的发现证实早在殷商晚期新疆玉已大量输入中原。此后,交往不绝,绵延不息。玉石作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往、传播的枢纽,早于“丝绸之路”,是一条闻名于世的“玉石之路”,它为西域古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疆玉石以和田玉质地最好,有名贵的墨玉、脂玉、翠玉等。墨玉墨而透亮,脂玉光泽如羊脂,翠玉绿如碧玉,翡翠是装饰品中的珍品,流传极广,蜚声中外。杨汉臣等著《新疆宝石和玉石》一书中写着:“商代是我国琢玉工艺发展的重要时期..周的礼器、秦的玉玺、汉的玉衣、唐的玉莲花、宋的玉观音、元的渎山大玉海、明的子冈别子..历代这些玉器大都是由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利用和田玉琢成的玉器,堪称我国玉器的瑰宝,内含东方传统文化装饰性审美意趣,和田美玉可与世界上的精美玉石相媲美,令世人赞叹不已。
古拙的青铜器、金器装饰纹样
青铜器、金器饰物的出现,显示着装饰性饰物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新疆的和静县察吾乎文化曾出土了一面青铜器——为公元前8年至公元前5世纪的一面圆形铜镜。为新疆地区仅见的早期铜镜,镜面中心镶一个弧形的钮,主体纹饰为凶猛的巨兽,它圆目大睁,血盆大口露出巨齿,啮咬着尾部,使丰满的兽尾四散飞扬,与发达的肢体蜷曲于纹饰之中。狞厉威严的兽纹渗透着一种奇拙、怪异的意蕴,犹如原始初民深信的图腾物。野兽纹饰具有雄浑的鄂尔多斯造型风格,在绿洲草原古遗址与岩画中多有发现。野兽纹饰已非常物,它在古代原始初民的观念中,融入的原始宗教渐渐被神化,形成一种带有原始特征的艺术形式,野兽纹饰中怪异的纹饰,具有某种象征符号,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权威神力观念。
据载:“吐鲁番艾丁湖潘坎出土‘虎叼羊纹铜饰牌’,长11.1厘米,宽5.3厘米,厚0.3厘米。正面铸成一只透雕的老虎,睁目竖耳,张口叼着一只羊。猎获物到口后老虎不慌不忙迈步回山林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背面有三个环状钮,头端二个,尾端一个,布局呈三角形,以供附缀于其图33白玉斧。新石器时代于罗布泊采集。此玉斧形似长方形,刃部留有琢磨痕迹,至今仍很锋利、流畅。玉斧质地为名贵的羊脂玉,晶莹洁白,细润光滑,经阳光照映,熠熠生辉。新疆考古所藏他物件..以往,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关系时,很少引用新疆的资料。木垒县收集的野猪搏马纹铜饰牌,与西伯利亚出土的同类饰牌构图,造型非常相似。吐鲁番新发现的虎叼羊纹铜饰牌,与1975年在萨格雷河谷斯基泰时代的古墓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简直雷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新疆地区的广泛分布,填补了区域空白与这一草原文化传播链条上的缺环。”①撰文具体地写着吐鲁番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的造型、质地及与鄂尔多斯纹样的内在联系。
“虎叼羊纹铜饰牌”与上述“野兽纹饰铜镜”都具有鄂尔多斯纹样风格,但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变化。前者纹饰酣畅、饱满,突出它巨大的身躯与明显夸张的口部,呈现出野兽的凶猛与猎获时的种种神态;后者虽张开血盆大口,却首尾摆动,又夸张其肢体,于其动态之中蕴含一种神性的张力,赋予一种神秘力量。实际上,新疆已发现多处鄂尔多斯式纹饰的造型饰物,它反映北方草原文化圈的一种形态特征。在这个文化圈内,由于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彼此相似,草原游牧人之间彼此交流往来的互融性,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亦呈现出一致性和稳定性,西域地区更受中亚文化的影响,因此,纹饰中蕴含着多种文化因素。
金器纹饰的不断发现,显示着西陲边塞进入了文明的黄金时代。考古者在伊犁河流域,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塞人墓葬发现了金簪、金耳环、铜耳环、铜发钗等金、铜饰物,又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古遗址发现了战国时期最富特色的黄金饰物。它色泽纯正,闪闪发亮,制作手艺高超,堪称传世金饰中的代表作。其中一具“虎形金箔腰带饰”,长25.4厘米,宽3.3厘米,金光灿灿,造型构思巧妙,刻画出猛虎奔跑、跃动、张嘴啮咬的雄威与出没山野的巨兽体态。两虎相对,它们的头部、肩与腿部都做了有力地夸张,刻画坚实、粗壮、筋肉凸起,特别突出两虎的蹲伏状,翘起的尾部卷曲而又富有韵律感,创造了一种气焰逼人、奔放不羁的激烈气氛,连同那旋转式的旋纹,刻画得十分流畅。虎形纹样装饰,使观者获得一种生命的活力,反映出远古时代初民们的某种精神需求。
“虎纹圆形金饰牌”也是以猛虎为主体形象的黄金饰牌,突出虎的头部、身躯与四肢蜷曲于圆形饰牌中,并作跳跃奔跑之状,既突出虎的凶猛,又简化其肢体部位,适当地融入旋纹。
上述金属饰物与古代塞人有着密切联系。王炳华著《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书中曾提及这批出土的金器。他举例说:“在那座年仅20多岁的贵族女子墓中,装饰腰带的金牌就见到8块,每块金牌都重20克以下。蓬勃生气的造型,洋溢着生命的流动感,它夺目耀眼,切入动态变异中的熠熠光泽,透出造型迷人的神韵。”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曾经告诉人们:“塞族人王族享用着上天赐予的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有着黄金饰牌,人死后,要用黄金制品入葬……”在阿拉沟东口打开的塞族人贵族墓葬,为我们了解塞族人,了解吐鲁番的开发建设过程,提供了更为丰富详实的实物资料。
塞人是曾经驰骋于中亚草原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足迹也留在了西域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所留下的珍贵遗物可供历史学家补续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载:“塞种人,古代族名。历史上主要分布于中亚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曾散居中国西部。西方古典作家称之为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为塞卡人,中国史地文献称之为塞种、塞人。”塞人崇尚以虎、狮、熊为主体的装饰性图案,视其为表达情感的有生命的实体,创造出显示自己力量的膜拜偶像。一件件出土的表现得酣畅淋漓的装饰化饰物,传达了塞族人的审美倾向与观念。图案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朴拙的气质、奇异诡谲、飞扬流动的神采,绽放出巨大的、摄人心魄的魅力。
独特的造型特征,究其原因出于它的源流与生成,呈现着先民们的思维生存环境与情感的流露。即便是斯基泰风格或鄂尔多斯造型,也都同源于草原游牧文化圈内,是一种超越部族的文化形态,具有共性的特征。
金项链则是出土于阿拉沟古墓,它是古代妇女珍爱的宝物。它不仅璀璨夺目,且制作工艺精细,其金质项链采用极细的金丝编织成链状,相隔一定的距离镶上色泽柔和、温润光洁的白玉、翠绿的孔雀石,显得晶莹璀璨、华丽夺目、玲珑剔透,是件弥足珍贵的金、玉镶嵌首饰。
金耳环造型精致、铸纹流畅,也是一件少为人知的金饰。此耳环金色纯正,黄色中闪透光泽。其长2.5厘米,环径1.5厘米。耳环的上端为圆形金环,下端系着塔锥形坠饰,坠的上端铸出密集如珍珠的珠点纹,下端呈座状式,衬托整体金耳环饰。
葡萄坠金耳环其造型疏密有致,具有一种韵律感。耳环的上端系着一个圆环,直径仅1.3厘米,环的下端以两个小钩相连紧靠金坠。坠饰由8个空心圆形金泡组成,连接为一体,似一串丰硕的葡萄,它的色泽和亮度透出纹饰璀璨而闪烁。
这些金银饰物不是单纯欣赏、美化的装饰物,它所以被誉为珍宝,是因透射出时代的风尚变化,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开端,是古代人类集感情、审美、原始宗教、生活实用等诸多因素的产物,代表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神秘含义。那种对“纹饰”的特殊情感、认知与表达,传递出原始初民内心世界的某些隐秘。“纹饰”以“纹”为核心,它在文字诞生之前,也是一种记录历史与文化的方式。《易经》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晋人干宝注说:“四时之变悬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具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以“文明而化成天下,即所谓的‘文化’,而文明之文指天文、地文、人文,也即天纹、地纹、人纹,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迁变;地文谓地理气脉,山川植被形状;人文是人的文彩装饰,包括纹饰、文章、礼仪等内容①。”阐述了“纹饰”涵盖面的博深,包含着宇宙万物与哲理内容的精髓。一件件珍贵的装饰品使深埋地下数千年的古代宝物终于出世,它使人们从中悟到一个真谛:人类的繁衍生息与文化累积的延续,是靠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进取与实践获得的。实际上,人的生活需求只有靠人类自己,它也包含着人类的审美意识,那附着于金、铜饰上的纹饰与造型,那一串串色彩斑斓、晶莹剔透的装饰品,是原始人类认定的万物精灵,是他们心灵辉映的火花,是最早的精神寄托。同时,玉石、金铜饰物精巧的制作和应用,也表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与水平,反映出边塞城邦诸国、游牧民族时代的文明背景。人们透过感官、视觉,体会到古代人类的文明发展坎坷不平、生生不息地朝前迈进的艰难历程。
面饰的装饰化
文身、文面是人类文化中最原始的肤体装饰,纹样各异的装饰,构成一种无声的语言,其历史几乎和整个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纹饰的古拙或浓艳,多有特定的内涵,在世界某些地区曾流行过,且渐渐形成一种习俗,曾盛行东南亚、东北亚、非洲..我国台湾的高山族、云南的独龙族、傣族、海南的黎族、四川凉山彝族等似有文身、文面之俗。此俗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久远。《汉书·地理志》曰:“越人,文身断发,以辟蚊龙之害。”《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墨子·公孟篇》也有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越,方外之地,断发纹身之民也。”
西域与内地相隔万里之遥,过去与现今在各地居民中很少发现“文身文面”的习俗,然而,近年来,新疆考古人员却在偏远的南疆且末扎洪鲁克乡古墓,发现距今3000年前后的两具男、女古尸。由于当地干旱少雨,古尸保存完好,发现在他们的面部饰有布局对称、纹路清晰的纹饰,画在鼻、眼、额、颧骨部位,似用矿物原料,如雌黄、雄黄、铅黄以及赤铁矿等涂抹。男尸面部太阳穴处(两侧均有)画有卷曲的大羊角纹,它又似太阳,中心稍圆,四周呈放射状。女尸面部眼窝下端左右两侧显出对称的卷云纹。面纹的发现与古人对日月、天宇等大自然崇拜有着紧密关联。李砚祖在《纹样新探》中道:“研究《周易》的学者曾指出,卦爻辞的表现形式是‘假象喻意’,即拟取人们生活中习见常闻的物象..以‘八卦之象’为例,所谓‘八卦之象’,即八卦象八类事物。以自然界八种自然为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自然客观物象是人朝夕可见,其形其性都明白易察,深层的理性规范、哲理,所谓‘道’,一旦与人们所熟悉的自然物象的存在相比较,便能获得很好的传播和接受效应。”
真正见底蕴的是人类运用自然物,给予象征性表现与带有浓重的原始意识和先民对于大自然的认识,渐渐积沉于心灵与思维活动中,并反映在面饰的纹样上,由此又引发某种审美观念或原始宗教意识。面饰赋予人美的丰采,也含有取悦异性的崇美心态。
第六节 原始的、古老的衣冠服饰——铁板河出土衣冠
位于塔克拉玛干东缘,曾处于“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绿洲——古代楼兰,是人类活动、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从侯灿楼兰考古实地调查结语中获悉:“..采集的许多细石器文化标本与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其他地点的细石器文化遗迹比较,这里可能是史前人类的重要聚居点。”丝绸之路的兴起,促使了楼兰的发展与繁荣,形成为楼兰国,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史记·大宛列传》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记载着楼兰是“城郭之国”,盐泽即罗布泊。罗布泊是我国著名的湖泊,从第四纪起,受到造山运动的影响,形成罗布泊洼地。罗布泊又称“游移的湖”。随着塔里木用水量的增大,今孔雀河下游已经断流,罗布泊也早已干涸。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有历史记载的著名古代楼兰之国也销声匿迹,成了千古之谜。
“楼兰睡美人”——早期衣冠的发现
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队,由考古专家穆舜英主持,曾在楼兰古城、罗布泊北面铁板河地带古墓中,发现保存完好的女尸。此古尸于1992年在日本展出时引起轰动,震惊中外。古尸被誉为国宝级文物,是新疆迄今为止发现的早期古尸,成为考古学界的奇迹。据测定约有4000年历史。
古尸的发现,初步揭开了古楼兰人的穿着衣冠之谜。古尸被称为“睡美人”,其全长152厘米,外形特征:“下巴尖瘦,深目微闭,鼻子高而尖小,薄嘴唇,褐黄色头发披散肩上..”①她穿着粗纺毛披风式上衣,紧裹全身。衣的形式虽不清晰,更不完备,却能裹住身体。衣的前襟用磨光的尖细而光滑的木针别住,起着纽扣作用;头上戴着缀有毛线边饰与插羽毛的毡帽,呈尖顶形,能将护耳、护颈的功能连成一体,并有毛绳系于颏下。脚穿生牛皮短靴,形式虽不规范,却保护了脚面与脚后跟。
衣冠服饰的发现,揭开了原始初民衣饰创造的序幕。出土的衣物使人们顿悟:原始初民为了生存,具有一种对于生命渴求的冲动,他们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创制石质、骨质纺轮,开始选用羊毛、驼毛捻成毛纱,运用纺轮织成原始的粗纹毛织物,摆脱了以披兽皮为衣饰的状态,创造了古朴、厚拙按照人体长短编成的披风式衣饰。与披兽皮相比,毛织披风先进了一步,它在人类服饰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毡帽”的出现,可视为人类早期衣饰文化的精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种标志。毡帽上的羽毛饰,不是单纯的装饰品,它在原始初民的心目中,是一种偶像崇拜或象征物。羽毛冠既是狩猎人的头饰,又是一种保畜平安的吉祥物,是实用的功利性与美感形式结合的开端。
古罗布泊人创造的为护体需要的衣冠服饰,足以证明他们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步入以毛织为衣的时代。那顶护耳插羽毛的毡帽,毡色纯正,毡质平均、厚实。衣冠面质料的变化,是人类衣饰文化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和一个时代的象征。
石雕、木雕人形象
楼兰地区孔雀河古墓沟墓葬内的随葬品石雕、木雕人形象,多为女性,有的头戴尖顶圆形帽冠,胸前穿有毛纱,有的头发披散肩后。人形象随葬品无不烙上衣服穿着的印记。出土实物表明,当时居住罗布泊洼地的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氏族成员在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女性雕像的出现,说明女性尤受尊敬,似为一支以母系崇拜为特征的原始部落。她们已经离开穴居,改变了披兽皮、树叶遮身的状态。衣冠的穿戴,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和胜利的表征。
第七节 裘皮衣袍的发端——五堡出土衣冠服饰
哈密五堡出土的衣冠服饰颇具特色,这与哈密的地理位置与区域环境密切相关。哈密为新疆东部的门户,地处内地与新疆咽喉要道。从甘肃的嘉峪关到哈密,须经过玉门、安西等地,路途中尽是戈壁、沙漠,十分荒凉。到了哈密渐渐显现一片绿洲。清人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有确切描述:
玉门碛远度伊州,无数瓜畦望里收。
天作雪山隔南北,西陲锁钥镇咽喉。
哈密古称伊州、伊吾,历史悠久,地理位置显要,被考古界发现并承认为新石器文化点,曾采集到珍贵的用砾石制成的刮削器、锥形石核及坚硬玛瑙与石髓。社会发展到了青铜时代早期,曾发现距今3000年前的哈密五堡乡古墓群葬,一处竟葬好几百人,证实了哈密人活动频繁,是块休养生息的地方。
哈密五堡乡古墓出土的衣冠服饰丰富多样且形式清晰。哈密五堡乡古墓,“是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阶段的一种考古文化..由于死者入葬时的衣着、鞋、帽、铺垫的皮、毡大多未腐……提供了研究当时生活的丰富的实物资料。死者头戴尖顶毡帽、穿毛皮大衣或皮革大衣,着长筒皮裤、高靿皮靴..各种毛织物,色泽鲜艳如新..皮革鞣制、脱脂水准亦高,革制品柔软。这是研究我国早期毛织、制革手艺难得的实物资料。随葬的牛、羊、马骨,说明畜牧业经济在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还发现小米饼及青稞穗壳,表明了农业经济的状况。”①
裘皮衣袍的独特样式
绿色大自然的赐予,给予哈密地区水草丰盛的环境,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为服饰的原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御寒蔽体,裘皮衣袍脱颖而出。《易·系辞》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鲜明地提出人类离不开宇宙生态的大环境,人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创造了物质文化。
哈密人创造的裘皮衣袍,毛皮在内,皮板光滑面在外,形式为交领、对襟、双袖连缀手套,袖口与手套相连接的衣袍。衣袍与手套缝缀的皮袍御寒保暖,这种款式尚属少见,实际上也仅此一例。古代称谓的“袍”,即不为上衣与下裳的衣服,形式为长度过膝,呈直筒式,下摆宽大,便于骑马放牧、狩猎。彼得·波格达列夫在《作为记号的服饰》一文中曾说:“服饰的穿着不仅关系他自己的个人趣味,而且也顺应地域的需要,以符合它的环境标准。”实际上,不仅是环境的标准,更显示了区域文化的共融性,服饰样式的风采,同时受到环境的限制。
甲骨文中的“裘”字为象形文字“〓”,作毛在外的象形。《说文解字》也说:“裘之制毛在外,故像毛。”《诗·秦风》曰:“君子至止,锦衣狐裘。”毛皮在外,故又罩上一件锦衣。上述文字介绍了古代裘皮的概况,是记载汉文化先民的穿着样式。新疆出土的裘皮袍服,表现了游牧民族粗犷、雄伟的款式,它不仅适应环境,也体现了游牧人生命活动的一种形态。
原始初民的衣袍纽扣极为简单、粗放,像罗布泊人用树枝刮削成尖细光滑的木针,别在衣服上,保暖而不透风。哈密人又进了一步,它将树枝削成细小的长度约3厘米左右的小木针,在衣袍前襟间隔一段距离缝缀毛线纽襻,小木针套在纽襻处,一种新的纽扣形式便诞生了。纽扣,它既美观又能使衣袍合缝而不透风,物质文化的发展与变化,证实了人类对功利性及实用性的需求,是从人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变化、创造而获得的。
毛织衣袍的新变化
捻毛线纺织成粗毛布,是衣饰原料史上的一大进步。古代哈密人的粗毛布厚实、细密,质地上乘。以粗毛布为服饰原料,使衣袍柔软、耐用。其形式清晰,具有游牧地区衣袍的特征,是套头式、交领、直筒形长过膝的粗毛布衣袍。裁制方法与内地略有不同,袖子较短不超过手臂,连着上衣前片,与袍服相连,简便合体。
袍服色彩为褐色,显得平淡、深沉。但在衣袍的领口与边缘处却饰以墨绿色的毛线饰纹,使袍服增色生辉。
袍服附系的腰带,是用暗褐色,夹以红、蓝、绿色的毛线编织成辫状,垂着流苏式的毛线穗,赋形设色具有古代人的审美意蕴。由于冷暖色调搭配得恰到妙处,使这条毛织腰带柔丽夺目,呈现出神奇般的绚丽与自然色泽的韵律。
腰带起了紧身护体的作用,它的萌发揭示了这样一个真谛:“人猿揖别”之始,大自然显示了对人类无限的威慑力量,但是,当人类在各种物质创造性活动中展示出人的本质力量时,不仅能够征服自然,而且也孕育着人类审美意识的萌发,它是人的智慧、力量和意识的结晶。
尖顶毛线帽
哈密五堡古墓出土衣物中有一件距今3000年前的古代哈密人编织的尖顶形毛线帽,它不仅弥足珍贵,且结线编织方法竟与现代的毛线编织法相类似。
毛线帽是由捻成粗宽的浅驼、深驼两色毛线编织而成,显得厚实、纯净。从帽顶往下结出明显的辫状形边饰,致使整体呈波状似的纹路,编结规律有序,呈现出朴素大方的美感效果。
尖顶式帽冠不仅护头,还保护双耳与颈部,是抵御风寒的上品。尖顶帽式样流行于中亚、西域一带,孕育了地域性的共融与互补,呈现出游牧民族帽冠的特征。
第八节 服饰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扎洪鲁克出土衣冠服饰
扎洪鲁克古墓位于且末县约6公里处,处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一带。墓葬约在公元前9世纪,相当于中原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古墓随葬物、葬俗形式与古代土著居民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相关联,其中尤以衣冠服饰最为显著,具有浓郁的地域性特征,为研究、考证衣饰文化发展倾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毛织衣袍与裤装
据参加古墓发掘的克由木等人报道:“男着咖啡色平纹半长袷袢式粗毛质单衣袍。女着绛红色斜纹过膝粗毛织连衣裙和长裤。男女均穿毡袜和长筒薄底软皮靴。”
实际上,上述出土的两件毛织长袍、裙装,是西域早期衣饰形式的服饰文物,它的款式与形式对于西域地区的服饰影响极大,上述引文中提到的“袷袢”,即现在新疆少数民族长袍的称谓,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服饰的历史承袭性与延续性。
男式长袍形式为套头、交领,长度为袖口过手指,身长过膝下。交领衣是古老的上衣款式,前襟分左右两片,交掩于前胸。
女式裙装实则也是袍服,只是下摆宽大并拖至脚面。形式也是套头、交领。在绛红色的斜纹粗毛布的领口和下沿至衣饰边缘处以及上臂均镶饰有色泽为白、蓝相间的毛织纹饰。男袍也以同样的色泽与纹饰镶边,使袍服明丽而多彩,突出了服饰的审美主体特色。衣饰上细微的装饰与服饰色泽交相融合、和谐统一,不仅锦上添花,而且更突出了整体特征、审美情趣与地域性衣饰文化的色彩。
原始游牧生活以及广阔的绿色大地赐予扎洪鲁克人良好的生态环境。他们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的衣食来源,反映在衣饰原料上也是以毛纺织为质料。袍服的质地与色彩以及衣饰边缘的装饰,反映了扎洪鲁克人衣饰审美观念的历史性变化,特别是历经数千年而不变的染织色彩,证明古扎洪鲁克人已步入穿染色衣饰的时代。
服饰的设计与制作,反映着社会的审美情感与情趣,这种感情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向前演进,逐渐形成一条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长河,与人类生存息息相通,融为一体。扎洪鲁克人衣饰上显现的装饰美,满足了当时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
衣饰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与该地墓葬出土的古尸脸部的“面纹”,与随葬木栏、木叉等木祭器以及原始宗教、大自然崇拜、巫术流行有关。古老遗风的传播是衣饰形式能保持地域性特色的因素。扎洪鲁克人创制的美丽、古朴的毛织衣袍,是古代塔里木南缘衣饰文化的发展与升华,是服饰创造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裤装”也是出土于扎洪鲁克古墓的珍贵衣物,它应是古代早期着裤形式的实物,此裤为自纺毛布染成深绛色的男裤。腰宽近2米,裤腿各1米,长及脚面,腰胫下处缝缀一块菱形的裤裆,致使整个裤装严实合缝,它又外套一双长及膝部的毡袜(古尸出土时的穿着),此裤虽宽腰阔胫却折成两褶而护贴腰部,是足以适应寒冷地理环境而产生的裤装形式,与内地汉墓出土的无裆、开裆裤区别较大。此裤装的发现,证实了西域的裤装形式早于内地的历史,裤装不断发展演变,逐渐成为西域地区的主要服饰,它与上衣相结合,形成整体衣装形式的“裤褶服”。裤装,它展现了地域性衣饰文化的特征与文化观念的一致拓展,呈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智慧。
奇异的帽冠
“冠”是古代人头上装饰的总称。据说,冠的形成与大自然的鸟兽有关。《后汉书·舆服志》曰:“上古衣毛冒皮,后代圣人见鸟兽冠角,乃作冠冕冒。”另有史书记有:“黄帝以前以羽毛皮为冠,黄帝以后则以布帛为之,饰以冠冕缨緌之作,皆有所象也。”现介绍出土的几种毡帽类型为研究帽冠提供了考证的依据。
褐黑色尖顶毡帽 毡帽从帽檐至冠顶高达32.7厘米,缘径28厘米。采用两大片毡块裁成长三角形,用白色毛线缝缀,帽的边缘翻起,也用白色毛线缝边饰,从帽缘到帽冠呈斜坡形,因此,冠顶再高也不易倒塌,帽冠顶部呈圆形似鸟的头部,意趣盎然。
褐黑色尖顶毡帽高大而厚实,尖顶部犹如小小山峦,仿佛凝聚着一股潜力,呈现出大自然原始古拙、质朴无华与豪放不羁。而帽冠的结构、质地与造型,则深蕴着大漠、戈壁、绿洲、草原游牧文化圈粗犷、雄浑的气质。帽冠的实用性与先民朴实的追求、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尖顶式帽冠是游牧人帽冠的象征,流传极广,斯基泰人、塞人及游牧民族都爱戴此帽。过去只能在壁画、石刻画与泥俑形象上见到它,现在出土了实物,实为珍贵。
黑色圆形帽 此帽用黑色细毛线编织,毛线细密,织纹清晰,是用编织好的四个扇形毛坯交错缝缀成圆形,口缘部有伸缩性,帽的形式类似现今的“贝雷帽”。这顶帽子如果置放在今天的帽冠展览会上,人们一定会发现,它的编织技艺与帽冠造型充满了古老文化的诱惑力。
白色羊角形毡帽 这顶毡帽以两个呈半圆形白毡从中心缝合成圆形,突出缝合的部位类似帽饰的流行线。帽的顶部缝缀着用毛毡拧成的棒状羊角饰物,使毡帽主体呈现以羊角为饰物的冠帽,它不仅具有御寒的实用性,还含有以动物为装饰的神秘意蕴。格罗塞在《艺术起源》一书中曾说:“我们研究用具的装潢,尤其可以发现澳洲人的衣着、盾牌、棍棒上的装饰和他们画身的图样相仿,完全是模拟兽类的。想用同样的绘画把他们自己扮成兽的模样,是和原始人认定某一种兽类是他们同族的保护神,而喜欢模仿兽类形象的心理相去不远的。”以羊角形为饰物是游牧人对以畜类为经济来源的特殊情感,既崇拜为“保护神”,又盼望兴旺发达、保畜消灾,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朴实情感。
第九节 毛织衣袍的新奇款式——苏贝希古墓出土衣冠服饰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吐鲁番火焰山腹地发现一批珍贵文物,据判定为两千三四百年前,相当于内地的战国时期。
主持古墓发掘的吕恩国披露:“一批身着新颖奇特服饰的两千三四百年前的古尸,最近在火焰山腹地苏贝希村附近的古墓群中被发掘出来,同时还出土了300余件陶器、木器以及铁、银、石器等……一次发掘这么多保存如此完整的古尸和大批未朽的文物,这在新疆多年的考古工作中是少见的。发现的墓室、房屋、服饰、用具、食品、药物等具有明显特色,堪称稀世珍品,为丰富、补充、完善过去的考古成果,解决某些考古学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吕恩国详细地介绍了随葬衣物:“几乎全都是毛纺织品,犹如进入一个崭新的、奇异的服饰世界。那新奇的款式、那熟练的纺织技艺,堪称新疆游牧民族衣饰文化的一绝。”
战国时期前后,吐鲁番盆地曾经是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地方,水草丰沛、牛羊遍地,以畜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农业和手工业。王炳华著《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书中写道:“从2000年前保留至今的汉文史籍中,人们早就了解到,距今2200年前,雄踞吐鲁番大地的主人,自称为‘姑师’,后来又改称‘车师’。当时他们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有自己的都城。王国人口不算多,以吐鲁番盆地为舞台的车师前国,人口不过6050人。如果包括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人口也不过1.2万多人,但是它地跨天山南北,影响远及西域内外,不容轻视。”《史记·大宛列传》也曾记载过在楼兰、姑师这两个小国中,建有城郭,已经步入文明。它记载着吐鲁番盆地在两汉以前,当地族民是车师人。现介绍苏贝希颇具特色的出土衣冠。
尖顶高帽冠
此帽以突出尖顶部位为特征。帽冠中心竖起以牛皮为质地的尖顶,它的高度竟有近0.8米,突兀于顶端;帽缘呈大圆盘式,与帽冠相连,又以毡质为内心,外罩毛织网状护套,通体浑厚、深沉,泛着青色的光泽。帽冠造型富有游牧民族特点,呈现厚实的毛质感,显得庄重与挺拔。奇特新颖的款式,告诉世人,似乎在求得和大千世界的动态保持平衡。
裘皮大氅
一件形式清晰的裘皮大氅,凝聚着游牧民族的伟大创造与心血。大氅显示出宽大厚重的皮毛感,光板皮朝外,卷毛在里,交领开襟,袍长及足,袖长过手指。
交领衣是我国古代上衣的主要款式,它的裁剪与制作都比“贯头衫”更为复杂,是服饰制作的一大进步。
裘皮大氅是西域早期完整皮衣样式的袍服,它结实、凝重、宽大。白天,游牧人穿着它骑马放牧、狩猎、挡风御寒;夜间,则用它做睡被。裘皮大氅显示出强烈的地域性特色。
毛织裤装、连腿皮靴
此裤装为纺毛质地,柔软、轻薄,腰阔胫长,裤长多于覆足。在其膝部套上圆筒形狼皮毛在外的“膝裤”套缚双腿,再用毛绳束系并与裤腰带相连。古时的“膝裤”也称“胫衣”,有以革制,也有以厚棉。此狼皮“膝裤”实为草原文化圈游牧民族穿着的特征。
连腿皮靴则紧紧套住毛织布裤,与膝裤、裤装、靴履连成一体的形式。皮靴套上裤装,便于骑马驰骋,游猎四方。从独特的衣装可以联想到穿着的人,他曾是威武健壮的骑士形象。服饰的风格和气派是民族精神的反映,是一种赋予了顽强服饰文化生命力的表现,更是一种摆脱了简单粗陋的原始衣装,进入文明历史进程的着装模式。
毛织内上衣
毛织内上衣为男性内衣,衣饰形式是小圆领、开襟、窄袖的纺织纯白色上衣。毛纺精细,质地纯厚、柔软、轻棉,显示出毛纺织品自身的特质,且具有保暖性、遮蔽性,显示了当地的毛纺手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彩色毛纺筒裙
彩色毛纺筒裙系采用土黄、红、蓝、褐等色染织的毛纺筒状形裙装。以宽窄不等的横道纹,间以多色染织的裙装,构成一个由毛纺质地、线条组成的五彩绚丽的纹饰,其色泽经2400年仍鲜艳如昔。筒裙的腰部配以红、白两色的编织带,组成美丽的带饰,衬托出裙装无穷的魅力。这一事实又告示着人们:当地族民具有特殊的毛纺、染织技艺。
皮质面衣
“面衣”亦称“覆面”,是一种葬俗用品。皮质面衣较为罕见,它是一种经过鞣革的羊皮,又以白色矿石在面衣上画出浅浅的线纹,使轻薄的皮面衣产生一种纹饰感,它覆盖于女尸面部,给人一种安详、静穆的感觉。皮质面衣的发现,证实了新疆早在战国前后即有此葬俗。
毛织网罩与化妆袋
发式是妇女头部的重要装饰,它不仅增添其仪容的俊美,也是人体修饰的关键部位。笔者曾目睹苏贝希古墓女尸的头饰,其造型新颖别致,有异于其他头饰装扮。她们多梳长辫,或将黑色辫发盘挽于头部,在那弯曲的辫髻上,罩上自织的黑色毛纺织物,一种呈网状似的发套,既固定了发型,又是当地妇女重视发式修饰的一种表现。
化妆袋是妇女化妆的组成部分。此化妆袋系从女尸腋下发现的一个皮质的小袋,袋中装有磨制光滑尖细、适宜描眉的黑色“画眉石”,白色的小石块似涂抹面部的粉妆,红色的石块犹如胭脂般红艳。这些经过选择的矿石为苏贝希妇女修饰、装扮仪容增添了光泽。化妆蕴含着审美情趣,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精神风貌的重要表征,也充满了时代特色与地域性特色。
毛织内衣与皮手套
毛织内衣系女式内衣。用羊毛纺成,它是一种纯黑色轻薄的毛纱。内衣样式为小方领、长袖,领口用红色毛线镶边,略显一种简朴的装饰风采。皮手套是御寒佳品,它的形式是四指并连,大拇指分开的连指式,是光面朝外毛在内,保暖性强的皮质手套。
毡靴与毡帽
毡靴呈高筒形,靴底为皮质,结实耐用且可涉水草。其连接的上部为深褐色毡制成的圆形筒身,组合成一种皮、毡复合式的靴,轻便保暖,是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足履的佳品。
盔式毡帽连耳护颈,呈盔甲式武士帽冠,戴上此帽,呈现出游牧民族的骑士风范。出土时尚有皮质箭箙以及那待发的一支支利箭,可以由此联想当时体魄健壮、能骑善猎的苏贝希男性族民威武的身影。这是封闭的地理环境给予衣冠服饰浓重的地域性色彩。
苏贝希古墓出土的以毛纺织、皮革为主要质地的衣冠服饰,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纯白、多彩的羊毛织物,而且从织造均匀、细腻、轻柔、绵软的程度上,使我们看到当时毛纺技术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兽皮加工、鞣制技艺也相当出色,是苏贝希人为适应穿衣着靴的生活需求,在毛纺织业、皮革加工业方面促成的一次飞跃,伟大的奉献内含着一种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发展形态。
诚然,古老先民以其实用为目的的服饰文化,无论是取材于动物界、还是植物界;无论是自然形态的、抑或是加工创造的,这其中都孕育了人类对服饰审美的萌芽。因为衣冠服饰的缝制,包括衣饰款式、质地选择与色彩的偏爱,不仅与特定的地域环境、经济生产相关联,而且包括服饰结构的变更以及与人类个体生命密切相联,都获得了充分的表现。它是一种来自远古时代的历史回音,是人类在一定时期涉足历史舞台的印记。
第十节 青铜武士俑——巩乃斯出土塞人铜像造型
“青铜武士俑”出土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这个时代的社会是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这种巨变无不反映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西域的黄金时代。考古人员发现的这一时期罕见的具有青铜器文化特征的遗物,是弥足珍贵的。
“战国(或比战国稍早)到西汉时期,在西域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发生了某些古代民族(如塞人、月氏、乌孙等)的迁徙活动,西汉王朝统一新疆,以及丝绸之路的兴盛等,都为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十分重大的影响。”①
考古的重要发现,使古代西域的青铜器文化重放异彩。在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尼勒克县奴拉赛山谷中发现了两处古铜矿,在特克斯县发现了古代铜器。出土的铜器都具有民族特色,无论在质地、造型与纹饰的变化上,都比原始社会彩陶的表现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伊犁新源县发现的一尊铜武士俑,造型逼真、生动,向人们展示了当时人文性的特征。铜武士俑高约40厘米,重约3公斤,空心。武士面部深目高鼻,留有大鬓角,面部表情庄重肃穆,神态严峻,头戴尖顶大檐帽,帽后顶部呈尖刺弯钩状,双手作空握状,双腿一蹲一跪,上身裸露,腰系战裙,赤足,目光凝视前方,据考古专家鉴别为古代塞人形象。
塞人主要活动在中亚、西亚和西域。塞人常戴尖顶帽冠,故又有“尖顶塞人”之称。
塞人所戴尖顶帽也不尽相同,此铜武士俑的尖顶帽附有一尖刺弯钩,很可能是不同塞人部落所属。伊犁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是塞人游牧、活动的地区。《汉书·西域传》曰:“乌孙国..本塞地也。”在古代塞人的文化遗存中,还不断发现铜马衔、铜耳环、铜发钗、金耳环等用具与装饰品,各具特色的青铜器出土文物,代表着青铜文化的特异风采,不但赋予本地域的民族特征,而且表现出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原铸铜技艺输入的痕迹,因此,青铜文化在西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西域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一带不同的显著区别是,出土的文物中有铜器、石器、陶器,因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考古界为此定名为铜石并用时代。
第十一节 发型帽冠鞋履腰带
发型是人体的重要外观,古代初民是很注重的,特征多为蓄发而不剪。新疆考古队曾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的古楼兰遗址,发掘出距今约4000年前的古代罗布泊人古尸,这具女性古尸的头发为褐黄色,披散至双肩。哈密五堡乡古墓发现的女尸,约有3000年的历史,留有长到腰际的发辫。昭苏小洪那海古代石人像高1.91厘米,戴冠辫发,发辫多到9根,长垂于腰下。
古代匈奴、羌、乌孙、塞人等曾在西域辽阔的大地上游牧、生活,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将会不断被发现。《后汉书·西羌传》曰:“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由此看来,最早的原始初民不论男女都披发,辫发是披发的一种演变,束辫既好看又方便。
辫发习俗一直延续至今,闻名遐迩的新疆歌舞中,舞蹈者及演唱者几乎都是辫发。那又黑又亮又长的发辫,甩动旋转,优美飘逸,令人神往。
帽冠 帽冠是首服,也是实用性很强的头饰物,几乎与人类同有。古代原始初民常在头部裹上一块兽皮,用来抵御严寒风霜。原始人类既能顺应自然,也敢于同大自然搏斗。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古尸头戴尖顶毡帽,给予现代人深刻的启示:毡帽的出现,反映古代游牧人在封闭、严酷的大自然里与暴风雪、冰雹、野兽的一种斗争方式。毡帽的形状很多,有尖顶、圆形、簸箕形等,色泽有纯白、浅驼、褐黑等色,体现出游牧人在宇宙空间的生存、创造价值。制毡需要一定的技能,从选毛、擀毡到制成一顶毡帽,要经过好几道程序。毡不仅能隔潮、保暖,还具有轻软、厚实的特点,足以抵御大自然的种种侵袭。是边塞大地原始初民适应大自然生态环境的伟大创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帽冠除具有实用性,还兼有装饰性。以羽毛作头饰的习俗,是西域原始初民的帽冠特征。它反映在一幅举世罕见的,体现原始社会晚期生殖崇拜的巨型岩画上,即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该画在长约十多米的岩面上,凿刻了300多个人体图形,其中有些形象的头部即刻有明显的“羽毛饰”。
无独有偶,在罗布泊铁板河古墓出土的女尸头上也戴着毡帽,毡帽顶端插着两根雁翎。羽毛饰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美的内涵,极富装饰性。从头顶兽牺皮到戴上毡帽,进而发展到用羽毛做装饰,是帽冠发展中的一种进化。好像用羽毛装扮成动物的模样,却又有别于动物。“羽毛冠”最初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也是一种获得劳动成果的炫耀。羽毛亮丽耀眼,富有轻微张力,形态变化多端,是原始人对自然界的体验。羽毛是游牧人喜爱的头饰,它和非洲人以戴羽毛冠为英雄的标志同出一种心态,为当时人类的生活焕发出多彩的光辉。
羽毛束冠遗风延续到现在。现今的哈萨克族少女喜欢佩戴自己手工绣饰的圆顶帽冠,镶上串珠,绣上花卉图案,帽顶部插羽毛作为吉祥物,将其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审美情趣集于一身。
鞋履 鞋是现今的称谓,《释名》载:“着时缩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则舒解。”是指一种鞋面开缝、系带的、多用生皮制成的鞋。实际上,穿在脚上的、与地面接触的“足衣”都统称“鞋”。“履”即现今称谓的鞋,汉代以后称“鞋”为“履”,而“鞋”则是自唐代延续至今的称谓。《释名·释衣服》曰:“履,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
靴是古履的一种样式。史书记载:“鞮,履也,胡人速胫,谓之络鞳。”《中华古今注》曰:“靴者,盖古西胡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靴”为高靿皮鞋,是北方少数民族主要穿着。它便于跋山涉水,翻越雪岭,适合游牧人乘骑和抵御寒冷之用。
新疆的古代墓葬中,曾发现短靿的与高靿的皮靴,与古籍记载基本相符。出土的还有高靿毡靴,显出其地域性特征。反映了当时的鞣革、脱脂工艺和制毡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腰带 腰带是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饰物,因其所穿着的衣饰多长及过膝的衣袍且多无纽扣,因此腰带起着保暖与紧身的作用。腰带不仅方便于游牧民族骑马、放牧、狩猎,且可在腰带上附系若干小环扣,挂上必需的小物件。腰带的款式有宽有窄,宽的用皮革制成,窄的用毛织物缠成双股或多股状,中间系纽成结。腰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鞢。古籍记载:〓鞢七事,即火石、鼻烟壶、小刀、砺石、针筒、解结锥和荷包等七件。它是古代草原文化圈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必不可少的饰物。
大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地。“人猿揖别”之始,大自然就显示了对于人类无限的威慑力量。当人类在各种物质创造性活动中显出本质力量之时,它只能说明是人类征服了自然,其中蕴藏着人类衣饰穿着意识的萌芽。
宇宙万物千变万化、神奇莫测。据考古、历史、地质学家考证与研究,约在距今5万万年以前,现今新疆的这块宝地,原先是烟波浩渺的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几经地震与火山爆发,海底隆起无数山脉,盆地又渐渐升高,使新疆呈现一片波状大草原、参天大树、绿野丛林..巨大的爬行动物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随着造山运动的更迭,沧海桑田,水去陆现,生态环境的天翻地覆,造成生活在海洋中的“主人”终于葬身海底岩石下。
几经动荡,造山运动促使大自然发生巨变,人类成了大地的主人。“阿图什人头骨”①化石的发现,是新疆考古界发现的第一例古人类化石,填补了古人类化石的空白。据古人类学家鉴定,“阿图什人头骨”是属新石器早期人骨,似为18岁左右男性,距今约1万年。考古的发掘足以说明新疆在1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原始初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十分低劣,在漫长的蒙昧时期不断地劳作和积累原始文化。到了中石器时代,诸多原始石器造型不断出现,并渐渐趋于成熟。从新疆出土的石镞、石叶片等工具,即发现它们可嵌入木质或骨质的刻槽中,制成一把锋利的刮刀、切割器或投掷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工具。将石器再装上骨质、木质的长柄,它们就成为投掷武器,使用于狩猎飞禽或捕捉水中的游鱼,亦可作为原始初民处理各种兽类毛皮和食肉的必需用具。将其获得的兽皮用石器切割刮净,披挂于身上可御寒护体,较之赤身裸体又进了一步。与传说中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即有了文身等肤体装饰行为相比较,披盖原生皮毛,标志着人类衣着的萌芽与缘起。以实用功能为目的,是人类以护体穿着为模式走向文明之滥觞。《说文解字》曰:“衣,依也。”即人类依赖的穿衣护体也。
以生活需求为实用穿着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与动物的分离,而“骨针”的发明,则促成原始初民在穿着上的根本变化。考古工作者在天山北麓木垒县四道沟铜石并用时期遗址,发现与缝制衣服相关的“骨针”其类型有粗长、细短两种。细短的,一枚长5.4厘米,直径0.18厘米,呈肉皮色,带有骨质外露的浅驼色斑纹。粗长的一枚长8.8厘米,直径0.23厘米,通体布满深驼色斑纹。两枚“骨针”磨制精细,表面光滑、细腻。“骨针”的出土,证实了原始初民已经运用它缝缀衣服。这时,衣服才逐渐形成,改变了原始的赤身裸体或披兽皮、树叶的状况。有了骨针,能将兽皮大致缝合起来,肉体被遮盖,蔽体保暖,衣服成了文明的特征。“骨针”是体现人类智慧的“活化石”,是催化衣服雏形走向完善形制的原始珍品。
纺织是人类继穿兽皮之后的重要发明。西域的游牧民族以经营畜牧业为主体,最初的纺织原料是羊、驼等畜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提高了改进生产工具的意识,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原始狩猎人通过这种改变之力逐渐转变为游牧人。由于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提高,在一些绿洲开始有了原始农业,出现了通体凿成鱼鳞状的桂叶形石镞、石磨与石纺轮。
石纺轮不仅磨制平滑,造型别致,呈圆形,且凿有孔眼。孔眼作用很大,可以用骨棱或骨梳穿上手捻的毛纱(纬线)在经线上(纺轮)来回穿梭,纺织成粗质毛布。石纺轮的打磨、钻孔技艺高超,显示了新石器时期人类的伟大创造力,表现了人的生命时空及其制造工具实践活动的时空,就这样交替地被拓展。纺轮的出现,比骨针缝缀兽皮又前进了一步。纺织的毛布是衣服面料的新创造。它可根据人体部位量体裁衣,初具“领、襟、袖”等上衣形制和下身着“褶”,即前后开胯的“裤”装形制,衣服模型逐渐形成,形制也灵活多变,体现着人类衣冠创造活动的生生不息和变换常新。
帽冠的发明是伴随衣服的发展而产生,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原始初民、狩猎人为了捕获猎物,往往把自己扮成野兽模样,他们常戴兽头帽、兽角或系尾,以便靠近狩猎目标,提高狩猎效果,这与帽冠发明有着密切联系。为了防暑、御寒,或戴树叶蔽日,或戴兽皮护卫头顶,这是最原始的帽子。
人类在经过漫长的赤足时期之后才发明了鞋。新疆北部山区严寒地带,鞋的类型较多,起源较早,目的是保护双脚不被冻伤。最原始的是在脚面上覆一块兽皮再用皮绳系住,或穿毛皮窝子。狩猎人为抵御风雪侵袭,又在原有鞋的式样上改进、变化,将兽皮覆盖面加大,做成长筒形,这便是最早期的“靴”。
第二节 岩画中的原始衣冠
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比较,史前史研究最大特点在于其时代久远,缥缈洪荒,既缺实物,更无文字,仅仅靠推理,实难令人信服,而岩画的发现,填补了史前研究的某些空白。岩画是原始人类自我表达的一种形式,以其粗犷的原始意蕴,渗透出强烈的诱人魅力,包含着原始人类生命内在的律动感。在岩画的层面上,那匀称、粗野的凿点,刻画出一幅幅姿态生动、形体逼真的原始生活图录,记载着人类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以及文化积淀的内涵,也是原始先民萌发的原始思维与审美观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生活面貌。
在浩瀚、广袤的新疆大地,天山南北曾出现面积不等、时代不同、内容各异的岩画,是猎牧民的杰作。它作为原始人类在岩壁上的“投影”,记录了从石器时代延续至近代的人类生存活动的历史篇章,向人们展示了人类在宇宙洪荒年代野蛮而壮烈的历史画卷。
岩画形成的因素很多,是与地壳变化更迭有关,致使原先一片汪洋大海、湖泊、沼泽发生巨大变化。于是,昆仑山、阿尔泰山、天山更加雄奇壮观,重峦叠嶂。山崖的增多,为岩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岩画多刻在僻静的岩壁上,四周高山、森林,淙淙泉水流淌,绿色山野幽静,给予原始岩画一个特殊的层面。天山南北发现岩画,它又说明这些地方在远古时期是原始人类繁衍生息的活动场地。从已发现的岩画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原始人类生活与狩猎图像两大类,动物形象占据相当大的数量,展示了由野羊、山鹿、虎、牛、骆驼等组成的动物世界,揭示了新疆古代初民最早的生活方式是狩猎、游牧。岩画中有不少刻画了狩猎游牧民族的形象,以及他们穿着的衣冠,这对于研究游牧人最初的服饰文化是极为重要的依据与参考资料。
新疆岩画多刻在朝东向阳的黑砂岩、花岗岩、板岩、条状岩等岩面上,多采用粗线条的阴刻或浅浮雕的手法,也出现少量的彩色岩画,是以赭红色的砂物质做颜料,涂染显现朱红色,它是游牧人心目中象征生命永恒的色彩。
昆仑山岩画 不仅幅面规模宏伟,且表现人类在蒙昧、荒蛮时代同大自然搏斗的艰苦历程。凿刻朴拙、纯真,是原始初民童稚时代的一面镜子。胡邦铸等曾对新疆岩画做了论述,笔者结合实地考察,摘其要点,作衣冠穿着的赏析。
莫勒恰河谷口岩画 位于昆仑山脚下且末县莫勒恰河出口以南的山腰处,山形蜿蜒曲折,几千幅岩画凿刻在石壁上。据地质工作者考证,山崖的位置处在第四阶地的原始河床上。岩画层面宽阔,以动物图像占多数,羊的形象几乎占一半。它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原始初民居住的生态环境,它是古代羌族人的游牧生活区域。且末、若羌一带是古代羌族人的游牧之地。《汉书·西域传》云:“若羌,‘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这段记述与岩画内容基本相符,也是当时且末羌族人生活的写照。众多的岩画其突出的画面以“征战图”最为气魄宏伟,人物形象逼真,线刻准确,展示了当时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战斗的图像。它负载着一个沉重的、鲜为人知的丰厚文化,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珍贵历史图录。正如《后汉书·西羌传》云:“羌人,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这是它的内蕴含义,是“征战图”岩画刻凿人物形象的内在精神力量。
征战图 刻画写实动人,勾画一幅争战双方骑马互相进击的场面。追击者拉开弓箭,被追击者回首弯弓,神情紧张,预示一场战斗即将开始。画面中一骑士头戴一顶类似塞人的尖顶帽,帽耳至肩,还有一武士戴有“〓”形饰物,覆盖头顶,似其他民族或羌族人特征。双方手持长矛面向立在牛背上的武士猛刺,后者持盾阻挡长矛,盾为心形,上面刻有“升”形纹样。流畅的线条勾画出人物交战时的神态与作战双方的位置,产生了争战双方激战的情景。从一幅写实的、动人心魄的征战图不仅可以窥见羌族人、塞人在昆仑山中的战斗纪实,而且从中还能看出游牧民族帽冠的穿戴方式,那是当时生活衣着的真实写照。《说文解字·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羊的形象在岩画中占据面积很大,岩画中羊的形态、造型各异,想必与当时现实生活相符。羊是游牧人的主要衣食来源。
至于昆仑山岩画断代问题,翦伯赞先生的一段话是中肯的,他引用《秦汉史》中的有关羌族人记载:“以后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西羌之族,又循着天山北麓的天然走廊,徙人这个盆地西南。”
“也就是说,羌人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时间应当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这个时间也就是昆仑山岩画产生的年代,其下限可能延续至隋唐,文献记载着7世纪末武则天时西域的天山南麓还生活着‘群羌’。隋唐以后西域的羌族逐渐融合于吐蕃、回纥、汉族、吐谷浑诸民族之中,不再以独立的民族形象存在了①。”
狩猎人 昆仑山岩画表现狩猎人的形象,刻凿线条明朗,体型强健且富于变化。狩猎者那双有力的手,持弓搭箭瞄准着正在奔跑的野鹿、山羊。狩猎人与鹿和羊的头角、颈部、躯体及腿部之间构成与原型相近的力度感。骑马放牧人的雄伟英姿出现在岩画凿刻的层面上。马的使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岩画中狩猎人骑马放牧,是表现古代游牧骑士放牧、狩猎的情景。
狩猎图 位于温宿县天山林场的小库孜巴依岩画中有一幅颇有生气的狩猎图,狩猎者个个持弓拉箭做射猎状。猎人穿着的衣装非常引人注目:明显地刻出他们穿着宽大的衣袍,下摆大,给人以穿了厚重的毛质衣物的感觉,是岩画中少见的服饰。“袍”为长外衣,《诗经·秦风·无衣》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袍”始创于周,《后汉书·舆服志》云:“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形制多为身宽袖长,覆足及地。古时,西北游牧民族多穿袍,类似现在新疆少数民族穿的“袷袢”,是一种交领式长大衣。岩画刻凿狩猎者穿宽身袍装,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着装创制,袍服是抵御严寒的最好衣饰。
放牧图 此图是北疆富蕴县唐巴塔斯岩画,其中以“放牧图”展现草原生活风貌,具有浓郁北国风貌的情趣。此图的右上方是戴尖顶帽的牧人,他纵马扬鞭,飞奔驰骋,表现出急促的动感,似放牧归来;左下方是位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脚蹬长筒靴的牧人,似他家中的成员,好像在盼望骑马归来的亲人。简洁的刻凿勾勒出人物形象与家人等待、企盼的神态,传递、交流人物之间内在的真挚情感。四周空间浸润了大自然的灵性与活力,草原上奔跑着欢跳的牧羊狗,与天空上飞翔的小鸟,似乎都有“欢迎”主人归来的意思。充满浓厚生活情趣的“放牧图”给辽阔、静寂的大千世界增添了人间的温馨。牧人的穿戴,如长袍、尖顶帽冠、高筒长靴则与记载中的古代塞人穿着颇为相似,它又为塞人曾在此地区游牧、活动提供了证明。
狩猎图 位于温宿北境博孜敦乡,有一幅颇具特征的猎人狩猎的岩画。岩画以阴刻法凸显猎人张弓搭箭,瞄准前方奔跑的猎物。那牛、鹿、大角羊急驰于旷野,那蓄势待发的紧张神态,使观者获得了特定环境中的某种信息。岩画四周的环境赋予了一定的情境氛围,天山群峰、辽阔草原、莽莽林海,大自然赐予岩画创造者以鲜活的生命力。其中,有两位高约40厘米的猎人,他们身上披着似厚实的毡褐,这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披着的衣饰。《大唐西域记》一书中记载着龟兹人的服饰:“服饰锦褐,断发巾帽。”《文献通考》载:“衣毡褐皮氍,以缯缭。”毡褐是由细毡缝制而成,与史书记载龟兹细毡相符。博孜敦古时为姑墨地,与龟兹山水相依,地理位置相近,衣饰习俗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牧归图 则以简明的线条刻画,衬托散落四处的羊群,显出空间大面积的层面,在线与面的交融中,突出牧人一家在主妇的带领下,她双手拦着羊,流出欢庆丰收的喜悦之情。主妇穿着的衣裙呈现一种厚度感,衣服的质地似用细毡制成,那身宽厚的连衣裙装,明显地表示它是当时妇女的家常服。
上述库鲁克山古代岩画是古代游牧民族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人类早期的狩猎、祭祀或巫术礼仪,以及舞蹈、征战等图形,到长房建筑、栏杆式窝棚等刻凿图和意念性的各种图式符号,是记载古代游牧人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历史画廊。
这里岩画的产生年代:“……可以确定库鲁克山区岩画的上限时间应在纪元前5世纪以前。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居民大多系塞族人部落,是与斯基泰人同属的一大游牧文化群体,可认为其主人即创作者是塞族人。”①
争战图 位于哈密沁城岩画的“争战图”,人物刻凿写实逼真,争战双方交锋场面激烈,动人心魄。哈密是古代乌孙、匈奴、车师等民族活动过的地方。沁城距离哈密约7公里,在折腰沟处,横亘着一条流动的季节河,四周山麓崖畔上散堆着形态各异的黑色花岗质的巨石,岩画就刻在巨大的岩石上。“争战图”突出刻画九位骑马武士,轮廓清晰,武士们身着盔甲铁衣,面部刻凿线条明显,能粗略地窥见武士须眉与面部神色的疏密、细微差异。画面宽阔,长约16厘米,刻绘出九位武士鏖战双方精彩的一页。两阵对垒,战斗激烈,交战双方形态各异,特征独具。有的武士持枪跃马威风凛凛,与身边握枪的武士拼杀,刹那间,战马四蹄腾空,鬃尾飘动,虽舍去细部,却准确、清晰。武士穿戴的甲胄体现了盔甲的特征,是记载武士形象、穿着的原始记录。征战的气氛浓郁,与刻画的高度概括、取舍得当、抓取的特征相关,厮杀声犹如回荡在天宇之间。
猎人图 位于裕民县巴尔鲁克山简巴尔达湖的山坡岩壁上。猎人拿着盾牌,准备击中右上方的岩羊,一条狗也跟在羊的身后。猎人赤身裸体,头戴一顶四角状的帽冠,四角的距离相等,形同放射状,好像太阳的光芒普照大地。帽冠形状尚属首例,它象征原始狩猎人心中崇拜的太阳神,给人类带来温暖与光明,是原始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寄托。原始人类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大自然崇拜表现了虔诚的敬仰,在岩画中以头饰表现,阐释了头饰即首服的意义。对于大自然的崇拜,直接影响了新疆的后世子民。正如杨金祥在《宗教与维吾尔古代美术》一文中所说:“远在8世纪前,当东回鹘人还生活在漠北时期,在蒙古高原上建立回鹘汗国的可汗,要在自己名字前面加个‘捆’(Kil,湖泊的意思)字,以示自己是水神之裔。”《乌古斯汗》中的乌古斯可汗,分别取名“日、月、星、天、山、海”。这是先民对于大自然崇拜的延续,表明了他们的心迹。
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大型岩画 地处天山深处的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大型岩画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震惊。它是一幅反映原始人类文化的生动图像,同时也留下了原始人类服饰模式的印记。
岩画特定环境的选择会形成岩画独特的气氛与意境。康家石门子所在地山体色泽赭红,气势雄伟,水草丰盛,环境幽静,生态植被保持良好,是理想的高山牧场。岩画面积很大,它东西长14米,上下高约9米多,属地质史上新第三纪粉沙岩层面,刻画着约300人的男女人像,热烈地表达了各自的狂放、粗野的情感。凿刻技艺简洁、造型浪漫,使原始文化的虚幻性康家石门子岩刻人物特写与写实性融为一体,使神态各异的舞蹈者以及生殖崇拜的图像释放出独特的异彩,观赏者能从中领悟到生命微妙的奥秘。宏伟巨大的人像场面令人惊叹,动人魂魄。那一幅幅占有重要位置的原始生殖崇拜的岩刻,不仅使观者获得一种超越现实的神秘感,而且隐含着人类生存期望的内涵。
康家石门子岩画画风古拙、朴实。以浅浮雕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面部与形体,戴在头上的尖顶高帽或簸箕形帽冠(有的帽顶插有羽毛),显得神气非凡。大部分男女是裸体的,只有画面中心直立着穿着裙装,身高1.05米的女舞人。那简洁而抽象的裙衣,衬着左肩飘动的衣带,使她那宽胸细腰,优美的身姿在空间翩翩起舞,创造出一种空灵的情调与韵律。戴尖顶高帽是古代塞人的帽冠特征,表明古代塞人曾游牧天山一带。头饰羽毛是狩猎英雄的标记,代表光荣、美好。岩画中头饰羽毛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当代,现今的哈萨克族少女爱在帽饰插上羽毛,把它视为吉祥物,寓意“驱邪、消灾”。帽冠同时具有一种礼仪的形式,其历史性与价值取向是鲜明的。裙装则是当今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常服,妇女们在冬季也喜爱穿着裙装,下穿毛裤与长筒皮靴。岩画人物形象的着装与现代的民族装相似,表明它们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贯穿着历史的承袭性与传统习俗。
对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断代,我同意这种观点:“岩刻画,也直接显示出早晚相互叠压的痕迹,晚期的刻画,覆盖了早期的图像,应该是完成最早,也属于画面最上部的一列巨型女像,并显露出不同的思想信仰。因此,康家石门子岩刻的始创时代远比原始社会晚期的战国阶段要早,应是没有疑问的。”①
天山深处周围的岩画与原苏联、中亚一带、内蒙古岩画,从内容到形式表现上都有相似之处,都反映出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特征和相互融合,形成特殊形态的岩画艺术体系。至于断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一部分可能早到铜石并用时期,一部分则可能在公元前后,而也有可能在公元12或13世纪的蒙古时期,甚至更晚,如与元朝喇嘛传布有关的古藏文岩刻也有发现。”①
第三节 西王母的传说
《穆天子传》中记述周穆王巡游天下曾到新疆,会见居住在高原上的一位原始部落首领西王母,互赠礼品,传为千古佳话。神话般的动人传说,显示了秦汉以前我国古代中原和西域各国友好往来的景况。
西王母并非实有其人,迄今为止,尚找不到确凿的依据来说明或引证。周穆王却实有其人,是西周王朝第五代国君,姓姬名满。据《穆天子传》中记载的“昆仑”、“春山”,其地理位置与新疆的昆仑山和葱岭基本相符。著名的敦煌莫高窟第249窟、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以及内地画像石刻中都留有西王母的形象,有关西王母的传说深入而又广泛。
有关书中所指“西王母之邦”和“天子宾于西王母”等传说,在《山海经》中亦有记述。书中云:“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戴胜即指妇女首服,豹尾虎齿即指以虎头图腾为标记的某部落。
西王母的形象与衣冠服饰穿戴多流传各地。在西人著戴岳译的《中国美术史》书中插图即有武梁祠石刻画像,曰:“西王母戴五梁冠,端坐楼上。”梁冠为在朝文官所戴,三品五梁。在汉画石刻中也为贵妇戴冠。武梁祠石刻画像中又刻出五梁冠为西王母所戴,它仅为一种传说。
东汉嘉祥蔡氏园出土的“西王母像”,与山东嘉祥宋山汉画像石颇为相似。原题为西王母戴胜,此“胜”指妇女首饰,与《诗·齐风》中所说:“总角兮”;《礼记·内则》中“男角女羁”及《丧大记》中疏云:“髦者,幼时剪发为之,至年长则垂著两边”大体相近①。
山东两城汉像石,刻画技艺精巧,画像中表现了神话般的浪漫色彩。画像中刻画西王母的衣冠服饰与其造型反映一种神秘的意蕴,呈现了人们的希望与欲求,包含着宇宙万物。
汉代画像风尚流行一时,不仅有画像石,还有画像砖和帛画。题材多取自神话传说,奇禽异兽,也有少数描绘社会现实的。画像构图饱满、匀称,刻画风格为文与野、雅与俗的交汇融合,形成一种富有民俗性文化内涵的独特风韵,受到人们的喜爱。
《西王母》画像石刻怪诞奇特,是一幅装饰性浓郁的肖像画。西王母端坐正中,身着宽袖襦袍,双手拢袖,神态安详。头戴冠,冠顶站立青鸟,表现了《山海经》中的一个情节,即“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与图中下端两鸟对称呼应。
西王母全身披着帛巾,飘拂浮动,形成匀称的云纹,使主体人物似在云彩缭绕之中升腾。异样怪诞的两侧人物造型,是一男一女人首蛇躯,蛇身盘结缠绕,构建成绳纹图案的蛇尾座,勾画出一个总体形象,使神态威严的西王母稳坐蛇尾座上。蛇尾的末端幻化成两只生机盎然、勃勃灵动的青鸟,它似回首顾盼,挺立在神话般的天宇间。奇特的构成方式浸染着西王母的造型更具浓厚的神秘色彩,这是神话传说的魅力,是民间艺术丰富的想象力和工匠的独特手法。
由于历史的变迁,其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差异,西王母的形象由“豹尾虎齿”的凶神变成容貌端庄,戴冠着宽袖襦袍,或帔帛绕身的吉神、女神,揭示了民间对神的不同祈求与愿望,是神画像内涵在外形造像上的巨大变化。
总之,西王母的形象显然脱离了原发性的主体生命律动形式,反映民众主体的心理、情感与不同的文化层面。
第四节 胡服
据史籍记载,我国古代对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区各民族一般都泛称“胡”。《汉书·匈奴传》载:“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辞海》载:匈奴称为胡或北胡。乌桓、鲜卑等在匈奴东,故称东胡..西域各族在匈奴之西,故泛称西胡……
所谓“胡服”,即短衣齐膝、窄袖、左衽(即左边开襟)和紧身窄袖,下着裤装的衣装特征。此服饰轻便灵活,适宜骑马作战、放牧游猎,与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宽衣系带式汉装有较大差异。胡服不仅为作战时武士装束所需要,而且广为流传于民间,影响极大。
“胡服”形式实则是以“上衣下裳”制改下裳为裤装。“裳”即“裙”,呈筒式,上古时期男女都着“裙”,称“上衣下裳”。皆为遮护下身之服。所谓“胡人”,其多数为游牧人与马背民族,习于骑马,善涉水草,驰骋群山峻岭。他们的服饰以衣和裤为主要服装,称曰:“裤褶服。”《急就篇》云:“褶为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衣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左衽多是胡服衣饰的特点,广袖则为适应汉装,胡服则是窄袖。
“裤褶服”名称始见于汉末,但仅从新疆各古墓葬出土的衣冠服饰即可窥见,裤装为主要服饰形式,如且末扎洪鲁克古墓、哈密五堡古墓、墓葬古尸均为3000年前的当地民族。他们都着毛皮大衣,下穿裤装,还有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吐鲁番地区苏贝希古墓,古尸穿着皮衣、皮裤。自纺毛布衣裤、连靴套裤等。笔者从考古实物证实,“裤褶服”始于西域古代,可追溯到距今3000年前新疆哈密五堡古墓、扎洪鲁克古墓,其出土裤制就有合裆与〓裆裤。
以裤装为外服,自裤褶服始。春秋战国之际,奴隶社会溃崩瓦解,战事频繁。正在此时,出现了我国服饰史上最早的改革家——赵武灵王,他积极推广胡服(即裤褶服),因此服便于作战,便于骑射,所以改服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战争方式发展变化所驱使。当时的北方地理环境存在着局限性,战场从平原扩展到山区,形势逼人,作战方式必须改变。当时地处西北的赵国,为适应军事发展需求,采用以弓箭为主要武器,全军上下皆习骑射。“胡服”与骑射关系密切,窄袖、短衣、紧身裤、革靴等服饰便于作战,活动灵便。武灵王推广“胡服”影响极大,许多地区甚至民间皆仿效之。《事物原会》引《舆服杂事》云:“赵武灵王有裤褶之服。”武灵王服饰改革的贡献相当重大,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与胡服密切相关的是“靴”。赵武灵王改屦舄为着靴。《释名》云:“古有舄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事物纪原》云:“履三代皆以皮为之,单底为履,复底曰舄,盖祭服曰舄,朝服曰履。”《中华古今注》云:“靴者,盖古西胡服也,昔赵武灵王作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至马周改制长靿,取便乘骑也,文武百僚皆服之。”
赵武灵王仿效胡人腰带,因其便利骑射系束紧身,可将随身物件附系腰带之间,并附饰若干小环,将携带之物挂扣于革带之上。其仿制腰带曾有记载。《战国策·赵策》云:“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即古人革带镶饰黄金带钩。据周锡保著《中国古代服饰史》中论述:“但带饰之有鞢〓,即有环和加饰金银等,应自赵武灵王始。”
散见于全国各地的古代胡服尚不多见,新疆出土的古代服饰另有文章论述,此处不再重复。现仅举例,以资考证。
据周锡保著《中国古代服饰史》中所画山西省侯马出土陶范,为东周末期春秋时代胡人服饰。所画两人均为窄袖短袍,一为左衽,一为右衽和领,下身穿裤的服饰形式,与“裤褶服”相似。此陶范的出土其时间早于赵武灵王改革服制,证实改制胡服是有所依据的。
胡服流散各地的资料不算多,现列举一二以供观赏。《文物》1955年第1期发表一幅东周时期的“持竿胡女铜像”。此胡女铜像体型丰圆粗壮,身穿短袍窄袖,梳双辫垂于双肩,腰间束带珰的革带,足蹬靴,是古人少女服饰。
“战国铜人”是穿窄袖、短衣装的杂技艺人。原件在美国华府弗里尔美术馆。
“戴冠战国铜人”是穿窄袖齐膝短衣的男子。此件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
“战国银人像”是穿着窄短袍,腰束革带的胡人装。原件在日本。
“当户掌灯铜人”是穿着窄袖对襟短衣的仆从装。此件出土于河北满城。
第五节 原始装饰与审美
远古时期的边疆原始人类,从半兽半人、茹毛饮血的洞穴中走出来,他们既具备与大自然搏斗的能力,又有发展生产的渴求,这就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与生存竞争的结果。粗笨沉重的石器工具使原始人类捕猎了食物,但在生活上却造成许多艰难与不幸。面对严酷的现实,原始人从打制粗糙的石器进而发展到制作精巧的细石器,然后再装上木质或骨质的手柄。经过细致琢凿的工具,不仅外观得到改善,还能较快地处理各种兽类毛皮。装饰性工具的细微变化,孕育、萌发了人类对自然物的审美体验。
装饰性石器与骨饰件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位置,赐予了西域的楼兰等地区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活动。考古学者曾采集到柳叶形、桂月形石镞、石矛。这些细石器不仅使用方便,而且美观大方,有的石器通体被凿成鱼鳞状,其造型与刻纹透出粗野、淳朴的原始美。那饱满的构图,既匀称又变化无穷,予人以独特的美感。一件件装饰化物件的出现,意味着原始初民造型观念的拓展,装饰性造型融入了制作石器之中。
砾石坠 新疆考古队在阿斯塔那细石器文化遗址采集时,发现了发出迷人光彩的砾石坠。“砾石坠”呈桃形,中心部位对穿小孔,对称、均匀,显示了磨钻技艺的熟练。利用坚硬的砾石制作饰物,无论是欣赏或把玩,都充分体现了边疆古代初民在与大自然抗衡中,在游牧渔猎之余,仍然有着美化、装饰自己的情趣,这正是古代人类编织文明发展史的序曲。
心形骨饰件 此件制作巧妙,构思独特,是考古工作者在木垒县四道沟遗址采获的,为铜石并用时代的饰件,即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出现铜石、金石并用,对于生产、生活用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件用骨质制作的装饰品,长约6.2厘米,厚约0.8厘米,形状扁平略呈凸形,上端倒置呈三角形,适中的起着连接作用。边长约2.9厘米。三角形中镂空雕琢成心形,下端另接长约4.8厘米的心形,上下对称,蕴含心心相印。骨饰件的中心是镂空的,最下端还刻成凸形呈椭圆状骨钉,似带钩连结上端。它似项链又像独特的艺术品,在整体艺术结构中发挥得自由活泼,表现出率真的生命力,影射出古代某些生活气息和原始初民对自身创造价值的某种肯定,呈现出人类精神主体和意志相联系的审美愉悦。
考古所曾在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孔雀河古墓沟遗址发现一件件稀有的骨质项链、木质头簪、玉珠、骨针与木针。
骨质项链 其形有筒状、圆珠形之分。造型古朴、原始,由一颗颗骨质筒状、圆珠状连接串成,琢磨均匀、形状奇特,是件不可多得的装饰品瑰宝,其艺术价值并不逊色于现代的珍珠、玛瑙项链。
骨簪、木簪 簪,单股如针,以簪贯发为饰。古有骨簪、玉簪、金簪。此出土骨簪,上端呈椭圆、圆柱形,下端如针。木簪顶部呈长方形,并刻有简洁、朴素的几何纹,优美的曲线与四出菱形图案融会一处,构图均衡疏朗,含有一种韵律的节奏感,予人以活力,具有古朴的原始美。骨簪既精巧又美观,表现了原始初民对仪容美的重视,开始用簪固定发型,求得一种仪容的修饰美。仪容审美不仅是个人的爱好与兴趣,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的表征,它显示了东方民族审美思想的独特性。
骨针、木针 造型别致,纹饰各异。此骨针没有针眼,顶部精细地琢出桂叶形、四菱形、圆锥形、圆珠形等针柄,柄部刻出细纹,针部磨制光滑。“木针”是最原始的“纽扣”,既可别住无扣的上衣,又是一种装饰品。作为实用的装饰性物件,在特定的环境中,构成某种气氛,从而产生特有的审美效果。
原始初民不仅在佩戴装饰物件上讲究美化,而且在日常用具上也精琢细雕。据考古工作者羊毅勇报道:出土于新疆木垒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把骨梳,它的造型呈长方形,扁平而光滑,另一面是稍有麻点的骨质孔,长约8.3厘米,宽2.4厘米,共计6个尖状齿,这种造型的骨梳在新疆是首次发现。按其齿的形状、疏密与间隔的特点,可以看出,此梳主要是用作梳理兽毛,为制作毛纺织物图28骨针。孔雀河古墓沟出土做好了准备。
精美的玉石饰品
新疆盛产玉石,这是大自然赐予的得天独厚的珍贵宝藏,且历史悠久,蕴藏丰富。考古人员在楼兰地区采集到远在新石器时代高5.4厘米,宽5厘米,厚1.4厘米的“玉斧”。斧的刃部较厚,虽有自然裂纹,却闪烁着玉石的晶莹与光洁,以名贵的羊脂玉制成的“玉斧”,反射出古朴的造型情趣。
玉石珠饰出土于孔雀河古墓沟,是随葬品,为年轻女干尸颈部、腕部佩戴,软玉质,较有透明感,呈管状空心、菱形四角形、圆柱形,琢刻巧妙,细润光滑。不久又发现各种玉石珠饰,五光十色,耀眼夺目,象征着原始初民创造的光灿灿彩虹。爱美的心理融入饰物之中,体现出朦胧的人体装饰美感意识,以审美的观点来对待自己身体的完美性。
新疆玉石的开发利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中华民族祖先黄帝时期就有记载。《山海经》曰:“密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黄帝乃取密山之玉,而投于钟山之阳。”《贾子通政语》上篇曰:“黄帝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蚩山”、“密山”、“昆仑”都泛指新疆玉石产地。玉石,是古代西北少数民族装饰自己的佳品,也是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物证。据载: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一座古王府墓葬,出土了举世罕见的文物,而玉器多达700多件,经鉴定绝大多数玉器“基本上是新疆玉”。它的发现证实早在殷商晚期新疆玉已大量输入中原。此后,交往不绝,绵延不息。玉石作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往、传播的枢纽,早于“丝绸之路”,是一条闻名于世的“玉石之路”,它为西域古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疆玉石以和田玉质地最好,有名贵的墨玉、脂玉、翠玉等。墨玉墨而透亮,脂玉光泽如羊脂,翠玉绿如碧玉,翡翠是装饰品中的珍品,流传极广,蜚声中外。杨汉臣等著《新疆宝石和玉石》一书中写着:“商代是我国琢玉工艺发展的重要时期..周的礼器、秦的玉玺、汉的玉衣、唐的玉莲花、宋的玉观音、元的渎山大玉海、明的子冈别子..历代这些玉器大都是由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利用和田玉琢成的玉器,堪称我国玉器的瑰宝,内含东方传统文化装饰性审美意趣,和田美玉可与世界上的精美玉石相媲美,令世人赞叹不已。
古拙的青铜器、金器装饰纹样
青铜器、金器饰物的出现,显示着装饰性饰物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新疆的和静县察吾乎文化曾出土了一面青铜器——为公元前8年至公元前5世纪的一面圆形铜镜。为新疆地区仅见的早期铜镜,镜面中心镶一个弧形的钮,主体纹饰为凶猛的巨兽,它圆目大睁,血盆大口露出巨齿,啮咬着尾部,使丰满的兽尾四散飞扬,与发达的肢体蜷曲于纹饰之中。狞厉威严的兽纹渗透着一种奇拙、怪异的意蕴,犹如原始初民深信的图腾物。野兽纹饰具有雄浑的鄂尔多斯造型风格,在绿洲草原古遗址与岩画中多有发现。野兽纹饰已非常物,它在古代原始初民的观念中,融入的原始宗教渐渐被神化,形成一种带有原始特征的艺术形式,野兽纹饰中怪异的纹饰,具有某种象征符号,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权威神力观念。
据载:“吐鲁番艾丁湖潘坎出土‘虎叼羊纹铜饰牌’,长11.1厘米,宽5.3厘米,厚0.3厘米。正面铸成一只透雕的老虎,睁目竖耳,张口叼着一只羊。猎获物到口后老虎不慌不忙迈步回山林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背面有三个环状钮,头端二个,尾端一个,布局呈三角形,以供附缀于其图33白玉斧。新石器时代于罗布泊采集。此玉斧形似长方形,刃部留有琢磨痕迹,至今仍很锋利、流畅。玉斧质地为名贵的羊脂玉,晶莹洁白,细润光滑,经阳光照映,熠熠生辉。新疆考古所藏他物件..以往,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关系时,很少引用新疆的资料。木垒县收集的野猪搏马纹铜饰牌,与西伯利亚出土的同类饰牌构图,造型非常相似。吐鲁番新发现的虎叼羊纹铜饰牌,与1975年在萨格雷河谷斯基泰时代的古墓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简直雷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新疆地区的广泛分布,填补了区域空白与这一草原文化传播链条上的缺环。”①撰文具体地写着吐鲁番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的造型、质地及与鄂尔多斯纹样的内在联系。
“虎叼羊纹铜饰牌”与上述“野兽纹饰铜镜”都具有鄂尔多斯纹样风格,但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变化。前者纹饰酣畅、饱满,突出它巨大的身躯与明显夸张的口部,呈现出野兽的凶猛与猎获时的种种神态;后者虽张开血盆大口,却首尾摆动,又夸张其肢体,于其动态之中蕴含一种神性的张力,赋予一种神秘力量。实际上,新疆已发现多处鄂尔多斯式纹饰的造型饰物,它反映北方草原文化圈的一种形态特征。在这个文化圈内,由于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彼此相似,草原游牧人之间彼此交流往来的互融性,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亦呈现出一致性和稳定性,西域地区更受中亚文化的影响,因此,纹饰中蕴含着多种文化因素。
金器纹饰的不断发现,显示着西陲边塞进入了文明的黄金时代。考古者在伊犁河流域,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塞人墓葬发现了金簪、金耳环、铜耳环、铜发钗等金、铜饰物,又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古遗址发现了战国时期最富特色的黄金饰物。它色泽纯正,闪闪发亮,制作手艺高超,堪称传世金饰中的代表作。其中一具“虎形金箔腰带饰”,长25.4厘米,宽3.3厘米,金光灿灿,造型构思巧妙,刻画出猛虎奔跑、跃动、张嘴啮咬的雄威与出没山野的巨兽体态。两虎相对,它们的头部、肩与腿部都做了有力地夸张,刻画坚实、粗壮、筋肉凸起,特别突出两虎的蹲伏状,翘起的尾部卷曲而又富有韵律感,创造了一种气焰逼人、奔放不羁的激烈气氛,连同那旋转式的旋纹,刻画得十分流畅。虎形纹样装饰,使观者获得一种生命的活力,反映出远古时代初民们的某种精神需求。
“虎纹圆形金饰牌”也是以猛虎为主体形象的黄金饰牌,突出虎的头部、身躯与四肢蜷曲于圆形饰牌中,并作跳跃奔跑之状,既突出虎的凶猛,又简化其肢体部位,适当地融入旋纹。
上述金属饰物与古代塞人有着密切联系。王炳华著《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书中曾提及这批出土的金器。他举例说:“在那座年仅20多岁的贵族女子墓中,装饰腰带的金牌就见到8块,每块金牌都重20克以下。蓬勃生气的造型,洋溢着生命的流动感,它夺目耀眼,切入动态变异中的熠熠光泽,透出造型迷人的神韵。”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曾经告诉人们:“塞族人王族享用着上天赐予的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有着黄金饰牌,人死后,要用黄金制品入葬……”在阿拉沟东口打开的塞族人贵族墓葬,为我们了解塞族人,了解吐鲁番的开发建设过程,提供了更为丰富详实的实物资料。
塞人是曾经驰骋于中亚草原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足迹也留在了西域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所留下的珍贵遗物可供历史学家补续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载:“塞种人,古代族名。历史上主要分布于中亚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曾散居中国西部。西方古典作家称之为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为塞卡人,中国史地文献称之为塞种、塞人。”塞人崇尚以虎、狮、熊为主体的装饰性图案,视其为表达情感的有生命的实体,创造出显示自己力量的膜拜偶像。一件件出土的表现得酣畅淋漓的装饰化饰物,传达了塞族人的审美倾向与观念。图案中表现出丰富的想象,朴拙的气质、奇异诡谲、飞扬流动的神采,绽放出巨大的、摄人心魄的魅力。
独特的造型特征,究其原因出于它的源流与生成,呈现着先民们的思维生存环境与情感的流露。即便是斯基泰风格或鄂尔多斯造型,也都同源于草原游牧文化圈内,是一种超越部族的文化形态,具有共性的特征。
金项链则是出土于阿拉沟古墓,它是古代妇女珍爱的宝物。它不仅璀璨夺目,且制作工艺精细,其金质项链采用极细的金丝编织成链状,相隔一定的距离镶上色泽柔和、温润光洁的白玉、翠绿的孔雀石,显得晶莹璀璨、华丽夺目、玲珑剔透,是件弥足珍贵的金、玉镶嵌首饰。
金耳环造型精致、铸纹流畅,也是一件少为人知的金饰。此耳环金色纯正,黄色中闪透光泽。其长2.5厘米,环径1.5厘米。耳环的上端为圆形金环,下端系着塔锥形坠饰,坠的上端铸出密集如珍珠的珠点纹,下端呈座状式,衬托整体金耳环饰。
葡萄坠金耳环其造型疏密有致,具有一种韵律感。耳环的上端系着一个圆环,直径仅1.3厘米,环的下端以两个小钩相连紧靠金坠。坠饰由8个空心圆形金泡组成,连接为一体,似一串丰硕的葡萄,它的色泽和亮度透出纹饰璀璨而闪烁。
这些金银饰物不是单纯欣赏、美化的装饰物,它所以被誉为珍宝,是因透射出时代的风尚变化,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开端,是古代人类集感情、审美、原始宗教、生活实用等诸多因素的产物,代表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神秘含义。那种对“纹饰”的特殊情感、认知与表达,传递出原始初民内心世界的某些隐秘。“纹饰”以“纹”为核心,它在文字诞生之前,也是一种记录历史与文化的方式。《易经》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晋人干宝注说:“四时之变悬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具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以“文明而化成天下,即所谓的‘文化’,而文明之文指天文、地文、人文,也即天纹、地纹、人纹,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迁变;地文谓地理气脉,山川植被形状;人文是人的文彩装饰,包括纹饰、文章、礼仪等内容①。”阐述了“纹饰”涵盖面的博深,包含着宇宙万物与哲理内容的精髓。一件件珍贵的装饰品使深埋地下数千年的古代宝物终于出世,它使人们从中悟到一个真谛:人类的繁衍生息与文化累积的延续,是靠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进取与实践获得的。实际上,人的生活需求只有靠人类自己,它也包含着人类的审美意识,那附着于金、铜饰上的纹饰与造型,那一串串色彩斑斓、晶莹剔透的装饰品,是原始人类认定的万物精灵,是他们心灵辉映的火花,是最早的精神寄托。同时,玉石、金铜饰物精巧的制作和应用,也表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与水平,反映出边塞城邦诸国、游牧民族时代的文明背景。人们透过感官、视觉,体会到古代人类的文明发展坎坷不平、生生不息地朝前迈进的艰难历程。
面饰的装饰化
文身、文面是人类文化中最原始的肤体装饰,纹样各异的装饰,构成一种无声的语言,其历史几乎和整个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纹饰的古拙或浓艳,多有特定的内涵,在世界某些地区曾流行过,且渐渐形成一种习俗,曾盛行东南亚、东北亚、非洲..我国台湾的高山族、云南的独龙族、傣族、海南的黎族、四川凉山彝族等似有文身、文面之俗。此俗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久远。《汉书·地理志》曰:“越人,文身断发,以辟蚊龙之害。”《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墨子·公孟篇》也有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越,方外之地,断发纹身之民也。”
西域与内地相隔万里之遥,过去与现今在各地居民中很少发现“文身文面”的习俗,然而,近年来,新疆考古人员却在偏远的南疆且末扎洪鲁克乡古墓,发现距今3000年前后的两具男、女古尸。由于当地干旱少雨,古尸保存完好,发现在他们的面部饰有布局对称、纹路清晰的纹饰,画在鼻、眼、额、颧骨部位,似用矿物原料,如雌黄、雄黄、铅黄以及赤铁矿等涂抹。男尸面部太阳穴处(两侧均有)画有卷曲的大羊角纹,它又似太阳,中心稍圆,四周呈放射状。女尸面部眼窝下端左右两侧显出对称的卷云纹。面纹的发现与古人对日月、天宇等大自然崇拜有着紧密关联。李砚祖在《纹样新探》中道:“研究《周易》的学者曾指出,卦爻辞的表现形式是‘假象喻意’,即拟取人们生活中习见常闻的物象..以‘八卦之象’为例,所谓‘八卦之象’,即八卦象八类事物。以自然界八种自然为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自然客观物象是人朝夕可见,其形其性都明白易察,深层的理性规范、哲理,所谓‘道’,一旦与人们所熟悉的自然物象的存在相比较,便能获得很好的传播和接受效应。”
真正见底蕴的是人类运用自然物,给予象征性表现与带有浓重的原始意识和先民对于大自然的认识,渐渐积沉于心灵与思维活动中,并反映在面饰的纹样上,由此又引发某种审美观念或原始宗教意识。面饰赋予人美的丰采,也含有取悦异性的崇美心态。
第六节 原始的、古老的衣冠服饰——铁板河出土衣冠
位于塔克拉玛干东缘,曾处于“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绿洲——古代楼兰,是人类活动、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从侯灿楼兰考古实地调查结语中获悉:“..采集的许多细石器文化标本与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其他地点的细石器文化遗迹比较,这里可能是史前人类的重要聚居点。”丝绸之路的兴起,促使了楼兰的发展与繁荣,形成为楼兰国,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史记·大宛列传》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记载着楼兰是“城郭之国”,盐泽即罗布泊。罗布泊是我国著名的湖泊,从第四纪起,受到造山运动的影响,形成罗布泊洼地。罗布泊又称“游移的湖”。随着塔里木用水量的增大,今孔雀河下游已经断流,罗布泊也早已干涸。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有历史记载的著名古代楼兰之国也销声匿迹,成了千古之谜。
“楼兰睡美人”——早期衣冠的发现
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队,由考古专家穆舜英主持,曾在楼兰古城、罗布泊北面铁板河地带古墓中,发现保存完好的女尸。此古尸于1992年在日本展出时引起轰动,震惊中外。古尸被誉为国宝级文物,是新疆迄今为止发现的早期古尸,成为考古学界的奇迹。据测定约有4000年历史。
古尸的发现,初步揭开了古楼兰人的穿着衣冠之谜。古尸被称为“睡美人”,其全长152厘米,外形特征:“下巴尖瘦,深目微闭,鼻子高而尖小,薄嘴唇,褐黄色头发披散肩上..”①她穿着粗纺毛披风式上衣,紧裹全身。衣的形式虽不清晰,更不完备,却能裹住身体。衣的前襟用磨光的尖细而光滑的木针别住,起着纽扣作用;头上戴着缀有毛线边饰与插羽毛的毡帽,呈尖顶形,能将护耳、护颈的功能连成一体,并有毛绳系于颏下。脚穿生牛皮短靴,形式虽不规范,却保护了脚面与脚后跟。
衣冠服饰的发现,揭开了原始初民衣饰创造的序幕。出土的衣物使人们顿悟:原始初民为了生存,具有一种对于生命渴求的冲动,他们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创制石质、骨质纺轮,开始选用羊毛、驼毛捻成毛纱,运用纺轮织成原始的粗纹毛织物,摆脱了以披兽皮为衣饰的状态,创造了古朴、厚拙按照人体长短编成的披风式衣饰。与披兽皮相比,毛织披风先进了一步,它在人类服饰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毡帽”的出现,可视为人类早期衣饰文化的精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种标志。毡帽上的羽毛饰,不是单纯的装饰品,它在原始初民的心目中,是一种偶像崇拜或象征物。羽毛冠既是狩猎人的头饰,又是一种保畜平安的吉祥物,是实用的功利性与美感形式结合的开端。
古罗布泊人创造的为护体需要的衣冠服饰,足以证明他们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步入以毛织为衣的时代。那顶护耳插羽毛的毡帽,毡色纯正,毡质平均、厚实。衣冠面质料的变化,是人类衣饰文化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和一个时代的象征。
石雕、木雕人形象
楼兰地区孔雀河古墓沟墓葬内的随葬品石雕、木雕人形象,多为女性,有的头戴尖顶圆形帽冠,胸前穿有毛纱,有的头发披散肩后。人形象随葬品无不烙上衣服穿着的印记。出土实物表明,当时居住罗布泊洼地的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氏族成员在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女性雕像的出现,说明女性尤受尊敬,似为一支以母系崇拜为特征的原始部落。她们已经离开穴居,改变了披兽皮、树叶遮身的状态。衣冠的穿戴,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和胜利的表征。
第七节 裘皮衣袍的发端——五堡出土衣冠服饰
哈密五堡出土的衣冠服饰颇具特色,这与哈密的地理位置与区域环境密切相关。哈密为新疆东部的门户,地处内地与新疆咽喉要道。从甘肃的嘉峪关到哈密,须经过玉门、安西等地,路途中尽是戈壁、沙漠,十分荒凉。到了哈密渐渐显现一片绿洲。清人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有确切描述:
玉门碛远度伊州,无数瓜畦望里收。
天作雪山隔南北,西陲锁钥镇咽喉。
哈密古称伊州、伊吾,历史悠久,地理位置显要,被考古界发现并承认为新石器文化点,曾采集到珍贵的用砾石制成的刮削器、锥形石核及坚硬玛瑙与石髓。社会发展到了青铜时代早期,曾发现距今3000年前的哈密五堡乡古墓群葬,一处竟葬好几百人,证实了哈密人活动频繁,是块休养生息的地方。
哈密五堡乡古墓出土的衣冠服饰丰富多样且形式清晰。哈密五堡乡古墓,“是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阶段的一种考古文化..由于死者入葬时的衣着、鞋、帽、铺垫的皮、毡大多未腐……提供了研究当时生活的丰富的实物资料。死者头戴尖顶毡帽、穿毛皮大衣或皮革大衣,着长筒皮裤、高靿皮靴..各种毛织物,色泽鲜艳如新..皮革鞣制、脱脂水准亦高,革制品柔软。这是研究我国早期毛织、制革手艺难得的实物资料。随葬的牛、羊、马骨,说明畜牧业经济在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还发现小米饼及青稞穗壳,表明了农业经济的状况。”①
裘皮衣袍的独特样式
绿色大自然的赐予,给予哈密地区水草丰盛的环境,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为服饰的原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御寒蔽体,裘皮衣袍脱颖而出。《易·系辞》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鲜明地提出人类离不开宇宙生态的大环境,人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创造了物质文化。
哈密人创造的裘皮衣袍,毛皮在内,皮板光滑面在外,形式为交领、对襟、双袖连缀手套,袖口与手套相连接的衣袍。衣袍与手套缝缀的皮袍御寒保暖,这种款式尚属少见,实际上也仅此一例。古代称谓的“袍”,即不为上衣与下裳的衣服,形式为长度过膝,呈直筒式,下摆宽大,便于骑马放牧、狩猎。彼得·波格达列夫在《作为记号的服饰》一文中曾说:“服饰的穿着不仅关系他自己的个人趣味,而且也顺应地域的需要,以符合它的环境标准。”实际上,不仅是环境的标准,更显示了区域文化的共融性,服饰样式的风采,同时受到环境的限制。
甲骨文中的“裘”字为象形文字“〓”,作毛在外的象形。《说文解字》也说:“裘之制毛在外,故像毛。”《诗·秦风》曰:“君子至止,锦衣狐裘。”毛皮在外,故又罩上一件锦衣。上述文字介绍了古代裘皮的概况,是记载汉文化先民的穿着样式。新疆出土的裘皮袍服,表现了游牧民族粗犷、雄伟的款式,它不仅适应环境,也体现了游牧人生命活动的一种形态。
原始初民的衣袍纽扣极为简单、粗放,像罗布泊人用树枝刮削成尖细光滑的木针,别在衣服上,保暖而不透风。哈密人又进了一步,它将树枝削成细小的长度约3厘米左右的小木针,在衣袍前襟间隔一段距离缝缀毛线纽襻,小木针套在纽襻处,一种新的纽扣形式便诞生了。纽扣,它既美观又能使衣袍合缝而不透风,物质文化的发展与变化,证实了人类对功利性及实用性的需求,是从人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变化、创造而获得的。
毛织衣袍的新变化
捻毛线纺织成粗毛布,是衣饰原料史上的一大进步。古代哈密人的粗毛布厚实、细密,质地上乘。以粗毛布为服饰原料,使衣袍柔软、耐用。其形式清晰,具有游牧地区衣袍的特征,是套头式、交领、直筒形长过膝的粗毛布衣袍。裁制方法与内地略有不同,袖子较短不超过手臂,连着上衣前片,与袍服相连,简便合体。
袍服色彩为褐色,显得平淡、深沉。但在衣袍的领口与边缘处却饰以墨绿色的毛线饰纹,使袍服增色生辉。
袍服附系的腰带,是用暗褐色,夹以红、蓝、绿色的毛线编织成辫状,垂着流苏式的毛线穗,赋形设色具有古代人的审美意蕴。由于冷暖色调搭配得恰到妙处,使这条毛织腰带柔丽夺目,呈现出神奇般的绚丽与自然色泽的韵律。
腰带起了紧身护体的作用,它的萌发揭示了这样一个真谛:“人猿揖别”之始,大自然显示了对人类无限的威慑力量,但是,当人类在各种物质创造性活动中展示出人的本质力量时,不仅能够征服自然,而且也孕育着人类审美意识的萌发,它是人的智慧、力量和意识的结晶。
尖顶毛线帽
哈密五堡古墓出土衣物中有一件距今3000年前的古代哈密人编织的尖顶形毛线帽,它不仅弥足珍贵,且结线编织方法竟与现代的毛线编织法相类似。
毛线帽是由捻成粗宽的浅驼、深驼两色毛线编织而成,显得厚实、纯净。从帽顶往下结出明显的辫状形边饰,致使整体呈波状似的纹路,编结规律有序,呈现出朴素大方的美感效果。
尖顶式帽冠不仅护头,还保护双耳与颈部,是抵御风寒的上品。尖顶帽式样流行于中亚、西域一带,孕育了地域性的共融与互补,呈现出游牧民族帽冠的特征。
第八节 服饰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扎洪鲁克出土衣冠服饰
扎洪鲁克古墓位于且末县约6公里处,处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一带。墓葬约在公元前9世纪,相当于中原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古墓随葬物、葬俗形式与古代土著居民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相关联,其中尤以衣冠服饰最为显著,具有浓郁的地域性特征,为研究、考证衣饰文化发展倾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毛织衣袍与裤装
据参加古墓发掘的克由木等人报道:“男着咖啡色平纹半长袷袢式粗毛质单衣袍。女着绛红色斜纹过膝粗毛织连衣裙和长裤。男女均穿毡袜和长筒薄底软皮靴。”
实际上,上述出土的两件毛织长袍、裙装,是西域早期衣饰形式的服饰文物,它的款式与形式对于西域地区的服饰影响极大,上述引文中提到的“袷袢”,即现在新疆少数民族长袍的称谓,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服饰的历史承袭性与延续性。
男式长袍形式为套头、交领,长度为袖口过手指,身长过膝下。交领衣是古老的上衣款式,前襟分左右两片,交掩于前胸。
女式裙装实则也是袍服,只是下摆宽大并拖至脚面。形式也是套头、交领。在绛红色的斜纹粗毛布的领口和下沿至衣饰边缘处以及上臂均镶饰有色泽为白、蓝相间的毛织纹饰。男袍也以同样的色泽与纹饰镶边,使袍服明丽而多彩,突出了服饰的审美主体特色。衣饰上细微的装饰与服饰色泽交相融合、和谐统一,不仅锦上添花,而且更突出了整体特征、审美情趣与地域性衣饰文化的色彩。
原始游牧生活以及广阔的绿色大地赐予扎洪鲁克人良好的生态环境。他们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的衣食来源,反映在衣饰原料上也是以毛纺织为质料。袍服的质地与色彩以及衣饰边缘的装饰,反映了扎洪鲁克人衣饰审美观念的历史性变化,特别是历经数千年而不变的染织色彩,证明古扎洪鲁克人已步入穿染色衣饰的时代。
服饰的设计与制作,反映着社会的审美情感与情趣,这种感情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向前演进,逐渐形成一条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长河,与人类生存息息相通,融为一体。扎洪鲁克人衣饰上显现的装饰美,满足了当时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
衣饰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与该地墓葬出土的古尸脸部的“面纹”,与随葬木栏、木叉等木祭器以及原始宗教、大自然崇拜、巫术流行有关。古老遗风的传播是衣饰形式能保持地域性特色的因素。扎洪鲁克人创制的美丽、古朴的毛织衣袍,是古代塔里木南缘衣饰文化的发展与升华,是服饰创造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裤装”也是出土于扎洪鲁克古墓的珍贵衣物,它应是古代早期着裤形式的实物,此裤为自纺毛布染成深绛色的男裤。腰宽近2米,裤腿各1米,长及脚面,腰胫下处缝缀一块菱形的裤裆,致使整个裤装严实合缝,它又外套一双长及膝部的毡袜(古尸出土时的穿着),此裤虽宽腰阔胫却折成两褶而护贴腰部,是足以适应寒冷地理环境而产生的裤装形式,与内地汉墓出土的无裆、开裆裤区别较大。此裤装的发现,证实了西域的裤装形式早于内地的历史,裤装不断发展演变,逐渐成为西域地区的主要服饰,它与上衣相结合,形成整体衣装形式的“裤褶服”。裤装,它展现了地域性衣饰文化的特征与文化观念的一致拓展,呈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智慧。
奇异的帽冠
“冠”是古代人头上装饰的总称。据说,冠的形成与大自然的鸟兽有关。《后汉书·舆服志》曰:“上古衣毛冒皮,后代圣人见鸟兽冠角,乃作冠冕冒。”另有史书记有:“黄帝以前以羽毛皮为冠,黄帝以后则以布帛为之,饰以冠冕缨緌之作,皆有所象也。”现介绍出土的几种毡帽类型为研究帽冠提供了考证的依据。
褐黑色尖顶毡帽 毡帽从帽檐至冠顶高达32.7厘米,缘径28厘米。采用两大片毡块裁成长三角形,用白色毛线缝缀,帽的边缘翻起,也用白色毛线缝边饰,从帽缘到帽冠呈斜坡形,因此,冠顶再高也不易倒塌,帽冠顶部呈圆形似鸟的头部,意趣盎然。
褐黑色尖顶毡帽高大而厚实,尖顶部犹如小小山峦,仿佛凝聚着一股潜力,呈现出大自然原始古拙、质朴无华与豪放不羁。而帽冠的结构、质地与造型,则深蕴着大漠、戈壁、绿洲、草原游牧文化圈粗犷、雄浑的气质。帽冠的实用性与先民朴实的追求、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尖顶式帽冠是游牧人帽冠的象征,流传极广,斯基泰人、塞人及游牧民族都爱戴此帽。过去只能在壁画、石刻画与泥俑形象上见到它,现在出土了实物,实为珍贵。
黑色圆形帽 此帽用黑色细毛线编织,毛线细密,织纹清晰,是用编织好的四个扇形毛坯交错缝缀成圆形,口缘部有伸缩性,帽的形式类似现今的“贝雷帽”。这顶帽子如果置放在今天的帽冠展览会上,人们一定会发现,它的编织技艺与帽冠造型充满了古老文化的诱惑力。
白色羊角形毡帽 这顶毡帽以两个呈半圆形白毡从中心缝合成圆形,突出缝合的部位类似帽饰的流行线。帽的顶部缝缀着用毛毡拧成的棒状羊角饰物,使毡帽主体呈现以羊角为饰物的冠帽,它不仅具有御寒的实用性,还含有以动物为装饰的神秘意蕴。格罗塞在《艺术起源》一书中曾说:“我们研究用具的装潢,尤其可以发现澳洲人的衣着、盾牌、棍棒上的装饰和他们画身的图样相仿,完全是模拟兽类的。想用同样的绘画把他们自己扮成兽的模样,是和原始人认定某一种兽类是他们同族的保护神,而喜欢模仿兽类形象的心理相去不远的。”以羊角形为饰物是游牧人对以畜类为经济来源的特殊情感,既崇拜为“保护神”,又盼望兴旺发达、保畜消灾,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朴实情感。
第九节 毛织衣袍的新奇款式——苏贝希古墓出土衣冠服饰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吐鲁番火焰山腹地发现一批珍贵文物,据判定为两千三四百年前,相当于内地的战国时期。
主持古墓发掘的吕恩国披露:“一批身着新颖奇特服饰的两千三四百年前的古尸,最近在火焰山腹地苏贝希村附近的古墓群中被发掘出来,同时还出土了300余件陶器、木器以及铁、银、石器等……一次发掘这么多保存如此完整的古尸和大批未朽的文物,这在新疆多年的考古工作中是少见的。发现的墓室、房屋、服饰、用具、食品、药物等具有明显特色,堪称稀世珍品,为丰富、补充、完善过去的考古成果,解决某些考古学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吕恩国详细地介绍了随葬衣物:“几乎全都是毛纺织品,犹如进入一个崭新的、奇异的服饰世界。那新奇的款式、那熟练的纺织技艺,堪称新疆游牧民族衣饰文化的一绝。”
战国时期前后,吐鲁番盆地曾经是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地方,水草丰沛、牛羊遍地,以畜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农业和手工业。王炳华著《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书中写道:“从2000年前保留至今的汉文史籍中,人们早就了解到,距今2200年前,雄踞吐鲁番大地的主人,自称为‘姑师’,后来又改称‘车师’。当时他们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有自己的都城。王国人口不算多,以吐鲁番盆地为舞台的车师前国,人口不过6050人。如果包括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人口也不过1.2万多人,但是它地跨天山南北,影响远及西域内外,不容轻视。”《史记·大宛列传》也曾记载过在楼兰、姑师这两个小国中,建有城郭,已经步入文明。它记载着吐鲁番盆地在两汉以前,当地族民是车师人。现介绍苏贝希颇具特色的出土衣冠。
尖顶高帽冠
此帽以突出尖顶部位为特征。帽冠中心竖起以牛皮为质地的尖顶,它的高度竟有近0.8米,突兀于顶端;帽缘呈大圆盘式,与帽冠相连,又以毡质为内心,外罩毛织网状护套,通体浑厚、深沉,泛着青色的光泽。帽冠造型富有游牧民族特点,呈现厚实的毛质感,显得庄重与挺拔。奇特新颖的款式,告诉世人,似乎在求得和大千世界的动态保持平衡。
裘皮大氅
一件形式清晰的裘皮大氅,凝聚着游牧民族的伟大创造与心血。大氅显示出宽大厚重的皮毛感,光板皮朝外,卷毛在里,交领开襟,袍长及足,袖长过手指。
交领衣是我国古代上衣的主要款式,它的裁剪与制作都比“贯头衫”更为复杂,是服饰制作的一大进步。
裘皮大氅是西域早期完整皮衣样式的袍服,它结实、凝重、宽大。白天,游牧人穿着它骑马放牧、狩猎、挡风御寒;夜间,则用它做睡被。裘皮大氅显示出强烈的地域性特色。
毛织裤装、连腿皮靴
此裤装为纺毛质地,柔软、轻薄,腰阔胫长,裤长多于覆足。在其膝部套上圆筒形狼皮毛在外的“膝裤”套缚双腿,再用毛绳束系并与裤腰带相连。古时的“膝裤”也称“胫衣”,有以革制,也有以厚棉。此狼皮“膝裤”实为草原文化圈游牧民族穿着的特征。
连腿皮靴则紧紧套住毛织布裤,与膝裤、裤装、靴履连成一体的形式。皮靴套上裤装,便于骑马驰骋,游猎四方。从独特的衣装可以联想到穿着的人,他曾是威武健壮的骑士形象。服饰的风格和气派是民族精神的反映,是一种赋予了顽强服饰文化生命力的表现,更是一种摆脱了简单粗陋的原始衣装,进入文明历史进程的着装模式。
毛织内上衣
毛织内上衣为男性内衣,衣饰形式是小圆领、开襟、窄袖的纺织纯白色上衣。毛纺精细,质地纯厚、柔软、轻棉,显示出毛纺织品自身的特质,且具有保暖性、遮蔽性,显示了当地的毛纺手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彩色毛纺筒裙
彩色毛纺筒裙系采用土黄、红、蓝、褐等色染织的毛纺筒状形裙装。以宽窄不等的横道纹,间以多色染织的裙装,构成一个由毛纺质地、线条组成的五彩绚丽的纹饰,其色泽经2400年仍鲜艳如昔。筒裙的腰部配以红、白两色的编织带,组成美丽的带饰,衬托出裙装无穷的魅力。这一事实又告示着人们:当地族民具有特殊的毛纺、染织技艺。
皮质面衣
“面衣”亦称“覆面”,是一种葬俗用品。皮质面衣较为罕见,它是一种经过鞣革的羊皮,又以白色矿石在面衣上画出浅浅的线纹,使轻薄的皮面衣产生一种纹饰感,它覆盖于女尸面部,给人一种安详、静穆的感觉。皮质面衣的发现,证实了新疆早在战国前后即有此葬俗。
毛织网罩与化妆袋
发式是妇女头部的重要装饰,它不仅增添其仪容的俊美,也是人体修饰的关键部位。笔者曾目睹苏贝希古墓女尸的头饰,其造型新颖别致,有异于其他头饰装扮。她们多梳长辫,或将黑色辫发盘挽于头部,在那弯曲的辫髻上,罩上自织的黑色毛纺织物,一种呈网状似的发套,既固定了发型,又是当地妇女重视发式修饰的一种表现。
化妆袋是妇女化妆的组成部分。此化妆袋系从女尸腋下发现的一个皮质的小袋,袋中装有磨制光滑尖细、适宜描眉的黑色“画眉石”,白色的小石块似涂抹面部的粉妆,红色的石块犹如胭脂般红艳。这些经过选择的矿石为苏贝希妇女修饰、装扮仪容增添了光泽。化妆蕴含着审美情趣,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精神风貌的重要表征,也充满了时代特色与地域性特色。
毛织内衣与皮手套
毛织内衣系女式内衣。用羊毛纺成,它是一种纯黑色轻薄的毛纱。内衣样式为小方领、长袖,领口用红色毛线镶边,略显一种简朴的装饰风采。皮手套是御寒佳品,它的形式是四指并连,大拇指分开的连指式,是光面朝外毛在内,保暖性强的皮质手套。
毡靴与毡帽
毡靴呈高筒形,靴底为皮质,结实耐用且可涉水草。其连接的上部为深褐色毡制成的圆形筒身,组合成一种皮、毡复合式的靴,轻便保暖,是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足履的佳品。
盔式毡帽连耳护颈,呈盔甲式武士帽冠,戴上此帽,呈现出游牧民族的骑士风范。出土时尚有皮质箭箙以及那待发的一支支利箭,可以由此联想当时体魄健壮、能骑善猎的苏贝希男性族民威武的身影。这是封闭的地理环境给予衣冠服饰浓重的地域性色彩。
苏贝希古墓出土的以毛纺织、皮革为主要质地的衣冠服饰,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纯白、多彩的羊毛织物,而且从织造均匀、细腻、轻柔、绵软的程度上,使我们看到当时毛纺技术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兽皮加工、鞣制技艺也相当出色,是苏贝希人为适应穿衣着靴的生活需求,在毛纺织业、皮革加工业方面促成的一次飞跃,伟大的奉献内含着一种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发展形态。
诚然,古老先民以其实用为目的的服饰文化,无论是取材于动物界、还是植物界;无论是自然形态的、抑或是加工创造的,这其中都孕育了人类对服饰审美的萌芽。因为衣冠服饰的缝制,包括衣饰款式、质地选择与色彩的偏爱,不仅与特定的地域环境、经济生产相关联,而且包括服饰结构的变更以及与人类个体生命密切相联,都获得了充分的表现。它是一种来自远古时代的历史回音,是人类在一定时期涉足历史舞台的印记。
第十节 青铜武士俑——巩乃斯出土塞人铜像造型
“青铜武士俑”出土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战国。这个时代的社会是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这种巨变无不反映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西域的黄金时代。考古人员发现的这一时期罕见的具有青铜器文化特征的遗物,是弥足珍贵的。
“战国(或比战国稍早)到西汉时期,在西域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发生了某些古代民族(如塞人、月氏、乌孙等)的迁徙活动,西汉王朝统一新疆,以及丝绸之路的兴盛等,都为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十分重大的影响。”①
考古的重要发现,使古代西域的青铜器文化重放异彩。在新疆伊犁河流域的尼勒克县奴拉赛山谷中发现了两处古铜矿,在特克斯县发现了古代铜器。出土的铜器都具有民族特色,无论在质地、造型与纹饰的变化上,都比原始社会彩陶的表现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伊犁新源县发现的一尊铜武士俑,造型逼真、生动,向人们展示了当时人文性的特征。铜武士俑高约40厘米,重约3公斤,空心。武士面部深目高鼻,留有大鬓角,面部表情庄重肃穆,神态严峻,头戴尖顶大檐帽,帽后顶部呈尖刺弯钩状,双手作空握状,双腿一蹲一跪,上身裸露,腰系战裙,赤足,目光凝视前方,据考古专家鉴别为古代塞人形象。
塞人主要活动在中亚、西亚和西域。塞人常戴尖顶帽冠,故又有“尖顶塞人”之称。
塞人所戴尖顶帽也不尽相同,此铜武士俑的尖顶帽附有一尖刺弯钩,很可能是不同塞人部落所属。伊犁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是塞人游牧、活动的地区。《汉书·西域传》曰:“乌孙国..本塞地也。”在古代塞人的文化遗存中,还不断发现铜马衔、铜耳环、铜发钗、金耳环等用具与装饰品,各具特色的青铜器出土文物,代表着青铜文化的特异风采,不但赋予本地域的民族特征,而且表现出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原铸铜技艺输入的痕迹,因此,青铜文化在西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西域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一带不同的显著区别是,出土的文物中有铜器、石器、陶器,因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考古界为此定名为铜石并用时代。
第十一节 发型帽冠鞋履腰带
发型是人体的重要外观,古代初民是很注重的,特征多为蓄发而不剪。新疆考古队曾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的古楼兰遗址,发掘出距今约4000年前的古代罗布泊人古尸,这具女性古尸的头发为褐黄色,披散至双肩。哈密五堡乡古墓发现的女尸,约有3000年的历史,留有长到腰际的发辫。昭苏小洪那海古代石人像高1.91厘米,戴冠辫发,发辫多到9根,长垂于腰下。
古代匈奴、羌、乌孙、塞人等曾在西域辽阔的大地上游牧、生活,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将会不断被发现。《后汉书·西羌传》曰:“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由此看来,最早的原始初民不论男女都披发,辫发是披发的一种演变,束辫既好看又方便。
辫发习俗一直延续至今,闻名遐迩的新疆歌舞中,舞蹈者及演唱者几乎都是辫发。那又黑又亮又长的发辫,甩动旋转,优美飘逸,令人神往。
帽冠 帽冠是首服,也是实用性很强的头饰物,几乎与人类同有。古代原始初民常在头部裹上一块兽皮,用来抵御严寒风霜。原始人类既能顺应自然,也敢于同大自然搏斗。哈密五堡古墓出土的古尸头戴尖顶毡帽,给予现代人深刻的启示:毡帽的出现,反映古代游牧人在封闭、严酷的大自然里与暴风雪、冰雹、野兽的一种斗争方式。毡帽的形状很多,有尖顶、圆形、簸箕形等,色泽有纯白、浅驼、褐黑等色,体现出游牧人在宇宙空间的生存、创造价值。制毡需要一定的技能,从选毛、擀毡到制成一顶毡帽,要经过好几道程序。毡不仅能隔潮、保暖,还具有轻软、厚实的特点,足以抵御大自然的种种侵袭。是边塞大地原始初民适应大自然生态环境的伟大创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帽冠除具有实用性,还兼有装饰性。以羽毛作头饰的习俗,是西域原始初民的帽冠特征。它反映在一幅举世罕见的,体现原始社会晚期生殖崇拜的巨型岩画上,即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该画在长约十多米的岩面上,凿刻了300多个人体图形,其中有些形象的头部即刻有明显的“羽毛饰”。
无独有偶,在罗布泊铁板河古墓出土的女尸头上也戴着毡帽,毡帽顶端插着两根雁翎。羽毛饰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美的内涵,极富装饰性。从头顶兽牺皮到戴上毡帽,进而发展到用羽毛做装饰,是帽冠发展中的一种进化。好像用羽毛装扮成动物的模样,却又有别于动物。“羽毛冠”最初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也是一种获得劳动成果的炫耀。羽毛亮丽耀眼,富有轻微张力,形态变化多端,是原始人对自然界的体验。羽毛是游牧人喜爱的头饰,它和非洲人以戴羽毛冠为英雄的标志同出一种心态,为当时人类的生活焕发出多彩的光辉。
羽毛束冠遗风延续到现在。现今的哈萨克族少女喜欢佩戴自己手工绣饰的圆顶帽冠,镶上串珠,绣上花卉图案,帽顶部插羽毛作为吉祥物,将其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审美情趣集于一身。
鞋履 鞋是现今的称谓,《释名》载:“着时缩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则舒解。”是指一种鞋面开缝、系带的、多用生皮制成的鞋。实际上,穿在脚上的、与地面接触的“足衣”都统称“鞋”。“履”即现今称谓的鞋,汉代以后称“鞋”为“履”,而“鞋”则是自唐代延续至今的称谓。《释名·释衣服》曰:“履,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
靴是古履的一种样式。史书记载:“鞮,履也,胡人速胫,谓之络鞳。”《中华古今注》曰:“靴者,盖古西胡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靴”为高靿皮鞋,是北方少数民族主要穿着。它便于跋山涉水,翻越雪岭,适合游牧人乘骑和抵御寒冷之用。
新疆的古代墓葬中,曾发现短靿的与高靿的皮靴,与古籍记载基本相符。出土的还有高靿毡靴,显出其地域性特征。反映了当时的鞣革、脱脂工艺和制毡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腰带 腰带是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饰物,因其所穿着的衣饰多长及过膝的衣袍且多无纽扣,因此腰带起着保暖与紧身的作用。腰带不仅方便于游牧民族骑马、放牧、狩猎,且可在腰带上附系若干小环扣,挂上必需的小物件。腰带的款式有宽有窄,宽的用皮革制成,窄的用毛织物缠成双股或多股状,中间系纽成结。腰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鞢。古籍记载:〓鞢七事,即火石、鼻烟壶、小刀、砺石、针筒、解结锥和荷包等七件。它是古代草原文化圈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必不可少的饰物。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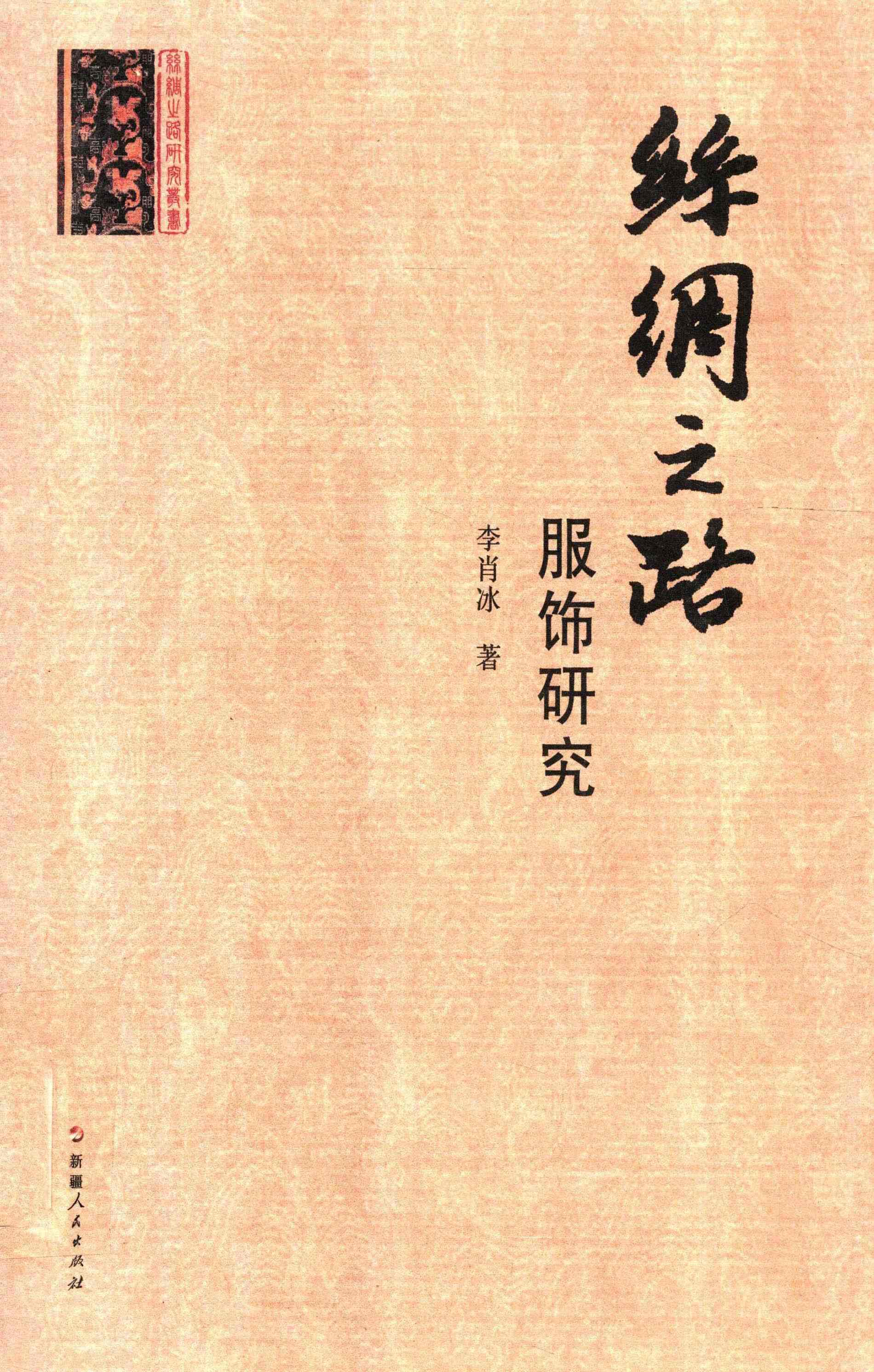
《丝绸之路服饰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正由于它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且展现出浓郁的民族衣饰风格,才使它独树一帜,别具风采。一部西域服饰文化的著成,应涵盖从古代到近代各族人民巨大的创造性。每一处墓葬出土的衣冠服饰珍品,每一幅壁画人物衣饰的穿着,以及雕刻衣装的草原石人、岩画、木雕、泥俑、塑像等人物的衣冠服饰造型,都足以说明西域服饰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载着它的兴衰,凝聚着先民的精魂。诚然,我们难以认定衣饰形式的确切年代,但却可以据此追溯到它的童稚时期,那经历了从人类混沌意识中的原始阶段,逐渐过渡到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