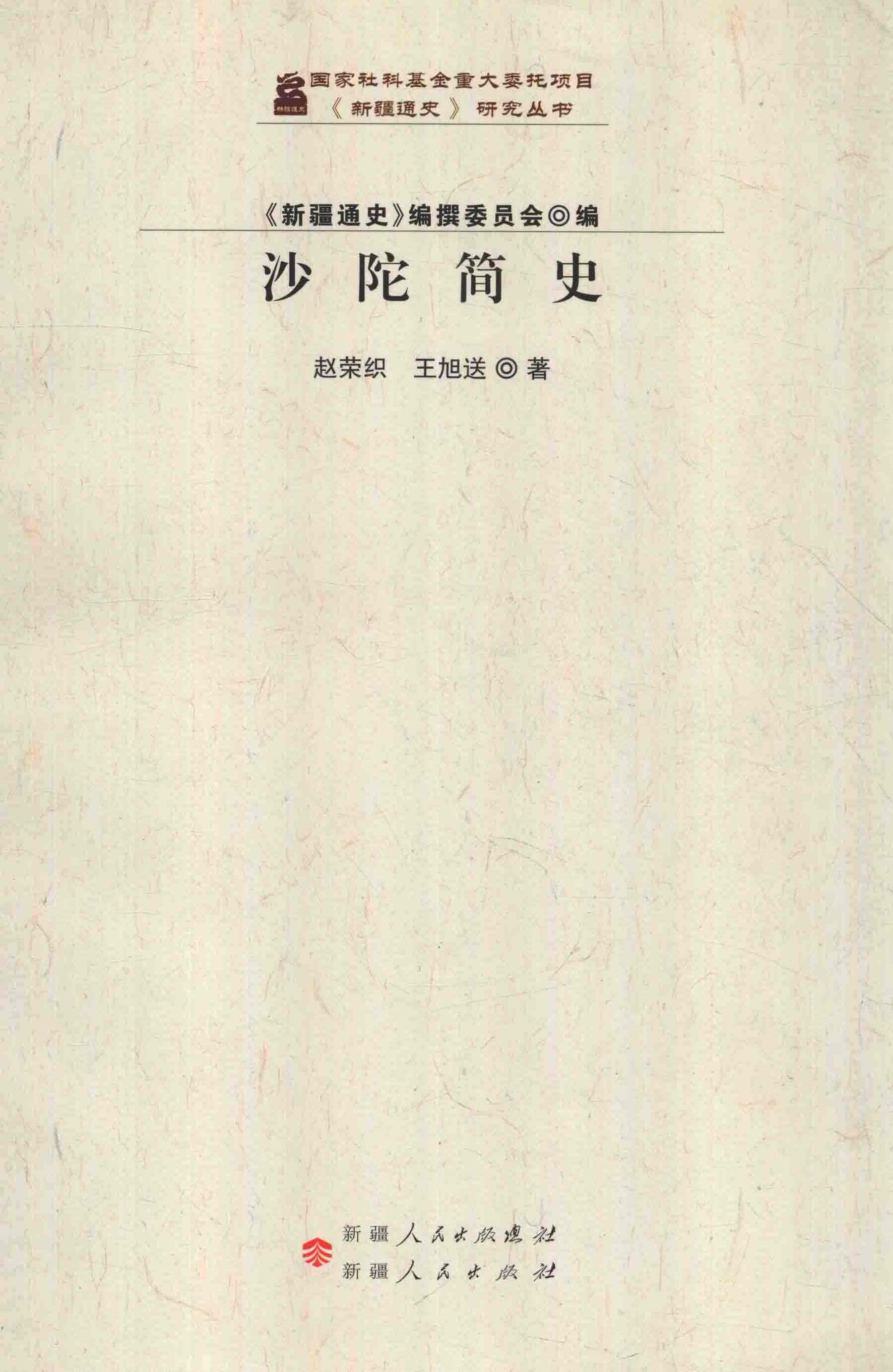内容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最终实现汉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比较典型的有匈奴自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汉化,鲜卑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以及满族人在清朝入关后的汉化。汉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面对先进的封建文化而做出的必然历史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①本文拟对沙陀的汉化做一全面勾勒。
沙陀于唐德宗贞元(785—804年)中因吐蕃急攻北庭加之回纥征求无厌,遂以部族七千帐依附吐蕃,并与之共陷北庭,之后,“吐蕃徙其部甘州,以尽忠为军大论”。迁入甘州之后,每逢“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为之冲锋陷阵。然而,后来“回纥取凉州,吐蕃疑(朱邪)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於河外,举部愁恐”。在遭吐蕃猜忌举部愁恐的情况下,沙陀遂揭橥东归大唐。
沙陀的内迁跨越了本质上殊异的两种生态与经济文化类型,即从相对寒冷西北的游牧、狩猎文化区跨入相对温暖、湿润的农耕文化区。内迁后的沙陀面临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生存环境:作为“夷狄”,内迁之前他们生活在“彼自安其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昏宦。驰突无恒之素”的环境之中;内迁之后则生活于“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昏姻仕进之可荣”①的新环境之下。生存环境的置换,使得沙陀不得不摈弃原有的游牧习俗,逐渐适应中原发达的封建农耕社会环境。由此,沙陀逐渐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并最终融入汉族当中。
一、内迁之前沙陀的社会状况
内迁之前沙陀依托东部天山地区广袤的草原,过着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衣皮毛”的游牧生活,他们创造的是典型的游牧文化。对于沙陀内迁前的社会生活,相关史书略有记载,同时我们亦可从沙陀内迁后所残存的一些游牧经济意识及游牧民族的习俗追溯到其内迁前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
沙陀内迁前主要从事畜牧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新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以处月、处密、姑苏、歌逻禄、卑失五姓叛..诏何力为弓月道大总管,率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统秦、成、岐、雍及燕然都护回纥兵人万讨之。处月酋硃邪孤注遂杀招慰使果毅都尉单道惠,据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数道,攀藟而上,急攻之..虏渠帅六十,俘斩万余,牛马杂畜七万,取处蜜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②显庆元年(656年)八月丙申,“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获刺颉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③。唐朝对沙陀的两次大的战役,每次均俘获万计甚至七万的牲畜,足见当时沙陀畜牧业之发达。在沙陀的畜牧业生产中,养马业尤为发达。《唐会要》记载,居住于西北地区各民族,向以多马著称。各族牧马,为了避免走失、混杂,都于马的特定部位上烙有印记。沙陀牧养的马,称之为“沙陀马”,印记为类似“B”的符号。沙陀的骁勇善战应与其善牧马密不可分。
沙陀虽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但从史料来看,部分沙陀统治阶层可能已经从事定居生活。如《新唐书·沙陀传》记载:“(乙毗)咄陆寇伊州,引二部兵围天山,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走之,拔处月俟斤之城。”①由此可见,沙陀已经建有城池,供统治阶层居住,但这仅属少数,多数沙陀人可能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据《旧唐书·焉耆传》记载,贞观十二年(638年)十二月,“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略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②。处月既攻陷焉耆,却不知经营,仅“略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可见其尚不知从事定居生活。
据史料记载,内迁前沙陀还过着人类社会原始阶段所特有的贵少贱老及男女混杂的生活。《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同。”③沙陀这种具有游牧社会特色的生活亦同样存在于匈奴社会。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④由此可见,内迁前沙陀尚处于低层次的氏族社会阶段,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沙陀仍然过着男女杂居生活;同时,为了保护有限的生活资源,沙陀内部利益至上,重视能够提供利益的青壮年,轻视老弱病残。
关于沙陀早期的一些习俗,我们可以从其内迁后的一些残存习俗略见一斑。首先,祭祀突厥神。《旧五代史·唐庄宗纪第六》载,同光二年(924年)七月,庄宗“幸龙门之雷山,祭天神,从北俗之旧事也”;该书同卷还记载,是年十一月,庄宗还在开封“祭蕃神于郊外”;《新五代史·明宗纪》载,六月庚子,明宗“幸白司马坡,祭突厥神,夷狄之事也”。祭天神也是突厥人重要的祭祀活动;《周书·突厥传》载,“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崇拜天神是突厥族的传统信仰,突厥语呼天位tangri,突厥儒尼文碑铭中多次提及天神。如《毗伽可汗碑》记载:“像天一样的,天生的突厥毗伽可汗”(东一行);“由于上天的保佑和由于我的努力,突厥部众胜利了”(东33行);“由于上面上天和神圣水土和我祖可汗在天之灵不悦,九姓铁勒部众弃其水土而去唐”(东36行)。又如,《暾欲谷碑》记载:“由于上天赐给(我)智慧,我敦促(他)为可汗”(6行);“上天保佑,我没有让全副武装的敌人在突厥部众中驰骋”(53行)。沙陀由于较早被西突厥征服,成为其别部,因此信奉突厥的天神。
第二,扑祭。扑祭即杀马而祭,这是突厥葬俗中的一种重要现象①,即使是内迁至中原有着相当汉化程度的突厥人,他们依然继承着这种葬俗。《唐文拾遗》卷一六收录有王知敬为内迁中原的突厥大将哥舒季通撰写的《大唐左监门卫副率哥舒季通葬马铭》,云:“爰有名骢,厥号云花,声高天厩,产重流砂,盖武德中尝以赐故越州刺史都督诸军事哥舒府君者也。府君既已就义戈行,维是名骢,亦从歼焉。孤子左监门卫副率季通,乌号血竭,鸡耸骨立,永怀罔极之悲,思广推恩之义,乃图厥形,葬之坟隅。肇锡嘉铭,用□雄特。其词曰:粤维泰运,异质斯生。坤元毓德,天驷流精。惟彼云花,驰声御枥。龙文表瑞,凤翥开绩。於赫府君,丕茂肤功。帝曰赉汝,骏尾方瞳。越国过都,逐星激电。体健腾骧,姿雄顾盼。绌力著德,合志同心。策勋奏凯,照古凌今。夫何不永,阳九当厄。倏□霜锋,早坠逸翮。瓦鸳羞全,缑鹤并飞。存亡既偕,神魄攸依。矫矫精忠,垂光丹□。翩翩者骓,扬华骥尾。云花顾影,杨叶嘶风。”②
内迁中原之后的沙陀人同样继承了草原游牧民族的这种特殊的马殉的祭祀方式。《新五代史·晋出帝纪》记载,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使右骁卫将军石德超以御马二,扑祭于相州之西山,用北俗礼也”。同年七月,皇祖母刘氏崩,“使石德超扑马于相州之西山”。杀牛马祭奠死者应源于游牧习俗。《周书·突厥传》载:“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牛马,陈于帐前,祭之。”沙陀此习俗当来源于突厥习俗。
其三,以箭为信。突厥族有以箭为信的习俗,《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征发兵马,科税杂畜”,用一金链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突厥的箭相当于中原的印信,可汗可以此对酋长发号施令,由此“西突厥分为十部,每部酋长各赐一箭,谓之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禄部,置五大啜;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通谓之十部落”。沙陀内迁之后,这一习俗也被保留下来。《旧五代史·晋高祖纪二》云:“遣内班史进能押信箭一对,往滑州赐符彦饶。”《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四》云:“传箭,番家之信符也,起军令众则使之。”
关于沙陀的这种习俗,《新五代史》有着较为深入的分析:“(霍)彦威徙镇平卢。朱守殷反,伏诛,彦威遣使者驰骑献两箭为贺,明宗赐两箭以报之。夷狄之法,起兵令众,以传箭为号令,然非下得施于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彦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礼,动多此类。”①
第四,收继婚。作为原始社会群婚制的残余,收继婚在边陲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如《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诸嫂”;《三国志·魏书·乌丸传》记载,乌桓“父兄死,妻后母、报(原作“执”,误。引注。)嫂。若无报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汉书·匈奴传》上记载,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父死,妻群母、后母,这种不同辈分之间的婚配,是一种典型的超越“乱伦禁忌”规限的血缘婚或集团内群婚的遗续;而兄死报嫂,即兄亡后,弟有娶其寡嫂的特权,则是与氏族外群婚及氏族中的财产继承权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收继婚直到我国近代仍然在南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流行。《新五代史·晋家人传第五》记载:“出帝皇后冯氏,定州人也。父濛,为州进奏吏,居京师,以巧佞为安重诲所喜,以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欢甚,乃为重胤娶濛女,后封吴国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悦之。高祖崩,梓宫在殡,出帝居丧中,纳之以为后。是日,以六军仗卫、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庄,见于高祖影殿。群臣皆贺。帝顾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任大庆。’群臣出,帝与皇后酣饮歌舞,过梓宫前,酹而告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绝倒,顾谓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后与左右皆大笑,声闻于外。”重胤,晋高祖之弟,对出帝来说是为叔父,冯氏则为叔母,出帝居丧中公然娶冯氏为妻,欢笑自若。胡三省斥责出帝:“斩焉衰絰之中,触情纵欲以乱大伦,又从而狎侮其先,何以能久!”这种收继婚虽为中原传统文化所不容,然其在周边突厥、回纥诸族中颇为常见。由此可见,沙陀虽定鼎中原汉化极深,但其早期游牧社会中的收继婚制仍有孑遗。
第五,妇人参政。在氏族社会早期,由于女子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女子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内迁前的沙陀基本上处于氏族社会的父系阶段,但是母系时期妇女执政的习俗还是有孑遗。这种习俗一直到沙陀内迁之后还偶有所见。如,天复元年朱全忠大举攻太原,沙陀军大败。李克用听信李存信之言,欲北投鞑靼。李国昌之妻刘氏语克用曰:“闻王欲委城入蕃,审乎?计谁出?”曰:“存信等为此。”刘曰:“彼牧羊奴,安办远计。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效之?且王顷居鞑靼,危不免。必一朝去此,祸不旋跬,渠能及北虏哉?”李克用醒悟,乃止①。又,后唐庄宗时期皇太后、皇后与皇帝差不多处于均等的势力地位:“是时皇太后诰,皇后教,与制敕交行于藩镇,奉之如一。”②《贞观政要》卷九记载,“北狄风俗,多由内政”,在突厥、回鹘之中,可敦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沙陀内迁之后,很明显保留了草原游牧民族早期母权制的遗风。
第六,拥有本民族所独有之语言。沙陀民族之语言不得而知,但是其拥有本民族之语言当确凿无疑,而且这种语言在其内迁后长期存在。《新唐书·逆臣下》载:“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壁荆门,使沙陀以五百骑钉辔藻鞯望贼阵纵而遁,贼以为怯。明日,诸将乘以战,而马识沙陀语,呼之辄奔还,莫能禁。”③这说明,沙陀语在沙陀内部还普遍流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沙陀政权的建立。《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一》载,明宗与契丹阿保机战,“以边语谕之曰:‘尔辈非吾敌,吾当与天皇较力耳’”,“边语”当然是指沙陀在代北时所用的沙陀语;《旧五代史·康福传》载:“福善诸蕃语,明宗视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谘访时之利病,福即以蕃语奏之。”①康福系出昭武九姓,昭武九姓早在沙陀内迁初期就以融入沙陀部,故其所云“蕃语”即为沙陀语。另,后唐闵帝李从厚,乃明宗第三子,其“小字菩萨奴”②,“菩萨奴”当时从沙陀语音译而来,亦说明直至沙陀在中原建立政权,其民族语言仍有所保留。
第七,轻视品级、尊卑、长幼之别。后唐末帝李从珂在位时,对石敬瑭猜疑颇大,石敬瑭亦疑心重重,二人矛盾日益尖锐。后来,石敬瑭起兵造反。他一面在朝廷内部从事策反活动,一面由掌书记桑维翰起草奏章,向契丹求援:请称臣,以父礼事契丹,约事捷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契丹。都押牙刘知远对父事之礼甚为不满,云:“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③对此,石敬瑭并不在意。石敬瑭此举显示,他的胡人气质并未消失,对契丹称臣、称子并不以为耻辱,而其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他没有接受汉人品级、尊卑、长幼的观念,视契丹为同类,未有夷夏之分④。
中国古代贵中华、贱夷狄,石敬瑭此举自然得不到汉人支持。石敬瑭的后晋政权是在契丹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石敬瑭自然对契丹人毕恭毕敬。但是,就在后晋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就发生了汉人吴峦闭门不迎契丹人之事。天福二年(937年)二月,“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还镇。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推峦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⑤。这件事说明,石敬瑭的这种胡人气质与汉人的“礼义之俗”背道而驰,因而遭到了汉人的抵触。
沙陀内迁中原并建立政权之后保留的某些游牧习俗,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沉迷畋猎,不知体恤稼穑之苦。后唐庄宗虽定鼎中原,然仍不忘沙陀之游牧生活,曾云:“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①后唐庄宗残存的游牧经济意识即使在即位后仍然经常付诸实际行动,史载:“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幸得伶人敬新磨知:“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诸伶共唱和之。”最终“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资治通鉴》记载:帝屡出游猎,从骑伤民禾稼,洛阳令何泽付于②。另,“丛薄,俟帝至,遮马谏曰:‘陛下赋敛既急,今稼穑将成,复蹂践之,使吏何以为理,民何以为生!臣愿先赐死。’帝慰而遣之。”③庄宗不注重农业生产,加之在位期间水旱灾害严重,仓廪空竭,故其统治很快结束。
二、沙陀汉化之表现
沙陀内迁之后失去了游牧经济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虽然保留了其原有的游牧生活的一些习俗,但是为了立足中原,不得不适应中原的生存模式。随着沙陀内迁日久,与中原政权接触日深,沙陀汉化日渐加深,并最终融入汉族当中。沙陀的汉化,既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潜移默化,又有制度上的主动靠拢。沙陀汉化的表现,我们在分析沙陀崛起及其代梁原因分析时有所表述,该部分从略。下面我们简要分析沙陀汉化的一些表现。
(一)学习儒家思想。
沙陀内迁直至李克用时期,尚无其接受儒家思想的直接证据,然到李存勖时期,史书开始有明确记载。《旧五代史·庄宗纪第一》记载,李存勖“十二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④;后唐明宗李嗣源一生戎马倥偬,未暇读书,但却特别关注经典。他曾戒秦王从荣云:“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见判官论说经义,虽不深达其旨,大约令人开悟。今朝廷有正人瑞士,可亲附之,庶几有益。吾见先皇在藩时,爱自作歌诗。将家子文非素习,未能尽妙,讽于人口,恐被诸儒窃笑。吾老矣,不能勉强于此,唯书义尚欲耳里频闻。”①后唐闵帝李从厚,“髫龀好读《春秋》,略通大义,貌类明宗,”其先回鹘人,后加入沙陀尤钟爱②。沙陀名将张从训,集团,然其喜“读儒书,精骑射,初为散员大将。天佑中,辖沙陀数百人,屯壶关十余岁”③。石敬瑭之子石重信则“为人敏悟多智而好礼”④。北汉主刘钧,“性孝谨,”幼而颖异,颇好学,工书⑤。更有甚者,沙陀内部不乏博学鸿儒之才。史载,出身沙陀三部落的“(史)匡翰刚毅有谋略,御军严整,接下以礼,与部曲语,未尝称名,历数郡皆有政声。尤好《春秋左氏传》,每视政之暇,延学者讲说,躬自执卷受业焉。时发难问,穷于隐奥,流辈或戏为“史三传。既自端谨,”沙陀内迁之后,耳濡目不喜人醉⑥。这些均已表明,染,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有的人甚至在经学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
(二)接受中原文化
首先,接受中原宗教。沙陀内迁后,对中原盛行的佛教、道教等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佛教早在佗钵可汗时期就已传入突厥人中⑦。内迁前沙陀人是否信奉佛教,史未明载,不得而知,然沙陀内迁后虔信佛教则毋庸置疑。首先,沙陀首领扶持佛教事业发展,《宋高僧传》卷七《后唐定州开元寺贞辩传》记载:“(贞)辩负笈抵太原城听习,时中山王氏与后唐封境相接,虞其觇间者,并州城内不容外僧。辩由次驱出,遂于野外古塚间宿。会武皇帝畋游,塚在围场中,辩固不知。方将入城赴讲,见旌旗骑卒,缩身还入穴中。武皇疑,令擒见,问其故,遂验塚中,敷草座,案砚疏钞罗布,遂命入府供养。时曹太后深加仰重,辩诉于太后曰:‘止以学法为怀,久在王宫不乐,如梏械耳。’武皇纵其自由,乃成其业。”沙陀人不但扶持佛教事业,而且本身十分崇信佛教。《册府元龟》卷五十二《帝王部·崇释氏二》记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九月,敕:天下应有本朝所造寺观,宜令所在长吏取寺司常住物添修,至万寿节日,须毕其功。”《宋高僧传》卷二十七《后唐五台山王子寺诚惠直传》记载:“(后唐)武皇躬拜(诚惠),感谢慈悲,便号国师矣..庄宗即位,诏赐紫衣,次宣师号。帝复宣厥后,再朝天阙,更极显荣。受恩一月,却返五台。”另,其时有僧名诚惠者,“初于五台山出家,能修戒律,称通皮、骨、肉三命,人初归向,声名渐远,四方供馈,不远千里而至者众矣。自云能役使毒龙,可致风雨,其徒号曰降龙大师。京师旱,庄宗迎至洛下,亲拜之,六宫参礼,士庶瞻仰,谓朝夕可致甘泽。祷祝数旬,略无征应。或谓官以祈雨无验,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及卒,赐号法雨大师,塔曰‘慈云之塔’”①。
庄宗之后,明宗皇帝亦痴迷佛教,《册府元龟》卷五十二《帝王部·崇释氏二》记载:“(后唐)长兴四年七月,命中使押绢五百匹施五台山僧斋料”;《旧五代史》卷六十七《赵凤传》记载,当时“有僧自西国取经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渍皴裂,进于明宗..时宫中所施已逾数千缗”。
后晋石敬瑭亦对佛教有浓厚兴趣,史载,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十二月,石敬瑭诏命,把他河阳旧宅(“潜龙旧宅”)改为开晋禅院,邢州旧居改为“广法禅院”以弘扬佛教②。安守忠,字信臣,并州晋阳人,其父审琦,则安守忠亦属沙陀人。守忠“终身不畜妓妾,而喜佞佛”③。甚至,有些驰骋疆场、戎马倥偬的武将也深谙佛理,如沙陀名将张从训之祖父张君政“识蕃字,通佛理”④,实属难能可贵。
此外,李克用家族中还有看破红尘,遁入佛门者。李克用第三子李存霸即属此例。史载:“存霸闻京师乱,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从弁不去。存霸乃剪发、衣僧衣,谒符彦超曰:‘愿为山僧,冀公庇护。’彦超欲留之,为军众所杀。”①
在佛教信仰中,沙陀人对毗沙天王(即“毗沙门天王”)的信仰情有独钟。毗沙天王是佛教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天王,他是印度古神话中北方的守护神,也是施福神。唐宋时期,毗沙天王演变成武神,香火非常旺盛。当时,无论朝廷还是民间,对“毗沙天王”的信仰十分盛行。在沙陀的统治者中,有多人钟情于毗沙天王信仰。首先是李克用,史载:“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济民之志,无何井溢,故未察其祸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与仆交卮谈。’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隐然出于壁间,见者大惊走,惟武皇从容而退,由是益自负。”②其二是后唐末帝李从珂,史载李从珂“在籓时,有相士言帝如毗沙天王,帝知之,窃喜。及即位,选军士之魁伟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卫,因诏诸道造此甲而进之”“宫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门③。其三是石敬瑭,史载:晋阳有北宫,天王,帝(石敬瑭)曾焚修默而祷之。”④
除佛教之外,沙陀对其他宗教亦表现出浓厚兴趣。后晋创立者石敬瑭对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史载,天福五年(940年)五月癸亥,石敬瑭赐予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通元先生”,“是时帝(石敬瑭)好《道德经》,尝召荐明讲说其义,帝悦,故有是命。寻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版,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⑤。
其次,沙陀内部出现了许多文学艺术修养很高的人。在沙陀内部,汉文学艺术造诣最高的当属后唐庄宗,《五代史补》记载:“庄宗为公子时,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⑥后唐明宗子从荣亦颇具文学修养,他尤喜诗歌。《册府元龟》卷二百七十云:“秦王从荣为诗,与从事高辇等更相唱和,自谓章句独步于一时。有诗千余首,号曰《紫府集》。”(《五代史补》卷二亦载此事)。史圭,“常山人也,其先与王武俊来于塞外”。可见,史圭亦属边陲夷狄,后入沙陀部。史载“圭好学工诗”①,也颇具文学造诣。
沙陀内迁后对中原音乐舞蹈亦颇感兴趣。沙陀内迁后相当长时期内一直保持着本民族传统的音乐舞蹈,直至石敬瑭即位,这种局面才打破。《旧五代史·乐志》记载:“古之王者,理定制礼,功成作乐,所以昭事天地,统和人神,历代已来,旧章斯在。洎唐季之乱,咸、镐为墟;梁运虽兴,《英》、《茎》扫地。庄宗起于朔野,经始霸图,其所存者,不过边部郑声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泯绝。当同光、天成之际,或有事清庙,或祈祀泰坛,虽簨〓犹施,而宫商孰辨?遂使磬襄、鼗武,入河、汉而不归;汤濩、舜韶,混陵谷而俱失。洎晋高祖奄登大宝,思迪前规,爰诏有司,重兴二舞。”②可见,石敬瑭登基之后,作为中原雅乐的“二舞”才占据主导地位。然沙陀本民族的音乐舞蹈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史载后晋出帝石重贵“自期年之后,于宫中间举细声女乐,及亲征以来,日于左右召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常谓侍臣曰:‘此非音乐也’”③。可见,出帝时胡、雅音乐并行,然胡不压雅,并不被认可为“音乐”。
第三,采用汉姓。沙陀内迁之后,特别是被赐李姓之后,姓名多用单姓,这也是其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胡语语意和音节与汉语不同,故胡姓大部分为多音节词,被汉人称为复姓。胡族用复姓使胡汉交往多有不便。如通婚,汉人即不喜胡之复姓,《北史》卷二十八《陆俟传附陆叡传》云,叡“年十余岁,袭爵平原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时孝文帝尚未改北人姓,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沙陀内迁之后,为立足中原,获得中原士人认可,遂自行改胡姓为汉姓,多为单姓,而且非常彻底,这在内迁夷狄当中实属少见。
(三)实行中原典制
沙陀对中原典制的采用,首先表现在对族望、地望及国号的选择上。
为构建其政权的合法性,沙陀政权在族望、地望及国号的选择上煞费苦心。沙陀所建立的几个政权均将地望更改为中原某地,在族望上浪托汉族先人为其远祖,在国号选择上则力求攀缘前代王朝。如,后唐建立者李存勖祖上朱邪赤心因平定庞勋起义有功,“入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名国昌,仍为郑王房”①。其后朱邪氏便以唐室后裔自居,至李存勖建国,遂定国号为“大唐”,以明其政权乃唐朝基业之延续;石敬瑭建立后晋之后,自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子孙流泛西裔②;刘知远建后关辅乱,”汉后,自称“四代祖讳湍,帝有天下,追尊为明元皇帝”,而刘湍乃东汉明帝刘昞的后代③。由此,刘知远便与东汉王朝攀上了关系,选择“汉”为国号既顺理成章,同时又使政权具有了正统性。
沙陀定鼎中原后,几个政权均明确宣布采用唐朝文物、典制实行统治。后唐庄宗即位后即下诏曰:“惩恶劝善,务振纪纲;激浊扬清,须明真伪。盖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必按旧章,以令多士。而有志萌僭窃,位忝崇高,累世官而皆受唐恩,贪爵禄而但从伪命,或居台铉,或处权衡,或列近职而预机谋,或当峻秩而掌刑宪,事分逆顺,理合去留。”④庄宗俨然以唐王朝的继承人自居,视唐朝典制为圭臬。后晋高祖石敬瑭于天福元年(936年)闰十一月甲申,夺取后唐政权,“车驾入内,御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⑤。天福三年二月又下诏,云:“朝廷之制,今古相沿..宜依唐礼施行。”⑥后汉高祖刘知远“昔莅戎籓,素亏物望,洎登宸极,未厌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来苏之望”⑦,无政绩可言,然其为巩固政权,遂附东汉刘氏之后,“追崇六庙”,特以“国号为大汉”⑧,其施政亦沿用中原典制。
为了表明其政权的正统性,后唐统治者甚至对后梁改制中不合唐制者,悉令革除。如后梁删改唐律令格式,后唐建立后,御史台奏:“硃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廷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庄宗“从之”①。
三、沙陀汉化评价
关于沙陀的汉化,学界观点不一,概其要者,重要有二:其一,沙陀内迁直至建立政权时期汉化程度不深,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持此种观点。他认为,“建立朝廷的人,都是半开化的、带游牧人习气的武夫,非常好战好杀,不知道要有所以立国的政治。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②;其二,沙陀内迁及建立政权时期完全汉化。陶懋柄认为,沙陀政权“与汉族地主所建的王朝并无区别”③。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认为,“沙陀自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随贺鲁降唐以来,一直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联系,逐渐汉化。李存勖奉唐高祖李渊为祖;刘知远则奉汉高祖刘邦为祖,说明沙陀已完全融合于汉族之中”④。
我认为,以上观点均有失偏颇,沙陀汉化应辩证去看。沙陀自内迁之后,为立足中原,主动吸收接纳汉人加入沙陀集团,并努力学习中原文化,最终崛起河东;定鼎中原后,沙陀为了巩固其统治,又继承唐制,主动学习唐朝的立国之本、治国之道。沙陀内迁并建立政权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逐渐改变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过程,至五代时,沙陀已基本上实现了汉化。然而,在沙陀内迁直至建立政权过程中,其游牧经济观念、游牧文化风俗一直不同程度地保持着。
沙陀自代北时期的较少染濡汉文化到全面汉化是一个比较漫长的阶段。《宋史》当中记载有宋初的几个沙陀历史人物,虽寥寥无几,亦清晰可辨,说明宋初时沙陀人仍以其独有的文化特征为世人所知,它还没有完全融合于汉族。宋的中后期不再见有沙陀人的记载,说明此时沙陀人已全面汉化,完全融合于汉族当中。因此沙陀人完全汉化融入汉民族应在宋的中期以后。
沙陀内迁后的汉化有如下特点:
第一,沙陀内迁及其汉化带动了一大批边陲民族的汉化。沙陀内迁之后,因其骁勇善战,很快吸引了一大批边陲民族的加入。在内迁初期,沙陀就吸引了昭武九姓胡人的加入,且其数量远远超过沙陀,由此形成“沙陀三部落”。其后,沙陀部继续吸引边陲部落的加入,如回鹘、吐谷浑、鞑靼等,数量相当可观。沙陀奉旨镇压黄巢起义就是借助于这些边陲民族的鼎力相助。天祐十五年秋八月,李存勖与后梁夹河而战之时,“大阅于魏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曜,师旅之盛,近代为最”①。可见,沙陀内部边陲民族人数之巨,沙陀的汉化亦是这些边陲民族的汉化。沙陀政权建立之后,对其他少数民族没有采取排斥、贬抑的态度,而是给予与汉民同等的地位。如,后唐政权建立之后,对少数民族的住房、盖房、买卖房舍、田地以及参加科举等,都有条文规定,对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给予正式的承认。这些英明的措施使少数民族获得了和汉族同等的发展机遇,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值得大写特写的事情②。
第二,在沙陀政权统治核心以汉人为主。沙陀建立的三朝一国,均未对汉族采取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其用人不分蕃汉,实际上起决策作用的人物都是汉人,始终未曾形成一个以沙陀贵族集团为统治核心的统治力量,其华夷关系呈现良性发展趋势,这与十六国、北魏及此后的辽、夏、金、元、清情形大不相同。据统计,《新五代史》记载的在后唐政府中任职的147名官员中,汉族90人,少数民族10人,其他不明民族成分47人;在后晋任职的85名官员中。汉族73人,少数民族6人,不明民族成分者6人;在后汉任职的39名官员中,汉族33人,少数民族3人,不明民族成分者3人。这几个政权大量任用汉族官员,并且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身居高位,起决策作用,在权力分配上没有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对汉族没有歧视的现象,这在其他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中是罕见的。
第三,汉化主动性、积极性高涨。建立政权的沙陀上层,都有积极得到汉族认同的倾向。他们在内迁之后,都已取用汉族姓氏,除后唐李氏是唐朝酬功所赠之外,如石敬瑭之石氏,刘知远之刘氏,俱无来历,显系自认。建立政权后,又与汉族封建王朝的所谓正统加以联系,如李存勖的后唐,自命延续唐祚,以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加上李存勖之曾祖及祖、考,立七庙于太原;刘知远的后汉,则远绍两汉,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以表明自己的政权渊源有序,确属正统。唯石敬瑭的姓氏于史不彰,无源可溯,只好因地立号。沙陀人康福自认汉人,以他人称之蕃人为耻:“福无军功,属明宗龙跃,有际会之幸,擢自小校,暴为贵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饫腹,与士大夫交言,懵无所别。在天水日,尝有疾,幕客谒问,福拥衾而坐。客有退者,谓同列曰:‘锦衾烂兮!’福闻之,遽召言者,怒视曰:‘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因叱出之,由是诸客不敢措辞。复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①与此相应的,后唐政治制度全沿唐制,认为“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完全按照汉族封建王朝的模式进行统治,后晋、后汉踵行不改。
第四,最高统治者广与汉族通婚。历史上许多边陲民族入主中原后,其最高统治阶层严格限制华夷间通婚,如清朝施行“满汉不通婚”,严惩违者,甚至不惜杀头。然沙陀于此最为开放,沙陀皇帝的后妃大部分是汉族出身,官员和百姓中不同民族间通婚的现象亦属普遍,血统性的民族融合从未受到限制。
第五,许多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识较为肤浅,尚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晚唐五代乃干戈扰攘之时代,攻伐相尚,勇武是崇,故沙陀统治集团都是依靠冲锋陷阵而崭露头角,最后立基开国的。值此之故,沙陀统治集团许多人的汉化只是低层次的,感性认识的方面居多。他们熟稔汉人一些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观念,自觉模仿效法,然而对汉文化的一些深层次上的东西知之甚少。石敬塘、刘知远自不必论,因二人出身低微,少年从军,没有接受汉文化教育的条件;后唐庄宗李存勖出生于沙陀最高统治者之家,条件优越,能够接受教育,但他的汉文化素养也很有限,他也只是“稍习《春秋》,通大义”而已;而明宗嗣源即位之后,臣下霍彦威、孔循等进谏,请改国号,而明宗竟不知“何为正朔”①;明宗登基七年尚不知封建皇位继承制度,不知预立储君。太仆少卿何泽上表请立太子,竟以为是迫他让位,以至于“览表泣下”②。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云,“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③,他们的汉化程度与北魏孝文帝相比,实难以望其项背。长期的割据和战乱,致使民族文化交流受到影响,这直接导致了沙陀汉化的不彻底。
沙陀于唐德宗贞元(785—804年)中因吐蕃急攻北庭加之回纥征求无厌,遂以部族七千帐依附吐蕃,并与之共陷北庭,之后,“吐蕃徙其部甘州,以尽忠为军大论”。迁入甘州之后,每逢“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为之冲锋陷阵。然而,后来“回纥取凉州,吐蕃疑(朱邪)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於河外,举部愁恐”。在遭吐蕃猜忌举部愁恐的情况下,沙陀遂揭橥东归大唐。
沙陀的内迁跨越了本质上殊异的两种生态与经济文化类型,即从相对寒冷西北的游牧、狩猎文化区跨入相对温暖、湿润的农耕文化区。内迁后的沙陀面临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生存环境:作为“夷狄”,内迁之前他们生活在“彼自安其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昏宦。驰突无恒之素”的环境之中;内迁之后则生活于“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昏姻仕进之可荣”①的新环境之下。生存环境的置换,使得沙陀不得不摈弃原有的游牧习俗,逐渐适应中原发达的封建农耕社会环境。由此,沙陀逐渐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并最终融入汉族当中。
一、内迁之前沙陀的社会状况
内迁之前沙陀依托东部天山地区广袤的草原,过着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衣皮毛”的游牧生活,他们创造的是典型的游牧文化。对于沙陀内迁前的社会生活,相关史书略有记载,同时我们亦可从沙陀内迁后所残存的一些游牧经济意识及游牧民族的习俗追溯到其内迁前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
沙陀内迁前主要从事畜牧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新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以处月、处密、姑苏、歌逻禄、卑失五姓叛..诏何力为弓月道大总管,率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统秦、成、岐、雍及燕然都护回纥兵人万讨之。处月酋硃邪孤注遂杀招慰使果毅都尉单道惠,据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数道,攀藟而上,急攻之..虏渠帅六十,俘斩万余,牛马杂畜七万,取处蜜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②显庆元年(656年)八月丙申,“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获刺颉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③。唐朝对沙陀的两次大的战役,每次均俘获万计甚至七万的牲畜,足见当时沙陀畜牧业之发达。在沙陀的畜牧业生产中,养马业尤为发达。《唐会要》记载,居住于西北地区各民族,向以多马著称。各族牧马,为了避免走失、混杂,都于马的特定部位上烙有印记。沙陀牧养的马,称之为“沙陀马”,印记为类似“B”的符号。沙陀的骁勇善战应与其善牧马密不可分。
沙陀虽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但从史料来看,部分沙陀统治阶层可能已经从事定居生活。如《新唐书·沙陀传》记载:“(乙毗)咄陆寇伊州,引二部兵围天山,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走之,拔处月俟斤之城。”①由此可见,沙陀已经建有城池,供统治阶层居住,但这仅属少数,多数沙陀人可能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据《旧唐书·焉耆传》记载,贞观十二年(638年)十二月,“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略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②。处月既攻陷焉耆,却不知经营,仅“略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可见其尚不知从事定居生活。
据史料记载,内迁前沙陀还过着人类社会原始阶段所特有的贵少贱老及男女混杂的生活。《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同。”③沙陀这种具有游牧社会特色的生活亦同样存在于匈奴社会。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④由此可见,内迁前沙陀尚处于低层次的氏族社会阶段,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沙陀仍然过着男女杂居生活;同时,为了保护有限的生活资源,沙陀内部利益至上,重视能够提供利益的青壮年,轻视老弱病残。
关于沙陀早期的一些习俗,我们可以从其内迁后的一些残存习俗略见一斑。首先,祭祀突厥神。《旧五代史·唐庄宗纪第六》载,同光二年(924年)七月,庄宗“幸龙门之雷山,祭天神,从北俗之旧事也”;该书同卷还记载,是年十一月,庄宗还在开封“祭蕃神于郊外”;《新五代史·明宗纪》载,六月庚子,明宗“幸白司马坡,祭突厥神,夷狄之事也”。祭天神也是突厥人重要的祭祀活动;《周书·突厥传》载,“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崇拜天神是突厥族的传统信仰,突厥语呼天位tangri,突厥儒尼文碑铭中多次提及天神。如《毗伽可汗碑》记载:“像天一样的,天生的突厥毗伽可汗”(东一行);“由于上天的保佑和由于我的努力,突厥部众胜利了”(东33行);“由于上面上天和神圣水土和我祖可汗在天之灵不悦,九姓铁勒部众弃其水土而去唐”(东36行)。又如,《暾欲谷碑》记载:“由于上天赐给(我)智慧,我敦促(他)为可汗”(6行);“上天保佑,我没有让全副武装的敌人在突厥部众中驰骋”(53行)。沙陀由于较早被西突厥征服,成为其别部,因此信奉突厥的天神。
第二,扑祭。扑祭即杀马而祭,这是突厥葬俗中的一种重要现象①,即使是内迁至中原有着相当汉化程度的突厥人,他们依然继承着这种葬俗。《唐文拾遗》卷一六收录有王知敬为内迁中原的突厥大将哥舒季通撰写的《大唐左监门卫副率哥舒季通葬马铭》,云:“爰有名骢,厥号云花,声高天厩,产重流砂,盖武德中尝以赐故越州刺史都督诸军事哥舒府君者也。府君既已就义戈行,维是名骢,亦从歼焉。孤子左监门卫副率季通,乌号血竭,鸡耸骨立,永怀罔极之悲,思广推恩之义,乃图厥形,葬之坟隅。肇锡嘉铭,用□雄特。其词曰:粤维泰运,异质斯生。坤元毓德,天驷流精。惟彼云花,驰声御枥。龙文表瑞,凤翥开绩。於赫府君,丕茂肤功。帝曰赉汝,骏尾方瞳。越国过都,逐星激电。体健腾骧,姿雄顾盼。绌力著德,合志同心。策勋奏凯,照古凌今。夫何不永,阳九当厄。倏□霜锋,早坠逸翮。瓦鸳羞全,缑鹤并飞。存亡既偕,神魄攸依。矫矫精忠,垂光丹□。翩翩者骓,扬华骥尾。云花顾影,杨叶嘶风。”②
内迁中原之后的沙陀人同样继承了草原游牧民族的这种特殊的马殉的祭祀方式。《新五代史·晋出帝纪》记载,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使右骁卫将军石德超以御马二,扑祭于相州之西山,用北俗礼也”。同年七月,皇祖母刘氏崩,“使石德超扑马于相州之西山”。杀牛马祭奠死者应源于游牧习俗。《周书·突厥传》载:“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牛马,陈于帐前,祭之。”沙陀此习俗当来源于突厥习俗。
其三,以箭为信。突厥族有以箭为信的习俗,《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征发兵马,科税杂畜”,用一金链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突厥的箭相当于中原的印信,可汗可以此对酋长发号施令,由此“西突厥分为十部,每部酋长各赐一箭,谓之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禄部,置五大啜;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通谓之十部落”。沙陀内迁之后,这一习俗也被保留下来。《旧五代史·晋高祖纪二》云:“遣内班史进能押信箭一对,往滑州赐符彦饶。”《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四》云:“传箭,番家之信符也,起军令众则使之。”
关于沙陀的这种习俗,《新五代史》有着较为深入的分析:“(霍)彦威徙镇平卢。朱守殷反,伏诛,彦威遣使者驰骑献两箭为贺,明宗赐两箭以报之。夷狄之法,起兵令众,以传箭为号令,然非下得施于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彦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礼,动多此类。”①
第四,收继婚。作为原始社会群婚制的残余,收继婚在边陲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如《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诸嫂”;《三国志·魏书·乌丸传》记载,乌桓“父兄死,妻后母、报(原作“执”,误。引注。)嫂。若无报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汉书·匈奴传》上记载,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父死,妻群母、后母,这种不同辈分之间的婚配,是一种典型的超越“乱伦禁忌”规限的血缘婚或集团内群婚的遗续;而兄死报嫂,即兄亡后,弟有娶其寡嫂的特权,则是与氏族外群婚及氏族中的财产继承权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收继婚直到我国近代仍然在南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流行。《新五代史·晋家人传第五》记载:“出帝皇后冯氏,定州人也。父濛,为州进奏吏,居京师,以巧佞为安重诲所喜,以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欢甚,乃为重胤娶濛女,后封吴国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悦之。高祖崩,梓宫在殡,出帝居丧中,纳之以为后。是日,以六军仗卫、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庄,见于高祖影殿。群臣皆贺。帝顾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任大庆。’群臣出,帝与皇后酣饮歌舞,过梓宫前,酹而告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绝倒,顾谓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后与左右皆大笑,声闻于外。”重胤,晋高祖之弟,对出帝来说是为叔父,冯氏则为叔母,出帝居丧中公然娶冯氏为妻,欢笑自若。胡三省斥责出帝:“斩焉衰絰之中,触情纵欲以乱大伦,又从而狎侮其先,何以能久!”这种收继婚虽为中原传统文化所不容,然其在周边突厥、回纥诸族中颇为常见。由此可见,沙陀虽定鼎中原汉化极深,但其早期游牧社会中的收继婚制仍有孑遗。
第五,妇人参政。在氏族社会早期,由于女子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女子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内迁前的沙陀基本上处于氏族社会的父系阶段,但是母系时期妇女执政的习俗还是有孑遗。这种习俗一直到沙陀内迁之后还偶有所见。如,天复元年朱全忠大举攻太原,沙陀军大败。李克用听信李存信之言,欲北投鞑靼。李国昌之妻刘氏语克用曰:“闻王欲委城入蕃,审乎?计谁出?”曰:“存信等为此。”刘曰:“彼牧羊奴,安办远计。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效之?且王顷居鞑靼,危不免。必一朝去此,祸不旋跬,渠能及北虏哉?”李克用醒悟,乃止①。又,后唐庄宗时期皇太后、皇后与皇帝差不多处于均等的势力地位:“是时皇太后诰,皇后教,与制敕交行于藩镇,奉之如一。”②《贞观政要》卷九记载,“北狄风俗,多由内政”,在突厥、回鹘之中,可敦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沙陀内迁之后,很明显保留了草原游牧民族早期母权制的遗风。
第六,拥有本民族所独有之语言。沙陀民族之语言不得而知,但是其拥有本民族之语言当确凿无疑,而且这种语言在其内迁后长期存在。《新唐书·逆臣下》载:“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壁荆门,使沙陀以五百骑钉辔藻鞯望贼阵纵而遁,贼以为怯。明日,诸将乘以战,而马识沙陀语,呼之辄奔还,莫能禁。”③这说明,沙陀语在沙陀内部还普遍流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沙陀政权的建立。《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一》载,明宗与契丹阿保机战,“以边语谕之曰:‘尔辈非吾敌,吾当与天皇较力耳’”,“边语”当然是指沙陀在代北时所用的沙陀语;《旧五代史·康福传》载:“福善诸蕃语,明宗视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谘访时之利病,福即以蕃语奏之。”①康福系出昭武九姓,昭武九姓早在沙陀内迁初期就以融入沙陀部,故其所云“蕃语”即为沙陀语。另,后唐闵帝李从厚,乃明宗第三子,其“小字菩萨奴”②,“菩萨奴”当时从沙陀语音译而来,亦说明直至沙陀在中原建立政权,其民族语言仍有所保留。
第七,轻视品级、尊卑、长幼之别。后唐末帝李从珂在位时,对石敬瑭猜疑颇大,石敬瑭亦疑心重重,二人矛盾日益尖锐。后来,石敬瑭起兵造反。他一面在朝廷内部从事策反活动,一面由掌书记桑维翰起草奏章,向契丹求援:请称臣,以父礼事契丹,约事捷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契丹。都押牙刘知远对父事之礼甚为不满,云:“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③对此,石敬瑭并不在意。石敬瑭此举显示,他的胡人气质并未消失,对契丹称臣、称子并不以为耻辱,而其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他没有接受汉人品级、尊卑、长幼的观念,视契丹为同类,未有夷夏之分④。
中国古代贵中华、贱夷狄,石敬瑭此举自然得不到汉人支持。石敬瑭的后晋政权是在契丹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石敬瑭自然对契丹人毕恭毕敬。但是,就在后晋政权建立的第二年就发生了汉人吴峦闭门不迎契丹人之事。天福二年(937年)二月,“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还镇。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推峦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⑤。这件事说明,石敬瑭的这种胡人气质与汉人的“礼义之俗”背道而驰,因而遭到了汉人的抵触。
沙陀内迁中原并建立政权之后保留的某些游牧习俗,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沉迷畋猎,不知体恤稼穑之苦。后唐庄宗虽定鼎中原,然仍不忘沙陀之游牧生活,曾云:“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①后唐庄宗残存的游牧经济意识即使在即位后仍然经常付诸实际行动,史载:“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幸得伶人敬新磨知:“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诸伶共唱和之。”最终“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资治通鉴》记载:帝屡出游猎,从骑伤民禾稼,洛阳令何泽付于②。另,“丛薄,俟帝至,遮马谏曰:‘陛下赋敛既急,今稼穑将成,复蹂践之,使吏何以为理,民何以为生!臣愿先赐死。’帝慰而遣之。”③庄宗不注重农业生产,加之在位期间水旱灾害严重,仓廪空竭,故其统治很快结束。
二、沙陀汉化之表现
沙陀内迁之后失去了游牧经济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虽然保留了其原有的游牧生活的一些习俗,但是为了立足中原,不得不适应中原的生存模式。随着沙陀内迁日久,与中原政权接触日深,沙陀汉化日渐加深,并最终融入汉族当中。沙陀的汉化,既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潜移默化,又有制度上的主动靠拢。沙陀汉化的表现,我们在分析沙陀崛起及其代梁原因分析时有所表述,该部分从略。下面我们简要分析沙陀汉化的一些表现。
(一)学习儒家思想。
沙陀内迁直至李克用时期,尚无其接受儒家思想的直接证据,然到李存勖时期,史书开始有明确记载。《旧五代史·庄宗纪第一》记载,李存勖“十二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④;后唐明宗李嗣源一生戎马倥偬,未暇读书,但却特别关注经典。他曾戒秦王从荣云:“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见判官论说经义,虽不深达其旨,大约令人开悟。今朝廷有正人瑞士,可亲附之,庶几有益。吾见先皇在藩时,爱自作歌诗。将家子文非素习,未能尽妙,讽于人口,恐被诸儒窃笑。吾老矣,不能勉强于此,唯书义尚欲耳里频闻。”①后唐闵帝李从厚,“髫龀好读《春秋》,略通大义,貌类明宗,”其先回鹘人,后加入沙陀尤钟爱②。沙陀名将张从训,集团,然其喜“读儒书,精骑射,初为散员大将。天佑中,辖沙陀数百人,屯壶关十余岁”③。石敬瑭之子石重信则“为人敏悟多智而好礼”④。北汉主刘钧,“性孝谨,”幼而颖异,颇好学,工书⑤。更有甚者,沙陀内部不乏博学鸿儒之才。史载,出身沙陀三部落的“(史)匡翰刚毅有谋略,御军严整,接下以礼,与部曲语,未尝称名,历数郡皆有政声。尤好《春秋左氏传》,每视政之暇,延学者讲说,躬自执卷受业焉。时发难问,穷于隐奥,流辈或戏为“史三传。既自端谨,”沙陀内迁之后,耳濡目不喜人醉⑥。这些均已表明,染,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有的人甚至在经学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
(二)接受中原文化
首先,接受中原宗教。沙陀内迁后,对中原盛行的佛教、道教等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佛教早在佗钵可汗时期就已传入突厥人中⑦。内迁前沙陀人是否信奉佛教,史未明载,不得而知,然沙陀内迁后虔信佛教则毋庸置疑。首先,沙陀首领扶持佛教事业发展,《宋高僧传》卷七《后唐定州开元寺贞辩传》记载:“(贞)辩负笈抵太原城听习,时中山王氏与后唐封境相接,虞其觇间者,并州城内不容外僧。辩由次驱出,遂于野外古塚间宿。会武皇帝畋游,塚在围场中,辩固不知。方将入城赴讲,见旌旗骑卒,缩身还入穴中。武皇疑,令擒见,问其故,遂验塚中,敷草座,案砚疏钞罗布,遂命入府供养。时曹太后深加仰重,辩诉于太后曰:‘止以学法为怀,久在王宫不乐,如梏械耳。’武皇纵其自由,乃成其业。”沙陀人不但扶持佛教事业,而且本身十分崇信佛教。《册府元龟》卷五十二《帝王部·崇释氏二》记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九月,敕:天下应有本朝所造寺观,宜令所在长吏取寺司常住物添修,至万寿节日,须毕其功。”《宋高僧传》卷二十七《后唐五台山王子寺诚惠直传》记载:“(后唐)武皇躬拜(诚惠),感谢慈悲,便号国师矣..庄宗即位,诏赐紫衣,次宣师号。帝复宣厥后,再朝天阙,更极显荣。受恩一月,却返五台。”另,其时有僧名诚惠者,“初于五台山出家,能修戒律,称通皮、骨、肉三命,人初归向,声名渐远,四方供馈,不远千里而至者众矣。自云能役使毒龙,可致风雨,其徒号曰降龙大师。京师旱,庄宗迎至洛下,亲拜之,六宫参礼,士庶瞻仰,谓朝夕可致甘泽。祷祝数旬,略无征应。或谓官以祈雨无验,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及卒,赐号法雨大师,塔曰‘慈云之塔’”①。
庄宗之后,明宗皇帝亦痴迷佛教,《册府元龟》卷五十二《帝王部·崇释氏二》记载:“(后唐)长兴四年七月,命中使押绢五百匹施五台山僧斋料”;《旧五代史》卷六十七《赵凤传》记载,当时“有僧自西国取经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渍皴裂,进于明宗..时宫中所施已逾数千缗”。
后晋石敬瑭亦对佛教有浓厚兴趣,史载,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十二月,石敬瑭诏命,把他河阳旧宅(“潜龙旧宅”)改为开晋禅院,邢州旧居改为“广法禅院”以弘扬佛教②。安守忠,字信臣,并州晋阳人,其父审琦,则安守忠亦属沙陀人。守忠“终身不畜妓妾,而喜佞佛”③。甚至,有些驰骋疆场、戎马倥偬的武将也深谙佛理,如沙陀名将张从训之祖父张君政“识蕃字,通佛理”④,实属难能可贵。
此外,李克用家族中还有看破红尘,遁入佛门者。李克用第三子李存霸即属此例。史载:“存霸闻京师乱,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从弁不去。存霸乃剪发、衣僧衣,谒符彦超曰:‘愿为山僧,冀公庇护。’彦超欲留之,为军众所杀。”①
在佛教信仰中,沙陀人对毗沙天王(即“毗沙门天王”)的信仰情有独钟。毗沙天王是佛教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天王,他是印度古神话中北方的守护神,也是施福神。唐宋时期,毗沙天王演变成武神,香火非常旺盛。当时,无论朝廷还是民间,对“毗沙天王”的信仰十分盛行。在沙陀的统治者中,有多人钟情于毗沙天王信仰。首先是李克用,史载:“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济民之志,无何井溢,故未察其祸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与仆交卮谈。’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隐然出于壁间,见者大惊走,惟武皇从容而退,由是益自负。”②其二是后唐末帝李从珂,史载李从珂“在籓时,有相士言帝如毗沙天王,帝知之,窃喜。及即位,选军士之魁伟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卫,因诏诸道造此甲而进之”“宫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门③。其三是石敬瑭,史载:晋阳有北宫,天王,帝(石敬瑭)曾焚修默而祷之。”④
除佛教之外,沙陀对其他宗教亦表现出浓厚兴趣。后晋创立者石敬瑭对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史载,天福五年(940年)五月癸亥,石敬瑭赐予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通元先生”,“是时帝(石敬瑭)好《道德经》,尝召荐明讲说其义,帝悦,故有是命。寻令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版,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⑤。
其次,沙陀内部出现了许多文学艺术修养很高的人。在沙陀内部,汉文学艺术造诣最高的当属后唐庄宗,《五代史补》记载:“庄宗为公子时,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⑥后唐明宗子从荣亦颇具文学修养,他尤喜诗歌。《册府元龟》卷二百七十云:“秦王从荣为诗,与从事高辇等更相唱和,自谓章句独步于一时。有诗千余首,号曰《紫府集》。”(《五代史补》卷二亦载此事)。史圭,“常山人也,其先与王武俊来于塞外”。可见,史圭亦属边陲夷狄,后入沙陀部。史载“圭好学工诗”①,也颇具文学造诣。
沙陀内迁后对中原音乐舞蹈亦颇感兴趣。沙陀内迁后相当长时期内一直保持着本民族传统的音乐舞蹈,直至石敬瑭即位,这种局面才打破。《旧五代史·乐志》记载:“古之王者,理定制礼,功成作乐,所以昭事天地,统和人神,历代已来,旧章斯在。洎唐季之乱,咸、镐为墟;梁运虽兴,《英》、《茎》扫地。庄宗起于朔野,经始霸图,其所存者,不过边部郑声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泯绝。当同光、天成之际,或有事清庙,或祈祀泰坛,虽簨〓犹施,而宫商孰辨?遂使磬襄、鼗武,入河、汉而不归;汤濩、舜韶,混陵谷而俱失。洎晋高祖奄登大宝,思迪前规,爰诏有司,重兴二舞。”②可见,石敬瑭登基之后,作为中原雅乐的“二舞”才占据主导地位。然沙陀本民族的音乐舞蹈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史载后晋出帝石重贵“自期年之后,于宫中间举细声女乐,及亲征以来,日于左右召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常谓侍臣曰:‘此非音乐也’”③。可见,出帝时胡、雅音乐并行,然胡不压雅,并不被认可为“音乐”。
第三,采用汉姓。沙陀内迁之后,特别是被赐李姓之后,姓名多用单姓,这也是其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胡语语意和音节与汉语不同,故胡姓大部分为多音节词,被汉人称为复姓。胡族用复姓使胡汉交往多有不便。如通婚,汉人即不喜胡之复姓,《北史》卷二十八《陆俟传附陆叡传》云,叡“年十余岁,袭爵平原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时孝文帝尚未改北人姓,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沙陀内迁之后,为立足中原,获得中原士人认可,遂自行改胡姓为汉姓,多为单姓,而且非常彻底,这在内迁夷狄当中实属少见。
(三)实行中原典制
沙陀对中原典制的采用,首先表现在对族望、地望及国号的选择上。
为构建其政权的合法性,沙陀政权在族望、地望及国号的选择上煞费苦心。沙陀所建立的几个政权均将地望更改为中原某地,在族望上浪托汉族先人为其远祖,在国号选择上则力求攀缘前代王朝。如,后唐建立者李存勖祖上朱邪赤心因平定庞勋起义有功,“入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名国昌,仍为郑王房”①。其后朱邪氏便以唐室后裔自居,至李存勖建国,遂定国号为“大唐”,以明其政权乃唐朝基业之延续;石敬瑭建立后晋之后,自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子孙流泛西裔②;刘知远建后关辅乱,”汉后,自称“四代祖讳湍,帝有天下,追尊为明元皇帝”,而刘湍乃东汉明帝刘昞的后代③。由此,刘知远便与东汉王朝攀上了关系,选择“汉”为国号既顺理成章,同时又使政权具有了正统性。
沙陀定鼎中原后,几个政权均明确宣布采用唐朝文物、典制实行统治。后唐庄宗即位后即下诏曰:“惩恶劝善,务振纪纲;激浊扬清,须明真伪。盖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必按旧章,以令多士。而有志萌僭窃,位忝崇高,累世官而皆受唐恩,贪爵禄而但从伪命,或居台铉,或处权衡,或列近职而预机谋,或当峻秩而掌刑宪,事分逆顺,理合去留。”④庄宗俨然以唐王朝的继承人自居,视唐朝典制为圭臬。后晋高祖石敬瑭于天福元年(936年)闰十一月甲申,夺取后唐政权,“车驾入内,御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⑤。天福三年二月又下诏,云:“朝廷之制,今古相沿..宜依唐礼施行。”⑥后汉高祖刘知远“昔莅戎籓,素亏物望,洎登宸极,未厌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来苏之望”⑦,无政绩可言,然其为巩固政权,遂附东汉刘氏之后,“追崇六庙”,特以“国号为大汉”⑧,其施政亦沿用中原典制。
为了表明其政权的正统性,后唐统治者甚至对后梁改制中不合唐制者,悉令革除。如后梁删改唐律令格式,后唐建立后,御史台奏:“硃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廷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庄宗“从之”①。
三、沙陀汉化评价
关于沙陀的汉化,学界观点不一,概其要者,重要有二:其一,沙陀内迁直至建立政权时期汉化程度不深,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持此种观点。他认为,“建立朝廷的人,都是半开化的、带游牧人习气的武夫,非常好战好杀,不知道要有所以立国的政治。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②;其二,沙陀内迁及建立政权时期完全汉化。陶懋柄认为,沙陀政权“与汉族地主所建的王朝并无区别”③。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认为,“沙陀自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随贺鲁降唐以来,一直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联系,逐渐汉化。李存勖奉唐高祖李渊为祖;刘知远则奉汉高祖刘邦为祖,说明沙陀已完全融合于汉族之中”④。
我认为,以上观点均有失偏颇,沙陀汉化应辩证去看。沙陀自内迁之后,为立足中原,主动吸收接纳汉人加入沙陀集团,并努力学习中原文化,最终崛起河东;定鼎中原后,沙陀为了巩固其统治,又继承唐制,主动学习唐朝的立国之本、治国之道。沙陀内迁并建立政权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逐渐改变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过程,至五代时,沙陀已基本上实现了汉化。然而,在沙陀内迁直至建立政权过程中,其游牧经济观念、游牧文化风俗一直不同程度地保持着。
沙陀自代北时期的较少染濡汉文化到全面汉化是一个比较漫长的阶段。《宋史》当中记载有宋初的几个沙陀历史人物,虽寥寥无几,亦清晰可辨,说明宋初时沙陀人仍以其独有的文化特征为世人所知,它还没有完全融合于汉族。宋的中后期不再见有沙陀人的记载,说明此时沙陀人已全面汉化,完全融合于汉族当中。因此沙陀人完全汉化融入汉民族应在宋的中期以后。
沙陀内迁后的汉化有如下特点:
第一,沙陀内迁及其汉化带动了一大批边陲民族的汉化。沙陀内迁之后,因其骁勇善战,很快吸引了一大批边陲民族的加入。在内迁初期,沙陀就吸引了昭武九姓胡人的加入,且其数量远远超过沙陀,由此形成“沙陀三部落”。其后,沙陀部继续吸引边陲部落的加入,如回鹘、吐谷浑、鞑靼等,数量相当可观。沙陀奉旨镇压黄巢起义就是借助于这些边陲民族的鼎力相助。天祐十五年秋八月,李存勖与后梁夹河而战之时,“大阅于魏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曜,师旅之盛,近代为最”①。可见,沙陀内部边陲民族人数之巨,沙陀的汉化亦是这些边陲民族的汉化。沙陀政权建立之后,对其他少数民族没有采取排斥、贬抑的态度,而是给予与汉民同等的地位。如,后唐政权建立之后,对少数民族的住房、盖房、买卖房舍、田地以及参加科举等,都有条文规定,对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给予正式的承认。这些英明的措施使少数民族获得了和汉族同等的发展机遇,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值得大写特写的事情②。
第二,在沙陀政权统治核心以汉人为主。沙陀建立的三朝一国,均未对汉族采取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其用人不分蕃汉,实际上起决策作用的人物都是汉人,始终未曾形成一个以沙陀贵族集团为统治核心的统治力量,其华夷关系呈现良性发展趋势,这与十六国、北魏及此后的辽、夏、金、元、清情形大不相同。据统计,《新五代史》记载的在后唐政府中任职的147名官员中,汉族90人,少数民族10人,其他不明民族成分47人;在后晋任职的85名官员中。汉族73人,少数民族6人,不明民族成分者6人;在后汉任职的39名官员中,汉族33人,少数民族3人,不明民族成分者3人。这几个政权大量任用汉族官员,并且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身居高位,起决策作用,在权力分配上没有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对汉族没有歧视的现象,这在其他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中是罕见的。
第三,汉化主动性、积极性高涨。建立政权的沙陀上层,都有积极得到汉族认同的倾向。他们在内迁之后,都已取用汉族姓氏,除后唐李氏是唐朝酬功所赠之外,如石敬瑭之石氏,刘知远之刘氏,俱无来历,显系自认。建立政权后,又与汉族封建王朝的所谓正统加以联系,如李存勖的后唐,自命延续唐祚,以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加上李存勖之曾祖及祖、考,立七庙于太原;刘知远的后汉,则远绍两汉,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以表明自己的政权渊源有序,确属正统。唯石敬瑭的姓氏于史不彰,无源可溯,只好因地立号。沙陀人康福自认汉人,以他人称之蕃人为耻:“福无军功,属明宗龙跃,有际会之幸,擢自小校,暴为贵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饫腹,与士大夫交言,懵无所别。在天水日,尝有疾,幕客谒问,福拥衾而坐。客有退者,谓同列曰:‘锦衾烂兮!’福闻之,遽召言者,怒视曰:‘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因叱出之,由是诸客不敢措辞。复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①与此相应的,后唐政治制度全沿唐制,认为“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完全按照汉族封建王朝的模式进行统治,后晋、后汉踵行不改。
第四,最高统治者广与汉族通婚。历史上许多边陲民族入主中原后,其最高统治阶层严格限制华夷间通婚,如清朝施行“满汉不通婚”,严惩违者,甚至不惜杀头。然沙陀于此最为开放,沙陀皇帝的后妃大部分是汉族出身,官员和百姓中不同民族间通婚的现象亦属普遍,血统性的民族融合从未受到限制。
第五,许多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识较为肤浅,尚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晚唐五代乃干戈扰攘之时代,攻伐相尚,勇武是崇,故沙陀统治集团都是依靠冲锋陷阵而崭露头角,最后立基开国的。值此之故,沙陀统治集团许多人的汉化只是低层次的,感性认识的方面居多。他们熟稔汉人一些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观念,自觉模仿效法,然而对汉文化的一些深层次上的东西知之甚少。石敬塘、刘知远自不必论,因二人出身低微,少年从军,没有接受汉文化教育的条件;后唐庄宗李存勖出生于沙陀最高统治者之家,条件优越,能够接受教育,但他的汉文化素养也很有限,他也只是“稍习《春秋》,通大义”而已;而明宗嗣源即位之后,臣下霍彦威、孔循等进谏,请改国号,而明宗竟不知“何为正朔”①;明宗登基七年尚不知封建皇位继承制度,不知预立储君。太仆少卿何泽上表请立太子,竟以为是迫他让位,以至于“览表泣下”②。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云,“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③,他们的汉化程度与北魏孝文帝相比,实难以望其项背。长期的割据和战乱,致使民族文化交流受到影响,这直接导致了沙陀汉化的不彻底。
相关地名
沙陀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