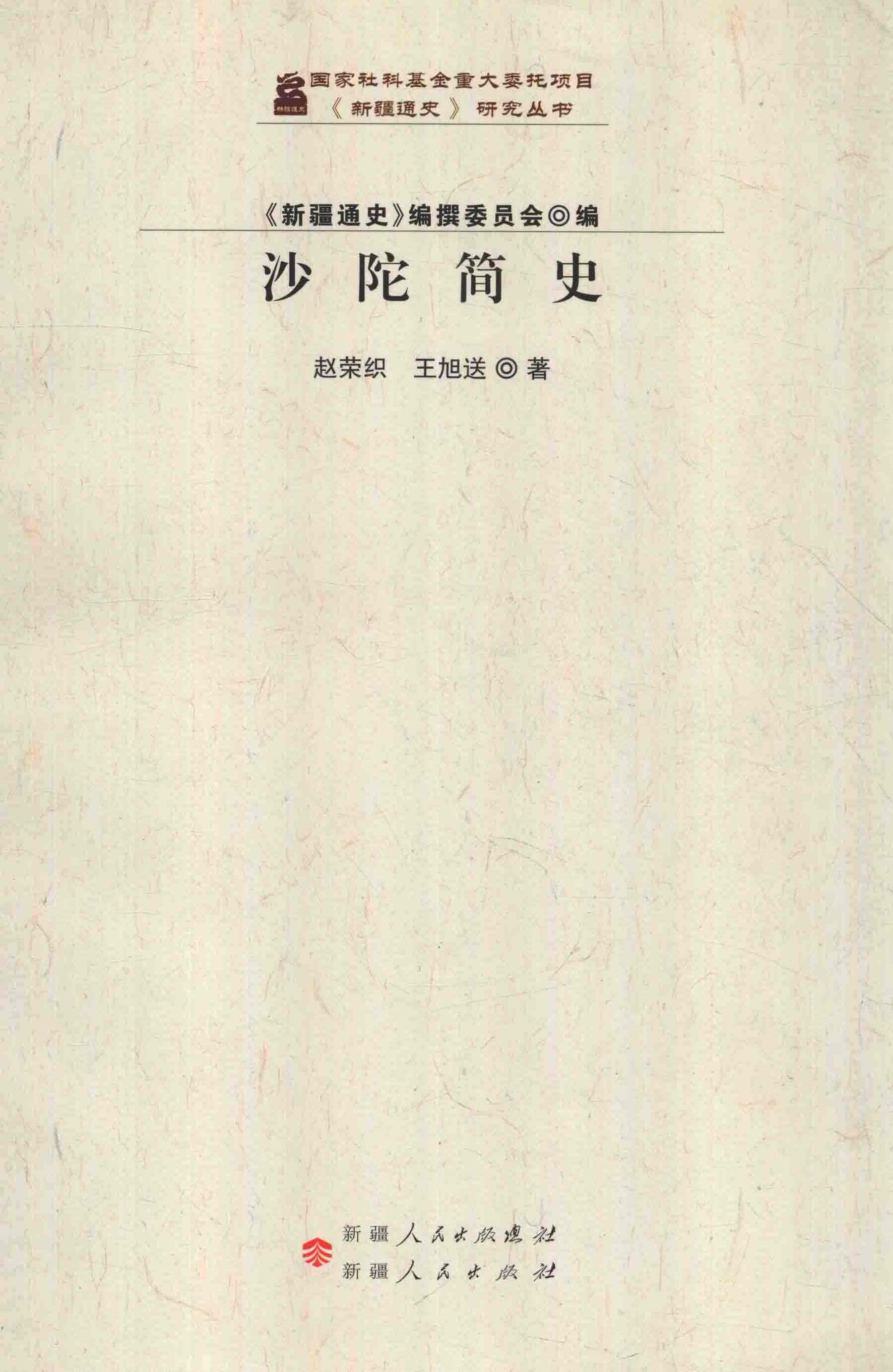内容
沙陀原为西突厥统辖之下的一弱小部落,其早期历史微不足道。沙陀内迁初期,人口不过万人,骑不过三千。然因缘际会,沙陀终发迹代北,崛起河东,定鼎中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本节试图从三个方面分析沙陀崛起河东的原因。
一、河东自然、人文之优势
唐末五代的河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大部,因其位于黄河以东,故谓之河东;又因位于太行山以西,今谓之山西。河东地区周围群山环绕,主要山脉东有太行山,南有中条山,北有恒山、五台山,中有霍山。群山中夹有许多川地,最大的是太原盆地及汾河中下游包括太原在内的广袤地区。群山环绕的地理特征虽对农业发展构成不利影响,但是在军事地理上却成为河东地区的天然屏障,从而获得“表里山河、称为顽固”的美誉。对于河东地区的军事地理优势,顾祖禹云: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①。
由于河东地区有诸山为屏、黄河为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华戎交界地区,当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时,河东肩负有护卫中原之责,故历代中原王朝在此屯有重兵;河东向西渡过龙门可直达长安,向东可由太行山径达河北,往往是争霸天下必由之路。
历史上有几个政权依托河东,成就了霸业:其一是春秋时期的晋国。立国于河东的晋国,在晋文公时,大败楚师于城濮,盟诸侯于践土,周天子乃命晋侯为伯。晋文公由此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是春秋五霸中维持霸业最久者。晋文公文治武功,显达千秋,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其二为北魏。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匈奴刘渊乘机起兵灭西晋,揭橥北五胡十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序幕,讫止北魏始统一北方。北魏的崛起即以河东为根据地,利用河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终混一方。
河东虽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但其处于农牧交接、亦耕亦农的区域,地势高寒、水草丰美,适于养马业的发展。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屈产(一说今山西吉县;一说今山西石楼东南)即以产良马而闻名①。史称河东“素多良骏”②,每逢入朝进贡之时,往往“远效名驹”③,“远输牵右之良”④。良马成为其进贡之品。在冷兵器时代,“马者,国之武备。天下去其备,国将危亡”⑤,马匹在国家军事战略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唐末藩镇割据的时代,任何势力要想割据称雄、拓展疆域、必须拥有一支骑兵劲旅,而马匹的拥有量则是决定其骑兵劲旅势力的基本条件。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有当时九个节度使拥有战马的数量,兹移录如下:
安西节度使2700范阳节度使13000
北庭节度使5000平卢节度使10800
河西节度使36700陇右节度使10950
朔方节度使18600剑南节度使4000
河东节度使28800
在这九个节度使中,河西节度使拥有马匹最多,河东次之。但河西地域广阔,草场众多,拥有马匹数量自然最多。而河东地处农牧混杂区,较其他八节度使,地域最为狭窄,然拥有马匹数量仅次于河西,足见其养马业之发达。充足的马源提高了河东地区的战斗力,史称河东“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业之资也”①。
沙陀自进入河东地区以来,非常重视发展畜牧业。后唐庄宗李存勖就曾说过“吾家以羊马为生”,并借此令康福牧马于相州。到后唐明宗时,“军势由是益盛”。②关于李克用时期沙陀牧马业发展情况,《旧五代史》卷四十四《唐书二十唐明宗纪第十》记载:“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这说明,早在李克用时期,沙陀依靠河东地区发达的畜牧业,已经建立起了一支七千铁骑的骑兵部队。对此,元代史学家胡三省也进行了专门说明:“后唐起于太原,马牧多在并、代。”③
河东除了拥有独特的军事地理优势外,在社会文化方面同样具有独特的优势。河东由于地处华戎交界之处,因此经常成为内附夷狄安置之处。如,《旧唐书·张嘉贞传》云:“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④;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回鹘特勤嗢没斯率众“诣振武降”,唐武宗令河东节度使刘沔“于云朔等州拣一空闲城垒”,令其居住;8世纪中叶,居住于盐、夏地区的昭武九姓胡人迫于吐蕃压力,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7年)东走石州(今离石),散居于云(今大同)、朔之间⑤;吐蕃攻陷安乐州之后,吐谷浑“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今俗多谓之退浑”⑥。隋唐时期内附河东的夷狄众多,他们与当地汉人长期杂居,不免使汉人习染夷狄习俗,潜移默化之下,极易形成尚勇崇武的风尚。此外,河东作为华戎交界之地,经常遭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当地人民为了生存,为了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必须增强自己的战斗力,长此以往,亦有助于养成尚武之习俗。
对于当时河东地区的风俗,史书多有记载。如《旧五代史》卷六九《张宪传》记载当时太原的风俗云:“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一云:“并州(即太原)近狄,俗尚武艺”;《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记载代州风俗云:“番民杂居,刚劲之心恒多,不测歉馑”①;卷四三记载晋州风俗云:“‘矜功名,薄恩少礼’”《别传》云:刚强多豪杰,②;卷四四记载辽州云:“蕃汉相杂,好武少士”③;卷四五引《汉书·地理志》云:“土广俗杂,其人大率粗急,高气势,”“轻为奸④;卷四十八记载隰州云:其人本号部落,久归汉法。”⑤
受尚武风俗影响,加之河东地区平原大川无多,不适合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故当地身体健壮抑或习于骑射者,自幼从军者甚多。其子孙沿袭祖、父辈从军者亦甚众。自幼从军者,如康义诚、张廷裕、符彦超等均少事李克用,李承嗣少仕郡补右职。子孙袭祖、父从军者,如史建瑭以父荫少仕军旅;安元信以将族子便骑幼时即侍从李克用;张敬询祖仲阮曾任胜州刺史,父汉环事李克用为牙将,而敬询则在李克用时掌甲坊。
与夷狄风俗习染下河东尚勇崇武风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唐时期河东汉族步兵的怯弱,如会昌年间讨回鹘乌介可汗时,即有人言“太原步兵钝弱,素为河朔所轻”⑥,讨昭义刘稹时,王逢更以“榆社、河东怯弱,终不堪用”⑦为由,再诏代北部落助讨。王逢曾盛称道:“代山向北军马,王逢曾经使用,郎校精强。今来是防秋时,请委节度使,除蔚州飞狐、灵丘与幽州接界外,代诸州军抽二千人,即得此二千人,已敌榆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约有一千人,敌已来极耐苦,一人敌十人,量抽五百人,将赴行营,每对与十人、五人,令入贼城,非常得力。”①可见,由于沙陀等少数民族迁移至河东境内,汉族步兵昔日之怯弱局面大为改观。
在夷狄风俗影响之下,河东军队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其中以沙陀军队最具代表性。在沙陀依附于吐蕃之时,吐蕃沙陀骁勇善战而封其首领朱邪尽忠以“军大论”的崇高荣誉,同时将沙陀迁往对唐朝作战的前沿地带——甘州,在对唐作战中“常以沙陀为前锋”②。内迁之后,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克用祖孙三代皆以冲锋陷阵著称,李克用统帅之军士皆着黑衣,时称鵶军。当李克用奉旨前往中原镇压黄巢,途经河中时,河中义军皆言“鵶军将至,当避其锋”。沙陀之骁勇善战,为当时群雄所叹服。沙陀大将安重霸因负罪奔梁,再负罪奔蜀时,“蜀以蕃人善骑射,因为亲将”③。又如,沙陀将领李承嗣、史俨一行援兖、郓不利,而魏博与沙陀交恶,其退路被切断,不得归,遂奔淮南。其二人之加入使原本善于水战,不知骑射的淮南,军声大振④。李承嗣、史俨皆河东骁将,李克用深惜之,遣使诣杨行密请之,杨行密惜其才,竟不得归。河东尚武之风俗一直延续至北宋,其时“河东一路间于戎虏,其民风俗素号忠厚,加之力穑勤俭,习尚材武,朝廷若稍加奖励,缓急足以自扦一方”⑤。
由于河东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社会风貌适于塑造军人,这为日后强大的沙陀军人集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沙陀统治阶层之拓展
沙陀虽源自西域,发迹代北,其早期集团成员大多来自沙陀本部和代北地区,其民族及地域特色十分明显。然沙陀并未囿于地域及民族之界限,而是随着势力之发展,地域之扩张,广泛吸收各族、各地、各阶层之精英,以充实其统治集团。由此,沙陀走出了一条有容乃大的道路。
沙陀统治阶层之拓展,首先表现在其不限于民族之别,于沙陀之外能充分吸纳各族精英加入其集团。沙陀迁入内地之初,人数不过万人,将士不过数千,然因其骁勇善战冠于边地,很快将昭武九姓等胡人纳入其中,形成“沙陀三部落”。沙陀集团早期主要以“沙陀三部落”人为主,其中属沙陀本部者主要有:李克修(李克用之弟)、李嗣昭(李克修子)、李克宁、李克恭、李克柔(以上为李克用诸弟)。除沙陀本部外的“沙陀三部落”人主要有:米海万、康君立、安金全、安金俊、安敬忠、安元信、石君和、史敬思、史建瑭(以上为加入“沙陀三部落”的昭武九姓胡人)、李尽忠、郭绍古、刘琠等。
然沙陀统治阶层之构成并未囿于“沙陀三部落”之族人,随着其势力的壮大、统治范围之扩张,沙陀逐渐吸纳了大量外族之人。如李存信,本为回鹘部人,早在李国昌时期就加入沙陀集团,备受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信任,后来官至蕃汉马步都指挥使①;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本代北夷狄,家世事沙陀②;李嗣恩,本姓骆,吐谷浑人,15岁时即侍从李克用于振武;康思立,阴山诸部人,少事李克用③;张万进,突厥人,以骑射著名④;康福,蔚州人,世本夷狄(虽未言其确切族属,但从其姓氏来看,极有可能为昭武九姓胡人)。
虽然沙陀集团吸纳了大量周边民族成分,但其吸纳的外族之人主要还是以汉人为主。早在沙陀发迹代北之时,沙陀集团就已经吸纳了大量汉族精英。如薛志勤、盖寓,代北蔚州人,均从沙陀起云中⑤;李存璋,云中人,从沙陀起云中⑥;张敬询,胜州金河人,世为振武牙校,专掌沙陀甲坊十五载①;李嗣昭,汾州太谷人,为李克用出猎之时,以金帛所取之②。尽管早在代北时期,沙陀就开始吸纳周边民族及汉族精英加入其统治阶层,但在其时这些人并不占主流。
之后,随着沙陀镇压庞勋、黄巢起义,沙陀势力逐渐扩张。在沙陀转战征讨过程中,沙陀集团又吸纳了大量的汉族精英,从而为沙陀集团增添了新的血液。沙陀势力扩张以上源驿之变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期。沙陀扩张初期加入沙陀集团的汉族精英主要有:李存进,振武人,李克用破朔州时所得③;伊广,兖州人,中和末年任忻州刺史,因天下大乱,委质李克用④;袁建丰,关中人,为沙陀镇压黄巢起义之时于华阴所得⑤;李存贤,许州人,少时加入黄巢义军,沙陀破陈、许两州时,降沙陀⑥。
上源驿之变后,沙陀集团扩张步伐加快,这一时期是沙陀吸纳汉族精英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加入沙陀统治阶层的汉族精英既有交争中战败归顺者,也有在其他阵营内部斗争中失利而主动归顺者。其中战败归顺者主要有:光启三年(887年),李克用同昭义节度使孟方立战于琉璃陂,孟方立军队战败,统军大将马溉、袁奉韬被俘,归顺沙陀;丁会,曾为朱全忠之部曲,后朱全忠以丁会为昭义节度使。天祐三年(906年),李嗣昭攻潞州,丁会以潞州归李克用⑦。属其他阵营内部斗争失利而归顺者,为数更多。主要有:王思同、李承约,两者均属刘仁恭帐下军校,天祐四年(907年)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两人率部属奔沙陀;张遵诲原为魏博牙军,天祐三年(906年),罗绍威诛牙军,张遵诲奔沙陀;李罕之,降沙陀之前为河阳节度使,与河南尹、东都留守张全义本属同一阵营,但李罕之任河阳节度使之后不可一世,经常向据守洛阳的张全义勒索。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为张全义所逐,遂降沙陀。与李罕之同降沙陀的还有其部下李建及、李存审等。
尽管沙陀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汉族精英加入其集团,但沙陀本部及沙陀发迹代北时的元从精英,仍在沙陀统治阶层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后来沙陀势力拓展时期,对于新占领土,沙陀亦往往派遣沙陀本部人及代北元从前往经营。如昭义节度使一职,历任者有:李克修(883—890年)、李克恭(890年)、康君立(890—894年)、薛志勤(894—898年)、孟迁(899—900年)、李嗣昭(906—923年);邢洺团练使一职,历任者有:安金俊(890年)、安知建(890—891年)、李存孝(891—894年)、马师素(894—898年);泽州刺史一职,历任者有:李罕之(888—898年)、李存璋(899—901年);振武节度使一职,由石善友(893—902年)担任。
由于沙陀集团原为西北边陲小族,以武力起家,加之河东“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沙陀本部极度缺乏文职官员。文职在当时藩镇割据争雄中地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藩镇之表奏、交聘等事物均需文职官员操持。《旧五代史·李袭吉传》云:“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李)袭吉齐名于时。”①其时藩镇中的文职主要有节度副使、掌书记、判官、推官等,其中掌书记地位尤显重要。唐人崔颢曾言:“愚以为军中书记,节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谅非容易,而可专据”②;李德裕于河东掌书记任内,曾谓:“非夫天机殊捷,学源浚发,含思而九流委输,挥毫而万象骏奔,如庖丁提刃,为之满志,师文鼓瑟,效不可穷,则不能称是也。”③由此可见,文职在藩镇行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沙陀本部缺乏文职人才,故沙陀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大量吸纳汉族中的文职精英为其效命。
沙陀为吸纳文职精英加入其集团,可谓不遗余力。除正当的延揽吸纳外,还通过强行截留的方式吸纳。在沙陀集团的文职官员中,为沙陀所重视且在沙陀集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有:李袭吉,原为河中幕府,李克用入主河东前任河东文吏。先后担任沙陀集团的掌书记、节度副使,李克用时期,书檄基本出于其手,李克用每每出征,李袭吉必紧随其后。李袭吉死后,卢汝弼继任河东副使,卢质任河东掌书记。卢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进士第,历台省。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迁昭宗于洛阳,卢汝弼惧祸渡河,北依潞州丁会。天祐三年(906年)闰十二月随丁会降晋。沙陀集团之谋士,唯卢汝弼登进士第且在朝为官,故备受礼遇。卢质原为陕虢幕府,天祐三年(906年),北游太原,李袭吉以女妻之,遂留晋阳,加入沙陀集团。马郁,原为幽州刘仁恭之掌书记,天祐三年随幽州大将李溥帅兵三万会于晋阳,助河东兵攻潞州,平潞州后,会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李克用留马郁不遣,以之为留守判官。卢质虽代为掌书记,然“自李袭吉卒,每有四方会盟,书檄多命(马)郁为之,《答吴蜀书》与《王檀书》皆郁文也”①。王缄,亦为刘仁恭文吏,天祐四年刘仁恭遣王缄出使凤翔,路径太原,及复命,燕、晋不通,克用留之。缄坚辞复命,书辞稍抗,克用下狱诘之,谢罪听命,乃署为巡官,历掌书记。天祐十二年,李存勖得魏博,任魏博节度判官。翌年,迁魏博节度副使②。
沙陀集团吸纳的汉族精英群体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宦官。宦官群体在朱全忠把持朝政之时,几遭灭顶之灾。史载:“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诛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余人。其在外者,悉诏天下捕杀之,而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是时,方镇僭拟,悉以宦官给事,而吴越最多。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以至于亡。”③在朱全忠遍杀宦官之时,以李克用为代表的诸藩镇却将之藏匿,而且委之以重任。如河东监军张承业,在朱全忠诛杀宦官之时,即受李克用保护,且复之为河东监军。因沙陀集团善待宦官,河东成为宦官向往之地。如,乾宁元年(894年),李茂贞并山南诸州,逃亡于此的宦官杨复恭再度逃亡,欲投靠河东之沙陀集团,不幸途中为华州兵所擒,为韩建所杀①。
由于沙陀集团厚遇宦官,故宦官为其死力,在沙陀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见诸史载,为沙陀重用的宦官重要者有张承业、张居翰。张承业在朱全忠诛杀天下宦官时,得沙陀庇护幸免于难,故于沙陀最忠,贡献亦最大。《旧五代史·张承业传》云:“承邺感武皇(李克用)厚遇,庄宗(李存勖)在魏州垂十年,太原军国政事,一委承业。而积聚庾帑,收兵市马,招怀流散,劝课农桑,成是霸基者,承业之忠力也。”②另一名宦官张居翰,本为幽州监军,朱全忠诛杀宦官时,赖刘仁恭免诛。天祐三年(906年),刘仁恭遣军助河东攻潞州时,张居翰随行监军,及刘仁恭为其子刘守光所囚,李克用遂留之不遣,以为潞州监军。其后,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每出征,必令居翰知留后事③。
沙陀统治阶层之拓展,还表现在其人才选拔上不唯出身,只唯才能。只要其英勇善战,均予擢用。如李嗣昭,本汾州太谷人士,为李克用出猎以金帛取之,足见其出身寒微。然其英勇善战,光化二年,沙陀即以显职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授予之④;李存信,本“代北牧羊儿耳”;⑤其他如李存孝、李嗣源、李存进、李嗣本、李嗣恩等早期均属李克用帐下家僮,出身可谓寒微。
三、广与地方大姓通婚
沙陀本为一弱小部族,内迁初期人数不过万人,即使日后整合昭武九姓胡人之后形成“沙陀三部落”,与当地汉人相比,其人数亦不占优势。作为夷狄部落,生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要想生存、发展,势必要与当地汉族大姓结交,以换取其支持。沙陀发迹代北、称霸河东之时,一直在与当地大姓结交,而最有效之方法莫过联姻。正是通过联姻,广交地方大姓,换取地方大姓之支持,最终走上称霸河东、问鼎中原的道路。
沙陀内迁初期,势力弱小,加之身为夷狄,无与地方大姓结交之资。朱邪执宜时期,尚无沙陀与当地大姓通婚之例证。至李国昌、李克用时,才出现沙陀与当地汉人通婚的记载。李国昌妻秦氏,当属汉人无疑。李克用“正室刘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①以《新五代史》之惯例,沙陀或其他异族之人,莫不标明其族类。则,李克用之妻刘氏、曹氏亦皆为汉人。然对于李国昌、李克用妻之出身,史书无明确记载,出身地方大姓之可能性不大。唯李克用妻刘氏“自太祖起兵代北”,“常从征伐。为人明敏多智略,颇习兵机,常教其侍妾骑射,以佐太祖”,上源驿之变时,“太祖左右有先脱归者,以难告夫人,夫人(刘氏)神色不动,立斩告者,阴召大将谋保军以还”②。从刘氏之表现来看,当出自地方豪门抑或大姓。
至李克用时期,随着沙陀征讨庞勋、黄巢起义有功,其势力日渐壮大,沙陀与河东及其周边地区大姓通婚者日多。以李克用家族为例,其家族与地方大姓通婚者有:一、李克用子李存勖,李克用为其娶韩恽之妹和伊广之女。韩恽,字子重,晋阳人。韩恽出身官僚世家,曾祖韩俊,为唐龙武大将军;祖父韩世则,任石州(今山西离石)司马;父亲韩逵,任代州刺史。韩恽的兄弟均任军职,韩恽则不同。他与儒士交游甚广,喜欢作歌赋诗,家中收集书籍数千卷,属典型儒者。唐昭宗乾宁(894—897年)中,韩恽以文学署交城、文水县令,后为太原少尹。伊广,元和中右仆射伊慎之后。中和末,伊广除授忻州刺史。二、李克用子李存霸,李克用为其娶张敬询之女。张敬询,胜州金河县人,祖仲阮,历胜州刺史,父汉环事李克用为牙将,张敬询则在李克用时掌甲坊十五载,以称职闻名。三、李克用子李存义,李克用为其娶郭崇韬之女。郭崇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人,沙陀名将、谋臣。初为唐朝昭义节度使李克修亲信,后归李克用,用为典谒,能临机应对。史无明载其是否为地方大姓,但从其行为表现,当出自地方大姓。四、李克用还以一女适任茂弘之子任团。任茂弘,本京兆人士,祖清,任成都少尹,属衣冠之家。“避地太原,有子五人,曰图、回、圜、团、囧,风彩俱异”③。
沙陀集团与地方大姓结交并非囿于河东一隅,为巩固、拓展其势力,沙陀除与其统辖范围内的大姓通婚外,还主动与当时尚未纳入其统治范围的周边地区大姓通婚。仍以李克用家族为例,李克用家族与周边大姓通婚者主要有:一、李克用一女适河中节度使王珂。王珂,中人,祖纵,盐州刺史,父重荣,河东节度使,破黄巢有大功,封琅琊郡王。王珂本重荣兄重简之子,出继重荣。唐僖宗光启三年,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害,推重荣弟重盈为蒲帅,以珂为行军司马。及重盈卒,军府推珂为留后。时重盈子洪为陕州节度使,瑶为绛州刺史,由是争为蒲帅。王珂遣使求援于太原,李克用为保荐于朝,昭宗可之。后昭宗以王珂为河中节度使,李克用亦因此以女妻之。二、李克用以一女适王处存之侄王邺①。王处存,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世籍神策军。其祖辈为长安富族,财产数百万,父王宗,曾任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使。王处存少年时即以父荫,居右军镇使,后升为骁卫将军、左军巡使。乾符六年十月,出任检校刑部尚书、义武军节度使。三、李克用还以弟克让一女适孟知祥。孟知祥,字保风,又作保裔,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世代都在郡里为官。伯父孟方立官至邢洺节度使,叔父孟迁曾任泽潞节度使。孟家亦属地方大姓。
通过与地方大姓之通婚,沙陀赢得了河东及周边大姓之支持,从而为其日后问鼎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沙陀广与地方大姓通婚亦加快了沙陀集团的汉化过程。
一、河东自然、人文之优势
唐末五代的河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大部,因其位于黄河以东,故谓之河东;又因位于太行山以西,今谓之山西。河东地区周围群山环绕,主要山脉东有太行山,南有中条山,北有恒山、五台山,中有霍山。群山中夹有许多川地,最大的是太原盆地及汾河中下游包括太原在内的广袤地区。群山环绕的地理特征虽对农业发展构成不利影响,但是在军事地理上却成为河东地区的天然屏障,从而获得“表里山河、称为顽固”的美誉。对于河东地区的军事地理优势,顾祖禹云: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①。
由于河东地区有诸山为屏、黄河为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为华戎交界地区,当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时,河东肩负有护卫中原之责,故历代中原王朝在此屯有重兵;河东向西渡过龙门可直达长安,向东可由太行山径达河北,往往是争霸天下必由之路。
历史上有几个政权依托河东,成就了霸业:其一是春秋时期的晋国。立国于河东的晋国,在晋文公时,大败楚师于城濮,盟诸侯于践土,周天子乃命晋侯为伯。晋文公由此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是春秋五霸中维持霸业最久者。晋文公文治武功,显达千秋,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其二为北魏。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匈奴刘渊乘机起兵灭西晋,揭橥北五胡十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序幕,讫止北魏始统一北方。北魏的崛起即以河东为根据地,利用河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终混一方。
河东虽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但其处于农牧交接、亦耕亦农的区域,地势高寒、水草丰美,适于养马业的发展。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屈产(一说今山西吉县;一说今山西石楼东南)即以产良马而闻名①。史称河东“素多良骏”②,每逢入朝进贡之时,往往“远效名驹”③,“远输牵右之良”④。良马成为其进贡之品。在冷兵器时代,“马者,国之武备。天下去其备,国将危亡”⑤,马匹在国家军事战略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唐末藩镇割据的时代,任何势力要想割据称雄、拓展疆域、必须拥有一支骑兵劲旅,而马匹的拥有量则是决定其骑兵劲旅势力的基本条件。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有当时九个节度使拥有战马的数量,兹移录如下:
安西节度使2700范阳节度使13000
北庭节度使5000平卢节度使10800
河西节度使36700陇右节度使10950
朔方节度使18600剑南节度使4000
河东节度使28800
在这九个节度使中,河西节度使拥有马匹最多,河东次之。但河西地域广阔,草场众多,拥有马匹数量自然最多。而河东地处农牧混杂区,较其他八节度使,地域最为狭窄,然拥有马匹数量仅次于河西,足见其养马业之发达。充足的马源提高了河东地区的战斗力,史称河东“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业之资也”①。
沙陀自进入河东地区以来,非常重视发展畜牧业。后唐庄宗李存勖就曾说过“吾家以羊马为生”,并借此令康福牧马于相州。到后唐明宗时,“军势由是益盛”。②关于李克用时期沙陀牧马业发展情况,《旧五代史》卷四十四《唐书二十唐明宗纪第十》记载:“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这说明,早在李克用时期,沙陀依靠河东地区发达的畜牧业,已经建立起了一支七千铁骑的骑兵部队。对此,元代史学家胡三省也进行了专门说明:“后唐起于太原,马牧多在并、代。”③
河东除了拥有独特的军事地理优势外,在社会文化方面同样具有独特的优势。河东由于地处华戎交界之处,因此经常成为内附夷狄安置之处。如,《旧唐书·张嘉贞传》云:“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贞奏请置军以镇之,于是始于并州置天兵军”④;会昌二年(842年)四月,回鹘特勤嗢没斯率众“诣振武降”,唐武宗令河东节度使刘沔“于云朔等州拣一空闲城垒”,令其居住;8世纪中叶,居住于盐、夏地区的昭武九姓胡人迫于吐蕃压力,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7年)东走石州(今离石),散居于云(今大同)、朔之间⑤;吐蕃攻陷安乐州之后,吐谷浑“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今俗多谓之退浑”⑥。隋唐时期内附河东的夷狄众多,他们与当地汉人长期杂居,不免使汉人习染夷狄习俗,潜移默化之下,极易形成尚勇崇武的风尚。此外,河东作为华戎交界之地,经常遭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当地人民为了生存,为了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必须增强自己的战斗力,长此以往,亦有助于养成尚武之习俗。
对于当时河东地区的风俗,史书多有记载。如《旧五代史》卷六九《张宪传》记载当时太原的风俗云:“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一云:“并州(即太原)近狄,俗尚武艺”;《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记载代州风俗云:“番民杂居,刚劲之心恒多,不测歉馑”①;卷四三记载晋州风俗云:“‘矜功名,薄恩少礼’”《别传》云:刚强多豪杰,②;卷四四记载辽州云:“蕃汉相杂,好武少士”③;卷四五引《汉书·地理志》云:“土广俗杂,其人大率粗急,高气势,”“轻为奸④;卷四十八记载隰州云:其人本号部落,久归汉法。”⑤
受尚武风俗影响,加之河东地区平原大川无多,不适合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故当地身体健壮抑或习于骑射者,自幼从军者甚多。其子孙沿袭祖、父辈从军者亦甚众。自幼从军者,如康义诚、张廷裕、符彦超等均少事李克用,李承嗣少仕郡补右职。子孙袭祖、父从军者,如史建瑭以父荫少仕军旅;安元信以将族子便骑幼时即侍从李克用;张敬询祖仲阮曾任胜州刺史,父汉环事李克用为牙将,而敬询则在李克用时掌甲坊。
与夷狄风俗习染下河东尚勇崇武风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唐时期河东汉族步兵的怯弱,如会昌年间讨回鹘乌介可汗时,即有人言“太原步兵钝弱,素为河朔所轻”⑥,讨昭义刘稹时,王逢更以“榆社、河东怯弱,终不堪用”⑦为由,再诏代北部落助讨。王逢曾盛称道:“代山向北军马,王逢曾经使用,郎校精强。今来是防秋时,请委节度使,除蔚州飞狐、灵丘与幽州接界外,代诸州军抽二千人,即得此二千人,已敌榆社五千人。又向北烽子约有一千人,敌已来极耐苦,一人敌十人,量抽五百人,将赴行营,每对与十人、五人,令入贼城,非常得力。”①可见,由于沙陀等少数民族迁移至河东境内,汉族步兵昔日之怯弱局面大为改观。
在夷狄风俗影响之下,河东军队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其中以沙陀军队最具代表性。在沙陀依附于吐蕃之时,吐蕃沙陀骁勇善战而封其首领朱邪尽忠以“军大论”的崇高荣誉,同时将沙陀迁往对唐朝作战的前沿地带——甘州,在对唐作战中“常以沙陀为前锋”②。内迁之后,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克用祖孙三代皆以冲锋陷阵著称,李克用统帅之军士皆着黑衣,时称鵶军。当李克用奉旨前往中原镇压黄巢,途经河中时,河中义军皆言“鵶军将至,当避其锋”。沙陀之骁勇善战,为当时群雄所叹服。沙陀大将安重霸因负罪奔梁,再负罪奔蜀时,“蜀以蕃人善骑射,因为亲将”③。又如,沙陀将领李承嗣、史俨一行援兖、郓不利,而魏博与沙陀交恶,其退路被切断,不得归,遂奔淮南。其二人之加入使原本善于水战,不知骑射的淮南,军声大振④。李承嗣、史俨皆河东骁将,李克用深惜之,遣使诣杨行密请之,杨行密惜其才,竟不得归。河东尚武之风俗一直延续至北宋,其时“河东一路间于戎虏,其民风俗素号忠厚,加之力穑勤俭,习尚材武,朝廷若稍加奖励,缓急足以自扦一方”⑤。
由于河东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社会风貌适于塑造军人,这为日后强大的沙陀军人集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沙陀统治阶层之拓展
沙陀虽源自西域,发迹代北,其早期集团成员大多来自沙陀本部和代北地区,其民族及地域特色十分明显。然沙陀并未囿于地域及民族之界限,而是随着势力之发展,地域之扩张,广泛吸收各族、各地、各阶层之精英,以充实其统治集团。由此,沙陀走出了一条有容乃大的道路。
沙陀统治阶层之拓展,首先表现在其不限于民族之别,于沙陀之外能充分吸纳各族精英加入其集团。沙陀迁入内地之初,人数不过万人,将士不过数千,然因其骁勇善战冠于边地,很快将昭武九姓等胡人纳入其中,形成“沙陀三部落”。沙陀集团早期主要以“沙陀三部落”人为主,其中属沙陀本部者主要有:李克修(李克用之弟)、李嗣昭(李克修子)、李克宁、李克恭、李克柔(以上为李克用诸弟)。除沙陀本部外的“沙陀三部落”人主要有:米海万、康君立、安金全、安金俊、安敬忠、安元信、石君和、史敬思、史建瑭(以上为加入“沙陀三部落”的昭武九姓胡人)、李尽忠、郭绍古、刘琠等。
然沙陀统治阶层之构成并未囿于“沙陀三部落”之族人,随着其势力的壮大、统治范围之扩张,沙陀逐渐吸纳了大量外族之人。如李存信,本为回鹘部人,早在李国昌时期就加入沙陀集团,备受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信任,后来官至蕃汉马步都指挥使①;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本代北夷狄,家世事沙陀②;李嗣恩,本姓骆,吐谷浑人,15岁时即侍从李克用于振武;康思立,阴山诸部人,少事李克用③;张万进,突厥人,以骑射著名④;康福,蔚州人,世本夷狄(虽未言其确切族属,但从其姓氏来看,极有可能为昭武九姓胡人)。
虽然沙陀集团吸纳了大量周边民族成分,但其吸纳的外族之人主要还是以汉人为主。早在沙陀发迹代北之时,沙陀集团就已经吸纳了大量汉族精英。如薛志勤、盖寓,代北蔚州人,均从沙陀起云中⑤;李存璋,云中人,从沙陀起云中⑥;张敬询,胜州金河人,世为振武牙校,专掌沙陀甲坊十五载①;李嗣昭,汾州太谷人,为李克用出猎之时,以金帛所取之②。尽管早在代北时期,沙陀就开始吸纳周边民族及汉族精英加入其统治阶层,但在其时这些人并不占主流。
之后,随着沙陀镇压庞勋、黄巢起义,沙陀势力逐渐扩张。在沙陀转战征讨过程中,沙陀集团又吸纳了大量的汉族精英,从而为沙陀集团增添了新的血液。沙陀势力扩张以上源驿之变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期。沙陀扩张初期加入沙陀集团的汉族精英主要有:李存进,振武人,李克用破朔州时所得③;伊广,兖州人,中和末年任忻州刺史,因天下大乱,委质李克用④;袁建丰,关中人,为沙陀镇压黄巢起义之时于华阴所得⑤;李存贤,许州人,少时加入黄巢义军,沙陀破陈、许两州时,降沙陀⑥。
上源驿之变后,沙陀集团扩张步伐加快,这一时期是沙陀吸纳汉族精英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加入沙陀统治阶层的汉族精英既有交争中战败归顺者,也有在其他阵营内部斗争中失利而主动归顺者。其中战败归顺者主要有:光启三年(887年),李克用同昭义节度使孟方立战于琉璃陂,孟方立军队战败,统军大将马溉、袁奉韬被俘,归顺沙陀;丁会,曾为朱全忠之部曲,后朱全忠以丁会为昭义节度使。天祐三年(906年),李嗣昭攻潞州,丁会以潞州归李克用⑦。属其他阵营内部斗争失利而归顺者,为数更多。主要有:王思同、李承约,两者均属刘仁恭帐下军校,天祐四年(907年)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两人率部属奔沙陀;张遵诲原为魏博牙军,天祐三年(906年),罗绍威诛牙军,张遵诲奔沙陀;李罕之,降沙陀之前为河阳节度使,与河南尹、东都留守张全义本属同一阵营,但李罕之任河阳节度使之后不可一世,经常向据守洛阳的张全义勒索。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为张全义所逐,遂降沙陀。与李罕之同降沙陀的还有其部下李建及、李存审等。
尽管沙陀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汉族精英加入其集团,但沙陀本部及沙陀发迹代北时的元从精英,仍在沙陀统治阶层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后来沙陀势力拓展时期,对于新占领土,沙陀亦往往派遣沙陀本部人及代北元从前往经营。如昭义节度使一职,历任者有:李克修(883—890年)、李克恭(890年)、康君立(890—894年)、薛志勤(894—898年)、孟迁(899—900年)、李嗣昭(906—923年);邢洺团练使一职,历任者有:安金俊(890年)、安知建(890—891年)、李存孝(891—894年)、马师素(894—898年);泽州刺史一职,历任者有:李罕之(888—898年)、李存璋(899—901年);振武节度使一职,由石善友(893—902年)担任。
由于沙陀集团原为西北边陲小族,以武力起家,加之河东“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沙陀本部极度缺乏文职官员。文职在当时藩镇割据争雄中地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藩镇之表奏、交聘等事物均需文职官员操持。《旧五代史·李袭吉传》云:“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与(李)袭吉齐名于时。”①其时藩镇中的文职主要有节度副使、掌书记、判官、推官等,其中掌书记地位尤显重要。唐人崔颢曾言:“愚以为军中书记,节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谅非容易,而可专据”②;李德裕于河东掌书记任内,曾谓:“非夫天机殊捷,学源浚发,含思而九流委输,挥毫而万象骏奔,如庖丁提刃,为之满志,师文鼓瑟,效不可穷,则不能称是也。”③由此可见,文职在藩镇行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沙陀本部缺乏文职人才,故沙陀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大量吸纳汉族中的文职精英为其效命。
沙陀为吸纳文职精英加入其集团,可谓不遗余力。除正当的延揽吸纳外,还通过强行截留的方式吸纳。在沙陀集团的文职官员中,为沙陀所重视且在沙陀集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有:李袭吉,原为河中幕府,李克用入主河东前任河东文吏。先后担任沙陀集团的掌书记、节度副使,李克用时期,书檄基本出于其手,李克用每每出征,李袭吉必紧随其后。李袭吉死后,卢汝弼继任河东副使,卢质任河东掌书记。卢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进士第,历台省。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迁昭宗于洛阳,卢汝弼惧祸渡河,北依潞州丁会。天祐三年(906年)闰十二月随丁会降晋。沙陀集团之谋士,唯卢汝弼登进士第且在朝为官,故备受礼遇。卢质原为陕虢幕府,天祐三年(906年),北游太原,李袭吉以女妻之,遂留晋阳,加入沙陀集团。马郁,原为幽州刘仁恭之掌书记,天祐三年随幽州大将李溥帅兵三万会于晋阳,助河东兵攻潞州,平潞州后,会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李克用留马郁不遣,以之为留守判官。卢质虽代为掌书记,然“自李袭吉卒,每有四方会盟,书檄多命(马)郁为之,《答吴蜀书》与《王檀书》皆郁文也”①。王缄,亦为刘仁恭文吏,天祐四年刘仁恭遣王缄出使凤翔,路径太原,及复命,燕、晋不通,克用留之。缄坚辞复命,书辞稍抗,克用下狱诘之,谢罪听命,乃署为巡官,历掌书记。天祐十二年,李存勖得魏博,任魏博节度判官。翌年,迁魏博节度副使②。
沙陀集团吸纳的汉族精英群体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宦官。宦官群体在朱全忠把持朝政之时,几遭灭顶之灾。史载:“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诛唐宦者第五可范等七百余人。其在外者,悉诏天下捕杀之,而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而不杀。是时,方镇僭拟,悉以宦官给事,而吴越最多。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以至于亡。”③在朱全忠遍杀宦官之时,以李克用为代表的诸藩镇却将之藏匿,而且委之以重任。如河东监军张承业,在朱全忠诛杀宦官之时,即受李克用保护,且复之为河东监军。因沙陀集团善待宦官,河东成为宦官向往之地。如,乾宁元年(894年),李茂贞并山南诸州,逃亡于此的宦官杨复恭再度逃亡,欲投靠河东之沙陀集团,不幸途中为华州兵所擒,为韩建所杀①。
由于沙陀集团厚遇宦官,故宦官为其死力,在沙陀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见诸史载,为沙陀重用的宦官重要者有张承业、张居翰。张承业在朱全忠诛杀天下宦官时,得沙陀庇护幸免于难,故于沙陀最忠,贡献亦最大。《旧五代史·张承业传》云:“承邺感武皇(李克用)厚遇,庄宗(李存勖)在魏州垂十年,太原军国政事,一委承业。而积聚庾帑,收兵市马,招怀流散,劝课农桑,成是霸基者,承业之忠力也。”②另一名宦官张居翰,本为幽州监军,朱全忠诛杀宦官时,赖刘仁恭免诛。天祐三年(906年),刘仁恭遣军助河东攻潞州时,张居翰随行监军,及刘仁恭为其子刘守光所囚,李克用遂留之不遣,以为潞州监军。其后,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每出征,必令居翰知留后事③。
沙陀统治阶层之拓展,还表现在其人才选拔上不唯出身,只唯才能。只要其英勇善战,均予擢用。如李嗣昭,本汾州太谷人士,为李克用出猎以金帛取之,足见其出身寒微。然其英勇善战,光化二年,沙陀即以显职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授予之④;李存信,本“代北牧羊儿耳”;⑤其他如李存孝、李嗣源、李存进、李嗣本、李嗣恩等早期均属李克用帐下家僮,出身可谓寒微。
三、广与地方大姓通婚
沙陀本为一弱小部族,内迁初期人数不过万人,即使日后整合昭武九姓胡人之后形成“沙陀三部落”,与当地汉人相比,其人数亦不占优势。作为夷狄部落,生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要想生存、发展,势必要与当地汉族大姓结交,以换取其支持。沙陀发迹代北、称霸河东之时,一直在与当地大姓结交,而最有效之方法莫过联姻。正是通过联姻,广交地方大姓,换取地方大姓之支持,最终走上称霸河东、问鼎中原的道路。
沙陀内迁初期,势力弱小,加之身为夷狄,无与地方大姓结交之资。朱邪执宜时期,尚无沙陀与当地大姓通婚之例证。至李国昌、李克用时,才出现沙陀与当地汉人通婚的记载。李国昌妻秦氏,当属汉人无疑。李克用“正室刘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①以《新五代史》之惯例,沙陀或其他异族之人,莫不标明其族类。则,李克用之妻刘氏、曹氏亦皆为汉人。然对于李国昌、李克用妻之出身,史书无明确记载,出身地方大姓之可能性不大。唯李克用妻刘氏“自太祖起兵代北”,“常从征伐。为人明敏多智略,颇习兵机,常教其侍妾骑射,以佐太祖”,上源驿之变时,“太祖左右有先脱归者,以难告夫人,夫人(刘氏)神色不动,立斩告者,阴召大将谋保军以还”②。从刘氏之表现来看,当出自地方豪门抑或大姓。
至李克用时期,随着沙陀征讨庞勋、黄巢起义有功,其势力日渐壮大,沙陀与河东及其周边地区大姓通婚者日多。以李克用家族为例,其家族与地方大姓通婚者有:一、李克用子李存勖,李克用为其娶韩恽之妹和伊广之女。韩恽,字子重,晋阳人。韩恽出身官僚世家,曾祖韩俊,为唐龙武大将军;祖父韩世则,任石州(今山西离石)司马;父亲韩逵,任代州刺史。韩恽的兄弟均任军职,韩恽则不同。他与儒士交游甚广,喜欢作歌赋诗,家中收集书籍数千卷,属典型儒者。唐昭宗乾宁(894—897年)中,韩恽以文学署交城、文水县令,后为太原少尹。伊广,元和中右仆射伊慎之后。中和末,伊广除授忻州刺史。二、李克用子李存霸,李克用为其娶张敬询之女。张敬询,胜州金河县人,祖仲阮,历胜州刺史,父汉环事李克用为牙将,张敬询则在李克用时掌甲坊十五载,以称职闻名。三、李克用子李存义,李克用为其娶郭崇韬之女。郭崇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人,沙陀名将、谋臣。初为唐朝昭义节度使李克修亲信,后归李克用,用为典谒,能临机应对。史无明载其是否为地方大姓,但从其行为表现,当出自地方大姓。四、李克用还以一女适任茂弘之子任团。任茂弘,本京兆人士,祖清,任成都少尹,属衣冠之家。“避地太原,有子五人,曰图、回、圜、团、囧,风彩俱异”③。
沙陀集团与地方大姓结交并非囿于河东一隅,为巩固、拓展其势力,沙陀除与其统辖范围内的大姓通婚外,还主动与当时尚未纳入其统治范围的周边地区大姓通婚。仍以李克用家族为例,李克用家族与周边大姓通婚者主要有:一、李克用一女适河中节度使王珂。王珂,中人,祖纵,盐州刺史,父重荣,河东节度使,破黄巢有大功,封琅琊郡王。王珂本重荣兄重简之子,出继重荣。唐僖宗光启三年,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害,推重荣弟重盈为蒲帅,以珂为行军司马。及重盈卒,军府推珂为留后。时重盈子洪为陕州节度使,瑶为绛州刺史,由是争为蒲帅。王珂遣使求援于太原,李克用为保荐于朝,昭宗可之。后昭宗以王珂为河中节度使,李克用亦因此以女妻之。二、李克用以一女适王处存之侄王邺①。王处存,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世籍神策军。其祖辈为长安富族,财产数百万,父王宗,曾任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使。王处存少年时即以父荫,居右军镇使,后升为骁卫将军、左军巡使。乾符六年十月,出任检校刑部尚书、义武军节度使。三、李克用还以弟克让一女适孟知祥。孟知祥,字保风,又作保裔,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世代都在郡里为官。伯父孟方立官至邢洺节度使,叔父孟迁曾任泽潞节度使。孟家亦属地方大姓。
通过与地方大姓之通婚,沙陀赢得了河东及周边大姓之支持,从而为其日后问鼎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沙陀广与地方大姓通婚亦加快了沙陀集团的汉化过程。
相关地名
沙陀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