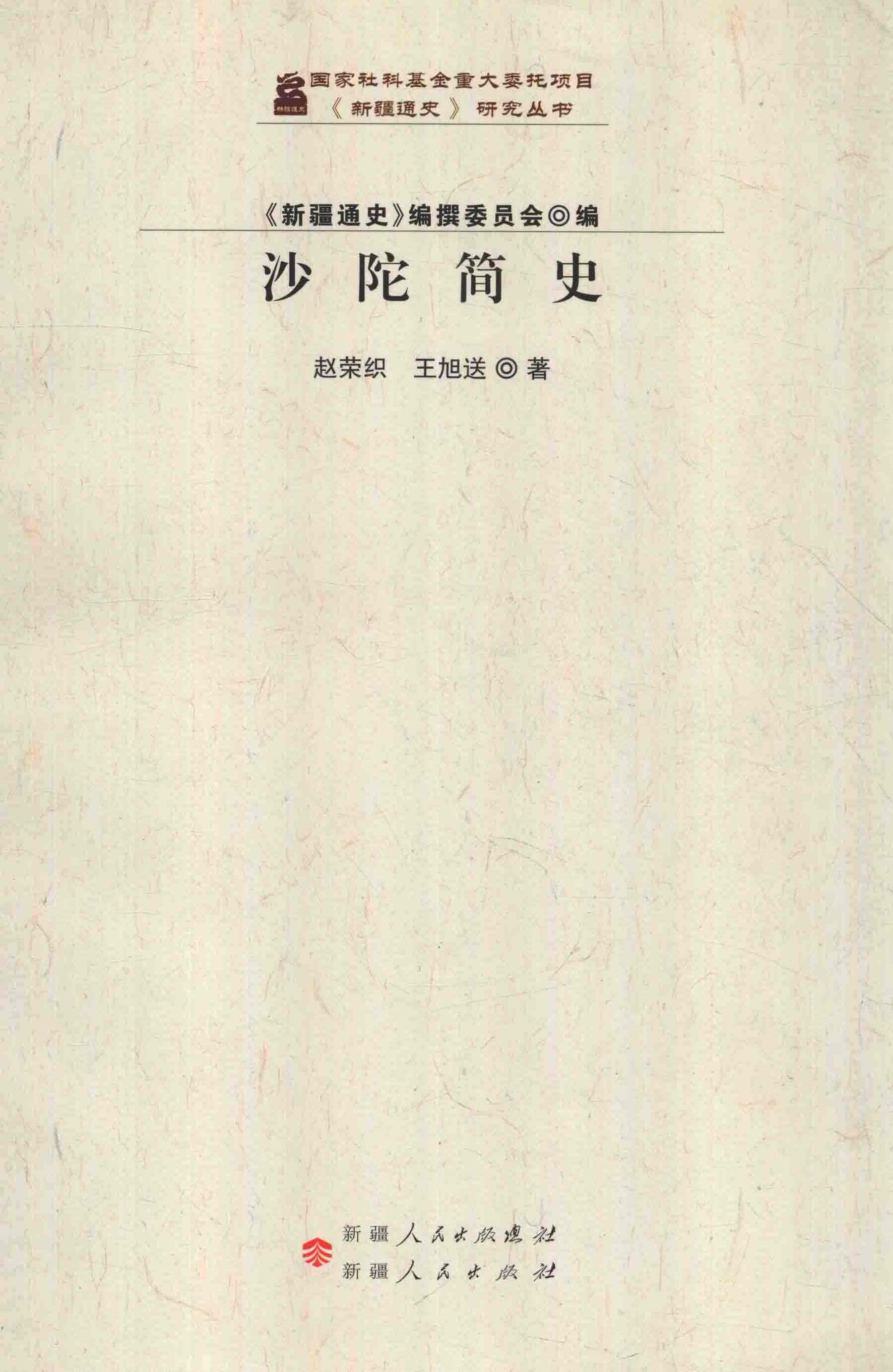内容
一、沙陀内迁的原因
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安置在甘州地区,游牧于祁连山一带。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因归附吐蕃有功,被吐蕃赞普封为“军大论”。“大论”一词藏文作blonchedpo,在吐蕃王朝中只有王族高等官员才有资格享有此衔①。尽管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得到了吐蕃赐予的崇高荣誉,但并没有给整个沙陀部落带来好运,吐蕃封朱邪尽忠“军大论”看中的是沙陀的骁勇善战,目的是驱使沙陀为其冲锋陷阵。史载:“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吐蕃)同,而驰射趫悍过之,虏倚其兵,常苦边。及归国,吐蕃繇此亦衰。”①由此可见,沙陀军队骑马射箭勇猛矫捷,在吐蕃之上。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吐蕃安置在吐蕃与唐朝、回纥战争的前沿——甘州,每逢战事,则令沙陀冲锋陷阵。
沙陀在甘州待了二十余载,最终不堪忍受吐蕃的统治,整体脱离吐蕃统治,东迁归唐。关于沙陀脱离吐蕃统治,东迁归唐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元和三年(808年),回奉诚可汗曾一度打败吐蕃,从其手中夺回凉州。由此,可能有人在赞普面前进谗言云:“沙陀本回纥部人,今闻回纥强,必为内应。”于是,吐蕃欲将沙陀迁到河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以散弱其类”②。就甘州地理位置而言,所谓“河外”指的是“今青海省境黄河之南地域,即黄南州、海南州东部之地。这一带被黄河从南、西、北三面围绕,中古时代较为荒凉偏僻”③。迁到河外无异于绝种,为保持种族不被灭绝,沙陀最终选择了脱离吐蕃统治,东归大唐④。第二种观点认为,元和时期,唐朝朔方、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听说沙陀“北方推其勇劲”,故“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⑤。
我们认为,沙陀归唐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上述两种观点都具有合理因素。首先,沙陀与回纥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平定安史之乱时沙陀曾与回纥并肩抗击叛军,沙陀首领沙陀金山还曾担任过回纥的副都护,《后唐懿祖纪年录》则径直称沙陀为回纥部人;吐蕃侵犯北庭之时双方又并肩抗击吐蕃的入侵。因此,吐蕃怀疑“尽忠持两端”、“贰于回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次,当时镇守边陲的节度使范希朝是一名具有极高声望的大将。史载,范希朝镇朔方时,大力加强边防设施,在要处建堡栅,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居官清廉,对诸蕃部落进献的奇驼名马“一无所受”;他见边地树木稀少,“于它处市柳子,令军人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因此,当时人将他比作西汉名将赵充国,号称当世善将①。投归范希朝门下对于身处绝境中的沙陀而言算是一条光明大道。与此同时,作为封疆大吏,范希朝也需要像沙陀这样的劲旅为其冲锋陷阵、保卫边疆。因此,第二种观点亦有其合理性。此外,吐蕃对待沙陀过于残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迁至甘州之后,每逢“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其伤亡肯定很大。
除了上述直接原因之外,沙陀内迁还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首先,是唐王朝民族政策的吸引力。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从唐初以来,“四夷”各族就纷纷内附。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以内附部落设置的羁縻府州有856个,比正州多出528个。唐王朝也欢迎各族的归附,对他们予以种种优惠待遇。如在经济上,唐朝《赋役令》中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者一年以上复三年,二年以上复四年,三年以上复五年。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外蕃人投化”唐朝者竟比唐人“没落外蕃得还者”在免征赋役上优惠出许多。在政治上唐太宗曾一再标榜自己“不猜忌异类”、对夷、夏“爱之如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有的甚至做到了高②。唐朝提拔起一大批蕃胡族人担任军事首领,级将领。在武将的提拔任用上,胡人往往要优于汉人。对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贵族则提供优厚待遇,赐予高官田宅,从政治、经济上加以笼络。在文化上,唐人不排斥胡人文化,胡舞胡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其至进入皇家宫廷;胡服、胡食则为庶民百姓乃至上流社会所接受、喜好。这种社会现实无疑会对沙陀贵族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内迁的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生存之需,而是在华夷一家的内地谋求更好的发展。
其次,汉族先进的物质、精神文化及中原地区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吸引力。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其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能不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自然吸引力。甘霖在《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0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指出:“东亚的黄河流域..富裕的文明中心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特别是唐朝时期,政治统一、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无疑对周边民族有巨大的吸引力,沙陀人也不例外。
再次,沙陀对唐朝统治的认可及其汉化的加深。沙陀人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归附了唐朝,成为唐朝臣民。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羁縻州性质的金满、沙陀都督府,隶属北庭都护府。自此以后,沙陀数世为唐朝守边,至元和三年(808年),沙陀人内迁中原时己有一个多世纪,其间沙陀首领还数度前往长安朝贡,亲眼目睹中原灿烂的文化。一个多世纪的耳濡目染,沙陀人内心深处已经形成民族认同思想。《后唐懿祖纪年录》中记载的朱邪执宜与其父朱邪尽忠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吾家世为唐臣,不幸陷虏,为他效命,反见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复归本朝。”①当时朱邪执宜仅“及冠”之年,涉世不深,但他却自觉将自己视为“唐臣”,将唐朝视为“本朝,”可见其沙陀人对唐朝的认可程度。同时,沙陀在同唐朝的接触中,已经呈现汉化趋势。前引吐鲁番文书《朱邪部落请纸牒》,是开元十六年迁居西州的一支沙陀朱邪部落向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沙陀本是游牧部落,“随地治畜牧,”唐初以羁縻之道治之,当无请纸笔之需。从这件西州朱邪部落请纸牒可以看出,文书用汉文所写,且符合唐代公文之规范,即使该文书非朱邪人所写,亦能说明朱邪部落已对汉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说明其本身开始汉化。
二、沙陀的初次内迁
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部在朱邪尽忠父子率领下开始东归大唐,为吐蕃发现之后,派军队对沙陀进行了围追堵截。为此,沙陀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的东迁路线。本来甘州距离灵州不过几百公里,可径直前往,但是沙陀却选择了沿甘州东北方向蒙古草原上的乌德鞬山①向东的路线。艾冲先生认为,沙陀的这种迁移路线“与彼时政治形势、地理形势相矛盾,而且过于迂远绵长,对于沙陀突厥来说,实际是不可能的”,并认为史书所载之“乌德鞬山”属史官之笔误,“乌德鞬山”当为“西倾山②。我们认为,西倾山”误写为“乌德鞬山”的可能性不大,艾先生之说法过于牵强。沙陀与回纥关系极为密切,回纥攻陷凉州之举被吐蕃怀疑为沙陀与之勾结的结果,亦绝非空穴来风。故,沙陀为摆脱吐蕃之围追堵截,选择取道回纥归唐的迂回方式应是一种减少伤亡的明智选择。
即便如此,沙陀亦未能避免吐蕃的围追堵截。沙陀向东北方向行军三日之后,吐蕃追兵赶上,沙陀被迫向南迁移,一直到洮河(今甘肃临洮地
区)。自洮河开始,沙陀与吐蕃军队边打边走,一直转战至石门关(宁夏固原西北地区)。本来数百公里的距离,沙陀却“委曲三千里”③。
沙陀东迁归唐之路崎岖坎坷,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史载,沙陀与吐蕃交战“凡数百回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太半”④。最终,“执宜裹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⑤。
朱邪执宜父子率领的沙陀主部东归大唐之后,仍有残部陆续归唐。其一,部分溃散的沙陀“童耄”(老弱病残)自凤翔府、兴元府者、太原府辗转至盐州与沙陀主部聚合。其二,同年六月,朱邪尽忠之弟葛勒阿波率部众七百人,抵达振武边塞归降。
关于沙陀东迁的时间,《后唐懿祖纪年录》将之定为贞元十三年(797年)⑥,而《资治通鉴》则将之定为元和三年(808年),而且司马光还对《后唐懿祖纪年录》所云之贞元十三年进行了考证:“据《德宗实录》,贞元十七年无沙陀归国事。《范希朝传》,德宗时为振武节度使,元和二年乃为朔方、灵盐节度使,诱致沙陀。元和元年亦无沙陀朝见。《纪年录》恐误,今从《实录》、《旧传》、《新书》。”①可见,沙陀东迁时间当在元和三年。
关于沙陀归唐之前及归唐之初的人数,史载不一。《新唐书》云:“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旁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裹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②;《资治通鉴》云:“酋长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自归于唐,遂帅部落三万,循乌德鞬山而东,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大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诣灵州降”③;《册府元龟》云:“本出甘州有九千余人,五月到灵州者,才二千余人,橐驼千余头,马六七百匹,馀皆战死、馁死及散失。”④
以上三种记载出入很大:首先,沙陀脱离吐蕃统治东归大唐之初的人数,《资治通鉴》云“部落三万”,而《新唐书》云“三万落”,相差悬殊。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云为确。《太平广记》卷一四七《裴仙先》条记载:“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⑤;《资治通鉴》载: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⑥。则,沙陀在北庭之时人数不过万帐。沙陀被吐蕃迁往甘州之后,沙陀在甘州居住时间仅20余年,且时常为吐蕃冲锋陷阵,伤亡甚众,其人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增长,故《新唐书》所云“三万落”有误。
其次,沙陀到达灵州后所剩人数,《新唐书》云“士裁二千,骑七百”;《资治通鉴》云“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册府元龟》云“才三千余人”,相差亦甚远。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云为确。因为,《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归唐之后不久,范希朝即“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以领之,为其战斗,所至有功。如是,则沙陀归唐之前骑当在千二百之上,故《新唐书》、《册府元龟》所云有误。《资治通鉴》所载沙陀至灵州者犹近万人,骑三千数目较为合理。
沙陀东迁归唐之后,仍有小部在甘州游牧,他们活动的地区主要在甘州南百余里祁连山中的鹿角山,因此这支沙陀余部被称为“鹿角山沙陀”。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张匡邺出使于阗,路经甘州,曾经获知这一沙陀余部的简单情况,被记录在五代平居诲所撰《于阗国行程记》中。记载如下:“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①这支部落明显是沙陀主部东迁灵武之后遗留之部分。
三、沙陀的再迁
沙陀东迁归唐是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摆脱了灭种的危机,而且逐渐走向辉煌。自此以后,沙陀由一个仅万人的小部落,逐渐吸纳其他民族成分,成为称霸一方的藩镇,并最终在中原建立三个王朝。
东迁归唐的沙陀部受到了唐朝政府的高度重视: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亲自率众迎接于塞上;唐宪宗“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葛勒阿波归降之后,唐廷又任命葛勒阿波为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都督府都督。沙陀历来强悍好斗,范希朝想利用沙陀部来抵御夷狄入侵,故沙陀东迁归唐之后,范希朝除了专门设阴山都督府安置他们外,还为沙陀购买牛羊,扩大他们的畜牧业,以使他们休整繁衍;同时,范希朝对沙陀军队亦给以特殊照顾,如元和四年三月辛未,范希朝“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朝廷“许之”②。
为了答谢唐朝政府的优抚,沙陀部首领朱邪执宜在沙陀部安顿之后,亲自到唐都长安觐见唐宪宗。唐宪宗为酬劳沙陀归唐之功,“赐(朱邪执宜)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
沙陀在盐州被妥善安置之后,很快成为灵、盐地区的一支劲旅,“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①。
沙陀在盐州待的时间很短,仅隔一年左右,元和四年(809年)六月便因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也随其迁转河东。迁转原因有三:首先,范希朝需要像沙陀这样一支刚强彪悍的劲旅为其守疆,同时范希朝因厚遇沙陀亦甚得沙陀之信任;其次沙陀居住之盐州靠近吐蕃统治区,唐朝怕其再度投靠吐蕃;第三,沙陀加入盐州之后,使当地人口大增,唐朝害怕当地粮食因此供应紧张。
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举军从之”。到达河东之后,范希朝挑选沙陀劲骑一千二百,号称沙陀军,并且设置军使进行管理;剩下的士兵则被范希朝安置在定襄川。朱邪执宜“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亦记载其事,云:“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之定襄神武川新城。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关于迁往河东的沙陀人数,《新五代史》记载恐有误。因为,沙陀迁至灵州之时仅有万余人,骑兵三千,其军队数量不可能在短短数年内骤增至“数万骑”。
关于沙陀军队驻扎之“黄花堆”,《资治通鉴》卷二百四胡三省注云:黄花堆“按朔州有黄花堆,在神武川②;关于神武川,意即黄瓜堆,”“”《资治通鉴》卷二三七胡三省注云:“神武川在汉代郡桑乾县界,后魏置神武郡,后周废郡为神武县,属朔州。此时其地在马邑善阳县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九云:“后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宁武府神池县东北。”唐代善阳县即今山西朔州市,则沙陀军队当时驻扎之地就在今山西朔州市及今神池县东北一带。关于“定襄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九云:“定襄川,唐定襄县之川也,在今大同府大同县西北”;《大事记续编》卷六三云:“忻州定襄郡有定襄县。”两相比较,当以后者为是。因为,大同一带地处唐代边塞,乃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不断,唐朝不可能将一群老弱病残安置于战争的前沿。故,沙陀“童耄”所居之“定襄川”当在今忻州定襄县牧马河一带。
沙陀甫迁河东,便显示了其强劲的军事势力。元和五年(810年),朝廷命范希朝等四军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王承宗、朱邪执宜率领700人为先锋。在这次战争中,朱邪执宜与王承宗埋伏在木刀沟,与数万敌军相遇,飞矢如雨,执宜率军杀入敌阵,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大败镇州。战后,朱邪执宜因功被升任为蔚州(今河北蔚县)刺史。
之后不久,王锷代范希朝出任河东节度使。王锷家财颇丰,常有行贿之举,但具治边才干。王锷任河东节度使之前,河东兵员不过3万,马匹不足600。王锷到任之后,兵员达到5万,马匹达到5000,仓库物资亦十分充盈。王锷看到沙陀强劲剽悍,且聚族而居,恐其势力强大后难于控制,于是上疏云:“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于是,朝廷设置十府,安置沙陀。
元和八年(813年),回鹘军队越过漠南,攻取西城、柳谷①。唐宪宗下诏,令朱邪执宜率沙陀军驻守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右旗西南“西受降城”),以阻止回鹘军队南下。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擅袭节度使自封统帅,窃取兵权。兵燹舞阳、叶县,略襄城、阳翟,许州、汝南人民深陷战乱之苦。唐宪宗以乌重胤兼汝州刺使,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帅,率领大军征讨吴元济。朱邪执宜率沙陀军队随李光颜参战。战争中,沙陀军队英勇作战,在时曲打败蔡人,并攻取凌云栅。吴元济叛乱被平定之后,朱邪执宜因功被升为检校刑部尚书,但仍隶属李光颜军。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朱邪执宜亲自到唐都长安朝贡,唐穆宗赐其“官诰、绵綵银器”②;同时,唐穆宗留朱邪执宜在朝宿卫,并拜其为金吾卫将军①。
大和四年(830年),柳公绰出任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善于治边及安抚少数民族,史载柳公绰任河东节度使之前,“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遇。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②。
沙陀骁勇善战,“为九姓六州胡③所畏伏”,柳公绰上任河东节度使之后,给予沙陀部以重任。史载:“公绰奏以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而朱邪执宜本人温雅知礼,亦博得柳公绰的信任。史载:“执宜与诸酋长人谒,神采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后来,朱邪执宜母亲、妻子前去拜见,柳公绰让夫人与她们一起饮酒,并且馈赠礼物给她们。朱邪执宜非常感激柳公绰的知遇之恩,做事竭尽全力。史载:“塞下旧有废府十一,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④
沙陀不仅为唐朝竭力守边,而且对当时叛乱藩镇的拉拢给以坚决拒绝。太和元年(827年),王庭凑帮助原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之子李同捷叛乱,为了增加叛乱的力量,王庭凑派遣使者带着重礼贿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希望朱邪执宜能与其联兵共同抗击唐朝,朱邪执宜对这种叛乱分裂的行径给以坚决拒绝⑤。
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安置在甘州地区,游牧于祁连山一带。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因归附吐蕃有功,被吐蕃赞普封为“军大论”。“大论”一词藏文作blonchedpo,在吐蕃王朝中只有王族高等官员才有资格享有此衔①。尽管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得到了吐蕃赐予的崇高荣誉,但并没有给整个沙陀部落带来好运,吐蕃封朱邪尽忠“军大论”看中的是沙陀的骁勇善战,目的是驱使沙陀为其冲锋陷阵。史载:“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吐蕃)同,而驰射趫悍过之,虏倚其兵,常苦边。及归国,吐蕃繇此亦衰。”①由此可见,沙陀军队骑马射箭勇猛矫捷,在吐蕃之上。归附吐蕃后的沙陀被吐蕃安置在吐蕃与唐朝、回纥战争的前沿——甘州,每逢战事,则令沙陀冲锋陷阵。
沙陀在甘州待了二十余载,最终不堪忍受吐蕃的统治,整体脱离吐蕃统治,东迁归唐。关于沙陀脱离吐蕃统治,东迁归唐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元和三年(808年),回奉诚可汗曾一度打败吐蕃,从其手中夺回凉州。由此,可能有人在赞普面前进谗言云:“沙陀本回纥部人,今闻回纥强,必为内应。”于是,吐蕃欲将沙陀迁到河外,企图通过这种方式“以散弱其类”②。就甘州地理位置而言,所谓“河外”指的是“今青海省境黄河之南地域,即黄南州、海南州东部之地。这一带被黄河从南、西、北三面围绕,中古时代较为荒凉偏僻”③。迁到河外无异于绝种,为保持种族不被灭绝,沙陀最终选择了脱离吐蕃统治,东归大唐④。第二种观点认为,元和时期,唐朝朔方、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听说沙陀“北方推其勇劲”,故“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⑤。
我们认为,沙陀归唐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上述两种观点都具有合理因素。首先,沙陀与回纥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平定安史之乱时沙陀曾与回纥并肩抗击叛军,沙陀首领沙陀金山还曾担任过回纥的副都护,《后唐懿祖纪年录》则径直称沙陀为回纥部人;吐蕃侵犯北庭之时双方又并肩抗击吐蕃的入侵。因此,吐蕃怀疑“尽忠持两端”、“贰于回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次,当时镇守边陲的节度使范希朝是一名具有极高声望的大将。史载,范希朝镇朔方时,大力加强边防设施,在要处建堡栅,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居官清廉,对诸蕃部落进献的奇驼名马“一无所受”;他见边地树木稀少,“于它处市柳子,令军人种之,俄遂成林,居人赖之”。因此,当时人将他比作西汉名将赵充国,号称当世善将①。投归范希朝门下对于身处绝境中的沙陀而言算是一条光明大道。与此同时,作为封疆大吏,范希朝也需要像沙陀这样的劲旅为其冲锋陷阵、保卫边疆。因此,第二种观点亦有其合理性。此外,吐蕃对待沙陀过于残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迁至甘州之后,每逢“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其伤亡肯定很大。
除了上述直接原因之外,沙陀内迁还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首先,是唐王朝民族政策的吸引力。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从唐初以来,“四夷”各族就纷纷内附。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以内附部落设置的羁縻府州有856个,比正州多出528个。唐王朝也欢迎各族的归附,对他们予以种种优惠待遇。如在经济上,唐朝《赋役令》中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者一年以上复三年,二年以上复四年,三年以上复五年。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外蕃人投化”唐朝者竟比唐人“没落外蕃得还者”在免征赋役上优惠出许多。在政治上唐太宗曾一再标榜自己“不猜忌异类”、对夷、夏“爱之如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有的甚至做到了高②。唐朝提拔起一大批蕃胡族人担任军事首领,级将领。在武将的提拔任用上,胡人往往要优于汉人。对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贵族则提供优厚待遇,赐予高官田宅,从政治、经济上加以笼络。在文化上,唐人不排斥胡人文化,胡舞胡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其至进入皇家宫廷;胡服、胡食则为庶民百姓乃至上流社会所接受、喜好。这种社会现实无疑会对沙陀贵族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内迁的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生存之需,而是在华夷一家的内地谋求更好的发展。
其次,汉族先进的物质、精神文化及中原地区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吸引力。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其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能不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自然吸引力。甘霖在《变局——前11世纪以来至20世纪中国区域发展与社会变迁》指出:“东亚的黄河流域..富裕的文明中心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特别是唐朝时期,政治统一、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无疑对周边民族有巨大的吸引力,沙陀人也不例外。
再次,沙陀对唐朝统治的认可及其汉化的加深。沙陀人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归附了唐朝,成为唐朝臣民。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羁縻州性质的金满、沙陀都督府,隶属北庭都护府。自此以后,沙陀数世为唐朝守边,至元和三年(808年),沙陀人内迁中原时己有一个多世纪,其间沙陀首领还数度前往长安朝贡,亲眼目睹中原灿烂的文化。一个多世纪的耳濡目染,沙陀人内心深处已经形成民族认同思想。《后唐懿祖纪年录》中记载的朱邪执宜与其父朱邪尽忠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吾家世为唐臣,不幸陷虏,为他效命,反见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复归本朝。”①当时朱邪执宜仅“及冠”之年,涉世不深,但他却自觉将自己视为“唐臣”,将唐朝视为“本朝,”可见其沙陀人对唐朝的认可程度。同时,沙陀在同唐朝的接触中,已经呈现汉化趋势。前引吐鲁番文书《朱邪部落请纸牒》,是开元十六年迁居西州的一支沙陀朱邪部落向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沙陀本是游牧部落,“随地治畜牧,”唐初以羁縻之道治之,当无请纸笔之需。从这件西州朱邪部落请纸牒可以看出,文书用汉文所写,且符合唐代公文之规范,即使该文书非朱邪人所写,亦能说明朱邪部落已对汉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说明其本身开始汉化。
二、沙陀的初次内迁
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部在朱邪尽忠父子率领下开始东归大唐,为吐蕃发现之后,派军队对沙陀进行了围追堵截。为此,沙陀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的东迁路线。本来甘州距离灵州不过几百公里,可径直前往,但是沙陀却选择了沿甘州东北方向蒙古草原上的乌德鞬山①向东的路线。艾冲先生认为,沙陀的这种迁移路线“与彼时政治形势、地理形势相矛盾,而且过于迂远绵长,对于沙陀突厥来说,实际是不可能的”,并认为史书所载之“乌德鞬山”属史官之笔误,“乌德鞬山”当为“西倾山②。我们认为,西倾山”误写为“乌德鞬山”的可能性不大,艾先生之说法过于牵强。沙陀与回纥关系极为密切,回纥攻陷凉州之举被吐蕃怀疑为沙陀与之勾结的结果,亦绝非空穴来风。故,沙陀为摆脱吐蕃之围追堵截,选择取道回纥归唐的迂回方式应是一种减少伤亡的明智选择。
即便如此,沙陀亦未能避免吐蕃的围追堵截。沙陀向东北方向行军三日之后,吐蕃追兵赶上,沙陀被迫向南迁移,一直到洮河(今甘肃临洮地
区)。自洮河开始,沙陀与吐蕃军队边打边走,一直转战至石门关(宁夏固原西北地区)。本来数百公里的距离,沙陀却“委曲三千里”③。
沙陀东迁归唐之路崎岖坎坷,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史载,沙陀与吐蕃交战“凡数百回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太半”④。最终,“执宜裹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⑤。
朱邪执宜父子率领的沙陀主部东归大唐之后,仍有残部陆续归唐。其一,部分溃散的沙陀“童耄”(老弱病残)自凤翔府、兴元府者、太原府辗转至盐州与沙陀主部聚合。其二,同年六月,朱邪尽忠之弟葛勒阿波率部众七百人,抵达振武边塞归降。
关于沙陀东迁的时间,《后唐懿祖纪年录》将之定为贞元十三年(797年)⑥,而《资治通鉴》则将之定为元和三年(808年),而且司马光还对《后唐懿祖纪年录》所云之贞元十三年进行了考证:“据《德宗实录》,贞元十七年无沙陀归国事。《范希朝传》,德宗时为振武节度使,元和二年乃为朔方、灵盐节度使,诱致沙陀。元和元年亦无沙陀朝见。《纪年录》恐误,今从《实录》、《旧传》、《新书》。”①可见,沙陀东迁时间当在元和三年。
关于沙陀归唐之前及归唐之初的人数,史载不一。《新唐书》云:“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吐蕃追之,行且战,旁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忠死之,执宜裹瘢伤,士裁二千,骑七百,杂畜橐驼千计,款灵州塞”②;《资治通鉴》云:“酋长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自归于唐,遂帅部落三万,循乌德鞬山而东,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大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诣灵州降”③;《册府元龟》云:“本出甘州有九千余人,五月到灵州者,才二千余人,橐驼千余头,马六七百匹,馀皆战死、馁死及散失。”④
以上三种记载出入很大:首先,沙陀脱离吐蕃统治东归大唐之初的人数,《资治通鉴》云“部落三万”,而《新唐书》云“三万落”,相差悬殊。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云为确。《太平广记》卷一四七《裴仙先》条记载:“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⑤;《资治通鉴》载: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⑥。则,沙陀在北庭之时人数不过万帐。沙陀被吐蕃迁往甘州之后,沙陀在甘州居住时间仅20余年,且时常为吐蕃冲锋陷阵,伤亡甚众,其人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增长,故《新唐书》所云“三万落”有误。
其次,沙陀到达灵州后所剩人数,《新唐书》云“士裁二千,骑七百”;《资治通鉴》云“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册府元龟》云“才三千余人”,相差亦甚远。我们认为,《资治通鉴》所云为确。因为,《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归唐之后不久,范希朝即“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军使以领之,为其战斗,所至有功。如是,则沙陀归唐之前骑当在千二百之上,故《新唐书》、《册府元龟》所云有误。《资治通鉴》所载沙陀至灵州者犹近万人,骑三千数目较为合理。
沙陀东迁归唐之后,仍有小部在甘州游牧,他们活动的地区主要在甘州南百余里祁连山中的鹿角山,因此这支沙陀余部被称为“鹿角山沙陀”。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张匡邺出使于阗,路经甘州,曾经获知这一沙陀余部的简单情况,被记录在五代平居诲所撰《于阗国行程记》中。记载如下:“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①这支部落明显是沙陀主部东迁灵武之后遗留之部分。
三、沙陀的再迁
沙陀东迁归唐是其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摆脱了灭种的危机,而且逐渐走向辉煌。自此以后,沙陀由一个仅万人的小部落,逐渐吸纳其他民族成分,成为称霸一方的藩镇,并最终在中原建立三个王朝。
东迁归唐的沙陀部受到了唐朝政府的高度重视: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亲自率众迎接于塞上;唐宪宗“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葛勒阿波归降之后,唐廷又任命葛勒阿波为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都督府都督。沙陀历来强悍好斗,范希朝想利用沙陀部来抵御夷狄入侵,故沙陀东迁归唐之后,范希朝除了专门设阴山都督府安置他们外,还为沙陀购买牛羊,扩大他们的畜牧业,以使他们休整繁衍;同时,范希朝对沙陀军队亦给以特殊照顾,如元和四年三月辛未,范希朝“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朝廷“许之”②。
为了答谢唐朝政府的优抚,沙陀部首领朱邪执宜在沙陀部安顿之后,亲自到唐都长安觐见唐宪宗。唐宪宗为酬劳沙陀归唐之功,“赐(朱邪执宜)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
沙陀在盐州被妥善安置之后,很快成为灵、盐地区的一支劲旅,“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①。
沙陀在盐州待的时间很短,仅隔一年左右,元和四年(809年)六月便因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也随其迁转河东。迁转原因有三:首先,范希朝需要像沙陀这样一支刚强彪悍的劲旅为其守疆,同时范希朝因厚遇沙陀亦甚得沙陀之信任;其次沙陀居住之盐州靠近吐蕃统治区,唐朝怕其再度投靠吐蕃;第三,沙陀加入盐州之后,使当地人口大增,唐朝害怕当地粮食因此供应紧张。
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举军从之”。到达河东之后,范希朝挑选沙陀劲骑一千二百,号称沙陀军,并且设置军使进行管理;剩下的士兵则被范希朝安置在定襄川。朱邪执宜“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新五代史》卷四《庄宗纪》亦记载其事,云:“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之定襄神武川新城。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关于迁往河东的沙陀人数,《新五代史》记载恐有误。因为,沙陀迁至灵州之时仅有万余人,骑兵三千,其军队数量不可能在短短数年内骤增至“数万骑”。
关于沙陀军队驻扎之“黄花堆”,《资治通鉴》卷二百四胡三省注云:黄花堆“按朔州有黄花堆,在神武川②;关于神武川,意即黄瓜堆,”“”《资治通鉴》卷二三七胡三省注云:“神武川在汉代郡桑乾县界,后魏置神武郡,后周废郡为神武县,属朔州。此时其地在马邑善阳县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九云:“后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宁武府神池县东北。”唐代善阳县即今山西朔州市,则沙陀军队当时驻扎之地就在今山西朔州市及今神池县东北一带。关于“定襄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五九云:“定襄川,唐定襄县之川也,在今大同府大同县西北”;《大事记续编》卷六三云:“忻州定襄郡有定襄县。”两相比较,当以后者为是。因为,大同一带地处唐代边塞,乃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不断,唐朝不可能将一群老弱病残安置于战争的前沿。故,沙陀“童耄”所居之“定襄川”当在今忻州定襄县牧马河一带。
沙陀甫迁河东,便显示了其强劲的军事势力。元和五年(810年),朝廷命范希朝等四军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王承宗、朱邪执宜率领700人为先锋。在这次战争中,朱邪执宜与王承宗埋伏在木刀沟,与数万敌军相遇,飞矢如雨,执宜率军杀入敌阵,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大败镇州。战后,朱邪执宜因功被升任为蔚州(今河北蔚县)刺史。
之后不久,王锷代范希朝出任河东节度使。王锷家财颇丰,常有行贿之举,但具治边才干。王锷任河东节度使之前,河东兵员不过3万,马匹不足600。王锷到任之后,兵员达到5万,马匹达到5000,仓库物资亦十分充盈。王锷看到沙陀强劲剽悍,且聚族而居,恐其势力强大后难于控制,于是上疏云:“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于是,朝廷设置十府,安置沙陀。
元和八年(813年),回鹘军队越过漠南,攻取西城、柳谷①。唐宪宗下诏,令朱邪执宜率沙陀军驻守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右旗西南“西受降城”),以阻止回鹘军队南下。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擅袭节度使自封统帅,窃取兵权。兵燹舞阳、叶县,略襄城、阳翟,许州、汝南人民深陷战乱之苦。唐宪宗以乌重胤兼汝州刺使,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帅,率领大军征讨吴元济。朱邪执宜率沙陀军队随李光颜参战。战争中,沙陀军队英勇作战,在时曲打败蔡人,并攻取凌云栅。吴元济叛乱被平定之后,朱邪执宜因功被升为检校刑部尚书,但仍隶属李光颜军。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朱邪执宜亲自到唐都长安朝贡,唐穆宗赐其“官诰、绵綵银器”②;同时,唐穆宗留朱邪执宜在朝宿卫,并拜其为金吾卫将军①。
大和四年(830年),柳公绰出任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善于治边及安抚少数民族,史载柳公绰任河东节度使之前,“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遇。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②。
沙陀骁勇善战,“为九姓六州胡③所畏伏”,柳公绰上任河东节度使之后,给予沙陀部以重任。史载:“公绰奏以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而朱邪执宜本人温雅知礼,亦博得柳公绰的信任。史载:“执宜与诸酋长人谒,神采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后来,朱邪执宜母亲、妻子前去拜见,柳公绰让夫人与她们一起饮酒,并且馈赠礼物给她们。朱邪执宜非常感激柳公绰的知遇之恩,做事竭尽全力。史载:“塞下旧有废府十一,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④
沙陀不仅为唐朝竭力守边,而且对当时叛乱藩镇的拉拢给以坚决拒绝。太和元年(827年),王庭凑帮助原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之子李同捷叛乱,为了增加叛乱的力量,王庭凑派遣使者带着重礼贿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希望朱邪执宜能与其联兵共同抗击唐朝,朱邪执宜对这种叛乱分裂的行径给以坚决拒绝⑤。
相关地名
沙陀
相关地名